《论语》孔子“五十以学易”考辨
先秦古籍之成书、流传多有不明晰处,《论语》也不例外,今知汉代传本主要有三——《古文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在篇章、字句上各有差异。历代一直有学者注解《论语》,惟汉人所注至今大多亡佚,少数残存的主要爲东汉末年郑玄(120-200)以《鲁论语》爲基础,其集合《古文论语》、《齐论语》编校为一个版本,并加以注释。但郑玄注本约在唐代后散失,现今传世的是后人辑佚本和近代以来的出土残本。
魏晋南北朝有魏何晏(190-249)的《论语集解》,又有梁皇侃(488-545)以何晏《集解》为底本的《论语义疏》。至唐代,韩愈、李翱同注《论语笔解》,因当时科举考试而重视经典,故被勒石成文,供时人参读,也益于后人抄录校对。
宋代,有北宋邢昺(932-1010)基于何晏的《集解》所成的《论语注疏》,亦称《论语正义》,而南宋朱熹(1130-1200)集前朝大成的《论语集注》。元明两朝因前代着作严谨且参考价值高,故时人对《论语》的研读相较之下没那么突出。
清代考据学兴起,相关着作如雨后春笋涌现,代表着作有刘宝楠(1791-1855)的《论语正义》后来因病停笔由儿子刘恭冕(1821-1880)续写,程树德(1877-1944)的《论语集释》。近代以来,又有杨树达(1885-1956)的《论语疏证》、钱穆(1895-1990)的《论语新解》、杨伯峻(1909-1992)的《论语译注》。现今如孙钦善(1934-)的《论语注译》、杨逢彬(1956-)的《论语新注新译》,和傅佩荣(1950-)解读后出版的《论语》诸着作等等。
可见,《论语》作为记载孔子言行最重要的经典,其文本言简而意深,因此历代诠释层出不穷。其中〈述而第七〉“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句常见学者引述,但其内涵却较少为人关注,钱穆早年曾指出“此条解者,从来不一”1,本文则尝试在其基础上,从通假、误读、句读诸角度着眼,详细分析历代诸家之说,以见是非得失处。
贊成一方认为“加我数年”等同于“假我数年”。如,朱熹注曰:“刘聘君见元城刘定公,自言尝读他论,‘加’作‘假’〔……〕盖加、假声相近而误读。”2声相近而义相通,戴望注曰:“加,当言假,假之言暇。时子尚周游四方,故言暇我数年也。”3由此可见,“加”“假”之别并不影响意思理解,故通假一说言之成理。
反对一方则从孔子说此句时的具体年龄考究,来判断应用“加”还是“假”,其中分歧为此句当在孔子五十前或后时说。
多数学者认爲此章是孔子在五十岁之前、大约四十多岁时所说的,故认为应作“加我数年”。郑玄在《论语注》曰:“加我数年,年至五十以学此《易》,其义理可无大过。孔子时年四十五六,好《易》,玩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其意,故云然也。”而皇侃于《论语义疏》指出,孔子时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数年”4。另,邢昺于《论语正义》曰:“此章孔子言其学《易》年也。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5
亦有学者提出孔子当时应年过五十。朱熹在《论语集注》认爲此章乃孔子近七十岁时所说。
今人郭沂认爲,孔子若是在五十岁前提出,他须先意识到自己接近寿终,才能使语义合乎逻辑,故他认爲此句是孔子在五十几岁之后、六十岁之前说的6,有“借年”之意7。在这个语境下,可以解读推溯作“假如我再年轻几岁”。所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而五十则知天命。由此推论,这其实更适合放在孔子在总结一生的情景当中説出。
纵观来说,“假”字说,目前文本证据有《史记·孔子世家》云:“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8《风俗通义•穷通》引《论语》作“孔子曰:假我数年乎”9。以“假”字流传至今的传本与注释本比较鲜见,今人多採“加我数年”之説,如孙钦善《论语注译》10、杨逢彬的《论语新注新译》11、和傅佩荣本《论语》12等,可见目前学界已有共识。
朱熹在《论语集注》提及:“刘聘君见刘忠定聘,自言尝读他《论》……“五十”作 “卒”。……“卒”与“五十”字相似而误分也。13”
后世多反对意见。元陈天祥(1230-1316)《四书辨疑》曰:“以‘五十’爲‘卒’,‘卒以学《易》’,不成文理。”清毛奇龄(1623-1716)持相近看法,惟认爲非形似之由,并曰:
鲁鱼亥豕,必其字形俱相类者,故曰形近致误。卒与五十,不近也。案:《説文》,五者,互也,从二从乂,谓隂阳交互于二大间也。卒者,隷人给事名也。古以染衣题识,故从衣从十,谓衣饰有异色也。则试以今文观之,五字与衣字相近乎,否乎?即因而观古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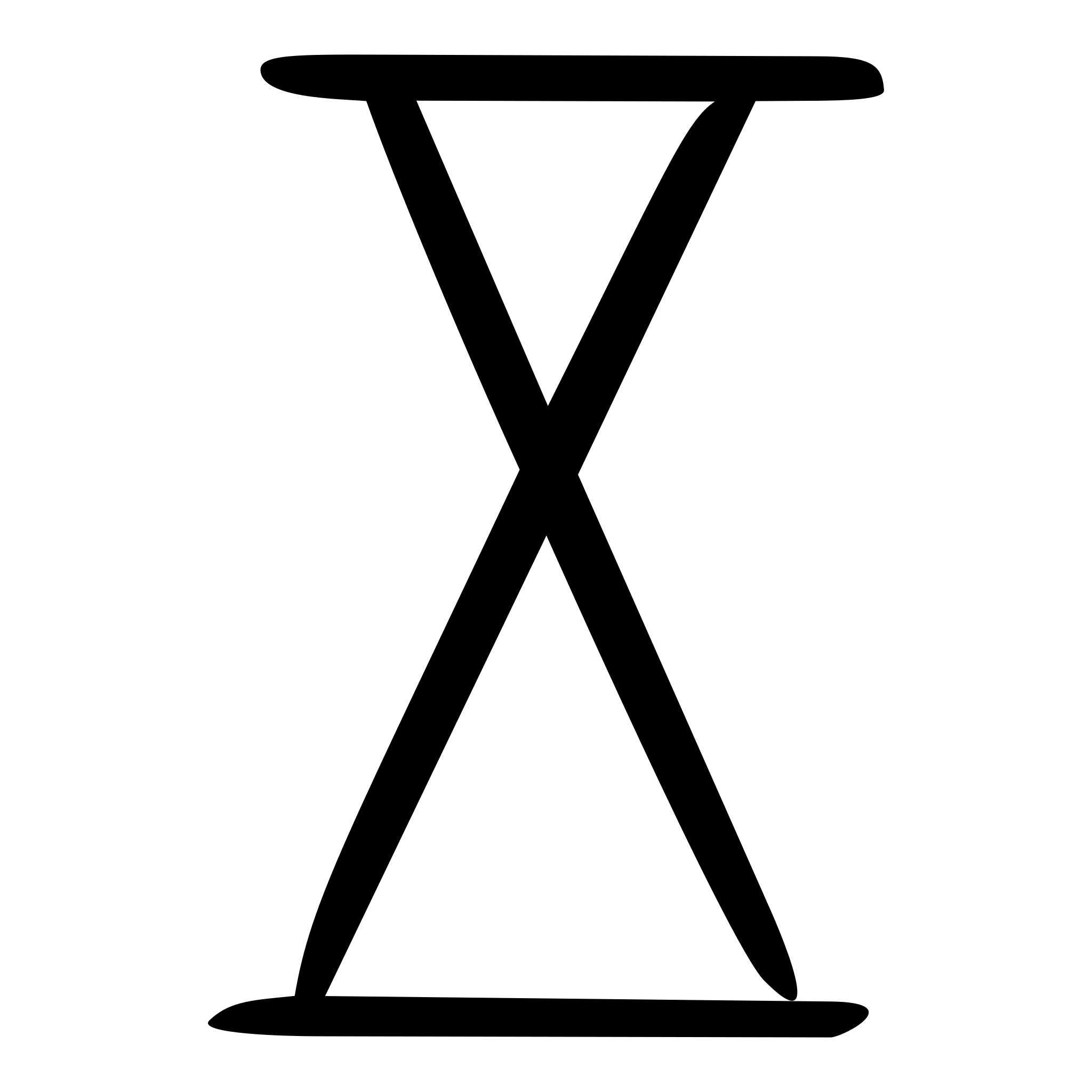 与
与 相近乎,否乎?毋亦宋后陋儒习见草书,有草卒字者以卆字,合九十为文,九字近五,故以云。14
相近乎,否乎?毋亦宋后陋儒习见草书,有草卒字者以卆字,合九十为文,九字近五,故以云。14
朱子所引,可能是古时文字皆竖写“五十”误认为“卒”,方才有形似一说。但从上述所论,形近而误之说十分牵强,且无实据,于文意而言也不通畅,因此今人的传本与注释本基本都不取此说。
上述两争议至今学者多有共识,而下述之分歧现今仍未统一。
从古到今,此章中的“易”字,大多数学者将其理解为《易经》。譬如何晏、皇侃、邢昺、朱子等,今人也多无异见。此则受孔子“五十知天命”或《史记·孔子世家》所云“孔子晚而喜《易》”之影响。但历代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易”字为通假字,当释为“亦”。
此说最早见于《鲁论》,未为通行,至清人发复之。如,惠栋《论语古义》云:“《鲁论》易为亦,君子爱日以学,及时而成。五十而学,斯为晚矣。然秉烛之明,尚可寡过,此圣人之谦辞也。”陈鱣《论语古义》云:“五十以学者,即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无大过矣者,即欲寡其过意也。”15
从孔子生平来观晚而学《易》一説,清人林春溥(1775-1862)《开卷偶得》卷六曰:“《正义》以为四十七时语,尝疑其无据,及读《史记》,孔子四十七岁以阳虎叛不仕,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乃知斯语之非妄。”16再结合钱穆《孔子传》指,“孔子以五十一出宰中都,其前皆不仕。《正义》四十七时语,盖为近是。惟古者无六经之目,《易》不与《诗》《书》《礼》《乐》同科,孔子实未尝传《易》,今《十传》皆不出孔子。〈世家〉亦但言孔子四十七不仕而修《诗》《书》《礼》《乐》,并不及《易》。而《正义》谓言其学《易》之年,明为误矣。〈世家〉又谓:‘孔子晚而喜《易》,序《易传》’,盖皆不足信。” 17由此可见,孔子晚而学《易》一説脱离史实。
从版本方面来説,日本经学家本田成之也説:“鲁论语易字作亦……齐、鲁、古论语若有歧异时,须从鲁论为正,谁以无异议者。”18周浩治补充,汉代张禹讲授《论语》是以《鲁论》爲主,兼採齐、鲁《论语》说,《张侯论》爲当时所贵;而东汉末大儒郑康成校注《论语》,篇章概依《鲁论》,《齐论》与《古论语》均供参考;后世传诵,便多以郑氏校注本爲据。即使从古论作“易”,“易”字也作“亦”字解。19黄怀信亦指出:“诸本及唐写本同,定州简本‘易’作‘亦’。”20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作“亦”,与《鲁论》同,更突显《鲁论》的参考价值更高。
从语义方面来説,王叔岷说:“从《古论》作易,易字亦当属下读,易、亦古通。”《荀子·儒效篇》:‘抑亦鬓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元本、明沉津百家类纂本、清《百子全书》本亦并作易。《黄帝内经》、《素问·气厥论》篇:‘谓之食亦。’唐王冰注:‘亦、易也。’……后人不识易为亦之借字,误信孔子传易之说,遂以易字属上断句耳。”21可见“亦”“易”语义相通。
综上所説,主流学者将“易”释为《易》,可能是受前人注释影响,但释为“亦”其实也合理且更符合逻辑,惟此説却一直爲人忽略。
综上所述,《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古今学者于此句解释有四种争议:“加”“假”通假之说、“五十”为“卒”字之误、“五十”作二字解、 “易”“亦”通假等。如此,则此句有三种读法:一是今通行本,“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二是通行本之变例,“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三是《鲁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上述争议迄今仍有讨论空间,或将等待更多可信之新材料问世才能彻底解决。
专着
1.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 〔魏〕何晏解;〔唐〕陆德明音义;〔宋〕邢昺疏:《宋蜀刻本论语注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3. 〔梁〕皇侃;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4. 〔宋〕朱熹:《宋本论语集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
5. 〔清〕毛奇龄:《毛诗稽古篇》,《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
6. 〔清〕戴望注,郭晓东校疏:《戴氏注论语小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7.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8. 傅佩荣解读:《论语》,臺北:立绪文化,1999年。
9. 黄怀信主撰:《论语彙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10. 孙钦善:《论语注译》,香港:商务印书局,2019年。
11. 钱穆:《孔子传》,臺北:三民书局,2022年。
12. 钱穆:《先秦诸子繫年》,臺北:东大,2020年。
13. 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4. 周浩治:《论孟章句辩正及精义发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
15. 王叔岷:《慕庐杂着•论语斠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期刊论文
16. 郭沂:〈孔子学《易》考论〉,《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页4-14。
脚注
[1] 钱穆:《先秦诸子繫年》(臺北:东大,2020年),〈孔子五十学易辨〉,页26。
[2] 〔宋〕朱熹:《宋本论语集注2》(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页25-26。
[3] 〔清〕戴望注,郭晓东校疏:《戴氏注论语小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页129-130.
[4] 〔梁〕皇侃;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167。
[5] 〔魏〕何晏解;〔唐〕陆德明音义;〔宋〕邢昺疏:《宋蜀刻本论语注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182-183。
[6] 郭沂:〈孔子学《易》考论〉,《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页9-10。
[7] 《说文·人部》:“假,非真也。”段玉裁注::“又部曰:‘叚,借也。’然则假与叚义略同。”〔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374。
[8]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卷47,页1937。
[9] 〔汉〕应劭:《风俗通义》(上海:商务印书局,2019年),页33。
[10]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引自孙钦善:《论语注译》(香港:商务印书局,2019年),页84-85。
[11]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引自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138。
[12]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引自傅佩荣解读:《论语》(臺北:立绪文化,1999年),页166。
[13] 同[2]。
[14] 〔清〕毛奇龄:《毛诗稽古篇》,《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年),卷4,页4下至5上。
[15] 以上转引自钱穆《先秦诸子繫年》,〈孔子五十学易辨〉,页26。
[16] 以上转引自钱穆《先秦诸子繫年》,〈孔子五十学易辨〉,页26。
[17] 钱穆《先秦诸子繫年》,〈孔子五十学易辨〉,页26;《孔子传》(臺北:三民书局,2022年),页146。
[18] 转引自周浩治:《论孟章句辩正及精义发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页44。
[19] 周浩治:《论孟章句辩正及精义发微》,页42-45。
[20] 黄怀信主撰:《论语彙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页607-611。
[21] 王叔岷:《慕庐杂着·论语斠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162。
< 原创文章/视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欢迎留言:
请登入/登记成为会员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