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孔子“五十以學易”考辨
先秦古籍之成書、流傳多有不明晰處,《論語》也不例外,今知漢代傳本主要有三——《古文論語》、《齊論語》、《魯論語》,在篇章、字句上各有差異。歷代一直有學者注解《論語》,惟漢人所注至今大多亡佚,少數殘存的主要爲東漢末年鄭玄(120-200)以《魯論語》爲基礎,其集合《古文論語》、《齊論語》編校為一個版本,並加以注釋。但鄭玄注本約在唐代後散失,現今傳世的是後人輯佚本和近代以來的出土殘本。
魏晉南北朝有魏何晏(190-249)的《論語集解》,又有梁皇侃(488-545)以何晏《集解》為底本的《論語義疏》。至唐代,韓愈、李翱同注《論語筆解》,因當時科舉考試而重視經典,故被勒石成文,供時人參讀,也益於後人抄錄校對。
宋代,有北宋邢昺(932-1010)基於何晏的《集解》所成的《論語注疏》,亦稱《論語正義》,而南宋朱熹(1130-1200)集前朝大成的《論語集注》。元明兩朝因前代著作嚴謹且參考價值高,故時人對《論語》的研讀相較之下沒那麽突出。
清代考據學興起,相關著作如雨後春筍湧現,代表著作有劉寶楠(1791-1855)的《論語正義》後來因病停筆由兒子劉恭冕(1821-1880)續寫,程樹德(1877-1944)的《論語集釋》。近代以來,又有楊樹達(1885-1956)的《論語疏證》、錢穆(1895-1990)的《論語新解》、楊伯峻(1909-1992)的《論語譯注》。現今如孫欽善(1934-)的《論語注譯》、楊逢彬(1956-)的《論語新注新譯》,和傅佩榮(1950-)解讀後出版的《論語》諸著作等等。
可見,《論語》作為記載孔子言行最重要的經典,其文本言簡而意深,因此歷代詮釋層出不窮。其中〈述而第七〉“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句常見學者引述,但其內涵卻較少為人關注,錢穆早年曾指出“此條解者,從來不一”1,本文則嘗試在其基礎上,從通假、誤讀、句讀諸角度著眼,詳細分析歷代諸家之說,以見是非得失處。
贊成一方認為“加我數年”等同於“假我數年”。如,朱熹注曰:“劉聘君見元城劉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2聲相近而義相通,戴望注曰:“加,當言假,假之言暇。時子尚周遊四方,故言暇我數年也。”3由此可見,“加”“假”之別並不影響意思理解,故通假一說言之成理。
反對一方則從孔子說此句時的具體年齡考究,來判斷應用“加”還是“假”,其中分歧為此句當在孔子五十前或後時說。
多數學者認爲此章是孔子在五十歲之前、大約四十多歲時所說的,故認為應作“加我數年”。鄭玄在《論語注》曰:“加我數年,年至五十以學此《易》,其義理可無大過。孔子時年四十五六,好《易》,玩讀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其意,故云然也。”而皇侃於《論語義疏》指出,孔子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4。另,邢昺於《論語正義》曰:“此章孔子言其學《易》年也。加我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5
亦有學者提出孔子當時應年過五十。朱熹在《論語集注》認爲此章乃孔子近七十歲時所說。
今人郭沂認爲,孔子若是在五十歲前提出,他須先意識到自己接近壽終,才能使語義合乎邏輯,故他認爲此句是孔子在五十幾歲之後、六十歲之前說的6,有“借年”之意7。在這個語境下,可以解讀推溯作“假如我再年輕幾歲”。所謂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六十而耳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而五十則知天命。由此推論,這其實更適合放在孔子在總結一生的情景當中説出。
縱觀來說,“假”字說,目前文本證據有《史記·孔子世家》云:“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8《風俗通義•窮通》引《論語》作“孔子曰:假我數年乎”9。以“假”字流傳至今的傳本與注釋本比較鮮見,今人多採“加我數年”之説,如孫欽善《論語註譯》10、楊逢彬的《論語新注新譯》11、和傅佩榮本《論語》12等,可見目前學界已有共識。
朱熹在《論語集注》提及:“劉聘君見劉忠定聘,自言嘗讀他《論》……“五十”作 “卒”。……“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13”
後世多反對意見。元陳天祥(1230-1316)《四書辨疑》曰:“以‘五十’爲‘卒’,‘卒以學《易》’,不成文理。”清毛奇齡(1623-1716)持相近看法,惟認爲非形似之由,並曰:
魯魚亥豕,必其字形俱相類者,故曰形近致誤。卒與五十,不近也。案:《説文》,五者,互也,从二从乂,謂隂陽交互于二大間也。卒者,隷人給事名也。古以染衣題識,故从衣从十,謂衣飾有異色也。則試以今文觀之,五字與衣字相近乎,否乎?即因而觀古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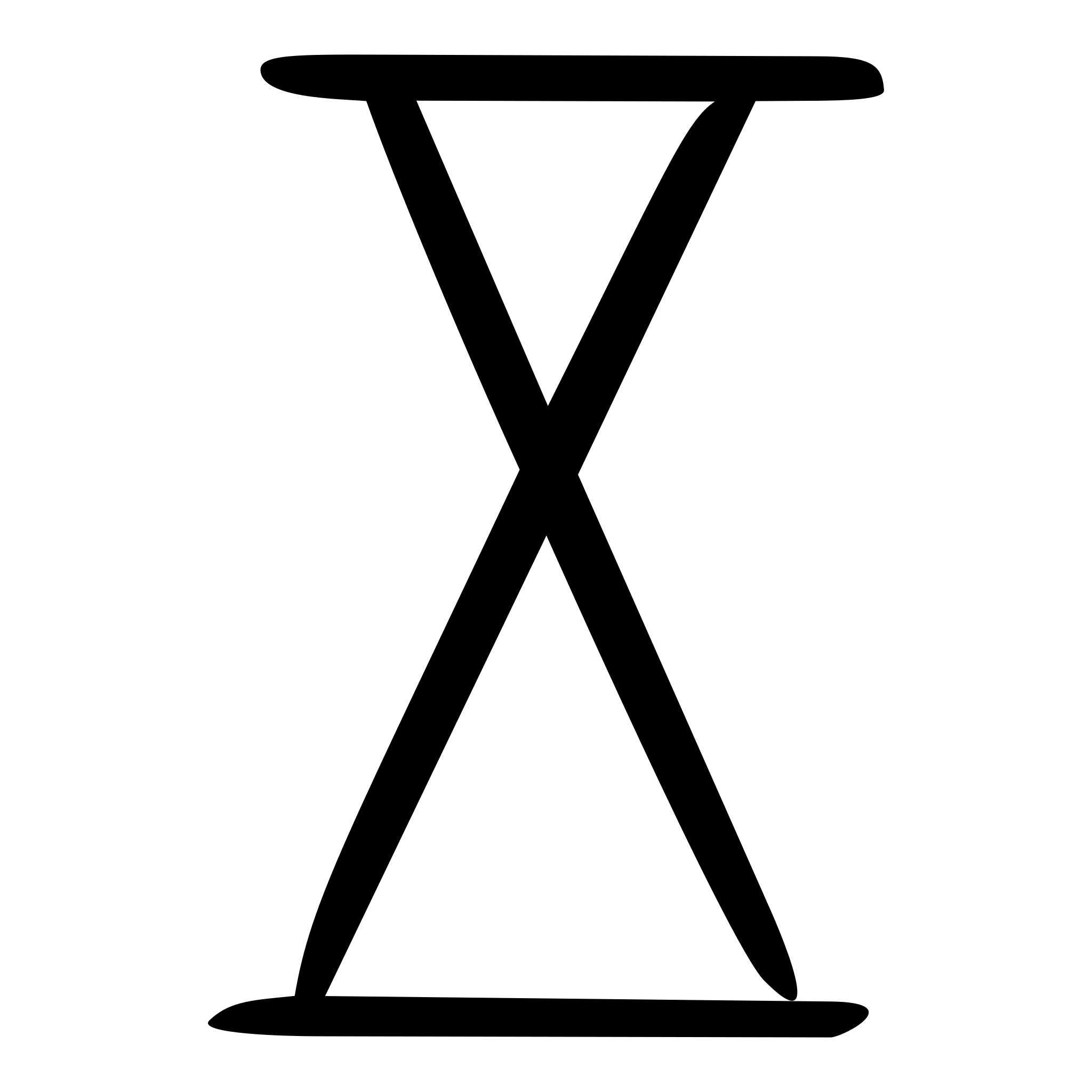 與
與 相近乎,否乎?毋亦宋後陋儒習見草書,有草卒字者以卆字,合九十為文,九字近五,故以云。14
相近乎,否乎?毋亦宋後陋儒習見草書,有草卒字者以卆字,合九十為文,九字近五,故以云。14
朱子所引,可能是古時文字皆豎寫“五十”誤認為“卒”,方才有形似一說。但從上述所論,形近而誤之說十分牽強,且無實據,於文意而言也不通暢,因此今人的傳本與注釋本基本都不取此說。
上述兩爭議至今學者多有共識,而下述之分歧現今仍未統一。
從古到今,此章中的“易”字,大多數學者將其理解為《易經》。譬如何晏、皇侃、邢昺、朱子等,今人也多無異見。此則受孔子“五十知天命”或《史記·孔子世家》所云“孔子晚而喜《易》”之影響。但歷代也有學者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易”字為通假字,當釋為“亦”。
此說最早見於《魯論》,未為通行,至清人發覆之。如,惠棟《論語古義》云:“《魯論》易為亦,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而學,斯為晚矣。然秉燭之明,尚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陳鱣《論語古義》云:“五十以學者,即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無大過矣者,即欲寡其過意也。”15
從孔子生平來觀晚而學《易》一説,清人林春溥(1775-1862)《開卷偶得》卷六曰:“《正義》以為四十七時語,嘗疑其無據,及讀《史記》,孔子四十七歲以陽虎叛不仕,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乃知斯語之非妄。”16再結合錢穆《孔子傳》指,“孔子以五十一出宰中都,其前皆不仕。《正義》四十七時語,蓋為近是。惟古者無六經之目,《易》不與《詩》《書》《禮》《樂》同科,孔子實未嘗傳《易》,今《十傳》皆不出孔子。〈世家〉亦但言孔子四十七不仕而修《詩》《書》《禮》《樂》,並不及《易》。而《正義》謂言其學《易》之年,明為誤矣。〈世家〉又謂:‘孔子晚而喜《易》,序《易傳》’,蓋皆不足信。” 17由此可見,孔子晚而學《易》一説脫離史實。
從版本方面來説,日本經學家本田成之也説:“魯論語易字作亦……齊、魯、古論語若有歧異時,須從魯論為正,誰以無異議者。”18周浩治補充,漢代張禹講授《論語》是以《魯論》爲主,兼採齊、魯《論語》說,《張侯論》爲當時所貴;而東漢末大儒鄭康成校注《論語》,篇章概依《魯論》,《齊論》與《古論語》均供參考;後世傳誦,便多以鄭氏校注本爲據。即使從古論作“易”,“易”字也作“亦”字解。19黃懷信亦指出:“諸本及唐寫本同,定州簡本‘易’作‘亦’。”20定州漢墓竹簡本《論語》作“亦”,與《魯論》同,更突顯《魯論》的參考價值更高。
從語義方面來説,王叔岷說:“從《古論》作易,易字亦當屬下讀,易、亦古通。”《荀子·儒效篇》:‘抑亦鬓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元本、明沈津百家類纂本、清《百子全書》本亦並作易。《黄帝內經》、《素問·氣厥論》篇:‘謂之食亦。’唐王冰注:‘亦、易也。’……後人不識易為亦之借字,誤信孔子傳易之說,遂以易字屬上斷句耳。”21可見“亦”“易”語義相通。
綜上所説,主流學者將“易”釋為《易》,可能是受前人注釋影響,但釋為“亦”其實也合理且更符合邏輯,惟此説卻一直爲人忽略。
綜上所述,《論語·述而》“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古今學者於此句解釋有四種爭議:“加”“假”通假之說、“五十”為“卒”字之誤、“五十”作二字解、 “易”“亦”通假等。如此,則此句有三種讀法:一是今通行本,“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二是通行本之變例,“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三是《魯論》,“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上述爭議迄今仍有討論空間,或將等待更多可信之新材料問世才能徹底解決。
專著
1.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2. 〔魏〕何晏解;〔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宋蜀刻本論語注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
3. 〔梁〕皇侃;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4. 〔宋〕朱熹:《宋本論語集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
5. 〔清〕毛奇齡:《毛詩稽古篇》,《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年。
6. 〔清〕戴望注,郭曉東校疏:《戴氏注論語小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7.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8. 傅佩榮解讀:《論語》,臺北:立緒文化,1999年。
9. 黃懷信主撰:《論語彙校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10. 孫欽善:《論語註譯》,香港:商務印書局,2019年。
11. 錢穆:《孔子傳》,臺北:三民書局,2022年。
12.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臺北:東大,2020年。
13. 楊逢彬:《論語新注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14. 周浩治:《論孟章句辯正及精義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
15. 王叔岷:《慕廬雜著•論語斠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期刊論文
16. 郭沂:〈孔子學《易》考論〉,《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頁4-14。
腳註
[1]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臺北:東大,2020年),〈孔子五十學易辨〉,頁26。
[2] 〔宋〕朱熹:《宋本論語集注2》(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頁25-26。
[3] 〔清〕戴望注,郭曉東校疏:《戴氏注論語小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29-130.
[4] 〔梁〕皇侃;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167。
[5] 〔魏〕何晏解;〔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宋蜀刻本論語注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182-183。
[6] 郭沂:〈孔子學《易》考論〉,《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頁9-10。
[7] 《說文·人部》:“假,非真也。”段玉裁注::“又部曰:‘叚,借也。’然則假與叚義略同。”〔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374。
[8]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卷47,頁1937。
[9] 〔漢〕應劭:《風俗通義》(上海:商務印書局,2019年),頁33。
[10]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引自孫欽善:《論語註譯》(香港:商務印書局,2019年),頁84-85。
[11]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引自楊逢彬:《論語新注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38。
[12]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引自傅佩榮解讀:《論語》(臺北:立緒文化,1999年),頁166。
[13] 同[2]。
[14] 〔清〕毛奇齡:《毛詩稽古篇》,《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1983年),卷4,頁4下至5上。
[15] 以上轉引自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孔子五十學易辨〉,頁26。
[16] 以上轉引自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孔子五十學易辨〉,頁26。
[17]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孔子五十學易辨〉,頁26;《孔子傳》(臺北:三民書局,2022年),頁146。
[18] 轉引自周浩治:《論孟章句辯正及精義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頁44。
[19] 周浩治:《論孟章句辯正及精義發微》,頁42-45。
[20] 黃懷信主撰:《論語彙校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607-611。
[21] 王叔岷:《慕廬雜著·論語斠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62。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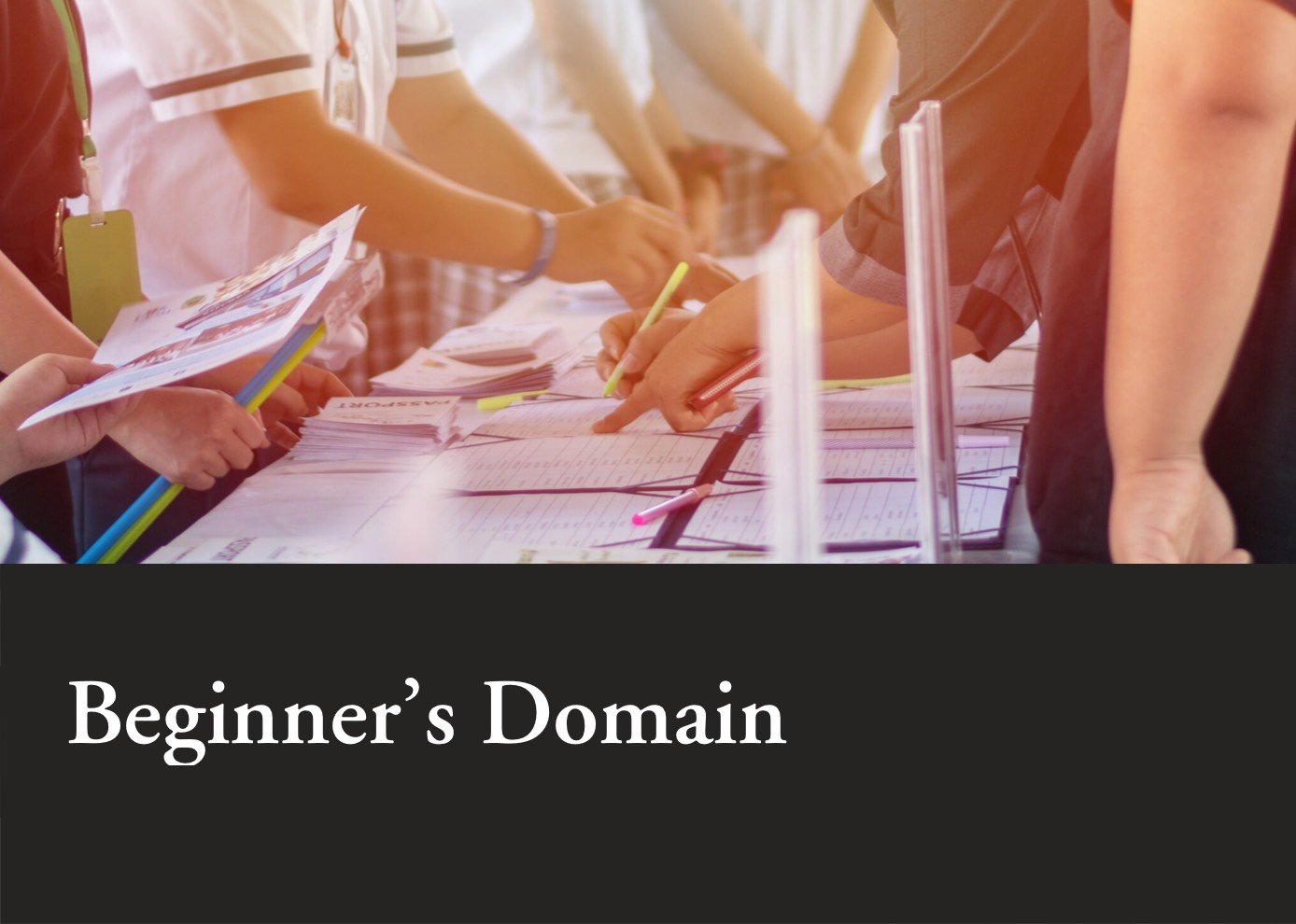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