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小传承
本文节选自孙天伦教授著作《中国心理学》,
由陆国权中华文化传承研究基金研究员沉诗麟编辑审校。
总体背景
《红楼梦》的抄本最早出现于1754年左右,现流传的版本分别为80回本与120回本。学界普遍认为前80回是由曹雪芹(约1715 – 约1763)创作的,而后40回则由后人所续写。如今,与《红楼梦》相关的艺术作品,包括小说、戏曲、现代芭蕾舞剧、电视剧和电影基本上都是依据120回的版本改编而成的。
《红楼梦》故事的其中一条主线就是京城四大豪门望族之一的贾氏家族的盛衰兴亡。在小说的开篇,贾家受先祖功业的庇荫,位列京城四大家族之一,但随着剧情的推进,在内家族的势力因其成员的无能与腐化而日渐式微,在外家族的政治靠山尽失,最终于朝中失势,落得抄家败亡的结局。 《红楼梦》之所以引人入胜,就在于它于叙事的过程中成功地塑造了30位主要角色和大约400名次要角色,而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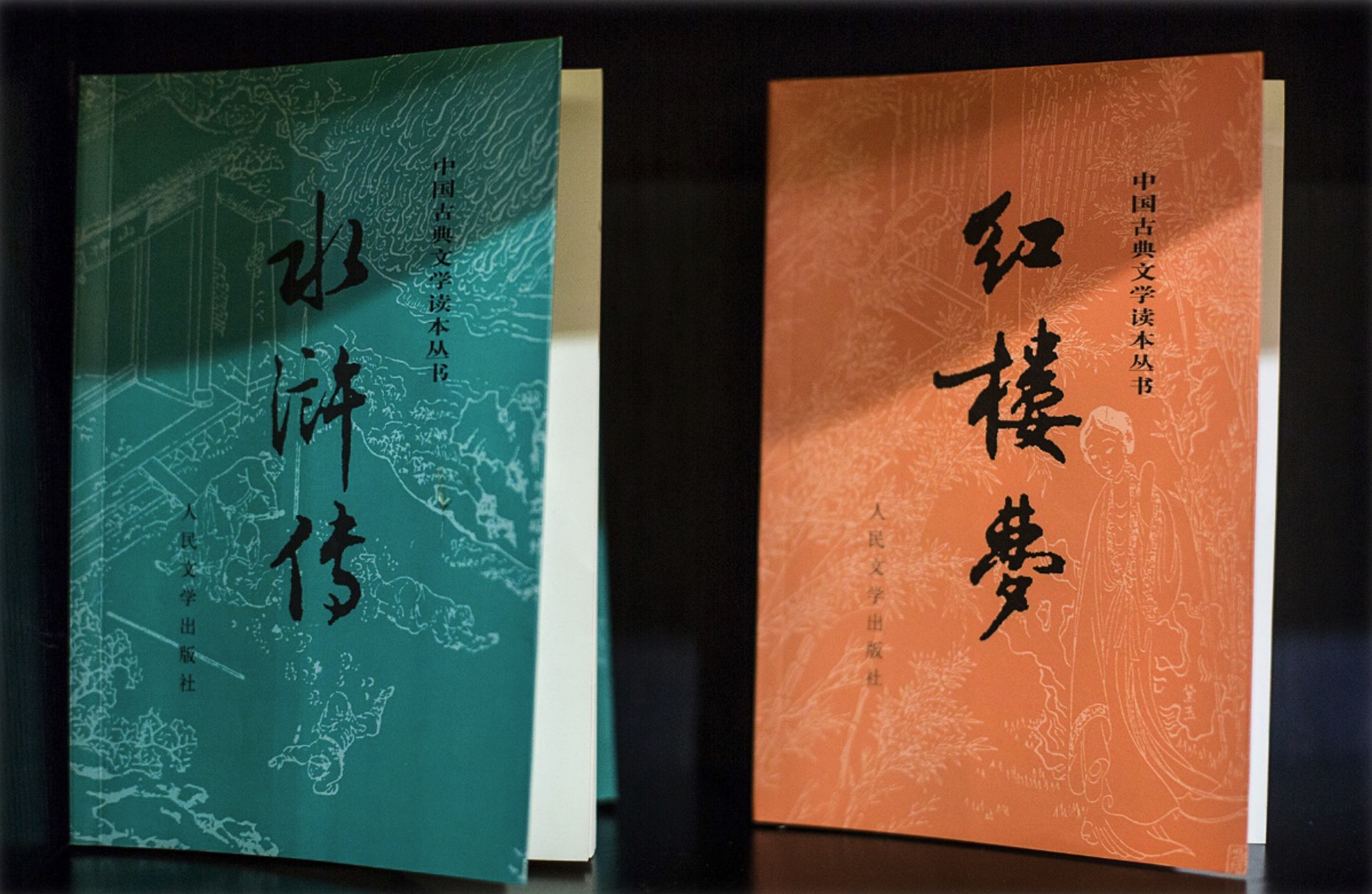
神话渊源
《红楼梦》的另一条主线为男女主角的爱情悲剧,其以中国著名传说故事女娲补天为背景,在120回本的设定中女娲以石补天后剩下了一块石头,此石在吸取了天地精华具有了灵性。之后又恳求偶遇的道士与和尚带它去凡间见识一番。而这块石头曾在赤霞宫充当神瑛侍者,用甘露灌溉过绛珠仙草。后来,这块石头转世成为一名男子,而这株绛珠仙草则转世为一名女子回报前者的灌溉之恩。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贾宝玉即是这块灵石的转世,他因出生口中含了一块宝玉,遂得其名。而那颗绛珠仙草则是女主人公之一的林黛玉的前世。虽然两人相互爱慕,但贾宝玉终因封建礼教迎娶了他的表姐薛宝钗。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贯穿这一故事线。

《红楼梦》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以道教中神仙被贬下凡的主题作为故事框架。在道教的观念中神仙会因各种原因而下入凡间 (Sun,1997),或为教化众生,或为体验疾苦,或为犯错赎罪。但在经历了尘世的历练后,神仙们都会重返天界。基于这种结构的小说会渲染宿命论,相互依赖的共同起源和业力的观点。孙逊(1994)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展现了大众文化的方方面面,如饮食、服饰、园林设计、戏剧、艺术、习俗、娱乐和茶文化。同时其指出小说从天界开始,在凡间展开,最后再回到天界;这就是说业力可以超越前世、今生和来世 (Sun,1997)。在设计故事情节的过程中,作者扩大了故事的承载范围和表现力。如果故事情节仅局限于俗世中各个人物之间发生的事和神话渊源,那将缺少业力和转世轮回的部分,使得整个故事的哲学意义流于表面,不够充分。

女性和婚姻
《红楼梦》中几乎所有的婚姻都是包办婚姻,家族中女性长辈的心结,就是为自己的儿女寻一桩门当户对的亲事。小说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真心相爱,但注定做不成夫妻,因为在奉行一个集体主义的封建社会,婚姻的基础并非两人的爱情,而是双方家庭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显赫的贾氏家族对于社会、政治地位低微的林家,显然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存在。
在曹雪芹所处的年代,尽管中国女性已经摆脱了公然的奴役状态,但人口买卖依然屡见不鲜。穷人家的女儿常常被当做商品买卖:或嫁给有钱人做妾或卖给富裕人家做丫鬟。 《红楼梦》里有两位丫鬟选择了自杀——其中贾迎春的丫鬟思棋因碍于封建礼教,无法与爱人潘又安成婚,撞墙而亡;另一位则是王夫人的丫鬟金钏,因宝玉与之调情的场景被王夫人撞破,被扣上了“不贞”的印记,更要被赶出贾家,最终以死自证清白。自杀是当时女性反抗当时社会不公正对待的一种主要方式。 (Lee & Kleinman, 2000)
道教和佛教的影响
道教对这部小说的影响显而易见。在大观园中,贾宝玉和一群女眷生活在一起,过着怡然自得,不受社会传统制约的生活。他并不恪守儒家教义也不求功名利禄,只想着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同时他也与多位女性角色存在着男女关系。因此,大观园呈现出一半原始时代的各种限制、冲突和痛苦。宝玉拒绝考取功名,也不在乎由功名带来的社会地位与政治身份。这些举动都有悖于儒家提出的追求社会荣誉的观念。他对传统的成长和发展道路感到不屑,因此选择了一种原始的存在状态,或是道家思想描绘的和谐/混沌的状态。他的生活之道令其在朝为官的父亲贾政深感不满,可在面对贾母对宝玉的维护时又无可奈何。但其他任何怂恿宝玉沉溺于“混沌”行为的人都会被他永久逐出贾府。
最终,宝玉被迫接受了长辈们精心安排的婚姻并搬出了大观园,这预示着儒家的训诫开始发挥作用了,而道家的乐土则变成了一座废弃的院落,可见,在封建社会贵族的生活中,道家的价值观无法与主流的儒家价值观相抗衡。然而宝玉却不甘被驯服,他选择了削发为僧,表明佛教有效地实现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妥协。

文学成就
孙逊教授(2004)还指出《红楼梦》是第一部有别于中国“大团圆”式结局的重要小说。早前的中国小说一般都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结局往往以正义一方的胜利与邪恶一方的惩罚而收尾。而《红楼梦》则大胆地描述了一个贵族家庭的兴衰和人物的悲剧命运。
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红楼梦》在此脱离了传统小说的模式。故事中的贾、林二人并非因相互之间的外貌吸引坠入爱河,思想相同才是两人爱情的基础。这与封建社会的传统背道而驰,在封建社会,匹配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是父母和媒人的首要考虑条件。因此小说中的男女主角的爱情终以悲剧收场:林黛玉死于肺病,贾宝玉则出家为僧。
此外,与其他三部由几代人口口相传的传说故事结合历史史实而成的经典著作不同,《红楼梦》是由一位作家创作的,他细心挖掘当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塑造出小说中一个个独一无二、栩栩如生的人物。
之前的文学作品中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女性被贬为次要或微不足道的角色,而《红楼梦》则详细描述了中国女性的生活、希望、志向和情感。如此一来,这部小说成为了第一部客观地剖析中国女性心理的著作。

最后,《红楼梦》没有采用传统文学作品惯用的复杂和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下,展示各个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寻常故事。因为社会定位 (K. S. Yang, 1995, 2006)和关系定位 (Ho, 1998)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点,这种方法或许可以揭示出那个时代下人们的真实心里状态和沟通模式。在语言方面,作者运用了当时北京的方言,便于普通人的理解。
价值观、信念和因果归因
在描述中国贵族家庭日常生活的过程中,《红楼梦》展现了封建中国盛行的价值观、信念和因果归因,尤其是社会倾向模式的各个方面(Yang, 1995)。这些包括重视家庭和睦;团结;荣誉和繁荣;坚持关系形式主义,相互依赖、和谐、宿命主义和决定论;展现对权威的敏感、崇拜和依赖;在乎他人的意见;高度重视声誉和一致行为。此外,《红楼梦》还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
- 尊从儒家礼教、对帝王(天子)绝对效忠。小说中贾宝玉的胞姐贾元春被封为妃,整个贾家将此视作皇室对其的恩赐与荣耀。
- 有别于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贾宝玉喜欢跟女孩子相处,既不专注于研习经典著作,也不渴望考取功名,这让其父苦恼不已。
- 强调等级尊卑。贾母在贾家享有不容置疑的最高权威。无论何时贾宝玉受到父亲的斥责或体罚,丫鬟会立即向贾母求救。贾家为所有人的角色和权利进行了明确划分,从而将人际冲突最小化或掩盖起来。然而,和谐的表面下却涌动着一股强大的暗流,里面充斥着非议、不满和诋毁。
- 尊重阶级制度。在封建中国,贵族和平民百姓、主人和仆人之间有着严格的极限。在这两对二元关系中,如果地位较低的一方言行造次,他们将立即受到严厉的惩罚。从这点意义上说,贾宝玉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觉得自己和丫鬟、仆人都是平等的。
- 尊重知识和文学成就。在《红楼梦》中,年轻人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参加诗社,以诗会友。
- 佛教中的“缘”。三人的爱情纠葛就体现了“缘”。在小说结尾,贾宝玉出家为僧,表明他已经看破红尘,决意挣脱“缘”的束缚。
- 情感克制。封建社会反对人们表露情感,所以喜怒形于色的林黛玉常常不招人喜欢,被看做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心智不成熟的人,而薛宝钗则善于压制自己的情感,她从不公开表示自己对某物或某人的厌恶之情,她成熟的社交能力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主要参考文献
1、孙逊(1994)。 〈中国小说文化述略〉。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3,78-82。
2、孙逊(1997)。 〈释道“转世、谛世”观念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 《文学遗产》,4,69-77。
3、孙逊(2004)。 〈《红楼梦》对于传统的超越与突破〉。 《红楼梦学刊》,1,131-141。
4、Ho, D. Y. F. (1998).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relationship dominance: An analysi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n applicatio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In U. Kim, H. C. Triandis, C. Kagitcibasi, S. C. Choi, & G. Yoon (Ed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pp. 137-156). Saga.
5、Lee, S. & Kleinman, A. (2000). Suicide as resistance in Chinese society. In E. Perry & M.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pp. 221-240). Routledge.
6、Yang, K. S. (1995). 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In T. Y. Lin, W. S. Tseng, & Y. K. Yeh (Eds.), Chinese social and mental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Zhou, Z. (2001). Chaos and the gourd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8、T'oung Pao, 87(4/5), 251-288.
< 原创文章/视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欢迎留言:
请登入/登记成为会员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