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小傳承
本文節選自孫天倫教授著作《中國心理學》,
由陸國權中華文化傳承研究基金研究員沈詩麟編輯審校。
總體背景
《紅樓夢》的抄本最早出現於1754年左右,現流傳的版本分別為80回本與120回本。學界普遍認為前80回是由曹雪芹(約1715 – 約1763)創作的,而後40回則由後人所續寫。如今,與《紅樓夢》相關的藝術作品,包括小說、戲曲、現代芭蕾舞劇、電視劇和電影基本上都是依據120回的版本改編而成的。
《紅樓夢》故事的其中一條主線就是京城四大豪門望族之一的賈氏家族的盛衰興亡。在小說的開篇,賈家受先祖功業的庇蔭,位列京城四大家族之一,但隨著劇情的推進,在內家族的勢力因其成員的無能與腐化而日漸式微,在外家族的政治靠山盡失,最終於朝中失勢,落得抄家敗亡的結局。《紅樓夢》之所以引人入勝,就在於它於敘事的過程中成功地塑造了30位主要角色和大約400名次要角色,而其中的大多數都是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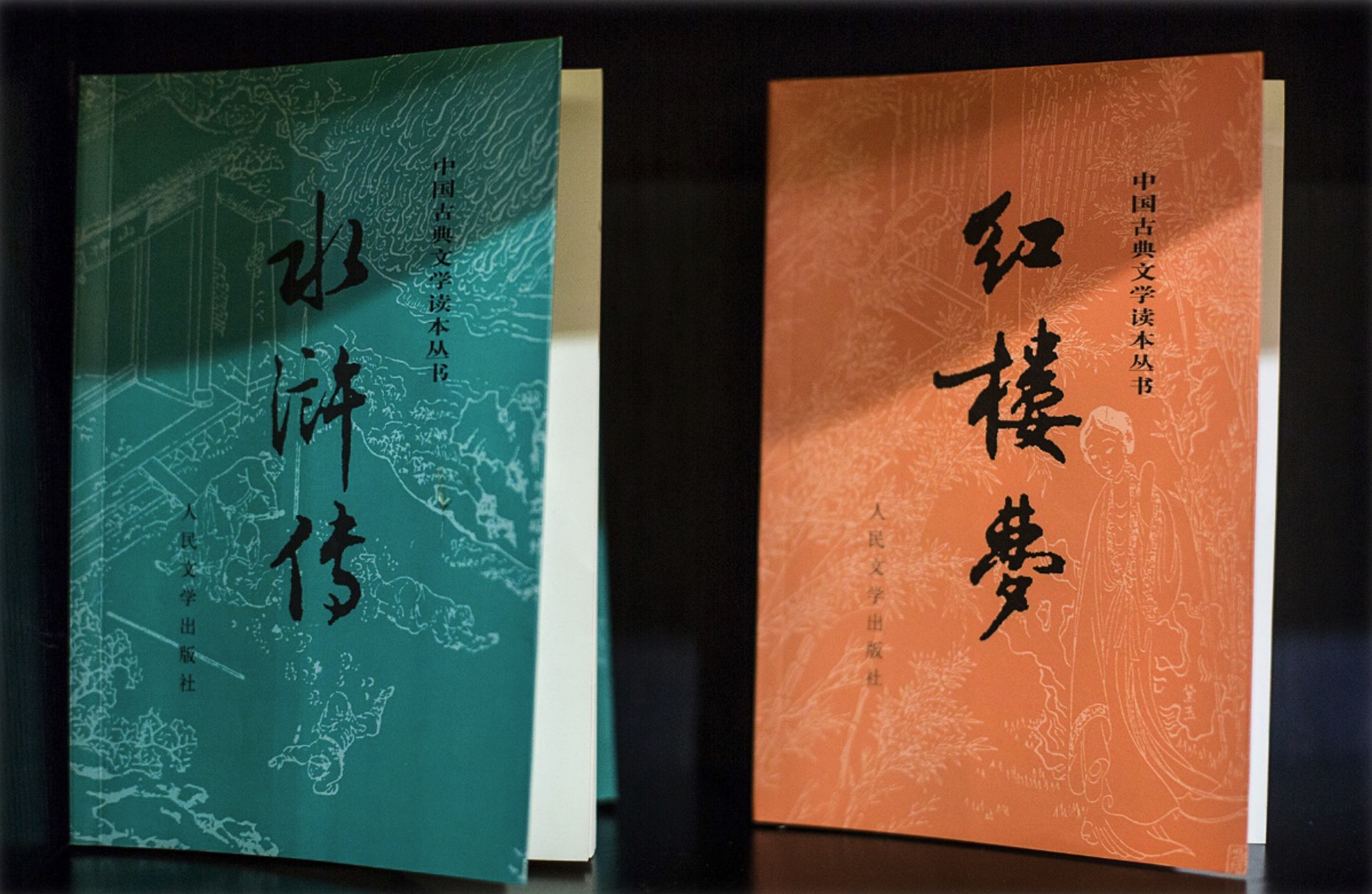
神話淵源
《紅樓夢》的另一條主線為男女主角的愛情悲劇,其以中國著名傳說故事女媧補天為背景,在120回本的設定中女媧以石補天后剩下了一塊石頭,此石在吸取了天地精華具有了靈性。之後又懇求偶遇的道士與和尚帶它去凡間見識一番。而這塊石頭曾在赤霞宮充當神瑛侍者,用甘露灌溉過絳珠仙草。後來,這塊石頭轉世成為一名男子,而這株絳珠仙草則轉世為一名女子回報前者的灌溉之恩。小說中的男主人公賈寶玉即是這塊靈石的轉世,他因出生口中含了一塊寶玉,遂得其名。而那顆絳珠仙草則是女主人公之一的林黛玉的前世。雖然兩人相互愛慕,但賈寶玉終因封建禮教迎娶了他的表姐薛寶釵。三人之間的感情糾葛貫穿這一故事線。

《紅樓夢》被認為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小說以道教中神仙被貶下凡的主題作為故事框架。在道教的觀念中神仙會因各種原因而下入凡間 (Sun,1997),或為教化眾生,或為體驗疾苦,或為犯錯贖罪。但在經歷了塵世的歷練後,神仙們都會重返天界。基於這種結構的小說會渲染宿命論,相互依賴的共同起源和業力的觀點。孫遜(1994)認為《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它展現了大眾文化的方方面面,如飲食、服飾、園林設計、戲劇、藝術、習俗、娛樂和茶文化。同時其指出小說從天界開始,在凡間展開,最後再回到天界;這就是說業力可以超越前世、今生和來世 (Sun,1997)。在設計故事情節的過程中,作者擴大了故事的承載範圍和表現力。如果故事情節僅局限於俗世中各個人物之間發生的事和神話淵源,那將缺少業力和轉世輪回的部分,使得整個故事的哲學意義流於表面,不夠充分。

女性和婚姻
《紅樓夢》中幾乎所有的婚姻都是包辦婚姻,家族中女性長輩的心結,就是為自己的兒女尋一樁門當戶對的親事。小說中,賈寶玉和林黛玉真心相愛,但註定做不成夫妻,因為在奉行一個集體主義的封建社會,婚姻的基礎並非兩人的愛情,而是雙方家庭的政治和經濟實力。顯赫的賈氏家族對於社會、政治地位低微的林家,顯然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存在。
在曹雪芹所處的年代,儘管中國女性已經擺脫了公然的奴役狀態,但人口買賣依然屢見不鮮。窮人家的女兒常常被當做商品買賣:或嫁給有錢人做妾或賣給富裕人家做丫鬟。《紅樓夢》裡有兩位丫鬟選擇了自殺——其中賈迎春的丫鬟思棋因礙於封建禮教,無法與愛人潘又安成婚,撞牆而亡;另一位則是王夫人的丫鬟金釧,因寶玉與之調情的場景被王夫人撞破,被扣上了“不貞”的印記,更要被趕出賈家,最終以死自證清白。自殺是當時女性反抗當時社會不公正對待的一種主要方式。 (Lee & Kleinman, 2000)
道教和佛教的影響
道教對這部小說的影響顯而易見。在大觀園中,賈寶玉和一群女眷生活在一起,過著怡然自得,不受社會傳統制約的生活。他並不恪守儒家教義也不求功名利祿,只想著隨心所欲地享受生活。同時他也與多位女性角色存在著男女關係。因此,大觀園呈現出一半原始時代的各種限制、衝突和痛苦。寶玉拒絕考取功名,也不在乎由功名帶來的社會地位與政治身份。這些舉動都有悖於儒家提出的追求社會榮譽的觀念。他對傳統的成長和發展道路感到不屑,因此選擇了一種原始的存在狀態,或是道家思想描繪的和諧/混沌的狀態。他的生活之道令其在朝為官的父親賈政深感不滿,可在面對賈母對寶玉的維護時又無可奈何。但其他任何慫恿寶玉沉溺於“混沌”行為的人都會被他永久逐出賈府。
最終,寶玉被迫接受了長輩們精心安排的婚姻並搬出了大觀園,這預示著儒家的訓誡開始發揮作用了,而道家的樂土則變成了一座廢棄的院落,可見,在封建社會貴族的生活中,道家的價值觀無法與主流的儒家價值觀相抗衡。然而寶玉卻不甘被馴服,他選擇了削髮為僧,表明佛教有效地實現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妥協。

文學成就
孫遜教授(2004)還指出《紅樓夢》是第一部有別於中國“大團圓”式結局的重要小說。早前的中國小說一般都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觀念,結局往往以正義一方的勝利與邪惡一方的懲罰而收尾。而《紅樓夢》則大膽地描述了一個貴族家庭的興衰和人物的悲劇命運。
在愛情和婚姻問題上,《紅樓夢》在此脫離了傳統小說的模式。故事中的賈、林二人並非因相互之間的外貌吸引墜入愛河,思想相同才是兩人愛情的基礎。這與封建社會的傳統背道而馳,在封建社會,匹配的政治和經濟實力是父母和媒人的首要考慮條件。因此小說中的男女主角的愛情終以悲劇收場:林黛玉死于肺病,賈寶玉則出家為僧。
此外,與其他三部由幾代人口口相傳的傳說故事結合歷史史實而成的經典著作不同,《紅樓夢》是由一位作家創作的,他細心挖掘當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並塑造出小說中一個個獨一無二、栩栩如生的人物。
之前的文學作品中都是以男性為主導的,女性被貶為次要或微不足道的角色,而《紅樓夢》則詳細描述了中國女性的生活、希望、志向和情感。如此一來,這部小說成為了第一部客觀地剖析中國女性心理的著作。

最後,《紅樓夢》沒有採用傳統文學作品慣用的複雜和離奇的故事情節,而是在複雜的人際關係網下,展示各個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尋常故事。因為社會定位 (K. S. Yang, 1995, 2006)和關係定位 (Ho, 1998)是中國文化的突出特點,這種方法或許可以揭示出那個時代下人們的真實心裡狀態和溝通模式。在語言方面,作者運用了當時北京的方言,便於普通人的理解。
價值觀、信念和因果歸因
在描述中國貴族家庭日常生活的過程中,《紅樓夢》展現了封建中國盛行的價值觀、信念和因果歸因,尤其是社會傾向模式的各個方面(Yang, 1995)。這些包括重視家庭和睦;團結;榮譽和繁榮;堅持關係形式主義,相互依賴、和諧、宿命主義和決定論;展現對權威的敏感、崇拜和依賴;在乎他人的意見;高度重視聲譽和一致行為。此外,《紅樓夢》還特別強調了以下幾點:
- 尊從儒家禮教、對帝王(天子)絕對效忠。小說中賈寶玉的胞姐賈元春被封為妃,整個賈家將此視作皇室對其的恩賜與榮耀。
- 有別于傳統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賈寶玉喜歡跟女孩子相處,既不專注於研習經典著作,也不渴望考取功名,這讓其父苦惱不已。
- 強調等級尊卑。賈母在賈家享有不容置疑的最高權威。無論何時賈寶玉受到父親的斥責或體罰,丫鬟會立即向賈母求救。賈家為所有人的角色和權利進行了明確劃分,從而將人際衝突最小化或掩蓋起來。然而,和諧的表面下卻湧動著一股強大的暗流,裡面充斥著非議、不滿和詆毀。
- 尊重階級制度。在封建中國,貴族和平民百姓、主人和僕人之間有著嚴格的極限。在這兩對二元關係中,如果地位較低的一方言行造次,他們將立即受到嚴厲的懲罰。從這點意義上說,賈寶玉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他覺得自己和丫鬟、僕人都是平等的。
- 尊重知識和文學成就。在《紅樓夢》中,年輕人最喜歡的娛樂活動就是參加詩社,以詩會友。
- 佛教中的“緣”。三人的愛情糾葛就體現了“緣”。在小說結尾,賈寶玉出家為僧,表明他已經看破紅塵,決意掙脫“緣”的束縛。
- 情感克制。封建社會反對人們表露情感,所以喜怒形於色的林黛玉常常不招人喜歡,被看做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心智不成熟的人,而薛寶釵則善於壓制自己的情感,她從不公開表示自己對某物或某人的厭惡之情,她成熟的社交能力得到了眾人的認可。
主要參考文獻
1、孫遜(1994)。〈中國小說文化述略〉。《上海師範大學學報》,3,78-82。
2、孫遜(1997)。〈釋道“轉世、諦世”觀念與中國古代小說結構〉。《文學遺產》,4,69-77。
3、孫遜(2004)。〈《紅樓夢》對於傳統的超越與突破〉。《紅樓夢學刊》,1,131-141。
4、Ho, D. Y. F. (1998).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relationship dominance: An analysi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n applicatio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In U. Kim, H. C. Triandis, C. Kagitcibasi, S. C. Choi, & G. Yoon (Ed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pp. 137-156). Saga.
5、Lee, S. & Kleinman, A. (2000). Suicide as resistance in Chinese society. In E. Perry & M.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pp. 221-240). Routledge.
6、Yang, K. S. (1995). 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In T. Y. Lin, W. S. Tseng, & Y. K. Yeh (Eds.), Chinese social and mental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Zhou, Z. (2001). Chaos and the gourd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8、T'oung Pao, 87(4/5), 251-288.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歡迎留言:
請登入/登記成為會員後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