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随笔:由《红楼梦》「蘅芜苑夜拟菊花题」看「大方」诗学观
「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核心思想,立论基础则在于胸襟、人格之「大」,认为「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1,根本原因在于李煜「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2,一己悲欢中寄寓着「天下万世之真理」3。其《文学小言》也提出,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等,非惟「文学之天才」,且具「高尚伟大之人格」,故能成其「高尚伟大之文学」4。王氏推尊《红楼梦》为「彻头彻尾之悲剧」,是「宇宙之大著述」、「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原因也在于曹雪芹「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名字之下」 ,具备普遍象征意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 sup>5从艺术与人生乃至宇宙之关系,道出了审美鉴赏、文艺研究之真谛。遗憾的是,「红学」界盛行一种非文学性的伪「考古」思维,倾向于将《红楼梦》中的艺术形象坐实为某一历史人物,无谓之谈刺刺不休,反败坏了《红楼梦》之「大境界」与「大精神」。当然,客观地看,《红楼梦》艺术境界之「大」,既有海纳百川之势,兼包各色人等;则「红学」论域之「大」,无妨百家争鸣,探赜「索隐」,也是一途。
无论就认识观念而言,还是就实际层面而论,所谓「大/小」关系问题,乃相对待而得以成。换言之,《红楼梦》之为「大著述」,无疑基于众多之「小」。譬如第四十回就借助秋爽斋室内描写这一「小场景」,写出了「大气象」。又如第三十七回写「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这一「小事件」,体现的却是探春以「脂粉」超迈「须眉」之「大心志」;而同回所写「蘅芜苑夜拟菊花题」,则于闲谈式的「小过程」中,呈现了《红楼梦》有关诗学理想层面的「大方」之思。此所谓「大」,亦以「小家气」为衬托:
这里宝钗又向湘云道:「诗题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诗中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了,若题过于新巧,韵过于险,再不得有好诗,终是小家气。6
待她们拟好诗题,湘云抄录完毕,「又看了一回,又问:『该限何韵?』」宝钗应道:
我平生最不喜限韵的,分明有好诗,何苦为韵所缚。咱们别学那小家派,只出题不拘韵。原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乐,并不为此而难人。
诗词之「格律」,包括用韵,固然重要;然而,倘以「格律」为炫技之要务、诗艺之全体,实乃颠倒本末之举。我们看诗歌盛世之唐代,虽不乏精于诗律之高手,但在度量规矩上,整个时代的「格律」观念,却存在一种相对宽松、包容之趋向。初唐元竞的「调声术」,已经开始「简化」沈约以来「四声八病」之科条7,有助于律诗之定型。盛唐殷璠之诗论,更进一步提出「古体、新声」两无妨之主张,以为古诗名家如三曹、七子,「诗多直语,少切对,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而逸驾终存」;在声律方面,以为「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8。如此宏通之论,确能折射盛唐诗坛之大气象,与斤斤计较平仄、韵脚之小家派相比,直是天壤之别。曹雪芹透过上引薛宝钗言论,同样体现了有别于「小家派」、「小家气」的「大方」诗学观念。
这种「大方」诗学观,关键在于「立意清新」。因此,前引宝钗「终是小家气」语后,她紧接着便说:「诗固然怕说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头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词就不俗了。 」到了第三十八回,作者写「林潇湘魁夺菊花诗」,林黛玉所作〈咏菊〉、〈问菊〉、〈菊梦〉,允为众作之冠,原因是「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恰是此种「大方」诗学观之具体展现。诗之「新」境,要在脱「俗」,岂能一味拘执于「菊花」物象本身,而宜「景物/人事」兼顾、「虚/实」并举,乃成其「大」。这一点,湘云、宝钗议论诗题时,已经提到:
如今以菊花为宾,以人为主,竟拟出几个题目来,都是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实字便用「菊」字,虚字就用通用门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赋事,前人也没作过,也不落俗套。赋景咏物两关着,又新鲜,又大方。
她们以「菊」为吟咏对象,一口气拟出十二题,依次为:〈忆菊〉、〈访菊〉、〈种菊〉、〈对菊〉、〈供菊〉、〈咏菊〉、〈画菊〉、〈问菊〉、〈簪菊〉、〈菊影〉、〈菊梦〉、〈残菊〉。湘云认为「十二个便全了」,宛如以「菊」为题材之画册、菊谱;宝钗更觉得以〈忆菊〉「起首」、「末卷便以〈残菊〉总收前题之盛。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粗略地看,无非两个年少女子讨论一件小事,仔细体会,其间则有「大气象」在:脱「俗」之为「大」,贵在清新有创意,已如前述;此「十二」之数、「三秋妙景妙事」,何尝不关涉天地运行、四季时序以及人间情事之「大」?
按,「小」中寓「大」,细微处寄「大精神」,此乃中国传统艺术哲学思想之一端。鸢飞鱼跃,物小而生气淋漓;咫尺含万里之势,乾坤之「大」纳于方寸之间9。 《红楼梦》作为一部「巨著」,其艺术世界之「大」,不仅体现在吞吐大荒、涵摄前世今生之大思维与大智慧,也体现在以日常琐事包蕴「大意义」、呈现「大魅力」方面,用第三十八回末尾的话来说,就是:「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讲的是宝玉及众姊妹「持螯赏桂」所作之诗,故事内容确实不「大」,而其「大意、大才」之说,移以譬喻曹雪芹及其《红楼梦》之特点,不亦宜乎?
冶寒斋主
草于甲辰岁重阳日
(本文原载于WeChat公众号「海日江春读书天」,2024年10月11日)
注释:
1.王国维撰,彭玉平疏证:《人间词话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页428。
2.王国维撰,彭玉平疏证:《人间词话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页364。
3.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着:《美学三境》,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页2。
4.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着:《美学三境》,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22年,页19。
5.洪治纲编:《王国维文选》,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23年,页149。
6.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4版,页503。本文引用《红楼梦》原文,均据此版本,下不出注。
7.参见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天卷《调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页156-167。
8.殷璠编:《河岳英灵集》,傅璇琮等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页156-158。
9.参见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宗白华著:《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80-98。
< 原创文章/视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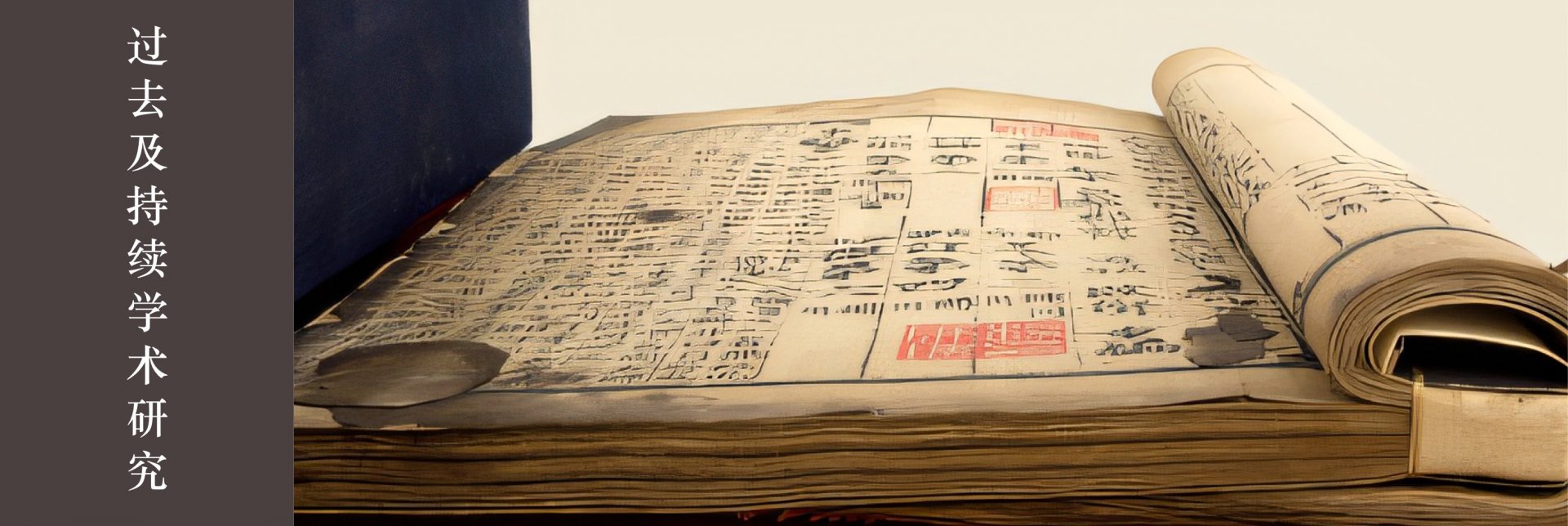



欢迎留言:
请登入/登记成为会员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