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寒斋学术随笔:《红楼梦》贾政形象三题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末尾写道:「那空空道人听了,仰天大笑,掷下抄本,飘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说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併閲者也不知。不过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为作者缘起之言更转一竿头云: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1后四十回虽属续作,聚讼不休,但「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这一「更转」之言,无疑有助于提醒读者:红楼一梦,非唯见载书中,看书之人,论争诸家,何曾不在「梦」裡。按佛理说法,「痴」者,「无明」也,俗谓「愚昧无知」,与「贪、瞋」并称「三毒」。吾等读书之馀,或聊资閒谈,或搦管评说,亦不过「痴」人说「梦」尔。此或为《红楼梦》这一古今「大」悲剧意义之所在。换言之,从《红楼梦》书中悲剧人物身上,总能见出个体生活、社会现实乃至整个人类之悲剧幻影。
试以书中人物贾政为例。按照《红楼梦》第一回的说法,作者之本意,乃着重书写「当日所有之女子」,不令「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随世「泯灭」,因而,除了「通灵」之宝玉,包括贾政在内的其他「鬚眉浊物」,自然不是重点人物。但是,贾政同样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悲剧形象。何谓「悲剧」,各家说法见仁见智,各表「悲剧」内涵之一端。窃以为「悲剧」作为人类共同之命运,大而言之,不外一「慾念」而已;一生为二,即所谓「理想/现实」矛盾冲突之悲;具体而言,其基本内涵,或有两层:一者,一己之愿念,难以见容于现实社会、不被理解与接受之悲;二者,天生气性难以尽情发挥,或者自设牢笼之悲。贾政也是二「悲」兼备者。
学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论及贾政似多贬斥。或曰:『贾政者,假正也。』或曰:贾政是『典型的伪君子』、『不学无术的欺世盗名的假道学』。」2此种评价,显然不合实情,故时有论者撰文反思3。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内涵遭遇读者之误解,尤其是近乎「恶諡」式之曲解,不仅是作者之悲哀,也是人物形象本身之悲哀。即便在文学世界裡,贾政之良苦用心,同样遭遇不解乃至怨怒。最典型的例子,无过于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一事,也就是一些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选段「宝玉挨打」,写得真是异彩纷呈,夺人魂魄。或以为此一情节反映了「封建卫道者」贾政与「封建叛逆者」贾宝玉之间第一次剧烈的「面对面的冲突」,「非常真实、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丑恶」。如此理解这一情节之「悲剧」义,虽然不无道理,但显然失于粗浅。因而,有论者从传统文化、当下现实的双向角度予以阐释:「贾政对宝玉也并非无真情,说『试才』时脂砚斋在『贾政「一声断喝,无知的孽障」』下批之道:『爱之至,喜之至,故作此语。』但这种爱子之真情,却是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贾政爱子真情之所以被扭曲的文化原因⋯⋯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望子成龙文化心理在作怪⋯⋯当儿子难以成龙,『计深远』而难以奏效时,爱子之真情就异化成『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逼子成龙』的扭曲心态,如贾政之所为⋯⋯而放眼当今中国之为父者群体中,继承贾政之衣鉢者大有人在。他们之中,达者,产生出子肖于父的肖子文化心理;穷者,则衍变出望子胜于父的补偿心理。」4如此理解贾政形象之悲剧,无疑更进一层。不过,仔细玩味,似犹有未足,无妨补说。窃以为贾政「笞挞」宝玉这一事件之「悲剧」义,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贾政身为人父,同样怀有「子不教,父之过」一类的责任感,觉得宝玉「在家不读书也罢,怎麽又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来」、「致使生出这暴殄轻生的祸患」。此间不无偏听、误会之处,但情急之下,「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等语,只喝令『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当他发现自己一番苦心不仅不被儿辈理解、认同,而且牵出伤天害理事体时,难免恼羞成怒,「一叠声」地喊「拿宝玉」、「立刻打死」。此其为父角色之悲也。
其二,在家族关係中,贾政一心想的是「教训儿子,也为的是光宗耀祖」,可是,他自己作为儿子,却不得其母的理解——痛打宝玉,因其「不肖」与「不孝」;结果,在贾母目前,贾政自己却同时成为「不孝」之子,故贾母训斥他:「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怎麽教训你来!」贾政自己也深感无颜面对祖上:「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所以,贾母一到,贾政狼狈异常,一会儿「躬身陪笑」、「又陪笑」,一会儿「忙跪下含泪道」、「忙叩头哭道」,终至于「灰心,自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由此看来,宝玉挨打一节,固然可以看作父子之间剧烈的「面对面的冲突」,其实更是贾政内心多种角色的剧烈冲突。人在各种家庭关係中,很多时候难免遇上类似之内心冲突。即此而言,贾政之悲剧,似具有一种普遍象徵意味。
其三,引申开来,这一情节实际上也透露了贾政一生悲剧之缘由:贾政不属于《红楼梦》着力表现的、最重要的那一等人物,但相比于贾府裡任一个人物,他所面对的,无疑是更多更複杂的各种「关係」,譬如朝廷、王爷、地方官、亲戚、宗族、母亲、妻妾、儿女等等。这种种「关係」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或明或暗地笼罩、限制着主体意愿,令其无法如贾赦、贾珍、贾琏乃至王熙凤、薛蟠那样任性而为。因此,第三回写林如海称贾政「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仕宦之流」;又有作者议论:「这贾政最喜的是读书人,礼贤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风。」可见祖上荣光带给贾政的,更多的是一种自律与上进精神。但其结局,却一如论者所言:《红楼梦》「生动地展示出贾政事与愿违、 动辄得咎的人生两难困境:忠臣未做成,严父没当好,家长不治家,孝子未尽孝,整个是一个处处碰壁的人生悲剧」5。这是就贾政以家族命运荣誉为己任这一愿念与现实相冲突而言,所以到了「锦衣军查抄宁国府」之时,贾政「独自悲切」,感慨「我贾家何至一败如此」、「种种罪孽,叫我委之何人」、「家门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侄,所以至此」。细参此间之「悲剧」义,又另有一层:以家族命运荣誉为己任之强烈愿念不能实现,固然可悲;復因此而抑制了自家禀赋中比宝玉还乖张任诞之天性,同样可悲。第八十四回写贾母当众说他:「想他那年轻的时候,那一种古怪脾气,比宝玉还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妇,才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儿。」此回属续作,大体上切合贾政性情之实,因为第七十八回原作中,即有类似说法:「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这「诗酒放诞」,彷佛魏晋名士阮籍、嵇康、刘伶乃至陶渊明之风流。但是,贾政成人立家后,「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儿」,逐渐扛起护持宗族荣光之大任,天生气性只得隐藏于内,难得发挥。这无疑也是「心灵扭曲」之人生「悲剧」义。
人生于天地牢笼、世间尘网中,不如意、难遂心事十有八九。第七十六回林黛玉与史湘云聊天,有几句话颇在理:「湘云笑道:『得陇望蜀,人之常情。可知那些老人家说的不错。说贫穷之家自为富贵之家事事趁心,告诉他说竟不能遂心,他们不肯信的;必得亲历其境,他方知觉了⋯⋯』黛玉笑道:『不但你我不能趁心,就连老太太、太太以至于宝玉、探丫头等人,无论是大事小,有理无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如此说来,贾政种种不遂心之悲剧,就像李白所慨叹「人生在世不称意」一样,直可视如人间万古千秋、四海十方所同者矣⋯⋯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部分,有一大段文字,写贾雨村阔论「天地生人」之道,重点讲了天地间「所馀之秀气」如何与「残忍乖僻之邪气」偶尔相遭遇,「正不容邪,邪復妒正,两不相下⋯⋯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禀受此「正邪两赋而来」者,或为「情痴情种」,或为「逸士高人」,或为「奇优名倡」,往往兼备「聪俊灵气之气」与「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作为典型例证,包括了许由一类的高士,陶渊明、阮籍、嵇康、刘伶等也赫然在列。由于史湘云性豪爽,「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又宣称「『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因此,学界多注重将此一形象与魏晋名士风流、曹雪芹性情特点结合起来讨论6。从贾雨村的言论看,贾政显然不属于这「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论贾政者,亦少涉及「名士风流」一类话题。不过,细细品味,其实不难发现贾政这一艺术形象与魏晋名士,尤其是陶渊明相彷佛之处。择其要者,有如下四端。
其一,在面对祖上荣光方面,二者具有相同的责任意识。从家族史角度看,有趣的是,陶氏一族,以军功名世,尤其是陶渊明曾祖陶侃,勋业卓着,被封为长沙公;《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祖上起家也是行伍,驰骋疆场,出生入死,受封为宁国公、荣国公。从现世人生及其结局看,贾政与陶渊明自然不能相提并论:前者认真地奔波于仕途,虽经曲折,最后仍为官身,且得圣旨而承袭「荣国公世职」;后者屡仕屡隐,最后一赋「归去来兮」而诀别宦海。但是,完整的人生,毕竟由两面构成,可见者形迹,难见者心性。二者之间,或内外相符,或表里不一,波诡云谲,所谓「人心惟微」,宜含此义。依此寻思,贾政与陶渊明之间,又不无相通之处。
譬如,贾政颇以护持、弘扬祖上荣光为己任,光宗耀祖乃其一生行事之鹄的,为人亦「大有祖风」。陶渊明虽以逸民高士、「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垂范千古,但从他传世的文字裡,也不难见其家族荣光以及由此带来的紧迫感。笔者曾于多年前撰写一文,专门讨论陶渊明诗文创作与其「家族勋业传统」之关係7。我们看他写的〈命子〉诗,首先就从「悠悠我祖,爰自陶唐」说起,中间历数陶氏家族之勋功德业,尤其赞颂其曾祖、东晋重臣、长沙公陶侃:「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后面则谈及自己不能发扬祖上勋业传统之愧疚:「嗟余寡陋,瞻望弗及。」8即便如此,后人也觉得陶渊明是能够继承家族风规者9。陶渊明屡次入军幕,〈荣木〉诗自我鞭策:「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10均体现了对祖上名臣陶舍、陶侃勋业的高度推崇与敬仰。因此,贾政、陶渊明在践行家族勋业传统精神方面,隐显有别,选择的人生道路也不同,但钦服于宗族风规、将个人置入家族历史之自觉意识,又何其相似。
其次,在挂怀家族未来方面,贾政、陶渊明看似截然相反,实则不无一致处,主要体现在如何对待儿辈之学业上。陶渊明以淡泊高情闻名于世,但对于儿女学业,同天下父母心一样,也无法彻底洒脱起来。杜甫就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原因之一则在于「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11。前引〈命子〉诗之写作,即缘于长子降生、取名寄意之事,在大篇幅回顾家族历史之后,言归正传:一谓自己「顾惭华鬓,负影隻立」,二谓「三千之罪,无后为急」,如今孩儿出世,无愧于传宗接代之孝心,且寄予厚望:「温恭朝夕」;「尚想孔伋」;「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初为人父,期待甚切,希望儿子能够秉持儒家为人准则,朝夕温和恭敬,如孔伋子思那样,成为肖孙;严以律己,成人成材。陶渊明说,天下为人父母者,大凡都怀有此心:「凡百有心,奚特于我。」12以此「心」看贾政之教育子弟,不难理解何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说有何不同,主要在于:贾政、陶渊明虽然都从家族角度热切期盼子孙务正业、守德行,但确有固执、潇洒之别。
陶渊明说,如果孩儿实在不成材,实属无奈,何必强求:「尔之不才,亦已焉哉!」13贾政不同,对于宝玉,「望他成人性儿太急了一点」14,要求严苛,必须顺从其意愿,且严加管教,所以他特别叮嘱宝玉业师贾代儒:「倘或不听教训,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管教他,才不至于有名无实的白耽误了他的一世。」由此可见,贾政、陶渊明在教子观念上,其实都渊源于儒门传统,德行、学业皆如此。不同之处在于:陶渊明不乏宽容的馀地,贾政则无可商量,以为子必遂父愿。当然,到了贾政年迈之时,也终于明白了一点,第七十八回有言:「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况母亲溺爱,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到后来续书写「锦衣军查抄宁国府」,贾家经此大风波,贾政对宝玉的心态,居然更转一层,如第一百二十回所言:「众人道:『宝二爷果然是下凡的和尚,就不该中举人了。怎麽中了才去?』贾政道:『你们那裡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裡的精灵,他自具一种性情。你看宝玉何尝肯念书,他若略一经心,无有不能的。他那一种脾气也是各别另样的。』说着,又叹了几声。」这种心态,与陶渊明〈责子〉诗所言,倒不无契合了:「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15孩儿们不爱读书文术,贾政最后以为这是「贾门之数」,陶渊明说这是「天运」,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其三,陶渊明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16;又说「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17。贾政也是「自幼酷喜读书」,几成其一生之情结:第十七至十八回写「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政与众人经过「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之所,即后来名为潇湘馆者,文中写道:「贾政笑道:『这一处还罢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第七十一回写贾政在外为官数年,因「赐假一月在家歇息」,除了「母子夫妻共叙天伦庭闱之乐」,其他「一应大小事务一概益发付于度外,只是看书⋯⋯」此与第四回写贾政「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遥相呼应。陶渊明一众儿辈「不好纸笔」与「文术」,贾府子弟像贾珍「那裡肯读书」、贾琏「也是不肯读书」的;在众人眼中,宝玉更是「顽劣异常,极恶读书」。与此相比,陶渊明、贾政皆好读书,相似之处更值得关注。
陶渊明、贾政之好读书,均非外在力量督导、管制之结果,而是本乎天性志趣。与此相关,二人均不擅家庭俗务,拙于经营,疏懒之意显然。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序〉坦言:「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生生所资,未见其术。」18他虽然深知「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19,「民生在勤,勤则不匮」20,但又明白「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21,以适意为尚,懒于计较一家生计。贾政长于富贵之家,虽无匮乏之忧,且「训子有方,治家有法」,但「族大人多」,「公私冗杂,且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馀事多不介意」。就连起造大观园这样的重要事务,第十六回也是这麽写:「贾政不惯于俗务,只凭贾赦、贾珍、贾琏、赖升、林之孝、吴新登、詹光、程日兴等几人安插摆佈。下朝閒暇,不过各处看望看望,最要紧处和贾赦等商议商议罢了。」后四十回续书中,也提到「众人知贾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着急」;又说「贾政本是不知当家立计的人」。如此疏于家政管理,最后他自己也后悔不迭,因为一经锦衣军抄家,表象繁华背后的亏空一併暴露无遗,第一百零六回:「贾政不看则已,看了急得跺脚道:『这了不得!我大量虽是琏儿管事,在家自有把持,岂知好几年头裡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为什麽不败呢!』」面对贾母,也不敢隐瞒这一实情:「昨日儿子已查了,旧库的银子早已虚空,不但用尽,外头还有亏空⋯⋯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儿了。」据第一百零七回所述,贾政如此「不知理家」,倘非皇帝开恩,念他「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属勤慎」,差一点儿连自身也要被处以「治家不正之罪」。与陶渊明不善经营生计而令儿辈「幼而飢寒」22,或全家「夏日抱长飢,寒夜无被眠」23境况相比,贾政不知理家之恶果,显然要严重得多。
其四,陶渊明的赋归园田与贾政的「归农之意」24。陶渊明〈归园田居〉开篇即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25意在表明个人天性适于山林田园,而非官场仕途。但是,由于名利思想传统的影响,包括家族风规之熏陶,仍自谓「勐志固常在」26;或者出于生计之需:「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27或如〈与子俨等疏〉所言:「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28但终究心繫田园,即便身在宦海,陶渊明也常惦念静好之园林:「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29或曰:「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30因此,在「仕/隐」之间,陶渊明有过屡次徘徊,但佔据主导地位的,则是隐居田园之心志,最后彻底告别仕宦,赋归田园。
贾政与陶渊明的不同之处,乃其人生之旅始终奔走于仕途。《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部分就提到:「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临终时遗本一上……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续书第一百二十回则这样写道:「贾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说:『大老爷大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说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书,能够上进。朝裡那些官儿难道都是城裡的人麽?』」又说:「提起村居静养,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报耳。」对比原作、续书,一头一尾两端文字,意味深长,因为其间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贾政」之名从第一次出现到最后一次收场,都在事与愿违的悲剧之中——原本心愿是走科举一途,结果额外受恩,领「主事之衔」;心中一直怀想「村居静养」境界,却因「受恩深重」无法脱身。稍加观察,可知「莫说村居不好」,确非贾政违心之言,第十七至十八回有两处或可体现这一点:
一处写众人游走于大观园中,「一面走,一面说,倏尔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牆,墙头皆用稲茎掩护。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裡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熘青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辘轳之属。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漫然无际」,宛然一幅陶渊明笔下的园田居图:「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簷,桃李罗堂前。」31难怪贾政见了,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𨯳,此时一见,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我们且进去歇息歇息。」另一处写众人「步入茆堂,裡面纸窗木榻,富贵气象一洗皆尽。贾政心中自是欢喜。」当他听宝玉说此处「不及『有凤来仪』多矣」,随即训斥道:「无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那裡知道这清幽气象。终是不读书之过!」所谓「清幽气象」,便指山林之趣,洗尽富丽铅华,茅堂木榻,近似村居。综合此类描写,大体可知贾政恰如陶渊明笔下的「恋旧林」之「羁鸟」、「思故渊」32之「池鱼」,内心怀着一份「归农」、「村居」之情愫,无奈身在宦海,沐浴天恩,欲归而不得。因此,虽说陶渊明、贾政都有仕宦、村居两种心念,但结局却大相迳庭:陶渊明最终摆脱「误落」之「尘网」,在经历「久在樊笼裡」之后,终归「復得返自然」33;而贾政除了年少时「古怪脾气」、「诗酒放诞」,「成人」之后却难得返归此一天性,因此,村居归农一类的自由生活,也就成了其内心深处的理想天国34,由此又不难见出陶渊明之影子。
总而言之,表面上看,陶渊明乃高蹈隐逸之士,贾政则属于宝玉所深恶的「蠹禄」之流,似不宜同日而语。然而,无论是历史上的出类拔萃者,抑或是小说中鲜活生动之人物形象,在複杂人性、幽微人心层面,自有相通之处。细细体会,可知贾政这一形象中,其实蕴含着类似陶渊明精神的若干侧影。据《红楼梦》第八回,贾政书斋名「梦坡」,可见其如何神往苏东坡那样的洒脱旷怀,而苏轼是极其推崇陶渊明的。此一细处,或许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贾政与陶渊明精神之关係,进而更深入地解读贾政这一形象内涵。
前文提到的贾政「梦坡」书斋,具体情节见于《红楼梦》第八回:贾宝玉想起养病在家的薛宝钗,「意欲去望他一望」,因担心路上「或可巧遇见父亲」,于是「宁可绕远路」。众嬷嬷跟随着,偏遇见了贾政门下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老嬷嬷因问:「二位爷是从老爷跟前来的不是?」或许二人也知宝玉怕见贾政,便应道:「老爷在梦坡斋小书房裡歇中觉呢,不妨事的。」这原本是说给宝玉听的,重点在「歇中觉、不妨事」;脂砚斋关注的重点则是斋名,故曰:「妙!梦遇坡仙之处也。」坡仙即东坡居士苏轼。
一般而言,人们很难将贾政与苏轼联繫起来,原因之一,在于未必留心《红楼梦》文本细微处,且往往先行接受了「贾政」即「假正经」35一类的论家成见。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贾政之言行及其性格整体特点,大体如作品中写到的:「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朝乾夕惕,忠于厥职」,「兢兢业业,勤慎恭肃」;「这般古执」;「古朴忠厚」;「居官尚属勤慎」;「贾政最循规矩」、「纯厚成性」、「贾政忠厚」。总之,属于比较古板、严正乃至固执类型。这与读者心目中洒脱旷达、才情横溢的苏轼形象,反差甚大,难以相提并论。
不过,「梦坡斋」之「梦」,用笔精细,值得玩味。此处所谓「梦」,无妨理解为「日有所思故夜有所梦」之「梦」,属于虽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的一种愿念或理想。如此揣测,应该符合贾政内心实情。因为自其禀赋而言,贾政自具近似苏轼那样放旷不羁之气性。第四回写他「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第七十八回说他「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怎奈长大成人,家族、社会、官场等责任佔据了主导地位。此即贾母所言:「你这会子也有了几岁年纪,又居着官,自然越历练越老成。」与此「老成」相对的,则是其早年展露的天性:「想他那年轻的时候,那一种古怪脾气,比宝玉还加一倍呢。」当「潇洒、放诞、古怪」天生禀性逐渐退隐至内心深处而难以发泄时,以「梦」的形式自我补偿,何等契合人类一般心理规律。因此,贾政书斋题曰「梦坡」,寓意幽微,缘起则在于一己内心愿景。
又,苏轼放旷不羁,诙谐幽默乃重要表现之一。贾政一向不苟言笑,严正恭肃,但天性偶一流露,亦属本色而非「假作」。例如第七十五回写中秋之夜贾府载笑载言,「贾政见贾母喜悦,只得承欢」,凑趣说了一个笑话,才说了一句「一家子一个人最怕老婆的」,「大家都笑了。因从不曾见贾政说过笑话」,偶露峥嵘,恰是其内心真面目之体现。难怪脂砚斋对此赞叹有加,一曰「竟能使政老一谑,真大文章矣」;再曰「这方是贾政之谑,亦善谑矣」;又曰「偏写贾政戏谑,已是异文」。可惜的是,他虽然有此天赋,却因「越历练越老成」,终究不能如东坡那般逍遥适性。当然,也算难能可贵,因为贾政虽「老成」持重,却并未泯灭其天性。书斋之「梦坡」,得其宜也。
与此「忠厚」品质相关的是,贾政治家为官均认真严正,以至于固执、古板。这一点,与苏轼之「不合时宜」,亦相彷佛。第九十九回「守官箴恶奴同破例」部分,贾政与管门的李十儿有一段对话,颇能说明这一点:
李十儿道:「百姓说,凡有新到任的老爷,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钱的法儿⋯⋯所以那些人不说老爷好,反说不谙民情。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爷最相好的,他不多几年已巴到极顶的分儿,也只为识时务能够上和下睦罢了。」贾政听到这话,道:「胡说,我就不识时务吗?若是上和下睦,叫我与他们猫鼠同眠吗。」
对话之起因,是贾政离京,「往江西监道」,严守官箴,以「做好官」、「当清官」自期,并不懂得「外省州县折收粮米勒索乡愚这些弊端」,也不明白一干随从衙役盼着「主人放了外任」以便狐假虎威、「在外发财」之私心,结果「便觉样样不如意」。李十儿试图晓以利害关係,告诉贾政:「那些书吏衙役都是花了钱买着粮道的衙门,那个不想发财?俱想养家活口。」而贾政「这位老爷呆性发作,认真要查办起来,州县馈送一概不受」。这是贾政任地方官「不合时宜」处。其实,即便在家庭内部,他又何尝合时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一事中,贾政的万端慨叹:「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训一番,又有众人护持。」听了王夫人的哭诉,他又「不觉长叹一声,向椅子上坐了,泪如雨下」。或许正因如此「不合时宜」,所以历来读者更同情的是惨遭笞挞之苦的宝玉以及护着他的贾母、王夫人,而未必给予贾政哪怕一丝之「同情的理解」。
第八十二写宝玉再次入家塾念书,贾代儒曾这样劝勉他:「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好生记着我的话。」贾政处处不合时宜,正是「成人不自在」的典型体现。在世人看来,至少从作品中的思想境界看,苏轼似乎达到了「成人」又「自在」的境界。果真如此,则贾政虽然因「不自在」而自我屏蔽了潇洒天性,但是,借助「梦坡」这一书斋名号,不也在努力固守自己的那份禀气吗?总之,贾政的「不自在」,其实也是众生现实境况的一面镜子36。「梦坡斋」三个字,启人深思:如何于「不自在」的生命旅程中给个体留一方相对「自在」的理想空间?
行文至此,出于好奇心,上网络搜寻了一番,惊讶地发现,曹雪芹看似不经意地提及的这个「梦坡斋」,勾起不少「红迷」的强烈「索隐」兴趣,大体按照「谐音」读法,将「梦坡斋」一名「翻译」为「梦破哉」或「梦婆灾」,进而「侦探」各种历史政治或人物命运之「隐喻」,令「梦坡斋」也显得「热闹」起来。读罢这些长短不一的网文,又想起《红楼梦》中的那副联语:「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既然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乃至思维方式原本遵循「真/假、有/无」互存、对转原理,何不更进一层着想:「隐」处或即「显」处、「假」相或有「真」义?即便如流行甚广的「贾政,假正经也」之说,为何不能再反转过来理解:表面「假正经」,或许恰恰预示着内裡之「真性情」。如此想去又想来,越发觉得「梦坡斋」三字,意味确深长,值得玩味一番。
1.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4版,页1605。本文引用《红楼梦》原文,均据此版本,下不出注。
2. 吕立汉:〈封建末世正统文人的艺术写照——贾政形象试论〉,《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1期,页243。
3. 如黄炽〈一个真贾政〉,《齐鲁学刊》,1987年第2期;高时阔〈论贾政亲子之情的异化与回归〉,《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1辑;贾穗〈一个被曲解的人物——贾政〉,《海南师院学报》,1993年第2期;关四平〈无可奈何花落去——论贾政的人生悲剧及其文化意藴〉,《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辑;吕立汉〈封建末世正统文人的艺术写照——贾政形象试论〉,《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1期。
4. 关四平:〈无可奈何花落去——论贾政的人生悲剧及其文化意藴〉,《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辑,页150-151。
5. 关四平:〈无可奈何花落去——论贾政的人生悲剧及其文化意藴〉,《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辑,页136。
6. 如:吕啓祥〈湘云之美与魏晋风度及其它——兼谈文学批评的方法〉,《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2辑;薛瑞生〈是真名士自风流——史湘云论〉,《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3辑;张丽〈红楼人物史湘云的话题性及其名士风度解读〉,《明清小说研究》,2020年第1期;俞晓红〈「湘云醉眠」与魏晋名士风流〉,《学语文》,2021年第1期。
7. 参见拙文:〈抚剑风迈:从〈命子〉诗看陶渊明与家族勋业传统之关係〉,《红岩》特刊《重庆评论》,2019年第2期,第25-36页。
8.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27-28。
9. 如《陶诗汇注》之〈命子〉诗夹注引赵泉山曰:「靖节之父,史逸其名⋯⋯惟〈命子〉诗曰: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其父子风规盖相类。」 认为陶渊明与其父一脉相承的家门风气,与长期以来形成的陶渊明形象特徵相一致。
10.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页16。
11. 杜甫:〈遣兴五首〉其三,杜甫着,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563。
12.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页28-29。
13.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页29。
14.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第八十一回塾师贾代儒对宝玉说:「如今论起来,你可也该用功了。你父亲望你成人恳切的很。」。
15.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页106。
16.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页175。
17.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页133。
18.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159。
19.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84。
20.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25。
21.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69。
22.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187。
23.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49-50。
24. 有关贾政的「归农之意」,关四平〈无可奈何花落去——论贾政的人生悲剧及其文化意藴〉一文曾论及,虽未明确以陶渊明思想为分析角度,参考价值却不言自明。《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辑,页143-144。
25.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40。
26.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页138。
27.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页159。
28.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页187。
29.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页74。
30.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页75。
31.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页40。
32.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页40。
33. 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页40。
34. 具体表现就是,只能在公务之暇,「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4版,页66。
35. 俞平伯:「贾政者,假正也,假正经的意思。书中正描写这麽样一个形象。」俞平伯:《红楼梦小札》,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页35。
36. 李白所谓「人生在世不称意」,倒也道出天下人「不称心」之共同悲剧,一如「不自在」之意也。《红楼梦》第七十六回林黛玉对史湘云说的几句话,意思与此相近:「不但你我不能趁心,就连老太太、太太以至宝玉、探丫头等人,无论事大事小,有理无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况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4版,页1065。
< 原创文章/视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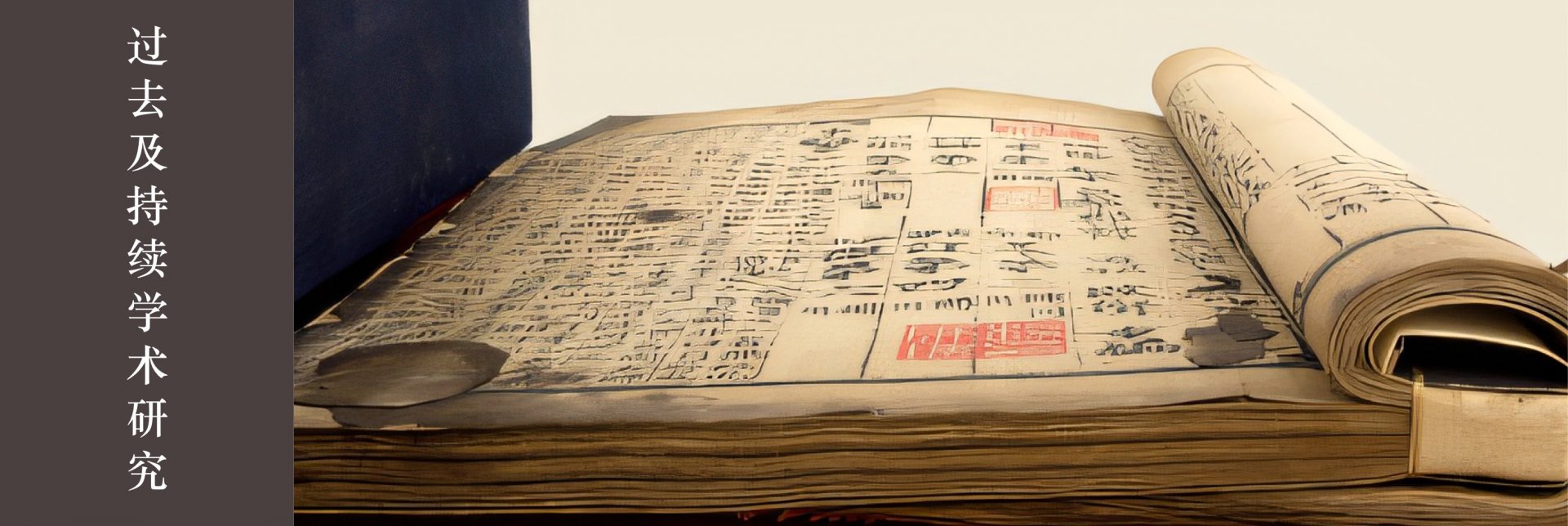



欢迎留言:
请登入/登记成为会员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