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賈政形象三題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末尾寫道:「那空空道人聽了,仰天大笑,擲下抄本,飄然而去。一面走著,口中說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併閲者也不知。不過遊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為作者緣起之言更轉一竿頭云: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1後四十回雖屬續作,聚訟不休,但「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這一「更轉」之言,無疑有助於提醒讀者:紅樓一夢,非唯見載書中,看書之人,論爭諸家,何曾不在「夢」裡。按佛理說法,「癡」者,「無明」也,俗謂「愚昧無知」,與「貪、瞋」並稱「三毒」。吾等讀書之餘,或聊資閒談,或搦管評說,亦不過「癡」人說「夢」爾。此或為《紅樓夢》這一古今「大」悲劇意義之所在。換言之,從《紅樓夢》書中悲劇人物身上,總能見出個體生活、社會現實乃至整個人類之悲劇幻影。
試以書中人物賈政為例。按照《紅樓夢》第一回的說法,作者之本意,乃著重書寫「當日所有之女子」,不令「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隨世「泯滅」,因而,除了「通靈」之寶玉,包括賈政在內的其他「鬚眉濁物」,自然不是重點人物。但是,賈政同樣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悲劇形象。何謂「悲劇」,各家說法見仁見智,各表「悲劇」內涵之一端。竊以為「悲劇」作為人類共同之命運,大而言之,不外一「慾念」而已;一生為二,即所謂「理想/現實」矛盾衝突之悲;具體而言,其基本內涵,或有兩層:一者,一己之願念,難以見容於現實社會、不被理解與接受之悲;二者,天生氣性難以盡情發揮,或者自設牢籠之悲。賈政也是二「悲」兼備者。
學界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論及賈政似多貶斥。或曰:『賈政者,假正也。』或曰:賈政是『典型的偽君子』、『不學無術的欺世盜名的假道學』。」2此種評價,顯然不合實情,故時有論者撰文反思3。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內涵遭遇讀者之誤解,尤其是近乎「惡諡」式之曲解,不僅是作者之悲哀,也是人物形象本身之悲哀。即便在文學世界裡,賈政之良苦用心,同樣遭遇不解乃至怨怒。最典型的例子,無過於第三十三回「不肖種種大承笞撻」一事,也就是一些中學語文教材中的選段「寶玉挨打」,寫得真是異彩紛呈,奪人魂魄。或以為此一情節反映了「封建衛道者」賈政與「封建叛逆者」賈寶玉之間第一次劇烈的「面對面的衝突」,「非常真實、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會的腐朽和醜惡」。如此理解這一情節之「悲劇」義,雖然不無道理,但顯然失於粗淺。因而,有論者從傳統文化、當下現實的雙向角度予以闡釋:「賈政對寶玉也並非無真情,說『試才』時脂硯齋在『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孽障」』下批之道:『愛之至,喜之至,故作此語。』但這種愛子之真情,卻是以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賈政愛子真情之所以被扭曲的文化原因⋯⋯還有至關重要的一點,即望子成龍文化心理在作怪⋯⋯當兒子難以成龍,『計深遠』而難以奏效時,愛子之真情就異化成『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逼子成龍』的扭曲心態,如賈政之所為⋯⋯而放眼當今中國之為父者群體中,繼承賈政之衣鉢者大有人在。他們之中,達者,產生出子肖於父的肖子文化心理;窮者,則衍變出望子勝於父的補償心理。」4如此理解賈政形象之悲劇,無疑更進一層。不過,仔細玩味,似猶有未足,無妨補說。竊以為賈政「笞撻」寶玉這一事件之「悲劇」義,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賈政身為人父,同樣懷有「子不教,父之過」一類的責任感,覺得寶玉「在家不讀書也罷,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致使生出這暴殄輕生的禍患」。此間不無偏聽、誤會之處,但情急之下,「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淫辱母婢等語,只喝令『堵起嘴來,著實打死!』」當他發現自己一番苦心不僅不被兒輩理解、認同,而且牽出傷天害理事體時,難免惱羞成怒,「一疊聲」地喊「拿寶玉」、「立刻打死」。此其為父角色之悲也。
其二,在家族關係中,賈政一心想的是「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可是,他自己作為兒子,卻不得其母的理解——痛打寶玉,因其「不肖」與「不孝」;結果,在賈母目前,賈政自己卻同時成為「不孝」之子,故賈母訓斥他:「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初你父親怎麼教訓你來!」賈政自己也深感無顏面對祖上:「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眾人護持。」所以,賈母一到,賈政狼狽異常,一會兒「躬身陪笑」、「又陪笑」,一會兒「忙跪下含淚道」、「忙叩頭哭道」,終至於「灰心,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由此看來,寶玉挨打一節,固然可以看作父子之間劇烈的「面對面的衝突」,其實更是賈政內心多種角色的劇烈衝突。人在各種家庭關係中,很多時候難免遇上類似之內心衝突。即此而言,賈政之悲劇,似具有一種普遍象徵意味。
其三,引申開來,這一情節實際上也透露了賈政一生悲劇之緣由:賈政不屬於《紅樓夢》著力表現的、最重要的那一等人物,但相比於賈府裡任一個人物,他所面對的,無疑是更多更複雜的各種「關係」,譬如朝廷、王爺、地方官、親戚、宗族、母親、妻妾、兒女等等。這種種「關係」織成一張巨大的網,或明或暗地籠罩、限制著主體意願,令其無法如賈赦、賈珍、賈璉乃至王熙鳳、薛蟠那樣任性而為。因此,第三回寫林如海稱賈政「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之流」;又有作者議論:「這賈政最喜的是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風。」可見祖上榮光帶給賈政的,更多的是一種自律與上進精神。但其結局,卻一如論者所言:《紅樓夢》「生動地展示出賈政事與願違、 動輒得咎的人生兩難困境:忠臣未做成,嚴父沒當好,家長不治家,孝子未盡孝,整個是一個處處碰壁的人生悲劇」5。這是就賈政以家族命運榮譽為己任這一願念與現實相衝突而言,所以到了「錦衣軍查抄寧國府」之時,賈政「獨自悲切」,感慨「我賈家何至一敗如此」、「種種罪孽,叫我委之何人」、「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侄,所以至此」。細參此間之「悲劇」義,又另有一層:以家族命運榮譽為己任之強烈願念不能實現,固然可悲;復因此而抑制了自家稟賦中比寶玉還乖張任誕之天性,同樣可悲。第八十四回寫賈母當眾說他:「想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還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婦,才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兒。」此回屬續作,大體上切合賈政性情之實,因為第七十八回原作中,即有類似說法:「近日賈政年邁,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個詩酒放誕之人,因在子侄輩中,少不得規以正路。」這「詩酒放誕」,仿佛魏晉名士阮籍、嵇康、劉伶乃至陶淵明之風流。但是,賈政成人立家後,「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兒」,逐漸扛起護持宗族榮光之大任,天生氣性只得隱藏於內,難得發揮。這無疑也是「心靈扭曲」之人生「悲劇」義。
人生於天地牢籠、世間塵網中,不如意、難遂心事十有八九。第七十六回林黛玉與史湘雲聊天,有幾句話頗在理:「湘雲笑道:『得隴望蜀,人之常情。可知那些老人家說的不錯。說貧窮之家自為富貴之家事事趁心,告訴他說竟不能遂心,他們不肯信的;必得親歷其境,他方知覺了⋯⋯』黛玉笑道:『不但你我不能趁心,就連老太太、太太以至於寶玉、探丫頭等人,無論是大事小,有理無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如此說來,賈政種種不遂心之悲劇,就像李白所慨嘆「人生在世不稱意」一樣,直可視如人間萬古千秋、四海十方所同者矣⋯⋯
《紅樓夢》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部分,有一大段文字,寫賈雨村闊論「天地生人」之道,重點講了天地間「所餘之秀氣」如何與「殘忍乖僻之邪氣」偶爾相遭遇,「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必至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泄一盡始散」。稟受此「正邪兩賦而來」者,或為「情痴情種」,或為「逸士高人」,或為「奇優名倡」,往往兼備「聰俊靈氣之氣」與「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作為典型例證,包括了許由一類的高士,陶淵明、阮籍、嵇康、劉伶等也赫然在列。由於史湘雲性豪爽,「愛吃酒,吃了酒才有詩」,又宣稱「『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因此,學界多注重將此一形象與魏晉名士風流、曹雪芹性情特點結合起來討論6。從賈雨村的言論看,賈政顯然不屬於這「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論賈政者,亦少涉及「名士風流」一類話題。不過,細細品味,其實不難發現賈政這一藝術形象與魏晉名士,尤其是陶淵明相仿佛之處。擇其要者,有如下四端。
其一,在面對祖上榮光方面,二者具有相同的責任意識。從家族史角度看,有趣的是,陶氏一族,以軍功名世,尤其是陶淵明曾祖陶侃,勳業卓著,被封為長沙公;《紅樓夢》中的榮寧二府,祖上起家也是行伍,馳騁疆場,出生入死,受封為寧國公、榮國公。從現世人生及其結局看,賈政與陶淵明自然不能相提並論:前者認真地奔波於仕途,雖經曲折,最後仍為官身,且得聖旨而承襲「榮國公世職」;後者屢仕屢隱,最後一賦「歸去來兮」而訣別宦海。但是,完整的人生,畢竟由兩面構成,可見者形跡,難見者心性。二者之間,或內外相符,或表裏不一,波詭雲譎,所謂「人心惟微」,宜含此義。依此尋思,賈政與陶淵明之間,又不無相通之處。
譬如,賈政頗以護持、弘揚祖上榮光為己任,光宗耀祖乃其一生行事之鵠的,為人亦「大有祖風」。陶淵明雖以逸民高士、「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垂範千古,但從他傳世的文字裡,也不難見其家族榮光以及由此帶來的緊迫感。筆者曾於多年前撰寫一文,專門討論陶淵明詩文創作與其「家族勳業傳統」之關係7。我們看他寫的〈命子〉詩,首先就從「悠悠我祖,爰自陶唐」說起,中間歷數陶氏家族之勳功德業,尤其讚頌其曾祖、東晉重臣、長沙公陶侃:「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後面則談及自己不能發揚祖上勳業傳統之愧疚:「嗟余寡陋,瞻望弗及。」8即便如此,後人也覺得陶淵明是能夠繼承家族風規者9。陶淵明屢次入軍幕,〈荣木〉诗自我鞭策:「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10均體現了對祖上名臣陶舍、陶侃勳業的高度推崇與敬仰。因此,賈政、陶淵明在踐行家族勳業傳統精神方面,隱顯有別,選擇的人生道路也不同,但欽服於宗族風規、將個人置入家族歷史之自覺意識,又何其相似。
其次,在掛懷家族未來方面,賈政、陶淵明看似截然相反,實則不無一致處,主要體現在如何對待兒輩之學業上。陶淵明以淡泊高情聞名於世,但對於兒女學業,同天下父母心一樣,也無法徹底灑脫起來。杜甫就說「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原因之一則在於「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11。前引〈命子〉詩之寫作,即緣於長子降生、取名寄意之事,在大篇幅回顧家族歷史之後,言歸正傳:一謂自己「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二謂「三千之罪,無後為急」,如今孩兒出世,無愧於傳宗接代之孝心,且寄予厚望:「溫恭朝夕」;「尚想孔伋」;「夙興夜寐,願爾斯才」——初為人父,期待甚切,希望兒子能夠秉持儒家為人準則,朝夕溫和恭敬,如孔伋子思那樣,成為肖孫;嚴以律己,成人成材。陶淵明說,天下為人父母者,大凡都懷有此心:「凡百有心,奚特於我。」12以此「心」看賈政之教育子弟,不難理解何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說有何不同,主要在於:賈政、陶淵明雖然都從家族角度熱切期盼子孫務正業、守德行,但確有固執、瀟灑之別。
陶淵明說,如果孩兒實在不成材,實屬無奈,何必強求:「爾之不才,亦已焉哉!」13賈政不同,對於寶玉,「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14,要求嚴苛,必須順從其意願,且嚴加管教,所以他特別叮囑寶玉業師賈代儒:「倘或不聽教訓,還求太爺認真的管教管教他,才不至於有名無實的白耽誤了他的一世。」由此可見,賈政、陶淵明在教子觀念上,其實都淵源於儒門傳統,德行、學業皆如此。不同之處在於:陶淵明不乏寬容的餘地,賈政則無可商量,以為子必遂父願。當然,到了賈政年邁之時,也終於明白了一點,第七十八回有言:「近日賈政年邁,名利大灰⋯⋯近見寶玉雖不讀書,竟頗能解此,細評起來,也還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們,各各亦皆如此,雖有深精舉業的,也不曾發跡過一個,看來此亦賈門之數。況母親溺愛,遂也不強以舉業逼他了。」到後來續書寫「錦衣軍查抄寧國府」,賈家經此大風波,賈政對寶玉的心態,居然更轉一層,如第一百二十回所言:「眾人道:『寶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尚,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麼中了才去?』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裡的精靈,他自具一種性情。你看寶玉何嘗肯念書,他若略一經心,無有不能的。他那一種脾氣也是各別另樣的。』說著,又嘆了幾聲。」這種心態,與陶淵明〈責子〉詩所言,倒不無契合了:「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15孩兒們不愛讀書文術,賈政最後以為這是「賈門之數」,陶淵明說這是「天運」,道理其實是一樣的。
其三,陶淵明說自己「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16;又說「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17。賈政也是「自幼酷喜讀書」,幾成其一生之情結:第十七至十八回寫「大觀園試才題對額」,賈政與眾人經過「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之所,即後來名為瀟湘館者,文中寫道:「賈政笑道:『這一處還罷了。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不枉虛生一世。』」第七十一回寫賈政在外為官數年,因「賜假一月在家歇息」,除了「母子夫妻共敘天倫庭闈之樂」,其他「一應大小事務一概益發付於度外,只是看書⋯⋯」此與第四回寫賈政「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著棋而已」,遙相呼應。陶淵明一眾兒輩「不好紙筆」與「文術」,賈府子弟像賈珍「那裡肯讀書」、賈璉「也是不肯讀書」的;在眾人眼中,寶玉更是「頑劣異常,極惡讀書」。與此相比,陶淵明、賈政皆好讀書,相似之處更值得關注。
陶淵明、賈政之好讀書,均非外在力量督導、管制之結果,而是本乎天性志趣。與此相關,二人均不擅家庭俗務,拙於經營,疏懶之意顯然。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序〉坦言:「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生生所資,未見其術。」18他雖然深知「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19,「民生在勤,勤則不匱」20,但又明白「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21,以適意為尚,懶於計較一家生計。賈政長於富貴之家,雖無匱乏之憂,且「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但「族大人多」,「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為要⋯⋯餘事多不介意」。就連起造大觀園這樣的重要事務,第十六回也是這麼寫:「賈政不慣於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罷了。」後四十回續書中,也提到「眾人知賈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著急」;又說「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如此疏於家政管理,最後他自己也後悔不迭,因為一經錦衣軍抄家,表象繁華背後的虧空一併暴露無遺,第一百零六回:「賈政不看則已,看了急得跺腳道:『這了不得!我大量雖是璉兒管事,在家自有把持,豈知好幾年頭裡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為什麼不敗呢!』」面對賈母,也不敢隱瞞這一實情:「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了。」據第一百零七回所述,賈政如此「不知理家」,倘非皇帝開恩,念他「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屬勤慎」,差一點兒連自身也要被處以「治家不正之罪」。與陶淵明不善經營生計而令兒輩「幼而飢寒」22,或全家「夏日抱長飢,寒夜無被眠」23境況相比,賈政不知理家之惡果,顯然要嚴重得多。
其四,陶淵明的賦歸園田與賈政的「歸農之意」24。陶淵明〈歸園田居〉開篇即謂:「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25意在表明個人天性適於山林田園,而非官場仕途。但是,由於名利思想傳統的影響,包括家族風規之熏陶,仍自謂「猛志固常在」26;或者出於生計之需:「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27或如〈與子儼等疏〉所言:「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28但終究心繫田園,即便身在宦海,陶淵明也常惦念靜好之園林:「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29或曰:「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30因此,在「仕/隱」之間,陶淵明有過屢次徘徊,但佔據主導地位的,則是隱居田園之心志,最後徹底告別仕宦,賦歸田園。
賈政與陶淵明的不同之處,乃其人生之旅始終奔走於仕途。《紅樓夢》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部分就提到:「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爹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升了員外郎了。」續書第一百二十回則這樣寫道:「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大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書,能夠上進。朝裡那些官兒難道都是城裡的人麼?』」又說:「提起村居靜養,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報耳。」對比原作、續書,一頭一尾兩端文字,意味深長,因為其間涉及一個共同的問題:「賈政」之名從第一次出現到最後一次收場,都在事與願違的悲劇之中——原本心願是走科舉一途,結果額外受恩,領「主事之銜」;心中一直懷想「村居靜養」境界,卻因「受恩深重」無法脫身。稍加觀察,可知「莫說村居不好」,確非賈政違心之言,第十七至十八回有兩處或可體現這一點:
一處寫眾人遊走於大觀園中,「一面走,一面說,倏爾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築就矮牆,墻頭皆用稲莖掩護。有幾百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數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橰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宛然一幅陶淵明筆下的園田居圖:「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31難怪賈政見了,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𨯳,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另一處寫眾人「步入茆堂,裡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當他聽寶玉說此處「不及『有鳳來儀』多矣」,隨即訓斥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為佳,那裡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所謂「清幽氣象」,便指山林之趣,洗盡富麗鉛華,茅堂木榻,近似村居。綜合此類描寫,大體可知賈政恰如陶淵明筆下的「戀舊林」之「羈鳥」、「思故淵」32之「池魚」,內心懷著一份「歸農」、「村居」之情愫,無奈身在宦海,沐浴天恩,欲歸而不得。因此,雖說陶淵明、賈政都有仕宦、村居兩種心念,但結局卻大相逕庭:陶淵明最終擺脫「誤落」之「塵網」,在經歷「久在樊籠裡」之後,終歸「復得返自然」33;而賈政除了年少時「古怪脾氣」、「詩酒放誕」,「成人」之後卻難得返歸此一天性,因此,村居歸農一類的自由生活,也就成了其內心深處的理想天國34,由此又不難見出陶淵明之影子。
總而言之,表面上看,陶淵明乃高蹈隱逸之士,賈政則屬於寶玉所深惡的「蠹祿」之流,似不宜同日而語。然而,無論是歷史上的出類拔萃者,抑或是小說中鮮活生動之人物形象,在複雜人性、幽微人心層面,自有相通之處。細細體會,可知賈政這一形象中,其實蘊含著類似陶淵明精神的若干側影。據《紅樓夢》第八回,賈政書齋名「夢坡」,可見其如何神往蘇東坡那樣的灑脫曠懷,而蘇軾是極其推崇陶淵明的。此一細處,或許也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賈政與陶淵明精神之關係,進而更深入地解讀賈政這一形象內涵。
前文提到的賈政「夢坡」書齋,具體情節見於《紅樓夢》第八回:賈寶玉想起養病在家的薛寶釵,「意欲去望他一望」,因擔心路上「或可巧遇見父親」,於是「寧可繞遠路」。眾嬤嬤跟隨著,偏遇見了賈政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老嬤嬤因問:「二位爺是從老爺跟前來的不是?」或許二人也知寶玉怕見賈政,便應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這原本是說給寶玉聽的,重點在「歇中覺、不妨事」;脂硯齋關注的重點則是齋名,故曰:「妙!夢遇坡仙之處也。」坡仙即東坡居士蘇軾。
一般而言,人們很難將賈政與蘇軾聯繫起來,原因之一,在於未必留心《紅樓夢》文本細微處,且往往先行接受了「賈政」即「假正經」35一類的論家成見。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賈政之言行及其性格整體特點,大體如作品中寫到的:「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朝乾夕惕,忠於厥職」,「兢兢業業,勤慎恭肅」;「這般古執」;「古樸忠厚」;「居官尚屬勤慎」;「賈政最循規矩」、「純厚成性」、「賈政忠厚」。總之,屬於比較古板、嚴正乃至固執類型。這與讀者心目中灑脫曠達、才情橫溢的蘇軾形象,反差甚大,難以相提並論。
不過,「夢坡齋」之「夢」,用筆精細,值得玩味。此處所謂「夢」,無妨理解為「日有所思故夜有所夢」之「夢」,屬於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的一種願念或理想。如此揣測,應該符合賈政內心實情。因為自其稟賦而言,賈政自具近似蘇軾那樣放曠不羈之氣性。第四回寫他「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著棋而已」;第七十八回說他「起初天性也是個詩酒放誕之人」,怎奈長大成人,家族、社會、官場等責任佔據了主導地位。此即賈母所言:「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紀,又居著官,自然越歷練越老成。」與此「老成」相對的,則是其早年展露的天性:「想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還加一倍呢。」當「瀟灑、放誕、古怪」天生稟性逐漸退隱至內心深處而難以發泄時,以「夢」的形式自我補償,何等契合人類一般心理規律。因此,賈政書齋題曰「夢坡」,寓意幽微,緣起則在於一己內心願景。
又,蘇軾放曠不羈,詼諧幽默乃重要表現之一。賈政一向不苟言笑,嚴正恭肅,但天性偶一流露,亦屬本色而非「假作」。例如第七十五回寫中秋之夜賈府載笑載言,「賈政見賈母喜悅,只得承歡」,湊趣說了一個笑話,才說了一句「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的」,「大家都笑了。因從不曾見賈政說過笑話」,偶露崢嶸,恰是其內心真面目之體現。難怪脂硯齋對此讚嘆有加,一曰「竟能使政老一謔,真大文章矣」;再曰「這方是賈政之謔,亦善謔矣」;又曰「偏寫賈政戲謔,已是異文」。可惜的是,他雖然有此天賦,卻因「越歷練越老成」,終究不能如東坡那般逍遙適性。當然,也算難能可貴,因為賈政雖「老成」持重,卻並未泯滅其天性。書齋之「夢坡」,得其宜也。
與此「忠厚」品質相關的是,賈政治家為官均認真嚴正,以至於固執、古板。這一點,與蘇軾之「不合時宜」,亦相仿佛。第九十九回「守官箴惡奴同破例」部分,賈政與管門的李十兒有一段對話,頗能說明這一點:
李十兒道:「百姓說,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錢的法兒⋯⋯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幾年已巴到極頂的分兒,也只為識時務能夠上和下睦罷了。」賈政聽到這話,道:「胡說,我就不識時務嗎?若是上和下睦,叫我與他們貓鼠同眠嗎。」
對話之起因,是賈政離京,「往江西監道」,嚴守官箴,以「做好官」、「當清官」自期,並不懂得「外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也不明白一干隨從衙役盼著「主人放了外任」以便狐假虎威、「在外發財」之私心,結果「便覺樣樣不如意」。李十兒試圖曉以利害關係,告訴賈政:「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著糧道的衙門,那個不想發財?俱想養家活口。」而賈政「這位老爺呆性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縣饋送一概不受」。這是賈政任地方官「不合時宜」處。其實,即便在家庭內部,他又何嘗合時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三十三回「不肖種種大承笞撻」一事中,賈政的萬端慨嘆:「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訓一番,又有眾人護持。」聽了王夫人的哭訴,他又「不覺長嘆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或許正因如此「不合時宜」,所以歷來讀者更同情的是慘遭笞撻之苦的寶玉以及護著他的賈母、王夫人,而未必給予賈政哪怕一絲之「同情的理解」。
第八十二寫寶玉再次入家塾念書,賈代儒曾這樣勸勉他:「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好生記著我的話。」賈政處處不合時宜,正是「成人不自在」的典型體現。在世人看來,至少從作品中的思想境界看,蘇軾似乎達到了「成人」又「自在」的境界。果真如此,則賈政雖然因「不自在」而自我屏蔽了瀟灑天性,但是,借助「夢坡」這一書齋名號,不也在努力固守自己的那份稟氣嗎?總之,賈政的「不自在」,其實也是眾生現實境況的一面鏡子36。「夢坡齋」三個字,啟人深思:如何於「不自在」的生命旅程中給個體留一方相對「自在」的理想空間?
行文至此,出於好奇心,上網絡搜尋了一番,驚訝地發現,曹雪芹看似不經意地提及的這個「夢坡齋」,勾起不少「紅迷」的強烈「索隱」興趣,大體按照「諧音」讀法,將「夢坡齋」一名「翻譯」為「夢破哉」或「夢婆災」,進而「偵探」各種歷史政治或人物命運之「隱喻」,令「夢坡齋」也顯得「熱鬧」起來。讀罷這些長短不一的網文,又想起《紅樓夢》中的那副聯語:「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既然作者的世界觀、人生觀乃至思維方式原本遵循「真/假、有/無」互存、對轉原理,何不更進一層著想:「隱」處或即「顯」處、「假」相或有「真」義?即便如流行甚廣的「賈政,假正經也」之說,為何不能再反轉過來理解:表面「假正經」,或許恰恰預示著內裡之「真性情」。如此想去又想來,越發覺得「夢坡齋」三字,意味確深長,值得玩味一番。
1.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第4版,頁1605。本文引用《紅樓夢》原文,均據此版本,下不出注。
2. 呂立漢:〈封建末世正統文人的藝術寫照——賈政形象試論〉,《明清小說研究》,1997年第1期,頁243。
3. 如黃熾〈一個真賈政〉,《齊魯學刊》,1987年第2期;高時闊〈論賈政親子之情的異化與回歸〉,《紅樓夢學刊》,1989年第1輯;賈穗〈一個被曲解的人物——賈政〉,《海南師院學報》,1993年第2期;關四平〈無可奈何花落去——論賈政的人生悲劇及其文化意藴〉,《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4輯;呂立漢〈封建末世正統文人的藝術寫照——賈政形象試論〉,《明清小說研究》,1997年第1期。
4. 關四平:〈無可奈何花落去——論賈政的人生悲劇及其文化意藴〉,《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4輯,頁150-151。
5. 關四平:〈無可奈何花落去——論賈政的人生悲劇及其文化意藴〉,《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4輯,頁136。
6. 如:呂啓祥〈湘雲之美與魏晉風度及其它——兼談文學批評的方法〉,《紅樓夢學刊》,1986年第2輯;薛瑞生〈是真名士自風流——史湘雲論〉,《紅樓夢學刊》,1996年第3輯;張麗〈紅樓人物史湘雲的話題性及其名士風度解讀〉,《明清小說研究》,2020年第1期;俞曉紅〈「湘雲醉眠」與魏晉名士風流〉,《學語文》,2021年第1期。
7. 參見拙文:〈撫劍風邁:從〈命子〉詩看陶淵明與家族勳業傳統之關係〉,《紅岩》特刊《重慶評論》,2019年第2期,第25-36頁。
8.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27-28。
9. 如《陶詩匯注》之〈命子〉詩夾注引趙泉山曰:「靖節之父,史逸其名⋯⋯惟〈命子〉詩曰: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慍喜。其父子風規蓋相類。」 認為陶淵明與其父一脈相承的家門風氣,與長期以來形成的陶淵明形象特徵相一致。
10.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6。
11. 杜甫:〈遣興五首〉其三,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63。
12.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28-29。
13.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29。
14.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夢》第八十一回塾師賈代儒對寶玉說:「如今論起來,你可也該用功了。你父親望你成人懇切的很。」。
15.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06。
16.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75。
17.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33。
18.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59。
19.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84。
20.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25。
21.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69。
22.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87。
23.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49-50。
24. 有關賈政的「歸農之意」,關四平〈無可奈何花落去——論賈政的人生悲劇及其文化意藴〉一文曾論及,雖未明確以陶淵明思想為分析角度,參考價值卻不言自明。《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4輯,頁143-144。
25.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40。
26.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38。
27.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59。
28.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87。
29.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74。
30.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75。
31.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40。
32.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40。
33. 陶淵明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40。
34. 具體表現就是,只能在公務之暇,「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為要」。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第4版,頁66。
35. 俞平伯:「賈政者,假正也,假正經的意思。書中正描寫這麼樣一個形象。」俞平伯:《紅樓夢小札》,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7年,頁35。
36. 李白所謂「人生在世不稱意」,倒也道出天下人「不稱心」之共同悲劇,一如「不自在」之意也。《紅樓夢》第七十六回林黛玉對史湘雲說的幾句話,意思與此相近:「不但你我不能趁心,就連老太太、太太以至寶玉、探丫頭等人,無論事大事小,有理無理,其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況你我旅居客寄之人哉!」〈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第4版,頁1065。
All articles/videos are prohibited from reproducing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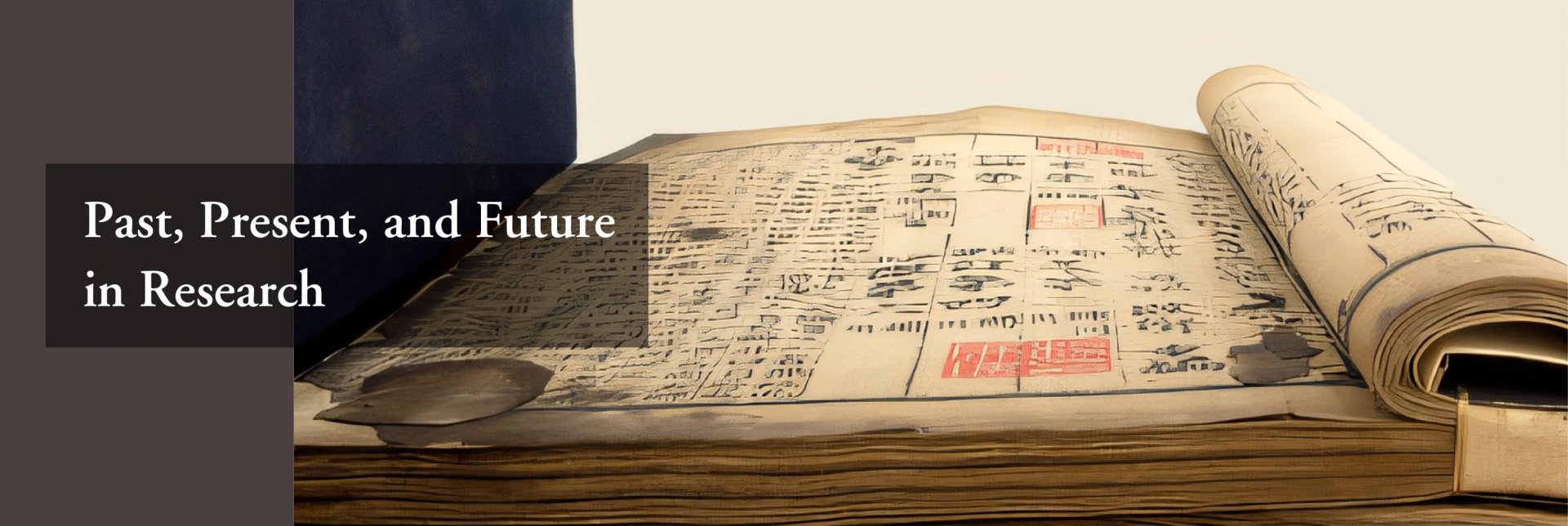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