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人」与「禽兽」之别
孔子,名丘,字仲尼,约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约西元前551- 479年) 。孔子上继尧、舜、汤、文、武、周公之文化系统,下开中华民族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家精神。孔子的伟大,不单在于开创教育新概念: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更在于他指出「人」除满足欲望,拚命求生外,还有一个「仁」的道德境界。孔子周游列国,宣扬仁政,力挽狂澜于既倒。可惜诸国以力争权,以战掠地的形势已矗然而成。孔子游说诸侯,只落得积极款待,却被冷落的局面。仲尼失意,退而讲学于乡,并以继承及发扬传统文化为己任。孔子之后,有子思者,其再传弟子孟子,以继承孔子学说,发扬儒家精神为使命,鼓其勇气,舌战时流,维护孔子学说。
《史记》曰:「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孟子一书中引《诗》者有30次之多,论《诗》有4次;引《书》则有18次,论《书》则有1次。如此,即孟子是以诗、书—儒家的主要教材—作为辩论及思想的依据。如《孟子‧告子上》:「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从上列记载可知,孟子是以承接儒家的学术思想为任。
孔子虽祖述周文化,对三代文明亦有所损益,但周代文明,但春秋时礼乐崩坏,已不復旧观。孟子生战国之世,士与庶民的阶层产生变化,孟子对人性本质有更深的体会,因此对王道思想、民贵主张、天爵人爵等概念有较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孔子重仁重礼,带有谦和的中庸思想,呈现出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和情绪状态;而孟子居仁由义,故英气勃勃,面对战国诸王及霸主,在其留难与对辩中,仍处处显露出其浩然正气。
《孟子‧万章下》:
北宫錡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
《孟子‧离娄上》: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尧舜之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从上列两则记载可知,孟子终身不放弃王道思想,以拯救万民为己任,而且基本上是拥护传统制度。孟子周游列国,无非宣扬王道,匡时济世。虽然其思想被摒弃于时流,但那种追求理想的执着,救民于水火的热炽心情,百世而后仍觉其锋。
战国之世,战争频仍,人与人及国与国之间是以奇谋巧诈为尚,以篡弑叛逆为高。孟子眼见邪行歪风炽盛,以其忧患忧道之心,负起了捍卫儒家思想的责任,提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孙丑上),更说明自己对孔子是心悦诚服。当其时杨朱、墨翟之徒遍天下,思想普遍归于自然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及绝对至公主义;其次,告子性无善恶论,纵横家权力争夺的思想等都严重影响孔学中爱有等差,内仁外礼的学说。非儒主义流行于当世,孟子要重整儒学馀绪,力挽狂澜,故展其雄辩之才,评驳杨、墨、告子、纵横诸家。在在指出,人困于欲望名利,其「人性」将受蒙蔽,并作出损人利己的行为。
所谓「人」,基本上具有两种性向:一是具有种种原始要求欲望的身体的人,其行为乃随着身体的欲望而出发,与禽兽无异的性向;二是人类独有的善与道德感,,即孔子所说「成人(仁)」,其行为本诸爱人而出发,即所谓仁者爱人。修仁是要发挥与生俱来的人(仁)性,生活中的一切活动乃可全依仁而出发。
当人有与禽兽无别的欲望时,自然追求的生理的需要(生物性)。孔子、孟子从来没有否定此种生理需求的人,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明确指出饮饮食食,即身体五官的享用,及男男女女,即男女之间的爱慕,其终极的要求是繁殖,此亦是身体觉受中最令人有快感的活动。此两种欲望是人类最大的欲望,无可否认,此两种欲望是源于人类原始动物性,与禽兽共通。这是自然而然,没有甚麽善与不善,只有是不是过份,违背社会普遍接受的程度。唐君毅先生对此有解释:
我们看出人性根本是善的,同情、节欲、求真、求美、自尊、自信、信人、宽容之器度、爱人以德等,固然都是人所公认为善之活动。即是求个体生存之欲,男女之欲本身,亦非不善。1
自然之欲望,不应以善与不善处之。孟子见齐宣王,力陈行王道之重要,宣王屡次反驳,认为孟子之言「大哉」,基本上是不能行,更说出「寡人有疾」:好勇、好货、好色(梁惠王下)。这裡可以看出,齐宣王根本无心行仁政,推王道,其所急切者无非攻城掠邑,扩展版图,满足个人欲望。所谓「仁、义、礼、知」只能作口头说话,不付诸实行。笔者最初看到此节,心感孟子的难堪,直觉上感到孟子在千方百计的讨好宣王,希望宣王接受及运用其主张治国。当人生经验稍为丰富,对孟子的了解加深以后,才知道孟子从没有讨好宣王。宣王所陷的好勇、好货、好色,根本就是人类普遍所陷溺者,就如饮食一样,只有程度上的严重性差距,很难说对错,就如富人吃一顿晚餐,可以是穷人一年的收入。因此,孟子不否定宣王的本性,反而因势利导,指出举国有积粮,男子有妻室,则王好货、好色无伤于治国。倘若孟子大加鞑伐,除不见用于宣王外,亦可算不通人情。
唐君毅先生再将这些欲望推展至人类的精神发展:
人有求个体生存及男女之欲,而后有人的生命之继续存在;有人的生命之继续存在,而后有表现各种高贵的精神活动之人。…求名求权,就其最初动机言,是求人贊成我之活动,亦是求一种我与他人之精神接触,便亦不能说定是不好。2
我想孟子是想透过男女饮食、权力名气这些欲望,带领宣王认识本心,而推行善政。这裡试借用西方着名心理学家佛洛伊德 (S. Freud)3的研究成果作一阐释。佛洛伊德将人类人格的构成分为三个层面,即本我(id),内地学者译作伊底、自我 (ego)及超我 (superego)。所谓「本我」即人类原始欲望,是生物性的,主要呈现性本能及侵略性冲动。此欲望亦成为人类生命的动力(drive),亦即是欲望的动力。佛洛伊德对人性是处于消极及悲观的一面,他认为人的奋斗无非是满足身体的觉受,身体的快感是人人所追求的觉受,无必要否则和摒弃,故不否定享乐原则 (Principle of pleasure)。人类出世的一天开始,就是步向死亡;人类亦很难逃过欲望的枷锁,特别是性。佛氏的研究很多均集中研究性对人类的影响,例如他认为人的行为受五岁前的性经验所决定,并将之分为口慾期、肛门期及性徵期。他的《梦的解析》的案例,很多都与性有关。
所谓「自我」是指透过有系统的理性化过程,而意识到人在「人类」群中的理性行为。此自我是大部分在意识层面显示,而自我的精神活动是依照「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和续发思考步骤(secondary thinking process)来进行。亦即是「人」透过理性的分析知道如何与群体相处,清楚知道群体所不接纳和接纳的行为。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协定,和适应社会、传统的要求。
所谓「超自我」是人类的良知和道德感,超自我是监察及约束本我和自我的行为。在此,佛氏没有否定人的高尚情操,但我们可以相信佛氏所接触的个案大多呈现人类的原始性、生物性,使他对生命产生负面的理念。认为人类随性欲而走,由于生命的不肯定,主张寻求快乐是生命主要环节。
佛氏的学说直接影响近代欧美国家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被接受及认定。本我(伊底)的理论,普遍被接受;当然佛氏的理论受到西方思想家的冲击,如罗哲斯 (C. Rogers,又译作罗杰斯)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其主张的同理心 (Empathy) 更普遍运用于辅导技巧中;容格 (C. G. Jung, 又译作荣格)的心理分析学派都是对佛氏的理论作出反响。
另外一位着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马斯洛4,也提出「需求层次理论」,即金字塔理论。马氏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受尊重的需要、自我成就的需要五层,后期再加入第六层灵性需要。其理论是能满足第一层的需要,就会提升至第二层需要,最后是能自我成就。此理论亦是指人类必需满足饮食男女,才能有更高的情操。可是,当我们验证于现实世界,未必一定要满足生理、安全需要,才能到达爱与归属的需要。本文引用佛氏及马氏的理论,主要是学者知道,人类在物质世界所遇到的问题二氏均将精神境界放置最后,这与东方文化有差异,我们相信人会有日悟道,也相信人类当中,有天生的伟人。
佛氏的理论,很多已被现代心理学家否定,而马氏的需求层次,亦未准确反映人类的需求。可是,马氏的理论发展成人本主义心理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提出「当事人中心」治疗法的罗杰斯(Carl Roger)。不以过往的心理历史而预测未来的心理状况,着重此时、此地的治疗法。从佛氏及马氏的理论可知道,中外思想家,第一关要过的,就是生理需要。孔、孟的伟大,就是不把生理欲望放在第一位,而提出人类独有的道德。故唐君毅先生说:
我们必须相信人性是善,然后人不断发展其善才可能。我们必须相信人性是善,然后了解人类之崇高与尊严,而后对人类有虔敬之情。我们必须相信人性是善,然后我们对人类之前途之光明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人性是善,然后相信人能不断的实践其性中所具之善,而使现实宇宙改善,使现实宇宙日趋于完满可贵。5
可是,无论如何,人类不能否定的就是生物性。我们可抚心自问,在我们的思维中曾多少次出现过鬼卑鄙下流的思想、意识或意念。因此,我们亦不能否定或否认我们具有与禽兽无异的渴欲。佛氏的理论就是不否认人是有这种原始的生物性。我们若将佛氏的本我理论与孔孟作一比较,不难看出,孔子和孟子亦从没有否定人的自然欲望。试看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诗无邪!」,所谓「诗无邪!」是指诗经谈及男女爱慕的诗篇,没有带有邪念,纯然是男女爱慕之情,、是超越性的渴慕,而达至互爱的境界。所以,孔子用肯定的语气在回答问题,男女爱慕是可以超越性的需求。诗经之中,言及男欢女爱者比比皆是:关雎、姣童、氓、柏舟、蒹葭等等。孔子倡仁执礼,竟然赞美诗经中的爱情诗篇,我想孔子是清楚,人类是可以将性欲的需求、昇华至怜爱牺牲的情操。试想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究竟有甚麽不对?
孟子究竟是不是讨好齐王而不否定其好勇、好货、好色?试看看孟子的浩然正气: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认为君主在平民国家之下,甚类似现代所说的「公僕」。在阶级观念甚重的古代,孟子能振臂而呼以民为贵,不可不勇。
孟子的勇不独呈现于理论上,更呈现于行为上,《孟子》记载:
〈梁惠王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
〈万章下〉: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複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
〈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
当着一国之主的面前直斥残害国家的君主不能称为君,只是一夫,所谓一夫即一个只会伤害别人的男人,说得明白点就是此种人死不足惜。孟子更不惜得罪齐王,说出了千百年以后民众的愿望,就是君主失德,我们就换了他。我想要一个人当国家领导人或一国之总统,这样直接的说出这话,实在很困难,亦正好表示孟子并无讨好君主的意图或行为,〈万章〉篇的记载可看到齐王听了之后是勃然色变—发脾气了。人是相对的感情,就算是君主也不例外,人无必要为昏君而忠心。千古而后,其气魄仍震人心脉。就如孟子所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究竟有几人能做得到?以此推论,则孟子不否定宣王的欲望,并不是讨好他,而清楚明暸「人」根本就必定有这种欲望,问题在于如何将之合理呈现,简单说,即是使之合于「礼」。
孟子如何界定人与禽兽之别?孟子曰: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又曰:
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
生活饱足,閒来无事,游游荡荡,这种生活是近于禽兽,罪恶就容易产生。这些人会陷溺于欲望,唐君毅先生说:
一念陷溺于饮食之美味,使人继续求美味,成为贪食的饕餮者。一念陷溺于男女之欲,使人成为贪色之淫荡者。一念陷溺于得人贊成之时矜喜,使人贪名贪权。由贪欲而不断驰求外物,而与人争货、争色、争名、争权。6
若果人只跟欲望走,而且认为必须得到满足。很可怕,就是「满足」的定义无法准确定立。齐桓公嚐尽天下美味,至终竟烹孩儿而食。这样令人呕心残忍的食物,齐桓公可能觉得尚未满足。还有历代的淫乱君主,蓄养以万计的宫女,供其淫辱,在他们的心中,可能仍是未满足。人若无限扩展自己的欲望,则较禽兽,更禽兽。
所谓「人」,要知人伦,明进退,对别人有责任感。孟子批评杨氏的为我主义和墨子的无君理论,是禽兽的行为。禽兽不知道有义、有信,倘若人缺乏了这种道德的责任感,那麽,与禽兽就没有分别。
孟子曰: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
又曰: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公孙丑上)
孟子继之而推演人性,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是因为有发自内在本性的「善」,此「善」已具有仁、义、礼、智诸德,是不假外求,亦不须教育,是本有的。人之所以看不见性善,是因为受到蒙蔽,不能寻找本心。人之所以行义,是因为内在已具有仁义之心,并不是受过仁义的教育才行行义。孟子正气凛然说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性本善,我们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人性」。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孙丑上)。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不忍人之心是源于性善。在〈梁惠王上〉中,孟子因齐宣王放生一用作衅钟的牛,而指出宣王的不忍其「觳觫而就死地」就是仁者之心,具备仁者之心必定能推行仁政。孟子并解释由个体的关怀及爱而能推演至对整个民族国家的关怀及爱,此称为「推恩」,能推恩,治国就可「运于掌上」。这种「仁」心是人类逸出个体形躯而与他物产生共感,及于物、及于人、及于万物、及于宇宙,怜悯、爱护、博爱、仁慈等等道德都呈现出来。
孔子的道,内存仁,外呈诸于礼,全是见之于行为表现。《论语》一书的记载,也没有论及「为甚麽我们会有道德?」这一命题。然而,孔子提出的「天命」,已从只适用于君王,而达至所有人都受天命约束。上天赋予人类的使命,并凭着此使命而实现自身与宇宙的合一,即「天人合一」的境界。余英时有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引用两位学者的见解:
第一、刘殿爵在一九七九年《论语》英译本质导言中论及「天命」说时:「在孔子时代的唯一发展,是天命不再局限于君王。所有人都受天命的约束,天要人有道德,人也有责任达到天命的要求。」第二、日本学者小野泽精一在一九七八年的着作中也有根据金文研究而得到类似的观察,他说:「即使作为处于那种天命信仰范围的情况,心被当作受入侧的主体加以确立,也是划时代的情况。因此可以说,提出『心』和『德』行就金文来看,立场是前进了。但是,必须说,天命威严,在体制中的心本身的自立性,还是缺乏的。…到了孔子时代,儘管同样是信仰天命,但可以看到从支撑王朝政治,天降之物向个人方面作为宿于心中之物的转换。」7
而孟子绍述孔子的道统,由发现「性本善」而推演至天人合一的境界,从伦理的观念伸述至人道之所以与天道之必然合一的理论。因此解释了道德的必然性,即性本善和道德价值的普遍性,即仁、义、礼、智,为人类茫然若失的生命价值找到安身立命的依归,亦为「人」与「禽兽」之别下了定义。
在此再申论一些辩题。有论者认为四端不独见之于人,亦见之于禽兽,如乌鸦之反哺、狗犬之护主。无疑,此等行为是孝的表现,是义的表现,但牠们的行为并不是发自其良知,是大自然给牠们的自然反应。从另一角度看,即是没有不反哺的乌鸦,没有不守义的狗犬,是没有选择权,没有是非的判断。因此我们会说一些人只知忠心,而不识判断是非者是狗,就是这个原因。禽兽的生理反应受大自然支配,思春期来临便思春,产卵期来临便产卵。
禽兽于生理反应只有满足和不满足的分别,而人类则可以滥,亦可以淡。中间涉及人对外界的判断与良知,动物争食不会让,而人会;人会「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动物不会。
孟子屡屡说人与禽兽有别,就是人能成仁,而禽兽不会。我们先理解「仁」,《论语》、《孟子》所言「仁」有两种意义:诸德的总称和诸德之一。
〈子路〉:「刚毅木讷近仁」,又云:「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能行恭宽信敏惠于天下者皆为仁,而克伐怨欲与宽信敏惠相对,故仁者涵诸德之善,不仁者则诸德全不显现。又〈子张〉载:「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由是观之,仁的盖涵范围非常之宽大。甚至及于日常的生活礼仪均呈现仁德,如〈八佾〉载人如不仁如礼乐何,则仁贵乎礼乐。
至于孟子将仁解作总德者大概只有一章,〈公孙丑〉: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如耻之,莫如仁。」后两仁字,朱熹训为全德之仁,谓:「仁、义、礼、知皆天所与之良贵,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统四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故曰尊爵在人,则为本心全体之德。又曰:「不知礼义者,仁该全体,能仁,则三者在其中矣。」
仁乃诸德之一,则见诸于各章,如《论语》:「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仁者必有勇,勇者未必有仁」、「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宪问)。〈阳货〉篇更以「仁、知、信、直、勇、刚」为六德,则仁为众德之一甚明。
孟子论仁以全德之义为中心者较少,通常是仁义并用。如
〈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知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知也。」;
〈尽心下〉:「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
〈尽心上〉:「仁义礼知根于心」等等。
孟子以仁与诸德并列,明显凸出仁乃德行的一种。 在《论语》中,只有〈学而〉载有子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如此,则仁并不等于孝悌,要行孝悌,必须先具备仁的心。又子曰「仁者爱人」,均说明不同环境依恃着仁呈现不同的德行。
人如何成就全德的「仁」,即如何成就终极的道德境界,亦即是后世所说的「完人」。人具有与禽兽无异的原始欲望,同时亦具人类独有的善。两者之间如何协条?
要达至仁的境界,就要反躬求诸己。甚麽是「反躬求诸己」?就是先要相信人有性善的根器,而人虽有仁的根器,可惜受利欲所薰染,时生疑惑,所以必须时加反省,体察自己的行为;故必须「日三省吾身」、「克己復礼为仁」、「苟志于仁,无恶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等。「三省吾身」是思考自己的行是否正确?「克己復礼为仁」就是修,就是戒,凡违背礼者要坚持拒绝,要「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所谓「克」是有压制、强抑的意思,即日常生活我们必定遇到一些诱惑,诱惑出现,要以礼作为衡量,不合礼者不为。亦即是,人要支配自己而对抗外界的引诱,使自己行为合乎道德人情,唐君毅先生说:
你首先当认识:支配自己是比支配世界更伟大的工作。西方的谚语「拿破崙能支配世界,然而不能支配自己。」因为他不能控制他在岛上时的烦闷。你能支配世界,战胜世界,只是表示你的意志力,能破除一切阻碍。而支配自己,战胜自己,则表示你能主宰「用以破除外界一切阻碍之意志力」之本身。8
我们的行为过份,伤害别人,我们的欲望,盖过我们的理性时,我们的善性就难发展出来。故此,必须经常提醒自己,使道德之心不退。当我们知道甚麽是「仁」的行为后,就不会随便放弃仁的行为,此境界亦即是明代理学家王守仁所说的「知行合一」,你不行,是因为你不知。人类总把自己的力量向外移,向外发展,用尽心思气力去支配外在的一切,少将心思气力,反照自身,自我检讨提升。因此,反躬自省是大丈夫的行政为,肯为自己的负面行为思想,作审视及改正。儒家有一把尺(标准)去量度自己的行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公孙丑上〉:「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行为上有问题,就要自我反省。「不怨胜己者」就是反求诸己,是不是自己有不足之处。「不怨天,不尤人」,甚至横逆加于身,亦必自省。所以,唐君毅先生说:
如欲求自觉的道德生活,我们首先要把我们全部的生活习惯,翻转过来,把力量往内用。所以我们首先要支配自己的价值,看成比支配世界高,去作如上之思维。9
〈离娄下〉:「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恆爱之,敬人者恆敬。有人于此,其待我心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倘若自己以为已具备仁爱、礼敬之心及行为,仍遇「横逆」者,最后亦是要自省。当然,经反复自省及思考后,发觉自己的行为没有错误、理念上没有私心,所作皆合乎道义,则要有「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气概去坚持。人当有「道德自我主体力量」,人是自由的,自我选择行为,所谓「你作的行为是你作的行为」(唐君毅先生语),自我负责。正如〈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一切道德,本自具足,领悟箇中道理,是人生最大乐事。
四端虽与生俱来,但不懂得自我反省,不能持久呈现。〈告子上〉: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谓美乎?…..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离禽兽不远矣!
仁是心,义是实践。不要放弃求仁的决心,否则与禽兽无异,因为禽兽不会反省,不会求仁,禽兽一切的行为都是生物性的自然反应。倘若人放弃人独有的追求善、追求仁的心,则与禽兽有何分别?人之所以行恶,迹同禽兽,主要是未见到自己的善性,故唐君毅先生说:
如果你甘愿纵欲为恶,莫有人能限止你。但是如果你真知道了,纵欲者终当被索还其由纵欲而生之乐,谁復还要自觉的去纵欲?如果为恶者,将来终被良心逼迫而为善,谁復还自愿在现在为恶?10
唐氏的见解,是建基于人本性善的基础上。若人本性为善,其为恶的良心责备早晚会出现,这亦是儒家思想对人性有信心的明证。〈滕文公上〉:「分人以财为之惠,教人以善为之忠,为天下而得仁者谓之仁。」仁者所作的行为皆合乎道,因此可以内圣外王。内成就自我的道德境界,外则影响别人,使其同追求品德的提昇。佛家提出「戒、定、慧」去面对五浊世界的诱惑,孔孟提出礼治、反省,而使本性自有的「仁」(涵盖诸德者),呈现于生活中。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请留意,这两句说话不是学问,而是实践。没有在生活中,生命的过程中反復思考检讨,那只是空谈,只是用来调剂生活的文字。佛家所说的小悟数百次,大悟只需一次,其实亦适用于儒家。如果有日我们清楚自己本性为善的时候,对过往为恶的行为必然产生后悔或反省。
孟子所提出仁政、王道、王政等概念,是基于他提出的性善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梁惠王上)推己及人,而遍于天下,如此则大同小康的社会便会出现。齐宣王的好货好色,孟子亦不加以批评,指出「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下〉。是承认人的原始动物本能,但动物性外,还有一个令人类足被称为人的「善」。发挥本有的性善,人就无往而不利。所谓「举斯心加诸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孔子的忠恕是「内圣」,而孟子的「仁政」是外王。能内圣就能外王,孟子的性善论就是说人人皆能内圣外王,因为人人皆性善。「内圣」是成就自己的精神世界,「外王」是面对物质世界种种事物的适当行为。〈公孙丑上〉指出人生而皆有四端:仁、义、礼、知,并引孺子将入于井,人自然的心理反应作为例子,不造作、不用思考的行为,明确指出人的本性是「善」。
人无异于禽兽者饮食情慾,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乃人具有四端。人倘若放纵慾望,过分着重感官的享受,就会「陷溺其心」〈告子上〉,使与生俱来的善性受到蒙蔽。容格的一段说话足以表达现代世界最大的问题:
人类最大的敌人不在于饥荒、地震、病菌或癌症,而是在于人类本身,因为,就目前而言,我们仍然没有任何适当的方法,来防止远比自然灾害更危险的人类心灵疾病的蔓延。
请反復思量,我们人类是享受欲望,抑或是受制于欲望而埋没了本性。精神世界是无限的,我们可以感觉宇宙的存在,为世界的和谐而感动,此无限郄能呈现于我们有限的物质身体世界。凡此种种精神世界的元素,均能限制我们的欲望,而达至进退有据,不离本性的行为的境界。最后,我以唐君毅先生的说话作结:
从外看人是隶属于现实的物质身体之世界;从内看人则隶属于超越现实的纯精神界。而物质身体的世界之所以为物质身体世界,即在能表现人之精神。所以人之精神,必需表现于物质身体之现实世界。精神实在所要求的,即是表现于现实世界,其能表现于现实世界,即所以成其为精神实在。精神实在之本身是无限,无限必需表现于有限。因为由有限之超越破除,而后才显出无限。11
原載於《「第二屆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孔教學院,2006年。
< 原创文章/视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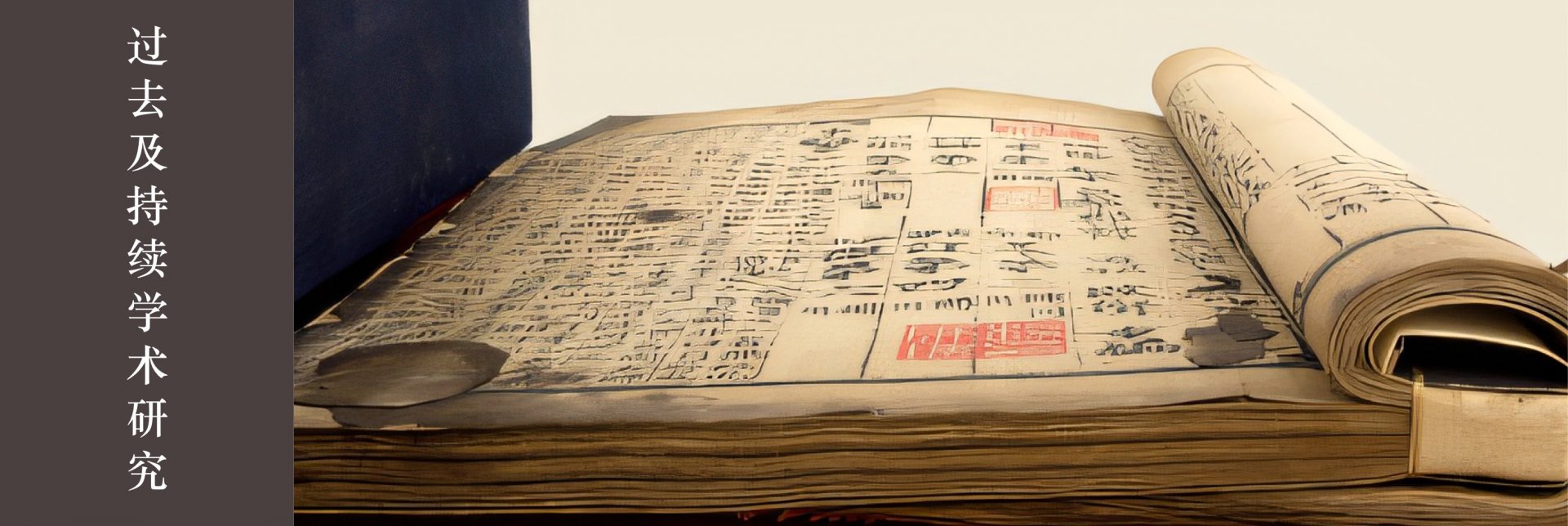



欢迎留言:
请登入/登记成为会员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