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孟子「人」與「禽獸」之別
孔子,名丘,字仲尼,約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約西元前551- 479年) 。孔子上繼堯、舜、湯、文、武、周公之文化系統,下開中華民族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儒家精神。孔子的偉大,不單在於開創教育新概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更在於他指出「人」除滿足欲望,拚命求生外,還有一個「仁」的道德境界。孔子周遊列國,宣揚仁政,力挽狂瀾於既倒。可惜諸國以力爭權,以戰掠地的形勢已矗然而成。孔子游說諸侯,只落得積極款待,卻被冷落的局面。仲尼失意,退而講學於鄉,並以繼承及發揚傳統文化為己任。孔子之後,有子思者,其再傳弟子孟子,以繼承孔子學說,發揚儒家精神為使命,鼓其勇氣,舌戰時流,維護孔子學說。
《史記》曰:「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孟子一書中引《詩》者有30次之多,論《詩》有4次;引《書》則有18次,論《書》則有1次。如此,即孟子是以詩、書—儒家的主要教材—作為辯論及思想的依據。如《孟子‧告子上》:「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盡心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從上列記載可知,孟子是以承接儒家的學術思想為任。
孔子雖祖述周文化,對三代文明亦有所損益,但周代文明,但春秋時禮樂崩壞,已不復舊觀。孟子生戰國之世,士與庶民的階層產生變化,孟子對人性本質有更深的體會,因此對王道思想、民貴主張、天爵人爵等概念有較深入的分析和闡釋。孔子重仁重禮,帶有謙和的中庸思想,呈現出溫良恭儉讓的行為和情緒狀態;而孟子居仁由義,故英氣勃勃,面對戰國諸王及霸主,在其留難與對辯中,仍處處顯露出其浩然正氣。
《孟子‧萬章下》: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
《孟子‧離婁上》: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堯舜之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從上列兩則記載可知,孟子終身不放棄王道思想,以拯救萬民為己任,而且基本上是擁護傳統制度。孟子周遊列國,無非宣揚王道,匡時濟世。雖然其思想被摒棄於時流,但那種追求理想的執著,救民於水火的熱熾心情,百世而後仍覺其鋒。
戰國之世,戰爭頻仍,人與人及國與國之間是以奇謀巧詐為尚,以篡弒叛逆為高。孟子眼見邪行歪風熾盛,以其憂患憂道之心,負起了捍衛儒家思想的責任,提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孫丑上),更說明自己對孔子是心悅誠服。當其時楊朱、墨翟之徒遍天下,思想普遍歸於自然主義、極端利己主義及絕對至公主義;其次,告子性無善惡論,縱橫家權力爭奪的思想等都嚴重影響孔學中愛有等差,內仁外禮的學說。非儒主義流行於當世,孟子要重整儒學餘緒,力挽狂瀾,故展其雄辯之才,評駁楊、墨、告子、縱橫諸家。在在指出,人困於欲望名利,其「人性」將受蒙蔽,並作出損人利己的行為。
所謂「人」,基本上具有兩種性向:一是具有種種原始要求欲望的身體的人,其行為乃隨著身體的欲望而出發,與禽獸無異的性向;二是人類獨有的善與道德感,,即孔子所說「成人(仁)」,其行為本諸愛人而出發,即所謂仁者愛人。修仁是要發揮與生俱來的人(仁)性,生活中的一切活動乃可全依仁而出發。
當人有與禽獸無別的欲望時,自然追求的生理的需要(生物性)。孔子、孟子從來沒有否定此種生理需求的人,孔子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明確指出飲飲食食,即身體五官的享用,及男男女女,即男女之間的愛慕,其終極的要求是繁殖,此亦是身體覺受中最令人有快感的活動。此兩種欲望是人類最大的欲望,無可否認,此兩種欲望是源於人類原始動物性,與禽獸共通。這是自然而然,沒有甚麼善與不善,只有是不是過份,違背社會普遍接受的程度。唐君毅先生對此有解釋:
我們看出人性根本是善的,同情、節欲、求真、求美、自尊、自信、信人、寬容之器度、愛人以德等,固然都是人所公認為善之活動。即是求個體生存之欲,男女之欲本身,亦非不善。1
自然之欲望,不應以善與不善處之。孟子見齊宣王,力陳行王道之重要,宣王屢次反駁,認為孟子之言「大哉」,基本上是不能行,更說出「寡人有疾」:好勇、好貨、好色(梁惠王下)。這裡可以看出,齊宣王根本無心行仁政,推王道,其所急切者無非攻城掠邑,擴展版圖,滿足個人欲望。所謂「仁、義、禮、知」只能作口頭說話,不付諸實行。筆者最初看到此節,心感孟子的難堪,直覺上感到孟子在千方百計的討好宣王,希望宣王接受及運用其主張治國。當人生經驗稍為豐富,對孟子的了解加深以後,才知道孟子從沒有討好宣王。宣王所陷的好勇、好貨、好色,根本就是人類普遍所陷溺者,就如飲食一樣,只有程度上的嚴重性差距,很難說對錯,就如富人吃一頓晚餐,可以是窮人一年的收入。因此,孟子不否定宣王的本性,反而因勢利導,指出舉國有積糧,男子有妻室,則王好貨、好色無傷於治國。倘若孟子大加韃伐,除不見用於宣王外,亦可算不通人情。
唐君毅先生再將這些欲望推展至人類的精神發展:
人有求個體生存及男女之欲,而後有人的生命之繼續存在;有人的生命之繼續存在,而後有表現各種高貴的精神活動之人。…求名求權,就其最初動機言,是求人贊成我之活動,亦是求一種我與他人之精神接觸,便亦不能說定是不好。2
我想孟子是想透過男女飲食、權力名氣這些欲望,帶領宣王認識本心,而推行善政。這裡試借用西方著名心理學家佛洛伊德 (S. Freud)3的研究成果作一闡釋。佛洛伊德將人類人格的構成分為三個層面,即本我(id),內地學者譯作伊底、自我 (ego)及超我 (superego)。所謂「本我」即人類原始欲望,是生物性的,主要呈現性本能及侵略性衝動。此欲望亦成為人類生命的動力(drive),亦即是欲望的動力。佛洛伊德對人性是處於消極及悲觀的一面,他認為人的奮鬥無非是滿足身體的覺受,身體的快感是人人所追求的覺受,無必要否則和摒棄,故不否定享樂原則 (Principle of pleasure)。人類出世的一天開始,就是步向死亡;人類亦很難逃過欲望的枷鎖,特別是性。佛氏的研究很多均集中研究性對人類的影響,例如他認為人的行為受五歲前的性經驗所決定,並將之分為口慾期、肛門期及性徵期。他的《夢的解析》的案例,很多都與性有關。
所謂「自我」是指透過有系統的理性化過程,而意識到人在「人類」群中的理性行為。此自我是大部分在意識層面顯示,而自我的精神活動是依照「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和續發思考步驟(secondary thinking process)來進行。亦即是「人」透過理性的分析知道如何與群體相處,清楚知道群體所不接納和接納的行為。可以說是人與人之間的協定,和適應社會、傳統的要求。
所謂「超自我」是人類的良知和道德感,超自我是監察及約束本我和自我的行為。在此,佛氏沒有否定人的高尚情操,但我們可以相信佛氏所接觸的個案大多呈現人類的原始性、生物性,使他對生命產生負面的理念。認為人類隨性欲而走,由於生命的不肯定,主張尋求快樂是生命主要環節。
佛氏的學說直接影響近代歐美國家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功利主義等被接受及認定。本我(伊底)的理論,普遍被接受;當然佛氏的理論受到西方思想家的衝擊,如羅哲斯 (C. Rogers,又譯作羅杰斯)所提出的人本主義,其主張的同理心 (Empathy) 更普遍運用於輔導技巧中;容格 (C. G. Jung, 又譯作榮格)的心理分析學派都是對佛氏的理論作出反響。
另外一位著名的美國社會學家馬斯洛4,也提出「需求層次理論」,即金字塔理論。馬氏將人的需求分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愛與歸屬的需要、受尊重的需要、自我成就的需要五層,後期再加入第六層靈性需要。其理論是能滿足第一層的需要,就會提升至第二層需要,最後是能自我成就。此理論亦是指人類必需滿足飲食男女,才能有更高的情操。可是,當我們驗證於現實世界,未必一定要滿足生理、安全需要,才能到達愛與歸屬的需要。本文引用佛氏及馬氏的理論,主要是學者知道,人類在物質世界所遇到的問題二氏均將精神境界放置最後,這與東方文化有差異,我們相信人會有日悟道,也相信人類當中,有天生的偉人。
佛氏的理論,很多已被現代心理學家否定,而馬氏的需求層次,亦未準確反映人類的需求。可是,馬氏的理論發展成人本主義心理學派,其代表人物是提出「當事人中心」治療法的羅杰斯(Carl Roger)。不以過往的心理歷史而預測未來的心理狀況,著重此時、此地的治療法。從佛氏及馬氏的理論可知道,中外思想家,第一關要過的,就是生理需要。孔、孟的偉大,就是不把生理欲望放在第一位,而提出人類獨有的道德。故唐君毅先生說:
我們必須相信人性是善,然後人不斷發展其善才可能。我們必須相信人性是善,然後了解人類之崇高與尊嚴,而後對人類有虔敬之情。我們必須相信人性是善,然後我們對人類之前途之光明有信心。我們必須相信人性是善,然後相信人能不斷的實踐其性中所具之善,而使現實宇宙改善,使現實宇宙日趨於完滿可貴。5
可是,無論如何,人類不能否定的就是生物性。我們可撫心自問,在我們的思維中曾多少次出現過鬼卑鄙下流的思想、意識或意念。因此,我們亦不能否定或否認我們具有與禽獸無異的渴欲。佛氏的理論就是不否認人是有這種原始的生物性。我們若將佛氏的本我理論與孔孟作一比較,不難看出,孔子和孟子亦從沒有否定人的自然欲望。試看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詩無邪!」,所謂「詩無邪!」是指詩經談及男女愛慕的詩篇,沒有帶有邪念,純然是男女愛慕之情,、是超越性的渴慕,而達至互愛的境界。所以,孔子用肯定的語氣在回答問題,男女愛慕是可以超越性的需求。詩經之中,言及男歡女愛者比比皆是:關雎、姣童、氓、柏舟、蒹葭等等。孔子倡仁執禮,竟然讚美詩經中的愛情詩篇,我想孔子是清楚,人類是可以將性欲的需求、昇華至憐愛犧牲的情操。試想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究竟有甚麼不對?
孟子究竟是不是討好齊王而不否定其好勇、好貨、好色?試看看孟子的浩然正氣:
《孟子‧盡心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本思想,認為君主在平民國家之下,甚類似現代所說的「公僕」。在階級觀念甚重的古代,孟子能振臂而呼以民為貴,不可不勇。
孟子的勇不獨呈現於理論上,更呈現於行為上,《孟子》記載:
〈梁惠王下〉:「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
〈萬章下〉: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
〈離婁下〉:「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
當著一國之主的面前直斥殘害國家的君主不能稱為君,只是一夫,所謂一夫即一個只會傷害別人的男人,說得明白點就是此種人死不足惜。孟子更不惜得罪齊王,說出了千百年以後民眾的願望,就是君主失德,我們就換了他。我想要一個人當國家領導人或一國之總統,這樣直接的說出這話,實在很困難,亦正好表示孟子並無討好君主的意圖或行為,〈萬章〉篇的記載可看到齊王聽了之後是勃然色變—發脾氣了。人是相對的感情,就算是君主也不例外,人無必要為昏君而忠心。千古而後,其氣魄仍震人心脈。就如孟子所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究竟有幾人能做得到?以此推論,則孟子不否定宣王的欲望,並不是討好他,而清楚明暸「人」根本就必定有這種欲望,問題在於如何將之合理呈現,簡單說,即是使之合於「禮」。
孟子如何界定人與禽獸之別?孟子曰: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又曰: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滕文公下)
生活飽足,閒來無事,游游蕩蕩,這種生活是近於禽獸,罪惡就容易產生。這些人會陷溺於欲望,唐君毅先生說:
一念陷溺於飲食之美味,使人繼續求美味,成為貪食的饕餮者。一念陷溺於男女之欲,使人成為貪色之淫蕩者。一念陷溺於得人贊成之時矜喜,使人貪名貪權。由貪欲而不斷馳求外物,而與人爭貨、爭色、爭名、爭權。6
若果人只跟欲望走,而且認為必須得到滿足。很可怕,就是「滿足」的定義無法準確定立。齊桓公嚐盡天下美味,至終竟烹孩兒而食。這樣令人嘔心殘忍的食物,齊桓公可能覺得尚未滿足。還有歷代的淫亂君主,蓄養以萬計的宮女,供其淫辱,在他們的心中,可能仍是未滿足。人若無限擴展自己的欲望,則較禽獸,更禽獸。
所謂「人」,要知人倫,明進退,對別人有責任感。孟子批評楊氏的為我主義和墨子的無君理論,是禽獸的行為。禽獸不知道有義、有信,倘若人缺乏了這種道德的責任感,那麼,與禽獸就沒有分別。
孟子曰: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離婁下)
又曰: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公孫丑上)
孟子繼之而推演人性,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是因為有發自內在本性的「善」,此「善」已具有仁、義、禮、智諸德,是不假外求,亦不須教育,是本有的。人之所以看不見性善,是因為受到蒙蔽,不能尋找本心。人之所以行義,是因為內在已具有仁義之心,並不是受過仁義的教育才行行義。孟子正氣凜然說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人性本善,我們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人性」。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孫丑上)。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不忍人之心是源於性善。在〈梁惠王上〉中,孟子因齊宣王放生一用作釁鐘的牛,而指出宣王的不忍其「觳觫而就死地」就是仁者之心,具備仁者之心必定能推行仁政。孟子並解釋由個體的關懷及愛而能推演至對整個民族國家的關懷及愛,此稱為「推恩」,能推恩,治國就可「運於掌上」。這種「仁」心是人類逸出個體形軀而與他物產生共感,及於物、及於人、及於萬物、及於宇宙,憐憫、愛護、博愛、仁慈等等道德都呈現出來。
孔子的道,內存仁,外呈諸於禮,全是見之於行為表現。《論語》一書的記載,也沒有論及「為甚麼我們會有道德?」這一命題。然而,孔子提出的「天命」,已從只適用於君王,而達至所有人都受天命約束。上天賦予人類的使命,並憑著此使命而實現自身與宇宙的合一,即「天人合一」的境界。余英時有其《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引用兩位學者的見解:
第一、劉殿爵在一九七九年《論語》英譯本質導言中論及「天命」說時:「在孔子時代的唯一發展,是天命不再局限於君王。所有人都受天命的約束,天要人有道德,人也有責任達到天命的要求。」第二、日本學者小野澤精一在一九七八年的著作中也有根據金文研究而得到類似的觀察,他說:「即使作為處於那種天命信仰範圍的情況,心被當作受入側的主體加以確立,也是劃時代的情況。因此可以說,提出『心』和『德』行就金文來看,立場是前進了。但是,必須說,天命威嚴,在體制中的心本身的自立性,還是缺乏的。…到了孔子時代,儘管同樣是信仰天命,但可以看到從支撐王朝政治,天降之物向個人方面作為宿於心中之物的轉換。」7
而孟子紹述孔子的道統,由發現「性本善」而推演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從倫理的觀念伸述至人道之所以與天道之必然合一的理論。因此解釋了道德的必然性,即性本善和道德價值的普遍性,即仁、義、禮、智,為人類茫然若失的生命價值找到安身立命的依歸,亦為「人」與「禽獸」之別下了定義。
在此再申論一些辯題。有論者認為四端不獨見之於人,亦見之於禽獸,如烏鴉之反哺、狗犬之護主。無疑,此等行為是孝的表現,是義的表現,但牠們的行為並不是發自其良知,是大自然給牠們的自然反應。從另一角度看,即是沒有不反哺的烏鴉,沒有不守義的狗犬,是沒有選擇權,沒有是非的判斷。因此我們會說一些人只知忠心,而不識判斷是非者是狗,就是這個原因。禽獸的生理反應受大自然支配,思春期來臨便思春,產卵期來臨便產卵。
禽獸於生理反應只有滿足和不滿足的分別,而人類則可以濫,亦可以淡。中間涉及人對外界的判斷與良知,動物爭食不會讓,而人會;人會「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動物不會。
孟子屢屢說人與禽獸有別,就是人能成仁,而禽獸不會。我們先理解「仁」,《論語》、《孟子》所言「仁」有兩種意義:諸德的總稱和諸德之一。
〈子路〉:「剛毅木訥近仁」,又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能行恭寬信敏惠於天下者皆為仁,而克伐怨欲與寬信敏惠相對,故仁者涵諸德之善,不仁者則諸德全不顯現。又〈子張〉載:「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由是觀之,仁的蓋涵範圍非常之寬大。甚至及於日常的生活禮儀均呈現仁德,如〈八佾〉載人如不仁如禮樂何,則仁貴乎禮樂。
至於孟子將仁解作總德者大概只有一章,〈公孫丑〉: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如恥之,莫如仁。」後兩仁字,朱熹訓為全德之仁,謂:「仁、義、禮、知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又曰:「不知禮義者,仁該全體,能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乃諸德之一,則見諸於各章,如《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雍也),「仁者必有勇,勇者未必有仁」、「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憲問)。〈陽貨〉篇更以「仁、知、信、直、勇、剛」為六德,則仁為眾德之一甚明。
孟子論仁以全德之義為中心者較少,通常是仁義並用。如
〈離婁上〉:「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告子上〉:「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知也。」;
〈盡心下〉:「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
〈盡心上〉:「仁義禮知根於心」等等。
孟子以仁與諸德並列,明顯凸出仁乃德行的一種。 在《論語》中,只有〈學而〉載有子言:「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如此,則仁並不等於孝悌,要行孝悌,必須先具備仁的心。又子曰「仁者愛人」,均說明不同環境依恃著仁呈現不同的德行。
人如何成就全德的「仁」,即如何成就終極的道德境界,亦即是後世所說的「完人」。人具有與禽獸無異的原始欲望,同時亦具人類獨有的善。兩者之間如何協條?
要達至仁的境界,就要反躬求諸己。甚麼是「反躬求諸己」?就是先要相信人有性善的根器,而人雖有仁的根器,可惜受利欲所薰染,時生疑惑,所以必須時加反省,體察自己的行為;故必須「日三省吾身」、「克己復禮為仁」、「苟志於仁,無惡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等。「三省吾身」是思考自己的行是否正確?「克己復禮為仁」就是修,就是戒,凡違背禮者要堅持拒絕,要「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所謂「克」是有壓制、強抑的意思,即日常生活我們必定遇到一些誘惑,誘惑出現,要以禮作為衡量,不合禮者不為。亦即是,人要支配自己而對抗外界的引誘,使自己行為合乎道德人情,唐君毅先生說:
你首先當認識:支配自己是比支配世界更偉大的工作。西方的諺語「拿破崙能支配世界,然而不能支配自己。」因為他不能控制他在島上時的煩悶。你能支配世界,戰勝世界,只是表示你的意志力,能破除一切阻礙。而支配自己,戰勝自己,則表示你能主宰「用以破除外界一切阻礙之意志力」之本身。8
我們的行為過份,傷害別人,我們的欲望,蓋過我們的理性時,我們的善性就難發展出來。故此,必須經常提醒自己,使道德之心不退。當我們知道甚麼是「仁」的行為後,就不會隨便放棄仁的行為,此境界亦即是明代理學家王守仁所說的「知行合一」,你不行,是因為你不知。人類總把自己的力量向外移,向外發展,用盡心思氣力去支配外在的一切,少將心思氣力,反照自身,自我檢討提升。因此,反躬自省是大丈夫的行政為,肯為自己的負面行為思想,作審視及改正。儒家有一把尺(標準)去量度自己的行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公孫丑上〉:「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行為上有問題,就要自我反省。「不怨勝己者」就是反求諸己,是不是自己有不足之處。「不怨天,不尤人」,甚至橫逆加於身,亦必自省。所以,唐君毅先生說:
如欲求自覺的道德生活,我們首先要把我們全部的生活習慣,翻轉過來,把力量往內用。所以我們首先要支配自己的價值,看成比支配世界高,去作如上之思維。9
〈離婁下〉:「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恆愛之,敬人者恆敬。有人於此,其待我心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倘若自己以為已具備仁愛、禮敬之心及行為,仍遇「橫逆」者,最後亦是要自省。當然,經反覆自省及思考後,發覺自己的行為沒有錯誤、理念上沒有私心,所作皆合乎道義,則要有「雖千萬人而吾往矣」的氣概去堅持。人當有「道德自我主體力量」,人是自由的,自我選擇行為,所謂「你作的行為是你作的行為」(唐君毅先生語),自我負責。正如〈盡心上〉:「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一切道德,本自具足,領悟箇中道理,是人生最大樂事。
四端雖與生俱來,但不懂得自我反省,不能持久呈現。〈告子上〉: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謂美乎?…..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離禽獸不遠矣!
仁是心,義是實踐。不要放棄求仁的決心,否則與禽獸無異,因為禽獸不會反省,不會求仁,禽獸一切的行為都是生物性的自然反應。倘若人放棄人獨有的追求善、追求仁的心,則與禽獸有何分別?人之所以行惡,跡同禽獸,主要是未見到自己的善性,故唐君毅先生說:
如果你甘願縱欲為惡,莫有人能限止你。但是如果你真知道了,縱欲者終當被索還其由縱欲而生之樂,誰復還要自覺的去縱欲?如果為惡者,將來終被良心逼迫而為善,誰復還自願在現在為惡?10
唐氏的見解,是建基於人本性善的基礎上。若人本性為善,其為惡的良心責備早晚會出現,這亦是儒家思想對人性有信心的明證。〈滕文公上〉:「分人以財為之惠,教人以善為之忠,為天下而得仁者謂之仁。」仁者所作的行為皆合乎道,因此可以內聖外王。內成就自我的道德境界,外則影響別人,使其同追求品德的提昇。佛家提出「戒、定、慧」去面對五濁世界的誘惑,孔孟提出禮治、反省,而使本性自有的「仁」(涵蓋諸德者),呈現於生活中。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請留意,這兩句說話不是學問,而是實踐。沒有在生活中,生命的過程中反復思考檢討,那只是空談,只是用來調劑生活的文字。佛家所說的小悟數百次,大悟只需一次,其實亦適用於儒家。如果有日我們清楚自己本性為善的時候,對過往為惡的行為必然產生後悔或反省。
孟子所提出仁政、王道、王政等概念,是基於他提出的性善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梁惠王上)推己及人,而遍於天下,如此則大同小康的社會便會出現。齊宣王的好貨好色,孟子亦不加以批評,指出「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梁惠王下〉。是承認人的原始動物本能,但動物性外,還有一個令人類足被稱為人的「善」。發揮本有的性善,人就無往而不利。所謂「舉斯心加諸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孔子的忠恕是「內聖」,而孟子的「仁政」是外王。能內聖就能外王,孟子的性善論就是說人人皆能內聖外王,因為人人皆性善。「內聖」是成就自己的精神世界,「外王」是面對物質世界種種事物的適當行為。〈公孫丑上〉指出人生而皆有四端:仁、義、禮、知,並引孺子將入於井,人自然的心理反應作為例子,不造作、不用思考的行為,明確指出人的本性是「善」。
人無異於禽獸者飲食情慾,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乃人具有四端。人倘若放縱慾望,過分著重感官的享受,就會「陷溺其心」〈告子上〉,使與生俱來的善性受到蒙蔽。容格的一段說話足以表達現代世界最大的問題:
人類最大的敵人不在於饑荒、地震、病菌或癌症,而是在於人類本身,因為,就目前而言,我們仍然沒有任何適當的方法,來防止遠比自然災害更危險的人類心靈疾病的蔓延。
請反復思量,我們人類是享受欲望,抑或是受制於欲望而埋沒了本性。精神世界是無限的,我們可以感覺宇宙的存在,為世界的和諧而感動,此無限郤能呈現於我們有限的物質身體世界。凡此種種精神世界的元素,均能限制我們的欲望,而達至進退有據,不離本性的行為的境界。最後,我以唐君毅先生的說話作結:
從外看人是隸屬於現實的物質身體之世界;從內看人則隸屬於超越現實的純精神界。而物質身體的世界之所以為物質身體世界,即在能表現人之精神。所以人之精神,必需表現於物質身體之現實世界。精神實在所要求的,即是表現於現實世界,其能表現於現實世界,即所以成其為精神實在。精神實在之本身是無限,無限必需表現於有限。因為由有限之超越破除,而後才顯出無限。11
原載於《「第二屆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孔教學院,2006年。
All articles/videos are prohibited from reproducing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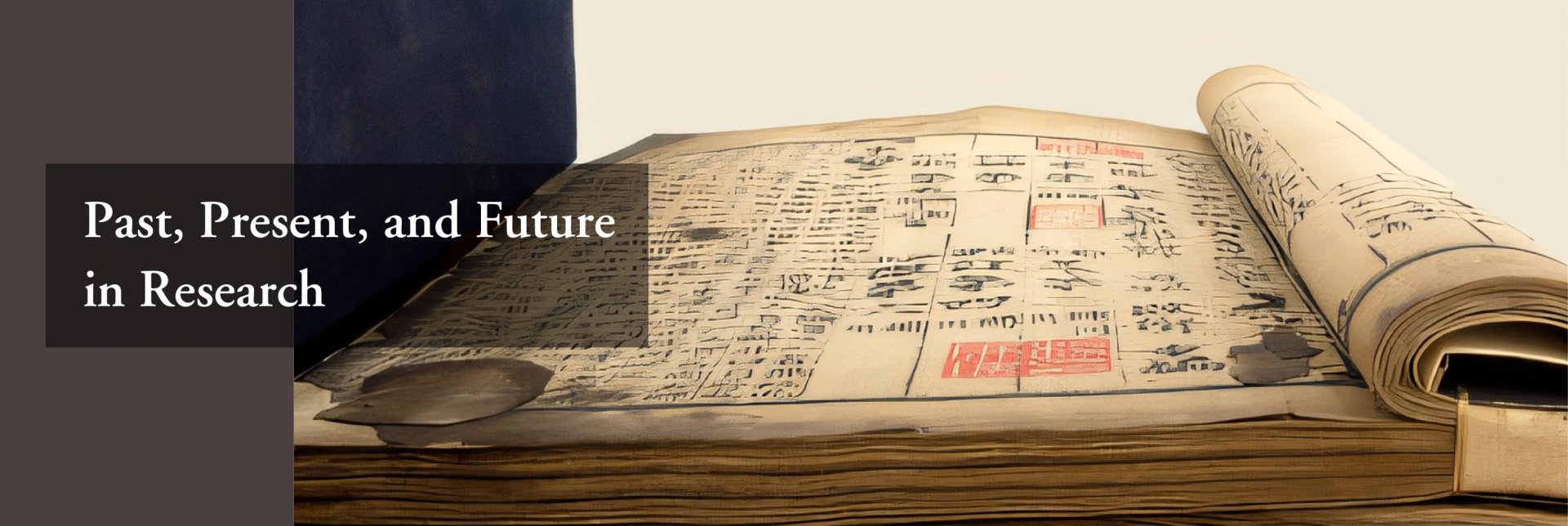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