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词考释中的艺术智慧——重读陈熙中先生《红楼求真录》札记
【内容摘要】《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读者甚众,影响深远;「红学」多历年所,名家辈出,歧解纷纭,已然跻身于「显学」之列。北京大学陈熙中教授精研古代小说及理论批评,蜚声海内外,尤以擅考据、释疑难闻名于「红学」界。其考释字词、辨析版本,不仅内证、外证并举,且贯之以艺术慧心,以文学审美之道资考据、见卓识,深化了古来「考据、义理、词章」三位一体之学术传统。
【关键词】字词考释;艺术智慧;《红楼梦》;陈熙中;学术精神
四十年前,即1984年12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熙中先生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发表〈皎然诗说并未涉及涉及意境〉一文;后收入《红楼疑思录》,题为〈释「境象非一,虚实难明」〉。一般认为,皎然是中国古典意境美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但其所作《诗议》提出的「境象非一,虚实难明」,究竟与「意境」有何关係,此前未曾得到反思、省察。〈皎然诗说并未涉及涉及意境〉一文率先发复,以文本之间的联繫为依据,明确指出:此所谓「境象」乃对偶技法常用名物类型之一,如日光、风、色、影等,其存在状态介于虚、实之间,无关乎后人盛称的「虚实相参」之「意境」美1。此文发表后,令人关注,引发相关讨论2。而大凡认真看过此文者,一般不再袭用固有成说,避免以「境象非一,虚实难明」为例阐释古典意境理论内涵。遗憾的是,或因年代稍远,且疏于了解学术源流,迄今不少论家仍以「意境」审美特征解说皎然「境象非一,虚实难明」语义3。此类「三人成虎」现象,每令切近实情之真知难以转化为学术新知。
不过,合乎事理之卓见,自有明眼慧识,诚心推赏,泽及文囿。比如,熙中先生曾应约校注冯梦龙《喻世明言》,不仅令约稿者兼责任编辑惊喜有加4,学界亦赞歎不已5。因此,该书于1994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初版之后,又于2014年被列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经典小说注释系列」丛书之一。迄2023年5月,中华书局版已印刷5次;在电子读物风行的网络时代,一部纸本图书仍如此广受读者青睐,或有助于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学术质量。
熙中先生长期耕耘于古典小说与理论批评史领域,不仅费钜力与人合作编着了影响深远的《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与吴小如、于洪江合着《小说论稿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而且在「红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成果。这些重要成果,或直接体现于2000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红楼疑思录》、20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求真录》两部论着中;或间接体现于《红楼梦》相关校注本中,如应约独立完成的简注本《红楼梦》6,多次受邀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校注工作顾问7。
有关这些方面的成就,多次参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校注工作的吕启祥先生有如下评述:「我是陈熙中教授文章的忠实读者。之所以喜爱,凡有所见必找来读,是因为他的文章篇幅短小、开门见山、笔力集中、论据充足、思致周密,终于『板上钉钉』,不由得你不心悦诚服⋯⋯常常是既有纵深,又能辐射,更可触类旁通,给予人的知识、趣味以至于智慧,就关涉到学问之大者了。」8就笔者学习心得而言,窃以为熙中先生治「红学」,颇多启人心智之法门,概言之,约略有三:一是如老子所言「为大于细」,一字不放鬆9;二是细处着眼而不乏方法论意味10;三是字词考释与艺术慧心相结合。鉴于目前学界尚未足够注意第三点之学术意义,本文拟稍加阐述。
(一)《红楼梦》文义考辨中的艺术审美之道
就中国古代学术传统而言,大体上可分为侧重「我注六经」之「汉学」、侧重「六经注我」之「宋学」。若再细分,又有「考据、义理、词章」各有侧重者。与此相关,则另有注重「考据、义理、词章」三位一体之主张。段玉裁即如此总结戴震治学理念:「称先生(戴震)者,皆谓考覈超于前古。始玉裁闻先生之绪论矣,其言曰:『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覈之学。义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覈、能文章。』……后之儒者,画分义理、考覈、文章为三,区别不相通,其所为,细已甚焉。」11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论学问之事,同样秉持此观念,〈述蓭文钞序〉曰:「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12不过,在理解「义理、文章、考证」三者关係时,一般认为「文章」乃表达义理、组织考据之载体,故不可偏废,此即章学诚所言:「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徵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13以此为参照,可知熙中先生不仅在考据方面并重内功、外功14,故能于理论观点层面独标胜义、一语破的,而且在词章表达层面要言不烦、简洁明晰。关于熙中先生学术文章之美,吴小如先生以为贵在「短小精悍」、「词锋锐健」、近乎「『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小品」,「可读性很强」15。笔者拟补充的是:熙中先生以考据、释义为要务的学术论文,不仅在语言表达层面自成一体,达到了前人所谓「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兼备之境,而且在词义考释过程中,往往贯穿着「词章」之学更深层的内涵,那就是考据、释义遵循词章艺术规律,力求切当;而论词章艺术又严守文本、词义阐释之规则。相得益彰,充实有辉光。兹以《红楼求真录》为例,略加阐述。
譬如〈曹雪芹患有癫痫病吗?〉一文,单刀直入,立题即点明要旨。全文针对「红学界」乐于「索隐」者观点而发,明确指出不宜「把小说中有关宝玉的描写,完全当作作者生活的实录,即所谓『实有之事』」。为了说明此一问题,作者从两个层面予以论析:首先,引用相关原文,细緻解读文本,以为脂砚斋批语「此是忘机大悟,世人所谓疯癫是也」,并非指贾宝玉「同神经衰弱或精神病之类有什麽关係」,而是指「宝玉的这种行为在『世人』看来是『疯癫』,其实不是」,破其他论家立论基础,令人信服。其次,作者更进一层,举例说明「小说中的贾宝玉」不等于「历史上的曹雪芹」;因此,退一步说,「即使主人公宝玉的症状很像是癫痫病,我们也没有理由因此而推断出作者曹雪芹年轻时也得过同样的病,除非我们把贾宝玉和曹雪芹完全等同起来」16。此一论述,理据兼备,尊重文学文本之义理逻辑,突出了文学作品与现实人生相「通」而未必相「同」这一常理。笔者八十年代初上大学时,第一学期有科目曰「文学概论」;老师授课,就讲到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现实原型之间的联繫与区别。可见此观念属于文学常识范畴。熙中先生的这篇短文,言简意赅,却实实在在地给读者两点启示:其一,平心静气地研读文本,至关重要,切忌成见在先而后断章取义;其二,文学研究不宜违背「常理」,将作品等同于史料,难免两伤:既偏离了文艺审美之道,也溷淆了现实之真。
在遵循文艺审美之道以资考据、见卓识方面,〈龄官究竟画了多少个『蔷』字?〉一文更具典范性。吕启祥先生对此评价甚高:「由此我们还可以悟得:读《红楼梦》不只要关注局部,还应统观整体;作家固重在写实,『不敢稍加穿凿』,亦无妨夸张形容,涉笔成趣;等等。」17按,此所谓「亦无妨夸张形容」者,实即文艺审美创造手法与规则之一。比较理想的古典文学研究,从版本考辨、文字校勘、词语训释到文义阐释,均不宜背离此一审美规则。熙中先生在讨论《红楼梦》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龄官画蔷痴及局外〉「已经画了有几千个『蔷』」一语校勘问题时,广泛收集《红楼梦》中的同类例证,以小说艺术审美之道为指引,提出如下新论断:「我们认为,『几千个「蔷」字』」『几万声』『一二百句「不敢」』,都是曹雪芹的原文。反之,『几十个「蔷」字』『几十声』『一二十句「不敢」』,都是后人的改文,因为很难想象,抄写者会逢『十』必错,把三个『十』字分别抄成『千』『万』『百』」,「不言而喻,曹雪芹在这些场合运用的都是艺术夸张的手法。从日常的眼光来看,它们也许显得不合情理;但在小说中,这种夸张手法不但是允许的,而且自有其独特的艺术效果」18,其认识超越了看似「确定无疑」的已有结论。这一考辨过程颇精彩,以艺术灵动之思,破除胶着拘执之蔽,反成考据之胜境,不由得令人想起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段着名公案19:北宋沉括评杜甫〈武侯庙柏〉(即〈古柏行〉)诗句「霜皮熘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曰:「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此亦文章之病也。」20而王观国则认为:「杜子美〈古柏行〉曰:『霜皮熘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存中(括)《笔谈》曰:『无乃太细长?』观国按:子美〈潼关吏〉诗曰:『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馀。』世岂有万丈馀城耶?姑言其高耳。四十围二千尺者,姑言其高且大也,诗人之言当如此,而存中乃拘拘然以尺寸校之,则过矣。」21关于夸张艺术,刘勰《文心凋龙·夸饰》篇以为「壮辞可得喻其真」,「文辞所被,夸饰恆存」;「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信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矣」22。可见其艺术效果之巨大。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倘能恰当运用此一美学原理,且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其于考据、谈艺之功效亦大矣。类似的个案,《红楼求真录》中所在多有,如〈「钗黛合一」的是与非〉、〈从贾宝玉的年龄说起〉、〈黛玉临死「含笑」辨〉等等,皆切情合理,颇中肯綮。
(二)《红楼梦》评点内涵阐释中的艺术审美之道
从《红楼疑思录》到《红楼求真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者,乃作者精于考证之功,实际上无妨补足一层:作者擅于考证而鞭辟入里,除了知识广博、学养渊深以及思力精微而外,谙熟小说艺术审美之道,以遵循艺术规律之思,令考证、释义工作如虎添翼,更上层楼。此一艺术智慧不仅体现在《红楼梦》文本校勘、字词阐释以及艺术匠心的论析中,而且也体现在有关《红楼梦》评点之理论内涵的理解方面。譬如《红楼梦》第九回宝玉上学「忽想起未辞黛玉」句下之脂戚本双行夹批:「妙极,何顿挫之至。余已忘却,(阅)至此心神一畅。一丝不走。」23有论者将「余已忘却」一句理解为评点者「脂砚斋本人小时候真有之事」,但「早已把这件事情忘掉了,看了小说以后才又想起往事来」24。这种研究思维,依然是将小说中的贾宝玉形象与现实中的评点者生活直接等同起来。熙中先生则从评语与小说情节内容关係角度,指出该评语的实际内涵「正在于称赞作者行文『善起波澜』,顿挫有致,能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25,因此,「余已忘却,至此心神一畅。一丝不走」云云,根本不是指评点者往事而言,而是指「我这个批书人都几乎忘了宝玉还没有和黛玉告辞呢,读到这里,真是叫人高兴,原来作者早有全局在胸,一笔不漏」26。看似简单的一句小说评点内涵之解读,其实隐含着小说艺术研究的重要原则问题:「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有些研究者或者由于对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特点认识不清,总是喜欢把小说和真人真事等同起来;或者由于对脂批本身缺乏全面的理解和研究,因而往往对一些批语作出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甚至随心所欲的解释。」27按,研究小说作品而忽略乃至无视小说艺术审美规律,或者研究古典文学而罔顾文学内在本质特性,此一思维方式本身即不无讽刺意味;倘因此随意申说、附会臆想,则所谓「文学研究」必名不副实、将遂讹滥。故熙中先生意味深长地说:「希望《红楼梦》研究者能够注意到并克服这个缺点,便是我写这篇小文的主要目的了。」28刘勰说「文果载心,余心有寄」29,面对当时文体解散、言贵浮诡之积弊,希望藉助《文心凋龙》以疗救之,大体也出于相似之心境。
在如何确切理解脂砚斋评语内涵方面,熙中先生对于《红楼梦》第十九回一条批语「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之辨析,给笔者留下非常深刻印象。因为此文正式发表前,他便在书斋中为诸生讲解问题关键之所在,以及如何切实理解之方法问题。现见收于《红楼求真录》,得以反復揣摩,平添读书乐趣,无妨简述其要点,分享其学术智慧。熙中先生指出:在吴世昌先生《红楼梦探源》英文版出版以前,「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情榜』以及『情不情』和『情情』这两个评语的意义。《探源》的解释和推测,虽不免有误,但它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探源》将「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翻译为如下意思:「对宝玉的评语是『多情而又无情的(恋人)』,对黛玉的评语是『具有纯洁爱情的恋人』。(The verdict on Pao-yü is ‘Passionate [Lover] yet without Passion at all ’, that on Tai-yü is ‘Lover with Pure Love’」30熙中先生援引其他相关材料,归纳了脂砚斋同类评语的基本意思:「脂砚斋是把『情不情』理解为『对不情者也有情』。从语法上来讲,就是把『情不情』看作是动宾结构,第一『情』字作为动词用,『不情』则是它的宾语。」「不用说,脂砚斋对黛玉的评语『情情』,也是作为动宾结构来理解的。『情情』者,对有情者有情之谓也。」作者从语法、宝玉及黛玉性格特点等角度说明了「脂砚斋对『情不情』和『情情』的理解是比较符合曹雪芹的原意的」,而「《探源》中的译法,恐怕与作者的原意就相去甚远了」31。如此论析,似乎只涉及《红楼梦》评语内涵的理解与英译问题,而贯穿其间的重要治学思路,仍然关乎小说艺术之创造,故作者特别指出:「我个人的看法,认为『情不情』和『情情』这两个评语,涉及曹雪芹塑造宝、黛形象的指导思想,很值得深入研讨。」32《红楼求真录》中的〈「今古未有之一人」——脂砚斋论贾宝玉〉、〈「真有是事」〉、〈「三字有神」〉、〈「深得《金瓶》壸奥」——略谈曹雪芹对《金瓶梅》的艺术借鉴〉等文,也同样体现了类似的治学理念,那就是艺术审美之道与学术难题考辨两相结合,共成胜境。
(三)学术渊源述略
熙中先生擅考据而文中常蕴艺术思维智慧之光,从学术传统上讲,自有渊源。譬如,熙中先生主张学问之基在读懂原文、一字不放鬆,与朱自清、吴小如诸先生学脉承传关係密切33,其注重文学文本自身情理、审美境界之道的学术取向,亦不离此学统。按,朱自清先生有言:「多义也并非有义必收:搜寻不妨广,取捨却须严⋯⋯断章取义是不顾上下文,不顾全篇⋯⋯往往支离破碎,不可究诘。我们广求多义,却全以『切合』为准;必须亲切,必须贯通上下文或全篇的才算数。」34 吴小如先生亦谓:「至于我本人,无论是在课堂上分析作品或写赏析文章,一直给自己立下几条规矩。一曰通训诂,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这一总的原则,由它来统摄以上四点。」35说法有别,精神则一,皆注重文本脉理之自洽也。又,吴组缃先生承朱自清、浦江清诸前贤教泽,在小说研究方面,给予熙中先生更直接的启迪:「大学期间,吴组缃先生给我们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誌异》和《红楼梦》等小说,先生精辟独到的艺术分析,令我们如醉如痴……吴先生本人又是着名的小说家,有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因而能深切把握小说的艺术特征……指出『凡是阉割了艺术的生命,抹杀了文学作品的特点,那方法都是错误的』。可以说,正是受了吴先生的影响,我对『索隐』之类始终不感兴趣。」36「回想当年听组缃先生讲课时,曾产生一种梦想,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像先生那样,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思想艺术有一种全面系统的领会把握。然而,受个人的才性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几十年来,我只能为古代小说研究这座大厦添加几块砖瓦而已,这是很惭愧的。但愿这几块砖瓦不是豆腐渣。」37峻宇牆深而虚怀若斯,愈加令人景仰;其追述吴组缃先生之治学精神,则有助于后学略窥艺术智慧、字词考释如何交相辉映之法门。
综合上列诸例之简要述评,则熙中先生治「红学」乃至古典小说与批评,其「艺术智慧」可概而言之:其一,读书谈艺,必求根柢不易其固,一字不放鬆,尽咬「文」嚼「字」之功,收确定难移之效;其二,简明扼要,直面问题,明察要害,具行文短小精悍之美;其三,字词考释,不拘执于局部,而是服务小说艺术规律这一大宗旨;其四,深谙文艺审美之道,在理据上为考证增添助力与光彩。又,熙中先生好书法,长期习草书,对汉字书写艺术深有体会,且融入《红楼梦》抄本文字的勘定、解读工作,几成独到之秘。譬如近期写成的〈读红零札二则〉,涉及《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史湘云、林黛玉联诗「寒塘渡鹤影,冷月葬(死、诗、花)魂」文字校订问题。庚辰本原写作「葬死魂」,但「死」字被点改为「诗」,另有一些版本则作「葬花魂」。因此,学界讨论之重点,基本上都是围绕「诗魂/花魂」展开,并未注意「死魂」之「死」这一字形暗藏之玄机。熙中先生根据《红楼梦》各种抄本、古人书写特点及习惯,列举相关书写案例,推断抄本「死魂」之「死」,其实是「鸳鸯」之「鸳」的简笔,原文宜作「鸳魂」38。此一见地,慧眼独具,证据确凿,有力推进了此一学术难题之研究。要言之,书法是一门传统艺术,如何识读古书抄本、稿本文字同样也是一门艺术,而《红楼梦》版本考辨、文字校勘、文义解读与文字书写研究关係甚密切,熙中先生于此多有创获,同样是艺术智慧之体现。限于篇幅,拟另文述评。
注释 :
1. 参见陈曦钟:《红楼疑思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页70-73。按,陈熙中先生常用笔名有陈曦钟、曦钟、闻而畏等,下文不再出注说明。
2. 参见陈曦钟:《红楼疑思录·后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页233-234。
3. 姑列举数例如次:1)「新浪博文」(2010年3月24日)〈取境与辩体——浅论皎然《诗式》的理论价值〉:「皎然《诗议》说:『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凡此等,可以偶虚,亦可以偶实。』意在说明:其一、『境』的形象美是由众多因素组成的……其二、上述诸因素要在变化中加以调节融合达到协调……强调艺术概括的重要作用。其三、『心』的总体概括作用,具体表现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关键是处理好『虚实』关係……这就需要虚实互用。」http://blog.sina.com.cn/u/1355698062;2024年7月16日14:49访问。2)陈望衡〈中华美学的唐诗品格〉:「皎然的『境』论有三点特别重要:一是诗之妙在圣……二是境之成在虚与无的统一,此统一为『境象』。『境象』之妙在虚。『境象不一,虚实难明』,虚,不是虚无,而是『渊奥』,它『可以意冥,难以言状』。三是境之美在情……」《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页49。3)李浩〈探寻唐诗境界美的奥秘〉:「皎然在《诗式》中也反復谈到『境』或『境象』。《诗议》中曾论及:『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谓『境』与『象』并非同一概念,所指各别,其中『境』『虚』而『象』『实』,但难以进一步说明。这两句话实际採用了互文句法,表达了这样几层理论含义:一是境与象,即境界与意象是有区别的;二是境虚而象实,即意象为有限,而境界则指向无限;三是意象与境界的奥妙都神秘难明。」《人民政协报》,2022年08月15日 第 11 版。4)张立文〈境界论〉:「人们体认意义、境界的道理,与蹄筌捕捉兔鱼的道理是相通的……此道或理是一种意义和境界,是一种『境象非一,虚实难明』的状态。超越象而达境理,超越虚实而澄明境界、境道⋯⋯这个真实存在是概念性、精神性、逻辑性的存在,是『虚实难明』的……」《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3期,页149。5)简圣宇〈唐代「境」的概念演化及其意义〉:「今日学者所用『意境』通常包含三个核心特徵:『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和『韵味无穷』……皎然在其《诗议》里提出:『夫境象不一,虚实难明……』在皎然看来,意境存在不同的显现状况,是一种由各种虚与实的成分结合而成的统一体。」《人文杂誌》,2023年第9期,页94。
4. 谢颖〈韩敬群:每本书都有一个故事〉:「我觉得独自面对他们的书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上课,是一个人的课堂,一对一的『私教』。这是我内心深处的真切体会。」「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熙中老师,我上研究生时选过他关于《二十四诗品》的课……后来我在出版社想做《三言》注本,当时《三言》有好的版本,但缺乏好的校勘注释本,我便想到请陈先生做《喻世明言》。坐在办公室里仔细读书稿,我才深深体会到陈老师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学术作风。」《人民政协报》,2019年11月第9期第05版「文艺副刊」。
5. 哥舒〈譬如积薪 后来居上——读陈曦钟《喻世明言》新注本〉:「新注本在校勘原文方面更为细緻,一些旧注本失校之处,在新注本中得到了校正。」「旧注本中有些注错了或注得不确切的地方,新注本多有补正。」「这个新注本的『新』更突出地体现在它新增加的注释条目上。许注(笔者按,指许政扬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共1600多条,而陈注则有3500多条,约12万字。从新增条目的内容来看,绝大部分属于应该出注的难词、典故、史实等。」「对于一些看似易懂而实际容易误解的词语,新注本的注释更使人感到大有裨益。」「这个新注本还有一些别的特色,如在注释中注意引用《水浒传》等古代小说作例证和比较等。」「钱锺书先生在〈钱仲联着《韩昌黎诗繫年集释》〉一文中说,完全能够代替旧注本,『对于一个后起的注本,这也许是最低的要求,同时也算得很高的评价了。』我认为,《喻世明言》 陈注本可说是符合这个『最低的要求』,同时也当得起这种『很高的评价』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页122-123。又,参见王峰〈「三言」校注的新成果〉,《中国图书评论》,1996年第3期,页59-60。
6. 曹雪芹着,高鹗续,陈熙中注释:《红楼梦》,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19年。
7. 刘梦妮:〈苦心校注字字较真,一修再修务求更「真」:接力近半世纪,只为一部更接近曹雪芹原着的《红楼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熙中多次为修订提供重要意见,在他看来,诸多抄本的陆续发现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抄本,我们只能读到120回的程高本,不可能再进行别的研究,接近曹雪芹原着的《红楼梦》恐怕也看不到了。』」《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11月4日第11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红楼梦》校注本四版修订说明〉:「北京大学中文系陈熙中教授作为特别邀请的顾问,提出了许多修订建议,提高了修订工作的学术质量。」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4版,页2。又,韩寒〈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推出新修订版〉:「作为红研所校注本《红楼梦》2022年版邀请的学术顾问,陈熙中提出了不少修订建议。而他的本心,也在于『接近曹雪芹原着的面貌』。」《光明日报》,2022年9月27日第8版。
8. 吕启祥:〈见微知着 言必有中——读陈熙中《红楼求真录》(代序)〉,陈熙中:《红楼求真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1。
9. 参见弘锋居士:〈师门「一字禅」〉,WeChat公众号「海日江春读书天」,2022年2月3日。
10. 如王希杰〈作为方法论原则的零度与偏离〉以熙中先生〈《红楼梦》语言中的一个谜:「足的」——兼谈庚辰本的真伪问题〉一文为例,概括其方法论意义:「他虽然没有说零度偏离,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他的方法论原则就是,在众多偏离形式中寻找那个能够产生出这众多偏离形式的零度形式。」《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页117。又,林嵩〈论校勘学上的零度与偏离原则——《王子年拾遗记》异文释例〉:「值得一提的是,陈曦钟(熙中)近年所写的〈读红零札〉、〈读《水浒传》零札〉等一系列文章,其总体思路都在践行零度偏离的分析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可以使一些似是而非的误改得到纠正……而且,通过对 『零度』的找寻,把这些点点滴滴的问题联繫起来看时,我们对于《 红楼梦》、《水浒传》等书的版本问题,也可以形成比较具体的认识⋯⋯」《文献》,2016年第4期,页69-70。
11.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震撰、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1。按,戴震〈与方希原书〉有言:「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长、孟坚、退之、子厚诸君子之为之,曰:『是道也,非艺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诸君子之文,亦恶睹其非艺欤?夫以艺为末,以道为本……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戴震撰、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143-144。
12. 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卷四,上海涵芬楼藏《四部丛刊》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页30。又,姚鼐〈復秦小岘书〉:「鼐尝谓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惜抱轩诗文集》卷六,上海涵芬楼藏《四部丛刊》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页52。
13. 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章学诚着、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799-800。
14. 吕启祥序有内功、外功考证之说,实即内证、外证并重之法。参见吕启祥:〈见微知着 言必有中——读陈熙中《红楼求真录》(代序)〉,陈熙中:《红楼求真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2-3。
15. 吴小如:《红楼疑思录·序》,陈曦钟:《红楼疑思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页1-3。
16. 陈熙中:《红楼求真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197-198。
17. 吕启祥:〈见微知着 言必有中——读陈熙中《红楼求真录》(代序)〉,陈熙中:《红楼求真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1。
18. 陈熙中:《红楼求真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144-145。
19. 参见申自强:〈用尺子「量」诗引起的美学官司——美学聚讼录之一〉,《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页93-94;周一农〈夸张的维度与古柏悖论〉,《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页166-167;景北记:〈杜诗沉评小议〉,《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页76。
20. 沉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页221。
21. 王观国撰,田瑞娟点校:《学林》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261-262。
22. 张少康:《文心凋龙注订语译》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页151-152。
23. 陈熙中:《红楼求真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214。
24. 陈熙中:《红楼求真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215。
25. 陈熙中:《红楼求真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215。
26. 陈熙中:《红楼求真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216。
27. 陈熙中:《红楼求真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216。
28. 陈熙中:《红楼求真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216。
29. 张少康:《文心凋龙注订语译》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页376。
30. 陈熙中:《红楼求真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210。
31. 陈熙中:《红楼求真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212。
32. 陈熙中:《红楼求真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213。
33. 参见弘锋居士:〈师门「一字禅」〉,WeChat公众号「海日江春读书天」,2022年2月3日。
34. 朱自清:〈诗多义举例〉,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八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版,页208页。
35. 吴小如:〈我是怎样讲析古典诗词的〉,吴小如:《古典诗词丛札•代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1-2。
36. 陈熙中:〈为古代小说研究添砖加瓦〉,黄霖主编:《我们起跑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復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1。又参见:曦钟〈风范长存——忆念吴组缃先生〉,《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编辑小组编:《吴组缃先生纪念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267-270。
37. 陈熙中:〈为古代小说研究添砖加瓦〉,黄霖主编:《我们起跑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復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11-12。
38. 参见陈熙中:〈读红零札二则〉,《曹雪芹研究》,2024年第1期,页32-34。
冶寒斋主
二〇二四年九月廿六日
谨草于南海之滨
(原载于2024年9月26日WeChat个人公众号「海日江春读书天」)
< 原创文章/视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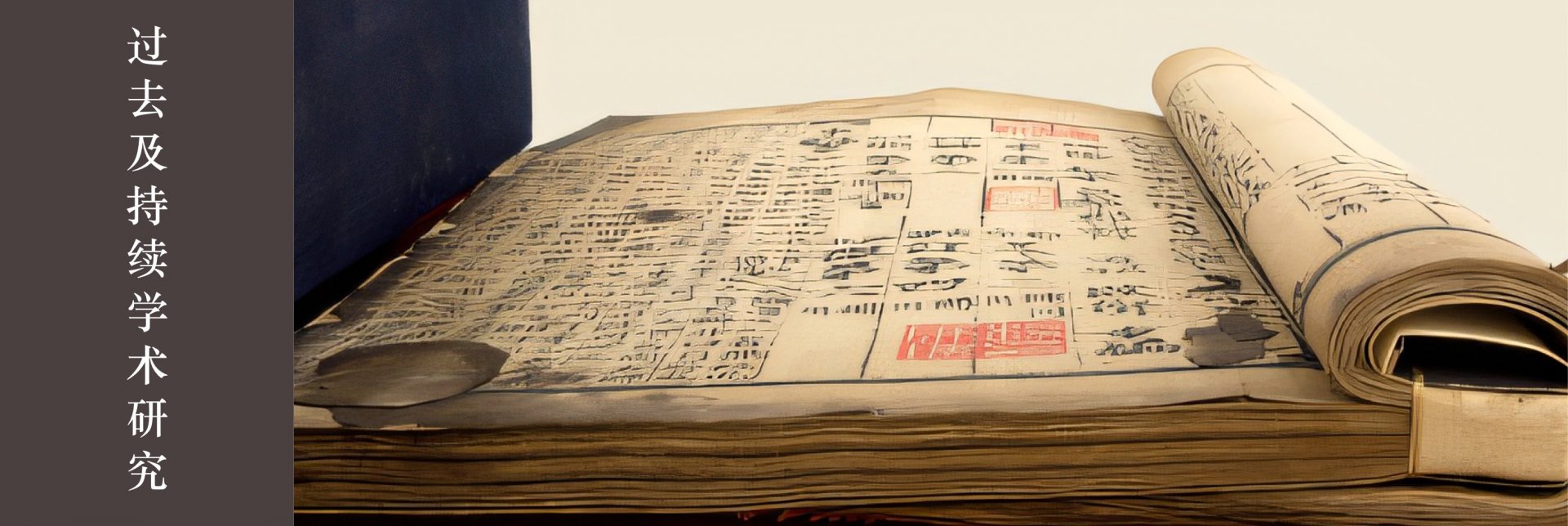



欢迎留言:
请登入/登记成为会员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