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公孙龙子》对本土心理学的启示
名家常被视为诡辩学说,但名家的方法论及其研究主旨常常被忽略。有别于逻辑实征主义的假设-演绎法 (hypothetical deductive method),名家的方法是先设立与常识有异的命题,然后从各种实证或推演中尝试找出可以证立这个和常识有异的命题的论证,从而扩阔人们对事物的领悟,在精神上这与现象学或解构方法有着相似之处。本报告从名家重要典籍《公孙龙子》中,发掘其关于心理语言学、概念生成过程、以及有关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的讨论。 (本研究为香港研资局资助项目,编号UGC/FDS15/H07/14))
关键字:名家 《公孙龙子》 心理语言学
名家的源头常追溯自惠施的「历物二十一事」(见《庄子‧天下》),在《庄子》一书的描述中惠施会召开国际的学术会议,并以一些表面上有违常识的命题,吸引不同的学者去思考这些表面上荒谬的情况下,到底可以追寻出什么样的道理出来,在《庄子》一书中,这些人统称「辩者」。这样的「辩者」和日后《鬼谷子》一书中呈现的那种政治说客的「辩者」本质上是有分别的 (虽然名家的「辩者」也可以这样的政治「辩者」作为职业,例如从《公孙龙子‧迹府》篇中,名家的主要人物公孙龙本身就是赵国平原君的幕僚及文胆,而惠施本人也是魏国的高级外交官员)(郑良树, 2000),于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学术式的辩者称为「名家」,而政治上的说客称为「纵横家」,两者各有不同的兴趣、术语、及不同的研究目标。名家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被贬为「诡辩」,总是被视为是专注于扭曲常识、纯綷满足于口舌之争的一派人物,而在不同的流派中,他们也是被打造成这样的负面形象,例如《韩非子‧外储》就描述当时一名叫儿说的宋国辩士喜爱拿「白马非马」的口号去逃避不交入城费,而被守军所不屑的事件。由此可见,名家的辩士都是无聊之辈,在「辩」之前总要加上「诡」这个字。
但若果「辩」只是口舌之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人类思想史中,大凡不是直接就涉及「实用」的东西,只要是「后设、难以直观理解」的,就是「诡」呢?这个「诡」字所代表的,是中国思想史以来的一个盲点﹕体系化的后设探讨,不论是何种形式,总是被「诡」字轻轻抹去;而其后续的生命力也遭到厄杀了。
当魏晋时代的大战乱令学者可以重新检讨传统价值观的时后,大家才重新发现公孙龙子;但这些古注也失传了,在《四库全书》中《公孙龙子注》的序言中提及《公孙龙子》被陈振孙以浅陋迂僻讥之在明钟惺本被更名为《辩言妄诞不经》, 似乎已是被视为「奇文共赏」而吊诡地反而因此得以留存,但也只有十四篇中存六篇 (而且〈迹府〉是后人所加的人物传记,则实际的学术篇章只有五篇),此可说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大缺口。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国时代的第一名心理学家─ 陈大齐先生在〈异白马于所谓马与白马非马〉(1951) 开始注意到《公孙龙子》的价值,但基本上停留在认为公孙龙是和墨家一样谈及范畴论的 (即讨论全体和局部的关系),而后来的本土心理学界对《公孙龙子》的讨论也并未热烈,亦未与后期墨家、荀子等就主要命题作出比较,因而难以获得较为整体的讨论。本篇的重点在重整《公孙龙子》在中国心理学史上的角色,从而略窥中国古心理学史的面貌,从其中希望理解到在「诡辩」的不公允评价下,以公孙龙为首的哲学的意旨为何。
本土心理学界通常较少引用《墨子》及《公孙龙子》两部书的内容,更遑论直接将之引入实际的应用之上,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因为这宣布了对于名家的研究永远停留在训诂层面,尤其是当《公孙龙子》呈现的是一种对心理语言学的严肃探讨时,对《公孙龙子》一书的关注可以填补本土心理学界对古代中国心理语言学的空白,其意义并不宥于纯綷心理学史的讨论,更多值得参考的是公孙龙如何在一个近乎空白的时空中创造出一套严密的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又与西方的现象学遥相呼应。若果深涩的现象学在西学也可以导引出现象学的心理学现究及存在主义疗法等等的应用,那么重新考掘名家,特别是《公孙龙子》一书,或许有助于本土心理学界能够承传、发展及再造出新形式的心理学。
Solomon (2013) 正确地指出名家至少可以分为两类﹕惠施的是「合同异」派;而公孙龙是「离坚白」派,而早期的以诠释法律条文的模糊地带而著称的邓析子又可说是早期的「辩者」(谭戒甫,1963)。这三种形态虽然表面上都违反常识、并且爱好辩论,但却有迥然不同的志趣﹕从现时看来,邓析子可以算是现代律师职业的鼻祖,专攻寻找法律的空隙以达致目标;而惠施探讨的是时间、空间表面上不可能性之中的新理解,很有可能是一种数学或物理探讨。例如《庄子‧天下》提到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就是探讨无限大与无限小的命题。可惜的是,惠施的著作全部都失传了。而公孙龙子的「离坚白」派却是探讨语言生成以及人类认知结构的流派,后世谈论公孙龙子多认为他只有讨论语言哲学 (例如〈白马〉篇提及「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也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很多时都被视为是纯语言学的探讨),但却忽略其与〈坚白〉篇中提及心理认知过程论的箇中联系。
《公孙龙子》一书为现存代表名家思想的主要文本,而争议性相对其他残留文本 (如《尹文子》)为低 (有关《尹文子》的争议,见宗静航, 2005)。现时《公孙龙子》六篇中,除《迹府》为公孙龙事迹之杂录,余五篇可视为统一的体系,亦有其他诸子可以相互参照的辩论。其中《公孙龙子》中的〈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都可直接与墨子《经》(及《经说》)、《小取》、《大取》篇有大量比照 (凡21条条目),后墨的做法是直接与公孙龙讨论辩题的内容和论证而后说其非,其主要进路是以全体-局部、以及概念生成的内涵来做讨论;并且认为事物的本质是自然存在于事物之中 (如坚、白、石)。在《墨子》的《经》和《经说》(两书需合并阅读,经是条目,经说是内容)中,〈白马〉〈通变〉 的内容多谈及范畴和语意的变化;而〈坚白〉则谈及各种感官之间的关系,是认知心理学的辩论。 〈指物〉和〈名实〉则谈论符号与物、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其中最多直接交锋的是〈白马〉〈通变〉和〈坚白〉。可以说,墨家和公孙龙的名家是这场古代心理学论战的直接参与者﹕
表一﹕《墨子》《经》《经说》《小取》《大取》中的相关条目
|
篇及句 |
内容 |
对应于《公孙龙子》篇章 |
|
小取4
|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
|
白马 |
|
小取7
|
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有乘于马,因为乘马矣。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不乘马
|
白马 |
|
小取8
|
之马之目盼则为之马盼;之马之目大,而不谓之马大。之牛之毛黄,则谓之牛黄;之牛之毛众,而不谓之牛众。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也,非两马而四足也。一马,马也。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
白马 通变 |
|
大取11
|
语经,语经也。非白马焉
|
白马 |
|
大取13
|
有有于秦马,有有于马也,智来者之马也。
|
白马 |
|
经上51
|
止: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若矢过楹。有久之不止,当马非马,若人过梁。
|
白马 |
|
经上67
|
坚白,不相外也。 于石无所往而不得,得二,坚。异处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 |
坚白 |
|
经上79
|
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1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声出口,俱有名,若姓字洒
|
名实 |
|
经下103
|
马麋同名俱斗、不俱二,二与斗也。包肝肺,子爱也。橘、茅,食与抬也。白马多白,视马不多视,白与视也。为丽不必丽,不必丽与暴也,为非以人,是不为非。若为夫勇,不为夫。为屦以买衣为屦,夫与屦也。 |
白马 通变 |
|
经下105
|
见不见离,一二不相盈,广修坚白
|
坚白 |
|
经下113
|
俱:俱一,若牛马四足;惟是,当牛马。数牛数马则牛马二;数牛马则牛马一。若数指,指五而五一 |
通变 |
|
经下115
|
不坚白,说在无久与宇
|
坚白 |
|
经下116
|
坚白,说在因
|
坚白 |
|
经下138
|
于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说在存。 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 |
坚白 |
|
经下139
|
有指于二,而不可逃,说在以二絫。 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举,重则。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举也,是一。谓「有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则当指之智告我,则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参直之也。若曰,「必独指吾所举,毋举吾所不举」,则者固不能独指。所欲相不传,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则是智是之不智也,恶得为一?谓而「有智焉,有不智焉」。 |
通变 |
|
经下140
|
所知而弗能指,说在春也、逃臣、狗犬、贵者。 所:春也,其执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处。狗犬,不智其名也。遗者,巧弗能两也。
|
指物 |
|
经下167
|
牛狂与马惟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曰之与马不类,用牛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若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是为类之不同也,是狂举也,犹牛有齿,马有尾。
|
通变 |
|
经下168
|
「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则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则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
|
通变 |
|
经下169
|
循此循此与彼此同。说在异。 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此此也。
|
名实 |
由上表所见,墨家对〈名实〉及〈指物〉的讨论相对较少;或者我们可以视〈名实〉〈指物〉为公孙龙对于墨家思想的一个概括性攻击;而〈白马〉〈通变〉及〈坚白〉三篇则直接纪录了名墨两家的辩论内容。由《公孙龙子》中纪录墨家的质询看来,这些质询和《经》《经说》《大取》《小取》都非常一致,可以推测《公孙龙子》一书的内容在《经》《经说》等之后,是名家对于墨家的回应 (相反的,墨经中较少提及公孙龙子的回应)。
而道家对于名家的攻击可以概括在以下一句说话之中。 《庄子‧齐物论》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庄子并非全盘否定名家,甚至认同「非指」和「非马」(见萧裕民, 2006)。庄子的切入点和墨家完全不同,庄子代表的道家虽然在根本上反对辩论,但其立足点是语言并没有可能导往完全的真理,必需要以语言之外的会意去体察万物 (所以符号不能带出符号以外的意旨)、而庄子对于公孙龙的心理主义 (即﹕「马」在本质上和「白马」是心理世界两个不同功能、不同概念、不同意涵的「物」) 认为可以推而广之,令人体察到在各种事物之间的「存在」,所以若果到达这种境界,则「非马」与「马」都可以消解,从「马」中就可以体验存在 (天下一马也)。可以说,若果墨家/ 名家的争论点是在学术理论内容而非方法论;则庄子所非难名家之处主要不是其内容,而是名家的方法。当然,公孙龙是否如庄子所理解的一般,「非马」与「非指」是否只是想表达世界及人类知识的虚妄、而又进而可以得出「一指」「一马」的存在,又当别论;若从《公孙龙子》一书的编排详细考察,则公孙龙探讨的是「变」而非「一」,这里可以视庄子为借题发挥。
而儒家的荀子亦直接参与名家的辩论,这里名家的「名」是解作语言,荀子的《正名》详谈语言、名实,认为是管治者发明一套语言,人类可以借此说明万物。因此,他认为要设立有关语言使用的具体规章,使语言不要开始分歧。而同样的字可以应用于两个或以上的意涵 (二实)、或者倒过来多个词语指向一个意涵 (化、一实)。荀子反对墨家以辩论能够带来新发现的说法、亦直接批评「有牛马、非马也」等公孙龙的命题,都是「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是以,必须定立详细定义 (验之名约),并且以概括的方式作出总结性评价 (以其所受,悖其所辞),更要对这种活动加以贬抑 (则能禁之矣)。
表二﹕荀子《正名》与《公孙龙子》的相关讨论范围
|
正名1-4
|
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
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性伤谓之病。节遇谓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然则所为有名,与所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
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
|
荀子认为语言的起源是创立社会规律、并借此表人类的各种心理活动。因此,对语言运用的常理的扰乱直接会影响人的心理活动,影响社会规范的正当性。 |
|
正名8-10 |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后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验之所为有名,而观其孰行,则能禁之矣。 「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验之所缘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则能禁之矣。 「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
|
回应墨家及名家,主要认为若语言系统是稳定的、不会随意改变定义的,就是「善名」(好的语言),而二实与化(一实)是语言的自然现象 (但不可不察)。而此处多处攻击墨家的命题、以及同时攻击公孙龙的「牛马」(〈通变〉)和「非马」(白马)。 |
由此可见,墨家反对名家是建基于学术讨论,而道家反对名家是建基于否定名家以词语系统有关的辩论可以达到「非指、非马」的境界、而儒家(荀子)反对名家则建基于儒家认为扰乱语言的常制、创立新的术语、打破旧有对字词定义的理解,都会导致民间的混乱。又,我们可以视之为不同学术科目之间的大战 (此为诸子百家争鸣的独有现象﹕不同的学术科目互相争夺显学地位),墨子代表科学、庄子代表灵性/ 养生学、儒家代表社会建制、则名家除却其颠覆者的形象 (此所以为「诡」),却也代表着古代心理学的成果。而随着汉代独尊儒术而墨、名两派皆失去传承,中国心理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
《公孙龙子‧坚白》最能表达公孙龙对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以下会尝试以现代语文翻译《公孙龙子》中的〈坚白〉〈白马〉和〈通变〉,带出《公孙龙子》反映的心理学意涵。本文的讨论会以《道藏》版无标点的《公孙龙子》一书为准,并不会以「衍文」或「错简」强行解说《公孙龙子》的内容。
一、坚白石二、坚白石三,与视觉残象及条件反射
「坚白」是墨家的《经‧经说》中的常见命题。墨家开出讨论战场如下
《经下》105条
不可偏去而二,说在见与俱、一与二、广与循。
见不见离,一二不相盈,广循坚白。
(好像长和阔,不能说两者单独存在。就算见到、不见到;两者都不妨碍对方,就像长/ 阔; 坚/ 白的例子。)
《经下》115条
不坚白,说在无久与宇。
(没有坚白的概念的话,就等于否定时间和空间这些概念)
《经下》116条
坚白,说在因。
无坚得白,必相盈也。
(坚白,两者是互动的,没有察觉到「坚」却察觉到「白」,最后还是会互相补充的。)
《经上》67条
坚白,不相外也。
于石无所往而不得,得二,坚。异处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
(坚硬和白色两者没有冲突。就算我们找不到石头,仍然知道它是硬的,就算它不在我们身边,这些特质也没有冲突。)
《经下》138
于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说在存。
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
(对于件事,有知觉到的、也有不知觉到的,但都有存在。在石头这一个概念中,有坚硬、白色两个子概念。有察觉到其一时忽略其余的,也是能的,但「坚硬」和「白色」是没有冲突的。)
这些都是希望说明,「石」是一个总体概念,而下面有「坚硬」和「白石」等等的特性,因此,「坚、白、 石」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以下为公孙龙子《坚白》的反击原文 (原文无标点)。他坚持「坚白石二」而不是「三」﹕
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谓无白得其所坚不可谓无坚而之石也之于然也非三也曰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曰天下无白不可以视石天下无坚不可以谓石坚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坚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不见离一一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坚见与不见二与三若广修而相盈也其非举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坚焉不定其所坚不定者兼恶乎其石也曰循石非彼无石非石无所取乎白石不相离者固乎然其无已曰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于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见焉有不见焉故知与不知相与离见与不见相与藏藏故孰谓之不离曰目不能坚手不能白不可谓无坚不可谓无白其异任也其无以代也坚白域于石恶乎离曰坚未与石为坚而物兼未与物为兼而坚必坚其不坚石物而坚天下未有若坚而坚藏白固不能自白恶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则不白物而白焉黄黑与之然石其无有恶取坚白石乎故离也离也者因是力与知果不若因是且犹白以 目见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坚以手而手以捶是捶与手知而不知而神与不知神乎是之谓离焉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
目见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坚以手而手以捶是捶与手知而不知而神与不知神乎是之谓离焉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
在阅读《坚白》前,必须注意「天下」是指「人的心理世界」的总和,这与名实篇的「天地」(宇宙) 全不相同。亦可以在此发现关于视觉残象 (afterimage)和条件反射 (reflex action) 的最早纪录1,2。
公孙龙子在这里证明了有意识 (神) 和下意识 (藏),两者构成的总和 (天下) 令人可以得到 「坚」(触觉)、「白」(视觉) 和 「石」(概念) 三者,而并非像后墨所言是因为「石」本身含有「坚性、白性、石性」三种元素才构成「石」,这就是「坚白石三」论,而公孙龙的「坚白石二」论则强调 「坚…白」是一类知觉,而「石」是概念,所以「坚白石二」。
问﹕坚白石三可以吗?
答﹕不可。
问﹕坚白石二可以吗?
答﹕可以。
问﹕为什么?
答﹕因为专注于石头的「白」时,只有「二」(白 + 石的概念),而专注于石头的「坚」时,也是二 (坚 + 石的概念)。
问﹕但既然有「白」,即「白」存在,不可说「没有白」。有「坚」,不可说「没有坚」,而石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那末不就是「三」吗。
答﹕视力不能够感受到「坚」,专注于视力就感受不到「坚」;触觉不能感受到「白」,专注于「坚」就感受不到「白」。
问﹕天下要有「白」才可以看到石,天下有「坚」才可以有「石」的称谓。那么,我们不如说,坚、白、石三种性质,不是外显的,而是内藏的三种条件。这样可以吗? 。
答﹕藏是藏了,但不是「存在于天地之间」,而是藏在自己的心理世界啊。
问﹕白和坚都需要靠石头这个外物才可以彰显,又如何说是藏在自己的心理世界呢?
答﹕因为得白、得坚两种感觉时,「见」与「不见」的知觉就进入「离」(dissociation)的状态,如果不是这样,两种知觉就不能交替发生,故有「离」的必要。
问﹕「石」与「白」;「石」与「坚」,「见」与「不见」,「二」与「三」,难道不可以视为若 长、阔 一样的互补概念,这又有何不可呢?
答﹕「物」是「白」的,还是不确定的相对感觉,「物」是「坚」,也不过是不确定的相感觉,两个加起来都尚且不确定,更何况「石」这一概念呢? (这又如何说可以找到「永恒固定」的「坚白石三」出来?)
问﹕找一块石头,没有这些特质就没有「石」,而没有「石」也就没有其上的「白」,所以石难道不是有其不相离的特性,又如何说没有呢。
答﹕「石」这一概念是「一」,「坚」「白」是其二阶内察,在「石」之下,故同时就有感觉到其一而不知其二 (有知焉有不知焉) ,亦在脑海有「见」与「不见」两部份。所以感觉 (sensation) 有分 知/ 不知,亦会有消退的时候 (相与离),而知觉 (见, perception) 就涉及下意识 (相与藏),既然有 “藏” (下意识),怎可说没有离 (dissociation) 呢?
问﹕目不能触摸坚硬物,手不能判别白色,不可谓无「坚」不可以说无「白」,只能说其功能各异,不能相互取代,而且既然「坚.. 白」都是在「石」这个概念之下的内容,这两特性又怎可以「离」呢?
答﹕「坚」本来不是因为知道「石」,只是因为其被某心理上的「物」所兼并。 (掌握到「坚」感后) 就算没有「坚」所附的「物」,也不必经过「石」,当「天下」不需要用到「坚」这一功能时,「坚」便是处于下意识中 (藏)。 「白」却是相对的视觉,不能「自白」只能是相对反映出来的知觉。所以「白」既然连先天的存库都没有,又岂能有自然的「白」令「石」变成白色?这种相对的知觉和「坚」(实物质感) 不同,没有所谓「白者必白」的事,所以不能不附在物上而生「白」的视觉,而黄色、黑色也同样道理的。在看事物、感觉事物时,根本不知道是「石」,又如何可以说「坚白石三」呢,在最初时白、坚都未引致「石」,此时「石」的概念是「离」的,此时就是 「因是」(所以而言) 的前认知状态。直到你用心力去将感觉得到一个结论 (力与知果),就没有这种「因是」状态了。 「白」与「坚」的不同可以用下列实证﹕目可以知觉到火,而火消失了,在意识上仍存在火,直到意识都见不到火了,知觉就消退了(离)。而坚是靠手去触摸,有时手会在被捶后反弹,居然意识上并没有知道 (不知) ,这是意识就处于「离」的状态,消退至「天下」(意识活动和下意识活动的总和)。 (所以,「白」和「坚」是不同类型的「知觉」[见, perception]与「感觉」[知, 感觉],当「离」进入「天下」就是知识的极限,所以只能独立地先预设为「正」。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公孙龙子》的坚白篇突破了《墨子‧经‧经说》的范畴论的框框,连结日常生活例子提出 (坚, 感觉) (白, 知觉) (石, 概念) 的三层次结论,并带出了 器官 (眼, 手) , 神 (意识) , 藏 (下意识) , 天下 (心理世界总和) 的现象学世界。由《坚白》篇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公孙龙子》的立论,对于「坚白」的讨论不是像墨家的,谈及事物特性的不同范畴,而是在心理语言的世界中,凡多重衍生的复合概念,已经是高阶的一种逻辑生成,而这样又会构成我们对世界的不同认知。而这一进路进一步反映在公孙龙的成名作﹕《白马》篇。
二、白马非马的「非」及心理世界与逻辑世界的分歧
很多人以局部-全体的方式讨论白马非马这一命题 (如冯友兰的「共相」)、也有学者以单数/ 众数去讨论中文没有众数变格所带来的误读 (如陈汉通….),并开始以语言学作为切入点。大部份都倾向将「非」定为「不等于」而不是「不是」,将之软化为「『白马』不等于『马』,因为… 」这样的句式,都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当成将「白马」和「马」视为「有共通但不全同」的概念。
然而,这样的观点是弱化了公孙龙的整个体系。事实上,公孙龙所强调的是,「白马」与「马」在心理世界上,的确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关键就在第一句﹕「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而整个论证最后都是想表明这一句的句式。
或者我们可以设想,若你在街上看见一个蓝色的人,你还会当他是「人」吗? (假定你知道他的皮肤颜色真的是蓝色)。而若果在咨询工作中,你听到案主不断强调,「我的父亲是蓝色的,他是蓝色人」,你会觉得这和一般谈论「父亲… 是生物学而言所定义的人类」一般思考吗?还是你会感到有点讶异,很想明白为何「父亲」是「蓝色」的「人」?你还会从逻辑/ 范畴论去思考这个「蓝人非人」的命题吗?
这就是公孙龙子「白马非马」的意涵﹕从心理学上来说,若果我们首先浮现的是「白」,则我们和一般情况下想到的「马」是不是同一回事,因为这个「白马」是特别的、想表达一些什么的、所以称为「有去」(这是特别的,不是普通的「马」可以表达);而不是「无去」的「马」(整体而言的「马」的普通概念)。这里或者可以想像,为何「白马王子」是要骑「白」马,而「白马」又代表了一种非一般的感觉… 。这已不是单纯讨论「局部-全体」,而是讨论为何「白马」的复合会带来心理世界的冲击。以下是《白马》的原文。
白马非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也不可谓无马者非马也有白马为有马白之非马何也曰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马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曰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可乎曰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曰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故曰白马非马未可曰以有白马为有马谓有白马为有黄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离白之谓也不离者有白马不可谓有马也故所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有白马为有马故其为有马也不可以谓马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
仔细阅读《白马》,论据铺排有致,全不似是真实情况的辩论,反而每一个后墨的问证都会引致名家答题更为有力的证据,由此可以猜测此篇是公孙龙子常用的自问自答书写方法。
问﹕白马非马,可以这样说吗?
答﹕可。
问﹕为什么?
答﹕马是命名「形状」的概念,而「白」是形容颜色的概念,「白」因此和「马」属不同层面的概念,其复合「白 … 马」自然和「马」不同。故此我们可以说﹕「白马」非「马」。
问﹕白马始终都是一只马,那么既然不可说白马不是一只马,又如何可以说非马,「白马」只是「马」的一个案例,如何可以说它是「非马」呢。
答﹕「马」这个概念没有限定颜色,黄黑马都可以应对,而「白马」是复合了命形和命色两个层面的概念 (即是super ordinate concept 及 sub ordinate concept两种不同的心理语言学概念)。如果「白马 = 马」,那末应该两者都可以交换,随便拿个黑马黄马都是白马了。不可以吧﹗为什么?不是因为表面颜色这么简单。所以黄、马等概念作为普通概念时,可以呼应马、却不可呼应白马,这就是白马非马的理由了。这就决定了啰﹗注意﹕本段很容易被人误以为白马是以 集合论 set theory, 亦即后墨的实存论作为证据,其实不然,仔细看公孙龙指出「白马」这个称谓因为是复合了 颜色-形状 的两个概念,在层次上有别于 「马」这个综合概念,故是 「不同的」(非)。
问﹕马本身都含有颜色的,天下也没有无色马,那末难道说天下就没有马吗?
答﹕马当然有颜色,所以才有白马的可能,若马无色,世上只有「马」,何需弄出「白马」这一名堂出来?但正因为这样,马不需要「白」,但「白」却需要附在「马」上,所以「白→ 马」和「马」才是两个层面的概念,所以「白马非马」。
问﹕这就不对了。 「马」本身就是「马」,而「白」的性质就是「白」,将两种特质合并,就叫「白马」,是一个复名,但这个复名既然两不相干,合并地叫后仍然保留两种特性,即「马」潜伏了「白」,就算「白」附在其上,都无影响「马」的特性,所以不可以说「白马非马」。
答﹕那末我就改一点点,叫「白马为马」,相反的命题,那末我可以将白马等同于黄马吗?
问﹕不可。
答﹕你既然说「白」加在「马」上不影响其特性,为何你在假设白马为马时,却又称白马不等于黄马,那末你的命题就是黄马非马了吗,黄马非马就可以,白马非马就不可以,就好像鸟飞入池潜水,棺要和椁放在两处安葬,这不是天下最大的胡说吗。
问﹕我所说的「有白马… 不可以说就是无马」是在不谈及「白」的情况下,比较两个「马」都有「马」性来说的。当然,你说到白马不和马是完全等同,就是站在故意将「白」抽离出「马」之外来说才可以成立的。所以有「马」,是因为马存有马的特质,而不是因为白或什么颜色才说它是马,所以我们才叫「马」,不叫「马马」。
答﹕白其实是相对概念,只能靠比较其他事物而来的,并没有什么「白」的特性,所以还是忘却了「白的特性」吧。白马,就是在语言中定义什么叫「白」,而这必要的条件是有「不是白」的马,才有「白马」。 「马」呢,就无这种叫「去取」的限定特性,所以什么色都可以配合。而「白马」是有限定的概念 (有去取),所以黄黑都被排除掉,唯白马可以独应。正是这两个概念「有去取」和「无去取」的性质不同,我才称之为「白马非马」。
「白马」和「马」的关系,是否纯綷是心理学所说的语意网络系统,(Semantic network, 特别是Lakoff, 1987)?如是,则这样的白马非马其实也是一种严格意义下的集合论,但即若如此,至少这个集合论的本质是心理语言学的,和后墨的实在论是完全不同的。后墨会认为就算白马黄马,只要有马的特质,都是马,因此白马是马,而既然白马是马,其相反的白马非马就必然是错的命题。而公孙龙明显是运用了不同的角度,先去证立「白马非马」,再去驳斥这种实在论。而从以下我们对〈指物〉和皮亚杰的异同之处,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论述更倾向是和皮亚杰所言的schema (基模) 更为接近。
三、《通变》中的概念生成与Jean Piaget 的基模 (schema)对比
《公孙龙子》〈通变〉一直未有令人满意的白话译本(见冯耀明, 2000),很多人以为〈通变〉所提的「牛羊足四,数足一,故五」以及「鸡足二,数足一,故三」仅仅是一种无聊的诡辩,而完全忽略〈通变〉篇的中心主旨﹕概念的生成和合并。本文以其与皮亚杰后期认知理论作出一个比较,从中我们可以互相比照这两个不同时空的认知理论的异同之处。
以下是《公孙龙子‧通变》的白话试译3
问﹕两个相异的东西,可以最后合并归一吗?
答﹕不可以。
问﹕两个东西相异,并且方在不同的位置,(价值的位置、方向的位置、时间的位置…),可以最后合并归一吗?
答﹕不可以。
问﹕「两个东西」可以全拨去其中一方作为结论吗?例如说,什么什么有好有坏,但整是好的。
答﹕不可以。
问﹕同样,两个东西有好有坏,但整体是坏的?
答﹕不可以。
问﹕只有好的一方,可以得出 “有两个元素” 的结论吗?
答﹕不可以。
问﹕只有坏的一方,可以得出 “有两个元素” 的结论吗?
答﹕也不可以。
问﹕将好坏并排,可以得出 “有两个元素” 的结论吗?
答﹕可以。
问﹕那末,我们发现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称为好的,这样可以视作「变」了吗?
答﹕可以。
问﹕这样,什么部份变了呢? 「好」的部份 (… 增加了)。这样,岂不是令人混乱,因为「好」增加了,也还是「好」,那末跟本没有质变,何以可以说是 「变」 呢?
答﹕其实,本来就无 “好” … “坏”,只有 “二”,但怎么 “二” 还是引致了 “好” “坏” 的想像,那就等于﹕牛羊合不等同于马,牛羊合也不同于鸡。
问﹕你在说什么?
答﹕羊与牛的唯一分别,假设是羊有牙齿而牛无牙齿吧,但羊和牛在一般人心中也还是 “家畜”,不可以说 “羊牛” 这个 集合 没有羊、没有牛。所以这两者的一个符号 (牙齿) 是不会俱在的,虽然两者被视为类同放在一处。而虽然羊有角牛有角,但俱有的特性只会令你归去一类,但不会说牛就等于羊。所以是同类但属于两种东西。加了一个新的元素,好像家畜﹕马,用另一种东西去判别开来,姑且就假设 “马有尾” “羊牛无尾” 吧。
无论怎样,牛, 羊怎样把其元素复合起来,都不是马。单单一只 “羊”, 不是 “二”,单一只 “牛”, 也不是 “二”, 两者并列就是 “二”,而且这两种东西都不是 “马”,这样是可以的。
这样一层一层的叠加排比起来,就会有不同类型的命题,就好像 牛/羊 如何复合 相对于 “马”,这就好比为何 “二” 会突然变了 “左…右” 加入了 位置。
牛羊有毛,而鸡有羽,虽然都有脚,但「脚」的称谓 (一) 之下只有两种数数的方法 (脚作为鸡的集体的脚,和作为左脚… 右脚 等定的脚),总共就只有三层。而 「牛… 羊」两者结合的集,在「脚」这一称谓之下有四种数数方法 (牛羊脚整体,牛/ 羊 其中一种的脚,牛/羊 整体的连结位置的脚 [牛羊 的左脚… 右脚…前脚….后脚….],牛羊个别品种的 特定的脚),连起称谓就有五层。所以同样是脚,鸡是就只有三层,而将牛, 羊结集后,就至少有五层。所以,虽然牛羊和鸡都有脚,但牛羊这个复合排除了 “鸡”,并不是因为 牛, 羊含有 “非鸡” 的元素这么简单,最终来说是 “鸡” 与 “牛羊” 处于不同的概念位置。
但其实就算是 “牛羊…马”,这些表面上较相似的东西,也是和 “牛羊…鸡” 一样荒谬的,只是我们惯了 “牛羊…马” 比起 “牛羊…鸡” 较好,因为较多的材料去将他们类比作为同类,但其实这句命题仔细看都是起源于 随意起名将某样东西结合,这可算是 “狂妄” 地题出命题吧。
问﹕说第二个论证吧…
我们暂时在这里止住,再从另一层中的对照去探讨公孙龙子的〈通变〉。
在两千二百年后,皮亚杰没有用牛羊马鸡去表达他的理论,但在他死后才发表的Reason 一文 (Piaget, 2006),里面以一些简单的公式整理了他关于概念生成过程的思考。他提出有两种概念合并﹕一种是自由并合的Free Conjunction AB (即p.q) (《公孙龙子》中的「鸡」)。而当后者是 obligated conjunction AB→A (即p.q >p) (即《公孙龙子》中的「牛羊」)
皮亚杰在第二部份,以一个小朋友办认人名的姓/ 氏时,A.B – B 为错;A.B→A 为对 (B为母集,A为子集) 然则,B= A+A’ ; A’=B-A;而在另一情况下,┐A’ = B-A; 则 两者同时出现,便成为不可能概念,难以进行任何纵深运算思考。 (《公孙龙子》中的「两明」)
《公孙龙子》中的两明是一种「道丧」,即知识无可能在此建立。而皮亚杰中,知识仍然可以得以建立,因为平衡过程 (equilibration)令其仿作 p→ (p vq)能够得以借指涉的、旁支的Op → O(p v q) 而建立出来。这是一种比喻多于实际的逻辑。所以,皮亚杰最晚期的思考已订明单单逻辑并不能解释图式 (Schema)的变化,必须考虑到类近图式借指令 (obligation)和结构同型的比喻方式而得以结合。
我们在这里可以接续《公孙龙子》的〈通变〉。在这里,皮亚杰的p→ (p vq)及 Op → O(p v q) 就是「黄」,是人类知识的起源;而种提炼就有别于单纯阵列的B= A+A’ ; A’=B-A;及┐A’ = B-A;并列的状态 (碧)﹕
以下我们接续〈通变〉4
说第二个论证吧…
好吧。以上论据用另一种说法,就好像拿起一块玉。将青色加诸白色,并不等于黄色。将白色加诸青色,并不变成碧绿色。
为什么?
本来玉之中的青色、白色,各走一锋但又可以视为可有关系的东西,是一对可以视为「相反」的东西。本不相邻,但于置在旁边,两者都不会混和,不会混和的话,就是一种「相反、相对」的情况。各得其所,就好似同一件事在二元排列时不会同时是左、右。这两者同时存在,就不能说「整体而言… 是青色的」或者「整体而言… 是白色的」。
这就奇怪了,为何我们会有调色学上的概念﹕青色加进白色中,就有黄色呢?黄色是「正举」,是我们觉得合符常识的事物,于是就成为好像 国→ 君→ 臣 的阶段式概念网,所以在常识中我们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由于我们已设定了青色比起白色是更为深色,所以这种认知是可以长久的存在于我们的常识。
青和白平行时,青和白两个表面上是相反的东西相对,却由于我们已设立了青-白的深浅体系,所以就只能说 「白」被青的元素加入后不再是白色,而不能说青渗入了白的元素后不再是青色,所以就算白再多,都不能抹去「青」,就好像木头不能胜过金属一样。这种木头对抗金属的情况就是「碧绿色」,就不是「正举」的合理推论了。
但若果我们没有建立起 「青 > 白」的常识体系,则就算将青放到白,或白放到青,都是没有办法说「何者抹去了另一方」,就出现了「两明」的局面﹕这么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这样,当然也可以说 白色 抹走了 青色,令到碧绿色出现啰。
与其这样,一般人都宁愿说青色放进白色就破坏了白色,衍生出黄色。这就好像上文「马」的例子。其实不论 「牛羊/马」也好,「青白/ 黄」也好,这种排比的先决条件是我们把它们事先编作一类。而白加在青中产生出碧绿色,就好像上文的「鸡」的概念,感觉上好像粗暴乱来。这样粗暴乱来代表没有「主… 次」的分位,两者互相可以逆向隶属,此谓两明。两明就箇中关系模糊,没有办法可以得到「正举」的合理推论。
没有「正举」就会令名-实的世界变得杂乱无当,各种颜色只能被感知为互相拼凑,所以就是「两明」。两明就没有一个知识体系可以得以建立,因为没有所谓的「正确」。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公孙龙子》中的「黄」是藉由平衡作用而来的新的基模 (schema),其运作与单纯的同化 (assimilation) 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此篇为何取名〈通变〉﹕这是指出我们常常遭遇到不同概念,有些较接近、有些则较疏远甚至互相排斥,但学习不单是创出新的「集合」(set),而是将之提拔到一种新的理解,就像「青」「白」变成「黄」一样。
四、〈指物〉中的语言柘朴学
从〈白马〉〈通变〉两篇,我们可以进而探讨《公孙龙子》最为深奥的〈指物〉一篇。撇开其哲学意识不谈,〈指物〉,可视为哲学文本的艺术精品,全篇用「指, 非指,非,物,天下,谓」等字重复多次就达到了一个哲学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度。 《指物》谈及的是柘朴函数理论。可以想像,这篇可能是对道家,特别是《庄子‧齐物论》的「是亦一旡穷,非亦一旡穷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的反驳。
全篇由于没有标点,句读需要极小心处理。这篇文字若以柘朴学中的Kuratowski Closure Axiom 及Morphism for all closure-preserving functions 的句式比较,可能得出不同的阅读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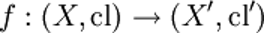
在此,A作为 X 的子集 (subset)

Cl 为 「天下」,X 为 「物」,→ 为「指」 (动词);(cl(A)) 为「指」 (名词);(f(A))为「非指」。 为「谓」。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谓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不为指而谓之指是兼不为指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
指非非指也指与物非指也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天下无物谁径谓指天下有指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径谓无物非指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
「物」都是「指 (名词)」并且指向「非指」 因为 (cl(A)) 和(f(A))的前题就是「物」(Das Ding)在心理世界的总和「天下」之中。
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 「天下」是空集的话,则抽不出 (cl(A)) 及cl’(f(A))。最初天下无指,物是无可以「谓」,因为未确立A作为X的子集,所以最初「天下无指」。
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谓指乎 「非指」是「天下」中的「物」的关系 f: (X, cl)→ (X’, cl’)的子集前题,由此才有 f(cl(A))cl’(f(A))。
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指是「物」的符号化代表,是「天下」中原本没有的东西,而在最初「天下」并无指,只有「物」,而「物」可以「谓」是一间接过程,所以两者并未可视为等同。
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天下」无「指」,而「物」此时尚未可以谓为「指」,而这个阶段「非指」可以代表一种前「被谓」的状态,「非指」必须要大前题﹕A作为 X 的子集 (subset)即「物莫非指也」才能得以确立出来。
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无指为何「物」不能被「谓」,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大前题「非有非指也」(没有「非指」),为何会没有「非指」,因为此时只有「物」和「指」,需要随后的「指(动词) 非指」过程才会产生 「非指」。
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不为指而谓之指是兼不为指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未可「天下」无指,但(指)生于「物」并因这「物」附着各种元素特质 (各有) 而来。单单是符号 (名) 不是「指」。纯綷符号却说之是「指」,是「双重空集」(兼不为指)。以有限的「指」去表达这种「无不为指」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元语言」。 (参照维根斯坦的《哲学研究》)。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与物非指也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天下无物谁径谓指天下有指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径谓无物非指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 指虽不在「天下」之中,但却是「天下」的衍生物 (「所兼」注﹕不同「所有」),「天下」若「无指」,「物」就不可以用「指」去形容为「无指」,为何不可以谓「无指」,因为没有了「非指」,没有「非指」的原因是 「物莫非指」,但「指」不等于「非指」,若果「无指」,则而「指」「物」都变了不能被指的「非指」。 → 但「天下」若没有了「物」又无「指」,又如何将「非指」说出来?天下无「物」又如何谈上「指」?天下若有「指无物指」(即纯綷符号,「名」,「兼不为指」的metalanguage) 则为什么又有「非指」出来,又如何说「无物非指」。而且若果「指」本身就可以指涉「非指」,则又为什么必需要「物」才能产生「指」呢?
在没有标点的情况下,句读在这篇綷理论的文章变得极度难以解读。但无论是否能够完全理解此篇,有几方面还是可以肯定的﹕1) 这篇《指物》是回应道家,以「道、德」或「气、自然」等概念尝试去达到「境界」,并且指说言是一种遮蔽,不如以无语言的方法去思考没有语言的「非指」境界,如此就能进入世界的终极境界 (从马之中悟「道」,从「指」之中悟「天下」)。这种带有反语言观点的道家系统与名家固然是相反的。名家首先视「天下」为心理活动总和。而「物」原本在「天下」中是影象的存有 (物之各有…) ,然后才以高阶的关系由天下→物→ 指的形式,以指作为物的柘朴函数。所以「物」与「指」之间有一「指向」的动作,而且残余 (residue)的、没有被注意到的就变成了「非指」,而世界并没有指向无物的「指无物指」,或者元语言 (metalanguage) ,因为无论怎样,当有指涉之时,已经可以视为「指」并必定和心理总和 (天下) 的「物」(das Ding) 产生指向 (指, 动词) 并且出现残留「非指」。最后的结论,就是证立上文的拓朴函数关系,而〈白马〉及〈通变〉就是〈指物〉的具体论证。最后,公孙龙将目光放到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五、名实与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将语言分为「能指」(signifier) 和「所指」(signified) (Saussure, 1983)。而在《名实》中,语言 (名) 与现实 (实) 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联系,而是有彼/ 此两面,这和索绪尔的能指/ 所指链环是相符合的。
名实是关于证立「彼…此」的通则的一篇古语言学文本。 《名孙龙子》中表面上最易被人解读的一篇,但因为一些词如「明王… 审其所谓」等常被误以为是政治思想有关君王「名实相乎」的文本 (如徐复观,1966)。同时受当时刻写在竹柬上的约束,「彼…此」的上下图式变为了连写的句子,令后世阅读变得极为困难。以下为原文及解说﹕
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其以当不当也不当而当乱也故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其以当而当也以当而当正也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至矣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甚其所谓至矣哉古之明王
天地 (世界) 产生「物」。物在时间中固定了,其内容便是「实」,「实」在空间中被固定了,便是被赋与「位」,偏离了「位」便是「不正」,处于适当位置便是「正」。必须有一个是「正」的,才能对照其余是否「不正」,从而使质疑某「实」是否「不正」成为可能。 「正」的主要目的是确立「实」的时空位置,而要正「实」必先正「名」。 「名」正代表了「彼, 此」相配 (能指、所指)。若某能指 (彼) 的应用相方不配合 (不唯),则这个称呼「不行」,不能被用于「正」的过程,而某所指 (此) 原来有亦两不配合(不唯),则亦不可用于「正」(不行)。必须有守则决定当与不当,不然不守守则 (不当) 都算做「当」就会出现乱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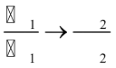 若 彼1 演变为 彼2 ,可以称为「行彼」;
若 彼1 演变为 彼2 ,可以称为「行彼」;
而同时 此1 演变为 此2 ,可以称为「行此」
两「行」相配 (当), 整个推论也就 「当」,就是「正」
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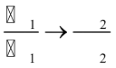 (彼彼此于彼;此此止于此),可。
(彼彼此于彼;此此止于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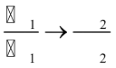 (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
(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
所谓的「名」,是「实」被说出来。所以在以下两个情况「不谓」(不说出来)
1) 此 = ~ 此 (非此)
2) 此= 此 (此的抹消,不在此)
相比起所指的两个情况,能指的「不谓」也建基于相似的原则﹕
1) 彼 = ~彼
2) 彼 = 彼
传说中的「明王」(智慧之王) 能够详审名实的关系,认真对待其说话。真伟大哉。
由此我们可以见到,公孙龙的学说实在和皮亚杰的认识论遥相呼应,而且此书有着一致的内部结构,为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心理学论述。
《公孙龙子》中的「白马非马」、「二无一」、「坚白石二」「指非指」及「彼此」的重新演绎对本土心理学有以下重要性﹕首先,这些历史素材是创建本土心理学的重要基础,对本土的重要思想史的档案缺乏整理,就难以建立丰富的本土心理学体系。另外,《公孙龙子》探讨的是人类的认识论的问题﹕到底人类的感觉、知觉和最后的认知的结构为何? (〈坚白〉),当我们说话时,听众是否单凭逻辑思考就能完全理解? (〈白马〉) 学习如何整由「牛、马」的相近概念慢慢至导出复合的概念?在面对被排除的成分时,又如何处理? (〈通变〉)、符号与心理物件 (〈指物〉)、语言与现实关系为何? (〈名实〉) 这些都是日后本土心理学课本中应该列入的心理学史教材。最难得的是,《公孙龙子》以精简的方法,带出日后心理学家就认识论和语言哲学所开拓的新课题。
主要参考文献
1、且犹白以目见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对「白」的视觉,可以用以下例子说明﹕眼睛见到了火,火移开了,则眼睛已见不到火,但意识 [神] 仍见到火,到 “意识” 都见不到火了,我们就说 “见” 这知觉已离开了 [见 … 离]。
2、坚以手而手以捶是捶与手知而不知而神与不知神乎是之谓离焉﹕对「坚」的感觉可以用以下例子说明﹕用捶敲手臂,手会有反应,而意识却不知道,这时的意识可以称为「离」。
3、《公孙龙子‧通变》原文上半部份。原文无标点。曰二有一乎曰二无一曰二有右乎曰二无右曰二有左乎曰二无左曰右可谓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谓二乎曰不可曰左与右可谓二乎曰可曰谓变非不变可乎曰可曰右有与可谓变乎曰可曰变只曰右曰右苟变安可谓右苟不变安可谓变曰二苟无左又无右二者左与右奈何羊合牛非马牛合羊非鸡曰何哉曰羊与牛唯异羊有齿牛无齿而羊牛之非羊也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类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类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马无角马有尾羊牛无尾故曰羊合牛非马也非马者无马也无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马可也若举而以是犹类之不同若左右犹是举牛羊有毛鸡有羽谓鸡足一数足二二而一故三谓牛羊足一数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鸡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鸡非有以非鸡也与马以鸡宁马材不材其无以类审矣举是乱名是谓狂举…
4、曰他辩曰青以白非黄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与而相与反对也不相邻而相邻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对各当其所若左右不骊故一于青不可一于白不可恶乎其有黄矣哉黄其正矣是正举也其有君臣之于国焉故强寿矣而且青骊乎白而白不胜也白足之胜矣而不胜是木贼金也木贼金者碧碧则非正举矣青白不相与而相与不相胜则两明也争而明其色碧也与其碧宁黄黄其马也其与类乎碧其鸡也其与暴乎暴则君臣争而两明也两明者昏不明非正举也非正举者名实无当骊色章焉故曰两明也两明而道丧其无有以正焉
5、商务印书馆 (1923)。 公孙龙子 (道藏版)上海﹕商务印书馆。
6、陈大齐 (1951)。异白马于所谓马与白马非马。 大陆杂志,2(2),6
7、谭戒甫 (1963)。 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北京﹕中华书局。
8、徐复观 (1966)。 公孙龙子讲疏。台北﹕学生书局。
9、郑良树 (2000)。论《迹府》的成书年代」。 文献季刊,2, 4-11。
10、冯耀明(2000)。 公孙龙子。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1、宗静航 (2005)。从语言学角度探讨《尹文子》真伪问题。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45, 321-330。
12、萧裕民 (2006)。 《庄子》「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析释。 文与哲,9, 89-108。
13、庄子。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版本
14、韩非子。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版本
15、荀子。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版本
16、墨子。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版本
17、Lakoff, G., (1987).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Piaget, J. (2006). On Reason.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24, 1-29
19、Saussure, F. (1983).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R. Harris. trans).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16).
20、Solomon, B.S. (2013). On the school of Names in Ancient China. Sankt Augustin (Germany):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 原创文章/视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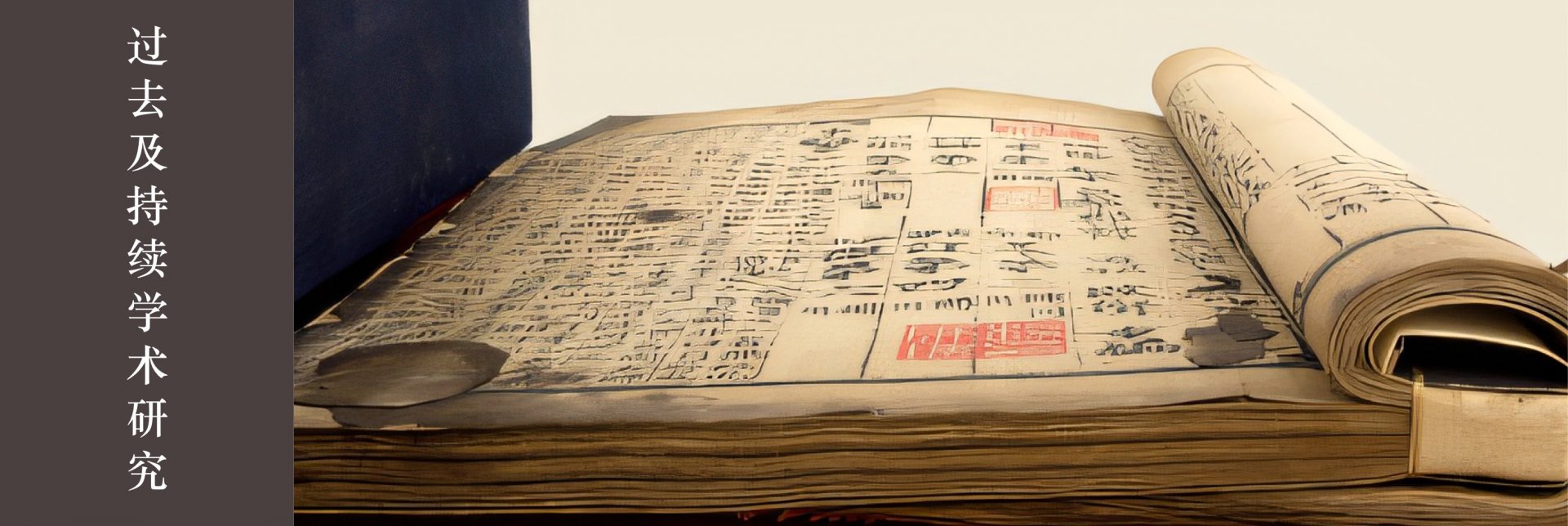



欢迎留言:
请登入/登记成为会员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