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公孫龍子》對本土心理學的啟示
名家常被視為詭辯學說,但名家的方法論及其研究主旨常常被忽略。有別於邏輯實徵主義的假設-演繹法 (hypothetical deductive method),名家的方法是先設立與常識有異的命題,然後從各種實證或推演中嘗試找出可以證立這個和常識有異的命題的論證,從而擴闊人們對事物的領悟,在精神上這與現象學或解構方法有著相似之處。本報告從名家重要典籍《公孫龍子》中,發掘其關於心理語言學、概念生成過程、以及有關語言與現實的關係的討論。 (本研究為香港研資局資助項目,編號UGC/FDS15/H07/14))
關鍵字:名家 《公孫龍子》 心理語言學
名家的源頭常追溯自惠施的「歷物二十一事」(見《莊子‧天下》),在《莊子》一書的描述中惠施會召開國際的學術會議,並以一些表面上有違常識的命題,吸引不同的學者去思考這些表面上荒謬的情況下,到底可以追尋出甚麼樣的道理出來,在《莊子》一書中,這些人統稱「辯者」。這樣的「辯者」和日後《鬼谷子》一書中呈現的那種政治說客的「辯者」本質上是有分別的 (雖然名家的「辯者」也可以這樣的政治「辯者」作為職業,例如從《公孫龍子‧跡府》篇中,名家的主要人物公孫龍本身就是趙國平原君的幕僚及文膽,而惠施本人也是魏國的高級外交官員)(鄭良樹, 2000),於是在中國學術史上學術式的辯者稱為「名家」,而政治上的說客稱為「縱橫家」,兩者各有不同的興趣、術語、及不同的研究目標。名家在中國學術史上一直被貶為「詭辯」,總是被視為是專注於扭曲常識、純綷滿足於口舌之爭的一派人物,而在不同的流派中,他們也是被打造成這樣的負面形象,例如《韓非子‧外儲》就描述當時一名叫兒說的宋國辯士喜愛拿「白馬非馬」的口號去逃避不交入城費,而被守軍所不屑的事件。由此可見,名家的辯士都是無聊之輩,在「辯」之前總要加上「詭」這個字。
但若果「辯」只是口舌之爭,那麼,我們是否可以理解人類思想史中,大凡不是直接就涉及「實用」的東西,只要是「後設、難以直觀理解」的,就是「詭」呢?這個「詭」字所代表的,是中國思想史以來的一個盲點﹕體系化的後設探討,不論是何種形式,總是被「詭」字輕輕抹去;而其後續的生命力也遭到厄殺了。
當魏晉時代的大戰亂令學者可以重新檢討傳統價值觀的時後,大家才重新發現公孫龍子;但這些古注也失傳了,在《四庫全書》中《公孫龍子注》的序言中提及《公孫龍子》被陳振孫以淺陋迂僻譏之在明鍾惺本被更名為《辯言妄誕不經》, 似乎已是被視為「奇文共賞」而吊詭地反而因此得以留存,但也只有十四篇中存六篇 (而且〈跡府〉是後人所加的人物傳記,則實際的學術篇章只有五篇),此可說是中華文化史上的一大缺口。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民國時代的第一名心理學家─ 陳大齊先生在〈異白馬於所謂馬與白馬非馬〉(1951) 開始注意到《公孫龍子》的價值,但基本上停留在認為公孫龍是和墨家一樣談及範疇論的 (即討論全體和局部的關係),而後來的本土心理學界對《公孫龍子》的討論也並未熱烈,亦未與後期墨家、荀子等就主要命題作出比較,因而難以獲得較為整體的討論。本篇的重點在重整《公孫龍子》在中國心理學史上的角色,從而略窺中國古心理學史的面貌,從其中希望理解到在「詭辯」的不公允評價下,以公孫龍為首的哲學的意旨為何。
本土心理學界通常較少引用《墨子》及《公孫龍子》兩部書的內容,更遑論直接將之引入實際的應用之上,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因為這宣佈了對於名家的研究永遠停留在訓詁層面,尤其是當《公孫龍子》呈現的是一種對心理語言學的嚴肅探討時,對《公孫龍子》一書的關注可以填補本土心理學界對古代中國心理語言學的空白,其意義並不宥於純綷心理學史的討論,更多值得參考的是公孫龍如何在一個近乎空白的時空中創造出一套嚴密的思想體系,而這個體系又與西方的現象學遙相呼應。若果深澀的現象學在西學也可以導引出現象學的心理學現究及存在主義療法等等的應用,那麼重新考掘名家,特別是《公孫龍子》一書,或許有助於本土心理學界能夠承傳、發展及再造出新形式的心理學。
Solomon (2013) 正確地指出名家至少可以分為兩類﹕惠施的是「合同異」派;而公孫龍是「離堅白」派,而早期的以詮釋法律條文的模糊地帶而著稱的鄧析子又可說是早期的「辯者」(譚戒甫,1963)。這三種形態雖然表面上都違反常識、並且愛好辯論,但卻有迥然不同的志趣﹕從現時看來,鄧析子可以算是現代律師職業的鼻祖,專攻尋找法律的空隙以達致目標;而惠施探討的是時間、空間表面上不可能性之中的新理解,很有可能是一種數學或物理探討。例如《莊子‧天下》提到的「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就是探討無限大與無限小的命題。可惜的是,惠施的著作全部都失傳了。而公孫龍子的「離堅白」派卻是探討語言生成以及人類認知結構的流派,後世談論公孫龍子多認為他只有討論語言哲學 (例如〈白馬〉篇提及「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也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很多時都被視為是純語言學的探討),但卻忽略其與〈堅白〉篇中提及心理認知過程論的箇中聯繫。
《公孫龍子》一書為現存代表名家思想的主要文本,而爭議性相對其他殘留文本 (如《尹文子》)為低 (有關《尹文子》的爭議,見宗靜航, 2005)。現時《公孫龍子》六篇中,除《跡府》為公孫龍事跡之雜錄,餘五篇可視為統一的體系,亦有其他諸子可以相互參照的辯論。其中《公孫龍子》中的〈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都可直接與墨子《經》(及《經說》)、《小取》、《大取》篇有大量比照 (凡21條條目),後墨的做法是直接與公孫龍討論辯題的內容和論證而後說其非,其主要進路是以全體-局部、以及概念生成的內涵來做討論;並且認為事物的本質是自然存在於事物之中 (如堅、白、石)。在《墨子》的《經》和《經說》(兩書需合併閱讀,經是條目,經說是內容)中,〈白馬〉〈通變〉 的內容多談及範疇和語意的變化;而〈堅白〉則談及各種感官之間的關係,是認知心理學的辯論。〈指物〉和〈名實〉則談論符號與物、語言和現實之間的關係。其中最多直接交鋒的是〈白馬〉〈通變〉和〈堅白〉。可以說,墨家和公孫龍的名家是這場古代心理學論戰的直接參與者﹕
表一﹕《墨子》《經》《經說》《小取》《大取》中的相關條目
|
篇及句 |
內容 |
對應於《公孫龍子》篇章 |
|
小取4
|
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
|
白馬 |
|
小取7
|
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
|
白馬 |
|
小取8
|
之馬之目盼則為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眾,而不謂之牛眾。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
白馬 通變 |
|
大取11
|
語經,語經也。非白馬焉
|
白馬 |
|
大取13
|
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
|
白馬 |
|
經上51
|
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矢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
|
白馬 |
|
經上67
|
堅白,不相外也。 於石無所往而不得,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 |
堅白 |
|
經上79
|
名:物,達也。有實必待之名1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若姓字灑
|
名實 |
|
經下103
|
馬麋同名俱鬥、不俱二,二與鬥也。包肝肺,子愛也。橘、茅,食與抬也。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白與視也。為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為非以人,是不為非。若為夫勇,不為夫。為屨以買衣為屨,夫與屨也。 |
白馬 通變 |
|
經下105
|
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修堅白
|
堅白 |
|
經下113
|
俱:俱一,若牛馬四足;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若數指,指五而五一 |
通變 |
|
經下115
|
不堅白,說在無久與宇
|
堅白 |
|
經下116
|
堅白,說在因
|
堅白 |
|
經下138
|
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 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 |
堅白 |
|
經下139
|
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絫。 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為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 |
通變 |
|
經下140
|
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 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
|
指物 |
|
經下167
|
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之與馬不類,用牛角、馬無角,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為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
|
通變 |
|
經下168
|
「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
|
通變 |
|
經下169
|
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 彼: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
|
名實 |
由上表所見,墨家對〈名實〉及〈指物〉的討論相對較少;或者我們可以視〈名實〉〈指物〉為公孫龍對於墨家思想的一個概括性攻擊;而〈白馬〉〈通變〉及〈堅白〉三篇則直接紀錄了名墨兩家的辯論內容。由《公孫龍子》中紀錄墨家的質詢看來,這些質詢和《經》《經說》《大取》《小取》都非常一致,可以推測《公孫龍子》一書的內容在《經》《經說》等之後,是名家對於墨家的回應 (相反的,墨經中較少提及公孫龍子的回應)。
而道家對於名家的攻擊可以概括在以下一句說話之中。《莊子‧齊物論》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莊子並非全盤否定名家,甚至認同「非指」和「非馬」(見蕭裕民, 2006)。莊子的切入點和墨家完全不同,莊子代表的道家雖然在根本上反對辯論,但其立足點是語言並沒有可能導往完全的真理,必需要以語言之外的會意去體察萬物 (所以符號不能帶出符號以外的意旨)、而莊子對於公孫龍的心理主義 (即﹕「馬」在本質上和「白馬」是心理世界兩個不同功能、不同概念、不同意涵的「物」) 認為可以推而廣之,令人體察到在各種事物之間的「存在」,所以若果到達這種境界,則「非馬」與「馬」都可以消解,從「馬」中就可以體驗存在 (天下一馬也)。可以說,若果墨家/ 名家的爭論點是在學術理論內容而非方法論;則莊子所非難名家之處主要不是其內容,而是名家的方法。當然,公孫龍是否如莊子所理解的一般,「非馬」與「非指」是否只是想表達世界及人類知識的虛妄、而又進而可以得出「一指」「一馬」的存在,又當別論;若從《公孫龍子》一書的編排詳細考察,則公孫龍探討的是「變」而非「一」,這裏可以視莊子為借題發揮。
而儒家的荀子亦直接參與名家的辯論,這裏名家的「名」是解作語言,荀子的《正名》詳談語言、名實,認為是管治者發明一套語言,人類可以藉此說明萬物。因此,他認為要設立有關語言使用的具體規章,使語言不要開始分歧。而同樣的字可以應用於兩個或以上的意涵 (二實)、或者倒過來多個詞語指向一個意涵 (化、一實)。荀子反對墨家以辯論能夠帶來新發現的說法、亦直接批評「有牛馬、非馬也」等公孫龍的命題,都是「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是以,必須定立詳細定義 (驗之名約),並且以概括的方式作出總結性評價 (以其所受,悖其所辭),更要對這種活動加以貶抑 (則能禁之矣)。
表二﹕荀子《正名》與《公孫龍子》的相關討論範圍
|
正名1-4
|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
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愨;愨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跡長矣。跡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
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
|
荀子認為語言的起源是創立社會規律、並藉此表人類的各種心理活動。因此,對語言運用的常理的擾亂直接會影響人的心理活動,影響社會規範的正當性。 |
|
正名8-10 |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
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為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緣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
|
回應墨家及名家,主要認為若語言系統是穩定的、不會隨意改變定義的,就是「善名」(好的語言),而二實與化(一實)是語言的自然現象 (但不可不察)。而此處多處攻擊墨家的命題、以及同時攻擊公孫龍的「牛馬」(〈通變〉)和「非馬」(白馬)。 |
由此可見,墨家反對名家是建基於學術討論,而道家反對名家是建基於否定名家以詞語系統有關的辯論可以達到「非指、非馬」的境界、而儒家(荀子)反對名家則建基於儒家認為擾亂語言的常制、創立新的術語、打破舊有對字詞定義的理解,都會導致民間的混亂。又,我們可以視之為不同學術科目之間的大戰 (此為諸子百家爭鳴的獨有現象﹕不同的學術科目互相爭奪顯學地位),墨子代表科學、莊子代表靈性/ 養生學、儒家代表社會建制、則名家除卻其顛覆者的形象 (此所以為「詭」),卻也代表著古代心理學的成果。而隨著漢代獨尊儒術而墨、名兩派皆失去傳承,中國心理學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也就結束了。
《公孫龍子‧堅白》最能表達公孫龍對認知心理學的理論。以下會嘗試以現代語文翻譯《公孫龍子》中的〈堅白〉〈白馬〉和〈通變〉,帶出《公孫龍子》反映的心理學意涵。本文的討論會以《道藏》版無標點的《公孫龍子》一書為準,並不會以「衍文」或「錯簡」強行解說《公孫龍子》的內容。
一、堅白石二、堅白石三,與視覺殘象及條件反射
「堅白」是墨家的《經‧經說》中的常見命題。墨家開出討論戰場如下
《經下》105條
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循。
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循堅白。
(好像長和闊,不能說兩者單獨存在。就算見到、不見到;兩者都不妨礙對方,就像長/ 闊; 堅/ 白的例子。)
《經下》115條
不堅白,說在無久與宇。
(沒有堅白的概念的話,就等於否定時間和空間這些概念)
《經下》116條
堅白,說在因。
無堅得白,必相盈也。
(堅白,兩者是互動的,沒有察覺到「堅」卻察覺到「白」,最後還是會互相補充的。)
《經上》67條
堅白,不相外也。
於石無所往而不得,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
(堅硬和白色兩者沒有衝突。就算我們找不到石頭,仍然知道它是硬的,就算它不在我們身邊,這些特質也沒有衝突。)
《經下》138
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
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
(對於件事,有知覺到的、也有不知覺到的,但都有存在。在石頭這一個概念中,有堅硬、白色兩個子概念。有察覺到其一時忽略其餘的,也是能的,但「堅硬」和「白色」是沒有衝突的。)
這些都是希望說明,「石」是一個總體概念,而下面有「堅硬」和「白石」等等的特性,因此,「堅、白、 石」是三個不同的概念。
以下為公孫龍子《堅白》的反擊原文 (原文無標點)。他堅持「堅白石二」而不是「三」﹕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其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于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于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物為兼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 目見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目見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在閱讀《堅白》前,必須注意「天下」是指「人的心理世界」的總和,這與名實篇的「天地」(宇宙) 全不相同。亦可以在此發現關於視覺殘象 (afterimage)和條件反射 (reflex action) 的最早紀錄1,2。
公孫龍子在這裏證明了有意識 (神) 和下意識 (藏),兩者構成的總和 (天下) 令人可以得到 「堅」(觸覺)、「白」(視覺) 和 「石」(概念) 三者,而並非像後墨所言是因為「石」本身含有「堅性、白性、石性」三種元素才構成「石」,這就是「堅白石三」論,而公孫龍的「堅白石二」論則強調 「堅…白」是一類知覺,而「石」是概念,所以「堅白石二」。
問﹕堅白石三可以嗎?
答﹕不可。
問﹕堅白石二可以嗎?
答﹕可以。
問﹕為甚麼?
答﹕因為專注於石頭的「白」時,只有「二」(白 + 石的概念),而專注於石頭的「堅」時,也是二 (堅 + 石的概念)。
問﹕但既然有「白」,即「白」存在,不可說「沒有白」。有「堅」,不可說「沒有堅」,而石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那末不就是「三」嗎。
答﹕視力不能夠感受到「堅」,專注於視力就感受不到「堅」;觸覺不能感受到「白」,專注於「堅」就感受不到「白」。
問﹕天下要有「白」才可以看到石,天下有「堅」才可以有「石」的稱謂。那麼,我們不如說,堅、白、石三種性質,不是外顯的,而是內藏的三種條件。這樣可以嗎?。
答﹕藏是藏了,但不是「存在於天地之間」,而是藏在自己的心理世界啊。
問﹕白和堅都需要靠石頭這個外物才可以彰顯,又如何說是藏在自己的心理世界呢?
答﹕因為得白、得堅兩種感覺時,「見」與「不見」的知覺就進入「離」(dissociation)的狀態,如果不是這樣,兩種知覺就不能交替發生,故有「離」的必要。
問﹕「石」與「白」;「石」與「堅」,「見」與「不見」,「二」與「三」,難道不可以視為若 長、闊 一樣的互補概念,這又有何不可呢?
答﹕「物」是「白」的,還是不確定的相對感覺,「物」是「堅」,也不過是不確定的相感覺,兩個加起來都尚且不確定,更何況「石」這一概念呢?(這又如何說可以找到「永恒固定」的「堅白石三」出來?)
問﹕找一塊石頭,沒有這些特質就沒有「石」,而沒有「石」也就沒有其上的「白」,所以石難道不是有其不相離的特性,又如何說沒有呢。
答﹕「石」這一概念是「一」,「堅」「白」是其二階內察,在「石」之下,故同時就有感覺到其一而不知其二 (有知焉有不知焉) ,亦在腦海有「見」與「不見」兩部份。所以感覺 (sensation) 有分 知/ 不知,亦會有消退的時候 (相與離),而知覺 (見, perception) 就涉及下意識 (相與藏),既然有 “藏” (下意識),怎可說沒有離 (dissociation) 呢?
問﹕目不能觸摸堅硬物,手不能判別白色,不可謂無「堅」不可以說無「白」,只能說其功能各異,不能相互取代,而且既然「堅.. 白」都是在「石」這個概念之下的內容,這兩特性又怎可以「離」呢?
答﹕「堅」本來不是因為知道「石」,只是因為其被某心理上的「物」所兼併。(掌握到「堅」感後) 就算沒有「堅」所附的「物」,也不必經過「石」,當「天下」不需要用到「堅」這一功能時,「堅」便是處於下意識中 (藏)。「白」卻是相對的視覺,不能「自白」只能是相對反映出來的知覺。所以「白」既然連先天的存庫都沒有,又豈能有自然的「白」令「石」變成白色?這種相對的知覺和「堅」(實物質感) 不同,沒有所謂「白者必白」的事,所以不能不附在物上而生「白」的視覺,而黃色、黑色也同樣道理的。在看事物、感覺事物時,根本不知道是「石」,又如何可以說「堅白石三」呢,在最初時白、堅都未引致「石」,此時「石」的概念是「離」的,此時就是 「因是」(所以而言) 的前認知狀態。直到你用心力去將感覺得到一個結論 (力與知果),就沒有這種「因是」狀態了。「白」與「堅」的不同可以用下列實證﹕目可以知覺到火,而火消失了,在意識上仍存在火,直到意識都見不到火了,知覺就消退了(離)。而堅是靠手去觸摸,有時手會在被捶後反彈,居然意識上並沒有知道 (不知) ,這是意識就處於「離」的狀態,消退至「天下」(意識活動和下意識活動的總和)。(所以,「白」和「堅」是不同類型的「知覺」[見, perception]與「感覺」[知, 感覺],當「離」進入「天下」就是知識的極限,所以只能獨立地先預設為「正」。
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公孫龍子》的堅白篇突破了《墨子‧經‧經說》的範疇論的框框,連結日常生活例子提出 (堅, 感覺) (白, 知覺) (石, 概念) 的三層次結論,並帶出了 器官 (眼, 手) , 神 (意識) , 藏 (下意識) , 天下 (心理世界總和) 的現象學世界。由《堅白》篇出發,我們可以發現《公孫龍子》的立論,對於「堅白」的討論不是像墨家的,談及事物特性的不同範疇,而是在心理語言的世界中,凡多重衍生的複合概念,已經是高階的一種邏輯生成,而這樣又會構成我們對世界的不同認知。而這一進路進一步反映在公孫龍的成名作﹕《白馬》篇。
二、白馬非馬的「非」及心理世界與邏輯世界的分歧
很多人以局部-全體的方式討論白馬非馬這一命題 (如馮友蘭的「共相」)、也有學者以單數/ 眾數去討論中文沒有眾數變格所帶來的誤讀 (如陳漢通….),並開始以語言學作為切入點。大部份都傾向將「非」定為「不等於」而不是「不是」,將之軟化為「『白馬』不等於『馬』,因為… 」這樣的句式,都將公孫龍的「白馬非馬」說當成將「白馬」和「馬」視為「有共通但不全同」的概念。
然而,這樣的觀點是弱化了公孫龍的整個體系。事實上,公孫龍所強調的是,「白馬」與「馬」在心理世界上,的確是兩種不同的東西,關鍵就在第一句﹕「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而整個論證最後都是想表明這一句的句式。
或者我們可以設想,若你在街上看見一個藍色的人,你還會當他是「人」嗎?(假定你知道他的皮膚顏色真的是藍色)。而若果在諮詢工作中,你聽到案主不斷強調,「我的父親是藍色的,他是藍色人」,你會覺得這和一般談論「父親… 是生物學而言所定義的人類」一般思考嗎?還是你會感到有點訝異,很想明白為何「父親」是「藍色」的「人」?你還會從邏輯/ 範疇論去思考這個「藍人非人」的命題嗎?
這就是公孫龍子「白馬非馬」的意涵﹕從心理學上來說,若果我們首先浮現的是「白」,則我們和一般情況下想到的「馬」是不是同一回事,因為這個「白馬」是特別的、想表達一些甚麼的、所以稱為「有去」(這是特別的,不是普通的「馬」可以表達);而不是「無去」的「馬」(整體而言的「馬」的普通概念)。這裏或者可以想像,為何「白馬王子」是要騎「白」馬,而「白馬」又代表了一種非一般的感覺… 。這已不是單純討論「局部-全體」,而是討論為何「白馬」的複合會帶來心理世界的衝擊。以下是《白馬》的原文。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馬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為有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于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于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仔細閱讀《白馬》,論據舖排有致,全不似是真實情況的辯論,反而每一個後墨的問證都會引致名家答題更為有力的證據,由此可以猜測此篇是公孫龍子常用的自問自答書寫方法。
問﹕白馬非馬,可以這樣說嗎?
答﹕可。
問﹕為甚麼?
答﹕馬是命名「形狀」的概念,而「白」是形容顏色的概念,「白」因此和「馬」屬不同層面的概念,其複合「白 … 馬」自然和「馬」不同。故此我們可以說﹕「白馬」非「馬」。
問﹕白馬始終都是一隻馬,那麼既然不可說白馬不是一隻馬,又如何可以說非馬,「白馬」只是「馬」的一個案例,如何可以說它是「非馬」呢。
答﹕「馬」這個概念沒有限定顏色,黃黑馬都可以應對,而「白馬」是複合了命形和命色兩個層面的概念 (即是super ordinate concept 及 sub ordinate concept兩種不同的心理語言學概念)。如果「白馬 = 馬」,那末應該兩者都可以交換,隨便拿個黑馬黃馬都是白馬了。不可以吧﹗為甚麼?不是因為表面顏色這麼簡單。所以黃、馬等概念作為普通概念時,可以呼應馬、卻不可呼應白馬,這就是白馬非馬的理由了。這就決定了囉﹗注意﹕本段很容易被人誤以為白馬是以 集合論 set theory, 亦即後墨的實存論作為證據,其實不然,仔細看公孫龍指出「白馬」這個稱謂因為是複合了 顏色-形狀 的兩個概念,在層次上有別於 「馬」這個綜合概念,故是 「不同的」(非)。
問﹕馬本身都含有顏色的,天下也沒有無色馬,那末難道說天下就沒有馬嗎?
答﹕馬當然有顏色,所以才有白馬的可能,若馬無色,世上只有「馬」,何需弄出「白馬」這一名堂出來?但正因為這樣,馬不需要「白」,但「白」卻需要附在「馬」上,所以「白→ 馬」和「馬」才是兩個層面的概念,所以「白馬非馬」。
問﹕這就不對了。「馬」本身就是「馬」,而「白」的性質就是「白」,將兩種特質合併,就叫「白馬」,是一個復名,但這個復名既然兩不相干,合併地叫後仍然保留兩種特性,即「馬」潛伏了「白」,就算「白」附在其上,都無影響「馬」的特性,所以不可以說「白馬非馬」。
答﹕那末我就改一點點,叫「白馬為馬」,相反的命題,那末我可以將白馬等同於黃馬嗎?
問﹕不可。
答﹕你既然說「白」加在「馬」上不影響其特性,為何你在假設白馬為馬時,卻又稱白馬不等於黃馬,那末你的命題就是黃馬非馬了嗎,黃馬非馬就可以,白馬非馬就不可以,就好像鳥飛入池潛水,棺要和槨放在兩處安葬,這不是天下最大的胡說嗎。
問﹕我所說的「有白馬… 不可以說就是無馬」是在不談及「白」的情況下,比較兩個「馬」都有「馬」性來說的。當然,你說到白馬不和馬是完全等同,就是站在故意將「白」抽離出「馬」之外來說才可以成立的。所以有「馬」,是因為馬存有馬的特質,而不是因為白或甚麼顏色才說它是馬,所以我們才叫「馬」,不叫「馬馬」。
答﹕白其實是相對概念,只能靠比較其他事物而來的,並沒有甚麼「白」的特性,所以還是忘卻了「白的特性」吧。白馬,就是在語言中定義甚麼叫「白」,而這必要的條件是有「不是白」的馬,才有「白馬」。「馬」呢,就無這種叫「去取」的限定特性,所以甚麼色都可以配合。而「白馬」是有限定的概念 (有去取),所以黃黑都被排除掉,唯白馬可以獨應。正是這兩個概念「有去取」和「無去取」的性質不同,我才稱之為「白馬非馬」。
「白馬」和「馬」的關係,是否純綷是心理學所說的語意網絡系統,(Semantic network, 特別是Lakoff, 1987)?如是,則這樣的白馬非馬其實也是一種嚴格意義下的集合論,但即若如此,至少這個集合論的本質是心理語言學的,和後墨的實在論是完全不同的。後墨會認為就算白馬黃馬,只要有馬的特質,都是馬,因此白馬是馬,而既然白馬是馬,其相反的白馬非馬就必然是錯的命題。而公孫龍明顯是運用了不同的角度,先去証立「白馬非馬」,再去駁斥這種實在論。而從以下我們對〈指物〉和皮亞傑的異同之處,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論述更傾向是和皮亞傑所言的schema (基模) 更為接近。
三、《通變》中的概念生成與Jean Piaget 的基模 (schema)對比
《公孫龍子》〈通變〉一直未有令人滿意的白話譯本(見馮耀明, 2000),很多人以為〈通變〉所提的「牛羊足四,數足一,故五」以及「雞足二,數足一,故三」僅僅是一種無聊的詭辯,而完全忽略〈通變〉篇的中心主旨﹕概念的生成和合併。本文以其與皮亞傑後期認知理論作出一個比較,從中我們可以互相比照這兩個不同時空的認知理論的異同之處。
以下是《公孫龍子‧通變》的白話試譯3
問﹕兩個相異的東西,可以最後合併歸一嗎?
答﹕不可以。
問﹕兩個東西相異,並且方在不同的位置,(價值的位置、方向的位置、時間的位置…),可以最後合併歸一嗎?
答﹕不可以。
問﹕「兩個東西」可以全撥去其中一方作為結論嗎?例如說,甚麼甚麼有好有壞,但整是好的。
答﹕不可以。
問﹕同樣,兩個東西有好有壞,但整體是壞的?
答﹕不可以。
問﹕只有好的一方,可以得出 “有兩個元素” 的結論嗎?
答﹕不可以。
問﹕只有壞的一方,可以得出 “有兩個元素” 的結論嗎?
答﹕也不可以。
問﹕將好壞並排,可以得出 “有兩個元素” 的結論嗎?
答﹕可以。
問﹕那末,我們發現有更多的東西可以稱為好的,這樣可以視作「變」了嗎?
答﹕可以。
問﹕這樣,甚麼部份變了呢?「好」的部份 (… 增加了)。這樣,豈不是令人混亂,因為「好」增加了,也還是「好」,那末跟本沒有質變,何以可以說是 「變」 呢?
答﹕其實,本來就無 “好” … “壞”,只有 “二”,但怎麼 “二” 還是引致了 “好” “壞” 的想像,那就等於﹕牛羊合不等同於馬,牛羊合也不同於雞。
問﹕你在說甚麼?
答﹕羊與牛的唯一分別,假設是羊有牙齒而牛無牙齒吧,但羊和牛在一般人心中也還是 “家畜”,不可以說 “羊牛” 這個 集合 沒有羊、沒有牛。所以這兩者的一個符號 (牙齒) 是不會俱在的,雖然兩者被視為類同放在一處。而雖然羊有角牛有角,但俱有的特性只會令你歸去一類,但不會說牛就等於羊。所以是同類但屬於兩種東西。加了一個新的元素,好像家畜﹕馬,用另一種東西去判別開來,姑且就假設 “馬有尾” “羊牛無尾” 吧。
無論怎樣,牛, 羊怎樣把其元素複合起來,都不是馬。單單一隻 “羊”, 不是 “二”,單一隻 “牛”, 也不是 “二”, 兩者並列就是 “二”,而且這兩種東西都不是 “馬”,這樣是可以的。
這樣一層一層的疊加排比起來,就會有不同類型的命題,就好像 牛/羊 如何複合 相對於 “馬”,這就好比為何 “二” 會突然變了 “左…右” 加入了 位置。
牛羊有毛,而雞有羽,雖然都有腳,但「腳」的稱謂 (一) 之下只有兩種數數的方法 (腳作為雞的集體的腳,和作為左腳… 右腳 等定的腳),總共就只有三層。而 「牛… 羊」兩者結合的集,在「腳」這一稱謂之下有四種數數方法 (牛羊腳整體,牛/ 羊 其中一種的腳,牛/羊 整體的連結位置的腳 [牛羊 的左腳… 右腳…前腳….後腳….],牛羊個別品種的 特定的腳),連起稱謂就有五層。所以同樣是腳,雞是就只有三層,而將牛, 羊結集後,就至少有五層。所以,雖然牛羊和雞都有腳,但牛羊這個複合排除了 “雞”,並不是因為 牛, 羊含有 “非雞” 的元素這麼簡單,最終來說是 “雞” 與 “牛羊” 處於不同的概念位置。
但其實就算是 “牛羊…馬”,這些表面上較相似的東西,也是和 “牛羊…雞” 一樣荒謬的,只是我們慣了 “牛羊…馬” 比起 “牛羊…雞” 較好,因為較多的材料去將他們類比作為同類,但其實這句命題仔細看都是起源於 隨意起名將某樣東西結合,這可算是 “狂妄” 地題出命題吧。
問﹕說第二個論證吧…
我們暫時在這裏止住,再從另一層中的對照去探討公孫龍子的〈通變〉。
在兩千二百年後,皮亞傑沒有用牛羊馬雞去表達他的理論,但在他死後才發表的Reason 一文 (Piaget, 2006),裏面以一些簡單的公式整理了他關於概念生成過程的思考。他提出有兩種概念合併﹕一種是自由併合的Free Conjunction AB (即p.q) (《公孫龍子》中的「雞」)。 而當後者是 obligated conjunction AB→A (即p.q >p) (即《公孫龍子》中的「牛羊」)
皮亞傑在第二部份,以一個小朋友辦認人名的姓/ 氏時,A.B – B 為錯;A.B→A 為對 (B為母集,A為子集) 然則,B= A+A’ ; A’=B-A;而在另一情況下,┐A’ = B-A; 則 兩者同時出現,便成為不可能概念,難以進行任何縱深運算思考。(《公孫龍子》中的「兩明」)
《公孫龍子》中的兩明是一種「道喪」,即知識無可能在此建立。而皮亞傑中,知識仍然可以得以建立,因為平衡過程 (equilibration)令其彷作 p→ (p vq)能夠得以藉指涉的、旁支的Op → O(p v q) 而建立出來。這是一種比喻多於實際的邏輯。所以,皮亞傑最晚期的思考已訂明單單邏輯並不能解釋圖式 (Schema)的變化,必須考慮到類近圖式藉指令 (obligation)和結構同型的比喻方式而得以結合。
我們在這裏可以接續《公孫龍子》的〈通變〉。在這裏,皮亞傑的p→ (p vq)及 Op → O(p v q) 就是「黃」,是人類知識的起源;而種提煉就有別於單純陣列的B= A+A’ ; A’=B-A;及┐A’ = B-A;並列的狀態 (碧)﹕
以下我們接續〈通變〉4
說第二個論證吧…
好吧。以上論據用另一種說法,就好像拿起一塊玉。將青色加諸白色,並不等於黃色。將白色加諸青色,並不變成碧綠色。
為甚麼?
本來玉之中的青色、白色,各走一鋒但又可以視為可有關係的東西,是一對可以視為「相反」的東西。本不相鄰,但於置在旁邊,兩者都不會混和,不會混和的話,就是一種「相反、相對」的情況。各得其所,就好似同一件事在二元排列時不會同時是左、右。這兩者同時存在,就不能說「整體而言… 是青色的」或者「整體而言… 是白色的」。
這就奇怪了,為何我們會有調色學上的概念﹕青色加進白色中,就有黃色呢?黃色是「正舉」,是我們覺得合符常識的事物,於是就成為好像 國→ 君→ 臣 的階段式概念網,所以在常識中我們覺得這是可以接受的。這樣,由於我們已設定了青色比起白色是更為深色,所以這種認知是可以長久的存在於我們的常識。
青和白平行時,青和白兩個表面上是相反的東西相對,卻由於我們已設立了青-白的深淺體系,所以就只能說 「白」被青的元素加入後不再是白色,而不能說青滲入了白的元素後不再是青色,所以就算白再多,都不能抹去「青」,就好像木頭不能勝過金屬一樣。這種木頭對抗金屬的情況就是「碧綠色」,就不是「正舉」的合理推論了。
但若果我們沒有建立起 「青 > 白」的常識體系,則就算將青放到白,或白放到青,都是沒有辦法說「何者抹去了另一方」,就出現了「兩明」的局面﹕這麼也可以,那樣也可以。這樣,當然也可以說 白色 抹走了 青色,令到碧綠色出現囉。
與其這樣,一般人都寧願說青色放進白色就破壞了白色,衍生出黃色。這就好像上文「馬」的例子。其實不論 「牛羊/馬」也好,「青白/ 黃」也好,這種排比的先決條件是我們把它們事先編作一類。而白加在青中產生出碧綠色,就好像上文的「雞」的概念,感覺上好像粗暴亂來。這樣粗暴亂來代表沒有「主… 次」的分位,兩者互相可以逆向隸屬,此謂兩明。兩明就箇中關係模糊,沒有辦法可以得到「正舉」的合理推論。
沒有「正舉」就會令名-實的世界變得雜亂無當,各種顏色只能被感知為互相拼湊,所以就是「兩明」。兩明就沒有一個知識體系可以得以建立,因為沒有所謂的「正確」。
於是,我們可以看出,《公孫龍子》中的「黃」是藉由平衡作用而來的新的基模 (schema),其運作與單純的同化 (assimilation) 是不一樣的。這也是此篇為何取名〈通變〉﹕這是指出我們常常遭遇到不同概念,有些較接近、有些則較疏遠甚至互相排斥,但學習不單是創出新的「集合」(set),而是將之提拔到一種新的理解,就像「青」「白」變成「黃」一樣。
四、〈指物〉中的語言柘樸學
從〈白馬〉〈通變〉兩篇,我們可以進而探討《公孫龍子》最為深奧的〈指物〉一篇。撇開其哲學意識不談,〈指物〉,可視為哲學文本的藝術精品,全篇用「指, 非指,非,物,天下,謂」等字重複多次就達到了一個哲學家所難以企及的高度。《指物》談及的是柘樸函數理論。可以想像,這篇可能是對道家,特別是《莊子‧齊物論》的「是亦一旡窮,非亦一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的反駁。
全篇由於沒有標點,句讀需要極小心處理。這篇文字若以柘樸學中的Kuratowski Closure Axiom 及Morphism for all closure-preserving functions 的句式比較,可能得出不同的閱讀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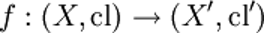
在此,A作為 X 的子集 (subset)

Cl 為 「天下」,X 為 「物」,→ 為「指」 (動詞);(cl(A)) 為「指」 (名詞);(f(A))為「非指」。為「謂」。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
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物」都是「指 (名詞)」並且指向「非指」 因為 (cl(A)) 和(f(A))的前題就是「物」(Das Ding)在心理世界的總和「天下」之中。
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 「天下」是空集的話,則抽不出 (cl(A)) 及cl’(f(A))。最初天下無指,物是無可以「謂」,因為未確立A作為X的子集,所以最初「天下無指」。
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 「非指」是「天下」中的「物」的關係 f: (X, cl)→ (X’, cl’)的子集前題,由此才有 f(cl(A))cl’(f(A))。
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指是「物」的符號化代表,是「天下」中原本沒有的東西,而在最初「天下」並無指,只有「物」,而「物」可以「謂」是一間接過程,所以兩者並未可視為等同。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天下」無「指」,而「物」此時尚未可以謂為「指」,而這個階段「非指」可以代表一種前「被謂」的狀態,「非指」必須要大前題﹕A作為 X 的子集 (subset)即「物莫非指也」才能得以確立出來。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無指為何「物」不能被「謂」,是因為當時並沒有大前題「非有非指也」(沒有「非指」),為何會沒有「非指」,因為此時只有「物」和「指」,需要隨後的「指(動詞) 非指」過程才會產生 「非指」。
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天下」無指,但(指)生於「物」並因這「物」附著各種元素特質 (各有) 而來。單單是符號 (名) 不是「指」。純綷符號卻說之是「指」,是「雙重空集」(兼不為指)。以有限的「指」去表達這種「無不為指」是不可能的。所以,沒有「元語言」。(參照維根斯坦的《哲學研究》)。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指雖不在「天下」之中,但卻是「天下」的衍生物 (「所兼」註﹕不同「所有」),「天下」若「無指」,「物」就不可以用「指」去形容為「無指」,為何不可以謂「無指」,因為沒有了「非指」,沒有「非指」的原因是 「物莫非指」,但「指」不等於「非指」,若果「無指」,則而「指」「物」都變了不能被指的「非指」。→ 但「天下」若沒有了「物」又無「指」,又如何將「非指」說出來?天下無「物」又如何談上「指」?天下若有「指無物指」(即純綷符號,「名」,「兼不為指」的metalanguage) 則為甚麼又有「非指」出來,又如何說「無物非指」。而且若果「指」本身就可以指涉「非指」,則又為甚麼必需要「物」才能產生「指」呢?
在沒有標點的情況下,句讀在這篇綷理論的文章變得極度難以解讀。但無論是否能夠完全理解此篇,有幾方面還是可以肯定的﹕1) 這篇《指物》是回應道家,以「道、德」或「氣、自然」等概念嘗試去達到「境界」,並且指說言是一種遮蔽,不如以無語言的方法去思考沒有語言的「非指」境界,如此就能進入世界的終極境界 (從馬之中悟「道」,從「指」之中悟「天下」)。這種帶有反語言觀點的道家系統與名家固然是相反的。名家首先視「天下」為心理活動總和。而「物」原本在「天下」中是影象的存有 (物之各有…) ,然後才以高階的關係由天下→物→ 指的形式,以指作為物的柘樸函數。所以「物」與「指」之間有一「指向」的動作,而且殘餘 (residue)的、沒有被注意到的就變成了「非指」,而世界並沒有指向無物的「指無物指」,或者元語言 (metalanguage) ,因為無論怎樣,當有指涉之時,已經可以視為「指」並必定和心理總和 (天下) 的「物」(das Ding) 產生指向 (指, 動詞) 並且出現殘留「非指」。最後的結論,就是證立上文的拓樸函數關係,而〈白馬〉及〈通變〉就是〈指物〉的具體論證。最後,公孫龍將目光放到語言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關係。
五、名實與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將語言分為「能指」(signifier) 和「所指」(signified) (Saussure, 1983)。而在《名實》中,語言 (名) 與現實 (實) 的關係並不是直接的聯繫,而是有彼/ 此兩面,這和索緒爾的能指/ 所指鏈環是相符合的。
名實是關於證立「彼…此」的通則的一篇古語言學文本。《名孫龍子》中表面上最易被人解讀的一篇,但因為一些詞如「明王… 審其所謂」等常被誤以為是政治思想有關君王「名實相乎」的文本 (如徐復觀,1966)。同時受當時刻寫在竹柬上的約束,「彼…此」的上下圖式變為了連寫的句子,令後世閱讀變得極為困難。以下為原文及解說﹕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實以實其所實而不曠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當亂也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甚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
天地 (世界) 產生「物」。物在時間中固定了,其內容便是「實」,「實」在空間中被固定了,便是被賦與「位」,偏離了「位」便是「不正」,處於適當位置便是「正」。必須有一個是「正」的,才能對照其餘是否「不正」,從而使質疑某「實」是否「不正」成為可能。「正」的主要目的是確立「實」的時空位置,而要正「實」必先正「名」。「名」正代表了「彼, 此」相配 (能指、所指)。若某能指 (彼) 的應用相方不配合 (不唯),則這個稱呼「不行」,不能被用於「正」的過程,而某所指 (此) 原來有亦兩不配合(不唯),則亦不可用於「正」(不行)。必須有守則決定當與不當,不然不守守則 (不當) 都算做「當」就會出現亂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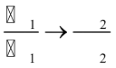 若 彼1 演變為 彼2 ,可以稱為「行彼」;
若 彼1 演變為 彼2 ,可以稱為「行彼」;
而同時 此1 演變為 此2 ,可以稱為「行此」
兩「行」相配 (當), 整個推論也就 「當」,就是「正」
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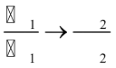 (彼彼此於彼;此此止於此),可。
(彼彼此於彼;此此止於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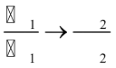 (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
(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
所謂的「名」,是「實」被說出來。所以在以下兩個情況「不謂」(不說出來)
1) 此 = ~ 此 (非此)
2) 此= 此 (此的抹消,不在此)
相比起所指的兩個情況,能指的「不謂」也建基於相似的原則﹕
1) 彼 = ~彼
2) 彼 = 彼
傳說中的「明王」(智慧之王) 能夠詳審名實的關係,認真對待其說話。真偉大哉。
由此我們可以見到,公孫龍的學說實在和皮亞傑的認識論遙相呼應,而且此書有著一致的內部結構,為中國學術史上罕見的心理學論述。
《公孫龍子》中的「白馬非馬」、「二無一」、「堅白石二」「指非指」及「彼此」的重新演繹對本土心理學有以下重要性﹕首先,這些歷史素材是創建本土心理學的重要基礎,對本土的重要思想史的檔案缺乏整理,就難以建立豐富的本土心理學體系。另外,《公孫龍子》探討的是人類的認識論的問題﹕到底人類的感覺、知覺和最後的認知的結構為何?(〈堅白〉),當我們說話時,聽眾是否單憑邏輯思考就能完全理解?(〈白馬〉) 學習如何整由「牛、馬」的相近概念慢慢至導出複合的概念?在面對被排除的成分時,又如何處理?(〈通變〉)、符號與心理物件 (〈指物〉)、語言與現實關係為何?(〈名實〉) 這些都是日後本土心理學課本中應該列入的心理學史教材。最難得的是,《公孫龍子》以精簡的方法,帶出日後心理學家就認識論和語言哲學所開拓的新課題。
主要參考文獻
1、且猶白以目見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對「白」的視覺,可以用以下例子說明﹕眼睛見到了火,火移開了,則眼睛已見不到火,但意識 [神] 仍見到火,到 “意識” 都見不到火了,我們就說 “見” 這知覺已離開了 [見 … 離]。
2、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對「堅」的感覺可以用以下例子說明﹕用捶敲手臂,手會有反應,而意識卻不知道,這時的意識可以稱為「離」。
3、《公孫龍子‧通變》原文上半部份。原文無標點。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曰變隻曰右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變安可謂變曰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羊合牛非馬牛合羊非雞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牛之非羊也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亂名是謂狂舉…
4、曰他辯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
5、商務印書館 (1923)。公孫龍子 (道藏版)上海﹕商務印書館。
6、陳大齊 (1951)。異白馬於所謂馬與白馬非馬。大陸雜誌,2(2),6
7、譚戒甫 (1963)。公孫龍子形名發微。北京﹕中華書局。
8、徐復觀 (1966)。公孫龍子講疏。台北﹕學生書局。
9、鄭良樹 (2000)。論《跡府》的成書年代」。文獻季刊,2, 4-11。
10、馮耀明(2000)。公孫龍子。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11、宗靜航 (2005)。從語言學角度探討《尹文子》真偽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5, 321-330。
12、蕭裕民 (2006)。《莊子》「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析釋。文與哲,9, 89-108。
13、莊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版本
14、韓非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版本
15、荀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版本
16、墨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版本
17、Lakoff, G., (1987).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Piaget, J. (2006). On Reason.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24, 1-29
19、Saussure, F. (1983).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R. Harris. trans).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16).
20、Solomon, B.S. (2013). On the school of Names in Ancient China. Sankt Augustin (Germany):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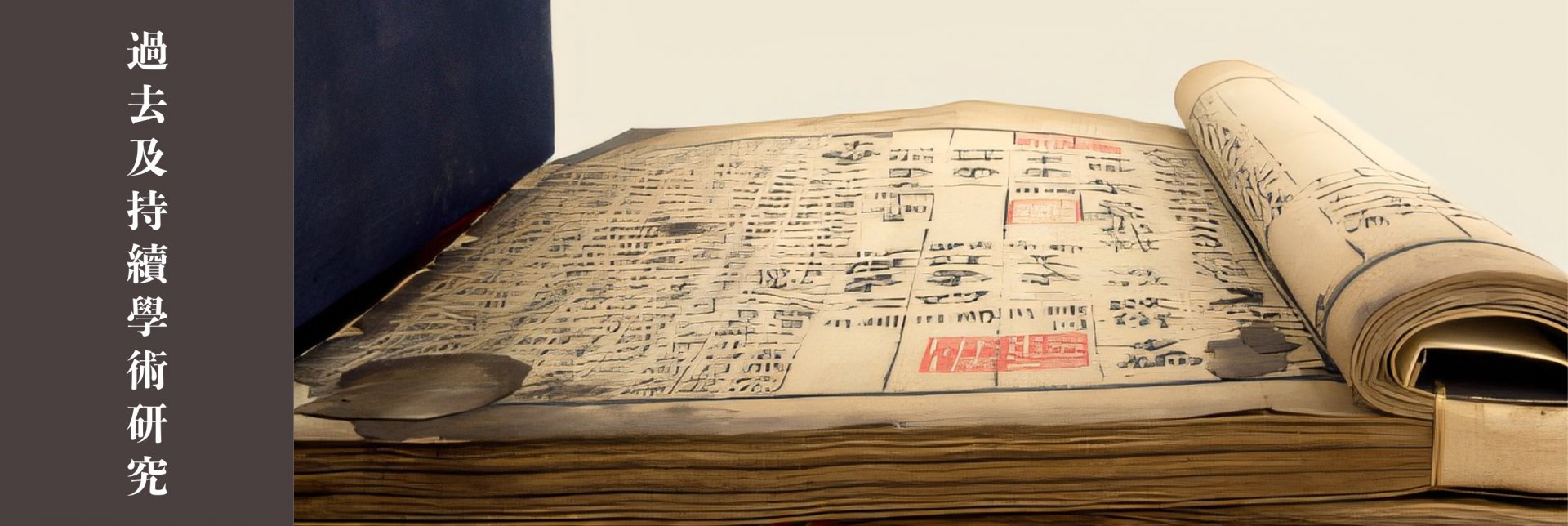



歡迎留言:
請登入/登記成為會員後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