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一反派高俅(?-1126)事迹新考
北宋武将中,广为大众所知而臭名四播的,《水浒传》的第一反派高俅高大尉,可说是数一数二。在与《水浒傅》有开的戏曲、电影、电视剧渲染下,高俅给人的印象,是比以蔡京(1047-1126)为首的「宣和六贼」还要坏。高俅在小说中,具体干的坏事,大陆的《水浒傅》学者王利器 (1912一1998)教授概括为「逼走王进,陷害林冲,排斥杨志,进攻宋江」1。至于他在小说裹的下场,《水浒傅》续书《水浒后传》写他在靖康之难后,被劫后余生的梁山好汉砍杀于中牟县(今河南中车县)。 2小说家言与历史事实自然有很大的出入,宋史上的高俅,虽确是出身宋徽宗(1100—1125 在位)藩邸,受徽宗宠信而掌禁旅多年的佞臣:但他既非横死,亦与梁山好汉无直接纠葛。关于高俅的真实事迹,据王利器教授之研究,早在清代,王士植 (1634-1711)、阮葵生 (1727-1789)及俞樾(1821—1906)等三人,已注意到南宋人王明清 (1127一1215后)《挥麈录•后录》一则不足三百八十字、简述高俅一生事迹的笔记,正是小说家衍说高俅事的来源。 3当代学者论著涉及高俅事迹的,除了王利器教授前述一篇包括高俅在内之水浒人物考证专论外,邓之诚 (1887—1960)教授在 1959年注《东京梦华录》时,也引用过这则笔记,以高俅善踢毯的事来注解书中「毬杖踢弄」的一条。另翁同文 (1915一1999)教授也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据此则笔记考出高俅与徽宗、苏轼(1036一1101)及王说(1048—1104后)的关系。翁氏一文除指出此则笔记即为《水浒传》高俅事迹张本外,更指出 《水浒傅》在何处改动了史实。 4另外,就笔者所见,有几位大陆研究《水浒傅》的学者,在王利器教授研究的基础上,写过好几篇论高俅的文章。至于宋史学者专文考证高俅其人其事的,在九十年代初有陈绍栋教授一文。另外,1998年初李裕民教授也发表了一篇短文。 5上述多位学者,除了根据上述《挥尘录 •后录》的记载外,6还参考了《宋史》、《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乐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靖康要录》、《玉照新志》、《夷坚志》、《两朝纲目备要》等史籍中的零星记载,用以考办高俅的事迹。笔者翻阅有开史料时,发觉上述各书,尚有多则有关高俅事迹之记载,未被采用:而宋人文集、笔记、方志、诏令中,记载高俅一家事迹者,也有不少。笔者因此不避浅陋,试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再进一步钩寻考索高俅之事迹,兼论高俅在宋代武将中之类型。
主要参考文献
1、王利器:〈水浒的真人真事〉(续完),载《水浒导鸣》(宜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二辑,页33。按该文的上半篇发表于《水浒导鸣》 (1982年),第一辑。
2、陈忧 (1613-1670后):《水游后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页200-- 201,243 --247。
3、王利器:〈水蔚的真人真年〉(纤完),页31:王士桢:《居易录》,文渊圈《四康全街》本,卷七,菜5上下:阮葵生:《茶余容话》(北京:中华替局,1959年),卷十八〈高俅〉、页540一550:的想(撰),贞凡、顾医、徐敏假(点校):《茶香室旅钞•三钞》(北京:中华香局点校本,1995年),卷三〈高俅〉,页1040—1041。另潘永因在湾前期所绵的《末科频钞》也收入《挥堡录 •发录》这则记越,并提出此当是《水浒傅》高俅故女的来源。参见潘永因(编):<宋稗面钞>・文渊开く四库金习)本,巻三,叶8下至9下。
4、孟元老(2一1147)(撰),跳之诚(注):《东京麦华录注》(香港:商务印书馆,1961年),巻之元 <京瓦伎艺・秘杖踢界>・买141ー142。抜:进者所引用之香港商务印楼馆1961年版,拣鄂珂所编的〈外之成先生主县落作目录>职,该替最初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在1959 年出版・香港版営系城此重印。参见邓科(编):《邓之诚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456: 翁同文:<王诜生平考略>,载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1970年)・第五辑・真135ー168・
5、王利器:<水浒的真人真事> (续完)・页31一35:欧阳健:<水浒新议>(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页167-179: 王珏、李殿元:《水浒传中的悬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95-106,358-360:陈绍棣:<高俅其人>,载《宋辽金史论丛》(北京:中华数据,1991年),第二辑,页218一223:李裕民:〈历史上的高俅及其子弟〉,《晋阳学刊》,1998年第3期,页100-101。笔者撰写初稿时,未引用陈、李两教授之专论。承马幼垣教授、曾瑞龙兄相告,仅此致谢。按陈教授一文所引史料与本文部分相同,惟观点看法有异,请读者加以比较。另本文不具名之评稿人指出尚在王健飞发表于1989年之<高俅生平事迹考略——水浒人物历史原型探源>一文,但登载之刊物不详。后查知刊于《湖北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2期,惟本文未见。
6、王明清这则笔记注明时胡元功所云。胡元功是什么人?多位学者都没有加以考索。就笔者查检所得,朱熹(1130-1200)的同年、后官至给事中、敷文阁学士的平江府长洲(今江苏吴县市)人胡元质(1127-1189)有弟名胡元功。考胡元质在绍兴十八年(1148)登科,而胡元功则在龙兴元年(1163)登第。胡元质登第时年二十二,胡元功概年轻十数岁,在时间上,胡氏兄弟成年时之年月距高俅之死尚不远,大有可能从高俅之亲故后人或徽、钦朝遗老处,知闻高俅之生平事迹(按:高俅之子高尧明、姪高尧咨分别在绍兴十七年(1147)及干道三年(1167)仍活跃于宦海)。虽然我们对胡家兄弟生平所知有限,考胡元质官至给事中,生平见《吴郡志》:胡元功官至尚书,有女号惠齐居士,婿则为淳熙八年(1181)榜之状元黄由(?-1181后):但笔者相信这个胡元功,就是告诉王明清有关高俅的事的人。考王明清这则笔记,后来又为成书于南宋中、晚期的《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所因袭,《水浒传》中有关高俅之发迹描写大概亦本于此。当代宋史学者撰写高俅简史,或旁及高俅事迹时,也主要根据王明清的这条笔记。参见王明清:《挥尘录·后录》(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卷七,页176: 章定(?-1208后):《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叶18下至19上:不着撰人:《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叶25上,113下:范成大(1126-1193)(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二十七,页393-394:卷二十八,页409-411:王鏊(?-1506后):《正德姑苏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卷五十一,页16-18:卷五十七,页29: 邓广铭(1907-1998)(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高俅·俞宗宪撰>,页406: 任崇岳:《风流天子宋徽宗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65-166:周必大(1126-1204):《文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九十九<缴高尧咨转官不当状>,叶10下至12上。
高俅官拜太尉,晋位使相,又爵封国公。说来是官高权大,位极人臣;然而,未知何故,《东都事略》及《宋史》都不为他立传。 7而李枣 (1115--1184)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又不幸佚去了徽宗和钦宗 (1126-—-1127 年在位)两朝,至于杨仲良(?一1184后)的《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未》,就仅保留得一条有开高俅的记载,故此高俅之事迹,只能常群书零星之记载逐一考辨。 8
高俅的里籍,《水浒传》倒说得不差,据《建炎以来击年要录》的记载,高俅确是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人。 9至于他的家属,《水浒传》所说的过继子「花花太岁」高衙内,区懂得使妖法的高唐州(按:宋代无高唐州,只有高唐县,元初始置高唐州,今山东高唐县东)知州高廉,自然是小说家杜撰的人物。历史上的高俅,他的亲人姓名可考的,计有他的父亲高敦复(?-1123)、他两个兄弟高伸(?—1127)和高杰(?-1127 后),他四个儿子高尧卿(?—1126)、高尧辅(?-1126后)高尧康(?—1126后) 和高尧明(?—1147后),以及高伸的儿子高尧咨(?-1167后)。
高敦复是什么出身? 《挥麈录.后录》并没有提及,只说他后来建节为节度使。 10《宋大诏令集》收录有他在宣和二年(1120)五月,自崇信军(即随州,今湖北随州市)承宣使建节为建武军(即邕州,今广西南宁市)节度使之诏令,诏中称许他「谨畏而小心,沉毅而有勇,任职滋久,而未管有过,遇事不择,而居惟尽忠」。 11这篇官样文章说他「有勇」,看来他是靠枪棒谋活的人;不过,他任武官在高俅发迹之前,还是在高俅显达之后,就未可考。李若水 (1093—1127) 在高俅死后翻他的旧账,说高俅「以市井之流,售充胥史之役,论其人则甚贱也」。 12看来高敦复即使真的武官出身,也是地位低微的,是故从没有人称高俅为将家子。似乎高敦复出任武职,一直做到节度使,完全是父凭子贵。高敦复在宣和五年 (1123)正月病卒,徽宗赐谥「康简」,真可说是庸人多福。 13
高俅三兄弟中,谁人居长,群书记载很不一致,高俅是老几,学者并没有结论。惟据徽宗在宣和七年 (1125) 十二月赐高伸的一首七律的诗题,笔者认为高伸居长,高俅行二,高杰最幼的可能性最大14。和高俅及高杰不同,高伸一直任文官。据《挥麈录·后录》所说,高伸「自言业进士,宣赴殿试,后登八座」。高伸是否真的进士及第?文献无征,笔者相信他也是靠高俅得以入仕。他不举无炫,贪婪无比,因高俅得宠而担 任显官,历任殿中监、户部尚书、保和殿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最后充资政殿大学士。但当徽宗退位,高俅失势后,他先被贬贵降职为延康殿学士,最后落得个抄家身败的下场。 15高杰的生平事迹,史书所载,比高伸还少,他和父兄一样出任武官,然他无才无德,无功无劳,倚着高俅之势,累宫至左金吾卫大将军,他也像高伸一样,当高俅失势后,被贬职抄家。 16
高俅四子一侄,在高俅当权得宠时,不过是一班乳臭未干的小儿,但凭着高俅之恩荫,却都轻易取得百战沙场的老将以及官海浮沉多年之土大夫所难得到的高位。计高尧卿官至岳阳军(即岳州,今湖南岳阳市)承宜使,高尧辅做到安国军(即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承宣使,高尧唐做到桂州(今广西桂林市)观察使,高尧明做到户部员外郎,高尧咨做到直秘阁。 17其荒谬之地方,诚如李若水所言:「子孙弟姪或尘政府,玷污班。儿童被朱紫,媵妾享封号:膳奴廊卒,名杂仕流。」。 18当然,一荣皆荣,一枯尽枯,高俅兄弟失势后,他们的子姪也就树倒猢狲散,再也不复当年之富贵。 19
主要参考文献
7、王玨认为高俅败坏军政,是造成金人长驱之罪首,所以《宋史»不为其立傅。此说有误,按被指为宜和六贼的蔡京、蔡攸 (1077--1126)、王黼 (1079-1126)、童贯 (1054—1126)、梁师成 (2—1126)和朱勔(1075--1126)等人,《宋史》均有立傅。高俅无傅,也许因官方记录散佚所致。考徐梦莘(1126—1207)忘《三朝北盟会编》,访求搜集雨宋之际之大事史料,可谓丰富详尽,在蔡京等人相开条目下都至少附有小传,惟在高俅相关条目下,却没附有什么碑传记载,可见商俅之史料散佚,连徐梦莘也搜集不到。另李裕民教授则认为商俅既无滔天大恶,亦无赫赫政绩,故(宋史)不为其立传。然笔者认为史料散佚,大概才是《宋史〉不能为高俅立傅的原因。参克王珏•举殿元:《水浒传中的悬案》页96,李裕民 :(历史上的高俅及其子弟),页101。
8、杨仲良:《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收入赵铁寒(1908-1976)(主编):《宋史资料萃编》(台北:文害出版社,1967年11月),第二辑,卷一百四十八,叶6上下。
9、李心传(1166—1243)。 《建炎以来联年要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一,叶16上(以下简称《要录》),施耐庵(?-1365后)(集撰),罗贯中 (?ー1400后)(篡修):《水浒全传》,邓振铎 (1898-1958)1953 年点校本(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页16。
10、《挥麈录.后录》,页176。
11、不着撰人(编),司义祖(点校):《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卷一百零五<高敦复建武军节度使醴泉观使制>,页391。
12、李若水:《忠愍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再论高俅札子>,叶6下。按李若水载靖康元年(1126)五月先后两度上奏,反对惟高俅举哀,又请削夺高俅官爵。他这两度札子提供了不少有关高俅生平之史料。 《宋史·李若水传》曾节录过这两篇札子的内容,王利器教授之专论曾加以引用。参见脱脱(1314-1355)(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卷四百四十六<李若水传>,页13160:王利器:<水壶的真人真事>(续完),页32。
13、徐松(1781-1848)(辑):《宋会要辑稿》,国立北平图书馆1926年本,(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职官七十七之十二、十三>(以下简称《会要》):《挥尘录·后录》,卷五,页139。
14、《水浒传》称高俅为高二,然高俅三兄弟谁人居长,群书中所记就很混乱。据《挥尘录·后录》所载,高伸为兄,高俅为弟;但《玉照新志》及《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则以高俅为兄,高伸为弟。然《靖康要录》又以高杰为兄,高伸为弟;而《要录》又以高杰、高伸都是高俅之兄;然《三朝北盟会编》又以高俅、高伸为兄,高杰为弟。王珏先后引用元人王明山及明人李宗山之考辨,但仍未确定高俅排行第几。学者们大概失看了徽宗赐高俅的一首诗。该诗载于岳珂(1182-1242后)的《宝真齐法书赞》内,诗题作「宣和己巳冬祀大礼,卿以执绥待玉辂回銮,礼毕以诗来上,俯同元韵赐伸,乃宣至俅、杰」,据此,高氏兄弟之行第,应该如徽宗所称,以高伸为长,而高俅、高杰为次。参见《挥尘录·后录》,卷七,页176;王明清(撰),汪新森、朱菊如(校点):《玉照新志》(与《投辖录》合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三,页49;《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二十,叶19下(按:此处引朱胜非(1082-1144)的说法):汪藻(1079-1154:《靖康要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一,叶1下:《要录》,卷一叶30下至31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三十二,叶8上(以下简称《会编》)。王珏、李殿元:《水浒传中的悬案》,页102-104:岳珂:《宝真齐法书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徽宗皇帝御制冬祀诗御书>,叶6上至7下。
15、据《会要》所记,高伸在政和元年(1111)十一月十七日已以殿中监之衔上《六尚供举敕令》(按他的文阶官,在政和三年〔1113〕二月时为朝请郎)。至政和五年 (1115)二月钦宗册为太子时仍任殿中监(照《夷坚志》的说法,这书是他人代编的)。按刘安上(1069一1128)的《给事集》,收有高伸殿中监转官制。考刘安上于政和元年冬召为中书舍人,执掌诰命,而高伸在政和元年十一月己任殿中监,二记正脗合 :惟不知高伸迁何官。按从殿中监升侍郎再迁尚书,在正常情况至少要数年。考《夷击志》一则记载,称高伸为尚书,而事紧于在张商英(1043一1122)为相时。考张商英在大观四年 (1110)六月拜相,政和元年八月能,然这并不是说高伸在政和元年二月至八月间已升任尚书,只是宋人以他后来担任最高的官位来称呼他。他在重和元年(1118)闰九月前已任户部尚书,在任内,他奉宰相郑居中 (1059一1123) 之命,推行讲画经费局,征收诸路白地钱,又增加酒价商税,以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后来受到朝臣反对,怀疑高伸乘机敛财。他在宣和四年(1122)前,授保和殿学士(按:初名宣和殿学士,政和中始置,至宣和元年 〔1119〕 二月改名保和殿)、提举上清宝录宫兼侍读,在同年十二月再擢保和殿大学士,后再加资政殿大学士之职。他在销康元年四月自资政股大学士降为延康殿学士,到了同年十二月更落职。在洪游 (1123一1202)《夷坚志》的笔下,高伸是一不学无术之徒,连政典为何都不知。他在芽康二年(1127)正月金兵破城后被抄家,纷人搜出大量金银,其为官贪墨可知。陈均(1174-1244):《九朝编年术要》,文渊阁 《四库全街》本,卷二十六,叶53下:卷二十八,叶43下至 44上:《会要》,〈刑法一之二十七〉、〈袋制三之四十四〉、〈职官十九 一、十、十一〉:《端康要录》,卷一,叶4上:港四,叶31下:卷十一,叶1下:刘安上:《给帮乐》,文渊开《四库全书》本,卷二〈酸中监高伸股中丞王逊转官〉,药14上下:卷万<附录• 刘安上行状〉,叶15上下:徐度(?-1138俊):《却扫编》,文渊开《四库全替》本,卷中,叶2下至了上:《要录》,卷一,叶30下至31上:《宋史》,卷二十〈徽宗纪二〉,页 384—386:卷一百六十四<职官志四 •殿中省〉,页3880—3881:洪道(提),何卓(点校):《夷坚志》(北京,中华梦局点校本,1981年),丁志,卷三,页557—558:23《宝真斋法书赞》,卷二 〈微宗皇帝傅旨御批〉,叶10下至11上。
16、《靖康要录》,卷十一,叶1下至2上。高杰在靖康二年正月,亦以隐匿金银,自左金吾街大将军降充左街率府率。
17、《靖康要录》,卷四,叶2上,31下:卷五,叶42下至43下:《要录》,卷四十八,叶9上:卷九十一,叶1上:《西要》,〈职信三十六之一百二十二〉。考王珏看到了《会要》这一条记载,知道高俅有两儿名尧康、尧辅,但错误理解了《宋史,卷二十二〈徽宗纪〉一条记载,把徽宗第三十子、封为昌国公的赵柄 (1122一1132),作为高俅的儿子「高柄」,另不知高俅尚有两儿名尧卿、尧明。参见王珏、李殿元:《水浒傅中的悬案》,页99一104:确庵(?一1164后)、耐庵(?一1267 俊)(编),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靖康稗史之三 • 开封府状笺证》,页95—96。
18、《忠愍集》,卷一,叶6下至7下。
19、考高尧明和商凳咨在绍兴、干道年间还担任知县之类的小官,参见本文第六节。
高俅的出身,《水浒传》曾有一段很有趣的描写。研究高俅事迹的学者,都点出《水浒传》的说法,实在本于《挥鉴录•后录》的记载。只是在小说裹,小苏学士苏辙 (1039--1112)取代了大苏学士苏轼,而又杜撰了临淮(即泗州,今安徽泗县)闲汉柳世权和开封药铺老閟董将士二人,另又在一些次要情节加以改动而已。 20不过,《挥麈录•后录》并没有记载高俅投靠东坡前,出身是什么? 《水浒传》描写高俅人苏门前,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自少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毯」。又说他「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后来不合做了一个富人王氏之儿子帮闲,因教唆主子花天酒地,而给主子之父去开封府告了一状,结果被判四十脊杖,发配临淮三年。21有趣的是,《水浒传》这段高俅前史,竟然有点事实根据。考上文提到的李若水,他所写的〈再论高俅剳子〉,便揭露了高俅不光彩的出身,说高俅「以市井之流,尝充胥史之役:论其人则甚贱也,恃愚矜暴,数被杖责,考其素则甚凶也」22。我们从李寨水的记载,可以知道高俅出身市井,家世卑微,发迹前还多次吃过苦头,屡遭杖责。
据《挥盐录•后录》的记载,高俅的发迹,始于做东坡的小史,开键在成为王诜的亲随。这一点却有学者怀疑,尤其是苏轼有否用高俅为小史的问题上。 23笔者以为王明清的记载可信,首先,在高俅是否做过胥史的问题上,李若水两道上奏宋廷的札子,一再称商俅「以胥会之才,和「省充育史之役」,正是《挥毫录•后录》说法可信的有力旁证。 24其次,当我们细心考查东坡一家与高俅关系时,会发现王明清所言非为道听途说。
考《挥玺录•后录》记,高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即定州),留以子曾文崩(按:即曾布,1036--1107),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俅)极其富实,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 25东坡与高俅的关系,虽然除了这条材料外,我们暂找不到其他的佐证:但是,我们却能找到比 《挥肇录•后录》 更早、更一手的记载,证明王明清所说高俅不忘东坡知遇之恩,厚待其子弟之说法不假。
大陆前数年几位研究东坡第三子苏过 (1072—1123 ) 生平事迹的学者,在撰写苏过年谱及校注他的《斜川集》时,引用了苏过好友趟鼎臣(1068?—1124后)在政和六年 (1116)所撰一首赠苏过的七律,这首七律的诗题作「闻苏权禁至京,客于高殿帅之馆,而未管相开,以诗戏之」。这首诗的诗题清楚不过地揭示了一个事实,苏过与高俅交情决非泛泛;一方面苏过入京而选择住在名声不好的高俅家,令赵鼎豆也笑他「朱门伹识将军第,陋巷难逢长者车」;另一方面,高俅居然纡尊降贵,去款待当时尚未完全获平反的元佑大豆子弟的苏过。倘二人不是如王明清所说的有那机的渊源,实难以解释。 26
其实,倘我们仔细阅读苏过的《斜川集》,我们还会找到二人交往的蛛丝马迹。按《斜川集校注》的编者舒大刚从《永乐大典》辑出一篇苏过的佚文,题为「代人贺启」,而舒氏在其《三苏后代研究》之〈苏过年谱〉卷下考定此启是苏过在政和二年(1112)代人贺张近 (?—1112后)帅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而作。不过,笔者以为这篇佚文其实是苏过贺高俅陆任股前都指搬使而写的。大概因高俅名声不好,编次苏过文集的人,就隐去了受贺人的身份,而且改为苏过代人作贺启。当然,舒大陶既不是考索高俅生平的「有心人」,又不是专业治宋代制度史的学者,故此,就看不出文中称受贺人「进长殿酸,荐分符节」,乃是专指出任殿帅而领节度使的人。也就不会联想到这篇贺启的受文人,很有可能是他在〈苏过年谱〉裹提到的高殿帅高俅。我们若细味贺启中那些歌功颂德的话,例如称受贺人「德并河岳,学参天人;才足以润色皇猷,道足以跻民寿域。徘徊赵魏,磨畏之如敌国长城:出人岩廊,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君臣合德,始终一心。顷居宥密之司,夙见倚毗之重。方伫登庸于元老,遂怀补外之高风」,再比对 《挥蹙录•后录》等有关高俅事迹之记载,我们会发现,苏过这篇贺辞,用在高俅身上,从身份、官位以至与徽宗的开系,都是贴切不过的。另外,苏过在这篇贺启之末,称「旧扫门屏,久暌星躔。岂图樗散亡余生,复托监书之未吏。沟中之断,虽绝意于青黄:辙下之鳞,犹有冀于升斗。丘山之惠,没齿何忘?燕雀之情,贺厦敢后」?倘受贺人碓是曾照顾过苏氏兄弟的高俅,苏过这番满带感恩的话,也是很合适的,而非泛泛之谀词。 27附带一谈,王明清的《挥尘录·第三录》曾记一事,称在宣和中,苏过游京师,居于景德寺。一日忽然获徽宗宣召,命他作画。徽宗表示知他是东坡之子,善画窠石,故有此召。苏过画成,徽宗称数之余,肠酒厚货遣归。苏过忽来此好运,就像做梦一般。 28这个故事倘不假,我们会问,是谁向徽宗推荐苏过作蜚?笔者以为最有可能的人,就是既与苏过交好,又知他的行踪,而又是徽宗亲信的高俅。考这则故事,王明清注明是胡元功所传述。而胡元功正是在《挥玺录•后录》中传述高俅事迹的人。我们若从这层关系去推想。则在这条笔记中,使苏过交上好运的人,就呼之欲出了。 29
虽然在东坡现存之诗文中,我们尚找不到高俅任东坡小史之记载;但高俅善待东坡子弟的事,却文献有征。根据以上的考证推论,我们可以相信《挥麈录 •后录》之记载不假:高俅有感于东坡知遇及举荐之德,当他发迹后,就善待东坡子弟以报故主之恩。
高俅在东坡门下当了多少年胥史?王明清没有说。笔者相信至少有一段日子,高俅才会给人「笔札颇工」之考语而蒙东坡赏识,而绝不会像《水浒传》所说那样在苏府住上几天便走。 《挥麈录•后录》记,高俅从东坡小史成为王诜的亲随,始于东坡出寸中山之年。考东坡在元佑八年 (1093) 九月后离京出知定州,30则高俅人王诜之门当在是年底。檬《挥麈录•后录》所说,高俅要到元符末(即元符三年,1100)才巧遇徽宗,并成为徽宗藩邸亲随。这样说,高俅在王诜府中当亲随首尾共七年。可惜,目前见到之史料,除了《挥灵录• 后录》多外,我们尚见不到其他关于高俅与王诜往来之记载。不过,既然我们已能证明东坡父子与高俅大有渊源之专不假,而大量史料又证实高俅为徽宗藩邸旧人(哗见下文),而翁同文教授考证王诜生平之专论,又充份论证了东坡与王诜的深厚交情,以及徽宗登位前与王诜之亲密交往,31则高俅因东坡之荐而成为王诜亲随之说法,笔者认为可能性甚高。
高俅第二个主人王诜,是北宋有名之大画家。他宇晋卿,是太祖功臣王全斌(908—976)之后,仁宗 (1022—1063 在位)朝马军副都指挥使王凯(996-1061)之孙。他在神宗 (1068_1085 在位)即位初,以左卫将军选尚神宗二姊蜀国长公主(1051--1080):不过,他生性风流,行为不检,神宗因姊姊之故才一再优容他。蜀国长公主在元丰三年 (1080)病逝,神宗怒他不善待公主,将他贬黜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后徙颍州(今安徽阜阳市)。他在哲宗 (1086—1100 在位)登位后恢复驸马都尉名位;32不过当哲京亲政后,他因与旧裳之关系,并不大得意。论号份,他是哲宗和徽宗的姑叉。据《挥麈录 •后录》所说,封为端王的徽宗在藩邸时,因「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王诜与这个内姪投缘,自然因彼此对书画古玩有共同的喜好所致。另外,也可能看出徽宗「贵不可言」,而加以交结。 33《挥麈录•后录》说王诜在元符末(按:哲宗于元符二年正月崩,元符末当指元符二年底至三年初) 见任枢密都承旨,在上朝时在殿厅待班,碰见徽宗。徽宗问王诜借用篦刀理餐。王诜见徽宗喜爱此物,就在当晚派高俅送一式两副的篦刀到端王府给徽宗,结果给高俅带来好运。 34这条记载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王诜派高俅送礼的时间。考徽宗在绍圣三年 (1096)三月封端王,并出就傅,到元符二年 (1099)五月出居外第35,这脗合《挥麈录•后录》所载,王诜派高俅送礼到端王府后「逾月」,徽宗就登位的说法。不过,李若水后来说高俅「事上皇三十年」,若从靖康元年上推,到元符二年,首尾为二十八年,还差两年才足三十之数。当然,李若水可以将二十八年笼统的称作三十年;36不过,笔者怀疑高俅人徽宗藩邸可能略早于元符二年底,盖依《挥尘录 •后录》之说,高俅入徽宗藩邸才一月,便被徽宗倚为腹心,乃是不可想像的事。第二是王诜在元符末年的职位。王明清称王诜当时任枢密都承旨;不过,考诸群书,未有记载王诜在哲宗朝担任过枢密都承旨。而据 《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在元符元年 (1098)四月,当曾布对哲宗言及王诜之「薄劣」时,哲宗的反应是「亦晒之,讫不用也」。要说哲宗会用他为枢密都承旨之可能实不大。另王诜在元符二年闻九月,因被御史劾奏匿藏妇人,又教令写文字投雇,及虚作逃亡之事,而被哲宗罚铜三十斤;然《资治通鉴长编》在此条下只称他为驸马都尉,而没有提及他当时职位是枢密都承旨;此外,邵伯温 (1056—1134)的《邵氏闻见录》及《宋史》均载他在建中靖国元年 (1101),因做不成枢密都承旨而迁怒尚书右丞范纯礼 (1031—1106),可见他在哲宗晚年任枢密都承旨之可能性不高。反而,人称「大王都尉,的王师约(1044—1102)却在元符三年初,徽宗即位后曾任福密都承旨。笔者怀疑是胡元功或王明清错把「大王都尉,的宫位误作「小王都尉」的。 37
主要参考文献
20、对于《水浒传》将高俅原本投靠苏轼,改写为投靠苏辙的事,王玨曾提出一些解释,他认为《水浒传》作者不想将他丑化的高俅,与大文豪苏轼扯上关系,故此将这笔账算在「比较风流倜傥」而又与王诜关系好的小苏学士苏辙头上。不过,小说作者大概不想罗织苏辙太甚,故不明说是苏辙,而只说是「小苏学士」。另外,王玨又点出《水浒传》在哪些次要情节作出改动,例如王诜叫高俅送徽宗的礼物,从原来的篦刀改为玉龙笔架与镇纸玉狮子。最后王玨提出不相信高俅真的当过东坡的小史,以为《挥壁录·后录》是野史不足信。 《水浒传》作者为何有此改动,很难知真实理由:不过,王玨却不知东坡要比乃弟与王诜关系更深,情谊更厚,另外,说苏辙比较风流,也不知何所依据。关于高俅与东坡之渊源,下文将会详述。 《挥壁录·后录》虽属私家记述之「野史」但可信程度之高,非王玨能所料。参见《水浒全传》,第二回,16—18:王玨、李殿元:《水浒传中的悬案》,页95—105,页97—98。
21、《水浒全传》,页16。又据香港《水浒传》学者马幼垣教授的研究,现藏于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的《(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和藏于日本日光轮王寺的《京本增补校正全像水浒志传评林》均载高俅落难在灵州灵璧县,而不是临淮:另照顾他的是军吏柳世雄,而不是柳世权。当然,灵州(今宁夏灵武市西南,一说在宁夏吴忠市南金积乡附近)既不属宋所有,而灵璧县(今安徽灵璧县)也不在西北之灵州,而在临淮(泗州)附近的宿州(今安徽宿州市)。小说家之言自然不辨地理,不计历史。又考《陇右金石录》,在政和元年六月,担任会州(今甘肃靖远县)怀戎堡巡检的人亦名柳世雄。不知事属巧合,还是《水浒传》作者确有所本。是条资料,承同门好友曾瑞龙兄赐告,仅此致谢。参见马幼垣:く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水浒残叶书后》,载马幼垣:《水浒论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页8:张维(?—1941 后)(编):《陇右金石录》,民国三十年(1941)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本,收入《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七辑,<宋上>,页508—510。
22、《忠愍集》,卷一,叶6下。
23、参见注释20。
24、《忠愍集》,卷一く駮不当为高俅举挂箚子》、<再论高俅箚子>,叶5上下,6上下。
25、《挥壁录·后录》,卷七,页176。
26、舒大刚:《三苏后代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苏过年谱》,下,页250;亦见曾枣庄、舒大刚:く苏过年谱>苏过(撰),舒大刚(等点校):斜川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收入,页778。赵氏这首诗,可参见赵鼎臣:《竹隐畸士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叶3上。
27、考张近字几仲,开封人,《宋史》有传。他进士出身,官至显谟阁直学士。他与东坡父子均有交,但他从未当过「殿岩」之殿帅,也未建节。他当非该贺启之受文人。参见《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近传>,页11145—11146:《斜川集校注》,卷十,页719—720:舒大刚:《三苏后代研究》,《苏过年谱》,下,页234;《文忠集》,卷四十八《跋东坡与张近帖》,叶19上下。
28、《挥麈录·第三录》,卷二,页240。
29、关于胡元功的事迹,参看注释6。
30、按李焘以东坡初除定州,在元佑八年六月,后不行,而再除定州在九月。毕沅(1730—1797)考定东坡离京赴定州在是年十二月。而孔凡礼则仍以东坡出知定州在九月二十六日之后。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1995年),卷四百八十四,页11515(以下简称《长编》):毕沅:《续资治通鉴》(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57年),卷八十三,页2109;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卷三十二,页1102-1104。
31、参见注释4。
32、王诜早在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因牵连在东坡乌台诗案中,被追两官勒停。元丰三年公主病重,神宗为安慰公主,就恢复王诜原官。公主病卒不久,神宗查出王诜对不起公主之事,便将他贬谪。到哲宗即位,在元佑元年(1086)九月才复驸马都尉、登州(今山东蓬莱市)刺史。参见《会要》,く职官六十六之十》:《长编》,卷三百零一,页7333:卷三百八十七,页9428;《宋史》,卷二百四十八く魏国大长公主传>,页8779—8780;卷二百五十五<王凯传附王诜传>,页8926。
33、关于徽宗与王诜之交往,除见于《挥壁录·后录》卷七之记载外,亦见载于《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这条记载引述蔡京子蔡条(?—1126后)之说,称徽宗在「潜邸时独喜读书学画,工笔札,所好者古器山石,异于诸王。又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令穰游。二人者,有时名,繇是上望誉闻于中外」。另外蔡条在其《铁围山丛谈》里也记徽宗为端王时与王诜互赠名画之事。参见《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八く花石网>,叶16上下;蔡绦(撰),冯惠民、沉锡麟(点校):《铁园山丛谈》(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卷四,页78。
34、据庄绰(?—1150后)所记,「河间府善造篦刀子,以水精美玉为靶,鈒镂如丝发」。大概王诜送给徽宗就是此物。参见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卷上,页33;《挥盛录·后录》,卷七,页176。
35、《宋史》,卷十八く哲宗纪二》,页344:卷十九<徽宗纪一>,页357:《长编》,卷五百十,页12146。
36、《忠愍集》,卷一,叶6下。
37、据邵伯温所记,王诜在徽宗继位后,曾上简子向徽宗求为枢密都承旨。徽宗自然答允,但仍垂帘听政的向太后(1046—1101)反对,说王诜浮薄,若任之为都承旨,就会坏了枢密院之事。向太后以另一驸马王师约在哲宗朝为此官称职,主张改由王师约出任。徽宗只好照办。邵伯温又说,曾布早就想排挤范纯礼,于是对王诜讹称他做不成都承旨,是因范纯礼的反对。王诜信了曾布的话,深恨范纯礼,后来他因馆伴辽使,而乘机诬告范纯礼在押宴时,席间语犯徽宗之名。结果范被罢右丞之职。 《宋史·范纯礼传》所记相同。这里附带一谈王诜与曾布的关系。有人或许认为曾布既然在哲宗前说王诜的坏话,徽宗及王诜后来就不可能派高俅去联络他,争取他的支持。笔者以为持这种看法的人,倘有注意曾布后来能向王诜中伤范纯礼的事实,就知二人的关系并不是外人所看那么简单。以曾布投机的性格,为迎合哲宗而骂一下王诜,但暗地里和他眉来眼去,暗通消息,又有什么稀奇?笔者以为要判断二人是友抑敌,不能只看曾布一次骂王诜的事,而要全面查察二人以前及以后的动作。王师约是太祖功臣王审琦(925—974)玄孙,治平三平(1066)尚英宗长女徐国公主(?—1085),据《宋史》本传所载,他在徽宗即位初,的确曾任枢密都承旨。邵伯温所记不误。至于他在哲宗朝曾否任都承旨,则暂无其他佐证。据《宋史·职官志》所载,似乎王师约在哲宗朝并未在枢府供职。又据近人梁天锡之宋枢密院制度专著的枢密都承旨表,王师约和王诜在哲宗朝均榜上无名。综合群书所载,王诜在元符末年担任枢密都承旨的说法,当是误传。参见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卷五,页43—44;《宋史》,卷一百六十二く职官二》,页3801;卷二百四十八<楚国大长公主传>,页8779:卷二百五十く王师约传>,页8820:卷三百十四く范纯礼传》,页10279;《长编》,卷四百九十七,页11834:卷五百十六,页12270;梁天锡:《宋枢密院制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上册,页111。
高俅深得徽宗宠信的缘故,《挥尘录•后录》说得非常戏剧化,称高俅奉王诜命送礼至端王府,遇上徽宗在园中蹴毯,高俅时来运到,偏巧他精于此道,而得以在徽宗前露了一脚好功夫。徽宗大喜之余,马上把高俅留下作亲随,而王诜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欣然同意高俅过府。高俅此后日见亲信,后来徽宗登位,他作为从龙之臣,就得以飞黄腾达。徽宗后来对其他藩邸旧僚言及高俅得到重用的原因,也半真半假地说因高俅踢得一脚好毬所致。这也就是《水浒传》说高俅原来叫高毬的故事张本。 38《挥麈录.后录》条记载的真实性有多少,实在教人怀疑。无疑,徽宗喜爱踢毬,而高俅出身市井,会此道也不出奇,但若说高俅因踢毬而获徽宗宠信,就似乎有渲染夸张的成份。高俅是徽宗的从龙之臣,宋人官私方面都有充份可信的记载。徽宗御笔称高俅「系随龙」,又赐书阁名日「风云庆会」;而在拜他为股前都指挥使的制诰中说他「尝事潜藩,永肩诚节」:在拜其父为节度使之制诰中,又称许他「事予潜满,赤心左右,一节初终,如宋昌以谋议而戴孝文,如王常以亲信而从光武」;另在拜他为使相之制诰中又说「爱念勋劳之旧,孰可与:载惟攀附之良,见存无几」:而李若水则说他「事上皇于潜邸,夤缘遭遇,超躐显位」,「事上皇三十年,朝夕左右,略无裨益」。 39以上种种,都可以见到徽宗与他不比寻常的君臣开系。笔者以为高俅受到徽宗无比的宠信,并不因他工于笔札,或是会踢几脚好毬所致。笔者怀疑徽宗对他信任不替,除了他对主子忠心耿耿,以及知情识趣外,最重要的是他在徽宗从藩王人继大统之事立下大功,才会得到徽宗无比的信任。
上文所引、徽宗在宣和二年五月拜高俅父为节度使的制诰,将高俅比作辅助西汉文帝(前180—前157在位)、东汉光武帝(25—57 在位)得成帝业之从龙功臣宋昌(?一前176)和王常 (?—36),40正好透露了高俅当年的从龙之功,并非跟在主子后面坐享富贵那么简单,他实在出过大力,才膺日后之厚赏。考徽宗继位,并非一帆风顺,宰相章惇 (1035—1105) 就极力反对:只因向太后坚持,而知福密院事曾布带头附和太后之议,才使徽宗登上宝座。 41笔者以为徽宗也像其他兄弟一样,眼见哲宗多病而无子,早就暗中营谋帝位。 42他交结驸马王诜和宗室赵令穰 (?—1144),博取好学儒雅之名。 43但笔者以为徽宗能得到向太后的欢心,大有可能是受到王诜等所造之与论影响。而徽宗得立的开键人物曾布,所以肯全力支特徽宗,除了想取章惇之相位自为外,笔者怀疑徽宗曾暗中做了收买工夫,而高俅正做了居中联络的人。据《挥壅录 •后录》所载,当年东坡出守定州,本来想把高俅交托给曾布的;只是曾布以府中胥史已多,才没有接受。曾布虽然没有做高俅的主人,准二人按理不会不相识。绍圣以后一直在京的曾布,相信与高俅仍有过从。微宗要找人联络曾布,高俅自然是最理想的人选。后人都以为徽宗荒唐糊涂,然观乎徽宗在登位前之从容不逼姿态,以及他在位时的用人手段,他也有其精明的一面。寓居澳洲的道教史权威柳存仁教授,二十多年前早从徽宗注《道德经》之精审,洞察出徽宗其实「深思睿然,精通南面术。」44《挥垒录•后录》 说徽宗在元符末年一次朝堂相遇中向王诜借篦刀,而王诜选择晚上派高依送礼。我们有谁知道王诜送上的,是否真的只是一对虽然名贵,但价值终有限之篦子刀那么简单?笔者怀疑曾被神宗斥贵「泄漏禁中语」的小王都尉,45这次其实送上极其重要的情报。而信差高俅就是王诜极为信任,不会泄漏秘密的人。大概高俅的缜密与干练为徽宗所识,故此就耍求留用高俅。至于踢毬之事,笔者以为是徽宗故意说出去以掩人耳目。
概而言之,笔者相信高俅所以后来得到徽宗无比的宠信,绝不会是只因晓得踢几脚毬那么儿戏,而是由于他居中联络(甚至有份说服)以曾布为首的大臣,支持徽宗继统有大功所致。他在徽宗幕邸的地位,由于史料缺乏,暂难确定他是否徽宗的谋主。不过他对徽宗忠心不贰,兼出谋献策,奔走联络,是可以肯定的。后来徽宗将他比作汉文之宋昌、光武之王常,大概他当年是加此评定高休之功劳的。
主要参考文献
38、《挥壁录·后录》,卷七,页176:《水浒全传》,页17—19。又据江少虞(?—1145后)所记,不独徽宗好此道,连他的儿子高宗(1127—1162在位)亦精敏于蹴鞠之艺,并置供御打毬供奉之官。参见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五十二,<蹴鞠>,页684。
39、《会要》,く职官七十七之十二、十三》;《挥麈录·后录》,卷七,页164;《宋大诏令集》,卷一百零二く高俅拜太尉制>,页377;く高俅除使相制》,页379:卷一百零五く高敦复建武军节度使醴泉观使制>,页391;《忠愍集》,卷一,叶5下至6下。
40、考宋昌是汉文帝为代王时代国之中尉,当京中大臣平定诸吕,使人迎立文帝时,他力排众议,主张文帝接受。文帝入京,他随驾保护,又先入京打探情况,确知并无危险,就还报文帝。文帝抵渭桥(即中渭桥,约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二十里),他又使京中大臣向文帝恭行臣礼。文帝即位,任他为卫将军,统率南北军,并以掖赞之功,封壮武侯。他是文帝得以自外藩入继帝位的最大功臣。至于王常是光武帝守昆阳(今河南叶县)时之部下,刘玄(23—24在位)称帝时任为廷尉,行南阳(今河南南阳市)太守事,封邓王。但他一直忠于光武兄弟,光武称帝翌年四月,即率众来降,光武欢喜地说:「吾见王廷尉,不忧南方矣。」并即拜他为左曹,封山桑侯。是年十一月,光武拜他为汉忠将军,副岑彭(?—35)南征,光武当众称许王常,说他「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参见司马光(1019—1086):《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卷十三,页435—443;卷三十九,页1240—1243,1256—1257:卷四十,页1302,1305—1306。
41、据《九朝编年备要》所记,入内内侍省都知梁从政(?—1101后)初给事哲宗生母钦成皇后(1052—1101),后受钦成之命,交结章惇,使章惇支持哲宗同母弟简王似(?—1106)继位。章惇后来果然抬出以长当立申王佖(?一1106),以礼当立简王来反对微宗继统。从这里可以侧面见到哲宗晚年,诸王已为继位问题而暗中交结大臣。又据《会要》所记,当向太后召见梁从政,询及定策之事,他即附和章惇。到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当徽宗亲政后,即算旧账,由宰相韩忠彦(1038—1109)出面,将梁从政参劾贬逐。参见《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五,叶23下至24下:《长编》,卷五百二十,页12356—12367;《宋史》,卷二百四十三く神宗钦圣宪肃向皇后传>、く钦成朱皇后传》,页8630—8631:卷二百四十六<吴荣穆王佖传>、《楚荣宪王似传>,页8722—8724:卷四百七十一<章惇传>,页13713;<曾布传>,页13716:《会要》,《职官六十七之三十三>。
42、蔡绦的《铁围山丛谈》揭露了徽宗在登位前许多营谋帝位的举动,绝非意外地被人捧上帝位。又《九朝编年备要》载有一个隶太史局的人郭天信(?—1109后)在元符末年得以常出入禁中。徽宗每退朝,他就遮道多次向徽宗说他当得大位。后来徽宗登位,对他信任有嘉,给他恩泽如从龙之人,后来连蔡京也在他攻劾下罢相。这个人显然是徽宗布在内廷的线眼,为徽宗刺探情报,才得到徽宗的宠信。此外,周辉(1124—1195后)的《清波杂志》也记载徽宗在登位前一再暗使人持其生辰八字,到相国寺找一个会术数的人陈彦测论。徽宗登位后,即厚宠此人,授以高官。关于徽宗营谋帝位的问题,有人认为徽宗当时年仅十八,一直长于深宫,出居外第才数月,不该有这种智谋与城府。笔者认为若仅以年龄作为判断一个人智计的唯一标准,那是昧于常识的浅见。历代皇帝比徽宗即位时更年轻而更有智计谋略的,大不乏人,我们随便的即可以举出明世宗(1522—1566在位)、清圣祖(1662—1722在位)等好几个。即在北宋,仁宗、神宗即位时亦不过十多岁,不比微宗继位时年长;但他们心智却早已成熟。另一方面,笔者认为长于深宫的人,不但不会缺乏历练,反而在险恶的环境中生活,更会比常人在政治上早熟。有人认为徽宗就算要联络曾布,也不会派出投他不久而身份属家仆的高俅。笔者以为,徽宗不派随他日久的心腹,而改派新参且毫不起眼的家仆高俅联络曾布,正是他厉害之处,正是他教其竞争对手疏于防范之手段。徽宗成功的地方,就是不让普通人看出他暗中营谋帝位。他不会像钦成后一样,竟派内侍中地位甚高的梁从政去联络章惇,而招人话柄。参见《铁围山丛谈》,卷一,页1,5—6:卷三,页41—42;《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七,叶43上:周辉(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卷六,页241—242。另外研究宋徽宗的任崇岳教授,指出徽宗既非纨姱子弟,也不是昏庸之辈,他在哲宗诸弟中,是营谋帝位最积极的一个,既将自己扮成好学儒雅的人,又交结有时誉的大臣,制造兴论;另外暗中占卜休咎,觊觎大位。又懂得收买宫内宫外的人,刻意讨好向太后。参见任崇岳:《风流天子宋徽宗传》,页1—4。考徽宗如何博得向太后欢心,任氏也没有列出史料证明。笔者以为能出入宫禁的王诜和赵令穰等人,是最有可能为微宗在宫中营造美名的人。
43、赵令穰是太祖的五世孙,字大年。他是北宋末书画名家,尤工草书,生平喜欢收藏晋、宋以来的法书名画,他自年青时已有好读书及能文之美名,在哲宗时因端午进画扇而受到哲宗赏识。大概因他能出入宫廷,而又是徽宗的同道,故徽宗刻意的交结。他官至崇信军节度观察留后,到高宗朝仍健在,曾与苏辙之孙苏籀(1091—1164后)有交。参见不着撰人:《宣和画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く墨竹挺节凌霜图一>,叶4下至5上:邓椿(?—1167后):《书继》,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く侯王贵戚>,叶2上下;舒大刚:《三苏后代研究》,<苏籀年谱》,卷下,页331。有人认为王诜名声不佳,一直不为哲宗甚至向太后所喜,徽宗如何会借他博取时誉?笔者以为王诜不为哲宗等所喜容是事实;但他是饮誉士林艺坛的大名士,是苏轼及其门下一大批士大夫始终引为知己的人,徽宗借王诜争取苏轼一班元佑旧臣的支持,是很化算事,也实在情理之中。
44、参见柳存仁:《道藏本三圣注道德经之得失》,载柳存仁:《和风堂读书记》(香港:龙门书店,1977年),上册,页25,27,31—33。是条资料蒙何汉威学长提示。
45、《会要》,《职官六十六之十》。
徽宗对助他登位之人,均予以酬庸,曾布得偿所愿,取代章惇为相,王诜也擢至节度观察留后,46而高俅也获徽宗提拔,步步攀升。 《挥麈录•后录》说高俅在徽宗登位后,「眷渥甚厚,不次迁拜。…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 47大致得其实。考高俅在徽宗朝任官的最早记载,是哲宗、徽宗朝直臣邹浩 (1060一1111)的文集《道乡集》所保存的一道〈高俅转官制〉。考邹浩在建中靖国元年八月前除中书舍人,大概在是年十—月前迁吏部侍郎,则他撰这道制诰当在是年八月至十一月间。 48这道制诰没说高俅转什么官,制文只说「亟迁秩序,密奉轩墀,朝廷盛选也,朕不虚授。惟尔试艺应格,逢时致身,故以是命焉」。我们从其辞句推敲,高俅是经过试艺(按指武艺)的手续,而获迁在宫禁随侍徽宗的优差。至于职位,相信是供奉官合门祗候一类的武臣近职。高俅本来颇通文墨,不过,由于出身不好,兼没有科第之资历,就不像其见高伸走文官的路子,而改从武官之途仕进。 49
《水浒传》说徽宗「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50考《水浒传》这段描述,除了最后说高俅只用半年便当上殿帅这一点不确外,其余都大致不差。正如上文所述,徽宗的确先让高俅经试艺后,做他驾前的小使豆。然俊又找机会给高俅立边功,以便擢升他。章颖(1140-1217)的《宋南渡十将傅》即记:「先是,高俅誉为端王邸官露,上(徽宗) 即位,欲显擢之。旧法,非有瀀功不得为三衙。时(刘)仲武为边帅,上以俅属之 ,俅竟以边功至殿帅。」51因史料散佚,及宋人可能有意删落高俅事迹的记载,除了《宋南渡十将传》这条记载外,晢时没能找到有关高俅因立边功而得到擢升的具体记载。当然,笼统的说高俅立有边功的记载,在《宋大诏令集》所收有关高俅的三篇制诰都有提及。按政和七年 (1117)正月,高俅拜大尉的制文即说他「暊临边寄,国奏战多」:而宣和二年五月其父高敦复建节的制文更说他出使敌国有大功,说他「亏者杖使节以载驱,街王命而抗论:凛凛而义形于色,谔谔而言皆匪躬。相如入秦,烂然完壁之迹;苏武守节,壮哉引佩之辞」。另宣和四年五月他拜使相之制文,也说他「将币婆庭,耀使华于漠北:收疆戎塞,耸战气于山西」。 52
高俅在何年随刘仲武 (1048—1120)立边功?考徽宗在崇宁二年(1103)开始向西疆用兵,同年六月收复湟州(今青海乐都县)。这次军事行动,刘仲武以兰州(今甘肃兰州市)第九将的身份从征有功。九月,以刘仲武权领湟州事。是年十二月,刘仲武又以洮西安抚之身份率兵解循化城(即一公城,今甘肃夏河县北)之围,以功改知河州(今甘肃临夏市),进东上阁门使。崇宁四年 (1105) 四月,刘仲武再破夏兵于清平寨 (即溪兰宗堡);不久再破吐蕃,复西宁州(今青海西宁市),进客省使、荣州(今四川自贡市)防乐使。 53考高俅在崇宁四年五月以容省使副龙图阁直学士林塘 (?—1110后)出使辽国,54他随刘仲武出征,似当在崇宁二、三年 (1104)间,当刘出任湟州、河州守豆时。高俅立了什么战功?居然可以在短短四、五年间越过诸司使臣一级而升任横班使豆次高职位的客省使?笔者以为高俅的战功都是因人成事居多,刘仲武显然揣摩到徽宗的心意,有战功都给高俄一份。高俅有了 「边功」,微宗也就名正言顺的不次提升他。
高俅从横班使臣擢升为「礼继二府」的三衙管军,相信是赏他崇宁四年五月出使辽国之功。据睪书所载,高俅这次出使,过程充满火药味。考辽国于是年四月因西夏之求援,遗使质问宋廷,为何攻西夏而取其地。五月宋廷即派林塘使辽,并以高俅为副。林是宰相蔡京的死煎,他出使前,蔡暗中授意林摅,要他故意激怒辽廷而启灵。林撼抵辽后,果然采高姿态,既盛气凌人,又处处与辽人抗争。他见到辽主,又力数西夏的不是,并抗言辽国不能约制贵备西夏,现在凭什么责怪宋廷,还要为西夏讲话?林撼一番辞锋凌厉而出其不意的话,弄得辽廷君臣不知所答。到他辞行准备返宋时,辽廷要他向宋廷代递辽方的国书,仍要求宋归还在夏境所建之城寨。但林撼的回答很强硬,不肯应承辽的要求。辽人大怒,不顾外交礼仪,将林撼、高俅等住的驿馆的所有供应停止,断他们食水粮食三天,又羁留他们多月,才让他们返宋。林撼这次与辽人针锋相对,绝不妥协,反对他的人说他是「怒邻生事」,但在徽宗看来,他实在为宋廷争了很大的面子,替宋廷出了口恶气。结果林摭升任礼部尚酱,以赏出使之功。 55上文引述的制文,吹嘘高俅前都指挥使职事,以使相之身统领禁军。徽宗在制文褒对高俅溢美不止,说他「智敏而行完,才宏而量博:弧矢之威天下,妙臻百中之能,诗礼之帅中军,雅着异闻之善,:又说他「峻更三帅之雄,嗣董周厅之次;侍殿陛者几二十载,护貔旅者逾百万夫。号令严明,肃和门而无犯,轩墀邃密,拱宸扆以攸宁」。在这些善于舞文弄墨的翰林学士笔下,出身市井而实在见不到有什么将略的高大尉,居然成为文武全才的儒将。这里我们把这些宫样文章抄下,为的是立此存照,让我们在下一节裹,比较一下高俅在失势后宋廷对他的评价。
高俅并无大勋大功,二十年间而能位极人臣,做到「出将人相」,只为徽宗对他的信任,要他统领禁旅,把关看家。宣和五年正月,高俅之父病死,本来要丁忧守制;但徽宗御笔下旨,实行「夺情」,要他继续统率禁军,随身护驾。至于他能否打仗杀敌,整肃军伍,就不在徽宗考虑之内。他由始至终,都不过是徽宗的家臣家将,他的武将生涯因徽宗登位而始,亦因徽宗之退位而终。
主要参考文献
46、《宋史》,卷十九く徽宗纪一》,页359—360:卷二百五十五く王诜传>,页8926。考苏轼亦于元符三年四月获赦返内地居住,不知道是否王诜、曾布等为他说情所致。
47、考《长编》载徽宗登位后,优迁他的「随龙人」多人官职,相信高俅也在其中,只是他当时地位尚低,故史籍不载其名。参见《长编》,卷五百二十,页12381—12382:《挥麈录·后录》,卷七,页176。
48、四库馆臣认为这道制话不被删落,而能保存下来,是因为邹浩之子「编类之时,搜采未备,去取亦未尽当」。又邹浩在建中靖国元年何月出任中书舍人不详,据其文集三处自述以及李幼武(?—1163后)所记,他在建中靖国元年任舍人,至是年郊祀时已迁吏部侍郎。而《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邹浩在是年八月已为中书舍人,而考《宋史·徽宗纪》,是年郊祀在十一月。以此推论,邹浩任中书舍人,不晚于是年八月,而在十一月前。参见邹浩:《道乡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提要》;卷十一<追感董敦逸梦授侍郎>,叶2上:卷十六く高俅转官制》,叶6下:卷三十六く至明弟墓志铭>,叶12下至13上:卷三十八く黄陵庙祝文二首》,叶1上下:《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九,叶5下:《宋史》,卷十九<徽宗纪一》,页362—363;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三く邹浩吏部侍郎>,叶12上下。
49、考《长编》载,在元符二年七月己未,「军头司引见殿前、马军司拣试到散祗候等殿待长行八十人试艺」,其中箭法突出的两人换左班殿直,并减三年磨勘。相信高俅应的试艺,和上述的类似。以高俅从无阶无品的王府小吏入仕,这次转官,应该还是在三班使臣之内,而加合门祗候之近职,就可称得上「密奉轩墀」,而高俅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能得到这职位,已算是超授了。参见《长编》,卷五百十三,页12200;《道乡集》,卷十六く高俅转官制>,叶6下。
50、《水浒全传》,页19。
51、章颖:《宋南渡十将传》,《芋园丛书》本,卷一<刘锜>,叶1上下。
52、《宋大诏令集》,卷一百零二(高俅拜太尉制>,页377—379:卷一百零五<高敦复建武军节度使醴泉观使制>,页391—392。
53、《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九,叶5上,19上至20下:卷一百四十,叶1下,13上至15上:《宋史》,卷三百五十<刘仲武传》,页11081—11082:李事(1161—1238):《皇宋十朝网要》,收入赵铁寒主编:《宋史资料萃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1月),第一辑,卷十六,叶8上,12上至13下。
54、《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六,叶13上。
55、《宋史》,卷二十《徽宗纪二〉,页374 :卷三百五十一く林据传〉,页11101112:《皇宋十朝网要》,卷十六,叶13上至14上。据《皇宋十朝网要》载到崇宁四年八月戊子,宋廷再派礼部侍郎刘正夫(1062—1117)充北朝国信使,「以林越街命未还」。可见林、高二人被游方国留至少三月多。考蔡京之子蔡条对林据这次出使,有什为没染之记裁。替中称林据抵游后坚持不行辽人之礼仪。又说林据在辽人亮出兵刃,逼他看虎国时,常从人皆泣,他却一点也不怕,还不管辽人之忌译,称国中老虎为南朝之狗。最后林摅不屈而还。总之,在蔡条之笔下,林据似要比简相如更刚猛英雄。至于高依的表现如何,是同样不屈?还是在「从者泣」之内,察条就没有提及。参见《铁园山丛谈》卷三,页54。
高俅及其家人得以高信厚禄,权势薰天,并非有何本事,只是凭徽宗的恩宠。宣和七年十二月,金人以宋败盟,分兵两路南侵。徽宗见金兵来势沟沟,自问无法应付危局,而朝臣又请求让太子监国时,在是月二十四日,他就干脆把这个包袱丢给他那个少不更事的儿子钦宗,实行内禅,自已退居太上皇。在靖康元年正月初二,当金兵尚未兵临城下前,大概在童贯等怂恿下,徽宗带同心腹近臣,包括蔡仫、高伸等离开京师,向南方逃跑。手握兵权的童贯与高俅率胜捷军及禁军扈从。 56一朝天子一朝臣,徽宗才退位。宋廷朝臣便马上奏劾以蔡京为首的徽宗佞臣。太常少卿李网 (1083--1140) 便率先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上书,痛劾童赏、王黼、蔡收、朱动、李彦及高俅误国,请将他们贬黜。其中高俅被指「恃宠眷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白卫,失禁旅之心」。而太宰白时中 (?-1127)也转风驶舵,在靖康元年正月,将京中禁旅不堪作战之责任,归答于「外则童贯失陷,内则高俅不招刺,军政不修」。 57考在徽宗在位时,人们纵使不満,地不敢对炙手可热的高殿帅有何公开的批评。最多以童谣的方式,间接表达他们对高俅一家弄权专横的不满。 58为讨好主子,宋廷那些负贵写制诰的文臣,只会搜索枯肠,引经据典,拼命对高俅歌功颂德,写下一篇又一篇上一节所引、肉麻不堪的制文。当高俅兄弟随徽宗南逃后,在靖康元年正月十二日,宋廷就开始对徽宗之佞臣包括高俅兄弟开刀,差官往他们家,查抄他们之金银家当,要他们送纳国库,并且明令「若有徇情隐庇或转为藏隐,许诸色人告,给半充赏,隐藏之人并行军法」。 59
当高俅在京之府第被抄查时,他们父子兄弟在泗州亦成为丧家之犬。大概高俅与童贯等在是否继续往南逃往镇江府(今江苏镇江市)之事上蠢见不合,童贯就假传征宗之命,令高俅留在泗州守乐,不得南行。据高俅奇给留在京师之亲弟高杰书信所言,童贯不许他们护驾,甚至不让他们见到徽宗。有术士要跟随,就给童贯之亲兵胜捷军射倒。 60童买逭番举动,倒让高俅可以和他划清界限。当宋廷朝臣对童贯等猛加奏劾,指他们欲挟持徽宗以谋叛时,髙俅就侥幸脱身,不受牵连。他很快便以疾请解军职,返回京师。 61早在正月六日,钦宗便已委任他的母舅、比高俅更坏大事,更教人寒心的王宗港(?一1131后),以殿前都虞候权管干股前司公事,收回高俅执掌十多年的兵权。 62高俅肯乖乖的交出兵权,钦宗倒不像对付童贯般对付他。到是年三月,当宋廷己将蔡京、王黼、童贯、染师成等人或诛或贬时,钦宗居然还以他扈送徽宗有劳,进封简国公。 63是年四月三日,徽宗从镇江返京,高俅选因此得以加官检校太保。但是月底,朝臣却不放过高俅一家,御史台追究当日高伸、高尧明跟随高俅南逃,而擅离职守之罪。钦宗已算宽大,只将高伸自资政殿大学士降为延康殿学士宫祠,将高尧明追五官勒停。这时,高俅己是自身难保,能有这样的结果,己算钦宗手下留情。 64
高俅在是年五月十四日病卒,得年多少不详。因他死时还带着开府仪同三司的头街,依照仪制,使相薨,朝廷要挂服举哀。大常博士李若水本管此事,即连上两道札子,反对钦宗为他挂服,并列举高俅生前过恶罪状,认为高俅得全要领而死,实在便宜了他,认为他实在死有余辜。在李若水等眼中,高俅最大之罪过,是他败坏军政,遵致金人南侵时,宋军无力抵御。至于高家为宫贪墨聚饮,还在其次。李若水痛言金人能长聒京师郊甸,「正坐军政刓激,士不贾勇」,而宋军弄到如此不堪作战,正因高俅「抚恤无恩,训练无法,,却叉「占役上军,修筑第宅,或借权费以缩私欢,,他说弄到丧师辱国之田地,「虽三尺之童皆知童贯、高依粟坡军政之故」。而高俅「久握兵柄,衡与童贯分内外之寄,厥罪惟均」,既然童贯受到远察之贵,天下称快,而高俅未就典刑便死了,实在不公亚。他指出高俅之死,「中外交贺」:借要为高俅举哀行褛,实在没有道理,应该追夺他的官爵,以为奸谀之戒オ是。 65
钦宗大概想给徽宗留一点颜面,不想马上清算乃父最宠信之近臣,对于李若水的箚子的回应,是先在是月十六日,下旨暨不为高俅翠哀,并正式宣布高俅之罪过,称他「率领笔兵,败坏纪律,果有言章」,给他的处分是追降其官职,而其子孙有幸冒的,亦与降等授官 。两天后擦吏部之报告,再下旨正式追夺高俅检校大保和开府仪同三司的加官,而高俅三个儿子尧卿、尧辅、尧唐则自承宣使和观察使降授右武大夫及武功大夫,仍领遥都刺史,余宫并夺,至于高俅诸孙就免追究。对于钦宗如此宽大处理高俅一家,以李若水为首的朝臣,自然不肯罢休。圣旨一出,即有朝臣(疑叉是李若水)再严效高俅,这道奏章比李若水前两道节子,更具体指出高俅败坏军政的过悪,现录如下:
谨按高俅初由胥吏,遭遇夤缘辛会,致位使相、检校三公。不思竭力图报,乃敢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重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凡所招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权幸。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教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士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管他业,虽禁车亦皆僦力取直,以为衣食。全废教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会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缀急之际,又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己求和,实俅恃宠营私所致。贪财误国之奸,不减蔡收,偶有司失刑,遂免远窜,得终牖下。令来止追前官,不惟不足以厌公论,亦无以诫后来。 66
在朝臣之压力下,钦宗最后在五月二十一日再下诏,追夺高俅奉国军节度使和简国公的职街,至此,高俅所有官爵都被削夺。不过,朝臣仍未罢休,继续有人指责高俅误国,好像王亵(?一1131 后)在是年六月底上奏时,便指禁卫精兵,「高俅坏之于内,童贯毙之于外。数十年闲,不知其销折几何人。皇城诸班之地,今为殿间池台矣;京城废管之地,今为苑票甲第矣。郡县之民,佃空营地以自给者,盖千百计。富室大家,尚养健仆数人,以待暴容」,最后弄到「皇城之内,无诸班以宿卫:京城之中,少禁旅以镇守」。 67
高家作恶多端,天道不爽,他们的报应发生在是年闻十一月底金兵攻陷汴京后。在玉石俱焚之情况下,己失然的高家子弟,自然是众矢之的。首先在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开宝寺大火,宋廷下令将邻近的高俅赐第拆掉,将木材卖给百姓。 68到了靖康二年正月二日,高伸、高杰兄弟被女侍检举私藏金银不肯缴纳,二人立被降职,而他们一家子食墨所得的家财,就尽数被充公,转奉金人。 69
高氏一门的家财被充公了,更大的报应是高伸兄弟最后连命也保不住。在靖康二年二月,金人押送北末宗室大臣家属往北方,高俅一家当年威风一时,现时也就逃不过玉石俱焚之劫,他们一家在被收押之列。高伸在是年五月前身死,而高杰与及高俅几个儿子大概都惨死异域。侥幸逃出虎口,似乎只有高尧明和高尧咨。 70
对于高俅败坏军政,间接导致汴京失守的事实,继统的高宗是清楚不过的,71宋廷的文豆,也就没有放过己成落水狗的高俅,继续对他口诛笔伐。除了李綗继续痛骂高俅外,曾在螬康年间掌权的吴敏 (?---1133),便对高宗说:「自蔡京、王黼坏文,高俅、童质坏武,网纪大乱」,72把靖康之难的责任都推在蔡京、高俅等宣和佞豆上,那就可卸去他们自己的货任。
不过,高宗对高俅并没有太大的个人恶感,且高俅兄弟已死,对高家就不再追究。为表示宽大,高宗还在绍兴元年十月,在朝臣的反对下,仍给起复的高尧明,授宣教郎并知建康府溧水县(今江苏溧水县)的小官。考高尧明知溧水县,一直做到绍兴四年(1134)二月才离任。 73此后,高尧明还当过温州永嘉(今浙江永嘉县)知县,到绍兴十四年 (1144)五月,又以右朝散大夫出知明州之鄞县(今浙江鄞县),直至十七年 (1147)七月离任。明州军号为奉国军,曾是高俅所领之节度州,高尧明出任乃父生前所领节镇属县县令,也算是巧合。高尧明以后之事迹不详。 74除高尧明外,高宗也在绍兴五年 (1135)七月,授子高尧咨右承奉郎监西京中岳庙一职,虽然不算皇恩浩荡,但在高家破败之余,也算是特恩。高尧咨浮沉官海多年,在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按:孝宗〔1163—-1189 在位〕己纤位),做到无为军巢县(今安徽巢湖市)知县,本来他以措置召募万餐营卒一百零三人有功,获转一官:但权给事中周必大以高尧咨并无功劳,封还诰命,反对给他迁官,周之意见后得到宋廷的接纳。高尧咨在干道元年 (1165)至三年 (1167) 曾知池州东流县(今安徽东至县)。他后来官运如何,就史所不载。 75
高家第三代的情况,根据岳飞 (1103—1142)孙子岳珂所记,到了宁宗 (1191一1224 在位)之世,已到了坎坷贫困的境地。奇籍南方的高伸的子孙,以及流落在开封的一支高氏后人,分别在嘉定十二年 (1219)及十六年 (1223),将徽宗赐给祖宗之书帖,辗转宝给岳珂,赖以活命。 76在笔者目前可见之史料,高俅之后代事迹可考的,仅此而己。大概高俅的后代没有什么长进,可补祖宗过失的人物,故此,自南宋以降,除了王明清替高俅留下一条笔记式的小传外,似乎没有人为高俅写过一篇像梯的墓志铭或行状。明朝人记在苏州曾找到他的堉并蓦碣,然却是真假难辨。 77世事难言,高俅事蹪湮没无闻百载后,想不到他的名宇,却凭小说家生花妙笔,再得以在人间傅开。对高俅不幸的是,在小说家渲染下,他从此成为家传户䁱的大奸臣、大恶棍。
主要参考文献
56、考童贯与高俅护驾之兵,《靖康要录》的作者与周必大均称童贯带胜捷军三千·高俅带禁军三千:陈东(986—1127)则称童贯带兵二万:惟《要录》则记二人率军三万五千。按宜和末年,宋军自黄河兵败后,京中禁旅人数大减·连胜捷军在内·童贯、高俅应不可能带走几万军队,疑《要录》误。又徽宗对高伸一直总能有嘉·据岳珂所记·徽宗在高伸每年生日时,特许他前二日受赐·另给他许多额外恩数·故徽宗出走,也命高伸随从。参见《靖康要录》·卷三·叶23上:《文忠集》·卷三十·<徽猷阁待制宋公映墓志铭》·叶7上:《要录》卷一·叶16上:《宋史》·卷二十二<徽宗纪四》,页417:陈东:《少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登闻检院再上钦宗皇帝书》·叶10上:《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叶10下至11下。
57、李网:《梁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四十二く上渊圣皇帝实封言事奏状》,叶1上至3上:《会编》,卷二十七,叶14上。
58、在南宋初年,大臣张网(1083—1166)上奏时,提到在微宗时,正言陈伯强因指资高俅「妄造圣语」,便马上得罪被贬。可见高俅的权势。又据南宋人之笔记所载,当徽宗龙臣何执中(1044—1117)居相位时(按:何于大观三年(1109)拜相),京师有童谣说:「杀了穜窝割了菜,吃了羔羊儿荷叶在。」时人以指童贯、高俅、蔡京和何执中。参见张纲:《华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七く驳陈伯张恩泽指挥》,叶2上下:曾敏行(1118—1175)(撰),朱杰人(点校):《独醒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九,页86。
59、《靖康要录》·卷一·叶24上下。
60、《少阳集》,卷一《登闻检院三上钦宗皇帝书》,叶12上下。据南宋人之笔记所载,徽宗等抵泗州,童黄坐在帐中,而令高俅(原文写高球,当为笔误)于南山把隘。后徽宗在十多日后始抵浙中。见赵彦卫(1140—1205后)(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6年),卷七,页122。
61、高俅什么时候称病自泗州返京不详,考陈东在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上书,提到从高杰家书,知道高俅被童贷勒令留在泗州之事,则高俅返京,最快当在是年二月。见《会编》,卷三十二,叶7上至8下:《挥壁录·后录》,卷七,页176。
62、考钦宗即位时,他便向徽宗提出罢免曾与他争夺储位的郸王楷(?—1127后)之皇城司职位,另外又提出以他的母舅王宗濋同管殿前司公事,接掌高俅殿前司的兵权。对钦宗的要求,微宗均同意。按王宗濋是钦宗生母显恭王皇后(1084—1108)的兄弟,其父是德州刺史王藻。排辈份,王宗濋是太祖开国功臣王审琦的六世孙。当高俅交出殿前司兵权时,因殿前副都指挥使姚古(?一1127后)统兵在外,故王宗濋以殿前都虞候权领殿前司。到六月姚古援太原失利革职,王便升任殿前副都指挥使,真除殿帅。史称王宗濋「素骄贵,不能任事,自高俅领殿前,纪律驰废,既敌国入受,遽命宗濋,识者为之寒心」。高宗在绍兴元年(1131)三月谈到王宗濋时,也指出「宗濋自可用,但当时用非所宜,兼戚里不当管军」。考张邦炜教授在其论微宗、钦宗父子在靖康年间之反目一文中,曾论及钦宗以王宗濋取代高俅,以取回京师兵权,另张氏也认为高俅随徽宗南逃,未必报知钦宗,另也论及高俅在泗州与童货反目后,先期回朝后,为钦宗封为简国公之理由。参见《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六《钦宗内禅》,叶9下:《皇宋十朝网要》,卷十九,叶6下至8上:《宋史》,卷二十三く钦宗纪》,页425,433:卷二百四十五く后妃传下·微宗显恭王皇后传》,页8638;《会编》,卷二十八,叶4下至5上:翟汝文(1076—1141):《忠惠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く赐权管干殿前司公事王宗濋辞免殿前都处候恩命不允韶》,叶6下至7上:《要录》,卷四十三·叶4上:胡寅(1098—1156)(撰),容肇祖(1897—1994)(点校):《斐然集》(与《崇正辨》合本)(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3年),卷二十六く吴国太夫人王氏墓志铭>,页578—579:张邦炜:《靖康内讧解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页74—78。
63、《少阳集》,卷一《登闻检院再上钦宗皇帝书》、く登闻检院三上钦宗皇帝书》,叶10下至19上:《靖康要录》,卷三,叶9下:《会编》,卷三十一,叶2下至3下:卷三十二,叶14上至15上:卷四十五,叶1至2下。考张邦炜教授认为钦宗竞将「分明有罪」的高俅加官晋爵,是策略的运用,志在分化微宗亲信。见张邦炜:《靖康内讧解析》,页78。
64、考《靖康要录》所记,高俅再在靖康元年四月十六日,加检校太保。考同书卷三已记高俅在是年三月四日,自检校少傅加检校太保:而今又加检校太保,似不当,疑三月四日加检校少师,四月十六日始加检校太保。见《靖康要录》,卷四,叶20下,31下。
65、 《忠愍集》,卷一《驳不当为高俅举挂箚子》、《再论高俅箚子》,叶5上至8上。
66、《靖康要录》这里只说臣僚上言,没明载是何人上奏,比较此奏的措辞用语,与李若水前引两道箚子相近,疑是李若水所撰,只是《忠愍集》漏收此奏。参见《靖康要录》,卷五,叶42下至43下。
67、王襄此奏题为「上钦宗论彗星」,考靖康元年六月壬戌(二十七),「彗出紫微垣」。王襄此奏大概上于六月底。考王襄责备高俅之余,他自己后来败军失律,被资为宁远军(即容州,今广西容县)节度副使,到绍兴元年三月始以赦叙复为正义大夫。参《宋史》,卷二十三く钦宗纪》·页429:赵汝愚(1140—1196)(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四十五く上钦宗论彗星·王襄撰》,页480:《要录》,卷四十三,叶12上。
68、这所赐第是徽宗在宣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赐给高俅的,才不过五年多,便化为鸟有。又高俅第被拆毁以资作柴薪事,《会编》系于靖康二年二月一日。参见《会要》,く方域四之二十三》:《靖康要录》,卷十,叶50下:《会编》,卷七十八,叶4上下。
69、《靖康要录》,卷十一,叶1下至2上:《会编》,卷七十四,叶2上下。 77 据《会编》所载,高伸在靖康二年五月十八日前已身死。他是怎样死的?史所不载,看来多半死于金人之手。参见《靖康要录》,卷十一,叶48下:《会编》,卷一百十二,叶6上下。
70、据《会编》所载,高伸在靖康二年五月十八日前已身死。他是怎样死的?史所不载,看来多半死于金人之手。参见《靖康要录》,卷十一,叶48下:《会编》,卷一百十二,叶6上下。
71、高宗对于徽、钦末年京师禁军不堪作战的情况,十分清楚。他在绍兴元年正月便对臣下言及他在靖康年间,曾对钦宗痛陈「京师甲士虽不少,然皆游惰羸弱,未尝简练,敌人若来,不败即渋」。参见《要录》,卷四十一,叶10下至11上。
72、李纲撰写《靖康传信录》,为自己辩护的同时,又窜改了陈东的宣和六贼说法,将高俅的名字加入,而去掉本来的王黼。 《宋史·李网传》的作者照抄《靖康传信录》,于是教人误以为高俅名列宣和六贼之中。参见《梁溪集》,卷一百七十二《靖康传信录》,中,叶9上下:《宋史》,卷三百五十八く李网传》,页11245:《少阳集》,卷一《登闻检院三上钦宗皇帝书》,叶12上下:《宋名臣言行录·续集》·卷二《吴敏》,叶2下。
73、当时朝臣程俱(1078—1144)反对给高尧明授官,但高宗仍依例授官,并给他叙官为宣教郎,没有歧视他。参见程俱:《北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九<缴江东大使司辟持服人状》,叶11下至12下:《要录》,卷四十八,叶9上:《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七(溧水县厅壁记》,叶22上。
74、高尧明何时知永嘉县不详,相信在出知鄞县前。参见张津(?—1169后)(修):《干道四明鬪经》,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五册,卷二く鄞县县宰题名>,叶27上:胡矩(?—1227后)(修):《宝庆四明志》,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五册,卷十二《鄞县县令》,叶4下:王环(?—1448后)(编集):《弘治温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卷八,页23。
75、《要录》,卷九十一,叶17上:《文忠集》,卷九十九く缴高尧咨转官不当状》,叶10下至12上:何绍基(1799—1873):《重修安徽通志》,清光绪三年(1877)重修本,(台北:华文书局,1967年),卷一百十五く职官表志》,叶26下。
76、据岳珂所记,在嘉定十二年,有卖书帖人持着徽宗御批高伸受赐贴,在郎舍向他求售。卖帖人称高氏孙尚居于京师(按:指临安,即杭州)之外,「家甚窭、待此以晨炊」。结果岳珂以万钱贸了徽宗这幅真迹(按:据王瑞来所考,岳珂在嘉定十二年八月,以承议郎权发造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在建康(即今南京市)任官,直至十四年八月除军器监淮东总领,徙往京口[即镇江)。他当是在建康买到这帖子的)。到嘉定十六年十月,岳珂在扬州(今江苏扬州市),遣间谍至河南。课者舍于一开封民家,该民家自言是高氏子孙。谍者从该民手中购得微宗赐高伸的御制冬祀诗真迹,并带回给岳珂。参见《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叶7下,10下至11上:王瑞来:<岳珂生平事迹考述》,《文史》第二十三辑(1984年11月),页119。
77、据明人徐鸣时(?—1629后)所记,在万暦年间,苏州横塘镇人赵应奎葬父黄山北麓,掘地得石碣,上书「宋高俅墓」,而碣下即其冢,据说赵应奎仍将高墓封盖。至于碣上有否墓志铭,徐书就没有提及。徐氏又称苏州志载郡城西北隅有高师巷(疑为高「帅」巷之讹),相傅是高俅所居处。考高俅死于开封,他的墓若说在苏州,本来难令人致信,而高俅也未曾在苏州住过,所谓高师巷,只怕也是以讹传讹。不过,我们不能完全否定高尧明及高尧咨等高家后人,后来有否移居或任职苏州,并将高俅骸骨迁葬于此。另外一条不宜忽略的线索,是《挥璺录·后录》的高俅事迹传述人胡元功,正巧是苏州人。胡元功为何能知道高俅秘史?笔者以为他多半得自高家后人。倘若我们将两件事合在一起去推想,事实可能是这样:高家后人将高俅迁葬苏州,并定居于人们所称的高师(或高帅)巷。而本籍苏州的胡元功因为结识了高家后人,故此能够知晓高俅的事迹。参见注释6,并见徐鸣时:《横溪录》,明抄本,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二,页277-278。
高俅败坏军政,令宋京师禁军在金人围城时不堪一战,他自是难辞其咎。南宋初年的名臣如张守 (?—1145)、胡安国1074—1138)等均痛斥高俅败壤军政。直至南宋中药,理学名臣真德秀 (1178一-1235) 及魏了翁 (1178—-1237) 仍继续指责高俅败坏军政之过恶,真德秀说:「自童买、高俅迭主兵柄,教阅训练之事尽废,上下阶级之法不行。溃败者不诛而招以金帛,死敌者不恤而诬以逃亡,于是赏罚无章而军政大坏矣。」魏了翁更说:「高俅以恩被遇,则纪律尽费,仅存三万人。靖康之祸,京师削弱,外寇凭陵,盖基于此。78白靖康之难作,宋人就普遍将国土沦亡的责任归罪于以蔡京为首的政、宣奸臣和佞臣:其次再咎责靖康当国诸臣。79宋人当然不敢公开批评徽宗、钦宗,其实,明眼人都知道靖康之难,最要货责的是徽、钦二帝。高俅不过是徽宗一员家豆家将,最坏不过是一只依附人君的城狐社鼠。他作的恶、弄的权,都是徽宗所许所授。高俅本是东坡门下一个胥史,会一点拳棒,本来没有半点领兵管军的本事,那是他的主子最清楚不过的:偏偏徽宗要抬举他,要他出任执掌京师禁旅的殿帅。他能不失职,就是奇迹。事赏上,从北宋中叶开始,宋军能够作战的都是在西北边塞的西兵,而不是在京师享福的东兵。而宋室君臣对京师禁军的要求,不是他们的战斗力是否强横,而是他们的绍对忠诚。殿帅的选拔,全视乎他们的可靠程度,至于他们驭军练兵的才能,就并不重要。像高俅这种庸将,而受委担任三衙管军的,在整个北未实在不少见。好像继高俅出任殿帅的王宗濋,骄慢无识,就比高俅更怀事。他后来居然信什么六甲神兵,以致汴京失守,城破后又率众逃遁,他误国的贵任,只有比高俅更大。80是故,我们要骂高俅误国,就更应骂把他放在要位的徽宗。光骂奴才,而不骂用奴才的庸主,那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论,高俅在徽宗诸佞臣中,己算安份,他既未似蔡京般公然坑陷正人,也没有像王补、童贯的贪功,弄出联金灭辽的祸根,引火自焚:也没有像朱劻、李彦等搅到民变四起。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载,当徽宗取燕云 「成功」后,居然以为宋廷武功盖世,竟想向西夏进攻,收复领州(今宁夏矮武市西南,一说在宁夏吴忠市南金积乡附近),而命曾在西夏立有边功的高俅统筹伐夏的事。徽宗御笔条蜚攻取之计,令高俅遵行。据说高俅有自知三明。不敢依旨行事,才没有挑起另一火头。 81是故,虽然宋人一直骂他是罪无可恕的佞臣,但他的过恶,在宋人心中,和「宣和六贼」相比,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若细心去考察,高俅当权时,他聪明地采低姿态,尽量不招人忌;有时,他还在徽宗前作态表示谦退,不肯接受徽宗给他的赏赐。 82他虽教文儿子弟满门贵显,但他并不明目张胆地招权纳贿,也没有去树巢拉帮。没有证据显示他和蔡京或童贺一伙走在一起,狼狈为奸。当童贯护送徽宗至镇江时,高俅便聪明的和童贾划清界限,结果也就救了他自己一命。 83高俅的道理是容易理解的,他与徽宗既有特殊的渊源,他就没必要再投靠依附谁。他只要好好侍候徽宗,得到主子的信任,就可确保富贵。而徽宗所要的,是他绝对的忠心和可靠,而不容许他结党:要他控制着亰师的武装力量,以厘平所有存在或潜在对帝位的威胁:而不在乎他能否把京师禁军练成劲旅。在这方面来说,高俅己达到徽宗的要求 。他既没有挟军乱政,也没有纵军害民,他的过恶,相对其他人来说,实在末到万恶不赦的地歩。
高俅有否嫉贤忌能,像小说裹那样逼害武功高强的将校王进和林冲?因文献无徽,我们不宜一口咬定有或没有。不过,从可见的史料所载,他倒推荐过贤才。他第一个推荐的贤才,是南宋抗金名将刘锜(1098-1162)。宣和二年,微宗忽然想起已逝的刘仲武,就询问高俅关于刘仲武儿子的情况,高俅即举荐刘锜,结果刘锜得到徽宗召见,并得到擢用。 84高俅推荐刘锜,当然有报恩的成份:不过,他有眼光这一点,也不能抹煞。高俅第二个推荐的贤才,是有儒将之称的张撝(?-1128)。高俅在大观二年十二月举荐当时为通直郎的张撝,称誉他「潜心武略,久习兵书」。并说他「曩在有司已尝试艺,昨缘其父恩例奏名文资,比又获贼,蒙恩改官」。又称「其才力于武尤长,伏望特依王厚例,换一武职,付以边任,。徽宗结果接受高俅的推荐,特授张撝礼宾副使,令枢密院给予差遭。85后来张搭无负高俅的推荐,历任要职:他在宜和六年正月以武略大夫使金,在靖康年间,既在金兵围城时,在京领守军奋勇杀敌,又曾出任接伴使,刺探敌情。高宗即位后,他随宗泽(1060一1128)在汴京一带抗金。建炎二年(1128)二月,金兵再犯滑州(今河南滑县),张拼当时官知滑州、果州(今四川南充市)防御使,于是自愿率兵五千往援。张在途中遇敌,虽然敌人众多:但他死战不退,结果阵亡殉国。86张撝虽然军事才能远不及刘锜,但舍生取义之节烈,堪称贤士,高俅抱没有看错人。高俅第三个推荐的贤才,是仁宗驸马都尉钱鲎臻 (?-1126后)之姪钱怿( ?--1122后)。高俅于政和三年,推荐当畤官朝散郎的钱怿,由文宫转为武职。高俅以钱怿「才カ劲强,知识明敏,留心武略,深晓兵机」,而他又「凡历数任,压获强盗」。高俅即认为钱怿的才能在武备,将他转为武官,更能发挥他的才能。徽宗准奏,钱怿于是换职为武义大夫。钱怿虽然没有刘锜的将咯、张撝的节义,但他不失为一捕盗的能臣,他在宣和三年便以大名府路廉访使省的身份捕除河北群盗有功。 87
毫无疑问,高俅一家都贪财好货,都利用手上的职权,克扣军费,括削民脂,以饱私残。他们后来给人搜出偌大的家财,就是明证。然而,徽、钦二朝的当政大臣,能清廉自爱的实在为数不多,若独责高俅,也有点不公。有徽宗这样不理人民死活,而只知享乐的皇帝,就自然有蔡京、高俅一班逢君之恶的佞臣。比起蔡京等宣和六贼,高俅所作的恶事,程度上已算较轻,而高俅明目张胆的恶事也不大多。这个出身东坡门下,而又对故主子孙能报恩的徽宗佞豆,从其所作所为,可以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什也。
主要参考文献
78、张守痛言:「本朝之兵,自童贯、高俅等坏之,而勤沮之法废,骄惰之风成。出戍则亡,遇敌则溃,小则荷戈攘夺以逞,大则杀掠婴城而叛,天下可用之兵无几矣。」考张守此奏日期不详,从文中所云「伏靓建炎元年十一月诏」,疑此奏上于建炎元年十二月张守擢为监察御史时。胡安国在绍兴二年八月上言,亦称:「本朝鉴观前代,三衙分掌亲军,虽崇宁间旧规犹在,及至高俅得用,军政废弛,遂以陵夷。」按真德秀之奏,上于宁宗嘉定九年 (1216)十二月,而魏了翁之奏,则上于理宗(1224—1264在位)端平元年 (1234)正月。参《要录》,卷十一,叶23下:卷五十七,叶8下至9上:张 守:《毗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く又乞疾速讲求防秋事务箚 子》,叶16下至17下:真德秀:《西山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五<江东泰论边事状》,叶19下至20下:佚名(编),汝企和(点校): 《续编两朝网目备要》(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5年),卷十五,页278— 279:魏了翁:《鹤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八《应诏封事》, 叶24下至25上。
79、好像李纲便将靖康之难的发生,理解为「靖康之初,所以致寇者,其病源于崇观以来军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靖康之末,所以致寇者,其病源于春初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战』。另外汪应辰(1119—1176)也指钦宗当国之臣「罕可称述」,而「皆未有能称其任」,认为没有人值得配飨钦宗庙。参见《梁溪集》,卷一百十一<别幅》,叶10下至11上:汪应辰:《文定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く论钦宗配飨功臣疏》,叶8下至10上。
80、考王宗濋以率众遁走之罪,责授定国军(即同州,今陕西大荔县)节度副使,直至绍兴元年二月,高宗才以他为钦宗外家,以赦叙复他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团练使。参《会编》,卷六十五·叶1下至2下:卷六十九,叶1下至9上:《梁溪集》,卷三十四く戒飨武臣诏》,叶3上下:《要录》,卷四十三,叶4上。
81、徽宗命高俅伐西夏,《会编》未载是哪一年。据胡寅所载,微宗在宣和七年命童贯率五路兵攻西夏,打算取天德州(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五加河东岸)、云内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但金人南侵,才收回成命。以此推之,徽宗命高俅伐西夏,当在宣和四年到六年(1124)间。参见《会编》,卷二百十五,叶7下:《斐然集》,卷十二《左朝请大夫王公墓志铭》,页595-596。
82、好像在政和七年七月,他便向微宗婉谢赐给他的额外从人。见《会要》,く职官三十二之八>。
83、参见注释68。考宋人多将童贯与高俅相提并论,好像吕中(?—1247后)便批评徽宗将「高俅、童贯之徒妄加节钺」。其实高俅一直与童贯保持距离。参吕中:《宋大事记讲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治体论》,叶6上。
84、《宋南渡十将传》,卷一,叶1上下。关于高俅荐刘锜的年月,徐规教授考为宣和二年冬或稍后,参见徐规、王云裳:く刘锜事迹编年》,载岳飞研究会(编):《岳飞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三辑,页195。
85、《会要》,《职官六十一之十七》。
86、《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四,叶6上:《梁溪集》,卷五十く奏知防守酸枣门并乞分遣执政官分巡四壁守御箚子》、く奏知酸枣门守票捍退贼马箚子》、《奏知再遣王师古等兵会合何灌兵出战简子》、く奏知已遣王师古出援张摘勾引召募人马箚子》,叶2下至5上:卷八十二《辨余堵事箚子》,叶11下:宗泽:《宗泽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七く遗事》,页105:《会要》,《仪制十一之二十九》。关于张捣战死滑州之事,研究宗泽的学者也有论及,只是张为与高俅的渊源,就没有提到。参见许序雅(等):《宗泽评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页134—135。
87、《会要》,く职官六十一之十七、十八》、《兵十二之二十六、二十七》。
高俅是北宋什么频型的武官?他在当权时,那些奉命撰写制诰的翰林学士,几乎要将颇通笔札,会点拳棒的高俅说成文武全材的儒将。实际上高俅的所谓边功战功,都是因人成事。他能够成为徽宗朝军职最高的武将(不算童质几个内臣),只为他是徽宗的从龙功臣,而得到徽宗的信任所致。从太宗(976-997在位) 开始,帝皇洁邸酱臣中的武臣,以家臣家将的身份,虽无颣赫战功,或统率三军之オ能,却常常渡委为枢府执政或三衙省军,执掌军权。 88北宋统治者这种任人惟亲的做法,几乎无代无之,好像真宗(997ー1022 在位)之龙信王继思(?一1023后)、张者(? 一1048)、崇动 (976-1045)、夏守恩(?一1037)等;89仁宗之擢用安俊(?—1044 后),莫不如此。 90高俅因缘际会,成为徽宗之家臣家将,而得以统率禁旅,位列将相。在大平时期,像高俅这等庸才,占一席高位,吃一口闲饭,还不会对国家构成太大的伤害:但一旦边廷告急,这批在帝皇身边而无真本事的奴才,却常会胡作安为,或嫉贤忌能,大大破坏军心士气,而或带来严重的后果。高俅若早死几年,也许他的恶行会被一掩而过:偏偏金兵圈城,国将不保的时候才身死,虽然逃得过刑责,却逃不过清议。
历史上的高俅,自从给《水汁传》的作者丑化为书中最大的反派后,他和他的「衙内,儿子就成为民间流传的武将歹角典型。91说来地有点冤枉,高俅在史籍保留下来的事迹,其实很有限:但在有限的记载下,却仍给小说家添油添酱,成为大恶棍、大妊人,那是高氏后人(假若在元代还有)哭笑不得的事!说来有趣,在く水浒传>襄和高俅形象相反、被尊称为「老种」、「老种经路相公」的北末未名将种师道(1051-1126),事蹪历历见于史籍,但小说作者却着盘不多,甚至没有真正出过场!种师道和高俅同卒于靖康元年金兵圝城后而汴京尚未失陷前,在宋人眼中,前者忠勇为国,后者贪庸误国;前者文武全才,后者滥竽充数;92然前者后人所知不多,后者则几乎无人不晓。歴史舞台与小说世界的实与虚、真与假,乃教人玩味不已的。
主要参考文献
88、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太宗对其晋邸旧人的任用,参见蒋复璁(1898—1990):《宋太宗晋邸幕府考》,载蒋复璁:《珍帚斋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卷三《宋史新探》,页60—81:至于晋邸佞臣对宋初军事之负面影响,可参阅本书的另一篇文章く论宋太宗朝武将之党争》,页87-135。
89、《宋史》,卷二百七十九<王继忠传>,页9471—9472:卷二百九十く张耆传》,页9709—9711:く杨崇动传》页9713—9714:《夏守恩传》,页9714—9715。按《宋史·王继忠传》后附载真宗即位后,除上述数人外,真宗其他藩邸武臣受到擢用之名单。
90、《宋史》,卷三百二十三<安俊传》,页10467—10468
91、欧阳健曾从文学创造的角度,以及市民阶级的立场,解释为何高俅被《水浒传》作者写成大反派。参见欧阳健:《水浒新议》,页167-177
92、关于种师道的事迹,特别是从微宗未年到靖康之难一段,可参阅本书的另一篇文章<论靖康之难中的种师道(1051—1126)与种师中(1059—1126)>,页551-584。
< 原创文章/视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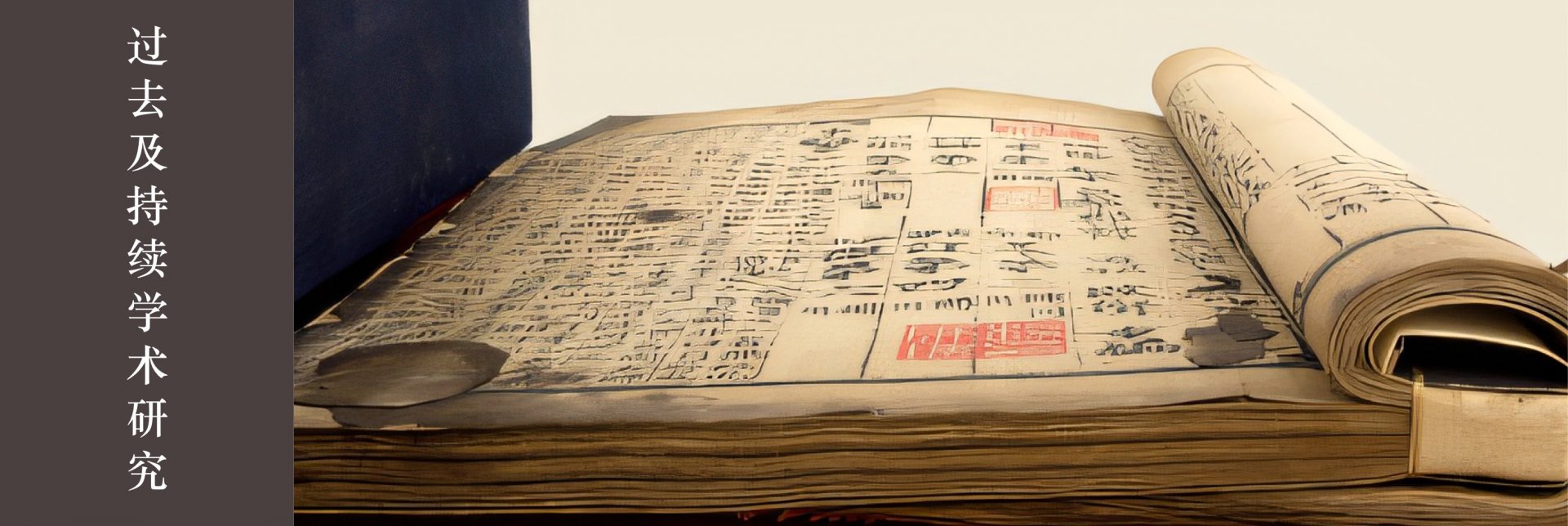



欢迎留言:
请登入/登记成为会员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