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扎作与传统节庆文化:
以观音诞为研究个案
韩明均
2024年4月12日
谢 辞
本毕业论文,承蒙彭师淑敏博士四年来之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不仅传授
学术知识,也积极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课馀与学生进行讨论,谆谆教导。研究过程中严格训练,提供论文架构、文献资料搜集等技巧,并在口述历史访问及实地考察等积极推荐和提供宝贵意见。是次研究得以顺利完成,谨此对恩师致上衷心感谢。撰写论文期间,又曾得下列人士/机构予以协助,本人併此致谢。
1.香港树仁大学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
2.香港扎作业联会主席冒卓祺先生接受口述历史访问。
3.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教师何其亮教授、罗永生博士、周子峯博士、区志坚博士、何冠环教授与朱心然博士这四年的悉心栽培与严格训练。
4.朋友何萍华小姐、叶海欣小姐、陈家俊先生、邓乐添先生及吴卓璘先生同行。
5.父亲韩锦章与母亲黄雅秀的悉心照顾与关怀。
中国扎作技艺在香港经过百年传承,已然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宣扬传统节庆文化的窗口,我们常会在观音诞、盂兰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庆中看见其踪影。1 近年,扎作技艺展示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等文化机构相继在馆内展出并介绍不同的节庆扎作品,例如火龙、狮头、花灯等,向公众展现扎作的多元面貌,足见坊间对扎作文化传承的重视。2 在诸多传统节庆中,观音诞的扎作元素不仅多元化,且观音为香港「入屋」的神祇之一,在不同族群都具有其影响力。3 因此,本论文将以观音诞的扎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与传统节日的关係、它们的历史价值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第一节:研究回顾
长春社文化古蹟资源中心副执行总监黄竞聪博士所着的《城西溯古——西营盘的历变》一书指出「扎作」囊括了所有以纱纸、竹篾、浆煳等材料製成的节庆扎作、装饰扎作、丧葬扎作和龙狮扎作。4 中国最早的扎作品是出自新疆吐鲁番彁斯塔那唐代(618-907年)墓葬中的纸棺,5 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扎作」主要在葬礼中应用,亦常会把「扎作」与「纸扎」溷为一谈,但两者其实有细微的差异,「纸扎」是冥器的一种,只会运用于丧葬或祭祀仪式中,但从定义来看,「扎作」是一个大类,节庆扎作同样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6 因为它能够表现出扎作品除了能够用于悼念先人外,还是喜庆的标誌。
中国传统扎作技艺约于清朝(1644-1911年)从广东一带传入香港,并在五、六十年代进入繁盛期。当时的扎作品除了花炮、花牌等作品外,还包含了广告牌,款式十分多样。7 狮头、花灯等节庆扎作更曾是带动香港扎作业发展的重要元素。它们在内地禁运期间被出口至欧美地区,以应付华人群体的需求。8 在中国传统节日期间,扎作品比平日更受欢迎,不少报章都曾报导过扎作业在节日期间的兴旺,例如扎作工人在中秋期间最为繁忙,收入也会大幅增加。9 可惜随着时代更迭,人们的教育水平和环保意识开始加强,中秋佳节的纸灯笼被电子灯笼代替,年轻人更愿意在空调房里办公,扎作业也回不到过去的辉煌。10 不过,该行业至今仍有师傅坚持营运与推广,以吸引更多年轻人来传承他们的匠人精神和传统文化,足以说明传统扎作工艺仍有受众,具有社会及历史价值。
大众在观音诞期间对传统扎作品的需求较多,这与民间普及的观音信仰有关。观音信仰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糅合了佛、道两教的元素,又经过「本土化」,因应人们对于生活的寄託与嚮往出现了不同的形象,应对百姓不同祈愿,同时成为妇女生活的折射,于是人们总会趁着观音诞向观音表达感恩。11 香港观音诞的庆典与习俗会因族群的背景与生活习惯而异,为增强民众社区认同感的重要平台之一。而花炮、狮头与麒麟头、花牌等扎作便是维持平台运作的工具,例如观音诞期间众人会集结起来「抢花炮」,祈求得到观音祝福,所以花炮亦被视为神诞的符号。12 因此,本论文期望通过以观音诞扎作为例,分析扎作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
第二节:研究对象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观音诞与扎作技艺。「观音诞」与「扎作技艺」都在2014年公佈的《首份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被分别列于「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和「传统手工艺」。13 近年,坊间对观音信仰的关注度有上升的趋势,香港佛教联合会与香港菩提学会相继举办「观音文化节」作宣传,亦有学者出版专书,例如《观心自在:香港观音诞与观音信仰探源》;扎作技艺则被列入2017年公佈的首份《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当中。14 自2016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开办与节庆扎作相关的展览:例如2021年的「香港节庆与民间工艺」展览,旨在让人们意识到扎作技艺的生活化。15 这些都是对扎作技艺和观音诞文化价值的认可。
观音诞的扎作品以花炮、醒狮、麒麟和花牌为主,每逢佳节这些作品总会在不同环节先后进入大众视野,例如抢花炮、舞麒麟等。《市影匠心:香港传统行业及工艺》一书曾对以上扎作品的特点及功能作出简略介绍:花炮是观音诞「抢花炮」的环节中必须具备的扎作元素,是历史故事、粤剧人物、中国传统吉祥物和扎作技巧的展示台。16 而醒狮和麒麟作为传统节庆扎作,在表演环节中扮演重要角色,除了调节气氛外,还有辟邪的功能,《武舞民间——香港客家麒麟研究》、《香港狮艺传奇》等书籍皆有专门的介绍。17 花牌在神诞期间则有庆贺、宣传和指引的功能,其发展情况在非遗资料库中有所记录。这些文献都记录了观音诞扎作及扎作行业与社会变迁的关係。
现时,华人庙宇委员会辖下以观音作主祀神的庙宇有3所,另有18所庙宇以其为配祀神,虽然数量不算多,但香火不断,可见人们长久以来对观音的尊敬。18 各区庆祝观音诞的日子和习俗会依照着人们生活的习性有细微的调整,连同扎作品的特点也会随之变化。故此,观音诞扎作品是反映各族群民俗和生活剪影的重要渠道,亦是研究的意义所在。唯现时该节庆活动和扎作技艺的从业人士及参与者都停留于中老年人及固定团体,使观音诞扎作的影响力始终难以扩大,其历史价值亦鲜有人知,幸得扎作师傅坚持推广及传承该项技艺。
第三节:研究资料
有关扎作技艺及观音诞的历史,古籍及现代中港学者的着述皆有记载及探讨。首先,《事物纪原》、《大唐新语》、《佛山忠义乡志》等古代文献曾谈及扎作品在战争、生活和传统节日中的功能与特点,记录了扎作技艺在古代的痕迹。19 《新安县志》虽只有隻言片语提到扎作品,但验证了清朝为香港扎作技艺发展历程中的起点。20 而其后的发展历程则主要运用报章及《简明香港华人风俗史》等现代学者所着之文献进行论述,藉此总结各年代扎作行业概况,包括业内工人工资、从业人数、国内外的供需等内容,同时突出节庆扎作对整个扎作行业的重要性。21
对于观音诞及相关扎作品的历史与特点,笔者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官方网页资料、学界论文及专书作为主要参考资料。有关观音诞的信仰特点、习俗与源流,《观心自在:香港观音诞观音信仰探源》、《大慈大悲观世音》等书籍都有较详尽的综述,包括「观音」从男神变为女神的过程、民间传说、传播途径、香港观音信仰的普及度等,彰显观音信仰及观音诞深厚的民众基础。22 而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中则有清楚记录舞麒麟、花牌扎作技艺和狮头扎作技艺的历史沿革、特色和製作流程,有助于准确地了解观音诞扎作。23
针对观音诞扎作的传承,本论文会辅以口述历史资料及实地考察作分析。是次研究邀请了香港扎作业联会主席冒卓祺师傅进行访问。冒师傅从19岁开始学习扎作技艺,至今仍醉心于製作麒麟、狮头等手工艺品,同时致力于推广扎作艺术,并于2019年设立扎作技艺展示馆,目的为向大众展示古今的扎作品。24 故是次访问的重点会集中于冒师傅对扎作技艺被纳入非遗以后的看法。从扎作师傅的角度出发,探讨这项技艺被纳入非遗名单后,文化机构及政府的推广及保育措施情况。另外,是次实地考察期望以2023年古洞村观音宝诞作为考察对象,从而了解现时观音诞的举办情况与扎作的特点,从中总结观音诞及其扎作背后的意义。
第四节:内容架构
本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内容主要包括与是次论文相关的学术回顾、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简述及内容架构。
第二章以「节庆扎作的流传」为题,分别在三个章节中敍述中国传统扎作的历史源流,然后分析该项技艺得以在清朝流传至香港的契机及其在香港的发展历程,同时以过往扎作行业在节庆期间的经营情况进一步带出节庆与扎作相辅相承的关係,作为全文导引的部分。
第三章以「观音诞与扎作」为题,先敍述香港观音诞的历史与文化,其后介绍观音诞主要运用的扎作品(即花炮、醒狮、麒麟及花牌)的由来、特点、相应的例子及背后的含意,以及现时传承观音诞扎作所须面对的挑战,藉此探究观音诞与扎作的文化内涵及历史意义,同时了解其流传状况。
第四章以「扎作的创新与传承」为题带出扎作技艺与观音诞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及收录进非遗名单后对传承观音诞扎作的影响。此章节亦会探讨近年来扎作师傅在观音诞扎作中的创新和他们对扎作技艺传承的影响,以及在疫情下的观音诞如何成为传统扎作技艺的载体,让其在百废待兴的阶段仍能稳定发展。
第五章的「结语」将会以前文为基础,宏观地概述香港扎作与传统节庆文化的关係及其历史意义,并审视其传承的现况。
扎作品的用途在不同时期都会发生改变:从探查地势与军情,到丧葬、祭祀,再到节日庆典,它既能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祭祀、娱乐等功能,也能在军事、经济、文化三方面默默推动城市及国家的发展。在香港,扎作品更是被人欣赏的艺术品,甚至一度成为备受外国人欢迎的出口商品,只是在新兴事物不断涌现的社会中,扎作这样费时的技艺,逐渐失去年轻的市场。
第一节:中国传统扎作
中国扎作技艺之源流可上溯至汉代(前206-220年)。据《事物纪原》记述:「高祖之征陈豨也,信谋从中起,故作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欲以穿地隧入宫中也。」,指出韩信(公元前231-196年)曾使用风筝量度距离,但纸张在东汉(25-220年)以后才得以普及化,这段文字似乎很难证明扎作在此时便已存在。25 但结合韩信以牛皮製作风筝,「下置善笛之人吹思乡之曲」使「楚军弟子八万皆散去」的事迹,则大致能够确定汉代是扎作技艺诞生的时期。26 而风筝或许是最早出现的扎作品,可见扎作最初是作军事用途的,而非单纯地只用于丧葬与祭祀。
随着纸张的普及,扎作成为百姓的生计、娱乐和祭品,亦更多地被记载于私人着述和正史中,扎作品在唐代及宋代(960-1279年)尤为流行。现代的扎作品有很多都是始于唐代,例如花灯、舞狮等,连同祭祀形式也因纸扎而发生改变。27 有关唐代节庆扎作,《大唐新语‧文章第十八》提及「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28 ,期间有「火树银花合」29 之景,可见唐朝已有花灯,呈现空前盛况。而宋代扎作则多见于《梦粱录》和《东京梦华录》,例如元宵节用长竿搭成百馀丈的「灯山」,「纸煳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飞仙」;中元节则「以纸煳架子盘游出卖」,单在杭州大街上便有两家纸扎舖。30 从以上种种记载可知,唐宋时期的扎作技艺已初具规模。
明(1368-1644年)、清与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扎作沿袭了唐宋的扎作特点、文化与作品种类,且更为系统,上海同行更是一同成立「纸扎业公所」以便统一管理。31 众多地区中,当以佛山扎作工艺发展最为兴盛,《佛山忠义乡志‧卷第六‧实业志》中写有各式行业,把「扎作行」与「灯笼行」作了区分,并提及「本乡扎作极有名,人物故事尤精,外乡多来购之,又有不倒翁为行酒令之具,外省销流极广」,可见当时佛山扎作享负盛名。32
佛山扎作流行的因素主要有二,分别是独特的地区民俗文化与地理优势。首先,佛山扎作品融入了地区民俗和文化,例如每逢秋色赛会和北帝诞,型态各异的花灯便会出现,如鱼灯、虾灯、蟾蜍灯等,还有一举成名的「佛山大爆」,这些习俗促使扎作的需求增加,其发展也自然更迅速。33 民间传说也会影响佛山扎作品,以佛山狮头为例,人称明代初年,农家常受怪兽侵扰,于是扎作师傅便以竹篾和彩纸製成「独角狮」,以怪治怪,此造型一直沿用至今。34 「佛山彩灯」与「佛山狮头」更被收录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足见其在扎作文化中的代表性。35 其次,佛山自明清以来便是贸易重镇,因其位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交通交汇处,「西接肇梧,通川广云贵。下连顺新,通江门澳门。东达番东,通石龙、惠州」,同时也是商家往返广州的必经之地,吸引并带动外省商人往来交易,扎作品因而不愁销路,足够当地扎作店舖维持营生。36 中国扎作技艺也随着这些有利条件一直传承及发展。
第二节:流传到香港的扎作
直到清朝,中国传统扎作技艺流传到香港,落地生根。从经济和社会情况分析,五、六十年代为扎作业的兴盛期,然后逐渐式微。37
有关香港扎作行业,最早的记载是在康熙和嘉庆两版的《新安县志》中,内文均有以「元宵,张灯作乐。凡先年生男者,以是晚庆灯。」记录当时的点灯活动。38 不论活动所用的「庆灯」是由本地製作,还是从外地购置,都能证明港人对扎作品的应用是从清朝开始,而且因为扎作品与本土风俗已互相融和,他们未来对此的需求是有持续性,只是仍须内地工艺的支持。因此,1869年才会出现由「省城高第悦昌号」和「佛山口口新景昌」供应的戏曲人物故事箱,儘管到了1881年,香港陆续有约百位本地的冥镪商贩和灯笼师傅通晓扎作手艺,广州师傅依然在香港市场佔有一席之地。39
香港扎作行业依赖内地供应商的原因之一是佛山等地的扎作行业比香港更早开始发展,所以技术和规模较为成熟,产品质量较有保证;此外,香港被英国佔领后,建立港口、仓库、马路等有利经济发展的设施,吸引上万华人到港谋生,其中包括华南沿海的疍户、广东商人等群体,他们对内地货品的信任度较高,加上航运的便利和华人风俗不受英籍政府干预,所以每有华人丧礼、喜事和节庆内地扎作都会较受欢迎。40
时至1920至1940年代,香港扎作行业规模开始扩大,招收工人,并成立工会组织规范管理业内人士,以及维护业内人士的权益。1922年《香港华字日报》中曾报导过一则油牛洋烛扎作工人向工会争取加薪,并要求聘请工会会员,由此可见扎作工会在该年以前已有雏型,经过多次改组更名后才正式成长为如今港人认知的「港九油烛纸业扎作职工会」,唯其后于2008年结束营办。41 而在规模方面,有关香港扎作业的统计由个体的数量变为对扎作舖的统计,意味着扎作的从业人员日渐增多,例如在1939年,《香港九龙商业分类行名录》共录得香港扎作舖132间。42 1940年代末,内地师傅和移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到港谋生,为行业增添专业人材和廉价劳动力,成了扎作业踏入兴盛期的前奏。43
1950至60年代,从扎作行业的就业情况、应用场景和经济效益中可以得知扎作业发展正式迎来全盛时期,中港的社会局势变动是其中的助力。1950年代,国庆、英女皇加冕会景巡游等节日和重大庆典,无不需要扎作品作装饰,甚至成为电影元素,一时之间客户也多了起来。44 而且行业人员更替迅速,不愁无人继承这一门手艺,当时扎作工人都称:「后浪推前浪,新人替旧人」,竞争激烈。45 正因如此,规模较小的纸料店请不起「老师傅」,连同三年学师制度也难以谨守,这或许便是行业发展壮大后产生的副作用。46 工人和师傅的薪金不固定,约8元至300元不等,虽然与1922年的10元左右相比,整体工资虽呈上升趋势,但人力资源追不上大幅增加的市场需求,扎作工人的工时一天可长达15小时,但工资却不足100元,最终爆发劳资纠纷。47 总体来说,虽然扎作行业在五十年代市况良好,但缺乏妥善管理,时有出现工时工资不成比例、收入不稳定、培训不足等问题。
1960年代起,本港扎作师傅数量增加,行业开始重新强调技术上的培训,扎作品甚至能够远销海外。首先,在从业人数方面,内地文化大革命使传统扎作工艺无法在内地发展,迫使相关人士迁至香港维生,让香港扎作行业加入新力。48 本港入行人数直到1969年仍能收录约2000位学徒,可见其发展趋势依然平稳。49 当时,扎作的样式开始更新,如「往昔扎作是没有飞机的,而今飞机可以扎作出来」,于是师傅的技术便是扎作品好坏的关键,过去的「学师制」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下,学师年期缩减至1 年。50 精美的作品不但受本地居民追捧,更有邻邦友人的欣赏。51 同时,受美国对中国实施禁运的影响,许多国内货物只能通过香港购置及输出,于是诸如花灯、狮头等扎作品开始经由香港对外输出,主要对象是远居欧美地区的华人团体,销售网络复盖英美、瑞典、加拿大等国家。52 因此,六十年代的扎作行业就业机会多,生意稳定,又能外销,处于兴盛期。
1970年代以后,香港扎作业在中港两地的社会及经济变动下逐渐走上「下坡路」。首先,就本地情况而言,扎作师傅「亦工亦商半资」,连他们自己也难以将自己定位为「手艺人」或「商人」,部分师傅只将此作为自己的副业,加上行业待遇低,再难吸引新人入行,该行业仅有的生存空间依赖各宗教善信的支持。53 另外,在售价和样式方面,由内地运来的扎作品成本和售价更低,所以即使本地师傅不断创新,销量仍比不上内地来货。54 加上人们开始追求环保、安全和新颖,传统纸灯笼或迎节扎作逐渐被代替。55 时值内地改革开放,发展工业,劳工和原料的成本都较香港低,更易获利,扎作市场便从香港转移到内地。56 基于以上因素,香港扎作行业难以回到五、六十年代的光景。
第三节:扎作与节庆的关係
综合各类文史资料,扎作品与节庆息息相关,凡遇华人节庆,扎作店总会忙得不可开交,营利也会较平日多。以1959年的中秋节为例,市民在「祀神品及纸料扎作」的总消费达百万元,当中走马灯与纸扎灯饰因受儿童欢迎,销量较佳。57 从前每逢中秋佳节,扎作业便踏入旺季,相关报道也从不间断。扎作工人会趁此时身兼多职,增加个人收入。58
中秋节其实只是扎作业的其中一个旺季,重阳、盂兰胜会等节日都令扎作师傅收益不少,花牌扎作在节日中尤其受追捧,部分店舖会僱用临时散工帮忙,减轻人手负担。59 不过,扎作工人最为忙碌的时段,当属农曆年关:他们一般都须延时工作,从农曆初一的1小时到最后阶段的17小时,需要轮流当值到通宵,但却没有「补水」,相当辛苦。60 这些都证明节庆与扎作业发展是相辅相承的。
华人之所以会在节庆期间使用扎作品,一则是用于装饰,增添节日气氛;二则是取其象徵的寓意,寄託自己的愿景,例如麒麟扎作有送子的寓意、福鼠象徵富贵兴隆等;三则用作祭祀,例如观音诞的舞麒麟、盂兰胜会的士大王等。故此,时至今日,我们仍能在中国传统节日里看见花牌、彩灯、舞狮等扎作品的影子,可见节庆扎作是扎作行业中需求量最大,也最能代表华人传统的艺术品。而具有本土特色的扎作是观音诞中的重要元素,观音诞也是展示传统扎作品的平台,这便是论文以观音诞扎作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民间观音诞有四天:分别为农曆二月十九日的观音生辰、六月十九日的成道日、九月十九日的出家日及十一月十九日的成水神之日,而香港大型观音诞庆祝活动主要于农曆二月十九日及六月十九日进行,以及在农曆正月二十六进行「观音开库」。61 主办单位在节诞前都会认真筹备,准备各式扎作,以花炮、醒狮、麒麟与花牌较常见,都具有特别的寓意和造型。观音诞是扎作的载体,扎作也承载着善信们对未来的愿景,所以才会有人愿意代代传承,不过传承的过程必须面对时代更迭所带来的挑战。
第一节:观音信仰与观音诞的源始
历代研究观音的学者对观音信仰的本源提出了各种推测。综合造像、经籍、传说以及学者们的观点后,较合理的说法指出观音信仰的雏型应诞生于古印度的东南沿海地区,而其「救难」的形象则源自五百商人从「黑风海难」与「罗刹鬼难」中得救的传说。62 故事中,救人的主角从《增一阿含经》记载的「马王」,再到《佛说罗摩伽经》的「夜天」,都突出了观音「观世」、「救苦救难」的特质,后来《撰集百缘经》中救难的事迹与佛教结合,于是「救难」成为了佛陀的职能。63 据经籍所载:
有五百贾客,欲入大海採取珍宝。……值大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迴波黑风。时诸商人,各各跪拜诸天善神,无一感应救彼厄难。中有优婆塞,语商人言:「有佛世尊,常以大悲,昼夜六时,观察众生,护受苦厄,輙往度之。汝等咸当称彼佛名,或能来此,救我等命。」时诸商人,各共同时,称南无佛陀。尔时世尊,遥见商客极遇厄难,即放光明,照耀黑风,风寻消灭。64
这些文献中虽尚未具体提及「观世音」(梵语为Avalokitesvara),但在内容上初步塑造了观音的神格,作为观音信仰发展的萌芽期和舖垫。
及后,随着印度佛教体系日趋完善,救世之任从佛陀转移到菩萨身上,观音信仰逐渐开始成形。65 《妙法莲华经》中曾提及:「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66 以及其「辟支佛身」、「声闻身」、「梵王身」等33种应化身。再结合《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中「此大光明,是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入大阿鼻地狱之中为欲救度一切受大苦恼诸有情故。救彼苦已復入大城。救度一切饿鬼之苦。」、「圣马王者即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是」等对观音的描述,67 可见观音会观察世间的声音,能够为普渡众生而化为不同形态。同时,因为继承了传说中在海上「救苦救难」的神职,自此观音以「海上守护神」的身份于沿海地区广泛传扬,所以祂是除天后以外较受渔民重视的神祀。
有关印度观世音菩萨的原始性别,佛教主张「法无定相」,即救渡世人并无男女之分,所以观音为世人解难时绝不会囿于以男身或女身出现,佛教流行以前便有传观音原为畜身,形象源于「双马童」的说法,但坊间的观音形象以男身为主。68 《大方广佛华严经》及《愣严经》中虽有女身观音的记载,例如比丘尼、优婆夷,但《妙法莲华经》、《悲华经》及《华严经》等经籍大多都以「善男子」、「勇勐丈夫」等男性身份称呼祂,当中的《悲华经》在讲述其身世时更指出观音成为菩萨前为「转轮圣王太子不眴」,有贵族身份,可见在经籍中,男身为观音的主流形象。69
在造像方面,观音造像最早起于公元二世纪(101-200年)左右,呈现的形式为身着王族服饰、有短髭的「莲华手观音」,从生理特徵上凸显其为男性的身份。70 由以上两个元素可见,印度佛教较认可观音为男性,同时这也是人们后期把信仰具象化后,根据社会价值观赋予祂的。这是基于古印度对女性的歧视,认为女子是男子的附庸,所经历的磨难要比男子更多,因此被视为带有前世罪孽轮回的罪人,故观音高贵的菩萨之身不会以女子为形。71 于是,佛门中人在两种性别之间选择让观音以男身现世。
观音传入中国后,逐渐衍生出女身观音,也出现了不同的宗派:后世将其分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及「民间信仰」三种,各自呈现出较强的民族性与地域性,而观音信仰在宗教属性转化的过程中糅合了儒释道。72 东汉时期,安息僧安世高(生卒年不详)到访洛阳被视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开端,因为他开启了汉译佛教经籍的篇章,尤其是首次提及「观音」的《成具光明定意经》,这可能是人们第一次认识观音信仰。73
随着汉译的佛教经典日渐增多,观音信仰的渗透亦越趋深入,及至魏晋南北朝(220-589年)全面输入。74 两晋时期(265-420年),《正法华经》、《妙法莲华经》等经籍开始介绍观音不论阶级、普世救人和慈悲为怀的神性,并出现了莲花手观音造像及「西方三圣祖像」,为神情安详、蓄鬚的男身。75 及至南北朝(420-589年),相关的经籍与造像的种类增加,更详细地解释了观音能够解救现世受难的人和引渡亡灵到极乐世界的缘故,这让渴望在现实因政局动荡和战乱中得到救助的大众有了精神寄託,加上帝皇的支持,使观音信仰踏入兴盛期。76 在此期间,主张「身心修行」的密教也沿着西藏传入及发展,包括经咒、真言、法门、造像等内容,使「藏传佛教」逐渐成形,但中原观音信仰仍以「汉传佛教」作为蓝本,结合中国本土的社会和文化特徵进行演化,形成了不受教条限制的「民间观音信仰」,「女身观音」亦由此而生。77
据考古发现,莫高窟中南北朝的观音画像及造像展现很符合佛教经籍的中性形象,有利于观音信仰在男女之间流行,成为隋朝(581-618年)至宋朝观音女性化的前奏和基础,而唐朝为其中的关键时期。78 其所涉因素颇多:第一,武则天当政期间,女性地位提升,佛教僧人大肆宣扬其为「弥勒佛降世」,弥勒佛又与观音度化世人的属性相似,引导观音女性化的趋势;第二,中国古代长期处于「男尊女卑」及「母凭子贵」的思想环境下,女性遭受的苦难比男性更多,所以迫切地需要一个能象徵妇女群体的女神倾诉与解难,而观音有「送子」的神职,其神性与慈母的身份契合,所以观音以女相或女身呈现更符合社会价值观和需要;第三,唐朝的社会审美倾向于丰腴体态,所以出现了一部分带有女性特徵的观音画像与造像,例如水月观音像,其造像尚存于敦煌与莫高窟遗址。79
自宋代起,儒释道「三教合一」,使观音信仰中出现了道教及儒家的元素,渐趋世俗化。北宋期间(960-1127年),从唐代一直流传的「妙善公主」的故事在这一时期影响最广。故事记载着妙善公主因决意潜心修道而不愿出嫁,遭妙庄王贬谪,但在他身患恶疾,需要至亲的手眼才能治癒之际,妙善公主挺身而出割下手与眼。其孝举感动上天,于是被赐予千手千眼,成为「千手千眼观音」,从此她的生辰——农曆二月十九日被定为观音诞辰。80 这个故事中融合了道教修仙和儒家忠与孝的元素,观音当时更被纳入道教神祗,化为「泗州大圣信仰」。81 随着各类观音显灵的小说及传说出现,观音亦因着民众的生活需求被赋予了更多功能,如送子、招财、治病、消灾等,其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背景亦吸引了不少女信徒,直到观音信仰传入香港后仍然受女性崇拜,参与观音诞的女性众多。82 可见,中国神祀的形象是百姓生活和帝皇统治思想等方面的投射,观音信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观音信仰传入香港的时间及过程难以追溯,但水上人与客家族群应为主要推动者及参与者。首先,观音在印度时便是受渔民崇敬的神祗,其原始神职就是在海上救难,所以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依然会受水上人及航海的商客欢迎。宋代及后,往来经过观音信仰中心——普陀山的商客和渔民都会上岸向观音祈福后才继续行程或工作,因此他们很有可能把观音信仰带到经过或扺达的地点,这也能证明为何香港供奉观音的寺庙在沿海地区较密集,而且部分沿海地区更会大肆庆祝观音诞,例如白沙湾、大澳等。83 当中,白沙湾村会于农曆六月十九日的观音得道日举办观音诞庆典。主要目的是配合当地渔民的出海日程,错开新年前后和捕渔期,让他们在回港避风时再筹办活动。白沙湾观音诞最有独有的环节便是进行「焚烧大士王」的仪式,据称这是由于渔民在海上漂泊,常遇神鬼之事,因而需要通过道教仪式祈求观音驱散邪祟。84
另一观音信仰的集中地是客家族群居住的地区,他们也是传扬观音诞习俗的重要群体。客家人因战乱和天灾进行南迁时,带同能够庇佑自己的神祇到达香港等地,当中包括观音,所以部分客家村落会在农曆二月十九日举行观音诞庆典,进行抢花炮、舞麒麟等活动。85 所以,观音诞的仪式及扎作元素会具有族群或地方特色的。
第二节:观音诞扎作元素的发展
除此之外,观音诞扎作元素的多样性与观音的多重神格相关。因为观音传说及显灵故事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框架与版本,以致其原型一直难以有准确的定论。故观音虽然在根源上为佛教神祇,但后来糅合了道教和儒家的色彩,被人们赋予了不同的神性,形成香港民间流传的观音信仰。由于民闁信仰的规条限制较少,部分围村村民或渔民不会仔细区分佛教与道教观音,寺庙中亦会将两者同列,例如蕉径龙潭观音古庙。86 观音的形象也因而千变万化,除了前文的「千手千眼观音」,还有「送子观音」、「南海观音」等,祂们有各自的神职,以回应民众的诉求,部分更融入于花炮当中。87 神诞中所应用的扎作种类繁多,但花炮、花牌、醒狮和麒麟是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元素,故以下将集中分述这四项扎作元素。
花炮
花炮常在香港观音诞的「抢花炮」活动中出现,唯有关花炮的起源与传入香港的机遇缺乏文献的支持,难以考证。最早的记录称明朝景泰三年(1452年)三月初三的北帝诞,佛山祖庙前有「抢花炮」这一环节,可见花炮自明朝起便是神诞的传统元素。88 若从中外贸易的历史来看,香港神诞使用花炮的民俗从广东传入的可能性较大,因为香港自古便是来往广州的关口之一,中外商人补给站、交易点或转口港,加上清末民初广州炮竹商常经香港转销货品到新加坡、荷兰等国,1920年代末又有炮竹厂迁至香港,所以「抢花炮」的习俗或许是通过两地的商品贸易而传入香港的。89
在香港,花炮的种类与样式五花八门,香港历史博物馆曾概括过该扎作品的主要特徵:
花炮是用竹架和纸製成的流动神庙,内设供奉有神像的神龛,而花炮上挂满生薑、柏叶、灯笼、麒麟、龙及凤等寓意吉祥的製饰品,并饰有纸花及纸製的五虎将、紫微、八仙等神像,是神诞庆典时用酬神的纸扎供品。90
以上所列的装饰品各有寓意,花炮的形制也有不同,全凭扎作师傅配搭。
香港花炮大致分为小型花炮及大型花炮两种:小型花炮一般高4呎至20呎,大型花炮的高度达30呎至40呎,主要分为炮顶、炮身和炮趸三部分:炮顶会冠上花炮会名称,同时以蝙蝠或孔雀开屏的图纹作装饰,有富贵兴隆、驱邪的寓意及作用;炮身有1至8层不等,「不同尺寸的花炮有不同的比例,越高的花炮就越阔,不能不断加高,只加高的话花炮会太『瘦』,所以要一边加高一边加阔,即所谓『一阔三大』」91 ,同时伴有象徵「继后香灯」的灯笼、意指圆满的七彩鱼等吉祥物作装饰,也会摆放财神、紫薇神等各方神祇或粤剧英雄的塑像,观音神像则会被放置预留好的「炮胆」之上。92
花炮中,第一炮至第三炮为最受欢迎的花炮:据民众普遍的认知,第一炮为「财炮」、第二炮为「丁炮」和第三炮为最重要的「丁财炮」,所以它们的体积更大,装饰品更鲜艳。以2023年上水古洞村观音诞所列出的花炮为例,炮身放置了「南海观音」的神像,以祈求众人在疫情下都能平安渡过,部分挂上了生薑,代表该村落有人家添丁,其中「第一炮」的高度明显比其他花炮更高,较为醒目,代表最具意义的花炮。93 每年观音诞,扎作师傅会根据每一个花炮的主题自行搭配和设计,所以花炮的样式十分多变。
在活动形式方面,在早期的神诞期间,「抢花炮」是由主办方准备好竹籤、木片或挂上铁环的红绸球等代表花炮的物件,并标上不同的号码,然后用火药从竹筒中发射到空中,落地后众人开始抢夺,再按照夺得的编号领取纸扎花炮及对应的观音像回到各自村落供奉,于次年「还炮」。94 可惜因过往神诞举办「抢花炮」时屡次发生冲突及骚乱,尤以天后诞情况较严重,例如1983 年榕树湾天后诞的警民冲突、1984年南丫岛索罟湾天后诞掷石的溷乱等。95 为避免同类事件发生,加上政府于1967年起禁止民众存有烟花炮竹,抢花炮的形式开始以抽籤代替,一直沿用至今。96 2023年的古洞村观音诞「抽花炮」活动共有十个社区组识参与,包括古洞义和堂花炮会、蕉径联合堂花炮会等,聚集了不少围观市民,气氛热烈,为疫情缓和后的神诞活动「打响头炮」。活动过程中,各组织会轮流展示自己的花炮,参加者也会互相分享彼此近况,反映人们对生活满足与期盼,使花炮活动成为社区联谊的平台,增加社区凝聚力。97
狮头与麒麟头
狮头与麒麟头同为观音诞常备的扎作品,其样式、面貌五花八门,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意义。中国舞狮的传统可上溯至汉代。《汉书‧西域传下》提及文景之际「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勐犬、大雀之食羣于外囿。」98 这便是中国对狮子最早的记载。后来,有人模彷狮子的神态、动作舞动,北魏时期的一次候佛诞巡游便有人披上兽皮装成「辟邪师子」在队伍前引路。99 及至唐朝,舞狮变成礼乐元素。当时,有胡人随着丝绸之路到访中国,向中国皇帝描述了狮子的外形、特徵,其后工匠据此以纸製成彷真狮子,并聘用了杂技艺人进行舞狮表演。100 《通典‧乐六》所载的「太平乐」便描述了该活动的概况:
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挚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衣,象其俛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抃以从之,服饰皆作崑崙象。101
这便是「北狮」的由来。
舞狮流传到民间后随着中原移民的流动在南方衍生出另一种流派——「南狮」(亦称「醒狮」),当中又主要分为「佛山装」与「鹤山装」,前者为现时香港观音诞最常用的种类。102 五代十国(907-960年)及后,中原陷于乱局,加上后来蒙元入主当政,当地居民纷纷南迁避祸,把北狮文化带往岭南地区,衍生出南狮文化,以广东为中心进入萌芽期。103 及至明清时期,「以怪治怪」、「舞狮拜年」和「食青反清」的传说出现,民间开始在重大节日以舞狮辟邪和助庆,狮头扎作行业随之被带动。104 上文所提及的佛山,正是南狮扎作流行的地区之一,现时的香港狮头扎作也大多来自该地,而香港本地相关的店舖则只有零丁数家。105
有关麒麟的历史,甲骨文上曾记录着当时在战争中擒获的「白麟」,证明麒麟文化从殷商时期(前1600-前1046年)便已开始。106 《史记》曾记载孔子看见被捕获的麒麟后感叹「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107 ,既是表示自己不久于人世,也是在暗示盛世不再。自此,麒麟成为了天下太平的象徵,并衍生出各种麒麟的图腾与辟邪的凋像,不过一直未见有相关的拟兽作品出现。108
直到唐朝,宫廷中出现了让驴模彷麒麟的游戏:「今餔乐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复之驴上」109 ,这是麒麟首次具象地出现在人们眼前。此后,再次出现模彷麒麟的活动可能是明朝皇室的「麒麟圣舞」,这个宫廷仪式在明朝灭亡后被管理文娱活动的官员带到民间,广为传授,后来掌握技艺的客家人在南迁时将这门手艺带到深圳及香港,于是在节诞舞麒麟成为了他们的习俗。110 民国时期,麒麟扎作技艺开始定型,因为当时的麒麟是「以纸煳麒麟头,画五彩」再「缝锦被为麟身」,最贴近现代客家麒麟的形态。111 从舞狮与舞麒麟的历史源流可见,扎作的发展历程反映族群迁徙及社会变迁的轨迹。
狮头扎作的步骤分为扎作、扑纸、写色和装饰:先以竹蔑、铁线、胶篾及浆煳扎成醒狮的轮廓及框架,即行内所称的「囊」,然后依次从狮头背部裹上纱纸和绸绢,再为狮头着色和加上花纹,并「上光油」,色彩主要按照所代表的角色搭配:例如黄底五彩纹的刘备狮、红底黑纹的关羽狮、以黑白为主调的张飞狮、绿底黑纹的赵云狮等等,最后把眼珠、狮口、狮耳等配件装上,才算是完成了整个狮头扎作。112 麒麟头扎作与狮头扎作的流程相似,其中以「施彩」最考验扎作师傅的创意与色彩搭配技巧,例如调色、撞色等,但普遍较常用浅色作底色,例如白色、淡黄色等,从而突出彩色的花纹,而如果用红色、紫色等较艳丽的颜色作主色,就要考虑以「撞色」来凸显麒麟头上的彩花,以描绘麒麟的神韵。113 2023年古洞村观音诞期间,便有刘备狮、关羽狮等舞狮亮相,而麒麟有白底彩花的,也有黑色与黄色作配搭的。114
舞狮与舞麒麟一直是节庆期间的传统项目,因为「狮」本身具有驱邪降福的能力,所以人们总希望以其祈求消灾除害、求吉纳福,这对于出海作业又要面对诸多变数的水上人而言十分重要。115 而麒麟除了是客家文化的象徵,其本身也是化解煞气的瑞兽,是太平盛世的象徵,所以观音诞会以舞麒麟作为人们对平安生活的盼望。116 它们能够衬托出节日气氛,也可以凸显水上人的生活与客家文化的独特性。
花牌
对于花牌的由来,坊间有诸多猜测:一则指其为节庆筹办者按照中式牌楼的模式扎成的活动出入口,二则指出这是彷照宫廷吉祥装饰创造出来,让活动顺利举办的工艺品。117 而就现时花牌的应用情况来看,两者皆有可能:因为现时大部分节庆活动的花牌都摆放于出入口处,以及在内场进行排佈,并附上吉祥的图纹与祝福语。蔡荣基师傅曾提及香港花牌最早约见于百年前,「当时的楼房大多只有一层,挂一个花牌上去,等同高了一倍,鹤立鸡群,宣传效果卓越」,它们起初会以鲜花及纸花作为材料的一部分,其中文字也是以手写字为主。118 香港的花牌扎作从四十年代开始便已经被用于各类场所,例如诞辰和店舖开业典礼。119 五、六十年代始,花牌日渐开始流行于婚礼、节庆等各种喜庆的场合,然后在七十年代踏入黄金时代,当时业内有逾一千名工人,「熟手工人」月薪可达400多元,「普通工人」则能月入300多元,即使是初始学师的工人每月也有150元作工资,可见当时花牌扎作行业的盛况。120
花牌「以竹及竹籤为支架,配以真花或假花、各式纸类及布料作装饰,用于红白二事如节庆、婚礼、开幕、丧礼等」121 ,是香港常见的扎作品,也是观音诞会出现的必需品,其中的形制和文字都值得探讨。近代花牌的形制没有太多限制,但讲求平行、对称,牌身可达20至30呎,主要以「凤顶」、「锑花」、「珠」、「龙柱」、「兜肚」、「四方包」和「长」构成,由师傅按照场地空间进行排列。122 功能上,观音诞花牌有宣传、指引和祈福的作用,例如2023年古洞村观音诞村口有花牌指示「早上十一时前往蕉径龙谭古庙进香」,让参与者了解活动流程。123 内容上,观音诞花牌大多会写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酬谢神恩等吉祥的祝福和对观音表示感恩的话语,以及赠送花牌的社会组织和製作花牌的机构。花牌上能够表示各个组织对观音诞的敬贺,与他们对观音的敬仰及感激。
第三节:传承扎作技艺的挑战
随着时代更迭,社会的新兴事物层出不穷,人们的消费欲望日益增长,所以大多年轻人会倾向选择高薪及稳定的工作。传统节庆的参与者也主要集中于中老年人或固定族群,加上新一代缺乏对传统事物的了解,对传统节庆活动提不起兴趣。因此,大众对观音诞扎作的关注度不足及尚未明朗的就业前景就是传承观音诞传统扎作品的挑战。
观音诞扎作的传承与民众对扎作行业的刻划印象和对传统节庆的热情减退有很大关係。人们每每看见扎作舖,难免联想到清明节、重阳节、盂兰节等与鬼神和祭祀相关,令人心生忌讳的节日,长此以往使人们对扎作行业望而却步。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其一是历史遗留问题,其二是新一代仍缺乏更直接的平台接触该项工艺。在以往的记载中,扎作品更多是作为祭品或陪葬品出现,节庆扎作也主要以中秋节及七夕节中的花灯为主,甚少提及花炮和花牌。124
而且,近代年轻人对西方节日的热情比中国传统节庆,导致不少节日仪式被精简,例如古时的七夕节有花灯把玩,但现代情侣却大多更愿意在西方的情人节期间互赠礼物,可见西方的节日比传统节日的吸引力更大,所以他们对观音诞的了解不会太深入。在仪式方面,观音诞的仪式看似一直被完整地保留,但碍于安全问题,「抢花炮」的仪式以较温和的抽籤代替发射炮竹。125 当然,适当地跟随社会需要改变活动形式能够令传统文化延续,但往昔热烈的气氛却再难重现。
此外,扎作行业的就业前景与金融业、医护业等主流行业相比,较为迷茫。从业人士一般须经过数年的「学徒制」,待师傅退休再接手经营,学习的年期较长。过去,物价平稳,市民物欲较低,求职不会预先考虑职业前景,有收入便已足够。然而,时移势易,行业的薪酬、未来发展和稳定性都成为吸引年轻人入行的关键。而且,他们期望在工作中得到满足感,但每一个扎作品的製作流程都是漫长的,只有成品出现后才能获得一刻的成功感,及不上即时的回报。而对于从业人士而言,他们虽然乐于培养下一代传承人,亦频频在校园推广扎作技艺,但真正投身行业的年轻人似乎仍然不多。
至于有关市区城市发展会否压缩了扎作技艺生存空间的问题,冒师傅指出不论新界还是市区,只要传统节庆依然存在,就会有扎作品的出现。126 因此,观音诞扎作的传承主要是先提高年轻人的兴趣,持续地进行文字记录,扩大扎作品的应用层面,才能使其在节日与祭礼之外出现在大众视野,吸引人们关注。只是,民间的力量始终较单薄,所以政府的支援十分重要。127
观音诞扎作历史悠久,是水上人与客家人的生活投影,具有文化价值,因而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观音诞」与「扎作技艺」在清单中虽然分属于「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及「传统手工艺」,但能够互为彼此的载体。纳入清单后,民众可以通过官方平台系统地知悉现存的传统文化习俗,不少民间团体亦开始从不同的渠道推广观音诞及相关扎作,其形制也为了适应时代变迁在保留传统底蕴的前提下进行材料和呈现形式的创新。
第一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及非遗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同时将其划分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及「传统手工艺」五大类别,以便系统地管理与保护,即进行「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各国纷纷响应加入。128
2006年,香港紧随世界步伐应用《公约》内的条款,于香港文化博物馆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组」,该组织后于2015年被升格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于次年在三栋屋博物馆设立「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129 民政事务局亦于2008年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谘询委员会」(或称「非遗谘委会」)督导非遗之普查及保护事宜,下设「非遗资助计划委员会」及「非遗项目委员会」分别负责各非遗项目的运行及非遗清单的研究、出版和更新。130 机构组织上的改变使香港对非遗项目的管理和保育逐渐成熟及系统化,为本土传统文化提供有利的发展空间。
为尽量完整地保留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民政事务局在非遗谘委会成立之初便提议编製清单,特此将本港调查地区划分为「普查范围A(A区)」及「普查范围B(B区)」,开展「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131 经公开招标后,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分别于2009年8月及2010年2月开始B区与A区的调查工作,分为「文献资料搜集」和「实地考察和口述历史调查」两个部分进行,从各机构之文字记录、档案、视像资料与实地田野研究考察本土传统的流传情况。132 及至2013年,研究中心整理出约800个项目的资料呈交至非遗谘委会,再经历该委员会之审议及为期4 个月的公众谘询,最终统整为「首份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共囊括480个非遗项目,上水蕉径、白沙湾与大澳的「观音诞」也在其列。133 当中,包括「扎作技艺」在内的20个「具有高文化价值和急需保存的项目」更于2016年被非遗谘委会推荐纳入「首份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最后于2017年8月14日确定公布。134
2018年,非遗办事处获批3亿元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协助传承人及传承团体进行「社区主导项目」与「伙伴合作项目」,同时建立「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加强对非遗的保护和普及。135 清单与名录之订立使政府能够针对及有序地就各个项目制定保育计划,争取各界财政及人力资源的支持,以确保本土文化不会在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中被淘汰或流失。资料库成立至今已录入「狮头扎作技艺」、「花牌扎作技艺」、「舞狮」、「舞麒麟」等与观音诞相关的节庆扎作与活动,观音诞与花炮扎作虽暂未被收录于资料库与国家级非遗,不过这并不代表其文化与历史价值逊色于其他项目。因为前者是客家人与水上人的文化标誌,而后者作为扎作品之一支撑着整个神诞仪式的推进,甚至「支持整个民族的生活」136 。
香港非遗项目在保育时可以获得更多社会和政府资源,维持相关商舖的营运和进行民间推广计划,取得公众关注,而是次论文中所提及的两个主体作为官方保护的首要目标自然也会受益,但也难免受疫情影响。
第二节: 疫情下的观音诞庆典
2019年,新冠病毒肆虐,不少大型节庆活动的仪式被简化,甚至被取消,节日安排难以确定,观音诞亦同样受到波及。在2020至2022年间,白沙湾观音诞只在2021年举办了「八仙贺寿」的演出,其他活动环节均被取消,但观音古庙仍遵照防疫规例有限度地开放,供信众进香。137 上水古洞村则透过保留观音诞特色神诞活动,继续庆祝观音诞,例如舞麒麟、抢花炮等,亦有扎作花牌以作宣传,唯这一段时期的记录片段显示参与情况不及疫情以前热闹。138 时至2023年,古洞村首先大肆復办观音诞庆典,吸引大批群众参与,往昔盛况才得以重现。139 可见,基于防疫条款下的种种限制,疫情对观音诞期间的大型庆祝活动影响颇深,亦令所须的扎作品大大减少。
观音诞庆贺仪式的简化非单单削弱过往浓厚节日氛围,还会使观音诞扎作的普及度大大减弱,可能会影响其传承的进程。首先,神诞活动是巩固观音信仰的重要渠道。有传统信仰的民众会根据神明的威力和其所给予的回报而对该神明有不同程度的责任感和依赖,故此对于不同神诞的参与度各异。140 在参与度与筹办情况方面,从以上情况分析,客家人似乎更重视观音诞,所以即使在疫情下仍然极大程度地保留了大部分扎作元素及传统活动,维繫着族群独特的人文精神。因此,为了让其变成家族或族群内代代相传的信仰,借助神诞活动巩固及延续该信仰,增强善信对自己身份认同是必要的。
其次,文化的传承需要延续性,一旦出现停顿,便可能会出现许多变数,观音诞的传统礼俗便是例子之一。以「抢花炮」为例,邓家宙博士曾在接受访问时指出:「此文化习俗在疫情下面临沉重打击,年长者感心淡,少数弟子无法维生被迫转行」,并对復办后规模萎缩及停办成为常态的可能性表示担忧,认为需要新一代及时以文字配合现存的建筑进行记录。141
不过,观音诞既是流传多年的传统节日,理应不会轻易就此停办。加上,疫情期间,民间组织及历史机构均有进行出版或举行相关活动,持续向公众普及观音诞的资讯。出版方面,《观心自在:香港观音诞与观音信仰探源》十分具代表性,因为它详细向大众介绍了观音信仰的由来、观音的种类、香港观音信的流传情况等资讯,并于第一届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中得奬。142 活动方面,「香港节庆与民间工艺」专题展览在疫情期间间接为大众提供了关于观音诞扎作品特点与源流的资料。143 香港佛教联合会与香港菩提学会依然坚持举办「观音文化节」,按照不同的主题为大众提供了关于观音信仰的信息,让他们明白观音文化的社会价值。这些都成为了传承观音诞及其扎作的关键。
第三节:观音诞扎作的创新
对传统扎作品进行创新也是振兴和保护花炮、狮头、麒麟头、花牌等观音诞扎作的关键。这与扎作师傅的经营理念和风格息息相关,他们所製作的扎作品在色彩、配饰和形制方面都各有千秋,所以更新的元素也是因人而异。另外,扎作品的改变也须顺应各族群的喜好及环境,导致其中所运用的材料与从前的作品大相迳庭,使这项技艺得以在现代社会继续存活。
上文曾提及有鑑于「抢花炮」的危险性,现时的观音诞改以「抽花炮」的形式继续,这是基于社会安全的顾虑。除了活动形式上的变化,花炮的形态自传入香港后便形成了本土特色。由于其所应用的场合主要是神诞庆祝,所以往往会以精美作为製作标准,成品也以大型花炮为主,装饰元素基本上没有太多变化,一直沿用传统的吉祥物。不过,花炮供应源头和製作地点却不断变迁:扎作业的全盛时期,香港扎作店皆会亲力亲为承包花炮的製作,但后来这一门手艺随着工厂和人手迁移至内地,加上在城市发展下,扎作师傅要寻找合适店舖落地生根实属不易,冒卓祺师傅也曾面临此困扰,于是他「先是在街市置舖,但经常收到投诉;其后搬到屯门工厂区,又因搬运不便,最后搬迁到元朗白沙村」。144 至于花炮扎作是否最终会没落,应视乎其本身的民俗价值:只要观音诞仍然保留「抽花炮」的习俗,花炮便不会流失。
至八十年代始,狮头便一直革新,务求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使其形象更生动、更轻巧。过去,香港的狮头扎作沿用中国传统的样式,以历史人物作为创作原型,狮头以雄壮威勐的色调和造型为主,但后来却被形象温和、价廉、轻便、款式多样的马拉狮取代了其主流地位,导致本地狮头扎作在此期间沉寂。145 于是,如何吸引大众订购及欣赏香港狮头扎作便成为各狮头扎作师傅的首要考虑。
因此,新一代传承人不再固守旧有的框架,从颜色和展示形式开始革新,令传统狮头扎作能够有更高的曝光率。以许嘉雄师傅为例,他对于狮头扎作有较新颖的理解:
舞狮过去只允许男性参与,传统认为属于女性的颜色,如粉红色或紫色是不会用于狮头上,但随着舞狮由武馆独有文化变为大众运动,现在甚至会出现水晶狮和Hip Hop狮等合作,现在的狮头创作可以说是没有限制的。146
狮头不但能够与流行元素结合,有时还可以与时装设计相融合,例如2020年《匠艺古今》展览中的展品——「再世卢亭」便是以香港独有的神话人物卢亭为基础,结合传统又具威严的狮头和富有现代美感的鱼尾製成,鱼尾的每一部分都能在拆分后装扮到身上,传统与犘登的碰撞赋予了狮头扎作新的生命。147 而麒麟头则在不改变外形与神兽特徵的前提下,从颜料、图案、原材料等方面作出适当调整,例如以广告彩代替瓷漆、利用机器生产沙纸等,从而丰富及加固扎作品,使其製作程序更有弹性。148
至于花牌的创新,则主要集中在其呎吋和材料。「李炎记」花店的学徒针曾就当今社会重视效率的现象和缩窄的城市空间,提出了许多花牌的改良之处:例如花牌上的棉花字和手写字可改由电脑打印、製作可放置于室内的小型花牌。149 除此以外,过往花牌上的真花及纸花都改以锑花,灯饰也以亮度较高和较环保的「LED灯」取代钨丝灯泡。150
传统大型花牌常出现于节日期间,年轻人在日常实在难以接触,但若结合文学及视觉艺术的元素举办校内活动,吸引学生参与,便可以提升他们对传统花牌扎作的兴趣。圣士提及书院的学生曾在「南区文学径:创意写作及花牌创作计划」中与黄乃忠师傅学习扎作工艺,其后在花牌中加入西洋技法画成的白鸽与梅花,使作品成为中西合璧的新花牌。151 这些改变其实都是为让传统节庆扎作在不改变其风貌前提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更好地代代相传。
本论文讨论香港扎作与传统节庆文化的研究,并以观音诞扎作为个案,通过讲述扎作技艺与观音信仰的缘起、传入香港的契机、文化意义、公众重视程度及创新之处,藉此突出观音诞扎作的传承与保育价值。
本论文以书籍、文章、报章等各类资料记述观音诞扎作的历史进程。在讲述香港扎作技艺发展过程的部分运用了不少报章,如援引〈访问扎作工人〉、〈扎作工友注重技术〉等篇章,以当时的报导直观地证明扎作行业曾为香港的重要产业之一。在专书及文章方面,笔者在敍述观音信仰的历史时着重使用了李利安教授的《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中国观音信仰的基本体系〉等着述。在提及观音从「男身」到「女身」的转变时引用了《中国观音史》、〈观音形象在汉地女身化的途径与原由〉等资料。在历史记录与前人研究中,观音诞和扎作技艺鲜有被同时提及,即使有记录也只粗略介绍,未有强调两者的联繫。但整合这些片段后,其实不难发现观音诞一直是中国传统节庆扎作的展示平台之一,而扎作品也是观音诞的文化符号。
本论文首先追溯中国传统扎作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传入香港后的发展,指出中国传统节庆与扎作技艺密不可分的关係。文中提及扎作的出现可能并非是为祭祀或庆典,而是基于古人对军事通讯的需求,但真正让扎作进入兴盛期的是传统节日。因为人们为营造节日气氛创作的「灯山」、「佛山大爆」等扎作品受人欢迎,感染力更强。所以,即使香港社会和经济结构不断变更,扎作行业也不曾被淘汰。
而后,本论文从观音信仰的流传及香港观音诞扎作的特点出发,指出节庆扎作是社会结构与百姓生活变迁的象徵。正如观音男身与女身的变换是为了适应社会男女对生活的诉求,同时对于女性统治者而言,女身观音是对政治地位的认可。到了香港,观音诞展现出较强的地域性,每个族群庆祝观音诞都有一定差别,例如水上人会焚烧大士王、客家人会舞麒麟等,过程中所使用的扎作品都是族群的文化符号,难以取代,这也是观音诞扎作的研究意义所在。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及宣传扎作技艺与观音诞,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香港佛教联会、香港菩提学会等相关机构都在疫情期间坚持向公众发佈相关资源。扎作师傅亦与时并进,在材质、式样、工具等方面寻求创新,继而使扎作技艺吸引更多年轻人注意。
总括而言,观音诞扎作种类繁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节庆扎作品。虽然该研究尚未能尽述,只能集中以花炮、狮头、麒麟头与花牌作为诸多扎作中的代表,但足以说明观音诞对扎作技艺传承的重要性。而这些扎作品背后代表的不止是中国传统工艺的延续,更是从古到今人们生活的印记,十分值得世人持续关注。
附录一:香港观音诞期间女信众参拜之盛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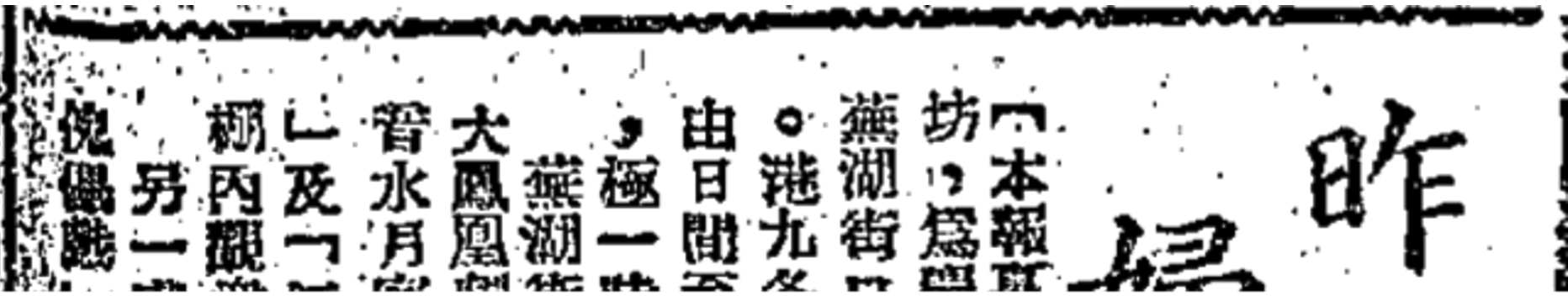
附录二:香港扎作业联会主席冒卓祺先生访问
受访者:冒卓祺先生(香港扎作业联会主席、扎作店「祺麟店」创办人)
访问日期:2023年3月10日
访问时间:下午2时30分至下午2时40分
访问地点:上水古洞村
访问纪录:
1. 麒麟扎作一般流程会包括扎骨架、贴纱纸、施彩等等,师傅过去探访曾提到施彩的部分会花较心思,可不可以详细介绍一下传统麒麟施彩有甚麽注意事项,例如传统上约定俗成的配色?
麒麟一般以白色、淡黄色、绿色等浅色为主。有部分师傅会用红色,但这三种颜色运用得较多。例如白底是浅色,画甚麽、画任何色都可以上色,色彩便能被显现出来。因为是白色打底,「画七彩就有七种颜色」,但如果是红色打底便少了红色,要考虑撞色。
2. 白沙湾在观音诞期间有「焚烧大士王」的仪式,但古洞村却没有,原因为何?
因为那里(白沙湾)有一个道教仪式,会请喃呒进行。例如明天观音诞,今天就请喃呒师傅前来诵经、超幽。因为水上人生活在海边,可能「灵异」事件或故事较多,他们亦「很相信」神鬼之事,所以趁着观音诞的大日子请喃呒师傅前来诵经、超幽。
3. 扎作在新界一带的生存机会是否比市区更多?具体的原因为何(例如历史因素、市区城市空间狭窄等等)?
不是。因为扎作任何中式节日,任何宗教节日,或喜庆节日,又或康文署、非遗办事处举办的年宵、中秋活动都会被使用,不一定新界才会更多。
4. 传统节庆的存在是否能够让扎作技艺一直被社会需要?除传统节日和丧葬外,扎作是否还有其他展示的平台?
这个问题要视乎从业员或师傅如何看待自己的手艺和非遗项目。这些事件「很个人」,没有规定扎作有(展示的平台)后其他项目就能有(展示的平台)。这个首先需要政府部门的配合,其次是传承人的个人想法。
5. 扎作技艺被列入非遗后是否对推广及传承扎作技艺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具体例子为何?
扎作技艺被列入非遗后的确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首先是让更多人重视、关注及认识,因为有官方部门用文字,用书写的方法介绍这一种文化。我们只能讲述与分享製作方法、习惯,至于撰写文章,以文字教授这些文化则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或学术机构去做会较理想。因为我们只是分享自己的经验,但要编辑成文字,翻译成各种语言,让更多人认识香港扎作要依靠多个部门的配合,单单依靠我们是不足够的。
附录三:蕉径龙潭观音古庙内的各式观音造像
资料来源:笔者摄于2023年3月10日实地考察。
附录四:2023年上水古洞村观音诞花炮
资料来源:笔者摄于2023年3月10日实地考察。
附录五:2023年上水古洞村观音诞「抽花炮」仪式
资料来源:笔者摄于2023年3月10日实地考察。
附录六:2023年上水古洞村观音诞舞狮
资料来源:笔者摄于2023年3月10日实地考察。
附录七:2023年上水古洞村观音诞麒麟头扎作

附录八:2023年上水古洞村观音诞花牌
资料来源:笔者摄于2023年3月10日实地考察。
附录九:2023年上水古洞村观音诞盛况
资料来源:笔者摄于2023年3月10日实地考察。
中文资料
政府档案:
1.〈CB(2)1090/08-09(01)号——全港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2009年3月20日资料文件。
2.〈CB(2)1448/17-18(01)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博物馆措施提供资助〉,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2018年5月28日讨论文件。
3.〈CB(2)842/16-17(01)号——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草拟名单〉,民政事务委员会2017年2月27日讨论文件。
4.〈CB(2)855/16-17(06)号——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草拟名单〉,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2017年2月27日的会议。
5.〈CB(2)957/10-11(03)号——全港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进度报告〉,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2011年2月11日资料文件。
6.〈首份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828638/First_hkich_inventory_C.pdf,浏览日期:2023年1月13日。
7.〈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the_representative_list_of_hkich.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3日。
8.〈第8067号公告——职工会条例(第332章)〉,职工会登记局2008年11月12日公告。
古籍:
9.[汉]班固,许东方校订:《汉书》。台北:宏业书局有限公司,1992。
10.[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1970。
11.[西秦]沙门圣坚译:《佛说罗摩伽经》。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21。
12.[北魏]杨衒之,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3.[北魏]昙无谶:《悲华经》。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8。
14.[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21。
15.[唐]杜佑,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全1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6。
16.[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
17.[宋]天息灾译:《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上海:佛学书局,1935。
18.[宋]吴自牧:《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9.[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0.[宋]高承撰,[明]李果订:《事物纪原》。北京:中华书局,1989。
21.[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
22.[清]曼陀罗室主人:《观音菩萨的故事》。西安:陝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3.[民国]陈伯陶:《东莞县誌》。台北:成文出版社,1912。
书籍:
24.于君方着,陈怀宇、姚崇新、林佩茔译:《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5.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8。
26.元建邦编:《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27.王国华主编,何佩然、彭淑敏等着:《香港文化导论》。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
28.司徒嫣然:《市影匠心:香港传统行业及工艺》。香港:香港市政局,1996。
29.弘学编:《妙法莲华经》。成都:巴蜀书社,2002。
30.石守谦、颜娟英主编:《艺术史中的汉晋与唐宋之变》。台北: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31.吴燕:《中国观音文化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32.李利安:《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33.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4.周子峰:《葬之以礼:香港殡仪文化初探》。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0。
35.施志明:《本土论俗——新界华人传统风俗》。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
36.徐艺乙:《风筝史话》。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2。
37.秦宏:《香港工业设计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2。
38.高宝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香港》。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
39.张一兵点校:《深圳旧志三种》。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
40.陈子安:《渔村变奏:庙宇、节日与筲箕湾地区历史(1872-2016)》。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
41.陈守仁:《香港神功戏》。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
42.陈桂洲:《扎作:承‧传》。香港:鼎丰文库,2007。
43.超媒体编辑部:《香港狮艺传奇》。香港:超媒体出版有限公司,2015。
44.黄竞聪:《城西溯古——西营盘的历变》。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2。
45.黄竞聪:《简明香港华人风俗史》。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
46.叶春生:《广府民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47.刘继尧、袁展聪:《武舞民间——香港客家麒麟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8。
48.蔡志祥、韦锦新编:《延续与变革:香港社区建醮传统的民族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
49.蔡志祥:《酬神与超幽:节日和香港的地域社会》。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
50.卢维干:《大慈大悲观世音》。香港:华人庙宇委员会,2016。
51.霍松林、赵望秦主编:《宋本史记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52.骆慧瑛:《观心自在:香港观音诞与观音信仰探源》。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20。
53.关宏:《佛山彩灯》。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54.StellaSo:《粉末都市——消失中的香港(增订版)》。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
期刊:
55.王敏:〈菩萨造像的中性化与观音造像的女性化〉,《民族艺术》3期(2011年8月),页125-127。
56.朱光磊:〈观音形象在汉地女身化的途径与原由〉,《世界宗教文化》6期(2016年12月),页67-70。
57.李利安:〈中国观音信仰的基本体系〉,《人间佛教》34期(2021年7月),页68-79。
58.李志清:〈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乡土社会的存在意义(三)——族际交往中的抢花炮〉,《体育科研》27卷6期(2006年11月),页10-18。
59.李欣:〈中土观音女性化成因别释——兼议汉文明「乾坤并建」之教化原则〉,《世界宗教文化》6期(2016年12月),页71-77。
60.李红:〈佛山彩灯传承和创新的若干思考〉,《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37卷4期(2022年7月),页1-9。
61.邢金善:〈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麒麟舞的传承与发展〉,《山东体育学院学报》3期(2011年3月),页44-47。
62.侯坤宏:〈观音信仰的流传与衍化〉,《人间佛教》10期(2017年7月),页14-41。
63.梁正君:〈广州陈氏书院建筑装饰工艺中的吉祥文化〉,《岭南文史》2期(2003年6月),页7-11。
64.温金玉:〈观音菩萨与女性〉,《中华文化论坛》4期(1996年10月),页86-91。
65.冯诗淇:〈浅析南狮运动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变化——以舞剧《南狮梦》为例〉,《艺术评鉴》5期(2019年3月),页65-66。
66.黄慧莹:〈广东醒狮发展沿革及其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传承》12期(2013年10月),页136-137。
67.刘钊:〈「小臣牆刻辞」新释——揭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復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期(2009年1月),页4-11。
68.薛源、王雨璿、陈杨梅、陈浩:〈传统南狮的流派及其运动特点研究〉,《科技资讯》22期(2021年11月),页177-180、183。
硕士学位论文:
69.周萍:〈东莞市清溪镇客家麒麟舞的传承与保护〉(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70.姜喜平:〈「南狮」历史文化与发展现状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71.刘婕:〈近代省港烟花爆竹贸易研究(1859-1948)——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为中心〉(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报章:
72.〈元宵花灯上市扎作工友开夜工〉,《华侨日报》,1960年2月9日。
73.〈扎作工会定期成立〉,《华侨日报》,1949年3月18日。
74.〈各界隆重庆祝孔圣诞辰永安街悬花牌庆贺〉,《华侨日报》,1947年8月27日。
75.〈油牛洋烛扎作工人要求加薪〉,《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11月13日。
76.〈花牌扎作旺〉,《华侨日报》,1969年8月1日。
77.〈花牌扎作保留传统尝试求变〉(2016年12月31日),《大公网》,http://www.takungpao.com.hk/culture/text/2016/1231/50014.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6日。
78.〈花牌扎作就业工人增加年假告满工作復趋繁忙〉,《华侨日报》,1969年2月21日。
79.〈南丫岛索罟湾庆祝天后诞抢花炮滋事份子捣乱掷石击伤多人〉,《华侨日报》,1984年5月19日。
80.〈昨日观音诞妇女进香狂〉,《工商晚报》,1951年3月27日。
81.〈秋节节品实销结算〉,《华侨日报》,1959年9月19日。
82.〈纸扎业公所成立纪〉,《申报》,1920年8月23日。
83.〈纸料扎作工友开始加时工作〉,《华侨日报》,1970年2月9日。
84.〈纸料扎作情形特殊亦工亦商半劳半资〉,《华侨日报》,1975年5月6日。
85.〈酒楼喜庆宴会特多花牌扎作工作转旺〉,《华侨日报》,1970年1月30日。
86.〈扎作工友注重技术〉,《华侨日报》,1960年1月31日。
87.〈访问扎作工人〉,《华侨日报》,1957年7月14日。
88.〈港九各区街坊居民筹祝双十大典〉,《华侨日报》,1951年10月8日。
89.〈华商总会一番新气象〉,《工商晚报》,1948年7月16日。
90.〈华达公司製十馀丈蜈蚣〉,《华侨日报》,1956年5月19日。
91.〈传统花牌展现文学情怀〉,《经济日报》,2012年4月13日。
92.〈榕树湾祝天后诞抢花炮警民冲突三名村民头破血流〉,《香港工商日报》,1983年5月6日。
93.〈庆祝加冕会景巡游筹委会委员亲出募经费〉,《华侨日报》,1953年4月19日。
94.佚名:〈一竹一纸传统再现〉(2019年9月8日),《政府新闻网》,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9/20190906/20190906_145115_745.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4日。
95.宋霖铃:〈创新传统狮头鱼尾两代扎作人合璧再世卢亭〉(2020年6月3日),《明报新闻网》,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9%AF%E5%88%8A/article/20200603/s00005/1591123562926/%E5%89%B5%E6%96%B0%E5%82%B3%E7%B5%B1-%E7%8D%85%E9%A0%AD%E9%AD%9A%E5%B0%BE-%E5%85%A9%E4%BB%A3%E7%B4%AE%E4%BD%9C%E4%BA%BA-%E5%90%88%E7%92%A7%E5%86%8D%E4%B8%96%E7%9B%A7%E4%BA%AD,浏览日期:2023年1月16日。
96.许宣白:〈「抢花炮」停办两载 百年传统渐凋零〉(2021年5月6日),《文汇网》,https://www.wenweipo.com/s/202105/06/AP60933f80e4b0476859ba5381.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5日。
97.郭玉桔:〈港首间扎作展示馆〉(2019年12月16日),《香港商报网》,https://www.hkcd.com/content/2019-12/16/content_1169938.html,浏览日期:2022年10月14日。
98.曾莲:〈孝子承父业精益求精传扬花牌工艺〉(2019年2月13日),《大纪元时报》,https://hk.epochtimes.com/news/2019-02-13/36644627,浏览日期:2023年1月16日。
99.蒋琳:〈记载社区变迁传承扎作工艺元朗举办历史图片与花炮展〉(2017年6月29日),《香港商报网》,https://www.hkcd.com/newsTopic_content.php?id=1054917,浏览日期:2023年1月16日。
网上资料:
100.〈【传统之美:花炮传情】〉,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watch/?ref=external&v=1734459783367447,浏览日期:2022年12月28日。
101.〈古洞村-1953恭祝观音宝诞酧神演戏委员会〉,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kttkyc?locale=zh_HK,浏览日期:2023年1月14日。
102.〈白沙湾观音诞〉,香港记忆,=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local_festivals/festivals/lunar6/6_2/index_cht.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3日。
103.〈西贡白沙湾观音古庙〉,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8%A5%BF%E8%B2%A2%E7%99%BD%E6%B2%99%E7%81%A3%E8%A7%80%E9%9F%B3%E5%8F%A4%E5%BB%9F/100064936624023/,浏览日期:2023年1月14日。
104.〈花炮及其装饰元素〉,香港记忆,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tin_hau/TinHau_Flower/index_cht.html,浏览日期:2022年12月28日。
105.〈花牌扎作〉,传耆,https://www.eldage.com/collections/%E8%8A%B1%E7%89%8C%E7%B4%AE%E4%BD%9C,浏览日期:2022年12月29日。
106.〈佛山忠义乡志〉,中国国家图书馆,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403&bid=69082.0,浏览日期:2022年12月12日。
107.〈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ich_funding_scheme_introduction.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4日。
108.〈非物质文化遗产谘询委员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ich_advisory_committee.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3日。
109.〈非遗项目─扎作技艺〉,赛马会「传‧创」非遗教育计划,https://ichplus.org.hk/tc/ich/project/paper-crafting-technique,浏览日期:2023年1月12日。
110.〈甚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what_is_intangible_cultural_heritage.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2日。
111.〈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https://hkheritage.hkust.edu.hk/,浏览日期:2023年1月13日。
112.〈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hkichdb.gov.hk/zht/index.html,浏览日期:2022年12月12日。
11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32540_chi/PDF/132540chi.pdf.multi,浏览日期:2023年1月12日。
114.〈扎作小知识(舞狮龙头篇)〉,香港电台,https://www.rthk.hk/chiculture/bamboocraft/c2_tips.htm,浏览日期:2023年1月16日。
115.〈扎作与文化(舞狮龙头篇)〉,香港电台网站,https://www.rthk.hk/chiculture/bamboocraft/c2_culture.htm,浏览日期:2022年12月29日。
116.〈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https://www.ihchina.cn/project.html,浏览日期:2022年12月12日。
117.〈第一届得奖项目〉,第2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https://hknextwriter.org/%e7%ac%ac%e4%b8%80%e5%b1%86%e5%be%97%e7%8d%8e%e9%a0%85%e7%9b%ae/,浏览日期:2023年1月15日。
118.〈循声觅道展览系列一:香港节庆与民间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lost_and_sound_exhibition_series_1.html,浏览日期:2022年10月14日。
119.〈传承火龙文化〉,大坑火龙文化馆,https://www.firedragon.org.hk/inherit-the-fire-dragon-culture/,浏览日期:2022年10月14日。
120.〈舞狮历史及传说〉,香港中国国术龙狮总会,http://www.hkcmaa.com.hk/eng/intro/lion.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日。
121.〈藉狮头扎作坚持旧我同时发现新我【文化者.专访】〉,文化者,https://theculturist.hk/2019/02/%E6%96%87%E5%8C%96/%E8%97%89%E7%8D%85%E9%A0%AD%E7%B4%AE%E4%BD%9C%E5%A0%85%E6%8C%81%E8%88%8A%E6%88%91-%E5%90%8C%E6%99%82%E7%99%BC%E7%8F%BE%E6%96%B0%E6%88%91%E3%80%90%E6%96%87%E5%8C%96%E8%80%85%EF%BC%8E%E5%B0%88%E8%A8%AA/,浏览日期:2023年1月16日。
122.王征、余晴峰:〈[港人港事]第471期花牌扎作〉,《中国旅游》,http://www.hkctp.com.hk/travels/id/2877,浏览日期:2022年12月30日。
123.林国辉:〈纸扎工艺在香港:历史、传承与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711288/Paper_Crafting_optionC_re8_ol.pdf,浏览日期:2022年10月16日。
124.邹兴华:〈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二年:回顾与前瞻〉,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660266/Retrospect%2band%2bProspects%2bSafeguarding%2bthe%2bIntangible%2bCultural%2bHeritage%2bof%2bHong%2bKong%2bOver%2bthe%2bPast%2b12%2bYears.pdf,浏览日期:2023年1月13日。
口述历史访问:
125.〈香港扎作业联会主席冒卓祺先生访问〉,上水古洞村,2023年3月10日,访问者: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四年级学生韩明均。
脚注:
1. 关于中国节庆文化的研究,参阅彭淑敏:〈民俗文化〉,王国华主编,何佩然、彭淑敏等着:《香港文化导论》(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页119-147。
2. 郭玉桔:〈港首间扎作展示馆〉(2019年12月16日),《香港商报网》,https://www.hkcd.com/content/2019-12/16/content_1169938.html,浏览日期:2022年10月14日;〈传承火龙文化〉,大坑火龙文化馆,https://www.firedragon.org.hk/inherit-the-fire-dragon-culture/,浏览日期:2022年10月14日;〈循声觅道展览系列一:香港节庆与民间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lost_and_sound_exhibition_series_1.html,浏览日期:2022年10月14日。
3. 黄竞聪:《简明香港华人风俗史》(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页49。
4. 黄竞聪:《城西溯古——西营盘的历变》(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2年),页187;高宝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香港》(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页195。
5. 林国辉:〈纸扎工艺在香港:历史、传承与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711288/Paper_Crafting_optionC_re8_ol.pdf,浏览日期:2022年10月16日。
6. 黄竞聪:《城西溯古——西营盘的历变》,页187。
7. 陈桂洲:《扎作:承‧传》(香港:鼎丰文库,2007年),页20。
8. 黄竞聪:《城西溯古——西营盘的历变》,页190。
9. 黄竞聪:《城西溯古——西营盘的历变》,页190。
10. 狮头、花灯等扎作都是节庆期间较常用的扎作,例如观音诞的花炮也会以花灯作装饰,且都由来已久,具有历史价值。参阅黄竞聪:《简明香港华人风俗史》,页170。
11. 侯坤宏:〈观音信仰的流传与衍化〉,《人间佛教》,2017年10期(2017年7月),页22-23。
12. 蔡志祥、韦锦新编:《延续与变革:香港社区建醮传统的民族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页330。
13. 〈首份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828638/First_hkich_inventory_C.pdf,浏览日期:2023年1月13日。
14. 骆慧瑛:《观心自在:香港观音诞与观音信仰探源》(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20年),页312-316;〈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the_representative_list_of_hkich.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3日;〈第一届得奖项目〉,第2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https://hknextwriter.org/%e7%ac%ac%e4%b8%80%e5%b1%86%e5%be%97%e7%8d%8e%e9%a0%85%e7%9b%ae/,浏览日期:2023年1月15日。
15. 〈循声觅道展览系列一:香港节庆与民间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lost_and_sound_exhibition_series_1.html,浏览日期:2022年10月14日。
16. 司徒嫣然:《市影匠心:香港传统行业及工艺》(香港:香港市政局,1996年),页190-196。
17. 刘继尧、袁展聪:《武舞民间——香港客家麒麟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页69、72、97-98;超媒体编辑部:《香港狮艺传奇》(香港:超媒体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页20。
18. 卢维干:《大慈大悲观世音》(香港:华人庙宇委员会,2016年),页78、81。
19. [宋]高承撰,[明]李果订:《事物纪原》(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卷8,〈舟车帷幄部四十〉,页434;[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卷8,〈文章第十八〉,页127;〈佛山忠义乡志〉,中国国家图书馆,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403&bid=69082.0,浏览日期:2022年12月12日。
20. 林国辉:〈纸扎工艺在香港:历史、传承与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711288/Paper_Crafting_optionC_re8_ol.pdf,浏览日期:2022年10月16日。
21. 黄竞聪:《简明香港华人风俗史》,页49、64、92、170。
22. 骆慧瑛:《观心自在:香港观音诞与观音信仰探源》,页55-67、296-316;卢维干:《大慈大悲观世音》,页18-20、60-81。
23. 〈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hkichdb.gov.hk/zht/index.html,浏览日期:2022年12月12日。
24. 郭玉桔:〈港首间扎作展示馆〉(2019年12月16日),《香港商报网》,https://www.hkcd.com/content/2019-12/16/content_1169938.html,浏览日期:2022年10月14日。
25. [宋]高承撰,[明]李果订:《事物纪原》,卷8,〈舟车帷幄部四十〉,页434。
26. 徐艺乙:《风筝史话》(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2年),页3。
27. 薛源、王雨璿、陈杨梅、陈浩:〈传统南狮的流派及其运动特点研究〉,《科技资讯》,2021年22期(2021年11月),页178。
28. [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8,〈文章第十八〉,页127。
29.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页750。
30.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卷6、卷8,〈元宵〉、〈中元节〉,页173、186、218;[宋]吴自牧:《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卷13,〈铺席〉,页116。
31. 〈纸扎业公所成立纪〉,《申报》,1920年8月23日。
32. 〈佛山忠义乡志〉,中国国家图书馆,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403&bid=69082.0,浏览日期:2022年12月12日。
33. 「佛山大爆」花炮与花灯的集结品,因为它需要以爆破的形式展示花灯。参阅[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卷16,〈器语〉,页444-445;关宏:《佛山彩灯》(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页20-23、34-35;李红:〈佛山彩灯传承和创新的若干思考〉,《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37卷4期(2022年7月),页2-4。
34. 梁正君:〈广州陈氏书院建筑装饰工艺中的吉祥文化〉,《岭南文史》,2003年2期(2003年6月),页8;黄慧莹:〈广东醒狮发展沿革及其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传承》,2013年12期(2013年10月),页136。
35.〈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https://www.ihchina.cn/project.html,浏览日期:2022年12月12日。
36. 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376。
37. 〈扎作技艺〉,香港非物文化遗产资料库,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274d76dd-c685-4fe8-816d-bb7548e3ae89,浏览日期:2022年12月13日。
38. 张一兵点校:《深圳旧志三种》(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年),页287、643。
39. 据1881年之统计,当时香港分别有47位「冥镪商贩」与63位灯笼师傅。参阅林国辉:〈纸扎工艺在香港:历史、传承与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711288/Paper_Crafting_optionC_re8_ol.pdf,浏览日期:2022年12月13日。
40. 周子峰:《葬之以礼:香港殡仪文化初探》(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页164;元建邦编:《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页10、110-112。
41. 〈油牛洋烛扎作工人要求加薪〉,《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11月13日;〈扎作工会定期成立〉,《华侨日报》,1949年3月18日;〈第8067号公告——职工会条例(第332章)〉,职工会登记局2008年11月12日公告,页1。
42. 黄竞聪:《城西溯古——西营盘的历变》,页188。
43. 元建邦编:《香港史略》,页10、110-112。
44. 〈港九各区街坊居民筹祝双十大典〉,《华侨日报》,1951年10月8日;〈庆祝加冕会景巡游筹委会委员亲出募经费〉,《华侨日报》,1953年4月19日;〈华达公司製十馀丈蜈蚣〉,《华侨日报》,1956年5月19日。
45. 〈访问扎作工人〉,《华侨日报》,1957年7月14日。
46. 〈访问扎作工人〉,《华侨日报》,1957年7月14日。
47. 黄竞聪:《城西溯古——西营盘的历变》,页189-190。
48. 黄竞聪:《城西溯古——西营盘的历变》,页191。
49. 〈花牌扎作就业工人增加 年假告满工作復趋繁忙〉,《华侨日报》,1969年2月21日。
50. 〈扎作工友注重技术〉,《华侨日报》,1960年1月31日;〈花牌扎作就业工人增加 年假告满工作復趋繁忙〉,《华侨日报》,1969年2月21日。
51. 〈元宵花灯上市 扎作工友开夜工〉,《华侨日报》,1960年2月9日。
52. 黄竞聪:《城西溯古——西营盘的历变》,页190。
53. 〈纸料扎作情形特殊亦工亦商半劳半资〉,《华侨日报》,1975年5月6日。
54. 黄竞聪:《城西溯古——西营盘的历变》,页191-192。
55. 黄竞聪:《简明香港华人风俗史》,页170。
56. 黄竞聪:《城西溯古——西营盘的历变》,页192-193。
57. 〈秋节节品实销结算〉,《华侨日报》,1959年9月19日。
58. 黄竞聪:《城西溯古——西营盘的历变》,页190。
59. 〈花牌扎作旺〉,《华侨日报》,1969年8月1日;〈盂兰盛会并无逊色花牌扎作应节而旺〉,《华侨日报》,1970年8月16日。
60. 〈纸料扎作工友开始加时工作〉,《华侨日报》,1970年2月9日。
61. 骆慧瑛:《观心自在:香港观音诞与观音信仰探源》,页306。
62. 李利安:《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页69、72-73。
63. 李利安:《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页73-74;[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21年),卷41,〈马王品第四十五〉,页735-736;[西秦]沙门圣坚译:《佛说罗摩伽经》(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21年),卷2,页30-31。
64. [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1970年),卷9,〈海生商主缘〉,页104。
65. 李利安:《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页75。
66. 弘学编:《妙法莲华经》(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卷7,〈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页275。
67. 弘学编:《妙法莲华经》,卷7,〈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页276-277;[宋]天息灾译:《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上海:佛学书局,1935年),卷3,页7、53。
68. 温金玉:〈观音菩萨与女性〉,《中华文化论坛》,1996年4期(1996年10月),页86;朱光磊:〈观音形象在汉地女身化的途径与原由〉,《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6期(2016年12月),页67-68。
69. 李欣:〈中土观音女性化成因别释——兼议汉文明「乾坤并建」之教化原则〉,《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6期(2016年12月),页71-72;[北魏]昙无谶:《悲华经》(台湾:中华电子佛典协会,2018年),卷2,〈大施品第三之一〉,页29。
70. 于君方着,陈怀宇、姚崇新、林佩茔译:《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页21-23。
71. 朱光磊:〈观音形象在汉地女身化的途径与原由〉,页67-68。
72. 李利安:〈中国观音信仰的基本体系〉,《人间佛教》,2021年34期(2021年7月),页69-70。
73. 于君方着,陈怀宇、姚崇新、林佩茔译:《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页43。
74. 侯坤宏:〈观音信仰的流传与衍化〉,页17。
75. 吴燕:《中国观音文化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47-49;石守谦、颜娟英主编:《艺术史中的汉晋与唐宋之变》(台北: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页194;[清]曼陀罗室主人:《观音菩萨的故事》(西安:陝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24。
76. 吴燕:《中国观音文化史》,页49-54;卢维干:《大慈大悲观世音》,页18-20。
77. 李利安:〈中国观音信仰的基本体系〉,页69-70。
78. 王敏:〈菩萨造像的中性化与观音造像的女性化〉,《民族艺术》,2011年3期(2011年8月),页125-126。
79. 朱光磊:〈观音形象在汉地女身化的途径与原由〉,页69-70;骆慧瑛:《观心自在:香港观音诞与观音信仰探源》,页24、296;温金玉:〈观音菩萨与女性〉,页91。
80. 卢维干:《大慈大悲观世音》,页60;骆慧瑛:《观心自在:香港观音诞与观音信仰探源》,页66-67。
81. 骆慧瑛:《观心自在:香港观音诞与观音信仰探源》,页61。
82. 骆慧瑛:《观心自在:香港观音诞与观音信仰探源》,页55、61-63、67;参阅附录一:〈香港观音诞女信众参拜盛况报导〉。
83. 骆慧瑛:《观心自在:香港观音诞与观音信仰探源》,页61、297;〈首份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828638/First_hkich_inventory_C.pdf,浏览日期:2023年1月13日。
84. 〈白沙湾观音诞〉,香港记忆,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local_festivals/festivals/lunar6/6_2/index_cht.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3日;参阅附录二:〈香港扎作业联会主席冒卓祺先生访问〉,上水古洞村,2023年3月10日,访问者: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四年级学生韩明均。
85. 刘继尧、袁展聪:《武舞民间——香港客家麒麟研究》,页69、72。
86. 参阅附录三:〈蕉径龙潭观音古庙内的各式观音造像〉。
87. 卢维干:《大慈大悲观世音》,页48、56。
88. 叶春生:《广府民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71。
89. 刘婕:〈近代省港烟花爆竹贸易研究(1859-1948)——以《中国旧海关史料》为中心〉(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页10-11。
90. 陈子安:《渔村变奏:庙宇、节日与筲箕湾地区历史(1872-2016)》(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页159。
91. 〈【传统之美:花炮传情】〉(2019年5月3日),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watch/?ref=external&v=1734459783367447,浏览日期:2022年12月28日。
92. 司徒嫣然:《市影匠心:香港传统行业及工艺》,页190;〈花炮及其装饰元素〉,香港记忆,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tin_hau/TinHau_Flower/index_cht.html,浏览日期:2022年12月28日;黄竞聪:《简明香港华人风俗史》,页64。
93. 参阅附录四:〈2023年上水古洞村观音诞花炮〉。
94. 秦宏:《香港工业设计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12年),页33;李志清:〈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在乡土社会的存在意义(三)——族际交往中的抢花炮〉,《体育科研》,2006年27卷6期(2006年11月),页11;司徒嫣然:《市影匠心:香港传统行业及工艺》,页190。
95. 〈榕树湾祝天后诞 抢花炮警民冲突 三名村民头破血流〉,《香港工商日报》,1983年5月6日;〈南丫岛索罟湾庆祝天后诞抢花炮 滋事份子捣乱 掷石击伤多人〉,《华侨日报》,1984年5月19日。
96. 蔡志祥:《酬神与超幽:节日和香港的地域社会》(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页109。
97. 参阅附录五:〈2023年上水古洞村观音诞「抽花炮」仪式〉。
98. [汉]班固,许东方校订:《汉书》(台北:宏业书局有限公司,1992年),卷96,〈西域传下〉,页3928。
99. [北魏]杨衒之,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卷1,〈城内〉,页43;〈舞狮历史及传说〉,香港中国国术龙狮总会,http://www.hkcmaa.com.hk/eng/intro/lion.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日。
100. 超媒体编辑部:《香港狮艺传奇》,页20。
101. [唐]杜佑,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全1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卷146,〈乐六‧坐立部伎〉,页3705。
102. 姜喜平:〈「南狮」历史文化与发展现状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页12。
103. 施志明:《本土论俗——新界华人传统风俗》(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页96;冯诗淇:〈浅析南狮运动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变化——以舞剧《南狮梦》为例〉,《艺术评鉴》,2019年5期(2019年3月),页65。
104. 司徒嫣然:《市影匠心:香港传统行业及工艺》,页196。
105. 司徒嫣然:《市影匠心:香港传统行业及工艺》,页196。
106. 刘钊:〈「小臣牆刻辞」新释——揭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復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2009年1月),页8。
107. 霍松林、赵望秦主编:《宋本史记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卷47,〈孔子世家〉,页1895。
108. 邢金善:〈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麒麟舞的传承与发展〉,《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1年3期(2011年3月),页45。
109. 刘继尧、袁展聪:《武舞民间——香港客家麒麟研究》,页25。
110. 周萍:〈东莞市清溪镇客家麒麟舞的传承与保护〉(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页5。
111. [民国]陈伯陶:《东莞县誌》(台北:成文出版社,1912年),页268。
112. 〈狮头扎作技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3b1ef5b5-f9d7-4298-a8e1-e0a1f1d65dbe,浏览日期:2023年1月2日。
113. 〈舞麒麟〉,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6e0c13d8-09c3-4053-80ba-c970644cca62,浏览日期:2022年12月30日。
114. 参阅附录六:〈2023年上水古洞村观音诞舞狮〉;参阅附录七:〈2023年上水古洞村观音诞麒麟头扎作〉。
115. Stella So:《粉末都市——消失中的香港(增订版)》(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页140;〈扎作与文化(舞狮龙头篇)〉,香港电台网站,https://www.rthk.hk/chiculture/bamboocraft/c2_culture.htm,浏览日期:2022年12月29日。
116. Stella So:《粉末都市——消失中的香港(增订版)》,页141;〈舞麒麟〉,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6e0c13d8-09c3-4053-80ba-c970644cca62,浏览日期:2022年12月30日。
117. 〈花牌扎作技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f340159e-365e-4292-aadc-8f3a246ba630,浏览日期:2022年12月30日。
118. 王征、余晴峰:〈[港人港事]第471期 花牌扎作〉,《中国旅游》,http://www.hkctp.com.hk/travels/id/2877,浏览日期:2022年12月30日;黄竞聪:《简明香港华人风俗史》,页92。
119. 〈各界隆重庆祝孔圣诞辰 永安街悬花牌庆贺〉,《华侨日报》,1947年8月27日;〈华商总会一番新气象〉,《工商晚报》,1948年7月16日。
120. 〈酒楼喜庆宴会特多 花牌扎作工作转旺〉,《华侨日报》,1970年1月30日。
121. 〈花牌扎作〉,传耆,https://www.eldage.com/collections/%E8%8A%B1%E7%89%8C%E7%B4%AE%E4%BD%9C,浏览日期:2022年12月29日。
122. 〈花牌扎作技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f340159e-365e-4292-aadc-8f3a246ba630,浏览日期:2022年12月29日。
123. 陈守仁:《香港神功戏》(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页18;参阅附录八:〈2023年上水古洞村观音诞花牌〉。
124. 〈非遗项目 ─ 扎作技艺〉,赛马会「传‧创」非遗教育计划,https://ichplus.org.hk/tc/ich/project/paper-crafting-technique,浏览日期:2023年1月12日。
125. 蔡志祥:《酬神与超幽:节日和香港的地域社会》,页109。
126. 参阅附录二:〈香港扎作业联会主席冒卓祺先生访问〉,上水古洞村,2023年3月10日,访问者: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四年级学生韩明均。
127. 参阅附录二:〈香港扎作业联会主席冒卓祺先生访问〉,上水古洞村,2023年3月10日,访问者: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四年级学生韩明均。
128.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32540_chi/PDF/132540chi.pdf.multi,浏览日期:2023年1月12日;〈甚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what_is_intangible_cultural_heritage.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2日。
129. 邹兴华:〈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二年:回顾与前瞻〉,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660266/Retrospect%2band%2bProspects%2bSafeguarding%2bthe%2bIntangible%2bCultural%2bHeritage%2bof%2bHong%2bKong%2bOver%2bthe%2bPast%2b12%2bYears.pdf,浏览日期:2023年1月13日。
130. 〈非物质文化遗产谘询委员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ich_advisory_committee.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3日。
131. 普查范围A包括北区、大埔、沙田、西贡、黄大仙、观塘、九龙城、深水埗及油尖旺;普查范围B括元朗、屯门、荃湾、葵青、离岛、中西区、湾仔、东区及南区。参阅〈CB(2)1090/08-09(01)号——全港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2009年3月20日资料文件,页5。
132. 〈CB(2)957/10-11(03)号——全港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进度报告〉,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2011年2月11日资料文件,页2-3;〈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https://hkheritage.hkust.edu.hk/,浏览日期:2023年1月13日。
133. 〈CB(2)855/16-17(06)号——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草拟名单〉,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2017 年 2 月 27 日的会议,页2;〈首份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828638/First_hkich_inventory_C.pdf,浏览日期:2023年1月13日。
134. 〈CB(2)842/16-17(01)号——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草拟名单〉,民政事务委员会2017 年 2 月 27 日讨论文件,页3;〈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the_representative_list_of_hkich.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3日。
135. 〈CB(2)1448/17-18(01)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博物馆措施提供资助〉,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2018 年 5 月 28 日讨论文件,页3;〈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ich_funding_scheme_introduction.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4日。
136. 佚名:〈一竹一纸 传统再现〉(2019年9月8日),《政府新闻网》,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9/20190906/20190906_145115_745.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4日。
137. 〈西贡白沙湾观音古庙〉,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8%A5%BF%E8%B2%A2%E7%99%BD%E6%B2%99%E7%81%A3%E8%A7%80%E9%9F%B3%E5%8F%A4%E5%BB%9F/100064936624023/,浏览日期:2023年1月14日。
138. 〈古洞村 - 1953恭祝观音宝诞酧神演戏委员会〉,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kttkyc?locale=zh_HK,浏览日期:2023年1月14日。
139. 参阅附录九:〈2023年上水古洞村观音诞盛况〉。
140. 蔡志祥:《酬神与超幽:节日和香港的地域社会》,页72-74。
141. 许宣白:〈「抢花炮」停办两载 百年传统渐凋零〉(2021年5月6日),《文汇网》,https://www.wenweipo.com/s/202105/06/AP60933f80e4b0476859ba5381.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5日。
142. 〈第一届得奖项目〉,第2届想创你未来-初创作家出版资助计划,https://hknextwriter.org/%e7%ac%ac%e4%b8%80%e5%b1%86%e5%be%97%e7%8d%8e%e9%a0%85%e7%9b%ae/,浏览日期:2023年1月15日。
143. 〈循声觅道展览系列一:香港节庆与民间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lost_and_sound_exhibition_series_1.html,浏览日期:2022年10月14日。
144. 蒋琳:〈记载社区变迁 传承扎作工艺 元朗举办历史图片与花炮展〉(2017年6月29日),《香港商报网》,https://www.hkcd.com/newsTopic_content.php?id=1054917,浏览日期:2023年1月16日。
145. 〈扎作小知识(舞狮龙头篇)〉,香港电台,https://www.rthk.hk/chiculture/bamboocraft/c2_tips.htm,浏览日期:2023年1月16日。
146. 〈藉狮头扎作坚持旧我 同时发现新我【文化者.专访】〉,文化者,https://theculturist.hk/2019/02/%E6%96%87%E5%8C%96/%E8%97%89%E7%8D%85%E9%A0%AD%E7%B4%AE%E4%BD%9C%E5%A0%85%E6%8C%81%E8%88%8A%E6%88%91-%E5%90%8C%E6%99%82%E7%99%BC%E7%8F%BE%E6%96%B0%E6%88%91%E3%80%90%E6%96%87%E5%8C%96%E8%80%85%EF%BC%8E%E5%B0%88%E8%A8%AA/,浏览日期:2023年1月16日。
147. 宋霖铃:〈创新传统 狮头鱼尾 两代扎作人 合璧再世卢亭〉(2020年6月3日),《明报新闻网》,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9%AF%E5%88%8A/article/20200603/s00005/1591123562926/%E5%89%B5%E6%96%B0%E5%82%B3%E7%B5%B1-%E7%8D%85%E9%A0%AD%E9%AD%9A%E5%B0%BE-%E5%85%A9%E4%BB%A3%E7%B4%AE%E4%BD%9C%E4%BA%BA-%E5%90%88%E7%92%A7%E5%86%8D%E4%B8%96%E7%9B%A7%E4%BA%AD,浏览日期:2023年1月16日。
148. 刘继尧、袁展聪:《武舞民间——香港客家麒麟研究》,页97-98。
149. 〈花牌扎作保留传统尝试求变〉(2016年12月31日),《大公网》,http://www.takungpao.com.hk/culture/text/2016/1231/50014.html,浏览日期:2023年1月16日。
150. 曾莲:〈孝子承父业 精益求精传扬花牌工艺〉(2019年2月13日),《大纪元时报》,https://hk.epochtimes.com/news/2019-02-13/36644627,浏览日期:2023年1月16日。
151. 〈传统花牌展现文学情怀〉,《经济日报》,2012年4月13日。
< 原创文章/视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欢迎留言:
请登入/登记成为会员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