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紮作與傳統節慶文化:
以觀音誕為研究個案
韓明均
2024年4月12日
謝 辭
本畢業論文,承蒙彭師淑敏博士四年來之親切關懷和悉心指導,不僅傳授
學術知識,也積極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課餘與學生進行討論,諄諄教導。研究過程中嚴格訓練,提供論文架構、文獻資料搜集等技巧,並在口述歷史訪問及實地考察等積極推薦和提供寶貴意見。是次研究得以順利完成,謹此對恩師致上衷心感謝。撰寫論文期間,又曾得下列人士/機構予以協助,本人併此致謝。
1.香港樹仁大學圖書館、香港公共圖書館
2.香港紮作業聯會主席冒卓祺先生接受口述歷史訪問。
3.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教師何其亮教授、羅永生博士、周子峯博士、區志堅博士、何冠環教授與朱心然博士這四年的悉心栽培與嚴格訓練。
4.朋友何萍華小姐、葉海欣小姐、陳家俊先生、鄧樂添先生及吳卓璘先生同行。
5.父親韓錦章與母親黃雅秀的悉心照顧與關懷。
中國紮作技藝在香港經過百年傳承,已然成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作為宣揚傳統節慶文化的窗口,我們常會在觀音誕、盂蘭節、中秋節等中國傳統節慶中看見其蹤影。1 近年,紮作技藝展示館、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等文化機構相繼在館內展出並介紹不同的節慶紮作品,例如火龍、獅頭、花燈等,向公眾展現紮作的多元面貌,足見坊間對紮作文化傳承的重視。2 在諸多傳統節慶中,觀音誕的紮作元素不僅多元化,且觀音為香港「入屋」的神祇之一,在不同族群都具有其影響力。3 因此,本論文將以觀音誕的紮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其與傳統節日的關係、它們的歷史價值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義。
第一節:研究回顧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副執行總監黃競聰博士所著的《城西溯古——西營盤的歷變》一書指出「紮作」囊括了所有以紗紙、竹篾、漿糊等材料製成的節慶紮作、裝飾紮作、喪葬紮作和龍獅紮作。4 中國最早的紮作品是出自新疆吐魯番彁斯塔那唐代(618-907年)墓葬中的紙棺,5 所以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紮作」主要在葬禮中應用,亦常會把「紮作」與「紙紮」混為一談,但兩者其實有細微的差異,「紙紮」是冥器的一種,只會運用於喪葬或祭祀儀式中,但從定義來看,「紮作」是一個大類,節慶紮作同樣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6 因為它能夠表現出紮作品除了能夠用於悼念先人外,還是喜慶的標誌。
中國傳統紮作技藝約於清朝(1644-1911年)從廣東一帶傳入香港,並在五、六十年代進入繁盛期。當時的紮作品除了花炮、花牌等作品外,還包含了廣告牌,款式十分多樣。7 獅頭、花燈等節慶紮作更曾是帶動香港紮作業發展的重要元素。它們在內地禁運期間被出口至歐美地區,以應付華人群體的需求。8 在中國傳統節日期間,紮作品比平日更受歡迎,不少報章都曾報導過紮作業在節日期間的興旺,例如紮作工人在中秋期間最為繁忙,收入也會大幅增加。9 可惜隨着時代更迭,人們的教育水平和環保意識開始加強,中秋佳節的紙燈籠被電子燈籠代替,年輕人更願意在空調房裏辦公,紮作業也回不到過去的輝煌。10 不過,該行業至今仍有師傅堅持營運與推廣,以吸引更多年輕人來傳承他們的匠人精神和傳統文化,足以說明傳統紮作工藝仍有受眾,具有社會及歷史價值。
大眾在觀音誕期間對傳統紮作品的需求較多,這與民間普及的觀音信仰有關。觀音信仰從印度傳入中國後,糅合了佛、道兩教的元素,又經過「本土化」,因應人們對於生活的寄託與嚮往出現了不同的形象,應對百姓不同祈願,同時成為婦女生活的折射,於是人們總會趁着觀音誕向觀音表達感恩。11 香港觀音誕的慶典與習俗會因族群的背景與生活習慣而異,為增強民眾社區認同感的重要平台之一。而花炮、獅頭與麒麟頭、花牌等紮作便是維持平台運作的工具,例如觀音誕期間眾人會集結起來「搶花炮」,祈求得到觀音祝福,所以花炮亦被視為神誕的符號。12 因此,本論文期望通過以觀音誕紮作為例,分析紮作的社會意義和歷史價值。
第二節:研究對象
本論文的主要研究對象為觀音誕與紮作技藝。「觀音誕」與「紮作技藝」都在2014年公佈的《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被分別列於「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和「傳統手工藝」。13 近年,坊間對觀音信仰的關注度有上升的趨勢,香港佛教聯合會與香港菩提學會相繼舉辦「觀音文化節」作宣傳,亦有學者出版專書,例如《觀心自在:香港觀音誕與觀音信仰探源》;紮作技藝則被列入2017年公佈的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當中。14 自2016年起,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開辦與節慶紮作相關的展覽:例如2021年的「香港節慶與民間工藝」展覽,旨在讓人們意識到紮作技藝的生活化。15 這些都是對紮作技藝和觀音誕文化價值的認可。
觀音誕的紮作品以花炮、醒獅、麒麟和花牌為主,每逢佳節這些作品總會在不同環節先後進入大眾視野,例如搶花炮、舞麒麟等。《市影匠心:香港傳統行業及工藝》一書曾對以上紮作品的特點及功能作出簡略介紹:花炮是觀音誕「搶花炮」的環節中必須具備的紮作元素,是歷史故事、粵劇人物、中國傳統吉祥物和紮作技巧的展示台。16 而醒獅和麒麟作為傳統節慶紮作,在表演環節中扮演重要角色,除了調節氣氛外,還有辟邪的功能,《武舞民間——香港客家麒麟研究》、《香港獅藝傳奇》等書籍皆有專門的介紹。17 花牌在神誕期間則有慶賀、宣傳和指引的功能,其發展情況在非遺資料庫中有所記錄。這些文獻都記錄了觀音誕紮作及紮作行業與社會變遷的關係。
現時,華人廟宇委員會轄下以觀音作主祀神的廟宇有3所,另有18所廟宇以其為配祀神,雖然數量不算多,但香火不斷,可見人們長久以來對觀音的尊敬。18 各區慶祝觀音誕的日子和習俗會依照着人們生活的習性有細微的調整,連同紮作品的特點也會隨之變化。故此,觀音誕紮作品是反映各族群民俗和生活剪影的重要渠道,亦是研究的意義所在。唯現時該節慶活動和紮作技藝的從業人士及參與者都停留於中老年人及固定團體,使觀音誕紮作的影響力始終難以擴大,其歷史價值亦鮮有人知,幸得紮作師傅堅持推廣及傳承該項技藝。
第三節:研究資料
有關紮作技藝及觀音誕的歷史,古籍及現代中港學者的著述皆有記載及探討。首先,《事物紀原》、《大唐新語》、《佛山忠義鄉志》等古代文獻曾談及紮作品在戰爭、生活和傳統節日中的功能與特點,記錄了紮作技藝在古代的痕跡。19 《新安縣志》雖只有隻言片語提到紮作品,但驗證了清朝為香港紮作技藝發展歷程中的起點。20 而其後的發展歷程則主要運用報章及《簡明香港華人風俗史》等現代學者所著之文獻進行論述,藉此總結各年代紮作行業概況,包括業內工人工資、從業人數、國內外的供需等內容,同時突出節慶紮作對整個紮作行業的重要性。21
對於觀音誕及相關紮作品的歷史與特點,筆者將以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官方網頁資料、學界論文及專書作為主要參考資料。有關觀音誕的信仰特點、習俗與源流,《觀心自在:香港觀音誕觀音信仰探源》、《大慈大悲觀世音》等書籍都有較詳盡的綜述,包括「觀音」從男神變為女神的過程、民間傳說、傳播途徑、香港觀音信仰的普及度等,彰顯觀音信仰及觀音誕深厚的民眾基礎。22 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中則有清楚記錄舞麒麟、花牌紮作技藝和獅頭紮作技藝的歷史沿革、特色和製作流程,有助於準確地了解觀音誕紮作。23
針對觀音誕紮作的傳承,本論文會輔以口述歷史資料及實地考察作分析。是次研究邀請了香港紮作業聯會主席冒卓祺師傅進行訪問。冒師傅從19歲開始學習紮作技藝,至今仍醉心於製作麒麟、獅頭等手工藝品,同時致力於推廣紮作藝術,並於2019年設立紮作技藝展示館,目的為向大眾展示古今的紮作品。24 故是次訪問的重點會集中於冒師傅對紮作技藝被納入非遺以後的看法。從紮作師傅的角度出發,探討這項技藝被納入非遺名單後,文化機構及政府的推廣及保育措施情況。另外,是次實地考察期望以2023年古洞村觀音寶誕作為考察對象,從而了解現時觀音誕的舉辦情況與紮作的特點,從中總結觀音誕及其紮作背後的意義。
第四節:內容架構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內容主要包括與是次論文相關的學術回顧、研究對象、研究資料簡述及內容架構。
第二章以「節慶紮作的流傳」為題,分別在三個章節中敍述中國傳統紮作的歷史源流,然後分析該項技藝得以在清朝流傳至香港的契機及其在香港的發展歷程,同時以過往紮作行業在節慶期間的經營情況進一步帶出節慶與紮作相輔相承的關係,作為全文導引的部分。
第三章以「觀音誕與紮作」為題,先敍述香港觀音誕的歷史與文化,其後介紹觀音誕主要運用的紮作品(即花炮、醒獅、麒麟及花牌)的由來、特點、相應的例子及背後的含意,以及現時傳承觀音誕紮作所須面對的挑戰,藉此探究觀音誕與紮作的文化內涵及歷史意義,同時了解其流傳狀況。
第四章以「紮作的創新與傳承」為題帶出紮作技藝與觀音誕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及收錄進非遺名單後對傳承觀音誕紮作的影響。此章節亦會探討近年來紮作師傅在觀音誕紮作中的創新和他們對紮作技藝傳承的影響,以及在疫情下的觀音誕如何成為傳統紮作技藝的載體,讓其在百廢待興的階段仍能穩定發展。
第五章的「結語」將會以前文為基礎,宏觀地概述香港紮作與傳統節慶文化的關係及其歷史意義,並審視其傳承的現況。
紮作品的用途在不同時期都會發生改變:從探查地勢與軍情,到喪葬、祭祀,再到節日慶典,它既能在日常生活中發揮祭祀、娛樂等功能,也能在軍事、經濟、文化三方面默默推動城市及國家的發展。在香港,紮作品更是被人欣賞的藝術品,甚至一度成為備受外國人歡迎的出口商品,只是在新興事物不斷湧現的社會中,紮作這樣費時的技藝,逐漸失去年輕的市場。
第一節:中國傳統紮作
中國紮作技藝之源流可上溯至漢代(前206-220年)。據《事物紀原》記述:「高祖之征陳豨也,信謀從中起,故作紙鳶放之,以量未央宮遠近,欲以穿地隧入宮中也。」,指出韓信(公元前231-196年)曾使用風箏量度距離,但紙張在東漢(25-220年)以後才得以普及化,這段文字似乎很難證明紮作在此時便已存在。25 但結合韓信以牛皮製作風箏,「下置善笛之人吹思鄉之曲」使「楚軍弟子八萬皆散去」的事跡,則大致能夠確定漢代是紮作技藝誕生的時期。26 而風箏或許是最早出現的紮作品,可見紮作最初是作軍事用途的,而非單純地只用於喪葬與祭祀。
隨着紙張的普及,紮作成為百姓的生計、娛樂和祭品,亦更多地被記載於私人著述和正史中,紮作品在唐代及宋代(960-1279年)尤為流行。現代的紮作品有很多都是始於唐代,例如花燈、舞獅等,連同祭祀形式也因紙紮而發生改變。27 有關唐代節慶紮作,《大唐新語‧文章第十八》提及「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28 ,期間有「火樹銀花合」29 之景,可見唐朝已有花燈,呈現空前盛況。而宋代紮作則多見於《夢粱錄》和《東京夢華錄》,例如元宵節用長竿搭成百餘丈的「燈山」,「紙糊百戲人物,懸於竿上,風動宛若飛仙」;中元節則「以紙糊架子盤遊出賣」,單在杭州大街上便有兩家紙紮舖。30 從以上種種記載可知,唐宋時期的紮作技藝已初具規模。
明(1368-1644年)、清與民國時期(1912-1949年)的紮作沿襲了唐宋的紮作特點、文化與作品種類,且更為系統,上海同行更是一同成立「紙紮業公所」以便統一管理。31 眾多地區中,當以佛山紮作工藝發展最為興盛,《佛山忠義鄉志‧卷第六‧實業志》中寫有各式行業,把「紮作行」與「燈籠行」作了區分,並提及「本鄉紮作極有名,人物故事尤精,外鄉多來購之,又有不倒翁為行酒令之具,外省銷流極廣」,可見當時佛山紮作享負盛名。32
佛山紮作流行的因素主要有二,分別是獨特的地區民俗文化與地理優勢。首先,佛山紮作品融入了地區民俗和文化,例如每逢秋色賽會和北帝誕,型態各異的花燈便會出現,如魚燈、蝦燈、蟾蜍燈等,還有一舉成名的「佛山大爆」,這些習俗促使紮作的需求增加,其發展也自然更迅速。33 民間傳說也會影響佛山紮作品,以佛山獅頭為例,人稱明代初年,農家常受怪獸侵擾,於是紮作師傅便以竹篾和彩紙製成「獨角獅」,以怪治怪,此造型一直沿用至今。34 「佛山彩燈」與「佛山獅頭」更被收錄於「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中,足見其在紮作文化中的代表性。35 其次,佛山自明清以來便是貿易重鎮,因其位處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交通交匯處,「西接肇梧,通川廣雲貴。下連順新,通江門澳門。東達番東,通石龍、惠州」,同時也是商家往返廣州的必經之地,吸引並帶動外省商人往來交易,紮作品因而不愁銷路,足夠當地紮作店舖維持營生。36 中國紮作技藝也隨着這些有利條件一直傳承及發展。
第二節:流傳到香港的紮作
直到清朝,中國傳統紮作技藝流傳到香港,落地生根。從經濟和社會情況分析,五、六十年代為紮作業的興盛期,然後逐漸式微。37
有關香港紮作行業,最早的記載是在康熙和嘉慶兩版的《新安縣志》中,內文均有以「元宵,張燈作樂。凡先年生男者,以是晚慶燈。」記錄當時的點燈活動。38 不論活動所用的「慶燈」是由本地製作,還是從外地購置,都能證明港人對紮作品的應用是從清朝開始,而且因為紮作品與本土風俗已互相融和,他們未來對此的需求是有持續性,只是仍須內地工藝的支持。因此,1869年才會出現由「省城高第悅昌號」和「佛山口口新景昌」供應的戲曲人物故事箱,儘管到了1881年,香港陸續有約百位本地的冥鏹商販和燈籠師傅通曉紮作手藝,廣州師傅依然在香港市場佔有一席之地。39
香港紮作行業依賴內地供應商的原因之一是佛山等地的紮作行業比香港更早開始發展,所以技術和規模較為成熟,產品質量較有保證;此外,香港被英國佔領後,建立港口、倉庫、馬路等有利經濟發展的設施,吸引上萬華人到港謀生,其中包括華南沿海的疍戶、廣東商人等群體,他們對內地貨品的信任度較高,加上航運的便利和華人風俗不受英籍政府干預,所以每有華人喪禮、喜事和節慶內地紮作都會較受歡迎。40
時至1920至1940年代,香港紮作行業規模開始擴大,招收工人,並成立工會組織規範管理業內人士,以及維護業內人士的權益。1922年《香港華字日報》中曾報導過一則油牛洋燭紮作工人向工會爭取加薪,並要求聘請工會會員,由此可見紮作工會在該年以前已有雛型,經過多次改組更名後才正式成長為如今港人認知的「港九油燭紙業紮作職工會」,唯其後於2008年結束營辦。41 而在規模方面,有關香港紮作業的統計由個體的數量變為對紮作舖的統計,意味着紮作的從業人員日漸增多,例如在1939年,《香港九龍商業分類行名錄》共錄得香港紮作舖132間。42 1940年代末,內地師傅和移民為了躲避戰亂,紛紛到港謀生,為行業增添專業人材和廉價勞動力,成了紮作業踏入興盛期的前奏。43
1950至60年代,從紮作行業的就業情況、應用場景和經濟效益中可以得知紮作業發展正式迎來全盛時期,中港的社會局勢變動是其中的助力。1950年代,國慶、英女皇加冕會景巡遊等節日和重大慶典,無不需要紮作品作裝飾,甚至成為電影元素,一時之間客戶也多了起來。44 而且行業人員更替迅速,不愁無人繼承這一門手藝,當時紮作工人都稱:「後浪推前浪,新人替舊人」,競爭激烈。45 正因如此,規模較小的紙料店請不起「老師傅」,連同三年學師制度也難以謹守,這或許便是行業發展壯大後產生的副作用。46 工人和師傅的薪金不固定,約8元至300元不等,雖然與1922年的10元左右相比,整體工資雖呈上升趨勢,但人力資源追不上大幅增加的市場需求,紮作工人的工時一天可長達15小時,但工資卻不足100元,最終爆發勞資糾紛。47 總體來說,雖然紮作行業在五十年代市況良好,但缺乏妥善管理,時有出現工時工資不成比例、收入不穩定、培訓不足等問題。
1960年代起,本港紮作師傅數量增加,行業開始重新強調技術上的培訓,紮作品甚至能夠遠銷海外。首先,在從業人數方面,內地文化大革命使傳統紮作工藝無法在內地發展,迫使相關人士遷至香港維生,讓香港紮作行業加入新力。48 本港入行人數直到1969年仍能收錄約2000位學徒,可見其發展趨勢依然平穩。49 當時,紮作的樣式開始更新,如「往昔紮作是沒有飛機的,而今飛機可以紮作出來」,於是師傅的技術便是紮作品好壞的關鍵,過去的「學師制」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在人手短缺的情況下,學師年期縮減至1 年。50 精美的作品不但受本地居民追捧,更有鄰邦友人的欣賞。51 同時,受美國對中國實施禁運的影響,許多國內貨物只能通過香港購置及輸出,於是諸如花燈、獅頭等紮作品開始經由香港對外輸出,主要對象是遠居歐美地區的華人團體,銷售網絡覆蓋英美、瑞典、加拿大等國家。52 因此,六十年代的紮作行業就業機會多,生意穩定,又能外銷,處於興盛期。
1970年代以後,香港紮作業在中港兩地的社會及經濟變動下逐漸走上「下坡路」。首先,就本地情況而言,紮作師傅「亦工亦商半資」,連他們自己也難以將自己定位為「手藝人」或「商人」,部分師傅只將此作為自己的副業,加上行業待遇低,再難吸引新人入行,該行業僅有的生存空間依賴各宗教善信的支持。53 另外,在售價和樣式方面,由內地運來的紮作品成本和售價更低,所以即使本地師傅不斷創新,銷量仍比不上內地來貨。54 加上人們開始追求環保、安全和新穎,傳統紙燈籠或迎節紮作逐漸被代替。55 時值內地改革開放,發展工業,勞工和原料的成本都較香港低,更易獲利,紮作市場便從香港轉移到內地。56 基於以上因素,香港紮作行業難以回到五、六十年代的光景。
第三節:紮作與節慶的關係
綜合各類文史資料,紮作品與節慶息息相關,凡遇華人節慶,紮作店總會忙得不可開交,營利也會較平日多。以1959年的中秋節為例,市民在「祀神品及紙料紮作」的總消費達百萬元,當中走馬燈與紙紮燈飾因受兒童歡迎,銷量較佳。57 從前每逢中秋佳節,紮作業便踏入旺季,相關報道也從不間斷。紮作工人會趁此時身兼多職,增加個人收入。58
中秋節其實只是紮作業的其中一個旺季,重陽、盂蘭勝會等節日都令紮作師傅收益不少,花牌紮作在節日中尤其受追捧,部分店舖會僱用臨時散工幫忙,減輕人手負擔。59 不過,紮作工人最為忙碌的時段,當屬農曆年關:他們一般都須延時工作,從農曆初一的1小時到最後階段的17小時,需要輪流當值到通宵,但卻沒有「補水」,相當辛苦。60 這些都證明節慶與紮作業發展是相輔相承的。
華人之所以會在節慶期間使用紮作品,一則是用於裝飾,增添節日氣氛;二則是取其象徵的寓意,寄託自己的願景,例如麒麟紮作有送子的寓意、福鼠象徵富貴興隆等;三則用作祭祀,例如觀音誕的舞麒麟、盂蘭勝會的士大王等。故此,時至今日,我們仍能在中國傳統節日裏看見花牌、彩燈、舞獅等紮作品的影子,可見節慶紮作是紮作行業中需求量最大,也最能代表華人傳統的藝術品。而具有本土特色的紮作是觀音誕中的重要元素,觀音誕也是展示傳統紮作品的平台,這便是論文以觀音誕紮作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
民間觀音誕有四天:分別為農曆二月十九日的觀音生辰、六月十九日的成道日、九月十九日的出家日及十一月十九日的成水神之日,而香港大型觀音誕慶祝活動主要於農曆二月十九日及六月十九日進行,以及在農曆正月二十六進行「觀音開庫」。61 主辦單位在節誕前都會認真籌備,準備各式紮作,以花炮、醒獅、麒麟與花牌較常見,都具有特別的寓意和造型。觀音誕是紮作的載體,紮作也承載着善信們對未來的願景,所以才會有人願意代代傳承,不過傳承的過程必須面對時代更迭所帶來的挑戰。
第一節:觀音信仰與觀音誕的源始
歷代研究觀音的學者對觀音信仰的本源提出了各種推測。綜合造像、經籍、傳說以及學者們的觀點後,較合理的說法指出觀音信仰的雛型應誕生於古印度的東南沿海地區,而其「救難」的形象則源自五百商人從「黑風海難」與「羅剎鬼難」中得救的傳說。62 故事中,救人的主角從《增一阿含經》記載的「馬王」,再到《佛說羅摩伽經》的「夜天」,都突出了觀音「觀世」、「救苦救難」的特質,後來《撰集百緣經》中救難的事跡與佛教結合,於是「救難」成為了佛陀的職能。63 據經籍所載:
有五百賈客,欲入大海採取珍寶。……值大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剎鬼國,迴波黑風。時諸商人,各各跪拜諸天善神,無一感應救彼厄難。中有優婆塞,語商人言:「有佛世尊,常以大悲,晝夜六時,觀察眾生,護受苦厄,輙往度之。汝等咸當稱彼佛名,或能來此,救我等命。」時諸商人,各共同時,稱南無佛陀。爾時世尊,遙見商客極遇厄難,即放光明,照耀黑風,風尋消滅。64
這些文獻中雖尚未具體提及「觀世音」(梵語為Avalokitesvara),但在內容上初步塑造了觀音的神格,作為觀音信仰發展的萌芽期和舖墊。
及後,隨着印度佛教體系日趨完善,救世之任從佛陀轉移到菩薩身上,觀音信仰逐漸開始成形。65 《妙法蓮華經》中曾提及:「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66 以及其「辟支佛身」、「聲聞身」、「梵王身」等33種應化身。再結合《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中「此大光明,是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入大阿鼻地獄之中為欲救度一切受大苦惱諸有情故。救彼苦已復入大城。救度一切餓鬼之苦。」、「聖馬王者即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是」等對觀音的描述,67 可見觀音會觀察世間的聲音,能夠為普渡眾生而化為不同形態。同時,因為繼承了傳說中在海上「救苦救難」的神職,自此觀音以「海上守護神」的身份於沿海地區廣泛傳揚,所以祂是除天后以外較受漁民重視的神祀。
有關印度觀世音菩薩的原始性別,佛教主張「法無定相」,即救渡世人並無男女之分,所以觀音為世人解難時絕不會囿於以男身或女身出現,佛教流行以前便有傳觀音原為畜身,形象源於「雙馬童」的說法,但坊間的觀音形象以男身為主。68 《大方廣佛華嚴經》及《楞嚴經》中雖有女身觀音的記載,例如比丘尼、優婆夷,但《妙法蓮華經》、《悲華經》及《華嚴經》等經籍大多都以「善男子」、「勇猛丈夫」等男性身份稱呼祂,當中的《悲華經》在講述其身世時更指出觀音成為菩薩前為「轉輪聖王太子不眴」,有貴族身份,可見在經籍中,男身為觀音的主流形象。69
在造像方面,觀音造像最早起於公元二世紀(101-200年)左右,呈現的形式為身着王族服飾、有短髭的「蓮華手觀音」,從生理特徵上凸顯其為男性的身份。70 由以上兩個元素可見,印度佛教較認可觀音為男性,同時這也是人們後期把信仰具象化後,根據社會價值觀賦予祂的。這是基於古印度對女性的歧視,認為女子是男子的附庸,所經歷的磨難要比男子更多,因此被視為帶有前世罪孽輪回的罪人,故觀音高貴的菩薩之身不會以女子為形。71 於是,佛門中人在兩種性別之間選擇讓觀音以男身現世。
觀音傳入中國後,逐漸衍生出女身觀音,也出現了不同的宗派:後世將其分為「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及「民間信仰」三種,各自呈現出較強的民族性與地域性,而觀音信仰在宗教屬性轉化的過程中糅合了儒釋道。72 東漢時期,安息僧安世高(生卒年不詳)到訪洛陽被視為佛教正式傳入中國的開端,因為他開啟了漢譯佛教經籍的篇章,尤其是首次提及「觀音」的《成具光明定意經》,這可能是人們第一次認識觀音信仰。73
隨着漢譯的佛教經典日漸增多,觀音信仰的滲透亦越趨深入,及至魏晉南北朝(220-589年)全面輸入。74 兩晉時期(265-420年),《正法華經》、《妙法蓮華經》等經籍開始介紹觀音不論階級、普世救人和慈悲為懷的神性,並出現了蓮花手觀音造像及「西方三聖祖像」,為神情安詳、蓄鬚的男身。75 及至南北朝(420-589年),相關的經籍與造像的種類增加,更詳細地解釋了觀音能夠解救現世受難的人和引渡亡靈到極樂世界的緣故,這讓渴望在現實因政局動蕩和戰亂中得到救助的大眾有了精神寄託,加上帝皇的支持,使觀音信仰踏入興盛期。76 在此期間,主張「身心修行」的密教也沿着西藏傳入及發展,包括經咒、真言、法門、造像等內容,使「藏傳佛教」逐漸成形,但中原觀音信仰仍以「漢傳佛教」作為藍本,結合中國本土的社會和文化特徵進行演化,形成了不受教條限制的「民間觀音信仰」,「女身觀音」亦由此而生。77
據考古發現,莫高窟中南北朝的觀音畫像及造像展現很符合佛教經籍的中性形象,有利於觀音信仰在男女之間流行,成為隋朝(581-618年)至宋朝觀音女性化的前奏和基礎,而唐朝為其中的關鍵時期。78 其所涉因素頗多:第一,武則天當政期間,女性地位提升,佛教僧人大肆宣揚其為「彌勒佛降世」,彌勒佛又與觀音度化世人的屬性相似,引導觀音女性化的趨勢;第二,中國古代長期處於「男尊女卑」及「母憑子貴」的思想環境下,女性遭受的苦難比男性更多,所以迫切地需要一個能象徵婦女群體的女神傾訴與解難,而觀音有「送子」的神職,其神性與慈母的身份契合,所以觀音以女相或女身呈現更符合社會價值觀和需要;第三,唐朝的社會審美傾向於豐腴體態,所以出現了一部分帶有女性特徵的觀音畫像與造像,例如水月觀音像,其造像尚存於敦煌與莫高窟遺址。79
自宋代起,儒釋道「三教合一」,使觀音信仰中出現了道教及儒家的元素,漸趨世俗化。北宋期間(960-1127年),從唐代一直流傳的「妙善公主」的故事在這一時期影響最廣。故事記載着妙善公主因決意潛心修道而不願出嫁,遭妙莊王貶謫,但在他身患惡疾,需要至親的手眼才能治癒之際,妙善公主挺身而出割下手與眼。其孝舉感動上天,於是被賜予千手千眼,成為「千手千眼觀音」,從此她的生辰——農曆二月十九日被定為觀音誕辰。80 這個故事中融合了道教修仙和儒家忠與孝的元素,觀音當時更被納入道教神祗,化為「泗州大聖信仰」。81 隨着各類觀音顯靈的小說及傳說出現,觀音亦因着民眾的生活需求被賦予了更多功能,如送子、招財、治病、消災等,其以女性為主角的故事背景亦吸引了不少女信徒,直到觀音信仰傳入香港後仍然受女性崇拜,參與觀音誕的女性眾多。82 可見,中國神祀的形象是百姓生活和帝皇統治思想等方面的投射,觀音信仰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觀音信仰傳入香港的時間及過程難以追溯,但水上人與客家族群應為主要推動者及參與者。首先,觀音在印度時便是受漁民崇敬的神祗,其原始神職就是在海上救難,所以觀音信仰傳入中國後依然會受水上人及航海的商客歡迎。宋代及後,往來經過觀音信仰中心——普陀山的商客和漁民都會上岸向觀音祈福後才繼續行程或工作,因此他們很有可能把觀音信仰帶到經過或扺達的地點,這也能證明為何香港供奉觀音的寺廟在沿海地區較密集,而且部分沿海地區更會大肆慶祝觀音誕,例如白沙灣、大澳等。83 當中,白沙灣村會於農曆六月十九日的觀音得道日舉辦觀音誕慶典。主要目的是配合當地漁民的出海日程,錯開新年前後和捕漁期,讓他們在回港避風時再籌辦活動。白沙灣觀音誕最有獨有的環節便是進行「焚燒大士王」的儀式,據稱這是由於漁民在海上漂泊,常遇神鬼之事,因而需要通過道教儀式祈求觀音驅散邪祟。84
另一觀音信仰的集中地是客家族群居住的地區,他們也是傳揚觀音誕習俗的重要群體。客家人因戰亂和天災進行南遷時,帶同能夠庇佑自己的神祇到達香港等地,當中包括觀音,所以部分客家村落會在農曆二月十九日舉行觀音誕慶典,進行搶花炮、舞麒麟等活動。85 所以,觀音誕的儀式及紮作元素會具有族群或地方特色的。
第二節:觀音誕紮作元素的發展
除此之外,觀音誕紮作元素的多樣性與觀音的多重神格相關。因為觀音傳說及顯靈故事一直沒有一個固定的框架與版本,以致其原型一直難以有準確的定論。故觀音雖然在根源上為佛教神祇,但後來糅合了道教和儒家的色彩,被人們賦予了不同的神性,形成香港民間流傳的觀音信仰。由於民闁信仰的規條限制較少,部分圍村村民或漁民不會仔細區分佛教與道教觀音,寺廟中亦會將兩者同列,例如蕉徑龍潭觀音古廟。86 觀音的形象也因而千變萬化,除了前文的「千手千眼觀音」,還有「送子觀音」、「南海觀音」等,祂們有各自的神職,以回應民眾的訴求,部分更融入於花炮當中。87 神誕中所應用的紮作種類繁多,但花炮、花牌、醒獅和麒麟是過程中必不可缺的元素,故以下將集中分述這四項紮作元素。
花炮
花炮常在香港觀音誕的「搶花炮」活動中出現,唯有關花炮的起源與傳入香港的機遇缺乏文獻的支持,難以考證。最早的記錄稱明朝景泰三年(1452年)三月初三的北帝誕,佛山祖廟前有「搶花炮」這一環節,可見花炮自明朝起便是神誕的傳統元素。88 若從中外貿易的歷史來看,香港神誕使用花炮的民俗從廣東傳入的可能性較大,因為香港自古便是來往廣州的關口之一,中外商人補給站、交易點或轉口港,加上清末民初廣州炮竹商常經香港轉銷貨品到新加坡、荷蘭等國,1920年代末又有炮竹廠遷至香港,所以「搶花炮」的習俗或許是通過兩地的商品貿易而傳入香港的。89
在香港,花炮的種類與樣式五花八門,香港歷史博物館曾概括過該紮作品的主要特徵:
花炮是用竹架和紙製成的流動神廟,內設供奉有神像的神龕,而花炮上掛滿生薑、柏葉、燈籠、麒麟、龍及鳳等寓意吉祥的製飾品,並飾有紙花及紙製的五虎將、紫微、八仙等神像,是神誕慶典時用酬神的紙紮供品。90
以上所列的裝飾品各有寓意,花炮的形制也有不同,全憑紮作師傅配搭。
香港花炮大致分為小型花炮及大型花炮兩種:小型花炮一般高4呎至20呎,大型花炮的高度達30呎至40呎,主要分為炮頂、炮身和炮躉三部分:炮頂會冠上花炮會名稱,同時以蝙蝠或孔雀開屏的圖紋作裝飾,有富貴興隆、驅邪的寓意及作用;炮身有1至8層不等,「不同尺寸的花炮有不同的比例,越高的花炮就越闊,不能不斷加高,只加高的話花炮會太『瘦』,所以要一邊加高一邊加闊,即所謂『一闊三大』」91 ,同時伴有象徵「繼後香燈」的燈籠、意指圓滿的七彩魚等吉祥物作裝飾,也會擺放財神、紫薇神等各方神祇或粵劇英雄的塑像,觀音神像則會被放置預留好的「炮膽」之上。92
花炮中,第一炮至第三炮為最受歡迎的花炮:據民眾普遍的認知,第一炮為「財炮」、第二炮為「丁炮」和第三炮為最重要的「丁財炮」,所以它們的體積更大,裝飾品更鮮艷。以2023年上水古洞村觀音誕所列出的花炮為例,炮身放置了「南海觀音」的神像,以祈求眾人在疫情下都能平安渡過,部分掛上了生薑,代表該村落有人家添丁,其中「第一炮」的高度明顯比其他花炮更高,較為醒目,代表最具意義的花炮。93 每年觀音誕,紮作師傅會根據每一個花炮的主題自行搭配和設計,所以花炮的樣式十分多變。
在活動形式方面,在早期的神誕期間,「搶花炮」是由主辦方準備好竹籤、木片或掛上鐵環的紅綢球等代表花炮的物件,並標上不同的號碼,然後用火藥從竹筒中發射到空中,落地後眾人開始搶奪,再按照奪得的編號領取紙紮花炮及對應的觀音像回到各自村落供奉,於次年「還炮」。94 可惜因過往神誕舉辦「搶花炮」時屢次發生衝突及騷亂,尤以天后誕情況較嚴重,例如1983 年榕樹灣天后誕的警民衝突、1984年南丫島索罟灣天后誕擲石的混亂等。95 為避免同類事件發生,加上政府於1967年起禁止民眾存有煙花炮竹,搶花炮的形式開始以抽籤代替,一直沿用至今。96 2023年的古洞村觀音誕「抽花炮」活動共有十個社區組識參與,包括古洞義和堂花炮會、蕉徑聯合堂花炮會等,聚集了不少圍觀市民,氣氛熱烈,為疫情緩和後的神誕活動「打響頭炮」。活動過程中,各組織會輪流展示自己的花炮,參加者也會互相分享彼此近況,反映人們對生活滿足與期盼,使花炮活動成為社區聯誼的平台,增加社區凝聚力。97
獅頭與麒麟頭
獅頭與麒麟頭同為觀音誕常備的紮作品,其樣式、面貌五花八門,蘊含着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歷史意義。中國舞獅的傳統可上溯至漢代。《漢書‧西域傳下》提及文景之際「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食羣於外囿。」98 這便是中國對獅子最早的記載。後來,有人模仿獅子的神態、動作舞動,北魏時期的一次候佛誕巡遊便有人披上獸皮裝成「辟邪師子」在隊伍前引路。99 及至唐朝,舞獅變成禮樂元素。當時,有胡人隨着絲綢之路到訪中國,向中國皇帝描述了獅子的外形、特徵,其後工匠據此以紙製成仿真獅子,並聘用了雜技藝人進行舞獅表演。100 《通典‧樂六》所載的「太平樂」便描述了該活動的概況:
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師子摯獸,出於西南夷天竺、師子等國。綴毛為衣,象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拂,為習弄之狀。五師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抃以從之,服飾皆作崑崙象。101
這便是「北獅」的由來。
舞獅流傳到民間後隨着中原移民的流動在南方衍生出另一種流派——「南獅」(亦稱「醒獅」),當中又主要分為「佛山裝」與「鶴山裝」,前者為現時香港觀音誕最常用的種類。102 五代十國(907-960年)及後,中原陷於亂局,加上後來蒙元入主當政,當地居民紛紛南遷避禍,把北獅文化帶往嶺南地區,衍生出南獅文化,以廣東為中心進入萌芽期。103 及至明清時期,「以怪治怪」、「舞獅拜年」和「食青反清」的傳說出現,民間開始在重大節日以舞獅辟邪和助慶,獅頭紮作行業隨之被帶動。104 上文所提及的佛山,正是南獅紮作流行的地區之一,現時的香港獅頭紮作也大多來自該地,而香港本地相關的店舖則只有零丁數家。105
有關麒麟的歷史,甲骨文上曾記錄着當時在戰爭中擒獲的「白麟」,證明麒麟文化從殷商時期(前1600-前1046年)便已開始。106 《史記》曾記載孔子看見被捕獲的麒麟後感嘆「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107 ,既是表示自己不久於人世,也是在暗示盛世不再。自此,麒麟成為了天下太平的象徵,並衍生出各種麒麟的圖騰與辟邪的雕像,不過一直未見有相關的擬獸作品出現。108
直到唐朝,宮廷中出現了讓驢模仿麒麟的遊戲:「今餔樂假弄麒麟者,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109 ,這是麒麟首次具象地出現在人們眼前。此後,再次出現模仿麒麟的活動可能是明朝皇室的「麒麟聖舞」,這個宮廷儀式在明朝滅亡後被管理文娛活動的官員帶到民間,廣為傳授,後來掌握技藝的客家人在南遷時將這門手藝帶到深圳及香港,於是在節誕舞麒麟成為了他們的習俗。110 民國時期,麒麟紮作技藝開始定型,因為當時的麒麟是「以紙糊麒麟頭,畫五彩」再「縫錦被為麟身」,最貼近現代客家麒麟的形態。111 從舞獅與舞麒麟的歷史源流可見,紮作的發展歷程反映族群遷徙及社會變遷的軌跡。
獅頭紮作的步驟分為紮作、撲紙、寫色和裝飾:先以竹蔑、鐵線、膠篾及漿糊紮成醒獅的輪廓及框架,即行內所稱的「囊」,然後依次從獅頭背部裹上紗紙和綢絹,再為獅頭著色和加上花紋,並「上光油」,色彩主要按照所代表的角色搭配:例如黃底五彩紋的劉備獅、紅底黑紋的關羽獅、以黑白為主調的張飛獅、綠底黑紋的趙雲獅等等,最後把眼珠、獅口、獅耳等配件裝上,才算是完成了整個獅頭紮作。112 麒麟頭紮作與獅頭紮作的流程相似,其中以「施彩」最考驗紮作師傅的創意與色彩搭配技巧,例如調色、撞色等,但普遍較常用淺色作底色,例如白色、淡黃色等,從而突出彩色的花紋,而如果用紅色、紫色等較艷麗的顏色作主色,就要考慮以「撞色」來凸顯麒麟頭上的彩花,以描繪麒麟的神韻。113 2023年古洞村觀音誕期間,便有劉備獅、關羽獅等舞獅亮相,而麒麟有白底彩花的,也有黑色與黃色作配搭的。114
舞獅與舞麒麟一直是節慶期間的傳統項目,因為「獅」本身具有驅邪降福的能力,所以人們總希望以其祈求消災除害、求吉納福,這對於出海作業又要面對諸多變數的水上人而言十分重要。115 而麒麟除了是客家文化的象徵,其本身也是化解煞氣的瑞獸,是太平盛世的象徵,所以觀音誕會以舞麒麟作為人們對平安生活的盼望。116 它們能夠襯托出節日氣氛,也可以凸顯水上人的生活與客家文化的獨特性。
花牌
對於花牌的由來,坊間有諸多猜測:一則指其為節慶籌辦者按照中式牌樓的模式紮成的活動出入口,二則指出這是仿照宮廷吉祥裝飾創造出來,讓活動順利舉辦的工藝品。117 而就現時花牌的應用情況來看,兩者皆有可能:因為現時大部分節慶活動的花牌都擺放於出入口處,以及在內場進行排佈,並附上吉祥的圖紋與祝福語。蔡榮基師傅曾提及香港花牌最早約見於百年前,「當時的樓房大多只有一層,掛一個花牌上去,等同高了一倍,鶴立雞群,宣傳效果卓越」,它們起初會以鮮花及紙花作為材料的一部分,其中文字也是以手寫字為主。118 香港的花牌紮作從四十年代開始便已經被用於各類場所,例如誕辰和店舖開業典禮。119 五、六十年代始,花牌日漸開始流行於婚禮、節慶等各種喜慶的場合,然後在七十年代踏入黃金時代,當時業內有逾一千名工人,「熟手工人」月薪可達400多元,「普通工人」則能月入300多元,即使是初始學師的工人每月也有150元作工資,可見當時花牌紮作行業的盛況。120
花牌「以竹及竹籤為支架,配以真花或假花、各式紙類及布料作裝飾,用於紅白二事如節慶、婚禮、開幕、喪禮等」121 ,是香港常見的紮作品,也是觀音誕會出現的必需品,其中的形制和文字都值得探討。近代花牌的形制沒有太多限制,但講求平行、對稱,牌身可達20至30呎,主要以「鳳頂」、「銻花」、「珠」、「龍柱」、「兜肚」、「四方包」和「長」構成,由師傅按照場地空間進行排列。122 功能上,觀音誕花牌有宣傳、指引和祈福的作用,例如2023年古洞村觀音誕村口有花牌指示「早上十一時前往蕉徑龍譚古廟進香」,讓參與者了解活動流程。123 內容上,觀音誕花牌大多會寫上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酬謝神恩等吉祥的祝福和對觀音表示感恩的話語,以及贈送花牌的社會組織和製作花牌的機構。花牌上能夠表示各個組織對觀音誕的敬賀,與他們對觀音的敬仰及感激。
第三節:傳承紮作技藝的挑戰
隨着時代更迭,社會的新興事物層出不窮,人們的消費欲望日益增長,所以大多年輕人會傾向選擇高薪及穩定的工作。傳統節慶的參與者也主要集中於中老年人或固定族群,加上新一代缺乏對傳統事物的了解,對傳統節慶活動提不起興趣。因此,大眾對觀音誕紮作的關注度不足及尚未明朗的就業前景就是傳承觀音誕傳統紮作品的挑戰。
觀音誕紮作的傳承與民眾對紮作行業的刻劃印象和對傳統節慶的熱情減退有很大關係。人們每每看見紮作舖,難免聯想到清明節、重陽節、盂蘭節等與鬼神和祭祀相關,令人心生忌諱的節日,長此以往使人們對紮作行業望而卻步。之所以會出現這個現象,其一是歷史遺留問題,其二是新一代仍缺乏更直接的平台接觸該項工藝。在以往的記載中,紮作品更多是作為祭品或陪葬品出現,節慶紮作也主要以中秋節及七夕節中的花燈為主,甚少提及花炮和花牌。124
而且,近代年輕人對西方節日的熱情比中國傳統節慶,導致不少節日儀式被精簡,例如古時的七夕節有花燈把玩,但現代情侶卻大多更願意在西方的情人節期間互贈禮物,可見西方的節日比傳統節日的吸引力更大,所以他們對觀音誕的了解不會太深入。在儀式方面,觀音誕的儀式看似一直被完整地保留,但礙於安全問題,「搶花炮」的儀式以較溫和的抽籤代替發射炮竹。125 當然,適當地跟隨社會需要改變活動形式能夠令傳統文化延續,但往昔熱烈的氣氛卻再難重現。
此外,紮作行業的就業前景與金融業、醫護業等主流行業相比,較為迷茫。從業人士一般須經過數年的「學徒制」,待師傅退休再接手經營,學習的年期較長。過去,物價平穩,市民物欲較低,求職不會預先考慮職業前景,有收入便已足夠。然而,時移勢易,行業的薪酬、未來發展和穩定性都成為吸引年輕人入行的關鍵。而且,他們期望在工作中得到滿足感,但每一個紮作品的製作流程都是漫長的,只有成品出現後才能獲得一刻的成功感,及不上即時的回報。而對於從業人士而言,他們雖然樂於培養下一代傳承人,亦頻頻在校園推廣紮作技藝,但真正投身行業的年輕人似乎仍然不多。
至於有關市區城市發展會否壓縮了紮作技藝生存空間的問題,冒師傅指出不論新界還是市區,只要傳統節慶依然存在,就會有紮作品的出現。126 因此,觀音誕紮作的傳承主要是先提高年輕人的興趣,持續地進行文字記錄,擴大紮作品的應用層面,才能使其在節日與祭禮之外出現在大眾視野,吸引人們關注。只是,民間的力量始終較單薄,所以政府的支援十分重要。127
觀音誕紮作歷史悠久,是水上人與客家人的生活投影,具有文化價值,因而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觀音誕」與「紮作技藝」在清單中雖然分屬於「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及「傳統手工藝」,但能夠互為彼此的載體。納入清單後,民眾可以通過官方平台系統地知悉現存的傳統文化習俗,不少民間團體亦開始從不同的渠道推廣觀音誕及相關紮作,其形制也為了適應時代變遷在保留傳統底蘊的前提下進行材料和呈現形式的創新。
第一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義
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提及非遺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達、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同時將其劃分為「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表演藝術」、「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及「傳統手工藝」五大類別,以便系統地管理與保護,即進行「確認、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傳承和振興」,各國紛紛響應加入。128
2006年,香港緊隨世界步伐應用《公約》內的條款,於香港文化博物館設置「非物質文化遺產組」,該組織後於2015年被升格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於次年在三棟屋博物館設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129 民政事務局亦於2008年成立「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或稱「非遺諮委會」)督導非遺之普查及保護事宜,下設「非遺資助計劃委員會」及「非遺項目委員會」分別負責各非遺項目的運行及非遺清單的研究、出版和更新。130 機構組織上的改變使香港對非遺項目的管理和保育逐漸成熟及系統化,為本土傳統文化提供有利的發展空間。
為盡量完整地保留有價值的傳統文化,民政事務局在非遺諮委會成立之初便提議編製清單,特此將本港調查地區劃分為「普查範圍A(A區)」及「普查範圍B(B區)」,開展「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131 經公開招標後,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分別於2009年8月及2010年2月開始B區與A區的調查工作,分為「文獻資料搜集」和「實地考察和口述歷史調查」兩個部分進行,從各機構之文字記錄、檔案、視像資料與實地田野研究考察本土傳統的流傳情況。132 及至2013年,研究中心整理出約800個項目的資料呈交至非遺諮委會,再經歷該委員會之審議及為期4 個月的公眾諮詢,最終統整為「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共囊括480個非遺項目,上水蕉徑、白沙灣與大澳的「觀音誕」也在其列。133 當中,包括「紮作技藝」在內的20個「具有高文化價值和急需保存的項目」更於2016年被非遺諮委會推薦納入「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並最後於2017年8月14日確定公布。134
2018年,非遺辦事處獲批3億元推行「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協助傳承人及傳承團體進行「社區主導項目」與「伙伴合作項目」,同時建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加強對非遺的保護和普及。135 清單與名錄之訂立使政府能夠針對及有序地就各個項目制定保育計劃,爭取各界財政及人力資源的支持,以確保本土文化不會在日新月異的社會環境中被淘汰或流失。資料庫成立至今已錄入「獅頭紮作技藝」、「花牌紮作技藝」、「舞獅」、「舞麒麟」等與觀音誕相關的節慶紮作與活動,觀音誕與花炮紮作雖暫未被收錄於資料庫與國家級非遺,不過這並不代表其文化與歷史價值遜色於其他項目。因為前者是客家人與水上人的文化標誌,而後者作為紮作品之一支撐着整個神誕儀式的推進,甚至「支持整個民族的生活」136 。
香港非遺項目在保育時可以獲得更多社會和政府資源,維持相關商舖的營運和進行民間推廣計劃,取得公眾關注,而是次論文中所提及的兩個主體作為官方保護的首要目標自然也會受益,但也難免受疫情影響。
第二節: 疫情下的觀音誕慶典
2019年,新冠病毒肆虐,不少大型節慶活動的儀式被簡化,甚至被取消,節日安排難以確定,觀音誕亦同樣受到波及。在2020至2022年間,白沙灣觀音誕只在2021年舉辦了「八仙賀壽」的演出,其他活動環節均被取消,但觀音古廟仍遵照防疫規例有限度地開放,供信眾進香。137 上水古洞村則透過保留觀音誕特色神誕活動,繼續慶祝觀音誕,例如舞麒麟、搶花炮等,亦有紮作花牌以作宣傳,唯這一段時期的記錄片段顯示參與情況不及疫情以前熱鬧。138 時至2023年,古洞村首先大肆復辦觀音誕慶典,吸引大批群眾參與,往昔盛況才得以重現。139 可見,基於防疫條款下的種種限制,疫情對觀音誕期間的大型慶祝活動影響頗深,亦令所須的紮作品大大減少。
觀音誕慶賀儀式的簡化非單單削弱過往濃厚節日氛圍,還會使觀音誕紮作的普及度大大減弱,可能會影響其傳承的進程。首先,神誕活動是鞏固觀音信仰的重要渠道。有傳統信仰的民眾會根據神明的威力和其所給予的回報而對該神明有不同程度的責任感和依賴,故此對於不同神誕的參與度各異。140 在參與度與籌辦情況方面,從以上情況分析,客家人似乎更重視觀音誕,所以即使在疫情下仍然極大程度地保留了大部分紮作元素及傳統活動,維繫着族群獨特的人文精神。因此,為了讓其變成家族或族群內代代相傳的信仰,借助神誕活動鞏固及延續該信仰,增強善信對自己身份認同是必要的。
其次,文化的傳承需要延續性,一旦出現停頓,便可能會出現許多變數,觀音誕的傳統禮俗便是例子之一。以「搶花炮」為例,鄧家宙博士曾在接受訪問時指出:「此文化習俗在疫情下面臨沉重打擊,年長者感心淡,少數弟子無法維生被迫轉行」,並對復辦後規模萎縮及停辦成為常態的可能性表示擔憂,認為需要新一代及時以文字配合現存的建築進行記錄。141
不過,觀音誕既是流傳多年的傳統節日,理應不會輕易就此停辦。加上,疫情期間,民間組織及歷史機構均有進行出版或舉行相關活動,持續向公眾普及觀音誕的資訊。出版方面,《觀心自在:香港觀音誕與觀音信仰探源》十分具代表性,因為它詳細向大眾介紹了觀音信仰的由來、觀音的種類、香港觀音信的流傳情況等資訊,並於第一屆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中得奬。142 活動方面,「香港節慶與民間工藝」專題展覽在疫情期間間接為大眾提供了關於觀音誕紮作品特點與源流的資料。143 香港佛教聯合會與香港菩提學會依然堅持舉辦「觀音文化節」,按照不同的主題為大眾提供了關於觀音信仰的信息,讓他們明白觀音文化的社會價值。這些都成為了傳承觀音誕及其紮作的關鍵。
第三節:觀音誕紮作的創新
對傳統紮作品進行創新也是振興和保護花炮、獅頭、麒麟頭、花牌等觀音誕紮作的關鍵。這與紮作師傅的經營理念和風格息息相關,他們所製作的紮作品在色彩、配飾和形制方面都各有千秋,所以更新的元素也是因人而異。另外,紮作品的改變也須順應各族群的喜好及環境,導致其中所運用的材料與從前的作品大相逕庭,使這項技藝得以在現代社會繼續存活。
上文曾提及有鑑於「搶花炮」的危險性,現時的觀音誕改以「抽花炮」的形式繼續,這是基於社會安全的顧慮。除了活動形式上的變化,花炮的形態自傳入香港後便形成了本土特色。由於其所應用的場合主要是神誕慶祝,所以往往會以精美作為製作標準,成品也以大型花炮為主,裝飾元素基本上沒有太多變化,一直沿用傳統的吉祥物。不過,花炮供應源頭和製作地點卻不斷變遷:紮作業的全盛時期,香港紮作店皆會親力親為承包花炮的製作,但後來這一門手藝隨着工廠和人手遷移至內地,加上在城市發展下,紮作師傅要尋找合適店舖落地生根實屬不易,冒卓祺師傅也曾面臨此困擾,於是他「先是在街市置舖,但經常收到投訴;其後搬到屯門工廠區,又因搬運不便,最後搬遷到元朗白沙村」。144 至於花炮紮作是否最終會沒落,應視乎其本身的民俗價值:只要觀音誕仍然保留「抽花炮」的習俗,花炮便不會流失。
至八十年代始,獅頭便一直革新,務求在降低成本的同時使其形象更生動、更輕巧。過去,香港的獅頭紮作沿用中國傳統的樣式,以歷史人物作為創作原型,獅頭以雄壯威猛的色調和造型為主,但後來卻被形象温和、價廉、輕便、款式多樣的馬拉獅取代了其主流地位,導致本地獅頭紮作在此期間沉寂。145 於是,如何吸引大眾訂購及欣賞香港獅頭紮作便成為各獅頭紮作師傅的首要考慮。
因此,新一代傳承人不再固守舊有的框架,從顏色和展示形式開始革新,令傳統獅頭紮作能夠有更高的曝光率。以許嘉雄師傅為例,他對於獅頭紮作有較新穎的理解:
舞獅過去只允許男性参與,傳統認為屬於女性的顏色,如粉紅色或紫色是不會用於獅頭上,但隨着舞獅由武館獨有文化變為大眾運動,現在甚至會出現水晶獅和Hip Hop獅等合作,現在的獅頭創作可以說是沒有限制的。146
獅頭不但能夠與流行元素結合,有時還可以與時裝設計相融合,例如2020年《匠藝古今》展覽中的展品——「再世盧亭」便是以香港獨有的神話人物盧亭為基礎,結合傳統又具威嚴的獅頭和富有現代美感的魚尾製成,魚尾的每一部分都能在拆分後裝扮到身上,傳統與犘登的碰撞賦予了獅頭紮作新的生命。147 而麒麟頭則在不改變外形與神獸特徵的前提下,從顏料、圖案、原材料等方面作出適當調整,例如以廣告彩代替瓷漆、利用機器生產沙紙等,從而豐富及加固紮作品,使其製作程序更有彈性。148
至於花牌的創新,則主要集中在其呎吋和材料。「李炎記」花店的學徒針曾就當今社會重視效率的現象和縮窄的城市空間,提出了許多花牌的改良之處:例如花牌上的棉花字和手寫字可改由電腦打印、製作可放置於室內的小型花牌。149 除此以外,過往花牌上的真花及紙花都改以銻花,燈飾也以亮度較高和較環保的「LED燈」取代鎢絲燈泡。150
傳統大型花牌常出現於節日期間,年輕人在日常實在難以接觸,但若結合文學及視覺藝術的元素舉辦校內活動,吸引學生參與,便可以提升他們對傳統花牌紮作的興趣。聖士提及書院的學生曾在「南區文學徑:創意寫作及花牌創作計劃」中與黃乃忠師傅學習紮作工藝,其後在花牌中加入西洋技法畫成的白鴿與梅花,使作品成為中西合璧的新花牌。151 這些改變其實都是為讓傳統節慶紮作在不改變其風貌前提下融入現代社會潮流,更好地代代相傳。
本論文討論香港紮作與傳統節慶文化的研究,並以觀音誕紮作為個案,通過講述紮作技藝與觀音信仰的緣起、傳入香港的契機、文化意義、公眾重視程度及創新之處,藉此突出觀音誕紮作的傳承與保育價值。
本論文以書籍、文章、報章等各類資料記述觀音誕紮作的歷史進程。在講述香港紮作技藝發展過程的部分運用了不少報章,如援引〈訪問紮作工人〉、〈紮作工友注重技術〉等篇章,以當時的報導直觀地證明紮作行業曾為香港的重要產業之一。在專書及文章方面,筆者在敍述觀音信仰的歷史時着重使用了李利安教授的《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播》、〈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體系〉等著述。在提及觀音從「男身」到「女身」的轉變時引用了《中國觀音史》、〈觀音形象在漢地女身化的途徑與原由〉等資料。在歷史記錄與前人研究中,觀音誕和紮作技藝鮮有被同時提及,即使有記錄也只粗略介紹,未有強調兩者的聯繫。但整合這些片段後,其實不難發現觀音誕一直是中國傳統節慶紮作的展示平台之一,而紮作品也是觀音誕的文化符號。
本論文首先追溯中國傳統紮作的來龍去脈,以及其傳入香港後的發展,指出中國傳統節慶與紮作技藝密不可分的關係。文中提及紮作的出現可能並非是為祭祀或慶典,而是基於古人對軍事通訊的需求,但真正讓紮作進入興盛期的是傳統節日。因為人們為營造節日氣氛創作的「燈山」、「佛山大爆」等紮作品受人歡迎,感染力更強。所以,即使香港社會和經濟結構不斷變更,紮作行業也不曾被淘汰。
而後,本論文從觀音信仰的流傳及香港觀音誕紮作的特點出發,指出節慶紮作是社會結構與百姓生活變遷的象徵。正如觀音男身與女身的變換是為了適應社會男女對生活的訴求,同時對於女性統治者而言,女身觀音是對政治地位的認可。到了香港,觀音誕展現出較強的地域性,每個族群慶祝觀音誕都有一定差別,例如水上人會焚燒大士王、客家人會舞麒麟等,過程中所使用的紮作品都是族群的文化符號,難以取代,這也是觀音誕紮作的研究意義所在。因此,為了更好地保護及宣傳紮作技藝與觀音誕,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香港佛教聯會、香港菩提學會等相關機構都在疫情期間堅持向公眾發佈相關資源。紮作師傅亦與時並進,在材質、式樣、工具等方面尋求創新,繼而使紮作技藝吸引更多年輕人注意。
總括而言,觀音誕紮作種類繁多,幾乎囊括了所有的節慶紮作品。雖然該研究尚未能盡述,只能集中以花炮、獅頭、麒麟頭與花牌作為諸多紮作中的代表,但足以說明觀音誕對紮作技藝傳承的重要性。而這些紮作品背後代表的不止是中國傳統工藝的延續,更是從古到今人們生活的印記,十分值得世人持續關注。
附錄一:香港觀音誕期間女信眾參拜之盛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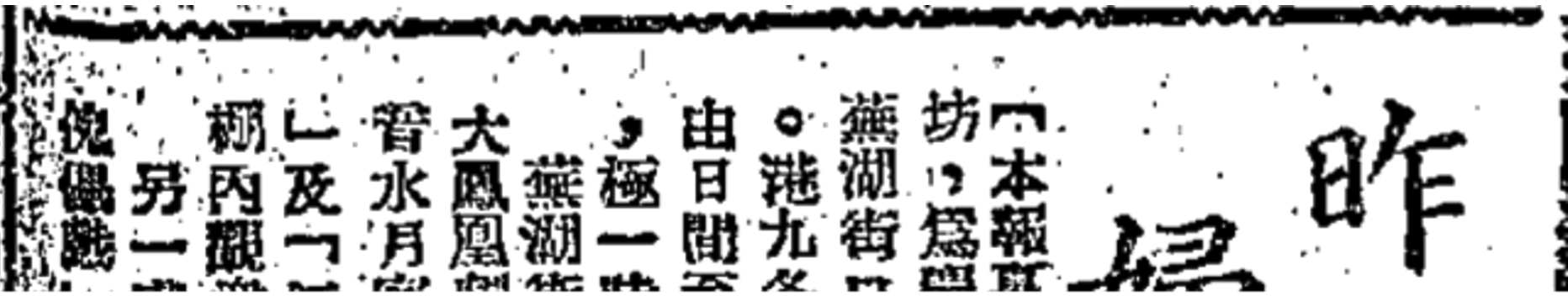
附錄二:香港紮作業聯會主席冒卓祺先生訪問
受訪者:冒卓祺先生(香港紮作業聯會主席、紮作店「祺麟店」創辦人)
訪問日期:2023年3月10日
訪問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2時40分
訪問地點:上水古洞村
訪問紀錄:
1. 麒麟紮作一般流程會包括紮骨架、貼紗紙、施彩等等,師傅過去探訪曾提到施彩的部分會花較心思,可不可以詳細介紹一下傳統麒麟施彩有甚麼注意事項,例如傳統上約定俗成的配色?
麒麟一般以白色、淡黃色、綠色等淺色為主。有部分師傅會用紅色,但這三種顏色運用得較多。例如白底是淺色,畫甚麼、畫任何色都可以上色,色彩便能被顯現出來。因為是白色打底,「畫七彩就有七種顏色」,但如果是紅色打底便少了紅色,要考慮撞色。
2. 白沙灣在觀音誕期間有「焚燒大士王」的儀式,但古洞村卻沒有,原因為何?
因為那裏(白沙灣)有一個道教儀式,會請喃嘸進行。例如明天觀音誕,今天就請喃嘸師傅前來誦經、超幽。因為水上人生活在海邊,可能「靈異」事件或故事較多,他們亦「很相信」神鬼之事,所以趁着觀音誕的大日子請喃嘸師傅前來誦經、超幽。
3. 紮作在新界一帶的生存機會是否比市區更多?具體的原因為何(例如歷史因素、市區城市空間狹窄等等)?
不是。因為紮作任何中式節日,任何宗教節日,或喜慶節日,又或康文署、非遺辦事處舉辦的年宵、中秋活動都會被使用,不一定新界才會更多。
4. 傳統節慶的存在是否能夠讓紮作技藝一直被社會需要?除傳統節日和喪葬外,紮作是否還有其他展示的平台?
這個問題要視乎從業員或師傅如何看待自己的手藝和非遺項目。這些事件「很個人」,沒有規定紮作有(展示的平台)後其他項目就能有(展示的平台)。這個首先需要政府部門的配合,其次是傳承人的個人想法。
5. 紮作技藝被列入非遺後是否對推廣及傳承紮作技藝帶來了一定的好處?具體例子為何?
紮作技藝被列入非遺後的確帶來了一定的好處。首先是讓更多人重視、關注及認識,因為有官方部門用文字,用書寫的方法介紹這一種文化。我們只能講述與分享製作方法、習慣,至於撰寫文章,以文字教授這些文化則需要相關的政府部門或學術機構去做會較理想。因為我們只是分享自己的經驗,但要編輯成文字,翻譯成各種語言,讓更多人認識香港紮作要依靠多個部門的配合,單單依靠我們是不足夠的。
附錄三:蕉徑龍潭觀音古廟內的各式觀音造像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2023年3月10日實地考察。
附錄四:2023年上水古洞村觀音誕花炮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2023年3月10日實地考察。
附錄五:2023年上水古洞村觀音誕「抽花炮」儀式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2023年3月10日實地考察。
附錄六:2023年上水古洞村觀音誕舞獅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2023年3月10日實地考察。
附錄七:2023年上水古洞村觀音誕麒麟頭紮作

附錄八:2023年上水古洞村觀音誕花牌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2023年3月10日實地考察。
附錄九:2023年上水古洞村觀音誕盛況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2023年3月10日實地考察。
中文資料
政府檔案:
1.〈CB(2)1090/08-09(01)號——全港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2009年3月20日資料文件。
2.〈CB(2)1448/17-18(01)號——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博物館措施提供資助〉,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2018年5月28日討論文件。
3.〈CB(2)842/16-17(01)號——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草擬名單〉,民政事務委員會2017年2月27日討論文件。
4.〈CB(2)855/16-17(06)號——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草擬名單〉,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2017年2月27日的會議。
5.〈CB(2)957/10-11(03)號——全港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進度報告〉,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2011年2月11日資料文件。
6.〈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828638/First_hkich_inventory_C.pdf,瀏覽日期:2023年1月13日。
7.〈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the_representative_list_of_hkich.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3日。
8.〈第8067號公告——職工會條例(第332章)〉,職工會登記局2008年11月12日公告。
古籍:
9.[漢]班固,許東方校訂:《漢書》。台北:宏業書局有限公司,1992。
10.[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1970。
11.[西秦]沙門聖堅譯:《佛說羅摩伽經》。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21。
12.[北魏]楊衒之,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3.[北魏]曇無讖:《悲華經》。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18。
14.[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21。
15.[唐]杜佑,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全12冊》。北京:中華書局,2016。
16.[唐]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
17.[宋]天息災譯:《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上海:佛學書局,1935。
18.[宋]吳自牧:《夢粱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9.[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20.[宋]高承撰,[明]李果訂:《事物紀原》。北京:中華書局,1989。
21.[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
22.[清]曼陀羅室主人:《觀音菩薩的故事》。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23.[民國]陳伯陶:《東莞縣誌》。台北:成文出版社,1912。
書籍:
24.于君方著,陳懷宇、姚崇新、林佩塋譯:《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25.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8。
26.元建邦編:《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27.王國華主編,何佩然、彭淑敏等著:《香港文化導論》。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
28.司徒嫣然:《市影匠心:香港傳統行業及工藝》。香港:香港市政局,1996。
29.弘學編:《妙法蓮華經》。成都:巴蜀書社,2002。
30.石守謙、顏娟英主編:《藝術史中的漢晉與唐宋之變》。台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
31.吳燕:《中國觀音文化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32.李利安:《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播》。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33.李孝聰:《中國區域歷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34.周子峰:《葬之以禮:香港殯儀文化初探》。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0。
35.施志明:《本土論俗——新界華人傳統風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
36.徐藝乙:《風箏史話》。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2。
37.秦宏:《香港工業設計史》。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12。
38.高寶齡:《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香港》。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
39.張一兵點校:《深圳舊志三種》。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
40.陳子安:《漁村變奏:廟宇、節日與筲箕灣地區歷史(1872-2016)》。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
41.陳守仁:《香港神功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
42.陳桂洲:《扎作:承‧傳》。香港:鼎豐文庫,2007。
43.超媒體編輯部:《香港獅藝傳奇》。香港:超媒體出版有限公司,2015。
44.黃競聰:《城西溯古——西營盤的歷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2。
45.黃競聰:《簡明香港華人風俗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
46.葉春生:《廣府民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
47.劉繼堯、袁展聰:《武舞民間——香港客家麒麟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8。
48.蔡志祥、韋錦新編:《延續與變革: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
49.蔡志祥:《酬神與超幽:節日和香港的地域社會》。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
50.盧維幹:《大慈大悲觀世音》。香港:華人廟宇委員會,2016。
51.霍松林、趙望秦主編:《宋本史記注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52.駱慧瑛:《觀心自在:香港觀音誕與觀音信仰探源》。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20。
53.關宏:《佛山彩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54.StellaSo:《粉末都市——消失中的香港(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
期刊:
55.王敏:〈菩薩造像的中性化與觀音造像的女性化〉,《民族藝術》3期(2011年8月),頁125-127。
56.朱光磊:〈觀音形象在漢地女身化的途徑與原由〉,《世界宗教文化》6期(2016年12月),頁67-70。
57.李利安:〈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體系〉,《人間佛教》34期(2021年7月),頁68-79。
58.李志清:〈儀式性少數民族體育在鄉土社會的存在意義(三)——族際交往中的搶花炮〉,《體育科研》27卷6期(2006年11月),頁10-18。
59.李欣:〈中土觀音女性化成因別釋——兼議漢文明「乾坤並建」之教化原則〉,《世界宗教文化》6期(2016年12月),頁71-77。
60.李紅:〈佛山彩燈傳承和創新的若干思考〉,《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37卷4期(2022年7月),頁1-9。
61.邢金善:〈非物質文化遺產視角下麒麟舞的傳承與發展〉,《山東體育學院學報》3期(2011年3月),頁44-47。
62.侯坤宏:〈觀音信仰的流傳與衍化〉,《人間佛教》10期(2017年7月),頁14-41。
63.梁正君:〈廣州陳氏書院建築裝飾工藝中的吉祥文化〉,《嶺南文史》2期(2003年6月),頁7-11。
64.温金玉:〈觀音菩薩與女性〉,《中華文化論壇》4期(1996年10月),頁86-91。
65.馮詩淇:〈淺析南獅運動傳統文化的創新與變化——以舞劇《南獅夢》為例〉,《藝術評鑒》5期(2019年3月),頁65-66。
66.黃慧瑩:〈廣東醒獅發展沿革及其存在問題與對策研究〉,《傳承》12期(2013年10月),頁136-137。
67.劉釗:〈「小臣牆刻辭」新釋——揭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祥瑞記錄〉,《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期(2009年1月),頁4-11。
68.薛源、王雨璿、陳楊梅、陳浩:〈傳統南獅的流派及其運動特點研究〉,《科技資訊》22期(2021年11月),頁177-180、183。
碩士學位論文:
69.周萍:〈東莞市清溪鎮客家麒麟舞的傳承與保護〉(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70.姜喜平:〈「南獅」歷史文化與發展現狀的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71.劉婕:〈近代省港煙花爆竹貿易研究(1859-1948)——以《中國舊海關史料》為中心〉(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
報章:
72.〈元宵花燈上市紮作工友開夜工〉,《華僑日報》,1960年2月9日。
73.〈扎作工會定期成立〉,《華僑日報》,1949年3月18日。
74.〈各界隆重慶祝孔聖誕辰永安街懸花牌慶賀〉,《華僑日報》,1947年8月27日。
75.〈油牛洋燭紮作工人要求加薪〉,《香港華字日報》,1922年11月13日。
76.〈花牌紮作旺〉,《華僑日報》,1969年8月1日。
77.〈花牌紮作保留傳統嘗試求變〉(2016年12月31日),《大公網》,http://www.takungpao.com.hk/culture/text/2016/1231/50014.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6日。
78.〈花牌紮作就業工人增加年假告滿工作復趨繁忙〉,《華僑日報》,1969年2月21日。
79.〈南丫島索罟灣慶祝天后誕搶花炮滋事份子搗亂擲石擊傷多人〉,《華僑日報》,1984年5月19日。
80.〈昨日觀音誕婦女進香狂〉,《工商晚報》,1951年3月27日。
81.〈秋節節品實銷結算〉,《華僑日報》,1959年9月19日。
82.〈紙扎業公所成立紀〉,《申報》,1920年8月23日。
83.〈紙料紮作工友開始加時工作〉,《華僑日報》,1970年2月9日。
84.〈紙料紮作情形特殊亦工亦商半勞半資〉,《華僑日報》,1975年5月6日。
85.〈酒樓喜慶宴會特多花牌紮作工作轉旺〉,《華僑日報》,1970年1月30日。
86.〈紮作工友注重技術〉,《華僑日報》,1960年1月31日。
87.〈訪問紮作工人〉,《華僑日報》,1957年7月14日。
88.〈港九各區街坊居民籌祝雙十大典〉,《華僑日報》,1951年10月8日。
89.〈華商總會一番新氣象〉,《工商晚報》,1948年7月16日。
90.〈華達公司製十餘丈蜈蚣〉,《華僑日報》,1956年5月19日。
91.〈傳統花牌展現文學情懷〉,《經濟日報》,2012年4月13日。
92.〈榕樹灣祝天后誕搶花炮警民衝突三名村民頭破血流〉,《香港工商日報》,1983年5月6日。
93.〈慶祝加冕會景巡遊籌委會委員親出募經費〉,《華僑日報》,1953年4月19日。
94.佚名:〈一竹一紙傳統再現〉(2019年9月8日),《政府新聞網》,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9/20190906/20190906_145115_745.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4日。
95.宋霖鈴:〈創新傳統獅頭魚尾兩代紮作人合璧再世盧亭〉(2020年6月3日),《明報新聞網》,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9%AF%E5%88%8A/article/20200603/s00005/1591123562926/%E5%89%B5%E6%96%B0%E5%82%B3%E7%B5%B1-%E7%8D%85%E9%A0%AD%E9%AD%9A%E5%B0%BE-%E5%85%A9%E4%BB%A3%E7%B4%AE%E4%BD%9C%E4%BA%BA-%E5%90%88%E7%92%A7%E5%86%8D%E4%B8%96%E7%9B%A7%E4%BA%AD,瀏覽日期:2023年1月16日。
96.許宣白:〈「搶花炮」停辦兩載 百年傳統漸凋零〉(2021年5月6日),《文匯網》,https://www.wenweipo.com/s/202105/06/AP60933f80e4b0476859ba5381.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5日。
97.郭玉桔:〈港首間紮作展示館〉(2019年12月16日),《香港商報網》,https://www.hkcd.com/content/2019-12/16/content_1169938.html,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4日。
98.曾蓮:〈孝子承父業精益求精傳揚花牌工藝〉(2019年2月13日),《大紀元時報》,https://hk.epochtimes.com/news/2019-02-13/36644627,瀏覽日期:2023年1月16日。
99.蔣琳:〈記載社區變遷傳承紮作工藝元朗舉辦歷史圖片與花炮展〉(2017年6月29日),《香港商報網》,https://www.hkcd.com/newsTopic_content.php?id=1054917,瀏覽日期:2023年1月16日。
網上資料:
100.〈【傳統之美:花炮傳情】〉,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watch/?ref=external&v=1734459783367447,瀏覽日期:2022年12月28日。
101.〈古洞村-1953恭祝觀音寶誕酧神演戲委員會〉,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kttkyc?locale=zh_HK,瀏覽日期:2023年1月14日。
102.〈白沙灣觀音誕〉,香港記憶,=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local_festivals/festivals/lunar6/6_2/index_cht.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3日。
103.〈西貢白沙灣觀音古廟〉,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8%A5%BF%E8%B2%A2%E7%99%BD%E6%B2%99%E7%81%A3%E8%A7%80%E9%9F%B3%E5%8F%A4%E5%BB%9F/100064936624023/,瀏覽日期:2023年1月14日。
104.〈花炮及其裝飾元素〉,香港記憶,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tin_hau/TinHau_Flower/index_cht.html,瀏覽日期:2022年12月28日。
105.〈花牌紮作〉,傳耆,https://www.eldage.com/collections/%E8%8A%B1%E7%89%8C%E7%B4%AE%E4%BD%9C,瀏覽日期:2022年12月29日。
106.〈佛山忠義鄉志〉,中國國家圖書館,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403&bid=69082.0,瀏覽日期:2022年12月12日。
107.〈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ich_funding_scheme_introduction.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4日。
108.〈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ich_advisory_committee.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3日。
109.〈非遺項目─紮作技藝〉,賽馬會「傳‧創」非遺教育計劃,https://ichplus.org.hk/tc/ich/project/paper-crafting-technique,瀏覽日期:2023年1月12日。
110.〈甚麼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what_is_intangible_cultural_heritage.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2日。
111.〈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https://hkheritage.hkust.edu.hk/,瀏覽日期:2023年1月13日。
112.〈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hkichdb.gov.hk/zht/index.html,瀏覽日期:2022年12月12日。
113.〈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32540_chi/PDF/132540chi.pdf.multi,瀏覽日期:2023年1月12日。
114.〈紮作小知識(舞獅龍頭篇)〉,香港電台,https://www.rthk.hk/chiculture/bamboocraft/c2_tips.htm,瀏覽日期:2023年1月16日。
115.〈紮作與文化(舞獅龍頭篇)〉,香港電台網站,https://www.rthk.hk/chiculture/bamboocraft/c2_culture.htm,瀏覽日期:2022年12月29日。
116.〈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https://www.ihchina.cn/project.html,瀏覽日期:2022年12月12日。
117.〈第一屆得獎項目〉,第2屆想創你未來-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https://hknextwriter.org/%e7%ac%ac%e4%b8%80%e5%b1%86%e5%be%97%e7%8d%8e%e9%a0%85%e7%9b%ae/,瀏覽日期:2023年1月15日。
118.〈循聲覓道展覽系列一:香港節慶與民間工藝〉,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lost_and_sound_exhibition_series_1.html,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4日。
119.〈傳承火龍文化〉,大坑火龍文化館,https://www.firedragon.org.hk/inherit-the-fire-dragon-culture/,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4日。
120.〈舞獅歷史及傳說〉,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http://www.hkcmaa.com.hk/eng/intro/lion.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日。
121.〈藉獅頭紮作堅持舊我同時發現新我【文化者.專訪】〉,文化者,https://theculturist.hk/2019/02/%E6%96%87%E5%8C%96/%E8%97%89%E7%8D%85%E9%A0%AD%E7%B4%AE%E4%BD%9C%E5%A0%85%E6%8C%81%E8%88%8A%E6%88%91-%E5%90%8C%E6%99%82%E7%99%BC%E7%8F%BE%E6%96%B0%E6%88%91%E3%80%90%E6%96%87%E5%8C%96%E8%80%85%EF%BC%8E%E5%B0%88%E8%A8%AA/,瀏覽日期:2023年1月16日。
122.王征、余晴峰:〈[港人港事]第471期花牌紮作〉,《中國旅遊》,http://www.hkctp.com.hk/travels/id/2877,瀏覽日期:2022年12月30日。
123.林國輝:〈紙紮工藝在香港:歷史、傳承與創新〉,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711288/Paper_Crafting_optionC_re8_ol.pdf,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6日。
124.鄒興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十二年:回顧與前瞻〉,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660266/Retrospect%2band%2bProspects%2bSafeguarding%2bthe%2bIntangible%2bCultural%2bHeritage%2bof%2bHong%2bKong%2bOver%2bthe%2bPast%2b12%2bYears.pdf,瀏覽日期:2023年1月13日。
口述歷史訪問:
125.〈香港紮作業聯會主席冒卓祺先生訪問〉,上水古洞村,2023年3月10日,訪問者: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四年級學生韓明均。
腳註:
1. 關於中國節慶文化的研究,參閱彭淑敏:〈民俗文化〉,王國華主編,何佩然、彭淑敏等著:《香港文化導論》(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119-147。
2. 郭玉桔:〈港首間紮作展示館〉(2019年12月16日),《香港商報網》,https://www.hkcd.com/content/2019-12/16/content_1169938.html,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4日;〈傳承火龍文化〉,大坑火龍文化館,https://www.firedragon.org.hk/inherit-the-fire-dragon-culture/,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4日;〈循聲覓道展覽系列一:香港節慶與民間工藝〉,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lost_and_sound_exhibition_series_1.html,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4日。
3. 黃競聰:《簡明香港華人風俗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頁49。
4. 黃競聰:《城西溯古——西營盤的歷變》(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2年),頁187;高寶齡:《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香港》(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頁195。
5. 林國輝:〈紙紮工藝在香港:歷史、傳承與創新〉,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711288/Paper_Crafting_optionC_re8_ol.pdf,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6日。
6. 黃競聰:《城西溯古——西營盤的歷變》,頁187。
7. 陳桂洲:《扎作:承‧傳》(香港:鼎豐文庫,2007年),頁20。
8. 黃競聰:《城西溯古——西營盤的歷變》,頁190。
9. 黃競聰:《城西溯古——西營盤的歷變》,頁190。
10. 獅頭、花燈等紮作都是節慶期間較常用的紮作,例如觀音誕的花炮也會以花燈作裝飾,且都由來已久,具有歷史價值。參閱黃競聰:《簡明香港華人風俗史》,頁170。
11. 侯坤宏:〈觀音信仰的流傳與衍化〉,《人間佛教》,2017年10期(2017年7月),頁22-23。
12. 蔡志祥、韋錦新編:《延續與變革: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330。
13. 〈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828638/First_hkich_inventory_C.pdf,瀏覽日期:2023年1月13日。
14. 駱慧瑛:《觀心自在:香港觀音誕與觀音信仰探源》(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20年),頁312-316;〈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the_representative_list_of_hkich.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3日;〈第一屆得獎項目〉,第2屆想創你未來-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https://hknextwriter.org/%e7%ac%ac%e4%b8%80%e5%b1%86%e5%be%97%e7%8d%8e%e9%a0%85%e7%9b%ae/,瀏覽日期:2023年1月15日。
15. 〈循聲覓道展覽系列一:香港節慶與民間工藝〉,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lost_and_sound_exhibition_series_1.html,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4日。
16. 司徒嫣然:《市影匠心:香港傳統行業及工藝》(香港:香港市政局,1996年),頁190-196。
17. 劉繼堯、袁展聰:《武舞民間——香港客家麒麟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頁69、72、97-98;超媒體編輯部:《香港獅藝傳奇》(香港:超媒體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頁20。
18. 盧維幹:《大慈大悲觀世音》(香港:華人廟宇委員會,2016年),頁78、81。
19. [宋]高承撰,[明]李果訂:《事物紀原》(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8,〈舟車帷幄部四十〉,頁434;[唐]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8,〈文章第十八〉,頁127;〈佛山忠義鄉志〉,中國國家圖書館,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403&bid=69082.0,瀏覽日期:2022年12月12日。
20. 林國輝:〈紙紮工藝在香港:歷史、傳承與創新〉,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711288/Paper_Crafting_optionC_re8_ol.pdf,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6日。
21. 黃競聰:《簡明香港華人風俗史》,頁49、64、92、170。
22. 駱慧瑛:《觀心自在:香港觀音誕與觀音信仰探源》,頁55-67、296-316;盧維幹:《大慈大悲觀世音》,頁18-20、60-81。
23.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hkichdb.gov.hk/zht/index.html,瀏覽日期:2022年12月12日。
24. 郭玉桔:〈港首間紮作展示館〉(2019年12月16日),《香港商報網》,https://www.hkcd.com/content/2019-12/16/content_1169938.html,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4日。
25. [宋]高承撰,[明]李果訂:《事物紀原》,卷8,〈舟車帷幄部四十〉,頁434。
26. 徐藝乙:《風箏史話》(北京: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1992年),頁3。
27. 薛源、王雨璿、陳楊梅、陳浩:〈傳統南獅的流派及其運動特點研究〉,《科技資訊》,2021年22期(2021年11月),頁178。
28. [唐]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卷8,〈文章第十八〉,頁127。
29. 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750。
30. [宋]孟元老撰,鄧之誠注:《東京夢華錄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卷6、卷8,〈元宵〉、〈中元節〉,頁173、186、218;[宋]吳自牧:《夢粱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卷13,〈鋪席〉,頁116。
31. 〈紙扎業公所成立紀〉,《申報》,1920年8月23日。
32. 〈佛山忠義鄉志〉,中國國家圖書館,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403&bid=69082.0,瀏覽日期:2022年12月12日。
33. 「佛山大爆」花炮與花燈的集結品,因為它需要以爆破的形式展示花燈。參閱[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16,〈器語〉,頁444-445;關宏:《佛山彩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20-23、34-35;李紅:〈佛山彩燈傳承和創新的若干思考〉,《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37卷4期(2022年7月),頁2-4。
34. 梁正君:〈廣州陳氏書院建築裝飾工藝中的吉祥文化〉,《嶺南文史》,2003年2期(2003年6月),頁8;黃慧瑩:〈廣東醒獅發展沿革及其存在問題與對策研究〉,《傳承》,2013年12期(2013年10月),頁136。
35.〈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https://www.ihchina.cn/project.html,瀏覽日期:2022年12月12日。
36. 李孝聰:《中國區域歷史地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76。
37. 〈紮作技藝〉,香港非物文化遺產資料庫,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274d76dd-c685-4fe8-816d-bb7548e3ae89,瀏覽日期:2022年12月13日。
38. 張一兵點校:《深圳舊志三種》(深圳:海天出版社,2006年),頁287、643。
39. 據1881年之統計,當時香港分別有47位「冥鏹商販」與63位燈籠師傅。參閱林國輝:〈紙紮工藝在香港:歷史、傳承與創新〉,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711288/Paper_Crafting_optionC_re8_ol.pdf,瀏覽日期:2022年12月13日。
40. 周子峰:《葬之以禮:香港殯儀文化初探》(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0年),頁164;元建邦編:《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頁10、110-112。
41. 〈油牛洋燭紮作工人要求加薪〉,《香港華字日報》,1922年11月13日;〈扎作工會定期成立〉,《華僑日報》,1949年3月18日;〈第8067號公告——職工會條例(第332章)〉,職工會登記局2008年11月12日公告,頁1。
42. 黃競聰:《城西溯古——西營盤的歷變》,頁188。
43. 元建邦編:《香港史略》,頁10、110-112。
44. 〈港九各區街坊居民籌祝雙十大典〉,《華僑日報》,1951年10月8日;〈慶祝加冕會景巡遊籌委會委員親出募經費〉,《華僑日報》,1953年4月19日;〈華達公司製十餘丈蜈蚣〉,《華僑日報》,1956年5月19日。
45. 〈訪問紮作工人〉,《華僑日報》,1957年7月14日。
46. 〈訪問紮作工人〉,《華僑日報》,1957年7月14日。
47. 黃競聰:《城西溯古——西營盤的歷變》,頁189-190。
48. 黃競聰:《城西溯古——西營盤的歷變》,頁191。
49. 〈花牌紮作就業工人增加 年假告滿工作復趨繁忙〉,《華僑日報》,1969年2月21日。
50. 〈紮作工友注重技術〉,《華僑日報》,1960年1月31日;〈花牌紮作就業工人增加 年假告滿工作復趨繁忙〉,《華僑日報》,1969年2月21日。
51. 〈元宵花燈上市 紮作工友開夜工〉,《華僑日報》,1960年2月9日。
52. 黃競聰:《城西溯古——西營盤的歷變》,頁190。
53. 〈紙料紮作情形特殊亦工亦商半勞半資〉,《華僑日報》,1975年5月6日。
54. 黃競聰:《城西溯古——西營盤的歷變》,頁191-192。
55. 黃競聰:《簡明香港華人風俗史》,頁170。
56. 黃競聰:《城西溯古——西營盤的歷變》,頁192-193。
57. 〈秋節節品實銷結算〉,《華僑日報》,1959年9月19日。
58. 黃競聰:《城西溯古——西營盤的歷變》,頁190。
59. 〈花牌紮作旺〉,《華僑日報》,1969年8月1日;〈盂蘭盛會並無遜色花牌紮作應節而旺〉,《華僑日報》,1970年8月16日。
60. 〈紙料紮作工友開始加時工作〉,《華僑日報》,1970年2月9日。
61. 駱慧瑛:《觀心自在:香港觀音誕與觀音信仰探源》,頁306。
62. 李利安:《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播》(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頁69、72-73。
63. 李利安:《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播》,頁73-74;[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21年),卷41,〈馬王品第四十五〉,頁735-736;[西秦]沙門聖堅譯:《佛說羅摩伽經》(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21年),卷2,頁30-31。
64. [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1970年),卷9,〈海生商主緣〉,頁104。
65. 李利安:《觀音信仰的淵源與傳播》,頁75。
66. 弘學編:《妙法蓮華經》(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卷7,〈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頁275。
67. 弘學編:《妙法蓮華經》,卷7,〈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頁276-277;[宋]天息災譯:《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上海:佛學書局,1935年),卷3,頁7、53。
68. 温金玉:〈觀音菩薩與女性〉,《中華文化論壇》,1996年4期(1996年10月),頁86;朱光磊:〈觀音形象在漢地女身化的途徑與原由〉,《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6期(2016年12月),頁67-68。
69. 李欣:〈中土觀音女性化成因別釋——兼議漢文明「乾坤並建」之教化原則〉,《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6期(2016年12月),頁71-72;[北魏]曇無讖:《悲華經》(台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18年),卷2,〈大施品第三之一〉,頁29。
70. 于君方著,陳懷宇、姚崇新、林佩塋譯:《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21-23。
71. 朱光磊:〈觀音形象在漢地女身化的途徑與原由〉,頁67-68。
72. 李利安:〈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體系〉,《人間佛教》,2021年34期(2021年7月),頁69-70。
73. 于君方著,陳懷宇、姚崇新、林佩塋譯:《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頁43。
74. 侯坤宏:〈觀音信仰的流傳與衍化〉,頁17。
75. 吳燕:《中國觀音文化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47-49;石守謙、顏娟英主編:《藝術史中的漢晉與唐宋之變》(台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頁194;[清]曼陀羅室主人:《觀音菩薩的故事》(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24。
76. 吳燕:《中國觀音文化史》,頁49-54;盧維幹:《大慈大悲觀世音》,頁18-20。
77. 李利安:〈中國觀音信仰的基本體系〉,頁69-70。
78. 王敏:〈菩薩造像的中性化與觀音造像的女性化〉,《民族藝術》,2011年3期(2011年8月),頁125-126。
79. 朱光磊:〈觀音形象在漢地女身化的途徑與原由〉,頁69-70;駱慧瑛:《觀心自在:香港觀音誕與觀音信仰探源》,頁24、296;温金玉:〈觀音菩薩與女性〉,頁91。
80. 盧維幹:《大慈大悲觀世音》,頁60;駱慧瑛:《觀心自在:香港觀音誕與觀音信仰探源》,頁66-67。
81. 駱慧瑛:《觀心自在:香港觀音誕與觀音信仰探源》,頁61。
82. 駱慧瑛:《觀心自在:香港觀音誕與觀音信仰探源》,頁55、61-63、67;參閱附錄一:〈香港觀音誕女信眾參拜盛況報導〉。
83. 駱慧瑛:《觀心自在:香港觀音誕與觀音信仰探源》,頁61、297;〈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828638/First_hkich_inventory_C.pdf,瀏覽日期:2023年1月13日。
84. 〈白沙灣觀音誕〉,香港記憶,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local_festivals/festivals/lunar6/6_2/index_cht.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3日;參閱附錄二:〈香港紮作業聯會主席冒卓祺先生訪問〉,上水古洞村,2023年3月10日,訪問者: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四年級學生韓明均。
85. 劉繼堯、袁展聰:《武舞民間——香港客家麒麟研究》,頁69、72。
86. 參閱附錄三:〈蕉徑龍潭觀音古廟內的各式觀音造像〉。
87. 盧維幹:《大慈大悲觀世音》,頁48、56。
88. 葉春生:《廣府民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71。
89. 劉婕:〈近代省港煙花爆竹貿易研究(1859-1948)——以《中國舊海關史料》為中心〉(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頁10-11。
90. 陳子安:《漁村變奏:廟宇、節日與筲箕灣地區歷史(1872-2016)》(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頁159。
91. 〈【傳統之美:花炮傳情】〉(2019年5月3日),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watch/?ref=external&v=1734459783367447,瀏覽日期:2022年12月28日。
92. 司徒嫣然:《市影匠心:香港傳統行業及工藝》,頁190;〈花炮及其裝飾元素〉,香港記憶,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tin_hau/TinHau_Flower/index_cht.html,瀏覽日期:2022年12月28日;黃競聰:《簡明香港華人風俗史》,頁64。
93. 參閱附錄四:〈2023年上水古洞村觀音誕花炮〉。
94. 秦宏:《香港工業設計史》(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12年),頁33;李志清:〈儀式性少數民族體育在鄉土社會的存在意義(三)——族際交往中的搶花炮〉,《體育科研》,2006年27卷6期(2006年11月),頁11;司徒嫣然:《市影匠心:香港傳統行業及工藝》,頁190。
95. 〈榕樹灣祝天后誕 搶花炮警民衝突 三名村民頭破血流〉,《香港工商日報》,1983年5月6日;〈南丫島索罟灣慶祝天后誕搶花炮 滋事份子搗亂 擲石擊傷多人〉,《華僑日報》,1984年5月19日。
96. 蔡志祥:《酬神與超幽:節日和香港的地域社會》(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頁109。
97. 參閱附錄五:〈2023年上水古洞村觀音誕「抽花炮」儀式〉。
98. [漢]班固,許東方校訂:《漢書》(台北:宏業書局有限公司,1992年),卷96,〈西域傳下〉,頁3928。
99. [北魏]楊衒之,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卷1,〈城內〉,頁43;〈舞獅歷史及傳說〉,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http://www.hkcmaa.com.hk/eng/intro/lion.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日。
100. 超媒體編輯部:《香港獅藝傳奇》,頁20。
101. [唐]杜佑,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全12冊》(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卷146,〈樂六‧坐立部伎〉,頁3705。
102. 姜喜平:〈「南獅」歷史文化與發展現狀的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頁12。
103. 施志明:《本土論俗——新界華人傳統風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頁96;馮詩淇:〈淺析南獅運動傳統文化的創新與變化——以舞劇《南獅夢》為例〉,《藝術評鑒》,2019年5期(2019年3月),頁65。
104. 司徒嫣然:《市影匠心:香港傳統行業及工藝》,頁196。
105. 司徒嫣然:《市影匠心:香港傳統行業及工藝》,頁196。
106. 劉釗:〈「小臣牆刻辭」新釋——揭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祥瑞記錄〉,《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1期(2009年1月),頁8。
107. 霍松林、趙望秦主編:《宋本史記注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卷47,〈孔子世家〉,頁1895。
108. 邢金善:〈非物質文化遺產視角下麒麟舞的傳承與發展〉,《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11年3期(2011年3月),頁45。
109. 劉繼堯、袁展聰:《武舞民間——香港客家麒麟研究》,頁25。
110. 周萍:〈東莞市清溪鎮客家麒麟舞的傳承與保護〉(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頁5。
111. [民國]陳伯陶:《東莞縣誌》(台北:成文出版社,1912年),頁268。
112. 〈獅頭紮作技藝〉,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3b1ef5b5-f9d7-4298-a8e1-e0a1f1d65dbe,瀏覽日期:2023年1月2日。
113. 〈舞麒麟〉,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6e0c13d8-09c3-4053-80ba-c970644cca62,瀏覽日期:2022年12月30日。
114. 參閱附錄六:〈2023年上水古洞村觀音誕舞獅〉;參閱附錄七:〈2023年上水古洞村觀音誕麒麟頭紮作〉。
115. Stella So:《粉末都市——消失中的香港(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頁140;〈紮作與文化(舞獅龍頭篇)〉,香港電台網站,https://www.rthk.hk/chiculture/bamboocraft/c2_culture.htm,瀏覽日期:2022年12月29日。
116. Stella So:《粉末都市——消失中的香港(增訂版)》,頁141;〈舞麒麟〉,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6e0c13d8-09c3-4053-80ba-c970644cca62,瀏覽日期:2022年12月30日。
117. 〈花牌紮作技藝〉,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f340159e-365e-4292-aadc-8f3a246ba630,瀏覽日期:2022年12月30日。
118. 王征、余晴峰:〈[港人港事]第471期 花牌紮作〉,《中國旅遊》,http://www.hkctp.com.hk/travels/id/2877,瀏覽日期:2022年12月30日;黃競聰:《簡明香港華人風俗史》,頁92。
119. 〈各界隆重慶祝孔聖誕辰 永安街懸花牌慶賀〉,《華僑日報》,1947年8月27日;〈華商總會一番新氣象〉,《工商晚報》,1948年7月16日。
120. 〈酒樓喜慶宴會特多 花牌紮作工作轉旺〉,《華僑日報》,1970年1月30日。
121. 〈花牌紮作〉,傳耆,https://www.eldage.com/collections/%E8%8A%B1%E7%89%8C%E7%B4%AE%E4%BD%9C,瀏覽日期:2022年12月29日。
122. 〈花牌紮作技藝〉,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https://www.hkichdb.gov.hk/zht/item.html?f340159e-365e-4292-aadc-8f3a246ba630,瀏覽日期:2022年12月29日。
123. 陳守仁:《香港神功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頁18;參閱附錄八:〈2023年上水古洞村觀音誕花牌〉。
124. 〈非遺項目 ─ 紮作技藝〉,賽馬會「傳‧創」非遺教育計劃,https://ichplus.org.hk/tc/ich/project/paper-crafting-technique,瀏覽日期:2023年1月12日。
125. 蔡志祥:《酬神與超幽:節日和香港的地域社會》,頁109。
126. 參閱附錄二:〈香港紮作業聯會主席冒卓祺先生訪問〉,上水古洞村,2023年3月10日,訪問者: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四年級學生韓明均。
127. 參閱附錄二:〈香港紮作業聯會主席冒卓祺先生訪問〉,上水古洞村,2023年3月10日,訪問者: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四年級學生韓明均。
128.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32540_chi/PDF/132540chi.pdf.multi,瀏覽日期:2023年1月12日;〈甚麼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what_is_intangible_cultural_heritage.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2日。
129. 鄒興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十二年:回顧與前瞻〉,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660266/Retrospect%2band%2bProspects%2bSafeguarding%2bthe%2bIntangible%2bCultural%2bHeritage%2bof%2bHong%2bKong%2bOver%2bthe%2bPast%2b12%2bYears.pdf,瀏覽日期:2023年1月13日。
130. 〈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ich_advisory_committee.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3日。
131. 普查範圍A包括北區、大埔、沙田、西貢、黃大仙、觀塘、九龍城、深水埗及油尖旺;普查範圍B括元朗、屯門、荃灣、葵青、離島、中西區、灣仔、東區及南區。參閱〈CB(2)1090/08-09(01)號——全港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2009年3月20日資料文件,頁5。
132. 〈CB(2)957/10-11(03)號——全港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進度報告〉,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2011年2月11日資料文件,頁2-3;〈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https://hkheritage.hkust.edu.hk/,瀏覽日期:2023年1月13日。
133. 〈CB(2)855/16-17(06)號——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草擬名單〉,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2017 年 2 月 27 日的會議,頁2;〈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10969700/23828638/First_hkich_inventory_C.pdf,瀏覽日期:2023年1月13日。
134. 〈CB(2)842/16-17(01)號——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草擬名單〉,民政事務委員會2017 年 2 月 27 日討論文件,頁3;〈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the_representative_list_of_hkich.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3日。
135. 〈CB(2)1448/17-18(01)號——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博物館措施提供資助〉,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2018 年 5 月 28 日討論文件,頁3;〈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ich_funding_scheme_introduction.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4日。
136. 佚名:〈一竹一紙 傳統再現〉(2019年9月8日),《政府新聞網》,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9/20190906/20190906_145115_745.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4日。
137. 〈西貢白沙灣觀音古廟〉,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people/%E8%A5%BF%E8%B2%A2%E7%99%BD%E6%B2%99%E7%81%A3%E8%A7%80%E9%9F%B3%E5%8F%A4%E5%BB%9F/100064936624023/,瀏覽日期:2023年1月14日。
138. 〈古洞村 - 1953恭祝觀音寶誕酧神演戲委員會〉,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kttkyc?locale=zh_HK,瀏覽日期:2023年1月14日。
139. 參閱附錄九:〈2023年上水古洞村觀音誕盛況〉。
140. 蔡志祥:《酬神與超幽:節日和香港的地域社會》,頁72-74。
141. 許宣白:〈「搶花炮」停辦兩載 百年傳統漸凋零〉(2021年5月6日),《文匯網》,https://www.wenweipo.com/s/202105/06/AP60933f80e4b0476859ba5381.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5日。
142. 〈第一屆得獎項目〉,第2屆想創你未來-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https://hknextwriter.org/%e7%ac%ac%e4%b8%80%e5%b1%86%e5%be%97%e7%8d%8e%e9%a0%85%e7%9b%ae/,瀏覽日期:2023年1月15日。
143. 〈循聲覓道展覽系列一:香港節慶與民間工藝〉,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https://www.lcsd.gov.hk/CE/Museum/ICHO/zh_TW/web/icho/lost_and_sound_exhibition_series_1.html,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4日。
144. 蔣琳:〈記載社區變遷 傳承紮作工藝 元朗舉辦歷史圖片與花炮展〉(2017年6月29日),《香港商報網》,https://www.hkcd.com/newsTopic_content.php?id=1054917,瀏覽日期:2023年1月16日。
145. 〈紮作小知識(舞獅龍頭篇)〉,香港電台,https://www.rthk.hk/chiculture/bamboocraft/c2_tips.htm,瀏覽日期:2023年1月16日。
146. 〈藉獅頭紮作堅持舊我 同時發現新我【文化者.專訪】〉,文化者,https://theculturist.hk/2019/02/%E6%96%87%E5%8C%96/%E8%97%89%E7%8D%85%E9%A0%AD%E7%B4%AE%E4%BD%9C%E5%A0%85%E6%8C%81%E8%88%8A%E6%88%91-%E5%90%8C%E6%99%82%E7%99%BC%E7%8F%BE%E6%96%B0%E6%88%91%E3%80%90%E6%96%87%E5%8C%96%E8%80%85%EF%BC%8E%E5%B0%88%E8%A8%AA/,瀏覽日期:2023年1月16日。
147. 宋霖鈴:〈創新傳統 獅頭魚尾 兩代紮作人 合璧再世盧亭〉(2020年6月3日),《明報新聞網》,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9%AF%E5%88%8A/article/20200603/s00005/1591123562926/%E5%89%B5%E6%96%B0%E5%82%B3%E7%B5%B1-%E7%8D%85%E9%A0%AD%E9%AD%9A%E5%B0%BE-%E5%85%A9%E4%BB%A3%E7%B4%AE%E4%BD%9C%E4%BA%BA-%E5%90%88%E7%92%A7%E5%86%8D%E4%B8%96%E7%9B%A7%E4%BA%AD,瀏覽日期:2023年1月16日。
148. 劉繼堯、袁展聰:《武舞民間——香港客家麒麟研究》,頁97-98。
149. 〈花牌紮作保留傳統嘗試求變〉(2016年12月31日),《大公網》,http://www.takungpao.com.hk/culture/text/2016/1231/50014.html,瀏覽日期:2023年1月16日。
150. 曾蓮:〈孝子承父業 精益求精傳揚花牌工藝〉(2019年2月13日),《大紀元時報》,https://hk.epochtimes.com/news/2019-02-13/36644627,瀏覽日期:2023年1月16日。
151. 〈傳統花牌展現文學情懷〉,《經濟日報》,2012年4月13日。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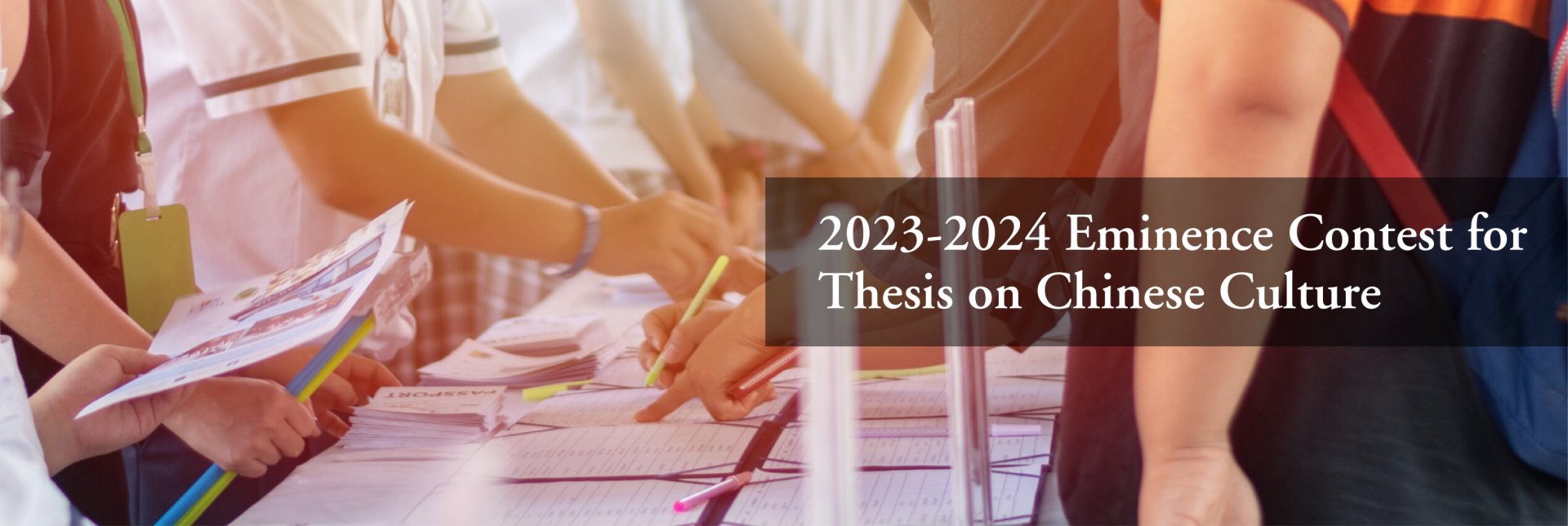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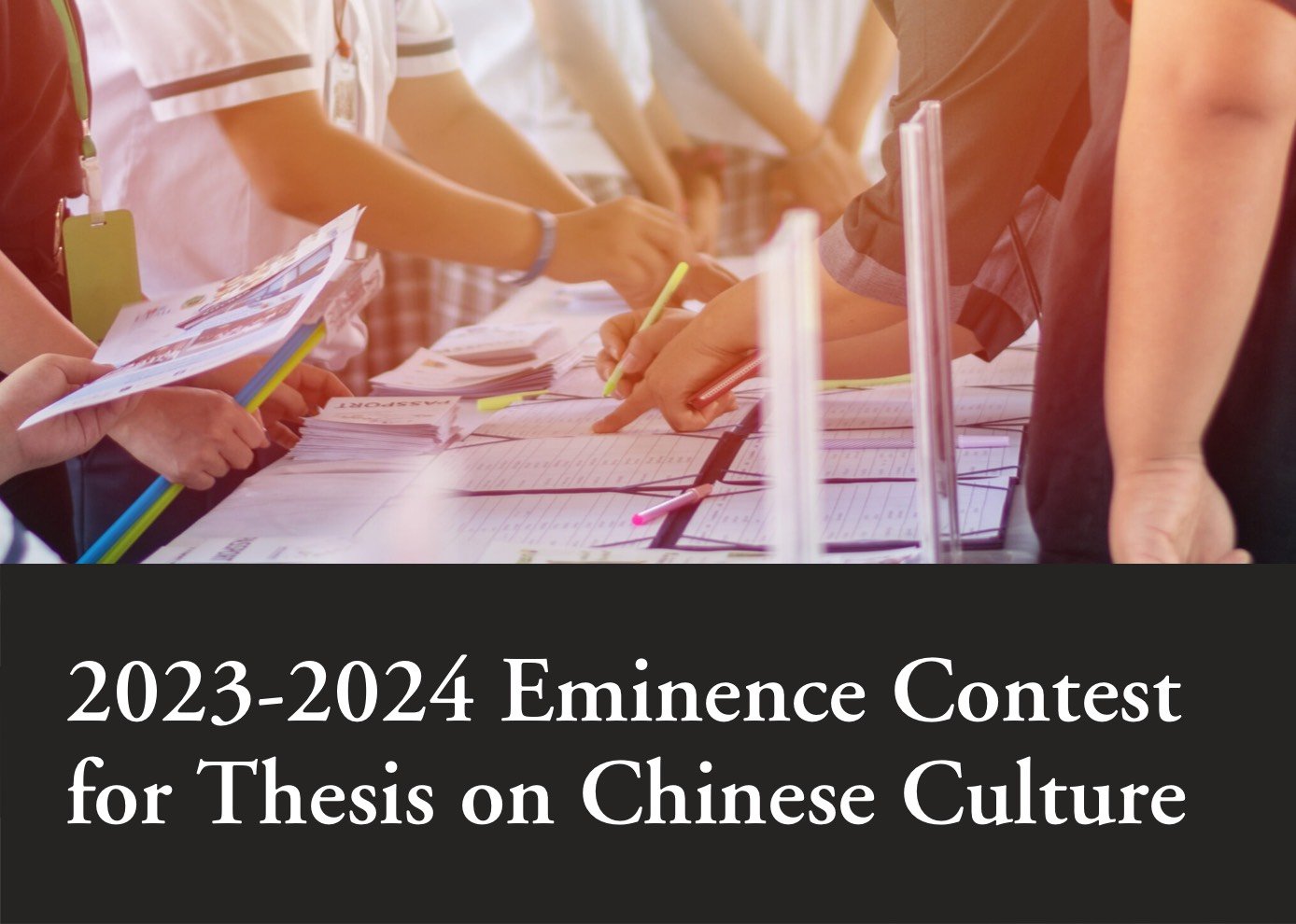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