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随笔:漫说「真力弥满」的《红楼梦》艺境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红楼梦•前言》曰:「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复杂的作家,《红楼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而又最复杂的作品。」1换言之,无妨理解为:曹雪芹《红楼梦》因其「最复杂」而成就其「最伟大」。所谓「复杂」,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红楼梦》涵括着众多「矛盾」,因「矛盾」而「张力」丛生,宛如宇宙之「黑洞」,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旧题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豪放》谓:「观化非禁,吞吐大荒⋯⋯真力弥满,万象在旁。」2这种「吞吐大荒」而形成的「真力弥满」境界,用以形容《红楼梦》之艺境,似亦确当。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便是从「大荒」说起:「原来女娲氏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3这讲的是宇宙洪荒之态,有空间,也有时间——十二丈、二十四丈、三万六千五百块,对应的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四季十二个月以及二十四节气;一块剩余,类似农历「闰年」之「闰」,多余者也。那么,其「张力」或「真力」何在?紧接着一句,似已回应此问题:「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性灵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艾,日夜悲号惭愧。」此中「自怨自艾」四字,真堪琢磨,尤其是重复出现二「自」字,已然道出《红楼梦》悲剧性之根源——「怨艾」因与他者「计较」而生,「计较」因无「用」欲念而生,归根究底,是由「心」之「自」生。此「心」之「自」生之欲念,即一切悲剧之种子,以及一切「矛盾」生成之内因。
关于此「一念」之心力,第五回写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曾提及:「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来如此。但不知何为「古今之情」,何为「风月之债」?从今倒要领略领略。』宝玉只顾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诸多世间悲剧,表面看似由于各种外在因素所导致,从究竟义上看,终归取决于「自心」之念想。宝玉生于王公贵族之家,在红尘中经历一遭,其悲剧之根,在于「木石前盟」之执念。放眼《红楼梦》荣宁二府乃至四大家族之兴衰,以及人间世种种悲剧,大凡不出于此「心念」及其背后之「欲念」。
明乎此,重读第一回,更清楚如下描述之深意:「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僧道二师奉劝道:「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可是,凡心既生,欲念愈增,不劝也罢,越劝反而越强烈,故曰:「此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哭求再四。」仔细体会此间蕴意,固然无妨从封建制度、时代因素、家族利益等层面探求《红楼梦》悲剧之成因,但不宜忽略了开篇第一回提及的「自心」欲念此一更具普遍意义之因由。《红楼梦》之能超越其他古典小说而成其「大著作」、「悲剧之悲剧」4
,重要原因之一,或许就在于作者虽然以荣宁二府及四大家族兴衰为表现对象,而隐含其间的,则是对于人世悲剧终极根源之思索,质言之,「自心」欲念而已。此乃作者更具哲学深度之措思。因此,《红楼梦》所写情事虽然「琐碎」具体,但总有诗性象征意味贯穿始终:「凡心」一动,歌哭随之;悲欢参半,终归「一梦」。这里就有强烈之「张力」:凡心欲念与现实境况之矛盾,此消彼长,循环往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热闹非凡而终归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或以为《红楼梦》作者透过贾宝玉厌弃功名利禄「经济之道」,批判当时封建制度之腐朽,固然不无道理。然而,即便感人肺腑之青春恋情,其实也如梦幻。此梦幻之根由,同样源自心念之动,如第一回所言:「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此「一事」背后,主因在于神瑛侍者「凡心偶炽」,因缘所及,绛珠仙子也生一「念」,随之「下世」为人。此后衍生人间悲欢、「儿女之真情发泄」等一系列「幻缘」,总其源头,皆本于「无材」补天之顽石的「凡心偶炽」。所以,作者特别提示:「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也决定了这部作品必定以悲剧为基调,无论人间世结局如何,歌舞升平也好,树倒猢狲散也罢,悲欢有别,如「梦」则一。作者之眼有「大悲」之光,亦是智慧之光。
《红楼梦》第五回以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为中心,借此总括「金陵十二钗」等一众女子命运因缘,乃关乎全书脉络之纲目,备受重视,此不待言也。除此以外,这一回中涉及的一「心」之念及其与世间悲剧之关系,同样值得关注。前引宝玉「情债」念起而「邪魔入膏肓」,即是典型一例。另有一处,亦属此类:宝玉「倦怠,欲睡中觉」,由秦氏引至房内「便惚惚的睡去」,「遂悠悠荡荡」入于梦间,「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希逢,飞尘不到」。于是,宝玉心生「欢喜」,一股念想随之而起:「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此间有两点无妨申说:第一,衔玉而生的贾宝玉虽已按第一回「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这一「凡心」念头,降生于富贵之家,但因不喜孔孟之道、读正经「四书」而「天天被父母师傅打」,不免心生厌倦,正应了第一回僧道二师所言:红尘中「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第二,正因有此「美中不足」之「多魔」,梦中之宝玉乃心执于此「人迹希逢」之幻境;执念既生,任凭警幻仙姑使出何等解数,也难令其一「悟」。故第五回有言:「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册籍,令彼熟玩,尚未觉悟;故引彼再至此处,令其再历饮馔声色之幻,或冀将来一悟」,用心良苦,结果仍是:「痴儿竟尚未悟!」于是仙姑又引宝玉「领略此仙闺幻境」,「秘授以云雨之事」,意在令其「万万解释」人间「尘境之情景」,「改悟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可惜宝玉执念甚深,又天生「一段痴情」,并未「速作回头」,而是一路前去,堕入「迷津」:「只听得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吓得宝玉汗下如雨⋯⋯」宝玉从梦幻中「醒来」,但并非「觉悟」,而是仍返回红尘之迷津。「自心」之欲念,诚为人间悲剧之总渊源。
又,第五回特意述及宝玉先祖亡灵之心,亦值得关注。文中说,警幻仙姑「今日原欲往荣府去接绛珠」,因「从宁府所过,偶遇宁荣二公之灵」,郑重托付:「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性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归引入正。幸仙姑偶来,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按,既明乎家族「运数合终」,又不甘于「不可挽回」之势,且寄希望于「禀性乖张」之「痴顽」者宝玉;但是,欲令「痴顽」者觉悟警醒、遏阻家族颓势,难于上青天矣。此亦构成《红楼梦》悲剧之大因缘,既与宝玉先祖之用心有关,也与宝玉痴心有关。话分两头,是祖、孙之「二心」,总其归途,仍为人类欲念丛生之「一心」。
前论以《红楼梦》第一回、第五回为中心,围绕「自心」生念这一主旨,述及「一念」如何缘乎欲而致人间矛盾丛生,又如何衍生如梦如幻之红尘故事。此或即王国维视《红楼梦》为「彻头彻尾之悲剧」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同时也是《红楼梦》「真力弥满」、魅力永在的重要源泉。《红楼梦》毕竟是一部艺术作品,并非空幻教义之「布道书」;其难能可贵处,在于作者化「空幻」为生动可感之「家庭闺阁琐事」、「闲情诗词」,有「真情发泄」,故感人至深。但不宜因此而忽略蕴藏红尘热闹故事之中的「万境归空」这一精髓。因此,第一回写空空道人抄录《石头记》而「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此一过程倒足以隐喻《红楼梦》全书宗旨:既非片面执于情色,亦非一味谈「空」论「幻」,而是即空即色、色不异空,交相辉映而成绝美艺境。
冶寒斋主
草于甲辰岁九月十三日
1.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4版,页1。
2. 司空图撰,陈玉兰评注:《二十四诗品》,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页57。
3.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4版,页2。本文引用《红楼梦》原文,均据此版本,下不出注。
4. 洪治纲编:《王国维文选》,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23年,页149。
< 原创文章/视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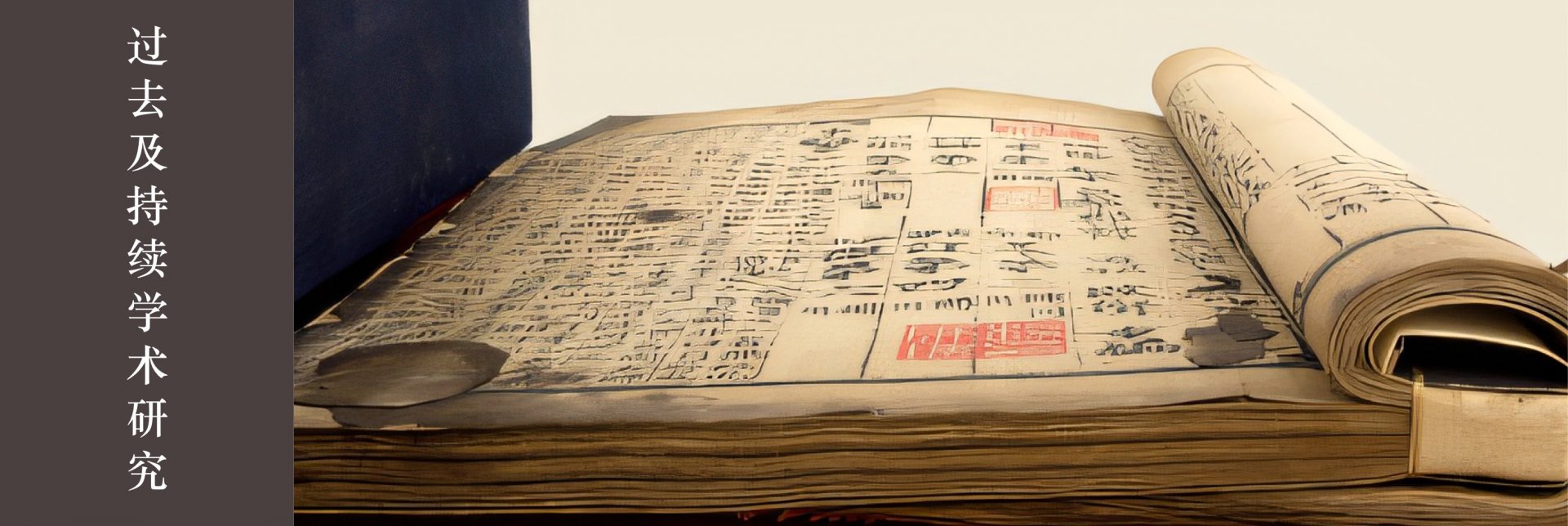



欢迎留言:
请登入/登记成为会员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