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隨筆:漫說「真力彌滿」的《紅樓夢》藝境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版《紅樓夢•前言》曰:「曹雪芹,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也是最複雜的作家,《紅樓夢》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而又最複雜的作品。」1換言之,無妨理解為:曹雪芹《紅樓夢》因其「最複雜」而成就其「最偉大」。所謂「複雜」,重要原因之一,在於《紅樓夢》涵括著眾多「矛盾」,因「矛盾」而「張力」叢生,宛如宇宙之「黑洞」,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舊題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豪放》謂:「觀化非禁,吞吐大荒⋯⋯真力彌滿,萬象在旁。」2這種「吞吐大荒」而形成的「真力彌滿」境界,用以形容《紅樓夢》之藝境,似亦確當。
《紅樓夢》開篇第一回便是從「大荒」說起:「原來女媧氏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單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3這講的是宇宙洪荒之態,有空間,也有時間——十二丈、二十四丈、三萬六千五百塊,對應的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四季十二個月以及二十四節氣;一塊剩餘,類似農曆「閏年」之「閏」,多餘者也。那麼,其「張力」或「真力」何在?緊接著一句,似已回應此問題:「誰知此石自經鍛鍊之後,性靈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艾,日夜悲號慚愧。」此中「自怨自艾」四字,真堪琢磨,尤其是重複出現二「自」字,已然道出《紅樓夢》悲劇性之根源——「怨艾」因與他者「計較」而生,「計較」因無「用」慾念而生,歸根究底,是由「心」之「自」生。此「心」之「自」生之慾念,即一切悲劇之種子,以及一切「矛盾」生成之內因。
關於此「一念」之心力,第五回寫寶玉夢遊太虛幻境時曾提及:「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倒要領略領略。』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諸多世間悲劇,表面看似由於各種外在因素所導致,從究竟義上看,終歸取決於「自心」之念想。寶玉生於王公貴族之家,在紅塵中經歷一遭,其悲劇之根,在於「木石前盟」之執念。放眼《紅樓夢》榮寧二府乃至四大家族之興衰,以及人間世種種悲劇,大凡不出於此「心念」及其背後之「慾念」。
明乎此,重讀第一回,更清楚如下描述之深意:「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說說笑笑來至峰下,坐於石邊高談快論。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仙玄幻之事,後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此石聽了,不覺打動凡心,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僧道二師奉勸道:「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倒不如不去的好。」可是,凡心既生,慾念愈增,不勸也罷,越勸反而越強烈,故曰:「此石凡心已熾,那裡聽得進這話去,乃復哭求再四。」仔細體會此間藴意,固然無妨從封建制度、時代因素、家族利益等層面探求《紅樓夢》悲劇之成因,但不宜忽略了開篇第一回提及的「自心」慾念此一更具普遍意義之因由。《紅樓夢》之能超越其他古典小說而成其「大著作」、「悲劇之悲劇」4
,重要原因之一,或許就在於作者雖然以榮寧二府及四大家族興衰為表現對象,而隱含其間的,則是對於人世悲劇終極根源之思索,質言之,「自心」慾念而已。此乃作者更具哲學深度之措思。因此,《紅樓夢》所寫情事雖然「瑣碎」具體,但總有詩性象徵意味貫穿始終:「凡心」一動,歌哭隨之;悲歡參半,終歸「一夢」。這裡就有強烈之「張力」:凡心慾念與現實境況之矛盾,此消彼長,循環往復;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台,熱鬧非凡而終歸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或以為《紅樓夢》作者透過賈寶玉厭棄功名利祿「經濟之道」,批判當時封建制度之腐朽,固然不無道理。然而,即便感人肺腑之青春戀情,其實也如夢幻。此夢幻之根由,同樣源自心念之動,如第一回所言:「恰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此「一事」背後,主因在於神瑛侍者「凡心偶熾」,因緣所及,絳珠仙子也生一「念」,隨之「下世」為人。此後衍生人間悲歡、「兒女之真情發泄」等一系列「幻緣」,總其源頭,皆本於「無材」補天之頑石的「凡心偶熾」。所以,作者特別提示:「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這也決定了這部作品必定以悲劇為基調,無論人間世結局如何,歌舞昇平也好,樹倒猢猻散也罷,悲歡有別,如「夢」則一。作者之眼有「大悲」之光,亦是智慧之光。
《紅樓夢》第五回以寶玉夢遊太虛幻境為中心,藉此總括「金陵十二釵」等一眾女子命運因緣,乃關乎全書脈絡之綱目,備受重視,此不待言也。除此以外,這一回中涉及的一「心」之念及其與世間悲劇之關係,同樣值得關注。前引寶玉「情債」念起而「邪魔入膏肓」,即是典型一例。另有一處,亦屬此類:寶玉「倦怠,欲睡中覺」,由秦氏引至房內「便惚惚的睡去」,「遂悠悠蕩蕩」入於夢間,「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於是,寶玉心生「歡喜」,一股念想隨之而起:「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縱然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呢。」此間有兩點無妨申說:第一,銜玉而生的賈寶玉雖已按第一回「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這一「凡心」念頭,降生於富貴之家,但因不喜孔孟之道、讀正經「四書」而「天天被父母師傅打」,不免心生厭倦,正應了第一回僧道二師所言:紅塵中「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個字緊相連屬」。第二,正因有此「美中不足」之「多魔」,夢中之寶玉乃心執於此「人跡希逢」之幻境;執念既生,任憑警幻仙姑使出何等解數,也難令其一「悟」。故第五回有言:「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覺悟;故引彼再至此處,令其再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用心良苦,結果仍是:「癡兒竟尚未悟!」於是仙姑又引寶玉「領略此仙閨幻境」,「秘授以雲雨之事」,意在令其「萬萬解釋」人間「塵境之情景」,「改悟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可惜寶玉執念甚深,又天生「一段癡情」,並未「速作回頭」,而是一路前去,墮入「迷津」:「只聽得迷津內水響如雷,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嚇得寶玉汗下如雨⋯⋯」寶玉從夢幻中「醒來」,但並非「覺悟」,而是仍返回紅塵之迷津。「自心」之慾念,誠為人間悲劇之總淵源。
又,第五回特意述及寶玉先祖亡靈之心,亦值得關注。文中說,警幻仙姑「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因「從寧府所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鄭重託付:「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故遺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性情怪譎,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歸引入正。幸仙姑偶來,萬望先以情慾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於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按,既明乎家族「運數合終」,又不甘於「不可挽回」之勢,且寄希望於「稟性乖張」之「癡頑」者寶玉;但是,欲令「癡頑」者覺悟警醒、遏阻家族頹勢,難於上青天矣。此亦構成《紅樓夢》悲劇之大因緣,既與寶玉先祖之用心有關,也與寶玉癡心有關。話分兩頭,是祖、孫之「二心」,總其歸途,仍為人類慾念叢生之「一心」。
前論以《紅樓夢》第一回、第五回為中心,圍繞「自心」生念這一主旨,述及「一念」如何緣乎慾而致人間矛盾叢生,又如何衍生如夢如幻之紅塵故事。此或即王國維視《紅樓夢》為「徹頭徹尾之悲劇」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同時也是《紅樓夢》「真力彌滿」、魅力永在的重要源泉。《紅樓夢》畢竟是一部藝術作品,並非空幻教義之「佈道書」;其難能可貴處,在於作者化「空幻」為生動可感之「家庭閨閣瑣事」、「閒情詩詞」,有「真情發泄」,故感人至深。但不宜因此而忽略蘊藏紅塵熱鬧故事之中的「萬境歸空」這一精髓。因此,第一回寫空空道人抄錄《石頭記》而「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此一過程倒足以隱喻《紅樓夢》全書宗旨:既非片面執於情色,亦非一味談「空」論「幻」,而是即空即色、色不異空,交相輝映而成絕美藝境。
冶寒齋主
草於甲辰歲九月十三日
1.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第4版,頁1。
2. 司空圖撰,陳玉蘭評註:《二十四詩品》,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57。
3.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第4版,頁2。本文引用《紅樓夢》原文,均據此版本,下不出注。
4. 洪治綱編:《王國維文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23年,頁149。
All articles/videos are prohibited from reproducing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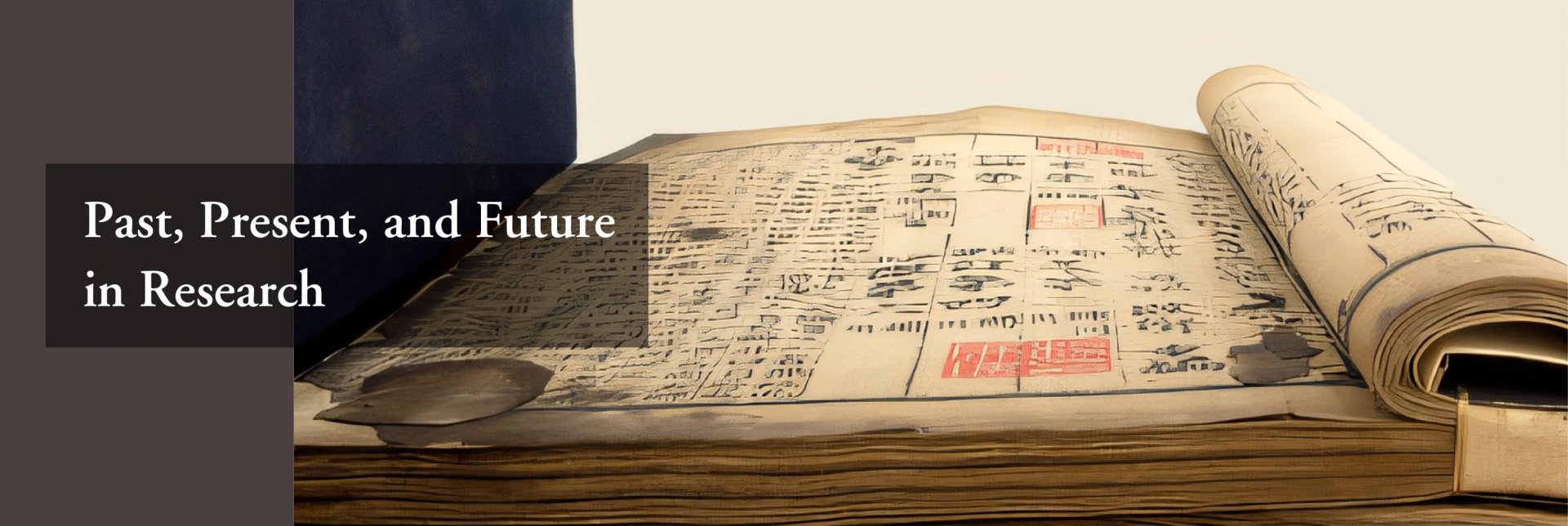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