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杨家将第三代传人杨文广(?-1074)事迹新考
在明人小说《杨家府演义》裹,北宋杨家将的第三代英雄,是杨宗保、穆桂英夫妇。他们的一双儿女杨文广和杨金花,构成杨家第四代,而文广的儿子杨怀玉兄弟则是杨门第五代。 1不过,在真实历史中,杨宗保和穆桂英都是虚构的人物,杨门第三代其实是杨文广。另外,他尚有两兄长,而并非杨六郎杨延昭(958-1014)一脉单传的独生子。此外·他随狄青(1008-1057)平定侬智高(?-1055)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将,而非小说所云年方弱冠的少年。 2至于杨文广的后代,史所不载,所谓杨怀玉者,大概是小说家随意的杜撰。 3考杨门三代中,杨文广的事迹载录于史传的最少,他的战功也远逊父祖;不过,论起实际的地位,他却比父祖为高。他最后官至步军都虞候,位列「礼继二府」的三衙管军。笔者怀疑杨业(935-986)所以被人尊称为「杨令公」,可能沾了孙儿的光,因文广擢步军都虞候而获追赠尚书令或中书令所致。 4根据《宋史·杨文广传》不足二百七十字的简略记载,杨文广虽然是名将之后,但他的前半生沉滞于下僚,几乎与二兄一样寂寂无闻;幸而他终能在仁宗(1022-1063在位)庆历三年(1043),当已步入中年时,获得平乱立功之机会,得以出头。然后他再有幸先后跟从范仲淹(989-1052)、韩琦(1008-1075)和狄青建功立业,终于大器晚成,中兴杨家,得以维持杨门将家之名声。
在随狄青南征侬智高、后来官至管军的七员大将中,杨文广的家世最显赫,他的名字也最为一般读者所知。不过,他的生平事迹在宋官私的记载则甚少。上一世纪,余嘉锡(1883-1955)教授早在其〈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中,据《隆平集》、《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皇宋十朝纲要》等书之有关记载,对《宋史·杨文广传》作出详瞻的索隐考证工夫。 5当代的宋史学者中,常征在其《杨家将史事考》中,补入一些宋人以至明人的记载,再对杨文广的生平事迹考索一番。 6不过,常氏的考证的最大问题,首先是对余嘉锡之研究视若无睹,不加引用。另外,史料搜集亦不够周全,而在使用史料时有欠严谨,推论过当。就笔者目前所知,近年有关杨文广生平事迹最值得参考之著作,是河陇史地研究专家陈守忠一篇实地考察杨文广所筑之大甘谷口寨(今甘肃通渭县南)和通渭寨(今甘肃通渭县)之报告。 7本文即在余、常二氏的研究基础上,重新考索杨文广之生平。笔者曾撰〈狄青(1008-1057)麾下两虎将——张玉(?-1075)与贾逵(1010-1078)〉一文,论及狄青部将之军旅生涯及自仁宗末年以来在众多武臣中出现的「狄青效应」。 8杨文广曾为狄青麾下大将,故本文亦可视为该文的续篇。
杨文广字仲容,是杨延昭第三子,生年不详。据曾巩(1019-1083)的《隆平集·杨延昭传》所载,杨文广的两位兄长名传永和德政(?-1031后)。 9 杨文广两位兄长的生平事迹,笔者目前所仅知,是其二兄杨德政在天圣九年(1031)以西头供奉官见任泽州(今山西晋城市)兵马监押兼在城巡检。 10 常征根据明初大儒宋濂(1310-1381)所撰的〈杨氏家传〉误信杨文广尚有一弟名充广,并因此错误推论播州(今贵州遵义市)杨氏出于太原杨氏。 11 当杨延昭于真宗(997-1022在位)
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在高阳关(今河北高阳县东旧城)副都部署任上卒时,杨传永、德政及文广均以父遗荫得官。杨文广兄弟获授什么官?从《隆平集》、《续资治通鉴长编》到《宋史》均未明言。余、常二氏从《宋史·杨文广传》所记杨文广「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结合宋代武臣迁官制度的有关记述,断定文广所授,当是三班奉职或借职,所论可取。考杨延昭卒时官英州(今广东英德市)防御使,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就在杨延昭死后第二年,即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宋廷颁布承天节(按:即真宗生辰)及南郊奏荫子弟恩荫新制,防御使一级的武臣,子授右班殿直,弟、姪、孙授三班奉职。杨延昭守边有大功,宋廷在新制颁行前一年录他三子官,似乎与新制相去不会太远。杨传永是长子,依制当授正九品的右班殿直,杨文广是老三,按理应比照弟、姪、孙,授从九品的的三班奉职或借职,而授三班借职之可能较高,当然,亦不排除只授予比借职还低的未入流武职。 12
杨文广出仕的年月,余氏未有考证,常氏则根据《宋史》所记杨文广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的线索,参照《宋会要辑稿》所载张海于仁宗庆历三年被平定的史实,再推论杨文广自三班借职升迁为殿直当经十余年,而考定杨文广出仕不应早于仁宗天圣年间。 13 然而,常氏显然将杨文广授官使臣和出补实职二事混为一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宋廷在庆历三年十一月所颁布的新恩荫制度指出,「荫长子孙,皆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 14 杨文广能受荫得官,即表明其父卒时,他已过了十五岁。当然授官不等于补实缺,杨文广未必能像其二兄杨德政一样,正常地在出仕后十八年,既迁四阶为西头供奉官,并已补实职为泽州兵马监押。据欧阳修在同一年的上奏,在「武官中近下班行,并无贤愚分别,一例以年岁递迁。自借职得至供奉官,须是三十余年」。 15 即是说平均五年迁一阶,此亦符合北宋武臣五年一迁的通例。倘《宋史》记载不误,杨文广真的要到平张海有功时才迁殿直(即使是左班殿直),那即是说他要等三十年才升三阶,即平均十年才升一阶,实在算得上是罕有之沉滞。为何杨文广的早年仕途如此不济?据曾巩、张方平(1007-1091)及上官均(1038-1115)所记,三班使臣在真宗天禧年间,已达四千余人;到仁宗庆历八年(1048),已达六千五百余人;到神宗(1068-1085在位)末年时更逾万人,宋廷实在没有太多的实缺可授。 16 杨文广虽是名将之后,但有两兄在前,补实职也要等待有特恩。笔者推测杨文广只能等其两兄身故或致仕后,才有机会补缺。常征推论杨文广「出仕」在仁宗天圣以后,但笔者认为杨文广很有可能要到明道以后两兄殁后才补上实缺,大概再用十年时间自三班借职迁一至两阶至右班殿直,然后因平张海立功而再迁左班殿直。
因史料匮乏,我们无法确知杨文广何年得补实职。至于他的年岁,假定他在大中祥符七年是十五岁,则他在庆历三年以功迁殿直时,当为四十四岁。杨文广到这年纪仍屈居下僚,常征感到很不解。其实,这种情况在宋代甚为普遍,我们随便在宋人碑铭即可找到许多一辈子做官不过使臣的武将例子。 17 大概常氏以为大名鼎鼎的杨家将后人(其实杨家大享盛名要到明代,并靠小说家吹嘘),不可能如此沉滞。然而,在北宋中叶以降,低级武臣升迁艰难,正是常态。太原杨氏其实不过是北宋众多将家之一,三代之后,他的子弟就没可能受到宋廷特别照顾,杨文广后来能超过两兄,出人头地,还得靠一点运气。
杨文广的运气,首先是他没有参预从康定元年(1040)正月爆发、以宋军惨败的三场宋夏战役,而得以逃过大劫。事实上,在康定元年正月的三川口(约在今陕西延安市西二十公里处)之役、庆历元年(1041)二月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西北好水)之役、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的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县中河乡)之役中,被俘或阵亡的宋将,许多是当时有名之骁将,而其中属于将家子的便不少。 18 当然,事情亦有两面,宋夏战争亦造就了许多人建功立业的机会。好像杨文广后来追随的狄青,在康定元年十一月前,不过是比他高两阶的右班殿直、鄜延路部署司指使的九品小武官;宋夏战争却给他大展身手之机会,此后他身经百战,屡立战功,而成为一代名将。 19 杨文广虽没有狄青凭御外侮建大功之运气;但他也能借平定内寇而初露头角。
就在宋军三败于西疆而元气大伤时,京西一带在庆历三年中,又遭剧贼张海、郭邈山率众劫掠。张海是什么人?余氏引用《续资治通鉴长编》两条记载略为陈说,称张海、郭邈山二人在庆历三年起事于陕西。常氏亦引用《宋会要辑稿》及《包拯集》两条资料,称郭邈山等早在明道元年(1032)已聚众于陕西的商州(今陕西商州市),并说张海本为陕南屯卒,亦与其党响应起事,转战京西、陕西一带十年,州县不能制。 20 论及张海之起事,常氏推论张海等劫掠州县已有「十年」而官府不能制。不过,当笔者翻检他所引的两条资料,却看不到其推论有何根据。根据欧阳修在庆历三年之上奏,其实盘据在商山(今陕西商州市东南)(不是商州!)十年的是郭邈山,而非张海。 21 关于张海的事迹,虽然《宋会要辑稿》及《宋史》记得不多;但《续资治通鉴长编》除了余氏所引两条外,尚有多条相关记载,另欧阳修等之文集亦有不少相关之篇章,惜常氏未有仔细搜集阅读,故有此错误之推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有关记载,郭邈山实为叛卒,于庆历元年正月前后起事于陕西。张海亦为「军贼」,本为李宗伙内「恶贼」,实起于京西。 22 有趣的是,本来是张海响应郭邈山,但宋官方之记载反而一直以张海为盗首,而以郭邈山、党君子、范三、李宗为其羽翼。 23 据李焘的考证,张海其实起于京西,不是陕西,而他响应郭邈山的年月,不会早于庆历元年。常征称他们横行十年,其实错解了史料。张海作乱始于邓州(今河南邓州市),本来实力不大,据范仲淹的说法,张海一众只有六十余人,虽各骑鞍马拥有弓弩器械;但当时知邓州柳植(?-1049后)没有防微杜渐,未能及时出兵擒捕,结果给他坐大,杀出邓州,焚掠京西数处州县。宋廷于庆历三年八月,才觉察事态不妙,于是下诏命左班殿直曹元诘、张宏,三班借职黎遂领禁兵擒捕张海等。 24
宋廷出师一月多,仍然无功。据欧阳修所奏,张海等人虽不多,但他们都有甲马,日行一、二百里,当马力困乏便弃,另夺民间生马乘骑,而教追捕他们的官军疲于奔命。 25 宋廷无奈,在是年九月,只好再派监察御史蔡禀(1002-1045)为京西安抚前去督捕。后见蔡禀驭下处置无方,几乎闹出兵变,只好又再任杜杞(1005-1050)为京西转运使,由他负责平乱。另一方面,又下诏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及诸州长吏,举荐所部兵马都监及监临场务使臣有材勇可出任巡检的,以名字上闻。宋廷并许诺,若捕盗有功,就不次擢迁。 26 杨文广相信就是在这时受到举荐,担任巡检,讨捕张海。谁人举荐杨文广的?杨文广在应召前担任哪一州的武职?因史料缺乏,均不可考。笔者猜测,杨文广的堂姪、在是年十月以殿中丞知岳州(今湖南岳阳市)被选为提点荆湖南路刑狱的杨畋(1007-1062),很有可能是推荐他的人。 27
杨文广有用武之机会,正因张海等之作乱,已成燎原之势。据枢密副使富弼(1004-1083)在是年九月中之陈奏,群盗乘京西诸州长吏庸碌,兼无兵无备,公然在白昼攻入州城劫掠府库,散钱财与其党及贫民。其中陕府(即陕州,今河南陕县)、西京(即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唐州(今河南唐河县)、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房州(今湖北房县)、金州(今陕西安康市)、商州、襄州(今湖北襄樊市)、邓州等州府,相去千余里,都被张海等大事劫掠,杀人放火,所在疮痍。 28 宋廷又祸不单行,同年十月,张海剽掠至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境上时,知军韩纲(?-1044后)率宣毅军三百人力拒来犯。当贼兵解围而去时,韩纲却因犒赏不公,激起兵变,叛兵首领邵兴从光化军向西,攻掠川北州县,与张海一东一西相呼应。 29
张海及其党羽其实所胁之众为数并不太多,不过千余人,只是他们专向无兵无备之京西州县攻掠,他们掠完便走,等到官兵赶到,他们早已遁去。比较之下,邵兴一路招诱失律兵卒,众至三千余人,还教宋廷忧虑。 30 当张海、邵兴等窜向川陕时,宋廷即以陕西宣抚使韩琦统一指挥扑减两股叛乱之行动,出动陕西、京西兵凡九千人,终于在是年十二月,先后平定张海与邵兴之乱。 31关于张海起事之缘由及所带来之损失,苏辙(1039-1112)在元佑元年(1086)闰二月,即乱平四十三年后,曾再作一个总结。他称张海起事,就像淳化时的李顺(?-992后)、熙宁中的廖恩(?-1077后),都是因官府厚赋敛,夺民利所致。苏辙又粗略估计宋廷在平乱之耗费,包括发兵命将、转运粮食,以及耗失兵械和募士赏功,连同张海等燔烧官寺,劫掠仓库之损失,至少要付出数百万贯的沉重代价。 32
杨文广在讨平张海之乱的具体战功不详,事实上,张海一伙不过是乌合之众,人数有限,战斗力不强,不是地方官养寇,早就平息。看来杨文广也没有怎样血战;不过,他总算立功,得到升迁为左班殿直。 33 他的顶头上司是韩琦和范伸淹(989-1052)双双举荐、以捕盗有名之悍将赵滋(?-1064)乱事平定,赵滋自右侍禁擢东头供奉官。当赵滋调为京东东路都巡检时,杨文广则仍留在陕西。教杨文广遗憾的是,他的堂姪杨畋却在是年底,因讨蛮徭兵败于孤浆峒而遭降职。 34
从庆历四年(1044)到皇佑五年(1053)前后十年间,杨文广的军旅生涯进入另一阶段,他首先有幸成为范仲淹的直接部属,然后在多年后,隶于狄青帐下,从征侬智高。虽然他追随范、狄二人的事迹可考的不多,但他后来得以被宋廷擢任管军,出任方面,显然是这十年磨剑所奠下的基础。
庆历四年六月,主持庆历新政的参知政事范仲淹,因承受不了朝中反对变革者之压力,自请出按西北边地,仁宗接受他的要求,任他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35 据《宋史·杨文广传》称,范仲淹「宣抚陕西,与语奇之,置麾下」。究竟范仲淹在何时何地召见杨文广的?余氏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认为当在庆历五年(1045)正月至十一月间,当范仲淹罢参政,改任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兼知邠州(今陕西彬县)时。不过,笔者认为杨文广亦有可能早在四年十月当范氏宣抚河东时已进入范幕。 36 至于推荐杨文广给范仲淹的,很有可能是韩琦或与范氏有交情的杨畋。 37
杨文广有什么地方教范仲淹称奇,而要将他纳为麾下?是否他武勇过人?考范仲淹在改任知邓州前,曾上奏力保前泾原都巡检孙用及瓦亭寨主(今宁夏固原县瓦亭乡)张忠(?-1052)复职,以他们有武勇可用,但杨文广就没有得到范氏这类的考语,恐怕范仲淹看得起杨文广,并非他有父祖之武勇。 38 关于这一点,常氏认为杨文广必是献上防范西夏的军计,而受知于范仲淹。他又进一步推论杨文广献纳了有关改革兵政的意见。然而,常氏之推论,既无佐证,也与情理不合。常氏说杨文广献纳防范西夏之军计,这样笼统的说法,自然不能说错;但要说杨文广有能力析论「将不专兵,兵不专将」之弊,实在将他看得太高。 39 笔者认为,杨文广的家世与经历,固然都能引起范仲淹的兴趣;不过,能令范仲淹「奇之」,并用为朝夕相见的幕僚,必因其能言范仲淹感到兴趣的话题,此话题相信是其祖父杨业修建堡寨的经验。考范仲淹重来西疆,第一番陈奏,便是请求在麟、府二州重修堡寨,以招纳蕃部,作长期防御。在范仲淹的筹划中,在宋夏边防要地修堡建寨,是防御西夏进攻的头等大事。他正需要一个精通此道的人,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当杨文广向他言及先祖修建堡寨之经验时,是如何正中他下怀,自然要马上将杨文广纳为幕僚了。事实证明,杨文广就是长于修筑堡寨之专家,他后来即奉韩琦之命在秦凤路大修堡寨(事见下文)。在这一点上,还有一项旁证。我们知道,在防御西夏之策略上,范仲淹与韩琦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二人志同道合,爱憎也相近。据李焘所记,韩琦在皇佑年间经略河东,按行堡塞所置处,发现它们多是杨业仕北汉时所修建,而佩服不已。考主张修建堡寨的事上,范仲淹比韩琦还要来得早,我们可以相信,范仲淹对于杨业当年的远略,当会和韩琦一样佩服不已,因而对深谙祖传修筑堡寨本领的杨文广就另眼相看。作为将家子,杨文广虽没有完全学得父祖冲锋陷阵的本领,但他能继承祖上修建堡寨的本事,也就够称守业了。 40 如值得注意的是,狄青当时与杨文广同在范仲淹陕西宣抚使辖下,但狄青因多立战功,名位已远在杨之上;41 杨文广在范仲淹邠州麾下,虽然在当时尚未受泾原部署狄青的直接指挥,但狄青对其才干能力肯定有相当的认识。
杨文广从庆历六年(1046)至皇佑五年(1053)的八年间,仕历不详。他有没有随范仲淹守邓州、荆南府(今湖北荆州市)、杭州(今浙江杭州市)及青州(今山东青州市)?目前看到的范氏文集,找不到有关杨文广事迹的记载。 42 考在庆历五年十一月代范仲淹出知邠州是原梓州转运使崔辅,而在庆历
六年二月接任陕西安抚使知永兴军(即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的,是原河北安抚使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程琳(988-1056)。倘杨文广没追随范仲淹,崔、程二人以及后来出任永兴军都部署的叶清臣(1000-1049),及程琳的继任人李昭亮(?-1063),以及当年平定张海、后任环庆都部署的杜杞,都有可能是他的上司。至于杨文广与狄青的从属关系,因史料缺乏,不易确定。考狄青在这八年中,先后任泾原仪渭兵马部署及鄜延经略安抚使,并曾知渭州(今甘肃平凉市)与延州(今陕西延安市),倘杨文广留在陕西,他成为狄青部属的可能性很大,后来狄青征他从征侬智高,大概因杨是他的旧部。 43
庆历七年十一月,河北贝州(今河北清河县)的宣毅卒王则据城反,并建号称尊。宋廷派参知政事文彦博(1006-1097)和权知开封府明镐(989-1048)调集河北各路军队围剿,高阳关都部署王信(988-1081)首先率本部兵赶至贝州城下,文、明二人抵贝州,即采挖地道的方法攻城。叛军强悍,非张海一类鸟合之众可比,宋军围攻至翌年闰正月,前后六十五日,才破城擒得王则。当战况激烈时,文彦博一度想调狄青之劲旅代替王信攻城,不过,文彦博还未发出调兵请求,乱事已平定。杨文广这次运气又差了一点,本来杨家上两代转战河北,他参预平叛,是人地相宜的事。可惜狄青最终没机会率部平乱,而他也就失去了一次立功及迁升的机会。考宋廷在平乱后不久,翰林学士张方平奉命上奏检讨这次叛乱,他在列举祖宗时之名将九人时,便包括杨文广的父亲杨延昭。假若杨文广这次有机会平叛立功,他一定让宋廷文臣刮目相看。教人感叹的是,今次一战成名的却是另一位杨氏英雄杨遂(?-1080),他凭奋勇先登破城之奇功,从此受知于文彦博,得以建功立业。 44 在这裹附带一提的是,当杨文广默默无闻时,他的族姪杨畋在庆历七年(1047)正月,因荆湖南路安抚使崔峄的推荐,由文资的太常博士改为武资的东染院使,出任荆湖南路钤辖,对付岭南徭族之叛。杨畋征战经年,到了皇佑元年三月,奏称得瘴雾之疾,请恢复文资,求近北一小郡。宋廷允准,即授他屯田员外郎、直史馆知随州(今湖北随州市)。未几又获召入朝出任户部判官,到皇佑二年(1050)五月,又出使河东路,计置粮草及处置盗铸铁钱等事。同是杨家后人,杨畋的际遇便好多了。 45 不过,杨家叔姪都不料到,他们在四年后,都得应召,征讨就在皇佑元年九月开始入寇邕州(今广西南宁市)的侬智高。 46
皇佑四年(1052)五月,宋廷一直轻忽的侬智高,已准备就绪,一举攻陷邕州,并建大南国,改年号为启历,并自称为仁惠皇帝。由于宋廷无备,侬智高很快又攻克广南东西路的横州(今广西横县)、贵州(今广西贵港市)、龚州(今广西平南县)、藤州(今广西藤县)、梧州(今广西梧州市)、封州(今广东封开县东南)、康州(今广东德庆县)、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等州,并围攻广州(今广东广州市)。宋廷大为震惊,除命当年平定邵兴有功的知韶州(今广东韶关市)陈曙(?-1053)及范仲淹旧部张忠、蒋偕领兵讨侬智高外,再在是年六月,急召素习蛮事但正在居父丧的余靖和杨畋平乱,余被任为广南西路安抚使知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杨畋被任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提举经制贼盗。教人遗憾的是,最具时望的范仲淹偏偏在这时病逝于徐州(今江苏徐州市)。这场大乱最后只能由他的爱将、刷在同月被仁宗破格擢为枢密副使的狄青才能平定。 47
教宋廷震惊的是,号为勇将的广东都监张忠及广东钤辖蒋偕,都先后在皇佑四年七月被侬智高击杀,而号称知蛮事的杨畋,也被击败,只能焚烧储粮,率残兵退守韶州。仁宗只好接受宰相庞籍(988-1063)的推荐,召用知兵的老臣孙沔(996-1066),自秦州徙为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抚使,不久再加广南东西路安抚使,统筹平乱行动。然当侬智高再破昭州(今广西平乐县西南)后,仁宗担心孙沔亦无法平乱,当狄青自请出师,而又得庞籍全力支持时,仁宗终下定决心,在是年九月,命狄青选将统兵,全权负责平定侬智高之乱。狄青请准在鄜延、环庆、泾原三路择蕃落、广鋭军曾经战斗各五千人,命逐路遣使臣一员,押赴广南行营。另又征召各路将校从征,他所挑选从征的将校中,据《宋史》所载,正有杨文广。 48
关于杨文广从征侬智高的事,除了《宋史》记载外,就只有明中叶纂修的《嘉靖南宁府志》和清初顾祖禹(1624-1680)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曾有提及。 《嘉靖南宁府志》称杨文广在「狄青南征时为广西钤辖知邕州,抚御有方,士卒乐为效死,时以名将称之」。 《读史方舆纪要》则引述旧志,称杨文广奉狄青命,追击侬智高至大理之阿迷州合江口,不及而还。 49 不过,《嘉靖南宁府志》说杨文广南征时为广西钤辖知邕州,显然是照抄《宋史》但又读不通《宋史》的断句,不知道杨文广知邕州其实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故后出的《嘉靖南宁府志》并无史料价值。至于比《嘉靖南宁府志》更晚出的《读史方兴纪要》,虽载有《宋史》所无之事。但它并未清楚注明所谓「志云」杨文广追击侬智高至大理之事出自何书,故它所说的事只能存疑(按:考诸群书自《长编》以下,所记追击侬智高的宋将,并无杨文广之名)。关于杨文广南征的间题,常征在未作任何考辨前,便贸然据《读史方舆纪要》上迹的传闻,绘影绘声的说杨文广奉狄青命,率精骑追击侬智高至大理国东境之合江口(今云南开远市北、南盘江与乐蒙河会合口),并于其地筑城屯兵而还。相较之下,余嘉锡便严谨得多,他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及《磨崖刻平蛮三将题名碑》均没载文广事迹,而颇疑《宋史》之说。虽然余氏也考虑到随狄青南征的文武官员二百三十一人,不可能全数具载于史籍。他猜测杨文广可能仅随军差遣,或已赴德顺军(今宁夏隆德县城关)任,不在将官之列,故不得题名,而功劳亦不显。 50 笔者曾检索余氏提到的《磨崖刻平蛮三将题名碑》,发现除了狄青、孙沔和余靖外,题名该碑上的文武官员仅三十四人,而在归仁铺(今广西南宁市东)一役有大功的勇将张玉(?-1075)、和斌(1011-1090)及杨遂,以及在《宋史》有著录的勇将李浩(?-1090后)(按:李浩之父皇城使李定〔?-1063后〕则名列第三将之首),均碑上无名。是故杨文广碑上无名,并不能证明他不在从征的二百三十一人内。 51 对于这问题,笔者以为其实比较有力的旁证,还是常征自己所引用、由沈遘(1028-1067)撰写的一道〈西京左藏库副使杨文广可供备库使〉制诰以下一番话:
敕某:前日南夷负恩为乱,以覆坏我郡邑,至于用师而后定。虽朕不德,不能怀服方外,而亦将吏不戒不习之罪也,故深察往失而推择所遣,益不敢轻。惟尔文广,材武忠勇,更事有劳,故今以尔总一道之兵,戍于邕管。 52
考沉遘写这道制诰,一开始即提到「南夷负恩为乱,以覆坏我郡邑,至于用师而定」。当然,沉遘所说的作乱「南夷」,固然可以指在「前日」即嘉佑五年底入寇邕州的交趾与甲峒蛮(详下文),但更有可能指数年前真正覆坏许多郡邑,要宋廷用重兵才能平定的侬智高之乱。按宋代制诰之普遍写法是先表扬受职人的旧勋,然后提出宋廷对受职人的期望。倘沉遘所言的「负恩南夷」确是侬智高,则杨文广被称许为「材武忠勇,更事有劳」,就当与前述的平侬智高事有关。要说杨文广在平侬智高之乱上毫无干涉,沉遘就不用这样写。
除了沉遘这道制文外,杨文广有份从征的另一个有力旁证,是笔者从宋人文集中找出来,确信是杨文广在治平二年(1065)拜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时的制文。考撰写这道制文的是在英宗(1064-1067在位)朝任知制诰的郑獬(1022-1072)。郑獬说杨文广「尝以忠谨佐骑兵,环徼道而侍,夙夜有劳」;故此「宜用次补」为管军。笔者认为郑獬这番话正是指杨文广当年率骑兵从征侬智高有劳的事。考郑獬之父郑纾,曾以都官员外郎从征侬智高,任孙沔第二将的管勾机宜。倘杨文广有份南征的事不假·郑獬在制文上,溢美一下乃父旧僚的旧劳,是顺理成章的事。 53
除了上述两道制文的旁证外,我们若从人脉关系的角度去看,杨文广被召从征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按杨文广既为范仲淹及韩琦所知,又毫无疑问为久在陕西的狄青所认识,即使不是韩、范所荐,狄青亦会征他从征。据曾巩的记载,狄青所征辟的将校,「皆青之素所与,以为可用者」。 54 杨文广既是狄青所认识的,本身又有才干,他若不被征召,才是怪事。大概杨文广在南征中并未担任重要的战斗角色,更未参预归仁铺一役之恶战(按:清人所传他追击侬智高之事只能存疑),55 故此他功劳不显,除了《宋史》本传外,就未载于其他史籍中。笔者认为,虽然有力旁证不多,但杨文广从狄青南征侬智高的可能性仍较高。
狄青的大军于皇佑五年正月,经过归仁铺一役之浴血大战,击溃了侬智高。 56 宋廷厚赏有功臣僚,除主帅狄青获擢枢密使,副帅孙沔升任枢副,余靖优迁为工部侍郎外,其余将校,原为诸司使臣的分三等迁官,迁者十三人,例如归仁铺一役有大功的贾逵,便自如京副使超擢为西染院使领嘉州(今四川乐山市)刺史;另荆南钤辖王遂,便以一等功,自左卫将军优迁为皇城使、资州(今四川资中县)刺史;至于三班使臣就分五等迁资,迁者凡七十二人,其中张玉由右班殿直超迁为大使臣之首的内殿承制,并任广西钤辖。杨文广大概在这七十二人中,而得以出知渭州之德顺军。 57
杨文广知德顺军的任期,《宋史》并没有提及。常征据沉遘前述的制诰,未经考究,便草率地认为杨文广在皇佑五年从征侬智高后,以功升西京左藏库副使知德顺军,并在翌年,即至和元年(1054)更超升四级为供备库使,自知德顺军升任广西钤辖兼判宜州(今广西宜州市)与邕州。 58 遗憾的是,常征犯了四项错误:第一,其实从皇佑五年开始到嘉佑五年(1060)底,知邕州一直是追杀侬智高有功的萧注(1013-1073)。至于广西钤辖就分别由张玉及卢政(1007-1081)担任,与杨文广并不相干;59 第二,在官阶方面,杨文广在皇佑五年不可能是西京左藏库副使。考杨在平张海之乱后迁殿直。我们假定杨因功所授是左班殿直,从庆历三年底到皇佑五年初的十年当中,若依循正常迁转,即使有范仲淹的保荐,在没有大战功的情况下,杨文广最多只能迁升三阶,即像乃兄杨德政那样做到西头供奉官。要说杨文广出守德顺军时已官至西京左藏库副使,除非他像张玉那样立下奇功,获得超擢,但并无证据证明这点。第三,沉遘这道制诰绝对不是至和元年写的。笔者根据《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皇宋十朝纲要》、《全宋文》及王安石撰的〈沉内翰墓志铭〉,考索沉遘的仕历,可以确信这道制诰最早只能在嘉佑六年(1061)初,最迟在嘉佑六年十二月,当沉遘担任知制诰时所撰;60 第四,据《宋史》所记,杨文广在知德顺军任满后,先调知宜州,才升为供备库使为广西钤辖知邕州,绝对不会如常征所说「兼判宜、邕两州」。早在皇佑四年十月,宋廷接受枢密副使王尧臣(1003-1058)的建议将广西分为三路,置宜州、容州(今广西容县)、邕州三州安抚都监,以融州(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和象州(今广西象州县)隶宜州;白州(今广西博白县)、高州(今广东高州市)、窦州(今广东高州市北)、雷州(今广东雷州市)、郁林州(今广西玉林市)、化州(今广东化州市)、南仪州(今广西岑溪市)、藤州、梧州、龚州、琼州(今海南海口市)隶容州;钦州(今广西钦州市)、宾州(今广西宾阳县西南)、廉州(今广西浦北县)、横州、海州(今广西桂平市)、贵州隶邕州。杨文广在知宜州时连广西钤辖都不是,怎会兼知两大州?事实上,在嘉佑六年,在杨文广调知邕州的同时,继他出任知宜州的是皇城使宋定。 61倘笔者考证不误,杨文广在皇佑五年出知德顺军时的官阶最多是大使臣的内殿承制,他要到嘉佑六年出知邕州前才累迁至西京左藏库副使。至于他任知德顺军时之年月,据笔者的推测,他当历两任,即共在德顺军六载,至嘉佑三年才南徙至广南西路的宜州。 62
德顺军即渭州陇竿城,据王尧臣在庆历三年正月从陕西考察回来所写的报告称,它与羊牧隆城(今宁夏西吉县将台乡南火家集西北)、静边(今甘肃静宁县红土嘴)、得胜(今宁夏西吉县硝河乡)四寨,在六盘山(今宁夏固原县西南,接隆德、泾源二县界)外,内则可作渭州的藩篱,外则为秦陇襟带,地土饶沃,人口众多。其中尤以笼竿城蕃汉交易,市邑富庶,胜过所有近边州郡。为此之故,西夏早有夺取之心,亦因笼竿城距西夏界较近且道路容易,但往宋的内地就有山川之阻,王尧臣当时即建议将笼竿城等四寨建置为军,择路分都监一员知军,专提举四寨,令修浚城堑,添屯军马,及时聚蓄粮草,以为备御。宋廷接纳王的意见,就在同月以陇竿城建为德顺军。 63 另据李焘所记,德顺军建置后,在至和年间,其静边寨由蕃部组成的壕外弓箭手尤为劲勇,诱使夏人多次来争,幸而因宋军已筑堡防守,夏人之谋不得遂。到嘉佑五年以后,宋廷更在德顺军及原、渭州置场收市,以解州盐引与蕃商交易良马八千。直到英宗治平年间,德顺军一直是宋廷与西蕃买卖战马的重镇, 64故杨文广获委为知德顺军,绝非闲职。杨文广在德顺军任上之事迹,史所不详,我们只能从沉遘制文中「材武忠勇,更事有劳」的评语,相信杨文广做得相当称职,而从上面李焘所记,西夏在至和年间多次进攻静边寨不得逞,也可推论到杨文广筑堡防守之本领相当不俗。据陈守忠往德顺军遗址的实地访查,在德顺军所辖的得胜寨,相传是杨文广点将之处,这亦与史实符合。 65
杨文广在知德顺军任上的上司,从至和元年四月始,直至嘉佑元年十一月以后,一直是龙图阁直学士、泾原经略安抚使兼知渭州任颛(990-1067)。任颛有谋略,长于守边,曾著《治戎精要》三卷,述西夏风物、山川、道路及出入攻取之要。狄青南征时,他又负青扼守后方潭州(今湖南长沙市),以诛除侬智高奸细有功。他除了与杨畋有旧外,相信亦与从征侬智高的杨文广相识。他以在潭州卑湿得脚疾,起初请调舒州(今安徽潜山县),最后宋廷命他出知渭州。杨文广调知德顺军,说不定是任颛的推荐。任颛守渭,史称「军中之政宽猛相济,将吏畏伏」。看来杨文广与任颛合作无间。可惜的是,任颛未几以年老求徙徐州,接着便致仕,未能对杨文广的仕途有什么帮助。 66
本来最能提拔杨文广的,是他的旧上司枢密使狄青。不幸的是,狄青在嘉佑元年(1056)八月,被猜忌他的文臣集团以不光明的手段逐出朝廷,且在翌年二月在陈州(今河南淮阳县)愤恨而亡。 67 狄青死后,能对杨文广仕途有助的朝臣,除了在嘉佑三年六月拜相的韩琦外,相信就是他的族姪杨畋。杨畋在皇佑五年正月被降职后,大概因余靖的极力说情及推荐,很快又回升为起居舍人、河东转运使。他在嘉佑三年八月前入为三司户部副使,不久又兼同勾当三班院,未几又升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判吏部流内铨,到五年中又改知制诰。到嘉佑六年中,杨畋又擢龙图阁直学士复知谏院。笔者相信,论关系与地位,杨畋与他的好友余靖,都是最有可能举荐杨文广出任要职的人。 68
杨文广从嘉佑三年至六年知宜州任上的事迹亦不详,只知他的继任人是官阶比他高的广南西路安抚都监皇城使宋定。 69 杨文广的官阶,相信在他调任知宜州时已升为西京左藏库副使。至于他在嘉佑六年被撰为广西钤辖兼知邕州,原因是广西又出了问题。考知邕州凡八年的广西都监萧注,为了立边功,早在嘉佑四年九月,便以利益厚结广源诸蛮,暗中修缮甲兵,准备攻略交趾。但萧注尚未动手,在嘉佑五年七月,其部将都巡检宋士尧便因追击入寇邕州的西平州峒将,进入交趾,虽初战得胜,但第二天,宋军便受到交趾与甲峒蛮的反击,以致全军覆没。交趾与甲峒蛮联军又乘胜追击,入寇钦州的永平寨(今越南高谅省禄平)。宋廷见事态严重,在同年八月命熟知蛮事的余靖以吏部侍郎、集贤院学士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使,往广西应付交趾的入侵。宋廷在同年十一月,又以萧注在广西所为不法,挑起祸端,将他贬职徙为荆南钤辖。他的遗缺就由余靖的副手如京使、知邵州(今湖南邵阳市)贾师熊出任。 70 余靖在六年五月将入寇邕州的甲峒蛮及苏茂州蛮击退后,便升任尚书左丞,调为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广州。当时岭南仍未平定,贾师熊却又力辞知邕州之任,大概因杨畋的推荐,余靖想起他当年平侬智高的旧部杨文广,就向宋廷举荐杨自邻近的宜州调任邕州。 71
杨文广在嘉佑六年调任广南西路钤辖知邕州时,他的官阶也自西京左藏库副使迁为供备库使,终于进入诸司正使的行列。他的上司是颇有智计的广西转运使李师中(1013-1078)。杨文广在邕州的治绩所载亦不多,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杨文广在邕州时,一直密切注视交趾的动向,一有风吹草动,就马上遣军校乘驿向李师中报告。 72 附带一谈的是,常征曾引用明清人的传闻,说杨文广曾知全州(今广西全州县)及柳州,不过,在未有确实的记载证明前,这类说法只能存疑。 73
杨畋于嘉佑七年五月病逝,74 对杨文广自然是坏消息,太原杨家两房,到了这时候,就以他们叔姪二人一文一武最有成就,最能维持家声。现时杨畋过世,杨家就只能靠年事已高的杨文广支撑了。
嘉佑八年三月,仁宗病逝,由其姪英宗继位。杨文广大概因新君嗣位的恩典得到迁升。据《宋史》本传所记,他在治平初年以前,已超升十五资为左藏库使并带御器械,为他日出任副都总管及管军累积了必须的资历。 75不过,体弱多病的英宗,才是教他大器晚成的伯乐。
假定杨文广在庆历三年是四十四岁,到英宗即位,他应已六十四岁。对武臣已言,像狄青那样晋位二府,是极之不易的;但只要有边功、有点运气,晋身「礼继二府」的三衙管军,却不是太难。
英宗继位翌年,即治平元年,三衙管军出现人事变动,多年前做过杨文广上司的步军都虞候赵滋在是年五月病逝。 76 到同年八月,殿前都指挥使李璋(1021-1073)解军职,英宗即以马军副都指挥使郝质(?-1083)升任殿帅,其余马帅、步帅、殿候、马候、步候就分别由贾逵、宋守约(?-1075)郭逵(1022-1088)、窦舜卿(985-1072)、石遇(?-1065)依次替补。至于捧日天武及龙神卫四厢两缺似乎未补人。 77 英宗大概要证明他御政的能力,在病体稍痊时,于是年十月就亲自检阅禁军诸军班直将校武艺,并擢授有才之将校。 78 到治平二年初,步军都虞候石遇卒,三衙管军共有三缺。英宗这次亲自决定升补的人选,在是年六月,英宗擢用他在藩邸时曾留有良好印象的杨遂,自绛州(今山西新绛县)团练使,岚(今山西岚县) 、石(今山西离石市)、隰州(今山西隰县)缘边都巡检使为步军都虞候,加登州(今山东蓬莱市)团练使。 79 考《宋史》称英宗在「治平中」擢用杨文广,按治平中当为二年,杨文广被擢为三衙管军的年月,极有可能与杨遂被擢之年月接近。又据刘挚(1030-1097)所记,杨畋所甚赏识的陶弼(1015-1078)在治平二年即以崇仪使知邕州,正脗合杨文广在是年召入朝出任管军之记载。据《宋史》载,当宋廷议论谁可补授「宿卫将的管军时,英宗即以杨文广为名将之后,且有战功,耀为成州(今甘肃成县)团练使,拜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杨文广这年当已过六十六岁,算得上是大器晚成。至于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一缺,便擢用另一员老将高阳关都钤辖卢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八员管军中,贾逵、杨遂、卢政和杨文广四人都是曾随狄青南征的大将,而二杨和卢政则分别从西边、西南及北边征召入朝,出掌禁旅。80
杨文广擢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在宋廷文臣眼中,是莫大的荣宠,诚如苏辙在元佑五年(1090)所论,「自祖宗以来,以管军八人总领中外师旅,内以弹压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职任至重」。 81 郑獬为杨文广撰的四厢都指挥使的制文,除称许他昔年从征侬智高之劳外,又期许他在治军时能「严法令,明白善恶,以率其不恪」,并将之比喻为汉宣帝(前73-前49在位)时之中郎将、平通侯杨恽(?-前54)。 82
杨文广能被擢为管军,除了受知于英宗外,相信亦受到宰相韩琦的极力推荐。虽然在现存的韩琦文集中,暂时找不到韩琦与杨文广交往的直接证据,但笔者却在韩琦心腹强至(1022-1076)的文集中,找到杨文广与强至通信的实证。强至在〈回杨四厢书〉中,有以下的描述:
向承高谊,远枉盛笺。论志意之欲为,顾言辞之甚壮。知是仁者之有勇,可使儒夫之闻风。间又相规,正如所愿,甚为钦感,尤剧感铭。 83
考强至这封信的撰写年月不详,暂难确定杨文广收信时,是在京中统率禁军,还是已出守秦凤?韩琦在治平四年十一月出守陕西时,强至即任其机宜书记,84 杨文广虽在韩琦麾下,但韩、强在永兴军,杨在秦州,二人通信,说是「远枉盛笺」,也说得通。不过,强至在这信中丝毫没道及杨在秦州供职之事,故笔者推测此信当撰于杨尚在京师时。我们从强至这封信,可以从侧面窥见杨文广在出任管军后,虽年事已高,但仍胸怀大志,给人老当益壮,勇气不减之感。另外,虽寥寥数语,但亦看出他与强至交情非泛泛。他后来随韩琦出守陕西,得到韩之倚重,实是顺理成章的事。
除了韩琦外,龙图阁学士张方平亦很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帮助杨文广擢升。首先,张方平早在皇佑五年十一月南郊大赦时,上奏请录用杨业等五员御边名将的子孙。这大概让英宗对杨家留下一个良好印象。 85 其次,当张方平在治平元年底出知郓州(今山东郓城县)前入对,向英宗论及管军的人选时,他除了指出根据祖宗的做法,若有履历才具适合的人,可以直接擢为副都指挥使或都虞候,不必经过四厢一阶;另外他又强烈批评「近日所补军职,人材器略多无素望,至于累劳,亦无显效,短中取长,苟备员而已,又递迁迅速,曾微事功」。他并特别点名批评刚在是年八月升任殿前都虞候的郭逵。虽然他推荐可任管军的人没有杨文广,但他的话显然加强英宗破格擢用杨遂、杨文广二人为管军的决心。 86
治平三年(1066)四月,三衙管军人事再有变动,因殿前都虞候郭逵被擢为同签书枢密院事,同年五月,就由马军都虞候窦舜卿升任殿前都虞候,至于马候一职,就由步候杨遂替补。原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卢政则升任步候。杨文广相信在这时,亦得以补升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至于他的遗缺,相信就由在是年九月在柔远寨(今甘肃华池县)立功的环庆副都总管张玉补授。 87
平治四年(1067)正月,英宗病逝,神宗继位,因新君嗣位,杨文广大概因此得迁为兴州(今陕西略阳县)防御使。 88 是年闰三月,神宗诏诸路帅臣及副总管移易,大概杨文广就在这时出为秦凤路副都总管。 89
是年九月,韩琦罢相出判相州。到年底却因知青涧城种谔(1027-1083)在十月袭取绥州(今陕西绥德县),宋夏又再交锋,是年十一月,神宗改命韩琦为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判永兴军,统筹陕西全局。 90神宗胸怀大志,有开疆辟土的机会,他绝不放过。他对付西夏的办法,在缓进方面,就秉承仁宗时范仲淹、韩琦的做法,在宋夏边上要塞之地,多建堡寨,招纳蕃部,以削弱西夏的国力。韩琦宣抚陕西,即积极执行这项政策,广建堡寨。在这环境下,擅于筑城的杨文广,终于英雄有用武之地。
大概在治平四年底或熙宁元年(1068)初,杨文广的上司、秦凤经略使知秦州马仲甫(?-1080)向韩琦建议,在秦州西边、渭河支流散渡河上之筚篥城故址(按:《宋史》作「筚栗」)筑城而垦耕之。筚篥原为秦州生户所居,面积有百里之广,因原居之生户被西夏劫走而无主。韩琦赞成其主张,但枢密使文彦博不同意,怕此举会引起夏人之争执。韩琦多番上奏,据理力争,认为在陕西各路缘边筑城,招纳蕃部防守,早有前例,绝非生事,他并且提出筑城后之具体安排,包括在何处调兵戍守,以及怎样置酒税场课利。韩琦且进呈有关筑城的图则。宋廷在是年七月,终听从韩琦的建议,准许在筚篥建城。 91
韩琦除了在筚篥故城筑堡外,又计划在距筚篥八十里的擦珠谷(按:《宋史》及《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未》作「喷珠」)筑堡。杨文广在是年七月奉韩琦命,分别在筚篥及擦珠谷筑城,据《宋史》及《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记载,杨文广晓得夏人会来争,就采取声东击西之计,对诸将佯称去擦珠谷筑城。当宋军在日暮前赶到该处时,杨文广马上下令掉头急行军赶去筚篥,并马上立寨安营,做好防御及战斗准备。当夏人知道中计,在翌晨赶到时已太迟,虽然夏兵为数不少,但见宋军有备,只好退兵。夏人临走时致书恐吓杨文广,声称会禀知夏主,出兵数万骑来争此城。杨文广看穿夏人其实色厉内荏,马上遣将追击,结果斩获甚众。杨文广这次出奇制胜,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别人问他致胜之道,他回答说作战要取得先机,所谓「先人有夺人之气」(按:《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未》作「夺人之心」。筚篥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就不能让夏人知道宋军有夺取之企图,因为夏人知道而快一步占领,宋军要取回就十分困难。杨文广占据筚篥,并击退夏人,筑城就顺利得多。就在是年九月,杨文广在簟篥筑好大甘谷寨,取名甘谷城(今甘肃通渭县南杨家城子);跟着他又在擦珠谷筑堡,到是年底竣工,取名通渭堡(今甘肃通渭县什川乡李家坪,按:熙宁五年升为通渭寨)。宋廷优诏嘉奖杨文广,并赐他对衣、金带及银鞍勒马。< sup>92
杨文广修筑甘谷城及通渭寨,可说是他戎马生涯中的一大杰作。他对敌情的准确判断、行军布阵之快速,以及筑城之效率,既见其智勇,亦显其杨门之绝艺。此外,甘谷城亦因杨文广之故,留下杨家将之传说。据陈守忠在1984年5月往二城寨的遗址实地考察,甘谷古城当地有一村杨姓人家,相传是杨家将的后代。陈守忠认为杨文广嫡派子孙留在此地可能性不大,但他帐下亲兵以主帅的姓为姓,留守在这裹,而留下后代,则甚有可能。陈氏的论断可取。 93
杨文广筑毕二城后,大概以三年任满,并因宋廷调整陕西各路帅臣人事之故,在熙宁二年(1069)以后徙知泾州的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县),至于秦凤副都总管之职,就由殿前都虞候窦舜卿接任。本来杨文广应兼任泾原副都总管,大概渭帅蔡挺(1020-1079)仍属意他的爱将张玉留任,也可能是判延州郭逵的要求,宋廷就安排杨文广徙知鄜州(今陕西富县),做郭的副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杨文广先权知鄜州,到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正式与知鄜州孟德基(?-1079后)对调差遣,由孟知镇戎军,杨知鄜州。未知何故,身为管军的杨文广,竟没兼鄜延副都总管。 94
就在杨文广徙知鄜州之时,西夏在熙宁三年八月举国入侵,兵锋直指环庆路诸州军城寨。因环庆经略使李复圭(?-1074后)措置无方,宋军损兵折将。宋廷于是命参知政事韩绛(1012-1088)为陕西宣抚使,统筹陕西全局。九月,韩绛抵陕西后,调兵遣将;不过,韩绛重用种家将第二代的种谔、种诊(?-1083后)兄弟之余,对杨文广就投闲置散。杨的上司郭逵因与韩绛意见不合,就被召还京师。 95
熙宁四年(1071)八月,神宗决意开边熙河,他派王韶(1030-1081)领兵出征,所部勇将包括泾原副都总管张玉和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1026-1085)。宋军从秦凤路出发,但久在秦凤的杨文广这次又未被选上从征,也许王韶觉得年过七十的杨文广已英雄迟暮了。 96
熙宁五年(1072)十一月,殿前都虞候、环庆副都总管窦舜卿以疾请解军职,他的遗缺就依次由马军都虞候杨遂补上,而卢政就由步军都虞候迁马军都虞候。杨文广虽然没有显赫战功,也得以晋升一级为步军都虞候,相信亦在这时,调离陕西,出任河北的定州副都总管,回到杨家将当年守御辽国的地方。 97
杨文广任定州副都总管时,他的上司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市)是通晓兵略的滕甫(1020-1090)。 98 不过,宋辽和好多年,河北防务早就松懈。对于辽人在熙宁六年(1073)六月开始有异动,神宗不无忧虑,他对臣下表示「北人渐似生事,今河北一路兵器皆抏敝不可用,加以将卒庸堕,何以待敌」?但主政的王安石正将注意力放在熙河开边,不想节外生枝,分散力量,就安慰神宗说:只要训练士兵,完缮城垒,选择将帅便成了。其实王安石并不将河北防务放在心上,故并未重用滕甫或杨文广等能吏宿将。 99
王韶在熙宁六年十月向宋廷奏报,已收复熙州(今甘肃临洮县)、洮州(今甘肃临潭县)、岷州(今甘肃岷县)、叠州(今甘肃迭部县)、宕州(今甘肃岩昌县)等州,开地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近二万人,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神宗和王安石君臣自然喜不自胜。王韶以下有功将士,连带陕西各路帅臣,都以支援之功,得到厚赏迁升。 100 但宋廷开心快活澴不到一个月,已谍知辽国打算争夺蔚(今河北蔚县)、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州市)三州地界。神宗担心辽夏会一齐侵边,怕两面受敌。王安石一面用乐观的分析以安神宗之心,认为辽国不会弃绝和好;另一方面清楚表明他的策略,就是「朝廷未宜有北事」,而夏人不足畏。即是说:一旦有事就对辽主守,对夏主攻。 101
王安石的乐观却事与愿违。熙宁七年(1074)正月,辽国开始在议界一事挑起争端,是年二月,神宗除命王安石设法改善河北防务外,也准备在辽使到来时进行谈判。但王安石不赞成力争,亦不相信辽会动武,认定可以慢慢与辽理论。王安石还力主在河北裁兵,又反对调熟知边事的郭逵知定州。最后神宗接受王的建议,派三司使、龙图阁学士薛向(1016-1081)出知定州,代替滕甫,成为杨文广的新上司。 102
是年三月,辽派萧禧到来,议蔚、应、朔三州边界。宋廷随即派刘忱、萧士元及吕大忠(?-1094后)往代州(今山西代县),与辽使商量地界,稍后再派天章阁待制韩缜(1019-1097)使辽。就在韩缜使辽途中,王安石被罢相。不过,继任为相的韩绛并没有改变对辽妥协的政策。 103 就在宋廷主张对辽让步,以求息事宁人的气氛下,杨文广却出人意表的向宋廷献上攻取幽燕的阵图和方略,不但反对割地妥协,还主张对辽用兵,收复失土。这裹,我们倒要探究一下,杨文广为何贸然上奏?究竟他是不甘寂寞,企图以大言引起神宗注意,还是深思熟虑,认定伐辽机会难逢?这一方面余嘉锡和常征都没有讨论此问题。 104
虽然今日我们看不到杨文广所上的奏状和阵图内容,但从杨文广一向谨慎低调的作风,笔者认为杨文广绝非信口开河,无的放矢的人,他一定经过周详的考虑,才会在宋廷倾向对辽妥协的环境上书。笔者认为杨文广确是在长期不得志的情况下,趁着辽国挑起争端之时机,尽他最大及最后的努力,希望说服及打动神宗,让他统军攻辽,完成父祖未完心愿,并为祖父复仇。笔者猜测杨文广其实已从他的上司、知定州滕甫处,洞悉神宗一直想攻辽,以报太宗为辽军所伤致死之大仇的心事。另外,他看透辽国其实色厉内荏,国力早已今非昔此,只要宋廷做足准备,再觅得有利时机,出兵幽燕并非无取胜机会。 105 至于他所进呈的阵图和奏状,肯定是据他在定州多年来打探得来的敌情,以及得自父祖的秘本编绘而成。神宗君臣不是草包,杨文广要说服神宗,他所进呈的东西,必定是精确的作战计划和图则,以及详尽的敌情分析。笔者相信杨文广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不幸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赏识杨文广的韩琦早罢相外任,而且韩琦在伐辽事上后来还持反对的态度(事见下文)。杨文广在两府并没有支持他的人,他的「奇策」就很「正常」地一直得不到宋廷的回应。朝中无人,是杨文广一直得不到重用的原因,这次也不例外。杨文广等不到宋廷的回覆,就在是年十一月赍志以殁。假定他在父卒时十五岁,他当得年七十五。宋廷在翌年闰四月,循例追赠他同州(今陕西大荔县)观察使。至于有否录他的子姪为官,则史所未载。 106
杨文广的谋议是否可行?后世景仰杨门忠烈的学者如余嘉锡等都只是赞叹,而惋惜它不被采纳。其实杨的奇策在他身故后四个月,即受到韩琦的严厉批评,韩琦还近于不点名批评他故去的部将。韩琦在熙宁八年(1075)三月应神宗之召议辽事即指「今好进之人,不顾国家利害,但谓边事将作,富贵可图。献策以干陛下者,必云「敌势已衰,特外示骄慢矣。以陛下神圣文武,若择将臣领大兵深入敌境,则幽蓟之地,一举可复」。 」。韩琦并且分析:「今河朔累岁灾伤,民力大乏;缘边、次边州郡刍粮不充,新选将官皆麄勇;保甲新点,未经训练。若驱重兵顿于坚城之下,粮道不给,敌人四向来援,腹背受敌,欲退不可,其将奈何?此太宗朝虽曹彬、米信名德宿将,犹以致歧沟之败也。」107 韩琦的分析是否得当,因我们今日看不到杨的原奏,故难以一面之辞作出评定;不过,从韩琦及同时应召言事的文彦博对伐辽之议的强烈反应,似乎杨文广的建议在宋廷中也有人认同,并在相当程度上打动了神宗,108 以致韩琦等非要用明确的措辞及看似无可争议的理由来反对。杨文广的谋议到底有多少真知卓见?杨文广主张伐辽的真正目的是收复失土,还是为了划界谈判故意做出不惜一战的姿态,以迷惑辽方的间谍? 109 可惜它和杨文广的后人一样,今日已无从稽考。
北宋杨家将的名声在明代以后,凭着小说戏曲的渲染,成为整个宋代最为人知的将门。然考诸史实,这个在宋代名声最响的将门,本来名过其实。即使将旁支的杨畋计算在内,太原杨氏到了第四代,已到了强弩之末的境地。杨家的第五代可考的是杨畋的独子杨祖仁(1061-1113后),他亦从文官之途仕进,然在哲宗(1086-1100在位)绍圣年间也只担任地方小官,以后的事迹亦不显。 110 有些学者如常征将播州杨氏以及南宋初年的庸将杨存中(1102-1166)也算作杨家将,是很有间题的。 111 我们感情上景仰杨门忠烈,但要接受的事实是太原杨家其实到了第三代,已和绝大多数的宋代将家一样,每下愈况,走向衰落。杨家的运气其实已算不错,当杨延昭长次两子无法克绍箕裘,家道中落之际,幼子杨文广却在步入中年时,交上好运,得以中兴杨家,勉强撑起家门将倒的旗帜。比起父祖,杨文广的实际地位最高,最后官至父祖不曾得到的管军高职:不过,他的军旅生涯实在平凡,父祖的「无敌」、「善战」似乎不曾在他身上出现过。虽然英宗称他「有功」,沉遘和郑獬代表宋廷说他「材武忠勇,更事有劳」、「忠谨佐骑兵,环徼道而侍,夙夜有劳」,而强至也称他「仁者之有勇」;惟据目前可见之资料,他平生并未经历什么恶战。考他出仕时从平张海,不过是与人数有限之鸟合之众交锋。后来他虽然随狄青南征侬智高,但并没有参预归仁铺之生死大战。至于戍守西南、西北及北面多个州军,除了在筑城筚篥一事上看出他的一点将略智谋外,就只能笼统地说他守边克尽阙职,没出纰漏。至于他所献的取幽燕谋议,当时就已被韩琦批评为不可行,不能以此过誉他的将略。我们从杨文广的经历和遭遇,可以看出曾经显赫一时的将门,要维持三代,实在极不容易。杨文广还能够大器晚成,自身的条件是他尚能掌握祖传的筑城绝技,而凭这点本事得到范仲淹及韩琦的赏识。另外,作为将家子,他也能顺应时势潮流,既懂得与文臣儒生交结,争取他们的支持,又能兼通文墨,执笔陈奏,争取君主之好感。在际遇运气方面,他正好碰上内乱与外患的环境,就教他有用武立功之机会。本事与机遇的结合,就是他能出人头地,重振家声的关键。当然,他不能像主将狄青一样,功名事业更上一层楼,亦与运气稍逊有关。杨家最大的不幸,就是杨文广竟没有一个较出息的子孙。最明显的证据是他的不肖子孙,竟然连为祖宗写一篇像样的墓志铭都做不来(按:与杨文广有交情的强至卒于熙宁九年〔1076〕,按理杨家子孙起码可找他为文广写墓铭),112 也无法保存杨文广的著作或奏议书柬,以致我们对杨文广生平事迹所知如此有限。究竟是杨文广教子无方?还是其子孙太不成材,就无法确知了。
创业维艰,守成更难,将家子要维持家声不坠,往往比白手兴家还要难。我们从狄青及其部将的兴家发迹之事例,亦可见一斑。考狄青及其七员官至管军的部将,除了狄青本人与和斌的下一代尚能勉强维持将门的声誉外,其余的人(包括杨文广)的后代均无法守业。 113 杨家能三代为将(若加上杨畋则为四代),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逾百载,实在已是得天独厚。杨氏将门从勃兴到衰败,与宋代众多将门之兴衰过程比较,其实并无显著的差异。只因小说家把杨家将渲染和神化得过份,我们才会对杨文广寄予厚望,并想不通杨家将「骤然」消失的缘由。
1、参阅纪振伦(?-1573后)(着),竺少华(标点):《杨家府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216-303。关于杨家将小说的版本及流传情况,特别是《南北宋志传》与《杨家府演义》之比较,最近期之研究,可参阅马力:〈《南北宋志传》与杨家将小说〉,《文史》第十二辑(1981年9月),页261一272。是条资料蒙马幼垣教授赐示,谨此致谢。另可参阅程毅中〈杨家将故事湖源〉,《燕京学报》新十期(2001年5月),页257-268及〈杨家将故事溯源补正〉,《燕京学报》新十一期( 2001年11月),页283-284;孙旭、张平仁:〈《杨家府演义》与《北宋志传》考论〉,《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页211-219。
2、 在《杨家府演义》中,狄青先奉命出征,因战败而仁宗改派年过半百的杨宗保为帅,并以年方弱冠的杨文广为先锋。至于在以狄青为主角的《五虎平南演义》中,杨文广亦是以「少年小将军」的身份出场。参见《杨家府演义》,页216-238;(清)佚名(撰),觉园、愚谷(标点):《五虎平南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35 。又据马力研究所得,《南北宋志传》所记杨文广征侬智高之事,在三个小节上与《杨家府演义》略有不同。参见马力:〈《南北宋志传》与杨家将小说〉,页271。
3、 考宋初确有杨怀玉(?-1022后)其人,但他是内臣,与杨家将并无关系,且年纪要比杨文广长。杨怀玉在真宗(977-1022在位)晚年以入内供奉官任寿春郡王(即仁宗)的伴读,并兼任京城西面巡检;后来在天禧四年(1020)七月因没及时举报周怀政(?-1020)谋叛被眨为杭州(今浙江杭州市)都监;到干兴元年(1022)后复召还为内侍押班。参见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1995年),卷八十六,页1973:卷九十六,页2208,2210:卷九十八,页2284(以下简称《长编》)。
4、 考杨业降宋后官至观察使,后来战死陈家谷(今山西朔州市西南),获追赠太尉、大同军(今山西大同市)节度使;但终太宗之世,并未获追赠中书令或尚书令之官,按理不应被称为令公。虽然小说家不懂宋官制,有胡杜撰官衔之嫌;但也可能有所本。按宋制,军职至三衙都虞候的,一般可获追封三代。例如与杨文广同属狄青部将的杨遂(?-1080),拜马军都虞候时,便获宋廷封赠二代:后来他升任殿前副都指挥使,再获封赠曾祖及祖父。笔者怀疑杨文广擢步军都虞候时,获追封三代之恩典,杨业因此获赠官中书令或尚书令,而给人尊称为令公。可惜杨文广拜步军都虞候及连带之赠官制诰不存,无法证明此点。参见脱脱(1314-1355)(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卷二百七十二〈杨业传〉,页9303-9306;苏颂(1020-1101 )(撰),王同策(等点校):《苏魏公文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卷三十五〈外制·侍衙亲军马军都虞候杨遂封赠二代〉,页538-539;王安礼(1035-1096):《王魏公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杨遂曾祖咏赠太子少保制〉、〈祖德皇不仕可赠太子少傅制〉、〈父进赠左武衙上将军太子太保制〉,叶18上下。
5、 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载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著》(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页456-461(以下简称〈考信录〉)。
6、 常征:《杨家将史事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95-208(以下简称《史事考》)。
7、 陈守忠:〈陇山左右宋代城寨遗址调查〉,载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迹》(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213-219。
8、 参见本书的另一篇文章〈狄青(1008-1057)麾下两虎将——张玉(?-1075)与贾逵(1010-1078)〉。
9、 杨文广二兄的名字,仅见于《隆平集·杨延昭传》,〈考信录〉已点出。按〈考信录〉及《史事考》均以杨文广长兄为杨传永:然笔者翻检《隆平集》,从字型去看,杨文广长兄的名字,似乎又像「傅永」,而不是「传永」。参见〈考信录〉,页456;《史事考》,页195;曾巩:《隆平集》,收入赵铁寒(1908-1976)(主编):《宋史资料萃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1月),第一辑,卷十七,叶4下。
10、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10月),第五册,卷一百九十七〈夏侯观·泽州龙堂记〉,页403-404。
11、 关于杨文广兄弟四人的名字,《史事考》在正文称见于《宋史》、《隆平集》和《宋学士文集》。不过常征的注释做得简单,既没有注明〈杨氏家传〉的卷页,也没有为《隆平集》有关篇章作注脚;但他在正文却说「《隆平集·杨延昭传》虽然也略附文广之事,然不及《宋史》之详」。笔者对各书逐一查证,发觉《宋史》仅载杨文广之名;而《隆平集》虽载有杨传永、杨德政、杨文广之名:但并没有如常氏所说「略附文广之事」 。笔者傻疑常氏没有直接引用《隆平集》。至于宋濂所撰之〈杨氏家传〉,笔者翻阅《四库全书》本的《文宪集》,发现该传其实是播州杨氏的家传,传中称杨延昭有子名充广,却说充< /p>
广是杨业的曾孙。又称杨充广「尝持节广西,与(播州土酋杨)昭通谱,昭无子,充广辍(其子)贵迁为之后,自是守播者皆(杨)业之子孙也」。笔者再翻检《长编》、《宋史》、《宋会要辑稿》等三书之人名索引,并及《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正续篇、《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均找不到任何有关杨充广的记载。考群书只言宋廷录杨延昭三子官,宋濂在二百年后写的一则记载,可信程度教人怀疑。光是说杨充广携子出使广西,而竟将儿子过继播州土酋一节,就很荒诞。笔者以为所谓杨贵迁是杨延昭孙儿的说法,出于播州杨氏自高声价的冒认居多。常征对宋濂这一传闻不加考证而深信不疑,他在毫无佐证下推杨充广在景佑二年(1035)出使广西,并将儿子杨贵迁过继给播州土酋杨昭;他又相信宋濂的记戴,说杨贵迁在皇佑四年(1052)侬智高被平定前被杀。然考《长编》卷二百四十五神宗熙宁六年(1073)五月癸卯条载,「夔州转运判官曾阜上言:播州杨贵迁在夷人中最强盛,以老,遣子光震、光荣献鞍马、牛黄、麝香。诏补光震三班奉职、光荣借职」(按《宋史》卷十五所记相同)。这条记载分明说杨贵迁在熙宁六年时只是老而未死,〈杨氏家传〉说他于皇佑四年死于仇家之手显然是误记。再说,倘杨贵迁果是现任步军都虞候杨文广幼弟之子,宋边吏怎会不知及不向宋廷禀明这关系?另李焘又怎会不在这一条下注明杨贵迁之来历?再者,杨贯还若真是杨文广之姪,则其年龄至少比杨文广年轻二十载,考杨文广在熙宁六年约七十岁,以此推论,杨贵迁当年最多不过是五十岁,如何算得是「老」?从年龄方面去看,显然杨贵迁不可能是杨文广幼弟之儿子。另外,杨贵迁子光震有子亦名文广,倘杨贵迁果是杨文广姪儿,杨光震怎会给儿子改上一个与伯祖父相同的名字?综合上述各点,笔者认为播州杨氏出于所谓杨文广幼弟杨充广的说法很难成立。杨文广有弟名充广之说,只能存疑。参见《隆平集》,卷十七,叶4下;《宋史》,卷十五〈神宗纪二〉,页283;卷二百七十二,页9308;《长编》,卷八十二,页1861;卷二百四十五,页5949;《史事考》,页64-75,195,340-341,343;宋濂:《文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杨氏家传〉,叶34上至37上。
12、 考杨延昭从姪杨琪(980-1050)初以父杨光扆卒于边补殿侍(按:杨光扆卒时官仅西头供奉官,故杨琪仅得不入流的殿侍),后来杨琪即以杨延昭之荫得补为三班奉职。猜想杨文广以幼子多半亦补三班奉职。附带一谈,在小说《杨家府演义》裹,杨延昭之八妹又巧合地名杨琪,小说家大概不知杨延昭有从姪亦名杨琪。参见《隆平集》,卷十七,叶4下;《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页9308;《长编》,卷八十二,页1861;卷八十四,页1911-1912 ;欧阳修(1007-1072)(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年),卷二十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页443-445;《史事考》,页195一196;〈考信录〉,页456;《杨家府演义》,页5。
13、 《史事考》,页195-197。
14、 《长编》,卷一百四十五,页3505。
15、 《欧阳修全集》,卷一百零三〈论班行未有举荐之法札子〉,页1577。另参见注释10。
16、 王称(?-1200后):《东都事略》,收入赵铁寒(主编):《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卷四十八〈曾巩传〉,叶3上;《长编》,卷一百六十三,页3924。另范仲淹在庆历三年主持变法时,也上奏指出「今三班使臣数千人,品流至多,难于区别」。至于上官均在哲宗(1085-1100在位)元佑元年(1086)八月上奏指出,当时大使臣共二千五百余人,小使臣一万三千余人。他说「举天下之员阙,不足以充入仕之人」。虽然在仁宗时的情况没有这么严重,但杨文广补缺升迁之难,却是铁一般之事实。参见《全宋文》(1990年5月),第九册,卷三百七十三〈范仲淹七·再奏乞两府兼判〉,页514(1994年8月),第四十六册,卷二千零三十三〈上官均二·乞清入仕之源流〉,页306。
17、 例如在王安石(1021-1086)所撰的墓志铭,便有好几个武臣,活到七十多岁,仍然官不过使臣。参见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香港:中华书局,1971年),卷九十四〈墓志·左班殿直杨君墓志铭〉、〈墓志·内殿崇班钱君墓碣〉,页972-974。又如五代宋初强藩焦继动(901-978)的孙儿焦君说(985-1041),在天圣中受父焦守节(?-1028后)荫为右班殿直,但浮沉宦海十五、六年,至死只迁两阶至右侍禁。杨文广父祖的官位尚不如焦继勋父子,而他所授的官职又比焦君说低,则他二十多年才迁一两阶,实不足怪。参见《全宋文》(1993年10月),第三十三册,卷一千四百二十六〈李昭文·大宋故右侍禁焦君墓志铭〉,页346-347。
18、 三场战役中,宋军骁将阵亡的计有郭遵、万俟政、张方、孟异、任福、王珪、武英、桑怿等人,而被俘和被杀的将家子,包括三川口之役中的宋军主将刘平(973-1040后)、石元孙(?-1046后),定川寨之役之主将葛怀敏(?-1042)、曹玮( 973-1030)的第三子曹俣,以及前述的骁将郭遵、武英等人,参见本书的另一篇文章〈败军之将刘平(973-1040后)兼论宋代的儒将〉;《长编》,卷一百二十六,页2968,2986,2994;卷百二十七,页3007-3008;卷一百二十八,页3042-3044;卷一百二十九,页3051;卷一百三十一,页3100-3103;《宋史》,卷二百八十九〈葛怀敏传〉,页9700-9704;卷三百二十五〈郭遵传〉,页10505;〈任福传〉,页10506-10507;〈王珪传〉,页10508-10509;〈武英传〉,页10509-10510;〈桑怿传〉,页10510-10512;《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行状墓表·彰武军箭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状〉,页928-930。
19、 《长编》,卷一百二十九,页3056-3057。
20、 《史事考》,页196-197;〈考信录〉,页456。
21、 《欧阳修全集》,卷一百〈论京西贼事札子〉,页1537。
22、 《长编》,卷一百三十,页3083-3084;卷一百七十五,页4221;《欧阳修全集》,卷一百,页1537。
23、 《长编》,卷一百四十五,页3519。
24、 《长编》,卷一百四十二,页3424。按:是条资料与常征所引之《会要辑稿》条相同。参见徐松(1781-1848)(辑):《宋会要辑稿》,国立北平图书馆,1926年本,(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兵十一之十九〉(以下简称《会要》)。考同书〈职官六十四之三十七〉,亦记柳植因当年养寇而在四年三月被眨(按:四年前脱年号)。参照《长编》,卷一百四十二,页3424;卷一百四十七,页3566,柳植是在庆历四年三月被眨。然《会要》的抄写者错将此条置于宝元二年前,而做成错觉,以为张海起事早在宝元二年之「景佑」四年。很有可能常征看了这一条后(按:《史事考》没注引这一条),而推论郭邈山及张海早在明道、景佑年间已起事。另见《全宋文》,第九册,卷三百七十六〈范仲淹十·奏乞召募兵士捉杀张海等贼人事〉,页575。
25、 《欧阳修全集》,卷一百,页1537。
26、 《长编》,卷一百四十三,页3447;《欧阳修全集》,卷三十〈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杜公墓志铭〉,页448-450;卷九十七〈论宜专责杜杞捕贼札子》,页1501-1502。附带一谈,蔡禀是范仲淹的姻亲,其弟是范的女婿。见《全宋文》,第九册,卷三百七十六〈范仲淹十·奏避蔡禀嫌〉,页572。
27、 杨畋是杨业弟杨重动(?-975)的曾孙,其父杨琪与杨文广为从兄弟,杨琪父杨光扆早卒,杨琪初以父卒于边授职殿侍,后来因杨延昭之荫得补为三班奉职,最后官至供备库副使。论辈份杨畋是杨文广堂姪,论关系杨延昭曾照顾过他们父子。当杨畋在庆历三年十月受命讨蛮猺。以他的职务,举荐堂叔为巡检捕贼,在公在私都是合宜的。参见《欧阳修全集》,卷二十九,页443-445;《史事考》,页44-47;《长编》,卷一百四十四,页3483。
28、 据欧阳修在庆历三年及四年(1044)二月点名的劾奏,知郢州(今湖北钟祥市)王昌运及接任的刘依都是老朽无能,败坏州政的庸吏;而知汝州鲍亚之、知邓州朱文郁都是老懦不才,从三司及转运使赶下来的人;另知金州王茂先、邓州顺阳县(今河南内乡县)令李正己均是老昧之辈,任由叛兵入城洗劫且留宿,不敢抵抗;而京西按察使陈洎、张升则昏庸失职,半年内并不按察一人。参见《长编》,卷一百四十三,页3450-3453;卷一百四十六,页3539;《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再论置兵御贼箚子〉,页1538-1539。
29、 《长编》,卷一百四十四,页3478;卷一百四十五,页3496。邵兴之要到是年十一月才被平定。
30、 《长编》,卷一百四十五,页3497,3519。
31、 据韩琦的说法,张海众至千人;但欧阳修则说官兵以八、九千之众去追捕敷百人,似乎说张海只有数百人;不过欧阳修又说张海虽死,但其众溃散,又去别处结集,在达州(今四川达川市)就有军贼数百人,则二人说法亦相近。又据《长编》记载,当张海窜入山中时,韩琦令部将谢云行等将缘边土兵追捕。杨文广可能也在其中。至于擒杀张海的,据包拯(999-1062)所奏,是右侍禁李用和(按:常征说是张永和,不知据何版本)。参见《长编》。卷一百四十五,页3517,3519;包拯(撰),杨国宜(整理):《包拯集编年校补》(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卷一〈论李用和捉获张海乞依赏格酬奖奏〉,页11-12;《史事考》,页197。
32、 《长编》,卷三百六十九,页8892。按苏辙将李顺、张海及廖恩相提并论,只是从其爆发原因相近而论,说到起事声势之盛和参预人数之多,张海和廖恩之起事,实不能与李顺之起事相比。
33、 杨文广升任殿直,是左班抑右班,史所未载。考擒捕张海有功的右待禁李用和授东头供奉官、合门祗候,共迁四阶,包拯仍以为赏薄,则杨文广大概迁两阶为左班殿直的可能性,比迁一阶的右班殿直为高。参见《包拯集编年校补》,卷一,页11-12。
34、 赵滋是开封(今河南开封市)人,与杨文广一样,同属将家子。其父赵士隆在天圣中战殁,他受荫为三班奉职。在庆历初年,以右侍禁为泾原仪渭镇戎军都巡检,因谕降德胜寨(今宁夏西吉县将台镇)叛兵有功,加合门祗候。因张海作乱久未平,以韩琦之荐,命为都大提举陕西、京西路捉贼。数月后乱平,升东头供奉官,调为京东东路都巡检。见《长编》,卷一百四十五,页3514;卷一百五十七,页3812;卷一百七十五,页4221;《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页9308 ;卷三百二十四〈赵滋传〉,页10495-10497。
35、 《长编》,卷一百五十,页3639。
36、 〈考信录〉,页456;《长编》,卷一百五十四,页3740;卷一百五十七,页3807。在下文笔者提到范仲淹在四年十月抵达河东,即考虑在麟(今陕西神木县北)、府(今陕西府谷县)二州修建堡寨。笔者以为,大概他在河东听到杨业曾在该处修堡的往事,于是马上召杨文广前来,查询其祖修堡之经验。故笔者以为,杨文广有可能早在庆历四年底即已入范幕。
37、 考杨畋与韩琦及范仲淹都有交情,在韩、范二人文集中均有和杨畋诗。杨畋先后荐其族叔与韩、范,甚有可能。参见范仲淹:《范文正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和杨畋孤琴咏〉,叶1下;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卷七〈次韵答运使杨畋舍人〉,页306。
38、 《长编》,卷一百五十七,页3813。
39、 《史事考》,页197-199。
40、 考范仲淹在庆历四年十二月即命知原州(今甘肃镇原县)蒋偕(?-1053)与知环州(今甘肃环县)种世衡(985-1045 )先后修筑细腰城和大虫巉。关于杨业修建边寨的情沉,可参见李裕民:〈杨家将史事新考〉,载李裕民:《宋史新探》(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209-214;另参见《长编》,卷一百五十二,页3709-3710;卷一百五十三,页3728。
41、 考狄青在庆历四年八月,已自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刺史、权并、代部署调升泾原部署,加惠州(今广东惠州市)团练使,并越过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一阶,泾授为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位列三衙管军。见《长编》,卷一百五十,页3685。
42、 考范仲淹改知邓州后两年,徙知荆南府;到庆历八年二月,又复知邓州,到皇佑元年中,又改知杭州。参见《全宋文》(1991年3月),第十五册,卷六百十〈富弼二·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页53-60;《长编》,卷一百六十三,页3918-3919;卷一百六十七,页4007。
43、 《长编》,卷一百五十七,页3808;卷一百五十八,页3820;卷一百五十九,页3839;卷一百六十,页3863,3874;卷一百六十一,页3886,3888;卷一百六十四,页3944;卷一百六十六,页3987,3996,4000;卷一百七十,页4098;卷一百七十二,页4138;余靖(1000-1064):《武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九〈宋故狄令公墓铭〉,叶1上至9上;《全宋文》(1991年1月),第十四册,卷五百七十七〈叶清臣·华阴县岳庙题名〉,页181-182。考程琳在庆历七年五月自知永兴军徙知延州,仍任陕西安抚使十月又判邠州,未几又复判延州,至皇佑元年(1049)二月再加平章事留任,直至是年三月调为河北安抚使兼北京留守。接程琳任陕西安抚使的是宣徽北院使李昭亮,李在是年五月改鄜延经略安抚使判延州,至皇佑三年(1051)七月徙澶州(今河南濮阳市)。狄青即在是年七月后接李昭亮,出任鄜延经略使知延州。至于翰林学士叶清臣则在庆历七年五月自青州徙知永兴军并兼本路安抚使,直至庆历八年四月入为权三司使;不过,据庆历八年的碑刻,杨文广似乎并不在永兴军叶清臣麾下。至于杜杞则在庆历八年四月,自河北转运使为天章阁待制,环庆都部署、经略安抚使。按杜杞在平张海之叛时,说得上是杨文广的上司。另名将张亢(994-1056)在庆历七年二月至九月曾任泾原副都部署知渭州,他亦以筑城著名,杨文广会否在他麾下,待考。
44、 参见《长编》,卷一百六十一,页3890-3892;卷一百六十二,页3902-3907;卷一百六十三,页3926;卷一百六十四,页3943;文彦博:《潞公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五〈徼纳具州宣敕·庆历八年闰正月》,叶6上。考宋廷在乱平后赏功极厚,文彦博即以功拜相,明镐则以功擢参政。
45、 《长编》,卷一百六十,页3859;卷一百六十六,页3991;卷一百六十八,页4041。
46、 《长编》,卷一百六十七,页4014-4015,4025。
47、 《长编》,卷一百七十二,页4142-4148,4153-4154。
48、 《长编》,卷一百七十三,页4163-464,4168-4169,4171-4175;卷一百七十四,页4196。杨畋以兵败被降职为屯田员外郎知鄂州(今湖北武汉市),到皇佑五年正月,再降为太常博士知光化军。
49、 郭棐(1529-1605)(纂修):《嘉靖南宁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国罕有地方志丛书》(北京:书目文就出版社,1990年),卷六,叶35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十一册,〈云南三·阿迷州〉,页161;〈云南三·合江口寨〉,页162。
50、 《史事考》,页200:〈考信录〉,页486。按常征没有注明他所据的《读史方舆纪要》卷页。有关之记载,可参阅注释49。至于余靖所撰的〈大宋平蛮碑〉、〈大宋平蛮京观志〉以及〈宋故狄令公墓铭〉均没有提到杨文广的名字。参见《武溪集》,卷五〈大宋平蛮碑〉,叶1上至4下:〈大宋平蛮京观志〉,叶4下至6上;卷十九〈宋故狄令公墓铭〉,叶1上至9上。
51、 参见《全宋文》(1992年4月),第二十一册,卷八百九十〈狄青·平蛮三将题名碑〉,页274-276。
52、 沉遘:《西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西京左藏库副使杨文广可供备库使〉,叶6下。按:常征所引之沉遘制诰,据称录自《宋文鉴》;但他所引的篇目却漏掉「西京」两字,另外他说《宋文鉴》为周必大(1126-1204)所编亦属胡说,不知该书实为吕祖谦(1137-1181)所纂,常氏之粗心大意于此可见一斑。
53、 考郑獬在嘉佑八年出任知制诰,讫治平四年九月,他当制期间,曾撰〈四厢指挥使制〉雨道,本文所引的是第一道。按这道制文没言授四厢都指挥使为何人,但制文引用汉杨恽的典故,显然受文者与杨姓武臣有关。杨文广在治平二年中拜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时间正脗合郑獬任知制诰;故笔者相信这道制盖的受文人,正是杨文广。参见《全宋文》,第二十一册,卷八百九十〈狄青·平蛮三将题名碑〉,页274-275;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卷五十二〈杂识二〉,页719-721;郑獬:《郧溪集》,文渊阁《四库至书》本,卷二〈四厢指挥使制一〉,叶14下至15上;卷十二〈荐钱公辅状〉,叶19上下;卷十八〈纪事〉,叶14上下。
54、 《曾巩集》(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卷五十二〈纪事〉,叶14上下。
55、 根据《长编》、《九朝编年备要》及《宋史》的记迹,再参照滕元发(1020-1090)所撰的〈孙威敏(按:即孙沔)征南录〉所载,有份参预归仁铺一役的宋将,除了立下奇功的贾逵与张玉,以及阵亡的孙节外,还有刘几(1008-1088)、和斌、杨遂、石全彬(?-1070)、祝贵及李定(按:《宋史·李浩传》称李定之子李浩有份从征侬智高,相信李定父子均在阵中)。参见本书的另一篇文章〈狄青(1008-1057)麾下两虎将——张玉(?-1075)与贾逵(1010-1078)〉,页345-350;《全宋文》(1993年10月),第三十一册,卷一千三百五十九〈滕元发·孙威敏征南录〉,页667-671;陈均(1174-1244):《九朝编年备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四,叶38下至41上。
56、 归仁铺一役之经过,可参阅本书的另一篇文章〈狄青(1008-1057)麾下两虎将——张玉(?-1075)与贾逵(1010-1078)〉,页345 -350。
57、 参见《长编》,卷一百七十四,页4205,4208-4209,4214;本书的另一篇文章〈狄青(1008-1057)麾下两虎将——张玉(?- 1075)与贾逵(1010-1078)〉,页349-350。考平定侬智高后出任广西钤辖的,一说是供备库副使李枢(993-1071)。总之并非杨文广。参见《苏魏公文集》,卷五十三〈碑铭·皇城使李公神道碑〉,页807-812。又余嘉锡据《元丰九域志》考出德顺军在庆历三年,以渭州陇竿城置。参见《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页9308;〈考信录〉,页486。关于德顺军之建置,参见注释63。
58、 《史事考》,页200-201。
59、 考萧注在皇佑五年二月以礼宝副使、广南西路安无都监权知昌州,至和元年五月以获侬智高母之功,迁西上合门副使,仍知邕州;到至和二年四月,萧以使人至大理杀侬智高有功再迁引进副使,仍留任邕州。到嘉佑三年(1058)四月,他迁为西上合门使,仍留任知邕州。直至嘉佑五年(1060)十一月,以交趾与甲峒蛮入寇兵败,降职为进副使徙为荆南钤辖,才离开邕州。参见《长编》,卷一百七十四,页4199-4200;卷一百七十六,页4255;卷一百八十,页4355;卷一百八十七,页4508;卷一百八十九,页4550;卷一百九十二,页4634-4647;另见《武溪集》,卷二十〈故萧府君墓志铭〉,叶11上至12上。
60、 据沉遘墓志铭所记,沉遘于庆历八年,年二十时登第。据《会要》记载,他在皇佑五年擢集贤校理。王安石称沈氏任校理八年后,即嘉佑六年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试知制诰。据《长编》,沉遘在嘉佑四年八月使辽时仍任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尚未知制盖。 《长编》未载沉遘知制诰年月,却载王安石于嘉佑六年六月戊寅(二十七)以同修起居注召知制诰。据《皇宋十朝纲要》,沉遘任知制盖,晚于祖无择,而在王安石之前。考祖无择在嘉佑六年正月前已知制诰,则沉遘应在这年初擢为知制诰。另外,当杨文广族姪杨畋在嘉佑六年初升龙图阁直学士知谏院时,正是由沈遘撰写制文,那正可证明沉遘为知制诰乃在嘉佑六年。另外,《全宋文》所收〈越帅沉公生祠堂记〉一文,即记沉遘在嘉佑六年十二月以右正言、知制诰出知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则清楚说明沉遘写这道制文,不能晚于六年十二月。参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三〈墓志·沉内翰墓志铭〉,页961-962;《会要》,〈选举三十一之三十三〉;《长编》卷一百九十,页4587;卷一百九十三,页4662,4677;卷一百九十四,页4711;李真(1161-1238):《皇宋十朝纲要》,收入赵铁寒(主编):《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卷四,叶6上;《西溪集》,卷六〈吏部员外郎知制盖兼侍读杨畋可依前官兼侍读充龙图阁直学士知谏院〉,叶25上下;《宋史》,卷三百,页9965;《全宋文》,第二十一册,卷八百九十一〈沉绅·越帅沉公生祠堂记(嘉佑七年八月)〉,页281-282。
61、 《长编》,卷一百七十三,页4177。考宋定在调知宜州前的官职是广南西路钤、皇城使、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位在杨文广之上。他继任宜州后,升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团练使广南西路安抚都监,仍在杨文广之上。沉遘在撰写制文时,一样称他「材武忠勇」。参见《西溪集》,卷六〈广南西路钤辖皇城使忠州刺史宋定可果州团练使旧官充广南西路安抚都监兼知宜州制〉,叶26下至27上。
62、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页9308。关于杨文广知德顺军的任期,本来按照常例,三年一任,杨应该在至和二年底任满。考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1008-1084)就曾在至和二年十月至十二月,五度上表弹劾另一位枢密使王德用(980-1058),指他的儿子王咸融收受西京左藏库副使马庆长贿赂为马庆长求得知德顺军的优差,且在马未赴任前,又授他接伴副使任务。赵抃的弹奏说明宋廷在至和二年底确委出马庆长接替杨文广知德顺军,不过马未上任即为赵所严劾。考《长编》及《宋史》未载赵抃上言之结果;不过在赵抃连番弹奏下,宋廷不可能派有行贿之嫌的马庆长接替杨文广,相信杨文广也因此得以留任,直至徙知宜州。参见赵抃:《清献集》,文渊阁《四库至书》本,卷七〈论王德用男纳马庆长马状·至和二年十月十六日〉,叶31下至32上;〈乞替马庆长接伴副使速正典刑状·十月十七日〉,叶33下至34上;〈乞罢免王德用状,十一月十一日〉,叶35上下;卷八〈乞勘鞫王咸融纳马庆长状·十二月十六日〉,叶4上下;〈论王德用乞正其罪札子〉,叶4下至5上。
63、 《长编》,卷一百三十九,页3339-3343。
64、 《会要》,〈兵二十二之六〉;《长编》,卷一百七十八,页4317;卷一百九十二,页4641-4644。
65、 陈守忠:〈陇山左右宋代城寨遗址调查〉,页218。
66、 《全宋文》(1992年6月),第二十二册,卷九百三十七〈祖无择四·赠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任公墓志铭〉,页319-325;《长编》,卷一百七十六,页4259;卷一百八十,页4356;卷一百八十四,页4456。
67、 《长编》,卷一百八十三,页4435;卷一百八十五,页4473-4474。关于狄青被逼走而致愤死之事,可参阅本书的另一篇文章〈狄青(1008一1057)麾下两虎将——张玉(?-1075)与贾逵(1010-1078)〉,页352 -354。
68、 《长编》,卷一百八十七,页4512,4519;卷一百九十一,页4614;卷一百九十二,页4648;卷一百九十四,页4712;卷一百九十五,页4720;《宋史》,卷三百〈杨畋传),页9964-9966;《武溪集》,卷十五〈免充集贤学士表〉,叶15下至16下。
69、 参见注释61。
70、 《长编》,卷一百九十,页4593;卷一百九十二,页4634,4636,4640,4647,4648;卷一百九十三,页4664-4665;《清献集》,卷九〈乞勘劾萧注状〉,叶9上下。按萧注在嘉佑六年四月再被李师中严劾,称他「治邕八年,有峒兵十万,不能抚而用之,乃入溪洞贸易,掊敛以失众心,卒致将卒覆败」,而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又大力支持李师中之奏,上表痛劾萧注,宋廷因此再责他为泰州团练副使。又按余靖平乱的经过,李师中曾为文以志。参见张鸣凤(?-1589后)(编):《桂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八〈平交趾记·李师中撰),叶10上至11下。
71、 《长编》,卷一百九十二,页4653,4654;卷一百九十三,页4668。
72、 《长编》,卷一百九十七,页4768;《西溪集》,卷五,叶6下。
73、 《史事靠》,页202。按柳州一度隶宜州,杨文广曾知宜州,他巡部到支郡的柳州而留下遗迹也有一点可能。
74、 《长编》,卷一百九十六,页4761。
75、 按左藏库使为诸司正使第六阶,在皇城使、宫苑使、左骐骥使、右骐骥使、内藏库使之下,是前列的诸司使臣,照例领遥郡刺史,疑《宋史》漏载杨文广所领之刺史职。至于带御器械是加给资深武臣之近职,根据宋制,带御器械的武臣,是须带总管才除授,为将来真除副都总管资基,而檐任副都总管,就有资格升任管军。又宜州亦在广南西路,在邕州东北。参见《长编》,卷一百九十八,页4792-4794;卷二百三十五,页5705;《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页9308。
76、 《长编》,卷二百零一,页4883-4884;卷二百零二,页4895。按余靖亦于是年七月卒。
77、 参见本书的另一篇文章〈狄青(1008-1057)麾下两虎将——张玉(?-1075)与贾逵(1010-1078)〉,页357-360。按窦舜卿自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径升马军都虞候,而石遇则自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径升步军都虞候,补赵滋之缺。参见《宋史》,卷三百四十九〈郝质传〉,页11050;〈窦舜卿传〉,页11052-11053;王安石(撰),唐武(标点):《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卷十三〈窦舜卿可四厢都指挥使〉、〈石遇四厢都指挥使〉,页139:《长编》,卷二百零三,页4911。
78、 《长编》,卷二百零三,页4911。
79、 参见《长编》,卷二百零二,页4895;卷二百零五,页4969;《会要》,〈仪制十一之十八〉。考《会要》在石遇赠官条原抄作「三月三月」,校对者改三月为三年:考杨遂于治平二年六月耀步候,至三年五月除马候;石遇不可能在治平三年三月前任步候;笔者疑抄写者漏抄石遇卒年,而将卒月重抄两次。校者误以三月为三年,而不审治平三年初任步候的是杨遂。笔者以为石遇卒于二年初。又杨遂在英宗登位前,曾以新城巡检救过濮王宫火,故英宗对他有好印象。另外杨遂又得到文彦博极力的推荐。关于是年三衙管军之调动升迁情况,可参见马光祖(?-1269后)(编),周应谷(?-1260后)(纂):《景定建康志》,收入《宋元方志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二册,卷二十六〈侍篇马军司题名记〉,叶32下至33上(以下简称〈题名记〉);《潞公文集》,卷三十九〈举杨遂〉,叶4下至5上。
80、 笔者怀疑英宗擢用杨遂与杨文广时,曾想到真宗朝「二杨」杨延昭与杨嗣(934-1014)同时被擢用的佳话,而有意识的同时擢用二人,以树立新一代的「二杨」风范。参见《宋史》,卷二百七十二〈杨延昭传〉,页9307-9308;卷三百四十九〈卢政传〉,页11055-11056;〈杨遂传〉,页11062;刘挚: 《忠肃集》,文渭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二〈东上合门使康州团练使陶公墓志铭〉,叶1上至2下。
81、 苏辙(撰),曾枣荘、马德富(校点):《乐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四十五〈乞定差管军臣僚札子·元佑五年十月〉,页1001-1002
82、 杨恽是司马迁(前145-前86)外孙,汉昭帝(前87-前73在位)时丞相杨敞(?-前73)的儿子,《汉书》有传。郑獬用杨惮在汉宣帝时任中郎将的事,比附杨文广领禁卫,又用杨恽罢山郎之弊政,以严法整顿郎官请谒货赂之弊端的故事,期许杨文广能整顿禁军军纪。不过,杨恽虽以告发霍氏谋叛受宣帝所用,后来却以得罪被革职,再被指怨望而为宣帝所杀。考杨恽任官中郎将,虽廉洁无私,郎官称公平;另对族人亦广加照顾,有轻财好义之名;但他自矜其能,又性刻害,好发人阴私,结果给仇家寻事攻倒,得罪身诛。郑獬用杨恽来喻杨文广,下场就太不吉祥。参见注释53及《耶溪集》,卷二〈四厢指挥使制一〉,叶14下至15上;班固(32-92);《汉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卷六十六〈杨敞、杨恽传〉,页2888-2898。
83、 强至:《祠部集》,文裫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八〈回杨四厢书〉,叶8上。按从仁宗至神宗三朝,姓杨而任四厢都指挥使的,只有杨文广一人,故可断定强至所覆的就是杨文广。
84、 考韩琦罢相出守永兴军,及徙镇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大名府,强至都一直追随韩琦,为他经办大小书奏的文字机宜工作,通四方之好。参见《曾巩集》,卷十二〈《强几圣文集》序〉,页202-203。
85、 按张方平此奏未明确注明写于何年,但行南郊大赦,从仁宗中期开始至英宗朝,只举行过三次,分别是庆历七年十一月、皇佑五年十一月和英宗治平二年十一月。按张方平在庆历七年底任权三司使、翰林学士;在皇佑五年十一月则任龙图阁学士判太常寺;在英宗治平元年十二月至三年正月前,则以龙图阁学士知徐州。换句话说,他上奏论南郊赦书,当在庆历七年或皇佑五年。若以张方平之职务论,笔者认为他在皇佑五年判太常寺时上此奏较为合理可信。参见《宋史》,卷十二〈仁宗纪四〉,页235;卷十三〈英宗纪),页258;《长编》,卷一百六十,页3876;卷一百六十一,页3881-3882,3890;卷一百七十五,页4235-4238;卷二百零七,页5022;张方平(撰),郑涵(点校):《张方平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二十〈郊禋赦书事目·录用近代有功边将子孙〉,页284。
86、 按张方平推荐可任管军的有济州(今山东巨野县南)防御使向传范(?-1074)(向传范是神宗向皇后[1046-1101]之伯祖)、沂州(今山东临沂市)防御使刘永年(?-1084)(按:刘永年是章献刘太后[1023-1033]摄政的族孙)和狄青另一员大将东上合门使、嘉州团练使刘几。参见《张方平集》,卷二十四〈论除兵官事奏〉,页372-373;《长编》,卷二百零三,页4927;卷二百零五,页4965;《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刘永年传〉,页13551-13552;卷四百六十四〈向传范传〉,页13579-13580。
87、 《长编》,卷二百零八,页5051,5062-5063;〈题名记〉,叶32下至33上;《宋史》,卷三百四十九,页11056。考郑獬另一道〈四厢指挥使制〉相信是为张玉晋升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而写的,制文中称受文人「沉毅而断,通于兵制,摄弓抚剑,以障河陇之戍,盖有能名。俾升刺部,入掌羽卫,拥虎戟以护建章」,完全符合张玉的身份和守西边之战功。参见《郧溪集》,卷二〈四厢指挥使制二首〉,叶15上。考〈题名记〉称窦舜卿在治平三年「二月」自马候改差,而载杨遂在三年五月除马候;笔者疑「二月」当作「五月」。又《宋史》未载杨文广迁捧日天武四厢,但后来杨得迁步军都虞候,按理应经过捧日天武四厢一级,疑《宋史》失载。
88、 《长编》,卷二百零九,页5073;《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页9308。
89、 考杨文广在熙宁元年七月已任秦凤副都总管,笔者疑他早在一年前已任此职参见《长编》,卷二百零九,页5088;《会要》 ,〈兵二十八之四〉。
90、 杨仲良(?-1184后):《资治鉴长编纪事本末》,收入赵铁寒(主编):《宋史资料萃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11月),第二辑,卷八十三〈种谔城绥州〉,叶1上至7上:《宋史》,卷十四,页266-267;《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七,叶49下至51下。
91、 《九朝编年备要》,卷十八,叶4上下;《宋史》,卷三百三十一〈马仲甫传〉,页10647。
92、 《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八十三〈韩琦筑甘谷城〉,叶14下至15下(按:今本《长编》缺熙宁元年至三年二月; 《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可稍补其缺;考李焘在这一条下注明杨文广乃杨业之孙,这是《长编》首次提到杨文广之名);《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页9308;《会要》,〈礼六十二之四十二〉、〈兵二十八之四〉、〈方域二十之七〉;《全宋文》(1994年4月),第四十册卷一千七百十七〈李清臣九·韩忠献公琦行状〉,页48-49。关于擦珠谷、喷珠之名,实为一地,按〈韩琦行状〉则以擦珠谷为「喷洙堡」,据陈守忠的实地调查,该处常年有流水,但流量很少。关于杨文广筑城之事,余嘉锡引用了《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的有关记载,参照《宋史》杨文广及马仲甫两传,而考得其实;常征却未引用《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这则重要记载,而曲解《宋史·杨文广传》的有关记载,望文生义地说杨文广「诈言筚篥堡有泉喷珠,鼓诱士卒一日夜急行一百八十里」;另外,他又解不通「先人有夺人之气」一句。另外,他又胡乱说韩琦论筑城筚篥一番话出自《长编》卷二百六十,其实韩琦这一番话出自《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上引的一条。参见陈守忠:〈陇山左右宋代城寨遗址调查〉,页214;〈考信录〉,页459-461;《史事考》页205-206。
93、 关于甘谷城和通渭寨的地理位置,陈守忠曾绘图清楚解说,按甘谷城今日所在为杨家城子,相信与杨家将传说有关。参见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迹》,插图五〈通渭县境古城遗址图〉;另页同书,214-216。又据《长编》所载,在熙宁初年,担任新筑成的知甘谷城的宋守臣是张就(?-1087),他曾有开边拓土的计议。参见《长编》,卷二百五十五,页6231。
94、 据苏颂所记,在熙宁元年秋(九月以后),龙图阁直学士孙永(?-1087)充秦凤经略安抚使知秦州,接替马仲甫。据苏颂说,熙宁三年前孙永的副帅是刘昌祚(1027-1094),不过,刘当时官职不高,只是秦凤兵马都监,并未担任秦凤副都总管,据《长编》,接任秦凤副都总管的是殿前都虞候窦舜卿。考孙永在秦州做得很不合神宗之心意,给神宗当众说他「前帅秦极不善」,而在熙宁三年四月降知和州(今安徽和县),宋廷即以李师中接任秦帅知秦州,但到是年六月,李师中徙永兴军,就权宜地由窦舜卿以副都总管兼知秦州。窦舜卿在熙宁八年,因与秦帅韩缜不协,徙为环庆副都总管。考《宋史·杨文广传》的断句,以杨文广先知泾州,再知镇戎军。余嘉锡则以杨文广不过只知泾州的镇戎军。按杨文广在熙宁三年自镇戎军权知鄜州,他不可能在两年间连知泾州、镇戎军和鄜州,余氏所断合理。又从熙宁元年开始,熟知边事的天章阁待制蔡挺长期担任泾原经略安抚使,而张玉就一直做他的副手,任泾原副都总管,到熙宁四年正月再获留任。按杨文广自秦凤副都总管调知泾州镇戎军,本来应兼本路副都总管,没有理由位在张玉之下。相信是张玉调职的问题谈不拢,故宋廷只好将杨文广再调往鄜延。至于鄜延副都总管是在熙宁四年正月前直是刘永年,他在四年正月任满后获留任。杨文广调知鄜州时,虽然官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在刘永年之上,但不知何故,宋廷仍由刘任本路副都总管。至于环庆副都总管,在熙宁三年八月前由杨遂担任,八月后因兵败去职,改由窦舜卿自秦凤路调任。至于秦凤副都总管之人选不详,不知是否由杨文广复任,待考。又鄜延帅从熙宁初年,一直由宣徽南院事判延州郭逵出任。参见《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页9308;《苏魏公文集》,卷五十三〈碑铭·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孙公神道碑铭〉,页798-801;《张方平集》,卷四十〈赠工部尚书蔡公墓志铭〉,页751-752;《长编》,卷二百十,页5094;卷二百十二,页5144,5160;卷二百十四,页5193,5220;卷二百十五,页5236;卷二百十八,页5302;卷二百十九,页5331;卷二百二十一,页5379;百四十,页5830;卷二百五十五,页6231;〈考信录〉,页461。
95、 李复圭因兵败去职,宋廷以王广渊代为环庆经略使,窦舜卿自秦凤副都总管改环庆,代替兵败的杨遂。韩绛所起用之宋将,包括种谔、种诊兄弟,韩且起用种谔为权鄜延钤辖兼知青涧城(今陕西青涧县城)。郭逵反对韩绛用种谔,故韩绛调走郭逵。见《长编》,卷二百十四,页5218-5220;卷二百十五,页5236,5241;卷二百十六,页254;卷二百十七,页5277,5283;卷二百十八,页5305-5304。
96、 《长编》,卷二百二十六,页5551-5554。
97、 《长编》,卷二百四十,页5829;卷二百四十七,页6023;〈题名记〉,叶33上;《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页9308。按杨文广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的职位,就由张玉替补。
98、 《长编》,卷二百四十,页5832。
99、 《长编》,卷二百四十五,页5972。
100、 《长编》,卷二百四十七,页6022-6023,6030。
101、 《长编》,卷二百四十八,页6046。
102、 《长编》,卷二百四十九。页6067;卷二百五十,页6082-6084;6087-6089。
103、 《史事考》,页207;《长编》,卷二百五十一,页6121-6123,6132-6133,6135-6137;卷二百五十二,页6168-6170;卷二百五十三,页6201-6202;卷二百六十二,页6386-6397。按常征称沈括、韩琦等反对对辽让步,并说他们与杨文广立场相同,其实常征弄不清楚沈括等主张对辽强硬,乃在杨文广死后。而且韩琦还曾不点名批评杨文广进平幽燕议为生事。关于韩琦上奏言辽事的年月,李焘已辨明不在熙宁七年十月,乃在熙宁八年三月。又宋辽划地交涉的最近期研究,可参阅蓝克利(着),颜良(译):〈政治与地理论辩——一零七五年的宋辽边界谈判〉,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182-197。
104、 余嘉锡只将杨文广献策,视为秉承杨家的忠义精神,说:「(杨)文广亦献策取幽燕,虽功皆不成,而祖孙三世,敌忾同仇。以忠勇传家,就将帅中所稀有。由是杨家将之名,遂为人所盛称,可谓豹死留皮,殁而不朽者斯欤?」参见〈考信录〉,页461。
105、 据南宋人王铚所撰之《默记》披露,神宗曾对滕甫亲口言及太宗在高梁河(在今北京市内)之役为辽军所射伤,太宗之箭疾岁岁必发,十八年后还因箭伤而死。滕甫后对王铚之父说,神宗对此不共戴天之仇,一直耿耿于怀,而对每年还输金帛于仇敌,尤觉耻辱,常思报复。按滕甫既对王铚之父言及此事,则他对祖父死于辽手的属下杨文广言及神宗这件心事,实在顺理成章。参见何冠环:〈宋太宗箭疾新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二十卷(1989),页33-57。
106、 《长编》,卷二百五十八,页6288;《会要》,〈仪制十一之十八〉。
107、 《长编》,卷二百六十二,页6390。
108、 据李焘引《神宗正史契丹外传》的记载,在熙宁八年三月辽使萧禧再来议地时,神宗向臣下明显地表露出想对辽强硬,甚至不惜一战的态度。他且说:「契丹亦何足畏,但谁办得用兵?而文彦博应召上言时,亦说:「窃料圣意重于举动,发言盈庭,容有异论;或日先发制人,意在轻动;或日乘其未备,袭取幽燕,事不审处,恐将噬脐,非王师万全之举也。」可见当时神宗确想过对辽用兵。参见《长编》,卷二百六十二,页6379,6385,6395。
109、 考王安石在同年闰四月,当辽使离去后向神宗报告,奏称传闻辽国的确畏惧宋出兵争地。另外,神宗在同月即下韶知定州薛向,要他具奏定州可供作战的民兵数目。辽方的反应是在是年五月向定州路所属的广信军(今河北徐水县西遂城)新河口铺及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县)发动试探性的攻击。就当时的情况而论,辽国的决策者不能不认真考虑宋方的反应;一旦宋廷的鹰派占上风,可能真会采纳杨文广之议,乘机出兵攻辽。事实上宋辽开战,双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辽国不过虚张声势,希求宋方在划界事上向辽妥协屈服,倘宋朝真的出兵来争,实非辽人所愿。宋方在谈判时,故意漏出朝中有人主张不惜一战的消息,以迷惑辽国的谍者,实在并不失算。参见《长编》,卷二百六十三,页6424,6452;卷二百六十四,页6462。
110、 欧阳修便将杨畋视为杨业后人,并称从杨畋处,得到罕传的《遁甲立成旁通历》一书,而追慕「继业善用兵,以见昔时名将皆精于所学,非止一夫之勇也」。按此书不传,内容不详;惟据仁宗景佑年间宋廷所编的同类书《景佑遁甲符应经》的序言所云:「稽夫遁甲之书,出于河图。黄帝之世,命风后创名,始立阴阳二遁,共一千八十局。迨太公约七十二局,留侯佐汉,议十八局。推历授时,超神接气,布门耀德,观兵取验,以明胜负,罔不抽吉。」杨畋从杨业得来的这部遁甲书,相信正是杨业当年用兵时所据以测定天时日历的行军册。杨畋虽被视为杨门子弟,也被欧阳修等许为通兵法,能将兵平乱之人;但他以进士出身,长期担任文官,虽一度转为武资,然最后仍复为文官。在部份宋人眼中,他近于儒将;而不似杨文广那样道道地地的武将。
是故太原杨氏的杨重勋一房,严格来说,其将家身份,到杨琪一代其实亦已终结。据目前可见之资料,杨畋有一妹(1036-1095),在杨安排下,嫁太子中舍张景儒(1018-1070)为继室,生男四人及女四人。杨畋似乎没有其他兄弟,据苏辙所记,杨畋死时,仅有一年方二岁的儿子杨祖仁,杨祖仁在绍圣二年(1095)时官右宣义郎、签书崇信军(即随州,今湖北随州市)节度判官厅公事。杨祖仁的姑姐卒时,他即为她篆墓盖。杨祖仁在政和三年(1113)官「大夫」,他的后人亦暂不可考。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宋人如司马光(1019-1086)虽亦点出杨畋为杨业族人;不过,却不认为杨畋有儒将才具,认定杨畋只是迂阔无威的一名儒者,故当杨畋受命平侬智高时,即不为诸将所服,而为宋廷所罢。另为杨畋妹撰写墓志铭的左朝奉大夫张峋,虽称「杨氏世将家」,但说杨畋「独以文章经术为仁宗皇帝识,擢任龙图阁直学士,当时称为名臣」。可见宋人已不以杨畋为世将。参见《全宋文》,第十四册,卷五百七十九〈陆经·朝奉郎守太子中舍骑都尉赐绯鱼袋张君墓志铭〉,页218-219;(1992年4月),第二十三册,卷九百八十四〈宋仁宗四十五·《景佑循甲符应经》序〉·页393:(1994年3月) ,第三十九册,卷一千七百零四〈张峋·宋故寿阳县君杨夫人墓志铭〉,页556-557;《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五〈书《遁甲立成旁通历》后〉,页2574-2575;《攀城集》,卷十八〈杨乐道龙图哀辞并序〉,页424-425;司马光(撰),邓广铭(1907-1998)、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9年) ,卷十三,页259。
111、 按常征将杨存中归入杨家将一员,只根据杨存中之四世祖名杨信,而断言此杨信即杨业之父,其实宋代名杨信就有多人,除了常氏提到的几个杨信外,他没提到的,至少还有太祖(960-976在位)、太宗(976-977在位)时官殿前都指挥使的宿将杨信(?-98 )。假若杨存中真是杨业后人,为他作墓志铭的人没有理由不大大吹嘘一番。至于常征所根据的《代县原平杨氏族谱》,其真实性和准确性犹有待考订,不能作为有力的旁证。关于播州杨氏源出所谓杨延昭幼子杨充广,上文已辨其不确。参见《史事考》,页57-71,209-238,239-249。
112、 《曾巩集》,卷十二,页202-203。
113、 考狄青及其七员官至管军的部将,除了杨文广和李浩外,都是起于行伍,第一代为将。狄青的雨个儿子狄咨(?-1100)与狄咏(?-1097后),虽然功业与乃父相去甚远,但以一般人的标准,他们都算得出息,都勉能维持家声。狄咨官至引进使、嘉州团练使;狄咏亦官至引进使,且数有战功。宣仁高太后(1032-1093)还一度想纳狄咨之女为哲宗后。不过,狄家第三代便不显。和斌的儿子和诜(1058-1124)尚算能继承父业。和诜在徽宗(1100-1125在位)朝号为守边能将,长期扼守雄州(今河北雄县),官至相州观察使。他又以制射远的强弓凤凰弓闻名,不过,却以首倡取幽燕而受非议。与狄家一样,和氏第三代亦不显。李浩是第二代为将,但他的后代亦无能者。至于贾逵、张玉、卢政及杨遂等,功业均及身而止,他们的下一代均无显者。参见《宋史》,卷二百九十,页9721;卷三百五十〈李浩传〉,页11078-11079;〈和斌传、和就传〉,页11079-11081;《长编》,卷四百五十七,页10945-10948;卷四百六十,页11002。
1999年12月23日初稿
补记:
笔者在今年年中偶翻台湾宋史座谈会编的《宋史研究集》第九辑(1977年5月),才发觉漏引李安的〈「杨家将」的事迹〉(页589-601)一文。该文述杨文广事迹,曾引用康熙四十九年(1710)修、乾隆五年(1740)补修的《保德州志》,以及乾隆四十八年(1783)修的《府谷县志》有关记载,称杨文广妻姓慕容氏,为保「州南慕塔村人,雄勇善战」。李氏并进一步推论小锐戏剧所云杨宗保妻穆桂英,可能是慕容氏的讹误(页599-600)。考杨文广妻的姓氏籍里,现时可见的宋人文献并无著录,不知上述两种清人方志所云「见旧志」何所根据。笔者以为此说目前只能存疑。又笔者于今年8月底,因路过西安,有缘拜谒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李裕民教授。笔者曾向李教授请教,李教授亦认为明清人所编之方志中有关杨家将的记载只能聊备一说,不足以作为考证史实的重要佐证。
2000年10月9日
(原载《岭南学报》新第二期 [2000年],页97-129。)
再增补后记:
笔者在去年(2001)中,偶阅葛剑雄教授所撰《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33-137),始知谭其骧教授(1911 -1992)早在1941年1月流寓遵义时所撰之〈播州杨保考〉一文,已指出宋濂所谓播州杨氏出于北宋太原杨氏之谬,并指出杨文广或「杨充广」与杨贵迁实不相干。据葛剑雄所记,其师这一篇考证在是年10月印成,后来发表于浙江大学的《史地杂志》第1卷第4期。当时只印数百册,虽引起当地人士注意,但该文一直流传不广。是故常征在1980年出版其《杨家将史事考》时,多半看不到谭氏此文。按谭氏直至1981年底才应贵州民族学院之请,将此文重新校勘发表,谭氏并据《文物》1974年第1期所载贵州博物馆所撰〈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附录的〈杨文神道碑〉,写成〈播州杨保考后记〉,一并在1982年的《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刊载。此二文后均收入谭氏学术论文集《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61-296)。
笔者数月前趁往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使用新装置的电子版《四库全书》的全文检索功能,查阅另一研究课题之便,又索阅多种清人编修的方志,查看明清方志中有关杨文广及其家人的记载,除了《山西通志》卷一百五十七〈列女九·保德州》条下所记杨文广妻子慕容氏与上面「补记」所引的几种清人方志所载相同外,笔者从《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七十三〈广南府〉条,知后人曾为杨文广立祠于广南府(在云南境)府治西。另外有趣的是,不知是否受小说的影响,在《湖广通志》卷十二〈铜锣滩〉条、卷七十九〈杨氏城〉条,《陕西通志》卷十六〈宜娘子关〉条及《广西通志》卷十三〈穿岩山〉条,均记载上述四处地方留有传说中的杨文广之妹「宜娘子」的遗迹。此外,在《陕西通志》卷十七〈僧道关〉条及《广东通志》卷五十三〈杨文广坝〉条,亦记载有传闻中的杨文广多处遗迹。上面所举,只是其中一部份例子,其他清代方志类似的记载尚有许多。这裹不一一著录。正如上面所述,这些方志所记关于杨文广及其家人之事睛,只能聊备一说,是故笔者今次修订本文,只增补了一些初稿漏引之资料,以及补入本文涉及的地名其今日所在。对于那些有待商榷的方志资料,仍不拟采用。
2002年10月19日于香港理工大学
本文收录于何冠环教授的著作
《北宋武将研究》
(香港:中华书局,2008年)
页385-436。
< 原创文章/视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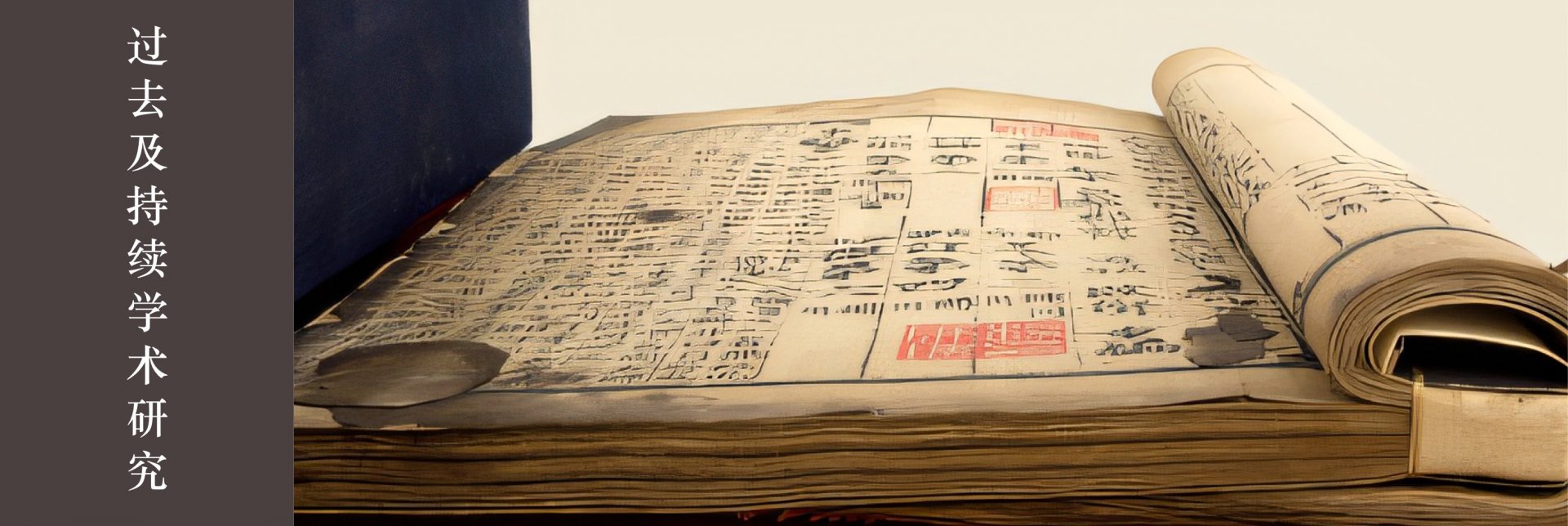



欢迎留言:
请登入/登记成为会员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