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楊家將第三代傳人楊文廣(?-1074)事跡新考
在明人小說《楊家府演義》裹,北宋楊家將的第三代英雄,是楊宗保、穆桂英夫婦。他們的一雙兒女楊文廣和楊金花,構成楊家第四代,而文廣的兒子楊懷玉兄弟則是楊門第五代。1不過,在真實歷史中,楊宗保和穆桂英都是虚構的人物,楊門第三代其實是楊文廣。另外,他尚有兩兄長,而並非楊六郎楊延昭(958-1014)一脈單傳的獨生子。此外·他隨狄青(1008-1057)平定儂智高(?-1055)時,已是年過半百的老將,而非小說所云年方弱冠的少年。2至於楊文廣的後代,史所不載,所謂楊懷玉者,大概是小説家隨意的杜撰。3考楊門三代中,楊文廣的事跡載錄於史傳的最少,他的戰功也遠遜父祖;不過,論起實際的地位,他卻比父祖為高。他最後官至步軍都虞候,位列「禮繼二府」的三衙管軍。筆者懷疑楊業(935-986)所以被人尊稱為「楊令公」,可能沾了孫兒的光,因文廣擢步軍都虞候而獲追贈尚書令或中書令所致。4根據《宋史·楊文廣傳》不足二百七十字的簡略記載,楊文廣雖然是名將之後,但他的前半生沉滯於下僚,幾乎與二兄一樣寂寂無聞;幸而他終能在仁宗(1022-1063在位)慶曆三年(1043),當已步入中年時,獲得平亂立功之機會,得以出頭。然後他再有幸先後跟從范仲淹(989-1052)、韓琦(1008-1075)和狄青建功立業,終於大器晚成,中興楊家,得以維持楊門將家之名聲。
在隨狄青南征儂智高、後來官至管軍的七員大將中,楊文廣的家世最顯赫,他的名字也最為一般讀者所知。不過,他的生平事跡在宋官私的記載則甚少。上一世紀,余嘉錫(1883-1955)教授早在其〈楊家將故事考信錄〉中,據《隆平集》、《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輯稿》、《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皇宋十朝綱要》等書之有關記載,對《宋史·楊文廣傳》作出詳瞻的索隱考證工夫。5當代的宋史學者中,常征在其《楊家將史事考》中,補入一些宋人以至明人的記載,再對楊文廣的生平事跡考索一番。6不過,常氏的考證的最大問题,首先是對余嘉錫之研究視若無睹,不加引用。另外,史料搜集亦不夠周全,而在使用史料時有欠嚴謹,推論過當。就筆者目前所知,近年有關楊文廣生平事蹟最值得參考之著作,是河隴史地研究專家陳守忠一篇實地考察楊文廣所築之大甘谷口寨(今甘肅通渭縣南)和通渭寨(今甘肅通渭縣)之報告。7本文即在余、常二氏的研究基礎上,重新考索楊文廣之生平。筆者曾撰〈狄青(1008-1057)麾下兩虎將——張玉(?-1075)與賈逵(1010-1078)〉一文,論及狄青部將之軍旅生涯及自仁宗末年以來在眾多武臣中出現的「狄青效應」。8楊文廣曾為狄青麾下大將,故本文亦可視為該文的續篇。
楊文廣字仲容,是楊延昭第三子,生年不詳。據曾鞏(1019-1083)的《隆平集·楊延昭傳》所載,楊文廣的兩位兄長名傳永和德政(?-1031後)。9 楊文廣兩位兄長的生平事蹟,筆者目前所僅知,是其二兄楊德政在天聖九年(1031)以西頭供奉官見任澤州(今山西晉城市)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10 常征根據明初大儒宋濂(1310-1381)所撰的〈楊氏家傳〉誤信楊文廣尚有一弟名充廣,並因此錯誤推論播州(今貴州遵義市)楊氏出於太原楊氏。11 當楊延昭於真宗(997-1022在位)
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在高陽關(今河北高陽縣東舊城)副都部署任上卒時,楊傳永、德政及文廣均以父遺蔭得官。楊文廣兄弟獲授什麼官?從《隆平集》、《續資治通鑑長編》到《宋史》均未明言。余、常二氏從《宋史·楊文廣傳》所記楊文廣「以班行討賊張海有功,授殿直」,結合宋代武臣遷官制度的有關記述,斷定文廣所授,當是三班奉職或借職,所論可取。考楊延昭卒時官英州(今廣東英德市)防禦使,據《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載,就在楊延昭死後第二年,即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宋廷頒佈承天節(按:即真宗生辰)及南郊奏蔭子弟恩蔭新制,防禦使一級的武臣,子授右班殿直,弟、姪、孫授三班奉職。楊延昭守邊有大功,宋廷在新制頒行前一年錄他三子官,似乎與新制相去不會太遠。楊傳永是長子,依制當授正九品的右班殿直,楊文廣是老三,按理應比照弟、姪、孫,授從九品的的三班奉職或借職,而授三班借職之可能較高,當然,亦不排除只授予比借職還低的未入流武職。12
楊文廣出仕的年月,余氏未有考證,常氏則根據《宋史》所記楊文廣以「班行討賊張海有功,授殿直」的線索,參照《宋會要輯稿》所載張海於仁宗慶曆三年被平定的史實,再推論楊文廣自三班借職陞遷為殿直當經十餘年,而考定楊文廣出仕不應早於仁宗天聖年間。13 然而,常氏顯然將楊文廣授官使臣和出補實職二事混為一談。據《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載,宋廷在慶曆三年十一月所頒佈的新恩蔭制度指出,「蔭長子孫,皆不限年,諸子孫須年過十五」。14 楊文廣能受蔭得官,即表明其父卒時,他已過了十五歲。當然授官不等於補實缺,楊文廣未必能像其二兄楊德政一樣,正常地在出仕後十八年,既遷四階為西頭供奉官,並已補實職為澤州兵馬監押。據歐陽修在同一年的上奏,在「武官中近下班行,并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十餘年」。15 即是説平均五年遷一階,此亦符合北宋武臣五年一遷的通例。倘《宋史》記載不誤,楊文廣真的要到平張海有功時才遷殿直(即使是左班殿直),那即是説他要等三十年才陞三階,即平均十年才陞一階,實在算得上是罕有之沉滯。為何楊文廣的早年仕途如此不濟?據曾鞏、張方平(1007-1091)及上官均(1038-1115)所記,三班使臣在真宗天禧年間,已達四千餘人;到仁宗慶曆八年(1048),已達六千五百餘人;到神宗(1068-1085在位)末年時更逾萬人,宋廷實在沒有太多的實缺可授。16 楊文廣雖是名將之後,但有兩兄在前,補實職也要等待有特恩。筆者推测楊文廣只能等其兩兄身故或致仕後,才有機會補缺。常征推論楊文廣「出仕」在仁宗天聖以後,但筆者認為楊文廣很有可能要到明道以後兩兄歿後才補上實缺,大概再用十年時間自三班借職遷一至兩階至右班殿直,然後因平張海立功而再遷左班殿直。
因史料匱乏,我們無法確知楊文廣何年得補實職。至於他的年歲,假定他在大中祥符七年是十五歲,則他在慶曆三年以功遷殿直時,當為四十四歲。楊文廣到這年紀仍屈居下僚,常征感到很不解。其實,這種情况在宋代甚為普遍,我們隨便在宋人碑銘即可找到許多一輩子做官不過使臣的武將例子。17 大概常氏以為大名鼎鼎的楊家將後人(其實楊家大享盛名要到明代,並靠小説家吹嘘),不可能如此沉滯。然而,在北宋中葉以降,低級武臣陞遷艱難,正是常態。太原楊氏其實不過是北宋眾多將家之一,三代之後,他的子弟就沒可能受到宋廷特别照顧,楊文廣後來能超過兩兄,出人頭地,還得靠一點運氣。
楊文廣的運氣,首先是他沒有參預從康定元年(1040)正月爆發、以宋軍慘敗的三場宋夏戰役,而得以逃過大劫。事實上,在康定元年正月的三川口(約在今陝西延安市西二十公里處)之役、慶曆元年(1041)二月的好水川(今寧夏隆德縣西北好水)之役、慶曆二年(1042)閏九月的定川寨(今寧夏固原縣中河鄉)之役中,被俘或陣亡的宋將,許多是當時有名之驍將,而其中屬於将家子的便不少。18 當然,事情亦有兩面,宋夏戰爭亦造就了許多人建功立業的機會。好像楊文廣後來追隨的狄青,在康定元年十一月前,不過是比他高兩階的右班殿直、鄜延路部署司指使的九品小武官;宋夏戰爭卻給他大展身手之機會,此後他身經百戰,屢立戰功,而成為一代名將。19 楊文廣雖沒有狄青憑禦外侮建大功之運氣;但他也能藉平定内寇而初露頭角。
就在宋軍三敗於西疆而元氣大傷時,京西一帶在慶曆三年中,又遭劇賊張海、郭邈山率眾劫掠。張海是什麼人?余氏引用《續資治通鑑長編》兩條記載略為陳説,稱張海、郭邈山二人在慶曆三年起事於陝西。常氏亦引用《宋會要輯稿》及《包拯集》兩條資料,稱郭邈山等早在明道元年(1032)已聚眾於陝西的商州(今陝西商州市),並說張海本為陝南屯卒,亦與其黨響應起事,轉戰京西、陝西一帶十年,州縣不能制。20 論及張海之起事,常氏推論張海等劫掠州縣已有「十年」而官府不能制。不過,當筆者翻檢他所引的兩條資料,卻看不到其推論有何根據。根據歐陽修在慶曆三年之上奏,其實盤據在商山(今陕西商州市東南)(不是商州!)十年的是郭邈山,而非張海。21 關於張海的事跡,雖然《宋會要輯稿》及《宋史》記得不多;但《續資治通鑑長編》除了余氏所引兩條外,尚有多條相關記載,另歐陽修等之文集亦有不少相關之篇章,惜常氏未有仔細搜集閱讀,故有此錯誤之推論。據《續資治通鑑長編》等有關記載,郭邈山實為叛卒,於慶曆元年正月前後起事於陝西。張海亦為「軍賊」,本為李宗夥內「惡贼」,實起於京西。22 有趣的是,本來是張海響應郭邈山,但宋官方之記載反而一直以張海為盗首,而以郭邈山、黨君子、范三、李宗為其羽翼。23 據李燾的考證,張海其實起於京西,不是陝西,而他響應郭邈山的年月,不會早於慶曆元年。常征稱他們横行十年,其實错解了史料。張海作亂始於鄧州(今河南鄧州市),本來實力不大,據范仲淹的説法,張海一眾只有六十餘人,雖各騎鞍馬擁有弓弩器械;但當時知鄧州柳植(?-1049後)沒有防微杜漸,未能及時出兵擒捕,結果給他坐大,殺出鄧州,焚掠京西數處州縣。宋廷於慶曆三年八月,才覺察事態不妙,於是下詔命左班殿直曹元詰、張宏,三班借職黎遂領禁兵擒捕張海等。24
宋廷出師一月多,仍然無功。據歐陽修所奏,張海等人雖不多,但他們都有甲馬,日行一、二百里,當馬力困乏便棄,另奪民間生馬乘骑,而教追捕他們的官軍疲於奔命。25 宋廷無奈,在是年九月,只好再派監察御史蔡稟(1002-1045)為京西安撫前去督捕。後見蔡稟馭下處置無方,幾乎鬧出兵變,只好又再任杜杞(1005-1050)為京西轉運使,由他負責平亂。另一方面,又下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及諸州長吏,舉薦所部兵馬都監及監臨場務使臣有材勇可出任巡檢的,以名字上聞。宋廷並許諾,若捕盗有功,就不次擢遷。26 楊文廣相信就是在這時受到舉薦,擔任巡檢,討捕張海。誰人舉薦楊文廣的?楊文廣在應召前擔任哪一州的武職?因史料缺乏,均不可考。筆者猜測,楊文廣的堂姪、在是年十月以殿中丞知岳州(今湖南岳陽市)被選為提點荊湖南路刑獄的楊畋(1007-1062),很有可能是推薦他的人。 27
楊文廣有用武之機會,正因張海等之作亂,已成燎原之勢。據樞密副使富弼(1004-1083)在是年九月中之陳奏,羣盗乘京西諸州長吏庸碌,兼無兵無備,公然在白晝攻入州城劫掠府庫,散錢財與其黨及貧民。其中陝府(即陝州,今河南陝縣)、西京(即洛陽,今河南洛陽市)、唐州(今河南唐河縣)、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房州(今湖北房縣)、金州(今陝西安康市)、商州、襄州(今湖北襄樊市)、鄧州等州府,相去千餘里,都被張海等大事劫掠,殺人放火,所在瘡痍。28 宋廷又禍不單行,同年十月,張海剽掠至光化軍(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境上時,知軍韓綱(?-1044後)率宣毅軍三百人力拒來犯。當賊兵解圍而去時,韓綱卻因犒賞不公,激起兵變,叛兵首領邵興從光化軍向西,攻掠川北州縣,與張海一東一西相呼應。 29
張海及其黨羽其實所脅之眾為數並不太多,不過千餘人,只是他們專向無兵無備之京西州縣攻掠,他們掠完便走,等到官兵趕到,他們早已遁去。比較之下,邵興一路招誘失律兵卒,眾至三千餘人,還教宋廷憂慮。30 當張海、邵興等竄向川陝時,宋廷即以陝西宣撫使韓琦統一指揮撲减兩股叛亂之行動,出動陝西、京西兵凡九千人,終於在是年十二月,先後平定張海與邵興之亂。 31關於張海起事之緣由及所带來之損失,蘇轍(1039-1112)在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即亂平四十三年後,曾再作一個總結。他稱張海起事,就像淳化時的李順(?-992後)、熙寧中的廖恩(?-1077後),都是因官府厚赋歛,奪民利所致。蘇轍又粗略估計宋廷在平亂之耗費,包括發兵命將、轉運糧食,以及耗失兵械和募士賞功,連同張海等燔燒官寺,劫掠倉庫之損失,至少要付出數百萬貫的沉重代價。 32
楊文廣在討平張海之亂的具體戰功不詳,事實上,張海一夥不過是烏合之眾,人數有限,戰鬥力不強,不是地方官養寇,早就平息。看來楊文廣也沒有怎樣血戰;不過,他總算立功,得到陞遷為左班殿直。33 他的頂頭上司是韓琦和范伸淹(989-1052)雙雙舉薦、以捕盗有名之悍將趙滋(?-1064)亂事平定,趙滋自右侍禁擢東頭供奉官。當趙滋調為京東東路都巡檢時,楊文廣則仍留在陝西。教楊文廣遺憾的是,他的堂姪楊畋卻在是年底,因討蠻徭兵敗於孤漿峒而遭降職。34
從慶曆四年(1044)到皇祐五年(1053)前後十年間,楊文廣的軍旅生涯進入另一階段,他首先有幸成為范仲淹的直接部屬,然後在多年後,隸於狄青帳下,從征儂智高。雖然他追隨范、狄二人的事蹟可考的不多,但他後來得以被宋廷擢任管軍,出任方面,顯然是這十年磨劍所奠下的基礎。
慶曆四年六月,主持慶曆新政的参知政事范仲淹,因承受不了朝中反對變革者之壓力,自請出按西北邊地,仁宗接受他的要求,任他為陕西、河東宣撫使。35 據《宋史·楊文廣傳》稱,范仲淹「宣撫陝西,與語奇之,置麾下」。究竟范仲淹在何時何地召見楊文廣的?余氏據《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記載,認為當在慶曆五年(1045)正月至十一月間,當范仲淹罷参政,改任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兼知邠州(今陝西彬縣)時。不過,筆者認為楊文廣亦有可能早在四年十月當范氏宣撫河東時已進入范幕。36 至於推薦楊文廣給范仲淹的,很有可能是韓琦或與范氏有交情的楊畋。37
楊文廣有什麼地方教范仲淹稱奇,而要將他納為麾下?是否他武勇過人?考范仲淹在改任知鄧州前,曾上奏力保前涇原都巡檢孫用及瓦亭寨主(今寧夏固原縣瓦亭鄉)張忠(?-1052)復職,以他們有武勇可用,但楊文廣就沒有得到范氏這類的考語,恐怕范仲淹看得起楊文廣,並非他有父祖之武勇。38 關於這一點,常氏認為楊文廣必是獻上防範西夏的軍計,而受知於范仲淹。他又進一步推論楊文廣獻納了有關改革兵政的意見。然而,常氏之推論,既無佐證,也與情理不合。常氏説楊文廣獻納防範西夏之軍計,這樣籠統的説法,自然不能説錯;但要説楊文廣有能力析論「將不專兵,兵不專將」之弊,實在將他看得太高。39 筆者認為,楊文廣的家世與經歷,固然都能引起范仲淹的興趣;不過,能令范仲淹「奇之」,並用為朝夕相見的幕僚,必因其能言范仲淹感到興趣的話題,此話題相信是其祖父楊業修建堡寨的經驗。考范仲淹重來西疆,第一番陳奏,便是請求在麟、府二州重修堡寨,以招納蕃部,作長期防禦。在范仲淹的籌劃中,在宋夏邊防要地修堡建寨,是防禦西夏進攻的頭等大事。他正需要一個精通此道的人,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當楊文廣向他言及先祖修建堡寨之經驗時,是如何正中他下懷,自然要馬上將楊文廣納為幕僚了。事實證明,楊文廣就是長於修築堡寨之專家,他後來即奉韓琦之命在秦鳳路大修堡寨(事見下文)。在這一點上,還有一項旁證。我們知道,在防禦西夏之策略上,范仲淹與韓琦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二人志同道合,愛憎也相近。據李燾所記,韓琦在皇祐年間經略河東,按行堡塞所置處,發現它們多是楊業仕北漢時所修建,而佩服不已。考主張修建堡寨的事上,范仲淹比韓琦還要來得早,我們可以相信,范仲淹對於楊業當年的遠略,當會和韓琦一樣佩服不已,因而對深諳祖傳修築堡寨本領的楊文廣就另眼相看。作為將家子,楊文廣雖沒有完全學得父祖衝锋陷陣的本領,但他能繼承祖上修建堡寨的本事,也就夠稱守業了。40 如值得注意的是,狄青當時與楊文廣同在范仲淹陝西宣撫使轄下,但狄青因多立戰功,名位已遠在楊之上;41 楊文廣在范仲淹邠州麾下,雖然在當時尚未受涇原部署狄青的直接指揮,但狄青對其才幹能力肯定有相當的認識。
楊文廣從慶曆六年(1046)至皇祐五年(1053)的八年間,仕歷不詳。他有沒有隨范仲淹守鄧州、荊南府(今湖北荊州市)、杭州(今浙江杭州市)及青州(今山東青州市)?目前看到的范氏文集,找不到有關楊文廣事蹟的記載。42 考在慶曆五年十一月代范仲淹出知邠州是原梓州轉運使崔輔,而在慶曆
六年二月接任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即長安,今陝西西安市)的,是原河北安撫使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縣)程琳(988-1056)。倘楊文廣沒追隨范仲淹,崔、程二人以及後來出任永興軍都部署的葉清臣(1000-1049),及程琳的繼任人李昭亮(?-1063),以及當年平定張海、後任環慶都部署的杜杞,都有可能是他的上司。至於楊文廣與狄青的從屬關係,因史料缺乏,不易確定。考狄青在這八年中,先後任涇原儀渭兵馬部署及鄜延經略安撫使,並曾知渭州(今甘肅平凉市)與延州(今陝西延安市),倘楊文廣留在陝西,他成為狄青部屬的可能性很大,後來狄青徵他從征儂智高,大概因楊是他的舊部。43
慶曆七年十一月,河北貝州(今河北清河縣)的宣毅卒王則據城反,並建號稱尊。宋廷派參知政事文彥博(1006-1097)和權知開封府明鎬(989-1048)調集河北各路軍隊圍剿,高陽關都部署王信(988-1081)首先率本部兵趕至貝州城下,文、明二人抵貝州,即採挖地道的方法攻城。叛軍強悍,非張海一類鳥合之眾可比,宋軍圍攻至翌年閏正月,前後六十五日,才破城擒得王則。當戰况激烈時,文彥博一度想調狄青之勁旅代替王信攻城,不過,文彥博還未發出調兵請求,亂事已平定。楊文廣這次運氣又差了一點,本來楊家上兩代轉戰河北,他参預平叛,是人地相宜的事。可惜狄青最終沒機會率部平亂,而他也就失去了一次立功及遷陞的機會。考宋廷在平亂後不久,翰林學士張方平奉命上奏檢討這次叛亂,他在列舉祖宗時之名將九人時,便包括楊文廣的父親楊延昭。假若楊文廣這次有機會平叛立功,他一定讓宋廷文臣刮目相看。教人感歎的是,今次一戰成名的卻是另一位楊氏英雄楊遂(?-1080),他憑奮勇先登破城之奇功,從此受知於文彥博,得以建功立業。44 在這裹附帶一提的是,當楊文廣默默無聞時,他的族姪楊畋在慶曆七年(1047)正月,因荊湖南路安撫使崔嶧的推薦,由文資的太常博士改為武資的東染院使,出任荊湖南路鈐轄,對付嶺南徭族之叛。楊畋征戰經年,到了皇祐元年三月,奏稱得瘴霧之疾,請恢復文資,求近北一小郡。宋廷允准,即授他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隨州(今湖北隨州市)。未幾又獲召入朝出任戶部判官,到皇祐二年(1050)五月,又出使河東路,計置糧草及處置盗鑄鐵錢等事。同是楊家後人,楊畋的際遇便好多了。45 不過,楊家叔姪都不料到,他們在四年後,都得應召,征討就在皇祐元年九月開始入寇邕州(今廣西南寧市)的儂智高。46
皇祐四年(1052)五月,宋廷一直輕忽的儂智高,已準備就緒,一舉攻陷邕州,並建大南國,改年號為啟曆,並自稱為仁惠皇帝。由於宋廷無備,儂智高很快又攻克廣南東西路的横州(今廣西横縣)、貴州(今廣西貴港市)、龔州(今廣西平南縣)、藤州(今廣西藤縣)、梧州(今廣西梧州市)、封州(今廣東封開縣東南)、康州(今廣東德慶縣)、端州(今廣東肇慶市)等州,並圍攻廣州(今廣東廣州市)。宋廷大為震驚,除命當年平定邵興有功的知韶州(今廣東韶關市)陳曙(?-1053)及范仲淹舊部張忠、蔣偕領兵討儂智高外,再在是年六月,急召素習蠻事但正在居父喪的余靖和楊畋平亂,余被任為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今廣西桂林市),楊畋被任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提舉經制賊盗。教人遺憾的是,最具時望的范仲淹偏偏在這時病逝於徐州(今江蘇徐州市)。這場大亂最後只能由他的愛將、刷在同月被仁宗破格擢為樞密副使的狄青才能平定。47
教宋廷震驚的是,號為勇將的廣東都監張忠及廣東鈐轄蒋偕,都先後在皇祐四年七月被儂智高擊殺,而號稱知蠻事的楊畋,也被擊敗,只能焚燒儲糧,率殘兵退守韶州。仁宗只好接受宰相龐籍(988-1063)的推薦,召用知兵的老臣孫沔(996-1066),自秦州徙為荊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撫使,不久再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統籌平亂行動。然當儂智高再破昭州(今廣西平樂縣西南)後,仁宗擔心孫沔亦無法平亂,當狄青自請出師,而又得龐籍全力支持時,仁宗終下定决心,在是年九月,命狄青選將統兵,全權負責平定儂智高之亂。狄青請准在鄜延、環慶、涇原三路擇蕃落、廣鋭軍曾經戰鬥各五千人,命逐路遣使臣一員,押赴廣南行營。另又徵召各路將校從征,他所挑選從征的將校中,據《宋史》所載,正有楊文廣。48
關於楊文廣從征儂智高的事,除了《宋史》記載外,就只有明中葉纂修的《嘉靖南寧府志》和清初顧祖禹(1624-1680)所著的《讀史方輿紀要》曾有提及。《嘉靖南寧府志》稱楊文廣在「狄青南征時為廣西鈐轄知邕州,撫禦有方,士卒樂為效死,時以名將稱之」。《讀史方輿紀要》則引述舊志,稱楊文廣奉狄青命,追擊儂智高至大理之阿迷州合江口,不及而還。49 不過,《嘉靖南寧府志》説楊文廣南征時為廣西鈐轄知邕州,顯然是照抄《宋史》但又讀不通《宋史》的斷句,不知道楊文廣知邕州其實是許多年以後的事,故後出的《嘉靖南寧府志》並無史料價值。至於比《嘉靖南寧府志》更晚出的《讀史方興紀要》,雖載有《宋史》所無之事。但它並未清楚註明所謂「志云」楊文廣追擊儂智高至大理之事出自何書,故它所説的事只能存疑(按:考諸羣書自《長編》以下,所記追擊儂智高的宋將,並無楊文廣之名)。關於楊文廣南征的間題,常征在未作任何考辨前,便貿然據《讀史方輿紀要》上迹的傳聞,繪影繪聲的説楊文廣奉狄青命,率精騎追擊儂智高至大理國東境之合江口(今雲南開遠市北、南盤江與樂蒙河會合口),並於其地築城屯兵而還。相較之下,余嘉錫便嚴謹得多,他以《續資治通鑑長編》及《磨崖刻平蠻三將題名碑》均沒載文廣事蹟,而頗疑《宋史》之説。雖然余氏也考慮到隨狄青南征的文武官員二百三十一人,不可能全數具載於史籍。他猜测楊文廣可能僅隨軍差遣,或已赴德順軍(今寧夏隆德縣城關)任,不在將官之列,故不得題名,而功勞亦不顯。50 筆者曾檢索余氏提到的《磨崖刻平蠻三將題名碑》,發現除了狄青、孫沔和余靖外,題名該碑上的文武官員僅三十四人,而在歸仁铺(今廣西南寧市東)一役有大功的勇將張玉(?-1075)、和斌(1011-1090)及楊遂,以及在《宋史》有著錄的勇將李浩(?-1090後)(按:李浩之父皇城使李定〔?-1063後〕則名列第三將之首),均碑上無名。是故楊文廣碑上無名,並不能證明他不在從征的二百三十一人内。51 對於這問題,筆者以為其實比較有力的旁證,還是常征自己所引用、由沈遘(1028-1067)撰寫的一道〈西京左藏庫副使楊文廣可供備庫使〉制誥以下一番話:
勅某:前日南夷負恩為亂,以覆壞我郡邑,至於用師而後定。雖朕不德,不能懷服方外,而亦將吏不戒不習之罪也,故深察往失而推擇所遣,益不敢輕。惟爾文廣,材武忠勇,更事有勞,故今以爾總一道之兵,戍於邕管。 52
考沈遘寫這道制誥,一開始即提到「南夷負恩為亂,以覆壞我郡邑,至於用師而定」。當然,沈遘所説的作亂「南夷」,固然可以指在「前日」即嘉祐五年底入寇邕州的交趾與甲峒蠻(詳下文),但更有可能指數年前真正覆壞許多郡邑,要宋廷用重兵才能平定的儂智高之亂。按宋代制誥之普遍寫法是先表揚受職人的舊勳,然後提出宋廷對受職人的期望。倘沈遘所言的「負恩南夷」確是儂智高,則楊文廣被稱許為「材武忠勇,更事有勞」,就當與前述的平儂智高事有關。要説楊文廣在平儂智高之亂上毫無干涉,沈遘就不用這樣寫。
除了沈遘這道制文外,楊文廣有份從征的另一個有力旁證,是筆者從宋人文集中找出來,確信是楊文廣在治平二年(1065)拜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時的制文。考撰寫這道制文的是在英宗(1064-1067在位)朝任知制誥的鄭獬(1022-1072)。鄭獬説楊文廣「嘗以忠謹佐騎兵,環徼道而侍,夙夜有勞」;故此「宜用次補」為管軍。筆者認為鄭獬這番話正是指楊文廣當年率騎兵從征儂智高有勞的事。考鄭獬之父鄭紓,曾以都官員外郎從征儂智高,任孫沔第二將的管勾機宜。倘楊文廣有份南征的事不假·鄭獬在制文上,溢美一下乃父舊僚的舊勞,是順理成章的事。53
除了上述兩道制文的旁證外,我們若從人脈關係的角度去看,楊文廣被召從征本來是順理成章的事。按楊文廣既為范仲淹及韓琦所知,又毫無疑問為久在陝西的狄青所認識,即使不是韓、范所薦,狄青亦會徵他從征。據曾鞏的記載,狄青所徵辟的將校,「皆青之素所與,以為可用者」。54 楊文廣既是狄青所認識的,本身又有才幹,他若不被徵召,才是怪事。大概楊文廣在南征中並未擔任重要的戰鬥角色,更未参預歸仁鋪一役之惡戰(按:清人所傳他追擊儂智高之事只能存疑),55 故此他功勞不顯,除了《宋史》本傳外,就未載於其他史籍中。筆者認為,雖然有力旁證不多,但楊文廣從狄青南征儂智高的可能性仍較高。
狄青的大軍於皇祐五年正月,經過歸仁鋪一役之浴血大戰,擊潰了儂智高。56 宋廷厚賞有功臣僚,除主帥狄青獲擢樞密使,副帥孫沔陞任樞副,余靖優遷為工部侍郎外,其餘將校,原為諸司使臣的分三等遷官,遷者十三人,例如歸仁铺一役有大功的賈逵,便自如京副使超擢為西染院使領嘉州(今四川樂山市)刺史;另荊南鈐轄王遂,便以一等功,自左衞將軍優遷為皇城使、資州(今四川資中縣)刺史;至於三班使臣就分五等遷資,遷者凡七十二人,其中張玉由右班殿直超遷為大使臣之首的内殿承制,並任廣西钤轄。楊文廣大概在這七十二人中,而得以出知渭州之德順軍。57
楊文廣知德順軍的任期,《宋史》並沒有提及。常征據沈遘前述的制誥,未經考究,便草率地認為楊文廣在皇祐五年從征儂智高後,以功陞西京左藏庫副使知德順軍,並在翌年,即至和元年(1054)更超陞四級為供備庫使,自知德順軍陞任廣西鈐轄兼判宜州(今廣西宜州市)與邕州。58 遺憾的是,常征犯了四項錯誤:第一,其實從皇祐五年開始到嘉祐五年(1060)底,知邕州一直是追殺儂智高有功的蕭注(1013-1073)。至於廣西鈐轄就分别由張玉及盧政(1007-1081)擔任,與楊文廣並不相干;59 第二,在官階方面,楊文廣在皇祐五年不可能是西京左藏庫副使。考楊在平張海之亂後遷殿直。我們假定楊因功所授是左班殿直,從慶曆三年底到皇祐五年初的十年當中,若依循正常遷轉,即使有范仲淹的保薦,在沒有大戰功的情况下,楊文廣最多只能遷陞三階,即像乃兄楊德政那樣做到西頭供奉官。要説楊文廣出守德順軍時已官至西京左藏庫副使,除非他像張玉那樣立下奇功,獲得超擢,但並無證據證明這點。第三,沈遘這道制誥絕對不是至和元年寫的。筆者根據《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鑑長編》、《皇宋十朝綱要》、《全宋文》及王安石撰的〈沈内翰墓誌銘〉,考索沈遘的仕歷,可以確信這道制誥最早只能在嘉祐六年(1061)初,最遲在嘉祐六年十二月,當沈遘擔任知制誥時所撰;60 第四,據《宋史》所記,楊文廣在知德順軍任滿後,先調知宜州,才陞為供備庫使為廣西钤轄知邕州,絕對不會如常征所説「兼判宜、邕兩州」。早在皇祐四年十月,宋廷接受樞密副使王堯臣(1003-1058)的建議將廣西分為三路,置宜州、容州(今廣西容縣)、邕州三州安撫都監,以融州(今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柳州(今廣西柳州市)和象州(今廣西象州縣)隸宜州;白州(今廣西博白縣)、高州(今廣東高州市)、竇州(今廣東高州市北)、雷州(今廣東雷州市)、鬱林州(今廣西玉林市)、化州(今廣東化州市)、南儀州(今廣西岑溪市)、藤州、梧州、龔州、瓊州(今海南海口市)隸容州;欽州(今廣西欽州市)、賓州(今廣西賓陽縣西南)、廉州(今廣西浦北縣)、横州、海州(今廣西桂平市)、貴州隸邕州。楊文廣在知宜州時連廣西鈐轄都不是,怎會兼知兩大州?事實上,在嘉祐六年,在楊文廣調知邕州的同時,繼他出任知宜州的是皇城使宋定。61倘筆者考證不誤,楊文廣在皇祐五年出知德順軍時的官階最多是大使臣的内殿承制,他要到嘉祐六年出知邕州前才累遷至西京左藏庫副使。至於他任知德順軍時之年月,據筆者的推测,他當歷兩任,即共在德順軍六載,至嘉祐三年才南徙至廣南西路的宜州。62
德順軍即渭州隴竿城,據王堯臣在慶曆三年正月從陝西考察回來所寫的報告稱,它與羊牧隆城(今寧夏西吉縣將台鄉南火家集西北)、靜邊(今甘肅靜寧縣紅土嘴)、得勝(今寧夏西吉縣硝河鄉)四寨,在六盤山(今寧夏固原縣西南,接隆德、涇源二縣界)外,內則可作渭州的藩籬,外則為秦隴襟带,地土饒沃,人口眾多。其中尤以籠竿城蕃漢交易,市邑富庶,勝過所有近邊州郡。為此之故,西夏早有奪取之心,亦因籠竿城距西夏界較近且道路容易,但往宋的內地就有山川之阻,王堯臣當時即建議將籠竿城等四寨建置為軍,擇路分都監一員知軍,專提舉四寨,令修濬城塹,添屯軍馬,及時聚蓄糧草,以為備禦。宋廷接纳王的意見,就在同月以隴竿城建為德順軍。63 另據李燾所記,德順軍建置後,在至和年間,其靜邊寨由蕃部組成的壕外弓箭手尤為勁勇,誘使夏人多次來爭,幸而因宋軍已築堡防守,夏人之謀不得遂。到嘉祐五年以後,宋廷更在德順軍及原、渭州置場收市,以解州鹽引與蕃商交易良馬八千。直到英宗治平年間,德順軍一直是宋廷與西蕃買賣戰馬的重鎮, 64故楊文廣獲委為知德順軍,絕非閒職。楊文廣在德順軍任上之事蹟,史所不詳,我們只能從沈遘制文中「材武忠勇,更事有勞」的評語,相信楊文廣做得相當稱職,而從上面李燾所記,西夏在至和年間多次進攻靜邊寨不得逞,也可推論到楊文廣築堡防守之本領相當不俗。據陳守忠往德順軍遺址的實地訪查,在德順軍所轄的得勝寨,相傳是楊文廣點將之處,這亦與史實符合。65
楊文廣在知德順軍任上的上司,從至和元年四月始,直至嘉祐元年十一月以後,一直是龍圖閣直學士、涇原經略安撫使兼知渭州任顓(990-1067)。任顓有謀略,長於守邊,曾著《治戎精要》三卷,述西夏風物、山川、道路及出入攻取之要。狄青南征時,他又負青扼守後方潭州(今湖南長沙市),以誅除儂智高奸細有功。他除了與楊畋有舊外,相信亦與從征儂智高的楊文廣相識。他以在潭州卑溼得腳疾,起初請調舒州(今安徽潛山縣),最後宋廷命他出知渭州。楊文廣調知德順軍,説不定是任顓的推薦。任顓守渭,史稱「軍中之政寬猛相濟,將吏畏伏」。看來楊文廣與任顓合作無間。可惜的是,任顓未幾以年老求徙徐州,接着便致仕,未能對楊文廣的仕途有什麼幫助。66
本來最能提拔楊文廣的,是他的舊上司樞密使狄青。不幸的是,狄青在嘉祐元年(1056)八月,被猜忌他的文臣集團以不光明的手段逐出朝廷,且在翌年二月在陳州(今河南淮陽縣)憤恨而亡。67 狄青死後,能對楊文廣仕途有助的朝臣,除了在嘉祐三年六月拜相的韓琦外,相信就是他的族姪楊畋。楊畋在皇祐五年正月被降職後,大概因余靖的極力説情及推薦,很快又回陞為起居舍人、河東轉運使。他在嘉祐三年八月前入為三司戶部副使,不久又兼同勾當三班院,未幾又陞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判吏部流內銓,到五年中又改知制誥。到嘉祐六年中,楊畋又擢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筆者相信,論關係與地位,楊畋與他的好友余靖,都是最有可能舉薦楊文廣出任要職的人。68
楊文廣從嘉祐三年至六年知宜州任上的事蹟亦不詳,只知他的繼任人是官階比他高的廣南西路安撫都監皇城使宋定。69 楊文廣的官階,相信在他調任知宜州時已陞為西京左藏庫副使。至於他在嘉祐六年被撰為廣西鈐轄兼知邕州,原因是廣西又出了問題。考知邕州凡八年的廣西都監蕭注,為了立邊功,早在嘉祐四年九月,便以利益厚結廣源諸蠻,暗中修繕甲兵,準備攻略交趾。但蕭注尚未動手,在嘉祐五年七月,其部將都巡檢宋士堯便因追擊入寇邕州的西平州峒將,進入交趾,雖初戰得勝,但第二天,宋軍便受到交趾與甲峒蠻的反擊,以致全軍覆沒。交趾與甲峒蠻聯軍又乘勝追擊,入寇欽州的永平寨(今越南高諒省祿平)。宋廷見事態嚴重,在同年八月命熟知蠻事的余靖以吏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往廣西應付交趾的入侵。宋廷在同年十一月,又以蕭注在廣西所為不法,挑起禍端,將他貶職徙為荊南鈐轄。他的遺缺就由余靖的副手如京使、知邵州(今湖南邵陽市)賈師熊出任。70 余靖在六年五月將入寇邕州的甲峒蠻及蘇茂州蠻擊退後,便陞任尚書左丞,調為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廣州。當時嶺南仍未平定,賈師熊卻又力辭知邕州之任,大概因楊畋的推薦,余靖想起他當年平儂智高的舊部楊文廣,就向宋廷舉薦楊自鄰近的宜州調任邕州。71
楊文廣在嘉祐六年調任廣南西路鈐轄知邕州時,他的官階也自西京左藏庫副使遷為供備庫使,終於進入諸司正使的行列。他的上司是頗有智計的廣西轉運使李師中(1013-1078)。楊文廣在邕州的治績所載亦不多,據《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記,楊文廣在邕州時,一直密切注視交趾的動向,一有風吹草動,就馬上遣軍校乘驛向李師中報告。72 附帶一談的是,常征曾引用明清人的傳聞,説楊文廣曾知全州(今廣西全州縣)及柳州,不過,在未有確實的記載證明前,這類説法只能存疑。73
楊畋於嘉祐七年五月病逝,74 對楊文廣自然是壞消息,太原楊家兩房,到了這時候,就以他們叔姪二人一文一武最有成就,最能維持家聲。現時楊畋過世,楊家就只能靠年事已高的楊文廣支撐了。
嘉祐八年三月,仁宗病逝,由其姪英宗繼位。楊文廣大概因新君嗣位的恩典得到遷陞。據《宋史》本傳所記,他在治平初年以前,已超陞十五資為左藏庫使並帶御器械,為他日出任副都總管及管軍累積了必須的資歷。 75不過,體弱多病的英宗,才是教他大器晚成的伯樂。
假定楊文廣在慶曆三年是四十四歲,到英宗即位,他應已六十四歲。對武臣已言,像狄青那樣晉位二府,是極之不易的;但只要有邊功、有點運氣,晉身「禮繼二府」的三衙管軍,卻不是太難。
英宗繼位翌年,即治平元年,三衙管軍出現人事變動,多年前做過楊文廣上司的步軍都虞候趙滋在是年五月病逝。76 到同年八月,殿前都指揮使李璋(1021-1073)解軍職,英宗即以馬軍副都指揮使郝質(?-1083)陞任殿帥,其餘馬帥、步帥、殿候、馬候、步候就分别由賈逵、宋守約(?-1075)郭逵(1022-1088)、竇舜卿(985-1072)、石遇(?-1065)依次替補。至於捧日天武及龍神衞四廂兩缺似乎未補人。77 英宗大概要證明他御政的能力,在病體稍痊時,於是年十月就親自檢閱禁軍諸軍班直將校武藝,並擢授有才之將校。78 到治平二年初,步軍都虞候石遇卒,三衙管軍共有三缺。英宗這次親自决定陞補的人選,在是年六月,英宗擢用他在藩邸時曾留有良好印象的楊遂,自絳州(今山西新絳縣)團練使,嵐(今山西嵐縣)、石(今山西離石市)、隰州(今山西隰縣)緣邊都巡檢使為步軍都虞候,加登州(今山東蓬萊市)團練使。79 考《宋史》稱英宗在「治平中」擢用楊文廣,按治平中當為二年,楊文廣被擢為三衙管軍的年月,極有可能與楊遂被擢之年月接近。又據劉摯(1030-1097)所記,楊畋所甚賞識的陶弼(1015-1078)在治平二年即以崇儀使知邕州,正脗合楊文廣在是年召入朝出任管軍之記載。據《宋史》載,當宋廷議論誰可補授「宿衞將的管軍時,英宗即以楊文廣為名將之後,且有戰功,耀為成州(今甘肅成縣)團練使,拜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楊文廣這年當已過六十六歲,算得上是大器晚成。至於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一缺,便擢用另一員老將高陽關都鈐轄盧政。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八員管軍中,賈逵、楊遂、盧政和楊文廣四人都是曾隨狄青南征的大將,而二楊和盧政則分别從西邊、西南及北邊徵召入朝,出掌禁旅。80
楊文廣擢為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在宋廷文臣眼中,是莫大的榮寵,誠如蘇轍在元祐五年(1090)所論,「自祖宗以來,以管軍八人總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81 鄭獬為楊文廣撰的四廂都指揮使的制文,除稱許他昔年從征儂智高之勞外,又期許他在治軍時能「嚴法令,明白善惡,以率其不恪」,並將之比喻為漢宣帝(前73-前49在位)時之中郎將、平通侯楊惲(?-前54)。82
楊文廣能被擢為管軍,除了受知於英宗外,相信亦受到宰相韓琦的極力推薦。雖然在現存的韓琦文集中,暫時找不到韓琦與楊文廣交往的直接證據,但筆者卻在韓琦心腹強至(1022-1076)的文集中,找到楊文廣與強至通信的實證。強至在〈回楊四廂書〉中,有以下的描述:
向承高誼,遠枉盛牋。論志意之欲為,顧言辭之甚壯。知是仁者之有勇,可使儒夫之聞風。間又相規,正如所願,甚為欽感,尤劇感銘。83
考強至這封信的撰寫年月不詳,暫難確定楊文廣收信時,是在京中統率禁軍,還是已出守秦鳳?韓琦在治平四年十一月出守陝西時,強至即任其機宜書記,84 楊文廣雖在韓琦麾下,但韓、強在永興軍,楊在秦州,二人通信,説是「遠枉盛牋」,也説得通。不過,強至在這信中絲毫沒道及楊在秦州供職之事,故筆者推測此信當撰於楊尚在京師時。我們從強至這封信,可以從側面窺見楊文廣在出任管軍後,雖年事已高,但仍胸懷大志,給人老當益壯,勇氣不减之感。另外,雖寥寥數語,但亦看出他與強至交情非泛泛。他後來隨韓琦出守陝西,得到韓之倚重,實是順理成章的事。
除了韓琦外,龍圖閣學士張方平亦很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幫助楊文廣擢陞。首先,張方平早在皇祐五年十一月南郊大赦時,上奏請錄用楊業等五員禦邊名將的子孫。這大概讓英宗對楊家留下一個良好印象。85 其次,當張方平在治平元年底出知鄆州(今山東鄆城縣)前入對,向英宗論及管軍的人選時,他除了指出根據祖宗的做法,若有履歷才具適合的人,可以直接擢為副都指揮使或都虞候,不必經過四廂一階;另外他又強烈批評「近日所補軍職,人材器略多無素望,至於累勞,亦無顯效,短中取長,苟備員而已,又遞遷迅速,曾微事功」。他並特別點名批評剛在是年八月陞任殿前都虞候的郭逵。雖然他推薦可任管軍的人沒有楊文廣,但他的話顯然加強英宗破格擢用楊遂、楊文廣二人為管軍的决心。86
治平三年(1066)四月,三衙管軍人事再有變動,因殿前都虞候郭逵被擢為同簽書樞密院事,同年五月,就由馬軍都虞候竇舜卿陞任殿前都虞候,至於馬候一職,就由步候楊遂替補。原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盧政則陞任步候。楊文廣相信在這時,亦得以補陞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至於他的遺缺,相信就由在是年九月在柔遠寨(今甘肅華池縣)立功的環慶副都總管張玉補授。87
平治四年(1067)正月,英宗病逝,神宗繼位,因新君嗣位,楊文廣大概因此得遷為興州(今陝西略陽縣)防禦使。88 是年閏三月,神宗詔諸路帥臣及副總管移易,大概楊文廣就在這時出為秦鳳路副都總管。89
是年九月,韓琦罷相出判相州。到年底卻因知青澗城种諤(1027-1083)在十月襲取綏州(今陝西綏德縣),宋夏又再交锋,是年十一月,神宗改命韓琦為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判永興軍,統籌陝西全局。90神宗胸懷大志,有開疆闢土的機會,他絕不放過。他對付西夏的辦法,在緩進方面,就秉承仁宗時范仲淹、韓琦的做法,在宋夏邊上要塞之地,多建堡寨,招纳蕃部,以削弱西夏的國力。韓琦宣撫陝西,即積極執行這項政策,廣建堡寨。在這環境下,擅於築城的楊文廣,終於英雄有用武之地。
大概在治平四年底或熙寧元年(1068)初,楊文廣的上司、秦鳳經略使知秦州馬仲甫(?-1080)向韓琦建議,在秦州西邊、渭河支流散渡河上之篳篥城故址(按:《宋史》作「篳栗」)築城而墾耕之。篳篥原為秦州生戶所居,面積有百里之廣,因原居之生戶被西夏劫走而無主。韓琦贊成其主張,但樞密使文彥博不同意,怕此舉會引起夏人之爭執。韓琦多番上奏,據理力爭,認為在陝西各路緣邊築城,招納蕃部防守,早有前例,絕非生事,他並且提出築城後之具體安排,包括在何處調兵戍守,以及怎樣置酒税場課利。韓琦且進呈有關築城的圖則。宋廷在是年七月,終聽從韓琦的建議,准許在篳篥建城。91
韓琦除了在篳篥故城築堡外,又計劃在距篳篥八十里的擦珠谷(按:《宋史》及《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未》作「噴珠」)築堡。楊文廣在是年七月奉韓琦命,分别在篳篥及擦珠谷築城,據《宋史》及《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的記載,楊文廣曉得夏人會來爭,就採取聲東擊西之計,對諸將佯稱去擦珠谷築城。當宋軍在日暮前趕到該處時,楊文廣馬上下令掉頭急行軍趕去篳篥,並馬上立寨安營,做好防禦及戰鬥準備。當夏人知道中計,在翌晨趕到時已太遲,雖然夏兵為數不少,但見宋軍有備,只好退兵。夏人臨走時致書恐嚇楊文廣,聲稱會稟知夏主,出兵數萬騎來爭此城。楊文廣看穿夏人其實色厲内荏,馬上遣將追擊,結果斬獲甚眾。楊文廣這次出奇制勝,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别人問他致勝之道,他回答説作戰要取得先機,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按:《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未》作「奪人之心」。篳篥既是兵家必爭之地,就不能讓夏人知道宋軍有奪取之企圖,因為夏人知道而快一步佔領,宋軍要取回就十分困難。楊文廣佔據篳篥,並擊退夏人,築城就順利得多。就在是年九月,楊文廣在簟篥築好大甘谷寨,取名甘谷城(今甘肅通渭縣南楊家城子);跟着他又在擦珠谷築堡,到是年底竣工,取名通渭堡(今甘肅通渭縣什川鄉李家坪,按:熙寧五年陞為通渭寨)。宋廷優詔嘉獎楊文廣,並賜他對衣、金帶及銀鞍勒馬。92
楊文廣修築甘谷城及通渭寨,可説是他戎馬生涯中的一大傑作。他對敵情的準確判斷、行軍佈陣之快速,以及築城之效率,既見其智勇,亦顯其楊門之絕藝。此外,甘谷城亦因楊文廣之故,留下楊家將之傳說。據陳守忠在1984年5月往二城寨的遺址實地考察,甘谷古城當地有一村楊姓人家,相傳是楊家將的後代。陳守忠認為楊文廣嫡派子孫留在此地可能性不大,但他帳下親兵以主帥的姓為姓,留守在這裹,而留下後代,則甚有可能。陳氏的論斷可取。93
楊文廣築畢二城後,大概以三年任滿,並因宋廷調整陝西各路帥臣人事之故,在熙寧二年(1069)以後徙知涇州的镇戎軍(今寧夏固原縣),至於秦鳳副都總管之職,就由殿前都虞候竇舜卿接任。本來楊文廣應兼任涇原副都總管,大概渭帥蔡挺(1020-1079)仍屬意他的愛將張玉留任,也可能是判延州郭逵的要求,宋廷就安排楊文廣徙知鄜州(今陝西富縣),做郭的副手。據《續資治通鑑長編》所載,楊文廣先權知鄜州,到熙寧三年(1070)十二月正式與知鄜州孟德基(?-1079後)對調差遣,由孟知鎮戎軍,楊知鄜州。未知何故,身為管軍的楊文廣,竟沒兼鄜延副都總管。94
就在楊文廣徙知鄜州之時,西夏在熙寧三年八月舉國入侵,兵鋒直指環慶路諸州軍城寨。因環慶經略使李復圭(?-1074後)措置無方,宋軍損兵折將。宋廷於是命參知政事韓絳(1012-1088)為陝西宣撫使,統籌陝西全局。九月,韓絳抵陝西後,調兵遣將;不過,韓絳重用种家將第二代的种諤、种診(?-1083後)兄弟之餘,對楊文廣就投閒置散。楊的上司郭逵因與韓絳意見不合,就被召還京師。95
熙寧四年(1071)八月,神宗决意開邊熙河,他派王韶(1030-1081)領兵出征,所部勇將包括涇原副都總管張玉和西京左藏庫副使高遵裕(1026-1085)。宋軍從秦鳳路出發,但久在秦鳳的楊文廣這次又未被選上從征,也許王韶覺得年過七十的楊文廣已英雄遲暮了。96
熙寧五年(1072)十一月,殿前都虞候、環慶副都總管竇舜卿以疾請解軍職,他的遺缺就依次由馬軍都虞候楊遂補上,而盧政就由步軍都虞候遷馬軍都虞候。楊文廣雖然沒有顯赫戰功,也得以晉陞一級為步軍都虞候,相信亦在這時,調離陝西,出任河北的定州副都總管,回到楊家將當年守禦遼國的地方。97
楊文廣任定州副都總管時,他的上司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市)是通曉兵略的滕甫(1020-1090)。98 不過,宋遼和好多年,河北防務早就鬆懈。對於遼人在熙寧六年(1073)六月開始有異動,神宗不無憂慮,他對臣下表示「北人渐似生事,今河北一路兵器皆抏敝不可用,加以將卒庸墮,何以待敵」?但主政的王安石正将注意力放在熙河開邊,不想節外生枝,分散力量,就安慰神宗説:只要訓練士兵,完繕城壘,選擇將帥便成了。其實王安石並不將河北防務放在心上,故並未重用滕甫或楊文廣等能吏宿將。99
王韶在熙寧六年十月向宋廷奏報,已收復熙州(今甘肅臨洮縣)、洮州(今甘肅臨潭縣)、岷州(今甘肅岷縣)、疊州(今甘肅迭部縣)、宕州(今甘肅岩昌縣)等州,開地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近二萬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帳。神宗和王安石君臣自然喜不自勝。王韶以下有功將士,連帶陝西各路帥臣,都以支援之功,得到厚賞遷陞。100 但宋廷開心快活澴不到一個月,已諜知遼國打算爭奪蔚(今河北蔚縣)、應(今山西應縣)、朔(今山西朔州市)三州地界。神宗擔心遼夏會一齊侵邊,怕兩面受敵。王安石一面用樂觀的分析以安神宗之心,認為遼國不會棄絕和好;另一方面清楚表明他的策略,就是「朝廷未宜有北事」,而夏人不足畏。即是說:一旦有事就對遼主守,對夏主攻。101
王安石的樂觀卻事與願違。熙寧七年(1074)正月,遼國開始在議界一事挑起爭端,是年二月,神宗除命王安石設法改善河北防務外,也準備在遼使到來時進行談判。但王安石不贊成力爭,亦不相信遼會動武,認定可以慢慢與遼理論。王安石還力主在河北裁兵,又反對調熟知邊事的郭逵知定州。最後神宗接受王的建議,派三司使、龍圖閣學士薛向(1016-1081)出知定州,代替滕甫,成為楊文廣的新上司。102
是年三月,遼派蕭禧到來,議蔚、應、朔三州邊界。宋廷隨即派劉忱、蕭士元及呂大忠(?-1094後)往代州(今山西代縣),與遼使商量地界,稍後再派天章閣待制韓縝(1019-1097)使遼。就在韓縝使遼途中,王安石被罷相。不過,繼任為相的韓絳並沒有改變對遼妥協的政策。103 就在宋廷主張對遼讓步,以求息事寧人的氣氛下,楊文廣卻出人意表的向宋廷獻上攻取幽燕的陣圖和方略,不但反對割地妥協,還主張對遼用兵,收復失土。這裹,我們倒要探究一下,楊文廣為何貿然上奏?究竟他是不甘寂寞,企圖以大言引起神宗注意,還是深思熟慮,認定伐遼機會難逢?這一方面余嘉錫和常征都沒有討論此問題。104
雖然今日我們看不到楊文廣所上的奏状和陣圖内容,但從楊文廣一向謹慎低調的作風,筆者認為楊文廣絕非信口開河,無的放矢的人,他一定經過周詳的考慮,才會在宋廷傾向對遼妥協的環境上書。筆者認為楊文廣確是在長期不得志的情况下,趁着遼國挑起爭端之時機,盡他最大及最後的努力,希望説服及打動神宗,讓他統軍攻遼,完成父祖未完心願,並為祖父復仇。筆者猜測楊文廣其實已從他的上司、知定州滕甫處,洞悉神宗一直想攻遼,以報太宗為遼軍所傷致死之大仇的心事。另外,他看透遼國其實色厲内荏,國力早已今非昔此,只要宋廷做足準備,再覓得有利時機,出兵幽燕並非無取勝機會。105 至於他所進呈的陣圖和奏状,肯定是據他在定州多年來打探得來的敵情,以及得自父祖的秘本編繪而成。神宗君臣不是草包,楊文廣要説服神宗,他所進呈的東西,必定是精確的作戰計劃和圖則,以及詳盡的敵情分析。筆者相信楊文廣已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不幸的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赏識楊文廣的韓琦早罷相外任,而且韓琦在伐遼事上後來還持反對的態度(事見下文)。楊文廣在两府並沒有支持他的人,他的「奇策」就很「正常」地一直得不到宋廷的回應。朝中無人,是楊文廣一直得不到重用的原因,這次也不例外。楊文廣等不到宋廷的回覆,就在是年十一月齎志以歿。假定他在父卒時十五歲,他當得年七十五。宋廷在翌年閏四月,循例追贈他同州(今陝西大荔縣)觀察使。至於有否錄他的子姪為官,則史所未載。106
楊文廣的謀議是否可行?後世景仰楊門忠烈的學者如余嘉錫等都只是讚歎,而惋惜它不被採納。其實楊的奇策在他身故後四個月,即受到韓琦的嚴厲批評,韓琦還近於不點名批評他故去的部將。韓琦在熙寧八年(1075)三月應神宗之召議遼事即指「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云「敵勢已衰,特外示驕慢矣。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将臣領大兵深入敵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韓琦並且分析:「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緣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皆麄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給,敵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此太宗朝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致歧溝之敗也。」107 韓琦的分析是否得當,因我們今日看不到楊的原奏,故難以一面之辭作出評定;不過,從韓琦及同時應召言事的文彥博對伐遼之議的強烈反應,似乎楊文廣的建議在宋廷中也有人認同,並在相當程度上打動了神宗,108 以致韓琦等非要用明確的措辭及看似無可爭議的理由來反對。楊文廣的謀議到底有多少真知卓見?楊文廣主張伐遼的真正目的是收復失土,還是為了劃界談判故意做出不惜一戰的姿態,以迷惑遼方的間諜?109 可惜它和楊文廣的後人一樣,今日已無從稽考。
北宋楊家將的名聲在明代以後,憑着小說戲曲的渲染,成為整個宋代最為人知的將門。然考諸史實,這個在宋代名聲最響的將門,本來名過其實。即使將旁支的楊畋計算在内,太原楊氏到了第四代,已到了強弩之末的境地。楊家的第五代可考的是楊畋的獨子楊祖仁(1061-1113後),他亦從文官之途仕進,然在哲宗(1086-1100在位)紹聖年間也只擔任地方小官,以後的事蹟亦不顯。110 有些學者如常征將播州楊氏以及南宋初年的庸將楊存中(1102-1166)也算作楊家將,是很有間題的。111 我們感情上景仰楊門忠烈,但要接受的事實是太原楊家其實到了第三代,已和絕大多數的宋代將家一樣,每下愈况,走向衰落。楊家的運氣其實已算不錯,當楊延昭長次兩子無法克紹箕裘,家道中落之際,幼子楊文廣卻在步入中年時,交上好運,得以中興楊家,勉強撐起家門將倒的旗幟。比起父祖,楊文廣的實際地位最高,最後官至父祖不曾得到的管軍高職:不過,他的軍旅生涯實在平凡,父祖的「無敵」、「善戰」似乎不曾在他身上出現過。雖然英宗稱他「有功」,沈遘和鄭獬代表宋廷説他「材武忠勇,更事有勞」、「忠謹佐骑兵,環徼道而侍,夙夜有勞」,而強至也稱他「仁者之有勇」;惟據目前可見之資料,他平生並未經歷什麼惡戰。考他出仕時從平張海,不過是與人數有限之鳥合之眾交鋒。後來他雖然隨狄青南征儂智高,但並沒有參預歸仁铺之生死大戰。至於戍守西南、西北及北面多個州軍,除了在築城篳篥一事上看出他的一點將略智謀外,就只能籠統地説他守邊克盡闕職,沒出紕漏。至於他所獻的取幽燕謀議,當時就已被韓琦批評為不可行,不能以此過譽他的將略。我們從楊文廣的經歷和遭遇,可以看出曾經顯赫一時的將門,要維持三代,實在極不容易。楊文廣還能夠大器晚成,自身的條件是他尚能掌握祖傳的築城絕技,而憑這點本事得到范仲淹及韓琦的賞識。另外,作為將家子,他也能順應時勢潮流,既懂得與文臣儒生交結,爭取他們的支持,又能兼通文墨,執筆陳奏,爭取君主之好感。在際遇運氣方面,他正好碰上内亂與外患的環境,就教他有用武立功之機會。本事與機遇的結合,就是他能出人頭地,重振家聲的關鍵。當然,他不能像主將狄青一樣,功名事業更上一層樓,亦與運氣稍遜有關。楊家最大的不幸,就是楊文廣竟沒有一個較出息的子孫。最明顯的證據是他的不肖子孫,竟然連為祖宗寫一篇像樣的墓誌銘都做不來(按:與楊文廣有交情的強至卒於熙寧九年〔1076〕,按理楊家子孫起碼可找他為文廣寫墓銘),112 也無法保存楊文廣的著作或奏議書柬,以致我們對楊文廣生平事蹟所知如此有限。究竟是楊文廣教子無方?還是其子孫太不成材,就無法確知了。
創業維艱,守成更難,將家子要維持家聲不墜,往往比白手興家還要難。我們從狄青及其部將的興家發迹之事例,亦可見一斑。考狄青及其七員官至管軍的部將,除了狄青本人與和斌的下一代尚能勉強維持將門的聲譽外,其餘的人(包括楊文廣)的後代均無法守業。113 楊家能三代為將(若加上楊畋則為四代),歷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六朝逾百載,實在已是得天獨厚。楊氏將門從勃興到衰敗,與宋代眾多將門之興衰過程比較,其實並無顯著的差異。只因小説家把楊家將渲染和神化得過份,我們才會對楊文廣寄予厚望,並想不通楊家將「骤然」消失的緣由。
1、參閱紀振倫(?-1573後)(著),竺少華(標點):《楊家府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16-303。關於楊家將小説的版本及流傳情况,特别是《南北宋志傳》與《楊家府演義》之比較,最近期之研究,可參閱馬力:〈《南北宋志傳》與楊家將小説〉,《文史》第十二輯(1981年9月),頁261一272。是條資料蒙馬幼垣教授賜示,謹此致謝。另可參閱程毅中〈楊家將故事湖源〉,《燕京學報》新十期(2001年5月),頁257-268及〈楊家將故事溯源補正〉,《燕京學報》新十一期(2001年11月),頁283-284;孫旭、張平仁:〈《楊家府演義》與《北宋志傳》考論〉,《明清小説研究》2001年第1期·頁211-219。
2、 在《楊家府演義》中,狄青先奉命出征,因戰敗而仁宗改派年過半百的楊宗保為帥,並以年方弱冠的楊文廣為先鋒。至於在以狄青為主角的《五虎平南演義》中,楊文廣亦是以「少年小將軍」的身份出場。參見《楊家府演義》,頁216-238;(清)佚名(撰),覺園、愚谷(標點):《五虎平南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35。又據馬力研究所得,《南北宋志傳》所記楊文廣征儂智高之事,在三個小節上與《楊家府演義》略有不同。參見馬力:〈《南北宋志傳》與楊家將小説〉,頁271。
3、 考宋初確有楊懷玉(?-1022後)其人,但他是内臣,與楊家將並無關係,且年紀要比楊文廣長。楊懷玉在真宗(977-1022在位)晚年以入內供奉官任壽春郡王(即仁宗)的伴讀,並兼任京城西面巡檢;後來在天禧四年(1020)七月因沒及時舉報周懷政(?-1020)謀叛被眨為杭州(今浙江杭州市)都監;到乾興元年(1022)後復召還為内侍押班。參見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1995年),卷八十六,頁1973:卷九十六,頁2208,2210:卷九十八,頁2284(以下簡稱《長編》)。
4、 考楊業降宋後官至觀察使,後來戰死陳家谷(今山西朔州市西南),獲追赠太尉、大同軍(今山西大同市)節度使;但終太宗之世,並未獲追赠中書令或尚書令之官,按理不應被稱為令公。雖然小說家不懂宋官制,有胡杜撰官銜之嫌;但也可能有所本。按宋制,軍職至三衙都虞候的,一般可獲追封三代。例如與楊文廣同屬狄青部將的楊遂(?-1080),拜馬軍都虞候時,便獲宋廷封赠二代:後來他陞任殿前副都指揮使,再獲封贈曾祖及祖父。筆者懷疑楊文廣擢步軍都虞候時,獲追封三代之恩典,楊業因此獲赠官中書令或尚書令,而給人尊稱為令公。可惜楊文廣拜步軍都虞候及連帶之赠官制誥不存,無法證明此點。參見脱脱(1314-1355)(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卷二百七十二〈楊業傳〉,頁9303-9306;蘇頌(1020-1101)(撰),王同策(等點校):《蘇魏公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8年),卷三十五〈外制·侍衙親軍馬軍都虞候楊遂封贈二代〉,頁538-539;王安禮(1035-1096):《王魏公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楊遂曾祖詠赠太子少保制〉、〈祖德皇不仕可赠太子少傅制〉、〈父進贈左武衙上将軍太子太保制〉,葉18上下。
5、 余嘉錫:〈楊家將故事考信錄〉,載余嘉錫:《余嘉錫文史論著》(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頁456-461(以下簡稱〈考信錄〉)。
6、 常征:《楊家将史事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95-208(以下簡稱《史事考》)。
7、 陳守忠:〈隴山左右宋代城寨遺址調查〉,載陳守忠:《河隴史地考迹》(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13-219。
8、 參見本書的另一篇文章〈狄青(1008-1057)麾下兩虎將——張玉(?-1075)與賈逵(1010-1078)〉。
9、 楊文廣二兄的名字,僅見於《隆平集·楊延昭傳》,〈考信錄〉已點出。按〈考信錄〉及《史事考》均以楊文廣長兄為楊傳永:然筆者翻檢《隆平集》,從字型去看,楊文廣長兄的名字,似乎又像「傅永」,而不是「傳永」。參見〈考信錄〉,頁456;《史事考》,頁195;曾鞏:《隆平集》,收入趙鐵寒(1908-1976)(主編):《宋史資料萃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1月),第一輯,卷十七,葉4下。
10、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10月),第五冊,卷一百九十七〈夏侯觀·澤州龍堂記〉,頁403-404。
11、 關於楊文廣兄弟四人的名字,《史事考》在正文稱見於《宋史》、《隆平集》和《宋學士文集》。不過常征的註釋做得簡單,既沒有註明〈楊氏家傳〉的卷頁,也沒有為《隆平集》有關篇章作註腳;但他在正文卻說「《隆平集·楊延昭傳》雖然也略附文廣之事,然不及《宋史》之詳」。筆者對各書逐一查證,發覺《宋史》僅載楊文廣之名;而《隆平集》雖載有楊傳永、楊德政、楊文廣之名:但並沒有如常氏所說「略附文廣之事」。筆者傻疑常氏沒有直接引用《隆平集》。至於宋濂所撰之〈楊氏家傳〉,筆者翻閱《四庫全書》本的《文憲集》,發現該傳其實是播州楊氏的家傳,傳中稱楊延昭有子名充廣,卻說充
廣是楊業的曾孫。又稱楊充廣「嘗持節廣西,與(播州土酋楊)昭通譜,昭無子,充廣輟(其子)貴遷為之後,自是守播者皆(楊)業之子孫也」。筆者再翻檢《長編》、《宋史》、《宋會要輯稿》等三書之人名索引,並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正續篇、《中國地方志宋代人物資料索引》,均找不到任何有關楊充廣的記載。考羣書只言宋廷錄楊延昭三子官,宋濂在二百年後寫的一則記載,可信程度教人懷疑。光是說楊充廣攜子出使廣西,而竟將兒子過繼播州土酋一節,就很荒誕。筆者以為所謂楊貴遷是楊延昭孫兒的説法,出於播州楊氏自高聲價的冒認居多。常征對宋濂這一傳聞不加考證而深信不疑,他在毫無佐證下推楊充廣在景祐二年(1035)出使廣西,並將兒子楊貴遷過繼給播州土酋楊昭;他又相信宋濂的記戴,說楊貴遷在皇祐四年(1052)儂智高被平定前被殺。然考《長编》卷二百四十五神宗熙寧六年(1073)五月癸卯條載,「夔州轉運判官曾阜上言:播州楊貴遷在夷人中最強盛,以老,遣子光震、光榮獻鞍馬、牛黄、麝香。詔補光震三班奉職、光榮借職」(按《宋史》卷十五所記相同)。這條記載分明說楊貴遷在熙寧六年時只是老而未死,〈楊氏家傳〉説他於皇祐四年死於仇家之手顯然是誤記。再説,倘楊貴遷果是現任步軍都虞候楊文廣幼弟之子,宋邊吏怎會不知及不向宋廷稟明這關係?另李燾又怎會不在這一條下註明楊貴遷之來歷?再者,楊貫還若真是楊文廣之姪,則其年齡至少比楊文廣年輕二十載,考楊文廣在熙寧六年約七十歲,以此推論,楊貴遷當年最多不過是五十歲,如何算得是「老」?從年齡方面去看,顯然楊貴遷不可能是楊文廣幼弟之兒子。另外,楊貴遷子光震有子亦名文廣,倘楊贵遷果是楊文廣姪兒,楊光震怎會給兒子改上一個與伯祖父相同的名字?综合上述各點,筆者認為播州楊氏出於所謂楊文廣幼弟楊充廣的說法很難成立。楊文廣有弟名充廣之說,只能存疑。參見《隆平集》,卷十七,葉4下;《宋史》,卷十五〈神宗紀二〉,頁283;卷二百七十二,頁9308;《長編》,卷八十二,頁1861;卷二百四十五,頁5949;《史事考》,頁64-75,195,340-341,343;宋濂:《文憲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楊氏家傳〉,葉34上至37上。
12、 考楊延昭從姪楊琪(980-1050)初以父楊光扆卒於邊補殿侍(按:楊光扆卒時官僅西頭供奉官,故楊琪僅得不入流的殿侍),後來楊琪即以楊延昭之蔭得補為三班奉職。猜想楊文廣以幼子多半亦補三班奉職。附帶一談,在小說《楊家府演義》裹,楊延昭之八妹又巧合地名楊琪,小說家大概不知楊延昭有從姪亦名楊琪。參見《隆平集》,卷十七,葉4下;《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頁9308;《長編》,卷八十二,頁1861;卷八十四,頁1911-1912;歐陽修(1007-1072)(撰),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2001年),卷二十九〈供備庫副使楊君墓誌铭〉,頁443-445;《史事考》,頁195一196;〈考信錄〉,頁456;《楊家府演義》,頁5。
13、 《史事考》,頁195-197。
14、 《長編》,卷一百四十五,頁3505。
15、 《歐陽修全集》,卷一百零三〈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頁1577。另參見註釋10。
16、 王稱(?-1200後):《東都事略》,收入趙鐵寒(主编):《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卷四十八〈曾鞏傳〉,葉3上;《長編》,卷一百六十三,頁3924。另范仲淹在慶曆三年主持變法時,也上奏指出「今三班使臣數千人,品流至多,難於區别」。至於上官均在哲宗(1085-1100在位)元祐元年(1086)八月上奏指出,當時大使臣共二千五百餘人,小使臣一萬三千餘人。他說「舉天下之員闕,不足以充入仕之人」。雖然在仁宗時的情况沒有這麼嚴重,但楊文廣補缺陞遷之難,卻是鐵一般之事實。參見《全宋文》(1990年5月),第九冊,卷三百七十三〈范仲淹七·再奏乞兩府兼判〉,頁514(1994年8月),第四十六冊,卷二千零三十三〈上官均二·乞清入仕之源流〉,頁306。
17、 例如在王安石(1021-1086)所撰的墓誌銘,便有好幾個武臣,活到七十多歲,仍然官不過使臣。参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香港:中華書局,1971年),卷九十四〈墓誌·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墓誌·内殿崇班錢君墓碣〉,頁972-974。又如五代宋初強藩焦繼動(901-978)的孫兒焦君說(985-1041),在天聖中受父焦守節(?-1028後)蔭為右班殿直,但浮沉宦海十五、六年,至死只遷兩階至右侍禁。楊文廣父祖的官位尚不如焦繼勳父子,而他所授的官職又比焦君說低,則他二十多年才遷一兩階,實不足怪。參見《全宋文》(1993年10月),第三十三冊,卷一千四百二十六〈李昭文·大宋故右侍禁焦君墓誌銘〉,頁346-347。
18、 三場戰役中,宋軍驍將陣亡的計有郭遵、萬俟政、張方、孟異、任福、王珪、武英、桑懌等人,而被俘和被殺的將家子,包括三川口之役中的宋軍主將劉平(973-1040後)、石元孫(?-1046後),定川寨之役之主將葛懷敏(?-1042)、曹瑋(973-1030)的第三子曹俁,以及前述的驍將郭遵、武英等人,參見本書的另一篇文章〈敗軍之將劉平(973-1040後)兼論宋代的儒將〉;《長编》,卷一百二十六,頁2968,2986,2994;卷百二十七,頁3007-3008;卷一百二十八,頁3042-3044;卷一百二十九,頁3051;卷一百三十一,頁3100-3103;《宋史》,卷二百八十九〈葛懷敏傳〉,頁9700-9704;卷三百二十五〈郭遵傳〉,頁10505;〈任福傳〉,頁10506-10507;〈王珪傳〉,頁10508-10509;〈武英傳〉,頁10509-10510;〈桑懌傳〉,頁10510-10512;《臨川先生文集》,卷九十〈行状墓表·彰武軍箭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状〉,頁928-930。
19、 《長編》,卷一百二十九,頁3056-3057。
20、 《史事考》,頁196-197;〈考信錄〉,頁456。
21、 《歐陽修全集》,卷一百〈論京西賊事劄子〉,頁1537。
22、 《長編》,卷一百三十,頁3083-3084;卷一百七十五,頁4221;《歐陽修全集》,卷一百,頁1537。
23、 《長編》,卷一百四十五,頁3519。
24、 《長编》,卷一百四十二,頁3424。按:是條資料與常征所引之《會要輯稿》條相同。参見徐松(1781-1848)(輯):《宋會要輯稿》,國立北平圖書館,1926年本,(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兵十一之十九〉(以下簡稱《會要》)。考同書〈職官六十四之三十七〉,亦記柳植因當年養寇而在四年三月被眨(按:四年前脱年號)。參照《長編》,卷一百四十二,頁3424;卷一百四十七,頁3566,柳植是在慶曆四年三月被眨。然《會要》的抄寫者錯將此條置於寶元二年前,而做成錯覺,以為張海起事早在寶元二年之「景祐」四年。很有可能常征看了這一條後(按:《史事考》沒註引這一條),而推論郭邈山及張海早在明道、景祐年間已起事。另見《全宋文》,第九冊,卷三百七十六〈范仲淹十·奏乞召募兵士捉殺張海等賊人事〉,頁575。
25、 《歐陽修全集》,卷一百,頁1537。
26、 《長編》,卷一百四十三,頁3447;《歐陽修全集》,卷三十〈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杜公墓誌铭〉,頁448-450;卷九十七〈論宜專責杜杞捕賊劄子》,頁1501-1502。附帶一談,蔡稟是范仲淹的姻親,其弟是范的女婿。見《全宋文》,第九冊,卷三百七十六〈范仲淹十·奏避蔡稟嫌〉,頁572。
27、 楊畋是楊業弟楊重動(?-975)的曾孫,其父楊琪與楊文廣為從兄弟,楊琪父楊光扆早卒,楊琪初以父卒於邊授職殿侍,後來因楊延昭之蔭得補為三班奉職,最後官至供備庫副使。論輩份楊畋是楊文廣堂姪,論關係楊延昭曾照顧過他們父子。當楊畋在慶曆三年十月受命討蠻猺。以他的職務,舉薦堂叔為巡檢捕贼,在公在私都是合宜的。参見《歐陽修全集》,卷二十九,頁443-445;《史事考》,頁44-47;《長編》,卷一百四十四,頁3483。
28、 據歐陽修在慶曆三年及四年(1044)二月點名的劾奏,知郢州(今湖北鍾祥市)王昌運及接任的劉依都是老朽無能,敗壞州政的庸吏;而知汝州鲍亞之、知鄧州朱文郁都是老懦不才,從三司及轉運使趕下來的人;另知金州王茂先、鄧州順陽縣(今河南内鄉縣)令李正己均是老昧之輩,任由叛兵入城洗劫且留宿,不敢抵抗;而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則昏庸失職,半年内並不按察一人。參見《長編》,卷一百四十三,頁3450-3453;卷一百四十六,頁3539;《歐陽修全集》,卷一百〈再論置兵禦賊箚子〉,頁1538-1539。
29、 《長編》,卷一百四十四,頁3478;卷一百四十五,頁3496。邵興之要到是年十一月才被平定。
30、 《長編》,卷一百四十五,頁3497,3519。
31、 據韓琦的説法,張海眾至千人;但歐陽修則說官兵以八、九千之眾去追捕敷百人,似乎說張海只有數百人;不過歐陽修又說張海雖死,但其眾潰散,又去别處結集,在達州(今四川達川市)就有軍賊數百人,則二人說法亦相近。又據《長编》記載,當張海竄入山中時,韓琦令部將謝雲行等將缘邊土兵追捕。楊文廣可能也在其中。至於擒殺張海的,據包拯(999-1062)所奏,是右侍禁李用和(按:常征說是張永和,不知據何版本)。参見《長編》。卷一百四十五,頁3517,3519;包拯(撰),楊國宜(整理):《包拯集编年校補》(合肥:黄山書社,1989年),卷一〈論李用和捉獲張海乞依賞格酬獎奏〉,頁11-12;《史事考》,頁197。
32、 《長編》,卷三百六十九,頁8892。按蘇轍將李順、張海及廖恩相提並論,只是從其爆發原因相近而論,説到起事聲勢之盛和参預人數之多,張海和廖恩之起事,實不能與李順之起事相比。
33、 楊文廣陞任殿直,是左班抑右班,史所未載。考擒捕張海有功的右待禁李用和授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共遷四階,包拯仍以為賞薄,則楊文廣大概遷兩階為左班殿直的可能性,比遷一階的右班殿直為高。參見《包拯集編年校補》,卷一,頁11-12。
34、 趙滋是開封(今河南開封市)人,與楊文廣一樣,同屬將家子。其父趙士隆在天聖中戰歿,他受蔭為三班奉職。在慶曆初年,以右侍禁為涇原儀渭鎮戎軍都巡檢,因諭降德勝寨(今寧夏西吉縣將台鎮)叛兵有功,加閤門祗候。因張海作亂久未平,以韓琦之薦,命為都大提舉陝西、京西路捉賊。數月後亂平,陞東頭供奉官,調為京東東路都巡檢。見《長编》,卷一百四十五,頁3514;卷一百五十七,頁3812;卷一百七十五,頁4221;《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頁9308;卷三百二十四〈趙滋傳〉,頁10495-10497。
35、 《長編》,卷一百五十,頁3639。
36、 〈考信錄〉,頁456;《長編》,卷一百五十四,頁3740;卷一百五十七,頁3807。在下文筆者提到范仲淹在四年十月抵達河東,即考慮在麟(今陝西神木縣北)、府(今陝西府谷縣)二州修建堡寨。筆者以為,大概他在河東聽到楊業曾在該處修堡的往事,於是馬上召楊文廣前來,查詢其祖修堡之經驗。故筆者以為,楊文廣有可能早在慶曆四年底即已入范幕。
37、 考楊畋與韓琦及范仲淹都有交情,在韓、范二人文集中均有和楊畋詩。楊畋先後薦其族叔與韓、范,甚有可能。参見范仲淹:《范文正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和楊畋孤琴詠〉,葉1下;韓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箋注):《安陽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卷七〈次韻答運使楊畋舍人〉,頁306。
38、 《長編》,卷一百五十七,頁3813。
39、 《史事考》,頁197-199。
40、 考范仲淹在慶曆四年十二月即命知原州(今甘肅鎮原縣)蔣偕(?-1053)與知環州(今甘肅環縣)种世衡(985-1045)先後修築細腰城和大蟲巉。關於楊業修建邊寨的情沉,可參見李裕民:〈楊家將史事新考〉,載李裕民:《宋史新探》(西安:陕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09-214;另参見《長編》,卷一百五十二,頁3709-3710;卷一百五十三,頁3728。
41、 考狄青在慶曆四年八月,已自秦州(今甘肅天水市)刺史、權并、代部署調陞涇原部署,加惠州(今廣東惠州市)團練使,並越過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一階,涇授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位列三衙管軍。見《長編》,卷一百五十,頁3685。
42、 考范仲淹改知鄧州後兩年,徙知荊南府;到慶曆八年二月,又復知鄧州,到皇祐元年中,又改知杭州。参見《全宋文》(1991年3月),第十五册,卷六百十〈富弼二·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頁53-60;《長編》,卷一百六十三,頁3918-3919;卷一百六十七,頁4007。
43、 《長編》,卷一百五十七,頁3808;卷一百五十八,頁3820;卷一百五十九,頁3839;卷一百六十,頁3863,3874;卷一百六十一,頁3886,3888;卷一百六十四,頁3944;卷一百六十六,頁3987,3996,4000;卷一百七十,頁4098;卷一百七十二,頁4138;余靖(1000-1064):《武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九〈宋故狄令公墓銘〉,葉1上至9上;《全宋文》(1991年1月),第十四冊,卷五百七十七〈葉清臣·華陰縣嶽廟題名〉,頁181-182。考程琳在慶曆七年五月自知永興軍徙知延州,仍任陕西安撫使十月又判邠州,未幾又復判延州,至皇祐元年(1049)二月再加平章事留任,直至是年三月調為河北安撫使兼北京留守。接程琳任陝西安撫使的是宣徽北院使李昭亮,李在是年五月改鄜延經略安撫使判延州,至皇祐三年(1051)七月徙澶州(今河南濮陽市)。狄青即在是年七月後接李昭亮,出任鄜延經略使知延州。至於翰林學士葉清臣則在慶曆七年五月自青州徙知永興軍並兼本路安撫使,直至慶曆八年四月入為權三司使;不過,據慶曆八年的碑刻,楊文廣似乎並不在永興軍葉清臣麾下。至於杜杞則在慶曆八年四月,自河北轉運使為天章閣待制,環慶都部署、經略安撫使。按杜杞在平張海之叛時,說得上是楊文廣的上司。另名將張亢(994-1056)在慶曆七年二月至九月曾任涇原副都部署知渭州,他亦以築城著名,楊文廣會否在他麾下,待考。
44、 参見《長編》,卷一百六十一,頁3890-3892;卷一百六十二,頁3902-3907;卷一百六十三,頁3926;卷一百六十四,頁3943;文彥博:《潞公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五〈徼纳具州宣敕·慶曆八年閏正月》,葉6上。考宋廷在亂平後賞功極厚,文彥博即以功拜相,明镐則以功擢参政。
45、 《長編》,卷一百六十,頁3859;卷一百六十六,頁3991;卷一百六十八,頁4041。
46、 《長編》,卷一百六十七,頁4014-4015,4025。
47、 《長編》,卷一百七十二,頁4142-4148,4153-4154。
48、 《長编》,卷一百七十三,頁4163-464,4168-4169,4171-4175;卷一百七十四,頁4196。楊畋以兵敗被降職為屯田員外郎知鄂州(今湖北武漢市),到皇祐五年正月,再降為太常博士知光化軍。
49、 郭棐(1529-1605)(纂修):《嘉靖南寧府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有地方志叢書》(北京:書目文就出版社,1990年),卷六,葉35下;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稿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十一冊,〈雲南三·阿迷州〉,頁161;〈雲南三·合江口寨〉,頁162。
50、 《史事考》,頁200:〈考信錄〉,頁486。按常征沒有註明他所據的《讀史方輿紀要》卷頁。有關之記載,可參閱註釋49。至於余靖所撰的〈大宋平蠻碑〉、〈大宋平蠻京觀誌〉以及〈宋故狄令公墓銘〉均沒有提到楊文廣的名字。參見《武溪集》,卷五〈大宋平蠻碑〉,葉1上至4下:〈大宋平蠻京觀誌〉,葉4下至6上;卷十九〈宋故狄令公墓銘〉,葉1上至9上。
51、 参見《全宋文》(1992年4月),第二十一册,卷八百九十〈狄青·平蠻三將题名碑〉,頁274-276。
52、 沈遘:《西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西京左藏庫副使楊文廣可供備庫使〉,葉6下。按:常征所引之沈遘制誥,據稱錄自《宋文鑑》;但他所引的篇目卻漏掉「西京」兩字,另外他說《宋文鑑》為周必大(1126-1204)所編亦屬胡說,不知該書實為呂祖谦(1137-1181)所纂,常氏之粗心大意於此可見一斑。
53、 考鄭獬在嘉祐八年出任知制誥,訖治平四年九月,他當制期間,曾撰〈四廂指揮使制〉雨道,本文所引的是第一道。按這道制文沒言授四廂都指揮使為何人,但制文引用漢楊惲的典故,顯然受文者與楊姓武臣有關。楊文廣在治平二年中拜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時間正脗合鄭獬任知制誥;故筆者相信這道制盖的受文人,正是楊文廣。參見《全宋文》,第二十一冊,卷八百九十〈狄青·平蠻三將题名碑〉,頁274-275;曾鞏(撰),陳杏珍、晁繼周(點校):《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4年),卷五十二〈雜識二〉,頁719-721;鄭獬:《鄖溪集》,文淵閣《四庫至書》本,卷二〈四廂指揮使制一〉,葉14下至15上;卷十二〈薦錢公輔状〉,葉19上下;卷十八〈紀事〉,葉14上下。
54、 《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4年),卷五十二〈紀事〉,葉14上下。
55、 根據《長編》、《九朝編年備要》及《宋史》的記迹,再参照滕元發(1020-1090)所撰的〈孫威敏(按:即孫沔)征南錄〉所載,有份参預歸仁铺一役的宋将,除了立下奇功的賈逵與張玉,以及陣亡的孫節外,還有劉几(1008-1088)、和斌、楊遂、石全彬(?-1070)、祝貴及李定(按:《宋史·李浩傳》稱李定之子李浩有份從征儂智高,相信李定父子均在陣中)。參見本書的另一篇文章〈狄青(1008-1057)麾下兩虎將——張玉(?-1075)與賈逵(1010-1078)〉,頁345-350;《全宋文》(1993年10月),第三十一冊,卷一千三百五十九〈滕元發·孫威敏征南錄〉,頁667-671;陳均(1174-1244):《九朝編年備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四,葉38下至41上。
56、 歸仁铺一役之經過,可參閱本書的另一篇文章〈狄青(1008-1057)麾下兩虎將——張玉(?-1075)與賈逵(1010-1078)〉,頁345-350。
57、 参見《長編》,卷一百七十四,頁4205,4208-4209,4214;本書的另一篇文章〈狄青(1008-1057)麾下兩虎将——張玉(?-1075)與賈逵(1010-1078)〉,頁349-350。考平定儂智高後出任廣西鈐轄的,一說是供備庫副使李樞(993-1071)。總之並非楊文廣。参見《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三〈碑銘·皇城使李公神道碑〉,頁807-812。又余嘉锡據《元豐九域志》考出德順軍在慶曆三年,以渭州隴竿城置。参見《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頁9308;〈考信錄〉,頁486。關於德順軍之建置,參見註釋63。
58、 《史事考》,頁200-201。
59、 考蕭注在皇祐五年二月以禮寶副使、廣南西路安無都監權知昌州,至和元年五月以獲儂智高母之功,遷西上閤門副使,仍知邕州;到至和二年四月,蕭以使人至大理殺儂智高有功再遷引進副使,仍留任邕州。到嘉祐三年(1058)四月,他遷為西上閤門使,仍留任知邕州。直至嘉祐五年(1060)十一月,以交趾與甲峒蠻入寇兵敗,降職為進副使徙為荊南鈐轄,才離開邕州。参見《長編》,卷一百七十四,頁4199-4200;卷一百七十六,頁4255;卷一百八十,頁4355;卷一百八十七,頁4508;卷一百八十九,頁4550;卷一百九十二,頁4634-4647;另見《武溪集》,卷二十〈故蕭府君墓誌銘〉,葉11上至12上。
60、 據沈遘墓誌銘所記,沈遘於慶曆八年,年二十時登第。據《會要》記載,他在皇祐五年擢集賢校理。王安石稱沈氏任校理八年後,即嘉祐六年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據《長編》,沈遘在嘉祐四年八月使遼時仍任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尚未知制盖。《長编》未載沈遘知制誥年月,卻載王安石於嘉祐六年六月戊寅(二十七)以同修起居注召知制誥。據《皇宋十朝綱要》,沈遘任知制盖,晚於祖無擇,而在王安石之前。考祖無擇在嘉祐六年正月前已知制誥,則沈遘應在這年初擢為知制誥。另外,當楊文廣族姪楊畋在嘉祐六年初陞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時,正是由沈遘撰寫制文,那正可證明沈遘為知制誥乃在嘉祐六年。另外,《全宋文》所收〈越帥沈公生祠堂記〉一文,即記沈遘在嘉祐六年十二月以右正言、知制誥出知越州(今浙江绍興市),則清楚說明沈遘寫這道制文,不能晚於六年十二月。參見《臨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三〈墓誌·沈内翰墓誌銘〉,頁961-962;《會要》,〈選舉三十一之三十三〉;《長編》卷一百九十,頁4587;卷一百九十三,頁4662,4677;卷一百九十四,頁4711;李真(1161-1238):《皇宋十朝綱要》,收入趙鐵寒(主編):《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卷四,葉6上;《西溪集》,卷六〈吏部員外郎知制盖兼侍讀楊畋可依前官兼侍讀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葉25上下;《宋史》,卷三百,頁9965;《全宋文》,第二十一册,卷八百九十一〈沈绅·越帥沈公生祠堂記(嘉祐七年八月)〉,頁281-282。
61、 《長编》,卷一百七十三,頁4177。考宋定在調知宜州前的官職是廣南西路鈐、皇城使、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刺史,位在楊文廣之上。他繼任宜州後,陞為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團練使廣南西路安撫都監,仍在楊文廣之上。沈遘在撰寫制文時,一樣稱他「材武忠勇」。参見《西溪集》,卷六〈廣南西路鈐轄皇城使忠州刺史宋定可果州團練使舊官充廣南西路安撫都監兼知宜州制〉,葉26下至27上。
62、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頁9308。關於楊文廣知德順軍的任期,本來按照常例,三年一任,楊應該在至和二年底任滿。考有鐵面御史之稱的趙抃(1008-1084)就曾在至和二年十月至十二月,五度上表彈劾另一位樞密使王德用(980-1058),指他的兒子王咸融收受西京左藏庫副使馬慶長賄賂為馬慶長求得知德順軍的優差,且在馬未赴任前,又授他接伴副使任務。趙抃的彈奏説明宋廷在至和二年底確委出馬慶長接替楊文廣知德順軍,不過馬未上任即為趙所嚴劾。考《長編》及《宋史》未載趙抃上言之結果;不過在趙抃連番彈奏下,宋廷不可能派有行賄之嫌的馬慶長接替楊文廣,相信楊文廣也因此得以留任,直至徙知宜州。參見趙抃:《清献集》,文淵閣《四庫至書》本,卷七〈論王德用男納馬慶長馬状·至和二年十月十六日〉,葉31下至32上;〈乞替馬慶長接伴副使速正典刑状·十月十七日〉,葉33下至34上;〈乞罷免王德用状,十一月十一日〉,葉35上下;卷八〈乞勘鞫王咸融納馬慶長状·十二月十六日〉,葉4上下;〈論王德用乞正其罪劄子〉,葉4下至5上。
63、 《長編》,卷一百三十九,頁3339-3343。
64、 《會要》,〈兵二十二之六〉;《長編》,卷一百七十八,頁4317;卷一百九十二,頁4641-4644。
65、 陳守忠:〈隴山左右宋代城寨遺址調查〉,頁218。
66、 《全宋文》(1992年6月),第二十二冊,卷九百三十七〈祖無擇四·贈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任公墓誌銘〉,頁319-325;《長編》,卷一百七十六,頁4259;卷一百八十,頁4356;卷一百八十四,頁4456。
67、 《長编》,卷一百八十三,頁4435;卷一百八十五,頁4473-4474。關於狄青被逼走而致憤死之事,可参閱本書的另一篇文章〈狄青(1008一1057)麾下兩虎將——張玉(?-1075)與賈逵(1010-1078)〉,頁352-354。
68、 《長编》,卷一百八十七,頁4512,4519;卷一百九十一,頁4614;卷一百九十二,頁4648;卷一百九十四,頁4712;卷一百九十五,頁4720;《宋史》,卷三百〈楊畋傳),頁9964-9966;《武溪集》,卷十五〈免充集賢學士表〉,葉15下至16下。
69、 參見注釋61。
70、 《長編》,卷一百九十,頁4593;卷一百九十二,頁4634,4636,4640,4647,4648;卷一百九十三,頁4664-4665;《清獻集》,卷九〈乞勘劾蕭注状〉,葉9上下。按蕭注在嘉祐六年四月再被李師中嚴劾,稱他「治邕八年,有峒兵十萬,不能撫而用之,乃入溪洞貿易,掊斂以失眾心,卒致将卒覆敗」,而有鐵面御史之稱的趙抃又大力支持李師中之奏,上表痛劾蕭注,宋廷因此再責他為泰州團練副使。又按余靖平亂的經過,李師中曾為文以誌。參見張鳴鳳(?-1589後)(编):《桂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平交趾記·李師中撰),葉10上至11下。
71、 《長編》,卷一百九十二,頁4653,4654;卷一百九十三,頁4668。
72、 《長編》,卷一百九十七,頁4768;《西溪集》,卷五,葉6下。
73、 《史事靠》,頁202。按柳州一度隸宜州,楊文廣曾知宜州,他巡部到支郡的柳州而留下遺跡也有一點可能。
74、 《長編》,卷一百九十六,頁4761。
75、 按左藏庫使為諸司正使第六階,在皇城使、宫苑使、左騏骥使、右騏驥使、內藏庫使之下,是前列的諸司使臣,照例領遙郡刺史,疑《宋史》漏載楊文廣所領之刺史職。至於带御器械是加給資深武臣之近職,根據宋制,帶御器械的武臣,是須帶總管才除授,為將來真除副都總管資基,而檐任副都總管,就有資格陞任管軍。又宜州亦在廣南西路,在邕州東北。參見《長編》,卷一百九十八,頁4792-4794;卷二百三十五,頁5705;《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頁9308。
76、 《長編》,卷二百零一,頁4883-4884;卷二百零二,頁4895。按余靖亦於是年七月卒。
77、 參見本書的另一篇文章〈狄青(1008-1057)麾下兩虎将——張玉(?-1075)與賈逵(1010-1078)〉,頁357-360。按竇舜卿自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逕陞馬軍都虞候,而石遇則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逕陞步軍都虞候,補趙滋之缺。參見《宋史》,卷三百四十九〈郝質傳〉,頁11050;〈竇舜卿傳〉,頁11052-11053;王安石(撰),唐武(標點):《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卷十三〈竇舜卿可四廂都指揮使〉、〈石遇四廂都指揮使〉,頁139:《長編》,卷二百零三,頁4911。
78、 《長編》,卷二百零三,頁4911。
79、 参見《長編》,卷二百零二,頁4895;卷二百零五,頁4969;《會要》,〈儀制十一之十八〉。考《會要》在石遇赠官條原抄作「三月三月」,校對者改三月為三年:考楊遂於治平二年六月耀步候,至三年五月除馬候;石遇不可能在治平三年三月前任步候;筆者疑抄寫者漏抄石遇卒年,而將卒月重抄兩次。校者誤以三月為三年,而不審治平三年初任步候的是楊遂。筆者以為石遇卒於二年初。又楊遂在英宗登位前,曾以新城巡檢救過濮王宫火,故英宗對他有好印象。另外楊遂又得到文彥博極力的推薦。關於是年三衙管軍之調動陞遷情况,可參見馬光祖(?-1269後)(編),周應谷(?-1260後)(纂):《景定建康志》,收入《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二冊,卷二十六〈侍篇馬軍司题名記〉,葉32下至33上(以下簡稱〈題名記〉);《潞公文集》,卷三十九〈舉楊遂〉,葉4下至5上。
80、 筆者懷疑英宗擢用楊遂與楊文廣時,曾想到真宗朝「二楊」楊延昭與楊嗣(934-1014)同時被擢用的佳話,而有意識的同時擢用二人,以樹立新一代的「二楊」風範。参見《宋史》,卷二百七十二〈楊延昭傳〉,頁9307-9308;卷三百四十九〈盧政傳〉,頁11055-11056;〈楊遂傳〉,頁11062;劉摯:《忠肅集》,文渭閣《四庫全書》本,卷十二〈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陶公墓誌銘〉,葉1上至2下。
81、 蘇轍(撰),曾棗荘、馬德富(校點):《樂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四十五〈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元祐五年十月〉,頁1001-1002
82、 楊惲是司馬遷(前145-前86)外孫,漢昭帝(前87-前73在位)時丞相楊敞(?-前73)的兒子,《漢書》有傳。鄭獬用楊憚在漢宣帝時任中郎將的事,比附楊文廣領禁衞,又用楊惲罷山郎之弊政,以嚴法整頓郎官請謁貨賂之弊端的故事,期許楊文廣能整頓禁軍軍紀。不過,楊惲雖以告發霍氏謀叛受宣帝所用,後來卻以得罪被革職,再被指怨望而為宣帝所殺。考楊惲任官中郎將,雖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另對族人亦廣加照顧,有輕財好義之名;但他自矜其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私,結果給仇家尋事攻倒,得罪身誅。鄭獬用楊惲來喻楊文廣,下場就太不吉祥。參見註釋53及《耶溪集》,卷二〈四廂指揮使制一〉,葉14下至15上;班固(32-92);《漢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62年),卷六十六〈楊敞、楊惲傳〉,頁2888-2898。
83、 強至:《祠部集》,文裫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十八〈回楊四廂書〉,葉8上。按從仁宗至神宗三朝,姓楊而任四廂都指揮使的,只有楊文廣一人,故可斷定強至所覆的就是楊文廣。
84、 考韓琦罷相出守永興軍,及徙镇相州(今河南安陽市)、大名府,強至都一直追隨韓琦,為他經辦大小書奏的文字機宜工作,通四方之好。参見《曾鞏集》,卷十二〈《強幾聖文集》序〉,頁202-203。
85、 按張方平此奏未明確註明寫於何年,但行南郊大赦,從仁宗中期開始至英宗朝,只舉行過三次,分别是慶曆七年十一月、皇祐五年十一月和英宗治平二年十一月。按張方平在慶曆七年底任權三司使、翰林學士;在皇祐五年十一月則任龍圖閣學士判太常寺;在英宗治平元年十二月至三年正月前,則以龍圖閣學士知徐州。换句話說,他上奏論南郊赦書,當在慶曆七年或皇祐五年。若以張方平之職務論,筆者認為他在皇祐五年判太常寺時上此奏較為合理可信。参見《宋史》,卷十二〈仁宗紀四〉,頁235;卷十三〈英宗紀),頁258;《長编》,卷一百六十,頁3876;卷一百六十一,頁3881-3882,3890;卷一百七十五,頁4235-4238;卷二百零七,頁5022;張方平(撰),鄭涵(點校):《張方平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二十〈郊禋赦書事目·錄用近代有功邊將子孫〉,頁284。
86、 按張方平推薦可任管軍的有濟州(今山東巨野縣南)防禦使向傳範(?-1074)(向傳範是神宗向皇后[1046-1101]之伯祖)、沂州(今山東臨沂市)防禦使劉永年(?-1084)(按:劉永年是章獻劉太后[1023-1033]攝政的族孫)和狄青另一員大將東上閤門使、嘉州團練使劉几。参見《張方平集》,卷二十四〈論除兵官事奏〉,頁372-373;《長編》,卷二百零三,頁4927;卷二百零五,頁4965;《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劉永年傳〉,頁13551-13552;卷四百六十四〈向傳範傳〉,頁13579-13580。
87、 《長編》,卷二百零八,頁5051,5062-5063;〈题名記〉,葉32下至33上;《宋史》,卷三百四十九,頁11056。考鄭獬另一道〈四廂指揮使制〉相信是為張玉晉陞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而寫的,制文中稱受文人「沉毅而斷,通於兵制,攝弓撫劍,以障河隴之戍,蓋有能名。俾陞刺部,入掌羽衞,擁虎戟以護建章」,完全符合張玉的身份和守西邊之戰功。参見《鄖溪集》,卷二〈四廂指揮使制二首〉,葉15上。考〈題名記〉稱竇舜卿在治平三年「二月」自馬候改差,而載楊遂在三年五月除馬候;筆者疑「二月」當作「五月」。又《宋史》未載楊文廣遷捧日天武四廂,但後來楊得遷步軍都虞候,按理應經過捧日天武四廂一級,疑《宋史》失載。
88、 《長编》,卷二百零九,頁5073;《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頁9308。
89、 考楊文廣在熙寧元年七月已任秦鳳副都總管,筆者疑他早在一年前已任此職參見《長編》,卷二百零九,頁5088;《會要》,〈兵二十八之四〉。
90、 楊仲良(?-1184後):《資治鑑長编紀事本末》,收入趙鐵寒(主編):《宋史資料萃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11月),第二輯,卷八十三〈种諤城綏州〉,葉1上至7上:《宋史》,卷十四,頁266-267;《九朝編年備要》,卷十七,葉49下至51下。
91、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八,葉4上下;《宋史》,卷三百三十一〈馬仲甫傳〉,頁10647。
92、 《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八十三〈韓琦築甘谷城〉,葉14下至15下(按:今本《長編》缺熙寧元年至三年二月;《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可稍補其缺;考李燾在這一條下註明楊文廣乃楊業之孫,這是《長編》首次提到楊文廣之名);《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頁9308;《會要》,〈禮六十二之四十二〉、〈兵二十八之四〉、〈方域二十之七〉;《全宋文》(1994年4月),第四十冊卷一千七百十七〈李清臣九·韓忠獻公琦行状〉,頁48-49。關於擦珠谷、噴珠之名,實為一地,按〈韓琦行状〉則以擦珠谷為「噴洙堡」,據陳守忠的實地調查,該處常年有流水,但流量很少。關於楊文廣築城之事,余嘉錫引用了《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的有關記載,參照《宋史》楊文廣及馬仲甫兩傳,而考得其實;常征卻未引用《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這則重要記載,而曲解《宋史·楊文廣傳》的有關記載,望文生義地說楊文廣「詐言篳篥堡有泉噴珠,鼓誘士卒一日夜急行一百八十里」;另外,他又解不通「先人有奪人之氣」一句。另外,他又胡亂説韓琦論築城篳篥一番話出自《長編》卷二百六十,其實韓琦這一番話出自《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上引的一條。参見陳守忠:〈隴山左右宋代城寨遺址調查〉,頁214;〈考信錄〉,頁459-461;《史事考》頁205-206。
93、 關於甘谷城和通渭寨的地理位置,陳守忠曾繪圖清楚解說,按甘谷城今日所在為楊家城子,相信與楊家將傳説有關。参見陳守忠:《河隴史地考迹》,插圖五〈通渭縣境古城遺址圖〉;另頁同書,214-216。又據《長編》所載,在熙寧初年,擔任新築成的知甘谷城的宋守臣是張就(?-1087),他曾有開邊拓土的計議。参見《長編》,卷二百五十五,頁6231。
94、 據蘇頌所記,在熙寧元年秋(九月以後),龍圖閣直學士孫永(?-1087)充秦鳳經略安撫使知秦州,接替馬仲甫。據蘇頌説,熙寧三年前孫永的副帥是劉昌祚(1027-1094),不過,劉當時官職不高,只是秦鳳兵馬都監,並未擔任秦鳳副都總管,據《長編》,接任秦鳳副都總管的是殿前都虞候竇舜卿。考孫永在秦州做得很不合神宗之心意,給神宗當眾説他「前帥秦極不善」,而在熙寧三年四月降知和州(今安徽和縣),宋廷即以李師中接任秦帥知秦州,但到是年六月,李師中徙永興軍,就權宜地由竇舜卿以副都總管兼知秦州。竇舜卿在熙寧八年,因與秦帥韓縝不協,徙為環慶副都總管。考《宋史·楊文廣傳》的斷句,以楊文廣先知涇州,再知鎮戎軍。余嘉錫則以楊文廣不過只知涇州的鎮戎軍。按楊文廣在熙寧三年自鎮戎軍權知鄜州,他不可能在兩年間連知涇州、鎮戎軍和鄜州,余氏所斷合理。又從熙寧元年開始,熟知邊事的天章閣待制蔡挺長期擔任涇原經略安撫使,而張玉就一直做他的副手,任涇原副都總管,到熙寧四年正月再獲留任。按楊文廣自秦鳳副都總管調知涇州鎮戎軍,本來應兼本路副都總管,沒有理由位在張玉之下。相信是張玉調職的問題談不攏,故宋廷只好將楊文廣再調往鄜延。至於鄜延副都總管是在熙寧四年正月前直是劉永年,他在四年正月任滿後獲留任。楊文廣調知鄜州時,雖然官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在劉永年之上,但不知何故,宋廷仍由劉任本路副都總管。至於環慶副都總管,在熙寧三年八月前由楊遂擔任,八月後因兵敗去職,改由竇舜卿自秦鳳路調任。至於秦鳳副都總管之人選不詳,不知是否由楊文廣復任,待考。又鄜延帥從熙寧初年,一直由宣徽南院事判延州郭逵出任。參見《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頁9308;《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三〈碑銘·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孫公神道碑銘〉,頁798-801;《張方平集》,卷四十〈贈工部尚書蔡公墓誌銘〉,頁751-752;《長編》,卷二百十,頁5094;卷二百十二,頁5144,5160;卷二百十四,頁5193,5220;卷二百十五,頁5236;卷二百十八,頁5302;卷二百十九,頁5331;卷二百二十一,頁5379;百四十,頁5830;卷二百五十五,頁6231;〈考信錄〉,頁461。
95、 李復圭因兵敗去職,宋廷以王廣淵代為環慶經略使,竇舜卿自秦鳳副都總管改環慶,代替兵敗的楊遂。韓絳所起用之宋將,包括种諤、种診兄弟,韓且起用种諤為權鄜延鈐轄兼知青澗城(今陝西青澗縣城)。郭逵反對韓絳用种諤,故韓絳調走郭逵。見《長編》,卷二百十四,頁5218-5220;卷二百十五,頁5236,5241;卷二百十六,頁254;卷二百十七,頁5277,5283;卷二百十八,頁5305-5304。
96、 《長編》,卷二百二十六,頁5551-5554。
97、 《長編》,卷二百四十,頁5829;卷二百四十七,頁6023;〈題名記〉,葉33上;《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頁9308。按楊文廣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的職位,就由張玉替補。
98、 《長編》,卷二百四十,頁5832。
99、 《長編》,卷二百四十五,頁5972。
100、 《長編》,卷二百四十七,頁6022-6023,6030。
101、 《長編》,卷二百四十八,頁6046。
102、 《長編》,卷二百四十九。頁6067;卷二百五十,頁6082-6084;6087-6089。
103、 《史事考》,頁207;《長編》,卷二百五十一,頁6121-6123,6132-6133,6135-6137;卷二百五十二,頁6168-6170;卷二百五十三,頁6201-6202;卷二百六十二,頁6386-6397。按常征稱沈括、韓琦等反對對遼讓步,並説他們與楊文廣立場相同,其實常征弄不清楚沈括等主張對遼強硬,乃在楊文廣死後。而且韓琦還曾不點名批評楊文廣進平幽燕議為生事。關於韓琦上奏言遼事的年月,李燾已辨明不在熙寧七年十月,乃在熙寧八年三月。又宋遼劃地交涉的最近期研究,可參閱藍克利(著),顏良(譯):〈政治與地理論辯——一零七五年的宋遼邊界談判〉,載《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182-197。
104、 余嘉錫只將楊文廣獻策,視為秉承楊家的忠義精神,説:「(楊)文廣亦獻策取幽燕,雖功皆不成,而祖孫三世,敵愾同仇。以忠勇傳家,就将帥中所稀有。由是楊家將之名,遂為人所盛稱,可謂豹死留皮,歿而不朽者斯歟?」參見〈考信錄〉,頁461。
105、 據南宋人王銍所撰之《默記》披露,神宗曾對滕甫親口言及太宗在高梁河(在今北京市内)之役為遼軍所射傷,太宗之箭疾歲歲必發,十八年後還因箭傷而死。滕甫後對王銍之父説,神宗對此不共戴天之仇,一直耿耿於懷,而對每年還輸金帛於仇敵,尤覺恥辱,常思報復。按滕甫既對王銍之父言及此事,則他對祖父死於遼手的屬下楊文廣言及神宗這件心事,實在順理成章。參見何冠環:〈宋太宗箭疾新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二十卷(1989),頁33-57。
106、 《長編》,卷二百五十八,頁6288;《會要》,〈儀制十一之十八〉。
107、 《長編》,卷二百六十二,頁6390。
108、 據李燾引《神宗正史契丹外傳》的記載,在熙寧八年三月遼使蕭禧再來議地時,神宗向臣下明顯地表露出想對遼強硬,甚至不惜一戰的態度。他且説:「契丹亦何足畏,但誰辦得用兵?而文彦博應召上言時,亦説:「竊料聖意重於舉動,發言盈庭,容有異論;或日先發制人,意在輕動;或日乘其未備,襲取幽燕,事不審處,恐將噬臍,非王師萬全之舉也。」可見當時神宗確想過對遼用兵。參見《長编》,卷二百六十二,頁6379,6385,6395。
109、 考王安石在同年閏四月,當遼使離去後向神宗報告,奏稱傳聞遼國的確畏懼宋出兵爭地。另外,神宗在同月即下韶知定州薛向,要他具奏定州可供作戰的民兵數目。遼方的反應是在是年五月向定州路所屬的廣信軍(今河北徐水縣西遂城)新河口鋪及安肅軍(今河北徐水縣)發動試探性的攻擊。就當時的情況而論,遼國的决策者不能不認真考慮宋方的反應;一旦宋廷的鷹派佔上風,可能真會採納楊文廣之議,乘機出兵攻遼。事實上宋遼開戰,雙方都沒有必勝的把握,遼國不過虚張聲勢,希求宋方在劃界事上向遼妥協屈服,倘宋朝真的出兵來爭,實非遼人所願。宋方在談判時,故意漏出朝中有人主張不惜一戰的消息,以迷惑遼國的諜者,實在並不失算。参見《長编》,卷二百六十三,頁6424,6452;卷二百六十四,頁6462。
110、 歐陽修便將楊畋視為楊業後人,並稱從楊畋處,得到罕傳的《遁甲立成旁通曆》一書,而追慕「繼業善用兵,以見昔時名将皆精於所學,非止一夫之勇也」。按此書不傳,内容不詳;惟據仁宗景祐年間宋廷所編的同類書《景祐遁甲符應經》的序言所云:「稽夫遁甲之書,出於河圖。黄帝之世,命風后創名,始立陰陽二遁,共一千八十局。迨太公約七十二局,留侯佐漢,議十八局。推曆授時,超神接氣,布門耀德,觀兵取驗,以明勝負,罔不抽吉。」楊畋從楊業得來的這部遁甲書,相信正是楊業當年用兵時所據以测定天時日曆的行軍冊。楊畋雖被視為楊門子弟,也被歐陽修等許為通兵法,能將兵平亂之人;但他以進士出身,長期擔任文官,雖一度轉為武資,然最後仍復為文官。在部份宋人眼中,他近於儒將;而不似楊文廣那樣道道地地的武将。
是故太原楊氏的楊重勳一房,嚴格來說,其將家身份,到楊琪一代其實亦已終結。據目前可見之資料,楊畋有一妹(1036-1095),在楊安排下,嫁太子中舍張景儒(1018-1070)為繼室,生男四人及女四人。楊畋似乎沒有其他兄弟,據蘇轍所記,楊畋死時,僅有一年方二歲的兒子楊祖仁,楊祖仁在紹聖二年(1095)時官右宣義郎、簽書崇信軍(即隨州,今湖北隨州市)節度判官廳公事。楊祖仁的姑姐卒時,他即為她篆墓蓋。楊祖仁在政和三年(1113)官「大夫」,他的後人亦暫不可考。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宋人如司馬光(1019-1086)雖亦點出楊畋為楊業族人;不過,卻不認為楊畋有儒將才具,認定楊畋只是迂闊無威的一名儒者,故當楊畋受命平儂智高時,即不為諸將所服,而為宋廷所罷。另為楊畋妹撰寫墓誌銘的左朝奉大夫張峋,雖稱「楊氏世將家」,但說楊畋「獨以文章經術為仁宗皇帝識,擢任龍圖閣直學士,當時稱為名臣」。可見宋人已不以楊畋為世将。参見《全宋文》,第十四冊,卷五百七十九〈陸經·朝奉郎守太子中舍騎都尉賜緋魚袋張君墓誌銘〉,頁218-219;(1992年4月),第二十三册,卷九百八十四〈宋仁宗四十五·《景祐循甲符應經》序〉·頁393:(1994年3月) ,第三十九冊,卷一千七百零四〈張峋·宋故壽陽縣君楊夫人墓志銘〉,頁556-557;《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五〈書《遁甲立成旁通曆》後〉,頁2574-2575;《攀城集》,卷十八〈楊樂道龍圖哀辞並序〉,頁424-425;司馬光(撰),鄧廣銘(1907-1998)、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9年) ,卷十三,頁259。
111、 按常征將楊存中歸入楊家將一員,只根據楊存中之四世祖名楊信,而断言此楊信即楊業之父,其實宋代名楊信就有多人,除了常氏提到的幾個楊信外,他沒提到的,至少還有太祖(960-976在位)、太宗(976-977在位)時官殿前都指揮使的宿將楊信(?-98)。假若楊存中真是楊業後人,為他作墓誌銘的人沒有理由不大大吹嘘一番。至於常征所根據的《代縣原平楊氏族譜》,其真實性和準確性猶有待考訂,不能作為有力的旁證。關於播州楊氏源出所謂楊延昭幼子楊充廣,上文已辨其不確。參見《史事考》,頁57-71,209-238,239-249。
112、 《曾鞏集》,卷十二,頁202-203。
113、 考狄青及其七員官至管軍的部將,除了楊文廣和李浩外,都是起於行伍,第一代為將。狄青的雨個兒子狄諮(?-1100)與狄詠(?-1097後),雖然功業與乃父相去甚遠,但以一般人的標準,他們都算得出息,都勉能維持家聲。狄諮官至引進使、嘉州團練使;狄詠亦官至引進使,且數有戰功。宣仁高太后(1032-1093)還一度想纳狄諮之女為哲宗后。不過,狄家第三代便不顯。和斌的兒子和詵(1058-1124)尚算能繼承父業。和詵在徽宗(1100-1125在位)朝號為守邊能將,長期扼守雄州(今河北雄縣),官至相州觀察使。他又以製射遠的強弓鳳凰弓聞名,不過,卻以首倡取幽燕而受非議。與狄家一樣,和氏第三代亦不顯。李浩是第二代為將,但他的後代亦無能者。至於賈逵、張玉、盧政及楊遂等,功業均及身而止,他們的下一代均無顯者。參見《宋史》,卷二百九十,頁9721;卷三百五十〈李浩傳〉,頁11078-11079;〈和斌傳、和就傳〉,頁11079-11081;《長编》,卷四百五十七,頁10945-10948;卷四百六十,頁11002。
1999年12月23日初稿
補記:
筆者在今年年中偶翻台灣宋史座談會編的《宋史研究集》第九輯(1977年5月),才發覺漏引李安的〈「楊家將」的事蹟〉(頁589-601)一文。該文述楊文廣事蹟,曾引用康熙四十九年(1710)修、乾隆五年(1740)補修的《保德州志》,以及乾隆四十八年(1783)修的《府谷縣志》有關記載,稱楊文廣妻姓慕容氏,為保「州南慕塔村人,雄勇善戰」。李氏並進一步推論小锐戲劇所云楊宗保妻穆桂英,可能是慕容氏的訛誤(頁599-600)。考楊文廣妻的姓氏籍里,現時可見的宋人文獻並無著錄,不知上述兩種清人方志所云「見舊志」何所根據。筆者以為此說目前只能存疑。又筆者於今年8月底,因路過西安,有緣拜謁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李裕民教授。筆者曾向李教授請教,李教授亦認為明清人所編之方志中有關楊家將的記載只能聊備一說,不足以作為考證史實的重要佐證。
2000年10月9日
(原載《嶺南學報》新第二期 [2000年],頁97-129。)
再增補後記:
筆者在去年(2001)中,偶閱葛劍雄教授所撰《悠悠長水——譚其骧前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33-137),始知譚其骧教授(1911-1992)早在1941年1月流寓遵義時所撰之〈播州楊保考〉一文,已指出宋濂所謂播州楊氏出於北宋太原楊氏之謬,並指出楊文廣或「楊充廣」與楊貴遷實不相干。據葛劍雄所記,其師這一篇考證在是年10月印成,後來發表於浙江大學的《史地雜志》第1卷第4期。當時只印數百冊,雖引起當地人士注意,但該文一直流傳不廣。是故常征在1980年出版其《楊家將史事考》時,多半看不到譚氏此文。按譚氏直至1981年底才應貴州民族學院之請,將此文重新校勘發表,譚氏並據《文物》1974年第1期所載貴州博物館所撰〈遵義高坪播州土司楊文等四座墓葬發掘記〉附錄的〈楊文神道碑〉,寫成〈播州楊保考後記〉,一併在1982年的《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刊載。此二文後均收入譚氏學術論文集《長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61-296)。
筆者數月前趁往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使用新装置的電子版《四庫全書》的全文檢索功能,查閱另一研究課題之便,又索閱多種清人編修的方志,查看明清方志中有關楊文廣及其家人的記载,除了《山西通志》卷一百五十七〈列女九·保德州》條下所記楊文廣妻子慕容氏與上面「補記」所引的幾種清人方志所載相同外,筆者從《大清一統志》卷三百七十三〈廣南府〉條,知後人曾為楊文廣立祠於廣南府(在雲南境)府治西。另外有趣的是,不知是否受小説的影響,在《湖廣通志》卷十二〈铜鑼灘〉條、卷七十九〈楊氏城〉條,《陝西通志》卷十六〈宜娘子關〉條及《廣西通志》卷十三〈穿岩山〉條,均記載上述四處地方留有傳説中的楊文廣之妹「宜娘子」的遺跡。此外,在《陝西通志》卷十七〈僧道關〉條及《廣東通志》卷五十三〈楊文廣壩〉條,亦記載有傳聞中的楊文廣多處遺蹟。上面所舉,只是其中一部份例子,其他清代方志類似的記載尚有許多。這裹不一一著錄。正如上面所述,這些方志所記關於楊文廣及其家人之事睛,只能聊備一説,是故筆者今次修訂本文,只增補了一些初稿漏引之資料,以及補入本文涉及的地名其今日所在。對於那些有待商榷的方志資料,仍不擬採用。
2002年10月19日於香港理工大學
本文收錄於何冠環教授的著作
《北宋武將研究》
(香港:中華書局,2008年)
頁385-436。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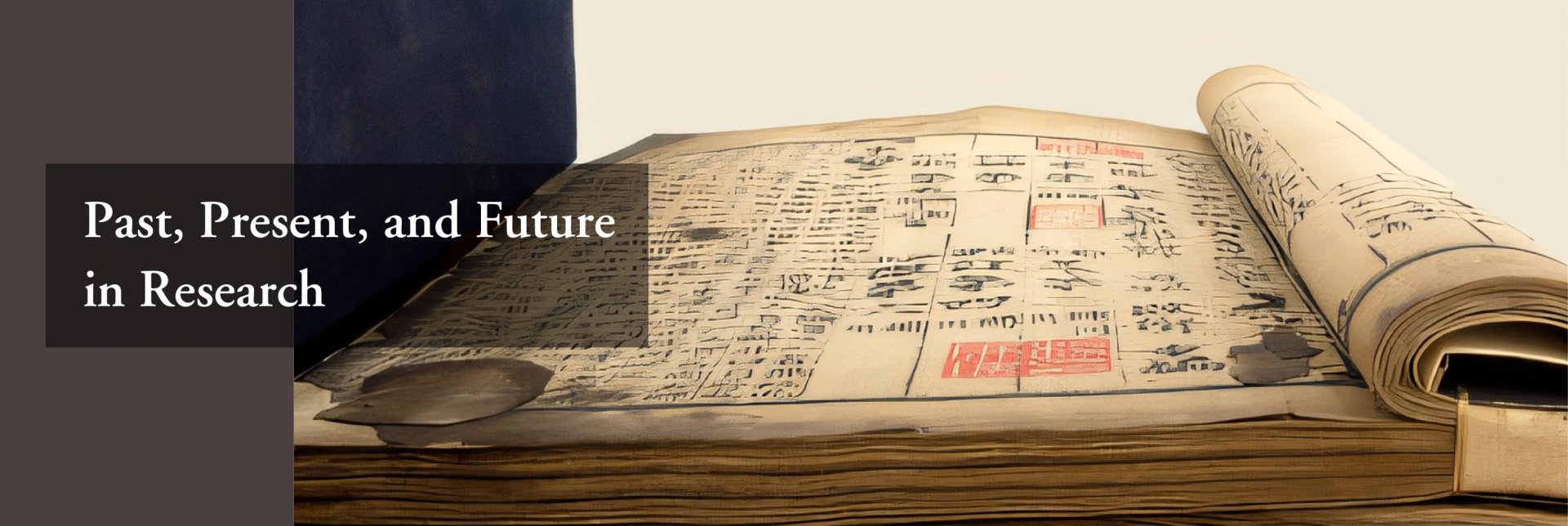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