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序志》篇「二夢」寓意補說
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陳述撰著動因時,提及其本人幼童時代和年過而立所出現的兩個夢境。學界對於這兩個夢象內涵之理解,頗多紛歧,有必要擇取新思路,結合若干新材料,補充說明如下三點:其一,從章法結構角度而言,根據相關文句之間的脈理、邏輯關係,可知劉勰「七齡」之夢、「齒在踰立」之夢的寓意,分別指卓越的天賦文才、立志文章寫作之宏偉抱負。其二,結合古來多以「七齡」智術超倫為「神童」代稱此一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歷史文化背景,可知劉勰「七齡」而夢「彩雲若錦」,意在強調自身文才之優異。其三,劉勰心目中的孔子形象,首先並非作為道德楷模,而是文章聖手——雅麗之文的傑出實踐者,「貴文」思想的宣導者。「徵聖立言,文其庶矣」,足以涵括劉勰「夢隨仲尼而南行」之根本宗旨。
關鍵詞:劉勰;夢象寓意;天賦才情;孔子;文章聖手
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篇陳述自己「搦筆和墨,乃始論文」之動因過程中,曾提及他幼童時代和「齒在踰立」所出現的兩個夢境。這兩個夢,對研究劉勰生平思想、《文心雕龍》成書時間以及文論主張,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即以清人劉毓崧〈書文心雕龍後〉一文為基礎,結合劉勰「齒在踰立」之夢,以為「假定彥和自探研釋典以至校訂經藏撰成《三藏記》等書,費時十年,至齊明帝建武三四年,諸功已畢,乃感夢而撰《文心雕龍》,時約三十三四歲,正與〈序志〉篇『齒在踰立』之文合」2。牟世金《劉勰年譜匯考》則進一步關注劉勰「七齡」幼童之夢,以為劉勰所述「夢彩雲若錦」云云,「乃吉祥之兆,所謂五采祥雲是也;劉勰又能攀而採之,則吉兆之中,又示劉勰少有奇志,當時正壯心滿懷也。由是可知,其父必卒於本年之後。若為新喪,則其悲猶在,不可能夜有此夢;若為早逝,則家境漸窘,更難生此吉慶心情。」3針對牟說,賈岸〈〈序志〉說夢因緣探賾——劉勰生年辨〉以為劉勰〈序志〉所言「七齡」之夢彩雲,「用《易經》解析實乃凶兆,正是劉尚戰死的那年(西元474年)」,凝結著劉勰因喪父而產生的「內心的悲慨、心靈的傷痕、幽微難明的複雜情懷」4。
在劉勰〈序志〉之夢與《文心雕龍》思想關係研究方面,周勳初〈劉勰的兩個夢〉一文堪稱力作。周文結合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說夢」之風氣、社會歷史政治背景以及受玄風影響而形成的「託夢示意的手法」特點等方面,以為「劉勰自言夢執丹漆之禮器而南行,表示他是一個儒家學派的信徒,追隨孔子之後,準備宣揚儒家教義於南土」,而「劉勰自言夢攀若錦之彩雲,目的可能也在暗示他從小與文學即若有宿緣」5。汪春泓〈夢隨仲尼而南行——論劉勰的「北人意識」〉則從「齊梁黃籍制度使南北人畛域分明」、「北南文化勢差與劉勰的經學自負感」、「〈宗經〉、〈徵聖〉和反對『多略漢篇,師範宋集』的對應關係,其本質即揚北抑南」等三個方面,以豐贍翔實之史料,說明「劉勰提倡〈宗經〉和〈徵聖〉,實質上就是以北方經學為旨歸,並且與其『北人意識』當有內在的關聯」,而「劉勰寫作《文心雕龍》,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其北人的自負」6。此後,又有余才林〈六朝夢得文才說透視〉,在梳理分析「六朝夢得文才故事」的基礎上,指出劉勰〈序志〉二夢「用傳統的故事形式曲折表達了關於文學起源的觀念,與〈原道〉中的文學起源論相表裡」,包括《文心雕龍》在內的「夢得文才」故事,意在「宣揚文才神授」,「反映了六朝以詩文為『文』的觀念,表現了六朝重文采的文學傾向」7。
以上不避辭費,撮要介紹了有關劉勰之夢研究的若干重要觀點8,意在說明:劉勰筆下描繪得如此真切的夢境,其深層內涵究竟如何,後人理解起來卻各有不同,且都不無一定道理;即使某些觀點相近,而分析角度也各有特點。當然,也存在解析同一種夢中意象而結論卻截然相反之情況。本文擬在既有相關研究基礎上,擇取一種新的思路,結合若干新的材料,對其中尚未引起足夠注意的三個問題,略作補說。
在〈序志〉篇中,劉勰如此描述其夢:「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采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9按照現代漢語標點及段落劃分辦法,「予生七齡」云云,是〈序志〉篇第二段的開始部分。這是有道理的。劉勰從自己七齡之夢說起,再引出以「隨仲尼而南行」為核心內容的「齒在踰立」之夢,為下文轉入說明自己為何要以「論文」方式「敷贊聖旨」,奠定了必要基礎。因此,從章法角度看,劉勰所述二夢,類似鋪墊,蓄積文勢,有助於引發後續之正題,具有明顯的「啟下」作用。劉勰〈章句〉篇有言:「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移之以評「予生七齡……」一節文字,有符焉爾。
當然,劉勰在「長懷序志」的篇章中自敘兩個夢象,其立意自不止於章法結構上的「啟下」之用。實際上,其「承上」之功能,也同樣清楚。只要我們將「予生七齡……」這一小節與此前的文字聯繫起來考察,即不難發現這一點。為便於直觀理解,試將相關文句順次臚列:
①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
②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製作而已。
③夫人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
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⑤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采之。
⑥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
從意義關聯性上說,①、③、⑤之間,都與「智術」有關;②、④、⑥三句,不離「製作」之事。具體而言,「予生七齡……」之前的文字,可以分為兩小節:第一小節為「夫宇宙緬邈……製作而已」(①、②兩句),第二小節為「夫人肖貌天地……不得已也」(③、④兩句)。這兩小節文字表述雖有不同,其中心點皆不離兩大問題:一是「智術」,二是「製作」。也就是說,第二小節其實是對第一小節的進一步申說與強化,所以,第二小節前半部分圍繞「智術」問題,以人類「肖貌天地,稟性五才」為依據,以「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感慨句式收束;後半部分則通過「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的鮮明對比,說明「君子處世,樹德建言」,乃不得已之事,同樣以具有強烈感歎意味的句式作結:「豈好辯哉,不得已也!」此處雖「樹德建言」二事並提,其重點乃在「建言」一端,也就是前半部分提出的「製作」之事業。
在以上兩小節文字之後,劉勰緊接著就說「予生七齡」如何,又說「齒在踰立」如何。從字面意義上講,似乎已經拋開前文提出的「智術」、「製作」兩大問題,所以容易引發質疑:「這段文字最易令人產生疑問:劉勰自敘著書旨趣時為什麼要突然插入這兩個夢?它與《文心雕龍》全書有什麼相干?」10儘管這兩個疑問已在一些探討劉勰二夢內涵的論文中得到了不同角度的解答,但筆者以為,還應當補充一點,即返回「予生七齡……」前的兩小節文字,照著前文「智術」、「製作」雙線並進的行文思路,可以大致確定緊接而下的二夢所包含的基本寓意:首先,「予生七齡」之「夢彩雲若錦」,其實是承接上文「智術」問題而來,突出的是劉勰本人幼年聰穎、稟賦卓越,具有天生之文才;其次,「齒在踰立」之夢,「隨仲尼而南行」,則意在表明自己如何傾心於孔夫子「熔鈞六經」之偉大事業,呼應上文所言「製作」問題。描述完第二個夢象之後,劉勰即情不自禁地讚歎說:「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其具體之所指,就是〈原道〉篇所說「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或如〈宗經〉篇所說「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
劉勰在〈章句〉篇中說:「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知音〉篇又說:「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由此看來,「披文以入情」之「文」,除了包括篇章構成的最基本元素——字,還包括「因字而生」之「句」,以及「積句而成」之「章」。因此,要領會、把握文章作者之「情」,除瞭解具體字詞的基本用法及涵義,還必須綜合考察句與句、章與章之間的關係。傳統訓詁之學,其實也很講究這些方面,在因形求義、因聲求義、詞例求義等基本方法之外,還注重根據具體情況,綜合運用「對文求義法」、「義理求義法」等。其中,「對文求義法」主要依據句內或句外行文結構上的對稱、互文關係,以考求詞義;「義理求義法」則指「利用詞語在具體上下文中意義之間的制約作用來考求詞義的方法」,包括「詞與詞之間的搭配、上下句子之間乃至上下段之間的意義關聯等」11。綜合這些意見及方法,我們從章法結構的角度,根據「予生七齡」云云與上下文句之間的脈理、邏輯關係,以為「七齡」之夢重在喻示劉勰本人卓越的天賦文才,「齒在踰立」之夢則體現了劉勰繼踵仲尼、立志「製作」之宏偉抱負。
如上所言,「七齡」之「夢彩雲若錦」,喻示了劉勰卓越之天賦文才。此一結論所由得出之基本依據,在於文本章法結構之內在關聯性,其根本宗旨,與學界既有之「暗示他從小與文學即若有宿緣」12、意在「宣揚文才神授」13等觀點大體相似。此外,另有論者以為劉勰「夢到自己竟然攀到如錦繡般美麗的彩雲上,這預示著他將成為優秀的文章作家,能寫出如錦繡般的文彩」14,更為具體地申述了劉勰文才智術的特點,即善為錦繡般美麗之文。如此闡釋是合理的。周勳初〈劉勰的兩個夢〉一文列舉《釋名·釋言語》、〈文賦〉、《世說新語》及《文心雕龍》等典籍「常用錦繡等物比喻文學」之例,已足以說明問題,茲不贅述。對於「夢彩雲若錦」的象徵意義,可作兩點補說。
第一,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例言》第五條曰:「《文心》為論文之書,更貴探求作意,究其微旨。」15但是,如果脫離了具體的上下文語境,所求得之「作意、微旨」或有離題萬里之虞。即以「彩雲」夢象而言,據「予生七齡,夢彩雲若錦」云云與上文所言「智術」、「稟性五才」之間的脈絡聯繫,此處「夢彩雲若錦」顯然只能在「天賦文才」的範圍內加以闡說,而不宜獨立引申開去,不顧上下文思理之聯繫,強解之為一般夢書所謂「吉祥之兆」或「凶兆」。又,自宋玉〈高唐賦〉言楚王夢巫山神女朝雲16,後人多以彩雲與道教神仙之思相勾連,如李白〈觀元丹丘坐巫山屏風〉:「昔遊三峽見巫山,見畫巫山宛相似……使人對此心緬邈,疑入高丘夢彩雲。」17柳宗元〈新植海石榴〉:「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月寒空階曙,幽夢彩雲生。」18而在一些與道教相關的典籍中,則直接喻示神仙世界,如梁陶弘景《真誥》卷十八:「泰和元年六月五日夕夢,忽聞天上有金石鐘鼓之音,仍仰看見彩雲如虹,氣狀爽爽,彌漫天上,從東直西趣,意中謂是女靈行,或呼為元君……」《太平廣記》卷三十一:(李玨)「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似有李玨字」,自謂「今洞府有名,我必仙人也」。雖然這些詩文均涉及彩雲之夢,且有學者以為劉勰家族或有信仰道教天師道之傳統19,《文心雕龍》亦接納道教思想之影響20,但皆不宜據此推斷劉勰〈序志〉所述彩雲之夢與上引諸夢寓意相通,原因是夢象雖同,而劉勰之夢彩雲,乃著意於文才智術,與致思神仙之夢判然有別。
其實,在《文心雕龍》中,除多處以「錦繡」之物比擬文采之美21,亦不乏以「雲彩」說「文飾」者,如〈原道〉「雲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時序〉「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至如〈神思〉「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以明「思理之致」;「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而表「萬塗競萌」之狀,亦直接與為文用心相關。這些與「雲霞」相關之意象,顯然也是理解劉勰「彩雲」之夢的重要「語境」。
第二,「予生七齡」之「七齡」,多被視作劉勰生平考證之一助,但其中所包含的最為基本之意蘊,似尚未引起足夠重視,惟周勳初先生提及一句:「劉勰自言七歲夢攀彩雲,目的在於說明入學前夕即與文學結緣,因為古人每於八歲時入小學,劉氏的情況諒亦如此。」22如若繼續引申一步,則可見劉勰自謂「七齡」而「夢彩雲若錦」,流露的正是年幼聰慧、文才卓犖的自豪感。王更生先生〈《文心雕龍》的經學思想》一文即持此說:「劉勰所以要大書特書做夢的事,究其主因,在暗示自己的文學素養,得自天授,有異乎常人的創作才華。」23為了便於理解這一點,無妨先參看王充《論衡·自紀》篇是如何描述其幼童時期之德、志、才:
建武三年,充生。為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六歲教書,恭願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24
應當說,這段自序,從「小兒」之事講到「六歲教書」,再及「八歲出於書館」,皆意在彰顯個人之才智、德行與大志。劉勰自序方式與此不同,委婉含蓄,以「夢話」出之,且重點在文才一端。但是,「七齡」一詞,卻在在表現了一種自負,令人不由得想起唐代詩人杜甫〈壯遊〉開頭數句:「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按,《九家注杜詩》引趙次公云:「七齡、九齡,字則梁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曰:『予生七齡,乃夢彩煙【雲】若錦,則攀而采之。』揚雄言其子童烏曰:『九齡而與我元文。』」25這裡的「七齡思即壯」與「九齡書大字」,皆意在突出年幼才高、聰敏早慧,自豪之情,溢於言表。由此反觀劉勰「七齡」之夢,其言外之意,亦灼然可知。若以〈才略〉篇「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數語擬之,則「七齡」之說,乃自道文才「異稟」,「彩雲若錦」即「綜文」以「凝錦」之謂。
據《大戴禮記·保傅》篇:「古者年八歲而出外就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許慎《說文解字·敘》謂:「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朱熹《大學章句·序》言之更詳:「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禦、書、數之文。」26依此常規,則劉勰「七齡」即於夢中知「攀采」若錦之「彩雲」,自是古來所稱「神童」之屬。考漢魏以來之風尚,可知通常情況下,未至「十五入大學」之年而智術超奇者,皆備受世人青睞,以為幼敏早慧之神童27竊以為此一傳統觀念,亦當作為詮釋劉勰「七齡」之夢的重要文化「語境」。
王子今〈兩漢童蒙教育〉一文指出:「大致正是在漢代前後,又出現了『神童』的說法……現在看來,(揚雄之子)楊信很可能是最早被稱作『神童』的聰慧幼兒了。」28除了「神童」之目,尚有「聖童」、「奇童」之稱,如《東觀漢記》:「張堪字君遊,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丘易》。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29《藝文類聚》卷三一引《先賢行狀》曰:「杜安入太學時,號曰『神童』。」其入太學之年早於常規性的「十五歲」,而是十三歲,《後漢書·樂恢傳》李賢注引《華嶠書》曰:「(杜)安亦節士也,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30
在這些神童、奇童的相關記載中,其年齡大小不一,如鍾會「少敏惠宿成」31,「年四歲」即「授《孝經》」32,而有些「神童」則大至十二、十四乃至十六者33。但細加考察,不難發現一個較為顯著的現象,即以「七齡」稱揚「神童」者,情況較為普遍。上引《九家注杜詩》趙次公注文「揚雄言其子童烏曰:『九齡而與我元文。』」此「九齡」之說,乃本揚雄《法言·問神》:「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不過,《華陽國志·先賢士女總贊論》則作「七齡」:「雄子神童烏,七歲預雄《玄》文。年九歲而卒。」《華陽國志·後賢志》附《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錄》「文學神童楊烏」句下注文亦曰:「雄子也,七歲預父《玄》文,九歲卒。」為進一步說明此一問題,試以與劉勰年代較為接近之《世說新語》為例。
劉義慶生當崇尚天賦才情的南朝劉宋時期,所著《世說新語》,特設〈夙慧〉一門。「夙慧」即早慧,指年少者悟性聰穎,智超常倫。楊勇曰:「慧,宋本作惠,古通用,今從唐卷。夙慧,謂素有成人之智慧也。」34據統計,《世說新語》除〈夙慧〉著錄7則,其他門涉及早慧者尚有31條,旁及者又數條35。在這些材料中,有的只是記其大概年齡,泛謂年幼36,有的則確切載其年齡。在有確切年齡記載的事例中,年在八歲者4例37,五歲、九歲各3例38,十歲2例39,六歲、十一、十二、十三歲各1例40,而年在七歲者為數最多,共7例:
1、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德行〉第33則)
2、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於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言語〉第51則)
3、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方正〉第1則)
4、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游。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雅量〉第4則)
5、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撲,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雅量〉第5則)
6、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夙慧〉第2則)
7、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41,在床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複生此寶。」(〈夙慧〉第4則)
以上材料中,第1例稱「時年七八歲」,略顯含糊,然亦當含「七歲」之意,其餘皆明言「七歲」。除《世說新語》外,其他相關文獻中也常以「七齡」之異稟,說明幼童聰穎秀出:
1、《後漢書·馬援傳》附馬嚴傳:(嚴子馬續)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群籍,善《九章算術》。
2、《後漢書·張霸傳》: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
3、《後漢書·黃瓊傳》附黃琬傳: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
4、《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裴松之注引《世語》:(夏侯榮)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
5、《三國志·魏書·常林傳》: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党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
6、《太平御覽》卷八三五引〈徐邈別傳〉:(徐邈)岐嶷朗慧聰悟,七歲涉學,詩賦成章。
7、《盈川集》卷六〈後周明威將軍梁公神道碑〉:惟公弱不好弄,卓爾不群。九歲明詩,七歲通易。
從以上所徵引的各類記載中42,可以看出:古人所稱道智術超倫之「神童」,雖然具體年齡有別,特異稟賦不一,但「七齡」之目相對居多,無妨視之為帶有一定象徵性的「神童」之代稱。其原因之一,或者跟被品賞者之真實年齡確為「七齡」有關,然也不必看殺。此外,一般而言,古代男童八歲當入「小學」43,各種載籍中多關注「七齡」之秀逸,或許跟強調其正式接受基礎教育前即已聰穎絕倫、突出其天賦秉性有關。以這些「七齡」而才華卓犖者為文化背景,則劉勰自稱「予生七齡,夢彩雲若錦」,其寓意乃在年幼聰慧、文才優異,似非牽強附會。
《雞肋編》卷下有言:「天下之事,有不學而能者。儒家則謂之天性,釋氏則以為宿習。其事甚眾。唐以文稱如白樂天,七月而識之、無二字;權徳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韓退之自云七歲讀書,十三而能文;杜子美亦自謂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嚢。李泌之賦方圓動靜,劉晏之正朋字,豈學之所能至哉!以羊佑識廋環之處推之,則宿習為言信矣。」以此推之,則劉勰「七齡」之夢,其欲彰顯一己之「夙習」,殆無疑義。劉勰在〈雜文〉開篇謂:「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這段文字,無妨作為劉勰自負幼年即富文才之注解。
又,劉勰論君子處世,當「樹德建言」,以求「名逾金石之堅」,而要達到這一目的,「智術」必不可少。此一「智術」,在劉勰看來,固然與後天勤奮磨礪有關,所謂「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神思〉)者是,但最為關鍵者,乃來自「五行之秀氣」,亦即天地自然所賦之「性靈」。劉勰談自己撰著《文心雕龍》,亦頗以幼年即有天賦文才而自豪。其〈諸子〉篇有言:「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徳,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徳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此不啻夫子自道,即以特達之英才,垂「炳耀」之文。惟其如此,崇尚才情、重視秉性,自然成為《文心雕龍》一以貫之的重要文論思想之一。他專設〈才略〉一篇,品評「富矣盛矣」的「九代之文」,傾心於「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他稱美先聖,重點亦在超凡之文才,故〈原道〉篇謂:「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制詩緝頌,斧藻群言。」〈徵聖〉篇曰:「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辨騷〉篇作為「文之樞紐」重要組成部分,頌揚「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原因之一,就在於「楚人之多才」,而〈明詩〉篇盛讚建安五言詩,以為「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是其優長;又說四言以「雅潤為本」,五言則「清麗居宗」,揀擇取捨之間,「華實異用,唯才所安」,可見作者才性稟賦如何,是選擇文體之首要依據。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皆足以體現其尚「才」崇「文」思想。
以上重點探討了劉勰「七齡之夢」的具體內涵,無論從〈序志〉篇「予生七齡,夢彩雲若錦」與上下文句之間的脈理邏輯關係看,還是就古來多以「七齡」智術超倫為「神童」代稱此一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歷史文化背景而言,劉勰所謂「七齡」而夢「彩雲若錦」,目的都是為了說明其自身文才之優異。這一點,與魏晉以來崇尚天賦才性的時代思潮相一致,也切合《文心雕龍》全書「才為盟主」、「以雕縟成體」的創作觀念。
《周禮·春官·占夢》將夢分為六類,鄭玄注: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謂「喜悅而夢」;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44。東漢王符《潛夫論·夢列》則更細緻地分為十類:「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45余嘉錫以為「潛夫所謂直夢,蓋即《周禮》之正夢,想夢即思夢也」46。若據此而論,則劉勰二夢,在類型上實有顯著區別:其「七齡」之夢,當屬「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之「正夢」,本於自然,具有一定的神授色彩,《潛夫論》所舉「直夢」之例亦如此47,而劉勰之重點,在於突出自己幼而聰穎、天賦文才。其「齒在踰立」之夢,若依《周禮》之說,則為「覺時而思念」之「思夢」;如按《潛夫論》之分類,則為「意精之夢」,與一般意義上的「思夢」或「記想之夢」略有差異。王符所說「記想之夢」,指的是「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側重於現實生活之人事,而「意精之夢」則神游古往,非注目當下,與夢者之人生志向有關,此「意精」之「意」即「志」也48,故王符舉孔子夢周公為例:「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49當時孔子立志「克己復禮」以「從周」,其所「思」之對象,乃往世「周公之德」以及由此所構建之「文」化典章制度50。顯而易見,劉勰之夢孔子,與孔子之夢周公,都是追慕、景仰已逝聖者所致,是其人生志向之表現。
《世說新語·文學》載樂令析夢有「想」、「因」之別,楊勇以為「『想』是有意識者,『因』是無意識者」51。即此而論,則劉勰「七齡」之夢可歸之於「無意識者」,重在自然神授之智術文才,講的是天賦因素;「齒在踰立」之夢則反之,屬於「有意識者」52,則重在強調有意識之努力。這種有意識之努力,可從兩個側面推知:一者,劉勰夢隨仲尼之後「怡然而喜」,且慨然歎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既曰「難見」,則可想見劉勰日思夜盼夢見夫子之強烈心理,「乃小子之垂夢歟」一句,著一「乃」字,可見其美好願望終得實現時喜出望外之情,以夢境之方式體現有為之意識;二者,〈序志〉謂「文心之作」當「師乎聖」,其具體內涵,則如〈徵聖〉篇所言:「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用思於聖人之文章,以聖人立言精神為典範,皆有為意識之表現。
本文開頭部分曾從章法結構的角度,分析了「齒在踰立」之夢與劉勰宣導「製作」以求「騰聲飛實」生命價值觀的內在關聯性,以為劉勰「夢隨仲尼而南行」,實質上體現了繼踵仲尼、立志「製作」之宏偉抱負。這裡擬作補說的問題是,劉勰所「夢隨」的仲尼,究竟屬於哪一個層面上的「仲尼」53?
此一問題的提出,乃緣於以下三點考慮:第一,有不少學者認為,既然劉勰心嚮往之者為聖人孔夫子,則《文心雕龍》基本文論立場即為儒家,並進一步以為劉勰所推崇之孔子,即倫理道德層面之萬代師表孔聖人,劉勰所「原」之「道」亦即儒道;第二,另有學者提出劉勰所推崇之孔子,「非春秋戰國時代之孔子」,而是一種精神象徵之偶像;第三,明清兩代,即有學者以為劉勰以仲尼為師,其實與孔子精神無涉,如明代程寬〈文心雕龍序〉曰:「蓋勰也,彩雲已兆七齡之初,丹漆獨隨大成之聖。夢之所寄,心亦寄焉;心之所寄,文亦寄焉。其志固,其幽芳,其歷時久,是故煥成一家,法垂百祀雲。惜也道崇金聲玉振,而謂雕琢性情;志雅樹德建言,而詫知術拔萃;宗經而無得於六經,養氣而固迷其正氣,此劉子文心之所以為雕龍也。自辨不群騶奭,詎能免誚虛車?」54以為劉勰《文心雕龍》「宗經而無得於六經,養氣而固迷其正氣」。錢大昕則謂:「齊、梁文人多好佛。劉彥和序《文心雕龍》,自言『夢見宣尼』,而晚節出家,名慧地,可謂咄咄怪事。」55凡此種種,確為理解劉勰文論思想過程中容易產生之疑點。所以,劉勰所推崇之孔子,究竟屬於何等形象,頗有必要予以梳理。
韓非子指出:「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邱也。」而孔子死後,「儒分為八」56。顧頡剛〈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早已指出:「各時代有各時代的孔子,即在同一時代中也有種種不同的孔子呢。各時代的人,他們心中怎樣想,便怎樣說,孔子的人格也就跟著他們變個不歇。」57比如,春秋戰國時期,雖有魯哀公立廟祭祀孔子,但終歸是布衣身份;自漢武帝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則逐漸升格為聖人,「爵之以公,垂以廟祀」58。與此相關,漢人所推重之儒家「經術」,則重在「引經決獄」和「以孝治天下」兩個方面,「格外推尊《春秋》與《孝經》這兩部儒家典籍」59。到了魏晉時期,雖然依舊尊崇孔子為「聖人」,但在佛學、玄學交互影響下,其形象內涵卻有了新的變化。比如王弼,就以「聖人體無」與「聖人有情」來闡釋孔子思想60,而佛徒則以「空」來涵括孔子學術61。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涉及孔子及其儒學經典時,雖然以相容並包的學術視野,對相關學說有所借鑒或吸納,但其最重要的特點,或者說最為獨特之處,則在於將「儒學」加以「文學化」,其前提則是將重教化、尚道德、講倫理的「孔聖人」,轉變為文章寫作的聖手和楷模。對於這一點,美國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曾著文指出:「在某種程度上,劉勰對儒學傳統的詮釋幾乎是在企圖重新界定經典的文學性意義,以及展示經典具備何等豐富的風貌、何等有力地表現了具體的真實……在整部《文心雕龍》裡,劉勰始終主張聖人最本質的條件就是明瞭如何創造性地透過優美的文字傳達『道』與人之情性。換言之,一個聖人首先必須是一個傑出的作家。事實上,從劉勰強而有力的讚賞孔子文章之『辭富山海』來看,他是堅信孔子這樣的文學成就已足以使其永垂不朽了。」62這一論斷,定位明確,頗為恰切地揭示了劉勰之聖人觀的實質。為了更好地理解劉勰筆下作為文章聖手的孔子形象特點,茲以〈徵聖〉篇為例,略加分析。
關於〈徵聖〉篇,紀昀以為「此篇卻是裝點門面,推到究極,仍是宗經」63。劉勰在〈原道〉篇說:「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所以,徵聖的最後目的「仍是宗經」,本是劉勰「文之樞紐」的必然邏輯;但是,由此判定〈徵聖〉只是「裝點門面」,實有悖劉勰之立意。當然,紀昀之所以如此論斷,根本原因還在於他將劉勰所推原之「道」,理所當然地理解為儒家倫理道德之「道」,而這樣的理解,也未能得劉勰之「道」的兩大特質:一是尊自然,二是尚文采。自然與文采,在劉勰看來,本是「道」之兩面,而紀昀卻將二者對立起來,其評〈原道〉篇曰:「齊梁文藻日競雕華,標自然以為宗,是彥和吃緊為人處。」看似肯定了劉勰之「自然」觀,實際上只是在文章風格體貌自然這一層面立論,而對於劉勰立自然以為宗,意在證成文章雕縟之美本於「自然之道」這一核心思想,似未了然。其實,細讀〈徵聖〉一篇,不難看出,劉勰正是在「自然之道」本貴麗藻雕縟這一「文」的層面,來論述聖人如何「原道心以敷章」(〈原道〉篇)的。
在〈徵聖〉篇中,論及「心」者,僅一見,即讚語最後一句:「百齡影徂,千載心在。」說的是像孔子這樣的聖人雖然已經逝去,其「心」則彰顯於流傳下來的著作中。此「心」既是〈序志〉篇所言「為文之用心」之「心」,同時又是〈原道〉篇所講之「道心」,也就是「天地之心」。聖人以「天地之心」為「心」,故其文章所表現之「文心」,亦即「天地之心」。〈原道〉篇說:「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徵聖〉篇正是循此思路而讚美聖人立言之道:「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生知」之說,出自《論語·季氏》篇孔子語:「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但是,其內涵之所指,則與〈子罕〉篇子貢推崇孔子「天縱多能」,關係更為密切:「太宰問於子貢:『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劉勰沿用之,重點即在讚美聖人原本即與「天地之心」,也就是「自然之道」相表裡;而劉勰所謂「秀氣成采」之「秀氣」,即天地靈秀之氣,也就是〈原道〉所謂「性靈所鍾」、「五行之秀」。聖人稟此「生知」,因「秀氣」以「成采」,憑「精理」以「為文」,亦本「自然之道」,也就是〈原道〉篇所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篇又說:「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可見「天地之心」的本質特徵與「自然之道」相通,重點都落在美麗之「文」上。〈原道〉篇以為「日月疊璧」是「道之文」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徵聖〉篇也指出聖人能夠「鑒周日月」、「鑒懸日月」——其涵義之一,當指聖人法天行道,從日月「麗天之象」得到啟示,從而創造了「辭富山海」的文章。因此,在劉勰看來,聖人之麗辭,與日月之「麗天之象」,其實都是自然「道心」之顯現。由此可知,〈徵聖〉篇最後說聖人「千載心在」,強調的也就是聖人依「天地之心」宣導斐然文采、創造「雅麗」文章的「用心」所在。如此立論,與統治者、一般儒家學者甚至玄學家之推崇孔子,側重點自有明顯區別。〈徵聖〉全篇之重點,皆以聖人立言如何崇尚「文采」為中心,原因正在於此。
〈徵聖〉首章自「夫作者曰聖」迄「秉文之金科矣」,主要是從「夫子文章」中擇取能夠體現「夫子風采」之「格言」。這些「格言」,都是「貴文」之論:有「政化貴文之徵」,有「事蹟貴文之徵」,還有「修身貴文之徵」,然後小結說:「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可見,夫子「貴文」,是其根本特徵,其中「志足」、「情信」是基礎,「言文」、「辭巧」是結果。劉勰心目中「獨秀前哲」的聖人,就是這樣一位處處以「文」為「貴」的宣導者。這是劉勰論文而欲「師乎聖」的首要緣由。
〈徵聖〉次章自「夫鑒周日月」迄「則文有師矣」。此雖「周孔」並提,其實重點仍在「孔」64,主要是以儒家經典所運用藝術表現手段為例,說明聖人如何「鑒周日月」而臻「思合符契」之境,又如何「妙極幾神」以收「文成規矩」之效。按照劉勰的理解與分析,儒家經典「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其中「簡」與「博」、「明」與「隱」,皆兩兩相對,總其兩端,概括說明聖人為文之法則,乃在於「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適會」。其中「繁略殊形,隱顯異術」八字是舉證,「抑引隨時,變通適會」八字是總結,也是規則原理。「隨時、變通」之義,就是強調聖人如何善於根據所要表達「志」、「情」之具體情況,選擇相應的表現手法。就此而言,劉勰認為:「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可見,次章在首章的基礎上,進一步確定了聖人乃後生當取法之「文師」。這與前人視聖人為道德楷模,視角亦自有別。
徵聖〉第三章自「是以論文必征於聖」迄「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本章重點講聖人文章總體特點,也就是「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體要」貴在「明理」,「微辭」則以「婉晦」為特點;「正言」即「簡言」,「精義」則多「曲隱」。劉勰以為聖文之偉大,也表現在這種「義」與「辭」的辯證對立統一關係中。這是對上一章「繁略殊形,隱顯異術」說法的進一步提升,也是對聖人文章特點的進一步深化理解。總起來說就是:「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為了更好地突出這一點,劉勰又論及顏闔之言:「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聖,弗可得已。」既充分肯定了聖人之「事華辭」,又指出聖人之「華辭」,乃因充實之情志而敷設,是「雅麗」之文,也就是「銜華而佩實」。所以,劉勰強調說:「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所謂「文章可見」,指的就是聖人貴文之思想、抑引隨時之法則、華實並重之境界,都體現於聖人文章之中。學習聖人,就是要認真鑽研、仔細體會聖人為文之「用心」。蔣祖怡〈《文心雕龍》發微〉指出:「劉勰的尊儒宗經,只是為了『重文』,並不是要求人們在文章裡宣揚儒家思想,更不是要求人們去注釋經書;一篇文章能做到『銜華佩實』即是達到他尊儒宗經的要求。」65這樣的看法,是符合劉勰本意的。
總而言之,劉勰「齒在踰立」而「夢隨仲尼而南行」,顯然不是意在宣揚儒家倫理道德教化之「道」,而是意在弘揚孔夫子的「貴文」主張,傳播「銜華佩實」的「雅麗」文風,達到懲治「言貴浮詭」、「文體解散」文壇弊端之目的。換言之,劉勰心目中的「仲尼」,充分體現了「自然」與「藻繪」兩位一體這一「三才」之「道」,是文章「聖手」與楷模,因為孔子不僅是雅麗之文的傑出實踐者,而且還是「貴文」思想的宣導者。明乎此,劉勰論「文心」而立志「師乎聖」,其立意及基本內涵,也就非常明確而易於把握了。質言之,「徵聖立言,文其庶矣」,足以涵括劉勰「夢隨仲尼而南行」之根本宗旨。
1、 本文部分內容曾以〈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七齡之夢」寓意補說〉為題,刊於《青海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全文收錄於拙著《文心雕龍疑思錄》,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61-290頁。
2、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下冊,〈序志〉篇第【六】條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731頁。
3、 牟世金:《劉勰年譜匯考》「宋後廢帝元徽元年(四七三)癸丑」條,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第11頁。
4、 賈岸:〈〈序志〉說夢因緣探賾——劉勰生年辨〉,《臨沂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5、 周勳初:〈劉勰的兩個夢〉,《周勳初文集》第三卷《文史探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4、106頁。
6、 汪春泓:〈夢隨仲尼而南行——論劉勰的「北人意識」〉,《文心雕龍研究》第1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7、 余才林:〈六朝夢得文才說透視〉,《華僑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8、 據筆者所見,還有幾篇專論劉勰之夢者,其觀點或以為「劉勰之夢彩雲並攀而折之,寄託了他對人生的某種強烈企求和渴望」,劉勰的「夢話」,「是他『奉時以騁績』,急功近利心態的反應」。(易健賢〈劉勰三夢和他的「奉時以騁績」心態——關於《文心雕龍》成書的思考〉,《貴州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第l期)。或以為「彩雲夢是劉勰兒時對美好未來的期盼;隨孔子南行夢是中年劉勰渴望自己的才能得到認可的心理反映」。(趙必珊〈劉勰二夢的心理分析〉,《湖北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或以為彩雲之夢「向人們昭示他深具寫作《文心雕龍》的技術前提」。(喬守春〈劉勰二夢論析〉,《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9、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534頁。本文引用《文心雕龍》文字,均依周注本,如無需要說明之處,以下不再出注。
10、 周勳初:〈劉勰的兩個夢〉,《周勳初文集》第三卷《文史探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3頁。又,姚思廉《梁書·劉勰傳》引錄〈序志〉篇時,無「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采之」十四字,明代嘉靖年間佘誨刻本、《廣文選》亦同。對於這一情形,簡良如論曰:「本夢僅慕自然之美,和該段後文敘述第二夢的人文之事不類,亦悖於《文心》全書突顯人文的態度,似有摘除之必要,是以佘本等亦認可《梁書》的處理……欲推斷原本《文心》究竟有無此夢,必須從《文心雕龍》對萬物之彩的態度,及對物采與文關係的討論切入,斟酌此夢之必要和在人文問題上所具有的階段意義,而非僅憑該段上下文評定。」《〈文心雕龍〉之作為思想體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351頁。
11、 參見楊琳《訓詁方法新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77-188、226頁。
12、 周勳初:〈劉勰的兩個夢〉,《周勳初文集》第三卷《文史探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6頁。黃景進〈讀〈序志〉〉亦以為:劉勰「夢到自己竟然攀到如錦繡般美麗的彩雲上,這預示著他將成為優秀的文章作家,能寫出如錦繡般的文彩」。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編:《論劉勰及其〈文心雕龍〉》,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第567頁。
13、 余才林:〈六朝夢得文才說透視〉,《華僑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14、 黃景進:〈讀〈序志〉〉,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編《論劉勰及其〈文心雕龍〉》,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第567頁。古風:〈劉勰對於「錦繡」審美模子的具體運用〉,《文學評論》2008年第4期。
15、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4頁。
16、 宋玉〈高唐賦〉:「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台,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焉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文選》卷一九,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64-265頁。
17、 李白著,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25頁。
18、 柳宗元著,王國安箋釋:《柳宗元詩箋釋》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頁。
19、 參見張少康等撰《文心雕龍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446-447頁;漆緒邦〈劉勰的天師道家世及其對劉勰思想與《文心雕龍》的影響〉,《北京社會科學》1995年第2期。
20、 參見楊清之《文心雕龍與六朝文化思潮》第五章第二節《道家生命哲學與劉勰的養氣說》,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
21、 如〈定勢〉:「雖複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總術〉篇:「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才略〉:「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縟錦之肆。」又贊曰:「一朝綜文,千年凝錦。」〈時序〉篇:「茂先搖筆而散珠,太衝動墨而橫錦。」
22、 周勳初:〈劉勰的兩個夢〉,《周勳初文集》第三卷《文史探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7頁。
23、 張少康編:《文心雕龍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7頁。
24、 北京大學歷史系《論衡》注釋組:《論衡注釋》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670-1671頁。
25、 《九家集注杜詩》卷十二,洪業等編纂:《杜詩引得》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9頁。
26、 關於古者入小學之年齡,亦有不同說法,如《尚書大傳》卷三〈金縢傳〉:「十有五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又說:「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但是,八歲之說更為常見,以上正文中所列舉者外,又有《春秋公羊傳注疏》卷十六:「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班固《漢書·食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養國子,教之六書。」又,《漢書·食貨志上》:「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
27、 《太平御覽》卷八三九引〈鄭玄別傳〉曰:「玄年十六,號曰『神童』。……侯相高其才,為修冠禮。」情況似較特殊。參見王子今〈兩漢童蒙教育〉,《史學集刊》2007年第3期。
28、 王子今:〈兩漢童蒙教育〉,《史學集刊》2007年第3期。
29、 「年六歲」,《後漢書·張堪傳》作「年十六」,王子今《兩漢童蒙教育》一文認為:如「『年十六,受業長安』則不足為奇,而『聖童』之號由來亦可疑。」
30、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四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478頁。
31、 《三國志》卷二十八《魏書·鍾會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784頁。
32、 《三國志》卷二十八《魏書·鍾會傳》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785頁。
33、 《說郛》卷五八下劉昭〈幼童傳〉:「任嘏。樂安任嘏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學幼而多慧。」《冊府元龜》卷七七三〈幼敏第一〉:「任昭,先名嘏,世為著姓,夙智蚤成。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周,三年中誦《五經》,皆曉其義,兼包群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為『神童』。」以上情況,參見王子今〈兩漢童蒙教育〉,《史學集刊》2007年第3期。
34、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533頁。
35、 呂菊:〈《世說新語》早慧現象探究〉,《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第3期。
36、 如有謂「尚幼」者,如〈排調〉第33條:「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有謂「總角」者,如〈品藻〉第7則:「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為成器。」〈賞譽〉第112則:「魏隱兄弟少有學義,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複有人。』」〈識鑒〉第5則:「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 本文引用《世說新語》文字及據以統計之文本,皆依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若從別本,另加說明。
37、 〈言語〉第5則孔融之子「小者八歲」、第46則「謝仁祖年八歲」、第50則注引〈孫放傳〉謂孫齊莊「年八歲」,〈排調〉第30則「張吳興年八歲」。
38、 〈識鑒〉第8則「衛玠年五歲」、〈夙惠〉第7條桓玄「年五歲」、〈言語〉第4則孔融之子「小者五歲」;〈言語〉第5則孔融之子「大者九歲」、〈言語〉第43則「梁國楊氏子九歲」、《言語》第2則徐孺子「年九歲」。
39、 〈言語〉第3則孔融「年十歲」、《假譎》第7則「王右軍年減十歲」。按,右軍之年,原文作「年減十歲」,徐震堮曰:「『減』,沈校本作『裁』,義並可通。」
40、 〈言語〉第4則孔融之子「大者六歲」,〈政事〉第3則陳元方「年十一」,〈夙惠〉第6則晉孝武「年十二」,〈言語〉第11則鍾毓、鍾會兄弟「年十三」。
41、 此與〈言語〉第51則謂「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於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略有出入。
42、 唐人亦多年在「七齡」而聰慧異常者,除杜甫「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一例外,尚有駱賓王,《全唐詩》卷七十九駱賓王〈詠鵝詩〉題注:「七歲時作。」胡應麟〈補《唐書》駱侍御傳〉:「賓王坐七歲,能詩,嘗嬉戲池上,客指鵝群令賦焉。應聲曰:『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客歎詫,呼神童。」《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九李泌本傳:「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為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三劉宴本傳:「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韓愈〈與鳳翔刑部尚書書〉:「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以文名於四方。」又〈感二鳥賦並序〉:「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又,佛門典籍也有不少此類材料,如《宋高僧傳》卷十三周金陵清涼文益:「年甫七齡,挺然出俗。」《禪林僧寶傳》卷五吉州禾山殷禪師:「七齡,雪峰存禪師見之,愛其純粹。」《五燈會元》卷十四投子義青禪師:「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
43、 《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曰:「女子七歲,腎氣實,齒更發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平均……」以七年為女性生長發育之週期。同書認為男性的生長週期為八年:「丈夫八歲,腎氣實,發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葵至,精氣溢泄,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古人規定男童八歲入小學,當與此有關。故《白虎通義·辟雍》篇謂:「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
44、 鄭玄注,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卷二十五,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808頁。
45、 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315頁。
46、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卷上之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78-179頁。
47、 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卷七〈夢列〉:「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為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315頁。又,明代林俊《見素集》卷十二〈覺軒記〉曰:「夫審像兆祥夢,見於經舊矣。其概想與因也。形神相接曰想,不接謂之因。夢游華胥,夢槐柯,想也;夢授筆,夢吐白鳳,因也。」
48、 《呂氏春秋·長見》:「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高誘注:「意,志也。」
49、 王符著,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315頁。
50、 《論語·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又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51、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81頁。
52、 這一點,頗似孔子之「從周」,乃「是對他所處生活環境有意識地作出的一種自覺反應」。參見林存光〈孔子:中國文明的守望者——試論孔子的「傳統」觀及其文化貢獻〉,《儒學的當代使命——紀念孔子誕辰256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二冊),第105頁。
53、 易健賢〈劉勰三夢和他的「奉時以騁績」心態——關於《文心雕龍》成書的思考〉:「劉勰夢中不隨孔子北行,而朝南走,這意味著什麼呢?佛教的發祥地在南方的古印度,劉勰所生活的南朝,已經將孔丘、顏淵、老子視為佛祖三弟子……有什麼理由一口咬定劉勰夢見的孔子就是春秋時代的那位孔子呢?」《貴州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第l期。
54、 轉引自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953頁。
55、 錢大昕著,楊勇軍整理:《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范縝神滅論」條,北京: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第329頁。
56、 《韓非子》卷十九〈顯學〉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57、 顧頡剛〈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顧頗剛古史論文集》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87頁。
58、 參見周峰〈孔子形象塑造之我見〉,《孔子研究》2006年第1期。
59、 參見林存光〈漢代尊孔的政治文化意向探析〉,《齊魯學刊》1993年第5期。
60、 參見余樹蘋〈王弼的聖人觀〉,《求索》2010年第3期。
61、 劉勰〈滅惑論〉即如此,故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通。」
62、 孫康宜〈劉勰的文學經典論〉,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編:《文心雕龍研究》第3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2-43頁。又,周振甫以為「劉勰提出『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因此要向聖人來學習道,通過聖人的文章來學習文」,但劉勰既「不是要求用儒家思想來寫作」,也「不是要求用經書的語言來寫作」,「他的宗經,正像〈徵聖〉、〈宗經〉裡講的,主要是講隱顯詳略的修辭手法,是講六義,內容的情深、事信、義直,風格的風清體約,文辭的文麗,要寫出有內容有文采的文章來。」不過,周振甫在歸納劉勰徵聖、宗經思想的成就時,則如此表述:「〈宗經〉還有更深刻的含意,是有關於創作的用意的。像〈文賦〉提出『詩緣情而綺靡』,即要求抒情而有文采。但《明詩》裡指出『詩言志』;『詩者持也,持人情性』,要求有『順美匡惡』的美刺作用……在〈情采〉裡又提到『詩人篇什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這樣的創作思想,突破了魏晉以來的文論,有了更高的要求,是從宗經裡來的。這是他在文學理論上得傑出成就,他的宗經,是文學理論上的革新。」《文心雕龍注釋·前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26-28頁。王鍾陵《中國中古詩歌史》也以為把「把聖和經文學化」是「《文心雕龍》的一個總的思想特徵」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2頁。 此外,《社會科學論壇》(學術研究卷)2008年第6期載胡培培〈文之樞紐:從儒家經典到文學經典〉,亦可參看。
63、 《紀曉嵐評文心雕龍》卷一,南京: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第27頁。
64、 張立齋《文心雕龍注訂》之〈徵聖〉篇題解:「聖指孔子,筆及周公,故舉孔子之言論為多。兩稱夫子,兩稱文章,皆指仲尼。是知徵聖者,徵驗孔子之文章也。」
65、 蔣祖怡:〈《文心雕龍》發微〉,《文心雕龍學刊》第1輯,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第411頁。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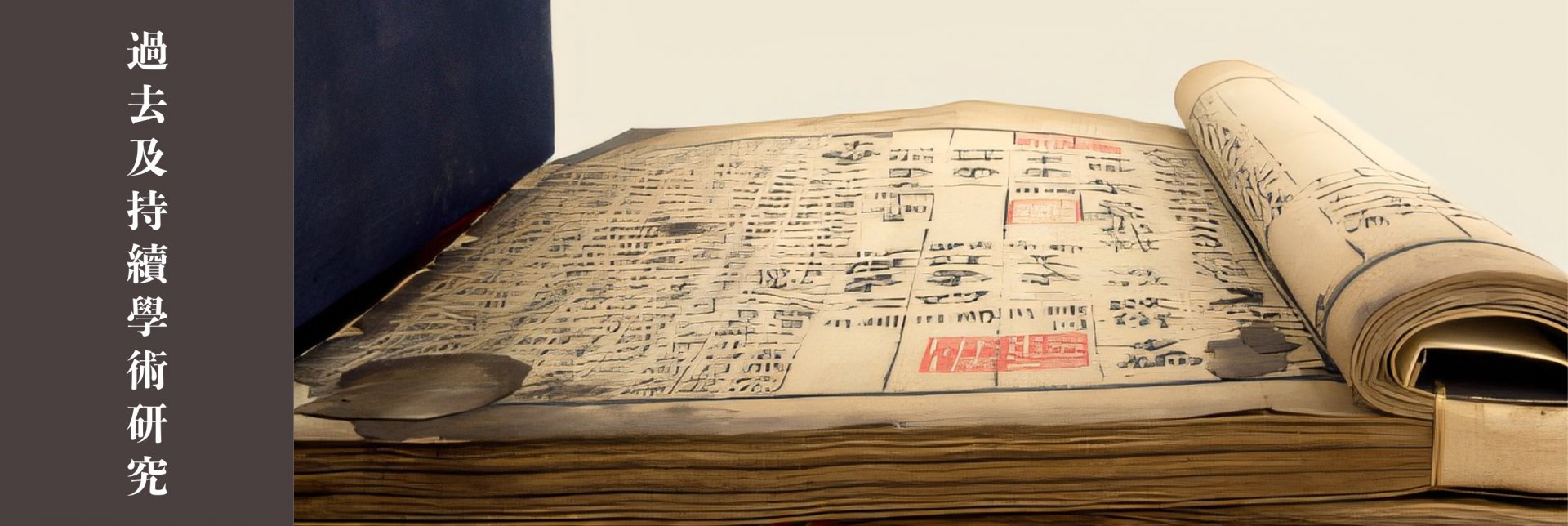



歡迎留言:
請登入/登記成為會員後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