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彈的歷史研究
本文源自何其亮教授在2012年6月5日,於上海師範大學所作的同名講座,
由《陸國權中華文化傳承研究基金》研究員黃小瑜編輯審校。
評彈是屬於江南的地方曲藝,在江南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民間藝術。越是地方性的東西文化,越具有國際性。評彈的研究,在國內欣欣向榮。歷史學界,也開始通過評彈來研究江南社會。何其亮教授所寫的關於評彈的研究著作,從評彈、國家與市場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出發,通過這樣嶄新的視角,構建了一種理論模式來進行深入研究。
首先介紹我寫這本書的前因後果,即我為什麼要進行評彈研究?其實,最初我並不是研究評彈的學者。2006年,我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做的博士論文是20年代的上海醜聞、轟動性新聞對於社會的影響。對於娛樂業和大眾文化的影響,我選取了兩個重要的例子,一個是謀殺案,一個是私奔案。這個私奔案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黃慧如與陸根榮,這個案子其實很有意思,不光是報紙報導了,而且很多媒體都有涉及。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來研究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的新聞業、出版業、戲曲、電影,不同媒體,不同社會人物,特別是政治人物,在這個事件中扮演的角色。2006年博士畢業以後,我想把這個話題繼續深入下去,我覺得私奔案這個案子,單獨就可以成為一個研究主題,其實我現在還是在做這個話題。後來我得到一個消息,說在上海有評彈演員和滬劇演員正在演出這一私奔案,一直延續到本世紀初。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我可以把這個話題一直延續到解放以後。所以當時我採訪了一位評彈演員蘇毓蔭和一位滬劇演員徐伯濤。那個時候是2007年,我當時的設想是:到了90年代以後,上海重新崛起,成為經濟發展的領頭羊,改革開放的領頭羊。然後中國重新加入國際大家庭,成為全球化的一部分。我覺得上海人對於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的那種懷舊,其實是契合了這一種思潮。上海人可以認為全球化,不僅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其實早就發生在30年代、40年代,所以對於上海的懷舊,其實就是一種上海身份地位的確認。我認為演出像黃慧如、陸根榮這樣的評彈或者滬劇,其實就是這個思潮的一部分,這個思潮最著名的當然就是所謂的張愛玲熱了。

所以我覺得去訪談這些演員,會得到一些答案。換句話說,他們的演出能得到領導的支援、市場的歡迎,就是因為出演過滬劇《黃慧如與陸根榮》。其實這個故事有各種版本,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有京劇、評彈、滬劇、越劇等等。徐伯濤改編了老版本,強化了一個反封建、反包辦婚姻的形象,所以是受到領導歡迎的,甚至他的節目還曾在上海電視臺播放過,《新民晚報》和《每週廣播電視報》都有報導。我問他有沒有受到一些阻力,不許他演出這個劇目,他說完全沒有。後來他將演出做成VCD,也沒有任何問題。這就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蘇毓蔭則相反,他告訴我,他在80年代受到了很大的壓力。我們先不論他演繹的《黃慧如與陸根榮》是否成功,這個長篇評彈藝術性是不是很強。80年代這一評彈表演在市場上確實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在政治上,他受到的壓力是非常巨大的,一直到80年代中後期,他都是被禁止演出的。80年代早中期,蘇毓蔭可以在江浙一帶表演,但在上海是被封殺的。評彈《黃慧如與陸根榮》走進上海,其實是在90年代以後。我這本書的第六章“星火燎原:“文革”前夕的集體所有制評彈團”談到了這個問題。這就是我研究評彈的一個出發點。
我當時在想,我手上的資料,本來是用來研究黃慧如與陸根榮的事件對長江三角洲一帶的影響。這個資料並不能完全契合我的想法,事實上它是讓我失望的。我在思考應該如何面對這個問題。是否應該跳過蘇毓蔭,直接講徐伯濤的成功呢?但是我不能那麼做,這個材料放在我面前,我不能完全忽視它。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東西。我認為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下,到底為什麼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所以我覺得評彈這個題目是非常有意思的。實際上蘇毓蔭告訴我的,不光是他怎麼演出,或是不允許演出《黃慧如與陸根榮》,他還告訴我很多別的東西。比如他作為一個評彈演員,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只有5年或6年的時間,是作為一個評彈團的演員。絕大多數時期,整個5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他都是單幹藝人。“文革”時期另當別論,必然是沒有機會說書的。但這對於我的一個固有的觀念是一種衝擊,我一直認為國家的力量是可以把所有的藝人都集合起來,集中起來,和集體化的形式一樣。但事實上,蘇毓蔭在絕大多數時期是單幹的,也就是說藝人的單幹現象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其實是比較普遍的,尤其是評彈。因為評彈有一種特性,就是個體化,即個人演出個人得利。
2007年,我開始思考評彈藝人單幹的問題,後來2007年12月份到2008年1月份,當時我去採訪了吳宗錫(原上海評彈團團長)。因為蘇毓蔭認為吳宗錫是那個政治上把他封殺掉的力量,所以我就直接採訪了吳宗錫。然而,吳宗錫認為他沒有做過這件事,也可能是他對於封殺野書這件事,已經不太記得了。但是既然大家有觀點衝突和矛盾,我認為評彈就是一個可以研究的主題。尤其是解放以後的評彈,事實上在美國是一個空白點。我這本書可以說是美國的評彈研究在歷史學領域中的第一本書,前面有人寫過評彈在30年代的發展,但那是一本博士論文,還沒有成書。其他還有些文章,但成書的,這將是第一本。

2008年的秋天,我寫了一篇文章,是關於《黃慧如與陸根榮》在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命運。《黃慧如與陸根榮》開始是一個中篇評彈,到了80年代才成為一個長篇評彈。這篇文章後來在《近代中國》發表,這是美國比較權威的中國研究雜誌。因此我才下定決心做評彈歷史研究。到2009年的夏天,我開始大量採訪評彈藝人、書場管理人員、評彈聽眾和票友,還有包括吳宗錫和周良在內的,一些過去管理評彈的領導幹部。所以我正式研究評彈是從2009年的夏天開始的,一直做到2011年,大概花了兩年的時間,然後去年年底投稿(英文版),中文版在今年3月份差不多。這就是我整個研究出書的歷程。
我使用的材料也不是特別專門化的。做評彈研究,肯定會用到出版物,報紙、檔案、口述材料(訪談)等等。大多數人做評彈,多多少少都會用到這一些。只不過是做的時間段有差異,側重點有所不同罷了。其實每一種史料都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每一種史料也都有它的優點和長處。
先說一說口述史料,我用的比較廣泛,而且對於1949年和1950年以後的評彈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那麼多評彈演員還健在,不光是評彈演員。還有那些管理評彈的領導幹部,以及老聽眾都還健在,這些都是寶貴的財富,不去挖掘的話,非常可惜。因為我們知道,那些老一代的評彈藝人,真的在這一年去了不少。很多評彈藝人包括我採訪過的一些演員,其實已經去世了。所以口述歷史的採訪一定要抓緊時間,趕早不趕晚。但是口述材料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你也許不喜歡受訪人,不喜歡他的作品,不喜歡他以前做過的事情。怎麼辦?還是要耐心地進行訪談,因為他能提供給你的,不儘是他以前的所作所為,他以前演出過的東西,他還會提供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材料。比如蘇毓蔭的訪談中得到的一些資訊,是我真的沒有想到的。第一個資訊就是他的單幹,現在來講就是個體戶。第二個資訊:他當時加入星火評彈團的1960年以後,所有的文化表演團體都有一個任務,就是下工礦、下廠給工人、農民做演出。當時我認為這就是政治宣傳。但是他告訴我,即使是這樣的演出,他們的星火團還是盈利的。例如他的一個朋友在團裡是講“焦裕祿”的,100分鐘40塊錢一場。他們團裡真的是靠這個賺了一些錢。這個故事告訴我,即使是政治化的東西,它也是可以賺錢的。一來也有娛樂性,二來也和市場有關係,這是一種新的,另一種形式的市場。我覺得應該更深入地探討一下這一種市場的性質,但現在來說可能有些蜻蜓點水了。第二點,很多老先生教育水準還是不高的,做訪談時,他們講話的邏輯性不強,重複、誇張、半天講不到重點,這都是可能發生的事情。例如我採訪蘇毓蔭,過去三年,我每年都去採訪他,不止一次,他重複的故事是大量的,我都聽過好幾遍了,他還以為我沒有聽過。因為年紀大。用說書的術語,這叫作“叻”。如果你們多研究說書的技巧的話,說書就是這樣的。但訪談時必須耐心,必須跟他們搞好關係,來從中得到最大量的資訊。第三點就是關於他們言語的真實性。我們不能完全相信,必須通過其他材料來多方求證。從檔案、從出版的東西、其他人的話,來多方求證。因為一來他們年事較高,他們的記憶可能會出現錯誤,或是發生扭曲。第二則是因為,他們是習慣於去編故事的。第四點,在進行採訪前需要準備好問題。不要誘導老藝人、老幹部、老聽眾,來得到你希望得到的答案。就像警員誘供一樣,這是不可取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讓他說,說到哪裡都行,也許沒什麼用,但總會有有用的地方。我其實覺得有時候,主題先行,然後讓別人給你一個你想要的故事,這是最不好的事情。有很多文章都是這樣寫的,比如說,為了表現新舊社會兩重天,非得說以前受流氓欺侮,解放以後什麼都好了。這就變成一個套路了。其實解放之後的很多文史資料,都會有這樣的問題。美國史學界已討論過文史資料這樣的東西,你們也會用文史資料,怎麼用這些東西。因為它就是為了表現新中國和舊社會的差異,反差,它就是有一種程式化的寫法,把很多問題都掩蓋了,或是誇大,或是縮小。在文學和歷史界,我們把這種手法叫作敘述法,就是為了達到一些目的,把發生過的事情,重新整理一下,變成一種敘述模式。在這一過程中,往往有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目的在裡面。所以這種敘述法是非常不可取的。所以不要觀點先行,去誘導受訪者說些你想要得到的東西,這是不行的。

第二種非常重要的材料是檔案。我估計研究50年代以前,評彈的檔案不是很多,除了一些市政、書場建設有關的檔案以外,藝人本身的檔案不算多。50年代以後的檔案不少,主要是因為政府著力將包括評彈藝人在內的表演者變為“文化工作者”,所以他們有很多會議記錄、報告和調查,都是關於評彈藝人和他們的演出的。這些東西非常珍貴。而且檔案的另一個優點就是,它們往往能涉及一些在報紙上不大能看到的情況。因為在報上往往會表揚一些藝人,而且這些藝人往往是政治權威們比較喜歡的藝人,但是在檔案裡會出現一些,批評性的東西,指責性的東西,主要是針對那些單幹藝人,或者說集體所有制團的人員,這個東西在別的地方是不太常見的。當然,這些報告一般來說都是党幹部寫出來的,有很強的主觀性。但是另一方面來講,它確實提供了一些我們在其他地方所不能得到的資訊。所以檔案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檔案有它的缺點,這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它是不全面的。我可以肯定地說,57年反右和“文革”十年檔案是不公開的,沒有辦法去搜集的,這就是我跳過文化大革命這一段的原因,很難做。我覺得不大可能完全依靠訪談來做文化大革命評彈這一段。而且,檔案有個規定,就是三十年以前的東西,是開放的,三十以後的不開放。現在是2012年,那麼1982年之前的是應該開放的。但是有很多1982年之前的檔案,仍被關在那裡,不開放。即使開放的檔案,也被重新加密。例如,以前我看過一個檔案說,上海評彈團一些年輕團員,著名的餘紅仙,還有其他人,曾經在60年代申請過脫團,自己組織團,這本來是好事。但在意識形態的高壓下,這也變成一個問題了。這個檔案本來是開放過一陣子,但後來你再去找,就不見了。因為這可能牽扯到敏感人、敏感事,也可能牽扯到現在還活躍在舞臺上的一些人的事情。這很難說清楚原因,但是它就是發生了。
關於檔案保存問題,僅就上海檔案館而言,上海檔案館的電子化正在進行中,檔案電子化是好事。但很多東西掃描以後,就看不清了。因為人眼睛的解析度,比掃描器要高,所以看掃描之後的東西,就是一團黑,無法辨認。最近做的另外一個項目,是關於盛宣懷出殯的葬禮。以前的紙質的檔案裡,有一份地圖,是一份路線路,我本來想複印,但後來再去,就已經電子化了。現在調出來以後,全是黑的,無法辨析了。這成了破壞檔案了。
關於檔案的好處。不僅可以告訴你已經發生的事情,還可以告訴一些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比如吳宗錫。1951年他在軍管會文藝處工作,他給市政府打報告,希望市政府發文給文化部,提倡封殺四個評彈作品。理由是,這些作品是封建的、美化帝王將相的。這份報告上交後,又被打下來。因為文化部認為不能這樣粗暴地打壓評彈書目、戲目及藝人,這對包括評彈在內的戲曲的發展是不利的,對藝人的生活也是有害的。通過這一事件可知,包括吳宗錫在內的文藝處,他們確實是想禁掉一些書目。這件事把評彈改進協會搞得非常緊張。但這件事沒有實現,市政府和文化部都不同意。這就說明,通過檔案,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一些想做而又沒有做的事情。關於斬尾巴,1951 —1953年,表面上是藝人自覺自願地和封建殘餘說再見,斬掉封建的尾巴。但事實上,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卻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份報告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多內情沒有表現出來。所以檔案可以讓我們知道很多沒有發生的事情。美國有位歷史學家叫高錚,他的一本書講的是50年代中共新政權在杭州改造藝人的情況。他就提到,檔案可以讓我們知道很多沒有發生的事情。很多檔案的用紙,可以讓我們知道當時的一些條件。比如他發現,那些報告用紙其實用的是國民黨的紙,他只不過是反過來寫,由此可知當時經濟條件是不行的,資源是短缺的,就可以得出很多有意思的結論。當然檔案電子化之後,我們或許就不能再得到這些資訊了。所以,做這種事情,也要趁早做。
關於報紙,報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研究解放以前的評彈。那些小報,連篇累牘的報導,那些評彈藝人的演出,私生活,以及他們的種種情況。報紙是不可或缺的。對做民國史來說,報紙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做文化史、經濟史,社會史還好一些,做文化史根本就不能離開報紙。當然,研究解放以後的評彈,也是這樣的。但有個問題在於報紙的主觀性。報紙上很多內容,不是事實。報紙是人寫的,人是有他的偏見,他的主觀想像的。這種現象最嚴重的時期,就是在中國報業的初期,就是辛亥革命時期。很多人為了宣導辛亥革命,其實是把他的想像寫出來了,其實他們根本沒有看到漢口開戰,但是報紙上已經登出了。所以對於報導和事實之間就要非常地小心謹慎。話又說回來了,這個世界上到底有沒有事實,還是個問題。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度來解釋和詮釋一些事件。所以事實實際上是一些非常模糊的東西。做經濟史、社會史研究的學者可能不會同意我的這個說法,但文化史是這樣講的。
我在寫光裕事件的時候,用了很多《新蘇州報》的報導。因為《新蘇州報》是對這一事件報導最全面的,也是保存最好的。《新蘇州報》寫得非常全面,有很多細節可以用,但也有問題:首先,它是黨報;其次,《新蘇州報》的記者,本身是參加了“光裕事件”的調查的,它是偏向于文化局、潘伯英,還有蘇州政府的,並非完全公平公正的一方。它既是一個裁判,又是一個運動員。所以可以說它是一個被利用的平臺。當然,《新蘇州報》也給黃異庵,就是後來被稱為是“光裕事件”的領導人物,可能是一兩次機會,給他發一點聲音。從這裡我們也能看出,不光是文化局,協會藝人也是有聲音的。所以各種東西、各種材料,都要謹慎處理,仔細分清它的用處。
評彈和文學研究之間的關係。應該不光是評彈與文學之間的關係,而是評彈與文學研究之間的關係。當然,這裡的文學是泛指的概念,是包括戲曲、影視、小說等各種文學題材、體例,都在一起。我估計現在國內也是這種情況,就是說,影視研究和戲曲研究都屬於文學研究類。估計現在差不多也是這樣。為什麼研究評彈,我們必須學一點文學,我認為:第一點是源自中國的老傳統——文史不分家。中國的史學就是文學。比如,我們可以說,司馬遷的傳統,就是小說史的寫作傳統,很多小說家都把司馬遷作為鼻祖。司馬遷《史記》裡的《遊俠列傳》可以作為武俠小說的鼻祖,是沒有問題的。司馬遷寫東西,主觀性非常強。,他寫了誰和誰講話,誰和誰私密的談話,他怎麼會知道?我非常懷疑這一點。他其實加了個人的主觀想象。但是司馬遷的文筆非常好,感染力特別強,所以他非常成功。可以說他確實開創了中國史學與文學兩個傳統。另一個問題是中國敘述文學和現實主義的傳統問題。從西方來說,西方有史詩,就像荷馬史詩等英雄史詩,西方也有傳奇,有時候也翻譯成羅曼史,這些其實都成為西方敘述文體、西方小說的一個源頭。但是,中國是缺乏這個東西的。在中國,文學是分為兩大類,一個是韻文類的,如詩歌;一個是敘述類的,就是後來的小說類。中國沒有史詩和傳奇類的傳統,所以中國小說的源頭,包括現實主義的源頭,都是歷史,當然不光是正史,也包括野史。所謂小說,在中國傳統來說,只不過是野史類的一部分。所以如果看回19世紀晚期20世紀早期,很多小說都叫某某野史,稗類鈔之類,其實就是中國文史不分家在近代的一個縮影。
第二點,評彈是文學研究的一個方面。近幾十年來,評彈一直是作為文學的一個領域來研究的。西方研究評彈的學者中有一位叫白素貞,還有一位叫馬克,他們兩個都是從文學角度來研究的。另外一些研究,很多人從文本,即你們稱為擬彈詞,比如說陳端生的《再生緣》。它也是文學領域中的一個東西。《再生緣》已經被諸多大家研究過了。陳寅恪、郭沫若都研究過了。很多人研究擬彈詞,都是以文學角度來研究的。評彈一直是作為文學來研究的,所以研究評彈一定要知道一些文學方面的內容。從國內來看,周良一般是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的,他收集了很多資料,抄寫了很多東西,確實是居功至偉的。這是個歷史學的傳統。然後,吳宗錫先生一般是以文學戲曲的角度來研究的。吳宗錫當然跟他的個人背景和愛好有關係。吳宗錫以前不喜歡評彈,後來由於工作關係,慢慢喜歡上了評彈。他作為文學青年,在聖約翰大學的時候,喜歡詩歌、喜歡西方文學,他喜歡交響樂,他喜歡這些東西。所以他在後來的幾十年,陸陸續續寫了很多介紹評彈的東西,很多是以戲曲和文學的理論來研究的。他致力於一種叫“打通”的工程。“打通”是錢鐘書說的,就是把西方和東方的觀點和概念聯繫在一起。所以這也是一個文學傳統。

第三點原因就是文本分析的問題。其實我們研究評彈,不光是研究演員、組織結構、和國家的關係、和社會的關係。我們不可避免的要研究他們的長篇、中篇故事,就是我們要把這些故事作為一個文本來分析,就像分析小說和戲曲一樣,我們要分析作品的人物、我們要分析它的結構,我們要分析它的情節的變化,我們要分析它的高潮和最後結尾,這些一系列的東西。事實上,我們就是在研究文學作品。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所以,不學文學,我覺得就不好把握這個評彈文本。
而且文學的風格流派,在各個時代是不一樣的。比如說50年代的評彈,我們就必須得研究流行在50年代的、60年代的、70年代的中國的文學流派、風格。最簡單的例子:毛時代,那個時候就是提倡現實主義的東西,那你就必須研究一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才能結合評彈來探討,為什麼50年代以後產生的很多作品是這種的風格、這種的類型。所以如果要研究評彈的話,我覺得文本分析這一個功課還是要做的。
最後一點是與歷史學之間的關係。文學理論對歷史學的幫助。這個是蠻重要的。我們都瞭解,我們研究歷史,並不是真的坐著時間機器回到過去。去觀察什麼東西,已經發生過了。或是沒有發生過,我們不可能的。我們怎麼做?我們無非就是翻書、翻檔案、翻出版物、翻舊報紙。所以“故紙堆”,這三個字非常形象。我們就是翻舊的紙張,在那裡做研究,做分析,寫一點東西。所以,我們與過去的事件,中間有一個媒介,也可以說是一個障礙,就是一堆一堆的紙。當然現在紙都電子化了。所以我們其實不是在真的分析過去,我們是在分析過去留下的紙,而這些紙、這些檔、這些出版物、這些文章,是人寫的,它不是自然而然產生了的。這就和我們讀小說沒有區別。不知道大家會否同意我這個觀點。我們是在讀一個人寫的東西,也許小說家寫的是那種如《戰爭與和平》似的巨著,而那些寫檔案材料的人,只不過是文筆也不怎麼好,但確實是有人寫的,懷著一定的目的。有一個中心思想。我們是要處理這些東西,我們不是處理真正發生了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就是研究這些東西為什麼被寫出來,背後的目的是什麼?他為什麼要這樣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個與文學沒有區別。所以以前。有人探討過歷史學和各種理論之間的關係,各種理論包括社會學理論、政治學理論、文學理論。後來有人得出結論,應該是杜贊奇(印度人,在美國學中國歷史,現在新加坡)說的:文學理論可能是唯一可以直接應用到歷史研究上的,其他的理論都是要商榷的。所以歷史對我們來說,是文本,我必須要強調這一點。我們真的不能回到過去,去看那個三維的世界了。我們看的都是二維的,都是平整的一張一張的紙,這就是一個問題。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
但是,文學不能代替歷史研究。我們不能被文學的理論、文學的方法框住,這就是我講的評彈與文學研究的下一部分,即評彈研究應該跳出文學。為什麼?
第一、評彈本身的反文本傾向。我書稿的第一章很明確,評彈它就是反文本的。在1949年之前,沒有劇本的說法。在紙上寫完了一篇稿子,叫大家照本宣科去說書,這個藝人肯定就沒有生意了。所以,它必須是反文本的,藝人必須每天進行大量的閱讀,然後反饋給聽眾。他必須穿插,他必須加噱頭,他必須加很多很多即興演出的東西,這才是評彈的魅力。在解放前來說,頂多是腳本,沒有劇本,劇本是1949年以後才有的。我的書稿裡,已經明確地說明了評彈劇本的出現是在1949年之後的事情,而且劇本的產生是政府管理評彈的一種手段,就是讓它固定住。不讓藝人自由發揮。不讓藝人自由發揮是什麼意思?就是不許亂說亂動。美國學者白素貞曾經和金聲伯(說《包公》、《七俠五義》)有長期的接觸。白素貞跟他接觸下來之後,她就覺得評彈的文本化是一種失敗的形式。金聲伯的《白玉堂》是被出版過的,它是寫下來出版的。白素貞認為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評彈演出是三維的,它有語言、有動作,還有言下之意,用語言是不能表達,你必須在現場和藝人互動之後,才能體會到的東西。但出版之後,這些東西,全都就沒有了,全都變成了平面的、很死板的、很蒼白的東西。所以評彈不能被文本化,這絕對是正確的。後來白素貞得出一個結論,她其實是有點失望的。她認為評彈是不能被管理,不能被研究,不能被治理的。她一輩子研究“白玉堂”這個故事,從清朝一直流變到金聲伯。但她最後的結論是,也許我們的努力都是沒用的,因為你永遠不會知道他(指評彈藝人)當時是在說什麼,你只能大概知道這個故事結構,大概有這麼一個提綱。但是它裡面的“肉”,那些內容豐富的東西,其實是不能被瞭解的。我後來發揮了這個觀點,就是說審查也是非常艱難的,審查評彈節目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除非真的有人天天派幹部,坐在那裡聽評彈說什麼。哪怕幹部天天坐在那裡聽,他(指藝人)也可以有別的辦法來說。其實評彈藝人早就學會了看什麼人,說什麼話,這是他們的基本訓練。所以評彈是反文本的。

第二點,歷史是反理論的。其實剛才我已經有一點點說到。什麼是理論?社會學理論、政治學理論,理論就是給你一個模式。社會科學的寫作方法就是這樣,先把理論提出來,再把具體發生過的事情套進去,然後探討一下這個理論成立不成立,再結合這件事情,如果不成立,哪些變數是需要重新來修訂的,然後我們的理論如何再來完善一下,這就是社會科學方法的一種寫作和研究方法。但是歷史學不是這樣的。在我們歷史學研究中,我們不能腦子裡有一個假定的東西先行,然後找材料來證明我們的這個假定是正確的,或者來修正一下。我們必須用大量的事實在前,然後才能得出一個結論。而且歷史研究的一個任務是變化。我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事情、很多事物、很多機構、很多人物關係是會變化的,我們就是探討這些變化背後的經濟和原因。所以我們講的是一種變化,而不是一種固定模式。其實,歷史研究的一個要義就是變化。這一點和佛教很像。佛日:諸行無常。即一切事物都是變化的。這一秒看到的事情,將不是下一秒看到的事情,因為它已經變化了。我們人生的悲哀就在想抓住這一秒的東西,其實到了下一秒已經變掉了,已經抓不住了。所以。任何事情都有“成住壞空”這四個階段,“成”就是發生,“住”就是保持,“壞”就是毀滅,“空”就是歸於空掉,就是沒有了。其實,我們歷史研究,多多少少就是研究事情發生的變化及其背後的原因,所以沒有一種模式能夠框死我們的歷史學,我們研究的是時間的變化。即隨著時間變化所發生的變化。所以我們研究評彈的歷史變化。比如說我們研究為什麼評彈會在上海興盛。在這裡租界起了什麼作用?電臺起了什麼作用?在上海的蘇州人起了什麼作用?不要小看這股勢力,在上海的蘇州人以文人為多,他們的愛好、他們的努力和他們的貢獻,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上海評彈事業的發展。其實這些研究都很多。
最後一點,謹防中國文化的本質化、靜態化。一切事物都是變化的,評彈也是變化的。兩百年來,評彈已經變化了很多很多。以前哪裡有中篇評彈?以前哪有那麼多女下手?都是變化出來的。所以不要用靜態的眼光來看待評彈,不要本質化。什麼是本質化?本質就是認為,一樣事物是由本質決定的,而這一本質是不會隨著時間而變化的。對我們學習歷史專業的人來說,這是反歷史的,這是非歷史的。扯遠一點,以前歐洲有個漢學傳統,漢學傳統主要任務就是研究那些中國古代的一些事物、文化和組織機構等方面。一些極端的漢學家會提出這樣的觀點:中國文化到了唐朝,就是頂點,以後的中國,都是壞掉的中國,都是變異的中國,即不能稱為中國文化的中國。變化過的中國文化他就不承認是中國文化了。這是什麼觀點?這是明顯的帝國主義觀點。大家也許認為我用這個詞語,是上綱上線的,比較過時的,但是帝國主義這個詞在西方文化中運用的是很多的。什麼是帝國主義的文化觀點?一個落後地區或者是被殖民地區的文化,是固定的、是靜態的、是古代的、是過去的,是不會變的,只有來自宗主國、來自先進地區的人,他才能研究、探討、再現這一文化。這就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也就是說被殖民地區的人是無法理解他們自己的過去的。這個用馬克思的話,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說法蘭西農民是不能再現自己的,他們必須被再現。其實這個解釋也可以用在一些西方研究漢學的傳統上。
關於戲曲問題,文人認為:藝人是不能再現、不能理解藝人自己的藝術的。其實學文化史,進行文化研究,是一定要學馬克思主義的。也許因為馬克思主義教學現在有點教條化,所以你們有一種逆反心理。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是很多文化理論的源頭。包括結構主義,包括福柯,包括後現代主義等等。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在美國的一個比較文學的課上看的。
所以話說回來,我們必須強調的是一種變化的觀點。評彈這樣東西,在過去200年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就是要探討:發生了什麼變化?為什麼發生這一變化?至於好和壞,我不大喜歡在歷史研究中,說到什麼變好了,什麼變壞了,作者不要做出判斷。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為什麼我們要研究文化史?特別是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研究民國時期,為什麼不研究蔣介石?為什麼不去研究李宗仁?如果是研究文化史,為什麼不去研究胡適?為什麼不研究魯迅?為什麼不研究瞿秋白?可以說人家都研究過了,我再研究沒飯吃。這不是個理由,這是逃避。當然我們也可以這樣回答這個問題。大眾文化受眾面比較廣,聽眾觀眾比較多,我們通過研究這些東西,京劇、越劇、評彈各種其他曲藝。我們可以將這些東西作為切入點,來研究當時人民群眾,乃至整個社會的情況。這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們必須瞭解,娛樂這個事物的本身。是有重要性的。娛樂不是一個平時大家笑過就忘記的東西。
娛樂業產生於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以前農業社會最根本的區別,其實是時間概念的區別。就是說以前農民種地,就是春天忙一陣,秋天忙一陣,其實他的時間是可以自己控制的,不需要說八點一定要去田裡種地。可是一個人去上班就有一個紀律性在裡面,比如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當然以前資本主義沒有那麼開心的。八個小時的工作時間。但是總是有一種很強的節奏感,很強的紀律性,所以人生就變得非常的單調、無趣。怎麼辦?需要娛樂作為潤滑劑。所以娛樂不是可有可無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在工業社會,它是一種潤滑劑,是讓工人可以繼續工作的營養品或生活調劑,所以它本身是有經濟和社會意義的。到現在,我認為,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對娛樂功能沒有一個正確的評價,所以經常會有政府干涉一些娛樂節目的事情。娛樂本身哪怕它沒有做出很大的忠孝節義,愛國家、愛人民這樣的主題,但它還是有它的社會和經濟意義在裡面的。
研究娛樂業和大眾傳統文化成為一個學術問題,它是有幾個源頭。第一個源頭,就是中國的左派傳統。如果我們去看二三十年代瞿秋白寫的東西。瞿秋白就特別提倡要把“五更調”這種東西都發動起來,發動工人、發動農民。為什麼?因為他們是文盲,你不能指望寫些歐化的、白話文小說去感動那些工人農民,就是要用最傳統的方式來發動人民群眾。這是左派傳統。第二個研究流行文化大眾文化的源頭,是一種民族自豪感,一種文化的階級性,特別是50年代以後。新中國成立後,我們肯定認為什麼事情都是有階級性的,文化肯定也是有階級性的,在討論如何看待傳統文化這方面,主流觀點,或大多數時期的觀點都認為,文化是有階級性的。在毛時代肯定是這樣認為的:一部分是帝王將相的文化,比如說儒家文化;一部分是勞動人民的文化,比如說山歌、比如說戲曲和曲藝。這樣的東西變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民族文化,而受到重視,由此受到一些學者的追捧。所以這也是一個研究大眾文化的一個源頭。第三個,就是政府宣傳。評彈被稱為政治宣傳的文藝輕騎兵,即評彈可以很有效地深入到社會各個角落,農村、礦場等地。這就是政治宣傳的需要,所以包括評彈在內的各個曲藝的研究都受到重視。

從國際上來說,為什麼大眾流行文化會得到相當多學者的研究。第一點,從屬階級的研究。什麼是從屬階級?就是女性、奴隸、被殖民者。一切被壓迫的階級群體都可以被作為研究的物件。他們的文化也可以被研究的物件。這個思潮和二戰之後亞非拉各地去殖民化的浪潮是一致的。第二點,戰後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法蘭克福學派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20世紀革命的傳統沒有了?什麼是革命的傳統,比如說巴黎公社,為什麼20世紀人們再也不參加或者領導革命了?法蘭克福學派覺得這個大眾文化肯定起了一個反作用。它把一個一個的階級打碎了,變成了各種電影、戲曲、小說的觀眾和讀者。換言之,階級的覺悟性沒有了,所以它認為大眾文化是反作用的。從這個假定出發,他們研究了電影之類的大眾文化,這也是一個源頭。再近一些,比如英國的文化研究。這些文化研究的東西是起源於60年代,反文化、亞文化的。特別是年輕人中,那些喜歡搖滾、有吸毒經歷、留著長頭髮的年輕人。這個傳統其實也是個馬克思文化主義傳統,這個傳統就是反主流、反精英的文化。當然要研究文化對於每個人的關係,每個人對於自己的定位和看法。
以上所講都是源流,我覺得國內的史學界,精英主義的傾向還是明顯的。這個想法可能不那麼貼合實際,因為我對國內史學研究不是那麼瞭解。但我覺得國內史學主流仍然是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大眾傳統文化的研究,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作者:何其亮教授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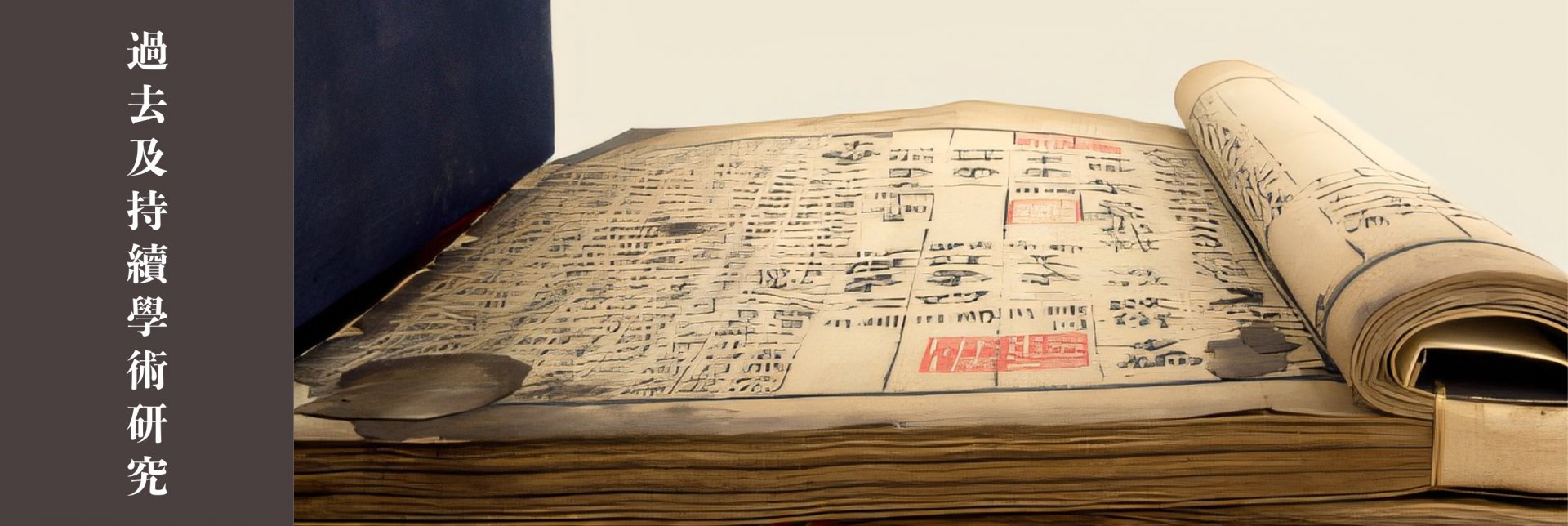



歡迎留言:
請登入/登記成為會員後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