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孟的勇
(修订稿)
我们为何要「勇」?自古以来,世界就有不平,社会就有不公义。人处身其中,一是同流合污,一是择善固执。君子可以亲,可以近,但不能劫,不能迫;可以杀,却不能辱。凡此种种行为,若没有了「勇」,是行不来的。具有寻求公义,勇往直前,择善而固执者,在先秦诸学说中,只有儒家思想有此气魄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八佾》) 孔子在此处说明「勇」必须具有无惧的本质,见到合乎义理的事情而不去处理,就是无勇。 可是,人生下来,如何培养这种见义而为的「勇」,人类又凭甚麽面对强权与欺压时,能力争公平合理?孟子在〈公孙丑〉一章中阐述「勇」的层次,并引例说明。孟子认为北宫黝的「勇」是自尊的勇,受辱而必还击;孟施舍的「勇」是忘记生死胜负的勇,没有所谓害怕不害怕;最后是行为合乎义理,其德配于天地的「勇」,此勇是至大至刚,有「千万人而吾往矣」的气概。
众多儒家思想论文中,专论「勇」的似乎不是很多,本文就此题目,作出较深入的阐释,且着意于实践方面。本文所引多是原始资料,所用皆流行本,故引用十三经及二十四史原文,不书明出版项,只写篇目、卷数。
在《论语》各章中,很少直接解释甚麽叫「勇」?然而,孔子常在行为表现上解说勇。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匡亚明解释:
智者由于他们的智慧,认识到行仁有利,他便行仁。这与仁人的不行仁便不安比起来虽然还逊一筹,已属难能可贵。智者能知人,能知言,因而可以通权达变。要成为仁人,只有仁没有智是不行的。勇即果敢,主要指道德实践方面的勇气。1
匡氏以「利」去解释智者行仁的思想,当然有点俗,但亦是反映一种普遍思维。正与墨家的「兼爱」,因为我爱你,所以你也爱我的回报式感情,毕竟较无私的爱低了一点。
当仁与智呈现,而面对公义时,如何能挺身维持义,就是勇的表现。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八佾》) 前句写不应谄媚他鬼以求福,指出所得必须符合正道;后句「见义不为」写勇气的基本来源,要激起内心对不公义的那点「火」,即不满。当人们有足够的智慧判断事情的道德性,知其为「义」时,却又不敢去实践,孔子认为这就是无勇。我们无「勇」,很多时是考虑到后果,譬如在街上我们看见有老人家被欺凌,上前制止,绝对是义的行为。可惜,我们会考虑他们是否一家人?别人的家事最好不管,或者欺凌者是谁?会不会惹上麻烦等?我们考虑后果,某程度上来说,都是智的表现,但行为呢?没有勇,就是不敢对不公义的事作出责难。有智了,有仁了,却没有勇,如此,则不能实践和发挥内在的道德,换句话,亦可说知与行不合一。儒家尚义,合乎义者,是不计较个人得失。张岱年对儒家、墨家的义、利有如下的阐释:
一说认为应当之表准即人民之大利或人群的公利。凡有利于大多数人民行为,即应当的;反之即不应当的。此墨家之学说。一说认为应当之表准在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凡表现或发挥人之所以为人的行为者的行为,即应当;反之即不应当的。此是儒家学说。2
张岱年在评定义与利范畴时,指出墨家的着重公利,即大部人的利益;而儒家是考量自己的行为是否人类独有,有异于禽兽。大部份人的利益,是量化,我们容易理解,但有异于禽兽的行为,就要特别解释。
所谓「人」,基本上可从两个概念去理解:一是生理人,即具有种种原始要求的身体的人,其行为乃随着身体的欲望而出发,即随感官觉受而行,没有思考伦理道理;二是仁人,即孔子所说「成人(仁)」,其行为本诸爱人而出发,即所谓仁者爱人,此即与禽兽有别的心。孟子十分强调要发挥此「心」,才能成仁,成君子。修仁就是要发挥与生俱来的人(仁)性,生活中的一切活动乃可全依仁而出发。3
所谓「生理人」,即具有与禽兽无别的欲望追求的生理人(动物性)。孔子、孟子从来没有否定此种生理需求的人,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明确指出饮饮食食,即身体五官的享用,及男男女女,即男女之间的爱慕,其终极的追求是延续生命及繁殖。此两种欲望是人类最大而且是最强的欲望,无可否认,此两种欲望是源于人类原始动物性,与禽兽共通。4若「饮食男女」附与人性,则有「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情操;男女肉体之爱可昇华至亲人伦理的层面,家就成为终日忙碌后的安身处,因为中间有爱存在,继而孝、悌,道德伦理就在此处开展。「扬名声、显父母」,自己的成就,与整个家族结合,荣辱共存。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 在面对欲望时,我们会犹疑,犯错,可是,我们要重视自己的行为,认真思考,在不断改过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能有不断自我提升的力量,认认真真面对自己的过失,需要莫大的勇气。
对勇作一简单的解说就是「胆量」与志气,要有勇气指正不正确的行为,包括在内,即自己的行为,过失;在外,即社会上种种不义的行为。如果勇,得不到适当的发挥,反而有害于社会。
有勇,有胆量,却未能掌握就会造成溷乱。大贼有胆量,劫匪有胆量,恶霸有胆量,这些都是为自身利益而出发的勇。这些勇,只会对社会造成溷乱,而这种勇是会气馁的,因为有愧于心。
孔子批评子路「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指出子路的勇较孔子还要高,可是子路不懂得去掌握,适当地显示自己的勇5。不适当的勇会造成溷乱的后果,如:「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 如果勇不受礼的约束,则容易产生乱。同样的,「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论语.泰伯》) 这句朱熹的解释是「好勇而不安分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6我对朱熹的解释有所保留,勇而不安份,而是乱的源头,解释合理。但人而不仁,为何不能「疾之已甚」?如果解作人而不仁的行为,是施者的行为,似较合理,即此人的不仁太过份了,也是乱的根源。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如果勇缺乏「礼」的调和,会乱;如果勇,不能安贫,会乱;如果勇,没有学养,一样乱。所谓「乱」,其小可令人不安,其极可致国家动乱,不可不慎。
又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明显说出,仁者必然具备勇,反过来,勇者未必有仁心。仁者有追求公义的心,也付诸实践,故不可能没有勇。乱世中,对着强权说公义,这「勇」,不可谓小。但我们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何我要有勇去挑战不公义?即:为何是我?这个就是涉及悲天悯人的仁者之心,亦即是道德的自觉,也可以说是不忍之心的呈现。这个「心」,这个「自觉」就是与禽兽有别的人类独有的自性。若果「人」,不从这心出发,去扩展对别人的善意,就浪费了人类独有的「性」。
「勇」是一种力。他可以推动道德,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另一方面,却可以是乱的根源。《红楼梦》的名句「拚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就是连死都不怕,任何事都「够胆量」去做,包括不公义的事,容易造成乱。如「勇」与「不忍」、「悲悯」同时呈现,就可以惊天动地,独对强权而自然,面对横逆而自省的行为。孔子对着横蛮的诸侯,耶稣对着传统势力,甘地面对英国政府,曼德拉对着南非白人政府等等,身处的环境,包括威逼与引诱,「勇」这时必须成为道德最大的支持动力。
「勇」该如何适当的呈现?勇必须有「志」,即目标或道德界线去维持。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朱熹解说匹夫之志在己,故不能夺,可夺者则不是志。有这个「志」,勇就随之而来,因为要成就自己的志。
孟子亦有解释这个「志」: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7
孔孟所说的「不惑」和「不动心」是指不受外界功名利禄所引诱,亦不受媚辞谄语所迷惑。人生经验丰富,阅历足够,对自己的行事认真反省,相信已有能力和经验去判断是非黑白,亦能分辨出哪些说话是真?哪些是假?这个能判断的心,再进就是不动,自己成为自己「心」的主宰。
孟子为何说「告子先我不动心」。我想有两个理由,一是不动心很容易,连告子也可以,似有讽刺的意味,二是只要想达到,就能达到,告子也不动心。内文又说「先我」,孟子究竟这样说?真的要慢慢推敲。
告子的「言、心、气」关係,朱子有这样的解释:
告子谓于言有所不达,则当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于心有所不安,则当力製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于气,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动之速也。
朱子认为告子的意思是语言不能表达的,就放弃用语言表达,也不必寻求于「心」的理解;心不能思虑完满的,不必求助于气。这样,就可以加强不动心了。杨伯峻将言训为言语、心训为思想、气训为意气8。「气」,有两种理解,一是赵岐所解释的,是「直怒之气」,即为感情之情,动于五中而引起的情绪;二是体气,即人的气魄。杨伯峻认为,孟子本章的「气」是具有这两种涵义。9
孟子贊成「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但反对「不得于言,勿求于心」的论点。孟子解释「志、气、心」的关係是志是带动气的主体,气能充盈整个身体。故此,志要达到甚麽程度,气就能到达甚麽程度。所以,要有坚定的志,不随便暴露自己的气。志专一则能动气,气专一则能鼓志。倘若有气而没志,就会动了心。动了甚麽的心,就是趋炎附势,向名向利不择手段的心。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孟子,如果我们不能说服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则不必坚持;但说服不了自己,就必须寻求思想上的理解,去判断是与非。
心受外缘影响,产生种种欲望,寻求欲望的力同样的大,倘若有志,去带领内在的气,则可化成浩然正气,至大至刚。用另一种方法解释,志就目标,定立目标要有道德,即正心。心已正,所行虽不中,亦不远矣。气有正邪,立心坏则气邪,立心正则气正。但「心」,经常受外缘引诱其离正道,故心要不动。
如何发挥勇。我们有志,这个志可以是公义。我们追求公义而不得,就力求,求之以道,求之以礼。合道合礼,则气魄自在。就算是君子,若果勇没有义在其中,亦是乱。义,简单理解是「公平合理」。匡亚明认为孔子论勇一般是侧重道德方面,未能全面展示智勇的内容。10义与利两者所产生的矛盾,就是孔子冀望能在伦理道德中得到平衡。《易‧乾卦‧文言》:「利者义之和也。」讲的就是义与利之间的和谐。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篡弑频仍,公平合理很难出现,但这是君子所追求的道义,故勇必然随之而至。我们会面对现实的不公世界,但精神上要追求合乎公义的社会。
若再深入阐释义,就要考虑孔子的思想及所处的环境。孔子的最高理想社会是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结构型态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二千多年下来,我们人类仍赞歎渴望这种社会的出现,寻求「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公义社会,反过来说,不讲信,老无所终,壮无所用,矜寡孤独废疾而无所养者就是不公义。另外,孔子所处的年代是战争频仍,统治者横徵暴敛,过着奢豪的生活,而人民却难得到饱足。故孔子提出「义然后取」、「见利思义」等行为,作为衡量提出他人利益的准则。《论语.阳货》: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有勇而无义为盗」,勇必须蕴涵「义」才是正道的勇。无论如何!人人饱足,贫富平均,人尽其力,在当时来说,只是理想。
当义利产生矛盾时,孔子必然是取义而捨利,如: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富与贵,是人人所期望的,但「不以其道」,即不合乎公义者,绝对不取,强调公义与合理。造次颠沛亦必然如此,当然,孔子指出这因为有仁者之心在,但能有造次颠沛的环境中,依然故我,这是勇的表现。孔子更说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豪语。当公义与富贵在眼前时,应毫不考虑的取义。取义这一行为,不可能没有「勇」为支持。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论语.阳货》)
此节经常发生在公事,不通情达理以为是行政,没有礼貌以为是勇敢率直。果然,这现象,仍然每日都见到。勇可见于日常人类的交往中,亦可见于国与国的交际中。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孔子答子路「成人」,举出臧武仲、公绰、卞庄子、冉求等人,却又再进而解释,如果能腹「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亦可以为成人。「见利思义」,一定要思考自己取利的行为是否合乎义,义是志,志是勇的来源。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所谓「夫子自道」,是孔子已具有仁、知、勇三种道德涵养。又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孔子反複的说,勇是一种动力的运用,这种勇气随着蕴涵者的内在意志而变动。所以,勇的运用是配合道德的运用方能成其大,反之,这种没有道德的勇,是乱的根源。
下列两则语录,表面与勇没有关係,其实内裡必然有勇的存在: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我们对人对事,行为与态度,直接反映自我们的内心,我们得罪了某些人而会害怕,做错某些事而惊慌。但「内省不疚」,就不忧不惧。留意,孔子说「勇者无惧」,是任何行为,经过反複思量,而确定毫无私心,合乎公义,这样才能产生不忧不惧。如何肯定自己的行为,至纯至真,就是勇者气的根源处。此节所指出的气魄,是纯然道德行为,试问,有几人能无私心?
绝粮而从者病,此环境若近绝境,子路生怨,而孔子说「君子固穷」。如此,则君子处于任何环境,必然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从精神高处看命,看环境,其心能处于适时顺世之境界。这种穷而坚守,穷而知命,不是勇,是甚麽?
孔子一生,从自己的行为表现去验证自己的境界。孔子的志是甚麽?继承尧、舜、汤、文、武传下来的文化道统。孔子困于匡,被误会是阳虎。弟子皆慌张,孔子却说出:「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这个就是志,勇是来自志,孔子的志是继承文王道统,要发扬光大。我相信孔子是认为这就是他来这世界的责任,故可以毫不恐惧的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豪言。
「夹谷之会」,孔子身为司寇,两度走上臺阶,制止齐国的无礼。一是齐国地方舞的表演,拿了盾、枪、旗、棒等表演。孔子喝止,避免齐国阴谋得逞。再者是表演宫廷音乐,毫不合章法。孔子认为是戏弄诸侯,请斩表演者。11最后,是齐国觉得自己理亏,归还鲁国城池郓、灌及龟阴三地。在一个国际会议场合,其实一切有所规定,孔子据礼而争,力挫齐国君臣,中间所显示的勇和气魄,震摄人魂。千秋以后,读之仍觉气魄充盈,合礼合节。
孔子总结一个寻求完满生命的人,他对勇有如此的总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孟子重要思想之一,是正气,这个「气」是不得了,此亦是后世儒者所嚮慕的境界。要清楚这个气的养成,要先从「不动心」说起。《公孙丑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不动心」是甚麽?孔子说「四十而不惑」,孟子说「四十不动心」,又为甚麽是四十?上文已提及是修养与阅历已达一定程度,便有此成就,此处不赘。〈公孙丑上〉又载:
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孟子首先指出三种不同的勇:北宫黝、孟施舍及曾子。此节要特别留意「养勇」的「养」字。养有培养、贮藏的意思,即是我们的勇是一步一步的累积而成。譬如小时候,遭受欺凌,一般不敢作声,人渐长,愈明白事理,会据理力争。这是一般人成长的过程,当然,勇的程度,因人,因时,因境,因利而各有不同。普通人的勇大多是来自意气或是利益,当然亦有来自高尚的情操,我只指出普遍性的勇。记得很多报章报导血案时,都说是一时冲动,弄伤甚至杀死对方。很多抗争的口号,是为公义和公理而战,但当中又有几多是为利而来?
北宫黝的勇,我认为是来自「自尊」,当中记载「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自尊与耻辱,就成为勇的行为的推动者。明显指出北宫黝是不接受任何伤害其自尊的侮辱行为,包括微不足道的语言说话。一个人连自己都不尊重自己,别人会尊重吗?这就是自尊的问题,即北宫黝不会忍受任何的耻辱,其前题是北宫黝是不会做令自己受辱的事。人必须自重,别人才尊重你。
孟施舍的勇是不理会生死胜败,只专心一致完成任务。原文「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视不胜犹胜,就是忘记失败后,可能会死亡这一节。这种忘却成败得失的勇,是目空一切,眼前只有如何去战的思维,已超越一切恐惧。所谓「除死无大碍」,连死亡都不怕,那还有甚麽好害怕?
两者的勇,最后是成就曾子的勇,孟子说第三个勇的层次是经过深思熟虑,知道自己的行为合乎义,合乎理,则「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此语,直是石破天惊,气势澎湃。我们亦应思考,甚麽是正确,甚麽是不正确?这点是非常重要,因为误判道德,其行为适得其反。
然而,我相信能到达第三层次的勇者必然具有前两者的特质,即重视自己的尊严和忘记生死成败。礼记儒行篇:「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个自尊不比平常的面子问题,而是受辱。笔者在很多场合遇见营营役役,为利奔走的人常常受辱。谋生养家是天职,但如何能不受辱,就是自己平日处事态度所致。可杀不可辱的勇、的气魄,是自我道德的确定,道德行为的乌确立,认知此心,此勇的来源,才能出现。
这种具有浩然正气的勇是来自「不动心」,继而「持其志,无暴其气」,再而「养气」。这种「气」,必须配合义与道,倘若无义或无道,则会衰退如此,所以说「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对慊有更深入的诠释:「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公孙丑下》) 别人可夸富夸贵,而君子所持的就是仁和义。唐君毅先生说:
孟子以养气之道在集义,而配义与道。道者当然之理,义者知此当然之理而为之,即知理而行之,以合当然之理。故养气必先『志于道』。12
这种气是「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閒」。冯友兰对浩然之气有这样的诠释:
如孟子哲学中果有神秘主义,则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即个人在最高境界中的精神状态。…此所谓义,大概包括吾人性中所有善「端」。是在内本有,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也。」此诸善「端」皆倾向于取消人我界限。即将此逐渐推扩,亦勿急躁求速,亦勿停止不进,…「集义」既久,行无「不慊于心」,而「塞乎天地之间」之精神状态,可得到矣。13
唐、冯两位先生都指出,要培养这种气,是要时时刻刻想着「义」和「道」,思考人类的善性,思考人类合乎道义的行为,久而久之,储养一定的气,当遇到事情时,思考其行为的合理性、公义性,如此,浩然之气自出,否则「馁」。能完善自己的道德行为,能合乎道义,则大勇之行为,将得到成就。
孟子是不重视主宰的天,而重视「义理之天」,认为人的心性觉悟是得之天理,故视仁义忠信,乃天爵。公卿大夫,乃人爵。他慨歎:「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今人只顾追逐明利爵禄,而忽略了上天付与的道德良知,此道德良知包含仁义忠信。若仁义忠信蕴涵于内,则不能坐视不公义事,此即「勇」的来源。
从《孟子》一书,我们可以窥见孟子的勇。孟子以继承孔子自居,力排当时流行的极端利己主义,不仁的法家思想和不分等差伦理的墨家。显示出「舍我其谁」的气魄,英气勃勃,刚气迫人,正如孟子自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梁惠王上》: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傢,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傢;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傢。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多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叟」一词是强烈的不尊重,虽然未有定论,但也称不上是尊重。从惠王初见孟子的态度,我们可以想象,孟子谈仁义,惠王却不愿的矛盾状态。面对国君,处于征战连绵的时代,孟子却直接了当的说「何必曰利」。若以「识时务」来判断孟子,就是不识时务。可是,孟子坚持自己理想,极力向惠王推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就是孟子的「义」,不能不说「仁义」。
下列数节,都是孟子面对国君,直接指出他们的错处,用辞不亢不卑,一些辞句,更是振聋发聩。
《孟子‧离娄下》: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虽然君主是高高在上,但臣下不一定绝对服从。态度方面,君臣之间要互相尊重,视我如手足,则我视汝为腹心。若视我如土芥,则我亦不必尊重你,虽然你有君主的身份,但你不尊重人,人亦不必尊重。这与后皇朝常说「君要臣死,臣不死视为不忠」的荒谬理论,恰好相反。
《孟子‧梁惠王下》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云:『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齐宣王不愿行仁政,因为自己好货好色,故不能行仁政。宣王以为仁政是与好货好色相违背,但孟子举史例直斥其非。最后,更引用譬喻,说明宣王不行仁政而令致国家不定安,借题发挥,问宣王如何处理「四境之内不治」的责任,令宣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万章下》: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複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
《孟子‧尽心下》: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上引两节,真是有惊天动地的气慨,试想一个国家元首在你面前,质问元首行暴政,是不是要推翻?有几多学者能人,能直接说身为元首国君,倘残害百姓,不能算是国君,就算杀了他,都只杀了一个满身私欲,害人无数的匹夫。从这角度去看,在孟子心目中,国君是一份职责,他必须为自己所处的地位而付出必要的心力,否则,这个人死不足惜。我们将此验证于后世君主,相信死后腐骨仍流汗。
齐宣王再问卿,孟子的答案就是后世所指的「十恶不赦」的谋反罪。君主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只顾享乐,就应该推翻这政权。所以,孟子的结论是民为贵,而君主最卑。不要少看这几节引文,千秋而下,仍感觉其凛凛风骨,真是惟大丈夫能本色。现代的中国人,或许与孟子有同样的理念,但对着高官权贵,能有足够的胆量这样表达自己吗?若不是对自己所认知的道德与理念,有绝对的信心,根本说不出这些话来。可是,我们要留意的事,孟子没有用带有侮辱性的辞语责难,只希望国君从对话中,触动起怜悯他人的悲心,减少私欲。你有权,你有势,但我有的是公义。甚麽是勇?请看孟子的行为言论。
《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捨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上节是孟子不遇时,去齐之语。虽然有客欲为齐王挽留孟子,从但孟子告诉来者,来者游说的应是齐王。孟子不豫是因为五百年将有王者兴,现在过了五百年,尚未见王者。这裡有两重意思,王者未兴,孟子推说是天不欲天下治,若果「天」希望天下大治,能用的只有孟子。其第二重意思是自己是惟一儒家道统的继承人。
张岱年:
所谓士节即坚持自己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包括人格独立意识与社会责任心,乃是人格独立意识与社会责任心的统一。一方面要坚持独立人格,不随风摇摆,不屈服于权势;另一方面更有社会责任心,不忘记自己对于社会应尽的义务。14
为坚持独立人格,为社会应尽的义务,背后是要与多少贪官污吏和既得利益者周旋。偶一失误,则自陷泥淖。「勇」,说来只一字,行来千万斤重。
我认为培养「勇」的第一步,是维持自尊,而生命所涉及的层面,必然包括物欲。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两种欲望:饮食、男女,是人类最大的渴求,要进入忘记生死成败的阶段,必须将欲望降至最低,「无欲则刚」是一种气魄,亦是一种修炼,使之成无欲的气,行为则刚。古今中外学者都将男女饮食作为「人」第一步的追求,如马斯劳(MarslowA.H.,1908-1970) 提出人类需求的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就是要首先满足;佛洛伊德(Freud, Sigmund,1856-1939)亦认为人的「本我」(id) 是饿、渴、睡、性等原始需求所推动。因此,我认为欲望是一切不道德行为的来源。减低欲望,或适当调节欲望,才可提升道德境界。这样,我们才可以培养浩然之气,使之长,不使之馁,要经常提醒自己,生命的价值何在。
较高的层次,是超越生死,即有些东西令你愿意牺牲。蔡仁厚:
孟子指出,人所愿欲的东西有超乎生命之上的,所以不愿意苟且偷生;人所憎恶的物事亦有甚于死亡的,所以人有时并逃避死亡的祸患。…而是想成就生命的纯洁清白,以免陷于不义而受辱,故能毅然以有限的生命,换取无限的精神价值。15
即所谓所恶有甚于死者,中国史上,为天下公义,为推翻暴政,前仆后继。这不独是儒家的理论,是普遍的真理。人类的悲悯之心起动,就愿意为其他人牺牲。但这牺牲,是否合乎仁义?另作别论。例如某人要「报仇」,仇超越了生命,但合乎义吗?
有了超越生死的勇,就要思想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义」?第三层次就是经反複思量,自觉行为与道德均合乎公义,寻求社会公义乃自我的责任,则自然产生杀身成仁,捨生取义的气魄。孔孟的理论,能贮大勇于后世士子,就在这节。颜杲卿痛骂安禄山,逼之以杀子,诱之以高禄,终不为所动,以致被节解断舌16,其情惨烈,但背后是大勇表现,持义以抗。张巡碎齿抗贼,被执神色若然,至死毫无惧色。17这些都是孔孟思想所蕴涵的大勇,就是超越生死的大勇。大勇是集义而至,合乎一切的公义,就有此气度。
孔孟认为君子是「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能够有这样的气魄的人物,必然是大仁大勇者。笔者每每读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就觉有沉重感。当中的责任感,当中不放弃的勇,是仁者、勇者的路向,不得不礼敬孔、孟。
脚注 :
1. 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223。
2.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页354。
3. 参考拙着〈论孟子「人」与「禽兽」之别〉,收在《「第二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孔教学院,2006年。
4. 同上注
5.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八佾》)
6. (宋) 朱熹:《四书集注》,香港:大中图书,出版年缺,〈上论‧卷四〉页52。
7. (宋) 朱熹:《四书集注》,香港:大中图书,出版年缺,〈上孟‧卷二‧公孙丑上〉,页38。
8.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页65。
9. 同上注,页70,注释22。
10. 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223。
11. 事见《史记‧孔子世家》。
1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台北:学生书局,页615。
1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02-103。
14.张岱年《心灵与境界》,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页300。
15. 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北:学生书局,1999年,页279-280。
16.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15,列传117〈忠义中‧颜杲卿传〉载:「贼胁使降,不应。取少子季明加刃颈上曰:『降我,当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卢逖杀之。杲卿至洛阳,禄山怒曰:『吾擢尔太守,何所负而反?』杲卿瞋目骂曰:『汝营州牧羊羯奴耳,窃荷恩宠,天子负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义,恨不斩汝以谢上,从尔反耶?』禄山不胜忿,缚之天津桥柱,节解以肉啖之,骂不绝,贼钩断其舌,曰:『復能骂否?』杲卿含煳而绝,年六十五。」
17. 同上注,卷215,列传117〈忠义中‧张巡传〉载:「城遂陷,与远俱执。巡众见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众不能仰视。子琦谓巡曰:『闻公督战,大呼辄眦裂血面,嚼齿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气吞逆贼,顾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齿存者三四。巡骂曰:『我为君父死,尔附贼,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节,将释之。或曰:『彼守义者,乌肯为我用?且得众心,不可留。』乃以刃胁降,巡不屈。又降霁云,未应。巡呼曰:「南八!男儿死尔,不可为不义屈!』霁云笑曰:『欲将有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与姚訚、雷万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
原載於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及樹仁大學中文系編《2012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 原创文章/视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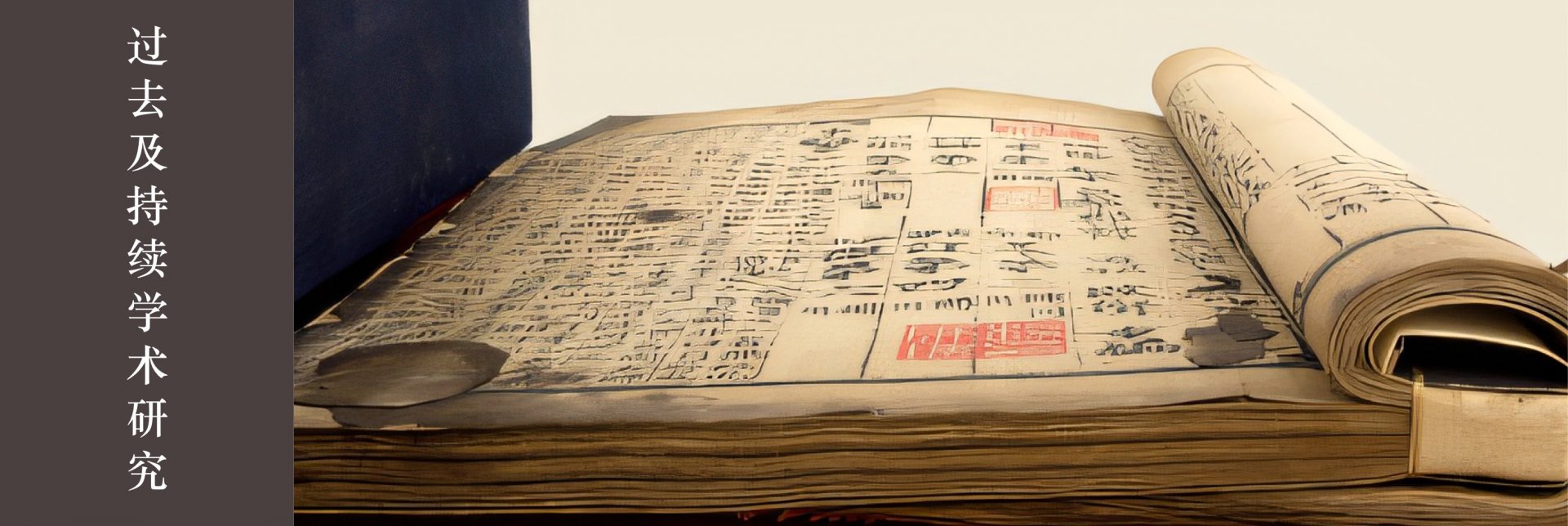



欢迎留言:
请登入/登记成为会员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