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孔、孟的勇
(修訂稿)
我們為何要「勇」?自古以來,世界就有不平,社會就有不公義。人處身其中,一是同流合污,一是擇善固執。君子可以親,可以近,但不能劫,不能迫;可以殺,卻不能辱。凡此種種行為,若沒有了「勇」,是行不來的。具有尋求公義,勇往直前,擇善而固執者,在先秦諸學說中,只有儒家思想有此氣魄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 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八佾》) 孔子在此處說明「勇」必須具有無懼的本質,見到合乎義理的事情而不去處理,就是無勇。 可是,人生下來,如何培養這種見義而為的「勇」,人類又憑甚麼面對強權與欺壓時,能力爭公平合理?孟子在〈公孫丑〉一章中闡述「勇」的層次,並引例說明。孟子認為北宮黝的「勇」是自尊的勇,受辱而必還擊;孟施舍的「勇」是忘記生死勝負的勇,沒有所謂害怕不害怕;最後是行為合乎義理,其德配於天地的「勇」,此勇是至大至剛,有「千萬人而吾往矣」的氣概。
眾多儒家思想論文中,專論「勇」的似乎不是很多,本文就此題目,作出較深入的闡釋,且著意於實踐方面。本文所引多是原始資料,所用皆流行本,故引用十三經及二十四史原文,不書明出版項,只寫篇目、卷數。
在《論語》各章中,很少直接解釋甚麼叫「勇」?然而,孔子常在行為表現上解說勇。孔子認為君子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匡亞明解釋:
智者由於他們的智慧,認識到行仁有利,他便行仁。這與仁人的不行仁便不安比起來雖然還遜一籌,已屬難能可貴。智者能知人,能知言,因而可以通權達變。要成為仁人,只有仁沒有智是不行的。勇即果敢,主要指道德實踐方面的勇氣。1
匡氏以「利」去解釋智者行仁的思想,當然有點俗,但亦是反映一種普遍思維。正與墨家的「兼愛」,因為我愛你,所以你也愛我的回報式感情,畢竟較無私的愛低了一點。
當仁與智呈現,而面對公義時,如何能挺身維持義,就是勇的表現。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八佾》) 前句寫不應諂媚他鬼以求福,指出所得必須符合正道;後句「見義不為」寫勇氣的基本來源,要激起內心對不公義的那點「火」,即不滿。當人們有足夠的智慧判斷事情的道德性,知其為「義」時,卻又不敢去實踐,孔子認為這就是無勇。我們無「勇」,很多時是考慮到後果,譬如在街上我們看見有老人家被欺凌,上前制止,絕對是義的行為。可惜,我們會考慮他們是否一家人?別人的家事最好不管,或者欺凌者是誰?會不會惹上麻煩等?我們考慮後果,某程度上來說,都是智的表現,但行為呢?沒有勇,就是不敢對不公義的事作出責難。有智了,有仁了,卻沒有勇,如此,則不能實踐和發揮內在的道德,換句話,亦可說知與行不合一。儒家尚義,合乎義者,是不計較個人得失。張岱年對儒家、墨家的義、利有如下的闡釋:
一說認為應當之表准即人民之大利或人群的公利。凡有利於大多數人民行為,即應當的;反之即不應當的。此墨家之學說。一說認為應當之表准在於人之所以為人者,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凡表現或發揮人之所以為人的行為者的行為,即應當;反之即不應當的。此是儒家學說。2
張岱年在評定義與利範疇時,指出墨家的著重公利,即大部人的利益;而儒家是考量自己的行為是否人類獨有,有異於禽獸。大部份人的利益,是量化,我們容易理解,但有異於禽獸的行為,就要特別解釋。
所謂「人」,基本上可從兩個概念去理解:一是生理人,即具有種種原始要求的身體的人,其行為乃隨著身體的欲望而出發,即隨感官覺受而行,沒有思考倫理道理;二是仁人,即孔子所說「成人(仁)」,其行為本諸愛人而出發,即所謂仁者愛人,此即與禽獸有別的心。孟子十分強調要發揮此「心」,才能成仁,成君子。修仁就是要發揮與生俱來的人(仁)性,生活中的一切活動乃可全依仁而出發。3
所謂「生理人」,即具有與禽獸無別的欲望追求的生理人(動物性)。孔子、孟子從來沒有否定此種生理需求的人,孔子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明確指出飲飲食食,即身體五官的享用,及男男女女,即男女之間的愛慕,其終極的追求是延續生命及繁殖。此兩種欲望是人類最大而且是最強的欲望,無可否認,此兩種欲望是源於人類原始動物性,與禽獸共通。4若「飲食男女」附與人性,則有「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的情操;男女肉體之愛可昇華至親人倫理的層面,家就成為終日忙碌後的安身處,因為中間有愛存在,繼而孝、悌,道德倫理就在此處開展。「揚名聲、顯父母」,自己的成就,與整個家族結合,榮辱共存。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 在面對欲望時,我們會猶疑,犯錯,可是,我們要重視自己的行為,認真思考,在不斷改過的過程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能有不斷自我提升的力量,認認真真面對自己的過失,需要莫大的勇氣。
對勇作一簡單的解說就是「膽量」與志氣,要有勇氣指正不正確的行為,包括在內,即自己的行為,過失;在外,即社會上種種不義的行為。如果勇,得不到適當的發揮,反而有害於社會。
有勇,有膽量,卻未能掌握就會造成混亂。大賊有膽量,劫匪有膽量,惡霸有膽量,這些都是為自身利益而出發的勇。這些勇,只會對社會造成混亂,而這種勇是會氣餒的,因為有愧於心。
孔子批評子路「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指出子路的勇較孔子還要高,可是子路不懂得去掌握,適當地顯示自己的勇5。不適當的勇會造成混亂的後果,如:「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論語.泰伯》) 如果勇不受禮的約束,則容易產生亂。同樣的,「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論語.泰伯》) 這句朱熹的解釋是「好勇而不安分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6我對朱熹的解釋有所保留,勇而不安份,而是亂的源頭,解釋合理。但人而不仁,為何不能「疾之已甚」?如果解作人而不仁的行為,是施者的行為,似較合理,即此人的不仁太過份了,也是亂的根源。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論語.陽貨》)
如果勇缺乏「禮」的調和,會亂;如果勇,不能安貧,會亂;如果勇,沒有學養,一樣亂。所謂「亂」,其小可令人不安,其極可致國家動亂,不可不慎。
又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明顯說出,仁者必然具備勇,反過來,勇者未必有仁心。仁者有追求公義的心,也付諸實踐,故不可能沒有勇。亂世中,對著強權說公義,這「勇」,不可謂小。但我們會出現另一個問題,就是:為何我要有勇去挑戰不公義?即:為何是我?這個就是涉及悲天憫人的仁者之心,亦即是道德的自覺,也可以說是不忍之心的呈現。這個「心」,這個「自覺」就是與禽獸有別的人類獨有的自性。若果「人」,不從這心出發,去擴展對別人的善意,就浪費了人類獨有的「性」。
「勇」是一種力。他可以推動道德,可以驚天地,泣鬼神;另一方面,卻可以是亂的根源。《紅樓夢》的名句「拚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就是連死都不怕,任何事都「夠膽量」去做,包括不公義的事,容易造成亂。如「勇」與「不忍」、「悲憫」同時呈現,就可以驚天動地,獨對強權而自然,面對橫逆而自省的行為。孔子對著橫蠻的諸侯,耶穌對著傳統勢力,甘地面對英國政府,曼德拉對著南非白人政府等等,身處的環境,包括威逼與引誘,「勇」這時必須成為道德最大的支持動力。
「勇」該如何適當的呈現?勇必須有「志」,即目標或道德界線去維持。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朱熹解說匹夫之志在己,故不能奪,可奪者則不是志。有這個「志」,勇就隨之而來,因為要成就自己的志。
孟子亦有解釋這個「志」: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7
孔孟所說的「不惑」和「不動心」是指不受外界功名利祿所引誘,亦不受媚辭諂語所迷惑。人生經驗豐富,閱歷足夠,對自己的行事認真反省,相信已有能力和經驗去判斷是非黑白,亦能分辨出哪些說話是真?哪些是假?這個能判斷的心,再進就是不動,自己成為自己「心」的主宰。
孟子為何說「告子先我不動心」。我想有兩個理由,一是不動心很容易,連告子也可以,似有諷刺的意味,二是只要想達到,就能達到,告子也不動心。內文又說「先我」,孟子究竟這樣說?真的要慢慢推敲。
告子的「言、心、氣」關係,朱子有這樣的解釋:
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製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
朱子認為告子的意思是語言不能表達的,就放棄用語言表達,也不必尋求於「心」的理解;心不能思慮完滿的,不必求助於氣。這樣,就可以加強不動心了。楊伯峻將言訓為言語、心訓為思想、氣訓為意氣8。「氣」,有兩種理解,一是趙岐所解釋的,是「直怒之氣」,即為感情之情,動於五中而引起的情緒;二是體氣,即人的氣魄。楊伯峻認為,孟子本章的「氣」是具有這兩種涵義。9
孟子贊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但反對「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的論點。孟子解釋「志、氣、心」的關係是志是帶動氣的主體,氣能充盈整個身體。故此,志要達到甚麼程度,氣就能到達甚麼程度。所以,要有堅定的志,不隨便暴露自己的氣。志專一則能動氣,氣專一則能鼓志。倘若有氣而沒志,就會動了心。動了甚麼的心,就是趨炎附勢,向名向利不擇手段的心。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孟子,如果我們不能說服自己的行為是否正確,則不必堅持;但說服不了自己,就必須尋求思想上的理解,去判斷是與非。
心受外緣影響,產生種種欲望,尋求欲望的力同樣的大,倘若有志,去帶領內在的氣,則可化成浩然正氣,至大至剛。用另一種方法解釋,志就目標,定立目標要有道德,即正心。心已正,所行雖不中,亦不遠矣。氣有正邪,立心壞則氣邪,立心正則氣正。但「心」,經常受外緣引誘其離正道,故心要不動。
如何發揮勇。我們有志,這個志可以是公義。我們追求公義而不得,就力求,求之以道,求之以禮。合道合禮,則氣魄自在。就算是君子,若果勇沒有義在其中,亦是亂。義,簡單理解是「公平合理」。匡亞明認為孔子論勇一般是側重道德方面,未能全面展示智勇的內容。10義與利兩者所產生的矛盾,就是孔子冀望能在倫理道德中得到平衡。《易‧乾卦‧文言》:「利者義之和也。」講的就是義與利之間的和諧。孔子所處的時代,禮崩樂壞,篡弒頻仍,公平合理很難出現,但這是君子所追求的道義,故勇必然隨之而至。我們會面對現實的不公世界,但精神上要追求合乎公義的社會。
若再深入闡釋義,就要考慮孔子的思想及所處的環境。孔子的最高理想社會是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結構型態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
二千多年下來,我們人類仍讚歎渴望這種社會的出現,尋求「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公義社會,反過來說,不講信,老無所終,壯無所用,矜寡孤獨廢疾而無所養者就是不公義。另外,孔子所處的年代是戰爭頻仍,統治者橫徵暴斂,過著奢豪的生活,而人民卻難得到飽足。故孔子提出「義然後取」、「見利思義」等行為,作為衡量提出他人利益的準則。《論語.陽貨》: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有勇而無義為盜」,勇必須蘊涵「義」才是正道的勇。無論如何!人人飽足,貧富平均,人盡其力,在當時來說,只是理想。
當義利產生矛盾時,孔子必然是取義而捨利,如: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里仁》)
富與貴,是人人所期望的,但「不以其道」,即不合乎公義者,絕對不取,強調公義與合理。造次顛沛亦必然如此,當然,孔子指出這因為有仁者之心在,但能有造次顛沛的環境中,依然故我,這是勇的表現。孔子更說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的豪語。當公義與富貴在眼前時,應毫不考慮的取義。取義這一行為,不可能沒有「勇」為支持。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論語.陽貨》)
此節經常發生在公事,不通情達理以為是行政,沒有禮貌以為是勇敢率直。果然,這現象,仍然每日都見到。勇可見於日常人類的交往中,亦可見於國與國的交際中。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
孔子答子路「成人」,舉出臧武仲、公綽、卞莊子、冉求等人,卻又再進而解釋,如果能腹「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亦可以為成人。「見利思義」,一定要思考自己取利的行為是否合乎義,義是志,志是勇的來源。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論語‧憲問》)所謂「夫子自道」,是孔子已具有仁、知、勇三種道德涵養。又說:「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孔子反複的說,勇是一種動力的運用,這種勇氣隨著蘊涵者的內在意志而變動。所以,勇的運用是配合道德的運用方能成其大,反之,這種沒有道德的勇,是亂的根源。
下列兩則語錄,表面與勇沒有關係,其實內裡必然有勇的存在: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論語‧顏淵》)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
我們對人對事,行為與態度,直接反映自我們的內心,我們得罪了某些人而會害怕,做錯某些事而驚慌。但「內省不疚」,就不憂不懼。留意,孔子說「勇者無懼」,是任何行為,經過反複思量,而確定毫無私心,合乎公義,這樣才能產生不憂不懼。如何肯定自己的行為,至純至真,就是勇者氣的根源處。此節所指出的氣魄,是純然道德行為,試問,有幾人能無私心?
絕糧而從者病,此環境若近絕境,子路生怨,而孔子說「君子固窮」。如此,則君子處於任何環境,必然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從精神高處看命,看環境,其心能處於適時順世之境界。這種窮而堅守,窮而知命,不是勇,是甚麼?
孔子一生,從自己的行為表現去驗證自己的境界。孔子的志是甚麼?繼承堯、舜、湯、文、武傳下來的文化道統。孔子困於匡,被誤會是陽虎。弟子皆慌張,孔子卻說出:「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這個就是志,勇是來自志,孔子的志是繼承文王道統,要發揚光大。我相信孔子是認為這就是他來這世界的責任,故可以毫不恐懼的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的豪言。
「夾谷之會」,孔子身為司寇,兩度走上臺階,制止齊國的無禮。一是齊國地方舞的表演,拿了盾、槍、旗、棒等表演。孔子喝止,避免齊國陰謀得逞。再者是表演宮廷音樂,毫不合章法。孔子認為是戲弄諸侯,請斬表演者。11最後,是齊國覺得自己理虧,歸還魯國城池鄆、灌及龜陰三地。在一個國際會議場合,其實一切有所規定,孔子據禮而爭,力挫齊國君臣,中間所顯示的勇和氣魄,震攝人魂。千秋以後,讀之仍覺氣魄充盈,合禮合節。
孔子總結一個尋求完滿生命的人,他對勇有如此的總結:「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
孟子重要思想之一,是正氣,這個「氣」是不得了,此亦是後世儒者所嚮慕的境界。要清楚這個氣的養成,要先從「不動心」說起。《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不動心」是甚麼?孔子說「四十而不惑」,孟子說「四十不動心」,又為甚麼是四十?上文已提及是修養與閱歷已達一定程度,便有此成就,此處不贅。〈公孫丑上〉又載: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孟子首先指出三種不同的勇:北宮黝、孟施舍及曾子。此節要特別留意「養勇」的「養」字。養有培養、貯藏的意思,即是我們的勇是一步一步的累積而成。譬如小時候,遭受欺凌,一般不敢作聲,人漸長,愈明白事理,會據理力爭。這是一般人成長的過程,當然,勇的程度,因人,因時,因境,因利而各有不同。普通人的勇大多是來自意氣或是利益,當然亦有來自高尚的情操,我只指出普遍性的勇。記得很多報章報導血案時,都說是一時衝動,弄傷甚至殺死對方。很多抗爭的口號,是為公義和公理而戰,但當中又有幾多是為利而來?
北宮黝的勇,我認為是來自「自尊」,當中記載「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自尊與恥辱,就成為勇的行為的推動者。明顯指出北宮黝是不接受任何傷害其自尊的侮辱行為,包括微不足道的語言說話。一個人連自己都不尊重自己,別人會尊重嗎?這就是自尊的問題,即北宮黝不會忍受任何的恥辱,其前題是北宮黝是不會做令自己受辱的事。人必須自重,別人才尊重你。
孟施舍的勇是不理會生死勝敗,只專心一致完成任務。原文「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視不勝猶勝,就是忘記失敗後,可能會死亡這一節。這種忘卻成敗得失的勇,是目空一切,眼前只有如何去戰的思維,已超越一切恐懼。所謂「除死無大礙」,連死亡都不怕,那還有甚麼好害怕?
兩者的勇,最後是成就曾子的勇,孟子說第三個勇的層次是經過深思熟慮,知道自己的行為合乎義,合乎理,則「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此語,直是石破天驚,氣勢澎湃。我們亦應思考,甚麼是正確,甚麼是不正確?這點是非常重要,因為誤判道德,其行為適得其反。
然而,我相信能到達第三層次的勇者必然具有前兩者的特質,即重視自己的尊嚴和忘記生死成敗。禮記儒行篇:「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這個自尊不比平常的面子問題,而是受辱。筆者在很多場合遇見營營役役,為利奔走的人常常受辱。謀生養家是天職,但如何能不受辱,就是自己平日處事態度所致。可殺不可辱的勇、的氣魄,是自我道德的確定,道德行為的烏確立,認知此心,此勇的來源,才能出現。
這種具有浩然正氣的勇是來自「不動心」,繼而「持其志,無暴其氣」,再而「養氣」。這種「氣」,必須配合義與道,倘若無義或無道,則會衰退如此,所以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孟子.公孫丑上》)。孟子對慊有更深入的詮釋:「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公孫丑下》) 別人可誇富誇貴,而君子所持的就是仁和義。唐君毅先生說:
孟子以養氣之道在集義,而配義與道。道者當然之理,義者知此當然之理而為之,即知理而行之,以合當然之理。故養氣必先『志於道』。12
這種氣是「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閒」。馮友蘭對浩然之氣有這樣的詮釋:
如孟子哲學中果有神秘主義,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即個人在最高境界中的精神狀態。…此所謂義,大概包括吾人性中所有善「端」。是在內本有,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也。」此諸善「端」皆傾向於取消人我界限。即將此逐漸推擴,亦勿急躁求速,亦勿停止不進,…「集義」既久,行無「不慊於心」,而「塞乎天地之間」之精神狀態,可得到矣。13
唐、馮兩位先生都指出,要培養這種氣,是要時時刻刻想著「義」和「道」,思考人類的善性,思考人類合乎道義的行為,久而久之,儲養一定的氣,當遇到事情時,思考其行為的合理性、公義性,如此,浩然之氣自出,否則「餒」。能完善自己的道德行為,能合乎道義,則大勇之行為,將得到成就。
孟子是不重視主宰的天,而重視「義理之天」,認為人的心性覺悟是得之天理,故視仁義忠信,乃天爵。公卿大夫,乃人爵。他慨歎:「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今人只顧追逐明利爵祿,而忽略了上天付與的道德良知,此道德良知包含仁義忠信。若仁義忠信蘊涵於內,則不能坐視不公義事,此即「勇」的來源。
從《孟子》一書,我們可以窺見孟子的勇。孟子以繼承孔子自居,力排當時流行的極端利己主義,不仁的法家思想和不分等差倫理的墨家。顯示出「舍我其誰」的氣魄,英氣勃勃,剛氣迫人,正如孟子自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梁惠王上》:
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傢,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傢;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傢。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多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叟」一詞是強烈的不尊重,雖然未有定論,但也稱不上是尊重。從惠王初見孟子的態度,我們可以想象,孟子談仁義,惠王卻不願的矛盾狀態。面對國君,處於征戰連綿的時代,孟子卻直接了當的說「何必曰利」。若以「識時務」來判斷孟子,就是不識時務。可是,孟子堅持自己理想,極力向惠王推擴「亦有仁義而已矣。」這就是孟子的「義」,不能不說「仁義」。
下列數節,都是孟子面對國君,直接指出他們的錯處,用辭不亢不卑,一些辭句,更是振聾發聵。
《孟子‧離婁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雖然君主是高高在上,但臣下不一定絕對服從。態度方面,君臣之間要互相尊重,視我如手足,則我視汝為腹心。若視我如土芥,則我亦不必尊重你,雖然你有君主的身份,但你不尊重人,人亦不必尊重。這與後皇朝常說「君要臣死,臣不死視為不忠」的荒謬理論,恰好相反。
《孟子‧梁惠王下》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齊宣王不願行仁政,因為自己好貨好色,故不能行仁政。宣王以為仁政是與好貨好色相違背,但孟子舉史例直斥其非。最後,更引用譬喻,說明宣王不行仁政而令致國家不定安,借題發揮,問宣王如何處理「四境之內不治」的責任,令宣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梁惠王下》: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孟子、萬章下》: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
《孟子‧盡心下》: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上引兩節,真是有驚天動地的氣慨,試想一個國家元首在你面前,質問元首行暴政,是不是要推翻?有幾多學者能人,能直接說身為元首國君,倘殘害百姓,不能算是國君,就算殺了他,都只殺了一個滿身私欲,害人無數的匹夫。從這角度去看,在孟子心目中,國君是一份職責,他必須為自己所處的地位而付出必要的心力,否則,這個人死不足惜。我們將此驗證於後世君主,相信死後腐骨仍流汗。
齊宣王再問卿,孟子的答案就是後世所指的「十惡不赦」的謀反罪。君主不能履行自己的職責,只顧享樂,就應該推翻這政權。所以,孟子的結論是民為貴,而君主最卑。不要少看這幾節引文,千秋而下,仍感覺其凜凜風骨,真是惟大丈夫能本色。現代的中國人,或許與孟子有同樣的理念,但對著高官權貴,能有足夠的膽量這樣表達自己嗎?若不是對自己所認知的道德與理念,有絕對的信心,根本說不出這些話來。可是,我們要留意的事,孟子沒有用帶有侮辱性的辭語責難,只希望國君從對話中,觸動起憐憫他人的悲心,減少私欲。你有權,你有勢,但我有的是公義。甚麼是勇?請看孟子的行為言論。
《孟子‧公孫丑下》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上節是孟子不遇時,去齊之語。雖然有客欲為齊王挽留孟子,從但孟子告訴來者,來者游說的應是齊王。孟子不豫是因為五百年將有王者興,現在過了五百年,尚未見王者。這裡有兩重意思,王者未興,孟子推說是天不欲天下治,若果「天」希望天下大治,能用的只有孟子。其第二重意思是自己是惟一儒家道統的繼承人。
張岱年:
所謂士節即堅持自己的主體意識。主體意識包括人格獨立意識與社會責任心,乃是人格獨立意識與社會責任心的統一。一方面要堅持獨立人格,不隨風搖擺,不屈服於權勢;另一方面更有社會責任心,不忘記自己對於社會應盡的義務。14
為堅持獨立人格,為社會應盡的義務,背後是要與多少貪官污吏和既得利益者周旋。偶一失誤,則自陷泥淖。「勇」,說來只一字,行來千萬斤重。
我認為培養「勇」的第一步,是維持自尊,而生命所涉及的層面,必然包括物欲。所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兩種欲望:飲食、男女,是人類最大的渴求,要進入忘記生死成敗的階段,必須將欲望降至最低,「無欲則剛」是一種氣魄,亦是一種修煉,使之成無欲的氣,行為則剛。古今中外學者都將男女飲食作為「人」第一步的追求,如馬斯勞(MarslowA.H.,1908-1970) 提出人類需求的五個層次,「生理需求」就是要首先滿足;佛洛伊德(Freud, Sigmund,1856-1939)亦認為人的「本我」(id) 是餓、渴、睡、性等原始需求所推動。因此,我認為欲望是一切不道德行為的來源。減低欲望,或適當調節欲望,才可提升道德境界。這樣,我們才可以培養浩然之氣,使之長,不使之餒,要經常提醒自己,生命的價值何在。
較高的層次,是超越生死,即有些東西令你願意犧牲。蔡仁厚:
孟子指出,人所願欲的東西有超乎生命之上的,所以不願意苟且偷生;人所憎惡的物事亦有甚於死亡的,所以人有時並逃避死亡的禍患。…而是想成就生命的純潔清白,以免陷於不義而受辱,故能毅然以有限的生命,換取無限的精神價值。15
即所謂所惡有甚於死者,中國史上,為天下公義,為推翻暴政,前仆後繼。這不獨是儒家的理論,是普遍的真理。人類的悲憫之心起動,就願意為其他人犧牲。但這犧牲,是否合乎仁義?另作別論。例如某人要「報仇」,仇超越了生命,但合乎義嗎?
有了超越生死的勇,就要思想自己的行為是否合乎「義」?第三層次就是經反複思量,自覺行為與道德均合乎公義,尋求社會公義乃自我的責任,則自然產生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氣魄。孔孟的理論,能貯大勇於後世士子,就在這節。顏杲卿痛罵安祿山,逼之以殺子,誘之以高祿,終不為所動,以致被節解斷舌16,其情慘烈,但背後是大勇表現,持義以抗。張巡碎齒抗賊,被執神色若然,至死毫無懼色。17這些都是孔孟思想所蘊涵的大勇,就是超越生死的大勇。大勇是集義而至,合乎一切的公義,就有此氣度。
孔孟認為君子是「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論語.泰伯》能夠有這樣的氣魄的人物,必然是大仁大勇者。筆者每每讀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就覺有沉重感。當中的責任感,當中不放棄的勇,是仁者、勇者的路向,不得不禮敬孔、孟。
腳註 :
1. 匡亞明:《孔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223。
2. 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354。
3. 參考拙著〈論孟子「人」與「禽獸」之別〉,收在《「第二屆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孔教學院,2006年。
4. 同上註
5.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八佾》)
6. (宋) 朱熹:《四書集註》,香港:大中圖書,出版年缺,〈上論‧卷四〉頁52。
7. (宋) 朱熹:《四書集註》,香港:大中圖書,出版年缺,〈上孟‧卷二‧公孫丑上〉,頁38。
8. 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65。
9. 同上註,頁70,註釋22。
10. 匡亞明:《孔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223。
11. 事見《史記‧孔子世家》。
12.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台北:學生書局,頁615。
13.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02-103。
14.張岱年《心靈與境界》,陜西:師範大學,2008年,頁300。
15. 蔡仁厚《孔孟荀哲學》,台北:學生書局,1999年,頁279-280。
16. (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215,列傳117〈忠義中‧顏杲卿傳〉載:「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並盧逖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罵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糊而絕,年六十五。」
17. 同上註,卷215,列傳117〈忠義中‧張巡傳〉載:「城遂陷,與遠俱執。巡眾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眾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為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為我用?且得眾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訚、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
原載於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及樹仁大學中文系編《2012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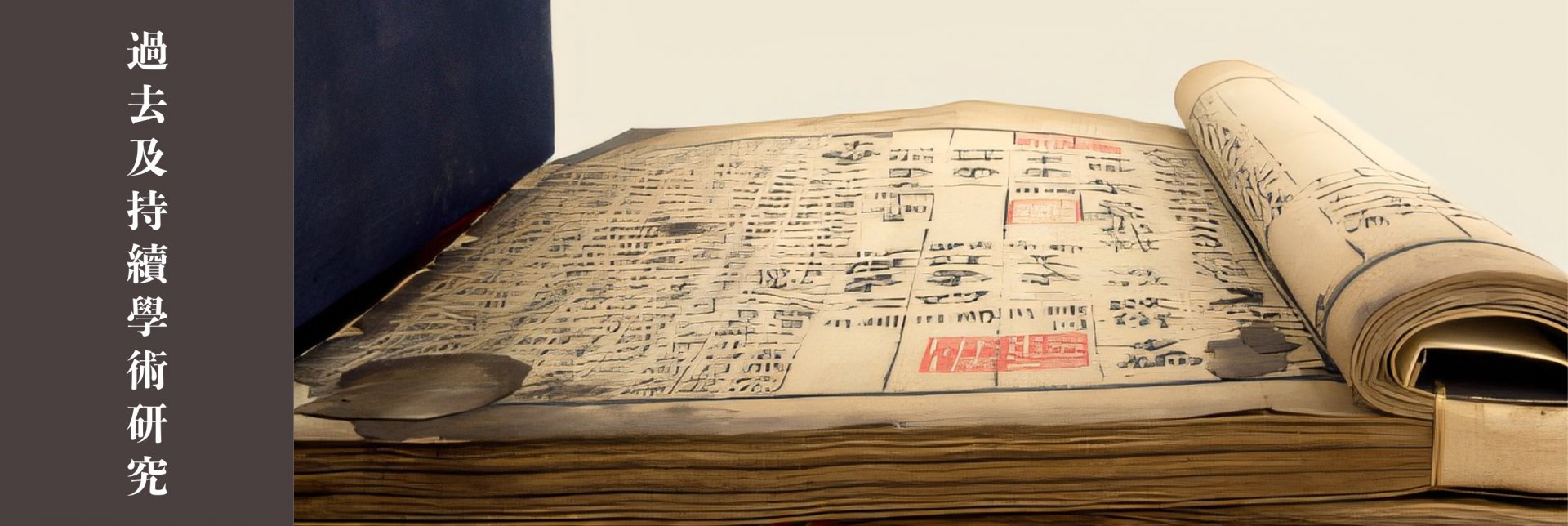



歡迎留言:
請登入/登記成為會員後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