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刘勰传》“家贫不婚娶”问题新探
陈允锋
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原刊载于香港《岭南学报》復刊第十八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6月,第89-110页)
【内容摘要】关于《梁书·刘勰传》所载“家贫不婚娶”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发表过颇有见地的意见。不过,如果重新细緻地研读《梁书·刘勰传》“家贫不婚娶”一段文字,并联繫相关史料,类比旁推,似尚有值得进一步辨析、阐释之馀地。譬如,从文义关係的角度出发,将《梁书·刘勰传》所载刘勰“家贫不婚娶”一事与前后文句联繫起来,或可得出新的认识——“家贫”问题与“勰早孤”相关联;“不婚娶”以及“依沙门僧祐”问题则跟“笃志好学”一句相呼应,并最终落实于“遂博通经论”这一结果上。如此阐释,“笃志好学”之说与“遂博通经论”之间,方显得义脉贯畅,而“家贫不婚娶”问题亦可得更为合理之解释。
【关键词】《梁书》;刘勰;家贫;婚娶;文义关係
姚思廉《梁书·刘勰传》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刘勰传记资料,对了解、研究刘勰生平思想具有重要价值。但由于记载比较简略,落实到某些具体问题,难免引发歧解乃至争议。譬如,关于《梁书·刘勰传》所载“家贫不婚娶”问题,即有诸多不同看法。为便于分析,兹抄录《梁书·刘勰传》该小节文字如次:
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1
关于刘勰“不婚娶”之原因,学界提出了多种说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信佛”说、“贫寒庶族”说、“士族婚俗”说以及“树德建言志趣”说等2。这些看法,对全面、深入地理解刘勰身世、生平及其人生观,显然具有重要啓示价值。不过,如果重新细緻地研读《梁书·刘勰传》“家贫不婚娶”一段文字,幷联繫相关史料,类比旁推,似尚有值得进一步辨析、阐释之馀地。譬如,究竟如何理解“家贫”之具体情形,方显得更合理?又如,“家贫”与“不婚娶”之间,究竟宜解作因果关係抑或併列关係?再如,从语气、语义关係而言,“遂博通经论”与前文“笃志好学”以及“不婚娶”之间,是否前后呼应?类似这些细节问题,还有必要再加斟酌,或有助于披文入情,探得其实。
首先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梁书·刘勰传》所载之“家贫”,由于没有更具体之描述,本身就易滋歧解。譬如杨明照先生《梁书刘勰传笺注》称:“按舍人早孤而能笃志好学,其衣食未至空乏,已可概见。而史犹称为贫者,盖以家道中落,又早丧父,生生所资,大不如昔耳。非以家徒四壁,无以为生也。如谓因家贫,致不能婚娶,则更悖矣。”3意谓刘勰之“家贫”,乃相对于“丧父”前家道殷实状况而言,泛指“生生所资,大不如昔”,而非“家徒四壁,无以为生”。王元化先生则认为:“刘勰少时入定林寺和不婚娶的原因,也只有用出身于贫寒庶族这件事才能较为圆满地说明”4,“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5。关于刘勰入定林寺前是否因“家贫”而“无力负担租役”问题,王元化先生另加解释:“《梁书》本传称勰少时家贫,这个说法曾经引起了不少怀疑。在刘氏世系中,穆之、秀之位望不可谓不高,家产不可谓不富,为什麽到了刘勰竟会变得贫穷起来了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首先我们必须注意:穆之、秀之的后嗣在齐代宋后,已经家道中落……刘勰丧父后,仍然会落入微贱贫穷境地。”6
上列两种意见,各自成理。但是,若深加追究,又不无可议之处。概括而言,主要有三。
其一,按照一般论者大致认可的刘勰世系,其间名望最着者,无疑就是刘穆之、刘秀之。前引论家以为“穆之、秀之的后嗣在齐代宋后,已经家道中落”,应该没有多大问题,而家道究竟如何“中落”,尚语焉未详,无妨略加补说。
按,刘穆之作为刘宋朝“佐命元勋”,虽然身后得刘裕顾念旧恩,追封为“南康郡公,邑三千户”7;但后嗣不淑,爵禄传承,日趋没落。《宋书》刘穆之传附传载:“穆之三子,长子虑之嗣,仕至员外散骑常侍卒。子邕嗣……卒,子肜嗣。大明四年,坐刀斫妻,夺爵土,以弟彪绍封。齐受禅,降为南康县侯,食邑千户。”8《南史》甚而说“坐庙墓不修,削爵为羽林监”9。刘穆之其他诸子,仕途亦不甚顺达,门庭日趋没落,如:“中子式之字延叔……在任赃货狼藉,扬州刺史王弘遣从事检校……长子敳……敳弟衍,大明末,以为黄门郎,出为豫章内史。晋安王子勋称伪号,以为中护军。事败伏诛。”10又,敳弟刘瑀“陵物护前,不欲人居己上”,“使气尚人”,“孝建三年,除辅国将军、益州刺史……坐夺人妻为妾,免官”11。又,“穆之少子贞之,中书黄门侍郎……子裒,始兴相,以赃货系东冶内”12。因此,有学者指出:“刘穆之的爵位由长子虑之嗣,后由虑之的儿子邕嗣,在宋孝武帝以前,有封国者地位还受到一定的尊重,但孝武帝时期,却使得有封国者在本地区的地位与威信有所降低……刘穆之的后代发展却并不太顺利。”13又说:“寒门功臣后代即使以清流起家,但他们在仕进道路上也仍是艰难的,刘穆之的曾孙祥因萧道成禅代而心怀不满,萧道成将他流放广州,说他‘位涉清途,于分非屈’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14
其二,前引论家以为“在刘氏世系中,穆之、秀之位望不可谓不高,家产不可谓不富”,似不宜一概而论。相对而言,刘穆之虽然“家本贫贱,赡生多阙”15,但生性“奢豪”,后来势力日盛,权位日高,“食必方丈,旦辄为十人馔。穆之既好宾客,未尝独餐,每至食时,客止十人以还者,帐下依常下食,以此为常”16。他本人对此也有所检省,“尝白高祖曰:……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17。可见已然由“贫贱”而趋“富贵”阶层。此一事也。刘秀之乃刘穆之从侄,同样出身贫寒,位望亦高,但为政、立身却迥然不同。《宋书》卷八一本传载:
刘秀之字道宝,东莞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秀之少孤贫,有志操……景平二年,除驸马都尉、奉朝请。家贫,求为广陵郡丞……秀之善于为政,躬自俭约……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营聚蓄,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僚,併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秀之为治整肃,以身率下,远近安悦焉……秀之野率无风采,而心力坚正。上以其莅官清洁,家无馀财,赐钱二十万,布三百匹。18
可见,刘秀之虽然早年“孤贫”,但确有“志操”,权位日隆而“莅官清洁”,以致身后“家无馀财”。秀之一系,“子景远嗣,官至前军将军。景远卒,子儁,齐受禅,国除”19。萧齐代宋,难保爵号封邑,其家境復归于贫,殆不难想见。因此,笼统地说刘勰祖上显赫人物“家产不可谓不富”,似不甚妥当。同时也可以看出:《梁书》本传说刘勰“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庶近乎刘秀之“善于为政,躬自俭约”,而迥异于刘穆之“奢豪”“诞节”。
其三,因史家并未明言刘勰“家贫”具体情形,后人拟议,自然歧解纷出。上引杨明照、王元化先生之不同看法,即显着之例。此外,由于不同论家所理解“家贫”标准未必一致,有些说法,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譬如杨明照先生《读梁书刘勰传札记》认为,刘勰之“家贫”,“绝不等于当时劳动人民的一贫如洗,朝不谋夕;只能理解为他是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出身的子弟,生活大不如昔就够了”,幷以《梁书·文学传》为例,指出:
在这篇合传里,目为“家贫”的共三人,除刘勰外,还有袁峻和任孝恭。《袁峻传》云:“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钞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任孝恭传》云:“家贫,无书;常崎岖从人假借。每读一遍,略无所遗。”可见袁峻和任孝恭儘管“家贫”,尚有借书钞读的雅兴,喫饭总不会有多大问题的。如果我们单把刘勰的“家贫”说得连饭都喫不上,那就未免太不了解历史了。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刘勰既是大族,又系达官之后,再穷也不至于此极吧。其所以要“依沙门僧祐”,固然不能说完全与生计无关;但谋生之道多端,朱百年的“以伐樵採箬为业”(见《宋书》卷九三《隐逸·朱百年传》),沉顗的“樵採自资”(见《梁书》卷五一《处士·沉顗传》),又何尝不是解决生活问题的办法。20
从这裡可以看出:或以为“一贫如洗”、“连饭都喫不上”才是“家贫”,或以为“家贫”不过泛指“没落贵族家庭出身的子弟,生活大不如昔”。其间标准之悬殊,显而易见。不过,杨明照先生援引与“家贫”相关资料以供参考,这一思路与方法,确有重要啓发意义。
“贫”与“富”相对,《说文》曰“贫,财分少也”,《六书故》曰“凡粟米丝麻材木可用者曰财”,本义指缺乏米粟布帛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故史籍曰某人“家贫”,一般指生计艰难、日用匮乏。如《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附:“丞相匡衡者,东海人也。好读书,从博士受《诗》。家贫,衡佣作以给食饮。”21又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郦生食其者,陈留髙阳人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22又如《晋书》卷九四陶潜传:“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尝着《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恆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23再以与刘勰同时代南朝人士为例:
《宋书·宗炳传》:(宗炳)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贫无以相赡,颇营稼穑。24
《南齐书·王智深传》:王智深……贫无衣……家贫无人事,尝饿五日不得食,掘苋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25
《南齐书·臧荣绪传》:荣绪幼孤,躬自灌园,以供祭祀……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一书……26
《南齐书·沉驎士传》:驎士少好学,家贫……永明六年,吏部郎沉渊、中书郎沉约又表荐驎士义行,曰:……家世孤贫,藜藿不给。27
《梁书·贺琛传》:……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28
上列数例,大部分与刘勰境遇相类:失怙,幼孤,家贫。其间,有“掘苋根食之”者,有“贩粟自给”者,亦有“藜藿不给”者。《梁书》刘勰传并未明言其“家贫”具体情形,不过,以同时代幼孤而家贫者为参照,依类而推,刘勰年幼丧父,其“家贫”概况,或许亦相彷佛。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在史籍所载“家贫”者中,像王智深、沉驎士等,确实到了前引论者所谓“家贫如洗”之境地。至于为人所熟知之陶潜“家贫”,不仅面临“缾无储粟”29,“夏日抱长飢,寒夜无被眠”30之困境,还留有《乞食》一诗。由此看来,若遽然断定刘勰之“家贫”、“衣食未至空乏”,并非“无以为生”,虽然不无可能,但毕竟难成笃定无疑之论。当然,更关键之问题乃在于:刘勰之“家贫”,是否一定导致“不婚”?具体讨论详下。
《梁书•刘勰传》“家贫”之后紧接着说“不婚娶”,按照一般阅读理解习惯,自然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因果关係。前引王元化先生观点,即依此思路而得出相应结论,故曰:“刘勰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不过,恰如杜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联,既可以理解为一种因果关係,也未尝不可理解为一种并列关係一样,刘勰之“家贫不婚娶”,同样可以有另一种理解,即“家贫”与“不婚娶”之间未必就是一种因果关係,而是客观陈述两种事实,亦即并列关係。《梁书》作者原本立意究竟如何?刘勰当年家境又如何?皆难以得其实情。所以,拓展史料之研阅范围,考察相关史籍所载古人“家贫”与“婚娶”之关係,择取同类可供参考之事例,或不失为努力接近历史真实之尝试。
前文曾引《宋书·刘秀之传》为例,可知“秀之少孤贫”,早年虽“除驸马都尉、奉朝请”,但仍难以摆脱生计困乏之窘境,故史籍曰:“家贫,求为广陵郡丞。”这种为解决家境贫困而求官之行为,在魏晋南朝时期,似颇常见。其着名者如陶潜,年近而立,即因“亲老家贫”而“求为州祭酒”;年近不惑,又因“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之“贫苦”而求为彭泽令。又如,与臧荣绪俱隐京口,“世号为二隐”之一的关康之,“四十年不出门。不应州府辟”,但是,到了晚年,仍“以母老家贫,求为岭南小县”31。因此,宗炳之孙宗测曾发感慨:“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先哲以为美谈。”32但是,刘秀之虽然家贫,却颇有“志操”与才器,得何承天之青眼,且以女妻之33。陶渊明虽然像五柳先生一样,“环堵萧然”,“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婚娶却是及其时的,而且“始室丧其偏”后,復娶柴桑翟氏34。至于关康之,虽“性清约,独处一室,稀与妻子相见,不通宾客”,但显而易见,也是属于及时婚娶、有家室者。为说明问题,再举数例如次:
《晋书》卷八八庾衮传:……初,衮诸父并贵盛,惟父独守贫约……父亡,作筥卖以养母……衮前妻荀氏,继室乐氏,皆官族富室,及适衮,俱弃华丽,散资财,与衮共安贫苦,相敬如宾。35
《晋书》卷八九王育传:王育字伯春……少孤贫,为人佣牧羊……忘而失羊,为羊主所责,育将鬻己以偿之。同郡许子章,敏达之士也,闻而嘉之,代育偿羊,给其衣食……子章以兄之子妻之。36
《南齐书》卷五五孝义传:永明元年,会稽永兴倪翼之母丁氏,少丧夫,性仁爱……同里陈穰父母死,孤单无亲戚,丁氏收养之,及长,为营婚娶。37
《梁书》卷四一褚球传:褚球字仲宝……球少孤贫……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诛灭,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㝢、王思远闻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为之延誉。38
从以上这些例子中,不难看出:在现实生活中,或许确实存在因家贫而无力婚娶者,但应该着重强调的是,在缺乏具体载述或相关确凿证据时,笼统地将“家贫”视作“不婚娶”之原因,似欠稳妥。从史籍记载看,“孤贫”者未必不能完成婚娶这一人生要务。即此而论,杨明照等学者在“家贫”因素之外,另求刘勰“不婚娶”之缘由,相对而言,显得更合理些。
正如上文所言,从语义关係看,“家贫”与“不婚娶”未必构成因果关係,未尝不可理解为一种并列关係,即“家贫”者一事,“不婚娶”者,另一事也。后一种理解的合理性在于:“不婚娶”之义,未必如一般学者所理解的“无力婚娶”,而未尝不是强调传主“不愿婚娶”。也就是说,即使孤立地看,“不婚娶”其实也暗含两种语义阐释之可能:一种因某些客观原因而无法实现婚娶之心愿,另一种则指因个人心志而不想、不愿婚娶。杨明照先生《梁书刘勰传笺注》曾作一设问:
……益见舍人之不婚娶,原非由于家贫。至谓当时门阀制度,甚为森严。托姻结好,必须匹敌。舍人既是贫家,高门谁肯降衡?其鳏居终身,乃囿于簿阀,非能之而不欲,寔欲之而不能也。此说虽辨,然亦未安。缘舍人入梁,即登仕途,境地既已改观,行年亦未四十。高即不成,低亦可就。如欲婚娶,犹未为晚。39
这裡提到的“至谓……”云云,乃指其他论者之认识。其间所及“能之而不欲”与“欲之而不能”之提法,颇有啓发意义。以“家贫”为“不婚娶”之原因者,认为刘勰是“欲之而不能”;杨明照先生既然强调刘勰“不婚娶”主要由于“信佛”,其思路自然偏于“能之而不欲”。这一点,杨明照《学不已斋杂着》所收《读梁书刘勰传札记》一文中有更明确表述:“刘勰的‘不婚娶’,我认为不是因为‘家贫’,而是由于信佛,试想一个达官大族的后代,即使家道没落,总不至于穷得到了不能结婚的地步。《梁书》《南史》只说‘不婚娶’,‘不’下并未着有其它字眼(如‘能’字之类),那就不应以意逆志地说成是连婚都结不起”40。刘勰“不婚娶”究竟是否由于“信佛”,学界意见不一,但影响很大41。不过,其间提到的《梁书》、《南史》“只说‘不婚娶’,‘不’下并未着有其它字眼(如‘能’字之类)”这一说法,似尚未引起必要关注。窃以为就语义理解来看,“不婚娶”之“不”字,诚不宜轻易放过,值得细加品味、琢磨。
按,《梁书·刘勰传》“不婚娶”之“不”字,其实未必另着其他字眼如“能”字之类,即可表达一种强烈的主观意愿,也就是自觉地选择“不婚娶”,而非由于“家贫”等外力之所迫。换言之,勰之“不婚娶”,乃基于主观、内在之心理意愿与志向信念——儘管这一意愿与信念未必如杨明照先生所言之“信佛”,而非由于生计困顿、家资贫乏。
有论者通过对楚简《老子》中“不”、“弗”二字语法功能的统计分析,指出:“‘不’在否定句中常用来表示当事人强烈的主观色彩或倾向性。具有强调特徵的‘不’句大多是对否定者的主观意愿表示强调……‘不’句有很多修饰语明显表示否定者的主观色彩……具有强调特徵的‘弗’句主要是说话人对客观不可能性表示判断和强调⋯⋯‘不’句大多数表示对否定者主观意志的强调。而具有强调特徵的‘弗’句大多表示说话人对客观不可能性的强调。”42这一结论是基于相关出土文献中“不、弗”用例之分析,自然不宜直接引作《梁书》刘勰传“不婚娶”之“不”字的阐释依据,但至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刘勰“不婚娶”,是否也属于一种具有明显主观意愿的自觉选择?以此为线索,徵之于史籍相关记载,说明这一理解大体符合实情。
检讨史籍,可知“不婚娶”、“不娶”以及“未婚娶”、“未娶”是两种常见的表述。通过考察“不”字句与“未”字句之差异,或许有助于解决《梁书》刘勰传“不婚娶”的语义理解问题。兹先列举与婚娶问题相关之“未”字句:
《后汉纪》姜肱传:……姜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隐居静处,非义不行,敬奉旧老,训导后进。尝与小弟季江俱行,为盗所劫,欲杀其弟。肱曰:“弟年稚弱,父母所矜,又未聘娶,愿自杀以济家。”43
《晋书》王国宝传:……是时王雅亦有宠,荐王珣于帝。帝夜与国宝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将至,国宝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倾其宠,因曰:“王珣当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见。”帝遂止,而以国宝为忠。将纳国宝女为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44
《晋书》庾衮传:庾衮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俭,笃学好问,事亲以孝称……而以旧宅与其长兄子赓、翕。及翕卒,衮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45
《魏书》韩麒麟传附子熙传:子熙与弟娉王氏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46
《宋书》颜延之传:颜延之字延年……饮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妹适东莞刘宪之,穆之子也。穆之既与延之通家,又闻其美,将仕之。47
《南齐书》豫章文献王:豫章文献王嶷字宣俨,太祖第二子……嶷临终,召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几何……虽才愧古人,意怀粗亦有在,不以遗财为累。主衣所馀,小弟未婚,诸妹未嫁。48
《南齐书》崔怀慎传附公孙僧远传:公孙僧远,会稽剡人也。治父丧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谨。年飢谷贵,僧远省餐减食,以养母、伯……兄姊未婚嫁,乃自卖为之成礼。49
以上诸例,说明“未婚”、“未娶”或“未婚娶”,一般指陈客观事实,或由于客观原因,如因孤贫而无力置办财礼,或因对方死亡等,造成想成婚者未能实现主观意愿。这类情形,事出无奈,欲为之而未能如愿。
与上列诸例所表示的情况不同,史籍曰某人“不娶”或“不婚娶”,则往往强调当事者明确的主观意愿,是一种“能而不欲”的自觉选择,如以下各例:
《后汉书》梁鸿传: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势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娉之。50
《后汉书》盛道妻传:犍为盛道妻者,同郡赵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乱,道聚众起兵,事败,夫妻执系,当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无生望,君可速潜逃,建立门户,妾自留狱,代君塞咎。”道依违未从。媛姜便解道桎梏,为赍粮货。子翔时年五岁,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应对不失。度道已远,乃以实告吏,应时见杀。道父子会赦得归,道感其义,终身不娶焉。51
《晋书》郭文传:郭文字文举,河内轵人也。少爱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弥旬忘反。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52
《晋书》杨轲传:杨轲,天水人也。少好易,长而不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常食粗饮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忧,而轲悠然自得。53
《晋书》公孙永传:公孙永字子阳,襄平人也。少而好学恬虚,隐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垦植,则不衣食之,吟咏岩间,欣然自得。54
《晋书》石垣传:石垣字洪孙,自云北海剧人。居无定所,不娶妻妾,不营产业,食不求美,衣必粗弊。55
《晋书》陶淡传: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父夏,以无行被废。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56
《南齐书》朱谦之传:朱谦之字处光,吴郡钱唐人也……谦之年数岁,所生母亡……谦之虽小,便哀戚如持丧。年长不婚娶。57
由上列诸例可见:前引论者所言“不”字作为古汉语常用否定副词,往往体现着施事者自觉、主动的一种抉择意识;这一“不”字所具备之语法功能、语义作用,在史籍有关“不婚娶”一类的文句中,同样是切合实际的。也就是说,上列史籍所言“不娶”、“不婚”、“不婚娶”者,一般意在强调传主无意娶妻,主观倾向至为明显。以此类推,《梁书·刘勰传》载“家贫不婚娶”,其立意重点,似不在“欲之而不能”,所强调者,乃刘勰在婚娶问题上“能之而不欲”之态度与选择58。
以上援引史籍相关载录,或有助于说明刘勰之“不婚娶”,谅非由于“家贫”所致,而是出于某种志向信念所作出的带有强烈主观意愿之选择。关于此种志向或信念,学界也有学者论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种说法:一者以为“信佛”,前引杨明照先生之观点,最有代表性;二者以为尽“孝”,范文澜先生有此说;三者以为“树德建言”,祖保泉先生《〈梁书·刘勰传〉注》曾有说明:“刘勰终生不娶,受生活环境的限制和‘树德建言’的志趣支配是重要原因,受佛教思想影响也是原因之一。‘因信佛而终身不娶’或‘为求奉时以骋绩而不娶’等论断,皆嫌偏执。”59徵诸实际,窃以为第三种说法相对稳妥,比较切合实际,因为此说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如“生活环境的限制”、“佛教思想影响”,其中对“信佛”说以及“奉时以骋绩”说,亦未全盘否定,而只是目之为“偏执”之见;同时,又根据《文心凋龙·序志》内容,将“树德建言”之志趣视作刘勰“不婚娶”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该注意的是,“树德建言”之志趣,见于《文心凋龙·序志》篇,是刘勰入定林寺,且“齿在踰立”之后。这是刘勰而立之年的人生志向,是否直接等同于刘勰少时情形,似尚可斟酌。但是,从人生“志趣”的角度探求刘勰“不婚娶”之原因,这一思路确实富有啓发意义。如果回到《梁书》本传,即不难发现,影响刘勰在“早孤”而“家贫”情形下,选择“不婚娶”之原因与目的,答案就在前后文:从原因说,是由于自幼“笃志好学”;从目标与结果说,则是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终于“积十馀年”之功,达到了“博通经论”之境。因此,从语义关係上分析,《梁书》刘勰本传所言“家贫”,其实是承接前文“早孤”二字——因“早孤”而“家贫”;“不婚娶”之原因,关键不在“家贫”,而是呼应前文“笃志好学”。总起来看,因为刘勰自幼笃志好学,“早孤”与“家贫”固然给他的学习带来种种障碍与困难;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有助于反激出更强烈的求知慾,更执着的学术追求。为了满足这种求知慾,实现人生目标,刘勰“不婚娶”且“依沙门僧祐”,确实有助于更好地以精专、勤谨之苦功与心力,努力达成人生理想——“遂博通经论”之“遂”字,其实已经标示了“博通”之境与“笃志好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考诸史籍,不难得知:史籍谓某人“家贫”,往往是为了突出某一品格或人生志向。如《南齐书》韩灵敏传:“韩灵敏……早孤,与兄灵珍并有孝性,寻母又亡,家贫无以营凶,兄弟共种苽半亩,朝採苽子,暮已復生,以此遂办葬事。”60婚、丧乃礼制规定之大事,韩氏兄弟因家贫而合力躬耕,意在备办其母丧葬。又如《梁书》冯道根传:“冯道根字巨基……少失父,家贫,佣赁以养母。”61再如《梁书》沉崇傃传:“崇傃六岁丁父忧,哭踊过礼,及长,佣书以养母焉……母卒……家贫无以迁窆,乃行乞经年,始获葬焉。”62类似这些“家贫”之载记,皆意在突出传主如何尽其孝道,表彰其品德之优秀。
当然,史籍载某人“家贫”,更常见的情况,是意在说明传主如何勤奋好学,如以下诸例:
《后汉书》荀悦传:悦字仲豫……家贫无书,每之人閒,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沉静,美姿容,尤好着述。63
《晋书》车胤传:车胤字武子,南平人也……胤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时惟胤与吴隐之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64
《魏书》许彦传:许彦,字道谟……彦少孤贫,好读书,后从沙门法叡受《易》。65
《宋书》颜延之传: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66
《南齐书》沉驎士传:……驎士少好学,家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吏部郎沉渊、中书郎沉约又表荐驎士义行,曰:“……家世孤贫……怀书而耕,白首无倦……”67
《梁书》王僧孺传:(王僧孺)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68
《梁书》褚球传:褚球字仲宝……球少孤贫,笃志好学,有才思。69
《梁书》袁峻传: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70
《梁书》刘峻传:峻好学,家贫,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终夜不寐,其精力如此。71
《梁书》任孝恭传:孝恭幼孤……精力勤学,家贫无书,常崎岖从人假借。每读一遍,讽诵略无所遗。72
这些例子所言“家贫”,显然并未止于客观记载,而是将“家贫”与“好学”之志联繫起来73,突出传主刻苦自励、精进不止之精神。《梁书·刘勰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与“家贫”,其立意殆亦与此相近。尤值得玩味者,乃以下诸例:
《后汉书》王充传:充少孤……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74
《晋书》王育传:王育字伯春……少孤贫,为人佣牧羊,每过小学,必歔欷流涕。时有暇,即折蒲学书……同郡许子章,敏达之士也,闻而嘉之……使与子同学,遂博通经史。75
《晋书》祈嘉传:祈嘉字孔宾,酒泉人也。少清贫,好学……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76
《梁书》沉约传:沉约字休文……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能属文。77
纵观此类事例,不难看出其共同表述方式与潜在思维:好学→家贫→如何求学→效果如何。《梁书·刘勰传》亦同此例: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遂博通经纶。弄清史家着述立意与思路,有助于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即《梁书·刘勰传》所言“家贫”,首先不是作为后一句“不婚娶”之原因,而是重在呼应前文,“家贫”与“早孤”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为了突出刘勰如何“笃志好学”,并以“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申述之,很好地说明了“博通经论”之成因。质言之,“遂博通经论”之“遂”字,其实与前文“笃志好学”遥相呼应。这种语气、语义之关係,与上文所举王充、王育、祈嘉、沉约传“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遂博通经史”、“遂博通经传”、“遂博通群籍”云云,在表达方式及着述旨意上,如出一辙。
综上所论,大致可得如下三点认识:第一,就史籍所载同类材料看,《梁书·刘勰传》所谓“家贫”,其具体内涵之理解,因缺乏明确而直接之证据,既不宜理所当然地解作“无以为生”,亦难以得出“衣食未至空乏”之判断,有待进一步考索。第二,无论是就文义关係而言,还是参照相关史料,刘勰之“家贫”,未必与“不婚娶”存在直接关係——“家贫”主要承接“早孤”而言,“不婚娶”则与“笃志好学”相关联;“不婚娶”之“不”字,主要不是指迫于“家贫”而无力及时婚娶,而是强调“能而不欲”之主观选择与意愿。第三,以史籍载记某人“家贫”之常见表述方式与立意宗旨为参照,可知《梁书·刘勰传》曰“家贫”,意在突出刘勰虽然“早孤、家贫”,但依然立志向学,最终臻于“博通经论”之境。如此理解,“笃志好学”与“家贫不婚娶”以及“遂博通经论”之间,文义关係前后照应,显得更为合理贯畅。
最后拟补充说明三点:第一,本文宗旨在于从语义关係的角度,借助史籍中的相关记载,与《梁书·刘勰传》“家贫不婚娶”一节表述方式进行比较类推,为刘勰生平研究中的一个疑难问题,提供另一种阐释之可能。在此过程中,注重同类史料的类比旁推、否定副词语气与语义之关係,此一研究对如何更好地运用文本细读法,发现并提炼史家写作立意与表述方式之关联,或有一定启发意义。第二,经由相关论证,说明《梁书·刘勰传》“家贫不婚娶”五字,不宜连读,「家贫」二字之后宜加点读。如此标点,给研究者带来更多的阐释空间。句读与文义关係甚为密切,关键之处不宜忽略,“家贫不婚娶”句义理解问题,或可视为一个比较典型之个案。第三,由于刘勰生平资料比较匮乏,亦难以找到魏晋六朝因“笃志好学”而“不婚娶”之相关例证,故文中所作推论、阐释,并未断然判定刘勰“不婚娶”主因在于“笃志好学”,而是依据相关史籍资料,参照史家共有的表述习惯及其基本立意,综合考量多种因素,进而形成如下推论:促成刘勰“不婚娶”且“依沙门僧祐”之原因有两点:一是精神层面的“笃志好学”,二是物质层面的因“早孤”导致之“家贫”,而“家贫”又进一步强化了“笃志好学”之心志。作为一种推论,在学界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阐释之可能,虽非确凿无疑之定论,毕竟有助于推动刘勰生平之研究。因篇幅限制,有关刘勰“笃志好学”之心志与《文心凋龙》相关理论观念之关係,未遑涉及,有待另文讨论,以期进一步显示本文提出的学术新认识对《文心凋龙》研究之助益。
徵引书目 :
1.王元化:《文心凋龙讲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Wang Yuanhua.Wenxin Diaolong jiangshu (Interpretation of Wenxnin Diaolong).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2012.
2.司马迁撰,裴駰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Si Maqian. Shiji (The Historical Records). Edited by Pei Yin, explored by Sima Zhen and expounded by Zhang Shoujie. Beijing: Zhonghua shuju, Second edition,1982.
3.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Li Yanshou. Nanshi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75.
4.沉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Shen Yue. Songshu (The Book of the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74.
5.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Fang Xuanling. Jinshu (The Book of the Jin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74.
6.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Fan Ye. Houhanshu (The Book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Edited by Li Xi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65.
7.祖保泉:《文心凋龙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Zu Baoquan.Wenxin Diaolong jieshuo(Explanation of Wenxnin Diaolong). Hefei: Anhui jiaoyu chuban she,1993.
8.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Yuan Hong. Houhanji jiaozhu (Annotation of the Records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Edited by Zhou Tianyou. Tianjin: Tianjin guji chuban she,1987.
9.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Yao Silian. Liangshu(The Book of the Li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73.
10.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凋龙〉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Zhang Shaokang. Liu Xie jiqi Wenxin Diaolong yanjiu (A Study on Liu Xie and Wenxin Diaolong).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 she,2010.
11.陶渊明着,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Tao Yuanming. Tao Yuanming ji (TaoYuanming Collection). Edited by Lu Qinli.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79.
12.甯赫、孙琳:《楚简〈老子〉否定副词“不”与“弗”的比较》,《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2004年3月),页26。Ning He, Sun Lin. Chujian Laozi fouding fuci “不” yu “弗” de bijiao (Comparison of Two Negative Adverbs “不” and “弗” on Guodian Bamboo Slips). Changchun gongcheng xueyuan xuebao 5.1(2004):pp.24-26.
13.杨明照:《增订文心凋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Yang Mingzhao. Zengding Wenxin Diaolong jiaozhu (Revised Proofreading and Annotation of Wenxnin Diaolong).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0.
14.——:《学不已斋杂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Xuebuyizhai zazhu (Collections of Xuebuyizha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 she,1985.
15.刘玉山:《“造宋”功臣后代在南朝的仕进研究(二)》,《殷都学刊》2011年第1期(2011年3月),页60-63。LIU Yushan. "Zaosong" gongcheng houdai zai nanchao de shiji yanjiu(On the Official Career of Descendants of Those Who Created Song Dynasty in South Dynasty).Yindu xuekan 1(Mar.2011): pp.59-64.
16.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Xiao Zixian. Nan qishu (The Book of the Southern Qi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72.
17.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Wei Shou. Weishu (The Book of the Wei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72.
脚注 :
1. 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0页。
2. 信佛说,参见杨明照先生《梁书刘勰传笺注》,《增订文心凋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页。贫寒庶族说,参见王元化先生《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文心凋龙讲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页。士族婚俗说,参见张少康先生《关于刘勰的生年和入定林寺的时间与原因》,《刘勰及其〈文心凋龙〉研究》第一章第三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树德建言志趣说,参见祖保泉先生《〈梁书·刘勰传〉注》,《文心凋龙解说》“附录”,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0页第④条注释。
3. 杨明照《增订文心凋龙校注》,第7页。
4. 王元化《文心凋龙讲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0页。
5. 王元化《文心凋龙讲疏》,第11页。
6. 王元化《文心凋龙讲疏》,第22页注释。
7. 沉约《宋书》卷四二刘穆之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07-1308页。
8. 沉约:《宋书》卷四二,第1308页。
9. 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7-428页。
10. 沉约《宋书》卷四二,第1309页。
11. 沉约《宋书》卷四二,第1310页。
12. 沉约《宋书》卷四二,第1310-1311。
13. 刘玉山《“造宋”功臣后代在南朝的仕进研究(二)》,载于《殷都学刊》2011年第1期(2011年3月),第60页。
14. 刘玉山《“造宋”功臣后代在南朝的仕进研究(二)》,第63页。
15. 沉约《宋书》卷四二,第1306页。
16. 沉约《宋书》卷四二,第1306页。
17. 沉约《宋书》卷四二,第1306页。
18. 沉约《宋书》卷八一,第2073—2076页。
19. 沉约《宋书》卷八一,第2076页。
20. 杨明照《学不已斋杂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35页。
21. 司马迁撰,裴駰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九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第2688页。
22. 司马迁撰,裴駰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九七,第2691页。
23.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60-2461页。
24. 沉约《宋书》卷九三隐逸传,第2278页。
25.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二,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96-897页。
26.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四,第936页。
27.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四,第943-944页。
28. 姚思廉《梁书》卷三八,第540页。
29.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序》,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9页。
30. 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二,第49-50页。
31.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四臧荣绪传附,第937页。
32.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四宗测本传,第940页。
33. 沉约《宋书》卷八一刘秀之本传:“东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第2073—2076页。
34. 逯钦立《陶渊明事蹟诗文繫年》:“太元十九年(西元三九四),陶渊明三十岁。十年丧妻。”逯按:“《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始室丧其偏。’吴谱:‘《礼》:三十曰壮,有室……先生盖两娶。本传称其妻翟氏……则继室实翟氏。’”《陶渊明集》附录二,第267页。
35.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八,第2280-2281页。
36.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九,第2309页。
37.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五,第959页。
38. 姚思廉《梁书》卷四一,第590页。
39. 杨明照《增订文心凋龙校注》,第8页。
40. 杨明照《学不已斋杂着》,第438页。
41. 具体表现是,以此一思路为参照,或贊之,如周绍恒;或驳之,如王元化;或修订之,如张少康、祖保泉等。
42. 甯赫、孙琳《楚简〈老子〉否定副词“不”与“弗”的比较》,载于《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2004年3月),第26页。
43. 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卷二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1页。
44.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五,第1971页。
45.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八,第2281页。
46. 魏收《魏书》卷六〇,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37页。
47. 沉约《宋书》卷七三,第1891页。
48. 萧子显《南齐书》卷二二,第405、417页。
49.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五,第956-957页。
50.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65-2766页。
51.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四,第2799页。
52.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四,第2440页。
53.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四,第2449页。
54.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四,第2451页。
55.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四,第2452页。
56.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四,第2460页。
57.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五,第962页。
58.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以下这种情形,即汉末魏晋以降,庶民阶层确实存在因“家贫”而“不婚娶”现象。王元化先生曾指出:刘勰“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晋书·范宁传》、《宋书·周朗传》都有当时平民‘鳏居每不愿娶,生儿每不敢举’的记载”。(王元化《文心凋龙讲疏》,第11页)按,“鳏居每不愿娶”二句,原文见于《宋书》卷八二《周朗传》,原文作“鳏居有不愿娶,生儿每不敢举”,是周朗上书谠言时政弊端之一:“凡为国,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广,患民之不育。自华、夷争杀,戎、夏竞威,破国则积尸竟邑,屠将则复军满野,海内遗生,盖不馀半。重以急政严刑,天灾岁疫,贫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鳏居有不愿娶,生子每不敢举。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绝,及淫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杀人之日有数途,生人之岁无一理,不知復百年间,将尽以草木为世邪?此最是惊心悲魂、恸哭太息者。”这裡讲的是影响“民之不育”的几类原因,包括连年边战、急政严刑、天灾岁疫以及青壮男丁“戍淹徭久,妻老嗣绝”,另加“淫奔所孕,皆復不收”等,所以形成一种“不愿娶”“不敢举”的社会风气,结果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力严重匮乏。此间值得注意的是:周朗所谓“鳏居不愿娶”者,主要针对庶民而言,以此说明有社会地位的“士人阶层”乃至“士族阶层”,显然不甚适宜。从东莞刘氏家族源流看,刘勰之家世及其社会地位,虽然无法与王、谢等高门甲族相提并论,但不同于一般底层之庶民,殆无疑义。张少康先生说:“刘勰一系属东莞刘氏,亦为层次较低的士族,因此,说他是地位低下的庶族出身恐怕不是很妥当。”(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凋龙〉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明乎此,则“鳏居不愿娶”之说,不宜用于解释刘勰“不婚娶”之成因,似不言而喻。又,周朗所讲“鳏居不愿娶”之原因,原本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包括“家贫”。不过,其中既然明言“不愿娶”,而非“不能娶”,则主观意愿之强烈,显而易见。类似的情况,在齐武帝永明七年《禁婚葬奢靡诏》,也可略见一斑:“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矩则。或裂锦绣,以竞车服之饰;涂金镂石,以穷莹域之丽。至斑白不婚,露棺累叶。苟相夸衒,罔顾大典。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復违犯,依事纠奏。”(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题并书《御选古文渊鉴》卷二六)这虽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奢靡之风对民间婚、丧礼制之影响,而造成“斑白不婚”之原因,但也与“家贫”相关。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此一诏令重点也是针对庶民。因此,顾炎武说:“侈于殡埋之饰,而民遂至于不葬其亲。丰于资送之仪,而民遂至于不举其女……岂知《召南》之女,迨其谓之⋯⋯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敛首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何至如《盐铁论》之云‘送死殚家,遣女满车’,齐武帝诏书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叶’者乎?马融有言:嫁娶之礼俭,则婚者以时矣;丧祭之礼约,则终者掩藏矣……周礼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停丧”条)
59. 祖保泉《文心凋龙解说》“附录”,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0页第④条注释。
60.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五,第958页。
61. 姚思廉《梁书》卷一八,第286页。
62. 姚思廉《梁书》卷四七,第648-649页。
63.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二,第2058页。
64.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三,第2177页。
65. 魏 收《魏书》卷四六,第1036页。
66. 沉 约《宋书》卷七三,第1891页。
67.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四,第943-944页。
68. 姚思廉《梁书》卷三三,第469页。
69. 姚思廉《梁书》卷四一,第590页。
70. 姚思廉《梁书》卷四九,第688页。
71. 姚思廉《梁书》卷五十,第701页。
72. 姚思廉《梁书》卷五〇,第726页。
73. 杨明照先生《梁书刘勰传笺注》谓:“六朝最重门第,立身扬名,干禄从政,皆非学无以致之。故史传所载少好学,少笃学,孤贫好学,孤贫笃志好学,比比皆是。舍人其一也。”并举谢灵运、范晔、关康之、刘瓛、江淹、孔子祛、沉约、袁峻等人为例。参见《增订文心凋龙校注》,第5页。
74.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九,第1629页。
75.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九,第2309页。
76.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四,第2456页。
77. 姚思廉《梁书》卷一三,第232-233页。
< 原创文章/视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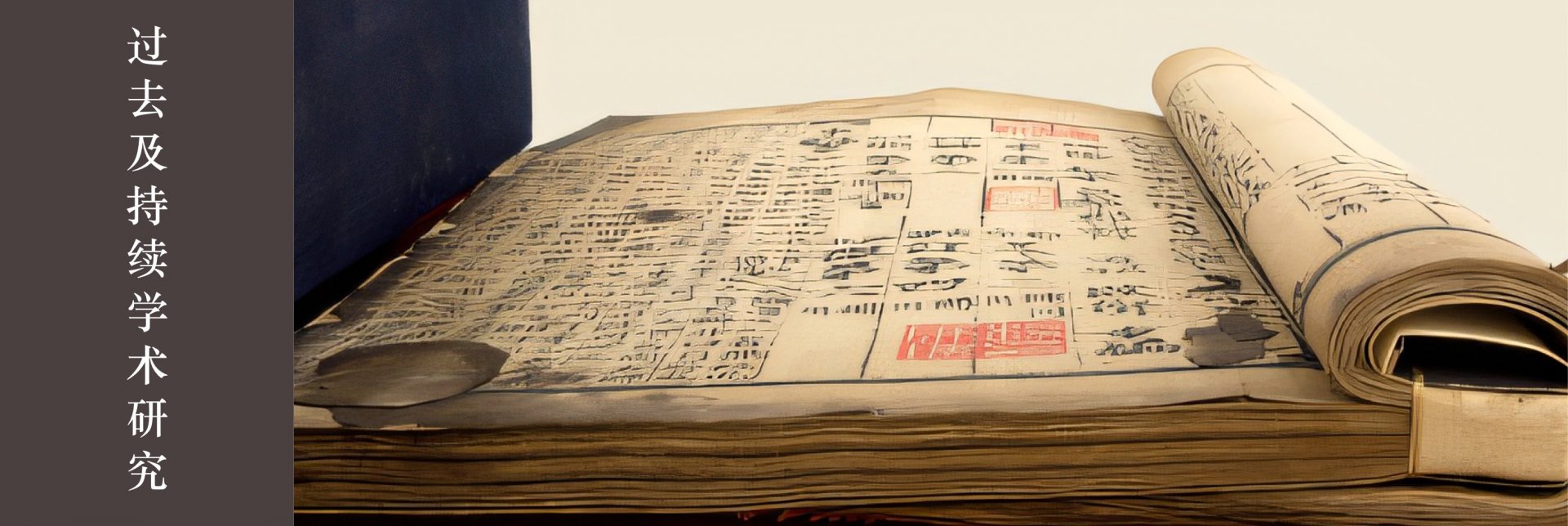



欢迎留言:
请登入/登记成为会员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