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Too Poor for Marriage" in Liu Xie’s Biography in Liang Shu
Chen Yunfeng
Pr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re, Hongkong Shu Yang University
(原刊載於香港《嶺南學報》復刊第十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6月,第89-110頁)
Abstract:Liu Xie’s Biography in Liang Shu, written by Yao Silian, mentioned that Liu Xie’s family lived in poverty, and he did not get married. There has been extensive debate in previous studies regarding this issue. Yet from re-reading the record of Liu Xie’s Biography, we could find another way of interpreting the interrelation among sentences, which suggests that Liu Xie’s bachelorism is not necessarily a result of his family’s poverty, but because he was too devoted to study. He was later converted to Seng You, who was an eminent monk, and settled in Dinglin Buddhist Temple, where he assiduously studied Buddhist Classics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and eventually became well-versed on the subject of Buddhism.
Keywords: Liang Shu (The Book of the Liang Dynasty);Liu Xie;family poverty; marriage; interrelation among sentences
姚思廉《梁書·劉勰傳》是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劉勰傳記資料,對了解、研究劉勰生平思想具有重要價值。但由於記載比較簡略,落實到某些具體問題,難免引發歧解乃至爭議。譬如,關於《梁書·劉勰傳》所載“家貧不婚娶”問題,即有諸多不同看法。為便於分析,茲抄錄《梁書·劉勰傳》該小節文字如次:
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1
關於劉勰“不婚娶”之原因,學界提出了多種說法。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信佛”說、“貧寒庶族”說、“士族婚俗”說以及“樹德建言志趣”說等2。這些看法,對全面、深入地理解劉勰身世、生平及其人生觀,顯然具有重要啓示價值。不過,如果重新細緻地研讀《梁書·劉勰傳》“家貧不婚娶”一段文字,幷聯繫相關史料,類比旁推,似尚有值得進一步辨析、闡釋之餘地。譬如,究竟如何理解“家貧”之具體情形,方顯得更合理?又如,“家貧”與“不婚娶”之間,究竟宜解作因果關係抑或併列關係?再如,從語氣、語義關係而言,“遂博通經論”與前文“篤志好學”以及“不婚娶”之間,是否前後呼應?類似這些細節問題,還有必要再加斟酌,或有助於披文入情,探得其實。
首先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梁書·劉勰傳》所載之“家貧”,由於沒有更具體之描述,本身就易滋歧解。譬如楊明照先生《梁書劉勰傳箋注》稱:“按舍人早孤而能篤志好學,其衣食未至空乏,已可概見。而史猶稱為貧者,蓋以家道中落,又早喪父,生生所資,大不如昔耳。非以家徒四壁,無以為生也。如謂因家貧,致不能婚娶,則更悖矣。”3意謂劉勰之“家貧”,乃相對於“喪父”前家道殷實狀況而言,泛指“生生所資,大不如昔”,而非“家徒四壁,無以為生”。王元化先生則認為:“劉勰少時入定林寺和不婚娶的原因,也只有用出身於貧寒庶族這件事才能較為圓滿地說明”4,“至於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於他是家道中落的貧寒庶族的緣故”5。關於劉勰入定林寺前是否因“家貧”而“無力負擔租役”問題,王元化先生另加解釋:“《梁書》本傳稱勰少時家貧,這個說法曾經引起了不少懷疑。在劉氏世系中,穆之、秀之位望不可謂不高,家產不可謂不富,為什麼到了劉勰竟會變得貧窮起來了呢?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困難。首先我們必須注意:穆之、秀之的後嗣在齊代宋後,已經家道中落……劉勰喪父後,仍然會落入微賤貧窮境地。”6
上列兩種意見,各自成理。但是,若深加追究,又不無可議之處。概括而言,主要有三。
其一,按照一般論者大致認可的劉勰世系,其間名望最著者,無疑就是劉穆之、劉秀之。前引論家以為“穆之、秀之的後嗣在齊代宋後,已經家道中落”,應該沒有多大問題,而家道究竟如何“中落”,尚語焉未詳,無妨略加補說。
按,劉穆之作為劉宋朝“佐命元勳”,雖然身後得劉裕顧念舊恩,追封為“南康郡公,邑三千戶”7;但後嗣不淑,爵祿傳承,日趨沒落。《宋書》劉穆之傳附傳載:“穆之三子,長子慮之嗣,仕至員外散騎常侍卒。子邕嗣……卒,子肜嗣。大明四年,坐刀斫妻,奪爵土,以弟彪紹封。齊受禪,降為南康縣侯,食邑千戶。”8《南史》甚而說“坐廟墓不修,削爵為羽林監”9。劉穆之其他諸子,仕途亦不甚順達,門庭日趨沒落,如:“中子式之字延叔……在任贓貨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長子敳……敳弟衍,大明末,以為黃門郎,出為豫章內史。晉安王子勳稱偽號,以為中護軍。事敗伏誅。”10又,敳弟劉瑀“陵物護前,不欲人居己上”,“使氣尚人”,“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坐奪人妻為妾,免官”11。又,“穆之少子貞之,中書黃門侍郎……子裒,始興相,以贓貨系東冶內”12。因此,有學者指出:“劉穆之的爵位由長子慮之嗣,後由慮之的兒子邕嗣,在宋孝武帝以前,有封國者地位還受到一定的尊重,但孝武帝時期,卻使得有封國者在本地區的地位與威信有所降低……劉穆之的後代發展卻並不太順利。”13又說:“寒門功臣後代即使以清流起家,但他們在仕進道路上也仍是艱難的,劉穆之的曾孫祥因蕭道成禪代而心懷不滿,蕭道成將他流放廣州,說他‘位涉清途,於分非屈’其實是有一定道理的。”14
其二,前引論家以為“在劉氏世系中,穆之、秀之位望不可謂不高,家產不可謂不富”,似不宜一概而論。相對而言,劉穆之雖然“家本貧賤,贍生多闕”15,但生性“奢豪”,後來勢力日盛,權位日高,“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16。他本人對此也有所檢省,“嘗白高祖曰:……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17。可見已然由“貧賤”而趨“富貴”階層。此一事也。劉秀之乃劉穆之從侄,同樣出身貧寒,位望亦高,但為政、立身卻迥然不同。《宋書》卷八一本傳載: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司徒劉穆之從兄子也……秀之少孤貧,有志操……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奉朝請。家貧,求為廣陵郡丞……秀之善於為政,躬自儉約……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併京邑貧士,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為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安悅焉……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蒞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18
可見,劉秀之雖然早年“孤貧”,但確有“志操”,權位日隆而“蒞官清潔”,以致身後“家無餘財”。秀之一系,“子景遠嗣,官至前軍將軍。景遠卒,子儁,齊受禪,國除”19。蕭齊代宋,難保爵號封邑,其家境復歸於貧,殆不難想見。因此,籠統地說劉勰祖上顯赫人物“家產不可謂不富”,似不甚妥當。同時也可以看出:《梁書》本傳說劉勰“出為太末令,政有清績”,庶近乎劉秀之“善於為政,躬自儉約”,而迥異於劉穆之“奢豪”“誕節”。
其三,因史家並未明言劉勰“家貧”具體情形,後人擬議,自然歧解紛出。上引楊明照、王元化先生之不同看法,即顯著之例。此外,由於不同論家所理解“家貧”標準未必一致,有些說法,也只能作為一家之言。譬如楊明照先生《讀梁書劉勰傳札記》認為,劉勰之“家貧”,“絕不等於當時勞動人民的一貧如洗,朝不謀夕;只能理解為他是一個沒落貴族家庭出身的子弟,生活大不如昔就夠了”,幷以《梁書·文學傳》為例,指出:
在這篇合傳里,目為“家貧”的共三人,除劉勰外,還有袁峻和任孝恭。《袁峻傳》云:“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任孝恭傳》云:“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略無所遺。”可見袁峻和任孝恭儘管“家貧”,尚有借書鈔讀的雅興,喫飯總不會有多大問題的。如果我們單把劉勰的“家貧”說得連飯都喫不上,那就未免太不了解歷史了。門閥制度盛行的時代,劉勰既是大族,又系達官之後,再窮也不至於此極吧。其所以要“依沙門僧祐”,固然不能說完全與生計無關;但謀生之道多端,朱百年的“以伐樵採箬為業”(見《宋書》卷九三《隱逸·朱百年傳》),沈顗的“樵採自資”(見《梁書》卷五一《處士·沈顗傳》),又何嘗不是解決生活問題的辦法。20
從這裡可以看出:或以為“一貧如洗”、“連飯都喫不上”才是“家貧”,或以為“家貧”不過泛指“沒落貴族家庭出身的子弟,生活大不如昔”。其間標準之懸殊,顯而易見。不過,楊明照先生援引與“家貧”相關資料以供參考,這一思路與方法,確有重要啓發意義。
“貧”與“富”相對,《說文》曰“貧,財分少也”,《六書故》曰“凡粟米絲麻材木可用者曰財”,本義指缺乏米粟布帛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故史籍曰某人“家貧”,一般指生計艱難、日用匱乏。如《史記》卷九六張丞相列傳附:“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21又卷九七酈生陸賈列傳:“酈生食其者,陳留髙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22又如《晉書》卷九四陶潛傳:“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23再以與劉勰同時代南朝人士為例:
《宋書·宗炳傳》:(宗炳)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24
《南齊書·王智深傳》:王智深……貧無衣……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25
《南齊書·臧榮緒傳》: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26
《南齊書·沈驎士傳》:驎士少好學,家貧……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驎士義行,曰:……家世孤貧,藜藿不給。27
《梁書·賀琛傳》:……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28
上列數例,大部分與劉勰境遇相類:失怙,幼孤,家貧。其間,有“掘莧根食之”者,有“販粟自給”者,亦有“藜藿不給”者。《梁書》劉勰傳並未明言其“家貧”具體情形,不過,以同時代幼孤而家貧者為參照,依類而推,劉勰年幼喪父,其“家貧”概況,或許亦相仿佛。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在史籍所載“家貧”者中,像王智深、沈驎士等,確實到了前引論者所謂“家貧如洗”之境地。至於為人所熟知之陶潛“家貧”,不僅面臨“缾無儲粟”29,“夏日抱長飢,寒夜無被眠”30之困境,還留有《乞食》一詩。由此看來,若遽然斷定劉勰之“家貧”、“衣食未至空乏”,並非“無以為生”,雖然不無可能,但畢竟難成篤定無疑之論。當然,更關鍵之問題乃在於:劉勰之“家貧”,是否一定導致“不婚”?具體討論詳下。
《梁書•劉勰傳》“家貧”之後緊接著說“不婚娶”,按照一般閱讀理解習慣,自然很容易被視為一種因果關係。前引王元化先生觀點,即依此思路而得出相應結論,故曰:“劉勰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於他是家道中落的貧寒庶族的緣故。”不過,恰如杜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一聯,既可以理解為一種因果關係,也未嘗不可理解為一種並列關係一樣,劉勰之“家貧不婚娶”,同樣可以有另一種理解,即“家貧”與“不婚娶”之間未必就是一種因果關係,而是客觀陳述兩種事實,亦即並列關係。《梁書》作者原本立意究竟如何?劉勰當年家境又如何?皆難以得其實情。所以,拓展史料之研閱範圍,考察相關史籍所載古人“家貧”與“婚娶”之關係,擇取同類可供參考之事例,或不失為努力接近歷史真實之嘗試。
前文曾引《宋書·劉秀之傳》為例,可知“秀之少孤貧”,早年雖“除駙馬都尉、奉朝請”,但仍難以擺脫生計困乏之窘境,故史籍曰:“家貧,求為廣陵郡丞。”這種為解決家境貧困而求官之行為,在魏晉南朝時期,似頗常見。其著名者如陶潛,年近而立,即因“親老家貧”而“求為州祭酒”;年近不惑,又因“生生所資,未見其術”之“貧苦”而求為彭澤令。又如,與臧榮緒俱隱京口,“世號為二隱”之一的關康之,“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但是,到了晚年,仍“以母老家貧,求為嶺南小縣”31。因此,宗炳之孫宗測曾發感慨:“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32但是,劉秀之雖然家貧,卻頗有“志操”與才器,得何承天之青眼,且以女妻之33。陶淵明雖然像五柳先生一樣,“環堵蕭然”,“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婚娶卻是及其時的,而且“始室喪其偏”後,復娶柴桑翟氏34。至於關康之,雖“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但顯而易見,也是屬於及時婚娶、有家室者。為說明問題,再舉數例如次:
《晉書》卷八八庾袞傳:……初,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父亡,作筥賣以養母……袞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35
《晉書》卷八九王育傳:王育字伯春……少孤貧,為人傭牧羊……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子章以兄之子妻之。36
《南齊書》卷五五孝義傳:永明元年,會稽永興倪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同里陳穰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氏收養之,及長,為營婚娶。37
《梁書》卷四一褚球傳:褚球字仲寶……球少孤貧……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㝢、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為之延譽。38
從以上這些例子中,不難看出:在現實生活中,或許確實存在因家貧而無力婚娶者,但應該著重強調的是,在缺乏具體載述或相關確鑿證據時,籠統地將“家貧”視作“不婚娶”之原因,似欠穩妥。從史籍記載看,“孤貧”者未必不能完成婚娶這一人生要務。即此而論,楊明照等學者在“家貧”因素之外,另求劉勰“不婚娶”之緣由,相對而言,顯得更合理些。
正如上文所言,從語義關係看,“家貧”與“不婚娶”未必構成因果關係,未嘗不可理解為一種並列關係,即“家貧”者一事,“不婚娶”者,另一事也。後一種理解的合理性在於:“不婚娶”之義,未必如一般學者所理解的“無力婚娶”,而未嘗不是強調傳主“不願婚娶”。也就是說,即使孤立地看,“不婚娶”其實也暗含兩種語義闡釋之可能:一種因某些客觀原因而無法實現婚娶之心願,另一種則指因個人心志而不想、不願婚娶。楊明照先生《梁書劉勰傳箋注》曾作一設問:
……益見舍人之不婚娶,原非由於家貧。至謂當時門閥制度,甚為森嚴。托姻結好,必須匹敵。舍人既是貧家,高門誰肯降衡?其鰥居終身,乃囿於簿閥,非能之而不欲,寔欲之而不能也。此說雖辨,然亦未安。緣舍人入梁,即登仕途,境地既已改觀,行年亦未四十。高即不成,低亦可就。如欲婚娶,猶未為晚。39
這裡提到的“至謂……”云云,乃指其他論者之認識。其間所及“能之而不欲”與“欲之而不能”之提法,頗有啓發意義。以“家貧”為“不婚娶”之原因者,認為劉勰是“欲之而不能”;楊明照先生既然強調劉勰“不婚娶”主要由於“信佛”,其思路自然偏於“能之而不欲”。這一點,楊明照《學不已齋雜著》所收《讀梁書劉勰傳札記》一文中有更明確表述:“劉勰的‘不婚娶’,我認為不是因為‘家貧’,而是由於信佛,試想一個達官大族的後代,即使家道沒落,總不至於窮得到了不能結婚的地步。《梁書》《南史》只說‘不婚娶’,‘不’下並未著有其它字眼(如‘能’字之類),那就不應以意逆志地說成是連婚都結不起”40。劉勰“不婚娶”究竟是否由於“信佛”,學界意見不一,但影響很大41。不過,其間提到的《梁書》、《南史》“只說‘不婚娶’,‘不’下並未著有其它字眼(如‘能’字之類)”這一說法,似尚未引起必要關注。竊以為就語義理解來看,“不婚娶”之“不”字,誠不宜輕易放過,值得細加品味、琢磨。
按,《梁書·劉勰傳》“不婚娶”之“不”字,其實未必另著其他字眼如“能”字之類,即可表達一種強烈的主觀意願,也就是自覺地選擇“不婚娶”,而非由於“家貧”等外力之所迫。換言之,勰之“不婚娶”,乃基於主觀、內在之心理意願與志向信念——儘管這一意願與信念未必如楊明照先生所言之“信佛”,而非由於生計困頓、家資貧乏。
有論者通過對楚簡《老子》中“不”、“弗”二字語法功能的統計分析,指出:“‘不’在否定句中常用來表示當事人強烈的主觀色彩或傾向性。具有強調特徵的‘不’句大多是對否定者的主觀意願表示強調……‘不’句有很多修飾語明顯表示否定者的主觀色彩……具有強調特徵的‘弗’句主要是說話人對客觀不可能性表示判斷和強調⋯⋯‘不’句大多數表示對否定者主觀意志的強調。而具有強調特徵的‘弗’句大多表示說話人對客觀不可能性的強調。”42這一結論是基於相關出土文獻中“不、弗”用例之分析,自然不宜直接引作《梁書》劉勰傳“不婚娶”之“不”字的闡釋依據,但至少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思考:劉勰“不婚娶”,是否也屬於一種具有明顯主觀意願的自覺選擇?以此為線索,徵之於史籍相關記載,說明這一理解大體符合實情。
檢討史籍,可知“不婚娶”、“不娶”以及“未婚娶”、“未娶”是兩種常見的表述。通過考察“不”字句與“未”字句之差異,或許有助於解決《梁書》劉勰傳“不婚娶”的語義理解問題。茲先列舉與婚娶問題相關之“未”字句:
《後漢紀》姜肱傳:……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隱居靜處,非義不行,敬奉舊老,訓導後進。嘗與小弟季江俱行,為盜所劫,欲殺其弟。肱曰:“弟年稚弱,父母所矜,又未聘娶,願自殺以濟家。”43
《晉書》王國寶傳:……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為忠。將納國寶女為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44
《晉書》庾袞傳: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翕。及翕卒,袞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45
《魏書》韓麒麟傳附子熙傳:子熙與弟娉王氏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46
《宋書》顏延之傳:顏延之字延年……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47
《南齊書》豫章文獻王: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幾何……雖才愧古人,意懷粗亦有在,不以遺財為累。主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未嫁。48
《南齊書》崔懷慎傳附公孫僧遠傳: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飢谷貴,僧遠省餐減食,以養母、伯……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為之成禮。49
以上諸例,說明“未婚”、“未娶”或“未婚娶”,一般指陳客觀事實,或由於客觀原因,如因孤貧而無力置辦財禮,或因對方死亡等,造成想成婚者未能實現主觀意願。這類情形,事出無奈,欲為之而未能如願。
與上列諸例所表示的情況不同,史籍曰某人“不娶”或“不婚娶”,則往往強調當事者明確的主觀意願,是一種“能而不欲”的自覺選擇,如以下各例:
《後漢書》梁鴻傳: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娉之。50
《後漢書》盛道妻傳:犍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系,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賫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51
《晉書》郭文傳: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52
《晉書》楊軻傳: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粗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53
《晉書》公孫永傳: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岩間,欣然自得。54
《晉書》石垣傳: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粗弊。55
《晉書》陶淡傳: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谷,不婚娶。56
《南齊書》朱謙之傳: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唐人也……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57
由上列諸例可見:前引論者所言“不”字作為古漢語常用否定副詞,往往體現著施事者自覺、主動的一種抉擇意識;這一“不”字所具備之語法功能、語義作用,在史籍有關“不婚娶”一類的文句中,同樣是切合實際的。也就是說,上列史籍所言“不娶”、“不婚”、“不婚娶”者,一般意在強調傳主無意娶妻,主觀傾向至為明顯。以此類推,《梁書·劉勰傳》載“家貧不婚娶”,其立意重點,似不在“欲之而不能”,所強調者,乃劉勰在婚娶問題上“能之而不欲”之態度與選擇58。
以上援引史籍相關載錄,或有助於說明劉勰之“不婚娶”,諒非由於“家貧”所致,而是出於某種志向信念所作出的帶有強烈主觀意願之選擇。關於此種志向或信念,學界也有學者論及,其中比較重要的,有三種說法:一者以為“信佛”,前引楊明照先生之觀點,最有代表性;二者以為盡“孝”,范文瀾先生有此說;三者以為“樹德建言”,祖保泉先生《〈梁書·劉勰傳〉注》曾有說明:“劉勰終生不娶,受生活環境的限制和‘樹德建言’的志趣支配是重要原因,受佛教思想影響也是原因之一。‘因信佛而終身不娶’或‘為求奉時以騁績而不娶’等論斷,皆嫌偏執。”59徵諸實際,竊以為第三種說法相對穩妥,比較切合實際,因為此說綜合考慮了多種因素,如“生活環境的限制”、“佛教思想影響”,其中對“信佛”說以及“奉時以騁績”說,亦未全盤否定,而只是目之為“偏執”之見;同時,又根據《文心雕龍·序志》內容,將“樹德建言”之志趣視作劉勰“不婚娶”的重要原因之一。
應該注意的是,“樹德建言”之志趣,見於《文心雕龍·序志》篇,是劉勰入定林寺,且“齒在踰立”之後。這是劉勰而立之年的人生志向,是否直接等同於劉勰少時情形,似尚可斟酌。但是,從人生“志趣”的角度探求劉勰“不婚娶”之原因,這一思路確實富有啓發意義。如果回到《梁書》本傳,即不難發現,影響劉勰在“早孤”而“家貧”情形下,選擇“不婚娶”之原因與目的,答案就在前後文:從原因說,是由於自幼“篤志好學”;從目標與結果說,則是入定林寺“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終於“積十餘年”之功,達到了“博通經論”之境。因此,從語義關係上分析,《梁書》劉勰本傳所言“家貧”,其實是承接前文“早孤”二字——因“早孤”而“家貧”;“不婚娶”之原因,關鍵不在“家貧”,而是呼應前文“篤志好學”。總起來看,因為劉勰自幼篤志好學,“早孤”與“家貧”固然給他的學習帶來種種障礙與困難;從另一個角度看,又有助於反激出更強烈的求知慾,更執著的學術追求。為了滿足這種求知慾,實現人生目標,劉勰“不婚娶”且“依沙門僧祐”,確實有助於更好地以精專、勤謹之苦功與心力,努力達成人生理想——“遂博通經論”之“遂”字,其實已經標示了“博通”之境與“篤志好學”之間的內在關聯性。
考諸史籍,不難得知:史籍謂某人“家貧”,往往是為了突出某一品格或人生志向。如《南齊書》韓靈敏傳:“韓靈敏……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尋母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苽半畝,朝採苽子,暮已復生,以此遂辦葬事。”60婚、喪乃禮制規定之大事,韓氏兄弟因家貧而合力躬耕,意在備辦其母喪葬。又如《梁書》馮道根傳:“馮道根字巨基……少失父,家貧,傭賃以養母。”61再如《梁書》沈崇傃傳:“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踴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焉……母卒……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62類似這些“家貧”之載記,皆意在突出傳主如何盡其孝道,表彰其品德之優秀。
當然,史籍載某人“家貧”,更常見的情況,是意在說明傳主如何勤奮好學,如以下諸例:
《後漢書》荀悅傳:悅字仲豫……家貧無書,每之人閒,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63
《晉書》車胤傳: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64
《魏書》許彥傳:許彥,字道謨……彥少孤貧,好讀書,後從沙門法叡受《易》。65
《宋書》顏延之傳: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66
《南齊書》沈驎士傳:……驎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驎士義行,曰:“……家世孤貧……懷書而耕,白首無倦……”67
《梁書》王僧孺傳:(王僧孺)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68
《梁書》褚球傳:褚球字仲寶……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69
《梁書》袁峻傳: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70
《梁書》劉峻傳: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71
《梁書》任孝恭傳:孝恭幼孤……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72
這些例子所言“家貧”,顯然並未止於客觀記載,而是將“家貧”與“好學”之志聯繫起來73,突出傳主刻苦自勵、精進不止之精神。《梁書·劉勰傳》說勰“早孤,篤志好學”與“家貧”,其立意殆亦與此相近。尤值得玩味者,乃以下諸例:
《後漢書》王充傳:充少孤……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74
《晉書》王育傳:王育字伯春……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75
《晉書》祈嘉傳: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76
《梁書》沈約傳:沈約字休文……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能屬文。77
縱觀此類事例,不難看出其共同表述方式與潛在思維:好學→家貧→如何求學→效果如何。《梁書·劉勰傳》亦同此例: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遂博通經綸。弄清史家著述立意與思路,有助於明確這樣一個問題,即《梁書·劉勰傳》所言“家貧”,首先不是作為後一句“不婚娶”之原因,而是重在呼應前文,“家貧”與“早孤”有關,但更重要的是為了突出劉勰如何“篤志好學”,並以“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申述之,很好地說明了“博通經論”之成因。質言之,“遂博通經論”之“遂”字,其實與前文“篤志好學”遙相呼應。這種語氣、語義之關係,與上文所舉王充、王育、祈嘉、沈約傳“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遂博通經史”、“遂博通經傳”、“遂博通群籍”云云,在表達方式及著述旨意上,如出一轍。
綜上所論,大致可得如下三點認識:第一,就史籍所載同類材料看,《梁書·劉勰傳》所謂“家貧”,其具體內涵之理解,因缺乏明確而直接之證據,既不宜理所當然地解作“無以為生”,亦難以得出“衣食未至空乏”之判斷,有待進一步考索。第二,無論是就文義關係而言,還是參照相關史料,劉勰之“家貧”,未必與“不婚娶”存在直接關係——“家貧”主要承接“早孤”而言,“不婚娶”則與“篤志好學”相關聯;“不婚娶”之“不”字,主要不是指迫於“家貧”而無力及時婚娶,而是強調“能而不欲”之主觀選擇與意願。第三,以史籍載記某人“家貧”之常見表述方式與立意宗旨為參照,可知《梁書·劉勰傳》曰“家貧”,意在突出劉勰雖然“早孤、家貧”,但依然立志向學,最終臻於“博通經論”之境。如此理解,“篤志好學”與“家貧不婚娶”以及“遂博通經論”之間,文義關係前後照應,顯得更為合理貫暢。
最後擬補充說明三點:第一,本文宗旨在於從語義關係的角度,借助史籍中的相關記載,與《梁書·劉勰傳》“家貧不婚娶”一節表述方式進行比較類推,為劉勰生平研究中的一個疑難問題,提供另一種闡釋之可能。在此過程中,注重同類史料的類比旁推、否定副詞語氣與語義之關係,此一研究對如何更好地運用文本細讀法,發現並提煉史家寫作立意與表述方式之關聯,或有一定啟發意義。第二,經由相關論證,說明《梁書·劉勰傳》“家貧不婚娶”五字,不宜連讀,「家貧」二字之後宜加點讀。如此標點,給研究者帶來更多的闡釋空間。句讀與文義關係甚為密切,關鍵之處不宜忽略,“家貧不婚娶”句義理解問題,或可視為一個比較典型之個案。第三,由於劉勰生平資料比較匱乏,亦難以找到魏晉六朝因“篤志好學”而“不婚娶”之相關例證,故文中所作推論、闡釋,並未斷然判定劉勰“不婚娶”主因在於“篤志好學”,而是依據相關史籍資料,參照史家共有的表述習慣及其基本立意,綜合考量多種因素,進而形成如下推論:促成劉勰“不婚娶”且“依沙門僧祐”之原因有兩點:一是精神層面的“篤志好學”,二是物質層面的因“早孤”導致之“家貧”,而“家貧”又進一步強化了“篤志好學”之心志。作為一種推論,在學界已有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新的闡釋之可能,雖非確鑿無疑之定論,畢竟有助於推動劉勰生平之研究。因篇幅限制,有關劉勰“篤志好學”之心志與《文心雕龍》相關理論觀念之關係,未遑涉及,有待另文討論,以期進一步顯示本文提出的學術新認識對《文心雕龍》研究之助益。
徵引書目 :
1.王元化:《文心雕龍講疏》,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版。Wang Yuanhua.Wenxin Diaolong jiangshu (Interpretation of Wenxnin Diaolong). Shanghai: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2012.
2.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二版。Si Maqian. Shiji (The Historical Records). Edited by Pei Yin, explored by Sima Zhen and expounded by Zhang Shoujie. Beijing: Zhonghua shuju, Second edition,1982.
3.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Li Yanshou. Nanshi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75.
4.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Shen Yue. Songshu (The Book of the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74.
5.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Fang Xuanling. Jinshu (The Book of the Jin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74.
6.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Fan Ye. Houhanshu (The Book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Edited by Li Xi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65.
7.祖保泉:《文心雕龍解說》,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Zu Baoquan.Wenxin Diaolong jieshuo(Explanation of Wenxnin Diaolong). Hefei: Anhui jiaoyu chuban she,1993.
8.袁宏撰,周天遊校注:《後漢紀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Yuan Hong. Houhanji jiaozhu (Annotation of the Records of the Later Han Dynasty). Edited by Zhou Tianyou. Tianjin: Tianjin guji chuban she,1987.
9.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Yao Silian. Liangshu(The Book of the Lia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73.
10.張少康:《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Zhang Shaokang. Liu Xie jiqi Wenxin Diaolong yanjiu (A Study on Liu Xie and Wenxin Diaolong).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 she,2010.
11.陶淵明著,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Tao Yuanming. Tao Yuanming ji (TaoYuanming Collection). Edited by Lu Qinli.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79.
12.甯赫、孫琳:《楚簡〈老子〉否定副詞“不”與“弗”的比較》,《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2004年3月),頁26。Ning He, Sun Lin. Chujian Laozi fouding fuci “不” yu “弗” de bijiao (Comparison of Two Negative Adverbs “不” and “弗” on Guodian Bamboo Slips). Changchun gongcheng xueyuan xuebao 5.1(2004):pp.24-26.
13.楊明照:《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Yang Mingzhao. Zengding Wenxin Diaolong jiaozhu (Revised Proofreading and Annotation of Wenxnin Diaolong).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0.
14.——:《學不已齋雜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Xuebuyizhai zazhu (Collections of Xuebuyizha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 she,1985.
15.劉玉山:《“造宋”功臣後代在南朝的仕進研究(二)》,《殷都學刊》2011年第1期(2011年3月),頁60-63。LIU Yushan. "Zaosong" gongcheng houdai zai nanchao de shiji yanjiu(On the Official Career of Descendants of Those Who Created Song Dynasty in South Dynasty).Yindu xuekan 1(Mar.2011): pp.59-64.
16.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版。Xiao Zixian. Nan qishu (The Book of the Southern Qi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72.
17.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Wei Shou. Weishu (The Book of the Wei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shuju,1972.
腳註 :
1. 姚思廉《梁書》卷五十,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710頁。
2. 信佛說,參見楊明照先生《梁書劉勰傳箋注》,《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7頁。貧寒庶族說,參見王元化先生《劉勰身世與士庶區別問題》,《文心雕龍講疏》,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1頁。士族婚俗說,參見張少康先生《關於劉勰的生年和入定林寺的時間與原因》,《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研究》第一章第三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頁。樹德建言志趣說,參見祖保泉先生《〈梁書·劉勰傳〉注》,《文心雕龍解說》“附錄”,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0頁第④條注釋。
3. 楊明照《增訂文心雕龍校注》,第7頁。
4. 王元化《文心雕龍講疏》,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0頁。
5. 王元化《文心雕龍講疏》,第11頁。
6. 王元化《文心雕龍講疏》,第22頁注釋。
7. 沈約《宋書》卷四二劉穆之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307-1308頁。
8. 沈約:《宋書》卷四二,第1308頁。
9.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27-428頁。
10. 沈約《宋書》卷四二,第1309頁。
11. 沈約《宋書》卷四二,第1310頁。
12. 沈約《宋書》卷四二,第1310-1311。
13. 劉玉山《“造宋”功臣後代在南朝的仕進研究(二)》,載於《殷都學刊》2011年第1期(2011年3月),第60頁。
14. 劉玉山《“造宋”功臣後代在南朝的仕進研究(二)》,第63頁。
15. 沈約《宋書》卷四二,第1306頁。
16. 沈約《宋書》卷四二,第1306頁。
17. 沈約《宋書》卷四二,第1306頁。
18. 沈約《宋書》卷八一,第2073—2076頁。
19. 沈約《宋書》卷八一,第2076頁。
20. 楊明照《學不已齋雜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35頁。
21.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卷九六,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二版,第2688頁。
22.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卷九七,第2691頁。
23.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460-2461頁。
24. 沈約《宋書》卷九三隱逸傳,第2278頁。
25. 蕭子顯《南齊書》卷五二,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896-897頁。
26. 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四,第936頁。
27. 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四,第943-944頁。
28. 姚思廉《梁書》卷三八,第540頁。
29.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序》,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59頁。
30. 陶淵明《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卷二,第49-50頁。
31. 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四臧榮緒傳附,第937頁。
32. 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四宗測本傳,第940頁。
33. 沈約《宋書》卷八一劉秀之本傳:“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第2073—2076頁。
34. 逯欽立《陶淵明事蹟詩文繫年》:“太元十九年(西元三九四),陶淵明三十歲。十年喪妻。”逯按:“《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始室喪其偏。’吳譜:‘《禮》:三十曰壯,有室……先生蓋兩娶。本傳稱其妻翟氏……則繼室實翟氏。’”《陶淵明集》附錄二,第267頁。
35.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八八,第2280-2281頁。
36.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八九,第2309頁。
37. 蕭子顯《南齊書》卷五五,第959頁。
38. 姚思廉《梁書》卷四一,第590頁。
39. 楊明照《增訂文心雕龍校注》,第8頁。
40. 楊明照《學不已齋雜著》,第438頁。
41. 具體表現是,以此一思路為參照,或贊之,如周紹恒;或駁之,如王元化;或修訂之,如張少康、祖保泉等。
42. 甯赫、孫琳《楚簡〈老子〉否定副詞“不”與“弗”的比較》,載於《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2004年3月),第26頁。
43. 袁宏撰,周天遊校注《後漢紀校注》卷二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1頁。
44.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七五,第1971頁。
45.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八八,第2281頁。
46. 魏收《魏書》卷六〇,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337頁。
47. 沈約《宋書》卷七三,第1891頁。
48. 蕭子顯《南齊書》卷二二,第405、417頁。
49. 蕭子顯《南齊書》卷五五,第956-957頁。
50.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八三,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765-2766頁。
51.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八四,第2799頁。
52.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四,第2440頁。
53.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四,第2449頁。
54.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四,第2451頁。
55.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四,第2452頁。
56.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四,第2460頁。
57. 蕭子顯《南齊書》卷五五,第962頁。
58. 當然,我們也應該注意以下這種情形,即漢末魏晉以降,庶民階層確實存在因“家貧”而“不婚娶”現象。王元化先生曾指出:劉勰“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於他是家道中落的貧寒庶族的緣故。《晉書·范寧傳》、《宋書·周朗傳》都有當時平民‘鰥居每不願娶,生兒每不敢舉’的記載”。(王元化《文心雕龍講疏》,第11頁)按,“鰥居每不願娶”二句,原文見於《宋書》卷八二《周朗傳》,原文作“鰥居有不願娶,生兒每不敢舉”,是周朗上書讜言時政弊端之一:“凡為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及淫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為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這裡講的是影響“民之不育”的幾類原因,包括連年邊戰、急政嚴刑、天災歲疫以及青壯男丁“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另加“淫奔所孕,皆復不收”等,所以形成一種“不願娶”“不敢舉”的社會風氣,結果人口銳減,社會生產力嚴重匱乏。此間值得注意的是:周朗所謂“鰥居不願娶”者,主要針對庶民而言,以此說明有社會地位的“士人階層”乃至“士族階層”,顯然不甚適宜。從東莞劉氏家族源流看,劉勰之家世及其社會地位,雖然無法與王、謝等高門甲族相提並論,但不同於一般底層之庶民,殆無疑義。張少康先生說:“劉勰一系屬東莞劉氏,亦為層次較低的士族,因此,說他是地位低下的庶族出身恐怕不是很妥當。”(張少康《劉勰及其〈文心雕龍〉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頁)明乎此,則“鰥居不願娶”之說,不宜用於解釋劉勰“不婚娶”之成因,似不言而喻。又,周朗所講“鰥居不願娶”之原因,原本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包括“家貧”。不過,其中既然明言“不願娶”,而非“不能娶”,則主觀意願之強烈,顯而易見。類似的情況,在齊武帝永明七年《禁婚葬奢靡詔》,也可略見一斑:“三季澆浮,舊章陵替。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瑩域之麗。至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誇衒,罔顧大典。可明為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違犯,依事糾奏。”(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題並書《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六)這雖然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奢靡之風對民間婚、喪禮制之影響,而造成“斑白不婚”之原因,但也與“家貧”相關。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此一詔令重點也是針對庶民。因此,顧炎武說:“侈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豈知《召南》之女,迨其謂之⋯⋯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送死殫家,遣女滿車’,齊武帝詔書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五“停喪”條)
59. 祖保泉《文心雕龍解說》“附錄”,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0頁第④條注釋。
60. 蕭子顯《南齊書》卷五五,第958頁。
61. 姚思廉《梁書》卷一八,第286頁。
62. 姚思廉《梁書》卷四七,第648-649頁。
63.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六二,第2058頁。
64.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八三,第2177頁。
65. 魏 收《魏書》卷四六,第1036頁。
66. 沈 約《宋書》卷七三,第1891頁。
67. 蕭子顯《南齊書》卷五四,第943-944頁。
68. 姚思廉《梁書》卷三三,第469頁。
69. 姚思廉《梁書》卷四一,第590頁。
70. 姚思廉《梁書》卷四九,第688頁。
71. 姚思廉《梁書》卷五十,第701頁。
72. 姚思廉《梁書》卷五〇,第726頁。
73. 楊明照先生《梁書劉勰傳箋注》謂:“六朝最重門第,立身揚名,干祿從政,皆非學無以致之。故史傳所載少好學,少篤學,孤貧好學,孤貧篤志好學,比比皆是。舍人其一也。”並舉謝靈運、范曄、關康之、劉瓛、江淹、孔子祛、沈約、袁峻等人為例。參見《增訂文心雕龍校注》,第5頁。
74.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四九,第1629頁。
75.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八九,第2309頁。
76.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四,第2456頁。
77. 姚思廉《梁書》卷一三,第232-233頁。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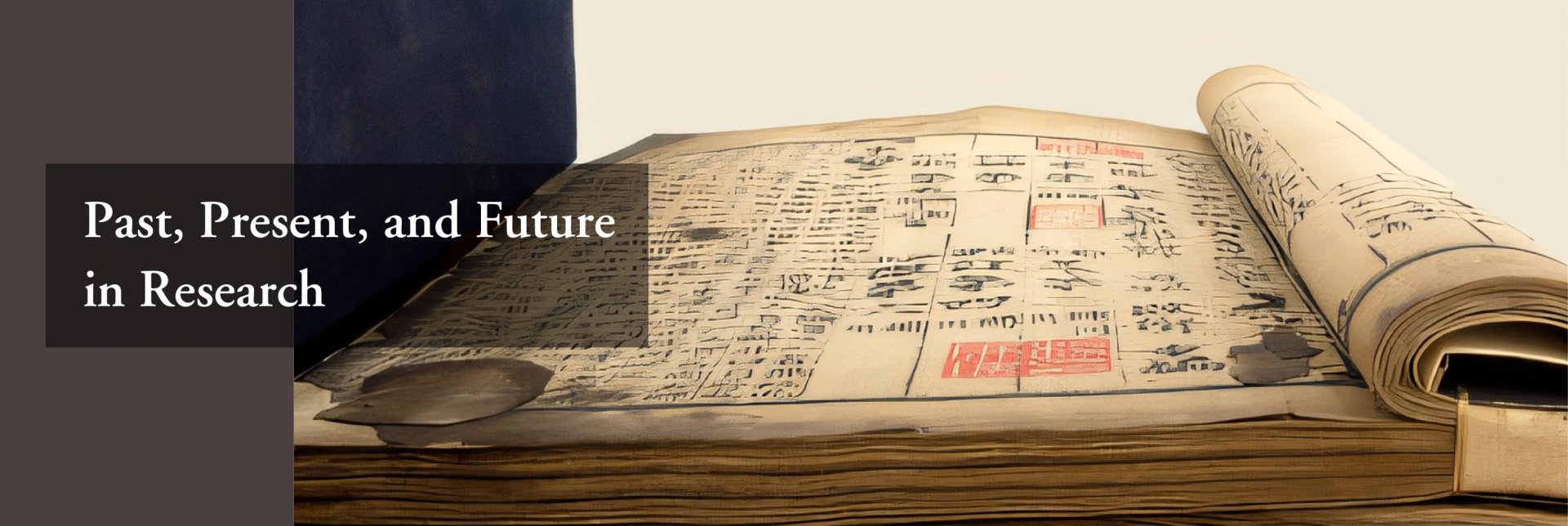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