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惡論的反思
性善、性惡的問題,困擾學者很久,各有見解。當年岑溢成老師說:「性善是人類獨有,性惡是與禽獸共有」,此解釋就長久存放在心裡。步入社會,所遇的人事與環境,使我經常重新思考。青年時憤世嫉俗,性格有點嫉惡如仇;到中年時,發覺立場與道德觀念的不同,每人都能解釋並原諒自己的性惡行為;到了負責行政,發現人性很難測度,自私自利幾乎是普遍現象。究竟人如何才能積善去惡?
文獻上紀錄,最初提出「性」的是孔子。他說「性相近,習相遠也」(《論語‧陽貨》)1從文句去理解,孔子在「性」方面,沒有加以詮釋。即此「性」可以含有「惡」,也可帶有「善」,但根據《論語》的內容,孔子認為人有向善的傾向,例如「仁者,愛人」。而此「性」字,亦顯示出孔子偉大之處。徐復觀先生認為:
由孔子而確實發現了普遍地人間,亦即是打破了一切人與人的不合理的封 域,而承認只要是人,便是同類,便是平等的理念。此一理念,實已妊育 於周初天命與民命並稱之思想原型中;但此一思想原型,究係發自統治者 的上層份子,所以尚未能進一步使其明朗化。此種理念之所以偉大,不僅在古代希臘文化中,乃至在其他許多古代文明中,除了釋迦、耶穌,提供 了普遍而平等的人間理念以外,都是以自己所屬的階級、種族來決定人的差等…孔子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很明顯地發現了,並實踐了普遍地人間的理念,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2
簡單一句「性相近,習相遠」,已明顯表達人類的天性是接近的,沒有特別高貴,特別卑微。孔子的「為仁由己」,是將道德的自主權回歸於人類。到《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直接表達人是性善。至孟子及荀子時代,才提出「性善」、「性惡」論,此命題亦成為後世諸賢所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一。
熊公哲簡略地解說過性善、性惡的各家學說的發展:
先儒論性,考之王充《論衡‧本性篇》約有七家。以為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之者,周人世碩也,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碩相出入。以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者,孟子也。以 為性無善無惡之分…告子也。以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作〈性惡〉之篇, 因以非難孟子者,荀子也。以為天生人以禮義為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者,陸賈也。以為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性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其陽氣,謂其性惡者,是其陰氣,而謂孟子、荀子二家各見其一端者,董仲舒也。以為性生而然,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出形於外, 形外則謂之陽,不發則謂之陰。又若反董仲舒之說者,劉子政也。…至於仲任(王充字)則頗以世碩、公孫尼子之徒得其正。別有〈率性〉一篇,自暢其說。外此諸儒,如楊子雲則曰:「人之性善惡混氣也者,其所由以適於善惡之焉也歟?」韓退之則本申鑒「上下不移,中則人事存焉」(荀悅作)之說,而演為三品之論。迨及有宋諸子,又揭舉「理」「氣」二字,謂性無不善,氣有清濁。3
據《論衡‧本性》載:「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4應是最早提出性善惡的問題。內文認為人有善惡,長養善則善,長養惡則惡。其後各朝代均有儒者論及之,各有己見,但所討論的,始終離不開孟子的性善論及荀子的性惡論。所以本文就以孟、荀二家作出討論中心,旁及宋、明諸儒。
本文內容先論性善惡的理據,再討論本善、本惡,此數節是集不同學者的見解而成,徐復觀先生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已有較詳細的分析;末章則是筆者的感悟,並論及近代諸學者如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傅佩榮等的研究成果。
孔子並沒有明確說出人是性善或性惡。孔子認為人類本性是接近的,可以這樣理解,人類原始的性是善,因不同的環境發展而有差距。孟子受業於子思的門人,是孔門嫡系。子思在《中庸》開宗明義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5這陳述句激起人類思考「人、天」的關係,人為甚麼是「人」?人的特質及內涵應該如何?「天命之謂性」已明確說出人類的「性」來自天命,上節已提到,天命自然是善。故孟子常常提及「人、禽」之別。徐復觀先生曾用「驚天動地」去形容《中庸》此三句,可知其重要性。
人,為甚麼是人?帶出不少思考的地方:第一,孔子說出性相近,有向善的傾向,但此向善的傾向的原動力,和這善性的「體」,究竟應如何理解?成為一個疑問。第二,天地萬物,只有人類能思考生命。花草樹木、礦物石塊,都是「無情」,即天地、日月、草木、山河等等,都應該是沒有感覺,說白一點,是沒有神經反應;而禽獸則是受制於生理,一切的活動均沒有自我意識,純粹是自然反應,例如沒有不忠心的狗,沒有不反哺的烏鴉,大象動情時的暴橫等,都是不自主。然而,人類卻有出賣親人、朋友的人,有不孝,也有孝順的人,有個人的自由意志。倘若天地萬物,沒有人類的感情去表達,沒有人類的讚歎,則宇宙萬物的美善,如同無物。只有透過人類的讚歎,宇宙就存在著美善。故老子說:「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所謂「人亦大」是透過人類呈現宇宙的美善。
孟子是子思的再傳弟子,是孔子的信徒,他提出「四端」是與生俱來的本性,不須假求於外而自有,是切合了「天命之謂性」的天命。即人類的至善本性是上天付與人類的天然自性,只要你是人,你就自然具足「仁、義、禮、智」(四端)的本性。這理論同時亦填補了孔子解釋人類有向善傾向的缺口,是性善論的主要依據。如何確定四端是本有,不假外求?孟子說: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6
孟子並以人「見孺子將入於井」的心理反應,證明人是性善,其理據是人皆有挽救將陷阱孺子的心,因而產生「怵惕惻隱」,並非討厭孺子之聲,並非要結交其父母,並非要在鄉黨爭取名聲。此行為,純粹出於自然的反應,而此「怵惕惻隱」反應,就是惻隱之心,自然而然,足以證明人是性善。
基於人是性善,孟子所提出仁政、王道、王政等概念,都本著性善論。〈公孫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7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不忍人之心是源於性善。在〈梁惠王上〉中,孟子因齊宣王放生一用作釁鐘的牛,而指出宣王的不忍其「觳觫而就死地」就是仁者之心,具備仁者之心必定能推行仁政。孟子並解釋由個體的關懷及愛,而能推演至對整個民族國家的關懷及愛,此稱為「推恩」,能推恩,治國就可「運於掌上」。此理論來自「親親民」的概念,人從環繞「我」的親人開始,擴而充之,而愛家族、愛社會、愛國家、愛天下。故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梁惠王上〉)8齊宣王的好貨好色,孟子亦不加以批評,指出「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梁惠王下〉,要與百姓同所好。孟子認為能「舉斯心加諸彼」,則所推行的必是仁政。
孔子的忠恕是「內聖」,而孟子的「仁政」是外王。能內聖就能外王,孟子的性善論就是說人人皆能內聖外王,因為人人皆性善。
人無異於禽獸者飲食情慾,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乃人具有四端。人倘若放縱慾望,過分著重感官的享受,就會「陷溺其心」〈告子上〉,故說「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使與生俱來的善性受到蒙蔽,人性皆平等,孟子認為人因為環境發展不同,而有不同的成就。若擴而充之,善性自然流露。
《荀子‧正名篇》:「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9及《性惡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10荀子先解釋何謂「性」?性者,天之就也,生之所以然者為性,也就是不學而能者。性有傾向惡的可能,但這並不是絕對的惡。〈正名〉篇所說的「精合感應」是指人對外界一切的刺激(筆者稱之「外緣」)的自然反應。這與「不事而然」「不可學不可事」同是與生俱來不必學習,不必教育,自然而然的。
不可學,又如何證明是「性惡」?《荀子‧性惡論》:
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惡疾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11
上列一節是荀子性惡論的重要論證,他認為從自然之性而帶出性惡,是普遍性,甚至是必然性。荀子解釋若從人的本性而行,則殘賊、淫亂、爭奪、暴亂者必然出現。
荀子的論證人是「性惡」:一,人生而好利、二,生而有惡疾(此惡疾是指嫉恨厭惡)、三,是耳目之欲,都是人的自然之性。若人順著此成惡性(順是),則衍成各種惡行。所謂「順是」即順自然情性之發展而不加節制之意。人與生俱來就有各種欲望,這是人的共通性。韋政通認為:
荀子性論從性之自然義出發,若僅抽象地說其為自然,則其與天之為自然義並無不同。但性之為自然義是一個具體的人所具有的自然之性…則性即生物生理之本能,此所言性,亦即人之所以同於禽獸者。12
指出荀子的性,是自然義,即本有的一切欲望及生存的基本要求。如果順著人性自然發展,則一生一世不斷的追求能填滿欲望的回報,可是,人類的欲望似乎是沒有底線。人與人之間就永遠處於爭奪中,就是為了滿足個人欲望,而人性為惡就成了必然的結果。從歷史諸暴君可見,人類欲望的恐怖,隋煬帝的五萬後宮,宋高宗、慈禧太后,一餐超過一百款菜式,都使人覺得像是染有精神病的欲望。
荀子認為,如要導化人的惡性,則必須依靠由人創定的禮義(偽)。因為荀子深信人的惡性可以經由禮義之教化而變為善性,即「化性起偽」,是將原本的「惡性」,即性,經過禮義的教化,逐漸歸於善,即偽。這裡又產生另一個問題,即人本身是—原本具有善的元素或本質的個體,故能透過「偽」而呈現出來。這「偽」不是虛偽,而是「人為」的意思,所有善是經過教化而出現。
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性」與「偽」都是一個概念,荀子認為人的行為可以被改變(被治的性)和能改變惡的行為的禮義(能治的偽),這樣就顯示出「化性起偽」兩者的因果關係。在性上加上禮義行為,謂之偽,偽者,文理隆盛也。偽是經過教育及學習而得來的,人人皆可有成就。禮義就是「偽」,人為的。這些人為的行為,使性出現善行,這亦稱為「反性」,即違反本來的惡性,亦即是「化性起偽」。
荀子引伸禮義的出現,是經過聖王的經驗而得出來的,有禮義的內涵,「人」更要自我教育、內心修養及節制情欲。當環境適當,就可以「化性起偽」。聖人與凡人的不同,是在於「積偽」和「不積偽」。人性不會改變,但積偽則可改變行為。「積偽」就是積思慮,是心的問題,心要明白道,道為善,知善而行善成習慣,就可成為聖人。小人反是,不能積偽,順性而行。在性的本質上,聖人與小人無異,其分別在於能否積偽。這表示積偽與性並無本質上的關係。(以上理論見於〈性惡〉篇)。因上述的因果關係,故荀子提出: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13
「化性起偽」的重點就是「師法」,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這亦是荀子提出通過禮義改變人的性惡的理論。人性本惡,積禮義則是後天的,化其本性,使之合乎禮義。
有關「性」的理解,勞思光有如下的詮釋14:
(I)「性」字之用法,在「性善論」中屬於孟子之特殊語言,與古代日常語言用法不同。古代哲人當發現一新問題時,不能另造新語言以表達其意義,只能取已有之詞語予以新意義,遂形成特殊語言。特殊語言斷不能化歸日常語言以解釋,否則即將所加之新意義消去,全失立說者原意。
(II)「性」字在古代日常語言中原指生而具有之能力,但孟子欲強調人與其他動物之不同(即所謂「人之異於禽獸者」),故以「性」字指人生而具有又不為其他動物所有之能力,以此顯示人之文化之基礎可能性所在。不只指生而具有之能力。
(III)「性善」指人以求「善」之價值意識為其本有而又獨有之能力;換言之,人有理性意志或道德意志,即是人之「性」。
(IV)人之「性」須自覺求擴張,方能成道德生活及文化,非謂不作努力,自然得「善」。
勞思光的意思是孟子特別採用「性」去形容人性,與原先性字的本義解釋有不同,將之特別指人的性與禽獸有異,帶有善的性,而且可以擴而充之,對其他人,社會、國家產生善意。此善意是包括「仁、義、禮、智」,故人有理性、意志、能力去達至性善。陳大齊也有同樣的見解:
孟子所用的性字,似乎專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那一點幾希而言。耳目的知覺與嗜好,是人類與禽獸所共有,不屬於那點幾希。唯有仁義禮智,為人所獨有而不為禽獸所共有,纔屬於那點幾希。孟子既稱耳目的知 覺與嗜好為命而不稱之為性,故孟子所用的性字,若代作定義,可云:性是人所獨得於天而非禽獸所與共的。15
陳大齊與勞思光均認為孟子對「性」附以特別的意義,並不是與禽獸共有的性。孟子特別將這些口味、目色、安佚的身體感官享受稱為「命」: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16
孟子認為這些感覺雖然是與生俱來,但是否得到滿足,每個人的際遇境況都不同,故稱之為「命」,不稱為「性」。至於「性本善」與「性本惡」,孟子原文沒有「本善」一辭。性本善的「本」字可以有三種可能的涵義:
(一)「本」為本質:性本善指人性的本質(essence)是善的。人性的本質是善,即說人性中不可或缺的,使人與他物有所區分的性質是「善」。
(二)「本」為本原:性本善指人性原本是善的。人性原本是善的,即是說人天生的,未受環境學或學習改變之前,本來是善的。
(三)「本」為本體:性本善指人性之本體為善。本體指終極實在,萬物中永恆的,根本的真實存在。人性之本體為善,即是說人性具本體意義,此本體是善的。或說,人性中具本體意義的部分是善的。17
後世論及「本善」,往往是環繞上列三種涵義。那甚麼是「善」?傅佩榮給了一個解釋:
善是行為(包括言語在內),這種行為必須落在「一人與別人之間的關係」上。若一人獨處(如沉思、閱讀、聽音樂),則無善惡問題。《大學》談到「慎獨」時,指出一人獨處時仍須謹慎,有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準備隨時與人相處時可以恰當實踐「我與別人的適當關係」。18
傅氏給「善」下了一個精簡的解釋,就是「一人與別人之間的關係」。「善」就呈現在生活上與別人交際的過程中,對父母要孝、對兄弟要悌、對朋友要信等等,這些態度及行為就是善。傅氏認為行仁的要求來自人性,人性與善有直接的關連,做為人,就是應該行善;為善而有所犧牲,正是完成人性的要求。19
「本善」論應始於唐代李翱,他的《復性書》20就是要人回復本性,回復本性則成為聖人,他說「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又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睹其性焉。」李翱指出人之所以不能復性,就好像清水受到泥淖所污染,「水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久而不動,沙泥自沉。……人之性,亦猶水之性也」。久而久之,經過沉澱,必會回復水性。意思是說人性呈現惡,是受世間的惡行、惡念蒙蔽了本性,如泥染污水;當惡念惡行漸漸消失,則「性」自呈現,而此「性」必然是善的。故李翱的主張是「性」其本質是「善」。聖人與凡人都同屬善,差別是在於有沒有將惡性逐漸消除。至朱熹以後,「性本善」幾乎成為普遍認受的儒家觀點。
如果人是性善,又為何作惡?宋代朱熹先將性分為「天地之性」及「氣質之性」。所謂「天地之性」就是與天道合一,屬至善;而「氣質之性」是由情欲而來,故理學家尋求變化氣質。「天地之性」是普遍性,人人共有;而「氣質之性」則因人而異。
至〔明〕王陽明,否定心外有理,主張心就是性,就是理,就是天。他在《傳習錄》說「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21、「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22「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也。」23「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24、「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25
他提出「心即性,性即理」,認為人自是善,自有良知,自知善惡,天命之性是至善,所以提出「心即理」、「致良知」,而在實踐方面則是「知行合一」。
他對弟子解釋有人不孝,有不悌的出現與「知行合一」的關係:
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飢,必已自飢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什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26
又解釋:
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閑說話。27
知而行,才是真知,二者並立。王陽明又認為世間一切,無非是主觀意識的作用,故認為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即表示是非自我分明,不行善則未知,真知必行善。至陽明晚年,留下四句教給後人:「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至於「惡」的涵義,大體各家沒有太大異議,荀子指出的「好利」、「疾惡」、「耳目之欲」而產生種種惡的行為:爭奪、殘賊、淫亂、暴亂等。為何產生惡?傅佩榮歸納了五點原因:(一)經濟差;(二)教育偏;(三)形勢強;(四)人心放;(五)邪說出。28首三項是社會經濟狀況而影響,末兩項屬思想層面。
我們可以用孟子的四端來考量何謂「惡」!仁、義、禮、智四端呈現出四種心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如是,則沒有惻隱心、羞惡心、辭讓心、是非心,就是惡。相對於荀子的惡,是爭奪、殘賊、淫亂、暴亂等的行為,似乎無法對比。一方是心靈上道德行為,是形而上的概念,是超越性;一方是能見的行惡行為,屬現實行為。這裡又產生另一問題,如何衡量惻隱心和其他三心?是不是有「怵惕」的心,就是仁者的心?
朱熹將之分為「天性」與「氣質」,是指惡行可以改善,氣質也可變化。如是,朱熹的理論似乎較接近荀子,荀子說:
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29
枸木需要烝矯才能成直,鈍金需要礱厲才能成利,即是經過時間的歷練而變化。正如朱氏所說變化氣質,當然,其中又涉及為何能變化的問題,這裡不在討論之列。因此,王陽明認為心是善,是不假外求。故有謂王陽明是直承孟子心學,亦是合理。
筆者另一困擾的問題是孟子從沒說過「人欲」是惡,故面對齊宣王的好勇、好貨、好色,孟子隱約表達只要合理、不過份、不傷害其他人就可接受,《孟子‧梁惠王下》: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30
宣王好貨,百姓好貨,如各得其所,能與百姓共同富足,好貨不是缺點。又說: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31
孟子指出太王也好色,如此舉例,是說好色是自然的事,只要推己及人,達至「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所說是指人人皆可好色,如果人人能有正常的婚姻生活,則好色也不是缺點。這樣的解說,即人類欲望不是「性惡」,而後世儒者的「去人欲,存天理」就產生問題了。宋明理學家,多以「好色、好名、好利」為惡,欲望越少,則天理越明。理學家所說的是在修行方面發展,無疑欲望少,引誘自然少,行為越能正確。但筆者認為這不是孟子對惡詮釋的本意,孟子是接受合理的欲望,而且不是惡。王陽明宗此論見,說「心即理」,可惜王學末流,出現縱欲無行的士人,束書不觀,而日言心性。〔明〕李贄亦贊同合理的欲,對人是正面的。
我們可以概括「善」與「惡」的涵義,善是與生俱來對萬物人事所產生的憐憫愛護之心,當中包含惻隱,對弱者或受傷害者,或受痛苦者的同情感;羞惡,對作出自己的錯誤,對別人產生的傷害,感到羞恥與厭惡,是內心對負面行為的自我反省;辭讓,對不應得的東西不取,別人需要的就辭讓,對其他人必然有恭敬心;是非,人事行為與世事變化,是正確或不正確,均有判斷力。仁、義、禮、智呈現在這四種能力心態上,是與生俱,是「善」的表現,呈現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
荀子的「惡」,無疑是經過觀察而得出的結果。順著人類的欲望而行,必然產生爭奪、淫亂等事。告子說「食、色,性也」,是將人類的生理基本要求說成是人性。這些生理需求,與禽獸無異,所謂「人性」,當應是人類獨有的天性。故人之所以異於禽獸,是因為有仁、義、禮、智。單說「食、色,性也」,未免將「人」看得太低。
孟子與告子的爭辯,可謂精彩。告子先以水喻性: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32
告子認為人性如水,決於東則東,決於西則西,因環境而變,故性無所謂善與不善。孟子辯之以水無分於東西,但卻分於上下,水永遠向下,表示人性永遠是善。告子又以「白」喻性: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33
這次以白喻性,給孟子追問得告子不知如何回答。如果告子所說成立,則犬性、牛性、人性是相同。當然,後世有為告子作辯的,如〔清〕翟灝《四書考異》引司馬公說「告子當應之曰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34
告子又概括「食、色,性也」,而引伸至仁內外義的命題上。孟子與告子爭論人類是善是惡的命題上,極力維持人類的尊嚴,與禽獸有別,亦不應將人類與禽獸共有的生理需求視為惡。退一步解釋,就是不過份、不傷害別人,或能人人共有,這些欲望並不是「惡」。
我們可以在《荀子》、《韓非子》各篇章中找到不少的事例、比喻、歷史故事等證明人是性惡。我們也可從中國歷史上權力鬥爭中的慘無人道的殘殺屠盡中,亦可看到掌權者為一己之淫慾享受,造出滅絕人性,貪殘無道的非人類行為。真如荀子所說,順是,則人漸變為禽獸。
驗證於現實,似乎性惡有其普遍性。姑勿論荀子如何證明人是性惡,但荀子無法解釋第一位訂立道德標準的聖人,其理據從何而來?何者是性惡行為?譬如爭奪是惡,但據理力爭,或為應得的利益而爭,是不是惡?如何才是傷害仁義?如何才是淫亂?都難有一定的標準,畢竟判斷善惡是有主觀的意向在內,如歷代帝王,少則數十妃嬪,多則以千計、萬計!這不是淫亂是甚麼?可是,歷代名臣,理學家,少有以此責難帝王。
雖然荀子指出是聖王憑經驗與思考定立禮義,但問題是「聖人的道德標準是如何的出現?」能定這道德標準的人,必然是有道德心,這個道德心是否與生俱來?即為甚麼孝是道德行為?為甚麼信是道德行為?為甚麼禮是道德行為?即判斷這些行為的聖王,他們早已有一標準在心,而以此標準是普遍的真理。亦即是大家心底裡都會認同某些行為是道德行為,即是此類性善行為普遍存在人的思想裡。荀子始終說服不了道德的行為標準是如何訂立。如果說聖人經過觀察就知哪些是惡?哪些是善?即聖人心中早有一衡量的標準,譬如獅子捕殺獵物,必先一番戲弄,滿足其心的殺念才殺死獵物。獅子會反醒這行為嗎?而人,卻會反省自己的行為,是否過份,不合人性?故唐君毅先生認為荀子是「對心言性」,荀子之言「性惡」是與人之「偽」或慮積能習,勉於禮義相對照比較而說,而「心」是一能向道之心。(《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如此解說,即心是有向善的傾向,經過「積偽」逐漸成為善。
徐復觀先生則認為荀子所持乃一經驗主義的人性論,並指出荀子的「性」的內容有三:即一、官能的欲望、二、官能的能力,以及三、性的可塑性。(《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進一步解釋:一、「性」受官能刺激而有反應,對外緣會尋求更高的官能享受;二、官能有增強及完善道德的能力;三、性可以透過教育、學習而改善。
人類最大的身體欲望,是食與色。孔子也不否認,他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食慾與情慾是人類是大的欲望,亦是人類得以在地球延續下去的兩大因素。「食慾」是指進食的機制是由人空腹時開始的,空的胃壁互相摩擦,產生一種稱為「飢餓痛」(hunger pangs)的感覺。人類因為飢餓而引起食慾,但從心理學解釋,人類可以因為食物的色、香、味、口感而引起食慾,不一定是飢餓,不因飢餓而食,則不是自然反應,是欲望。因此筆者又產生另一個問題:「追求享受是不是惡?」孔子的「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又是否「惡」?另外,「食」是可減除部份身體壓力,更可使身體有愉快感。
至於「性慾」的同義詞有性衝動、性吸引、情慾。學者對性慾的解釋:
性慾是一種主觀感受,其可指向內外部線索。人們可能會,但不一定會因性慾而從事性行為。想像和幻想能使人產生性慾。具性吸引力者同樣亦能使其他人產生之。性慾也可以因性緊張而起或加深。當性慾未能夠得到滿足時,就會產生性緊張。35
人類又為何容易溺陷於色慾?人類為繁衍後代,會自然地產生交配行為,即性交。上天為此,又給與人類繁衍後代的回報,就是身體官能的高度刺激。交配過程中會產生高潮:
出現的一種逐漸升高的興奮、緊張狀態,當這種狀態積累到頂點時會出現爆發,這種爆發伴隨著極度愉悅的感受。男性和女性都能產生性高潮。性高潮由神經系統和內分泌系統共同作用產生,在神經系統中與骨盆神經、下腹神經、會陰神經和迷走神經有關,在內分泌系統中則與雄激素、雌激素和孕激素等有關。36
「食」能有愉快感,而「性」會產生高潮,使身體高度興奮。人類就容易「陷溺」其中,以至放肆情欲、愛欲而達於亂,暴亂、淫亂以至於違反常理人情。這些情況屢見於歷史及現代人事中,不可謂不恐怖。宋明諸賢就以限制欲望,導入正常生活中,儒者需檢視自我行為。諸儒認為,人欲越少,天理越明。可是,用另一角度來看,如果食欲與性欲是維持人類生存最基本的因素,以此判斷,又怎會是惡?故筆者認為透過不正常的行為去滿足自己的欲望,才是惡。孔孟所反對的不是正常的欲望,而是由邪念所產生的縱欲。
荀子認為,「情者,性之質也」,是「性」之本質,而「欲者,情之應也」,有欲就自然有情,如是「性」、「情」、「欲」互相關連,故荀子是「以欲說性」在欲望的層面解釋「性」,自然是「性惡」。然而,荀子卻贊成人是具有認識能力的心,能夠判斷善,透過判斷,使「惡」改進為「善」。「虛、壹、靜」就是心的作用,以此明「道」,臻「善」。所謂「虛」,不要以過往所學,妨礙新的知識與認知,「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壹」是思想專一,別無他念,「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靜」是思想寧靜,不受干擾「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這樣,「心」就能知「道」。以此而達至「大清明」境界,明瞭宇宙真理。
「虛、壹、靜」是修持方法,荀子在這理論當中,顯示出矛盾。這是透過修持而明白「道」,但能判斷「善」的能力或認識心是從何而來?能判斷善的心當然是善,那「性本惡」就不成立。荀子又認為人有辨知心,「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正名)由於辨知的能力,可以退卻邪說。那又出現另一問題,既然這心有辨知及退卻邪說的能力,這個不是「是非心」,是甚麼?
勞思光認為傳統的中國士人偏重人性本善的理論,少了制衡式的約制,著重個人的自我反醒。在整個中國政治及社會上忽略了有形的監察系統,較重視社會上的道德約制,如明清時期的儒商,大都是自我的約制。勞氏對中國社會的道德發展作了客觀的描述,就如商業交易常說「說了算」,沒有文件或法制上的規則限制,例如早期香港的南北乾貨米糧交易,大多是口頭承諾,從電台的紀實片看見老一輩的行內人,仍然緬懷這種互信行為。樂觀的去看,是見到人性善的一面,悲觀的去看,隨時被騙。就算人的性善成立,但惡的行為仍然容易產生,畢竟是與生俱來的動物性。
至於性善,中外不少學者都是傾向相信人是性善的,如阿當‧史密斯 (Adam Smith)在其《道德情操論》指出人類的「同情感」是人類的根本傾向。他認為:
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這種本性就是憐憫或同情,就是當我們看到或逼真地想像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時所產生的感情。我們常為他人的悲哀而感傷,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不需要用什麼實例來證明。這種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樣,決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備,雖然他們在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銳。最大的惡棍,極其嚴重地違犯社會法律的人,也不會全然喪失同情心。37
進一步闡釋正義、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產生的根源,是源於出自天性的「同情」。除同情外,同書論及其他的重點包括「公正的旁觀者」、「良心」及「美德」。整本論著,就是指出人有道德的自覺性,與儒家思很吻合。
法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愛彌兒》提出的教育理念,其前提是人性是善。他提出的自然人,即不受社會任何感染,具有自然天生的本性自然人。盧梭指出「遵從良心者即是遵從自然」,是自然教育思想,由於自然人未受污染,因此其行為必然是善,明顯主張性善論。盧梳認為一個有道德的人,同時是可以自愛,即尋求更美好的生活。若超越界線,就會變成自私,要避免對別人的痛苦和不幸而無動於衷。
我們看著小朋友長大,除了荀子所說的「飢而欲飽,寒而欲暖」的自然生理反應外,都看見他們是天真無邪,傾向善性。近代很多心理學家、哲學家,研究人性都相信「人」須先滿足基本生理需要,才能提升道德領域,如馬思勞的〈需求層次理論〉,最底層就是飲食、性欲。筆者絕對相信每個個體均有「善」的元素,而飲食、性欲從自然需要方面去理解,不能算是惡。享受覺受,只要合乎自然,以「善」培養自己的道德,「人」終必達至道德完滿的境界,即孔子所說「從心所欲」。
牟宗三先生說「道德的善就在性之中,或者說性就是道德的善本身」38就超越面而言,性就是善,善就是性,就是創生不已的天道實體。仁者必善,而且仁有創生義,仁體為一種精神實體,能「覺潤創生萬物」。「仁是理、是道、也是心」39
也就是說,主體及此心之性,與客觀的天道、理體,是同一件事,可謂之本心性體。這個心或性,是超越的,要從心靈體現此實在的天道,不能單從經驗得到。牟先生說:
唯吾人平常只知經驗的,心理學的心念之起伏生滅為心,而不承認有一超 越的心體……凡決定人生之方向而理想地發展其人格者,皆需有此類超越真心之肯定,而且是本有,是真實,是呈現。40
他的的結論「性」就是「善」。這在同一文中討論佛教的「性宗」及儒道佛互相影響的關係時,牟先生說「象山陽明固是孟子靈魂的再現,即竺道生慧能亦是孟子靈魂之再現于佛家」41即超越性的性,無論是任何宗派,其必為善。
傅佩榮於一九八五年提出「人性向善論」,他以血氣層次的飢餓開始,解釋人類與動物無異的本能,漸次提升至選擇、思考、真誠、利他、以行「仁道」。述明人類有向善的傾向性,他解釋「向」字幾個意義42:
(一)「向」字肯定了人性是動力論的而不是本質論的。
(二)「向」字顯示於人心之不安。
(三)「向」字連繫了一個人的內與外,知與行,自我與別人,自我與天命。
他指出人性向善的焦點在於人心,因此亦可說「人心向善」,心是動態的,有自覺能力而未必一定會自覺。如果人只活在血氣層面,即飲食、性欲等,就永遠沒法獲得自由。上天付與人類的就是選擇能力、向善的能力。孟子的四端是對心之「存、養、充、擴」,即是具體實踐了「仁、義、禮、智」,這四者才是我們一般人所理解的「善」。孔子亦高度自覺要求自己的心要處於「安仁」的境界43求道而忘身。傅氏這理論,調和了性善、性惡的爭論。他不否定血氣層次的欲望,但作為人,必然有提升自我道德之能力及心態。
最後,筆者對性善惡有如下的看法:荀子對性惡的立論始終有矛盾及不足之處,他是一代大儒,已有周詳的分析,其缺憾就是沒法解釋這個「客觀的善」從何而來,而不是早存在人性之內?若果說人「能善」,即有行善的能力,那善就是本有的,而且善是超越性的體驗,是個人的自我感悟。傅佩榮的向善論,將孟子的「擴而充之」解釋為向善力,其立論應承認人的原始本性是善。當然,無論是贊成性善或性惡,大都認為人類是有向善的能力。
1、謝冰瑩等:《新譯四書讀本‧論語》,台北:三民書局,民90年,頁274。
2、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商務印書館,年缺,頁64-65。
3、熊公哲:《荀子今註今譯》,台北: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540-541。
4、〔東漢〕王充:《論衡‧本性》,網址:〈論衡 -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ctext.org)〉,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5日。
5、謝冰瑩等:《新譯四書讀本‧中庸》,台北:三民書局,民90年,頁26。
6、謝冰瑩等:《新譯四書讀本‧孟子》〈公孫丑上〉,台北:三民書局,民90年,頁381。
7、同上註。
8、同上註,頁326。
9、熊公哲:《荀子今註今譯》〈正名篇〉,頁510。
10、熊公哲:《荀子今註今譯》〈性惡篇〉,頁543。
11、同上註,頁541。
12、韋政通:〈荀子「天生人成」—原則之構造〉,收在項維新、劉福增主編:《中國哲學思想論集‧先秦篇》,台北:牧童出版社,民66年(1977),頁196。
13、熊公哲:《荀子今註今譯》〈性惡篇〉,頁541。
14、勞思光先生存稿整編‧性善論》,取自網址:〈http://phil.arts.cuhk.edu.hk/project/LSK_mss/?p=1550〉,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9日。
15、陳大齊:〈孟子與告子的辯難〉,收在項維新、劉福增主編:《中國哲學思想論集‧先秦篇》,台北:牧童出版社,民66年(1977),頁120。
16、謝冰瑩等:《新譯四書讀本‧孟子》〈盡心下〉,頁643。
17、「本」字的三種涵意,見網頁〈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性本善論 〉,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1日。
18、傅佩榮等:《人性向善論發微》,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民101(2022)年,頁92。
19、同上註,頁93。
20、〔唐〕李翱《復性書》,下引內文均取自網頁百度網:〈https://baike.baidu.hk/item/復性書〉,瀏覽日期:2022年10月11日。
21、〔明〕王陽明著、李生龍注譯:《新譯傳習錄‧答顧東撟書》,台北:三民書局,2021年,頁204。
22、同上註,頁200。
23、同上註,頁203。
24、〔明〕王陽明著、李生龍注譯:《新譯傳習錄上‧徐愛錄》,頁27。
25、同上註,頁8-9。
26、同上註,頁15-16。
27、同上註,頁16-17。
28、傅佩榮等:《人性向善論發微》,頁109。
29、熊公哲:《荀子今註今譯》〈性惡篇〉,頁541。
30、謝冰瑩等:《新譯四書讀本‧孟子》〈梁惠王下〉,頁345。
31、同上註,頁345-346。
32、謝冰瑩等:《新譯四書讀本‧孟子》〈告子上〉,頁556。
33、同上註,頁557。
34、同上註,頁558,註釋3。
35、引文概念來自右列三書:Spector, I. P.; Carey, M. P.; Steinberg, L. The sexual desire inventory: Development, factor structure, and evidence of reliability. Journal of Sex & Marital Therapy. 1996, 22 (3): 175–90. ; Beck, J.G.; Bozman, A.W.; Qualtrough, T. The Experience of Sexual Desire: 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in a College Sample.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991, 28 (3): 443–456.; Toates, F. An Integra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Sexual Motivation, Arousal,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009, 46 (2–3): 168–193.取自網頁:〈https://zh.wikipedia.org/wiki/性欲〉,瀏覽日期:2022年10月20日。
36、取自百度網址:〈 https://baike.baidu.com/item/性高潮〉,瀏覽日期:2022年10月20日。
37、亞當‧史密斯:《道德情操論》,取自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zh-tw/性善論〉
38、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第九講 對於性之規定 〉,收在《牟宗三全隻》第28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
39、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第四講 儒家系統之性格〉,頁79。收在《牟宗三全隻》第29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
40、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一)》,台北:正中書局,民78年(1989),頁586〈附錄〉:〈佛家體用義之衡定〉。
41、同上註,頁579。
42、傅佩榮等:《人性向善論發微》,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民101(2022)年,頁69。
43、傅佩榮等:《人性向善論發微》,頁75。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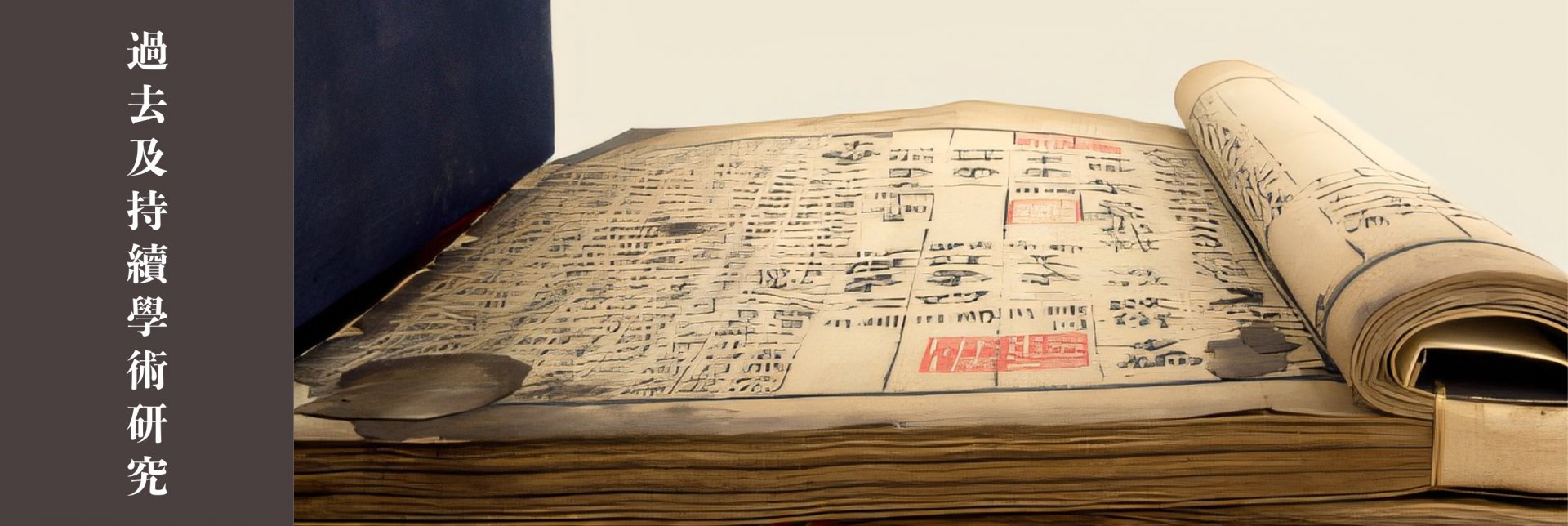



歡迎留言:
請登入/登記成為會員後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