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賦中所揭示的女性形象和地位
周詠琳
2024年4月18日
提要
賦是中國文學上具有代表性的文體之一,它講求文采、韵律,兼具詩歌和散文的性質。賦原為一種文學的表現方法,是《詩經·大序》中“六義”之一,即直指其事。在漢代,賦文體興起,結合了先秦文學的敍事方法和詩體的音韻規律。而六朝繼承了漢賦用韻的方式,多變為駢賦。六朝賦的題材不再像漢賦限於宮廷生活。而六朝賦家在婚戀題材中,描述了各種女子,包括宮廷和平民女性,豐富了中國古代女性的形象,使我們從中了解到她們的生活面貌。因此,本文將會從四個部分對六朝婚戀賦的女性進行研究:第一章為六朝賦中女性的分類,對各種女性進行分類,探究她們在婚戀中的身份和形象。第二章為六朝賦中女性的形象特徵,研究六朝封建社會下,對女性外在美和內在美的規範而塑造的女性形象特徵。第三章為六朝賦中女性的地位,研究女性在社會上,尤其在宮庭和家庭中,在封建制度和男性的凝視下,如何造成她們擁有低下的地位。第四章為結論,梳理前三章對六朝婚戀賦中女性的角色,她們所共同擁有的形象特徵,及當中所反映她們的性別地位低下,最後得出六朝賦豐富了中國古代女性的生活狀況和精神面貌的結論,對後代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啟迪作用。
在研究六朝賦中的女性形象之前,必須說明本文的時間界限問題。本論文於六朝(222-589)文學的劃分包括三國吳、東晉、南北朝的宋、齊、梁、陳。以賦而論,產生於戰國末年,到兩漢以後400餘年間,成為佔據文壇統治地位的主要文學樣式,產生了數以千計的作品1,但漢代不是賦作的最高峰時期。其後的六朝駢體抒情小賦,皆具有思想和藝術價值。在建安之後,社會的動亂和文人思想的解放,使抒情賦於魏晉南北朝興起,打破了漢賦描寫於宮廷的生活範圍,擴大賦體的題材和內容,如悼亡、懷人、思婦等。在各種題材中,婚戀賦對女性描寫豐富了中國古代女性形象和有著極大的發展。此外,亦反映了六朝女性的社會生活狀況和精神面貌,重塑了當時女性的生命價值。
一、 文獻回顧與研究價值
前代研究者對六朝賦作中女性形象關注不多,只有寥寥數篇論文,如劉田田〈魏晉婚戀賦研究〉2,研究魏晉婚戀賦的文體變化和美學體現、田子君〈漢魏六朝賦中的女性形象〉3,探究六朝賦中女子的階層分類和形象特徵。而六朝賦的研究更多關注意象、詞藻章法等,如張正體、張婷婷《賦學》4,歸納了六朝賦藝術特色。林佳燕〈漢魏六朝賦中的鸚鵡意象〉5和侯立兵〈漢魏六朝賦中的蟬意象〉6,則研究六朝賦中動物的意象。
然而,在過去的研究中,尚未有關於六朝女性題材的賦學專著,而大多的專著只以少幅的篇章研究婚戀賦,如于浴賢《六朝賦述論》7和池萬興《六朝抒情小賦概論》8,當中只有少數章節分析六朝婚戀賦。另外,學者多以六朝賦中女性的感情狀況或情態流露作研究,如靳青萬〈漢魏六朝女性賦述論〉9和陳元瑞〈漢魏六朝女性詩歌的題材分析〉10、〈漢魏六朝女性詩歌的情感基調〉11等。
因此,是次研究將梳理及整合前人對六朝賦中已進行的女性研究,及補充當中的不足之處。
二、 研究動機
本文旨在通過六朝賦中女性的婚戀經歷,探討她們的地位,及當中反映的時代生活和精神面貌,重塑中國古代女性的生命價值。這對於我們現今社會而言,也極具價值和意義,能加深瞭解當時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及社會地位,以文學觀照社會生活。例如在六朝婚姻賦方面,曹植和曹丕的《出婦賦》描寫了王宋因無子而被休棄一事,揭露封建制度下男尊女卑的現象。又如曹丕和潘岳的《寡婦賦》,皆以寡婦的視角訴說孤寂、悲苦之情,以男性身份寫第一身視角的寡婦思夫,對封建社會中女性只能依靠男性的狀況,更顯諷刺。另外,在六朝戀情賦方面,王粲、陳琳、楊修等多位作家皆有創作同名《神女賦》,仔細描寫“神女”的容貌、姿態,透過男性對女性的凝視,可見女性在男性審美中的形象特徵。通過是次研究六朝賦中的女性形象,並進行分類,將更全面呈現出中國不同地位的婦女形象。
三、研究方法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六朝賦的女性形象研究中,過去對六朝賦的文本分析已取得一定的成果。因此,本文旨在拓展六朝婚戀賦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以六朝婚戀賦為文本,對當中所描寫的女性進行分類和形象分析,藉此研究女性的地位,窺探六朝時期社會普遍流行的女性觀。附錄中的原文皆採用馬積高的《歷代辭賦總匯》。
具體研究方法:
第一,文本細讀法,對六朝婚戀賦的文學體裁中,所出現的女性進行細緻的分析和形象特徵。
第二,比較分析法,通過對比六朝時期賦體男性作家所創作相同賦題,研究當中對於女性形象的不同描繪,分析六朝時期的女性觀。
第三,歸納法,研究對六朝婚戀賦中的女性形象,歸納賦中女性的特點,從而得出結論。
第四,文史結合法,通過對歷史背景與文學相互依據和印證,研究六朝社會的女性觀
六朝賦的發展是前代文學的集大成,其中的女性形象既延續了先秦文學的傳統,又有了新的變化,形成了豐富的女性人物形象。本章主要回顧六朝時期女性形象的繼承,以及就賦中女性的特徵,對其進行分類研究。
第一節 神女
神女與佳人的戀情描寫出現較早,繼《詩經》、楚辭的《九歌》和《九章》後,宋玉的《高唐賦》和《神女賦》繼承了《楚辭》的戀情描寫,開啟六朝一系列的神女才子相戀賦的發展。神女形象是作家心中的理想,她們皆美貌如花、才智過人、精通音律,並於夢中與作家相戀。在建安時期,不少作家都曾在賦中描寫過她們心中的女神形象,如應瑒、楊修、王粲、陳琳、張敏等,皆創作同名賦篇《神女賦》。在賦中,他們不只是描繪女子的容貌特徵,亦有突出神女們的智慧和才藝。
在王粲的《神女賦》中,更仔細地描繪出神女的美貌:
“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 發似玄鑒,鬢類削成。質素純皓,粉黛不加。朱顏熙曜,曄若春華。口譬含丹,目若瀾波。美姿巧笑,靨輔奇葩。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曄。襲羅綺之黼衣,曳縟繡之華裳。體纖約而才足,膚柔曼以豐盈。”12
王粲描寫出神女從頭髮到妝容,再到穿戴,以至整個神情。而在賦的開首即道出天地陰陽孕育麗人,帶出神女的由來,以及突出其不染世俗的的特徵。神女的豔麗是“超希世而無群”,可見其情極為罕見。而她不僅對作者“探懷授心,發露幽情”,更“稅衣裳兮免簪笄”。神女不能自持而主動和他示好,但作者卻極為冷靜而“回意而自絕”13。王粲不顧神女的絕色美貌,以禮教打敗情愛,可見《神女賦》的描寫,不只是停留於神女的外貌描寫,同時亦反映出作者的思想。
張敏《神女賦》則在賦的結構上與建安時期其他的《神女賦》有所不同。他在賦中加入了問答的手法,使賦裏所使用的描述角度有所不同。當中的神女容貌、體態、才華等描述,不再只限於男性角度,而是加入神女的自我陳述。張敏在《神女賦》的序中云:
“世之言神女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至如弦氏之婦,則近信而有證者, 夫鬼魅之下人也,無不羸疾損瘦。今義起平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處,縱情極意,豈不異哉!餘覽其歌詩,辭旨清偉,故為之作賦。”14
此賦為張敏對弦超和神女智瓊之間的故事而作。在當時的社會中,世人相信人若和鬼魅相處,會使身體和精神羸弱虧損,但弦超與神女同食同眠,又恣意縱情卻安然無恙,打破了世俗的傳言。然而,在弦超與神女相會之前,亦曾受到言論影響,對其身份有所懷疑。因此,在確認神女貞潔賢淑後,才與她“極長夜之歡情”15。而且,賦中運用到主客問答,使神女貞淑有禮的形象以自述的方法呈現,使人物更為豐富。
在眾多描寫神女的賦中,曹植的《洛神賦》具有代表性,其對神女進行更詳細的描繪。全賦共用了六段來鋪陳作者與神女的戀情:第一段交代作者從洛陽回封地時,看到美人宓妃佇立於山崖,受宋玉《神女賦》感發而創作此賦。第二段詳細地描繪洛神形象、德行等。第三段表達自己對神女的愛慕之情。當中,曹植把“翩若驚鴻,婉若遊龍”16的女神形象描畫得栩栩如生,其描寫超越了同時期其他的神女賦。在賦中,曹植運用大量篇幅來形容神女,例如“肩若削成”、“腰如約素”等描述神女的容貌;“戴金翠之首飾”、“踐遠遊之文履”等描述神女的衣著打扮;“體迅飛鳧”、“淩波微步”形容神女動作;“轉眄流精”、“氣若幽蘭”等描繪神女神態17。同時又對女神形象進行了心理描寫,使傾國傾城的神女更活靈活現。
在描寫神女的賦中,作者皆運用藝術想像和聯想的方法,給讀者創造了與神女相戀的夢境。而且,對神女進行各式的外貌、才華描繪,則繪畫出一個完美超凡的女神人物,加強了現實對神女可望而不可及的朦朧美。因此,眾多的神女賦家多會在夢中大膽與神女相戀、更有被神女露骨追求。
第二節 棄婦
在先秦時期,《詩經》記載著許多女性被丈夫背叛、甚至拋棄的命運,而六朝賦亦繼承了女性在婚姻遭到不幸的題材。在建安末年,軍閥劉勳喜歡了司馬氏家的女子,隨後以無子為理由休棄了髮妻王宋。此事引起部分文人的關注,例如曹植、曹丕、王粲皆創作同名賦作—《出婦賦》,為王宋抱不平,憤嘆其所受到的不公待遇。
曹植《出婦賦》中揭露了“負心漢”的喜新厭舊、忘恩負義的本質。“悅新婚而忘妾,哀愛惠之中零…痛一旦而見棄,心忉怛以悲驚”18,劉勳在喜歡上司馬家女子後,忘記了髮妻,貪新厭舊,使妻子王宋因其無情、忘恩負義,休棄自己而悲感萬分。在賦中首四句,曹植為王宋代言,認為自己才識淺薄,配不上丈夫的清高。因此她“承顏色而接意,恐疏賤而不親”,謹慎侍奉丈夫、恐怕有過失而被疏遠。然而,丈夫卻“悅新婚而忘妾”,貪新忘舊。在被休棄後,穿著當初嫁入劉家的嫁衣。而丈夫不送行,只有侍從攙扶上車、為其痛哭流淚。她“恨無愆而見棄”,但卻又無可奈何19。儘管此賦是曹植代言以述,但把女性被逐出夫家時的淒涼情景描繪得真摯動人。這不但深刻揭解了封建制度下,男女不平等的罪惡現象,表達了作者對遭受迫害的婦女的深切同情。
曹丕《出婦賦》比曹植《出婦賦》更為感人肺腑,對王宋被休棄後的情景寫得淒婉動人。曹丕為王宋代言,“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悲谷風之不答,怨昔人之忽故”20,把被休的過錯、原因歸咎與自己,認為妻子年老色衰而被疏離、無子而被休棄乃人之常情,自己只是無奈悲傷無法與丈夫長相廝守。但她最為怨恨的是丈夫的突然變心。其後,作者描畫出各種動物為王宋被逐出家門而哀愁的場面。當中,陳振鵬、章培恆等學者指出飛鳥“哀鳴而相慕”與劉勳的“不答”形成鮮明的對比,突出劉勳的無情21。此外,池萬興認為此賦反映了婦女的初步覺醒,“在那視婦女如玩物的封建上層社會,這種人道主義的同情,充斥著民主思想的光輝”22。但筆者認為這單純只是同時期作家為婦女在不幸婚姻中無奈的哀嘆而己。而且,當時社會現象為女性在婚姻中,多處於被動的狀態,因此筆者認為這一小撮被代言的棄婦,也只是因為聲名大噪的丈夫,才被小部分的作家所關注。故此,是否所有婦女擁有覺醒意識是存疑的。
王粲《出婦賦》的“君不篤兮終始,樂枯荑兮一時。心搖蕩兮變易,忘舊姻兮棄之”23,反映了丈夫喜新厭舊、妻子色衰被棄的事實。相較於前兩首賦作,王粲在賦的前部分主要集中敍述王宋年輕貌美時與丈夫關係和諧,對比年老色衰時與丈夫關係的疏遠。當中亦有讚美了女子恭敬侍奉家人的良好品德,如“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饋兮恪勤”24,自己敬慎勤勉地處理好家中大小事務。與曹丕不同的是,王粲的《出婦賦》和曹植的《出婦賦》一樣,對於妻子被棄的原因,沒有歸咎於社會法度,而是因為男子的始亂終棄。
由兩漢到曹魏時期,女子的地位降低,被棄的原因更為複雜,當中包括因無子被休棄的妻子,又或因嫉妒猜忌而被拋棄的女子。另外,時代的不同亦造就棄婦不同的性格。在兩漢時期,部分女子面對丈夫的拋棄,存在一定的反抗意識,例如漢樂府詩《白頭吟》、《孔雀東南飛》等,皆在得知丈夫變心時,作出實際行動—自請離家,以維護自己的尊嚴。而到六朝時期,大部分女性就如上述的王宋一樣,更多的是無奈地接受,獨立性相對減弱。
第三節 寡婦
在建安時期,東漢末年的朝廷腐敗,“所任誠不良”25使“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26的悽涼慘況。群起戰亂,大量青壯年被迫從戎,保家衛國。混亂殘酷的戰爭使這些男性隨時面臨喪失性命的風險,而他們的伴侶亦要承受失去丈夫的痛苦。因此六朝時期,寡婦的數目上升。故此,寡婦的女性形象是在較特殊的狀況(如戰亂)中所產生的類型。有關描寫寡婦一類女性人物的作品,主要有曹丕的《寡婦詩》和《寡婦賦》、王粲的《寡婦賦》、潘岳的《寡婦賦》等同名賦章。前兩者皆為阮瑀妻子代言,對阮瑀英年早逝、留下遺孤寡妻之事而感到悲憫。潘岳則為小姨子楊氏代言,對其喪夫感到憐憫。
曹丕為阮瑀妻子喪夫一事創作了《寡婦詩》和《寡婦賦》。根據《三國志·魏書·阮瑀傳》道:“瑀以十七年卒。”27而曹丕等人與阮瑀交情甚好,憐惜其孤子寡妻,便創作了《寡婦詩》,當中描繪了一個“守長夜兮思君”、“悵延佇兮仰視” 28、思念丈夫的寡婦形象。《寡婦賦》為阮瑀妻子代言,整篇以寡婦的口吻,敍述她孤單寂寞的悽苦之情:
惟生民兮艱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處兮歡樂,我獨怨兮無依。撫遺孤兮太息,俯哀傷兮告誰?三辰周兮遞照,寒暑運兮代臻。歷夏日兮苦長,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隕兮集庭,燕雀飛兮我前。去秋兮既冬,改節兮時寒。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29
所有人都歡樂融融,而自己卻孤寂無依,只能撫著孩子,獨自哀嘆。在夏季長長的白晝,或是秋季漫漫的黑夜,尤其感到寂寞難耐。儘管“去秋兮既冬”30,依舊心傷不堪,十分想念已逝的丈夫。作者藉此賦抒發自己對朋友早逝的惋惜,亦塑造出一個孤獨、癡情的寡婦形象。
王粲《寡婦賦》與曹丕《寡婦賦》稍有不同。王粲在賦的開首寫了一個失去丈夫的妻子舉步維艱的生活狀態,“闔門兮卻掃,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31在封建社會制度下的女性尤為艱難。寡婦在失去丈夫後,足不出戶、閉門謝客,閉關在像牢籠似的庭院裏,照顧遺孤是她唯一能做的事。而身邊只有僕人和孩子的陪伴,唯有獨自懷念丈夫。隨後,王粲與曹丕皆運用襯托手法,曹丕以燕雀成雙、王粲以別人遊樂,來襯托出自己一人孤苦伶仃。此外,王粲描寫阮瑀妻子在幽室無所事事,而使其出現各種愁緒,更突顯出寡婦孤零寂寞的形象。
自建安之後,潘岳的《寡婦賦》為寡婦代言的代表作之一。潘岳在賦序中提到:
“樂安任子鹹……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餘遂擬之,以敍其孤寡之心焉。”32
他認為其妹夫早逝,妻妹守寡、獨自養育遺孤,為她的艱辛應到同情。因此,他仿效王粲等人的《寡婦賦》,為其妻妹作賦。然而,其賦與以上所述的寡婦賦稍有不同。此賦更為詳細地描寫妻子在守靈的場景,和刻畫出寡婦的心理。在賦的開首,寡婦自述她的身世及努力自修,但丈夫卻“適命奇薄”、“忽以捐背”33。她“口鳴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沾衣”34,可見其少婦新寡守靈悲傷極至的情緒。“時暖暖而向昏兮”35、 “雀群飛而赴楹兮”36等景物進一步突出她的悲痛欲絕。在亡夫的靈柩前,她彷彿聽到丈夫的聲音、看到丈夫的笑容。這種想像幻化,更使她悲泣不己。賦的後段亦詳盡地表達出寡婦的複雜情緒,如長夜的哀傷、許願於神靈的期盼、“甘捐生而自引”的癡情、“顧稚子兮未識”的母愛等37。清代何焯評:“此代寡婦以言情,備極哀愴”38。
以上的賦作皆為寡婦代言賦中上乘之作。當中,對寡婦細膩真摯的心理描繪,悲痛淒涼的景物描寫。賦作從多層次、多角度地鋪墊出寡婦喪夫的哀慟,使“寡婦”此一人物形象生動飽滿,真摯動人。寡婦於未嫁時期望著將來丈夫的寵愛,然而丈夫英年早逝。她們只能恭謹守寡,強忍著喪夫之痛,一面照顧著遺孤,另一面要處理亡夫的身後事。因此,這些寡婦的遭遇悽楚動人,尤為催人淚下。
在六朝賦作品中,女性形象特徵的描寫,集中展示出中國古代社會對女性的理想審美。這些賦作多描繪出當時社會對女性外貌美和內在美的偏好。從以上研究的女性分類中,對於不同身份的女性,作家會對其形象特徵的描寫有所側重。研究女性形象的特徵,對於探討當時社會審美特點和意識尤為重要。
第一節 貌美如花
從古到今,不論社會的審美觀如何,女性的外貌總會被整個社會所關注。而所謂“女為悅己者容”,女性的外表似乎是為取悅異性而為。雖然不同時代的審美觀相異,但“美”是共同認可的特徵。從先秦的《詩經·衛風·碩人》描繪出莊姜外型美麗的形象,到曹植《洛神賦》夢中神女的外貌超俗的形象,描寫女性容貌美的作品多不勝數,她們展現出當時社會,尤其男性眼中理想的女性形象。而其中一個六朝賦中的女性形象特徵,為擁有傾國傾城的美貌。在不同的賦中,作家對冠絕芳華的外貌,如五官、頭髮、牙齒等,皆有著相同的審美標準。
(一)、 杏腮桃頰
中國古代女子的肌膚以白為美。在大量的賦作中亦有描寫到女子皮膚白皙潤澤,如:
應瑒《正情賦》:“體蘭茂而瓊潔”39
楊修《神女賦》:“膚凝理而瓊絜"40
阮籍《清思賦》:“體清潔而靡譏"41
在應瑒賦句中,表達出女性像蘭花茂盛貌,似花一般美麗;楊修一句則指出,女性皮膚細緻光滑之美;阮籍一句則指出,女性容貌整潔的重要性。當中,在以上賦句中,賦家多以“潔”或“絜”二字來形容女性肌膚,皆指膚色潔白無瑕。除了肌膚如雪外,富有氣色、光澤和紅潤的臉頰,也體現了女性的好氣色,如:
王粲《神女賦》:“朱顏熙曜,曄若春華"42
曹植《靜思賦》:“紅顏曄而流光"43
阮瑀《止欲賦》:“顏㶷㶷以流光"44
從以上賦句可見,賦家多以“朱”或“紅”來形容女性白裏透紅的面容。而女性的肌膚往往會散發着光彩,突出女性吹彈可破、水潤光滑的面容。白裏透紅而非蒼白的肌膚代表著女性的健康、青春。以上所述的神女肌膚如玉,又充滿光澤。六朝賦家注重於女性的生命力,因此他們會把冰肌玉骨的女性形象特徵,抒寫在完美的夢中神女身上。
(二)、眉清目秀
六朝賦中描寫女性容貌的特徵之一為“蛾眉”。它的審美可見於《詩·衞風·碩人》“螓首蛾眉”45,以眉毛細長彎曲為美。而“蛾眉”亦成為六朝賦中女性的審美取向,如:
江淹《水上神女賦》:“真眉學月”46
庾信《春賦》: “眉將柳而爭綠”47
除了眉毛的描繪,眼睛亦多被賦家所描寫。所謂“眼睛是靈魂之窗”,它在賦中通常是明潔靈動、充滿神采之美,如:
王粲《神女賦》: “目若瀾波”48
蕭衍《淨業賦》:“美目清揚,巧笑蛾眉”49
眉目的形狀、神態是刻畫女性容貌和性格的關鍵。因此,作者在刻畫女性國色天香的容貌和各式各樣的性格時,往往通過對女性眉目的描寫,以突顯她們形貌之美。
(三)、唇紅齒白
中國古代常以“櫻桃”、 “朱丹”比喻女性的口唇,嘴唇以小巧、光澤紅潤為美。至於牙齒,在《詩經·衞風·碩人》中亦有提到“齒如瓠犀”50,女性的牙齒以潔白、小巧為美。在六朝賦中亦有提及到相同的唇紅齒白的審美,如:
王粲《神女賦》:“口譬含丹”51
曹植《洛神賦》:“丹唇外朗,皓齒內鮮”52
以上的“丹”字,在《說文解字》中指“巴越之赤石也”53 。因此,六朝女性會使用“唇脂”為自己添加氣色。此亦與臉頰紅潤的審美一樣,女性豐有生命力、健康氣色為美。
(四)、青絲如絹
中國從先秦時期開始,頭髮便以烏黑、濃密為美。在《詩經·鄘風·君子偕老》中,“鬒髮如雲,不屑髢也”54指宣姜頭髮茂密,不屑於使用增加髮量的假髮。在《太平御覽》云:“衛皇后,字子夫,與武帝侍衣得幸。頭解,上見其髪鬢,悅之,因立為後”55,武帝僅因衞子夫頭髮濃密而立為皇后。可見烏黑亮麗的頭髮對於女子的容貌有著重要的影響。在六朝賦中,亦有對女性頭髮的描寫,如繁欽《弭愁賦》:“綰玄髮以流光”56。女性頭髮不僅要多,還要烏黑順滑。因此,六朝賦的作家對女性的頭髮有著青絲如絹、烏黑亮麗而又濃密如雲的審美。
從以上賦作者對女性外貌的描寫,我們可以看到六朝賦家認為女性要杏腮桃頰、眉清目秀、唇紅齒白和青絲如絹的審美取向。但由於現實女性容貌相異、各有特色。因此,賦家會把這些他們認為具有女性美的形象特徵,描寫在他們夢中的神女身上。所以,神女的形象便是作者理想中的完美女性,她們與現實中的女性形象便有差距。
第二節 端莊守禮
中國社會自古以來有著女生要端莊有禮。女性要打扮整潔、行為要遵守規範。而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女性除了以上所述的外在美,她們亦要在衣服打扮上符合不同階層的規定。不同身份的女性,要跟從的衣著規矩有所不同。她們的行為舉止亦要符合社會對女性的形象規範。因此,六朝賦中女性從衣著服飾、舉止言談皆要達到端莊守禮的形象特徵。
(一)衣服
六朝時期,尤其身份地位高的女性,服飾打扮既有綺麗的錦繡,也更加繁縟華麗,如王粲的《神女賦》“龍羅綺之黼衣,曳縟繍之華裳。錯繽紛以雜袿,佩熠爚而焜熿”57、《七釋》“襲藻繍之縟彩,振纖縠之袿徽”58。而這些講究的衣裳,亦有因應不同的場合而穿著,如陳琳的《神女賦》中提到“飛羽袿之翩翩”59。《南齊書·輿服志》云:“袿屬大衣,謂之褘衣,皇后謁廟所服”60,可見穿著是須要遵循嚴格的禮儀制度。而神女是賦家理想中的女性、乃屬出塵的仙女。因此,她們便會穿著高貴、典雅的服裝。
(二)頭飾
六朝時期,女性的頭髮有各種造型。六朝賦作中多次描寫到“雲髻”、“玄髻”等,皆指女性髮髻高聳。如:
曹植《洛神賦》:“雲髻峨峨”61
張協《安石榴賦》:“蔭佳人之玄髻”62
庾信《春賦》:“釵朵多而訝重,髻鬟高而畏風”63
此外,女子在髻上亦會戴上林林總總的頭飾,如“鈿”、 “釵”等。它們會有不同的形狀,亦會鑲嵌金玉、寶石等。這些頭飾在賦作中也有所描述,如:
丁廙《蔡伯喈女賦》:“戴金翠之華鈿”64
劉緩《照鏡賦》:“搔頭欲髻,釵子縈鬟”65
從上可見,六朝女性對華美飾品的喜愛。而這些頭飾多被上層貴族女子配戴,以彰顯身份之高,同時亦代表著她們端莊優雅的形象特徵。
(三)佩飾
除了頭飾外,佩飾是女子的身份象徵之一。然而,六朝賦家甚少寫到女性佩飾。而若有在賦中提及,則皆為襯托出貴族女性服飾的華美、身份的高貴。如曹植《洛神賦》的“戴金翠之首飾, 綴明月以耀軀”66,出世脫俗的神女佩戴著精緻華麗的黃金與翠玉的飾物,而這些飾物上點綴的明珠,照亮了她的花容月貌。又如沈約的《麗人賦》中提到,“陸離羽珮,雜錯花鈿……垂羅曳錦,鳴瑤動翠”67。麗人佩戴著各式各樣的佩品,如“羽珮”、“花鈿”等,展示出其雍容華貴。因此,女性以美侖美奐的佩飾,彰顯其身份高尚、端莊大方的形象。
(四)行為舉止
以上女性的端莊守體皆體現在外在的打扮上,然而她們的言談舉止亦可體現出她們莊敬持重。六朝賦中的女性豐姿冶麗,在男女之情方面亦能自持守體。此品德是封建社會對女性內在美的希冀和規範,當中帶著男性獨有的凝視和審美。當時男性渴望女子既有傾國傾城的外在美,又有端莊持重的內在美,在家庭中成為男子的賢內助。而六朝婚戀賦中,賦家多運用正面和側面描寫,展現出女性的德行美。
在楊修的《神女賦》中,神女在面對男子的熱烈追求時,表現出“嚴厲而靜恭”68的態度,能冷靜自持、不違背禮教。可見神女即使面對熱忱的愛情時,仍會顧忌世俗的傳統禮教,保持其莊重守體的形象。在阮瑀《止欲賦》中寫到女子“執妙年之方盛,性聰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後申禮以自防。重行義以輕身,志高尚乎貞姜”69。這位女性是聰明賢慧、溫和純良的。她秉持著貞潔高雅的情操,能申述禮儀以自我防閑,重視品行和道義。她貞節守體的德行與貞姜無差別,這些女德完全符合當時男性對女性內在的審美取向。
因此,從六朝婚戀賦中可見當時社會不僅對女性的容貌衣著有著一定的要求和規範,她們的言行舉止亦要符合她們的身份地位,要遵從封建的禮教標準。而女性端莊自持的形象性格,則為禮教規範下所呈現的女性特徵之一。這符合六朝男性對理想和現實的女性內在德行美的取向。
第三節 賢淑癡情
六朝婚戀賦中,賦家所塑造的女性大多有著溫柔賢良的正面形象。女性“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她們恪守封建禮教加之於她們的各種約束,使她們的穿衣、情感和行為,皆要符合封建社會禮教。這種賢良淑德的形象多出現於出嫁女子身上。在婚姻中,她們辛苦勞作,要處理家庭大小事務,還有繁重的其他勞作,賢淑持家。而當作為家庭支柱的丈夫不幸逝世,她仍要遵守禮法,癡情專一於亡夫。女子本弱,為母則強。在養育幼子長大後,聽從其子。
在第一章所提及的王粲《寡婦賦》中寫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而複停”70。阮瑀寡妻在丈夫英華早逝後哀傷至極,一度企圖舉刀自殺,但想到遺子年幼,不忍拋下其一人,因此才放棄自我了結的想法。而曹丕的《寡婦詩》亦提到“願從君兮終沒,愁何可兮久懷”71,寡婦為了幼子從喪夫的深切悲痛中強作精神,放棄與丈夫共赴黃泉的想法,但其內心已發誓絕不另嫁。潘岳的《寡婦賦》又提到,“蹈恭姜兮明誓,詠 《柏舟》兮清歌”72。當中《柏舟》的典故源自《詩經》,《毛詩序》曰:“柏舟,恭薑自誓也。衛世子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73,可見女子在愛情中的芳心不改、至死不渝。
丁廙妻創作的《寡婦賦》中,女子也同樣面對著生活的艱辛。賦篇提到:
“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情塵。如懸蘿之附松,似浮萍之託津。”74
女性須要遵守歷代所規定的倫理和禮教。離開父母、遠嫁他鄉的女性需要無微不至地侍奉丈夫。而喪夫的寡婦“如懸蘿”失去“附松”75、“似浮萍”離開“托津”76。她“正閉門已卻掃”77,每日淚流滿面而無所訴苦,生活失去了希望。她只能“抱弱子以自慰”78,把情感寄託在幼子身上。時光飛逝,她在冬天時設祭於前廊,一面進行祭拜,一面傷心欲絕,在蕭瑟的寒冬中更顯淒涼寂寞。賦的尾句道,“計先後其何幾,亦同歸乎幽冥”79,寡婦想通雖在世時不能再與丈夫共聚,但將來歸老後她能在幽冥中與丈夫團聚。已遙想到百年死後與夫夫再次相見,可見其專一深情的形象。
賦家所描繪的寡婦生活充斥著困苦與艱辛,他們對寡婦們的不幸遭遇亦感到同情,可見六朝賦家對於這一女性群體有著一定的關注。因此,社會的動亂,使她們的丈夫被迫上戰場。這些女性只能對遠在戰火中的丈夫有所期待,盼望他們回歸。但若不幸命運使她們喪失生命的支柱、生活的依賴,她們亦只能強忍悲痛,跟從禮教的規矩,繼續照顧家中事務,立下絕不另嫁、與丈夫共聚黃泉的諾言。
六朝賦作中女性的賢淑癡情形象或許只能代表一部分女性人物(寡婦),但她們卻是六朝最常見,且有代表性的女性。不論是前代或是千年的後代中,像她們的女性多不勝數,她們的情感和生命意義早已經被封建社會規定好。這些女性從小耳濡目染於禮教的“三從四德”,所以賢淑癡情是她們以及整個封建社會所追求的女性的形象特質。因此,久而久之,這些六朝女性在遭到不公平待遇的時候,大多以逆來順受的態度面對。
第四節 女性形象出現原因
傳統女性倫理形成于兩漢、魏晉南北朝。隨著封建專制主義的完善,漢代董仲舒提出了三綱五常,確立了夫為妻綱的準則。後來,東漢的《白虎通》把“三綱”進一步發展成“三綱六紀”,把所有人加以規範。隨著後,各種對女性的道德規範陸續出現,如東漢班昭的《女誡》、三國諸葛亮的《女誡》、晉代李婉的《女訓》等,展示出封建時代女性道德的規範和行為的準則。漢代的女性倫理內容為妻子要“卑弱”、“屈從”,安於自己在家庭中低下地位、教導妻子怎麼樣去敬夫、順夫、“從一而終”。而六朝時期,雖風氣較為開放、女性不再受到前代的多種限制,但其在某程度上亦繼續了封建女德的思想,從而形成以上所述的女性形象。
在女性持家守禮的形象特徵方面,女性在歷史的長河中受到各種的禮制規範,從而形成該形象。《禮記·昏義》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婚姻需要“敬慎重正”80。而與漢代相比,六朝朝時期的門第婚姻趨向功利化。當時世族婚姻以獲取政治、經濟利益為目的,與買賣婚姻無所差異。而“士庶不婚”是世族遵從的封建規範,在婚姻中被動的女性,她們無選擇和話語權,最終犧牲自身的婚姻而成全家族的利益。因此,以家族利益為重、一切聽從安排的觀念根深蒂固。在《世說新語》云:“有女名絡秀,為了家族利益不惜自願為妾,謂‘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81從此可見,當時士人婚姻皆以門第家族利益為先。這是家族世代對女性婚姻的教育,同時亦是封建社會所推崇的風氣。只要能夠高攀上名門望族,委屈為妾也是在所難免。
當女性能延續家族香火,誕下兒子,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亦能隨之而改變,子嗣的“孝”把她們地位提高,變為更受尊敬的位置。在《世說新語·文學》云: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慷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 82
從上述可見,妻子不僅需要聰慧過人、持家有道,照顧公婆和家務事,還要遵守夫家家規,為下一代籌劃婚姻,維護夫家家族利益,完全地服從夫家。從女性的婚姻受娘家安排,轉為為夫家安排子嗣婚姻,從此不斷輪迴。而身為母親的女性同樣會像以往的父母一樣,堅持婚姻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觀念,加上上述的門第婚姻利益觀念,使婚姻中男女地位關係無法自由發展。因此,女性在婚姻關係中的矛盾,是傳統思想的規範和對自由戀愛的渴望、家族世代的利益和理想婚姻的追求。然而,她們最終還是堅守封建制度的規範,選擇成為一個賢良守禮的妻子。
至於在女性容貌特徵—貌美如花方面,則緣於建安時期繼承了漢代宮廷飲宴文化。因此,不少作家從中創作了許多相關的作品。曹植的《娛賓賦》描述了他在歌舞宴會中,和樂伎的輕歌曼舞。從中可見,女樂文化影響着建安文人的生活和創作。而樂妓在飲宴中的陪伴和交流,使她們在心靈情感上更能接近這些文人作家,因此為文人的詩意生活帶來了許多創作靈感。當中,文人對女性的情感和欲望的追求,留下了女妓的影子,如女性貌美的面容、婀娜多姿的形態等形象,揭示出文人對女性外在美的理想原型。
不僅如此,女性自持端莊的形象特徵方面,在建安時期不少的抒情小賦亦可從中窺探到。當中,作家進一步表達出對女性美的歌頌和追求。這些小賦通常在前半部分描寫女性之美,後半部分表達對其追求和嚮往。然而,建安的女性美不同於漢賦所描寫的宮廷女性刻飾之美。六朝賦中的女性洗去鉛華,把自然美與才性融合,例如曹植的《靜思賦》、阮瑀的《止欲賦應場》、應瑒的《正情賦》等,不只是刻畫女性的美貌,而是加入了女性的才德貞潔。正因為女性內在美與外在美兼得,文人與這類“完美女性”的愛情顯得格外非正常所見,使女性更加異常動人,突出她們既秀外慧中、端莊自持的形象特徵。
另一方面,女性賢淑專一形象的形成,歸因於該為文人理想的後盾。在陸機《為周夫人贈車騎詩》中,刻畫了一個閨中思婦的內心掙扎。她不知道丈夫的行蹤,同時認為“京城華麗所,璀璨多異人。男兒多遠志,豈知妾念君”83,擔憂男人在繁華的京城中不知去向,以及對丈夫不知妻子思念他的牢騷。“思君隨歲晚” 一句表達出她情感的專一和執著,直到年華逝去也會一直思念丈夫。當中亦隱含她過去對丈夫的掛念,同時也表達她於未來愛情的不變。這些既知禮隱忍而癡情專一的思婦形象,代表着六朝時期眾多宦游及在外文人,對遠在家鄉的妻子的期望,隱含了男性對理想婦女的規範。從眾多的賦中,可見文人對於代言體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男性對於理想女性的封建道德觀念。因此,六朝宦游和作家在外出仕時,需要閨中妻子表現出對丈夫絕對的忠貞守禮與癡情如一,而這亦是他們遠赴外地、實現理想時的精神後盾。正因如此,六朝文學中的女性貞淑、專一的形象,是當時封建制度的規範,同時亦是男性文人所寄寓的結果。
由此可見,封建社會的規範、家族的利益以及男性的理想寄託,塑造了各種女性的形象。從先秦時期開始,封建的文人創作各種書籍,規範女性的德行。而門第觀念使女性喪失婚姻選擇權、在夫婦關係中處於被動的狀態。而女性安於現狀,在安排子嗣婚姻時,與父母一樣,遵循守舊的門第觀念,犧牲子女的婚姻幸福,以夫家利益為重,塑造賢良守禮的妻子形象。此外,女性的容貌美、姿態美多為男性文人在樂妓身上所欣賞的特質,再加上閨中妻子為自己堅守貞潔、對自己癡情如一,使外在宦游的男性放心追逐理想,成為他們的精神後盾。
從以上各種女性的身份,她們所擁有的外在美和內在美,顯示出她們在當時社會地位低下的情況。女性在婚姻愛情的關係中一直都是被動的角色,因此她們就算被社會期待有著理想、完美的容貌和性格,她們都是採取接受的態度面對,跟從社會的期望成為“完美”的女性。而在婚姻中、不論是貴族女子還是普通婦女,她們在丈夫早逝、背叛的時候,皆以忍受的方式面對,完全地遵從封建社會下所加之於她們身上的枷鎖。在封建制度和男權凝視下,成為被剝削的對象。
第一節 封建社會的妻妾制度
中國古代社會實行一夫一妻多妾制,而且女子要遵從“三從四德”,尤其出身卑微的妾侍在婚姻中處於被動狀態,沒有話語權。《鹽鐵論·散不足》云:“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禦,富者盈室”84,可見高薪厚職的貴族官員所納的妾侍數目眾多。朱大渭《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提到,“媵妾是這個制度的產物,當時妾在封建家庭中的地位極為低賤”85,認為封建的婚姻和禮教制度是女性婚姻悲劇的元兇。在封建制度的薰陶下,伴侶是她們唯一的依靠。她們在戀愛關係中若受到命運的作弄、伴侶的背叛,必會造成自身精神世界的破滅。六朝賦中的女性不論是貴族女子,還是平民婦女,她們對愛情的憧憬是相同的。她們的悲劇不是因為愛而不得所致,而是因為得到後,被強行失去的背叛感。她們的花貌總會有凋謝的一刻,不能青春永駐。在年輕貌美時,當然能討得伴侶歡心,但當歲月流逝,傾國傾城的美顏也抵擋不住年華的逝去。
正如上述,六朝貴族統治階級生活奢靡,男性蓄婢納妾成為一股風氣,加劇男女性別不平等的狀況,女性無法要求男性於婚姻愛戀的關係保持專一。在六朝封建社會所造成的性別地位極度不平等的狀況下,男性妻妾成群、喜新厭舊的行為,對充滿著愛情憧憬的女性而言,是十分殘忍的。她們只能忍氣吞聲、卑微順從,又或使用偏激的方法,如張纘《妒婦賦》中認為女性“常因情以起恨,每傳聲而妄受”86,女性因對丈夫癡情才會嫉妒。當中,女子氣忿難平,採取極端的方式—公開閨房床笫的隱私,來反抗這種不平等的封建制度。然而,效果不如理想,甚至引起當時社會的大量批判。從極端的容忍,變為極端的反抗,是女性在封建社會中有所覺醒的先兆。
第二節 六朝賦隱含的階級意識
從六朝賦的一些篇章中,它們的賦題已隱含著這些男性賦家認為女性性別低下的封建思想。如蕭繹《蕩婦秋思賦》中,寫到: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況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妾怨回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歎。愁縈翠眉斂,啼多紅粉漫……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87
賦篇描寫一位原本是妓女的女性,後嫁為婦人,在出嫁後沒有得到丈夫的寵愛,獨守空房十年之久。她獨自在逐漸寒冷的秋日中思夫,“鬢飄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嘆”88,感嘆自己的身世命運,期望丈夫能早日回來。賦中描寫各種景物襯托自己的寂寞孤獨,在皎潔的明月下,沒有人和她共度時光。賦的內容分明是講述女子對丈夫的思念癡情。然而,賦題中卻對婦女使用帶有侮辱的“蕩婦”二字。女子既已不再是妓女,又嫁給他人作為人婦,蕭繹卻多次在賦中代言時,強調自己是“蕩婦”,認為婦人是一名地位低下,異性的“消費產品”。清代許槤在《六朝文絜》評:“逼真蕩婦情景,琢磨入細”89,可見就算經歷不同時代,封建制度依舊不變。因此,在賦題中已隱含著蕭繹剝削階級的審美意識。
庾信《蕩子賦》中寫到:
“蕩子辛苦逐徵行,直守長城千里。隴水恆冰合,關山唯月明。況復空床起怨,倡婦生離,紗窗獨掩,羅帳長垂,新箏不弄,長笛羞吹。”90
前四句先交代蕩子因征行,被派守長城而離開家鄉的背景。“況複空床”六句,描述婦人在丈夫從征後的生活,寫出思婦的孤獨寂寞、無心奏樂的心情。之後思婦開始回憶昔日夫妻在一起奏樂、跳舞的歡樂時光。然而,現在的情景大不如前。婦人沈浸在對丈夫的思念中,對任何事都提不起勁。所謂“女為悅己者容”,如今丈夫不在身邊,妻子無心梳洗打扮。因此妝奩前的明鏡不去擦亮。“合歡”兩句寫出出征的丈夫音信全無。在丈夫身死未卜的情況下,她無法分神編織成對丈夫深切思念的回文詩。思婦對丈夫日益擔心,內心充滿著惆悵,以至“遊塵滿床”、“細草橫生”91,仍然沒有心思去打掃乾淨。最後六句寫出思婦忽獲丈夫將歸的消息,感到安心後即愁眉舒展。思婦想像丈夫歸家時,自己含笑迎接的情景,而心花怒放。賦中的丈夫為國長征,實在稱不上“蕩子”。而身為“蕩子”的妻子,亦貞忠癡情。但賦家使用“蕩”字,則代表了這些普通階級的百姓,“蕩子”的妻子便為“蕩婦”。不僅剝削社會中卑微的百姓,同時亦間接地剝削普通婦女的地位。
以上兩篇賦作雖篇幅較短,但把思婦對丈夫的深刻思念、獨守空房的孤單寂寞寫得淋漓盡致。但賦家把思婦寫成倡婦、蕩婦,把征夫說成蕩子,隱含了社會上高層階級對下層百性的剝削意識,尤其使用“蕩婦”一字形容女性,更是一個嚴重的指控。而從內容方面,思婦皆忠於丈夫、對其一片癡心,沒有違背封建制度的規範,完全沒有放蕩的舉止,而征夫亦無放蕩的行為。因此,他們不該被稱為蕩子、蕩婦。
第三節 封建制度下對男權的服從
左棻《離思賦》中描寫左棻身處皇宮,作為貴族一員的宮妃,卻無限的苦悶:
“懷思慕之忉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晻曖而無光兮,氣懰慄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92
自從入宮後,她日夜焦慮,不受到皇帝寵幸的她孤苦萬分。而家人又遠隔宮門之外,更顯憂愁,只能以淚洗面。當中,“非草苗之所處兮,恆怵惕以憂懼”93一句指自己出身草根階層卻身處宮中生活,表達內心的忐忑惶恐。“不論美醜,女人其實都是以身體或美色在暗地裡滿足男人慾念的需索,卻又在表面因為身體美色遭受輕蔑、為人避忌”94,在這些封建社會下,女性就算有著姣好的面容,亦很難得到異性的尊重。此對於身處深宮的女子更是如此,何況左棻更是有才華但長相醜陋。她出身貧困,後因具才華而入宮,卻因姿色醜陋不受君王寵愛。她雖為皇帝的妃子,但實際上只是皇帝的文學侍從。因此,不受待見的左棻在宮廷中的生活十分孤獨。她把情愛中的孤獨,寄託到對遠方親人的思念上。她被困於皇宮的高牆內,與親人遠隔兩方而感到無比悲傷。因思念而“夜耿耿而不寐兮”,更“仰蒼天而泣血”95。可見對無法與親人相見的愁苦思念,對她來說是是痛徹心扉的。左棻沒有得到過愛情的美好,並非鍾情於皇帝。正因如此,伴侶及其寵愛並非她的精神依託,使她把牽掛、情感付諸於骨肉親人。在婚姻關係中,左棻是不幸的,她因才德受到皇上的青睞,但由此至終都沒有體驗君王的寵愛、愛情的美好。另一方面,左棻同時亦是幸運的。她有文學才華,使她能借助文字來抒發情緒、消解寂寞。然而,那些與她有著相同命運、不得帝王寵愛,又不得與親人共聚的深宮女子,不能反抗命運。她們只能隨著時間的變遷,在深宮中蹉跎一生來渴求君王的寵愛,卻落得無人問津的結局。因此,《離思賦》所描寫的,不只是左棻一人的哀愁,而是眾多貴族女子共同的悲哀。
曹植《湣志賦》描寫普通女子在婚姻中沒有選擇權,被迫與情郎分別,嫁與他人。賦雖殘缺,但語意完整。賦中描寫:
“竊托音於往昔,迄來春之不從。思同游而無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於永絕,悲莫悲於生離。豈良時之難俟,痛予質之日虧。登高樓以臨下,望所歡之攸居。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廬。欲輕飛而從之,迫禮防之我拘。”96
賦文前八句描寫女子另嫁他人的痛苦,後六句講述自己登樓所見所思。“望所歡之攸居”一句是她登樓眺望的目的。其中,“所歡”,指其情郎。從遙望自己思念極至的情郎所居處,想到了自己現今的無奈、令人生厭的處境。“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廬”97中,“君子”指她日思夜想的情郎,而小人指被迫嫁予的丈夫。曹植用“清宇”和“蓬廬”描述情郎和丈夫的居所,明確表露出她對兩人的愛憎感情,也隱含她婚姻狀況的不幸和生活環境的惡劣。因此,她對昔日美好的人和事念念不忘,想像生出雙翼,飛往情郎的身邊。然而,現實卻是她被牢牢拘束於封建制度裏,使她不能自由戀愛,只能在婚姻中作為被動者。
在六朝戰火不斷的混亂社會中,男性都對被迫出征而無可奈何,更何況不論貴族還是平民,那些被動、“人格附屬於男子”98的女子。另一方面,從現實的層面中,“一、女子沒有繼承遺產權;二、女子沒有獨立的謀生之權。結果,就是沒有獨立的經濟權,一切的生活需求,都需仰給於男子”99。從中可見,女性的日常生活全然倚靠男性。在封建社會下她們喪失了經濟能力,就算那不是她的如意郎君,她們也必須依附男性以維持生活。女性這種不幸的遭遇已可見其社會地位的低下。若她們依賴的丈夫離世又或把她休棄,這可謂雪上加霜。她們既無法反抗,階級低下的普通婦女又無法把自己的苦痛抒發,只能默默忍受不幸、被封建社會剝削女性地位,對男權無條件的屈服。
第四節 六朝賦中女性作為男性玩物
六朝賦繼續漢賦的宮體賦,多書寫宮廷生活。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中,對建安時期評價為“憐風月,狎池苑,述恩寵,敘酣宴”100。在六朝賦中有提到男性的娛樂多在宮廷宴食中。而他們的娛樂多為觀看女子歌舞,大量出現歌伎舞伎。因此,以宮廷樂舞為題的賦作數量眾多,而她們大部分皆為男主人的家妓。蓄養家妓對男性來說是一種娛樂。然而,對於被蓄養的女性而言,並不能從中感到歡樂。六朝以“舞蹈”為題的賦作如西晉夏侯湛和張載的《鞞舞賦》、南朝蕭綱的《舞賦》和顧野王的《舞影賦》等,六朝賦家從不同的角度欣賞歌伎樂伎,卻無人注意女性的心靈世界。如顧野王《舞影賦》中描寫到舞姬在富麗堂皇的宮殿中跳舞的姿態。賦的前兩句帶出宮殿的金碧輝煌,而當中“出妙舞於仙殿”。舞姬舞姿優美,“影嬌態于雕梁”、“圖長袖於粉壁”、“寫纖腰于華堂”,似鴛鳥飛翔101。作者認為冬宵短暫,要及時行樂。整篇賦作從男性的視角出發,視歌妓舞妓的女性為娛樂工具,毫不關心女性的內心世界。
尤其貴族男性能通過權利和金錢來獲得這種休閑娛樂,把女性視為娛樂工具。當娛樂一涉及性別後,被男權凝視下的弱勢女性則會被演變成“淫欲”的發洩工具,婢女姬妾能在貴族階層之間進行買賣交換,女性徹底地淪落為“玩物”、 “物件”。李善注的《文選》引臧榮緒《晉書》云:“崇有妓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乃勸倫殺崇,遂遇害”102,可見地位低下的侍婢在封建社會下成為貴族階層的利益工具,可以進行交換和買賣。除了在賦作可見女性作為男性消遣娛樂的工具,《玉台新詠》也描寫眾多歌妓、舞妓。它把這種男女閨情完全地展示出來,透露出貴族階級視女性為娛樂的工具,帶出階段的剝削意識。
六朝賦繼續了漢賦的形式,又進行創新,把題目擴大,不僅限於宮廷生活作為賦作題材。當中,婚戀賦作為六朝賦作的代表題材之一,其所描寫各種身份、階級的女性,豐富了中國古代女性的面貌。藉着是次研究,我們觀察到六朝婚戀賦中所描述的女性形象多樣而豐富,既有夢中神女、被休棄的棄婦、丈夫早逝的寡婦等。一方面,這些女性大多有著相同的形象特徵。她們有著姣好的容貌、莊重守禮的德行和對伴侶一片丹心的癡情。然而,這些形象皆是封建社會所期望女性能達到的、是封建制度諸加於女性的拘束。女性在婚姻關係中處於被動的角色,她們沒有話語權,是依附男性的人格。而在男權的凝視和封建社會的規範下,女性完全地淪為貴族男性的玩物,剝削性別階級意識嚴重。
然而,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六朝抒情賦的專著不足,對於六朝婚戀賦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數。而且,因年代久遠,部分賦作或有缺失。種種的研究限制或影響研究內容。雖然如此,從本論文的研究中了解了更多六朝女性的生活狀況和精神面貌,揭示她們在六朝時期的性別地位。
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六朝時期女性形象與當時社會經濟政治的關係。此外,亦可以和其他朝代的女性形象作對比,研究她們在面對社會對她們的期望和限制時的態度異同。
最後,希望本論文的研究,能夠對理解六朝時期的女性形象和地位有所貢獻,並為當代社會的性別平等議題,提供啟示和思考。
(一).古籍
1.(漢)桓寬:《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2.(漢)許慎著:《說文解字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3.(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4.(梁)蕭統:《文選》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5.(宋)李昉:《太平禦覽》(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95年。
6.(清)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7.(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8.(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9.(清)嚴可均:《全後漢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10.(清)嚴可均:《全三國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二).專著
1.陶秋英:《中國婦女與文學》(北京:北新書局),1932年。
2.黃永武:《字句鍛鍊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
3.王雲五:《禮記今注今譯下》(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1970年。
4.張正體、張婷婷:《賦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
5.於浴賢:《六朝賦述論》(河北:河北大學出版社),1990年。
6.朱大渭:《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7.鄭毓瑜:《性別與家園—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
8.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下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9.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上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10.張強:《歷代辭賦選評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
11.劉淑麗:《先秦漢魏晉婦女觀與文學中的女性》(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年。
12.池萬興:《六朝抒情小賦概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13.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14.馬積高:《歷代辭賦總匯》(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
15.池萬興:《《史記》與小賦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6.魏耕原:《歷代小賦觀止》(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
(三).學位論文
1.吳從祥:《唐前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5月)。
2.陳曉燕:《漢魏六朝引《詩》研究》(青島:中國海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5月)。
3.劉佳媚:《曹魏文學中的女性形象研究》(遼寧: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6月)。
4.田子君:《漢魏六朝賦中的女性形象》(河南: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6月)。
5.劉田田:《魏晉婚戀賦研究》(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5月)。
(四).期刊論文
1.靳青萬:〈漢魏六朝女性賦述論〉,《中州學刊》第3期(總第129期),2002年5月。
2.侯立兵:〈漢魏六朝賦中的蟬意象〉,《求索》第10期,2007年。
3.梁慕瑜:〈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女性地位〉,《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7卷第11期,2008年11月。
4.陳元瑞:〈漢魏六朝女性詩歌的題材分析〉,《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0卷第3期,2011年3月。
5.陳元瑞:〈漢魏六朝女性詩歌的情感基調〉,《天水師範學院學報》第36卷第1期,2016年1月。
6.林佳燕:〈漢魏六朝賦中的鸚鵡意象〉,《華人文化研究》第九卷第二期,2021年12月。
腳註:
1. (漢)班固:《兩都賦序》,見(梁)蕭統 編,(唐)李善 注,《文選》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
2. 劉田田:〈魏晉婚戀賦研究〉(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5月)
3. 田子君:〈漢魏六朝賦中的女性形象〉(河南: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6月)。
4. 張正體 張婷婷:《賦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
5. 林佳燕:〈漢魏六朝賦中的鸚鵡意象〉,《華人文化研究》第九卷 第二期,2021年12月,頁 219-228。
6. 侯立兵:〈漢魏六朝賦中的蟬意象〉,《求索》第10期,2007年,頁168-170。
7. 于浴賢:《六朝賦述論》(河北:河北大學出版社),1990年。
8. 池萬興:《六朝抒情小賦概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9. 靳青萬:〈漢魏六朝女性賦述論〉,《中州學刊》第3期 總第129期,2002年5月,頁53-57。
10. 陳元瑞:〈漢魏六朝女性詩歌的題材分析〉,《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0卷 第3期,2011年 3月,頁47-50。
11. 陳元瑞:〈漢魏六朝女性詩歌的情感基調〉,《天水師範學院學報》第36卷 第1期,2016年 1 月,頁6-9。
12. (清)嚴可均:《全後漢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907。
13. 同上。
14. 馬積高:《歷代辭賦總匯》(湖南:湖南文藝出版社),2014年,頁797。
15. 同上。
16. 同上,頁457。
17. 同上。
18. 同上,頁469。
19. 同上。
20. 同上,頁449。
21. 同上。
22. 池萬興:《《史記》與小賦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298-299。
23. 同14,頁401。
24. 同上。
25. (清)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47。
26. 同上。
27. (晉)陳壽:(南朝宋)裴松之 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599。
28. (清)嚴可均:《全三國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37。
29. 同14,頁450。
30. 同上。
31. 同上,頁402。
32. 同上,頁656-657。
33. 同上。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同上。
37. 同上。
38. 魏耕原:《歷代小賦觀止》(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頁185-191。
39. 同14,頁431。
40. 同上,頁441。
41. 同上,頁520-521。
42. 同12。
43. 同14,頁462。
44. 同上,頁392。
45.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 1989年,頁204-205。
46. 同14,頁959。
47. 同上,頁1115-1116。
48. 同12。
49. 同14,頁996-998。
50. 同42。
51. 同12。
52. 同17。
53. (漢)許慎:《說文解字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18。
54. (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226。
55. (宋)李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95年,頁1720。
56. 同14,頁435。
57. 同12。
58. 同14,頁410-412。
59. 同上,頁423。
60.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342。
61. 同17。
62. 同14,頁718。
63. 同44。
64. 同14,頁442-443。
65. 同上,頁1012。
66. 同17。
67. 同上,頁942。
68. 同37。
69. 同41。
70. 同29。
71. 同25。
72. 同30。
73. 同51,頁216。
74. 同14,頁444。
75. 同上。
76. 同上。
77. 同上。
78. 同上。
79. 同上。
80. 王雲五:《禮記今注今譯 下》(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1970年,頁791。
81.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下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620。
82.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上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06。
83. 劉淑麗:《先秦漢魏晉婦女觀與文學中的女性》(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年,頁354。
84. (漢)桓寬:《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56。
85. 朱大渭:《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262。
86. 同14,頁1024。
87. 同上,頁1051-1052。
88. 同上。
89. 引自黃永武:《字句鍛鍊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頁108。
90. 同14,頁1119。
91. 同上。
92. 同14,頁746。
93. 同上。
94. 鄭毓瑜:《性別與家園—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頁20。
95. 同88。
96. 同上,頁469。
97. 同上。
98. 陶秋英:《中國婦女與文學》(北京:北新書局),1932年,頁9。
99. 同上。
100. 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60。
101. 同14,頁1065。
102. 同1,頁1291。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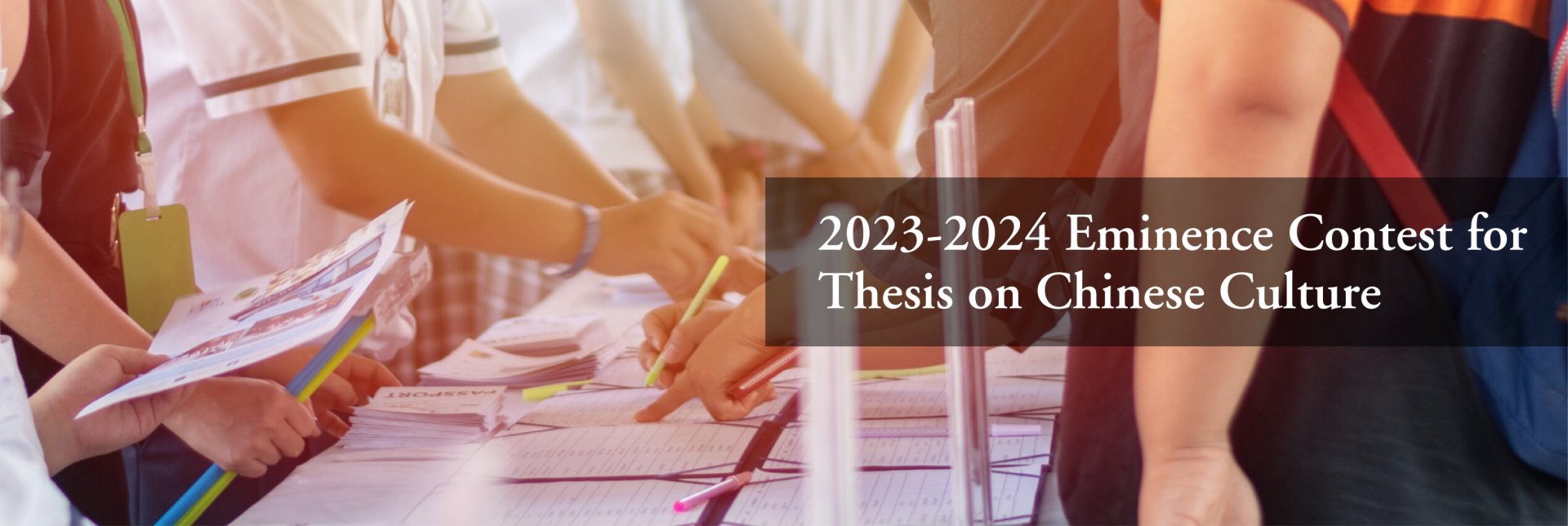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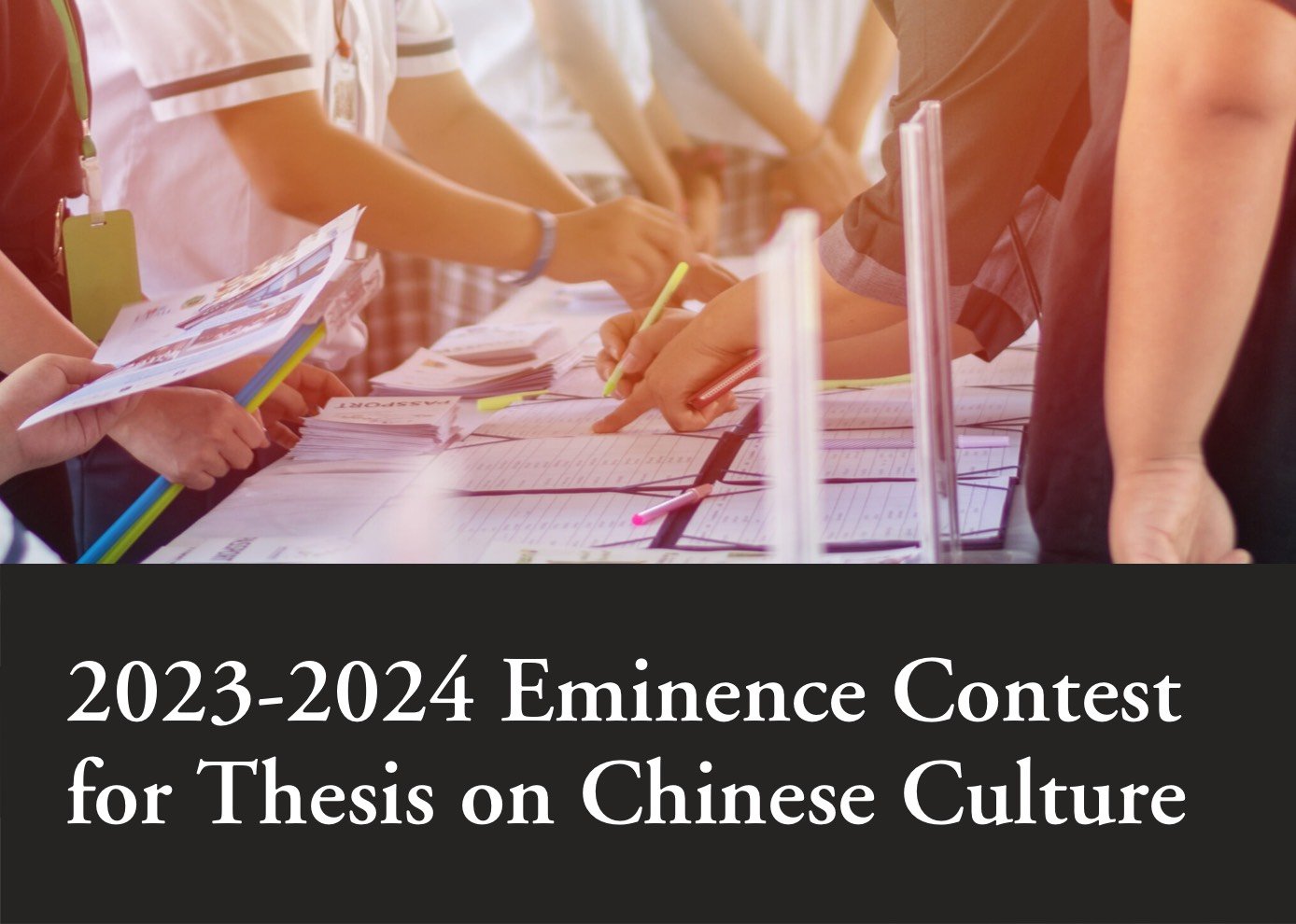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