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歷史的身體書寫:
纏足與晚清放足運動
司徒奕彤
2024年4月11日
謝 辭
本畢業論文,承蒙歷史系老師何其亮教授悉心指導,得以完成,謹此衷心感謝。其次感謝我的父母,在此期間的鼓勵及支持;然後,我想感謝自己一路的努力與堅持,走到這一步屬實不易;最後,也非常感謝撰寫論文期間,曾得下列人士/機構予以協助,本人併此致謝。
纏足,又稱為「裹腳」,是中國古代獨有的一種文化現象,上至皇家公主下至山野農婦皆以纏足為美,甚至將女性的一雙腳打造成一個畸形的歷史舞台,人們沉醉其中,感受著小腳的嬌小與柔弱,甚至把小腳與女性本身畫上等號。至此,小腳成為美的象徵;甚至成為貞節、女德的標誌。直至近代,纏足依然保持著特殊的習俗地位,每當女孩到了五、六歲的年紀,其母親就會用數道長長的布條緊纏她們四隻小腳趾(拇指除外)於足心並用針線縫牢。其目的是為了限制女孩們腳部的正常發育,直到雙腳血枯筋斷,脛折皮躁,足底部成為兩個弓形方能將布帶放開,這就形成了舊時人人都稱讚的「三寸金蓮」,1(附錄一)同時也是世上獨一無二,僅中國存有的畸形審美觀。而這種以身體毀傷為代價的「美」,一直以來都被評價為是男權社會之下對女性身體的壓迫和摧殘表現,畢竟在一個遵守「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國家,偏偏出現了此等叛逆、使人費解的行為,屬實難解,。加上得以流傳百年,並成為一個正面抑或習以為常的形象,即使是十九世紀前來華的西方人士們自述中,對纏足的也並未有過多否定和批評性的評論。
然而,隨著鴉片戰爭(1840年-1842年)的發生,近代來華傳教士與中國人有了長期的接觸,他們對纏足進行了深入的考察,並且將此所聞以不同渠道帶回了西方,然後用上現代攝影技術及照骨術(x光片)的探測,終發現了纏足的弊處。至此,纏足固有的形象不僅被顛覆,他們還從基督的教義將纏足視為野蠻的行為,畢竟他們的宗教觀念是覺得「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兩足,男女無二致」,故希望國人可以禁止纏足的行為。其實對於反足,筆者發現,我國晚清時期的太平天國(1851年—1864年)也曾有過放足的經歷。可以說是我國近代放足的萌芽時期,也是第一次挑戰男權社會下男性的權威。當時身為領導的洪秀全(洪日,814年—1864年)因信奉「拜上帝教」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義,所以當時的教眾們都追崇「男女平等」。洪秀全還頒布了放足令,女性們不但不需要纏足,還專門組織女子軍團,擔任重要職位,可惜她們並未擁有自由的婚配、財產繼承以及政治上的實質權,所以地位也並未有任何提高的改變,而在太平天國控制的地區上,男性們依然是妻妾成群。2 在當時的「放足」行動中,更多的似乎是一種權宜之計以及政治口號,為的只是希望更多人追隨太平天國。後來隨著他們的失敗,「放足」運動也淹沒在歷史的長流中,原本在此區放足的女性又開始將腳「纏回去」了。由於外來傳教士與太平天國的放足都是基於上帝的教義,因此可謂同根同源了。傳教士們除了勸喻放足,還以生理學、醫學的角度紛紛痛訴纏足是對女性身體健康的傷害,例如在1884年的時候,德國基督教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年-1899年)提出纏足會使婦女「血氣不舒,易生疾病」、「身體多弱,生子亦弱」,並且將纏足歸咎為阻礙國家富強的原因之一;並且引用中國古典中的《孝經》來解釋婦女們纏足的不是。之後的來華傳教士開始身體力行地開展了一系列的反纏足運動,務求解放中國的女性,雖然他們的反纏足運動初衷是為了傳道,但是對於近代中國社會和婦女解放可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這一路的艱難,也是不可抹滅的存在。3 早期的西方傳教士們是從宗教的方面主張反纏足的,所以在當時的社會裡,除了教徒們外,其實並未引起中國知識份子們的附和。而從醫學、政治等方面來反對纏足的思想,在維新運動(1898年-1898年,戊戌年)前引起國人的贊同也並不多。不過,傳教士們卻做到了一個啓發性的開頭,在他們不遺餘力的宣傳下,使得國人們開始意識到纏足的敝處,並且如雨後的春筍般紛紛加入傳教士們反纏足的戰隊中,藉此希望透過放足達到振興中華的目的。
筆者希望透過這篇論文可以深入探討中國歷史上纏足的現象及其形成的原因,儘管纏足已作古,但這種風俗的迅速興起、風靡一時及長盛不衰必定有它的特殊之處。其次,筆者將梳理過去學者們對纏足以及反纏足的研究,希望從現有的資料中了解中外學者們從不同見解、立場或意識形態等,研究他們對這兩個方面的看法,從中可以激發筆者有新的想法或意見。再者就是說明來華傳教士在中國如何使用宣傳攻勢動搖傳統輿論導向,之後建設女校以及天足會,務求緩慢、漸進的對國人進行教育和影響。畢竟,在筆者看來以一個外來者的身分想讓國人打破千年來的不良風習,並且改變他們根深蒂固的觀念,實屬難比登天。而且對於傳教士們來說,做這些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基於這種背景之下,本文希望可以揭示在面對放足一事上,不同的群體們會存有那些不同的觀點,如西方的傳教在闡釋纏足問題時,更多的是從宗教角度視纏足為中國的一個陋習,並且希望透過放足來擴大宗教的影響;中國男性知識份子則試圖通過反纏足再次掌握自己對於家庭的控制權;而處於漩渦中的婦女們卻呈現「失語」的狀態,無一人能聆聽她們的想法。終歸反纏足運動看似是一場為女性們發聲的運動,實則背後暗流湧動,各懷鬼胎,是每個群體間的權利抗爭。而以往學術界研究這些當局者們的文章甚少,望藉此可以彌補當中的不足之處。
在學術界裡對於纏足相關的研究成果可謂十分豐富,大體可分為兩大類型:首先是近代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對纏足的描述和分析,此部分多由外國學者所著。相對地,中國學者在此時期的學術研究相對較少。其次是近代階段的研究,重點更多地放在反纏足運動上,這部分明顯受到了中國學者的更多關注,故有較多的學術論文發表。
在《終結小腳》一書中,秦軍校指出:被達芬奇(Leonardo di ser Piero da Vinci,1452年—1519年)讚為「工程學的傑作和藝術品」的腳,卻在中國一千年的封建歷史中成為充滿著啞言和痛苦的隱痛點,更成為一代代中國婦女不醒的噩夢。「三寸金蓮是外婆給女兒的贈禮,又是母親給女兒的贈禮。」作為贈禮,秦軍校認為小腳的長期存在,原因有三:其一即為觀賞,清人袁枚(1716年3月25日—1797年1月3日)在《答人求妾書》中說:「令人每入花叢,不仰觀雲髻,先俯察裙下。」古人為小腳的觀賞制定了若干標準,並發展出品蓮學這一特殊學問,足以證明觀賞性的重要。其二便是程朱理學對於女性的束縛,封建社會為女性設置了懿德、馨德、賢德、薏質、淑質、芳蘭之質等要求,女性必須在這樣的固定格局中塑造自己;其三即為性,小腳的神秘和隱晦正好滿足了性的要求。4 而此種纏足現象也引起了海外學者的注意和興趣,霍華德・S・列维(Howard S Levy,1923-?)就是其中一個。他曾專門出版了一本關於纏足的著作《Chinese Footbinding: The History of a Curious Erotic Custom》,書中詳細說明了纏足的歷史起源和蓬勃的發展背景,並且從婦女解放以及地位提高的視角,詮釋近代以後自由派改革者和傳教士為廢除纏足所做的各種努力。書中大量內容都以「奇異」描述居多,諸如蓮迷、蓮鞋、小腳與男性性心理的關聯等等,不過對於題目中的「風俗」本身卻着墨不多。5 而高洪興在《纏足史》一書中更為系統地全面探討了纏足發生的原因,通過對纏足歷史淵源的追溯以及纏足原因的梳理,其主要從審美觀念、禮教觀念、心理因素以及婚姻與纏足幾個方面進行分析,找出其長期存在的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以及纏足至今仍然受到世人關注的各種原因。6 最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學者高彥頤(Dorothy Ko,1956年—)對明末清初江南才女的研究。她在書中明確說明不贊成把纏足視為中國女性被迫害的象徵,而是肯定了女性的主體意識,通過這些「才女」探討纏足女性內心的想法與身體感受。7
而對於反纏足的研究,內地學者對此研究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增多的,但多數研究是對反纏足運動進行階段性敘述,且大多集中於晚清階段,尤其是戊戌維新時期,對民國以後的情況則涉獵甚少。這些文章的一個明顯特點是從婦女解放運動的立場來做立論,將不纏足運動視為反封建反壓迫的運動。
在楊興梅(1971年—?)出版的《身體之爭近代中國反纏足的歷程》一書中:她將近代中國的纏足及反纏足運動都統一納入當時的歷史環境中看待,以時間為序,詳細梳理纏足與反纏足觀念的變遷和反纏足方式的發展變化,結合各省情況,描述近代中國的纏足與反纏足運動進程。對於女性纏足歷史的關注,不僅僅只局限於國內,國外學者同樣對其深感驚歎。好奇究竟人們處於什麼樣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狀態,才會生發出纏足這樣的事物,基於種種疑惑,他們進行了深入探索。如剛剛提及的美國學者高彥頤,也列舉了眾多國外思想家對於中國婦女纏足的看法。諸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認為纏足是對女性雙腳的閹割,纏足帶來的小腳和弓鞋成為男性愛不釋手的東西,以此滿足了男性的戀物癖;社會學家范伯倫(Thorstein Bunde Veblen,1857年—1929年)則提出「炫耀性消費」的理論,他認為西方文化中的「束緊腰身」,以及「中國人的毀損雙足」都是有閒階級家庭財富充裕的象徵,只有生活、衣食無憂的貴族階級才有資本生發出這樣的奇思妙想,通過這些行為炫耀自身擁有的財富和地位從而滿足虛榮和獵奇心理。8
此外,西方的來華傳教士可謂是近代中國發起反纏足運動觀念的主要提倡者,對於他們的主張以及影響,在不纏足的歷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1965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就有一篇研究基督教不纏足運動的碩士論,文中採用了大量教會會務報告及各種在華教徒的記載,主要說明基督教教會,尤其是天足會對不纏足運動的貢獻。9國內的學者陳文聯、張夢的《來華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的反纏足運動》中都詳細分析了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的反纏足運動的關係,並且指出傳教士的反纏足輿論雖然主要目的是為了傳教服務,但無心插柳柳成蔭地當了「歷史的工具」,不自覺地推動了近代反纏足運動的開展,影響了一部分的有識之士。10 此外,傅瓊、李浩在《來華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的戒纏足思潮》中也認同來華傳教士與戒纏足思潮有密切的聯繫,對於中國的反纏足運動有著一定的推動作用。11 之後也有學者摒棄以往只着重政治發展和社會運動的研究向度,轉為用不同角色的視角重新檢視纏足歷史,透過針對纏足婦女本身,尋找真正不同的聲音,呈現歷史中往往最容易被忽視的角度。之前提到的高彥頤著作中的《Cinderella's Sisters :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中就表達出她認為纏足的面相不只單種,而是有很多種,由一直變化着的經濟、社會和交化的力量推動,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表達。 並且加入父權壓迫這個新角度,解剖男性對纏足的渴望並非源於性變態,而是與文化懷舊、地區競爭和男性特權主張等更大的擔憂有關。 12而貝維利·傑克遜(Jackson Beverley,1928年-2020年)的《Splendid Slippers:A Thousand Years of an Erotic Tradition》就着重以相片及圖片的形式,記錄和呈現纏足婦女的身體、生活及文化習俗,嘗試追尋纏足婦女的主體性。 13而在姚靈犀(1899年-1963年)的《採菲錄》14中紀錄了纏足源由、弓鞋研究、各地纏足狀況等大量珍貴史料,特別是對不纏足運動在二十年代後發展基本狀況,並對運動中出現的社會阻力現象和一些偏差行為也有所瞭解。 可以說是現今收集最多的中國婦女纏足史料。
上述所提及的並非本文引用的全部資料,因此在文章結尾附有「參考文獻」附錄。筆者已盡可能地收集與纏足的起源、晚清傳教士以及不同群體的觀點等相關主題的主要史料,以呈現歷史的完整面貌。然而,晚清時期的資料極為龐大,難以完全涵蓋所有細節,其中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明代著名學者湖應麟(1551年-1602年)曾經對纏足進行了「博考」,故他有著對纏足演進的明確見解:「如書籍之雕板,婦人之纏足,皆唐末五代始之,盛於宋,極於元,而又極盛于今。 二事顛末絕相類。纏足本閨帷瑣屑,故學者多忽之。」15 可見,纏足文化由南唐始。根據《道山新聞》載:
「後主作金蓮六尺,飾以寶物,令官娘以帛繞腳,纖小屈做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四旋有凌雲之體態。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鈿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端蓮,令官娘以帛繞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形,素襪舞雲中,迴旋有凌雲之態![]() 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16
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16
李後主李煜(937年—978年,為南唐的第三任和最後一任君主)為了讓窅娘的舞姿更輕盈好看而纏足,其他女子見狀也開始效仿。但剛開始的纏足僅僅限制在宮廷和貴族中流行,而平民家的婦女們並沒有纏足之說。究其原因,根據北宋詩人徐積(1028年-1103年)《詠蔡家婦》中:「但知勤四支,不知裹兩足。」可見,下層婦女因需要執行大量的勞動,而未有纏足的行為。後來,隨著文人們陸續在創作文學作品的時候,不斷反覆讚美纏足之美還將其作用大事宣揚,導致當時風尚漸以纖小為貴,如宋代文學家蘇軾(1037年—1101年)的《菩薩蠻·詠足》:「塗香莫惜蓮承步。長愁羅襪淩波去。只見舞回風,都無行處蹤。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躃困。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可見,就連偉大的文學家也對小腳有著特殊的喜好與讚揚,而這種頌揚導致了民間對纏足的普及,後來就逐漸成為評判女子美麗的重要標準,並將纏足的尺寸追求從感官上的「纖小細緻」,進一步發展到後來的極致「三寸金蓮」。
這種畸形習俗得以持續千年,並且尺寸愈來愈小,實在離不開當時父權社會深受男性至上的思想影響,而女性一直被灌需「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從者,從其教令)」的禮教,而「從」即是「從其教令」的意思,17 所以女子只能聽從、依附男性,開始漸漸失去地位。此後,男性喜愛小足,為了討好和取悅男性,女性不得不納入纏足習俗,使其日益盛行。當小腳成為社會流行的模式後,許多女性便開始由被動轉向主動的追求,而隨著傳統禮教觀念對女性束縛得日益加緊,如果說纏足一開始是女子為迎合社會普遍審美觀的自覺行為,那麼隨著男權社會逐漸發現了纏足的另一妙處,即可以通過這一方式束縛女性的活動範圍,達到拘管女子行動的目的。如在《清苑詩謠》中說「裹上腳、裹上腳,大門以外不許你走一圈」,就可以見到對於男性來說,女性就如同他們的私人物件,纏足不利於行走,自然容易看管,則纏足開始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走向規範性的壓力。
筆者根據整理現有資料,發現小腳的「美」不但是男性所普遍認可,也為廣大女性的外在需求,18 儘管這種習俗在現代看來是令人難以置信和無法理解的,但對當時的人來說卻是很自然、平常不過一件事情,因當時的他们對「美」的追求就是體現在小腳上。正如現在的婦女為了視角上讓小腿更「美」,她們會選擇去穿高跟鞋,而這個行為都是違背自然的現象,同樣是折傷筋骨,同樣是痛苦,這不就與千年前的婦女行為不謀而合嗎?可能再過幾百年後,後人也許會認為這些也是婦女的酷刑,也會認為是不可思義的行為吧!加上,在這種吃人的父權社會中,個別女子不願意忍痛纏足或沒有資格纏足都會成為社會的另類,她們不僅無法享受到纏足所帶來的便利,反而會受到社會的嘲弄,尤其是同性的諷刺。畢竟在女性尚是幼女時候根本不懂得纏足是何物、危害有多大的時候,她們的父母就為之選擇了追隨社會要求的道路,故在她們僅有的認知裡必定覺得纏足是件「好事」。並且一個家族如果大腳的妻子或者女兒出現,那麼她們家族裡的男子必定會受到周圍人的諷刺和挖苦,甚至整個家族受到他人的議論和恥笑,於是為了家族或男性的臉面,女性不得不忍痛選擇纏足。19 由此,我們可以確定纏足雖然表面上是女性的自覺行為,但事實上並不能由女性自由選擇。
此外,人們的嫁娶擇與這種審美觀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在奉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社會,士人的道德修養自然成為民間社會中最理想的「良婿」標準。由於許多士大夫、文人對纏足極盡讚美高歌,甚至出現了許多讚美小腳的文章、論著。漸漸地,小腳經過士大夫、文人們讚揚開始演變成為其擇偶的首要條件,使女子為了選擇到良好的丈夫,不得不迎合這一審美標準。自古以來,漢族的女性美學觀念都崇尚陰柔之美,認為女性應該柔弱如風中之柳,步履輕盈,而纏足恰好滿足了這種審美觀。林語堂(1895年—1976年)先生曾描述過女子纏足後的步態:「中國女子的纏足,完全地改變了女子的風采和步態,致使她們粉臀肥滿而向後凸出,其作用等於摩登姑娘穿高跟皮鞋,且產生了一種極拘謹纖婉的步態,使整個身軀形成弱不禁風,搖搖欲倒,以產生楚楚可憐的感覺」20 此感覺可以激發男性的保護慾,使人們想入非非,所以這種習俗在漢族中廣泛流傳,女性們認為不纏足就是一種恥辱,沒有資格做新娘,使她們誤以為小腳就等於擁有幸福,因此為了下一代幸福,母親不僅主動為女兒纏足,還要想盡辦法將女兒的腳纏得比別家女兒小,在這種循環下,更多婦女進入纏足的行列。儘管歷朝歷代都曾出現一些批評女子纏足的聲音,但纏足之風依舊愈演越烈,到清朝即使嚴明禁止纏足習俗仍然繼續。
從上述描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父權社會下,士大夫、文人審美日益走向畸形和病態化。纏足不僅成為了「美」「醜」的區別標誌,更是成為束縛婦女的一種手段,與其說這是為女性設立的道德標準,不如說是給女性戴上了「緊箍咒」,而纏足逐漸演化成封建教條的執行者,開始約束女性、維護貞操、取悅男子,使婦女變得無以自主從而必須完全依附於男子,成為他們的掌中玩物。雖然有些女性因追求美麗而選擇纏足,但當時的審美觀卻是完全構建在男性的主觀上,故此女性忍受錐「腳」之痛,一心想從纏小腳中收穫所謂的人生幸福,為自己謀求安身之地。然而,纏足卻使她們變得更加不幸,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進一步下降。因此,女性在這惡性循環中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直至鴉片戰爭後,伴隨著《北京條約》21、《黃埔條約》22、《天津條約》23等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各項被禁限的傳教活動相繼解除,傳教士來華傳教。當他們看到中國婦女的纏足行為後深感震驚和不解;有的以獵奇眼光來看待;有的則加以譏笑,不過。傳教士如英國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年—1905年)認為「纏足是華人風俗,相沿成風,與我教無關,可不必更增取厭之為難也。 」24畢竟,在他們看來,這僅僅只不過是中國的風俗,其任務是在中國傳播聖教,讓更多國人投入主的懷抱,其他的不必太在意。後來,經過深入了解,傳教士們意識到纏足與教會的關聯是相互的,纏足不僅僅危害婦女的身心健康,而且他們認為人類肉體和靈魂是上帝給予的,纏足的行為與基督教教義是相悖的。因而主張「廢弛纏足」,他們認為:
上帝創造世人,男女並重。凡有道之邦,即信上帝之真道者,其男女無不平等,無道之邦,即不信上帝之真道,而別有所謂一切道者,其男女無一平等。觀教化者,必觀其女人。無論男女手足皆同。今觀天下,除中國外,婦女均無纏足,可見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無二致,此古今之通義也25
最重要是女性纏足限制了她們走出家門到教會接受福音,「婦女既纏足,多不能赴稍遠之會堂聽道禮拜」26,那麼教徒人數就不能增加,這大大危害了他們在華傳教發展。故西洋傳教士除了傳教播道,並率先在中國提倡放足。27他們通過創辦報刊宣傳纏足之害、設立女校反纏足以及創立天足會團體反對纏足等方式宣導中國女性戒纏足,希望「爭取婦女歸主並最後引導全家歸主」28,由於中國婦女長期處於被壓制和束縛的狀態,她們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撫慰。基督教的博愛思想和對美好未來的勾畫正好能夠滿足她們的精神需求。因此,傳教士認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為基督教的發展對象。
隨著中國知識份子意識到國家的危機和衰退,他們開始倡導學習西方文化。維新派代表人物康有為(1858年—1927年)把中國纏足與西方各國不纏足兩行為作出對比,指出中國的纏足使人體弱而不堪,而西方列強因不纏足而身體強健。「試觀歐、美之人,體直氣壯,為其母不裹足,傳種易強也;回觀吾國之民,旭弱纖僂,為其母裹足,故傳種易弱也。」29 他們認為,纏足不僅僅是個人或家庭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大問題。如果任由中國婦女繼續纏足,「中國四萬萬人民,世世永永,傳此弱種」30,顯然纏足是「於保民非榮,於仁政大傷。」31所以纏足也成為他們變革的重要內容。為了推廣這一觀念,他們大力宣傳纏足的害處,詳細闡述戒除纏足的好處。受到來華傳教士的影響,他們積極創辦反纏足會和女子學校,並在社會上發起了反纏足的運動。這場運動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參與,進一步強化了反對纏足的觀念。
(一):創辦報刊
在鴉片戰爭前,來華傳教士就已經創辦了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份現代化中文報刊,其主要目的是「以闡揚基督教義為根本要務」32。由於該報刊未得到中國官方的認可,因此受到禁教政策的嚴格限制。為了避免被禁,傳教士開始與清政府建立良好的關係,並在報刊編輯上採取了一些適應中國情況,以及迎合中國人心理、思想和習慣的策略,例如使用基督教來解釋儒學,或者用儒學來論證基督教,從而讓中國人更容易接受基督教。
戰後,西方傳教士獲得了在華傳教和出版報刊的特權和立足點。因此,教會報刊迅速擴大,報刊的數量大幅增加。據統計,到1890年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在中國出版的報刊已達76種33。在這一時期,為了滿足中國人追求「師夷長技」和「西學為用」的需求,許多報刊大量介紹西方知識,將西學作為傳教的輔助手段。而當中的《萬國公報》是傳教士報刊中發行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最具社會影響力的一份刊物,其前身是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Andrew Young John William Allen,1836年—1907年)於1868年9月5日創辦的《中國教會新報》,並於1874年9月5日更名為《萬國公報》,該報刊涉及宗教、政治、經濟、社會風俗等多方面的內容,也是第一個開始關注纏足問題的中國近代報刊。創始人林樂知認為,纏足之俗是「為中國最惡之風俗,亦為中國漢人獨有之風俗,與政府無涉也。究之作淫巧殘形有百害無一利,未有如纏足之甚者。」34 因此,他公開探討中國女性的足部,討論是否應該戒除纏足或繼續保留,成為中國近代報刊倡導戒纏足的先聲。在《萬國公報》中發表的有關女性觀念的207篇文章中,論述反纏足觀點的文章共有43篇,佔比例約為20.7%,內容涉及纏足之因、纏足之害、戒纏足之法和放足之效等幾個方面。35(附錄二)
他們從個人、家庭、國家等三個層面進行分析。對於傳教士而言,纏足的最明顯危害是對身體造成傷害,「初纏也,痛必切骨,苦難名狀。或日夜呻吟,或坐臥不安,萬一因纏致潰,皮破肉爛,膿流血淋,偶爾失治,即成廢疾。」36此外,纏足女子走路姿態左右搖擺,縮肩駝背的,實在是難以評價為「美」。再者,纏足對女性行動的限制大大降低了她們的勞動能力,「步履不便,操業艱難,除中饋女紅外,他事非所能為」,37導致女性在經濟上無法獨立,只能依附於男性,增加男性的經濟壓力。更嚴重的是,「纏足會遺害於子孫萬代,且裹足之女子,嘗少走動,血氣不舒,易生疾病,產子艱難,其身多軟弱,故生子女亦少強壯」38這不但違背傳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思想,也與基督教教義不符。最後,傳教士將纏足的危害提升到國家層面,認為西方近代的進步,女性所作的貢獻是非常重要的。而纏足使得中國大部分女性幾乎變成了殘疾人,無法在社會生產中充分發揮作用,「今時婦女纏足,不能操作,致使男人而作女工,以此民用空乏而國計困窮也」,39成為中國衰退的主要原因。從中可以看出,傳教士強烈地將纏足的危害從個人提升到國家和民族的層面,就是要極力強調纏足為「中國最惡之風俗」。而消除這種不良風俗的方法是信仰上帝,「西方所得最有益之事,實為拜獨一之真神,即創造天下萬物之主宰...... 泰西文明教化之盛軌,其根源皆源於此」。40可見,他們利用報刊宣傳女性觀念的行為具有濃厚的功利性色彩,其想透過福音化中國的目的不言而諭,所以宣傳女性觀念的文章中,我們總是能或隱或顯的探尋到上帝的影子。
在戊戌維新時期,以維新派為代表的國人也掀起了自辦報刊的熱潮,希望透過報刊的力量使不纏足運動「更上一城樓」,力求破除這一惡習,實現女性的解放。維新派報刊在其中承擔了報導和宣傳的重任。其中最早的一份婦女報刊是創辦於1898年的《女學報》,全國各地陸續出版的婦女報刊約有33種。41 這些報刊不僅呼籲廣大女性戒除纏足,獲得身體自由的權利,還發表了了很多纏足對於女子傷害的文章,如《哀女子之行為不自由也(一名勸解纏詩)》一文,文中痛陳了纏足給女性帶來的傷害:「寂然不動木雞然,肉爛筋摧大可憐」,42在對纏足進行批判的同時,文中最後也提出了女子也當具有自由身的觀點。其次,學報還宣導女性勇敢擺脫依附男性的命運,反抗封建婚姻與家庭制度。
此外,《湘報》作為湖南的第一份同報,創辦於1898年3月7日,其風格大膽與激進,「此報既風行湖南,全省之人皆震動,學堂、演說會、不纏足會等到處回應。西洋人至呼為湖南獅子吼。」43《湘報》作為維新派的輿論陣地,發表了大量宣傳不纏足的文章,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是言論方面,刊載了許多抨擊纏足害處的文章;二是新聞報導方面,及時發佈湖南不纏足會的各種告示,報導各地不纏足會的相關情況;三是宣傳及廣告方面,主要是「印送不纏足歌」和「定做不纏足雲頭方式鞋」的廣告。
可見,無論是來華傳教士還是維新派,都深刻認識到報刊媒介的強大影響力,充分利用其在不纏足運動中的潛力。維新派一方面大力載文抨擊纏足之害,另一方面,積極報導與不纏足組織相關的各種消息,刊登章程、發佈告示,刊登題名,並頻繁地報導不纏足會的活動。這些努力使得許多進步的人士形成了反纏足的觀念,對纏足的陋習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不纏足的里程碑上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值得注意的是,在傳教士的話語體系中,中國女性的形象逐漸被塑造為苦難、悲慘、受困於桎梏的弱勢群體。這種形象釋放出一種信息,即女性需要依賴基督教文明才能獲得解放。傳教士將女性定義為「被拯救」的角色,而基督則成為「拯救者」,通過福音傳播,來「拯救」身處黑暗中的「異教」女性。此外,報刊也為天足會和女校的建立奠定了輿論基礎,並在宣傳反纏足和傳教活動中起到了重要的宣傳作用。
(二):創立女校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女子教育一直未被納入歷代學制系統,受到「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識字多致誨淫」等封建觀念的束縛,中國女性長期被局限在家庭角色中。傳統的女子教育圍繞《女誡》、《烈女傳》、《女孝經》、《閨範》以及《女範》之類的女教內容,其教育目的是培養封建女子成為「賢妻良母」,這與男子所接受的以改變社會地位和背負家族期望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中國古代女子長期缺乏系統的文化教育,處於一種蒙昧的狀態,這嚴重地阻礙了女子教育的發展。隨著法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了《黃埔條約》,其中規定:「凡法蘭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無論人數多寡,聽其租賃房屋及行棧貯貨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法蘭西人亦一體可以建造禮拜堂、醫人院、周即院、學房、墳地各項......倘有中國人將法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損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罰。」44在前期,外來傳教士為了傳播福音,透過報章、小冊子、通俗易懂的民謠以及傳單來宣揚(附錄三),然而不幸的是傳教士發現他們所發的宗教小冊子不是當廢品賣掉,就是用來包東西或者做鞋底,成效可謂微乎其微。加上他們發現,中國婦女佔人口的一半,幾乎都是文盲和纏足女子,除了社會地位驚人的低下,女人無法通過閱讀獲知教義更加影響他們傳播福音的速度,畢竟纏足無法到稍遠的教會聽道禮拜,如郭弼恩神父(Charles le Gobien ,1653年-1708年)的信中曾提到:「中國婦女從不走出家門,也不接待男士們的訪問…… 以至於她們最關心的是將腳纏小,自己剝奪自己行走的權利。」45
於是「教徒中,很多人明確信奉男女平等的原則,而且決心投人一場十字軍運動,以爭取中國男女平等的權利。」46傳教士意識到必須通過學校教育能培養出一批略具知識的基督教徒,「特基督教會之學校,初非專門之教育家所設立,其志並不在教育人才以促進教育之進步,乃欲以學校為一補助之物,以助其宣傳福音之業。」47以擴大基督教在中國人心中的影響。另一方面,通過高一級的學校教育培養中國未來的傳教者和精神領袖,將來對中國施加永久的和最有力的影響。此外,傳教士還意識到通過教會女子學校教女性教徒學字,「為各教堂的中國傳教士培養所謂的賢內助以便其結婚後能説明其夫做傳教的工作。」48 還可以增加信徒的人數。由此,為了更好傳播福音,傳教士走上了興女學、辦女校之路。
中國女子學校之設立,創始於一八二五年。是年一英國女子名格蘭脫(Miss Grant)者,始設一教授中國婦女之學校於新加坡,九年後又有若干英國婦女,組織一東方婦女教育促進會。閱三年,即一九三七年,此會中之一傳教士亞爾德西女士(Miss Aldersey)又設一教授中國女子之學校於爪哇。 一八四二年五口通商,亞爾德西女士乃赴寧波,閱兩年乃在該處設立中國最大之女學校焉。於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六零年之間,又有十一教會女學校,設立於五埠焉。49因各傳教士紛紛效仿故開創了「教會所至,女塾接軌」。的局面。(附錄四)
寧波教會女校的創立始於鴉片戰爭之後,當時由於「時風未開,甬人頗疑慮,裹足不前」50,加上戰爭在寧波人們心中留下的恥辱和痛苦,還沒有抹去,所以人們對於西方的事物十分恐懼,進而普遍抵制傳教士的傳教活動,而作為教會附屬物的寧波教會女校,當然也不太受歡迎。在女校招生之初,各種謠言四起,人們紛紛傳播她是魔鬼化身,能殺害親人再來算計他人的孩子;說她辦學是假,為把孩子騙取挖眼珠、煉藥水是真。51 因此,女校的招生一度陷入困境。除此之外,中國女子一直都是以家庭教育的方式來進行培養的,是不能進入學校學習的,西方傳教士打破了這一千年的傳統,為女性設立學校,這與中國的封建觀念和當時社會的思維背道而馳。因此招致了中國封建勢力的強烈反對;加上在舊時的中國社會裡,只有男孩才需要上學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也使得傳教士們開辦女學的行為在當地人看來是不可理喻的,所以一直有著「男孩上學還可以,至於女孩教她們何用」52 的質疑聲。即使有貧苦的女孩入學,也很快因輿論壓力而退學,如柯夫人創辦的長老會女塾最初就只有2名女學生。「學生入學的不多,而中途退學的還不少,女校尤為如此。」53可見,教會女校創辦初期,舉步維艱,於是傳教士們實行了免費教育,非但實行免費教育,甚至學校還對上學的女孩「倒貼」,「最初之時所能招到的學生,不過是使婢棄女及最窮苦者的女孩,因校中有衣食之供給,所以敢冒與洋人接近的危險。」54此時的女校並未有放足之說,畢竟因生源不足,即使「三寸金蓮」違背教徒們「崇尚天然」的思想,他們也對纏足女子一般不加禁止,畢竟在傳教士們看來要使中國福音化,就必須創造一個有利福音傳播的途徑,這時期的女性巧合地滿足了這個作用,她們大部分不是孤兒就是貧困者,處於無依無靠的情況下一旦接受基督的幫助,不但對宗教思想不反感,反而更加虔誠信奉,有利福音傳播。而這些女性也會成為教會女校的「門面」,向其他人展示,進入女校不但有學習的機會,還能擺脫女性地位低微的局面,與教會中的男性教徒平起平坐。
到了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中國掀起了一陣「西藝熱」。這一時期,大量的美國女傳教士隨著丈夫或是經由國家派遣,或是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到1890年,女傳教士佔到美國傳教士人數的60%。55這些女傳教士以「婦女工作為婦女」(Women's Work for Women)作為其傳教活動的核心動力。她們多數擁有高等學歷,來到中國後主要從事教育活動,實踐女性教導女性的原則,避免了「男女授受不親」的道德觀,除了使中國婦女更容易接受而進入女校外,她們還可以到女子家中進行教學和傳道,故「教會創辦的女子日校和寄宿學校達到120多所,學生2100多人。」56 在這種情況下,教會女校不再需要擔心生源問題,因此開始明確禁止纏足女子入學,甚至開設體育課程,讓女性漸漸通過體操課體會到不纏足和體育鍛煉帶來的身心愉悅。女學生對放足本能的抗拒到逐漸接受,紛紛放寬自己的腳,成為反纏足運動的主力軍。英國女傳教士林惠生夫人(Mrs D.B.Drake,?—?)稱「我們絕對不採取強制的和壓服方法,是因為我們希望她們這樣做是出於醒悟,而不僅為了取悅我們,或者看作是教會的一種習慣。57 可以看出,教會女校已成為反纏足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對於數千年以來被剝奪平等教育權的中國女性來說,是一次空前的解放,它結束了中國婦女「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腐觀念。然而,教會女校最基本的職責和使命仍然是以傳播基督教福音為主,其反纏足和辦學活動主要是為了吸引女性入教。因此,在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中,曾公開表示:「將來從教會學校畢業的男男女女,將會成為將中國轉變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的關鍵。」58
戊戌時期,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人士深刻認識到,只有使女性獲得知識,改變其封建的愚昧觀念,讓她們能夠走出家門,不再成為依附於男性的「吸食者」,才能真正成為國家的「出力者」。他們認為,這是改變當時國家虛弱和民族衰退現狀的關鍵。他們堅信,不能再讓女性在學習的年齡階段,得不到正確的教育而反而受到纏足之苦。
因此,在1898年5月31日,中國人自主創辦的第一所女學校在上海成立,最初名為「桂墅里女學會書塾」,後來更名為「中國女學堂」,又稱「經正女學」或「經氏女學」。該校是由上海電報局局長經元善(1840年—1903年)發起創辦,並得到了康有為、梁啟超(1873年—1929年)、嚴復(1854年—1921年)等維新人士的大力支持。59在他們看來:「今者欲救國,先救種,欲救種,先去其害種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如纏足乎」,以及「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因此,他們呼籲廣大女性勇敢地解除腳上的束縛,走出困住她們的四面牆,進入女校接受教育。
並將「禁止纏足」視為「興女學」的基本條件。在這一基礎上,維新人士在教會女校推動體育活動的推動下,在《萬國公報》上發表了名為《上海創設女學堂記》的文章,文中描述了中國女學堂首開女學風氣的盛況,並在介紹課程中強調:「兼及體操,針黹,琴學之類,以資質之高下,定課程之多寡」。60由此可見,維新人士放足運動中將女子的纏足提升到「強種保國」、「救亡圖存」方面的思想,為後來維新人士接受女子體育、宣導女子體育、重視女子體育與發展學校女子體育做了思想的鋪墊。而且1907年,清政府學部更頒布了《學部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61「以不纏足為第一要義」為目的。62女學堂章程中明文規定,明確規定:「女子纏足最為殘害肢體有乖體育之道,各學堂務一律禁除,立矯弊習」63將放足運動正式的引入了學校,還專門制定了反纏足的教科書,如1906年翰墨林書局印行的《勸不纏足淺說》與1909年學部圖書局印行的《初等小學堂五年完全科圖文教授書》中《戒纏足》課文。64
儘管中國社會中男女意識的差異逐漸減弱,男女平等的觀念也逐漸傳播,但教會女校無疑對中國傳統的男女角色模式產生了震撼。通過女校的教學,中國女性在身體、智力和精神上逐漸得到了解放。然而,這一切似乎都是基督教傳教士為傳播福音而採取的手段。如筆者在上文有提及過,教會創辦女校主要目的是培養女性成為福音工作者或助手,並樹立高雅的女性基督徒形象作為受福音影響的範例。因此,他們協助女性提升認知和反對纏足的目的並不是真正為了女性的利益,而是為了方便女性為教會和傳教士服務。事實上,除了必修的宗教課程外,女校的其他英文課本都是宣傳美國的強大,這些都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之上,旨在進一步「洗腦」女校學生使她們更加信奉教會。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女性的人生似乎已被預先安排,她們依然無法擺脫「工具人」的命運,只是主宰她們的從中國男性變成了傳教士。
此外,儘管基督教宣揚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也存在保守的觀念,例如認為女人出自男人的肋骨、女人被創造出來是為了協助男人作工等,女子需服從、支持丈夫,其生活的重心依舊在家庭之。65 這就與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具有相似之處,那麼在此等環境灌輸之下,傳教士連自己國家的女性都沒能從家庭中解救出來,談何為中國女性謀求平等,這一切的一切,這似乎只是為了更容易傳入中國的教義。
而維新人士也將鼓勵女性不纏足、進入學校學習視為一種救國策略。他們認為,如果女性不再纏足,就能更加努力地投入生產,為家庭和國家賺取更多收入,從而改善困境。然而,這並不是真正考慮到女性能夠獨立地承擔家庭和社會責任,而是男性在背後操縱一切。
(二):戒纏足會
1874年,麥嘉溫(Macgowan John,?—1922年)是倫敦宣教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員,其在廈門成立了中國的第一個勸禁纏足團體。為了使當地的人們更容易接受,故斟酌了當地的信仰和用語,將此命名為「Heavenly Foot Society」,雖然直譯為「天(賦)足會」,但其正式的中文會名為「戒纏足會」。 因麥嘉溫覺得雖然中國人對於上帝的概念並不熟悉,但他們所稱的「天」,也是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某些面向上類似於上帝。因為根據古聖先賢的教誨,人乃授命於天66。既然如此,女性也是同一股力量的產物,因此,小女孩天生的雙足,其優美的構造,同樣也是上天的傑作。67對於創戒纏足會此事,抱拙子(?-?)曾在報刊上評價:對於不纏足,「誨者雖諄諄,而聽者殊藐藐。牧師見信徒積習未肯卒改,心焉慮之,於是乃共設一會」68由於天足會作為一個自願的組織,沒有任何強迫性,入會與否完全是個人的自由,加上因教會性質,在宣傳反纏足時,還利用教會信徒對於上帝的信仰,言明「纏足之事,實僭上帝之權,犯罪匪輕」。因此,起初只有極少數有勇氣的婦女在麥氏的誓約書上簽字,根據麥克高回憶,天足會成立之時共有九人加人。隨後聲勢逐漸擴大,1879年,自願加人天足會的有80餘家。雖然廈門戒纏足在當時影響十分有限,但是對之後各地的戒纏足起了一個借鑑。
在1895年4月,以英國立德夫人(Alicia Bewicke,1845年-1926年)為首的外籍婦女聯合傳教士主動致函《萬國公報》諄囑譯登宣傳,「曩在上海,創立一會,取名天足,劢勸大家閨秀,兼及小家碧玉,務使白蓮萬朵,同放瑤池,用杜殘忍之機心,而完自然之本體」69。於是以上海為總會的「天足會」就此誕生。立德夫人明白中西方風俗的差異「是故西國有西國之風俗,中國有中國之風俗,以不可強人而就我也」70故該會以「普勸人不纏足」,使中國婦女「皆保有天然之足」為宗旨,並規定凡不願為女兒纏足者均可入會,並要求入會成員的孩子必須與不纏足的女子結婚,這個宗旨也成為了以後不同戒纏足會的基本規矩。為了推動廢除裹足運動,天足會會長立德夫人曾到中國南方展開了她的反對裹足之行,一方面勸教會以外的人愛其妻女,推動天足,另一方面向基督教會中人傳播天足資訊,「當辟門講道之時,兼勸華人,速解妻女之雙行纏,以廣愛人之量」71如天足會在修道院演說,雖有語言障礙,但她們也沒有放棄,而是選擇寫文章及聚會鼓勵女播道中人,肩負勸戒纏足之任。因女播道會中人,皆能用華語勸戒,更易於宣揚天足。72天足會初期「蓋各省所托辦事之人,多為教會牧師,傳教馀閒兼及此事,蓋甚便易」73可見立德夫人等西方寓華女性並不通中文,如果沒有傳教士的説明,根本無法深入更廣大的地區,所以她們必須借力於各地教會,通過他們的翻譯傳達反纏足理念,利用他們已有的社會網路,將天足會的宣傳著作和言論發放擴散到廣大群眾之中,傳教士則成為她們最為重要的喉舌,但是傳教士的任務是以傳道為主,故勸戒纏足為次。74不幸的是,回應者多屬各地之教會學校的學生和一些較為開明的地方官紳,而一般人民對於與教會或西人有關的事務,多採敬而遠之的態度,甚至漠視、破壞,在這種情況之下,天足會勸導放足變得難上加難。75根據立德夫人演說亦有留下文字記載「而十年前,不僅西人笑餘等以無成,即華人之中亦多譏餘等為狂妄者」。76
期後適逢甲午戰爭失敗,為了救國圖存,國人從國家大義的角度開始積極倡導廢除纏足的陋習。故不久即有人在《萬國公報》上讚文呼應說:「西人寓華已久,深知此為風俗之一大弊,故亟思設會以救之吾知中華不乏有識之士,亦必有著為論說,挽此頹風,與西人相為表者。使於餘年之惡習,竟有改革之一日。」77 於是,支持不纏足的中國士人也紛紛開始回應,最積極莫過於之前維新運動波及的地區,幾乎都成立了「不纏足會」、「戒纏足會」和「立天足會」組織,其中包括由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1865年—1898年)、唐才常(1867年—1900年)這樣的維新健將,都是不纏足運動的當然首領。而筆者認為各地這麼多人回應,除了國人對於救國的使命,也離不開前期立德夫人到處宣傳,才使天足思想在中國許多地方散播,讓不同地區的國人有一個基本的認知,後期才得到這麼多人的回應,使長期束縛中國女性的纏足陋習得以鬆動,故立德夫人在戒纏足上功力是不可抹滅的。康有為深知女性纏足純為了男性,了解纏足對於中國婚姻的重要性,「纏足不知所自始也,要而論之,其必起於汙君獨夫民賊賤丈夫。」78所以必須解決這個根深蒂固的婚姻問題:男子愿意娶不纏足的女子為妻,家庭愿意接受不纏足的媳妇;同時也必須讓女子的家庭相信,他們的「大腳」女兒也是能找到好人家作為歸宿的。故其會規定「凡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凡入會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纏足之女。凡入會人所生女子,其已經纏足者,如在八歲以下,須一律放解。如在九歲以上,不能放解者,須於會籍報明,方准其與會中人婚娶」外,更明確規定「使會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無所顧慮,庶幾流風漸廣,革此澆風。」79然而,雖然不纏足會希望透過纏足的根源來對症下藥,使纏足能自禁,但纏足問題是多源的,即使根源破壞,不是代表纏足問題就能解決。如湖南的不纏足會最初是由地方長官湖南學政徐仁鑄(1863年—1900年)、按察使黃遵憲(1848年—1905年)創辦的,贊助者為12位湖南籍地方紳士,會員約1060人,全是男性,而會裡雖有互通婚姻的規定,卻僅僅在官紳之間,而與貧困之家是決不能聯姻的。比如,有的不纏足會規定「入此會者專約士紳倡優,隸卒不與」80,顯示出會內仍然遵循的是封建時代的門當戶對的婚姻觀念。
再者,不纏足會或天足會表面上是一人入會,實際上是代表全家人加入,畢竟當時參加不纏足會的全部是男性會員,而男性在家裡有絕對的權力,畢竟這樣才有「管理家庭不再纏足之權」,81能夠保證女兒不纏足或不娶纏足女性作媳婦,這樣才能「實行家庭永遠不纏足之責任。」82而這個過程中,男子始終的角色是宣導、鼓吹、訂協定的,而真正被放足的婦女卻根本沒有參與的話語權。放足變成名曰為婦女做好事,但男權意識依舊強橫。即使有同時期婦女組織的不纏足團體,但卻寥寥無幾。而這些女性組成的不纏足會制定的章程只是宣傳放足的益處、如何放足以及放足之後所穿鞋樣式等,並沒有通婚的規定,可見婚姻大事也只是男性主導的,83不纏足運動的聲音也理所當然的變成男性中心主義的話語。這個時候,高喊興民權的維新志士顯然沒有真正意識到婦女的權利和地位問題,即使想到了也會心安理得地將之放在男人附庸的位置上。在《湘報》上,倡議不纏足的文章是與褒揚殉夫的烈婦之文排在一起的。84
中國女子的纏足起源於南唐,宋朝時逐漸興起,明清時期達到鼎盛,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這背後的原因複雜而多樣,包括審美觀念的推崇、禮教觀念的規制、擇偶標準的約束、上行下效的模仿以及文人騷客的宣揚和鼓吹。因此,「悠悠千載一金蓮」不僅束縛了中國女性的身體,更深層地束縛了她們的心靈,成為摧殘婦女肢體的行為。女子幼年纏足備受苦楚,長大成人後,雙足猶如釘上腳鐐,終生步履蹣跚,行走不便,嚴重影響了她們從事生產和日常生活。然而,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女性不能也不願說不,畢竟她們需要依附於男人,沒有選擇的權利。
鴉片戰爭的戰敗,西方新思潮的湧入中國,帶來了男女平等、天賦人權等理念。來華傳教士和西方婦女為首等外來力量,通過辦報、集會演說、開辦女子學堂、創設天足會等多種方式,力開展「召痼疾」、「戕生命」的廢纏足論宣傳與不纏足實踐活動。而國內有識之士受西方傳教士的影響,也產生禁纏足與發展學校女子體育的萌芽,並且以「強種保國」、「救亡圖存」的口號推動放足運動與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大家在反纏足的過程中相互影響、借鑑,這樣聲勢浩大且主題看起來像是解放婦女的運動,實際卻僅僅以此為旗號,為各自的陣營謀劃。
在外來的傳教士眼中,他們創立的報刊介紹了大量關於西方近代科學、文化、思想、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知識,主要是為了借助西學來輔助傳教,試圖透過西學的宣傳展示西方文明的優越性,以獲得中國人對傳教士的尊重和信任,進一步減少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抵觸情緒,使基督教在中國得到傳播和接受。他們最終的目的是要「從根本上改組中國文化」85 因此反對婦女纏足只是他們多種手段中的一項。其所建立的教會女校和天足會的初衷也是為了更好傳教而誕生的,畢竟千年來女性一直被纏足束縛,如果傳教士可以幫助她們解除束縛,女性就會感恩以及信任他們,教會就會吸收大量女性信徒,這樣不但可以為本地傳道準備同樣信仰基督教的妻子,還可以以女學生為渠道,從而與她們的家庭、鄰里建立起聯繫,吸引更多的信徒。再者,教會女校培養的學生可能會成為中國社會上「有頭有臉」的成功人士,「他們在將來要對中國同胞施加最巨大的和最有力的影響。」86畢竟,在悠久的中國歷史上,只有那些受過儒家教育的士人才能勝任國家重要的位置,如果「從受到儒家思想教育的人那裡奪取他們現在所佔有的地位,我們必須培養受過基督教和科學教育的人,使他們能夠勝過中國的舊士大夫。」87 可見,傳教士對於反纏足的付出只是出於佈道傳教之需要,為了能夠讓基督教會在中國紮根,改變中國人的思想、信仰而做出的舉動。
而維新人士雖然表面上站在女性的立場,協助她們拋棄束縛她們的千年纏足,卻有意無意地將纏足扣上了禍國罪名,把不纏足和國家強盛畫上等號,實際上是把「救亡圖存」的責任拋到婦女頭上去。儘管表面上是為了婦女著想,卻隱藏著濃厚的男性主義觀念。在這些提倡不纏足者的口吻裏,女性被牢固地定位在家和生育領域,通過興女學和女子體育提高中國女性知識和健康水準,目的不過是為了讓女性更好地服務家庭,去培養和教育後代,可見仍將女性定位在「賢妻良母」的範疇內,這顯然沒有擺脫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封建觀念模式。再者,對於這些提倡不纏足者來說,纏足本應是家庭內部事情,或者說是閨閣之內的事情,這些對於他們男人來說是有著絕對的權力和控制,畢竟女性是他們的財產之一。但是在外來傳教士們的集會中,纏足被赤裸裸地呈現在公眾面前,成為攻擊他們的利器。因此,為了自己的臉面,他們試圖將自己從纏足的源頭抹去,化身為鼓勵女性放足的支持者,卻忘了女性一開始纏足為的是「博君一笑」,從而得到他們的愛,而現在他們喜歡反足,女性同樣為了他們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他們依舊是不可一世的統治者,反纏足再一次變成他們手中的權力,女性的人生再次被他們主導。不纏足淪為一場遊戲,一場滿足男性控制權的遊戲,女性只能再次順從。
(一)書籍:
1.米憐:《基督教在華最初十年之回顧》(香港:馬六甲英華書院,1820年),頁10-23。
2.莊俞賀、聖鼐:《中國三十年之中國教育》(北京:商務印書館,1931年),頁111。
3.姚靈犀:《採菲錄》(天津:天津書局,1934年),頁10。
4.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319。
5.晴波、彭國興編校:《陳天華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頁15
6.英德貞:《施醫信錄纏足論》(台北:台灣華文書局印行,1968年),頁28-30。
7.林樂知:《論女俗為教化之標誌》(台北:華文書局影印合訂本,1968年),頁70-87。
8.陶宗儀:《南村綴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8。
9.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49。
10.高時良:《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頁26。
11.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36。
12.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上冊,頁19。
13.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頁15。
14.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頁557。
15.李楚材:《帝國主義侵華教育史料—教會教育》(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5。
16.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中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80。
17.虞和平編:《經元善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320。
18.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頁22。
19.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34。
20.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一卷,頁353。
21.劉廣京編:《劍橋晚清中國史上冊》(北京:對禮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627。
22.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96。
23.李又寧、張玉法合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臺灣:龍文出版社,1995年7月),下冊,頁875。
24.林語堂:《林語堂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頁3-5。
25.何曉夏 史靜寰:《教會學校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37。
26.閻光芬:《中國女子與女子教育》(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頁212。
27.花之安:《自西徂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116-119
28.秦軍校:《為小腳女人留影》(香港:中國圖書出版社,2005),頁2-12。
29.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五十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頁242。
30.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177。
31.張傳保修、陳訓正、馬瀛纂:《民國鄞縣通志·政教志》(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年),頁1122。
32.高洪興:《纏足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7年),頁52-324。
33.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1,〈玉杯〉第2,頁8。
34.丁韙良:《中國覺醒》(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頁228。
35.楊興梅:《身體之爭:近代中國反纏足的歷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頁89。
36.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37.Howard S Levy, Chinese Footbinding :The History of a Curious Erotic Custom(Gravesend: Bell Publishing,1966).
38.Ida Belle Lewis, The Education of Girls i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19).
39.Jackson Beverley, Splendid Slippers:A Thousand Years of an Erotic Tradition(Berlekey: Ten Speed Press,1997).
40.Jane Hunter,The Gospel of Gentility: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China(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41.John Macgowan, How England Saved China(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3).
42.Virginia Chui Tin Chau, The Anti-Footbinding Movement in China(1850-1912)(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65).
(二)期邗論文:
1.崔運武:〈近代中國教會女子教育淺析〉,《史學月刊》,第2期,(1988年2月),頁43-45。
2.閔傑:〈戊戌維新時期不纏足運動的區域、組織和措施〉,《貴州社會科學》第6期,(1993年6月),頁103。
3.夏晓红:〈清末的不纏足與女學堂〉,《中國文化》,第11期,(1995年6月),頁205。
4.趙新平:〈淺析清末不纏足運動巾的避向勢力〉,《忻州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2002年6月),頁76。
5.傅瓊、李浩:〈來華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的戒纏足思潮〉,《南方文物》,第1期,(2003年1月),頁97-98。
6.郝先中:〈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的放足運動〉,《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2004年1月),頁109-111。
7.趙新平:〈淺析清末不纏足運動巾的避向勢力〉,《忻州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2004年8月),頁76。
8.李穎:〈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的反纏足運動—以福建為中心〉,《東方論壇》,第4期,(2004年8月),頁96。
9.王海鵬:〈《萬國公報》與天足會〉,《貴州社會科學》,第1期,(2006年1月),頁137-138。
10.曹開菊:〈傳教士反對中國婦女纏足的主要方式〉,《法治與社會》,第1期,(2006年10月),頁205。
11.左芙蓉:〈纏足與近代中國婦女解放研究述評〉,《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8期,(2007年12月),頁24-27。
12.儀亞敏:〈教會女校的興辦及對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的影響〉,《才智學報》,第1期,(2008年11月),頁128。
13.張軍亭:〈20世紀初中國婦女參政運動興起探析〉,《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4期,(2008年7月),頁471。
14.劉人鋒:〈晚清婦女報刊誕生原因探析〉,《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8年8月),頁91-94。
15.郭彥華:〈淺析中國古代女子纏足〉,《中國校外教育:中旬》,第1期,(2010年10月),頁10。
16.卞昭:〈西方教會與近代中國女子教育的興起〉,《世界經濟與政治學報》,第7期,(2011年11月)頁14-15。
17.萬笑男:〈淺談纏足女性的主體意識〉,《蘭州教育學院學報》,第9期,(2012年12月),頁13。
18.周慶:〈論晚清女子教育對婦女解放的作用〉,《大學教育學報》,第9期,(2012年6月),頁37-38。
19.李叔君:〈女性身體與權力滲透:纏足在話語中的歷史呈現〉,《社會科學家學報》,第6期,(2012年6月),頁36-38。
20.蘇全有、游思靜:〈從詩歌看清末國人緣何反對纏足〉,《平頂山學院學報》,第4期,(2013年8月),頁26-27。
21.雷俊霞、祁凱麗:〈近代不纏足運動的啓示〉,《神州百家論壇》,第10期,(2013年2月),頁232。
22.張慧:〈纏足源起及至全盛過程中文人扮演的角色〉,《青春歲月〉,第4期,(2013年03月),頁380-382。
23.肖慶群:〈戊戌維新派女子體育論〉,《體育文化導刊),第1 1期,(2013年11月),頁135-136。
24.陳文聯、張夢:〈來華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的反纏足運動〉,《雲夢學邗》,
第2期,(2014年3月),頁52-55。
25.王以芳:〈兩種符號秩序的衝突———19世紀美國傳教士塑造的中美女性形象的比較研究〉,《貴州社會科學》,第5期,(2014年5月),頁147-150。
26.劉方瑋:〈康廣仁與上海不纏足會關係探析〉,《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9期(2014年9月),頁101-102。
27.玉金壯:〈辛亥革命派女子教育論〉,《體育文化導刊》,第6期,(2014年6月)頁174。
28.王美英:〈晚清的女子教育與女性意識的覺醒〉,《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2014年1月),頁127-128。
29.文善、恬楊、慧馨、張選惠:〈纏足與女性民族傳統體育〉,《體育科學進展》,第2期,(2014年5月),頁52-56。
30.郭輝:〈簡論清末時新小說中的纏足書寫〉,《文學與文化》,第4期,(2015年11月),頁63。
31.秦方:〈近代反纏足話語下的差異視角——以19世紀末天津天足會為中心的考察〉,《婦女研究論叢》,第03期,(2016年5月),頁63-70。
32.楊慧:〈近代中國教會女子教育與婦女解放〉,《北方論叢》,第6期,(2016年11月),頁73。
33.吳泉成:〈美國在華教會與近代中國女子教育〉,《高教學刊》,第24期,(2016年12月),頁249-250。
34.秦方:〈從幽閉到出走———清末民初女性困頓-解放話語形成及實踐〉,《婦女研究論叢》,第4期,(2017年7月),頁46-57。
35.李思思:〈教會女學與近代中國女子教育〉,《呂梁學院學報》,第5期(2017年10月),頁56-57。
36.李晨希:〈從被纏足婦女角度看近代反裹足、放足運動〉,《絲綢之路學版),第1期(2017年6月),頁35-36。
37.趙彥喬:〈傳教士女性啟蒙文學譯介與中國婦女現代啟蒙〉,《中國地質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7年11月),頁145- 149。
38.李文泰:〈鼓浪嶼在中國婦女解放事業中的作用探析—以馬約翰的「天足會」為例〉,《鼓浪嶼研究》,第2期(2018年08月),頁52-55。
39.吳敏:〈立德夫人與清末反纏足活動研究〉,《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學報》,第2期(2019年3月),頁46-48。
40.楊圓夢:〈基督教傳教士與近代中國女性陋俗文化變革〉,《西部學刊》,第9期(2019年5月),頁69-70。
41.張蓮波:〈晚清不纏足會的特點—會員之間子女互通婚姻〉,《天中學刊》,第3期(2019年6月),頁131-134。
42.尹翼婷:〈「他者」眼中的近代中國新女性——以英國聖公會女部傳教士為個案〉,《宗教學研究》,第1期(2022年3月),頁222-229。
(三)學位論文:
1.陳欣:《清末教會女校的創興及其影響研究》(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頁21-24。
2.郑素青:《美國傳教士與中國女子教育》(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頁21-24。
3.鄭武良:《戊戌時期維新派不纏足運動研究》(浙江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頁18-21。
4.秦奋:《清朝晚期至民國中期福州女子教育研究(1850-1937)》(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頁10-16。
5.曾繁花:《晚清女性身體問題研究—基於若干報刊的考察》,(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頁14-20。
6.趙萍 :《近代浙江教會女校研究》(寧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頁10-11。
7.周曉玲 :《近代來華傳教士報刊與中國女性觀念啟蒙》(遼寧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頁18-25。
8.聂卉:《1840-1911年英國女性来華遊記研究》(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2年),頁21-23。
9.賴海平:《清末社會改良活動——以《大公報》為中心考察(1902-1911)》(天津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頁10-16。
10.周曉玲:〈近代來華傳教士報刊與中國女性觀念啟蒙》,(遼寧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頁18-25。
11.黃媛:《身體的解放:太平天國蓄髮、放足令探析》(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頁21-24。
12.王美玲:《從纏足習俗看中國古代的女性角色》(哈爾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頁20-36。
13.張夢嬌:《清代廣東鄉村婦女纏足與康有為粤中不纏足會研究》(華南農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頁24-36。
14.陳婷:《清末女學堂和女學生身體(1895-1911》(浙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頁13-25。
15.任巧:《從晚清反女子纏足看中國女權的發生》(西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頁15-31。
16.任巧:《從晚清反女子纏足看中國女權的發生》(西南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頁15-31。
17.李敏:《晚清來華西方人視域下的中國婦女生存狀況》(內蒙古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頁21-43。
18.胡金環:《近代中國放足運動與學校女子體育發展的關係研究》,(曲阜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頁39-56。
19.劉言:《晚清婦女報刊反纏足報導中的女權主義視角研究(1898—1912)》(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頁34-50。
(四):報章
1.《救世當然之理》,《萬國公報》,1874年9月5日。
2.〈廈門戒纏足會〉,《萬國公報》,1879年3月22日。
3.〈教會聚集續記〉,《萬國公報》,1887年10月27日。
4.〈聞泰西婦女設天足會感而書此〉,《申報》,1895年5月4日。
5.〈戒纏足會敘〉,《時務報》,1896年12月1日。
6.〈戒纏足錄跋〉,《萬國公報》,1897年。
7.〈衛足會譜凡例〉,《湘學報》,1898年2月。
8.〈戒纏足論〉,《萬國公报》,1898年11月。
9.〈論中國變法之本務〉,《萬國公報》,1903年2月21日。
10.〈常州不纏足會章程〉,《嶺南女學新報》,1903年6月。
11.〈哀女子之行為不自由也(一名勸解纏詩)〉,《女學報(上海 1904)》,1904年。
12.〈南豐天足會章程〉,《警鐘日報》,1904年07月25日。
13.〈論纏足之害及其關係〉,《萬國公報》,1905年11月。
14.〈錦州勸戒纏足淺說〉,《萬國公報》,1905年。
15.〈學部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時報》,1907年3月28日。
16.〈勸戒纏足俗歌〉,《天足會報》,1907年,丁未夏季。
17.〈天足會緣起並開會辦事始末記要),《天足會報〉,光緒丁未夏季。
18.〈女學生之愛國運動〉,《晨報》,1919年5月8日。
19.〈婦女傳教工作十年匯義〉《和團研究會通訊》,1992年。
20.〈清末的天足會(1895-1906)〉,《國史館館刊復刊),1994年6月。
腳註 :
1.雷俊霞、祁凱麗:〈近代不纏足運動的啓示〉,《神州百家論壇》,第10期,(2013年月份缺),頁232。
2.黃媛:《身體的解放:太平天國蓄發、放足令探析》,蘇州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2年,頁21-23。
3.趙新平:〈淺析清末不纏足運動巾的避向勢力〉,《忻州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2004年8月),頁76。
4.秦軍校:《為小腳女人留影》(香港:中國圖書出版社,2005年),頁2-12。
5.Howard S Levy, Chinese Footbinding :The History of a Curious Erotic Custom (Gravesend: Bell Publishing,1966), 234.
6.高洪興:《纏足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7年)頁52-201。
7.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13.
8.高洪興:《纏足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7年),頁324。
9.Virginia Chui Tin Chau, The Anti-Footbinding Movement in China (1850-191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65), 32.
10.陳文聯、張夢:〈來華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的反纏足運動〉,《雲夢學邗》,第2期,(2014年3月),頁52-55。
11.傅瓊、李浩:〈來華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的戒纏足思潮〉,《南方文物》,第1期,(2003年月份缺),頁97-100。
12.秦軍校:《為小腳女人留影》,頁32。
13.Jackson Beverley, Splendid Slippers:A Thousand Years of an Erotic Tradition (Berlekey: Ten Speed Press, 1997), 32.
14.姚靈犀:《採菲錄》(天津:天津書局,1934年),頁10。
15.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49。
16.陶宗儀:《南村綴耕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58。
17.丁鼎:《儀禮‧喪服傳》(香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12。。
18.李穎:〈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的反纏足運動—以福建為中心〉,《東方論壇》,第4期(2004年8月),頁96。
19.趙新平:〈淺析清末不纏足運動巾的避向勢力〉,頁76。
20.林語堂:《林語堂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年),頁19。
21.《北京條約》是1860年大清於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後在北京分別與大英帝國、法蘭西第二帝國、俄羅斯帝國各自簽訂的戰敗條約。其中有一條條約就是允許西方傳教士到中國租買土地及興建教堂。
22.《黃埔條約》(法語:Traitéde Huangpu或Traitéde Whampoa)又稱《中法五口通商章程》,是法國與清朝簽訂的一個不平等條約。其中有一條條約就是法國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墳地。清政府有保護教堂的義務。
23.《天津條約》是清咸豐八年(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法國、俄國、美國強迫清政府在天津分別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其中有一條條約就是俄國東正教士人內地自由傳教。
24.〈教會聚集續記〉,《萬國公報》,18787年10月27日。
25.林樂知:《論女俗為教化之標誌》(台北:華文書局影印合訂本,1968年) ,頁54。
26.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840--1918) 》(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頁22 。
27.陳文、聯張夢:〈來華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的反纏足運動〉,《雲夢學邗》,第2期,( 2014年3月),頁52-55。
28.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中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80。
29.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上冊,頁336。
30.同上,頁336。
31.同上,頁336-337。
32.米憐:《基督教在華最初十年之回顧》(香港:馬六甲英華書院,1820年),頁10-23。
33.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上冊,頁19。
34.〈論中國變法之本務〉,《萬國公報》,1903年2月21日。
35.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中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一卷,頁353。
36.〈戒纏足論〉, 《萬國公报》,1898年11月。
37.〈論纏足之害及其關係〉,《萬國公報》,1905年11月。
38.花之安:《自西徂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卷2,頁116-119
39.〈厦門戒纏足會〉,《萬國公报》,1879年3月。
40.John Macgowan, How England Saved China(London: T. Fisher Unwin,1913),35-36.
41.劉人鋒:《晚清婦女報刊誕生原因探析》,《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第4期(2008年8月),頁91-92。
42.〈哀女子之行為不自由也(一名勸解纏詩)〉,《女學報(上海1904)》,1904年。
43.晴波、彭國興編校:《陳天華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頁15 。
44.高時良:《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26。
45. 朱靜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第1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頁244。
46.費正清:《劍橋晚清中國史上冊》(北京:對禮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627。
47.李楚材:《帝國主義侵華教育史料—教會教育》(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5。
48.同[46],頁241。
49.李楚材:《帝國主義侵華教育史資料》(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240。
50.張傳保修、陳訓正、馬瀛纂:《民國鄞縣通志·政教志》(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年),頁1122。
51.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177。
52.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96。
53.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頁557。
54.閻光芬:《中國女子與女子教育》(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頁212。
55.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13.
56.崔運武:〈近代中國教會女子教育淺析〉,《史學月刊》,第2期(1988年2月),頁43-45。
57.〈婦女傳教工作十年匯義〉《和團研究會通訊》,1992年。
58.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34。
59.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五十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頁242。
60.〈廣學會·上海創設女學堂記〉,《萬國公報》,1899年。
61.丁韙良:《中國覺醒》(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頁228。
62.虞和平編:《經元善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320。
63.〈學部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時報》,1907年3月28日。
64.楊興梅:《身體之爭:近代中國反纏足的歷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頁89。
65.尹翼婷:〈「他者」眼中的近代中國新女性—— 以英國聖公會女部傳教士為個案〉,《宗教學研究》,第1期(2022年3月),頁222-229。
66.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8。
67.John Macgowan, How England Saved China(London: T. Fisher Unwin,1913),28-29.
68.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臺灣:龍文出版社,1995年7月),下冊,頁837。
69.李又寧、張玉法合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頁875。
70.〈天足會緣起並開會辦事始末記要),《天足會報〉,光緒丁未夏季。
71.丁韙良:《中國覺醒》,第766頁。
72.丁韙良:《中國覺醒》,第75頁。
73.天足會緣起並開會辦事始末記要),《天足會報〉,光緒丁未夏季。
74.吳敏:〈立德夫人與清末反纏足活動研究〉,《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學報》,第2期,(2019年3月),頁49。
75.林秋敏: 〈清末的天足會(1895-1906)〉,《國史館館刊復刊),16期, (1994年6月),頁123。
76.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頁837。
77.〈聞泰西婦女設天足會感而書此〉,《申報》,1895年5月4日。
78.〈戒纏足會叙〉,《時務報》,1896年12月1日。
79.閔傑:〈戊戌維新時期不纏足運動的區域、組織和措施〉,《貴州社會科學》,第6期(1993年6月),頁103。
80.〈衛足會譜凡例〉,《湘學報》,1898年2月。
81.〈常州不纏足會章程〉,《嶺南女學新報》1903年4月。
82.〈南豐天足會章程〉,《警鐘日報》,1904年07月25日。
83.張蓮波:〈晚清不纏足會的特點:會員之間子女互通婚姻〉,《天中學刊》,第3期(2019年6月),頁134。
84.閔傑:〈戊戌維新時期不纏足運動的區域、組織和措施〉,頁103。
85.劉廣京編:《劍橋晚清中國史上冊》(北京:對禮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584。
86.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34。
87.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頁15。
附錄一:


附錄二: 《萬國公報》反纏足文章
|
篇名 |
作者 |
時間 |
時間 |
|
保師母與年會議論纏足信 |
|
1875-1 16 |
320卷 |
|
纏足傷仁 |
錢梅溪 |
1875 4 24 |
333卷 |
|
裹足證據 |
錢梅溪 |
1875 5 1 |
334卷 |
|
裹足證據(續) |
錢梅溪 |
1875 5 15 |
336卷 |
|
勸漢裝女子尊古制 |
|
1875 5 15 |
336卷 |
|
年規議定傳教事宜 |
|
1876 1 8 |
370卷 |
|
革裹足敝俗論 |
張吉六 |
1877 2 10 |
426卷 |
|
裹足論 |
|
1878 8 31 |
503卷 |
|
廈門戒纏足會 |
抱拙子 |
1879 3 22 |
531卷 |
|
勸誡纏足 |
抱拙子 |
1882 10 14 |
710卷 |
|
引家當道-聲放足理兼情 |
楊格非 |
1883 1 20 |
724卷
|
|
自西姐東(貴保原質論) |
花之安 |
1883 6 9 |
743卷
|
|
纏足論衍義 |
秀耀春 |
1889 5 |
4冊 |
|
勸誡纏足 |
抱拙子 |
1893 3 |
50冊 |
|
纏足兩說:匡謬、正俗 |
天足會閨秀 |
1895 6 |
77冊 |
|
愛物及人 |
林樂知 |
1895 1 |
72冊 |
|
天足會徵文啟 |
|
1895 6 |
77冊 |
|
辯忠篇(下) |
林樂知 |
1895 9 |
80冊 |
|
纏足論 |
賈復初 |
1896 8 |
91冊 |
|
衛足說 |
番禺愚變 |
1897 2 |
97冊 |
|
勸釋纏腳說(並跋) |
趙增澤潤琴氏 |
1897 4 |
99冊 |
|
戒纏足錄跋 |
孔令偉慧仲氏 |
1897 10 |
105冊 |
|
戒纏足叢說跋 |
蔡爾康 |
1898 4 |
111冊 |
|
纏足足論(並序) |
永嘉祥 |
1898 11 |
118冊 |
|
去惡俗說 |
|
1899 12 |
131冊 |
|
天足會陳詞 |
|
1900 2 |
133冊 |
|
勸誡纏足叢說 |
立德夫人 |
1900 7 |
138冊 |
|
天足旁論 |
馮守之、顧之省 |
1900 8 |
139冊 |
|
論中國變法之本務 |
林樂知 |
1903 2 |
169冊 |
|
澄海縣禁纏足約示 |
|
1903 12 |
179冊 |
|
直督袁慰帥勸不纏足文 |
袁世凱 |
1904 1 |
180冊 |
|
天足會興盛述聞 |
|
1904 5 |
184冊 |
|
成都天足會近狀 |
李德夫人 |
1904 7 |
186冊 |
|
天足會來信 |
|
1904 10 |
189冊 |
|
記天足會演說事 |
泰百里 |
1905 1 |
493冊 |
|
記天足會第二集 |
秦百里 |
1905 3 |
194冊 |
|
錦州勸誡纏足淺說 |
高國光 |
1905 8 |
199冊 |
|
論纏足之害及其關係 |
|
1905 11 |
202冊 |
|
廈門天足會約章敘論 |
|
1905 11 |
202冊 |
|
天足會上年第九次年報單 |
任保羅述 |
1906 3 |
206冊 |
|
天足會第十次之報告 |
任保羅譯 |
1906 12 |
215冊 |
|
天足會年會紀略 |
任保羅譯 |
1907 1 |
216冊 |
|
天足會第十次報告 |
任保羅譯 |
1907 2 |
217冊 |
|
天足會長在無錫上海大會紀略 |
任廷旭譯 |
1907 3 |
218冊 |
附錄三: 教會宣傳

附錄四: 早期教會女校(1844-1860)
|
年份 |
地址 |
校名 |
創辦機構、創辦人 |
備註 |
|
1844 |
寧波 |
寧波女塾 |
埃尔德赛 |
|
|
1844 |
香港 |
女子寄宿學校 |
浸禮會,叔未士夫人 |
|
|
1846 |
香港 |
英華女校 |
倫敦會 |
|
|
1847 |
廣州 |
女子寄宿學校 |
美國傳教士,哈巴夫人 |
|
|
1850 |
上海 |
裨文女塾 |
公理會, 裨治文夫人 |
後改上海市第九中學 |
|
1850 |
上海 |
女塾 |
浸禮會,碧架 |
|
|
1850 |
福州 |
福州女塾 |
美以美会,麦利和夫人 |
|
|
1851 |
上海 |
文紀女塾 |
美國傳教士,琼斯 |
後改聖瑪利亞女校 |
|
1851 |
香港 |
女塾 |
浸禮會,約翰夫人 |
|
|
1853 |
上海 |
明德女校 |
法國天主教 |
後改上海市蓬莱中学 |
|
1853 |
廣州 |
女子日校 |
長老會,哈巴安德 |
|
|
1854 |
福州 |
女童寄宿學塾 |
公理會,卢公明 |
後發展為文山女塾 |
|
1854 |
廣州 |
女子學塾 |
循道会,俾士夫人 |
|
|
1855 |
上海 |
女子日校 |
長老會 |
后并入裨文女塾 |
|
1855 |
上海 |
徐匯女校 |
法國天主教 |
後改上海市第四中學 |
|
1857 |
寧波 |
女子學校 |
長老會 |
將艾爾德賽所辦女塾併入 |
|
1859 |
福州 |
毓英女校 |
美以美會 |
|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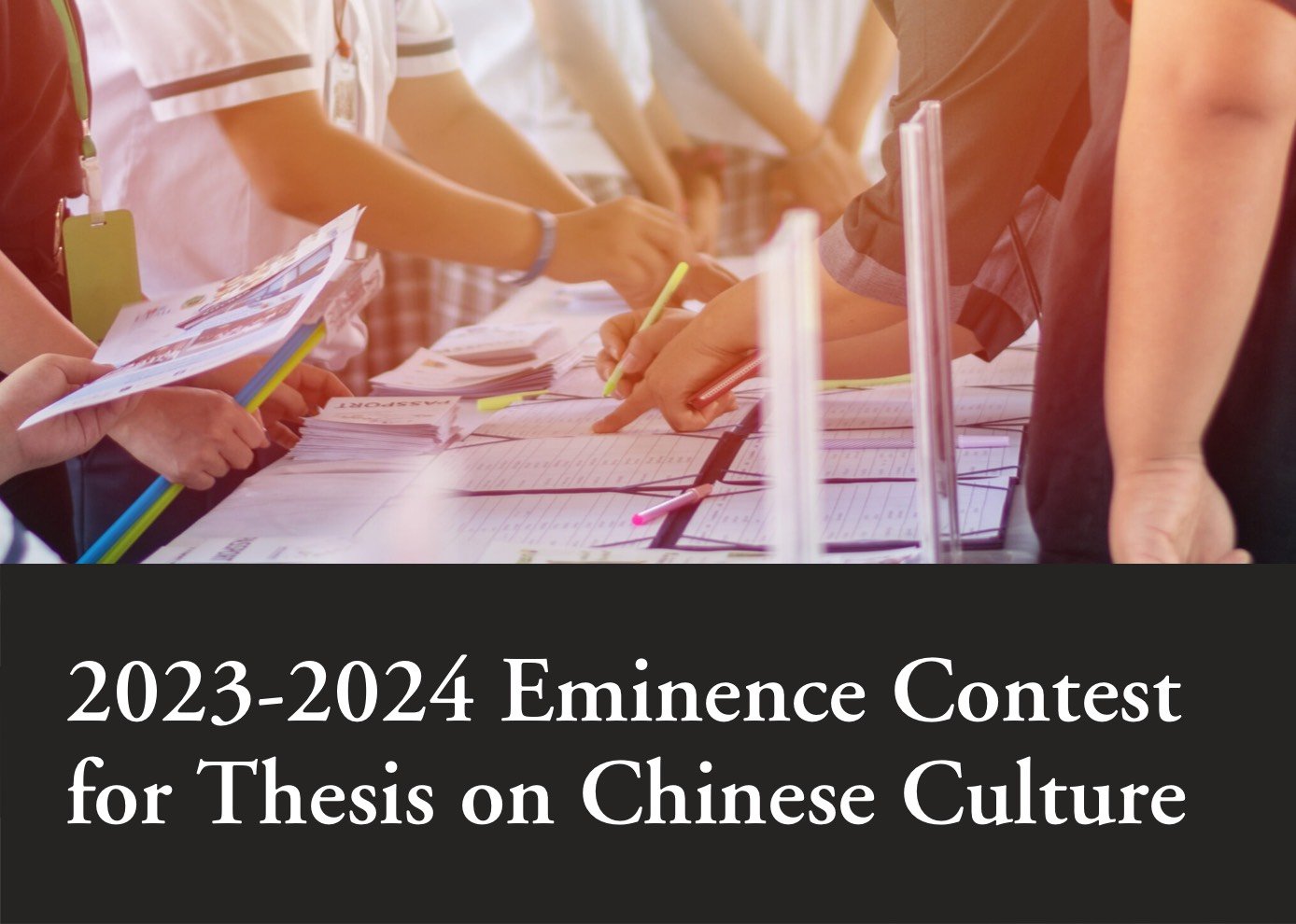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