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陸象山與朱熹研經讀書方法之異同
嚴婉姍
2024年4月19日
(一) 研究動機及目的
陸象山(1139-1193)和朱熹(1130-1200)都是宋代儒學代表人物,對於中國古代儒家經典的研究和教育有重要貢獻。雖同為儒者,二人對儒學的理解卻不盡相同。就此,二人曾多次以書信形式辯論,亦曾在鵝湖寺有過鵝湖之會。朱陸之辯,大抵源於各自對經書的了解和感悟之異處。所辯之事,既有宇宙論,亦有心性論。籠統而言,陸象山治心學而朱熹治理學。
本文認為,朱陸的思想分歧或許與自身的研經讀書方法有關。如:朱熹認 為讀書當求「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即泛泛而讀和廣泛而讀,不如精 讀某些作品並作精細的思考。就此,何謂精讀?朱熹謂:「今人讀書,務廣而 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1。不僅是 要精讀某些作品,而要求「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如此讀書過程,必是 刨根究底,講究對文字字義的理解;至於陸象山,則認為「大抵讀書訓詁既通 之后,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2,當內容、思想、價值大抵明白後,隱晦 不明的內容只須平常心對待,不用刻意揣摩。又言:「或未有通曉處,姑缺之 無害」,與「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大相逕庭。因二人對研經讀書方法的不同,衍生出不同的思想傾向。朱熹苦心為六經注釋,陸象山則「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兩人對著書態度因研經讀書方法的不同而有分歧;甚至,朱熹與陸象山相互批評對方「支離」和「易簡」,也可以從其研經讀書方法找到原因。前人多從陸朱心性論、宇宙論、工夫論分析其異同,卻較少探討二人讀書方法的異同。發前人之未發,這是本文的研究動機及目的。
(二)文獻回顧
前人對於朱熹及陸象山研經讀書的研究主要有三個角度。大多數學者研究朱熹「道問學」及陸象山「尊德性」之間的差異,指出朱陸之辨的主要爭論乃德智 之關係及相關的問題,亦即是學問與道德二者孰先孰後、孰輕孰重的討論。如張 岱年先生在《思想·文化·道德》中指出朱熹兼重問學與德性,提倡「格物窮理」, 而陸象山則講求「尊德性」,而不注重對於事物的認識。3陳鐘凡先生認為朱子與 象山的學術乃「經驗直覺,各趨一途,屹立並峙於南宋時期」而成為當時的兩大學派 。4
另外,有學者研究朱陸的教學實踐和指導學生讀書學習的經驗,從而分析出朱陸的讀書法之異同。劉天宇先生指朱子學生對朱熹讀書方法的概括為「循序漸 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而陸九淵的讀書 方法並沒有像朱子讀書法一樣形成統一的體系,後人對其讀書法的總結主要為 「循序漸進、熟讀精思、忠於原意、勇於存疑、辯論有進、實事實學」。劉先生 在文中亦對朱陸讀書方法進行比較,總結其異在於立志、心態、目的、辯論及師 友互助;其同在於二者皆強調讀書要循序漸進、熟讀精思、忠於原文之意。5
學界對於朱熹及陸象山讀書的原因亦多有論述,學界普遍認為朱子對於經典 及聖人之旨的態度是非常崇敬的,因此其讀書及對經典詮釋的態度是積極的。錢 穆在〈朱子論讀書法〉中指:「朱子教人讀書法,平實周詳,初視若大愚大拙,實 啟大巧大智之鍵。」更從「心」的角度進一步提出: 「此書乃朱子教人讀書最大 理據所在。我心與聖賢心本無二致,聖賢之心見於方策,我之讀書,正為由書以 求聖賢之心,亦不啻自求我心也。」錢先生指朱熹認為一般人之「心」與聖賢之 「心」是一樣的,而聖賢之心的表現被記錄於典籍之中,讀書是追求聖賢之心的 過程,亦是「明己心」的功夫。錢先生的觀點是將朱熹對於人心、聖人之意及經 典形成「同一性」的關係,因此追求成德之學是朱熹讀書的原因,亦是朱熹提倡 讀書的依據。6黃信二在〈明體達用:評象山心性論對其讀書方法之影響〉中評陸 象山以「心」為本,引象山之言「所貴乎學者,為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來說 明其讀書的原因及目的皆是為了「盡此心」,「盡心」是讀書的務本之道,而讀書 亦應該有義利之辯,學者在讀書前應確立自己追求「義理」的目標,因為「人之 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7
最後,亦有學者著重研究朱子「性即理」及陸象山「心即理」的主張對其讀 書方法的影響。馮友蘭先生指出朱熹支持程伊川說的「性即理」,陸象山卻支持 「心即理」,此一字之差存在著兩個學派的根本分歧。8張立文先生則認為朱陸的 世界觀與方法論與其「為學之方」密不可分9,朱熹強調「理」作為「客觀」精神 的主體,因此傾向於「唯理論」;陸九淵則強調本體與主體的結合,傾向於 「唯 心論」。而由於二者對於「心」及「理」理解上存在差異,導致他們的哲學體系 有不同見解。10而朱熹與陸象山在讀書方法上有一定差異,因此在思想上亦必定 產生分歧。
(三) 研究方法
本文擬以二人的研經讀書方法為研究核心,探究其中異同。既然論及異同,必先從陸朱個別的讀書方法論述。此一部分將引二人的語錄入手,輔以因讀書感 悟而有的詩作,研究其閱讀心得。再將論題的視點展開,略談二人因思想形態的 異同而讀書方法形成上的異同。
(一)宋明理學的時代背景
朱熹與陸象山乃同時期的人,要了解他們的哲學觀,必須從當時的時代背景
入手,因為哲學往往是按照當時的時代與社會而產生的。《宋史·道學傳》:「文王、 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 憲章,刪《詩》,修《春秋》,贊《易》、《象》,討論《墳》、《典》,期便五三聖人 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 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 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可見宋代理學興起的原因是為了重 建「五三聖人之道」,此「道」就是儒家之道,此道之所以要被重樹,主要原因 是唐末宋初處於長期戰爭狀態,不同民族的文化與佛、道兩家的思想興盛而導致 民眾價值觀混亂,而儒家倫與理道德觀念則能重建宋人的價值與倫理世界,因此 宋代儒學家皆致力於研究、確立和弘揚儒家倫理綱常及道德形上學,而朱熹與陸 象山的研究範疇也是由此而展開。
(二)朱熹的思想淵源
朱熹的思想主要繼承了二程,亦即程明道、程伊川,但更接近於程伊川。朱
熹師承李侗,李侗是羅豫章門人,羅豫章則是伊川門人,因此在學術淵源這方面, 朱熹主要沿襲了程伊川的思想。二程在學術上的差異在於對於「心」及「理」的 不同理解,程明道主張「唯心」,認同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程伊川則主張 「唯理」,指出「格物窮理」的重要性。朱熹極度讚揚程伊川的「為學之方」, 更誇讚其學術有孟子不及之處。朱熹云:「明道可比顏子 。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朱熹語類》卷九十三)11對於程伊川「性即理」的學說,朱熹更是讚不絕口。《二程集》中記載了 程伊川回答學生「性如何」的提問,其答案為「性即理也。 所謂理,性是也。 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12朱熹言「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 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朱熹語類》卷九十三)13朱熹認為「性即理」為儒家道德之所以存在的可能及必要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據。14朱熹的「性」是指人的本性或天性,「理」則是指天理,性具有理的特質,也就說人具備向善條件,但人有「氣質之性」,因此要通過學習及道德實踐來摒除內心的雜念,以達到聖人的境界。程伊川亦言 格物致知,朱熹受其學說的影響,肯定了「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的觀點。程伊 川提出的「今日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有支離、繁瑣之嫌,因為今日所格 之物之理與明日所格之物之理不一定存在聯繫,因此程伊川亦提出「須是今日格 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二程遺書》十八)只要 在不同事情上都理解通透,並且所格之物累積得夠多,總會找到物與物之間的聯 繫從而貫通知識。朱熹肯定二程的觀點,指「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 是零零碎碎湊合起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朱子語類》卷十八)因此,如 若能在認知層面上貫通不同事情,便能在實踐層面上舉一反三。
(三)陸象山的思想淵源
象山在學術淵源上指自己是「自得」、「自成」、「自道」,不依靠任何「師友載籍」(《陸九淵集》卷三十五)。而其在象山《語錄》中解釋「自得」為「因讀《孟子》而自得之。」15由此可見,陸象山的思想乃繼承孟子而來。陸象山的學生及當時的文人對於其與孟子的關係亦有相關論述,如陸象山大弟子楊簡曾曰:「孔孟既沒,日以湮微。賴我先生,主蒙正學。」16其指在孔孟之後,只有陸九淵能延續孔孟的儒家正統思想。又如王陽明在《象山文集》序中曾指出:「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17 其直指陸九淵的學問也就是孟子的學問。王陽明還說:「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 其大本大原,斷非余子所及也」18,在象山學說繼承自孟子之學方面,牟宗三歸 納出六點:「辨志」、「先立其大」、「明本心」、「心即理」、「簡易」、「存 養」。「辨志」延伸自孟子所言的「士尚志」及孔孟的「義利之辨」,指人應該 行仁義之舉,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先立其大」則源自孟子的「大體小體」之 辨,強調「心」對於行事的主導性,「明本心」源於孟子提出的「四端之心」, 即時惻隱、羞惡、辭讓與是非之心,而人皆有此四端之心,為性善論奠定基礎, 「心即理」與「理義悅心」、「心之所同然」、「仁義內在」有關,以此作為人性本善的依據;「簡易」則與孟子說的「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的精神相關,指天下間的道理其實就在眼前, 解決困難也不需要使用困難的方法,而尋求學問的方法就是把失去的本心尋回,; 而「存養」是孟子所言的「操則存,舍則亡」、「存其心,養其性」,「盡心」、 「知性」後便能「知天」,明白天道。以上六點即是「主體」,亦即是儒家所說 的「心性」,以及奠基於主體的「工夫實踐」。此主體及其實踐的內容是基於《孟 子》思路的「簡易」。 19
由此可見,陸象山的思想與孟子相似度極高,亦是繼承了孟子的思想。孟子 主張「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特別強調「自得」。陸象山承繼了此說法,並以「好 學」來加以解釋,進一步詮釋孟子之學問。九淵曾曰:「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 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 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20 九淵指出如果只主張自得便會有楊子之患(因行利己主義而迷失方向,最終一事無成),而只注重力行便會有墨子之患(墨子 贊成兼愛,而兼愛則有求利的目的),楊墨二人的行為與儒家典籍《中庸》、《孟 子》的主張有差異。21九淵亦曰:「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辨。自謂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22,指出博學與讀書自得並不相衝,如若為了追求 自得而排斥讀書則不是學者該有的讀書原則。由此可見,九淵不僅接受並承襲孟 子自得之說,並以好學之說來加以補充。九淵對孟子的思想加以解釋及補充,使 儒學的讀書原則更具全面性。
(一)格物致知及累積貫通
朱子強調,讀書是一個非常重要且綜合的過程,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他 認為,讀書的目的在於安頓自己的生命,因此讀書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只有通 過讀書,我們才能對抗存在中的種種困難,如微小而繁瑣的細節或人性中的私慾 及「惡」。經典書籍被視為「聖顯」,只有通過讀書,我們才能與聖人的智慧相遇, 並將其與我們自己的理解融合為一。然而,朱子指出,讀書過程能被單獨拆分為 不同的功夫,學習者需要專注於經典文本,進行多層次的閱讀,同時也需要在心 態上「切己」,以親身體驗、感受和觀察所讀之書的內容。 格物致知是朱熹思想重要的一環,而讀書方法也能夠在此思想下呈現。朱熹 注《大學》第一章中的八德目,並釋格物、致知為「致,推極也;知,猶識也。 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其極處無不到。」23 於朱熹而言,格物是「窮至事物之理而無不到」,致知是「推極吾心之知而無不盡」。「窮至事物之理」,是要將物與物背後的理窮格出來,於 朱熹而言,物必有其可窮之理,故曰「事事都有個極致之理」。而所格之物的範 疇,朱子曾說:「精粗大小,都要格它,久而會通」。無論物的「精粗大小」,亦 可格之。萬物皆有理可格,這是從理論層面言。但實際上,物與物之間有可貫通 之理,故曰:「格物不必窮盡天下之物......今若於一草一木上理會,有甚了期......徒 欲泛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格物,將物之理廣 泛普及地格至,即謂「無不到」。
研讀書籍,自然也是格物的一種。朱熹說,「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 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文字、語言、處事也都是物,因此有 其理可格。既是物,亦即有其貫通之理。累積及貫通是格物窮理而致知的重要過 程。知識也是累積的過程。格物以後便可致知。將廣泛普及地格至之理,盡在吾 人之心之知,是為「致知」。從生活獲得的經驗、書本讀到的知識,都是格物的 內容,在「窮至事物之理」的工夫後,便可「推極吾心之知而無不盡」。宋儒談 「知」,可就「德性之知」及「見聞之知」(借橫渠語)而言。德性之知,是孟子 所謂的「良知」,不需後天學習而得,存乎吾人心性之善,此天道性命相貫通之 義理依據。吾人只需破除遮蔽良心的物,便得此理之清澄。至於見聞之知,是透 過經驗、閱讀而得的知識。本文專就讀書方法而言,便須說明格物致知如何達致 見聞之知。朱熹說:「書之當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欲 其無不通也」,上文說到讀書也是格物,也如格物之理一樣可以貫通而無不到。 可見,格物的過程固然令到吾人的見聞之知增加。至於德性之知,因致知的知, 更著重在德性層面。如此,便須從致知之後的工夫來說。研經讀書,不僅需要文 字知識,更需要挑選記載聖賢思想的典籍,從中學習聖人之道。
朱熹曾論及「格物致知」具體方法,他的學生曾問如果遇到「錯疑似處」的 情況該如何「格物」,朱熹回答在此等情況下是不可能一次解決所有障礙,而是 首先需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然後「就裏面旋旋做細」,先從問 題的總體來看,接著先選擇理解了第一層較淺易的事理後,再去了解下一個層次 較深的事理,層層遞進,直到完全明白,才能達到極致,而這些步驟需要「博學 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才能完成。24
(二)誠意
除了累積貫通之外,朱熹強調「誠意」在格物致知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說過 「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格物致知是誠意的前提,通過格物致知,人們 能夠「明理」,並在應對事物時表現出真誠的態度。朱熹認為「誠」意味著真實 和真實性,「誠意」是內心真情的表達,而不是為了讓他人看到而刻意製造的「意」。 朱熹對「誠意」有許多論述,比如他曾說要使意念真誠,就必須先獲得真知,否 則就無法真正把握善惡的實際,所以要真誠地表達自己的意念,首先要掌握真正的知識。25他還說過在經歷物質的格物和真正獲得知識之後,誠意已經達到了八 九分之九。只是還需要在更高的層面上反省,就像用兵對抗敵人一樣,即使敵人 已經被消滅,仍然可能有一些微小的隱藏威脅,需要再次搜索才能找到。26「誠 意」使人在讀書後可以達到德性之知,而但是在格物的過程中則一定會涉及部分 的見聞之知。由此可見,朱熹對「誠意」是相當重視的。
從「格物致知」到「誠意」,朱熹嚴格依照《大學》的次第功夫,他曾言「《大 學》首三句說一箇體統,用力處卻在致知、格物。」27強調「格物致知」是《大 學》提出的重點,亦是功夫的發端之處,必須要在這一步將正確方向確定下來, 才能成事。朱熹曾言「誠只是實。雖是意誠,然心之所發有不中節處,依舊未是 正。亦不必如此致疑,大要只在致知格物上」如果心中不能完全達到「誠意」, 此時只需要在「格物致知」上下更多功夫便可,而人不能在「格物致知」一事莽 撞,否則會導致「見得似小,其病卻大」,若想修身而達到德行,則必須要在「格 物致知」上下功夫。朱熹隨後舉出一個譬喻,「譬如適臨安府,路頭一正,著起 草鞋,便會到。未須問所過州縣那箇在前,那箇在後,那箇是繁盛,那箇是荒索。」 28此比喻是為了說明一旦訂立了學習的目標,「格物致知」便是首要事情,這樣便 能一步一步朝著該目標前進,不需要對外界事情多加關注。
(一)發明本心
宋代學者對於「心」的理解分為有三種,分別是具有「生理功能與作用」的心、具有「心理知覺作用」的心及具備「有倫理道德品性」的心。而理學家們所講的「心」經常是指「有知覺之心」和「具有道德品性之心。」29陸象山曾言:「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30陸象山繼承孟子的學說,二者所言之心相同,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這是人與生俱來的心,也是孟子奠定性善論的基礎。陸九淵曾說關有關本心的言論:「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31指所有人的本心是一樣的,凡人之本心與聖人之本心並無差異,而此「心」是無不善的,但本心有時候會受外物蒙蔽而迷失,因此需要將本心恢復到最原始的狀態。陸九淵的「發明本心」,即「復其本心」,他曾多次在其文集中提及,如「本心若未發明,終然無益」又說:「復,是本心的復處。」32所以「發明本心」是象山學文的開端,也是陸象山心學的重點。33對於「發明本心」與讀書之間的關像,陸象山明言「孟子日,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人唯不立乎大者,故為小者所奪,以叛乎此理,而與天地不相似,誠能立乎其大者,則區區詩文之習,何足以汨沒尊兄乎。」34彭永捷先生認為陸九淵此言的意思是:「立乎其大就是樹立道德的主體意識或尊德樂道之心;先立乎其大就是要樹立與發揮心的主宰作用。」35一旦樹立此意識,學習知識和讀書都會變得簡單起來。陸象山曾以讀書與作文之間的關係來解釋「發明本心」是教育的本質。36讀書不一定是為了寫作文,但是讀書的結果就是會寫作文,在這個情況底下,讀書是「本」,寫作文是「末」,讀書的初衷不該被「末」影響。在陸象山心中,「發明本心」就是「本」,因此他說:「變本心以為主宰,既得本心,從此涵養,使日月光明。」37一切教育的目的都是為了讓學生擁有自覺的道德意識 。
(二)格物
陸九淵的「格物」與朱熹的「格物」不一樣,朱熹是為了窮理,而陸九淵則是為了「正心」及「明理」。象山曾說如果讀書只鑽研後人為典籍寫的注邊就說 自己明白了聖人所言的道理,就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 出便弟」,藉此來說明沒必要苦心鑽研每一個注,否則只會加重自己的負擔。陸 九淵提醒學者讀書如「倚於一說一行」,否則會「各以其私說而傅於近似之言者」 38,要求讀書應該追求學問的真實性,讀書不能只取「孔子一句」或 「孟子一句」, 減低曲解典籍原文之意思的機會,亦避免引用典籍原文之人失其本意。九淵在此 部分以繼承了孟子的基本立場,堅持認為讀書時應避免對原文的錯誤理解。另外, 陸象山強調不能盲目相信書本,閱讀書本時應該抱有懷疑的態度,並在學習的過39 程中學會明辨真偽,他曾說:「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 他亦言「苟不明於理,而惟書之信,幸而取其真者也;如其偽而取之,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者矣」40此言 強調了明理對於讀書的重要性,如果一個人能明理及理性判斷,則能分辨書中的 真偽,而如果一個人缺乏明理的能力,則會學習了錯誤的知識。此明理則是「發 明本心」中的一環,只有「發明本心」後,才能明理、辨志,分析書本中的知識 是否正確。陸象山的學問主要是要求人能反求諸心,以引起讀者回應之實感,該實感是每人皆有的本心,所以為學的必要條件不是學習經驗知識,象山並不以讀 書為第一義工夫,而認為本心未明而讀書,反會蔽塞精神。41
(一)支離及易簡——讀書方法的比較
淳熙二年五月,朱熹與陸象山在鵝湖會面,各自抒發對儒學及讀書不同方面的觀點。朱陸的爭論點主要在於是否需要讀書。朱子認為人若不讀書,就不會明 理,亦無法察覺自己的過失或著缺陷。因此朱熹認為讀書是認識理的必要途徑。 而陸九淵則不反對人讀書,他本人也鑽研學術,但發明本心才是陸象山學術的重 心,聖賢之學的重點在於明白本心,讀書是達到此目的的方法。朱子卻指不讀書 就講本心,是不尊重學問、不尊重聖賢的行為。42如此看來,朱陸對於讀書皆抱 持正面態度,亦沒有一方認為讀書是不重要的,而朱熹與陸象山在讀書方法上的 差異主要是於對知識與經典的該從何下手的工夫上。在讀書方法上,朱熹批評陸 象山「易簡」,陸象山則批評朱熹「支離」,更寫詩寄給朱熹,諷刺道「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43 (《鵝湖和教授兄韻母》)。上文提到陸九淵引孟子「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之言,此意思是讀書人應該廣泛地閱讀及學習, 並且詳盡地解釋學問,但所有學問都得回歸到簡約的境界,亦即是陸象山說的易簡。
陸象山主張在博覽群書前應該先「發明本心」,而朱熹則認為博覽群書應該是第一步。陸象山云:「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概使其本常重,不為末所累。」 44他明言他的教育重視「本」,即是「本
心」,希望學生不被「末」(讀書及其他事情)所影響,更在學生問該如何格物時 回答「萬物皆備與我,只要明理。」45但其實陸象山並不否認博學的重要性,他 曾教導其學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為?是不當為。」 46可見九淵對於「先知後行」的態度是支持的,必須要先讀書,再有所行動,而「先知後行」是上文提到「末」的一部分, 受「本心」制約,陸象山的為學順序是「本心」第一,「博學」第二,「力行」最後。
朱熹認為陸九淵先明本心的讀書方法是「上達而下學」,而朱熹本人的讀書 方法則是「下學而上達」。所謂「下學」便是學習知識,而「上達」則是達到聖 人的境界。朱熹指聖人教導人的時候,基本都是教導「下學事」,幾乎不提「上 達事」,因為只有學會了下學之事才能上達,因此朱熹曾言「格物、致知,是極粗底事;『天命之謂性』,是極精底事。但致知、格物,便是那『天命之謂性』底 事。下等事,便是上等工夫。」47,他更用耕田一事來比喻讀書的先後次序,指 如果不曾種下種子和努力耕耘,就不可能結出果實,藉此來說明「下學」是「上達」的前提,而在「下學」的範疇中,亦包含著貫通功夫,他曾言「一以貫之」, 此「一」就是貫穿銅錢的繩索,而「下學」就是銅錢,要同時擁有繩索和銅錢才 能將他們串連起來,48也就是說要不斷格物並將所學到的知識融會貫通。朱熹曾 批評陸九淵在不讀書的情況下能「發明本心」而有所覺悟是不真確的,因為所謂 的覺悟並不是基於知識的累積,而是出於個人的思想的產物,此種覺悟並非絕對 正確的。
在「下學而上達」及「上達而下學」方面,不難看出朱熹的讀書方法確實有 「支離」之嫌,因為「下學」之事有千千萬萬件,今日學到的與明日學到的未必 有關係,如果長久地學習「下學」之事,學到的知識難會出現過於零碎而無法貫 通的情況,從而無法將道理整合統一,知識學問的累積與德性生命的成長之間亦 缺乏必然性和一致性的關連。而陸九淵在讀書方面的教學之法屬於「易簡」,他 重視「先立乎其大」,主要就血脈上感化學生,他曾言:「吾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陸九淵集·年譜》) 49陸象山能就最簡易的方語言打動學生的內心,從而用簡單的道理教化學生。
(二)道問學與尊德性——讀書取態及旨趣的比較
「尊德性」與「道問學」出自於《中庸(二十七章》「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德性」 與「道問學」並列,前者指存心的工夫,後者指致知之業,朱子以「道學問」自 許,並將陸九淵的為學風格判斷為「尊德性」。朱子非常重視讀書,他認為「道 問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事情。他以對讀書的重視而聞名,無論何時何地,他幾 乎都在讀書。他把讀書視為最重要的教育方法,並且視其為教學的主要途徑。當 有門人問他有何教學宗旨時,他回答說他沒有具體的宗旨,只是視情況而讀書。 他的教學方法和他對讀書的重視在《語類》和《文集》等記錄中都有所體現。他 對陸象山不教人讀書一事感到非常不滿。更指出象山曾說:「如果前面有一個關 卡,只需要跳過那個關卡,就可以獲得結果」50這一說法是不可理喻的,如此含糊的學習方法對學者是有害的。朱熹指要揭示象山的謬誤,更指其說是異端,是 強行曲解的學說,此學說不是聖人的道。強調只要學者稍微虛心地向平實處下功 夫,就能看穿象山學說的迷惑之處。朱熹對陸象山的批評被認為是相當嚴厲的, 他指陸九淵的陸學是象山禪,是異端,此主要基於兩個原因:首先,朱熹指陸九淵不肯教人讀書;其次,他只追求摸索悟處。
然而,對於朱熹的批評是否存缺乏公允或誤解,學界一直存在著廣泛的討論。事實上,陸九淵本人是讀書的,並且並未教導人們不讀書,也對學界指責其「不 讀書」感到憤怒,並為自己辯解道:「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 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及「常說與子姪,以為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 某懶」51由此可見,象山本人在讀書方面是勤奮的,他已為自辯護道「人謂某不 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52以上所述,證明陸象山不僅勤於讀書,亦會鼓勵其學生讀書。然而,朱子的批評也並非毫無依據,因為陸象山強調發明本心, 心一旦覺悟,宇宙即成為自己的心,心即是宇宙。他認為即使不讀書,不認識任 何一個字,也不妨礙成為堂堂正正的人,並且以堯舜為例子,指堯舜之前根本沒 有所謂典籍,而堯舜不讀書也能成為聖人。因此,陸九淵曾說過「若某則不識一 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更說「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王陽明支 持陸象山的學說,亦表達自己了的看法,其曰「《六經》者, 吾心之記籍也,而 《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指六經是人心的記籍,而六經的實質已存在於人的 心中。因此,可以看出象山心學將經籍視為心性的附屬產物,雖然陸九淵從未教 人不讀書,但對他而言,讀書並不是與本質直接相關的首要工夫。另外,陸象山 亦指出如果人沒有道德心靈的感悟和自覺,並將其轉化為我們內在的生命動力, 即是在格物窮理之上獲得再多的理論知識,最終也只是一些空議論或閒知識,無 法在我們的價值生命上發揮作用。53
朱陸「道問學」及「尊德性」之差異亦呈現於從他們對於同一經典的不同詮 釋。在對於「《大學》中所提及的八條目中,二者對於「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的見解各有不同。上文曾提及朱熹對於「先致其知」的解釋為「推極吾之知識, 欲其所知無不盡也」54,這是就格物而言,亦是就知識及學問層面而言的,指格 物是達至誠意的前一步。而陸象山對於此句則有不同的詮釋,他言:「《大學》 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 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僅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 轅,愈騖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55陸象山與朱熹的「格物致知」不 一樣,陸象山解此「知」為「明善之知」56,是就道德層面上而言的。陸象山對此 句的理解與孟子一致,孟子曾就《大學》八條目言「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57,指出人若不能自我反省及明白至善之所在,就無法由內而外發出「誠」。從這個 例子,我們不難看出朱熹注重典籍中的學問,因此他屬於「道問學」;陸象山則注重於典籍中的道德價值,屬於「尊德性」。 在關於「心」的問題上,朱熹的「心」屬於「認知心」,而陸象山則是「德
性心」,對於「心」理解上的不同,導致他們讀書方法的差異。牟宗三指朱熹的 「心」是「心知之明之認知的作用」,是「照物之認知作用」58,所以朱熹強調 「格物」,是為了追求知識,以認知的型態去讀書,外求道德之理,從而使「心」 具「認知」功能。而陸象山主要學說則是以「發明本心」為重點,這一開始便強 調了「心」的重要,人「心」本具有道德意識,所以需要通過讀書而「復其本心」, 方能將「本心」具有的「德性」擴充在具體事物上。
作為儒家的弟子,幾乎所有人都認同道德實踐比理論思辯更重要,而讀書不 僅僅是為了獲取客觀知識,更是通往道德實踐重要的一環。朱子和陸象山在讀書 方法上或許存在一些差異,但他們都認同讀書是為了道德實踐,此觀點也可以被 視為儒學的共同立場。道德實踐的焦點主要是「性命之學」,無論是朱熹或是陸 九淵,建立在「性命之學」之上的關注道德實踐方面與前儒有所不同,他們更關 注如何實踐和體現自我的本質。這種價值抉擇途徑的轉變使得儒家經典成為追求 個人道德實踐的依據,重新回歸到「究天人之際、通幽明之故」的核心領域。59 在追求道德實踐的過程中,朱陸二者皆展現出內在超越的道德實踐層面。朱熹曾 說古人讀書的目的是為了追求道理,而今人不再關注這方面的道理,而是專注於 廣泛地涉獵各種知識,所以有了「道學」和「俗學」的區別。並通過「藥喻」進 行比喻,指配制藥品必須要與治病並行才有意義,只看著藥瓶子無法治療疾病的, 藉此來解釋只有在學懂知識後並內化於自己的身體中,才能真正理解並實踐。朱 熹更指如果僅僅依賴註解來解釋經典,是對理解聖賢思想沒有幫助的。因此,讀 書必然與關注個人的身心狀態以及如何在世間立足的問題相關聯,這些都是「道 德實踐」的議題。這也是為什麼朱熹在《讀書法》的開頭三次連續強調讀書是「第二義」、「第二事」的原因。60 朱熹指在求學問方面,最重要的是決定要成為聖賢,這才是第一要務。同時,朱熹反對追求名利而讀書的行為,認為此等行為是只學 到「下學」而不能體現道德實踐的「上達」,只注重知識的累積但缺乏對自我道 德的追求是沒有意義且浪費精力的。陸象山曾分析過當時知識份子讀書的目的, 第一類是把讀書視為博取名利的工具或者將其視為追求個人名聲的手段,他們讀 書的原因是基於讀書帶給他們的好處,而非發自內心地想要道德實踐。對於這類 沈迷在利益中的人,通過向他們闡述大義來喚醒他們的道德本心,將他們從名利 中解救出來。而第二類則是如朱熹般有高尚情操但過於追求格物窮理的知識分子, 這類人容易深陷於研究學術而迷失了成為聖賢的本心及原本的目標。對於陸九淵 而言,這類人對自己的信念十分堅固,並且善於為自己辯護,要說服他們找回成 為聖賢的本心並非易事。朱熹與陸九淵在讀書的目的是為了成為聖賢及體現道德 實踐一事上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他們的異同也不在於該讀什麼書,因為既然追求道德實踐是讀書的原因,那自然就應該讀聖人紀錄道理的書籍。在關於讀書與道 德實踐的關係一點上,朱熹和陸九淵並沒有太大的分歧。
總的來說,朱熹的「泛觀博覽」及「支離」是「以知識奠基道德行動」。而 陸象山的「發明本心」及「易簡」是「以本心統治知識」61,但他們的終極目標 皆是體現道德實踐。
總結而言,朱熹與陸象山雖同為宋代儒學大家,分別繼承了程伊川及孟子 的學說,導致二者在讀書方法上有相同及相異之處。雖然二位在學術上各執一 詞,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對對方的尊重與欣賞。過去的研究主要著重於陸象山和 朱熹思想的異同,對於他們的研經讀書方法相對較少探討。因此,本文的研究 動機在於填補這一研究空白。本文引了二人的書信、語錄及詩作來研究二者的 閱讀心得。然而,本文存在一些限制。由於資料有限,可能部分資料因為歷史 久遠而失傳,我們只能通過僅存資料來了解朱熹和陸象山的研經讀書方法,另 外,本文僅針對陸象山和朱熹進行比較,未涉及其他宋代儒學家的觀點,這可 能對結論的廣泛性產生一定影響。 二者讀書方法的差異不僅影響了他們對經典的理解和詮釋,也反映在他們 的思想傾向上。朱熹主張精讀和深思,認為讀書應該追求「刻苦者迫切而無從 容之樂」,並對文字字義進行深入理解,故其認為「格物窮理」是讀書之中最 重要的一件事情,其中包括「貫通」及「誠意」的工夫。而陸象山則主張在內 容、思想、價值的理解大致明白後,不必刻意揣摩隱晦不明之處,「發明本 心」才是最重要的一環,亦是讀書的前提,「發明本心」後才能明理,明理才 能辨別典籍中的真偽及對錯。
在讀書方法的比較方面,朱熹批評陸象山「易簡」,陸象山則批評朱熹「支 離」,此爭執的主要原因在於二人分別支持「上達而下學」及「下學而上達」。他 們對於「心」的定義有差異,從而導致他們讀書方法的差異。但無可否認的是, 無論陸象山或是朱熹,他們都不否認讀書的重要性,也一致認為讀書的目的是實 行道德實踐、成為聖人,因此在關於讀書與道德實踐的關係一點上,二者的觀點 是一致的。
參考書籍
1.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2. (宋)程顥、程頤著,塗宗瀛編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3. 張岱年,《思想·文化·道德》,(四川:巴蜀書社,1992 年)。
4. 陳鐘凡,《兩宋思想述評》,(臺北:東方出版社,1996 年)。
5. 錢穆,〈朱子新學案(三)朱子讀書法上〉,《錢賓四先生全集》(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
6.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年)。
7. 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 年)。
8. 張立文,《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想足跡》,(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9. 彭永捷,《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0. (宋)陸象山著,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11. (宋)李子原輯,(清)李紱增訂,《象山先生年譜》(臺灣:莊嚴文化出版社,1995 年)。
12. (明)王守仁著,吳光等編校:〈象山文集序〉,《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13. (宋)王陽明著,《王陽明全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4. (宋)朱熹著,《四書章句集註》,(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社中心,2016年)。
15. 侯外廬,邱漢生等編:《宋明理學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6. (宋)陸象山著,王雲五主編,《陸象山全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35年)。
17. 林繼平,《陸象山研究》,(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 年)。
18. 楊祖漢,《儒學與康德的道德哲學》,(北京:文津出版社,1987 年)。
19. 古清美,《宋明理學概述》,(臺北:臺灣書店,1996 年)。
20.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台北:正中書局,1968 年)。
參考論文
1. 劉天宇,〈淺析朱陸讀書方法之爭〉,《教育學術月刊》(2011 年),頁 104。
2. 黃信二,〈明體達用:評象山心性論對其讀書方法之影響〉,《哲學與文化》第39 期(2012 年)。
3. 林維杰,〈象山學問的詮釋性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45 期(2014年)。
4. 黃信二,〈陸象山孟子學之詮釋學意涵〉,《當代儒學研究》第 14 期(2013年)。
5. 黃明喜,〈陸九淵的「易簡」教學法及其歷史意義〉,《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 36 期(2016 年)。
6. 曾春海,〈朱熹、陸象山的書院理念及其現代意義〉,《哲學與文化》(2008年)。
7. 王雪卿,〈讀書如何成為一種功夫——竹子讀書法研究〉,《清華中文學報》第 13 期(2015 年)。
腳註 :
1.(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459。
2.(宋)陸象山著,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69。
3.張岱年,《思想·文化·道德》,(四川:巴蜀書社,1992年),頁49。
4.陳鐘凡,《兩宋思想述評》,(臺北·: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269。
5.劉天宇,〈淺析朱陸讀書方法之爭〉,《教育學術月刊》,2011年,頁104。
6.錢穆,〈朱子新學案(三)朱子讀書法上〉,《錢賓四先生全集》(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頁691。
7.黃信二,〈明體達用:評象山心性論對其讀書方法之影響〉,《哲學與文化》第39期(2012年),頁50。
8.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352。
9.張立文,《宋明理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491。
10.張立文,《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想足跡》,(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83-101。
11.同註1,頁36。
12.(宋)程顥、程頤著,塗宗瀛編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292。
13.同註1,頁220。
14.彭永捷,《朱陸之辯——朱熹陸九淵哲學比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38。
15.同註2,頁76。
16.(宋)李子原輯,(清)李紱增訂,《象山先生年譜》(臺灣:莊嚴文化出版社,1995年),頁149。
17.(明)王守仁著,吳光等編校:〈象山文集序〉,《王陽明全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45。
18.(宋)王陽明,《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93。
19.林維杰,〈象山學問的詮釋性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5期(2014年),頁97。
20.同註1,頁54。
21.黃信二,〈陸象山孟子學之詮釋學意涵〉,《當代儒學研究》第14期(2013年),頁127。
22.同註20。
23.(宋)朱熹著,《四書章句集註》,(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社中心,2016年),頁327。
24.同註1,頁329。
25.「意之所以誠,卻先須致知」,否則就會「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同註9,頁96。
26.「知若未至,何由得如此?蓋到物格、知至後,已是意誠八九分了。只是更就上面省察,如用兵禦寇,寇雖已盡翦除了,猶恐林谷草莽間有小小隱伏者,或能間出為害,更當搜過始得。」同註1頁126。
27.同註1,頁157。
28.同註1,頁239。
29.侯外廬,邱漢生等編:《宋明理學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560-561。
30.(宋)陸象山著,王雲五主編,《陸象山全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95。
31.同上註,頁288。
32.同上註,頁37。
33.林繼平,《陸象山研究》,(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104。
34.同註1,頁90。
35.同註14,頁187-188。
36.「為學日進為慰!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亦可知矣。」同註30,頁38
37.同上註,頁331。
38.同註2,頁54。
39.同註30,頁309。
40.同上註,頁309。
41.楊祖漢,《儒學與康德的道德哲學》,(北京:文津出版社,1987年),頁114。
42.古清美,《宋明理學概述》,(臺北:臺灣書店,1996年),頁117。
43.同註15,頁427。
44.同上註,頁407。
45.同上註,頁440。
46.同上註,頁443。
47.同註1,頁557。
48.同上註,頁3693-3694。
49.黃明喜,〈陸九淵的「易簡」教學法及其歷史意義〉,《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36期(2016年),頁105。
50.「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同註15,頁458。
51.同上註,頁463。
52.同上註,頁446。
53.曾春海,〈朱熹、陸象山的書院理念及其現代意義〉,《哲學與文化》(2008年),頁138。
54.同註23。
55.同註15,頁7。
56.同註21,頁133。
57.同註23,頁287。
58.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三)》,(台北:正中書局,1968年),頁396-397。
59.王雪卿,〈讀書如何成為一種功夫——竹子讀書法研究〉,《清華中文學報》第13期(2015,頁56。
60.同上註。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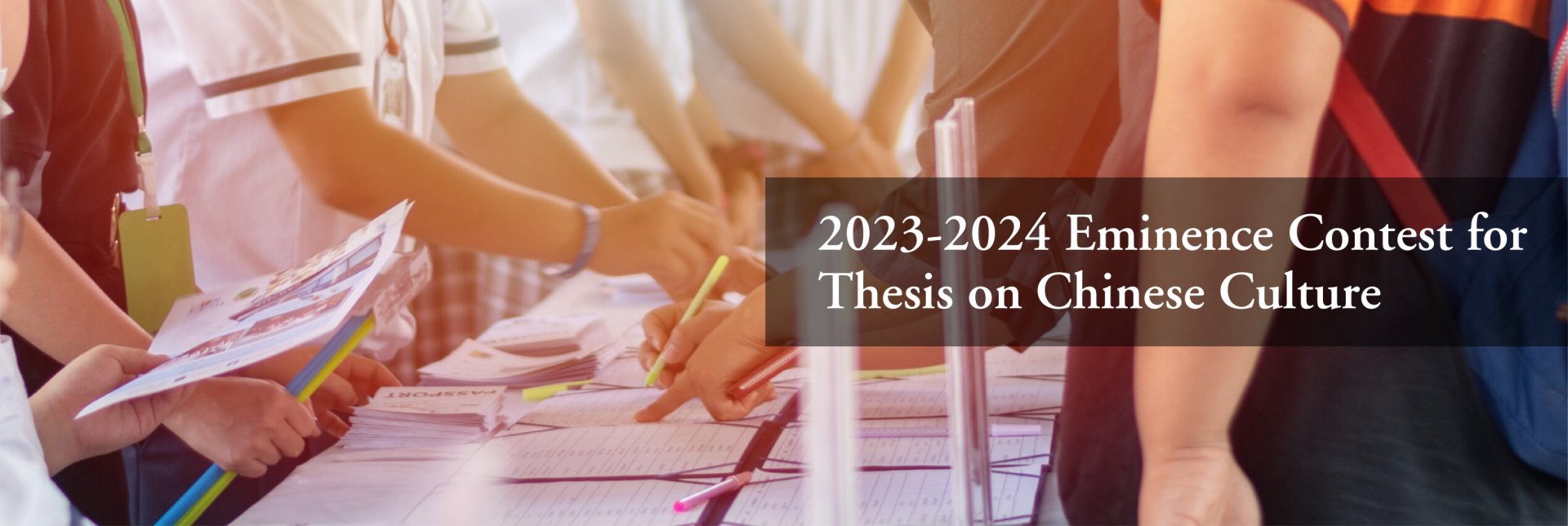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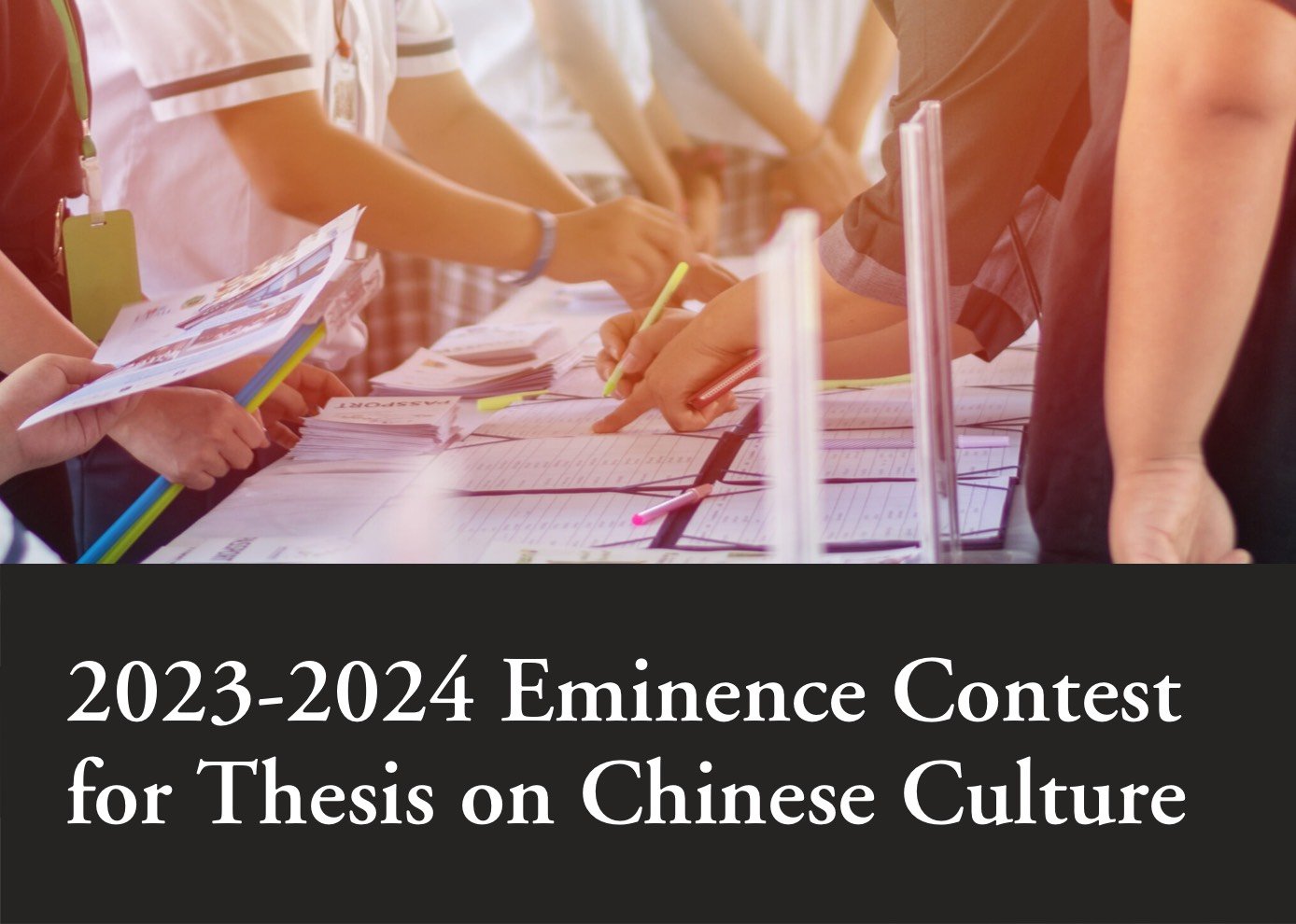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