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中葉,由於中英雙方簽定《南京條約》,西方傳教士因而有機會遷進香港,建立在華傳教基地。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教會一直處於動盪不安的環境當中。不過,由於《南京條約》容許了傳教士在香港傳教,加之位於海隅一處,香港教會可以相對地穩定發展,傳教士因而能夠來港傳道。傳教士除了致力傳道外,他們在認識中國文化上也得花上不少功夫,以融入中國人的思想體系當中。事實上,十九世紀初的來華傳教士精通中國文化,他們出版中文著作、翻譯《聖經》,和從事教育工作,學者稱他們為「傳教士–學者」。1可見,香港能夠容納早期來華「傳教士–學者」的事業,讓西學與中國文化得以融合。
本文的研究對象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為一位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傳教士。1843年,理雅各以傳道為由到港建立基地,並為了解中國人,開始著述有關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另外,他也致力於興辦學校,培育通曉中西的學生。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理雅各與香港華人知識分子關係密切,彼此進行了很多文化上的交流,例如一起翻譯中國經書和討論《聖經》中的一些重要術語。在十九世紀中國動盪不安的歷史背景中,香港作為一個中西交匯的地方,理雅各如何扮演傳教士–學者的角色,是本文的主要核心。
第一節:研究回顧
理雅各研究一直吸引研究不同課題的學者的關注,因為他牽及到中西文化交流、西方漢學,和新教在華史等諸多討論,理雅各在香港活動的議題也令人津津樂道。因此,學者們對理雅各的研究有不同的角度。從中西文化的交流看,有黃文江於1997年出版的專著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該書從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點(a place where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的視角出發,深入探討了理雅各如何透過教育與翻譯等工作,促進中西文化的融合。2書中詳細論述了理雅各在香港的重要事跡,如教育領域的貢獻、翻譯方面的成就,以及系統性地翻譯中國經典著作等。黃文江的著作全面綜合理雅各多方面的工作,以中西交流的框架來評估其貢獻,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理解理雅各歷史地位的視角。
理雅各於1843年到港,社會既充滿新機會,又處於一段十分不穩的階段,理雅各也受到影響。過去學者關注理雅各的漢學研究,多於他在香港的各種際遇與他的事業的關係。近年學者Marilyn Laura Bowman的著作的James Legge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A Brilliant Scot in the Turmoil of Colonial Hong Kong則回應了這個問題。顧名思義,本書的主論調是,以早期動盪不安的香港作為背景,講述理雅各如何在暗潮洶湧的時期中,完成他的各種事業。3本書的主要特色是,作者非常細緻入微地描述理雅各在香港的幾乎所有事蹟,並將理雅各與十九世紀中葉香港和中國的歷史事件連結起來,是一些關於理雅各宗教和哲學思想著作以外的專論研究。
理雅各與華人的關係是一個大部分研究這位傳教士的學者,都有涉獵的議題,因為他們的關係牽涉到中西方在宗教和思想互動的可能。費樂仁(Lauren F. Pfister)的研究對理解理雅各與華人之間的關係提供了重要的參考。4他對理雅各早期生涯,一共兩冊的大型研究 ‘The Whole Duty of Man’: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 中,詳細地分析了理雅各與十九世紀中葉一些重要華人的互動,他的研究顯示,理雅各在當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包括傳教士、牧師、老師,和學者。其他研究則有岳峰《架設東西方的橋樑: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書中設有一章論述理雅各在華的交游,論述到理雅各與不少相善的華人關係友好,經常彼此分享學術上的意見。5
其他關於理雅各生平有精彩描述的,包括吉瑞德(Norman J. Giradot) 的《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吉瑞德以嚴謹傳記的寫作手法,系統地梳理了理雅各一生的經歷。書中的前言〈聯結東西方的傳教士生涯〉尤其概述了理雅各在香港的主要事跡。6近年出版的有陳谷鋆《傳教士與漢學家:理雅各在中西文化上的傳譯貢獻》,書中系統性地分析了理雅各對儒學的研究,以及他翻譯經書的思路。
以上是學者對於理雅各研究不同面向的著作。在理雅各的生涯中,有很多值得被研究的課題,原因在於他涉獵廣泛,其著作有為後世稱頌。若集中看理雅各早期來華的時期,把他連結到當時的社會背景,更會發現他身處於中西方的激烈碰撞當中,那麼他的角色則別具歷史意義。
第二節:研究對象
理雅各,蘇格蘭傳教士和學者,出生於國內鴨巴甸的亨特利。自幼深受宗教生活7和語言知識8的薰陶,具備了前往海外傳教的基本素質。受到下文將提及的傳教士影響,他決定遠赴遠東開展傳教事業。1839年,他首先到馬六甲傳教,隨後於1842年轉至香港繼續其僌命,直到1873年離港。本文聚焦於他在香港的事蹟,探討其多重身份與貢獻。理雅各的事業不僅限於傳教,他還兼具翻譯與教育等多重角色。這些工作不僅將西方思想引入中國,也將中國的知識介紹給西方。
本文認為,理雅各能夠廣泛涉足這些領域,第一個原因在於其雙重身份:他既是傳教士,也是具有深厚中文造詣的學者,這種雙重身份使得他在香港能夠從事不同的知識性工作,如翻譯中國經書與推動教育。同時,他的身份為接觸華人提供了方便,通過傳道和合作,理雅各潛移默化地將西方知識傳播給中國知識界。
其次,香港的獨特性也為理雅各的事業提供了重要條件。這種獨特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當時香港的社會需要通曉中西之人,理雅各的教育理念因此得以實踐。第二,香港提供了相對安全的環境,讓理雅各進行傳教與學術工作。本文討論與理雅各接觸的兩位華人–何進善和洪仁玕(1822–1864)都因為各種原因來到香港,並與理雅各進行宗教和學術交流;香港早期提供有利的商業活動環境,也是理雅各學術著作得以出版的關鍵。
總結而言,本文的基本論點是,理雅各以傳教士與學者的雙重身份出現在十九世紀中葉的香港,這一歷史現象使他成為中西交流的橋樑。本文集中探討理雅各在香港與華人的關係,以及其知識傳播事業兩方面,論述他如何與香港產生一種互動關係,推動中西之間的交流。
第三節:研究資料
理雅各的私人書信及記錄於政府的報告都是本論文的研究資料。私人書信方面,來源主要是理雅各的女兒海倫(Helen Edith Legge,1860–1946)所著的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中譯《漢學家理雅各》),書中大幅輯錄了理雅各寫給親友的書信,能夠觀摩他在香港生活的心路歷程,以及對若干華人信徒的看法。9這部作品儘管在若干部分需要加以考證,但已經基本受到學界的肯定,並且被廣泛引用,其中吉瑞德更在其書籍中原文抄錄。政府的報告方面,資料庫Gale Primary Sources: 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藏有大量檔案可供使用,大部分為理雅各去信政府的記錄,亦有香港註冊署記載理雅各成立教育所的資料等等。
第四節:內容架構
第一章為本文緒論,交代文章的時代背景和主旨、研究回顧、研究對象,和研究資料。
第二章討論新教傳教士來華的歷史背景和脈略,並說明理雅各是在這脈略誕生的人物。十九世紀初,隨着西方列強的擴張,新教傳教士大規模地進入中國。這一時期的傳教活動不僅是宗教傳播,更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和知識傳播有密切關係。理雅各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成為一位兼具傳教士與學者雙重身份的人物。
第三章討論理雅各與兩位中國近代基督教史的重要人物–何進善和洪仁玕之間的關係,分析他們如何互相影響下,推動傳教和中國文化研究的工作,並揭示這些互動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
第四章聚焦於理雅各在知識傳播方面的貢獻,主要探討其《中國經典》的翻譯、學校的興辦,以及「官學生計劃」的推動。理雅各的身份使他在知識領域上貢獻,但同時香港的社會條件和需求也是重要因素。
第五章總結文章內容,指出理雅各的雙重身份和他在香港的活動,在十九世紀中葉中西交流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和他身處的時代背景之不可忽略性。
要了解理雅各為何在香港同時兼任了傳教士和學者,便先需要追溯至早於理雅各到訪遠東前傳教士來華的情況,以闡述理雅各如何受到影響,並論述他來華初期的遭遇。
第一節:第一代來華新教傳教士
19世紀初最具影響力的來華新教傳教士,首推1807年由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出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馬禮遜對後來傳教士在華播道的幫助,主要有兩項。第一,處理語言上的隔閡。馬禮遜來華的任務是為英國聖經公會(The 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翻譯聖經,並出版一本華漢字典。公會給予的任務,促使馬禮遜在華期間積極學習漢語,並在清政府嚴禁國人教授外人中國語言的律令下,私下僱請八位社會地位低的文士向他授課。在馬禮遜的努力下,最終學有所成,翻譯及撰寫出大量中文著作,這些作品受到後來的傳教士大幅度運用,在19世紀中英之間語言隔閡問題嚴重的背景下,相對地為傳教士的工作帶來方便。10
第二,建立傳教士在華基地。鑑於清政府的嚴謹律令,初期來華的傳教士難以尋找穩定和安全的地方立足,例如上述便指出馬禮遜只能偷偷地在廣州學習中文,助手米鄰(William Milne,1785–1822)也因而無法在廣州開展任何活動,因此希望找到一個「寧靜和平的隱修之地」。考慮到地域上與中國的距離、當地政府對新教傳教事業的支持,以至刻印書籍的便利條件,他們最終選擇了在馬六甲建立傳教基地。11馬六甲的歷史地位在於,它是中國遭到英國入侵前一個較為穩定,且較多華人集居的傳教點,它吸引了大量傳教士遠來開啟播道事業,包括了理雅各和他的老師吉德(Samuel Kidd,1799–1843)。總之,自馬禮遜起,南洋地區出現了一股新教來華的潮流,傳教士也建立了向華人傳教的基礎,例如處理了語言不通的問題,這個基礎成為了新教傳教士兼任漢學研究者的雛形。學者把這一傳教士來華的階段稱為「第一代新教傳教士」12,並稱他們為「傳教士–學者」13,下文討論第一代新教傳教士的這種範式如何承接到第二代,進而影響理雅各的生涯。
第二節:第一代傳教士吉德和米鄰對理雅各的影響
吉德和米鄰都是19世紀初的與馬禮遜同期的來華傳教士,屬「第一代傳教士」,以下簡述他們如何影響理雅各的生涯發展。吉德於1799年出身於蘇格蘭的韋爾頓(Welton),從小希望成為傳教士,受到系統的指導下,於1824年受聖職加入倫敦傳道會。隨後吉德在倫敦上馬禮遜的第一堂中文課,為赴遠東傳教作準備。1827年他被任命為設於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院長,1837年委任為倫敦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教授。從吉德的生平可知,他與大部分初期來華的傳教士一般,以傳教為學習中文的目的,並顯然出自馬禮遜建立的系統內。吉德的中文著作有六種,譯作三種14,黃文江評價他「至少在中國傳教士的圈子而言,能夠促進他們對中國研究的興趣」15。1838年,理雅各在倫敦開始上基德的中文課,所用材料正是馬禮遜編撰的英華字典及其《新約》漢譯本,而經過一年的課程,理雅各聲稱已經能夠對214個中文部首的理解中,找到馬禮遜字典中不同詞語的意思。16根據理雅各的自傳,他聲稱向吉德學習中文過程中「收穫了成倍的成果」,並在查閱馬禮遜字典感到困惑時,吉德能夠馬上指出學習困難的原因。17
理雅各受到米鄰的影響與吉德的有所不同,但基本脈略也是由「第一代傳教士」影響第二代。出生於1785年的米爾,其家鄉是蘇格蘭的,1809年申請進入倫敦傳道會並得到接納,1813年來到澳門,可惜不足三天便遭到驅趕,逐赴廣州。18由1815至1822年過世前的七年間,花費大量時間進行傳教工作和從事中文寫作工作,包括幫助馬禮遜翻譯《舊約》的一部分,和創辦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等,這份月刊以闡釋教義和介紹科學知識為目的。19另外,上述也提到米鄰是除馬禮遜以外,開創華南地區傳教體系的成員之一,如成立英華書院和成立恆河外方傳教團。理雅各受到米鄰影響的途徑,是閱讀米鄰的著作。米鄰家與理雅各家有着密切關係,他們同樣定居在鴨巴甸郡,並參與同一所教會的聚會。20據理雅各回憶,當米鄰在馬六甲定居時,曾經向家父寄出一些中文或勸道論著(Chinese treatises or persuasives to Christianity),理雅各回憶,這本書「經常引起我的注意」,閱讀過這些論著後,「有時產生了成為中國傳教士的念頭」。21
吉德與米鄰兩人都是有中文知識的傳教士,透過各種渠道,理雅各萌生成為中國傳教士的意念,並且得到了中國傳教士必順擁有的中文知識基礎,這些中文知識能夠讓他成為一名學貫中西的學者,亦可見他是「第一代傳教士」傳承而來的產物。
第三節:理雅各的來華及其歷史意義
理雅各在1839年開啟其遠東傳教的事業,第一站是馬六甲,並在1843年夏到港繼續他的事業,時值「南京條約」簽定約一年後。理雅各離開馬六甲轉至香港的原因可能有二。第一,享用條約帶來的人身安全保障進行傳教。第二,視香港為傳道於華人的較理想的地方,並希望將英華書院一同搬至香港。他曾寫信給倫敦傳道會說:「當地人十分愚妄,拒絕開化啟示,繼續崇拜偶像,滿足於自己的可悲狀態。」又寫道:「香港與中國本身都是比馬六甲有希望的地方。」並提醒到:「傳教士的目的不是馬來人,而是中國人。」22而其他傳教士都肯定了香港是較理想的地方。23可見,考慮到政治和傳道目標等因素,於理雅各而言,香港是當時較理想的選擇。理論上,他很大程度可以利用條約保護自身安全,進行傳教。然而,他在香港卻受到諸多不確定的因素挑戰。
理雅各來港的首要任務是傳教站和英華書院的建立事宜,然而,卻遭到突發意外和政府的阻撓。來港前,理雅各曾希望將英華書院發展高等教育學府,與大學課程接軌,並曾與馬儒翰(John Robertson,1814–1843)討論這些問題。鑑於馬儒翰與東印度公司的密切關係,他確保了公司能夠每年提供1200元的資助。可是,當理雅各正要處理這筆資助時,東印度公司卻以發展其他教育機構和英華書院未能提供政府急切需要的翻譯人員為由,把這筆資助轉發給馬禮遜教育協會,最終他只能依靠倫敦會的資助,24並將英華書院改為神學院。
此外為英華書院尋找住址的事上也受到阻撓。1843年8月,包括理雅各在內的倫敦會的六位中國和南洋傳教士聚集在香港,開啟「弟兄會議」,討論未來在中國的事工,其中一項的討論項目是英華書院的選址。會議後傳教士致函總督砵甸乍,介紹英華書院的理念,並希望政府能夠撥出灣仔摩利臣山的一幅地。怎料,政府並沒有批出地皮,並在回信中頗負面地評價了書院。25香港政府為何停止幫助英華書院,劉紹麟認為政府覺得過去書院沒有為鴉片戰爭出力,Bowman 則指英華書院早在馬六甲時已經名聲不好,政府甚至因此對所有教會學校都抱持懷疑態度,認為這些學校會阻礙他們開展工作。
理雅各也深受當時香港的社會和氣候問題困擾。開埠早期的香港提供了一個新的商業機會,然而新財富除了吸引商人,還令陸上犯罪活動和海盜變得猖獗。26資料顯示,理雅各不下一次遇到強盜的攻擊。理雅各女兒海倫為他撰寫的傳記中,於〈在香港的生活〉一章的開首便記錄了家裏遭到賊人和海盜的襲擊。27氣候導致的健康問題也常常為理雅各製造麻煩。不少歐籍人士無法適應香港的亞熱帶氣候而引致瘧疾和熱帶疾病,理雅各家庭也深受其害。舉例,理雅各與其家人曾經因為健康原因三次返英,他在香港寫的日記內,也不時提及生病以致的煩惱28。在香港,理雅各還失去了幾位家庭成員,包括其子女和妻子瑪麗(Marry Isabella Morison,1816–1852)。歐籍女姓在早期香港的死亡率很高,而懷孕導致她們的死亡危機增加,女傳教士叔何顯理(Henrietta Hall Shuck,1817–1844)便因為產後併發症過世29,瑪麗死前則出現了子癇等症狀30。
理雅各初在香港的日子充滿困難和不適應,然而,本文將要論述,儘管他面對各種阻撓,卻因為堅定地在香港完成工作,而創造了很多可能性。
理雅各在香港與華人接觸的機會不勝其舉,包括他的傳道對象、學生和工作助手等。其中不乏學問出眾的人,有些學生甚至被他帶往引見英女王。31本章嘗試集中理雅各與兩位華人知識分子互動過程,他們的成長背景不同,產生出來的文化碰撞卻既有相似,也有獨特之處。
第一節:理雅各與何進善(1817–1871)的聖經研究
何進善,字福堂,1818年於西樵山出生,以繼梁發後第二位華人牧師著稱。理雅各和何進善認識於1840年,當時何氏透過在英華書院負責印刷工作的父親,到學校工作和學習英語,以便他接受西方教育為未來人生作準備。32到校後,他立即接受理雅各的教育,學習西方知識,和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由於何進善小時候便在傳統師塾學習,並曾經到過加爾各答學習英語和神學,加上其語言造詣:他學習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只有兩年便能閱讀舊約和新約聖經,當時已經着手研究中國經書和翻譯的理雅各很快便邀請他擔任助手,進行翻譯和傳道等工作。1843年,理雅各將英華書院搬遷至香港,何進善隨之,並在1844年穩定生活後帶同在老鄉的妻子到港。1846年10月,在理雅各的要求下,倫敦會在佑寧堂(The Union Chapel)33按立何進善為牧師,34這場按立儀式規模很大,並採用了雙語模式,包括有中文佈道和詩歌,何進善也以英語通過了聖經概念的公眾考查,他被指有「很出色的英語能力」。35何進善畢生努力研究基督教和傳道,他甚至拒絕商號和政府的高薪禮聘,全心進行他的事業。可惜,何進善於1870年9月到廣州傳道,在他新建的教堂中不幸地遭到暴民攻擊,雖然他沒有受重傷,他的教堂卻遭到焚燒。何進善受到事件的嚴重打擊,健康日壞,1871年4月在香港逝世。36何進善有一生以傳揚基督為事業,也鑑於他作為早期研究基督教的一位重要華人學者,本章希望討論他與理雅各在研究基督教文化上的合作。
《聖經》註釋
至少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在基督教華人世界中能夠獨立處理《聖經》文字工作的人十分有限,他們一般以擔任來華傳教士的翻譯助手為主,例如進行筆錄、抄寫和校對譯文等工作。37何進善可謂這段時期第一位獨立進行《聖經》翻譯和注釋的華人,1918年美國新教雜誌《教務雜誌》形容他和翻譯聖經片段的嚴復為在負責翻譯《聖經》上取得了一次「主動權」38。在理雅各的建議下,何進善分別在1854年和1856年完成了《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的翻譯和注釋,經過理雅各的校訂,取名《馬太福音注釋》和《馬可福音注釋》。這兩部注釋的最大特色在於,何進善只對經文作出「基本的演繹」,沒有過多引經據典,以照顧一般讀者,儘管費樂仁的研究指出,何氏在注釋中其實甚有自己的解經傾向39。不過,理雅各對他的作品流露出充分的信任,例如在何進善的注釋合輯《新約全釋》的前言中說寫道,他跟理雅各說自己的註釋完全是根據原文,還引孔子《論語述而》,指自己「述而不作」,避免誤解上帝的旨意。而理雅各則告訴他不必擔憂,把作品付梓即可,與其他人分享。40 由此,反映了何進善和理雅各之間的充分信任,以致給予對方學術上的肯定。另一方面,我們能夠在何進善聖經註釋中的反映神學理論他如何受影響於理雅各。
我們可以從兩人持守的「後千禧年觀」(Postmillennialism)神學,探討何進善如何益得於理雅各。「後千禧年觀」神學流行於十九世紀,其核心思想圍繞《啟示錄》中描述的一千年上帝統治,通常被理解為基督再來並進行最後審判之前的最後主要階段。在十九世紀之前的主流神學觀點是「前千禧年觀」(Premillennialism),「前千禧年觀」認為耶穌基督最終會重返人間,並為世界帶來精神上的和平與人類繁榮的一千年。不過,「後千禧年觀」則主張,耶穌基督重返人間的時間將在一千年的末期。根據這一觀點,由於教會對基督精神的彰顯,世界將迎來和平的一千年,這段期間將受到基督的統治,直到耶穌基督再次降臨並進行上帝的審判。41換言之,「後千禧年觀」認為,基督在千禧年結束之前,並不會以肉身形式降臨人間,而是通過聖靈等方式,為人間帶來和平與轉化。
理雅各曾編輯其哥哥 George Legge(1802–1861)所撰Lectures on Theology, Science, and Revelation,這部著作其中的一些部分說明了他的神學立場,而理雅各在前言中表示了他深受George Legge的神學思想影響。42在Lecture XVI,他明確地表示反對「前千禧年觀」的主張,認為「聖經」中基督來臨的記載只是「天意的顯現」,並不是真的指「個人降臨」,正如舊約記載以諾預言上帝在大洪水中降臨、以賽亞預言主將傾覆巴比倫一般。43
何進善如何在他的聖經註釋中體現這種思想呢?這可以從他對「爾先求神之國,與其義,則此皆必加諸爾」一句的註釋中看出。首先,他解釋「神之國」為「福音」,而福音是神國的「妙理」,而「義」則是神命令人遵守的正義之道。他接着解釋,如果人先用心尋求神福音的義道,並且切實遵行,那麼人所需的衣服和食物等物質需求,必定會自然而然地得到滿足。他肯定這種註釋說,從來沒有哪位君子遵循這條法則而最終餓死的。44言下之意,何進善認為,上帝的子民所求的「神國」,應是一種精神原則,和對於上帝話語的體現,並非一個具體的實體降臨到世上。45
「God」的翻譯問題
來華傳教士的其中一個任務是翻譯聖經,然而,即使經過多次的修訂,他們也未能達成廣泛共識或令人滿意的結果。因此,1843年,在華各地差會於香港舉行了一次有關漢譯《聖經》的會議,理雅各為港區代表出席。會議中,最困擾的問題是如何翻譯「God」一詞(希伯來文的「Elohim」和希臘文的「Theos」)。這一難題的根源在於譯名需要符合中國文化對「至高神」的理解,各差會代表在會後也花了不少時間對「God」一詞進行了研究,並引發了一場辯論。理雅各起初收到恩師修德的影響,認為「神」是最合適的譯名。不過,經過反覆研究後,他改變其立場,主張「上帝」才是最合適譯名,並於1850年在一本名為An Argument for Sharg Te 的小冊子中發表了自己的新觀點,文中反對了美國傳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使用「神」的立場。46理雅各立場的轉變,其實收益於何進善。以下討論何氏怎樣參與其中。
1850年,理雅各撰寫了一本名 Letters on the Rendering of the Name Go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的小冊子,說明他對「God」一詞翻譯為「上帝」的立論過程,其中最後一頁附錄了何進善在1848年寫給理雅各的信件。47在引錄何進善的信件之前,理雅各提到自己擔心使用「上帝」一詞可能會被誤解為指涉道教寺廟中的上帝,但表示已經找到回應的方法:「有人說『我們走進上帝之廟,在那裡看到了上帝的肖像。我們是否要告訴中國人要崇拜這個偶像,或告訴他們這個偶像創造了天地萬物?』事實上,這些寺廟並不是那被稱為真神的上帝的寺廟。它們是道教上帝的廟宇,而它們的存在並不成為反對將「Elohim」翻譯為上帝的理由。」
然後,理雅各說道這回應方法源自何進善:「我很高興接受以下來自一位中國傳道者和基督教會牧師的來信所提出的反對意見。他對「上帝」 的看法完全不受外界影響。十一年前,他曾反對馬六甲的英國傳教士,因為他們用「神天」來稱呼上帝,我相信這是由馬禮遜博士發明的;當我建議他使用「神」這個詞時,他繼續堅定而平靜地宣揚『上帝』一詞。」
理雅各接着引述何進善向他說的話:中國「確實有皇天上帝的廟宇,但不是在經典中的上帝(the Classical Shang Te)的廟宇。這個真正的上帝(this true Shang Te)不可能有任何廟宇,因為只有皇帝作為全體人民的父親,才有權向他獻祭。」他接着解釋:「因此,百姓不敢為他立廟、祭祀。他們只能以服從方式來侍奉他。可能有玉皇上帝或者神天的廟宇,我見過這兩座廟宇的雕像,但我從未見過或聽過任何上帝的形象…事實上,在古代中國根本找不到他的形象。」48何進善以中國傳統祭天的規則回答了理雅各的疑難,指出了中國人在廟宇的祈求對象不是「上帝」(我想他說的是西方人角度的上帝,即中國的天),而是道教的「玉皇上帝」或「皇天上帝」,傳統中國上也沒有「天」的形象。由此可見,理雅各之所以可以堅定地回應那些以為中國人在廟宇內信奉有形象的「上帝」是中國傳統的「天」,完全是因為得到何進善幫助。事實上,從基督教文化的角度,人類只能在自己看見上帝的形象,對於其真實形象甚至如何詮釋並不敢妄下定論49,在中國傳統對「天」的看法而言,實有相通之處,何進善這簡短的回應,其實已經涉及他對兩種文化的深刻認識。
第二節:理雅各與洪仁玕(1822–1864)的基督教教義
洪仁玕,字謙益,1822年生於番禺,是洪秀全的族弟,也是太平天國後期的首輔大臣。50早年曾五次參加科舉,但均未能中第,1850年,即洪秀全發動團營起義的那一年,洪仁玕經歷了最後一次的落榜。1851年1月,洪秀全正式起義,建號太平天國,洪仁玕決定響應起義,然而多次與洪秀全會合未果,並屢遭官府追捕,四處逃亡。1852年,他逃到新安縣一所洪氏宗族家中,結識了與西方傳教士關係密切的洪升。洪升帶他到港,介紹給巴色會的瑞典傳教士韓山文(Theodore Hamberg,1819–1854),及當時在香港的理雅各。51由於在香港難以謀生,洪仁玕於1853年返回內地擔任塾師,其後,為幫助一位受洪秀全洗禮的友人李正高(生卒年不詳)尋求庇護,他再次前往到新安與韓山文重聚。韓山文此時為洪仁玕施洗,並系統性地教授他基督教和西方知識,洪仁玕在這個時候開始對這些知識產生濃厚的興趣。
1854年,韓山文因痢疾去世,洪仁玕二度赴港,得到倫敦會的接納,擔任布道師和傳教士助理等職務。此時,理雅各正着手《中國經典》的翻譯,便邀請熟讀經書的洪仁玕擔任助手。洪仁玕在香港流亡約四年,1858年決定赴天京向太平天國宣揚教義。期間,他與理雅各建立了一段深厚的私人友誼,理雅各更指他是惟一曾「勾肩搭背走路」的華人。52洪仁玕一直隨理雅各研讀、講道,吸收了正統的基督教思想,此外,他還借助理雅各豐富的藏書和出西學小冊子,廣泛學習各種西方知識,他在江西被審問時稱,在香港期間「學天文地理歷數醫道,盡皆通曉」。53事實上,理雅各對洪仁玕贊賞有嘉,在個人性格上,稱他「性情溫和而又友善」;基督教義的學習上「較過去增長許多,並且其皈依基督教的誠意不容置疑」,與其他中國人一起時更是一位「勸道者」,而且會「毅然剖明其謬誤」。54然而,正如夏春濤所言,洪仁玕在香港的心態僅是暫居,他的最終志向是報效天京,他的許多重要著作都是在天京發表的。55以下將以《資政新篇》中宗教思想為例,進一步分析洪仁玕的著作反映的思想與理雅各的關係,並剖析理雅各與這位投身太平天國的人物之間的複雜的互動。
洪仁玕的基督教思想:三位一體與「耶和華」的註釋
洪仁玕的基督教思想,與理雅各有着相當的關係,以下以「三位一體」與「耶和華」的註釋為例子。
三位一體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之一,主張上帝以聖父、聖子、聖靈三個位格存在,各自獨立活動,卻又同為一體。在洪仁玕《資政新篇》〈風風類〉一節中,表達了他對此一信條的肯定。文中,他批評中國人不能辨識真正有價值的事物:「中地素以驕奢之習為寶,或詩畫美艷,金玉精奇,非一無可取,第是寶之下也。」56他認為,真正的「寶」應當是「三位一體」的上帝:「夫所謂上寶者,以天父上帝、天兄基督、聖神爺之風三位一體為寶…」,衪能夠「格其邪心、寶其靈魂、化兰愚蒙、寶其才德」。57 隨後,洪仁玕進一步解釋他對「三位一體」的理解:「蓋上帝為爺,以示包涵萬象;基督為子,以示顯身指點;聖神上帝之風亦為子,則合父子一脈之至親,蓋子亦是由父身中出也,豈不是一體一脈哉!」58上帝是父,基督和聖靈(上帝之風)為子,父子之間血脈相連,這裡洪仁玕已經暗示了三個位格實為一體,密不可分。
傳統上,基督教對妄稱「上帝」之名十分忌諱。然而,在〈風風類〉一文中,洪仁玕卻堅定地表示「上帝之名永不必諱」,並認為「若諱至數百年之久,則又無人識天父之名」。59他以猶太譯音「耶和華」為例,指出這個詞有「『自有者』三字之意,包涵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自然而然、至公義、至慈悲之意」。洪仁玕對這些術語的見解,很可能受理雅各的影響。第一,如前所述,理雅各早已使用「上帝」一詞稱那至高者。第二,關於「耶和華」這個概念,在他的著作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中,有一篇題為 On The Name Jehovah. Is it Better to Translate it or Transfer it? 的短文,討論了「耶和華」一詞應該直接從希伯來語的意思轉移至中文,還是使用其他中文概念進行翻譯。60
文中,理雅各主張依照希伯來語裏「自有永有」的意思直接轉移,向中國人解釋「耶和華」的即為「自有者」。他同時抱怨其他傳教士用「神主」、「皇上帝」等詞彙來翻譯「耶和華」,並任意將它與其他概念結合,例如 將「Yehova-Elohim」譯為「上主皇上帝」等。理雅各認為,這種做法只會令中國人「理解這種組合是一個專有名稱」,並導致「耶和華一詞將貶低到假神的層次,只有用解釋、評論才能糾正這種邪惡」,相比之下,直接稱其為「自有者」更容易被理解,也更為簡潔明暸。61由此可見,洪仁玕的基督教義基本上與理雅各的相一致。然而,正如前述,洪仁玕以報效天京為己任,與何進善純粹希望播道福音的使命,顯然更具挑戰性,這導致了洪仁玕的關係變得複雜。
第三節:何進善和洪仁玕在中國傳道的嘗試和遭遇
理雅各與何進善和洪仁玕在基督教文化上的交流有着精彩的互動,不過,他們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報效福音,絕非只是將思想留存。不過他們在此遇到了種種困難,甚至葬送了生命。下文將會討論他們在中國傳道的困難,並帶出他們在香港與理雅各進行基督教活動的意義。
何進善與廣州教堂
何進善於1871年去世,其主因卻是一次在廣州傳道的打擊所致。1864年,何進善在佛山成立了自立教會,並於1870年在鶴山成立了一座完全由中國教徒捐款建起的「三自」教堂。62然而,這個鶴山小教堂卻令何進善耗費了不少精神,尤其在與村民解釋教堂並不會破壞風水的事上。63理雅各1870年由英國回港,對教堂興建一事上非常高興,原本也希望出席開幕儀式,然而,同年在天津發生了著名的「天津教案」,引起各地的反洋情緒,理雅各為了避嫌,沒有出席到儀式。同年9月,鶴山小教堂不幸地遭到暴民破壞,並放火燒燬之,何進善本人也被暴民追打。64事件後,何進善身心俱疲,加上本身已經有病患,1871年2月一度需要由家人安排到廣州接受治療,但沒有得到好轉,1871年4月在港辭世,理雅各回憶,何進善臨終前一個月「外觀完全改變,但仍然認得我並報以笑容,但我不清楚第二天他是否仍然認得我」。65
可幸的是,何進善臨終曾經努力向滿清政府交涉,要求政府賠償572英鎊,儘管政府一度認為何進善在華洋關係緊張之際興建教堂是缺乏政治觸角,拒絕負責,但經過幾番交涉後,最終願意賠償,而這筆賠償令日後可以興建一座更具規模的教堂。661872年1月,理雅各探訪這座新教堂,感到「極度喜悅」。67
洪仁玕和太平天國
根據理雅各女兒所寫的傳記,理雅各在於1858年因事回英,臨行前,曾經嚴令洪仁玕不要加入天京叛軍,好好待在香港。68不過,起初大部分的西方傳教士都沒有反對他走進天京的做法,因為他們認為太平軍正在替天行道,只是認為太平天國的基督教義需要被糾正過來。69有些傳教士更積極協助與參與其事,例如倫敦會傳教士湛約翰(John Chalmers,1825–1899)便以每月七月資助其家庭費用幫助在港的家人70,1860年7月,洪仁玕發信邀請傳教士到蘇州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和公理會(Congregational Church)的楊格(Griffith John,1831–1912)都積極應邀71。1860年,理雅各除了間中收到洪仁玕寄來的著作72已經與洪仁玕失聯,不過,當時理雅各對他仍抱有希望:「我仍不放棄接獲洪仁玕訊息的希望,他有可能已經抵達南京,只因某些原因無法和香港與上海的朋友聯繫。基督信仰與愛國熱忱是促成他此次冒險遠行的雙重動機,他是少數值得我感動與尊重的中國人之一。」73
理雅各得悉艾約瑟等人將與洪仁玕見面時,立即請他們告訴他洪仁玕的狀況。他興奮地在書信中寫道:「我們當初已經放棄了對他的希望,但是當我聽說叛亂分子已經從南京突圍,很快就會接近我們在上海的弟兄們時,我就寫信給他們,請求詢問一下他的情況…在叛亂的軍隊中,至少有一個人是完全熟悉真理的…當他從香港出發時,他說一旦抵達南京擁有權勢,其主要兩個目標是:首先糾正宗教上的錯誤、第二,實施一連串和外國人調和的政策,即使不能爭取到外國人的合作,至少要爭取到他們的同情。他值得大家為他真誠祈禱。」74然而,事情並不如理雅各想像得那麼理想化。
後來,理雅各得悉洪仁玕違犯了基督教的規條,例如,1861年初他從上海傳教士弟兄的報道中,知道他立了多個妃嬪,對他開始產生失望之情,不過他仍然對洪仁玕改變太平天國持一定的積極態度,例如理雅各認同派發聖經以激發民間的熱忱,但是接下來如何不組織政府,便很難推動革命。75 可惜,洪仁玕最終也是無能為力,在一封理雅各表達英政府對太平天國應該持中立立場的信中,他說道:「我的老朋友干王洪進,當時準備與他們探討與外國人的友好關係。如果我們在1860年或1861年願意與他們談判的話,我們會發現他們對我們的『外國教友』的稱呼,就會含有真正的善意。但是,當時干王的地位還不足以使他們能排除貫徹此種政策的障礙。」更糟糕的是,理雅各也認定他失去了當初熱忱的心:「有理由擔心,他的信仰和良心已經破滅。」76
何進善和洪仁玕二人都有一個令人感到可惜的結局,前者在內地傳福音卻差點遇害,後者的神學理論遭到其族兄忽視,最後隨着太平天國的失敗,死於朝廷的刀下。從這個角度看,理雅各的教導並沒有令二人獲得最終的成功,這固然是歷史上的偶然,因為如果何氏沒有遇到暴民,而洪仁玕成功逃過追捕,正如他前往香港前的那樣,他們也許在傳道上有更大的成就。不過,這反映了十九世紀中葉基督宗教在中國的障礙,內地不斷發生教案,加上太平天國導致群眾產生對基督教的懷疑態度,使得基督教的傳播困難重重。當然,理雅各很清楚時代給予他的困難,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在內地遇到攻擊77,然而他仍然相信報效福音是必須做的事,他對洪仁玕的堅決最終是予以肯定的。然而,另一方面,在這個不安定而基督教又有機會廣泛傳播的年代,一些新的文化衝擊卻正在出現,上述的例子表明,一些新的著作正是由傳教士和華人的合作而誕生的。從理雅各與兩位華人的來往的案例,反映了十九世紀中期中西文化,尤其在基督教上,如何獲得嶄新的發展。此外,也反映出香港在十九世紀中葉的特殊地位,它提供了一個讓中國基督教得以發展的機會,讓理雅各等傳教士,與華人信徒擁有接觸交流的機會,並作為向更大的中國傳播宗教的起點。
理雅各自1843年抵達香港以來,儘管工作十分繁忙,卻在知識傳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本章將探討他在香港知識傳播上的工作,與香港社會和理雅各雙重身份之關係。
第一節:《中國經典》的出版
對於一位中國傳教士而言,研究中國思想無疑是進入中國人內心的其中一個有效途徑。他們不但可以與中國人進行有效溝通,還能夠利用中國人的語言和思維來傳播教義。「四書五經」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寶庫,深刻地反映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理雅各非常了解這一點,因而決定通過研究和翻譯經典著作來探究中國文化,並且依此作為傳教事業的基礎。78理雅各於1873年離港之際,完成了他的翻譯合輯作品《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的第五卷,他的作品至今仍然是中國經書英譯本的標準版本。79
學者們一般對《中國經典》中的翻譯方法學、怎樣反映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如何體現耶儒合一等問題抱有濃厚與趣。然而理雅各的大部分翻譯著作和出版工作都是在香港完成的,而較少文章有系統地討論這現象。因此,本節期望探討他的翻譯工作可以在香港得以大規模實現,進一步說明香港在這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中國經典》的出版在兩方面收益於香港,第一,香港商人的出資、第二,香港英華書院的協助。
渣顛兄弟(Jardine Borthers)的出資
首先,《中國經典》的出版費用是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負責人渣顛兄弟付的。在《中國經典》第一卷的扉頁上,理雅各便注明了書籍的出版是以紀念渣顛兄弟:To the memory of The Hon. Joseph Jardine ESQ.。80約瑟夫.渣顛(1822–1861)隸屬怡和洋行其公司的總部於1842年從廣州遷至香港,在港發展包括鴉片的商業。《中國經典》緒論部分,以所當的篇幅描述了渣顛如何幫助書籍得以成功出版:
1856年,他(理雅各以第三人稱稱呼自己)第一次與一些朋友談論自己的目的,其中包括牧師衛斯理傳教會的喬賽亞‧考克斯 (Josiah Cox,1828–1906)。出版費用的問題出現了。作者的想法是,他很快就能消化他的材料,準備付印,然後,他就有可能在申請時得到英國和其他在華外國商人的鼓勵,從而使他能夠繼續實施他的計劃。不久之後,考克斯先生毫無預警地將此事告訴了他的朋友約瑟夫‧渣顛先生。由於考克斯向渣顛先生報告了作者的觀點,作者便探訪了這位先生,當時他非常慷慨地承諾承擔出版該作品的費用...渣顛先生對該出版計劃表示贊同,並說:「我知道中國商人的慷慨,他們中的許多人都願意為這樣的事業提供幫助,但你不必費心去徵求他們的意見。如果您準備好為出版付出辛勞,我將承擔出版費用。我們在中國賺錢,我們很樂意為任何有可能為中國帶來利益的事情提供幫助。」81
約瑟夫渣顛在1861年去世,此時《中國經典》第一卷已經完成。他的哥哥繼續為理雅各的著作出版提供經費,直到第四和第五卷完成。第五卷於1872年完成,其時距離理雅各離開香港還有一年。值得注意的是,渣顛兄弟是鴉片商,在教會的角度上存在爭議,倫敦傳道會便曾經批評理雅各接收的是「罪惡的捐贈」。82然而,渣顛兄弟的資助反而讓理雅各在研究上獲得更大的自由。
倫敦傳道會曾經支持理雅各的翻譯工作,但是他們也給出了兩個條件,其中一個是理雅各需要在翻譯過程中使用注釋進行駁斥,以指出孔子與基督教真理相左。83不過,渣顛兄弟並沒有對理雅各提出過多的要求和干預,這無疑對學者來說是重要的。因此,頗具諷刺的意味的是,香港的鴉片商比理雅各所屬的教會,更為他的《中國經典》翻譯工作提供了順利的條件。
英華書院的協助
其次,是香港英華書院的協助。這主要體現於兩方面,其一是書院的印刷技術,其二是書院提供的學術紛圍。
書籍的印刷是出版過程中的重要一環,而《中國經典》的印刷曾經收益於香港英華書院的技術支持。英華書院早在馬六甲時期已經擁有印刷技術,由傳教士戴爾籌備鑄字,發明了獨特外型的字粒,即後來所謂的「香港字」84。當書院搬遷至香港後,仍然保留了其鑄字技術和印刷所85。王韜曾經注意到,英華書院不僅「教以西國語言文字、造就人才」外,還「兼有機器活字版排印書籍」。英華書院印刷的書籍廣泛,涵蓋宗教、世俗、中文和教科書。《中國經典》便利用了英華書院的設備,成功地印刷了第一版的書籍。86另外,細觀《中國經典》內的字樣,即屬「香港字」。87
此外,英華書院內的學術也對理雅各研究中國典籍產生影響。英華書院初成立的其中一個宗旨,是促進中西文交流88:「讓雙方互相學習中國和歐洲的語言和文學。對於中國學生,由歐洲教授傳授英語、中國宗教原理和各門常識,透過漢語媒介,由本土教授講授歷史、哲學和文學。」書院還期盼「透過促進歐洲和東亞的文學、知識和友好交流,能夠促進人類的幸福。」89 理雅各於1840年11月成為英華書院校長,遷至香港後繼續擔任此職務,並且教授多位學生。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理雅各同時不斷提升中文水平,直至他有信心能夠翻譯深奧的《中國經典》,最終於1861年出版了第一和第二卷。儘管理雅各在馬六甲時期已經擔任校長,其大部分活動實際上在香港進行,香港也提供了較優質的環境讓書院繼續經營,並承繼了書院的優良設備和傳統。
19世紀中葉的香港,創造了良好的機遇,給商人和教會前往發展,而《中國經典》的出版在這樣的環境下,得以順利出版。理雅各的努力和中國文化的水平,固然是其著作的重要一環,然而他當初決心前往香港傳教的舉動,也是使得《中國經典》得以面世的動因。
第二節:教學及其教育理念
十九世紀在華新教傳教士的活動,並不局限於佈道、散發傳教書籍和舉行宗教儀式等「直接」的傳教內容。他們必順通過各種途徑接觸大眾,爭取親近他們的機會,並採用非直接、着眼於長期效果的方法。90他們也常常希望培養擁有西方知識和語言能力的華人,成為中西方交流的橋樑。91理雅各於1843年把英華書院改建為神學院,雖然其初衷是宗教目的,但他同時並行英語和世俗知識為核心的教學方案。可是隨着英華書院在1856年關閉,這一教育方案幾乎沒法延續,然而當時的政府卻在管治上需要這套方案,讓理雅各的教學理念得以保留和繼續發展。
英華神學院及其教學
上文提及,英華書院因為失去了政府的資助,未能升格為高等學府,而理雅各早在馬六甲時期,已經萌生了建立神學院以培訓中國牧師的想法92,因此順利成章地把書院改建為英華神學院(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為了幫助學生更好地準備課程學習,理雅各設立了預備班,期望中國學生能夠掌握一定程度的英語和西方知識,讓他們「平衡宗教世俗知識」。93為此,理雅各為特別編譯了一本名為《智環啟蒙塾課初步》(A Circle of Knowledge)的教科書,旨在提升學員英語水平和科學知識。不過,從結果來看,英華神學院的教學目標只實現了一半,因為所有入學的學生當中,最終沒有一位成為了神職人員94,不過,學生們卻能夠在畢業後找到理想的工作,施其樂(Carl T. Smith,1918–2008)的研究指出,他們一般擔任政府和法院的翻譯員,或在英商工作95,這些工作的薪金比牧師高,因此學生往往更願意投身當中。
然而,雖然沒有一位學生成為了神職人員,理雅各在英華神學院推行的教育政策和成果,恰好地展現了他堅持的理念,即對英語教育的重視。早在1845年,他便向港督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提議興建免費學校,以便讓更多學生學習英語和其他世俗知識,並建議聘請高質素的英國老師。然而,由於戴維斯認為計劃太過複雜和昂貴,加上英國政府希望降低在香港的開支,計劃始於未能實施。961853年,理雅各受邀成為教育委員會成員,97 他認為英語教育是管治的重要組成部份,而他過去的學生的確在畢業後為香港社會提供了服務。因此,儘管英華神學院計劃未能完全實現最初的目標,其後更於1856年因收生不足而關閉,它依然實現了理雅各長期以來堅持的教育理念,即通過英語教育推動社會進步與政府的有效治理。
世俗教育的推行
開埠以來,香港教育主要由教會機構主持。這一現象源於香港政府遵循英國的教育政策,即教育由教會掌控的傳統。儘管十九世紀初,國內的非國教徒(Non-conformist)不斷呼籲教育應該由政府負責,但官方受制於傳統觀念,採取消極地態度應對意見。98因此,教會學校在香港教育體系中佔據了主導地位。,例如在1849年成立的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便曾經得到政府的支持。根據教育家歐德理(Ernst Johann Eitel,1838–1908)的記載,聖保羅書院每半年便會舉行一次考試,旨在吸納香港最優秀的學生,曾有一次多達十一位學生由政府學生轉校到聖保羅書院。99作為聖公會屬下的學校,這所學校也以培訓教會的牧職工作為目的。100正如在〈諸論〉第二節中解釋,理雅各在蘇格蘭時曾是獨立教會的成員,對國教墨守成規的教義感不滿,立場上與非國教徒一致。歐德理指出,在聖公會和非國教徒的緊張關係下,理雅各一早便希望削弱聖公會在教育事務的影響力,並推動香港教育世俗化。101這可以體現於理雅各的各種課程提議中。例如,他在1853年便提議在當時的五所學校中,有兩間應該提供英語教育。他還建議,在聖經知識、英語、《四書》和地理成績優異的學生,可以獲得1元至1.5元的獎金。這顯示,他不僅重視除宗教知識,更強調世俗知識的重要性,尤其英語教育。
1860年,香港的教育體系經歷了一次重大變革。原有的「教育委員會」改為「教育局董事會」(The Board of Education)。由於德國傳教士羅存德(William Lobscheid,1822–1893)的請辭,理雅各隨即提出了著名的「理雅各計劃」(The Legge’s Scheme),提出一系列的世俗教育計劃。計劃書中,他對當時香港教育現狀提出了批評,指出學生出席率不穩定且難以計算,同時英語老師質素也普遍低下。102因此,他提出了三個建議:第一,集中辦學,建造一所建築,將香港幾處的學校集中起來;第二,引進專家,請來一位歐洲籍專家(European Master)專門負責學校的英語教育;第三,引入監督機制,該歐洲籍專家需要負責監督其他學校。103
他期望這些建議能夠達到以下成果:第一,政府參與,政府內能夠有一位官員積極地從事教育工作;第二,提升英語教學效率,在專家指導下進行的英語教育能夠更加系統化和高效化;第三,在中國學校接受過良好教育、並在香港與中國的商行和家庭有連繫的學生,能夠進入計劃中的英語課堂學習;第四,提升校內的中文教育的質素。104香港的司法和法律工作都以英語進行,因此計劃中強調英語教育是理應的,理雅各自信地稱:「這樣,影響力就會從這個島嶼發出來,廣泛地影響中國,啟蒙和造福於中國眾多人民。」105
理雅各自來港直至成為提出「理雅各計劃」,始終堅持推動英語和世俗知識的普及。歸納他的目的,主要有二:第一,培養學貫中西學問的牧者,讓他們介紹西方知識給中國人之餘,進行傳教工作;幫助政府更有效地管治香港,這可以體現於他提議集中教育於一所官立學校,以便提供對社會有利的教育,以及對作為官方語言的英語之重視。一些學者解釋到,理雅各在這兒之所以取得卓越成就,正是因為他不僅為教會着想,也致力於改善香港的未來,幫助政府實行有效管治,推動教育從宗教向世俗轉型。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理雅各從一開始便強調英語等世俗知識的重要性,致力於培養溝通中西的華人–這個眾多在華傳教士希望達到的目的,他甚至放棄以宗教為首的教育政策,推行世俗教育。歷史學家吳倫霓霞認為,正是因為理雅各的「傳教學校未能培養出本土牧師」和「逐漸了解中國人的性格」而漸漸不以傳播基督教為最終目標。106他也順着時勢決心行動,例如在羅存德辭職後,迅速接任教育委員會領導職務。這表明他並非一位不諳社會趨勢的溫和天真的學者–傳教士(a mild and naïve scholar-missionary)107。
第三節:與「官學生計劃」的關係
理雅各在香港培訓學貫中西的人才,其中一項值得關注的計劃是1861年推行的「香港翻譯官學生計劃」(Hong Kong Interpreter Cadetship Program)。108由於1850年代的香港欠缺優秀的譯員人才來擔任華人與洋人的溝通橋樑,政府因此提交了這項計劃,旨在在整個大英帝國考取優秀學生。109獲取者需要進行半年一次的考試。110在這項計劃實施後,理雅各憑藉其深厚的中文造詣,主要負責教授和考核學生,以及編排教科書111,因此,過去有學者便認為理雅各只是課程中的一名中文老師112,並將計劃歸功於向時任總督羅便臣(Hercules Robinson,1824–1897,任期1859–1865)113。不過,近年學界對此觀點進行了修正,指出理雅各實際上是這項計劃的提出者和主要策劃人。114
有幾項證據證明理雅各是計劃的提出者。第一,1872年,理雅各離港之際,在香港的一個大會堂(The City Hall)發表了其香港生涯的心得與自己的貢獻,其中一段便說道:
羅便臣爵士實施了另一個計劃,一樣是由我自負地逐一向歷任香港總督推薦的。自1844年起,我便認為,除非大部分的職位都由懂得中國語的官員擔當,而且需要理解本地人,否則,管治香港是不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的。為了達到目的,我提議讓年輕的紳士們成為官學生(student-cadet)。我冒昧地認為這計劃的理念是好的。115
第二,根據其女兒所撰回憶錄所記載:
1861年,羅便臣爵士發給理雅各一份建立某種培訓制度的計劃草案,要求根據他認為合適的情況,更改全部或部分條款。他非常喜歡這項計劃,因為該計劃準備提供大量所需的翻譯人員,並承擔起每隔六個月對培訓生和翻譯學員進行一次中文考核的任務。116
從以上證據可以反映,計劃的提出和策劃人正是理雅各,若非如此,羅便臣也不會把計劃的主導權給予理雅各。1861年的政府憲報在介紹香港官學生計劃(Hongkong Cadetships)時也明白地寫到,計劃為了「向香港公務員隊伍提供一支高素質的翻譯隊伍,政府設立一定數量的翻譯學員名額,學員抵達香港後順在一定時間內致力於學習語文」。117因此,這項為培養翻譯人才的計劃,實為理雅各所倡導與推動。
這項計劃的目的是培養翻譯人員,因此課程設計也以語言能力為重心。例如在考卷中,必答題包括了英文作文、拼字摘要、拉丁語翻譯及作品,以及多種語言(希臘文、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的測驗。其中計劃一大特色在於,考核過程中不涉及中文,這代表學生在參加考試前不需要具備中文知識基礎。然而,通過考試並到達香港後,學生需要接受為期兩年的中文學習。118由於理雅各已經研究中文多年,因此他完全有資格負責中文教學的部分。他編排的課程,主要特色是利用他的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知識套用其中,例如以《聖經》和儒家經典為教授和考核內容,要求學生把英文《聖經》翻譯成中文,和儒家經典翻譯成英語。119理雅各的教學內容不僅反映了他過往的學術工作,也體現了他將已有知識與經驗應用於培養香港譯員的實踐中。
從以上三個例子可以反映,理雅各與香港的關係是雙向的。他受益於英華書院和渣顛兄弟的支持,得以順利出版《中國經典》;同時,他也一直致力培養一批能夠在中西方之間進行溝通的人才(據上文,理雅各於1844年向港督提出培養翻譯員的計劃,以及在1845年提出應該提供免費的英語學校,反映理雅各對香港的雙語人才需求的先見之明)這促使他清楚知道如何具體地執行相關計劃,最終為香港教育帶來改革,並培育香港所需的翻譯員;他的宗教和語言學問,也在翻譯官學生計劃當中得到了充分應用。
理雅各於十九世紀中葉來華並到達香港,除了履行其傳教事業外,也為中西文化的交流上有所貢獻。不過,正如本文一再指出的那樣,理雅各雖然具備了兩大文明的知識,他還必順滿足於一些條件才能夠實現目標。
就傳道事業而言,起初理雅各在香港建立英華神學院並不順利,學院的學生也不熱衷於宗教事業,畢業後沒有選擇報效福音工作。然而,本文重點分析與理雅各交往的兩位人物–何進善和洪仁玕,他們為理雅各在中國傳教的目標帶來了轉機。他們致力於研究基督教文化,並且在傳道事業上花了很大的努力,只是鑑於時代因素,他們在中國傳揚基督教沒有得到重大成果。理雅各和二人的主要接觸地點都在香港,而正正因為香港為理雅各與兩位人物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和資源,一些重要的基督宗教思想才得以保存和書寫,並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
理雅各起初以傳教為目的,深入地研究了中文和中國文化,使他獲得了認識傳教目標的知識的優勢。本文討論了理雅各如何使用這種優勢放進他的教育體系當中,而香港政府也利用了其知識分子的身份,讓他處理香港的教育事務,培育學貫中西的學生。
在實際事務和管治層面而言,理雅各未必純粹為了宣揚文化知識,但其結果確實達到了這一點。他的《中國經典》也為往後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參考。香港在其事業上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忽視的,讓理雅各的教學理念得以實現;香港的社會條件也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中國經典》的出版。
到底是時勢造就人物,還是人物改變時勢,這種簡單的二分法通常不能夠套用於史學研究上,理雅各的個案也不例外。本文通過考察理雅各的來華,和他與知識分子的互動,以及知識傳播上的工作,反映他對於中西文化互動和交流的貢獻。
附錄一: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帶往英國的中國學生

資料來源: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https://www.npg.org.uk/collections/search/portrait/mw42742/James-Legge-Le-Kin-lin-Sung-Fuh-Keen-Woowan-sew
附錄二:成立於1845年的第一代香港佑寧堂 (The Union Church)

資料來源:Union Church. https://www.unionchurchhk.org/ministries/the-grace-of-giving/
附錄三:理雅各《中國經典》中的「香港字」

資料來源:Jame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London: Trubner&Co., 60 Paternoster Row., 1861).
附錄四:理雅各在《中國經典》感謝渣顛(Jardine)兄弟

資料來源:Jame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London: Trubner&Co., 60 Paternoster Row., 1861).
附錄五:理雅各及其女兒 Helen Legge(1860-1946)

資料來源:The British Columbia Review. https://thebcreview.ca/2018/09/26/134-resuscitation-of-james-legge/
附錄六:何進善的《馬太福音》釋註

資料來源:Lauren F. Pfister,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37.
中文書籍
1.[美]史蒂芬.普拉特著,黃中憲譯:《太平天國之秋》。新北市:衛城出版,2013。
2.[美]吉瑞德著,段懷清、周俐玲譯:《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1。
3.[英]理雅各(H. E., Legge)著,馬清河譯:《漢學家理雅各傳》。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
4.任東升著:《聖經漢譯文化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5.伊愛蓮等著,蔡錦圖譯:《聖經與近代中國》。香港:漢語聖經協會有限公司,2003。
6.吳義雄著:《在宗教與世俗之間: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
7.岳峰著:《架設東西方的橋樑: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8.夏春濤著:《從塾師、基督徒到王爺:洪仁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9.夏春濤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洪秀全洪仁玕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10.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香港:蜂鳥出版有限公司,2021。
11.陳谷鋆著:《傳教士與漢學家:理雅各在中西文化上的傳譯貢獻》。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20。
12.曾銳生著:《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3。
13.湯清著:《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出版社,2009年。
14.劉紹麟著:《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2003。
15.鄭宏泰著:《何福堂家族–走在時代浪尖的風光與跌宕》。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1。
16.關詩佩著:《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
17.蘇精著:《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
中文期刊
18.江丕盛:〈作為《上帝形象》的人–基督教人觀的初深〉,《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通訊》,第4期(2003年),頁4–5。
19.余娟:〈理雅各翻譯活動的贊助體系及特徵分析〉,《湖北函授大學學報》(第31卷第3期),頁154–165。
20.譚樹林:〈英華書院遷港後的出版活動探究〉,《文化雜誌》(2017),頁14–24。
21.龔道運:〈理雅各與基督教至高神譯名之爭〉,《清華學報》(三十七卷第二期),頁467–489。
英文書籍
22.Bowman L. Marilyn.James Legge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A Brilliant Scot in the Turmoil of Colonial Hong Kong(Victoria: Friesen Press, 2016).
23.ChowAlexander, ed.Scottish Missions to China: Commemorating the Legacy of James Legge (1815-1897), (Leiden/Boston: Brill, 2022).
24.Ng Lun Ngai-ha,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5.PfisterF.Lauren.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26.Smith T. Carl.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27.Wong Man-kong.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 Publishing Co., 1996).
28.Wylie Alexander,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英文期刊、論文
29.Government Notificatio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7, no. 115 (12 October 1861), 315.
30.Sweeting Anthony, ‘With the ease and grace of a born bishop’? – re-evaluating James Legge’s contribution to secular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in Hong Kong.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45 (2005).
31.Lethbridge J. H., Hong Kong Cadets, 1862-1941,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10, 1970, pp.36-56.
32.Legge George,Lectures on Theology, Science and Revelation, ed. James Legge and John Legge (London: Jackson, Walford and Hodder, 1863).
33.Legge James:Letters on the Rendering of the Name Go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Hongkong: Hongkong Register, 1850).
34.Legge 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London: Trubner&Co., 60 Paternoster Row., 1861).
35.“Mission of Hung-Jin to Tae-Ping Wang, Chief of the Chinese Insurgents at Nanking,”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 no. 293 (October 1860).
36.Pfister. F Lauren, The Mengzian Marix for Accommodationist Missionary Apologetics Identifying the Cross-Cultural Linkage in Evangelical Protestant Discourse within the Chinese Writing of James Legge(1815-1897), He Jinshan(1817-1871), and Ernst Faber(1839-1899),Monumenta Serica, 2002, Vol. 50(2002), pp. 391-416.
網上資料
37.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James legge; Le Kin-lin: Sung Fuh: Woowan-sew.https://www.npg.org.uk/collections/search/portrait/mw42742/James-Legge-Le-Kin-lin-Sung-Fuh-Keen-Woowan-sew
38.PCLU(2021):英華傳奇:千里尋找香港字。英華書院校友會。https://ywcoba.com/2021/01/28/%E8%8B%B1%E8%8F%AF%E5%82%B3%E5%A5%87-%E5%8D%83%E9%87%8C%E5%B0%8B%E6%89%BE%E9%A6%99%E6%B8%AF%E5%AD%97/.
39.The British Columbia Review (2018): Resuscitation of James Legge.https://thebcreview.ca/2018/09/26/134-resuscitation-of-james-legge/.
40.Union Church.https://www.unionchurchhk.org/ministries/the-grace-of-giving/.
腳註 :
1. Lauren F. Pfister: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6.
2. Wong Man-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 Publishing Co., 1996).
3. Marilyn Laura Bowman. James Legge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A Brilliant Scot in the Turmoil of Colonial Hong Kong (Victoria: Friesen Press, 2016).
4. Lauren F. Pfister: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pp.10-11.
5. 岳峰著:《架設東西方的橋樑: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6.[美]吉瑞德著,段懷清、周俐玲譯:《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1),頁1-59。
7.理雅各從基督教家庭長大,是獨立教會(An Independent Church)的成員,他們「有相當強烈的傳教意識」。這家教會起源於一場亨特利的宗教運動,當地一位長老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牧者考里(Cowie)認為傳教工作應該由世俗人士擔任,並非神職人員的專利,信徒應當到異地傳教,繼而與長老會產生衝突,離開舊會另立門戶。事實上,理雅各也曾經對墨守成規的教義表達不滿,他認為蘇格蘭的國教會,即長老會過於嚴謹地從遵安息日文化體制,例如需要進行冗長的教會服務事宜和布道訓戒,他形容這使得「摩西的聲音常常壓倒了基督的聲音」,可見他對如何信奉基督教有着強烈的意識。岳峰著:《架設東西方的橋樑: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頁31;[美]吉瑞德著,段懷清、周俐玲譯:《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1),頁7-8。
8. 理雅各12歲進入阿伯丁語法學校(the Grammar School)學習拉丁語,14歲獲取獎學金進入阿伯丁皇家學院(the King’s College),1835年畢業時已經精通拉丁語和希臘語。對理雅各在學時期影響較深的作家,是16世紀蘇格蘭歷史學者和詩人布坎南(George Buchanan,1506–1582)。他曾經任教法國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大學,後來成為蘇格蘭王的老師,其文字受到歐洲廣泛的賞識。另外,他的治史特色是,對古典文獻(例如寓言)進行批判性的解讀,並不盲目跟隨古籍。理雅各在學經常利用拉丁語翻譯布坎南的作品、詩歌,並在進行練習的過程中認識了一些文本批評和語言文獻學的方法,多少影響了他日後理解中國經典文獻的內容。[美]吉瑞德著,段懷清、周俐玲譯:《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1),頁11-12;Lauren F. Pfister: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pp. 52-53。
9. [英]理雅各著,馬清河譯:《漢學家理雅各傳》(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理雅各與女兒,可參閱附錄五:理雅各及其女兒 Helen Legge(1860-1946)。
10. 據湯清的研究,馬禮遜的翻譯及著作有四種,包括翻譯聖經、關於基督教信仰和生活以及教會組織和崇拜的著述、關於聖經歷史和教會的著述、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著述如《華英字典》,最重要者應為第一和第四種,稍後我們會看見這些作品如何幫助傳教士在傳教和漢學上的事業。見氏著:《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出版社,2009),頁93-94。
11. 馬禮遜和米鄰在馬六甲的建設主要有兩項:第一,設立英華書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目的是「向中國青年教授英語和基督教原理,特別為傳教士和其他人士提供中國語言和文化方面的教育」,是一傳教和漢學的早期重要據點;第二,建立「恆河外方傳教士聯合會」(The Ultra-Ganges Missionary Union),所謂「恆河外方」是指恆河以東的廣大地區,包括中南半島、南洋、日本、琉球、朝鮮等地,宗旨是將倫敦會傳教士聯合在一起,以合作建立學校、神學院、舉辦期刊等,可惜最終因為內部分歧,在1819年前後有幾個傳教士離開。無論如何,馬禮遜和米鄰在馬六甲建立了一個基本的華南傳教體系。看吳義雄著:《在宗教與世俗之間: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1807-185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頁39-55。
12. 所謂「第一代新教傳教士」,即指馬禮遜來到澳門(1807年)至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年)這段時間,一批在受到滿清統治或影響的東亞地區的傳教士,他們通常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工作;南京條約(1842年)簽定至第二次鴉片戰爭這段時間則為「第二代新教傳教士」,換言之,理雅各當屬「第二代新教傳教士」。看Lauren F. Pfister, The Mengzian Marix for Accommodationist Missionary Apologetics Identifying the Cross-Cultural Linkage in Evangelical Protestant Discourse within the Chinese Writing of James Legge(1815-1897), He Jinshan(1817-1871), and Ernst Faber(1839-1899), Monumenta Serica, 2002, Vol. 50(2002), pp. 391-416.
14.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p. 47-49.
15. 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6), p. 16.
16. Lauren F. Pfister,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p. 116.
17. James Legge, “Notes on My life”, from 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6), p. 17.
18.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p. 12-21
19. 吳義雄著:《在宗教與世俗之間: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1807-185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頁39-42。
20. 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6), p. 6
21. James Legge, “Notes on My life”, from 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6), p. 9.
22. A letter written by James Legge to the missionary society on 15 March 1842, the LMS Archives, China General, Personal Box 9.
23. 譚樹林:〈英華書院遷港後的出版活動探究〉,《文化雜誌》(2017),頁14–24。
24. 岳峰著:《架設東西方的橋樑: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頁133。
25. 劉紹麟著:《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2003),頁103-104。
26. 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香港:蜂鳥出版有限公司,2021),頁35。
27. [英]理雅各著,馬清河譯:《漢學家理雅各》(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頁49。
28. [英]理雅各著,馬清河譯:《漢學家理雅各》(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頁50。
29. 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香港:蜂鳥出版有限公司,2021),頁61。
30. Lauren F. Pfister,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p. 26.
31.《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頁34。見附錄一:被理雅各帶往覲見英女王的學生。
32. 鄭宏泰著:《何福堂家族–走在時代浪尖的風光與跌宕》(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1),頁26。
33. 佑寧堂成立於1845年,為理雅各所設立的一間香港教堂,旨在利用中英雙語進行崇拜。參閱附錄二:成立於1845的第一代香港佑寧堂 (The Union Church)。
34. Lauren F. Pfister, Reconfirming the Way: Perspectives from the Writings f Rev. Ho Tsun-Sheen. Ching Feng: A Journal o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1993, vol 36(1993), pp.218-259.
35. Marilyn Laura Bowman: James Legge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A Brilliant Scot in the Turmoil of Colonial Hong Kong (Victoria: Friesen Press, 2016), 179.
36. 鄭宏泰著:《何福堂家族–走在時代浪尖的風光與跌宕》(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1),頁45。
37. 任東升著:《聖經漢譯文化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頁214。
38. 同上註。
39. 費樂仁:〈述而不作:近代第一位新教神學家何進善(1817-1871)〉載於:伊愛蓮等著,蔡錦圖譯:《聖經與近代中國》(香港:漢語聖經協會有限公司,2003),頁159。
40. 原文如下:「原夫聖書,乃猶太人所著,泰西諸國,咸譯土音,今譯漢文,閒有淺陋,並不敢增減其一字者,重原本也,迨後中華儒士,序而記之,註而釋之,而稍加潤色,令人了然於心目間者,則有 英國理雅各先生校之本焉,敝國教士,曾商於理雅各先生曰:本局仍照原文,請全刻其序註,則述而不作,而能使真神聖子聖靈之旨…理雅各先生答曰:善與人同,又何分畛域之見耶,遂梓而行之。」何進善著:《馬太福音註釋》。原文錄於:Lauren F. Pfister,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37.
41. Lauren F. Pfister,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230.
42. George Legge, Lectures on Theology, Science and Revelation, ed. James Legge and John Legge (London: Jackson, Walford and Hodder, 1863), xcviii. 根據費樂仁的研究,與理雅各關係親近,並同為服務於倫敦傳道會的岳父 John Morison, 早於1832年已經出版一本名為The Self-Existence of Jehovah Pledged for the Ultimate Revelation of His Glory to All Nations 的著作,肯定了「後千禧年觀」的主張,這無疑對理雅各神學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Lauren F. Pfister,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377.
43. 原文如下:I object to the idea of a premillennial advent of Christ, as contrary to the express letter of revelation... True we read, oftentimes, both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of the coming of the Lord, of the day of the Lord. But the terms refer to a providential manifestation, not a personal advent. So according to Isaiah’s predictions the Lord came in the overthrow of Babylon. So according to his own fore-announcement, the Lord came in the destruction of Jerusalem. See George Legge, Lectures on Theology, Science and Revelation, ed. James Legge and John Legge (London: Jackson, Walford and Hodder, 1863), pp.245-246.
44. 神之國,指福音言,福音乃神國之妙理,是故救主屢以此名稱之,義者,神命人當行之義道也,言人惟先用心,以求神福音之義道,而遵行之,則此世之衣服飲食,自加諸身,蓋遵而行之君子,至為餓殍者,未之有也。何進善著:《馬太福音註釋》。原文錄於:Lauren F. Pfister,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37.
45. 何進善《馬太福音釋註》的頁面,可參閲附錄六:何進善的《馬太福音》釋註。
46. 龔道運:〈理雅各與基督教至高神譯名之爭〉,《清華學報》(三十七卷第二期),頁467–489。
47. James Legge: Letters on the Rendering of the Name Go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Hongkong: Hongkong Register, 1850).
48. James Legge: Letters on the Rendering of the Name Go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Hongkong: Hongkong Register, 1850).
49. 江丕盛:〈作為《上帝形象》的人–基督教人觀的初深〉,《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通訊》,第4期(2003年),頁4–5。
50. 夏春濤著:《從塾師、基督徒到王爺:洪仁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1。
51. 夏春濤著:《從塾師、基督徒到王爺:洪仁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21。
52. 岳峰著:《架設東西方的橋樑: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頁68。
53. 夏春濤著:《從塾師、基督徒到王爺:洪仁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43。
54. 夏春濤著:《從塾師、基督徒到王爺:洪仁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42。
55. 夏春濤著:《從塾師、基督徒到王爺:洪仁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頁24。
56. [清]洪仁玕著:《資政新篇》,載入夏春濤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洪秀全洪仁玕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頁253。
57. [清]洪仁玕著:《資政新篇》,載入夏春濤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洪秀全洪仁玕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58. [清]洪仁玕著:《資政新篇》,載入夏春濤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洪秀全洪仁玕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頁254。
59. [清]洪仁玕著:《資政新篇》,載入夏春濤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洪秀全洪仁玕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頁254。
60. James Legge: 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Hongkong: Hongkong Register, 1852).
61. James Legge: 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Hongkong: Hongkong Register, 1852), pp.138-139.
62. 岳峰著:《架設東西方的橋樑: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頁61。
63. 鄭宏泰著:《何福堂家族–走在時代浪尖的風光與跌宕》(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1),頁43。
64. 鄭宏泰著:《何福堂家族–走在時代浪尖的風光與跌宕》(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1),頁44。
65. Marilyn Laura Bowman. James Legge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A Brilliant Scot in the Turmoil of Colonial Hong Kong (Victoria: Friesen Press, 2016).
66. 鄭宏泰著:《何福堂家族–走在時代浪尖的風光與跌宕》(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1),頁44。
67. Marilyn Laura Bowman. James Legge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A Brilliant Scot in the Turmoil of Colonial Hong Kong (Victoria: Friesen Press, 2016).
68. [英]理雅各著,馬清河譯:《漢學家理雅各》(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頁92。大部分學者都援引此說,只有蘇精持懷疑態度,他認為,如果理雅各有此嚴令,他的同事湛約瑟不至於違背其意之餘,還給予洪仁玕經濟支援。我認為,不論理雅各起初有沒有反對洪仁玕前往天京,他其後也表現出了支持洪仁玕幫助太平天國的態度,因此這無阻本文的討論。見蘇精:〈洪仁玕與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的交情〉,載氏著:《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
69. [美]史蒂芬.普拉特著,黃中憲譯:《太平天國之秋》(新北市:衛城出版,2013),頁119。
70. 蘇精:〈洪仁玕與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的交情〉,載氏著:《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
71. [美]史蒂芬.普拉特著,黃中憲譯:《太平天國之秋》(新北市:衛城出版,2013),頁118-122。
72. Lauren F. Pfister,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p.63. 理雅各還說他在這些著作中認得一些訓誡,洪仁玕曾經在香港有佈道過。
73. LMS/CH/SC, 6.2.c., J. Legge to A. Tidman, Hong Kong, 28 January 1860. 引自:蘇精:〈洪仁玕與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的交情〉,載氏著:《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頁174。
74. “Mission of Hung-Jin to Tae-Ping Wang, Chief of the Chinese Insurgents at Nanking,” 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 no. 293 (October 1860), p.277.
75. 蘇精:〈洪仁玕與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的交情〉,載氏著:《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頁182。
76. Lauren F. Pfister,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Frankfurt: Peter Lang, 2004), p. 66.
77. 岳峰著:《架設東西方的橋樑: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頁45-46。
78. 他在《中國經典》第一卷的序中,便開宗明義說道自己研究中國經書之目的:「直至能夠完全掌握中國傳統書籍前,都不能聲稱有資格傳教。」(He should not be able to consider himself qualified for the duties of his position, until he had thoroughly mastered the Classical Books of the Chinese)Jame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London: Trubner&Co., 60 Paternoster Row., 1861), vii.
79. 陳谷鋆著:《傳教士與漢學家:理雅各在中西文化上的傳譯貢獻》(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20)。
80. Jame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London: Trubner&Co., 60 Paternoster Row., 1861). 參閱附錄四:理雅各在《中國經典》感謝渣顛(Jardine)兄弟。
81. Jame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London: Trubner&Co., 60 Paternoster Row., 1861).
82. 余娟:〈理雅各翻譯活動的贊助體系及特徵分析〉,《湖北函授大學學報》(第31卷第3期),頁154–165。
83. 余娟:〈理雅各翻譯活動的贊助體系及特徵分析〉,《湖北函授大學學報》(第31卷第3期),頁154–165。
84. PCLU(2021):英華傳奇:千里尋找香港字。英華書院校友會。https://ywcoba.com/2021/01/28/%E8%8B%B1%E8%8F%AF%E5%82%B3%E5%A5%87-%E5%8D%83%E9%87%8C%E5%B0%8B%E6%89%BE%E9%A6%99%E6%B8%AF%E5%AD%97/
85. 譚樹林:〈英華書院遷港後的出版活動探究〉,《文化雜誌》(2017),頁14–24。
86. 譚樹林:〈英華書院遷港後的出版活動探究〉,《文化雜誌》(2017),頁14–24。
87. 參閱附錄三:理雅各《中國經典》中的香港字。
88. Wong Man-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 Publishing Co., 1996), 56
89. To The British Public, Interested in The Promotion of Christianity, Morals, And Useful Knowledge Among Heathen Nations, This Accoun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Is Respectfully Addressed (Londo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25), pp.5-6.
90. 吳義雄著:《在宗教與世俗之間: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頁232。
91. 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6), 54.
92. 理雅各曾經說:「(傳教)這項偉大的工作應該由本地人來做,他們本國人之間可以像兄弟一樣交談,充滿熱情、隨意而沒有偏見。」The LMS Archives, China General, Personal, Box 9. 引自岳峰著:《架設東西方的橋樑: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頁134。
93. 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6), 59.
94. Anthony Sweeting. ‘With the ease and grace of a born bishop’? – re-evaluating James Legge’s contribution to secular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45 (2005), pp.5-25.
95.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47-149.
96. Wong Man-kong. Christian Missions, Chinese Culture, and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 Study of the Activities of James Legge and Ernest John Eitel in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 (Ph.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 122.
97. Wong Man-kong. Christian Missions, Chinese Culture, and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 Study of the Activities of James Legge and Ernest John Eitel in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 (Ph.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 pp.127-128.
98. 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6), 50-51.
99. Eitel,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320.
100. 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6), 72.
101. Eitel,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321.
102.‘The New System prepared by Dr. Legg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61, 106.
103.‘The New System prepared by Dr. Legg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61, 106.
104.‘The New System prepared by Dr. Legg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61, 106.
105.‘The New System prepared by Dr. Legg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1861, 106.
106. Ng Lun Ngai-ha, Interactions of East and West: Develop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40-41.
107. Anthony Sweeting. ‘With the ease and grace of a born bishop’? – re-evaluating James Legge’s contribution to secular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45 (2005), pp.5-25.
108. 關詩佩:〈漢學知識與實用課程:理雅各的官學生譯員計劃〉,載關詩佩著:《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頁343–395。
109. 曾銳生著:《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3),頁17。
110. H. J. Lethbridge, Hong Kong Cadets, 1862-1941,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 Vol.10, 1970, pp.36-56; 曾銳生著:《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3),頁16–17。
111. 關詩佩:〈漢學知識與實用課程:理雅各的官學生譯員計劃》〉,載關詩佩著:《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頁372–373。
112. Wong Man-kong, Christian Missions Chinese Culture, and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 Study of the Activities of James Legge and Ernest John Eitel in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dis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7), 20; Anthony Sweeting. ‘With the ease and grace of a born bishop’? – re-evaluating James Legge’s contribution to secular and religious educatio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45 (2005), pp.5-25.
113. H. J. Lethbridge, Hong Kong Cadets, 1862-1941,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 Vol.10, 1970, pp.36-56; 曾銳生著:《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3),頁16–17;張連興著:《香港二十八總督》(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頁83。
114. 關詩佩:〈漢學知識與實用課程:理雅各的官學生譯員計劃〉,載關詩佩著:《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頁343–395。
115. James Legge,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A Lecture in the City Hall, 5 November, 1872,” China Review 1, no.3 (1872-1873), pp. 173-174.
116. [英]理雅各(H. E., Legge)著,馬清河譯:《漢學家理雅各傳》(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頁151。
117. “Government Notificatio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7, no. 115 (12 October 1861), 315.
118. “Government Notificatio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 7, no. 115 (12 October 1861), 315.
119. 關詩佩:〈漢學知識與實用課程:理雅各的官學生譯員計劃〉,載關詩佩著:《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7),頁372–373。
All articles/videos are prohibited from reproducing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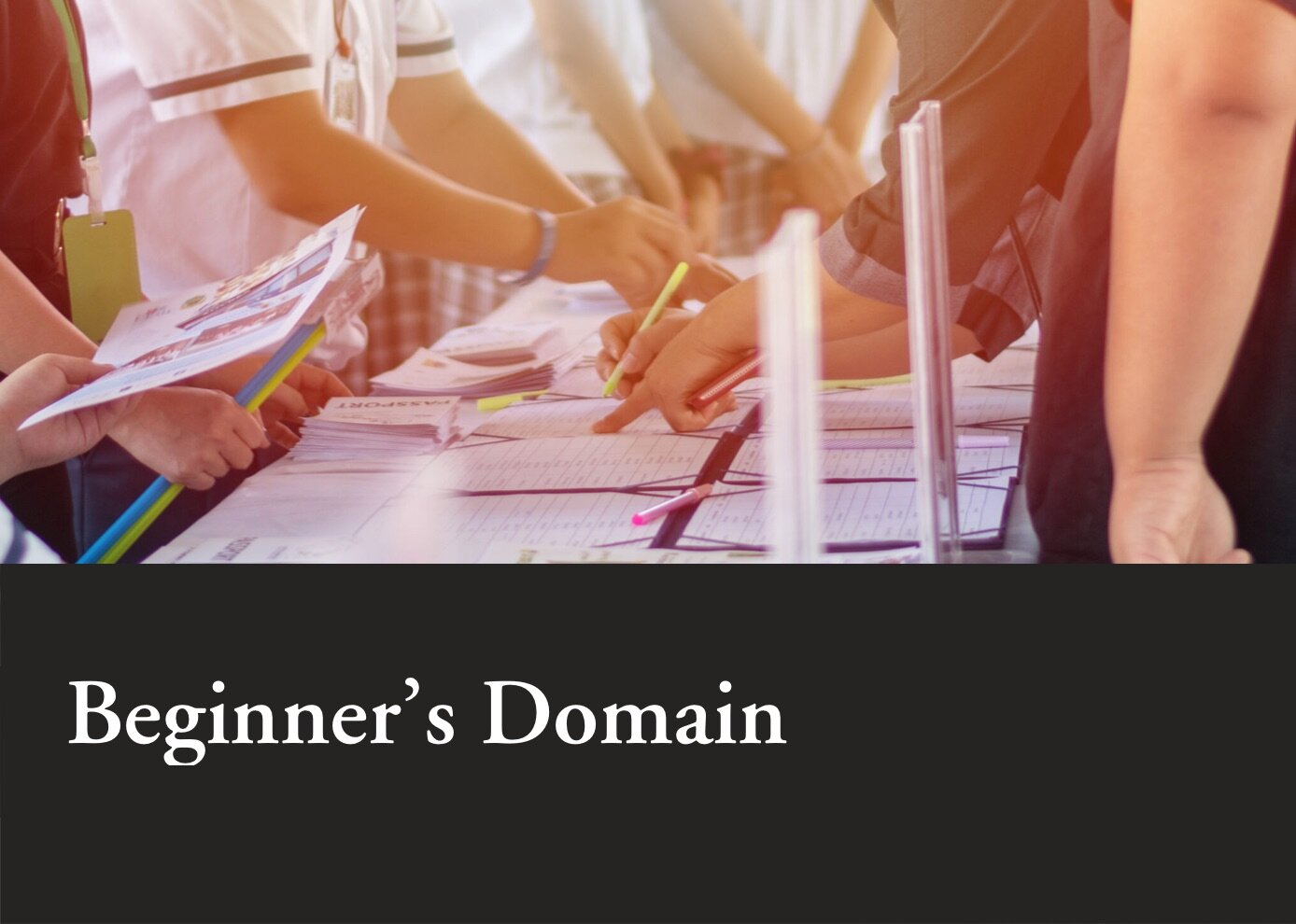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