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堯典》“安安”釋義〉
陳靖敏
《尚書·堯典》中的“安安”二字,歷來都有不同的說解和流傳版本,其中漢儒、宋儒、清儒、近人都有不同的解讀方式。而“安安”二字又有異文。以下會先探討“安安”的兩個主要版本流傳,說明在兩者之間取捨的原因。然後分析歷代主流的解讀方式,包括“安天下之當安”說和 “安安”二字合解的兩種理解。 “安安”二字合解,其中又有分歧,可以理解為對前四德的概括,也可以理解為堯的五項德性之一。而近人的理解,又有將融合前人“安天下之當安”與以“安安”為堯的德性的解讀方式。
《尚書·堯典》中的“欽明文思安安”一句,又作“欽明文塞晏晏”。在探討“安安”二字之義前,需要先在以上兩個流傳的版本中作取捨。〈考靈燿〉鄭玄(127-200)注曰:“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段玉裁(1755-1815)認為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不一致者,可從音韻入手。此法屬於聲訓,因聲求義,即取聲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來解釋字詞的意義。1段玉裁於《古文尚書撰異》於“欽明文思安安”下案:
《後漢書·祭祀志》注《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寬裕晏晏。”〈第五倫〉傳:“體晏晏之姿”,俗刻作“晏然”……此皆用《今文尙書》也。《爾雅》:“晏晏,溫和也。”古安、晏通用。2
段氏說明古代“安、晏”二字通假,漢人所作文章多引用今文《尚書》,乃因其時今文《尚書》列為學官,古文《尚書》則相對而言不受重視,這是歷史原因。時代背景對學術發展,文體特色,乃至版本流傳都有一定的影響。對字義的分析與研究,應盡量集中於字詞的本身。因此,在參考文獻材料的選取與分析上,也需要考慮其時代背景,盡量減低時代背景帶來的主觀因素,在環境因素上也要加以考慮,這一點會在後文作補充。段氏列舉《後漢書·祭祀志》注《東觀書》,〈第五倫〉等等,均屬漢人引用今文《尚書》之例,都以“安”作“晏”。林尹提出“凡字義必寄於其聲,所以就聲求義,乃能得字義的本原。”3指出了讀書時破假借的重要性。《漢書》,《古今人表》中的“晏孺子”,在清代,也通「安孺子」,是“安晏”二字相通的證明,故段氏引之以作說明,以便時人理解。“安、晏”同屬元韻,證明在上古音來說,二字音近,與《尚書》的成書時間相合。在同時期文獻中也有二字通假的用例,如《左傳·哀公六年》:“使胡姬以安儒子如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同一人物作 “晏儒子”。“晏儒子”作為人名,其可變性更低,是較為可靠的參照材料,“晏”寫作“安”,基本上可以排除字義改變的可能性。劉釗《甲骨文常用字典》:“安,通用為晏。”更說明二字的通假,在甲骨文時期已經出現。由此,可以證明〈堯典〉“晏晏”的版本,是源自於“安安”的通假。
唐人引用漢人所作之書緯,如“文塞晏晏”,不知其乃出自今文《尚書》,段玉裁、皮錫瑞(1850-1908)等學者,都指出“欽明文塞晏晏”是出自今文《尚書》4。漢初傳《尚書》之學始自伏生。《漢書·儒林傳》解釋了今文《尚書》的由來:
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5
今文《尚書》的成書是在漢文帝(劉恆,前203-前157;前180-前157在位),《尚書》在當時已經被認為亡佚,伏生在秦燔書之時藏之於壁,故得以保存。漢文帝得知伏生能夠講授,因而派晁錯受學於伏生,得《書》二十九篇。《文獻通考》一作伏生口授說,曰:“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6指出其中有夾雜齊魯的方言,有難以辨析之處。後來以孔壁古文《尚書》校之,亦有異文。而古文《尚書》的由來,《漢書·儒林傳》也有記載: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7
古文《尚書》是孔安國(前150-前90)從孔子舊宅墻壁中所得,並獻之於朝廷,由於孔壁本是以古文寫成,孔安國便將其從秦統一中國前使用的文字翻譯為今文,即隸書。但當時古文《尚書》未能立於學官,這也是它在當時流傳較窄的原因。以下是《文獻通考》對古文《尚書》流傳與興起的記載:
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為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至隋、唐閒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奧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且多古字是也。8
此段與《漢書·儒林傳》,都說明古文《尚書》未被立為學官。加上書寫字體冷僻,因而流傳甚窄,傳授者少。到隋唐時才開始受到重視。相對地,古文《尚書》所流傳的版本也沒有受到改動,而是維持原樣,仍是孔安國所改的隸書版本,沒有改從後來各朝的俗字,較大程度上保留了古文《尚書》文字表義的準確性和原始性。而古文《尚書》的“未嘗改以俗字”,是相對於今文《尚書》而言的。《尚書》的流傳,當以古文《尚書》為源頭。研讀經典或古籍,當取其本字,版本越早,所受到的改動便越少,又要避免受通假字之惑。而考慮到今文《尚書》或為伏生口授晁錯所得,文字出錯的可能性較古文《尚書》更高。故下文對“安安”的釋義,取“欽明文思安安”,即古文《尚書》的版本。
“安安”二字最早的解讀,當屬孔安國《傳》的“安天下之當安”,孔穎達(574-648)、林之奇(1112-1116)同採此說。孔安國《尚書正義》注曰:
勲,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欽明文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旣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9
孔安國以“曰若稽古”至“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為〈堯典〉的第一段。後文的理解也是以一段為整體,解讀“安安”二字。孔安國以“曰放勲”屬下句,後文的“言”字,說明他把“欽明文思安安”都理解為對“勲,功欽敬也”的解釋。他把整段的功績理解為堯仿效前人所得。引馬融(79-116)注,說明堯四德的具體指向,言堯既有“欽明文思”之四德,又能做到“信恭能讓”,故而其名耀及四海與天地。孔安國認為堯以“欽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在整體文意上,“安安”是指向前文的“勲,功欽敬也”,這是堯仿效前人之功績的成果。如此看來,孔安國是以“安安”分開作解的,前“安”為動詞;後“安”為形容詞,二字皆作安定解。“欽明文思安安”應作“欽、明、文、思,安安”。《說文》釋“安”曰:“靜也。从女在宀下。” 釋“靜”曰:“竫,亭安也。”釋“亭”曰:“民所安定也。”“安”字可遞訓為“安定”。可以作為孔安國說在“安安”字義上有其合理性的證明。
唯孔安國在以“安安”為堯仿效前人所得之功績的解讀上,尚有疑竇。在多家對〈堯典〉的注釋中,皆以“勲”屬上句,即“帝堯,曰放勲”,將“放勲”解讀為堯的名字,而非以“勲”單獨解釋作名詞“功勲”。在現今可見的《尚書》注本中,孔安國、孔穎達、蔡沈以“放勲”分開理解為 “仿效”與“功勲”,而孔安國與孔穎達兩家又是同源。“放勳”二字,在歷代的注釋中有兩種解讀,一為堯的名字,一為有實際意義的實詞。其中有實際意義的實詞又分為孔安國的“仿效前人的功績”,與蔡氏的“堯的德業”。孫星衍對此做出考證,認為“放勳”應釋作堯的名字。10如此,則二孔與蔡氏之說有誤。而孔安國以“放勳”為堯“仿效前人的功績”的說法,便不成立。因此,後文堯仿效前人的功績而安天下之當安的說法,失去了基礎。在〈堯典〉首段的文章結構上,“放勳”與後文亦沒有緊密的聯繫。
孔穎達《尚書注疏》,基本上遵從唐代注釋家“疏不破注”11的特點,在孔安國的解讀之上加以延伸,只是解讀孔安國的觀點,而沒有作任何改動。《尚書注疏》:
史將述堯之美……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心意恆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12
孔穎達是以“欽明文思”為四德,言堯以此四德安天下。孔穎達是以“欽明文思安安”為一句。《尚書正義》以“心意恆敬”釋“欽”。以“智慧甚明”釋“明”。以“發舉則有文謀”釋“文”。以“思慮則能通敏”釋“思”。孔穎達同時引鄭玄注說明四德的指向,是“欽明文思”。對於堯如何以四德安天下,孔穎達則結合後文作理解,認為後文是對 “安安”過程的描述與解釋。孔穎達《尚書注疏》卷二又注曰:
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13
此段說明“安安”之過程與具體對象,孔穎達認為堯“安”的對象是後文的“九族、百姓、萬邦”。堯作爲一國之君,能尊重德行超羣的人,讓他們幫助自己施行教化。用這種賢能的臣子對人民的教化,首先讓他們親近自己的九族。九族親戚蒙受教化,已經親密和睦了,又使他們和諧一致地顯耀於朝廷百官的同族。百官的同族親屬蒙受教化,有禮儀。再讓他們聚集協調遍及天下的諸侯國。這是一個由內到外的過程,堯先尊“克明俊德”之士,使之幫助九族的親睦,進而使百姓和睦,最後使萬國調和,這就是“安天下之當安”的完整過程。此說是建基於孔安國的理解之上的,可以與孔安國注歸為一說,由於孔疏很大程度上是解釋孔安國注的,因此相當於完善了孔安國的論述過程。
宋人林之奇的看法帶有典型的宋學色彩,《尚書全解》於“欽明文思安安”下注: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此其所以為大功也,大抵形容聖人之盛德……孔氏云:“安天下之所當安。然下文黎民於變時雍方,是安天下之所當安者。”此謂安安者,蓋言堯有欽明文思之四德,安而行之,非事於勉強,修為若孟子所謂性者也。14
林氏以“欽明文思安安”為堯德行之大者,又引孔安國注,解釋其“安天下之當安”一說。也就是說,林氏認同孔安國對“安安”的基本理解。後文是著墨於解釋“安安”背後的聖人內在的驅動力。林氏解經的方式與其他宋人非常接近,都是較為注重義理的闡發。林氏對〈堯典〉首個章節的理解,是堯聖人形象的體現。其中包括了四項德性,以四德安天下,是出於自然的行為。這種解釋方式,明顯受到宋學的影響,此說是出自於朱子對聖人的理解,此處不詳述,後文將加以解釋。聖人不需要後天的修習,這些德性都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本性,因此堯的功績,是本其本性而行之。雖然此說沒有反駁孔安國之說,將前“安”釋為動詞“使之安定”,後“安”釋為 形容詞“安定”,但林氏以聖人的德性解釋堯“安安”的行為,可以說是後文周秉鈞之說的雛形。林氏說雖突破前人所說,嘗試以德性理解“安安”,但在基本字義上的處理與前說無異,故仍與孔安國、孔穎達歸為一類。以解釋經典作為闡發個人思想的途徑,在宋學中非常普遍,雖說此法為闡釋經典提供了新的方向,但對文意的理解,則時有偏離或過分延伸。
在孔安國、孔穎達和林之奇的理解中,“欽明文思安安”一句,都應該斷作“欽、明、文、思,安安”,言堯以“欽、明、文、思”四德,安天下之當安。他們的學說雖然來自不同時代,其對《尚書》的理解或受時代的影響,但整體對“安安”的解讀方式都是“安天下之當安”。
在歷代對“安安”的解讀中,不乏將二字合解的。其中宋儒有朱熹(1130-1120)、蔡沈(1167-1230)等人;清儒有王鳴盛(1722-1798)。他們的解讀或有差異,但總體而言,都受到宋代心性之論的影響。以下分述之。
“安安”二字合解之說,實源自於朱熹。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於“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下注:
安安,無所勉強之貌。言其徳性之羙皆出於自然,而非強勉,所謂性之者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徳性而言也。15
朱熹對“安安”的解讀對宋學的影響頗深,多次被後學者徵引。朱熹將“安安”訓為“無所勉強之貌”,是將二字合解為形容詞,結合朱熹自己的理學思維,將“安安”理解為堯作為聖人的自然之德。朱熹的《近思錄》提出:“堯舜是生而知之……要之皆是聖人”16,可見朱熹認為堯作為聖人,其德性是與生俱來的。堯因為其源自於天的德性,所以能夠自然而然地做到“欽明文思”四德。在朱熹看來,“欽明文思安安”應斷作“欽、明、文、思,安安”,“安安”一詞,同時冠於前四德。與林氏不同之處,在於林氏理解為內在德性外顯的具體行為,朱熹則只理解為德性。蔡沈對“安安”的解讀與朱熹非常近似,是因其受學於朱熹,《書經集傳》更是受朱熹之命而著,其書自序曰:“《集傳》本先生所命。”17由此可見其師承以及著書原因。《書經集傳》注曰:
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其言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18
蔡氏的理解,是以“放勳”為堯的外在功績、德業,而這些行為都是其內在德性的外顯,而“欽明、文思”都是堯的內在德性。“安安”乃言堯的德行都是渾然天成的。此說的來源接近於朱熹“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19的觀點。蔡氏以“安安”作為“欽明、文思”兩項德性的總述,指出此二德皆堯生來便具有的。上文提及,“放勳”二字當釋為堯的名字,蔡氏說有誤。因而在段落的結構而言,與孔安國之說的解讀有同樣的問題。
清人王鳴盛對 “安安”的理解近於宋人。《尚書後案》於“欽明文思安安”下注:
又〈郅壽傳〉傷㥶晏之化,注引鄭〈攷靈燿〉注云:“道德純備謂之㥶,寛容覆載謂之晏。”是㥶卽思,晏卽安也。〈釋訓〉:“晏晏,温和也。”天地以温和覆載萬物,故寛容覆載爲晏。《傳》云安天下之當安,非也。20
王鳴盛引鄭玄注〈攷靈燿〉以證“安晏”二字通假,但沒有說明《尚書》流傳的今古文版本問題。引《爾雅·釋訓》、劉熙《釋名》,解釋“晏晏”的意思,認為“晏晏”有溫和,喜無動懼之義。王氏是引《爾雅》釋“晏晏”為“溫和”。以《爾雅·釋訓》考之,卻未能找到此句。〈釋訓〉:“晏晏溫溫,柔也。”古人引用他書,未必照式一樣地抄錄,多憑記憶引用。王氏或以化用的形式引用《爾雅》,以“溫和”釋 “柔”,其中緣由仍未可知。又,《爾雅》的流傳版本眾多,其中或有散佚,未能證明王氏所引之根據何在。“安安”二字,《爾雅》沒有將二字合解的,但有對“安”單獨說解的。《爾雅·釋詁》:“柔,安也。”又:“安,定也。”《易·繫辭下》:“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便作“定”解。在同時期的文獻,都以“安”為“安定”義。《詩經·大雅·皇矣》:“臨沖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鄭玄以“安然、舒緩貌”釋之。在先秦同時期的文獻中,以“安安”連讀的用例只有〈皇矣〉一例,若以此證明“安安”連讀,作“安然、舒緩貌”解,說服力不足,尚需更多例證。21
王鳴盛以鄭玄為得《尚書》之真義,故《尚書後案》一書,多次徵引鄭注,如“馬鄭注不可易也”等語,亦變相接受其以讖緯解經的治學之法,〈攷靈燿〉本身就是讖緯書。因此,王氏以鄭注〈攷靈燿〉“寛容覆載謂之晏” 作為正確的解讀方式。在此之上,加以延伸,得出“天地以温和覆載萬物,故寛容覆載爲晏”的理解,“安安”即是堯治理天下的態度。在“欽明文思”的解讀上,王氏引馬融鄭玄注,將四字各自理解為堯外在的行事方式、外在特徵。在“欽明文思安安”一句中,王氏以“安安”作為對“欽明文思”的總括,與蔡氏相同。唯蔡氏以“欽明文思”為四德,王氏理解為四個行事特點,前者側重於內在,後者側重於外在。通過對“欽明文思安安”整句的解讀,王氏認為孔安國“安天下之當安”一說不正確。
將“安安”二字合解的看法,多以宋儒或受宋學影響的學者為主,以宋學為治學之道,往往借經典以抒發己見,或以理學思想冠之以經,時有偏離文章本意的情況。雖說這種解讀方式可以為治經提供新的方向,卻難免忽略了字義等細節。在字義的考證上,還需要更多的證據和論述;在《尚書》的今古文問題上,也需有明確清晰的界線,方能使其“安安” 釋作“寛容覆載的自然之德”的觀點完全成立。
周秉鈞《尚書易解》於“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下案:
協,和也。黎,眾也……眾族昭明,又協調四方諸侯,眾民遞變至於和善。此言堯之德大,所化者廣也。釋“安安”之德。第一段,言堯之大德。22
周氏又案:“欽、明、文、思、安安,堯之五德也。”23“欽明文思安安”是總說堯之大德,大德分為五項。後文“允恭克讓”至“黎民於變時雍”,分述堯之五德。以“允恭克讓”釋“欽”。以“光被四表”釋“明”。以“格於上下”釋“文”。“克明俊德”至“平章百姓”四句釋“思”。言堯能自明大德,團結同族;族人既親,又辨明其他各族。周氏以〈堯典〉第一段中的句子,各自對應“欽、明、文、思、安安”之五德。“安安”是調和四方之族,使民向善之德,是堯內在德性的表現。周秉鈞對“安安”的理解,在詞義上近於孔安國“安天下之當安”之說,同是前“安”為動詞,後“安”為形容詞。不同之處在於經義上的進一步解釋,吸收了林氏之說,認為由堯的德行,外顯為“安天下之當安”的功績。考之以〈堯典〉的經義,鄭玄、馬融等漢儒,林之奇、朱熹等宋儒,王鳴盛等清儒,都認為〈堯典〉第一段是頌揚堯的德性與功績。然各人對文章結構的理解則各異。孔安國等人以“安安”為功績,以“允恭克讓”加上堯有的四德,解釋堯能夠使光輝遍佈四方的原因,但後文又解釋為堯的功績,難免使文意割裂。周氏在“安天下之當安”的基礎上,將其理解為堯內在的德性,而與前文“欽明文思”的解釋方式也相同,則於文意及文章整體結構而言更為通順。
如果將“安安”單純理解為功績,則“安安”二字與前文割裂。如果將“安安”理解為德行,則〈堯典〉首段整體都是說明堯的德行,是先總說堯五德之名目,再各自具體分說五德的具體意義與體現,在文章結構上較為工整完善,在經義上也能通順。周氏之說,比孔安國更為完善。
《尚書·堯典》中的“安安”二字,在今文《尚書》中也作“晏晏”,根據《尚書》今古文的來源,並考慮到它們文字的準確度及對字形的書寫,決定取古文《尚書》的“安安”版本。在“安安”的三種主要解讀方式中,各有側重的方向,以致解經的方式無絕對的對錯。唯研讀經典需要還原其原本面貌,最大程度上保留原文文意,因此宋儒“安安”二字合解的解讀未必是最優先的選擇。孔安國等人的“安天下之當安”說,內部邏輯完善,於字義可通,也有文獻用例證明,卻在結構上未能結合文章的上下文。此說未達到完善,但作為最早的《尚書》注解,孔安國的理解是值得參考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對後世的解讀方式起到奠基的作用。於孔安國之說的基礎上,周秉鈞以“安安”二字為堯的五項德性之一,能夠結合上下文意,邏輯自洽,完善了孔安國的“安天下之當安”說。
書籍
(漢)孔安國:《尚書注疏》(阮刻本)。
(漢)班固:《漢書》(武英殿本)。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日本覆印宋本)。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
(宋)朱熹:《近思錄》(四庫全書本)。
(宋)朱熹:《詩集傳》(中華學藝社借照東京靜嘉堂文庫藏宋本)。
(宋)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宋刊浙本)。
(宋)林之奇:《尚書全解》(四庫全書本)。
(宋)蔡沈:《書經集傳》(四庫全書本)。
(清)王鳴盛:《尚書後案》(清乾隆四十五年禮堂刻本)。
(清)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清光緒二十三年刻師伏堂叢書本)。
(清)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清乾隆道光間段氏刻經韻樓叢書本)。
(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冶城山管本)。
林尹:《訓詁學概要》(台灣:正中書局,2007年10月)。
周秉鈞:《尚書易解》(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6月)。
夏征農,陳至立:《大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9年11月)。
註釋
1. 夏征農,陳至立:《大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9年11月)。
2.(清)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清乾隆道光間段氏刻經韻樓叢書本),卷1,頁7上。
3. 林尹:《訓詁學概要》(台灣:正中書局,2007年10月),頁72。
4.(清)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清光緒二十三年刻師伏堂叢書本),卷1,頁13下: “今文作‘欽明文塞晏晏’。”
5.(漢)班固:(32-92):《漢書》(武英殿本),卷30,〈儒林傳〉第17。
6.(宋)馬瑞臨:(1254-1323):《文獻通考》,卷177,〈經籍考四〉。
7.(漢)班固:《漢書》(武英殿本),卷30,〈儒林傳〉第23。
8.(宋)馬瑞臨:《文獻通考》,卷177,〈經籍考四〉。
9.(漢)孔安國:《尚書正義》(日本覆印宋本),卷2,頁42上。
10. (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冶城山管本),第一上,頁6上,考證曰:“《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云放勳,堯名者。”《大戴禮·五帝德》、《孟子·萬章》、《春秋繁露》等書,都將“放勳”解釋為堯的名字。
11.(清)桂文燦《經學博采錄》卷3云:“唐人作疏, 惟知疏不破注。”(清)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23云:“疏不破注,此義疏之例也。”(清)皮錫瑞《經學歷史》云:“案(孔疏)著書之例,注不駁經,疏不駁注,不取異義,專宗一家。” 這些都可以作為孔穎達疏遵守“疏不破注”原則的補充說明。
12.(唐)孔穎達:《尚書注疏》(阮刻本),卷2,頁31下。
13. 同上注。
14. (宋)林之奇:《尚書全解》(四庫全書本),卷1,頁17下。
15.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卷65,頁5下。
16. (宋)朱熹:《近思錄》(四庫全書本),卷14,頁231下。
17. (宋)蔡沈:《書經集傳》(四庫全書本),頁2上。
18. (宋)蔡沈:《書經集傳》(四庫全書本),卷1,頁3下。
19. (宋)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宋刊浙本),卷65,頁7下。
20. (清)王鳴盛:《尚書後案》(清乾隆四十五年禮堂刻本),卷1,頁6下。
21. (宋)朱熹:《詩集傳》(中華學藝社借照東京靜嘉堂文庫藏宋本),卷16,頁378,釋“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曰:“安安,不輕暴也。”《毛傳》不釋“安安”,“安安”的解釋不明確。“不輕暴”之說,亦與“安然、舒緩貌”有異。如果將 “安安”釋為安然、舒緩貌,與文意不盡相合。因此,若以此例證明王氏之說,尚待考證。
22. 周秉鈞:《尚書易解》(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6月),頁10。
23. 同上注。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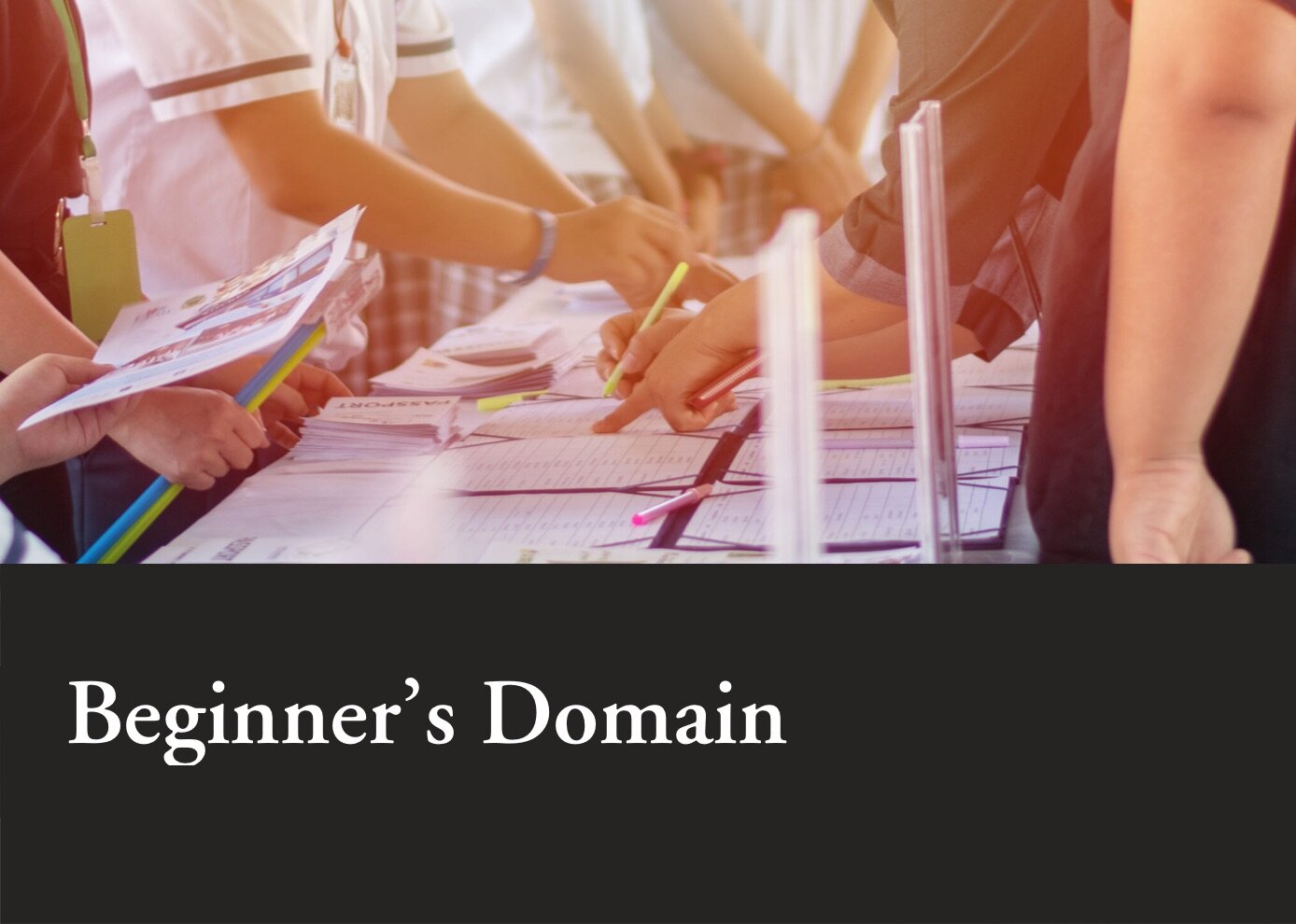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