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明清戲曲批評中對“音樂與敘事”一概念的討論〉
楊豪峰
本文探討戲曲批評中音樂與敘事的關係。追溯了學者對於戲曲中音樂和敘事如何交織的理解的演變,從早期對音樂具有"戲劇性敘事"特質的觀察,到更明確地認識到"言語和歌唱的敘事語言"。本文接著探討曲論家是否(或如何)在其批評論述中處理了這個"音樂和敘事"的層面。發現評論家通常間接地討論這一點,通過對劇作家技巧的批評,認為對音樂和敘事結構關係的粗心處理削弱了這種藝術形式。
關鍵字:戲曲,戲曲批評,音樂,敘事
戲曲是一結合音樂和敘事的文學。早於1970年,Johnson, Dale R.(1970)雖然沒有直接探討音樂與敘事在戲曲中如何產生作用,但已經在其研究之中將“諸宮調”一詞,翻譯為“dramatic narrative”1,此舉足以證明其時作者已有一定的意識認為戲曲中的音樂可以被理解為具有敘事的特質。及後的研究,要到2005年,Tian,M.(2005)則更明確地指出“narrative language of speech and singing”一語2,直接將“singing”即音樂,去定性為一種語言,一種敘事性的語言。直到Schoenberger, Casey(2024)最近的新作之中,通過比較北曲和南戲的音樂性質,去言及到北曲具有“grand melodies that tell a story”3,此言即使將範圍縮窄到北曲,但其言論仍未離開“音樂能敘事”的立場。不過,以上所說的“音樂與敘事”是於戲曲本身而言,但可見其為戲曲的主要性質,而作為副產品而生的戲曲批評究竟有無注意到這個特質,是可以發起疑問的。
在針對戲曲批評的研究之中,學者對於批評話語於此的觀察的研究並沒有太多。簡貴燈的一篇論文中曾提及:“隨著‘戲劇性’置換了‘音樂性’成為戲曲評價標準,‘曲本位’下的‘曲論’便嬗變為‘劇學觀’下的‘劇評’了。”4戲劇性其實與敘事並無太大分別,簡氏於此沒有探討音樂和敘事如何被並列論述,而且認為在曲論中於這個領域上的批評是具有一種遞變的趨勢,音樂和敘事並非互相交叉出現在批評話語當中,反而通過轉變二者的觀念,由注重音樂的曲論,趨向聚焦敘事的劇評。簡氏這一形式的看法並非獨一,於其前的張萍已經有類似的探討方向,她在其論文中的研究物件雖為呂天成《曲品》,但在論述過程中有提及到王驥德(?-1623)《曲律》,且更說明其與《曲品》“共同啟動了中國代戲曲批評從‘曲’的意識到‘劇’的觀念的至關重要的轉折”5,可見張氏此說已經有簡氏該論的跡象。可是,二者的研究皆未有完整地指出和解答一些問題:戲曲批評之中有否觀察到“音樂與敘事”?如有,他們又會對此作出怎樣的論述?此二問題,本文以下會以各種曲論原文為主要研究物件去嘗試為其進行解答。
戲曲批評之中,對於“音樂與敘事”的論述之中,並非如此直接地描述二者關係,但是他們會通過不同的書寫和表達方式去暗地裡探討“音樂與敘事”的這一特質。首先,他們其中一種表達是以反面的語言去指責劇作家等人的寫作手法,認為他們的胡亂寫作導致“音樂與敘事”此一特性被影響。這一類的批評雖然不會顯然地確“音樂能配合敘事”的這一論述,但可以透過對這些理解的進一步解讀,便可以得出他們對“音樂與敘事”的看法。
王驥德《曲律》〈論章法〉:
“只漫然隨調,逐句湊泊,掇拾為之。非不一間得一二好語,顛倒零碎,終是不成格局。”6
如前文所提到,王驥德的戲曲批評已經觸及到敘事的研究,在其主要作品《曲律》之中,於敘事相關的篇章則為〈論章法〉一節,在此一節之中,王驥德雖然主要說明在戲曲寫作之中應該如何安排劇本中“事”的安排,但是在其批評話語中,筆者發現他在無意中的述說中,碰觸到關於音樂的說明,而此節正是在論述戲曲中的敘事性,因此,王驥德此處對音樂的說明則會連系到敘事的探討,亦從而可以從中觀察到王驥德於其中如何討論“音樂與敘事”。
在以上所引的《曲律》原文當中,王驥德其實是在指:部分的作家隨意根據律調,每一句的曲詞都是湊成掇拾,即使期間的字句中有一二優美的句子,但宏觀地閱讀時,它們其實皆是顛倒零碎,沒有“格局”可言。“格局”一字,與“章法”一樣,同樣對結構敘事的一種指代說明。王驥德在此中認為作家們沒有認真謹慎去看待調律間的填寫,這種書寫的態度導致曲詞與事之間不能配合,不能成為一個可觀的格局,最後出來的作品頂多只有句子上的“好語”。王驥德的說法,劉二永有一概括式的觀點: “不同於樂府,在劇戲中,曲的結構要依事的結構來安排,也就是曲、事的關係是曲依事。”7劉氏之說並非無可取,如以上引文中王驥德批評在曲詞上的湊作,格局的不成亦因此而起。由此可見,王驥德的論述中根據律調而作的曲詞需要作家的嚴謹看待,反之則會影響敘事性的體現,嚴重者會失去敘事的可能。
沈寵綏(?-1645) 《度曲須知・弦律存亡》:
“詞人率意揮毫,曲文非盡合矩,唱家又不按譜相稽,反就平仄例填之曲,刻意推敲,不知關頭錯認,曲詞先已離軌,則字雖正而律且失矣。”8
沈寵綏這一段論述並非以敘事為出發點,從其出處〈弦律存亡〉一章的名字可知,沈氏此段論述的主要著眼點應該與音樂有關,甚至可以說沈氏從音樂方面出發,在論述的過程略為提及到與敘事相關的論點,而這個可能偶爾為之的說明,則可以作為一個切入點去討論,沈氏在批評當中,如何從劇作家的作法,繼而涉及到“音樂與敘事”。
沈寵綏大致上的論點如下:當時的詞人(即劇作家等人)隨意寫作,未必合乎曲文在格律上的規矩,而負責演唱之人亦沒有按照真正的曲譜進行調整,倒是按照作家那套隨意的作品演出,結果造成“關頭”不能被清晰分辨,口中所唱的曲詞亦不合規矩,雖然文字上的書寫合乎雅正,但在音律上卻失之千里。沈氏在論述開首與王驥德一樣,先批評當時作家的任意寫作。不過,及後的論述,沈氏則著眼于曲文在音樂上的規矩,而將此責更推及至表演者身上,指摘他們不按譜去為作家的錯誤產物做調整。沈氏認為作家和表演者在這種情況下的所作所為,令到“關頭”和曲詞發生錯誤。論及此處,沈氏則牽連到敘事身上,即“關頭”一詞。“關頭”與前文王驥德的“章法”一般,同樣是鋪排故事和故事結構的指代名稱,因而可以推論沈氏此說則強調了,曲詞在音樂上如果胡作非為,則會影響故事結構的清晰,亦即有礙於敘事,因為曲詞在戲曲中是能發揮敘事的功能。9沈氏的反面說明,雖只有只言詞組,但說明了曲詞需要被適當配合音樂,敘事結構才能被清晰地體現。
馮夢龍(1574-1646)〈大霞新奏序〉:
“又或運筆不靈,而故事填塞,侈多聞以示博;章法不講,而餖飣拾湊,摘片語以誇工:此皆世俗之通病也。作者不能歌,每襲前人之舛謬,而莫察其腔之忤合;歌者不能作,但尊世俗之流傳,而孰辨其詞之美醜。”10
馮夢龍于此大段的論著中,“音樂與敘事”於其間的論述實際上不太明顯,但在其論述之間,“音樂與敘事”二者所屬的元素交叉出現於此間,因而,通過額外為其所做的文本連結,可能從中亦隱約能知道馮夢龍如何牽涉到“音樂與敘事”。
馮夢龍開首已經提到,“故事填塞”由於“運筆不靈”,劇作家等人希望炫耀其博學,從而不講章法,以致東湊西湊,“摘片語”去顯露自己的優秀字句。繼而馮夢龍分開作者和表演者兩種戲曲相關人物,前者沒有表演的能力,只會依照前人的錯漏,導致腔調的不合。後者則不懂創作,只會按照世俗間的本來面貌,而沒有能力辨析曲詞中的好壞。
所謂“運筆”其實指向後文所寫的“作者”,因為如馮夢龍所言,表演者是不能創作的,因而能“運筆”的,必然是作者。不過,馮氏論調中的作者是一羣不具備足夠音樂知識和只顧標榜自己博學的人,在馮氏眼中,皆因有這樣的劇作家,因而令“故事填塞”、“章法不講”。故此,“音樂與敘事”的論述則變得明顯,在馮氏的說明中,敘事被忽略而致“填塞”,實取決於作者的音樂知識和書寫心態。沒有音樂知識而又自大的作者,只會重複前人的問題,徹底無視劇作中的音律錯誤。馮夢龍批評中的“音樂與敘事”則如上所說。
李漁(1611-1680)《李笠翁曲話》:
“嘗讀時髦所撰,惜其慘澹經營,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弦、副優孟者,非審音協律之難,而結構全部規模之未善也。”11
李漁的論著中,對於“音樂與敘事”較為隱晦,如引言所說,需要讀者進一步的解讀,從中可能可以得出一個不是斷章取義而成的結論,而該結論則有機會得出李漁是有論述至“音樂與敘事”的。引文當中某些重點字眼的頻繁出現,如“經營”、“結構”、“規模”等等敘事形式上的名詞,可以得知李漁此處是從敘事出發,在話語之間談及到音樂性。
李漁認為:時人所作的曲,在經營上雖有用心,但只能“慘澹”形容,引致不能與管弦音樂配合,無法為優孟等演藝人員作表演,這並非在音律上難以配合,而是在結構上的規模並未盡善。在最後一句之中,李漁看似排除了音樂在此間的影響力,直言與音律的難處無關,不過,當細察其因果邏輯,李漁其實是替換了角度,將“音樂與敘事”的關係,確定為敘事影響音樂的觀點。回看其前文的“慘澹經營”,這是因,而此因則導致其後“不得被管弦”,詳解的話即是說當戲曲中的規模結構“未善”,形成“慘澹經營”的狀態之時,便會滯礙了在表演中伴奏者的演出,亦即音樂的進行會受敘事好壞所擺動。因此,從而可以得知,李漁於此的說法,通過重新排列其邏輯組合,當中“音樂與敘事”的探討就能明確的顯現,而且更是有一新角度,不再是音樂帶動敘事,而是敘事會成為音樂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
何良俊(1506-1573)《四友齋叢說・詞曲》:
“他如〈走雨〉、〈錯認〉、〈上路〉、館驛中相逢數折,彼此問答,皆不須賓白,而敘說情事,婉轉詳盡,全不費詞,可謂妙絕。”12
何良俊此段曲論是對於《拜月亭》一戲的評價,此處為節錄,全段的評價在學術上亦有所研究。李克和首先提到:“何良俊之所以認為《拜月亭》勝於《西廂記》,其根本原因就是《拜月亭》的唱詞具有高度的敘事性。”13其後,陳維昭有較完整的說明:“在敘事修辭的層面上,他不以南北立論,他肯定《拜月亭》等南戲,並以之否定《西廂》、《琵琶》。他在戲曲史上首次提出《拜月》、《西廂》、《琵琶》優劣論。”14從二人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些何良俊論著的額外資訊:何氏對於《拜月亭》的評論是基於其敘事性,尤其是劇中唱詞的修辭,藉此認為《拜月亭》較他劇優勝。
當我們將關注點放回以上的引文時,其中的論述則為何良俊的主張提供了例子。何氏認為《拜月亭》的數折中的問答,沒有使用賓白,反而在沒有多餘曲詞的書寫下,詳盡地敘說情事。曲詞作為配合音樂而生之物,固然有其當中的音樂性,而且如前面所引劉二永的觀點:曲詞具有敘事性。《拜月亭》於該數折中的編排,借助有音樂性的曲詞為主要敘事工具,令何氏因而認為此舉令敘事婉轉,作出一個褒義的評價。同時,何良俊的此一評價亦體現出他的論調涉及到“音樂與敘事”的層面,他察覺到作為音樂元素的曲詞,在《拜月亭》一劇中被運用妥當,從而產出敘事良好的效果。
戲曲文本,即劇本上的文句雖由劇作家所定,但其並非一成不變。在該劇本被人選擇去演出時,其間劇本內容則會有可能遇到被更改,有機會在表演時演員即興改變,亦有機會在表演前被表演者眾人刻意地更改。在某些著名劇本能夠得以流傳的時候,在悠長歷史中,基於版本、流傳史等等的因素,內容受到改變的機會更大,不過本文並非在探討劇本內容改變史,因而此處略談。這種改變固然亦受到曲論家的目光注視,他們亦注意到劇本內容在改變前後對劇本本身的影響,甚至有的更留意到其間可能涉及“音樂與敘事”。
茅元儀(1594-1640)〈批點牡丹亭記序〉:
“雉城臧晉叔以其為案頭之書,而非場中之劇,乃刪其采、剉其鋒,使其合於庸工俗耳。讀其言,苦其事怪而詞平,詞怪而調平,調怪而音節平,于作者之意漫滅殆盡,並求其如世之詞人俯仰抑揚之常局而不及。”15
茅元儀此論見於其批點牡丹亭之時,茅氏的批評話語較前文所引眾人的文本都要長,因其於其中使用連續論證手法,去達致他的最後觀點。因此,需要通過理解其完整的論證過程,從中才能得知茅元儀在批點牡丹亭之時,如何被啟發到“音樂與敘事”相關的探討。
茅氏以臧晉叔為論述開端,臧晉叔即臧懋循(1550-1620),是《元曲選》的編者。茅氏提到臧晉叔曾認為《牡丹亭》是案頭文學,不能成為表演劇本,因此便“刪其采,剉其鋒”,其實即是對劇本進行了改動,令其能夠合乎“庸工俗耳”,也就是表演者和普通觀眾。茅氏隨即對臧氏的改動作出批評,提出“事怪而詞平,詞怪而調平,調怪而音節平”的一連串話語,續再說明被改動後,作者本意“漫滅殆盡”,劇本亦不及時人“俯仰抑揚”的常態。
茅氏的批評如何和“音樂與敘事”有關?答案需要先從那冗長的因果關係開始說明,茅氏後文的一切批評都是針對于臧氏所作的改動,而這個改動首先導致“事怪”,“事怪”是何意?其實即是沒有做到“俯仰抑揚”,換句話說,可以藉此作一個推論:臧氏所作的改動,導致《牡丹亭》的“事 ”未能抑揚頓挫,亦即故事鋪排上失准,也就是說敘事出現問題。而敘事一發生怪異的情況,則破壞了後面的“詞”、“調”和“音節”,尤其是後二者,是明顯屬於音樂範疇的元素,更甚,則是最終引致作者本意“殆盡”。因此,藉著拆解茅氏的論述,可以清晰知道茅氏指出了敘事被刪改所影響,便會導致後面一連串在音樂上的破壞,亦即是在討論“音樂與敘事”。
毛聲山(1632/1633-1709)〈第七才子書琵琶記批語〉:
“《西廂》純用北曲,每折自始至末,止是一人所唱,則其章法次第,井然不亂,猶易易耳。若《琵琶》則純用南曲,每套必用眾人分唱,而其章法次第,亦自井然不亂,若出一口,真大難事。試看李日華改《西廂》曲為南調,雖便於梨園之唱演,然將原曲顛倒前後,畢竟不免支離錯亂,然後歎《琵琶》之妙為不可及。”16
毛聲山此論是源於其對《琵琶記》的批點,從中涉及到戲曲中的南北之分,尤其是在音樂上。因此毛氏此論是從音樂性出發,通過比較二劇音樂性,從中帶出如經妄意更改,敘事結構則會受到牽連。
毛聲山首先帶出《西廂記》一戲,言及其為北曲的性質和表演手法,藉此表達其“章法次第,井然不亂”,而後則論至《琵琶記》,點出南戲的性質,同樣引致“章法次第,井然不亂”,批語最後,提到李日華為了便於歌唱對《西廂記》的改動,此舉導致“支離錯亂”,藉此烘托出《琵琶記》之可觀處。
“章法次第”,顯然地是在討論戲曲劇本中的敘事,至於“音樂與敘事”,則聚焦於批語的最後部分,即對李日華(1565-1635)的批評。毛氏因應李日華改動,述說他改動本為北曲的《西廂記》至南調,亦即是說音樂在此處發生了改變,而這個改變亦搖擺了毛氏在敘事上的批評,由“井然不亂”變至“支離錯亂”。毛氏此處的評價,明顯表達了他認為音樂有無適當搭配是會極大程度地牽連敘事結構,章法是井然還是支離,取決於曲調有無合法地使用。李日華錯誤地更改《西廂記》便是毛聲山提出的著名例子。
孔尚任(1648-1718)〈桃花扇凡例〉:
“各本填詞,每一長折,例用十曲,短折例用八曲。優人刪繁就簡,只歌五六曲,往往去留弗當,辜作者之苦心。”17
具有作者身份的批評者,在戲曲批評中並非罕見,孔尚任便是一例。孔氏在《桃花扇》的開端寫下這個〈凡例〉,於其中,他批評了一些當時表演者的行為。如果嚴格來說,孔氏此論的出發點是表演者,他藉優人的批評,希望自己的作品《桃花扇》不會遭受同樣的妄作。而孔氏從表演者出發的批評,亦無意間涉獵到敘事層面,而這種涉獵同樣觸及到音樂的元素。
孔尚任在〈凡例〉中提到:每一個劇本在被填詞之時,每一折中都會用上十首曲,如果該折為短,則減少至用八首曲。不過,“優人”,即當時的表演者,為了簡便演出,作出與李日華相似的行為——刪改劇本中的繁瑣處,只唱其中的五至六首曲。至此,“優人”的舉動令戲曲表演“去留弗當”,辜負作者的苦心。
孔尚任此段的論著,重點在更改後的“去留弗當”,“去留”不妨可以理解為劇情故事上的不同趨向,簡言之,即是敘事。“去留弗當”,即是在敘事失去了恰當的處理。之所以會敘事不恰,就是因為更改後,一折之中,曲的數目被改變,由八至十首,改至五至六首,即是說在音樂上的表演的不同,則會令到敘事上產生變化,而音樂變少,變簡,就導致孔氏所言的“去留弗當”。由此,清晰地可以觀察到孔尚任將敘事的關注歸究於音樂上的編排,當音樂因為表演者的纂改而失去合適的編排時,良好的敘事便會失效。
戲曲中所指的“音樂”可以包含很多方面,除了平仄、工尺、宮調等等,音韻亦可以被視為“音樂”的一部分,在填曲的時候,劇作家很可能需要遇到用韻的機會。而戲曲批評者等人,亦同樣留意到這一情況,在他們的論述之中,用韻也會被提及,而且有的更亦會涉及到“音樂與敘事”的說明。
徐復祚(1560-1630)《三家村老委談》:
“《琵琶》、《拜月》而下,《荊釵》以情節關目勝,然純是倭巷俚語,粗鄙之極;而用韻卻嚴,本色當行,時離時合。”18
徐復祚此論在評價三出不同的戲:《琵琶》、《拜月》、《荊釵》,而徐氏的主張主要是由敘事為出發點,在論述當中涉及到“用韻”一事,因而由此碰觸到“音樂與敘事”的特質。
徐復祚於其中認為:相比起《琵琶記》何《拜月亭》,《荊釵記》因其“情節關目”即敘事結構而優於前二者,可惜其用語低俗,但惟它能夠嚴謹遵守“用韻”,以“本色”書寫,形成“時離時合”的狀態。學者高暢曾言徐復祚的言論:“表示《荊釵》雖然語言不佳,但其情節內容高於《琵琶》《拜月》,可見徐復祚認為情節內容極為重要,高於音律和語言。”19
高暢言及徐復祚主張情節較音律重要,此言值得商榷,因為在以上徐氏的引文中,《荊釵記》雖以情節勝於二劇,但他亦提及用韻一事。徐氏此處對於二者的連系沒有明確的描述,但基於前文何良俊對於《拜月亭》音樂性曲詞的讚賞,徐氏仍能在《拜月亭》後指出《荊釵記》的用韻一事,可見,徐氏即使未能明晰地指出“音樂與敘事”,但仍然能同時道出用韻和敘事二者的評論。
宋徵壁(1602-1672)《客問十則》:
“夫才多則氾濫而溢格,才短則單弱而不及格。故其發端也貴渾,其承遞也貴圓,其用韻也貴和,其鎖尾也貴矯健而有餘思。”20
宋徵壁此論是從劇作家本身的才力出發去探討劇作家的才學如何影響劇作本身,而在論調之中,“音樂與敘事”則於其間被略為說明,另外,相關的論述的風格也類似茅元儀的一連串表達方式。
宋氏論述中的重點為自“故其發端”開始,他於其間述說了“發端”、“承遞”、“鎖尾”等等敘事性的元素,亦即是在說一劇中的起承轉合。在宋氏的說明直至不只是這些字眼,在字句間他書寫了一句“其用韻也貴和”,即是強調在“用韻”上需要達致“和”的境界,而這個“和”的狀態是存在於敘事當中,而這個敘事也有相應特定目標境界:“渾”、“圓”、“矯健而有餘思”。因而,從宋氏這種書寫方式的曲論當中,可以知道他其實在認為在有序良好的敘事之中,也需要注重“用韻”一事,亦同樣為其定下“和”的標準,從而,宋氏通過此種表達去致使其論著牽連到“音樂與敘事”的討論當中。
“音樂與敘事”,作為戲曲中的主要性質,戲曲本身在創作中固然會有所呈現,因為其本身就是二者的結合,如胡健生所言:“劇曲中必然含有大量敘事成分,因此具有很強的敘事功能。”21這樣明顯的特質當然能夠會被戲曲批評者所留意,但他們未必有強烈的意識,認為自己在探討“音樂與敘事”。不過,通過以上對各種類別的引文的解讀,其實可以從中見到,曲論家由相提並論到互相影響式的論調,會聚焦於音樂的不同元素,論及戲曲中“音樂與敘事”之間如何發生關係,以及他們的關係如何可能。
書籍
1. 王驥德著,陳多、葉長海注釋:《曲律注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頁160。
2. 李克和:《明清曲論個案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頁54。
3. 胡健生:《中國古典戲劇敘事技巧研究——以西方古典戲劇為參照(上)》(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年),頁20。
4. 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賦學曲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777。
5. 程炳達、王衛民編著:《中國歷代曲論釋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370。
6. Schoenberger, Casey,Music, mind, and language in Chinese poetry and performance: The voice extend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203.
論文
1. 高暢:〈徐複祚《曲論》戲曲理論研究〉,《中國京劇》第2期(2023年),頁56-59。
2. 張萍:〈試論呂天成《曲品》對傳統戲曲批評觀念的突破〉,《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6期(2006年),頁12-17。
3. 陳維昭:〈何良俊的戲曲批評與其“文統觀”〉,《文學遺產》第3期(2013年),頁97-105。
4. 劉二永:〈王驥德“曲”“事”結合機制論〉,《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2023年),頁106-112。
5. 劉二永:〈戲曲賓白與曲詞的敘事功能及相互關係〉,《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17年),頁72-77。
6. 簡貴燈:〈從“曲論”到“劇評”——戲曲批評的一種流變與生成路徑〉,《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15年),頁127-132。
7. Johnson, Dale R, “The Prosody of Yüan Drama,”T’oung Pao, Vol. 56, No. 1/3 (1970): 96–146.
8. Tian, Min, “Stage Directions in the Performance of Yuan Drama,”Comparative Drama, Vol. 39, No. 3/4 (2005): 397–443.
註釋
1. Johnson, Dale R, “The Prosody of Yüan Drama,” T’oung Pao, Vol. 56, No.1/3 (1970): 96–146.
2. Tian, Min, “Stage Directions in the Performance of Yuan Drama,” Comparative Drama, Vol. 39, No.3/4 (2005): 397–443.
3. Schoenberger, Casey, Music, mind, and language in Chinese poetry and performance: The voice extend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203.
4. 簡貴燈:〈從“曲論”到“劇評”——戲曲批評的一種流變與生成路徑〉,《海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頁127-132。
5. 張萍:〈試論呂天成《曲品》對傳統戲曲批評觀念的突破〉,《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6年第6期,頁12-17。
6. 王驥德著,陳多、葉長海注釋:《曲律注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頁160。
7. 劉二永:〈王驥德“曲”“事”結合機制論〉,《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5期,頁106-112。
8. 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賦學曲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777。
9. 劉二永:〈戲曲賓白與曲詞的敘事功能及相互關係〉,《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頁72-77。
10. 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賦學曲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715。
11. 程炳達、王衛民編著:《中國歷代曲論釋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370。
12. 程炳達、王衛民編著:《中國歷代曲論釋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94。
13. 李克和:《明清曲論個案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54。
14. 陳維昭:〈何良俊的戲曲批評與其“文統觀”〉,《文學遺產》,2013年第3期,頁97-105。
15. 程炳達、王衛民編著:《中國歷代曲論釋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244。
16. 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賦學曲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877-878。
17. 程炳達、王衛民編著:《中國歷代曲論釋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487。
18. 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賦學曲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698。
19. 高暢:〈徐複祚《曲論》戲曲理論研究〉,《中國京劇》,2023年第2期,56-59。
20. 陳良運主編:《中國歷代賦學曲學論著選》(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817。
21. 胡健生:《中國古典戲劇敘事技巧研究——以西方古典戲劇為參照(上)》(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年),頁20。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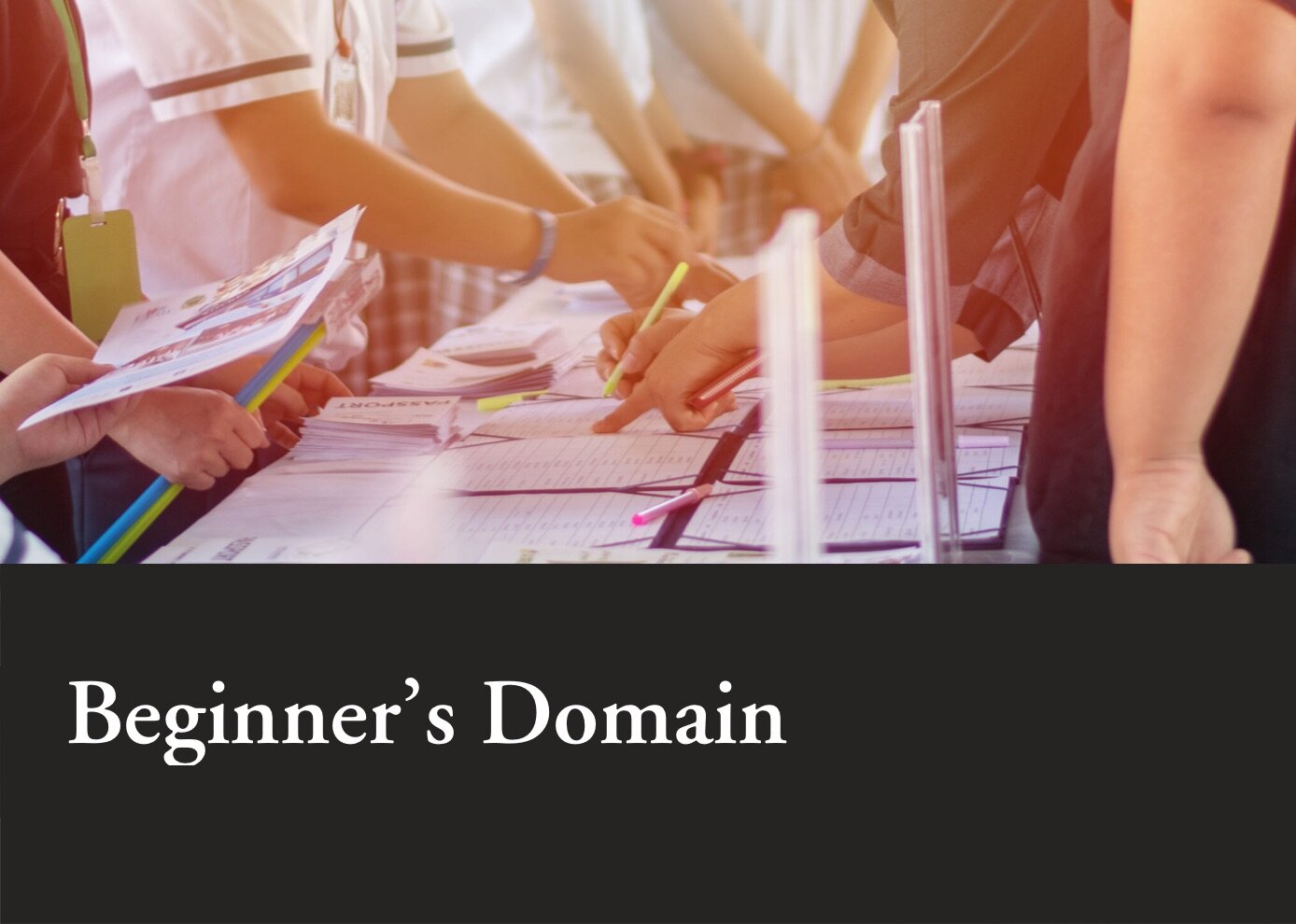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