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論證舉誤〉
陳靖敏
關於《尚書》的偽書問題,在學界而言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反對聲音。雖有一些學者,如楊善群,朱建亮等,提出對“偽古文《尚書》”是否真乃偽書提出過疑問,但也未能完全證實此說的正誤。惟閻若璩(1636-1704)《尚書古文疏證》(下稱《疏證》)一書,作為“偽古文《尚書》”之說的開山之作,其書本身的考證、論證過程卻有不足之處。閻氏《疏證》曰:“東晉元帝時,豫章内史梅賾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而只此篇數之不合,僞可知矣。”1其書論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之偽,認為其所獻之書在文辭與篇數上皆與真《尚書》不合,因而有偽作之嫌。雖說閻若璩的考據之學歷來多受讚譽,尤其為清人所推崇,但即使在清人所著《四庫提要》中,也對閻氏《疏證》作出批評。下文不探討“偽古文《尚書》”一說的正誤,只從閻氏《疏證》中,梳理其論證過程的問題所在,並就各問題列舉數條論證之誤。
不少學者對閻若璩《疏證》一書的考據成就予以認可。王俊義、于語和、范立舟等學者,都對其考據成就作出讚賞,認同其“偽古文《尚書》”一說。如“他的《尚書古文疏證》,以大量確鑿的實證,論證了東晉晚出古文《尚書》之偽,開清代考據辨偽之先河。”2“到清代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問世,前年偽書懸案始成定讞。閻氏之於學界,其功甚巨。”3“最難能可貴的是,閻若璩以其精湛的記憶力與思辨力將梅獻古文《尚書》所述內容的淵源一一指出,完成了證偽的工作。”4這些學者都對閻氏《疏證》高度讚譽,同時也將多篇古文《尚書》定為偽書,至今學界也多取此說。
然而,閻氏的考據之學,後來也不乏批評的聲音。清《四庫提要》予以認可的同時,也附帶一些批評。近代以來,也有學者對其嚴謹程度提出質疑。清人皮錫瑞(1850-1908)指出閻氏《疏證》的疏漏之處,曰:“徵君所引《論衡》,其前尙有數行未引,亦未及辨明。”5指出在閻氏引王充(27-約97)《論衡》說之前,尚有數句未有論及。閻氏直接由王充之說論定其誤,並對孔傳《尚書》作多項指控。王充之說與《史記》、《漢書》有異,關於其中的史實問題,大有考證的空間,例如兒寬(?-前103)受書是自歐陽生(?-?)、孔安國(?-408),而非晁錯(前200-前154)。《史記》言伏生(?-?)敎於齊、魯之時,已有二十九篇,無需老屋益一篇。《史記》和《漢書》同屬漢代具有記史性質的重要文獻材料,可以作為王充《論衡》的參照。閻氏既引後文,便定然看過前文,是有意節引,或沒有注意到此問題,沒有對此疑誤指出作解釋,對此問題避而不談。對此,《四庫提要》作出過類似的批評,曰:“《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竝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僞本鑿空之顯證,亦辨僞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疎略。”6此為閻氏考據學不嚴謹之一證也。
皮錫瑞又批評閻氏《疏證》,認為其中的論證有含糊之處,引文如下:
葢徴君專據孔疏之說,以馬、鄭、王所注《尙書》皆爲今文,惟僞孔增多者爲古文。不知馬、鄭、王亦是古文,惟歐陽、夏侯三家是今文,故其書於分別今、古文處多不了了也。7
今古文問題是處理《尚書》版本問題的基礎,在此之上才能清晰地梳理古文《尚書》的真偽。皮錫瑞指出閻氏論及《尚書》篇卷之真偽時,未有辨明今古文問題。這對專研考據的學者而言,是一個嚴重的疏漏。另外,閻氏專據孔穎達(574-648)之說,便論定《尚書》的今古文問題,沒有從更多文獻記載中求證,此亦一弊端。今古文問題尚且未能弄清,遑論分辨古文《尚書》之偽。《疏證》一書對偽古文《尚書》的論斷,基於如此不扎實的基礎上,難以立論與讓人信服。此為閻氏考據學不嚴謹之二證也。
楊善群對閻氏《疏證》作出批評,認為其書的證偽考據充滿欺騙性。其批評包括:典制、史實數據有不實之嫌;矛盾百出,使人頭暈目眩;用“竄入”“誤入”等語誤導讀者等。8這些評價也與《四庫提要》中的批評相對應。下文也會就這些問題,舉例證明楊氏之語並非錯判。
對於閻氏考據學的研究方法,不少當代學者都有論及。並指出其不足。“清代學者閻若璩寫《古文尚書疏證》把梅賾本多出的二十五篇定為《偽書》,所用的研究方法,叫‘由根底而之枝節’法。”9閻氏《疏證》曰:“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節也易,由枝節而返根柢也難。竊以考據之學亦爾。”10指出其考證偽書的方法。有學者對此法作出具體的解釋:“此法簡言之就是先論定某種結論,再以之作為原則去檢驗勘正違反這些原則的現象,並以之作為偽造的證據。”11由於此法是先有結論,再根據結論收集材料,所收集的只是符合論證結果的材料,對於與結論相悖的則加以忽略。又,對於某些重要材料未有采錄與論證。
閻氏的論證有時流於空泛無力,究其原因,也是出於其考證方法。孔安國獻孔壁古文《尚書》,在歷年的流傳下,或有多個版本,而閻氏是先有“孔壁古文《尚書》只有一個版本流傳”的結論,再在此之上進行論證。《疏證》曰:
古文傳自孔氏後,唯鄭康成所註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書》……曰“昧穀”,鄭曰 “柳穀”;“心腹賢腸”,鄭曰“憂腎陽”。12
閻氏見晚出孔《書》的用字與鄭注《尚書》有異,以此論證晚出孔《書》之偽。《尚書》在孔子之后傳習者甚多,版本流傳多樣。鄭氏、蔡氏所傳不過一是孔壁本,一是伏生的版本。閻氏若以僅憑今文《尚書》和孔壁古文《尚書》在漢代文獻《說文》《鄭注》等的引文,判斷古文《尚書》之偽,證據不充分。而晚出的孔安國古文《尚書》,有可能是孔壁本之異本,閻氏的論證顯得力度不足。
又如閻氏在考證古文《尚書》的篇數時,對《漢書·景十三王傳》關於河間獻王搜羅古文《尚書》的記載未有采錄。“〈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13此段指出河間獻王得先秦時期以古文所寫之書,其中就包括《尚書》,即後來被稱作古文《尚書》的版本。在論證“古文亡”之時,閻氏忽略《尚書正義》對古文傳授的記載。孔穎達《尚書正義》曰:
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歷及魏晉,方始稍興……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晩始得行。14
此段說明了古文《尚書》得於齊魯,傳授於歐陽、夏侯二家,而孔安國為之作注一事。同時說明了古文經在兩漢沒有得到廣大的重視,故雖然古文經早已出現,卻在較後期才通行的歷史。閻氏雖專據《尚書正義》,卻對此問題避而不談,或因這些文獻材料與其“古文《尚書》乃偽”的結論相悖,因而不予收錄,更不加以論證。這為閻氏在之上的立論留下疑竇。
朱建亮對閻氏“由根底而之枝節”的辨偽方法提出質疑,認為此法不過是引文分析法加上主觀臆斷法。他認為引文分析法是有其價值的,但必須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閻氏沒有做到這一點。15研究時,應先進行各方面材料的收集,再對材料進行分析,最後根據分析得出結論。如此,便可以較大程度上避免主觀因素帶來的偏差。閻氏的辨偽方法,沒有遵從上述的過程,而是先有結論,再根據結論尋求材料證明,便會導致辨偽的過程有主觀武斷的成分,論證得出的結果也不可靠,忽略了部分重要的相關材料。
《四庫提要》批評閻氏《疏證》曰:“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肯刪其前說。”16考之閻氏書,確實有此問題。以下列舉《疏證》之兩誤,以論證此說。
閻氏在論證梅賾所獻乃偽書,及證其偽造方法時,論證過程前後多有矛盾。閻氏認為偽造古文《尚書》者,是通過對其他書籍“采輯掇拾”而寫成的。“而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不可的知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17此處以偽書有“采輯掇拾”之處,作為梅賾所獻古文《尚書》乃偽作之證,但在同一卷又有矛盾之處,曰:
逮東晉元帝時,梅賾忽獻古文《尚書》。……《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釣。”……而晚出之古文獨遺此數語,非一大破綻乎!”18
閻氏既認定他書所引《書》語,“皆采輯掇拾”之所得,“遺此數語”一說便不成立。《墨子》中有大量對《書》的引用,是與閻氏所相矛盾的。又,《疏證》曰:“《說文》有〈虞書〉〈商書〉〈周書〉等曰,今忘采用。”19閻氏列舉《說文》所引自《尚書》之語,並於末處總結曰:“右皆魏晉間忘其采用者”,即魏晉之時偽造古文《尚書》者遺漏,沒有“采輯掇拾”的。閻氏在卷一提到梅賾所獻之古文《尚書》,凡他書所引《書》語,“皆采輯掇拾”。但下文的“遺此數語”,“忘乎采用”卻與此說相悖。既是“采輯掇拾”,便不會完全抄錄,不會存在遺漏數句沒有採用的問題。因此,閻氏的論證前後互駁,並不合理。
閻氏《疏證》在論證時,又會反駁自己已提出的觀點,讀者不免感到困惑,影響理解,也會導致文章冗長。最為重要的,是會使其論證的結果建立在不實的過程中,不知其立論建基於何處。如閻氏論證孔安國〈大序〉之偽,指出其書乃規摹自許慎〈說文解字序〉,其說如下:
安國〈大序〉一篇,……余直謂此篇蓋規摹許愼〈說文解字序〉而作。……按〈說文序〉以初造書契爲黃帝之史倉頡此自從《易·繫辭》及《世本》來,極確。安國〈大序〉妄以爲伏犧氏……孔安國序《尚書》,謂伏犧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愚嘗讀《易·繫辭》而知其非也。20
閻氏的主張是孔安國〈大序〉乃規摹自許慎(約30年-約124)〈說文解字序〉而成書。而後文不論證己說,而是論證《說文序》在造字歷史的相關內容上,與孔安國〈大序〉有不同之處。如〈說文序〉記載“初造書契爲黃帝之史倉頡”;孔安國〈大序〉記載則是“伏犧氏造書契”。既然兩者在內容上不相合,則閻氏前文所說無以為據,甚至是反駁了自己的觀點。閻氏卻在後文說:“〈說文序〉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之跡,初造書契。’則書契之作,斷斷乎始於黃帝世無疑矣,然則謂包犧氏爲萬世文字之祖者,其說非乎!”21此段指責孔安國〈大序〉錯認為伏犧氏是萬世文字之祖。閻氏先說出自己的看法:是孔安國〈大序〉乃規摹自〈說文解字序〉;再於後文根據自己的考證,反駁前說;最後又憑空指責孔安國〈大序〉。對孔安國〈大序〉的指責與前文論述毫無關聯,不知何故要放在此處,整段論述於邏輯不通,使人困惑。
《四庫提要》對閻氏《疏證》作出批評,如“其中偶爾未核者”等語, 都指出其書於某些地方未有核實。以下會就地理與官名和刑法,各列舉論證有誤之例。
1. 對地理與官名的考證
依閻氏《疏證》,〈周官〉屬偽書,支持其觀點的證據是〈周官〉中的官名有誤,與史實不符。其論述如下:
竊以唐虞時 “四岳”自官名,“百揆”非官名也……偽作〈周官〉者不過此義,竟認百揆典四岳俱官,各曰內有百揆四岳,其殆昔人所謂圖封偶親切者。”22
意思是“四岳”為官名, “百揆”則並非官名,偽作《周書·周官》者,錯把“百揆”當作官名,閻氏以此證〈周官〉之偽。查考閻氏所定《偽書》之〈周官〉,有“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句,還有“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句。據周秉鈞注釋,“四岳”即東岳、西岳、南岳、北岳。故此處的“四岳”並非正式的官名。“岳”字是借地名而代官名,“‘四岳’是代指四方諸侯之長。”23在《史記·伯夷列傳》可見其相關用例:“堯將遜位,讓於堯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此處的“岳”,便是借地名而代之,用作官稱。由此可證閻氏“竊以唐虞時‘四岳’自官名”一說有誤。“百揆”也不是正式的官名,《說文解字·手部》:“揆,度也。”說明至少在東漢或以前, “揆”都釋為審度,還沒有獨立解作宰相的意思。“揆”是“度”字用作動詞所借代的官名,“百揆”有“多件事情都負責審度”的意思,借指“宰相”。“揆”字是在後來才固定有“宰相”義。如《晉書·禮志上》:“桓溫居揆,政由己出。”字義隨著時代的不同,會發生變化,不能以後來的字義解釋以前的字義。閻氏所認定的真《尚書》〈堯典〉中,有“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句,“百揆”此處是二字分開理解的,並非官名。從上文例子可見,不論在《尚書》原文,或是在其他文獻中,“四”和“百”都作數字理解,“四岳”“百揆”都並非正式的官名。正如“三公”“ 九卿”都並非明確的官名。“公”“卿”是多個官名的總稱,“三”“九”作數字解。由上文論證,可見〈周官〉沒有將“四岳”“百揆”解讀為正式的官名,而是閻氏錯誤解讀或曲解〈周官〉之經義,稱其有官名上的錯誤,又把“百揆”當作它物,以證其偽。因此,閻氏對〈周官〉乃偽的判斷,便沒有實際的證據支持。
2. 對刑法的考證
閻氏認為〈泰誓〉中的刑法與《尚書》的記載不符,與歷史不相合,以此證〈泰誓〉為偽書。《疏證》曰:
古未有夷族之刑,即苗民之虐,說祗肉刑之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入〈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24
此段指出作偽書者,因見《荀子》中有族刑,便以此作為參照而偽造〈泰誓〉一篇。按閻氏說,真《尚書》中,不應有殘酷的夷族之刑。然考之於〈呂刑〉,作為閻氏認定的真《尚書》,就記載周代以前曾有過酷刑,苗民有濫用酷刑的歷史。按〈呂刑〉記載,周穆王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孔安國《傳》為〈周書〉作解,解釋“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曰:“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25解釋“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曰:“苗民於此施刑,幷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26這兩段都指出苗民施刑淫濫,即施刑時不減免無罪的人,施刑過度。又,對苗民“上帝不蠲,降咎於苗,苗民無辭於罰,乃絶厥丗。”27“乃絶厥世”即是斷苗民之後嗣,即族刑。28此段說明,周代以前曾有這類酷刑。因此,閻氏提出作偽書者在內容上“輕加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一說,沒有實際的證據。按閻氏說,既然〈泰誓〉因記載酷刑而為偽書,〈呂刑〉也當為偽書,而閻氏又不作此判斷,顯示出其判斷標準不一致。基於同一事實上做出兩種相反的判斷,這說明閻氏對〈泰誓〉〈呂刑〉是否真《尚書》的判斷中,無論如何都有一個是錯判。對於偽書是參照自《荀子》所作,亦沒有作出論證,缺乏證據支持。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一書,作為清代考據學的重要作品,雖歷來都備受推崇,但其中的考據及論證過程,卻仍有不足之處。此文就清人及今人所提出的批評,略舉數例以論證。《疏證》一書的問題大概可以分為四類:立論的基礎不穩、考據的方法不嚴謹、邏輯前後不通、證據不足而盲加指控。通過數個例子,證實前人對《疏證》的批評,以及對閻氏考據學嚴謹性的質疑確實有其根據。批評此書的學者,多從其論證過程的疑誤中,批評其“偽古文《尚書》”之說,然而,閻氏《疏證》雖然有部分論證不實之處,但仍不能否定其對後世《尚書》辨偽有啟發的價值。可以說,正是閻氏開創了後世對古文《尚書》的懷疑風氣,並積極探討其中的問題。
書籍
(漢)孔安國:《尚書》(景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日本覆印宋本)。
(清)皮錫瑞:《尚書古文疏證辯正》(清光緒二十三年思賢講捨刻本)。
(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內府藏本)。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乾隆眷西堂刻本)。
(清)戴震,段玉裁:《戴東原集》(景上海涵芬樓藏經韻樓刊本)。
于語和:《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辨偽方法評析》,《南開學報》第5期(1994年)。
王俊義:〈論閻若璩的治學道路、學術成就及其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松遼學刊》第1期(1986年)。
朱建亮:《〈偽古文尚書〉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7年9月)。
周秉鈞:《白話尚書》(湖南:岳麗書社,1990年)。
范立舟等:《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學術價值及其思想史意義》,《人文雜誌》2011年第3期。
楊善群:《中國學術史奇觀:偽古文〈尚書〉真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
註釋
1.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1,頁18下。
2. 王俊義:〈論閻若璩的治學道路、學術成就及其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松遼學刊》1986年第1期。
3. 于語和:《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辨偽方法評析》,《南開學報》1994年第5期,頁51。
4. 范立舟等:《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學術價值及其思想史意義》,《人文雜誌》2011年第3期,頁132。
5. (清)皮錫瑞:《尚書古文疏證辯正》(清光緒二十三年思賢講捨刻本),頁3下。
6. (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內府藏本),卷12。
7. (清)皮錫瑞:《尚書古文疏證辯正》(清光緒二十三年思賢講捨刻本),頁4下-5上。
8. 楊善群:《中國學術史奇觀:偽古文〈尚書〉真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
9. 朱建亮:《〈偽古文尚書〉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17年9月),頁15。
10.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2,頁97下。
11. 袁瑋:《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辨偽成就試論》,《檔案學通訊》,2010年。
12. 同前註,卷2,頁97下。
13. (清)戴震,段玉裁:《戴東原集》(景上海涵芬樓藏經韻樓刊本)卷1,頁5下。
14.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日本覆印宋本)序,頁5上。
15. 朱建亮:《〈偽古文尚書〉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7年9月),頁17。
16. (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內府藏本),卷12。
17.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1,頁21。
18. 同前註,卷1,頁41下。
19. 同前註,卷5,頁263下。
20.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7,頁527下-530下。
21. 同前註。
22.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4,頁175下。
23. 周秉鈞:《白話尚書》(湖南:岳麗書社,1990年),頁223。
24.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4,頁180下。
25. (漢)孔安國:《尚書》(景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卷6,頁63下。
26. (漢)孔安國:《尚書》(景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卷12,頁143下。
27. 同前註,卷12,頁168上-168下。
28. 周秉鈞:《白話尚書》(湖南:岳麗書社,1990年),頁223。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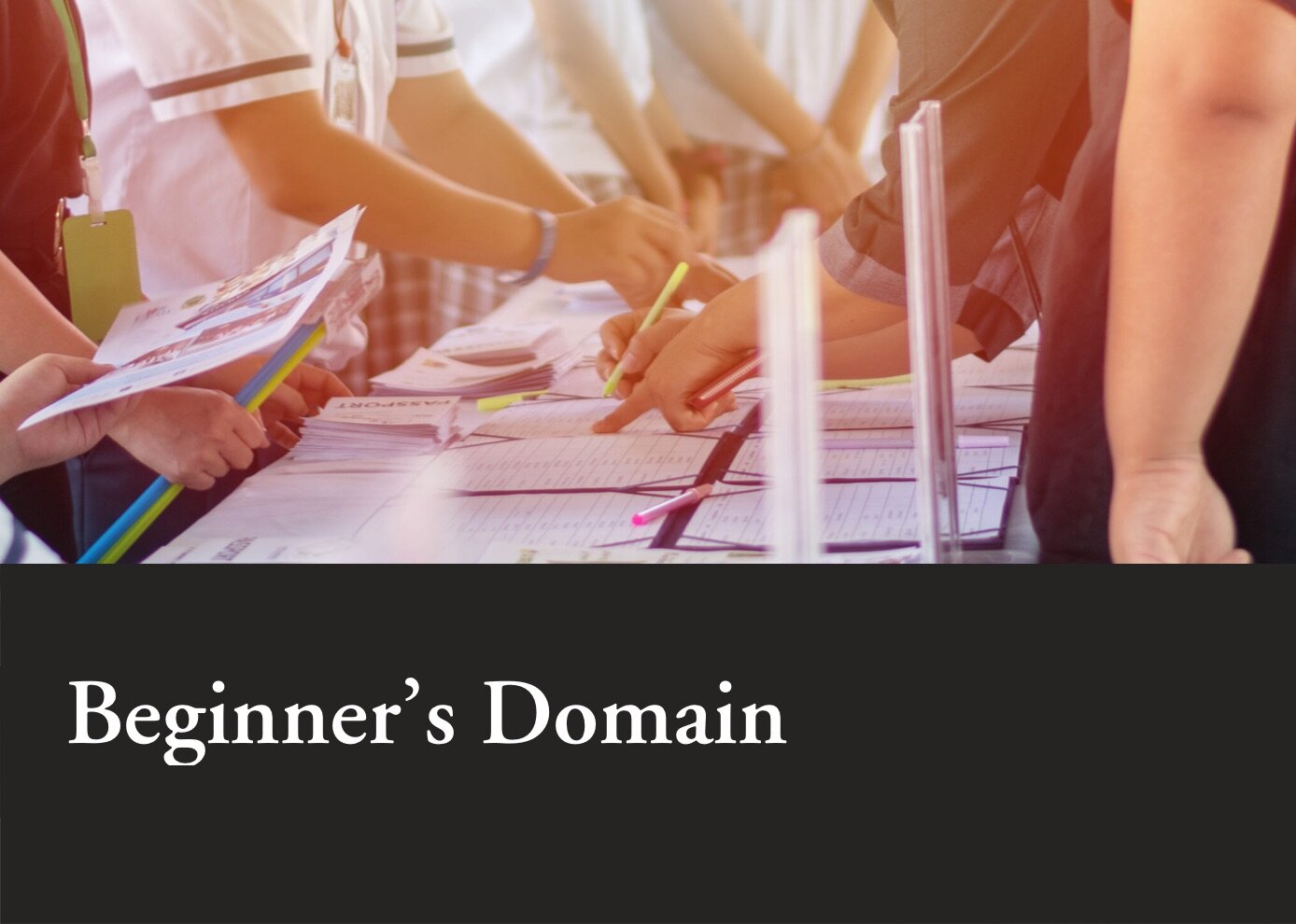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