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曹操的文化政策與文學作品看其哲學思想
曹操(155-220),東漢末年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後其子曹丕(魏文帝)追諡他為魏武帝。魏武是三國時期曹魏的奠基者——討伐董卓、挾天子以令諸侯、在官渡之戰中以少勝多,殲滅袁紹袁氏軍隊的勢力,取得統一北方的勝利,在之後的過半百年時間、三國鼎立的局面裡,即使天下仍處於戰亂不斷的局面,仍以曹氏的實力最為雄厚。1 然而,多才多藝的曹操除了在軍事、政治方面的傑出成就外,其豐富的文學修養及才華亦不容忽視。荀彧(163-212)曾稱讚開創延安文學新局面的曹操「外定武功,內興文學。」2曹操推行的一些文化政策以及其文學創作當中蘊含了他多元的哲學思想。本文旨在透過探討曹操的文化政策及文學作品,以揭示其哲學思想的核心內容。以下將選取部份相關的文化政策及文學作品,以探討項目當中蘊含的哲學思想及其為人處事。
曹操在東漢末年平定黃巾之亂成功討伐董卓後,建安元年迎接漢獻帝到許縣後便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非皇帝卻以皇帝的名義總攬朝政、討伐四方。3他的政治及軍事思想是豐富的。同時,二十歲舉孝廉的他,自幼接受的是傳統儒家思想的教育,加上他的閱歷豐富,在不同範疇都具有其獨特見解,而他的每個軍政行動和文學創作當中都存在著本人的哲學思想。曹操的哲學思想是有多元的特色,對各家思想和名家學說都有所濡染,例如黃老之學對他的影響、以法家思想對個人的提醒、兵家思想、道家黃老思想的各種參雜,又對神仙之說、道教方術等有所涉足,均可從不同作品中可見。4從曹操的眾多詔令及文學作品裡可見其思想模式是以儒家為核心,其他為附。他經常以儒家思想作為自己觀察及分析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其詩文也常提到仁義禮樂、忠孝節義等傳統儒家觀念。5接下的兩部份,將分別從曹操的文化政策及文學作品中選取相關的例子進行分析與探討。
用人也是一門學問,曹操就人才問題上所堅持的思想,從詩文反映出,既有與其教育主張一致的儒家思想,6 但也不能忽略其實用主義和墨家思想的存在。曹操曾發佈了有關求取賢才的三道詔令,被稱為「求賢三令」,分別是《求賢令》(建安十五年,210)、《欶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建安十九年,214)、《取賢勿拘品行令》(建安二十二年,217)。7雖然這三道詔令在不同時間頒佈,但都反映出曹操求才心切,而三者的取才標準都是以「唯才是舉」為主要目標。尤其是在赤壁之戰戰敗後,天下三分的形勢令曹操有感統一天下的事業之艱難,必須羅致更多人才以壯大己方實力。8 因此,早在《求賢令》的最後一句,曹操直接表明「唯才是舉,吾得以用之」;9然後在《欶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又是命令各主管選用人才要「唯才是用」。10 此時,曹操用人仍是強調儒家思想的,既要人才有治國安邦、行軍打仗的實際才能,也要有仁義忠孝的良好德行。後來的《取賢勿句品行令》則更為直接卻極端,標題明言取賢才時不要拘泥於品行,內文則更不言而喻,「凡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負治國用兵之術者,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11此令是「求賢三令」中最晚發出的詔令,當時的曹操用人已經不問出生及過去,不拘泥與其人之品性德行,哪怕是不仁不孝者,而最為重視其才幹,只要能協助曹操打天下、治理時政,曹操也必加以任用。這便是曹操的用人之道。綜合時局來看,三道詔令在曹操大致統一北方後期,三國鼎立的局面時發佈的。曹操有統一天下的決心,要打敗曹魏的敵人蜀漢和孫吳,自然是國家用人之時,或許當時已到了無法顧及人才是否性行淑均的地步,而只有一個目標:只要他是具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即可,哪怕從前是他敵人的手下。最為突出的例子便是許攸棄袁紹而來,曹操鞋子也來不及穿,便光著腳衝忙地出門迎接他。12這些都充分反映了曹操求人心切,以目標為本的實用主義。整體而言,「求賢三令」的共同目標都是與墨家思想相通的用人看重實際才能,不看重出身門第。13
除了曹操羅致人才使得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的文學帶來了演變和成績之外,曹操也曾提出過「厲俗」的問題。處理這個問題,曹操既有運用傳統儒家思想,也有墨子「兼愛尚同,疏者為戚」14的主張。曹操曾下過《禮讓令》及《整齊風俗令》兩令。前者,曹操認為禮讓是符合儒家經典的精神,並在令文裡對實行禮讓的內容作出了具體解釋——
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
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15
至於後者,曹操在《整齊風俗令》中所提出的「厲俗」與墨家的「兼愛」、「尚同」目的大致相同。16且看令文內容:
阿黨比周,先升所疾也。聞兾州宿,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弟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比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頓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為羞。17
令文盡舉一些不禮讓、不兼愛的不同行為,而這些行為必須嚴厲整頓。皆因東漢王朝極力推崇反動的孔學,導致整個官場以及知識分子中的風氣敗壞、極其虛偽,三國以降,學術風俗更是日益衰替。18曹操謀求國家之統一,以「反潮流的精神,對當時反動儒生中的歪風邪氣進行了嚴厲且堅決的申討及打擊。」19當中並非只有其個人在政治上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深層謀求,而更多的是以大局為重,抱持著認真嚴肅的態度面對社會風氣敗壞的問題,希望能夠重整社會秩序的美好期望,關於「厲俗」的兩道詔令,實不容忽視。20綜上可見曹操思想多元和實用的特色,他並非獨尊一家之說,而是按照社會、政治現實的需要,靈活運用各種符合需要的哲學思想,以求能夠重整社會成他理想中的模樣。
曹操的詩文融合了他多元的哲學思想及文學作風,如寫實主義和道家黃老思想;作品大多具創作色彩,又慣用樸質的形式披露其胸襟及個人風格,不但有開建安文學風氣的作用,也對後代文學有重要的影響。他的詩文除詔令外,全都是樂府歌辭,而五言樂府於當時而言是一種新體裁的詩歌。21雖然它沿用漢代樂府的古題,卻不沿用古詩的古意,相反,它們繼承了樂府民歌的「緣事而發」22、命題作文的風氣和精神,藉此反映新的社會現實面貌。23 曹操作為建安作家中僅次於孔融的前輩,其創作活動也開始的較早,其文學創作的新風格和突破的新精神都對後來的文學家和詩人有所影響。就創作時間而論,他在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寫下言詞激切,為蒙冤人申辯的《上書理竇武陳蕃》一文。24當時仍是漢靈帝在位時起,距離東漢王朝的結束(公元220年)尚有約四十年之久,曹丕兄弟尚未出生;而曹操所作流傳至今的詩當中,最早可能屬於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寫下的具寫實精神的《蒿里行》,當時他的兒子曹丕才十歲,曹植才五歲。25 該詩的內容只記述到建安二年,董卓之亂時期袁紹等人的爭權篡利及長期混戰對社會造成嚴重破壞、大量人命死亡、土地荒蕪的社會現實。26 可見曹操很早便開始他的文學創作之路,他的作品不少有命題而作,這亦促進了當時「命題作文」的文學新發展,例如魏文帝傷害阮瑀的寡妻,召集建安七子之徒作《寡妻賦》,又有《宮中槐樹賦》,具有競賽意味,使文人後來更為用心地作詩。27 他的兒子尤其是曹丕和曹植也繼承其父的創作風格,更被後人合稱「三曹」。
在曹操的詩歌創作中,當屬《短歌行》(其二)28最廣為流傳,也極具研究價值的文學作品。該詩充分表達了曹操懷著安定天下的雄心壯志,卻有功業未成,求賢若渴的心情。29更以周公自比,「周公吐哺,天下歸心。」30 這裡表示自己要以吐哺折節的精神,儘可能地招攬大量人才,以助他完成統一的大業。31《短歌行・對酒當歌》真實反映了曹操對人才真誠的渴求。至於面對他未能完成心懷大志的複雜心情和憂慮,「何以解憂?唯有杜康。」32 詩歌開首發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嘆,點出曹操感慨人生苦短、時光流逝,然功業未成,唯有借酒消愁,以解憂慮的心情——面對他對人才對渴求從而幫助完成其建功立業之雄心抱負,可惜時光易逝,其本人亦已逝去不少年華,時不待我的緊迫感隨之而來,更以清晨的露水比喻人生的短暫,因此必須抓緊當前剩餘的時光,進一步強調人生苦短的急切的心情,倒不如及時行樂,借助酣飲來排解那深沉的憂愁。33 但這不同於自東漢末年至魏晉時期學士文人「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34,選擇「今朝有酒今朝醉」這種消極的及時行樂精神;35相反,那卻是順應他自己的狀態,面對如此憂愁,先借酒消愁以處理好心情,然後再接再勵,到最後詩末的「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來表達自己有如周公一樣,求完成其統一天下的大業。當中可見曹操多少受到道家黃老思想的濡染,其性格、文風亦有著與道家思想和作風頗為關聯的「不遵禮法、放誕不羈、通脫自然」的一面。36
以上集合了有關曹操「求賢」、「厲俗」的令文,以及其部分文學創作,並進行簡述、分析與探討當中的思想。當中可見他的政治思想是以大局為重,以目標為本的具針對性的實用。在用人問題上,由最初的品德才能要兩者兼備,到後來回歸求賢的主要目標,只在乎才幹,這是就不同時期和情況下的一個調整,「根據現實政治的需要廣攝博取,融會貫通,是反傳統的,順應當時的社會潮流」37,可見其通融之處。並且,曹操是講究禮法的,這點尤其在上文提及的《禮讓令》和《整齊風俗令》中可以見得。同時,他的文學作品當中也與其令文一樣,皆有運用到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等不同的主張,反映了曹操的哲學思想並非單一的,而是多元的,這對於當時衝破傳統束縛的思想解放運動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並為後來的魏晉「新學」(玄學)埋下了種子。總括而言,曹操的思想模式是多元、實用的。
古籍
1. 〔漢〕班固:〈藝文志〉,《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2.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書籍
1. 朱自清、游國恩、羅庸、蕭滌非、聞一多、浦江清:《西南聯大文學課》,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
2. 夏傳才:《曹操集注》,中國:古籍出版社,1986年。
3. 馮友蘭、湯用彤、賀麟:《西南聯大哲學課》,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
4. 張亞新:《曹操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
5. 張蔭麟、雷海宗、陳寅恪、吳晗:《西南聯大國史課》,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
6. 傅斯年、游國恩、朱自清、蕭滌非、浦江清:《西南聯大文學課(續編)》,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
7.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臺灣:正中書局,1967年。
期刊論文
1. 王婧嫻:〈《短歌行》的政治隱喻與為文心態〉,《保定學院學報》,2022年4期(2022年7月),頁66-71。
2. 亦歌:〈曹操《短歌行》賞析〉,《孫子研究》,2016年3期(2016年4月),頁115-116。
3. 安徽師範大學中文系《法家文選》評注小組:〈曹操令文選注〉,《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74年3期(月份缺),頁60-63。
4. 徐穎瑛:〈淺析曹操詩文中的周公情結〉,《現代語文(學術綜合)》,2014年10期(2014年10月),頁8-9。
5. 黃雅莉:〈三曹詩歌的析評與比較〉,《中國學術年刊》,1998年19期(1998年3月),頁223-224。
6. 張玉明:〈曹操〈述志令〉及〈求賢三令〉探析〉,《雲漢學刊》,2018年36期(2018年9月),頁1-27。
7. 柳軒:〈從曹操的詩文看他的政治思想〉,《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1期(月份缺),頁48-53。
網頁
1. 〔明〕高濂:〈起居安樂箋・上卷〉,《遵生八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3912)。(瀏覽時間:2023年12月12日)
2. 游淑閔:〈從文學中認識曹操〉,南開大學(https://www.nhu.edu.tw/~society/e-j/92/A10.htm)(瀏覽時間:2023年12月11日)
腳註
[1] 雷海宗:〈第三章:雷海宗講魏、晉、南北朝〉,張蔭麟、雷海宗、陳寅恪、吳晗:《西南聯大國史課》(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頁112-113。
[2] 〔晉〕陳壽、裴松之:《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0,〈魏志・荀彧傳〉,頁317,注引《彧別傳》。
[3] 張亞新:《曹操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頁82, 85-86。
[4] 同[3],頁517-523。
[5] 同[3],頁518。
[6] 柳軒:〈從曹操的詩文看他的政治思想〉,《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1期(月份缺),頁52。
[7] 夏傳才:《曹操集注》(中國:古籍出版社,1986),頁123,153-154,162-163。
[8] 同[3],頁391。
[9] 同[7],頁123。
[10] 同[7],頁153-154,註釋1。
[11] 同[2],卷1,〈魏志・武帝紀〉,頁49,注引《魏書》。
[12] 同[3],頁406。
[13] 同[3],頁519-520。
[14] 同[7],頁1-3(曹操:《度關山》)。
[15] 同[7],頁183。
[16] 同[3],頁494。
[17] 同[11],頁27。
[18]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中)》(臺灣:正中書局,1967),頁57。
[19] 安徽師範大學中文系《法家文選》評注小組:〈曹操令文選注〉,《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74年3期(月份缺),頁60。
[20] 同[3],頁502-503。
[21] 羅庸:〈曹氏父子的「一家辭賦」〉,朱自清、游國恩、羅庸、蕭滌非、聞一多、浦江清:《西南聯大文學課》(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頁63。
[22]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30,〈藝文志〉第457,頁1756。「⋯⋯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23] 蕭滌非:〈蕭滌非講魏晉南北朝文學〉,傅斯年、游國恩、朱自清、蕭滌非、浦江清:《西南聯大文學課(續編)》(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3),頁120。
[24] 同[7],頁41,注釋1。
[25] 同[3],頁571。
[26] 同[3],頁573。
[27] 同[21],頁63。
[28] 同[7],頁24-26。
[29] 同[3],頁405。
[30] 同[7],頁25。
[31] 同[3],頁405。
[32] 同[7],頁24-25。「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33] 亦歌:〈曹操《短歌行》賞析〉,《孫子研究》,2016年3期(2016年4月),頁115-116。
[34] 〔明〕高濂:〈起居安樂箋・上卷〉,《遵生八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3912)。(瀏覽日期:2023年12月12日)「6. 仲長統曰:『⋯⋯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
[35] 湯用彤:〈湯用彤講魏晉玄學〉,馮友蘭、湯用彤、賀麟:《西南聯大哲學課》(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頁163。
[36] 同[3],頁520。
[37] 同[3],頁524。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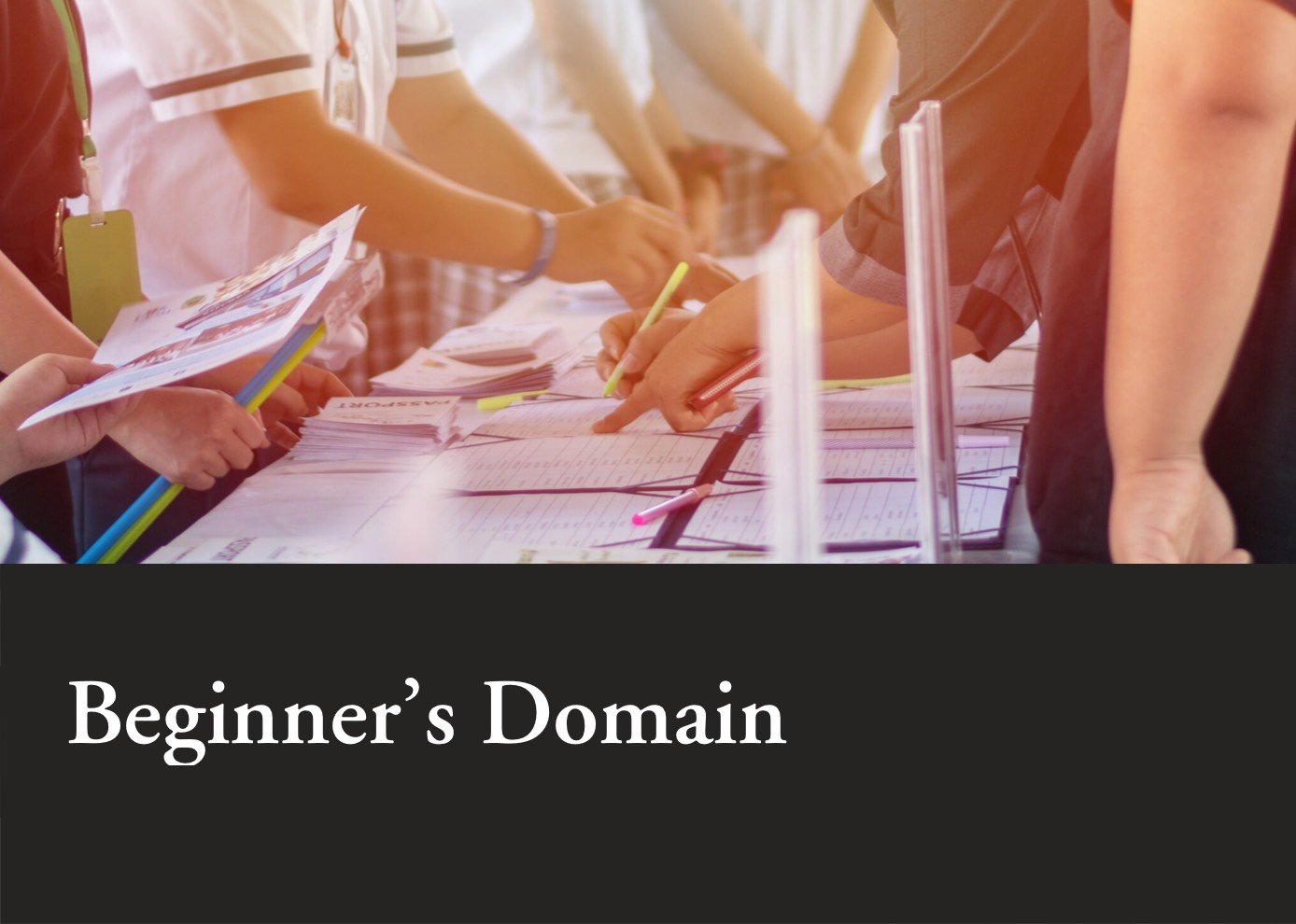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