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釋兵權”再解釋
“杯酒釋兵權”(下稱“杯酒”)故事,內容是北宋(960-1172)初年,宋太祖(趙匡胤,927-976,960-976在位)為強化中央集權,防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之歷史重演,他納趙普(922-992)之議,在酒席之中、杯酒之間,兵不血刃的讓禁軍將領主動交出兵權,並以皇室聯姻、高官厚祿等法安撫原禁軍將領,避免出現五代以來禁軍將領經常以禁軍奪取皇位之事。此事在北宋年間記載於文人的筆記小說,後來先後被(南宋)李燾(1115-1184)、(元)脫脫(生卒不詳)分別收錄於《續資治通鑑長編》(下稱《長編》)和《宋史》,故事被編入正史,自始流傳後世。直至上世紀40年代,學者丁則良(1915-1957)曾撰文〈杯酒釋兵權考〉,對“杯酒”故事的合理性進行質疑,並對太祖解決禁軍兵權之手法有新的說法,認為解決禁軍兵權非一酒宴可成,而是宋初君主經過多年時間,以資淺材庸之人取代原資深才高的將領,以此消除禁軍將領對皇權的威脅。1而上世紀80年代,學者徐規(1920-2010)、方建新亦有撰文〈“杯酒釋兵權”說獻疑〉再對“杯酒”的真確性提出質疑。然而,學術界亦有學者如柳立言、王育濟等認為“杯酒”確有其事。由於“杯酒”可謂北宋君主解除禁兵之標誌,乃北宋政治史的一個重要課題,並且是香港中學中國歷史科的教學內容之一,因此有澄清的必要。是故本文將綜合有關史料,詳參前人學者的研究,嘗試梳理出“杯酒”的真假,與宋初君主解除禁軍兵權的過程。
“杯酒”故事始見於宋仁宗年間(1022-1063)王曾(978-1038)撰寫的《王文正筆錄》(下稱《筆錄》)和丁謂(966-1037)之婿潘汝士所編的《丁晉公談錄》(下稱《談錄》),當中入正史者是王曾的《筆錄》。回顧《欽定四庫全書》對《筆錄》的提要,“所記朝廷舊聞,凡三十餘條,皆太袓、太宗、真宗時事,其下及仁宗初者,僅一二條而已”2,《筆錄》記事最遲之事乃宋仁宗(趙禎,1010-1063,1022-1063在位)即位之初,劉太后(969-1033)垂簾聽政之事。因此可知,《筆錄》的定稿時間最早只能是景祐年間(1034-1037),與“杯酒”的發生相隔七十餘年,史料價值本身不高。
繼王曾、丁謂者,可數半世紀以後的司馬光(1019-1086),其《涑水記聞》(下稱《記聞》)是司馬光“編雜錄宋代舊事,起於太祖,訖於神宗”3,把一些關於國家軍政大事、或歷代皇帝、或文武大臣、或朝章政典、或契丹、西夏等有關事項的所見所聞的記錄,以備將來撰寫“資治通鑑後記”,而其對“杯酒”的記載則較王丁二人更為詳細。4關於《記聞》對“杯酒”故事的出處來源,《記聞》中所記各則大多有注明出處,而在此則下有小注—“始平公云”,對此,學者丁則良作過考證,他推斷出“始平公”為皇祐年間(1049-1054)為相的龐籍(988-1063),而其所處之時間又晚於王曾,距開國時候近百年,且亦為所傳聞之證。5因此,若以文獻與事件發生的時距作考慮,《記聞》的可信性實不及《筆錄》。但由於司馬光於宋有崇高地位,6加上編纂《資治通鑑》的關係,導致《記聞》之地位被提高,使到之後的王闢之(1031-?)《澠水燕談錄》、邵伯溫(1057-1134)《邵氏聞見錄》等有關“杯酒”之記載,主要都是沿襲《筆錄》、《記聞》之說。
及南宋孝宗年間(1162-1189),李燾認為“杯酒”事關重大,但“《正史》、《實錄》皆畧之,甚可惜也,今追書”,而“王曾《筆錄》皆得其實,今從之。文辭則多取《記聞》,稍增益以丁謂《談錄》”7,因為被《長編》載錄,而該書在史事考證方面的權威使到“杯酒”故事定型。此後元代脫脫亦參考宋人筆記,將“杯酒”編入《宋史》的〈石守信傳〉,並廣傳至今。值得留意的是,“杯酒”故事的源流乃出自《筆錄》、《談錄》、《記聞》等筆記小說;而北宋官修的《太祖實錄》、《三朝國史》並沒有關於“杯酒”的記載,是後世史家對“杯酒”一事作出質疑的一大依據。
誠如前述,“杯酒”的一大疑點在於其並沒有出現於北宋的官方記錄,而與此同時,若重新審視《筆錄》、《談錄》、《記聞》、《長編》、《宋史》等史料,可以發現,這些史料有不少細節出現矛盾,甚至不合理之處。因為這些細節,我等學者就“杯酒”的真確性提出疑問,甚至否定該事件的存在。今回顧宋人筆記小說的對“杯酒”的記載,可見不同史料在“杯酒”的發生時間、宋太祖處理禁軍將領之法,以及部份史料記載的情況上,皆有其矛盾或不合理之處。
2.1 “杯酒釋兵權”時間上的不合理
關於“杯酒”的發生時間,不同的史料有不同之說法。首先,最早記載“杯酒”的《筆錄》是如此記載故事的開始時間:“太祖創業,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猶分典禁兵如故”,並無提供年月日期,只能推測是發生於太祖初年。至於《記聞》中的“杯酒”是在“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8之後開展的,與《筆錄》一樣沒有記下發生日期。但若司馬氏所言無誤,“杯酒”發生於“誅李筠、李重進”之後,按《長編》卷一,太祖建隆元年(960)十一月丁未條,李筠(?-960)、李重進(?-960)皆歿於建隆元年,故“杯酒”可以是建隆元年十一月之後。與先前史料不同,《長編》為“杯酒”提供日期,按《長編》卷二,此事乃發生於建隆二年(961)七月。9至於《宋史.石守信傳》,則將此事記於“乾德初”。10
綜合上述史料,《筆錄》、《記聞》、《長編》皆以為“杯酒”乃發生於平定二叛之後,當中只有《長編》有確實日期;《宋史》則為乾德(963-968)初。關於日期的可信性,丁則良認為《筆錄》載事起句“太祖創業,在位歷年”雖未著年月,但意思是太祖即位若干年後,與建隆二年未嘗不合,故《長編》之建隆二年說與其他史料較為吻合,相信可信;而《宋史.石守信傳》有文:“建隆二年,移鎮鄆州,兼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11,而《長編》與之對應之語為:“庚午,以侍衞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石守信爲天平節度使…守信兼侍衞都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12,按天平節度使駐於鄆州,因此若交叉考證《長編》與《宋史》便可得出石守信(928-984)“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之職於建隆二年變得有名無實,禁軍兵權被除,因此,參考《筆錄》、《長編》、《宋史》,將“杯酒”的發生日期定於建隆二年七月似乎不無道理。至於脫脫沒有證據便將“杯酒”繫於乾德初年,或因成書太忽而未有詳細考證而“臆度其為乾德初年”13。
丁氏比較各史料,故以為太祖收兵權一事發生於建隆二年七月乃較可信之說,然而此說有其漏洞。學者徐規指出,杜太后(902-961)於建隆二年六月逝世,而按《長編》卷二百零四,禮院奏稱“祖宗時,據《通典》為正”14,即宋太祖需為杜太后服喪二十八日,直到第二十九日方能服吉,而建隆二年六月只有二十九日,故太祖釋喪服之日應是七月初。但此為服喪之期而矣,杜太后於建隆二年十月才葬於安陵,即使太祖於十一月宴臣僚於廣政殿亦不作樂,故李燾在《長編》指太祖於建隆二年七月戊辰杯酒釋兵權,實在矛盾。15由是而觀,“杯酒”之發生日期,不論是《長編》的建隆二年七月說,抑或《宋史》之乾德初年說,皆有其矛盾或不合理之處。
2.2 太祖與諸將“結婚姻”與史料之矛盾
回顧“杯酒”的諸將結局,主要有兩種—“以散官就第”16與“結婚姻”17—當中李燾已然在《長編》指出:“按司馬光《記聞》,云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誤矣”18,故太祖在“杯酒”對禁軍將領之處理手法似乎是結婚姻。然而,丁則良從諸多史料中指出其矛盾或不合理之處。
關於太祖在“杯酒”對禁軍將領之處理手法,《筆錄》云:“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選尚,尋各歸鎮,幾二十年,貴盛赫奕,始終如一”19,當中丁氏認為“高、石、王、魏之族”所指的是高懷德(926-982)、石守信、王審琦(925-974)、魏仁浦(911-969)的家族。而當中有尚主之舉者是為高懷德本人、石守信之子石保吉(953-1009)、王審琦之子王承衍(952-1003)、魏仁浦之子魏咸信(949-1017)。然而,若按《長編》之說,即“杯酒”發生於建隆二年七月,再交叉對照《宋史》與“杯酒”的記載,就能發現太祖與“高、石、王、魏之族”通婚姻其實與“杯酒”並無關係。
首先,據《宋史.高懷德傳》,“太祖即位,拜殿前副都點檢,移鎮滑州,充關南副都部署,尚宣祖女燕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李筠叛上黨,帝將親征,先令懷德率所部…”20,又《宋史.秦國大長公主傳》,“太祖即位,建隆元年,封燕國長公主,再適忠武軍節度使高懷德,賜第興寧坊”21,時間上不但早於“杯酒”記載的“誅李筠、李重進”之後,而且早於李筠叛變。又按《宋史.列傳第七.公主》:
魏國大長公主,開寶三年,封昭慶公主,下嫁左衛將軍王承衍,賜第景龍門外…魯國大長公主,開寶五年,封延慶公主,下嫁左衛將軍石保吉…陳國大長公主,開寶五年,封永慶公主,下嫁右衛將軍魏咸信…22
可見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尚太祖之女是發生於開寶三年(970)和五年(972),乃“杯酒”發生之後九年的事。再者,按《宋史.魏咸信傳》:
初,太祖在潛邸,昭憲太后嘗至仁浦第,咸信方幼,侍母側,儼如成人。太后奇之,欲結姻好。開寶中,太宗尹京,成昭憲之意,延見咸信於便殿,命與御帶党進等較射,稱善。遂選尚永慶公主,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
從中可見,魏咸信與陳國大長公主之結姻之議,始於杜太后而成於太宗,與宋初兵制改革無關。另外,魏仁浦乃文臣而非武將,根本與“釋兵權”無關。
綜上可知,“杯酒”故事中所載太祖與諸將“結婚姻”,與史實相差一段時間,短則一年,長則十年。時間上已然出現明顯誤差,又為“杯酒”故事添一疑點。
2.3 趙普史料的不合理緘默
回顧“杯酒”故事的開始,自王曾《筆錄》至李燾《長編》,都離不開趙普對宋太祖的進言:
|
《筆錄》 |
太祖創業,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猶分典禁兵如故。相國趙(普)屢以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啟請授以他任,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相樂…23 |
|
《記聞》 |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鬬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24 |
|
《長編》 |
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衞。普數言於上,請授以他職,上不許。普乘間即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上悟,於是召守信等飲…25 |
|
《宋史.石守信傳》 |
乾德初,帝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酒酣,帝曰…26 |
從中可見,除《宋史》之外的大部份記載都認為“杯酒”的發生乃因趙普數次進言太祖,請其授禁軍將領他職,並指點太祖諸將部下難制,需提防“黃袍加身”之事,而太祖因此召石、王等人飲酒,遂罷兵權。然而,丁則良追趙普史料,未見任何與“杯酒”有關之記載;又追宋太宗(939-997,976-997在位)為趙普親撰的《趙中令公普神道碑》,只言及趙普輔助太祖,革五代之弊,未有提及“杯酒”之事。27值得留意的是,若“杯酒”為事實,必為太祖、趙普二人在政治上的一大成就,宋朝官修的實錄、國史絕無為其隱諱之需要,此事如丁氏所云:“此種追問,須全用史料之緘默為反證,難期完全無誤,但無論如何,此項緘默,實為一關係重大,且甚可引起懷疑之緘默也”28。
總括上文,“杯酒”的記載本源已然存疑,故事內容事關重大而北宋官修史料卻未有提及,而最先記載此事的乃事隔數十年的小說筆記,只因其書之《長編》、《宋史》才被廣為流傳。另外,就“杯酒”發生的年份,諸書用字含糊不清,只道平定二叛之後,而《宋史》所云之乾德初年與《長編》所云之建隆二年七月則先後被後世學者指出其不合理。就“杯酒”太祖對諸將“通婚姻”的處置,故事情節與史料記載亦出現明顯矛盾。就“杯酒”策劃者趙普,諸書肯定趙普在“杯酒”中扮演的角色,但有關趙普的文獻卻沒有相關記載。上述的蛛絲馬跡都為“杯酒”故事增添疑點。加之“杯酒”內容的記載,可以得出一種情況:“杯酒”的當時人並無留下直接記載,而距當時人生時不遠之神道碑、正史、實錄均無提及,但事隔數十年之後卻出現諸多詳盡記載,且觀其文辭用語,如撰書者親歷其境,觀其詳細程度,則隨時間而延長,情況正如上世紀以顧頡剛為首之古史辨派所倡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因此,觀其記載可信性之低,以及種種與史載相悖之處,乃宋人以訛傳訛,並隨年月不斷被人增添細節而逐漸成形的故事。當然,故事中有部分內容得與《宋史》、《長編》相吻合。29故筆者認為,“杯酒”—九分假一分真,假在“杯酒之間”,真在收回禁軍將領兵權。
有宋一代,禁軍將領出身的宋太祖發動“陳橋兵變”,得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且鑑於五代以降武人干政之情況,宋太祖立國之初便有需要從與之出生入死而具領兵才能的禁軍將領(如: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等)收回兵權。誠如前述,筆者認為“杯酒”乃宋人杜撰,惟“釋兵權”合乎史實。至於歷史現實中宋初君主收回禁軍將領兵權的過程,學者徐規、丁則良等,已然作出深入的研究,並認為解禁軍兵權、革五代之弊,乃一漫長過程。首先,太祖登位之後進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調動,將禁軍部門一分為三,之後繼續以人事調動形式逐漸以資淺材庸之士取代原來資深將領,防止五代以來武人干政之事,而此行為一直延續到宋真宗(968-1022,998-1022在位)時期。
3.1 縣空禁軍五大高位,分割禁軍
首先,據徐規的〈再論杯酒釋兵權—兼答柳立言先生〉,宋君收兵權始於太祖建隆元年正月,當時太祖五次對禁軍將領進行人事調動,將禁軍兩司的五個高級職位—殿前都點檢、殿前副都點檢、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侯—縣置而不補人,壓低禁軍武將位望,同時將侍衛親軍司一分為二,將禁軍二司二分為三,詳情可參以下諸表。
|
建隆元年正月人事調動 |
||||
|
職位 |
調動前 |
調動後 |
||
|
殿前司 |
||||
|
殿前都點檢 |
太祖 |
慕容延釗(?-964) |
||
|
殿前副都點檢 |
慕容延釗 |
高懷德 |
||
|
殿前都指揮使 |
石守信 |
王審琦 |
||
|
殿前都虞侯 |
王審琦 |
趙光義 |
||
|
侍衛親軍司 |
||||
|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
李重進 |
韓令坤(923-968) |
||
|
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 |
韓通(908-960) |
石守信 |
||
|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侯 |
韓令坤 |
張令鐸(911-979) |
||
|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
高懷德 |
張光翰(?-967) |
||
|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
張令鐸 |
趙彥徽(?-968) |
||
資料來源:徐規:〈再論杯酒釋兵權—兼答柳立言先生〉,見註釋。30
當中可見大部分將領都得到升遷,惟當中有兩位宿將遭罷免,是為李重進(?-960)和韓通;李重進的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改由韓令坤充任,韓通擔任的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則由石守信任職。當時韓通已死,屬一般人事變動。然而,李重進的情況較為特別。趙匡胤、李重進皆為後周舊臣;但李重進事周時便曾助周世宗南征北討,屢獲軍績,而趙匡胤本為周世宗的親信衛士,直到顯德元年(954)二月在高平之戰建立功勳後獲得升遷,與李重進分別被擢升為殿前都虞侯和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故論軍中資歷,李趙二人高下立見。顯德五年(958),世宗命李重進戍守揚州,握有重兵,而此時趙匡胤才被升為殿前都點檢,與遙領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的李重進同級。31及世宗病逝,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而得位。同為前朝最高禁軍將領、在軍中威望亦高於匡胤,李重進乃趙匡胤即位之初的一大威脅,而《宋史》亦指出“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太祖”,太祖很可能知悉此事,故未幾便派石守信等討伐之,順帶一提,按《筆錄》、《記聞》等史料之說法,“杯酒”乃發生於討伐李氏之後。32
|
建隆元年七月人事調動 |
||
|
職位 |
調動前 |
調動後 |
|
侍衛親軍司 |
||
|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
張光翰 |
韓重贇(?-974) |
|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
趙彥徽 |
羅彥懷(生卒不詳) |
(接下頁)
|
建隆二年閏三月人事調動 |
||
|
職位 |
調動前 |
調動後 |
|
殿前司 |
||
|
殿前都點檢 |
慕容延釗 |
不再徐授 |
|
侍衛親軍司 |
||
|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
韓令坤 |
石守信 |
|
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 |
石守信 |
空缺 |
|
建隆二年七月的人事調動 |
||
|
職位 |
調動前 |
調動後 |
|
殿前司 |
||
|
殿前副都點檢 |
高懷德 |
不再除授 |
|
殿前都指揮使 |
王審琦 |
韓重贇 |
|
殿前都虞侯 |
趙光義 |
張瓊(?-965) |
|
侍衛親軍司 |
||
|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
石守信,但“其實兵權不在也”33 |
|
|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侯 |
張令鐸 |
空缺25年 |
|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
韓重贇 |
劉廷讓(929-987) |
|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
羅彥懷 |
崔彥進(922-988) |
|
建隆三年九月人事調動 |
|
||
|
職位 |
調動前 |
調動後 |
|
|
侍衛親軍司 |
|
||
|
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 |
石守信 |
石守信自解軍職,後不再除授 |
|
諸表資料來源:徐規:〈再論杯酒釋兵權—兼答柳立言先生〉,見註釋。34
從上表可見,太祖自即位之初便開始對禁軍進行人事調動。自建隆元年正月至建隆三年九月期間,先是罷免李重進、韓通,解除最大威脅,然後逐漸將殿前司、馬步軍司正、副都指揮使及都虞侯等官職閒置起來,壓低禁軍武將位望,同時初步形成殿前司、侍衛馬軍司、步軍司由各自都指揮使及都虞侯管轄的局面,使到由殿前司、侍衛馬軍司及步軍司構成的禁軍三衙體制在實際上出現。35
3.2取締資深將領
宋初,除卻不授高職,降低禁軍武將位望,同時將禁軍部門二變為三;宋初君主亦以資淺材庸者或心腹代替資深將領,減低禁軍武將發動軍事叛變的可能。現存較為完整的北宋禁軍將領資料是收錄於南宋筆記《景定建康志》的〈侍衛馬軍司題名記〉,記載了宋初以降“侍衛馬軍司”高級將領的名冊。36今重新整理〈侍衛馬軍司題名記〉,按時序列出太祖至真宗時期任侍衛馬軍司高級宿將的人員及其資歷出身的變化,局部剖析宋初君主處理禁軍的人事調動安排。見下表:
|
太祖朝侍衛馬軍司 |
||
|
名稱 |
軍職/任職詳情 |
備註 |
|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
||
|
張光翰 |
建隆元年正月除都指揮使,八月罷。 |
無傳,但有翊戴之功。37 |
|
韓重贇 |
建隆元年八月除都指揮使,二年七月改差。 |
有翊戴之功,在太祖即位後,繼續為其征戰。38 |
|
劉匡義(生卒不詳) |
建隆二年七月除都指揮使,開寳六年(974)九月罷。 |
無傳。 |
|
党進(927-977) |
開寳六年九月除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二年(977)十一月罷。 |
助太祖敗北漢有功。39 |
|
侍衛馬軍都虞候 |
||
|
張廷翰(?-969) |
乾徳五年(968)正月除都虞候,開寳二年二月致仕。 |
後周將領,在太祖即位後為其征戰。40 |
|
李進卿(915-973) |
開寳二年八月除都虞候,九月改差。 |
後周將領,在太祖即位後為其征戰。41 |
|
李漢瓊(927-981) |
開寳六年九月除都虞候,太平興國二年十一月罷。 |
助太祖攻取南唐都城金陵有功。42 |
上表可見,太祖朝在侍衛馬軍司任高職者共有七位將領,當中韓重贇、張廷翰、李進卿、党進和李漢瓊五人在《宋史》均有傳,而上述諸將主要都有協助太祖東征西討。
(接下頁)
|
太宗朝侍衛馬軍司 |
||
|
名稱 |
軍職/任職詳情 |
備註 |
|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
||
|
白進超(?-980) |
太平興國二年十一月除都指揮使,三年四月改差。 |
無傳,無殊戰功,因。“小心謹密擾士卒”而致將帥。43 |
|
劉延翰(923-992) |
太平興國五年(990)十月權都指揮使,六年七月罷。 |
無傳,無領軍之才。44 |
|
米信(928-994) |
太平六年(991)八月遷都指揮使雍熙三年(986)七月罷。 |
後周時期禁軍,多行不法。45 |
|
李繼隆 |
端拱元年(988)二月遷都指揮使至道三年(997)五月罷。 |
太宗外戚,從軍多年。46 |
|
范廷召(927-1001) |
至道三年七月除都指揮使,咸平三年(1000)二月改差。 |
後周武將,宋太祖朝、太宗朝奉命征戰。47 |
|
侍衛馬軍都虞候 |
||
|
李繼隆(950-1005) |
雍熙三年七月除都虞候,端拱元年二月遷都指揮使。 |
見上。 |
|
王漢忠(949-1002) |
端拱二年(989)三月除都虞候,淳化五年(994)六月改差。 |
出身太宗藩邸,具領軍之材。48 |
|
王榮(947-1016) |
淳化五年闕。 |
出身太宗藩邸、多行不法。49 |
|
康保裔(?-1000) |
至道三年七月除都虞候,咸平三年正月死節河朔。 |
太祖朝至真宗朝年間參與多場戰役。50 |
從上表可見,及太宗朝,侍衛馬軍司任高職者的八位將領中,白進超、劉延翰、米信、王榮乃因循苛且、資淺材庸、多行不法之人。至於資歷較深的將領有康保裔、范廷召、李繼隆、王漢忠等,當中李、王二人分別是太宗的外戚和藩邸舊人;康、范等與太宗關係較不密切而又有領軍才能者乃屬少數。
至於真宗朝,在侍衛馬軍司任高職者共有十六位將領(見下頁表)。明顯可見,在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方面,真宗以太宗舊人—葛霸(933-1007)和高瓊(935-1006)接替太宗朝已在禁軍任職的范廷召、王漢忠,之後又以資淺的功臣子弟—曹璨(950-1019)取代葛、高;在副都指揮使和都虞侯方面,則先後任之以襄王府出身的蔚昭敏(?-1024)和劉謙(950-1009),以及張旻(生卒不詳)、鄭誠(生卒不詳)、高翰(生卒不詳)、王守贇(生卒不詳)、靳忠(生卒不詳)等無傳、非治軍之才的軍人。
誠然,有關宋初禁軍部門人員的史料並不多,目前相對完整的〈侍衛馬軍司題名記〉只是記錄了侍衛馬軍司的高級將領。不過,觀乎侍衛馬軍司在太祖朝至真宗朝的人員變動,可以推斷宋初三帝多次透過人事任免,將禁軍部門的高級將領由起初的資深將領取締為皇帝的心腹或資淺材庸的軍人,防止“陳橋兵變”歷史重演,解除五代以來禁軍將領對皇帝的威脅。
|
宋真宗朝侍衛馬軍司 |
||
|
名稱 |
軍職/任職詳情 |
備註 |
|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
||
|
至道三年七月除都指揮使,咸平三年二月改差。 |
見上。 |
|
|
王漢忠 |
咸平三年二月除副都指揮使,四年二月改差。 |
|
|
葛霸 |
咸平四年三月除都指揮使,景德二年十二月罷。 |
出身太宗藩邸。51 |
|
髙瓊 |
咸平六年五月權闕。 |
曾為太宗親衛,資深武將。52 |
|
曹璨 |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遷都指揮使,二年九月罷。 |
曹彬長子,沒有顯赫軍職。53 |
|
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 |
||
|
曹璨 |
景徳二年十二月除副都指揮使,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遷都指揮使。 |
見上。 |
|
張旻 |
大中祥符二年九月除副都指揮使,六年正月除樞密副使。 |
無傳。 |
|
蔚昭敏 |
大中祥符九年正月除副都指揮使,天禧二年七月改差。 |
襄王府出身。54 |
|
侍衛馬軍都虞候 |
||
|
劉謙 |
咸平六年五月權,景徳元年八月除都虞候二年十二月改差。 |
襄王府出身。55 |
|
景徳二年十一月除都虞候,大中祥符元年改差副都指揮使。 |
無傳。 |
|
|
鄭誠 |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權十二月除都虞候,二年九月改差。 |
無傳。 |
|
髙翰 |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到任,七年十月改差。 |
無傳。 |
|
王守贇 |
大中祥符七年十月除都虞候,九年正月改差。 |
無傳。 |
|
靳忠 |
大中祥符九年正月除都虞候,天禧三年六月改差。 |
無傳。 |
|
劉美(962-1021) |
天禧三年七月除都虞候,五年八月致仕。 |
原為銀匠,本與軍旅無緣。56 |
|
(接下頁) |
||
|
楊崇勲 |
天禧四年二月除都虞候,乾興元年正月改差。 |
品行拙劣。57 |
|
夏守贇 |
乾興元年二月除都虞候,天聖二年二月改差。 |
軍中無威望。58 |
以上三表資料來源:〈侍衛馬軍司題名記〉,見註釋。59
總結而言,本文認為“杯酒釋兵權”並無其事。首先,若“杯酒”確有其事,作為宋初的重要政治事件,國史、實錄沒有記載,已然令人懷疑,而首次記載“杯酒”的文本乃出現於距離“事發”時間至少半世紀的筆記小說,其撰者與之後有關史料的撰者都不可能親眼見證事件,故“杯酒”的記載本源可信度有限。其次,從文本內容上觀之,“杯酒”亦有幾個不合理之處。從事發的日期上觀,諸書只道平定二叛之後,惟《長編》與《宋史》分別指出“杯酒”乃發生於建隆二年七月和乾德初年,但先後被後世學者推翻;就太祖在“杯酒”之後安排諸將後人尚主的處置上,“杯酒”有關人士尚主的時間與史料記載出現了明顯誤差;就“杯酒”策劃者趙普方面的史料,諸書肯定了趙普在“杯酒”中扮演的角色,但關於趙普的官方文獻卻沒有“杯酒”的蛛絲馬跡。上述種種皆為“杯酒”的真確性增添疑點。
從宏觀上看,對於“杯酒”的“發生”,當時人並無留下直接記載,但事隔數十年之後卻出現諸多記載,且觀其文辭用語,如撰者得以親歷其境,觀其詳細程度,則時間愈長而愈多細節。其即如上世紀以顧頡剛為首之古史辨派所倡之“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因此,觀其記載可信性之低,以及種種與史載相悖之處,乃宋人以訛傳訛,並隨年月不斷被人增添細節而逐漸成形的故事。惟故事中有部分內容與《宋史》、《長編》吻合,故“杯酒”—九分假一分真,假在“杯酒之間”,真在收回禁軍將領兵權。
回顧史料與學者研究,北宋初年收回兵權的過程,始於太祖透過人事調動—縣空殿前都點檢、殿前副都點檢、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侯,壓低禁軍武將位望,同時令禁軍由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各自的都指揮使及都虞侯管轄的局面,將禁軍部門分割—由二變三,令之後的禁軍三衙體制在實際上出現。此外,北宋自太祖始至真宗,逐步以資淺材庸之軍人或君主信任之人取締資深將領,解除五代以來禁軍將領對君主的威脅,過程長達三十多年。故可知,從歷史證據觀察或從現實政治角度進行分析,解除禁軍兵權一事不可能透過一次酒宴便能解決,是故“杯酒釋兵權”純粹虛構。
甲、學術論文 / 期刊
1. 丁則良:〈杯酒釋兵權考〉,載氏著《丁則良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45。
2. 王育濟:〈論“杯酒釋兵權”〉,《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頁116-125。
3. 徐規:〈再論杯酒釋兵權–兼答柳立言先生〉,載氏著《仰素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616-633。
4. 陳峰:〈論宋初三朝的禁軍三衙將帥〉,《河北學刊》(第22卷第2期),2002年第2期,頁120-124。
乙、文獻材料
1. [宋]王曾撰;張其凡點校:《王文正公筆錄》(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2. [宋]王應麟:《玉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
3. [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5.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6.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15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7. [宋]李燾著;[清]黃以周等輯補:《續資治通鑑長編附拾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 [宋]馬光祖修、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六〈侍衛馬軍司題名記〉,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9. [元]脫脫:《宋史》(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10. [元]脫脫:《宋史》(第25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11. [元]脫脫:《宋史》(第26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12. [元]脫脫:《宋史》(第27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13. [元]脫脫:《宋史》(第28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14. [元]脫脫:《宋史》(第30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15. [元]脫脫:《宋史》(第38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腳註
[1] 丁則良:〈杯酒釋兵權考〉,載氏著《丁則良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45。
[2] [宋]王曾撰;張其凡點校:《王文正公筆錄》,(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16。
[3] [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涑水記聞十六卷〉,載[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391。
[4] 鄧廣銘:〈略論有關涑水記聞的幾個問題〉,載[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
[5] 丁則良:〈杯酒釋兵權考〉,載氏著《丁則良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3。
[6] 按:“文正”乃宋代文臣諡號最尊貴者,北宋僅司馬光、王曾、范仲淹三人獲諡“文正”。
[7]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2冊),卷二,宋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條,(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0。
[8] [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1。
[9]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2冊),卷二,宋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條,(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49。
[10] [元]脫脫:《宋史》(第25冊),卷二百五十,〈石守信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8810。
[11] 同上。
[12]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2冊),卷二,宋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條,(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0。
[13] 丁則良:〈杯酒釋兵權考〉,載氏著《丁則良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
[14]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15冊),卷二百零四,宋英宗治平二年三月壬午條,(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4953。
[15]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2冊),卷二,宋太祖建隆二年十月丙午條、十一月壬申條,(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5。
[16] [元]脫脫:《宋史》(第25冊),卷二百五十,〈石守信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8810、[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1。
[17] [元]脫脫:《宋史》(第25冊),卷二百五十,〈石守信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8810、[宋]王曾撰;張其凡點校:《王文正公筆錄》,(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16、[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1。
[18]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2冊),卷二,宋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條,(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0。
[19] [宋]王曾撰;張其凡點校:《王文正公筆錄》,(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16。
[20] [元]脫脫:《宋史》(第25冊),卷二百五十,〈高懷德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8822。
[21] [元]脫脫:《宋史》(第25冊),卷二百四十八,〈秦國大長公主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8771。
[22] [元]脫脫:《宋史》(第25冊),卷二百四十八,〈魏國大長公主〉、〈魯國大長公主〉,(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8772。
[23] [宋]王曾撰;張其凡點校:《王文正公筆錄》,(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16。
[24] [宋]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1。
[25]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2冊),卷二,宋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條,(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0。
[26] 註10。
[27] 丁則良:〈杯酒釋兵權考〉,載氏著《丁則良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6-8。
[28] 同上,頁8。
[29] 前文透過《宋史》、《長編》反映石守信之禁軍兵權乃於建隆二年被收,以證《宋史》將“杯酒釋兵權”之發生時間定於“乾德初”之謬。
[30] 徐規:〈再論杯酒釋兵權—兼答柳立言先生〉,載氏著《仰素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626-629。
[31] 王育濟:〈論“杯酒釋兵權”〉,《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頁116-125;徐規:〈再論杯酒釋兵權—兼答柳立言先生〉,載氏著《仰素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616-633。
[32] [元]脫脫:《宋史》(第40冊),卷四百八十四,〈李重進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13978。
[33]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2冊),卷二,宋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條,(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50。
[34] 徐規:〈再論杯酒釋兵權—兼答柳立言先生〉,載氏著《仰素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626-629。
[35] 按宋太宗後期和真宗即位初,一度任命田重進、傅潛及王超為馬步軍都虞侯,但自景德二年王超被罷黜後,馬步軍都虞侯從此不再授人。
[36] [宋]馬光祖修、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六〈侍衛馬軍司題名記〉,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29。
[37] [元]脫脫:《宋史》(第01冊),卷一,〈太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5。
[38] “宋初,以翊戴功,擢為龍捷左廂都校、領永州防禦使……討李重進,為行營馬步軍都虞侯”。見[元]脫脫:《宋史》(第25冊),卷二百五十,〈韓重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8823。
[39] “開寶二年,太祖師臨晉陽、置砦四面,命進主其東偏。師未成列,太原驍將楊業領突騎數百來犯,進奮身從數人逐業;業急入隍中,會援兵至,緣縋入城獲免。上激賞之。六年,改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鎮安軍節度”。見[元]脫脫:《宋史》(第26冊),卷二百六十,〈党進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018。
[40] “後世宗平淮甸,以功遷鐵騎右第二軍都虞侯”、“宋初……從平揚州,又以功遷控鶴左廂都指揮使……乾德中,興師伐蜀,以廷翰為歸州路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見[元]脫脫:《宋史》(第26冊),卷二百五十,〈張廷翰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007-9008。
[41] [元]脫脫:《宋史》(第27冊),卷二百七十三,〈李進卿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323-9324。
[42] “王師征江南,命領行營騎軍兼戰框左廂指揮使,自蘄春攻峽口砦,斬首數千級,獲樓船百艘,沿流拔池州,破銅陵,取當塗,作浮梁於牛渚以濟大軍。分圍金陵,率所部度秦淮……江南平,以功領振武軍節使度”。見 [元]脫脫:《宋史》(第26冊),卷二百六十,〈李漢瓊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020。
[43] “初無灼然戰功,徒以小心謹密擾士卒,故致將帥焉”。見[宋]李燾著、[清]黃以周等輯補:《續資治通鑑長編附拾補》,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165。
[44] 不通軍法,曾經不假思索地聽從太宗,佈八陣迎戰契丹,幸得監軍反對,改以前後二陣,才不致招敗。見[宋]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2645-2646。
[45] “信遂專恣不法,軍人宴犒甚薄,嘗私市絹附上計吏,稱官物以免關征,上廉知之”。見[元]脫脫:《宋史》(第26冊),卷二百六十,〈米信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023。
[46] 太宗明德李皇后之兄長;自太祖乾德年間至太宗年間,多次參戰,逐步晉級。見[元]脫脫:《宋史》(第26冊),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8963-8969。
[47] [元]脫脫:《宋史》(第28冊),卷二百八十九,〈范廷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697-9698。
[48] “漢忠有識略,軍政甚肅”。見[元]脫脫:《宋史》(第27冊),卷二百七十九,〈王漢忠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476。
[49] “(王)榮粗率,所為不中理,侵取官地蒔蔬,吝惜公錢,不以勞將士,且母老不迎養,供給甚薄”。見[元]脫脫:《宋史》(第27冊),卷二百八十,〈王榮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499。
[50] [元]脫脫:《宋史》(第38冊),卷四百四十六,〈康保裔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13150。
[51] [元]脫脫:《宋史》(第28冊),卷二百五十八,〈曹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8977。
[52] [元]脫脫:《宋史》(第28冊),卷二百八十九,〈高瓊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8984。
[53] [元]脫脫:《宋史》(第28冊),卷二百八十九,〈葛霸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699;“雖無攻戰之效,然累歷邊任,領禁衞十餘年,善撫士卒,忠厚謙靜,未嘗有過”。見[宋]李燾: 《續資治通鑑長編》(第 7 冊),卷九十四,宋真宗天禧三年七月戊辰條,(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2162。
[54] [元]脫脫:《宋史》(第30冊),卷三百二十三,〈蔚昭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10455。
[55] [元]脫脫:《宋史》(第27冊),卷二百七十五,〈劉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384。
[56] 陳峰:〈論宋初三朝的禁軍三衙將帥〉,《河北學刊》(第22卷第2期),2002年第2期,頁120-124。
[57] “性貪鄙…喜中傷人,人以是畏之”。見[元]脫脫:《宋史》(第28冊),卷二百九十,〈楊崇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714。
[58] “性庸怯,寡方略,不為士卒所服”。見[元]脫脫:《宋史》(第28冊),卷二百九十,〈夏守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9716。
[59] [宋]馬光祖修、周應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六〈侍衛馬軍司題名記〉,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宋元方志叢刊》(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29。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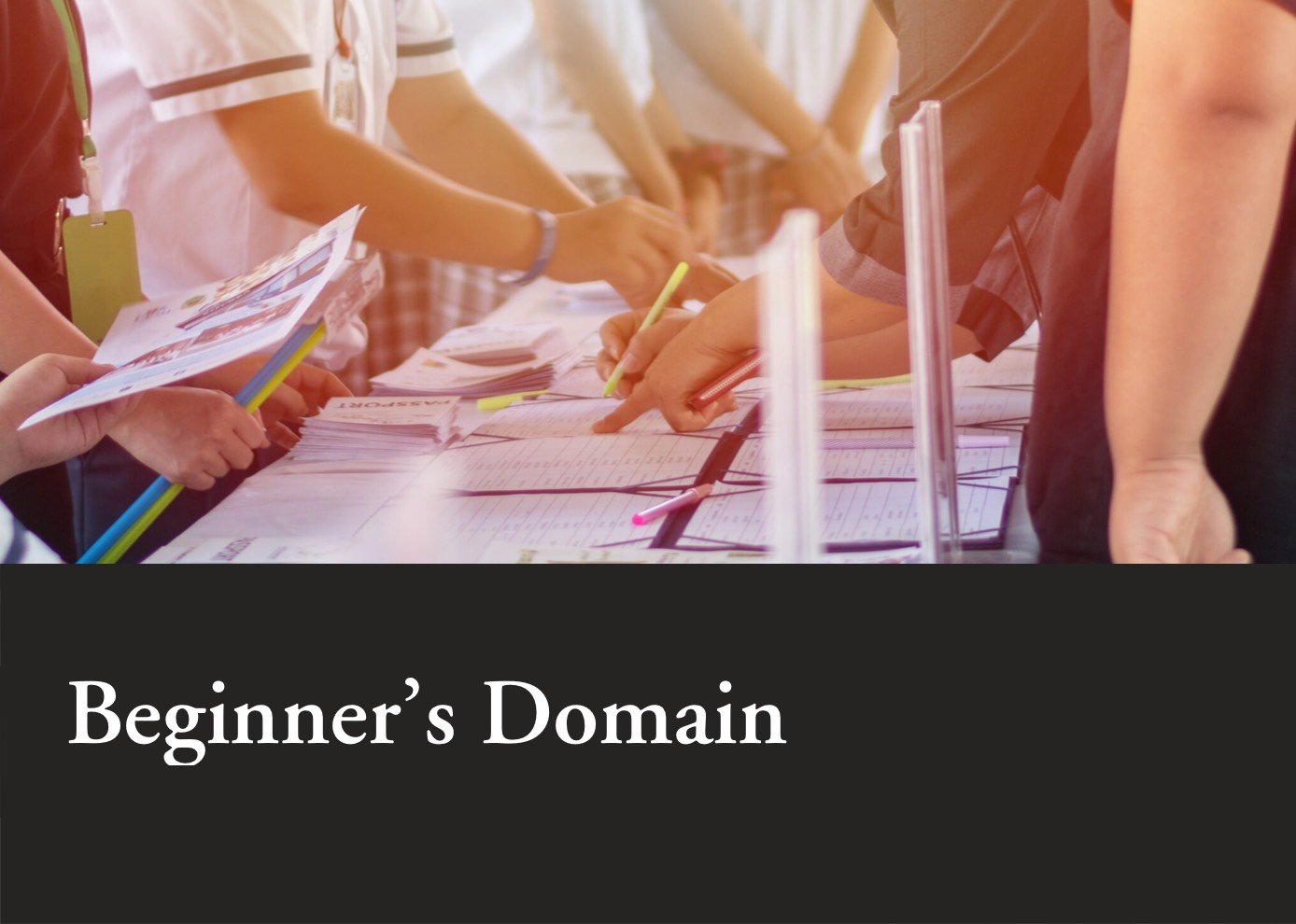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