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元宵節與宵禁的關係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以中國古代嚴謹的宵禁制度,所造成的平凡而且刻板到只有一種節奏而沒有變化的古代生活所需的調劑,與元宵節所特有的在這幾天的節令時間中不宵禁的鬆弛措施。而元宵節與其它歲時節令的一項重要的差異,便是先前所提到的幾天的節令時間,其並非為單日的節慶,而是日以繼夜的連續假期。以古代生活所需的調劑這一方向來闡述元宵節這一傳統文化節日在古代中國的必要性。
在葛兆光教授於〈嚴昏曉之節-古代中國關於白天與夜晚觀念的思想史分析〉一文中提及到有關於中國古代對於夜晚觀念的分析,當中原文如下:
時間分配,說到根本處是一個有關「秩序」的事。 在古代中國的一統社會裏面,時間分配是很重要的,無論民間和官方都一樣重視。 民間關心它,自有民間的理由,這是因為生產和作息需要,如果四季十二月流轉不息是物理的節奏,那麼黑夜與白晝的交替則關乎生理的節奏。 在沒有充足照明條件的時代,人們只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順應自然並不是為了表現「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情懷。官方重視它,也自有官方的道理,因為對作息時間的管理,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社會秩序的管理,大家步伐一致,各地時間一致,才會覺得像一個「民族」,一個「 國家」。1
因此,中國自古代到近代,兩千年來一直有「巡夜」的制度.,《周禮》的〈秋官司寇〉一篇中有記載到古代有「司寤氏」這個職官,其職責為「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2
在古代中國是以自然的晝夜交替為基礎所形成的一個基礎的社會秩序;換言之,即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習慣。而在燈火相對困難,需要憑藉日光的古代社會,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而是「天之經、地之義」,違背大家習慣的日夜秩序而「晝伏夜出」,常常需要非常特別的理由來解釋。因此歷代制度中關於法律的規定,往往也劃出了關於生活秩序的合法與非法、正常與非常的界線。
這種有關於生活秩序的制度規定來源很早,而最早可見其於法律上則是在唐宋時期。根據唐代(618-690、705-907)的律法,《唐律疏議》的規定,「依刻漏法:晝漏盡爲夜,夜漏盡爲晝。謂夜無事故,輒入人家,笞四十。」,見於《唐律疏議・卷第十八》中〈夜無故入人家〉一條。3 而此條例亦無更改的見於宋代(960-1279)的法律《宋刑統》中。
依照刻漏法,當時的一天被分為晝與夜兩半。據《唐律疏議·卷第二十六》中的〈犯夜〉一條,「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閉門鼓後、開門鼓前行者,皆爲犯夜。故,謂公事急速及吉、兇、疾病之類。」4,當時的律法規定了在閉門鼓後、開門鼓前,凡是夜行者都算是犯夜,只有公事急速及吉、兇、疾病之類可免。
到了元代(1271-1368),有關於宵禁的法律,也還是有所規定。據《大元聖政國朝典章》所載,「其夜禁之法,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有公事急速及喪病產育之類,則不在此限。違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七下,準贖元寶鈔一貫。」5
從以上三個朝代的律例中有關於日常生活秩序管制的法律,也即是規定了對於夜遊的懲罰。可以看到的是元代開始,對於日常生活秩序的控制就相當嚴厲,這一點可以從《大元聖政國朝典章》中犯夜者須笞二十七下,較之唐宋時為多。可見宵禁這項政策正是中國古代的統治階級用以穩固社會秩序或控制平民百姓生活作息,使其維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習慣。而這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秩序是傳統中國社會中的人們所普遍相信的生活秩序。由於宵禁制的嚴格執行,我們可以相信在古代中國社會,針對夜晚的管理很嚴格。而這種針對夜晚的嚴格管理,使得民間產生了許多關於夜晚混亂的傳說。由於這些傳說都發生在夜晚,又更使人相信夜晚與罪惡的關連。正所謂「月黑風高殺人夜」,這些話語都使人把「殺人放火」這些破壞秩序,違背社會良俗的行為與夜晚掛鉤。
對於元宵之於宵禁的意義,在陳熙遠先生的《中國夜未眠-明清時期的元宵、夜禁與狂歡》一文中有很好的闡述。
不論是「州官放火」,或是「百姓點燈」,慶祝的其實是一樣的元宵佳節。但反過來說,一樣是元宵節慶,州官本意在「點燈」,而百姓卻往往樂於「放火」──從禮教與法度所調控的日常秩序中解放出來。
原來元宵節既是歲時的節令之一,其實本是扣合在日常生活的環節,也是屬於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常生活所預設的常態的、慣性的空間與時間秩序裡,元宵節造成一種戲劇性的斷裂與幹擾,但這種斷裂與乾擾卻是藉由接續或彌縫日常生活裡的各種差序與界限而成;在「金吾弛禁」的默許下,元宵的嘉年華會裡「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縝素不分」。 換言之,元宵節乃以日夜接續、城鄉交通、男女雜處、官民同樂、以及雅俗並陳的方式,顛覆「禮典」與「法度」所調控定位的日常(everydayness)──從日夜之差、城鄉之隔、貴賤之別到男女之防。 而這種暫時性的越界與烏托邦裡的狂歡,可以解釋成盛世太平中民間活力的展現,也可以功能性地視為歲時生活的調節,或是積鬱力量的表達,但也可能被判定為對禮教規範與法律秩序的扭曲與破壞。6
當中所提及的「從禮教與法度所調控的日常秩序中解放出來」7,可以看出如果生活確實始終是那麼平凡而且刻板到只有一種節奏而沒有變化,人們會覺得需要調劑,而古代中國法律規定的幾天節令不宵禁,就是這種刻板生活的一種補充。
有關元宵節的由來,最晚在隋文帝時代,京城與各州已普遍有於正月望日「燎炬照地」的作法,並在夜裡進行各種慶祝活動。有關此事的記載可見於《隋書》中:
臣聞昔明王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導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視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袨服靚組,車馬填噎。菜餚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 盡室並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斷。8
在隋文帝時期可以看到這一放燈,觀燈的習慣只在正月望夜舉行。 而到唐代,上元觀燈,已經有三日之規,唐玄宗時燈節乃從十四日起至十六日,連續三天。宋太祖時追加十七、十八兩日,成「五夜燈」。據《帝京景物略》所載:
上元三夜燈之始,盛唐也,玄宗正月十五前後二夜,金吾弛禁,開市燃燈,永為式。上元五夜燈之始,北宋也,乾德五年,太祖詔曰:朝廷無事,年穀屢登,上元可增十七十八兩夜。上元六夜燈之始,南宋也,理宗淳佑三年,請預放元宵,自十三日起,巷陌橋道,皆編竹張燈。而上元十夜燈,則始我朝,太祖初建南都,盛為彩樓,招徠天下富商,放燈十日。 今北都燈市,起初八,至十三而盛,止十七乃罷也。9
此即元宵節的一些歷史背景,而對於元宵節之於宵禁的意義或許我們可以從南宋時期成書的《夢梁錄》中百姓對於元宵的態度中略窺一斑。
元夕之時,自十四為始,對支所犒錢酒。十五夜,帥臣出街彈壓,遇舞隊照例特犒。 街坊買賣之人,並行支錢散給。此歲歲州府科額支行,庶幾體朝廷與民同樂之意。…… 府第中有家樂,兒童亦各動笙簧琴瑟,清音嘹亮,最可人聽,攔街嬉戲,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燈火,處處管弦。…… 遊人玩賞,不忍捨去。諸酒庫亦點燈球,喧天鼓吹,設法大賞,妓女群坐喧嘩,勾引風流子弟買笑追歡。 諸營班院於法不得與夜遊,各以竹竿出燈球於半空,遠睹若飛星。又有深坊小巷,繡額珠簾,巧製新裝,競誇華麗。公子王孫,五陵年少,更以紗籠喝道,將帶佳人美女,遍地遊賞。…… 至十六夜收燈,舞隊方散。10
一向注重秩序而畏懼混亂的朝廷,一直嚴厲區分「貴賤」、「男女」、「緇素」的界限,格外擔心晝夜不分會引起混亂,竟然在這特別的時間裡允許混亂。最主要就是因為這一界限一直過於嚴厲和分明,白天和黑夜、上層和下層、男人和女人、世外和世內,常常是在一個單調刻板的節奏下重複。於是,不得不提供一個變化的機會,讓這種生活緊張鬆弛下來,這也就是元宵節等傳統節日之於宵禁的意義了。
近人論文
1. 葛兆光:《嚴昏曉之節-古代中國關於白天與夜晚觀念的思想史分析》,《臺大史學報》,第32期(2003年12月),頁33-55。
2. 陳熙遠:《中國夜未眠-明清時期的元宵、夜禁與狂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75期,第2卷(2004年6月),頁283-329。
古著
1. 《周禮・秋官司寇》,《十三經注疏》影印本《周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79)
2. (唐)長孫無忌等撰:《四部叢刊三編 史部 故唐律疏議 第2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5年)
3.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4. (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4冊。
5. (明)劉侗,(明)於奕正撰:《帝京景物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6. (宋)吳自牧:《夢粱錄》,(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
腳註
[1] 葛兆光:〈嚴昏曉之節-古代中國關於白天與夜晚觀念的思想史分析〉,《臺大歷史學報》,第32期(2003年12月),頁33-34。
[2] 《周禮・秋官司寇》,《十三經注疏》影印本《周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36,頁885。
[3] (唐)長孫無忌等撰:《四部叢刊三編 史部 故唐律疏議 第2冊》,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重印,(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5年),頁151。
[4] 同上,頁504。
[5]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卷51,〈刑部〉,卷13,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87冊,頁493。
[6] 陳熙遠:〈中國夜未眠——明清時期的元宵、夜禁與狂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75期,第2卷(2004年6月),頁328-329。
[7] 同上,頁328。
[8]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62,〈柳彧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4冊,頁1481-1483。
[9] (明)劉侗,(明)於奕正撰:《帝京景物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頁88。
[10] (宋)吳自牧撰:《夢粱錄》,(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頁2-3。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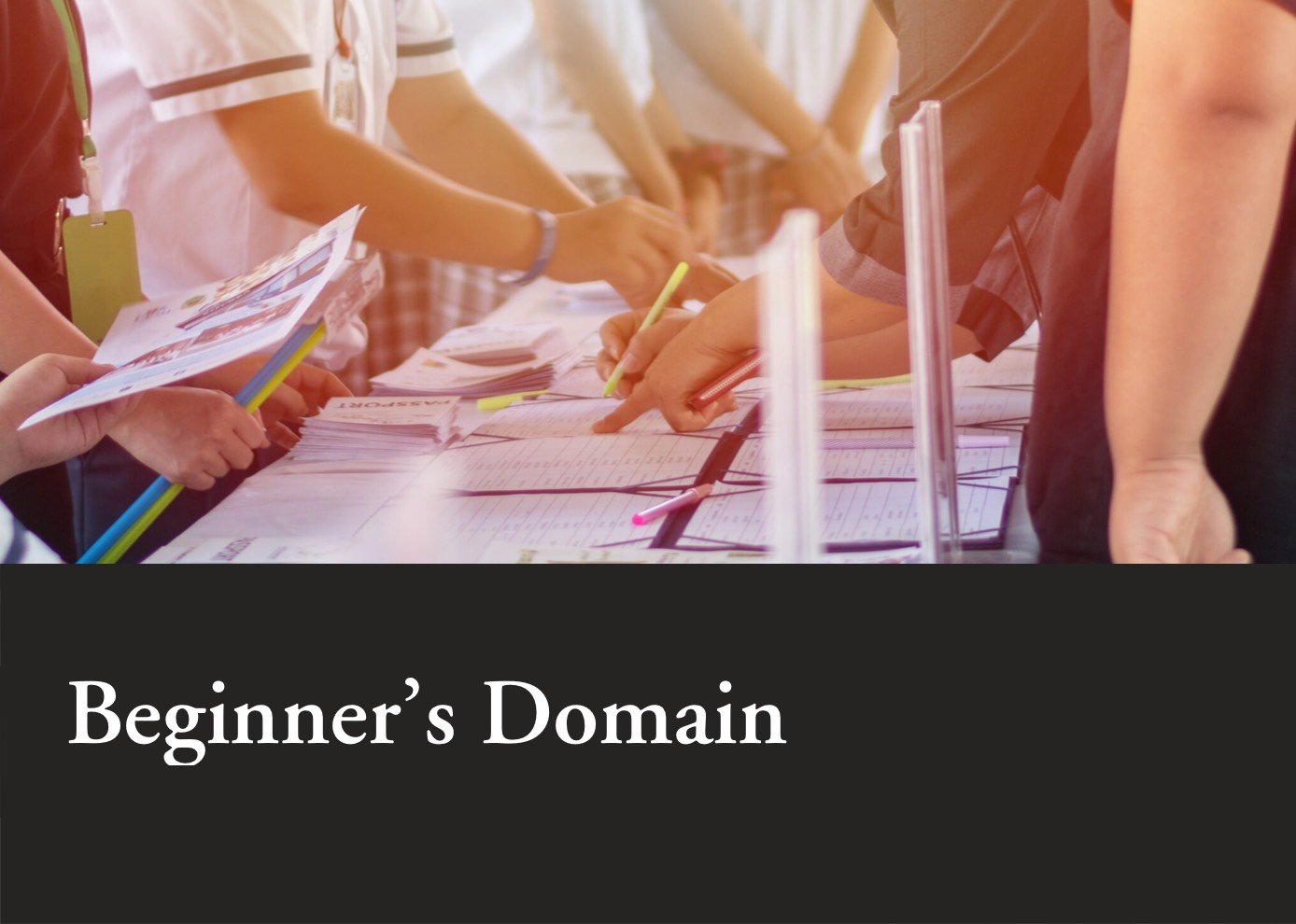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