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斯賓諾莎與老子自由觀之異同
斯賓諾莎“神、自然與實體”與中國的老子“道”有相似的理念,因而他們學說中的自由觀也有共同之處。惟將兩者比較的研究甚少,幾乎於無,為了進一步發掘兩者的差異,本文將仔細論述斯賓諾莎與老子的哲學思想及自由觀理念。
中國對於斯賓諾莎的認識始於梁啟超在日本出版的《西儒學案》,其中介紹斯賓諾莎這位荷蘭哲學家,1至今有不少學者鑽研其學說。曾有數篇與莊子哲學比較的論文,如和健偉的〈斯賓諾莎哲學與莊子哲學的比較研究〉,2但更多的文章只是探究斯賓諾莎個人的哲學觀念。難得將老子與斯賓諾莎共同研究的文章如〈老子的“道”與斯賓諾莎的“實體”〉,3作者潘斌對後者的思想卻不夠深入,以致對斯賓諾莎的神、自然與實體三位一體的觀念了解不足,不能對兩者作出詳盡比較。筆者將引用中國鑽研斯賓諾莎的權威學者洪漢鼎4的著作《斯賓諾莎哲學研究》為主,與老子思想進行比較,對兩者的自由觀進行探討。
在論述斯賓諾莎與老子的自由觀之前,必先了解兩者自由觀的基礎,即斯賓諾莎的“神、自然與實體”及老子的“道”,分別知道他們如何了解世界的最高規則,才可明白他們的自由觀是如何體現及兩者的差異。
別涅狄克特‧德‧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在1632年出生於荷蘭的猶太人商人家庭,自小接受猶太教的思想,他在青少年時期接觸有別於傳統神教的不同思想,令他反思一直以來接受的迂腐宗教思想。他變得漠視猶太教的教規儀式,不參加禮拜活動,更甚至不相信天使的存在,這些行為使他在二十四歲時被逐出猶太教。幸而他曾替他父親行商,過程中結識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他被逐出猶太教後,這些朋友給予他門路謀生,他們經常共同聚會討論學術。其後荷蘭政治鬥爭嚴重,共和政制與君主政制的衝突越趨激烈,斯賓諾莎支持共和政制,著成《神學政治論》、《政治論》等書,以示其神學、個人倫理及社會觀,以望改變當時混亂的社會,其一生致力於哲學思想與神學研究,對後來的德國哲學產生不少影響。5
斯賓諾莎的哲學糅合了不同哲學家的思想,當中包括笛卡爾的形而上學,霍布斯的君主政治觀等,在神的觀念上他擺脫笛卡爾的影響,走上自己獨特思想形成之路。在斯賓諾莎看來,在自然的概念下,6整個宇宙就是一個無限的龐大整體,宇宙中的每一個事物,甚至包括人類自身都只是這個整體的一個極其微小的部分,它們彼此聯繫,並與宇宙整體一致。7他學說中的神並不是一般被認為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人格神,而是類似一種世界自然生發的規律。他認為神不是萬物的外在因,而是萬物的內在因。內在因就是萬物之內的原因,因此神與自然是同一東西,神既沒有意志又沒有目的,它只是由它的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和動作,8否定神的創造活動具有目的。神的創造既然沒有目的,因此所謂神根據其純粹的意志自由預先決定一切事物,乃是一種絕對必然地預先決定一切事物,而萬物由神的永恒而必然的本性所決定。9萬物既然由神的永恒而必然的本性決定,自然乃是一個永恒必然的存在系統,因此醜惡和罪孽並不真正存在於事物的本質中,而只是存在於人們的想象中,10這與老子的相對觀念是一致的。
老子認為天地間的一切事物都依照自然的規律執行發展,其間並沒有人類所具有的好惡感情或目的性的意圖存在著。在這裡老子與斯賓諾莎一樣,都否定了主宰之說,強調天地間萬物自然生長的狀況,並以這種狀況來說明理想的治者效法自然的規律,也是任憑百姓自我發展。這種自由論,企求消解外在的強制性與干預性,而使人的個別性、特殊性以及差異性獲得充分的發展。11
老子認為,“道”是一切存在的根源,也是一切存在的始源,具有無窮的潛在力和創造力。萬物蓬勃的生長,都是“道”的潛在力之不斷創發的一種表現。從萬物生生不息、欣欣向榮的成長中,可以看出“道”有一種無窮的活力。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2這裡所說的“一” “二” “三”,即形容“道”的創生萬物的歷程;“道”逐步向下生成,而創生萬物。“道”創生萬物以後,還要使萬物得到培育,使萬物得到成熟,使萬物得到覆養。從這裡看來,“道”不只是創生萬物,它還內附在萬物中,畜養及培育它們。
老子認為“道”在品位上、在時序上都先於任何東西,它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不會因他物的生滅變化而有所影響,從這些⻆度來看,“道”是具有超越性的。從它的生長、畜養萬物來看,“道”又是內在於萬物的。13
過往將老子與斯賓諾莎進行對比的文章〈老子的“道”與斯賓諾莎的“實體”〉指出,老子的“反者道之動”與斯賓諾莎不變的實體是相悖的。老子的道,具有向相反方向轉化的規律。道與萬物是結合的,因此萬物的運動變化是道的運動法則的體現,觀察萬物的變化就可以已知的運動法則。文章作者潘斌認為“道”的運動變化與斯賓諾莎體系中實體的靜止不變,反映出中西方傳統哲學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斯賓諾莎不免受到西方傳統哲學的影響,實體的不變與樣態的可變正是為了區別原理世界與經驗世界。原理世界是根源經驗世界是表象,因此,斯賓諾莎的實體比具體的樣態更有邏輯的先在性,實體的不變體現了西方傳統哲學經驗世界與理念世界無涉的特徵。14
然而,斯賓諾莎在構想自己的體系時,早就面對西方哲學中原理世界與經驗世界兩離的傳統問題,他在這個問題上將實體與樣態以另一種方式論證,得出原理與經驗世界是互通的結論。實體是形而上學的實體觀念,實體是萬物的基礎,能自己存在而且其存在並不需要別的事物,是萬變中不變的東西。15斯賓諾莎體系的神、自然與實體三位一體的觀念中,實體是“在自身內的存在物”,而樣態是“在他物內的存在物”,亦是“出於神或神的任何屬性的必然性的一切事物”。16樣態就事物作為孤立存在的個別現象看,則事物都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聯繫的;就總體而言,事物就不是分離的、可分的,也不是有生有滅的。實體即神與自然,是一個整體。而樣態即個別事物,即是單獨的個別存在,又是作為整體的一部份。事物作為單獨的個別存在,是處於一定的時間和地點的關係中,因而是倏忽即逝的,而事物作為整體一部份的存在,可以存在於一切時間和地點的關係中,因而是永恒的。這種學說表現了斯賓諾莎把宇宙看作是各種事物相互聯繫的總體或系統的辯證思想,實體即是與神及自然三位一體的觀念。17因此實體的不變,就如老子的道是永恒的存在,但到了物質世界的個別事物時(即從實體而出的樣態),也是可變的,且樣態內蘊含着自然的性質。
簡略而言,斯賓諾莎的神或自然,與老子的道擁有共同內涵,即表示一種萬物生發的自然規律,而在萬物中又蘊含着規律賦予的本性,雖然兩種學說的推論過程完全不同,但對永恒的自然規律得出同樣結論。
斯賓諾莎在《倫理學》提及自由和必然的定義是:“凡是僅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為僅由它自身決定的東西叫做自由;反之,凡一物的存在及其行為均按一定的方式為他物所決定,便叫做必然或受制。”18其觀念不同於普遍認為的與必然相分離或對立的自由,他的自由與必然的區別不在於一個不是必然,另一個是必然。而是它們兩者都是必然,只不過自由是一種不是出於外在原因,而是出於自身內在本性的必然;而必然或受制即是被外在原因所決定的或強制的必然。19他認為自然的運動並不依照目的,因為神或自然的動作都是基於它所賴以存在的必然性,所以神不為目的而在,也不為目的而動作。20所以神是自由的,神是按其本性的法則而行動,神在斯賓諾莎的體系裏神是自由和必然的最高統一。
在斯賓諾莎的觀念裏“一切存在的事物莫不以某種一定的方式表示神的力量,而神的力量即是萬物的原因”,21在被產生的自然內,每一事物都有一種力求保存自己的存在的自然趨向。若不涉及外因,不會在物的本質中發現有可以消滅其自身的東西。22他把這種自然趨向稱為“努力”,這種努力在他看來就是事物的現實本質。23與神相較,人的自由需要努力才能達到。人或萬物存在於由無限多事物組成的世界,被各種外部原因影響,情感因而產生波動。斯賓諾莎將情感分為被動和主動,被動的情感是心靈俱有混淆的觀念,被外在的原因所決定而引起的情感;24主動的情感是具有正確的觀念,心靈是主動的。而主動的感情指借理性指導而自我保存的努力。25當人無法撇除外因而行動,被被動的情感牽制時,人就無法自由。要達到斯賓諾莎所說的“從自己本性決定存在與行為”的自由,就必須對自然的必然性有所認識。
斯賓諾莎提出五種方法以理性克制被動情感的方法,26當中一個方法是“以對事物必然性的知識替代單純想象的知識來克服被動的情感”。《倫理學》說明:“只要心靈理解一切事物都是必然的,那麼它控制情感的力量便愈大,而感受情感的痛苦便愈少”。27斯賓諾莎舉例,如當某人因失掉了他心愛的人或物體感到痛苦,但當他意識到這件事在任何時情況下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他的痛苦將會減輕。28
相比斯賓諾莎闡述“自由”的概念,老子《道德經》內只提及自然而沒有自由二字,但無為與自然的概念中已包含了自由的精神。在中國先秦思想中,最早提出“自由”這一概念的是莊子。莊子的逍遙意指讓萬物歸於本性,各得其所,這就是自由。其思想承老子而來,老子的“自化”也就是各得其所,是形上道體展現在物體中的本性。萬物各有天性,承天性而發展自我,所以萬物不同。但天性又上承自道體,因為這個本源,使人我可以相通,天人可以合一,物我可以和諧,道可以使萬物通而為一。
而想要令人能夠明白道,就必須明白道的規律,如上文曾提及的“反者道之動”。老子認為一切現象都是在相反對立的狀態下形成的。例如《道德經》第二章云: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而人間的存在價值也是相對形成的: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老子認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對立面,同時因著它的對立面而形成。並認為“相反相成”的作用是推動事物變化發展的力量。進一步,老子說明相反對立的狀態是經常互相轉化的,第五十八章云: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在老子看來,禍患的事情,或許潛藏著幸福的因素;幸福的事情,也可能藏有禍患的因子。老子認為一切事物都在對立的情狀中反覆轉變,這種轉化過程是無窮的,因此觀察事物不僅要觀看它的正面,也應該注視它的反面,兩方面都能兼顧到,才能算是對於一項事物作了全盤的瞭解。29
這就如同斯賓諾莎所說的想要達致自由,就必須擁有對神的知識,即對自然必然性的了解。人未能夠了解老子的道,正是因為人類限於自身有限的觀點,所以未能全面認知事實,不能明白事物正反兩面的對立反覆關係,就對正面的事物有所追求,昧於無明,人才會貪婪慾望。斯賓諾莎和老子都希望對自然規律有本質的認識,以使人自身不被外物控制,但斯賓諾莎與老子對自然的實際觀察有所不同。相較老子察覺到道的相反對立與循環關係,斯賓諾莎雖然在事物與神、自然及實體的邏輯上有十分紥實的論證,但他並沒有在自然的規律上有像老子一樣的發現,沒有提到經驗世界上的對立反覆,而是以一種普遍性原則看待生活。例如每人面對同樣情況,都會有着同樣的感悟,並不是自己特別不堪,其他人面對自己所面對的狀況時,都會有跟自己一樣的情緒。30斯賓諾莎提出的克制被動情緒的方法教導人適應生活上的痛苦,是一種實際的導人修心減欲的思考方法。雖然對於經驗世界中事物規律的方面斯賓諾莎的體悟尚未如老子的透徹,但兩者的學說都是希望讓人能夠降低自己的慾望,減少外在事物控制自己的情況,他們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如同老子的“法自然”,是完全出自個體的自主意識,而非外力的強迫就範。自由是個體自我控制後的成果,自我控制的愈好、愈無為寡欲,就愈能順“德”而生活。因而老子的自由,不是按人的想法肆意妄為,而是盡可能區別出“自然”、“人為造作”,去除人為造作的刻意行為,接受自然的結果,亦即無為。31斯賓諾莎的政治觀裏以類似無為的觀念為理想目標,拒絕殘害人民的暴政:
政府的目的絕不是把人從有理性的動物變成畜生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發展他們的心身,沒有拘束地運用他們的理智,既不表示憎恨、憤怒或欺騙,也不用嫉妒、不公正的眼加以監視。實在說來,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32
他與老子都希望人民在合理的管治下各得其所,使民歸於老子所言的“愚”,即歸於樸真的境界,才是人最幸福的自由。《道德經》第六十五章云: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老子的意思是統治者用智巧心機去管治國家,只會使人民多欲,則爭奪起而互相陷於危險。只有“愚”民,即令人民守其真順自然,知道“道”的法則,返歸於真樸,才能順從自然,達到真正的自由,33這與斯賓諾莎的觀念擁有共同思想。
從斯賓諾莎的“神、自然與實體”,與老子的“道”中,可以看出兩種思想中有着莫大的相似性。出生於西方十七世紀的學者斯賓諾莎,能夠超脫當時盛行的宗教價值觀,創成自己獨特的哲學;老子推斷是春秋時期陳國人,約生活於西元前 571 年至 471 年之間,面對春秋時期數國互相兼併侵略的混亂局面,深感“有為”統治下的人世之苦,悟出《道德經》的無為思想。34
即使斯賓諾莎與老子對於自然規律的理解稍有出入,但兩種學說的目的都是導人向善,擺脫外物影響,達致與道或神合一的德性。他們出生的時代相距不止千年,但對於世界的本質卻有高度相似的見解,對社會的混亂有同樣的憂愁。他們抱有改善社會的念想,希望人能靜心寡欲,在物質橫流、放縱慾望的世界中保持純樸的自我,尋求與神合一的知識,或是歸於道的真樸本性,只有這樣才是永恒的快樂與自由。這種思想放在現今社會也非常恰當,使人至善,教人專注自己,平復內心,有助人們修為自己,達到真正的自由。
專著
洪漢鼎:《斯賓諾莎哲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0-41、126-128、147、179、212-213、501-502、509-512、568、602-614。
陳鼓應:《老子註解及評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年),頁5-10、83、232-236、312-315。
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著,洪漢鼎譯:《斯賓諾莎書信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227。
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著,國立編譯館主譯、邱振訓譯:《倫理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124-125、141-142。
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著,温錫增譯:《神學政治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141-142。
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著,賀麟譯:《倫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頁33、97-98、139-140、226。
期刊論文
艾新強:〈淺談老子的生平與思想──國學研究系列之九〉,《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5期(2016年10月),頁74-80。
和建偉:〈斯賓諾莎哲學與莊子哲學的比較研究〉,《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6年12月),頁35-38。
曾瑞池:〈老子與柏林─自化與自由的對比〉,《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25期(2019年3月),頁115-145。
潘斌:〈老子的“道”與斯賓諾莎的“實體”〉,《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4期(2004年8月),頁14-17。
腳註
[1] 洪漢鼎:《斯賓諾莎哲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568。
[2] 和建偉:〈斯賓諾莎哲學與莊子哲學的比較研究〉,《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6年12月),頁35-38。
[3] 潘斌:〈老子的“道”與斯賓諾莎的“實體”〉,《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4期(2004年8月),頁14-17。
[4] 同註1,頁602-614。洪漢鼎先生學術成就甚多,是西方哲學權威人物。現任北京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山東大學中國詮釋學研究中心主任、中華全國西方哲學史學學會和現代外國哲學學會理事,以及國際斯賓諾莎學會(荷蘭、德國)理事。其著作《斯賓諾莎哲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曾獲北京市第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5] 同註1,頁20-41。
[6] 同註1,頁147。自然本是科學概念,指宇宙的無限性、多樣性以及現象事物之間的因果必然性。
[7] 同註1,頁179。
[8] 同註1,頁126。
[9] 同註1,頁127。
[10] 同註1,頁128。
[11] 陳鼓應:《老子註解及評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7年),頁83。
[12] 同註11,頁232-236。
[13] 同註11,頁5-6。
[14] 同註2,頁16。
[15] 同註1,頁147。
[16] 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著,國立編譯館主譯、邱振訓譯:《倫理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124。
[17] 同註1,頁212-213。
[18] 同註16,頁125。
[19] 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著,洪漢鼎譯:《斯賓諾莎書信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227。
[20] 同註16,頁141-142。
[21] 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著,賀麟譯:《倫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頁33。
[22] 同註21,頁97。
[23] 同註21,頁98。
[24] 同註21,頁139-140。《倫理學》中提出三種基本情感作為人類一切情感的原始情感,這就是快樂(laetitia)、痛苦(tristitia)和欲望(cupiditas)。欲望是一種對於自身力求保存的沖動的自覺。快樂指“一個人從較小的圓滿到較大的圓滿的過渡”,相反,痛苦則是指“一個人從較大的圓滿到較小的圓滿的過渡”圓滿指人的實在性,即指人保持自身存在的努力。較大或較小的圓滿指增加或促進人保持自己存在的努力或努力的情感,和減少或妨礙人保持自己存在的努力。
同註1,501-502。斯賓諾莎認為人類的所有其他情感都視作從這三個原始情感而出,或由這三個情感組合而成,例如敬愛、惋惜、貪婪、酗酒等。
[25] 同註1,頁502。
[26] 同註1,頁509-512。
一、以清楚明晰的正確觀念替代混淆的不正確觀念來克服被動的情感。
二、以對事物必然性的知識替代單純想象的知識來克服被動的情感。
三、以理智的秩序替代想象的秩序去整理或聯繫身體的情狀來克服被動的情感。
四、以對情感的多方面原因的思考替代對情感的單方面原因的思考來克服被動的情感。
五、以對自身德性的充分理解和對神的理智的愛來克服被動的情感。
[27] 同註21,頁226。
[28] 同註1,頁510。
[29] 同註11,頁7-10。
[30] 同註1,頁510。以理性克制被動情感的方法之二:以對事物必然性的知識替代單純想象的知識來克服被動的情感。
[31] 曾瑞池:〈老子與柏林──自化與自由的對比〉,《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25 期(2019年3月),頁127。
[32] 斯賓諾莎(Benedict de Spinoza)著,温錫增譯:《神學政治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272。
[33] 同註11,頁312-315。徐復觀說:“智多,即多欲;多欲則爭奪起而互相陷於危險。老子始終認為人民的所以壞,都是因為受了統治者的壞影響。人民的智多,也是受了統治者的壞影響。”
[34] 艾新強:〈淺談老子的生平與思想──國學研究系列之九〉,《廣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5期(2016年10月),頁74-75。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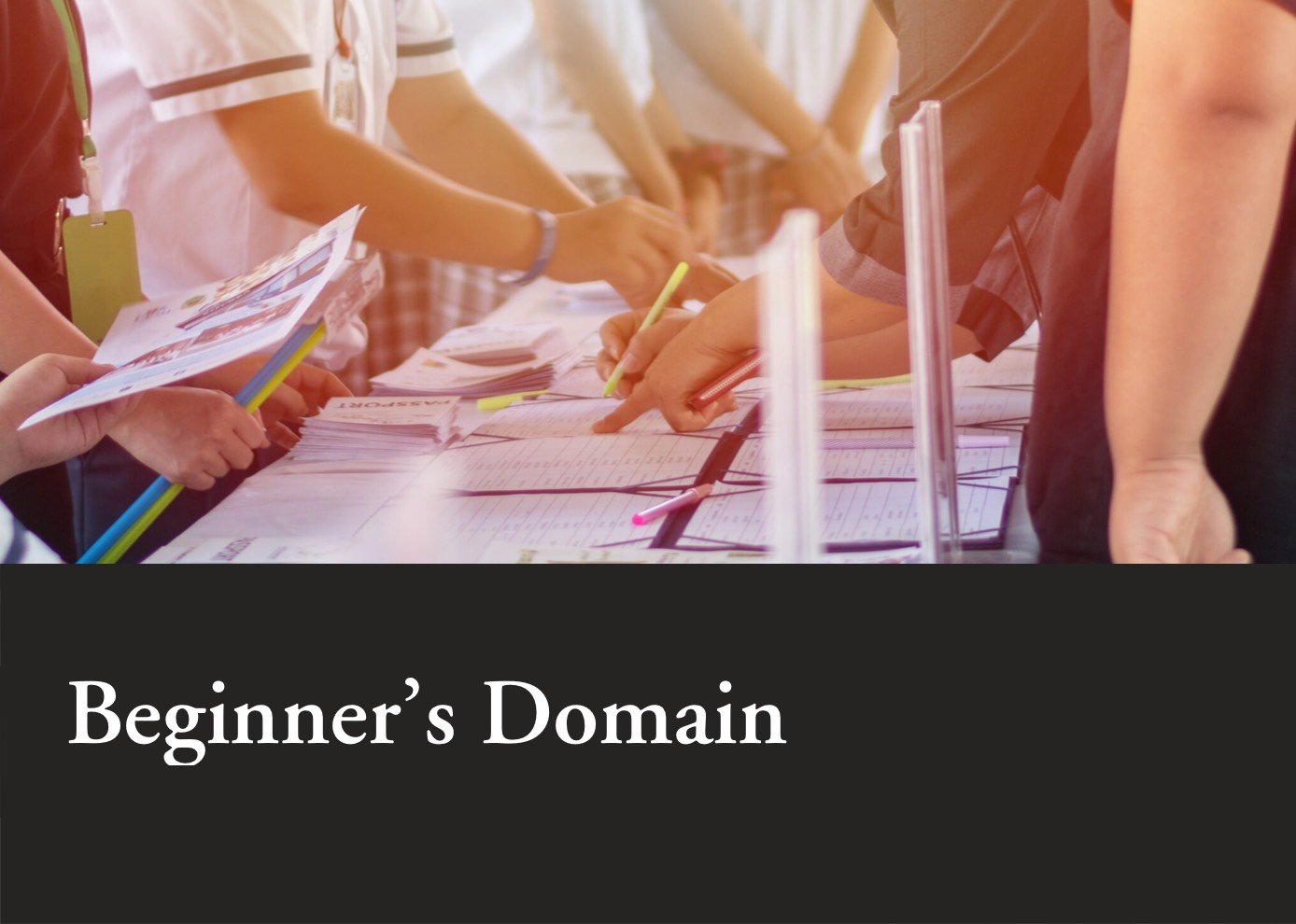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