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公主之楷模:
李遵勗妻獻穆大長公主(上)
北宋前期有兩家同出於潞州上黨的李氏外戚將門:其一是由太祖樞密副使李處耘起家,因其女成為太宗明德李皇後而成為外戚;另一家則是由太祖樞密使李崇矩起家,因其孫李遵勗尚太宗幼女獻穆大長公主而成為外戚。筆者於前者已撰有專著《攀龍附鳳:北宋潞州上黨李氏外戚將門研究》 中華書局詳論,後者則為本文之研究對象。
本文重點考論這一李氏外戚將門得以興起的兩個關鍵人物:李遵勗及其妻獻穆大長公主的生平事跡。本文所論述的獻穆大長公主,一直為宋人譽為公主的楷模。她在真宗至仁宗朝,特別是仁宗朝,雖居於宮外,但對宮闈的影響力,卻不可忽視。她的夫婿李遵勗,以功臣將家子而成為貴戚,因其尊禮佛陀而與朝臣楊億深相結納,而卷入以寇準、楊億為首的朝臣與真宗劉皇後的權力鬥爭。當寇準等權爭失敗,獻穆大長公主即憑尊貴的地位及其高明的政治手腕,既保護了夫婿一族,又保護了身處險境的侄兒仁宗。仁宗親政後,李遵勗夫妻深受仁宗尊禮,他們夫妻知禮守法,深受朝野敬重,而仁宗與公主姑侄親情深厚,愛屋及烏下,也對姑姑的親生兒子、他的親表弟李端懿、李端願兄弟另眼相看。公主以高壽過世後,仁宗對李家的恩寵不替,而李氏後人到英宗及神宗之世,仍是深受寵信的外戚。
李氏外戚將門在軍功方面不如另一李家顯赫,不過,值得註意的是,他們從李崇矩起,到李遵勗夫婦及其兒女,均是篤信佛教的大德。尤其是李遵勗更是為宋代沙門所尊崇的大檀越大護法。而他們李氏裔孫中,到南宋還出了一位民間家喻戶曉的佛門大師濟顛濟公(法名道濟,原名李修元)。
宋代的公主給人的印象一向較為模糊,不像好幾個曾垂簾聽政的太後性格形象鮮明地顯露於政治的前台。同為外戚,公主的夫族較後妃的父族在政治上的影響力為小。
宋史學者過去對宋代公主的研究多是宏觀、整體的論述,而主要論及宋代公主的制度。早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張邦煒教授在1993年於其專著《宋代皇親與政治》相關的章節。1遊彪教授2001年在其專著《宋代蔭補制度研究》亦有一章專論宋代公主的蔭補制度。2至於最近期的研究,則有華東師範大學兩篇碩士論文,分別是王珺於2008年提交的《宋代公主生活考略》及任傳寧於2011年提交的《略論宋代公主——兼與唐代公主比較研究》。3相較之下,單一、微觀及個案式的宋代公主研究就不多。就筆者所知,似乎僅有南宋初年假公主案的主角徽宗(1082—1135,1100—1125在位)女柔福帝姬(1110—1141)較受學者註意。4本文即試以個案研究的取向,選擇北宋最有代表性之獻穆大長公主(988—1051)做深入研究,特別細考其夫家潞州上黨李氏,在什麽樣的環境及機遇下,得以成為仁宗朝(1010—1063,1022—1063在位)以後一支在政治上頗有影響力的外戚將門,而她在其中扮演著什麽樣的角色。
在宋人的筆下,太宗(939—997,976—997在位)幼女、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幼妹獻穆大長公主(988—1051),被譽為整個宋代最有賢德的帝女公主。5而她下嫁的駙馬都尉李遵勗(988—1038),同樣是享有令名的貴戚,尤其是沙門所頌譽不已的大檀越、大護法。黃啟江教授在 1986 年對北宋著名沙門契嵩(1007—1072)的研究中便提到李遵勗一族,從其祖李崇矩(924—988)、其父李繼昌(948—1019)到其子李端懿(1013—1060)、李端願(?—1091)均篤信並護佑佛教的事實。6更值得註意的是,李遵勗夫妻篤信佛教,子孫相承下,李氏裔孫中,到南宋還出了一位民間家喻戶曉的佛門大師濟顛濟公(法名道濟,原名李修元,1150—1209)。7而她的夫家潞州上黨李氏,從真宗朝開始,就從功臣之家成為另一支外戚將門。8在真宗晚年,朝臣以元老重臣寇準(962—1063)為首,計劃由太子仁宗監國,以對抗野心勃勃的劉皇後(章獻劉太後,970—1033,1022—1033攝政)及以丁謂(966—1037)為首的附從者。李遵勗與他的平生至交翰林學士楊億(940—1020)是寇準的支持者。作為仁宗的至親,獻穆大長公主顯然也支持夫婿的立場。後來寇準等在權力鬥爭中失敗,李遵勗顯然靠著大長公主的特殊身份的保護,才不受牽連。劉太後攝政期間,大長公主夫婦一方面小心行事,以編纂佛書、弘揚佛教明其志;另一方面又接受劉太後的籠絡,與劉太後的姻家心腹樞密使錢惟演(977—1034)聯姻,降低劉太後的疑忌,從而暗裏明裏保護仁宗。
仁宗親政之後,大長公主是仁宗少數僅存的父系至親,她對親侄繼續悉心關顧。幼失怙持,欠缺母愛的仁宗,感情上對這唯一在世的姑姑(按:廣東人稱作姑姐)就由衷敬愛。而愛屋及烏,仁宗對姑姑的三個兒子、他的親表弟李端懿、李端願和李端慤(?—1098)就大加拔擢,尤其是李端懿,自小便是仁宗在宮中一起讀書玩樂、情同兄弟的友伴,也最受寵信。而大長公主的長女延安郡主(1010—1052)既與仁宗同齡,另自幼已隨母親出入宮禁,深受真宗寵愛,與仁宗也有特別的情分。仁宗兄姊均早夭,又沒有弟妹,與他同齡的從兄弟和表兄弟,稍為彌補了他這方面情感的寂寞。據現存史料所載,仁宗的從兄弟中,只有他的從兄、仁宗四叔陳王元份(969—1005)之第三子允讓(995—1059)是他的童年玩伴。真宗以允讓與仁宗年歲相近(他比仁宗年長五歲)而聰悟可親,就將他召入禁中與仁宗一起早晚學習及嬉戲,據說允讓“無一不中節”。等到仁宗成年出,才用《雲韶樂》導送他返回陳王元份邸。因為這一特別情分,仁宗後來對他的從兄恩寵有加。除了允讓外,仁宗八叔荊王元儼(985—1044)的幼子允初(1028—1064)亦曾養禁中,他年紀稍長後,劉太後本來想留他在宮中伴仁宗讀書,但因宰相呂夷簡(979—1044)的反對而遣返荊王府邸。他與仁宗似乎並沒有建立多深的感情。9是故仁宗少年的玩伴,除了允讓外,似乎只有李端懿姐弟等表弟妹。因是之故,潞州上黨李氏一門成為仁宗朝最受寵信的外戚之一。李端懿、李端願、李端慤兄弟及李端願子李評(1027—1078)等,後來繼續受到出於允讓一房的英宗(1032—1067,1063—1067 在位)及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的重用及寵信,潞州上黨李氏將門是北宋中後期很有政治影響力的外戚世家。
汪聖鐸先生曾在他所撰的《宋真宗》專著中,以兩頁多的篇幅描述真宗的“被人稱道的小妹”的生平事跡,也略論及李遵勗的事功,並甚有卓識地指出宋室對駙馬的防範遠低於諸王,是故駙馬如李遵勗可以做地方官和帶兵,與外界接觸的機會較多,而較有作為。10因篇幅所限,本文擬先考論獻穆大長公主及李遵勗之事跡,特別是他們與真宗、章獻劉太後及仁宗的關系。至於他們兒孫的事跡,當會另文詳考。另外,本文主角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公主稱號,本文除了在前言和余論使用“獻穆大長公主”的稱號外,就依她的身份,在太宗一朝以公主稱之,在真宗朝稱之為長公主,而在仁宗朝稱之為大長公主。又本文以獻穆大長公主傳記的角度撰寫,故也會旁及她的親人,包括趙宋宗室及外戚的相關事跡,從而論證了公主一家在親貴中的地位及影響力。
附:獻穆大長公主歷年封號
太宗端拱元年(988)至至道三年(997)五月廿二日:萬壽公主
真宗至道三年五月廿三日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一月廿九日:萬壽長公主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一日至大中祥符四年(1011)七月初四:隨國長公主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初五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正月十八日:越國長公主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正月十九日至天禧二年(1018)八月廿四日:宿國長公主
真宗天禧二年八月廿五日至乾興元年(1022)三月初四:鄂國長公主
仁宗乾興元年三月初五至明道元年(1032)十一月十六日:冀國大長公主
仁宗明道元年十一月十七日至皇祐三年(1051)三月廿五日:魏國大長公主
仁宗皇祐三年三月廿六日至元符三年(1100)三月:齊國獻穆大長公主(追封)
徽宗元符三年三月至政和四年(1114)十二月:荊國獻穆大長公主(追封)
徽宗政和四年十二月:獻穆大長帝姬(追封)
據《宋史·公主傳》、《宋會要輯稿》及《皇宋十朝綱要》,太宗有女七人,依長幼,按她們最後的謚號,分別是滕國大長公主、徐國大長公主(?—990)、邠國大長公主(?—983)、揚國大長公主(?—1033)、雍國大長公主(?—1004)、衛國大長公主(987—1024),以及本文主角荊國大長公主(獻穆大長公主)。11不過,《續資治通鑒長編》的兩條記載,卻說獻穆大長公主是太宗的第八女。12據《宋大詔令集》所記,後來出家的衛國大長公主,被稱為真宗的“皇第七妹”,則她之下的獻穆大長公主就順理成章是“皇第八妹”。為何群書記太宗有七女,而最幼的獻穆大長公主卻被稱為太宗第八女?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太宗另有一女早夭,雖有排行卻沒有名號,於是失載於《宋史》等書。13獻穆大長公主薨於皇祐三年(1051),得年六十四,以此推知,她當生於太宗端拱元年(988)。據《長編》卷九十所記,她可能生於是年的十二月。14至於她的閨名為何,群書均沒有記載。她的生母方貴妃(?—1031 後),據《皇宋十朝綱要》所載,還誕育了比她年長三歲、太宗的第八子周王元儼。巧合的是,公主是太宗第八女,而她的同母兄元儼又是太宗的第八子,兄妹二人都是太宗的幺子息女。值得註意的是,他們兄妹在仁宗朝,不但是宗室中最尊貴、最得仁宗尊禮的至親,他們在章獻劉太後攝政期間,還暗中保護了沖幼的侄兒,制衡了後黨的勢力。15
公主和長兄楚王元佐(966—1027)均貌類父親,故深為太宗所鐘愛,可說是天之驕女。太宗給她賜號曰“萬壽”,顯然希望她福壽安康,後來她的確比其眾多皇姊都高壽。她自幼不好嬉戲,也不喜玩物,甚至不出閨房。太宗曾經從宮中的寶庫拿出各樣的珍寶,任諸女擇取,從而察看她們的志向,她卻什麽也不取。為此,太宗更對她另眼相看。16不過,誠如張邦煒所論,太宗對女兒的取態是讓其“貴而不驕”,“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既限制她們的權勢,又不許她們有驕奢的行為,而深深鑒戒唐朝諸帝縱容公主而致她們驕橫的弊端。17當然,太宗在世期間,公主尚年幼,談不上什麽權勢。而據南宋人筆記所載,太宗給她的俸料錢,不過是每月五貫,沒有特別的優待。18
值得一提的是,比公主大一歲的、她的七姊壽昌公主據載生不茹葷,在端拱初年隨太宗幸延聖寺時,在太宗懷抱中卻對佛許願將來舍身為尼。19
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初十,被太宗視為王儲、公主的二兄許王元僖(966—992)意外地中毒身亡。太宗悲痛不已,後來更因查究元僖的死因而揭出不利他的隱情,而大大挫傷了太宗的心。20兄長元僖的橫死,以及背後隱藏的帝位繼承之爭,年方五歲的公主自然無從知曉。她的生母方貴妃當時在宮中地位低微,相信不敢也不會對女兒說什麽。
太宗在多方考慮,並得到他信任的大臣寇準支持下,在至道元年(995)八月十八日冊立公主的三兄真宗為皇太子。21然而,以明德李皇後(960—1004)、內臣王繼恩(?—999)為首的宮中勢力,仍在暗中反對真宗。至道三年(997)三月廿九日,太宗崩,在首相呂端(935—1000)的一力扶持下,真宗才得以順利繼位。22萬壽公主雖才十歲,但早識人事,對父崩傷悼不已,據說每晨起來,就“號慕不能勝”。23太宗晚年尤其至道年間一幕又一幕的險惡宮廷鬥爭,對於尚在童稚的萬壽公主的心靈有什麽影響?觀乎她成年後處事小心謹慎,從不介入宮廷鬥爭,筆者認為她幼年的經歷對她應有相當影響。
真宗繼位後不久,在至道三年五月廿三日,公主和她的三位從姊太祖女秦國公主(?—1008)、晉國公主(?—1009)、齊國公主(?—999),以及她的三位親姊宣慈公主、賢懿公主及壽昌公主,都晉位為長公主。因她尚未出閣,未獲國封,故真宗仍賜以萬壽長公主的封號。24長公主的七姊壽昌長公主卻乞度削發出家為尼,真宗起初不允,說:“朕之諸妹皆厚賜湯邑,築外館以尚天姻,酬先帝之愛也。汝獨願出家,可乎?”不過壽昌長公主卻回答說:“此先帝之願也。”堅決求請,真宗只好答允。25從此事可看到真宗甚重親情,在位的二十六年中,對其同胞兄弟妹,以至從姊弟妹及其他宗室均極其友愛。長公主尤其得到兄長的鐘愛,在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真宗更為她擇得甚為登對的佳婿李遵勗。本節先考述長公主出閣前的事跡。
長公主從鹹平元年(998)開始,便經歷兄姊至親陸續離世的人間不幸。是年七月,她的從姊秦國長公主婿、親貴中最尊長的太祖長婿、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承衍(947—998)病逝。26十二月,她另一從姊、太祖許國長公主病重,真宗親往視疾。惟延至翌年(鹹平二年,999)四月十四日不治。27整個鹹平時期,真宗窮於應付遼和西夏的交侵,敗仗連年兼且失去了西邊重鎮靈州(今寧夏銀川靈武西南,一說在寧夏吳忠南金積鄉附近)。而鹹平三年(1000)初在四川發生的王均之亂,也大傷了宋室的元氣。真宗在忙於國事之余,倒也盡長兄之責任,當為太宗之喪守制三年期告終後,他就安排兩個幼妹宣慈長公主和賢懿長公主先後於鹹平五年 (1002)五月初三和鹹平六年(1003)二月十六日出嫁:前者出降左衛將軍、駙馬都尉柴宗慶 (982—1044),晉位魯國長公主;後者出降右衛將軍、駙馬都尉王貽貞(後避仁宗諱改王貽永,986—1056),晉位鄭國長公主。28長公主在鹹平六年正是二八年華,喜見兩位皇姊先後出閣,分享她們的喜悅之余,卻也目睹兄長喪子的悲痛:真宗所鐘愛之獨子信國公玄祐(995—1003)不幸在是年四月廿二日夭亡,得年才九歲。29長公主在是年除喪侄外,還失去從兄右羽林將軍德潤(965—1003)和五兄兗王元傑(972—1003)。前者卒於是年二月廿九日,後者逝於七月廿五日。教長公主感慨的是,她這三位親人均壽年不永。30而長公主的嫡母明德李太後(萬安太後)也在是年十一月病重。31對親人連遭不幸,長公主大概會百感交集。
真宗在翌年(1004)正月改元景德。是月初十,真宗將他寵愛的後宮劉氏晉為美人。另晉後宮楊氏為才人。前者就是後來權傾一時並在仁宗初年垂簾的章獻劉太後,後者就是劉氏在宮中最大的心腹、後來的章惠楊太後(984—1036)。32她們後來與長公主的關系一直不錯,可以理解的是,她們對真宗鐘愛的幼妹當然是不敢怠慢,甚至會刻意討好。
這年三月十五日,長公主嫡母明德李太後病逝。四月初三,五姊鄭國賢懿長公主亦病逝。六月十七日,她另一從兄右羽林將軍德欽(974—1004)亦病卒。連喪母姊,長公主當悲傷不已,而為嫡母守喪之故,長公主雖年已十七,出閣之期就得延遲。33
長公主自幼遵守法度,不貪圖財寶,可她的三姊魯國長公主夫婦就剛好相反,是年九月廿五日,魯國長公主上奏真宗,說她派人往華州(今陜西渭南華縣)購買木材,請求免除征稅。真宗向宰臣表示,太宗曾切戒戚裏不得於西邊買木材,正怕他們因緣販賣,破壞法制。這次魯國長公主提出請求,就姑且通融一次。真宗其後即召見柴宗慶,表示下不為例。34其實不待真宗明示,長公主也不會像乃姊夫婦那樣嗜物貪財。
閏九月廿二,真宗方才將明德李太後的靈駕移於安肅門外旌孝鄉沙台之攢宮,遼國大軍已在承天蕭太後(953—1009)及遼聖宗(971—1031,982—1031在位)的統領下大舉入寇。幸而一直是宋廷心腹大患的西夏主李繼遷(963—1004)早在這年的二月,被西涼府六谷部長潘羅支(?—1004)擊殺,宋廷就不會兩面受敵。在真宗、宰相畢士安(938—1005)、寇準及樞密使王繼英(946—1006)的謀劃下,真宗在十一月二十禦駕親征。明德李太後之兄、宿將李繼隆(950—1005)獲任為駕前東面排陣使,太祖駙馬石保吉任為駕前西面排陣使,扈駕出征。而真宗四弟雍王元份就獲委為東京留守。35宋遼雙方君主親統大軍對峙於澶州(今河南濮陽),雙方都沒法戰勝對方,最後在真宗心腹,較早前兵敗降遼的王繼忠(?—1023)的斡旋下,加上宋使曹利用(971—1029)的努力,宋遼在十二月初達成和議。是月初七,真宗命西京左藏庫使、獎州刺史李繼昌假左衛大將軍銜,持宋方誓書與遼使姚柬之往遼營報聘。李繼昌到遼營,遼方滿意宋方的條件,就對他的館設之禮加厚。稍後,遼遣其西上閤門使丁振奉遼的誓書隨李繼昌前來開封。值得註意的是,李繼昌是太祖開國功臣、樞密使李崇矩之子,而長公主後來的夫婿李遵勗就是李繼昌子。36真宗在是年十二月十五從澶州班師回朝,十八日,真宗禦駕抵開封外的陳橋,李繼昌剛好與丁振抵達,就入見於行在。李繼昌就他所見之遼國國情奏報真宗,稱遼人頗遵用漢儀,不過也多雜用其本國之俗。遼主雖欲變改也不易得。據後來與李遵勗成為至交的楊億在景德二年(1005)四月八日所記,李繼昌出使遼國回程經過家鄉潞州,就上言請求真宗許他在故居改建禪院以納沙門,稱“以上黨舊邦,卜居累世,有環堵之室,乃先人之廬。而自參表著於朝內,占名數於京邑,喬木猶在,高台未傾,願為仁祠,以施開士。增飾輪奐,肅奉焚修,庶以眾善之,因仰助無疆之算”。真宗嘉納,並敕賜名“承天禪院”。真宗在景德三年(1006)三月初三又派他以西上閤門使、獎州刺史為契丹國母生辰副使,再次出使遼國。真宗對他出使大概很滿意,後來挑選他的兒子尚主,也許有一定關系。順帶一提的是,據楊億所記,李家信奉佛教,始於李崇矩和李繼昌父子。後來李遵勗便克紹箕裘,成為北宋時期著名的佛教大檀越大護法。而楊億與李家父子早就有交情。37從景德二年到四年(1007),真宗君臣得以度過一段相對安泰的日子。不過,真宗的至親以及倚信的宰執大臣卻有不少人在這期間辭世。首先是在景德之役建下殊勳的外戚宿將李繼隆在澶淵之盟締訂後不久,便在景德二年二月初五病卒。38同年八月初四,真宗所友愛的四弟雍王元份卒,得年才三十七。真宗哭之甚哀,及見到宰相,又再三流涕。39是年十月初十,真宗所信任的首相畢士安病卒。40到景德三年(1006)二月十四,真宗倚重的首樞王繼英亦病亡。41到五月十八日,真宗從兄、樂平郡公德恭(962—1006)卒,卒年四十五。德恭被疾,真宗在往視疾,兩天後德恭卒。真宗哭之慟,廢朝三日,賜德恭保信軍節度使,追封申國公。42到景德四年正月初六,真宗另一從弟右監門衛大將軍德鈞(?—1007)亦病卒。43這年四月十五,宋廷再遇上大喪:真宗章穆郭皇後崩,得年才三十二。真宗以代寇準為相的王旦(957—1017)為大行皇後園陵使。宗室、公主、文武臣僚都舉哀守喪。六月廿一,詔葬郭皇後於太宗永熙陵西北。44對於兄、嫂至親多人享年不永,長公主在恭臨多場喪禮之余,對人生之無常有何感觸,史所不載。值得註意的是,因章穆郭皇後之逝,為真宗寵愛的劉美人有望晉位中宮。史稱郭皇後死後,真宗就欲立她為後,只是大臣多加反對,真宗一時未能如願。45猜想劉美人除了交好外廷大臣如樞密使王欽若(962—1025)等以支持她晉位外,對於真宗寵愛的幼妹萬壽長公主,當也會刻意巴結。事實上,真宗向重骨肉之情,他對他兩位從姊秦國長公主和晉國長公主便一直十分尊重,屢次接受她們的請求加恩。46聰明如劉美人不會不懂得討好真宗的姊妹,以博取她們的支持。
真宗在翌年(1008)改元大中祥符,從這年開始,真宗聽信王欽若及丁謂等人的鼓動,開始了自欺欺人而旨在粉飾太平的天書封禪的鬧劇。47對長公主而言,這年的上半年,她雖再遭喪親之痛:先是嫡母明德李太後之弟、份屬她的季舅之殿前都虞候李繼和在是年二月廿五病卒,然後是她的從姊秦國長公主在五月十四薨逝;48但是年十二月初一,她成就了終身大事:在兄長的安排下,出降太祖開國功臣、樞密使李崇矩(924—988)之孫兒李遵勗,並獲晉封為隋國長公主。她的乘龍快婿李遵勗與她同庚,成婚之年都為廿一歲。李遵勗初名李勗,字公武,真宗命增“遵”字,授右龍武將軍、駙馬都尉,並令他升行輩為李崇矩子。他後來獲賜謚“和文”,故宋人都稱他為“李和文都尉”。真宗為什麽選中李遵勗?據載太祖當年本來屬意李遵勗父李繼昌為其主婿,但李崇矩不願,而沒有成事。49據宋人筆記所載,太宗似乎也對李遵勗另眼相看,曾賜以名畫《沒骨圖》。50真宗選擇李遵勗為妹婿,相信帶有達成太祖及太宗心願的動機。當然李遵勗自身的條件也很好,他身為將家子,少學騎射,有一次馳馬於冰雪上,馬突然失足,將他摔於崖下。從人以為他必死,他卻慢慢爬上崖,並無受傷。到他長大後,又喜好文詞,並舉進士,算得上是文武兼修。大中祥符元年初,真宗召李遵勗對於偏殿後,在年底就將幼妹許配予他。相信李當時應對得體,得到真宗的歡心。51據李遵勗父李繼昌的傳記所載,李繼昌在大中祥符元年初進秩為東上 門使,不久以目疾求歸京師,入對而勞問再三。大概真宗就在此時征詢李繼昌的意向。李繼昌這次不像乃父當年拒絕太祖的好意,於是真宗召見李遵勗,當面查考他的人品容貌,而最後決定以愛妹下嫁。52
真宗為幼妹完婚後,才在同月十五給宰執大臣及諸王宗室加官晉爵。翌年(大中祥符二年,1009)正月十三日,真宗又特封輩分最長的從姊晉國長公主為大長公主,三妹魯國長公主為韓國長公主,七妹壽昌長公主為陳國長公主。53至於新婚的長公主夫婦就沒有獲進一步加封。而長公主的家翁李繼昌大概推恩得以改官右驍衛大將軍,依舊領郡。54
真宗對他的姊妹愛護有加之余,也秉承乃父的教導,不讓她們驕奢及使用逾度。他的七妹陳國長公主自幼茹素,自願剃度出家,真宗在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十四日就只以保和坊的光教院賜給她修行。唯真宗而只許將光教院稍加修飾,本來在光教院的尼眾,就以舊布庫加以安置。55
李遵勗這位新主婿一開始便知禮及謙謹。當長公主下嫁時,真宗賜第京師永寧裏,她所居之堂壁或瓦壁多為鸞鳳狀,李遵勗下令將之磨掉。長公主服飾有虬龍飾紋的,亦都盡數收藏。真宗知道後大為嘆賞,又稱他好學。長公主在知禮謙謹方面,也不讓其夫。按李遵勗尚主後,依制升行輩為李崇矩子。這樣,李遵勗與其父李繼昌就成為同輩“兄弟”。56長公主這時倒不用思量見親翁之禮,因李繼昌是時出任西邊鄜延路鈐轄,到翌年(大中祥符三年)七月,李長公主出嫁後,仍在每月的朔望及節辰入見兄長,敘家人的天倫。據《長編》所記,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十七日,長公主的肩輿至右掖門,與入朝之騎乘混雜而入。皇城司以為不妥,即上奏真宗。真宗於是下詔以後南宮北宅的公主、郡縣主入謁時,若朝班未退,就悉由玄武門出入。到朝班散去,則聽任從他門進出。57
李遵勗成婚不久,在是年六月卻得疾在告。真宗愛妹心切,派醫者看視他的病狀,回報病情教人擔憂。真宗大概為了沖喜,就援引三妹婿柴宗慶歷環衛官不久即授刺史之例,得到宰相王旦的同意,就在同月初七,特授李遵勗自左龍武將軍、駙馬都尉領澄州刺史。58
真宗除了善待長公主外,對其他姊妹也一視同仁。是年八月廿一,下制晉封長公主的七姊陳國長公主為吳國長公主,授出家號“報慈正覺大師”,賜紫衣並法名“清裕”,為她建寺於都城之西,賜額曰崇真資聖禪院,並命有司擇日備禮冊命。並命兩制學士送於寺,又令他們作詩相送,然後賜齋宴。吳國長公主入院有日,真宗仍召她誨諭以嘉言,又怕她日久忘記,就錄下筆記賜之。真宗曾向王旦說:“諸妹出降,朕但教以婦道恭順而已。吳國今自主院事,不得不曲之為防。”真宗大概有鑒柴宗慶的僮仆先前從外州市炭入京師,得以免稅後,卻在雜買務出售取利的前科,而擔憂吳國長公主手下會借公主權勢擾民,就特詔公主所掌的崇真資聖禪院,自今於雜買務購物,必須具明數目以聞朝廷,不許擾民。當時藩國近戚及掖庭嬪禦願出家者,包括真宗六弟鎮王元偓(密恭懿王)女萬年縣主(977—1018)、七弟楚王元偁(即曹恭惠王)女惠安縣主(971—1014)等三十余人,均隨吳國長公主出家於崇真院。59九月十七日,真宗又以吳國長公主出家受戒畢,又特恩普度天下僧尼、道士。令宮觀和寺院每十人度一人,不滿十人及各禮師者亦度一人。60
是年十一月廿九日,長公主的從姊晉國大長公主病重,真宗得報馬上到大長公主宅視疾,但真宗甫離開不久,大長公主即病逝。真宗馬上臨奠並哭之慟,並下詔輟朝五日,賜謚賢靖。61長公主的三位從姊、太祖的三位公主到此時均歿。
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十四日,後宮李氏(後來追尊為章懿李太後,987—1032)誕下後來與長公主姑侄情深的仁宗。62真宗自周王歿後再得子,自然喜不自勝;不過,太祖的長孫、真宗的從侄安定郡公惟吉(966—1010)卻在五月初八病逝。惟吉輩分雖是真宗從侄,其實比真宗還年長兩歲。他是宗室中之賢者。真宗與他感情篤厚,惟吉發病後,真宗一直用各種方法為他療治。他病重時,真宗曾八天內省視五次。他病卒後,真宗往視而哭之慟,翌日對宰相語及又泣下。是月十八日,真宗再臨惟吉宅奠祭,並為他廢朝五日,贈中書令,追封南陽郡王,謚康孝。63長公主是否和兄長一樣痛悼惟吉之喪,文獻無征,難於判斷;不過,兄長中年得子,長公主相信是欣喜不已的。何況她也初為人母,在二十三歲之年,在同年十一月誕下長女於京師永寧第。這位後來封延安郡主的小郡主,在彌月後與母親入見真宗。真宗剛得佳子半載,心情極好,見到幼妹的女兒後,就歡喜地說:“女,吾之所出也,且有奇法。異時非才賢不以逑匹。”既贈小外甥女縑帛以為賀禮,又賜幼妹園林詩一首。真宗愛惜幼妹之女,而公主也同樣愛護長兄的獨子,而仁宗與他這位同年出生的小表妹在七歲那年便序齒相見。仁宗自幼便與姑姑隨國長公主一家熟稔。64大中祥符四年(1011)正月廿三日,真宗從京師出發往河中府(今山西運城永濟西)祀汾陰。長公主的家翁李繼昌被任為京師新城巡檢鈐轄,改左神武大將軍權判右金吾街仗,留守京師。65李繼昌方被委以重任,並得以含飴弄孫,卻未想到寶貝兒子駙馬爺李遵勗竟然荒唐透頂,私通長公主的乳母。在真宗及外人眼中,李遵勗本來頗有賢名。這趟大概因少年血氣,受不了女色誘惑,才犯了大錯。一直深受父兄寵愛、備受人尊敬的長公主這次面臨重大的考驗:她要維護夫婿而護短?還是向兄長和盤托出真相?當真宗在四月初一從河中府祀汾陰畢返抵京師時,李遵勗起初請入對奏告此事時,還想諉過於人。碰上真宗以祀汾陰大赦天下,他又改變主意,不願承認過失。但事情怎瞞得過真宗?李繼昌正管金吾,他怎敢包庇兒子隱瞞真相?當真宗派人(也許正是李繼昌本人)詰問李遵勗時,李仍砌詞狡辯,這就惹得真宗大怒。然而,長公主卻一直維護夫婿,沒向兄長言及夫婿一絲過失。真宗眼見幼妹一直顧全夫婿體面,就不忍傷害她的感情而深究李的罪責。不過輔臣卻不肯放過李遵勗,上奏請正刑典。真宗於是在四月初九,將李遵勗自左龍武將軍、澄州刺史責降為均州團練副使。李遵勗大概沒有面目留在京師,稍後以疾請求徙居蔡州(今河南駐馬店汝南縣)養病。真宗接受他的請求。66
比起她的三姊韓國長公主之“性妬”,不容夫婿柴宗慶納妾,以致他最後無子。67長公主不但包容夫婿過失,在兄長面前一力維護夫婿,還容許夫婿納妾生子。68司馬光在五十一年後便大大稱頌她“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重婦道,愛重其夫,無妬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69在男性為中心的傳統中國社會,長公主以金枝玉葉千金之軀,能這樣不妒忌、寬宏大量地包容夫婿的失德,確是值得司馬光這些迂腐的儒家士大夫讚美不已的。李遵勗能有這位如此識大體的妻子,他李氏外戚將門才能有貴顯的機會。
真宗才貶責了不肖的妹夫,他那最有賢名的駙馬妹婿、山南東道節度使知徐州(今江蘇徐州)吳元扆(962—1011)卻在是年六月初一逝於徐州任上。真宗甚悼惜之,贈吳中書令,謚中書令,吳氏子弟進秩者五人。真宗又以吳得疾後,本州不即上奏,詔劾其官屬。70
長公主在七月初五從隋國長公主晉封為越國長公主。她的兩位姊姊也同時獲得改封:韓國長公主晉封為衛國長公主,已出家的吳國長公主為楚國長公主。71
這年十一月,長公主的女兒滿周歲,母女二人入宮覲見真宗,真宗召至內省,親自視看她除發。真宗歡喜之余,厚贈他的小外甥女珍寶戲物百余種。愛屋及烏,真宗在翌年(大中祥符五年,1012)初,就寬恕了李遵勗,將他起為太子左衛率府副率,召還京師,稍後覆為左龍武軍將軍。72
當長公主一家在大中祥符五年初團聚時,真宗在是年五月十一,將他至為寵愛的劉修儀晉位為劉德妃,真宗並且隆重其事,下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這年十一月初五,真宗四弟元份次子右屯衛將軍允中(1012)卒。不過愛侄之卒也不妨礙真宗立後。十二月廿四日,劉德妃更正位中宮,成為劉皇後。73劉皇後當然知道真宗厚愛幼妹,她收養仁宗為己子,而仁宗又與長公主母女親近,以長公主之通曉人情,她們姑嫂關系應該不錯。相較之下,她的姊姊衛國長公主和夫婿柴宗慶卻不通人情,貪婪愛貨,在是年六月先後受到真宗的申誡。74
真宗冊立劉皇後翌年(大中祥符六年,1013)正月十九日,真宗再將三位皇妹改封:長公主自越國長公主進封宿國長公主,衛國長公主進封徐國長公主,楚國長公主報慈正覺大師進封邠國長公主,而真宗又以婕妤楊氏(章惠楊太後,984—1036)為婉儀,貴人戴氏為修儀,美人曹氏(?—1026)為婕妤。75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長公主的同母兄榮王元儼,這時行事卻率性而為,遠不及妹妹的知曉人情。正月廿九日,他在侍宴宮中時卻頗多言,他又請將原屬姊夫石保吉的伶人、新隸教坊者作戲。到他赴北園禦筵時,有伶人稍不合他意,他不但叱罵,還要捶撻。他的宮僚都不敢勸諫。見到真宗,他又請此一伶人演戲。真宗對他這樣任性的行為,就大為不悅,並對宰臣言及元儼的失禮。76
長公主在這年中誕下長子李端懿,長公主這年已二十六歲,誕下第一個兒子,自然喜悅不已。李端懿比仁宗小三歲,從小便是仁宗的玩伴,表兄弟情分匪淺。據他的墓志銘所記,“為兒時,上(仁宗)在東宮,真宗命公侍研席。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77是年十一月,長公主向真宗乞請在諸州河市物免稅,真宗有鑒於新晉封徐國長公主和邠國長公主的兩位皇妹貪圖小利的前科,怕幼妹有違條例,故於是月廿九,下詔申明長公主宅諸州河所置的舟船,只許免卻各種差徭。至於關市征算的路稅就如舊,不許豁免。78在這方面,長公主是循規守法,從來沒有讓兄長煩惱,宜乎她得到兄長的寵愛。
大中祥符七年(1014)三月廿二,仁宗已滿五歲。因王旦等之請求,真宗封仁宗為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月給俸錢二百千。劉皇後早就以他為己子,而由楊婉儀保視之。仁宗這時已呼劉後為大孃孃,楊婉儀為小孃孃,卻不知生母是宮人李氏。79宮內宮外的人識得利害,就沒有告訴仁宗真相。作為至親的長公主,就算知道真相,也不會透露。
是月底,長公主的七兄舒王元偁病重,真宗憂慮之余,罷遊金明池。然元偁到四月廿一終於不治,得年才三十四。真宗臨哭,翌日對輔臣發言出涕,悲不自勝。真宗追封他曹王,謚恭惠,廢朝五日。又責降醫官視疾無狀。元偁之死,對真宗兄妹無疑是另一次沈重打擊。值得一提的是,元偁與長公主夫婦都篤信佛教。80
六月十八日,大概因劉皇後的推許,真宗晉封楊婉儀為淑妃。史稱她“通敏有智思,周旋奉順後無所忤,後親愛之,故妃雖貴幸,終不以為己間”,楊淑妃成為劉皇後宮中頭號心腹。81為劉、楊兩後妃所撫養的仁宗,本來還有一位親姊姊妙元公主(?—1033),但她卻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十四和她的母親杜賢妃(?—1046)一樣,自願入道。82連唯一親姊也入道,仁宗的少年玩伴,就只剩下姑姑長公主的兒女和幾位宗室少年,說來也是很可憐的。
真宗在是年二月十五日,晉封健在的同母長兄楚王元佐為天策上將軍、興元牧,又特賜他劍履上殿和詔書不名。83真宗優禮兄長之余,又在三月初五幸六弟彭城郡王元偓宮視疾,十八日又大宴宗室,會射於禁苑中。但宗室中,先有真宗從兄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德彜(967—1015)在四月十九病卒,而到六月廿七,又有真宗從侄昌州團練使惟忠(?—1015)逝世。84不過,最令真宗沮喪的事,就是他的八弟榮王元儼,宮闈不慎,在四月廿三日,正當真宗為德彜制服發哀的同日,元儼所居的宮禁卻失火,從三鼓一直至翌日亭午才被救熄,波及了內藏左藏庫、朝元門、崇文院和秘閣,帶來極大的損失。真宗哀嘆:“祖宗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真宗在五月初三,查明是元儼的侍婢韓氏因盜賣金器,怕事發而縱火,就將不肖弟元儼之武信軍節度使官罷去,並降封端王,又令他出居石保吉的故宅。85
長公主在八兄元儼宮禁失火的事可有為他說情,文獻無征。不過這場大火讓真宗關註起諸妹的宅第安全。八月初五,為了妥善管理諸長公主宅事務,真宗特命入內副都知張景宗(?—1022後)同管勾長公主宅及郡縣主諸院公事。86
大中祥符九年(1016)二月十九日,仁宗接近七歲時,真宗命築堂於元符觀南,作為仁宗就學之所,賜名曰“資善”,又命他寵信的內臣入內押班周懷政(979—1020)為都監,入內供奉官楊懷玉(?—1022後)為壽春郡王伴讀,真宗又面誡兒子不得於堂中戲笑及陳玩弄之具。兩天後,又給仁宗的生母崇陽縣君李氏才人的封號。另外,真宗又委朝臣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964—1049)為壽春郡王友,輔導仁宗學習。87三月初四,真宗又召宗室觀書於玉宸殿。翌日(初五),又召宗室宴射苑中。真宗問諸王經史,都能好好回答,教真宗龍顏大悅。88已步入晚年的真宗,家人天倫之樂,是他所珍惜的。89
外戚中素來麻煩多多的武勝軍留後柴宗慶,在這年四月十二日又因從幸瓊林宴,給![]() 門糾彈他違制而被罰金二十斤。90相較之下,李遵勗自從在四年前召還京師後,就循規蹈矩,沒有再有犯禁。值得註意的是,他從大文豪翰林學士楊億作詩,更追隨他學佛,延高僧,開法會,為“禪悅深交”。史稱他“喜讀書,兼達釋氏性理之臬”。長公主夫唱婦隨,也去本宅東莊聽高僧講法。據王鞏(1048—1117)所記,有一次李遵勗召從官宴飲,大概一時忘形,還召來軍妓作樂至夜半。台官劾論他,楊億知道此事,就告訴宰相王旦,王旦就寫了一首小詩送給李遵勗,說以不能預會為恨。第二天真宗出台官彈劾李的章疏以問王旦。王旦表示知情,並以巧言為李辯解。李遵勗這次逃過罪責,正得力於楊億和王旦的幫忙。而據王鞏父王素(1007—1073)所記,其父王旦與李遵勗本有師友之誼。楊億曾對王旦稱許李遵勗,說“李侯為貴戚,好學樂善,賢侯也”。王旦於是作詩,寫於紅箋上送給李遵勗。據說李收到王旦的詩箋大喜,具啟事謝於門下。91
門糾彈他違制而被罰金二十斤。90相較之下,李遵勗自從在四年前召還京師後,就循規蹈矩,沒有再有犯禁。值得註意的是,他從大文豪翰林學士楊億作詩,更追隨他學佛,延高僧,開法會,為“禪悅深交”。史稱他“喜讀書,兼達釋氏性理之臬”。長公主夫唱婦隨,也去本宅東莊聽高僧講法。據王鞏(1048—1117)所記,有一次李遵勗召從官宴飲,大概一時忘形,還召來軍妓作樂至夜半。台官劾論他,楊億知道此事,就告訴宰相王旦,王旦就寫了一首小詩送給李遵勗,說以不能預會為恨。第二天真宗出台官彈劾李的章疏以問王旦。王旦表示知情,並以巧言為李辯解。李遵勗這次逃過罪責,正得力於楊億和王旦的幫忙。而據王鞏父王素(1007—1073)所記,其父王旦與李遵勗本有師友之誼。楊億曾對王旦稱許李遵勗,說“李侯為貴戚,好學樂善,賢侯也”。王旦於是作詩,寫於紅箋上送給李遵勗。據說李收到王旦的詩箋大喜,具啟事謝於門下。91
李遵勗這時的官位,據他的本傳所載,大概得益於數年來真宗封禪及其他大典的推恩,他已覆職為左龍武軍將軍,領宏州團練使。92
這年的下半年,真宗是憂喜參半。先是五月十一日, 他的從侄資州團練使惟憲(979—1016)卒,得年僅三十八。真宗對這位才貌均不俗之宗室優贈安德軍節度使兼侍中,追封英國公。93然後在從六月開始,蝗災在多處州郡包括京畿、京東西、河北、江淮南至河東諸路爆發,甚至在京師頭上掠過而為真宗所親見,加上久旱不雨,以天書封禪粉飾的太平盛世給戳穿。94到九月十三,才有降雨,一直憂形於色的真宗才稍得寬懷。95另外,曹瑋(973—1030)也及時給真宗捷報,九月宋軍在西邊擊敗蕃部宗哥。96長公主在這年十一月,也適時地給兄長帶來難得的天倫之樂。她的長女延安郡主滿七歲,獲真宗恩賜冠帔,長公主就帶同女兒入謝,並讓女兒與她的表兄仁宗相見。長公主知禮,命女兒向侄兒下拜。但真宗要二人先序齒定長幼,才讓外甥女向兒子下拜,真宗要眾人明白,外甥女向兒子下拜,是序兄妹長幼而非君臣尊卑。以後凡有宴會,常讓小外甥女侍坐旁,真宗對她的無比恩寵,非其他宗王及公主女所可比擬。這當然是真宗深愛幼妹所致。97
真宗在翌年(1017)改元天禧,正月舉行一連串祀天、南郊大典,李遵勗等駙馬先在是月初七與宰執及諸司三品、宗室、正任刺史及知雜禦史以上官員陪同真宗致齋。十四日,李遵勗及王貽貞二駙馬,又與皇侄守節(?—1039)以上之宗室,奉詔一同升殿陪位預聽宣讀天書。是月廿六,又命宰相王旦往兗州(今山東兗州)太極觀奉上冊寶。98二月初九,真宗加恩內外官員,他尚健在的兄弟楚王元佐、相王元偓和彭王元儼分別加官外,他的獨生子仁宗也加兼中書令。99李繼昌和李遵勗大概也在這時加官一級,分別晉升為獎州刺史和康州團練使。按李遵勗本官在乃父之上,他請班在父下,真宗自然同意,大概嘉他知禮。100
這年七月廿一,深受真宗信任的首任王旦多次以疾辭任,終於得到真宗的允準。本來次相向敏中(949—1020)也請罷職,但真宗不允。就在王、向二人相繼求退之時,長公主的從姊夫、太祖駙馬中碩果僅存的保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魏鹹信,在同月廿八日在京師病逝。真宗即往他這位最尊長的從姊夫之第臨哭,贈中書令,又錄其孫侄,遷官者七人。101
魏鹹信死後,主婿中最尊長的太宗駙馬右監門衛大將軍、獎州團練使王貽貞,過去一再請求補外郡試管民政,終於在十月十九日,得到真宗的同意,命知單州(今山東菏澤單縣東南)。真宗在他赴任前,召見他,誡他治郡務以“和眾靜治”為先。102至於長公主的夫婿李遵勗,這時尚未獲真宗的允許出補外郡。
這年十二月,長公主在她誕辰日,邀請她在京擔任權判右金吾街仗司的家翁李繼昌到其宅慶祝,她並以媳婦之禮謁拜獻壽。真宗知道後,就暗中贈以襲衣、金帶、器幣、內殿珍果美饌助其為禮。第二天,長公主入對謝恩,真宗就詢問李繼昌的飲食狀況,長公主奏稱家翁尚健康強壯。真宗因愛妹的推薦,嘉嘆之余,在同月廿四,就擢升年已七十的李繼昌自獎州刺史為連州刺史,委他出知西邊的涇州(今甘肅平涼涇川縣)。李繼昌到耆年仍得此任命,興奮之余,在離京赴任前曾對人說:“頃歲再命延安,不克奉詔,常以為恨,今獲死塞下,是吾願也。”103李繼昌在暮年能遂其宿願,自然是他的賢媳長公主的功勞。
長公主不只孝敬家翁,也持家有道,對人又寬厚。李遵勗非常好客,他的賓客都是一時的賢士,每逢李府宴客,長公主都親自視理宴會之飲食,務必賓客盡歡。她處事明察,曾有賊盜偷入駙馬府,真宗得報,即命有司拘捕嫌疑者。長公主懷疑所拘的並非真盜,就請真宗釋放被系捕的人,而她自己就用自己的錢募人偵查,果然獲得真盜。盜賊本來依法當死,她又請真宗免其一死。她的德行深為人所讚美。104
一踏入天禧二年(1018),真宗看來心情很好,他在正月初一便幸元符觀,然後宴宗室於仁宗讀書的資善堂。六天後(初六),臣下又奏報芝草生於真遊殿和劉皇後所居的崇徽殿,
真宗見此祥瑞,就作詩歌示宰相王欽若等。十一日後(十七),真宗又再幸元符觀和資善堂,宴從臣和仁宗之壽春郡王府官屬,真宗又出示群臣他所作的賜壽春郡王《恤黎民》等歌、《元符觀資善堂》等記頌,另外又向王欽若等出示仁宗所作的詩集和筆翰。105王欽若迎合真宗的心意,大大吹噓仁宗的德行,請真宗加封仁宗貴爵。真宗於是在二月初三,再授仁宗為建康軍節度使封升王並加太保。翌日(初四),再以仁宗的宮僚壽春郡王友張士遜、崔遵度(954—1020)並為升王府諮議參軍,左正言晏殊(991—1055)為記室參軍。就在真宗為兒子配置宮僚高高興興的日子,唯一掃興的是,就在初四晚上宗室蔡州團練使德雍宅起火,延焚數百間。真宗命禦史張廓查究,查出是德雍子供奉官承亮的屋舍起火,而起火原因是承亮的婢女陳氏留下火種所致。真宗大概心情好,對承亮及其婢只輕責。德雍奉表待罪,真宗也詔釋不問。106
德雍兒子婢引致這場大火,卻令長公主的六兄徐王元偓當時受驚而中風,甚至不能言語,真宗憂心不已,先後四次親臨省視。然到五月初三,元偓終於不治,得年才四十二。真宗臨奠慟哭,廢朝五日,贈元偓太師尚書令,追封鄧王,謚曰恭懿。他下葬日,真宗又親制挽詞。稍後,又取他的生平歌詩、文記編為六卷及墨跡三卷,並親制二序,藏之秘閣。107長公主又喪一兄長,除了真宗外,她的親兄尚在的,只有長兄楚王元佐和八兄彭王元儼。
真宗在六月廿八日,加恩劉皇後已歿的父親劉通和母親龐氏。詔贈劉通太師尚書令,謚武懿;龐氏贈徐國太夫人。並令張士遜具鹵簿鼓吹護葬二人於祥符縣的鄧公原。真宗親制祭文置靈坐之右,而劉皇後親臨祭奠。108長公主依制當會出席皇嫂父母之葬禮,並盡禮致哀。
真宗安撫了劉皇後後,就應群臣之請,在八月十五日正式冊立仁宗為皇太子,並賜名趙禎。因冊立太子,大赦天下,宗室及文武百官均加恩。宗室中最尊的楚王元佐在廿五日兼加興元牧,彭王元儼加太傅,為永清、橫海節度使,進封通王。而三位健在的長公主也加封:徐國長公主進封福國長公主,邠國長公主進封建國,長公主就而自宿國長公主進封鄂國長公主。九月初二,真宗又詔皇太子月給錢二千貫。同月初六,為表示太子需學謙遜,就不許宗室德雍所請向太子下拜的請求。109
真宗為了栽培仁宗,可說是費盡心機。除了安排好的師傅和方正的宮僚外,也給仁宗安排年齡接近的玩伴。長公主的長子李端懿,就是真宗選中的太子玩伴。據歐陽修所記,就在仁宗正位東宮時,真宗就命李端懿侍候仁宗於研席,所謂“陪太子讀書”。因李遵勗及長公主管教甚嚴,並聘名師教導,李端懿“於其家法習見安行,不待教告”,歐陽修吹噓他“少篤學問,長而孝友”,又記他興趣廣泛,知識豐富,“喜為詩,工書畫,至於陰陽、醫術、星經、地理無所不通”。從另一角度去看,仁宗這個小表弟兼玩伴,可以說自幼就是一個機靈討人喜歡又多點子的聰明人,難怪仁宗喜歡他,“上尤親愛,嘗解方玉帶賜之”。大概李端懿大得真宗歡心,他才滿七歲,即天禧三年(1019),就獲真宗授如京副使。110他的二弟李端願,相信稍後也有陪伴兄長入宮與仁宗一起讀書玩樂。111
天禧三年初,長公主的家翁李繼昌在涇州忽然中風,李遵勗聞訊,不待真宗批準,就離京探視。真宗不但沒有怪責他,還派人令他馳驛前往,並且立刻差使者及禦醫前去診治,又取寶丹封賜之,並許李繼昌坐肩輿還京師醫治。但使者未抵涇州,李繼昌已於三月初四卒於涇州。真宗即命中使護其喪歸。李遵勗扶父靈返京後,上表自劾擅離京師之罪。但真宗沒有降罪,還派輔臣撫慰他。又恩恤李家,錄李繼昌其他兒子官職。112真宗如此恩待李家,自然是看在愛妹份上。對於家翁逝世,長公主自然克盡媳婦之禮。
在李遵勗夫婦守制期間,宋廷已醞釀大變。真宗自覺病情漸重時,先在四月十二日召判永興軍府(長安,今陜西西安)的元老重臣寇準回京,準備接掌相位,輔助太子。而劉皇後也趁真宗有病,開始安插她的人馬於禁軍中。五月初三,真宗聽劉皇後的推薦,任命她認為兄長的洛苑使勤州刺史劉美(962—1021),自同勾當皇城司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而劉皇後另一心腹泰州防禦使夏守恩(?—1037)就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擢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控制禁軍的上四軍。二人在七月十七再分別遷馬軍都虞候和殿前都虞候。一月後,二人再分別權領馬軍司和權領殿前和步軍司。劉皇後將禁軍三衙的指揮權牢牢地控制於手中。113
王欽若在六月初九失寵罷相。四天後(十三),真宗任命回朝的寇準和丁謂分別為次相及參知政事。丁謂本來想巴結寇準,但寇準一回朝便公開奚落丁謂。真宗新任命以輔助仁宗的一對宰執一開始便心存芥蒂,劉皇後在旁已虎視眈眈,宋廷從此多事。114是月廿九日,真宗的從妹、秦王廷美長女長清郡主(?—1019)卒,真宗傷痛之余,特臨奠廢朝,先天節群臣上壽,真宗也下詔不舉樂。真宗又錄郡主二子官,並遷其秩。於真宗和長公主而言,郡主之喪自然又是叫人傷感之事;但比起山雨欲來的政局,這事又似是無足輕重了。115
十一月十九日,真宗舉行南郊大典,並大赦天下。十二月初九,真宗給宰執輔臣及百官加官。長公主的八兄元儼進封涇王,而她的長子李端懿大概也在這時獲授如京副使。值得註意的人事變動是,與寇準不睦的丁謂從參政升授樞密使,寇準另一對頭曹利用也授樞密使。而兩天後,真宗又委周起(971—1028)和任中正(961—1026)並為樞密副使。到天禧四年(1020)正月十三,真宗又召西邊有功的名將曹瑋回朝,授簽署樞密院事。新任的三員樞臣中,周起與曹瑋與寇準親近,任中正與丁謂友好。丁謂與曹利用為了抗衡寇準,不久便投靠劉皇後。116
天禧四年正月十七,真宗仍如常往元符觀及資善堂查看仁宗的學業。但到二月初一,不到半月,真宗卻“不豫”,只能視事於長春殿。偏偏在差不多兩個月後,在三月廿八日,雖久病卻在政治上仍舉足輕重的首相向敏中病逝。117四月初九,與李遵勗亦師亦友的楊億,因翰林學士承旨晁迥(951—1034)求解職,獲真宗覆任為翰林學士。118他一向與王旦和寇準親近,覆入翰苑,掌起草詔令之權,卻不免卷入往後的政爭。六月十六日,真宗聽了劉皇後的姻親兼心腹翰林學士錢惟演一面之詞,糊裏糊塗地把寇準罷免。本來真宗答應寇準以仁宗監國,而由寇準等為輔政,並逐走丁謂等。寇準已找楊億代擬表,請太子監國。偏偏寇準自己在酒後泄漏此大事,讓丁謂及曹利用知道。二人的靠山正是劉皇後,在劉皇後的授意下,錢惟演在真宗神志不清下對寇準發動攻擊,說他專權任事。真宗忘記以太子監國,是他答應寇準的,結果依從錢的建議,罷了寇準相位。不過,真宗又授寇準太子太傅封萊國公,仍留在朝中,寵信未衰。七月十二日,真宗便又召寇準與宗室、近臣等觀禁苑的嘉谷,又宴於玉宸殿。119
同月十七日,真宗聽了錢惟演的意見(其實是劉皇後的意見)後,以一貫的平衡術,擢任仁宗所喜的參政李迪為相,接替寇準之缺。但兩天後,又接受錢惟演的建議,將丁謂自樞密使擢升為首相,而馮拯(958—1023)和曹利用留任樞密使。真宗卻故意留下寇準,許他入對議事。丁謂等深受威脅下,便授意劉皇後的心腹客省使楊崇勳(976—1045)在是月廿五首告與寇準親近、又是東宮都監的內臣周懷政謀反。在曹利用控制下,雖然由曹瑋主持審訊,最後周懷政被定死罪,被殺。並且丁謂等以周懷政謀叛之事牽連寇準,同月廿八,寇準被降授太常卿知相州(今河南安陽),八月初五再貶知安州(今湖北孝感安陸)。廿三日,再以屬下朱能之叛貶道州(今湖南永州道縣)司馬。與寇準親近的朝臣盡被貶責。楊億因丁謂愛才,方幸免於貶。據宋人所記,有人(劉皇後最大嫌疑)想借周懷政謀叛事牽連仁宗,當時真宗也“意惑之”。幸得李迪善言化解,真宗才沒有做出廢黜仁宗的傻事來。這次為劉皇後除去寇準立下大功的錢惟演,在八月初六,就獲擢為樞密副使。真宗同日又覆任王曾為參知政事,而任中正也升授參政。120
在這場翻天覆地的政變中,李遵勗和長公主是否完全置身事外?據《東軒筆錄》所載,李遵勗與李迪、楊億、曹瑋及盛度都讚同寇準仁宗監國的計劃。121李遵勗後來沒受牽連,相信是丁謂顧忌李是長公主夫婿。另一方面,劉皇後與長公主夫婦都奉佛,共同信仰也讓姑嫂二人多一點親近。值得註意的是,錢惟演次子錢晦(?—1063後)後來娶了長公主的長女延安郡主。看來劉皇後對長公主是采拉攏的手段。上文曾交代,真宗一度有廢太子之意,賴李迪善言化解。筆者相信長公主在這件大事上當會竭盡其力幫助愛侄,力諫兄長不要聽信離間他父子感情的讒言。122
這年九月初八,真宗病體稍愈,恢覆在崇德殿視事。據僧釋則全(?—1045)的記載,李遵勗在此時向真宗委曲奏請,賜和他及楊億交好的四明法智尊者金知禮(960—1028)大師號,真宗準奏,特賜他“法智大師”。是月廿二,長公主的姊夫知徐州的王貽貞在決河浸徐州時,率軍民作堅堤城南,得以捍水患。京東勸農使將他的功績奏上,真宗詔獎之。王貽貞治郡有功,為外戚掙了面子,都是教真宗喜悅之事。123十月初五,真宗禦正陽門觀酺,仁宗侍坐共五日。真宗自病發以來,罕有臨幸。這次他公開活動,暫時穩定了人心。124
真宗在十一月十八對輔臣喜稱他寢膳已漸康覆,又表示仁宗年德漸成,而助他處理朝政的劉皇後又素來賢明,臨事平允,甚可托付而大表安慰。他說有意讓仁宗“蒞政於外,皇後居中詳處”。真宗以為政事已回覆正軌,卻未料到宋廷權爭並未因寇準等被貶而稍息,丁謂繼逐去與寇準親近的兩員樞臣周起和曹瑋後,又在十一月以巧計激怒一直盡力保護仁宗而開罪了劉後的李迪,令他糊裏糊塗地被罷去相位。王欽若偏偏在這時回朝,以為可以乘機重邀真宗及劉皇後的寵信而覆相。不過,一向以詭計打擊政敵的王欽若,卻鬥不過以前的黨羽、後來反目成仇的丁謂,而再被趕出京師。當李遵勗夫婦擔憂仁宗無援而儲位不保時,十二月初一,他們的摯友楊億卻病卒,對他們的打擊可謂不輕。李遵勗特為楊億制服並為他料理家事,葬楊億於許州(今河南許昌)之具茨山。據《東軒筆錄》所載,楊億臨終時,還將當日他所撰仁宗監國的詔誥及此事的始末經過,交給李遵勗收藏,作為他日為寇準及他們獲罪昭雪的憑證。125這年的閏十二月初,真宗又發病,因餌藥泄瀉,在前後殿均罷奏事。到了月底(廿九),才力疾禦承明殿,召丁謂等諭他們好好輔助尚未成年的仁宗。真宗又諭自今有大政,可以召入內都知參加會議,然後聞奏。真宗還以內有劉皇後在內廷輔助,應該無憂。丁謂滿口答應,安慰真宗好好休養。但朝臣都明白仁宗雖然聽政於資善堂。但什麽事都由劉皇後裁決,仁宗的地位其實不穩。親近仁宗的人包括長公主等皆以為憂,幸而王旦和寇準素來器重的參政王曾找到機會,向錢惟演申明一擲地有聲的道理,他說:“太子幼,非中宮不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後厚於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也。”王曾的話代表了主流朝臣的意向和態度,他們可以支持劉皇後掌權,條件是不能搖動仁宗的地位。王曾極有智謀,他並不像寇準和李迪選擇和劉皇後集團針鋒相對,為了保護了仁宗,他願意妥協,願意向劉皇後輸誠。錢惟演馬上向劉皇後稟報王曾極其重要的話。劉皇後衡量利害,知道無法撇開王曾等朝臣而獨攬大權,就接受王曾的建言,對仁宗親善,於是“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126劉皇後自此也對王曾另眼相看。劉皇後對仁宗不再猜忌,自然是宿國長公主等所樂見的。
天禧五年(1021)正月開始,真宗的健康稍為好轉,整個正月裏,真宗既能夠在延慶殿和承明殿接見及宴請輔臣,又能出席慶祝正旦而邀請文武臣僚、遼使參加的錫慶院春宴。真宗還前往啟聖院太宗神禦殿祭告亡父,稍後又撰《禦集》、《聖政紀》二序並出示輔臣。為了慶祝真宗康覆,宋廷又下詔減免秋稅,權罷滑州修河,另天下死罪者降等,流罪以下釋放。127二月,他又有雅興召輔臣觀書於龍圖閣,稍後又以蕊珠、群玉兩殿及天章閣上梁,宴近臣於承明殿。三月初,他又禦正陽門觀酺。稍後又以他的禦集和禦書奉於剛落成的天章閣,宴輔臣於閣下。又以天章閣成,給丁謂以下的輔臣加官晉爵。128朝局似乎穩定之余,真宗在四月初二,以劉皇後親信的內臣內殿崇班雷允恭(?—1022)為皇太子宮都監,同管勾資善堂、左右春坊司事,填補周懷政先前的職位,成為仁宗的大管家。129委任雷允恭擔此重任,究竟是真宗本人的主意,還是劉皇後控制仁宗的手段?筆者認為以後者居多。據《長編》所記,真宗後來對輔臣言及,“太子動息,後必躬親調護;暫去左右,則繼遣詢問,至於乳保、小臣,皆擇謹願歲久者,旦夕教其恭恪。”從正面去看,劉皇後可說是盡心保育仁宗,但從另一面去看,劉皇後對仁宗一舉一動都加以監察,很難說不是一種控制手段。130
是月十三日,仁宗十二歲生辰,宴宮僚輔臣於資善堂。丁謂等事後奏報真宗,吹噓仁宗“天姿英邁,好學不倦,親寫大小字示臣,天然有筆法”。而真宗繼在四月召集群臣往天章閣觀書並宴於群玉殿外,五月初一又禦崇政殿,觀錄京城系囚,下令死罪以下並減一等。七月初三,真宗又往謁他供奉天書的玉清昭應宮。131
在天禧五年的前半年,大概李遵勗也隨著群臣參加真宗親臨的宴會。至於長公主,可能也費神於教導延安郡主和李端懿兄妹,並且撫育尚年幼的次子李端願。真宗倒沒有忘記給他的親妹加恩,八月初五,樞密院奉真宗之意,以皇親諸宅置船,長公主二,郡縣主一。允許長公主等在京師諸河購物,豁免其差撥費用。真宗是月值得欣慰的事,是擔任洺州(今河北邯鄲永年縣東南)團練使的駙馬王貽貞於是月十一上奏諸州捕盜的問題,說得條理分明,足見他治郡勤勉,留心政務。然而,權傾朝野的劉皇後在是月卻遭到沈重的打擊,她賴以控扼禁軍的心腹馬軍都虞候劉美,在是月十八病卒。真宗對劉美恩恤甚厚,贈太尉、昭德軍節度使,並官給葬事。真宗又擢升他的兒子劉從德(1008—1031)自殿中丞為供備庫使,劉從廣(1021—1076)自供奉官為內殿崇班。劉氏旁親數人也加以遷補官職,又追封劉美亡妻宋氏為河內郡夫人。132劉美的兩個兒子年幼其官小,對劉皇後鞏固權力並不起作用。這對於保護仁宗的人來說,劉美在這關鍵時刻死亡,未嘗不是天助。
真宗的健康到十月後又逆轉,不能正常地視事,丁謂等請他五日一禦便殿,朔望才坐朝,春秋大宴及賜群臣會就止於內廷的錫慶院舉行。慶節和上壽,就改由仁宗押文武班。真宗只好接受臣下體恤他的安排。丁謂在十一月十三日,趁著真宗有病,又使出巧計,將在洛陽的對頭王欽若騙來京師療疾,然後又責他擅離職守,十七日,將他重貶為司農卿,分司南京(即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市)。133丁謂以為倚仗劉皇後的支持,就可以把他的政敵一一打倒。
長公主沒有想到,兄長才在翌年(1022)正月初一改元乾興,並在十三日命仁宗帶同師傅和宮僚朝拜啟聖院的太宗神禦殿。他在十七日還禦東華門觀燈。到二月初一,更禦正陽門,並以改元大赦天下,恩賞悉依南郊大典例。初四,他又接受群臣所上尊號“應天尊道欽明仁孝”。初五,下詔內外官並加恩。長公主和群臣大概以為真宗可以帶病延年幾時,但十天後(十五),當真宗召對宰相於寢殿東偏時,忽然疾作。四天後(十九)真宗崩於延慶殿。仁宗即位,尊劉皇後為皇太後,楊淑妃為皇太妃,因仁宗年方十三,不能親政,大權就由劉太後執掌,開始了她攝政掌權十二年的時代。134至於長公主夫婦,就小心翼翼與他們厲害的皇嫂周旋,暗中保護侄兒小皇帝。
(未完待續)
後記:
本文初稿在2013年5月3日至4日在台北東吳大學舉行的“第九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究會”上宣讀,蒙擔任本文評論人的黃啟江學長賜予寶貴意見,現據之加以修改,謹向黃學長致謝忱。
2013年8月25日香港理工大學
1、張邦煒:《宋代皇親與政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一章第三節 宋代的公主與駙馬,第90-121頁。
2、遊彪:《宋代蔭補制度研究》(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9月版),第八章第一節宗女蔭補制度,第190-208頁。又遊彪另有一文討論公主及其親屬的仕途,參見遊彪:《宋代特殊群體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8月版),公主及其親屬的仕途,第48-69頁。
3、王珺:《宋代公主生活考略》,(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5月版);任傳寧:《略論宋代公主──兼與唐代公主比較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5月版)。按兩篇碩士論文內容有不少地方重覆,又二文均論及宋代駙馬的情況。
4、目前在不少文學作品、影視戲劇都以柔福帝姬為題材。唯學術著作則較為少見。王曾瑜教授考論高宗(1107-1187,1127-1162在位)生母韋太後(1080-1159)之事跡時,曾旁及柔福帝姬真假的問題。參見王曾瑜:《宋高宗生母韋氏》,收入王著:《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608-623頁,有關柔福帝姬的事跡考述,見第622-623頁。至於近期的研究,可參見張明華:《南宋初年假冒宗室成員案發覆》,見《宋都開封與十至十三世紀國史國際學術研究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五屆年會論文集》,2012年8月版。
5、本文主角獻穆大長公主初封萬壽公主,真宗繼位後屢封萬壽長公主、隋國長公主、越國長公主、宿國長公主、鄂國長公主及冀國大長公主。仁宗即位後,晉位冀國、魏國大長公主,她在皇祐三年(1051)薨時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謚“獻穆”。因此之故,宋人筆下常稱他為“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徽宗後改封為荊國大長公主,政和年間又改封獻穆大長帝姬,後恢覆荊國大長公主之號,故《宋史》本傳以荊國大長公主稱之。為免稱呼混亂,本文之前言及余論即以她最後獲賜之謚號“獻穆大長公主”稱之。她被宋人所稱譽之處,下文將會交待。參見脫脫(1314—1355):《宋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11月版),卷二百四十五《宗室傳二·濮王允讓》,第8708頁;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荊國大長公主》,第8774-8775頁;李 (1161—1238):《皇宋十朝綱要》,收入趙鐵寒(1908—1976):《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年 1月版),卷二《太宗》,葉三上;徐松(1781—1848)(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11月影印國立北平圖書館1936年本),《帝系八之十六》。
(1161—1238):《皇宋十朝綱要》,收入趙鐵寒(1908—1976):《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年 1月版),卷二《太宗》,葉三上;徐松(1781—1848)(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11月影印國立北平圖書館1936年本),《帝系八之十六》。
6、除了黃啟江學長外,不少研究宋代佛教史的學者,都註意李遵勗在弘揚保護佛教,特別是禪宗的貢獻。有關李遵勗與佛教的相關研究,可參閱Chi-chiang Huang(黃啟江),Experiment in Syncretism:Ch’-Sung(1007—1072)and Eleventh-Century Chinese Buddhism,(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Ph.D.Dissertation,Unpublished,1986),Chapter2,pp.71-89;楊曾文:《宋元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七章第二節 北宋駙馬都尉李遵勗和禪宗,第536-547頁。
7、道濟是李遵勗次子李端願的玄孫,關於道濟的生平,可參閱許尚樞:《濟公生平考略》,載《東南文化》1997年第3期(總117期),第80-86頁;黃夏年:《湖隱方圓叟舍利銘考釋》,原文於2007年5月8日至10日之“海峽兩岸濟公文化研究會”宣讀,現發表於世界宗教研究網站(http://ziyi.qikan.com)。此條資料蒙黃啟江學長提示,謹此致謝。
8、李遵勗的祖父是太祖(927—976,960—976在位)的開國功臣、樞密使李崇矩(924—988)。李遵勗的父親李繼昌(948—1019)本來是太祖屬意的主婿,後來因李崇矩不願而罷。他屢有戰功,後官至左神武大將軍。參見《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崇矩附李繼昌傳,第8952-8956頁。又北宋初年的另外一顯赫外戚將門,由太祖的開國功臣、樞密副使李處耘(920—966)起家,因其女太宗明德李皇後(960—1004)成為外戚,而由其二子李繼隆(950—1005)、李繼和(963—1008)立功成名,也出於潞州上黨。這兩個潞州上黨外戚將門都是北宋前中期的顯赫世家。李處耘一家的事跡,筆者有專著討論。可參閱何冠環:《攀龍附鳳:北宋潞州上黨李氏外戚將門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5月版)。
9、《宋史》,卷二百四十五《宗室傳二‧周王元儼附允初傳》,第8707頁;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年8月至1995年4月),卷一百十二,明道二年四月己未條,第2612-2613頁;卷一百十七,景祐二年十一月乙巳條,第 2763 頁;卷一百三十七,慶歷二年閨九月癸酉條,第3295頁;蘇轍(1039—1112)撰,俞宗憲(點校):《龍川別志》(與《龍川略志》合本)(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4月版),卷上,第78-79頁。據李燾所考,允初生於天聖七年(1029),即使他稍長,也與仁宗的年齡有一段距離,不可能有什麽親密的感情。至於呂夷簡所以反對將允初留在宮中陪伴仁宗,是擔心劉太後有將允初取代仁宗之意。另太宗長子楚王元佐之長孫宗頡幼時亦侍仁宗於東宮,但他未及賜名便夭亡,也談不上與仁宗有任何感情。
10、汪聖鐸:《宋真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一章第四節 真宗的姊妹們,第14-16頁。
11、考《皇宋十朝綱要‧太宗》所記太宗七位公主的長幼次序與《宋史‧公主傳》及《宋會要輯稿‧帝系八‧公主》略有出入。《皇宋十朝綱要‧太宗》之次序是滕國大長公主、徐國大長公主、揚國大長公主、雍國大長公主、衛國大長公主、邠國大長公主、荊國大長公主。另外,《宋大詔令集》,則稱衛國大長公主為真宗的“皇第七妹”。據此,《宋史》和《宋會要輯稿》所記太宗七女的次序當較《皇宋十朝綱要》可信。又《宋大詔令集》又稱徐國大長公主為太宗的“皇第四女”似乎太宗尚有沒有名號的兩名女兒,在滕國大長公主後,而在徐國大長公主之前。又除了本文主角荊國大長公主的壽數及卒年確知外,只有後來出家的衛國大長公主知其壽數及卒年,其他五位公主只知卒年而不知其壽數,也就不知其生年。至於太宗長女滕國大長公主早夭,生卒年及壽數均不載。又除了確知揚國大長公主及衛國大長公主的生母為太宗臧貴妃(?—1022 後)外,其他五位公主的生母均不詳。參見《宋史》,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太宗七女》,第8773-8775頁;李 (1161—1238):《皇宋十朝綱要》,收入趙鐵寒(1908—1976)(主編):《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1月版),卷二《太宗》,葉一下至二上、三上;《宋會要輯稿》,《帝系八之八、九、十、十六》;不著撰人(編)、司義祖(點校):《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10 月版),卷三十六《皇女一‧封拜一》、《皇第四女蔡國公主進封魏國公主制‧淳化元年》、《皇第七妹陳國長公主封吳國長公主號報慈正覺大師制‧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癸卯》,第191頁;文瑩(?—1078後)著,鄭世剛、楊立揚(點校):《湘山野錄》(與《玉壺清話》合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7月版,卷上,第17-18頁。
(1161—1238):《皇宋十朝綱要》,收入趙鐵寒(1908—1976)(主編):《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1月版),卷二《太宗》,葉一下至二上、三上;《宋會要輯稿》,《帝系八之八、九、十、十六》;不著撰人(編)、司義祖(點校):《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10 月版),卷三十六《皇女一‧封拜一》、《皇第四女蔡國公主進封魏國公主制‧淳化元年》、《皇第七妹陳國長公主封吳國長公主號報慈正覺大師制‧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癸卯》,第191頁;文瑩(?—1078後)著,鄭世剛、楊立揚(點校):《湘山野錄》(與《玉壺清話》合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7月版,卷上,第17-18頁。
12、《長編》,卷七十,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丁亥朔條,第1579頁;卷一百七十,皇祐三年三月丙子條,第4085頁。
13、上文註已提及,徐國大長公主被稱為太宗的“皇第四女”,似乎在她之前尚有兩個姐姐。即是說太宗可能原本有九個女兒,兩個沒有名號而失載。不過,我們無從判定,徐國大長公主被稱為“皇第四女”,是與太宗的兒子一起按長幼而排,還是只按太宗的女兒長幼而定?參見《宋大詔令集》,卷三十六《皇女一‧封拜一》、《皇第四女蔡國公主進封魏國公主制‧淳化元年》、《皇第七妹陳國長公主封吳國長公主號報慈正覺大師制‧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癸卯》,第191頁;《宋史》,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太宗七女》,第8773-8775頁。
14、據《長編》所記,公主的家翁李繼昌在天禧元年(1017)十二月前以左神武大將軍、獎州刺史權判右金吾街仗司。長公主生日,就請他過府迎拜獻壽。是條記載系於天禧元年十二月戊子條,疑長公主的生日在十二月。參見《長編》,卷九十,天禧元年十二月戊子條,第2090頁。
15、《宋史》,卷二百四十五《宗室傳二‧周恭肅王元儼》,第8705-8706頁;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荊國大長公主》,第8774頁;《皇宋十朝綱要》,卷二,葉一下(第40頁);《長編》,卷一百十一,明道元年十月戊午條,第2591頁;卷一百三十五,三月庚申條;卷一百七十,皇祐三年三月丙子條。考方貴妃初封新安郡君,天禧二年(1018)九月晉美人。乾興元年(1022)四月進婕妤。天聖九年(1031)十一月進昭媛。她的卒年月闕。明道元年(1032)十月贈太儀。二年(1033)十一月,因荊國大長公主之請,贈德妃,慶歷四年(1044)九月贈淑妃,最後贈貴妃。又《宋史》元儼本傳及《長編》稱他的生母是王德妃,推據《皇宋十朝綱要》,太宗妃子中並沒有王德妃。不知是《宋史》及《長編》將方貴妃訛寫為王貴妃,還是《皇宋十朝綱要》漏記王昭媛之名,待考。
16、《宋史》,卷二百四十五《宗室傳二‧漢王元佐》,第8693頁;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荊國大長公主》,第8774頁;《長編》,卷一百七十,皇祐三年三月丙子條,第4085-4086頁。
17、張邦煒:《宋代皇親與政治》,第93-94頁。
18、洪邁(1123—1202):《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7月版),《齋三筆》第十四卷《夫人宗女請受》,第582頁。據洪邁所記,仁宗起初要定公主俸料錢,就詢問他的姑娘萬壽公主(獻穆大長公主),她起初不肯說,仁宗問之再三,才說出當初只得五貫錢。
19、《湘山野錄》,卷上,第17-18頁;《皇宋十朝綱要》,卷二,葉三上(頁43);《宋史》,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太宗衛國大長公主〉,第8774頁;據文瑩所記,壽昌公主俗壽三十八。按她卒於天聖二年(1024)五月,則她當生於雍熙四年(987),只比獻穆大長公主長一歲。端拱只有兩年,若據《湘山野錄》所記,她在端拱初年(988—989)隨太宗幸延聖寺許願為尼,最多只有三歲,此事的確實性待考。
20、《長編》,卷三十三,淳化三年十一月己亥條,第740-742頁。關於元僖被寵妾張氏錯手下毒致死,及後來他被揭發涉嫌曾暗中施行巫術,加害父兄之事,可參見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10月版),第33-34頁。
21、《長編》,卷三十八,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至十月乙亥條,第818-821頁。
22、《長編》,卷四十一,至道三年二月辛醜至五月甲戌條,第861-866頁。關於太宗晚年儲位的爭奪,以及真宗被冊為太子後的險惡環境,以及呂端等如何挫敗李皇後廢立真宗的陰謀,可參見何冠環:《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36-40頁。
23、長編》,卷一百七十,皇祐三年三月丙子條,第4086頁。
24、《宋史》,卷六《真宗紀一》,第 104-105 頁;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 大祖六女、太宗七女》,第 8772-8774 頁;《長編》,卷四十一,至道三年五月丁亥條,第 866 頁。按太祖的三位公主早就獲國封,真宗在是日就晉封他的兩位從姊秦國公主、晉國公主為秦國長公主和晉國長公主,輩分屬於真宗從妹的齊國公主就改封為許國長公主。至於他的四位親妹因尚未出閣而未獲國封,故宣慈公主(揚國大長公主)晉宣慈長公主,賢懿公主(雍國大長公主)晉賢懿長公主,壽昌公主(衛國大長公主)晉壽昌長公主,萬壽公主(荊國大長公主)晉萬壽長公主。考太宗的長女滕國大長公主、二女徐國大長公主及三女邠國大長公主已在太宗朝先後去世,真宗在這時沒有追封滕國大長公主,卻追封徐國大長公主自魏國公主為燕國長公主(按:徐國大長公主是哲宗後來的加封),邠國大長公主為曹國長公主(按:邠國大長公主在太宗朝出家為尼,號員明大師,她在太平興國八年卒,生時沒有得到公主的封號)。又按萬壽公主的封號當為太宗所賜,真宗即位後晉長公主。順帶一提,真宗在晉封姊妹為長公主翌日(廿四),才冊封秦國夫人郭氏(976—1007)為郭皇後。
25、《湘山野錄》,卷上,第17頁。考《湘山野錄》這條所記的申國大長公主即壽昌長公主及衛國大長公主。
26、《宋會要輯稿》,《禮四十一之三十九》;《宋史》,卷二百五十《王審琦傳附王承衍傳》,第8817-8818頁;《長編》,卷四十七,鹹平三年七月庚子條,第1022頁。按《宋史‧王承衍傳》以王承衍在鹹平六年以疾求罷節鉞,未幾卒,年五十二。顯然將鹹平元年訛寫為鹹平六年。考《長編》記,王承衍妻秦國長公主在鹹平三年七月廿五,便請為王承衍置守冢五戶。可見王承衍早在鹹平三年前已卒。《宋會要》記王承衍卒於鹹平元年七月蓋得其實。
27、太祖許國長公主是魏鹹信(949—1017)妻,她是真宗朝第一位逝世的長公主。又真宗的從弟、叔父秦王廷美(947—984)的第九子左武衛大將軍德願(976—999)也在鹹平二年閏三月庚寅(初七)卒,得年二十四。參見《宋史》,卷六《真宗紀一》,第108-109頁;卷二百四十四《宗室傳一‧魏王廷美》,第8670頁。
28、《長編》,卷五十二,鹹平五年五月戊戌條,第1130頁;卷五十四,鹹平六年二月丙子條,第1180頁;《宋史》,卷七《真宗紀二》,第121頁;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太宗七女‧揚國大長公主、雍國大長公主》,第8773-8774頁。柴宗慶是太宗朝樞密使柴禹錫(943—1004)孫,而王貽貞則是太祖朝宰相王溥(922—982)孫。
29、《長編》,卷四十七,鹹平三年四月壬申條,第1014頁;卷五十三,鹹平五年十一月己酉條,第1163頁;卷五十四,鹹平六年四月辛巳條,第1190頁;《宋史》,卷七《真宗紀二》,第121頁;卷二百四十五《宗室傳二‧悼獻太子》,第8707頁。周王的生母章穆郭皇後可說是連遭不幸,他的二兄西京左藏庫使郭祟仁(?—1000)在鹹平三年四月廿五卒,三年後她的獨子信國公玄祐又夭亡。玄祐是真宗的次子,唯其長兄溫王禔早夭,故在鹹平六年時,他是真宗的嫡長子,只差未正式冊封為太子。他在鹹平五年十一月十八才封左衛上將軍信國公,五個多月後卻夭亡。他之死對真宗和郭皇後自是打擊甚大。真宗追封他為周王,謚悼獻。
30、德潤是真宗叔父秦王廷美第七子,《宋史》本傳稱他頗好學而善為詩。卒年三十九,贈應州觀察使,追封金城侯。元傑是真宗五弟,長公主的五兄,真宗即位後自吳王改封兗王,《宋史》本傳也稱他穎悟好學,善屬詞又工書法。他在鹹平六年七月暴卒,得年才三十二。他卒時,真宗親臨其喪,哀動左右,廢朝五日,追封安王,謚文惠。同年九月初二,真宗又下詔以元傑之喪,秋宴不舉樂。參見《長編》,卷五十五,鹹平六年七月癸醜條,第1208頁;九月己醜條,第1211頁;《宋史》,卷七《真宗紀二》,第121-122頁;卷二百四十四《宗室傳一‧魏王廷美傳附德潤傳》,第 8674 頁;卷二百四十五《宗室傳二‧越王元傑》,第8700-8701頁。
31、《長編》,卷五十五,鹹平六年十一月甲戌至戊寅條,第1221頁。
32、《長編》,卷五十六,景德元年正月乙未條,第225-1226頁。
33、《長編》,卷五十六,景德元年三月丁酉至己酉條,第1232頁;四月丙辰條,第1233頁;《宋史》,卷七《真宗紀二》,第124-125頁;卷二百四十四《宗室傳一‧魏王廷美傳附德欽傳》,第8674頁。真宗對嫡母明德李太後病情加重時,就憂形於色,言必流涕。太後逝世,史稱他缞服慟哭見群臣。然而李太後曾有廢立真宗的重大嫌疑,史書所記真宗之哀傷,叫人懷疑真情有多少。對於親妹之喪,史稱真宗慟哭不勝哀。那應該是真情流露的。考真宗快要北征前,曾在是年十月癸巳(十三)幸鄭國長公主第拜祭。又德欽是真宗叔父廷美第六子,卒年三十一,贈雲中觀察使,追封雲中侯。輩分上他也是長公主的從兄,他也是得年不永。
34、《長編》,卷五十七,景德元年八月戊寅條,第1253頁;九月丙午條,第1259頁。按魯國長公主的家翁鎮寧軍節度使柴禹錫在景德元年八月廿六日卒。
35、《宋史》,卷七《真宗紀二》,第123-126頁。又李繼遷族兄李繼捧(趙保忠)亦於景德元年六月十七卒。
36、《長編》,卷五十八,景德元年十一月戊辰至十二月丙戌條,第1282-1292頁;十二月乙未至丁酉條,第1297頁。
37、《長編》,卷五十八,景德元年十二月丁酉條,第1297頁;卷六十二,景德三年三月乙巳條,第1391頁;楊億:《武夷新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潞州新敕賜承天禪院記〉,葉二十一下至二十四上。據楊億所記,李崇矩篤信佛教,“奉身甚約,事佛尤謹。生平飯僧七十萬,造千佛像。修紺殿以嚴寶剎,飾瑯函以秘金文。又以方牘,摹印《金剛》、《上生》等經,施於四眾。山門禪苑,多所繕完;什器道具,率用營置。”而李繼昌一再請求楊億為文以志此事,於是楊億在景德二年四月初八寫就這篇記文。
38、《長編》,卷五十九,景德二年二月癸未條,第 1315-1316 頁;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庚戌條,第1334頁。
39、《長編》,卷六十一,景德二年八月庚辰至丁亥條,第 1356-1357 頁;八月乙未條,第1359頁;九月甲寅條,第1364-1365頁;《宋史》,卷七《真宗紀二》,第129頁;卷二百四十五《宗室傳二‧商王元份》,第8699頁。考元份在這年五月十二病重,真宗曾親往視疾。元份死後,真宗在傷痛之余,將元份悍妬不仁之妻李氏削國封置之別所,而原為元份擔任東京留守時的官屬的翰林學士晁迥(951—1034)、雍王府記室參軍、兵部郎中楊澈、祠部郎中朱協均以輔導無狀而被貶官。又《宋史·真宗紀》以元份卒於八月初二。
40、《長編》,卷六十一,景德二年十月乙酉條,第1369-1370頁。
41、《宋史》,卷七《真宗紀二》,第130頁;《長編》,卷六十二,景德三年二月丁亥條,第1387-1388頁。
42、《長編》,卷六十三,景德三年五月己未條,第1402頁;《宋史》,卷七《真宗紀二》,第130-131頁;卷二百四十四《宗室傳一‧魏王廷美諸子》,第8671頁。德恭是真宗叔父秦王廷美的長子,字覆禮,長真宗六歲。他在景德三年二月初一發病,真宗親往北宅視疾,到五月十六德恭病篤,真宗再往視疾,兩天後德恭即病亡。
43、《長編》,卷六十五,景德四年正月癸醜條,第1442頁;《宋史》,卷七《真宗紀二》,第132頁;卷二百四十四《宗室傳一‧魏王廷美諸子》,第8674頁。德鈞是真宗叔父秦王廷美第五子,字子正,史稱他性和雅,善書翰。他生年不卒,大概得年三十余,份屬真宗從弟。在景德三年十二月發病,是月廿四真宗曾往北宅視疾。真宗追封他安鄉侯,贈河州觀察使。
44、《長編》,卷六十五,景德四年四月辛巳至乙未條,第1452-1454頁;六月乙卯條,第1464頁;《宋史》,卷七《真宗紀二》,第133頁;卷二百四十二《後妃傳上‧真宗章穆郭皇後》,第8611-8612頁。史稱郭皇後因獨子周王夭折,哀傷成疾而不起。又有司初謚郭皇後為莊穆皇後,仁宗時才改章穆。
45、《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後妃傳上‧真宗章獻明肅劉皇後》,第8612-8613頁。
46、真宗先後在景德三年四月初二及十二月廿四曾幸秦國長公主第。景德四年十月廿六,秦國長公主請擴大她一家修行的幹明寺內的無量壽院。不過這次真宗以要求擴大的步廊是寺眾出入之所,才沒有答應。而晉國長公主就一直為親屬求恩,景德四年十二月初十,她便求得真宗封其夫石保吉的庶女為樂陵郡主。參見《宋史》,卷七《真宗紀二》,第130、132頁;《長編》,卷六十七,景德四年十月己未條,第1501頁;十一月戊子條,第1508頁;十二月壬寅條,第1511頁。
47、關於真宗天書封禪的鬧劇的始末,學者論述者甚多。可以參閱汪聖鐸:《宋真宗》,第四章 天書降,封禪行,第87-115頁;第五章 聖祖降,崇道教,第116-150頁。
48、《宋史》,卷七《真宗紀二》,第136頁;卷一百二十四《禮志二十七》,第 2902 頁;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太祖魏國大長公主》,第8772頁;卷二百五十七《李繼和附傳》,第8974頁;《長編》,卷六十八,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庚戌條,第1526-1527頁;卷六十九,大中祥符元年五月癸酉條,第1544頁;《宋會要輯稿》,《禮四十一之三、四》、《禮四十一之十六》、《禮四十一之二十六》、《禮四十一之三十八》。按秦國長公主在大中祥符元年四月病重,真宗曾在四月十八日臨公主第視疾。真宗同日又幸晉國、魯國長公主第,並賜白金千兩、彩二千匹。李繼和及秦國長公主之喪,真宗都先後親臨祭奠,並分別輟朝三日及五日以致哀,秦國長公主賜謚賢肅。
49、《長編》,卷七十,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丁亥朔條,第1579頁;卷七十一,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己巳條,第1588頁;《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崇矩傳附李繼昌傳》,第8954頁;卷四百六十四《外戚傳中‧李遵勗》,第13567-13568頁;孫旭:《宋代駙馬升行探微》,載姜錫東、李華瑞(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十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51-61頁。關於真宗將王貽貞、柴宗慶及李遵勗三駙馬升行輩的原因,孫旭認為是為了維護皇族輩分的權宜之作。此說可取。又據《長編》所記,真宗曾對宰相說,太宗時公主出降,月俸百五十千,後來稍增至二百千。太宗晚年曾許諸公主增俸。真宗繼位後,明德李太後對真宗道及太宗的許諾,於是諸長公主之月俸增至三百千。真宗說如今初出降者,亦求此數,大概因他未對諸長公主解釋,初給俸時不應得三百千之數,才有這樣的請求。真宗說現在東封行慶典,他只會加她們美號,而不會增加們她的月俸。按這段話顯然是回應長公主出降應得多少的月俸數額。筆者以為,以長公主的性情,她當不會計較區區的月俸錢多少,可能是她的夫家提出而已。
50、據《圖畫見聞志》所記,太宗曾特贈李遵勗以徐崇嗣所畫芍藥五本的名畫“沒骨圖”,似乎已有擇其為其東床之意,該畫後來成為長公主的臥房中物。參見郭若虛(?—1074後)撰,鄧白註:《圖畫見聞志》(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卷六《沒骨圖》,第346-347頁。
51、《宋史》,卷四百六十四《外戚傳中‧李遵勗》,第13567-13568頁。
52、《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崇矩傳附李繼昌》,第8955頁。
53、《長編》,卷七十,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辛醜至丁未條,第1581-1582頁;卷七十一,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己巳條,第1588頁;《宋史》,卷七《真宗紀二》,第139頁;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太祖魯國大長公主、太宗揚國大長公主、太宗衛國大長公主》,第8772-8774頁。
54、《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崇矩傳附李繼昌》,第8955頁。據李繼昌的本傳所記,真宗召見李繼昌後,又遣尚醫診視他,假滿仍給他俸。他稍病愈,真宗令樞密院傳旨,將會真拜他刺史,覆任延州。李繼昌以疾上表休致,真宗不許,改右驍衛大將軍,依舊領郡。李遵勗成婚時,他當在京師主持婚禮。
55、《長編》,卷七十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子條,第1595頁;六月丙申條,第1611頁;《宋史》,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太宗衛國大長公主》,第9774頁。真宗本來派人為她修造寺院,沒想到執事人互持己見,屢有改易,反而勞費甚多,有違真宗初衷。真宗在六月十三下詔切責執事人。
56、參見《長編》,卷七十一,大中祥符六月庚寅條,第1610頁;《宋史》,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荊國大長公主》,第8774頁;卷二百五十七《李崇矩傳附李繼昌傳》,頁8952-8956;卷四百六十八《外戚傳中‧李遵勗》,頁13568。據《隆平集》所記,李遵勗夫婦所居的園池,他們聚集了許多來自數千裏外的奇花果美石,所費不匪。內中有“會賢”和“閑燕”二堂,東北隅有莊曰“靜淵莊”,引流水環繞莊舍下。據南宋人所記,永寧裏公主第為諸主第一,“靜淵莊”就在宅東隙地共百余畝,盡疏濬為池,俗稱李家東莊。參見曾鞏(1019—1083)撰,王瑞來校證:《隆平集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7月版),卷九《李崇矩傳附李遵勗》,第280頁;葉夢得(1077—1148)撰,徐時儀整理:《避暑錄話》,戴建國等編:《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十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1月版),卷下,第311頁。
57、《長編》,卷七十一,大中祥符二年五月辛未條,第1608頁。
58、《長編》,卷七十一,大中祥符二年六月庚寅條,第1610頁。遊彪認為李遵勗這次升官甚快。而隨著其官位的上升,其相應的待遇也迅速提高;不過,真宗並沒有像太祖及太宗那樣隨便給主婿實際的差遣。大概真宗考慮李遵勗資望年齡均淺。參見遊彪:《宋代特殊群體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8月版),上篇《趙宋宗室、官員子弟及其他》,第50頁。
59、按《長編》以陳國長公主為皇第八妹,據《宋史‧公主傳》,她在太宗諸女中排名第七,僅長於隨國長公主。而《宋大詔令集》所收的晉封她為吳國長公主的制文即稱她為“皇第七女”。另宋人筆記《湘山野錄》也稱他為太宗第七女,不知《長編》何所根據。又本來長公主賜師號,不當降制。為了增加她的榮寵,真宗就特別將妹妹晉封大國公主,而得以降制以榮之。這篇有276字的四六制文收入《宋大詔令集》。制文洋洋灑灑,有可能出自同樣禮佛楊億手筆。制文雲:“皇第七妹陳國長公主,爰自先朝,特鐘慈愛。出於至性,不茹葷辛。資夙習以非常,悟清幾而迥異。專師沖寂,深厭紛華。尤軫聖考之懷,俾服空王之教。朕頃侍左右,嘗聆誨言,早以仲妹之賢,已達竺幹之旨。棲心有素,從欲靡違。懿茲同氣之親,能繼出塵之跡。睿訓斯在,欽念惟寅。屢稽厘降之文,備形惇諭之意,而潔齋無改,至願彌堅。期以修練之勤,上報劬勞之德。矧先志之允屬,且素範之不渝。良難重違,徒積多尚。是用擇徽名於梵苑,疏茂渥於脂田。國邑進封,禪林錫號,並伸寵數,式示褒揚。”又據文瑩所記,當時兩制學士奉命作詩送公主,尚流傳的有翰林學士陳彭年(960—1017)的一首七律。參見《湘山野錄》,卷上,第17-18頁;卷下,第58頁;《長編》,卷七十二,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癸巳、癸卯條,第1628頁,第1631頁;《宋史》,卷二百四十五《宗室傳二‧鎮王元偓、楚王元偁》,第8702-8705頁;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太宗衛國大長公主》,第9774頁。參見《宋大詔令集》,卷三十六《皇女一‧封拜一》、《皇第七妹陳國長公主封吳國長公主號報慈正覺大師制‧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癸卯》,第191頁;《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十》。
60、《長編》,卷七十二,大中祥符二年九月戊辰條,第1634頁;《湘山野錄》,卷上,第18頁。
61、《長編》,卷七十二,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庚辰條,第1643頁;卷七十三,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壬子條,第1662頁;《宋會要輯稿》,《禮四十一之十六》、《禮四十一之二十六》。考晉國大長公主婿、駙馬都尉石保吉從陳州(今河南周口淮陽縣)趕回京師料理妻子的後事才五月,便在翌年(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初三日在京師病逝。真宗廢朝三日,贈中書令,謚莊武,喪禮畢,真宗並親臨其宅吊問。
62、《長編》,卷七十三,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癸亥條,第1666-1667頁;《宋史》,卷九《仁宗紀一》,第175頁;卷二百九十二《後妃傳上‧真宗李宸妃》,第8616頁。
63、《長編》,卷七十三,大中祥符三年五月丙戌條,第1670-1671頁;《宋會要輯稿》,《禮四十一之十六》;《宋史》,卷七《真宗紀二》,第143頁;卷二百四十四《宗室傳一‧燕王德昭附惟吉傳》,第8678-8679頁。惟吉是太祖長子德昭(951—979)長子。
64、據周必大(1126—1204)所記,真宗在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禦書《春日賜宿國長公主園林詩》。該幅真宗禦書留有仁宗在皇祐五年(1053)九月十六日的跋文,仁宗以此賜李端懿、李端願兄弟家藏。書後另有英宗於治平三年(1066)九月十四日的跋文,仍令李端願依舊家藏。按宿國長公主長女在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彌月,長公主帶同女兒入見真宗,真宗大概在禦苑園林寫下這首詩送給幼妹,向她祝賀。參見蔡襄(1012—1067)著,吳以寧點校:《蔡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版),《蔡忠惠集》,卷三十九《墓志銘二‧延安郡主李氏墓志銘》,第708頁;周必大:《文忠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百八十,葉九下至十上。
65、《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 147 頁;卷二百五十七《李崇矩傳附李繼昌》,第8955-8956頁。
66、真宗在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丁酉(廿三)從京師往河中府祀汾陰,二月壬戌(十八)禦朝覲壇,受群臣朝賀而大赦天下。至四月甲辰朔(初一)返京師。李遵勗私通乳母之事,疑早在四月前發生。據李燾引述《涑水記聞》一則來自劉攽(1022—1088)的記載,稱真宗本來極怒,甚至要殺李遵勗。他先召入隨國長公主,試探她的反應說:“我有一事欲語汝而未敢。”公主嚇得驚叫說:“李遵勗無恙乎?”並且流涕被面,僵仆於地。真宗見幼妹如此反應,就沒有殺李遵勗。劉攽又記,後來長公主逝世,李淑(1003—1059)受詔撰公主碑,他宣言“赦李遵勗事尤美,不可不書”。公主諸子以此事涉亡父失德之事,於是重賄李淑,叫他不要記下這事。李燾認為真宗性仁厚,不會為此事而馬上要殺李遵勗。他疑司馬光此一傳聞或人所厚誣而不足取。考今本《涑水記聞》並無《長編》所引述的一條,鄧廣銘在該書的附錄所引的一條系於《長編》輯出。筆者同意李燾的見解,李遵勗私通乳母,確實對不起隨國長公主,但罪不至死,真宗不會因此一過失而誅其妹夫。不過長公主愛夫情深,一力維護夫婿卻是可信的。參見《長編》,卷七十五,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丁酉條,第1708頁;二月壬戌條,第1712頁;四月甲辰朔、壬子條,第 1718-1719 頁;司馬光(1019—1086)撰,鄧廣銘(1907—1998)、張希清校註:《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8月版),附錄二,第357頁;《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148-149頁;卷四百六十四《外戚傳中‧李遵勗》,第13568頁。
67、《宋史》,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太宗揚國大長公主》,第8773-8774頁。
68、李遵勗有庶子李端憲(?—1048),生年不詳,官至供備庫使,他在慶歷八年(1048)三月卒,以李遵勗故贈澤州刺史。他並非魏國(隨國)長公主所出,但宋廷仍輟朝一日,議者以為是禮官之失。參見《宋會要輯稿》,《禮四十一之四十》、《儀制十之十二》。
69、司馬光撰,李文澤、霞紹暉點校:《司馬光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二冊,卷二十一《章奏六‧正家劄子‧嘉祐七年二月初四日上》,第583-584頁。
70、《長編》,卷七十一,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戊子條,第1600頁;卷七十六,大中祥符四年六月癸卯朔條,第1726頁;《宋史》,卷八《真宗紀八》,第149頁;卷二百四十四《宗室傳一‧魏王廷美附德存》,第 8675 頁;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太宗徐國大長公主》,第8773頁。吳元扆是太宗長女徐國大長公主婿,是太祖開國樞密使吳延祚(911—964)子。他給真宗的印象是賢而純謹謙遜,“在藩鎮有憂民之心,待賓佐以禮,處事畏慎”,是主婿之模楷。他在次年正月十五日下葬時,真宗又命上元燃燈節延一天舉行,以示哀悼。吳元扆卒後三天,即是月初四,真宗的從弟左羽林將軍德存(982—1011)亦病卒。德存是真宗叔父秦王廷美幼子,曾先後扈從真宗祠泰山和汾陰,是真宗信任的宗室。真宗贈他洮州觀察使,追封洮陽侯。真宗曾在五月廿八往德存宅視疾,德存在六天後卻病卒。
71、《長編》,卷七十六,大中祥符四年七月丙子、壬午、己醜條,第 1728-1730 頁;八月癸醜條,第1732頁;十一月癸巳條,第1742頁;《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149頁;卷二百四十四《宗室傳一‧秦王德芳附惟敘》,第8686頁;《宋會要輯稿》,《禮四十一之十六》。值得一提的是,楚國長公主所轄的崇真資聖禪院以買蔬菜事擾民,真宗就幹脆賜她以蔬圃。不過,當衛國長公主的夫婿泉州觀察使柴宗慶在是月十八日上表求邊任時,真宗卻以他“未嘗更事,豈堪邊事”而不允許所求。不過,在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廿四日,真宗應衛國長公主的多次請求,就特別加封柴宗慶母穆氏為河南郡君。附帶一談,在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十二日,另一員曾扈從真宗祀汾陰的宗室、真宗的再從侄左千牛大將軍河內侯惟敘(977—1011)病卒,有司言以他的身份,真宗無須行臨喪制服之禮。但真宗友愛宗族,仍在當日往惟敘院為他臨奠。惟敘是太祖次子秦王德芳長子,本傳稱他性純謹而頗好學,他在大中祥符四年曾從真宗祀汾陰,真宗在八月初五他病重時,曾往他宅省視,他得年才三十五。
72、考《宋史》本遵勗本傳記他徙蔡州後,“踰年,起為太子左衛率府副率,覆左龍武軍將軍”。他當在大中祥符五年初召還京師。按公主與他所誕的長子李端懿生於大中祥符六年,公主受孕當在五年,而李遵勗應在五年已返京師。參見《蔡襄集》,《蔡忠惠集》卷三十九《墓志銘二‧延安郡主李氏墓志銘》,第708頁;《宋史》,卷四百六十四《外戚傳中‧李遵勗》,第13568頁。
73、考真宗在是年九月已議立皇後,屬意劉德妃。宰執大臣,參知政事趙安仁(958—1018)以劉德妃出身寒微而反對,主張立沈才人。真宗不悅,將趙安仁罷政。而樞密使王欽若(962—1025)就極力讚同。宰相王旦起初態度曖昧,後來改變態度,於是劉後得立。參見《長編》,卷七十七,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戊寅條,第 1765 頁;卷七十八,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條,第1786-1787頁;卷七十九,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丙申條,第 1803-1804 頁;十二月丁亥條,第1810頁;《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 151-152 頁;卷二百四十五《宗室傳二‧商王元份》,第8699頁。
74、先是柴宗慶上言他自陜西市木至京,請免稅算。真宗以早前已向他戒諭不得如此,如今他竟還有此陳奏。於是命樞密院召他戒飭一番。稍後河東提點刑獄張懷寶又劾奏柴宗慶私自派人買馬卻不輸納稅,真宗以申飭過,就詔釋不問。至於衛國長公主也和夫婿一樣貪得無厭,她早在大中祥符五年二月,向真宗言及她在汴河內置船二只,牧載供宅物品,她請求免頭子力勝錢,真宗答應她的請求,免卻諸雜差使。她又不知足,請買比鄰華容縣主張氏的房舍,以廣其居。真宗命她按價購買方可。稍後真宗卻查知張氏不欲出售,就戒令公主不得強買。真宗仍賜錢二百萬,聽她在別處購買房舍。參見《長編》,卷七十八,大中祥符五年六月戊申條,第1770頁;《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十之一》。
75、據《宋會要》所載,真宗以聖祖降的恩典晉封三位妹妹公主時,他發覺大國公主之名號已遍封,沒有理由將尚未有封賜的小國公主名號給三位妹妹。不過王旦以為“亦有以小國美名升為大國進封者”。真宗接納王旦的意見,於是將本來屬於大國公主的衛國長公主、楚國長公主、越國長公主改封為本為小國公主的徐國、邠國和宿國長公主。為此,真宗又特別將徐國、邠國及宿國特升為大國,在衛國、楚國及越國之上。又真宗在大中祥符六年正月庚申(廿八)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在昭儀之上。又置司宮令,正四品,在尚宮上。同日即晉封楊氏等三人。按楊氏後來成為劉皇後的宮中助手,撫育仁宗。而戴氏為太宗朝殿前都指揮使、定武軍節度使戴興(?—999)女,乾興元年(1022)四月進婉儀,卒年月闕。慶歷四年(1044)九月贈順容。曹氏為太祖到真宗朝之樞密使曹彬(931—999)女,乾興元年四月進婉儀,天聖四年(1026)六月卒,皇祐元年(1049)十月贈賢妃。參見江少虞(?—1145後):《宋朝事實類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版),卷三十三《典故沿革‧親王公主封國》,第423-424頁;《長編》,卷八十,大中祥符六年正月辛亥至庚申條,第1816頁;《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153頁;《宋會要輯稿》,《帝系八之十六》;《皇宋十朝綱要》,卷三《真宗》、《皇後五》、《嬪妃七》,葉一下至二上(第82-83頁)。
76、《長編》,卷八十,大中祥符六年正月辛酉條,第1817頁;《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153頁;卷二百四十四《宗室傳一‧燕王德昭附惟和》,第8676頁、第8680-8681頁。真宗除了為弟弟元儼之行為煩惱外,這年六月初二,從兄燕王德昭之幼子右千牛衛大將軍惟和(978—1013)病卒,得年才三十六。真宗對惟和很欣賞,曾對王旦稱許他“好文力學,加之謹願,皇族之秀也”。對他之不壽,嗟悼久之,至於泣下。真宗且錄其稿二十二軸,並親作序,藏於秘閣。
77、據李端懿的墓志銘所記,他字符伯,是李遵勗和公主的長子,仁宗的嫡親表弟。他卒於嘉祐五年(1060)八月,得年四十八,以此上推,他當生於大中祥符六年(1013),唯哪一月不詳。參見歐陽修(1007—1072)撰,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 (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3月版),第二冊,卷三十三《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端懿)墓志銘》,第490-493頁。
78、《長編》,卷八十一,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丁巳條,第1853頁;《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十之一》。
79、《長編》,卷八十二,大中祥符七年三月丁未條,第1868-1869頁。考真宗早在大中祥符五年二月因衛國長公主之請,已免卻在諸州河市物的諸雜差徭,這次重申諸雜差徭可免,路稅不可免。
80、《長編》,卷八十二,大中祥符七年三月癸醜條,第1870頁;四月丙子條,第1872頁;《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155-156頁;卷二百四十五《宗室傳二‧楚王元偁》,第8704頁。真宗在三月甲辰(十九)已往元偁宮視疾,是月癸醜(廿八)真宗以元偁病重而罷遊金明池。最後終於不治。元偁素來體弱多病,景德之後,每有大祀典,他都擔任終獻。他的幼子先他而逝,真宗怕他傷痛,吩咐他家人不要告訴他此事。他好學善文,奉佛尤其恭謹,性慈恕。他曾於僧舍齋集,從者失一金灌器,不久擒獲竊賊,元偁請輕判其罪,並將所失之金器布施給僧舍。他有集三卷、筆劄一卷。真宗特為之作序,藏於秘閣。
81、《長編》,卷八十二,大中祥符七年六月壬申、乙亥條,第1882-1883頁。考同月廿一日,樞密使王欽若因與副使馬知節(955—1019)相爭,得罪了真宗,被罷樞職。因王旦的力薦,王欽若的對頭寇準回朝出任樞密使。
82、真宗有二女,長惠國公主早亡,妙元是次女,生卒年均不詳。母為真宗賢妃杜氏,《皇宋十朝綱要》記她幼亡。她在真宗朝的封號不載。她在明道二年(1033)十一月追封衛國長公主,號清虛靈照大師。慶歷七年五月初七追封魯國長公主,謚昭懷。她很有可能在明道二年前已卒。徽宗改封升國大長公主。她的母親杜賢妃,是太祖昭憲杜太後(902—961)的侄女,侍真宗於藩邸。真宗嚴禁銷金,但杜氏違制,在真宗東封泰山後竟以盛服迎接,大大惹怒了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癸巳(十一),勒令她於洞真宮入道,她要求與諸公主同例,真宗沒有答應。後授法正都監,號悟真大師,名瓊真。她於明道二年十一月才晉位婕妤,到慶歷四年(1044)九月累遷婉儀,稍後晉賢妃。六年(1046)八月初一卒,贈貴妃。仁宗以太常禮院之議,詔罷輟朝舉哀,以明真大師朱賢妃例,用一品儀仗葬之。按《長編》此則記載出自宋人筆記《孔氏談苑》。參見孔平仲(?—1102後)撰,楊描倩、徐立群點校:《孔氏談苑》(與《丁晉公談錄》等合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6月版),卷三《杜婕妤出家》,第228頁;《長編》,卷七十二,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癸巳條,第1629頁;卷八十四,大中祥符八年正月乙未條,第1914頁;卷一百五十九,慶歷六年八月戊申朔條,第3843頁;卷一百六十,慶歷七年五月辛巳條,第3874頁;《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157頁;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 真宗升國大長公主》,第8776頁;《皇宋十朝綱要》,卷三《真宗》,《嬪妃七‧貴妃杜氏》,葉二上(第83頁);《公主二‧升國大長公主》,葉二下(第84頁)。
83、長編》,卷八十四,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丙寅條,第1918頁;《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158頁,卷二百四十五《宗室傳二‧漢王元佐》,第8694頁。考《長編》稱元佐“久病”,其實他只是稱病不願見同母弟真宗。從真宗即位開始,元佐已是退居府中不見外人。本來據唐及後唐的做法,拜天策上將軍的人都會開府置僚;但真宗考慮長兄的情況,就只加上將軍號而不開府,仍然將他的新官職加在功臣銜上。因元佐授興元府(今陜西漢中東)牧,制度上興元府的官屬一定要向這位名義上的長官致意,真宗不想長兄受到騷擾,就命王旦馬上派人傳旨興元府,要他們不要前來。
84、《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 158 頁;卷二百四十四《宗室傳一‧魏王廷美附德彜》,第8763頁;《宗室傳一‧燕王德昭附惟忠》,第8680頁;《長編》,卷八十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戊辰條,第1926頁。德彜是真宗叔父秦王廷美的第三子,字可久,比真宗年長一歲。他當時是秦王廷美一房最尊長的人。他卒後,真宗臨奠,另廢朝三日,贈昭信軍節度使,追封信都郡王,謚安簡。他本來續娶故樞密使王顯(932—1007)的孫女,他逝世前已納釆,而女尚未過門。惟忠是德昭第四子,字令德,初名文起,生年及得年多少不詳。真宗贈他鄂州觀察使,追封江夏侯。
85、《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158頁;卷二百四十五,宗室傳二‧周王元儼》,第8705頁;《長編》,卷八十四,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申條,第1927頁;五月辛巳至壬午條,第1928頁。
86、《長編》,卷八十五,大中祥符八年八月壬午條,第1943-1944頁。本來真宗任命內臣供備庫副使麥守恩(?—1022後)擔任此職務,但麥大概自知官小職低,擔當不了此任務,就請求以入內都知同管勾。於是真宗任命張景宗同管勾。
87、《長編》,卷八十六,大中祥符九年二月甲午至丙申條,第1973頁;卷八十七,大中祥符九年五月戊午條,第1991頁;卷八十八,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己酉條,第 2015 頁。考張士遜在是年九月初八獲委出使遼國擔任賀正旦使。
88、《長編》,卷八十七,大中祥符九年三月戊申條,第1975頁。
89、真宗優禮宗室,在是年五月初二又建皇親禮會院於新昌坊,賜名嘉慶。參見《長編》,卷八十七,大中祥符九年五月乙巳條,第1988頁。
90、《長編》,卷八十六,大中祥符九年四月乙酉條,第1982頁。
91、《湘山野錄》,卷下,第49-50頁;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第311-312頁;王素撰,儲玲玲整理:《文正王公遺事》,載戴建國主編:《全宋筆記》第一編第五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94頁;王鞏撰,戴建國整理:《聞見近錄》,載《全宋筆記》第二編第二冊(2006 年 1 月),第 17 頁;夷門君玉撰,楊描倩、徐立群點校:《國老談苑》(與《丁晉公談錄》合本)(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6月版),卷二《李遵勗尊楊億》,第71-72頁;黃啟江:《泗州大聖與松雪道人:宋元社會菁英的佛教信仰與佛教文化》(台北:台灣學生書店,2009年3月版),第二章第二節 北宋婦女佛教信仰與修行,第122頁。考《湘山野錄》所記的“蕭國大長主”當是“肅國”的字誤,並是“宿國”長公主同音訛寫,按北宋諸公主並無蕭國大長公主。被邀到李家東莊“靜淵莊”講佛的有谷隱、石霜和葉縣三大禪師,而公主就在東莊的松巒閣設箔以觀。關於北宋皇室公主信慕佛教,且表現相當虔誠的,黃啟江學長已在其專著指出荊國大長公主(宿國長公主)是代表人物,提及他們夫婦都好浮屠法,尤尚禪宗。又據《避暑錄話》,楊億曾為李遵勗的詩文集《閑燕集》作序。而據宋人筆記《國老談苑》所記,李遵勗“折節待士,宗楊億為文,於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伸函丈之禮,刻石為記”。關於楊億與李遵勗的交誼,可參見楊曾文:《宋元禪宗史》,第七章第五節 楊億與駙馬都尉李遵勗,第561-562頁。
92、《宋史》,卷四百六十四《外戚傳中‧ 李遵勗》,第13568頁;《長編》,卷九十,天禧元年十二月戊子條,第2090頁。考李遵勗在大中祥符五年以後的仕歷遷升具體年月不詳,他在天禧元年十二月前已遷至康州團練使,筆者懷疑他在天禧元年四月前已任左龍武軍將軍、宏州團練使,四月遷康州團練使。
93、《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160頁;卷二百四十四《宗室傳一‧ 秦王德王附惟憲》,第8686頁。惟憲是真宗從兄秦王德芳次子,他本傳稱他“美豐儀,少頗縱肆,善射,好吟詠,多讀道書”。似是兼通文武的人。
94、《長編》,卷八十七,大中祥符九年六月甲申、丁酉條,第1995頁、1997頁;七月庚戌至戊寅條,第1998-2003頁;八月己卯條,第2004頁;九月庚午條,第2020-2021頁。
95、《長編》,卷八十八,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庚戌至丁巳條,第2016-2017頁。
96、《長編》,卷八十八,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己酉條,第2015-2016頁;十月庚寅條,第2024頁。
97、《蔡襄集》,《蔡忠惠集》卷三十九《墓志銘二‧延安郡主李氏墓志銘》,第708頁。
98、《長編》,卷八十九,天禧元年正月辛醜朔至丙寅條,第 2036-2038 頁;《宋會要輯稿》,《禮五十一之十八》、《瑞異一之三十四》;《宋史》,卷二百四十四《宗室傳一‧燕王德昭附守節》,第 8679 頁。考守節是燕王德昭長孫、南陽郡王惟吉子。
99、《長編》,卷八十九,天禧元年二月戊寅條,第2041頁。
100、《長編》卷八十九,天禧元年四月壬辰條,第2057頁;卷九十,天禧元年十二月戊子條,第2090頁;《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宗室傳一‧魏王廷美附德雍德文》,第 8670 頁、8673頁、8674-8675頁;卷四百六十四《外戚傳中李遵勗》,第13568頁。考《長編》於天禧元年十二月戊子條下記李遵勗“先是以左龍武軍將軍、宏州團練使為康州團練使,給觀察使俸料、公使錢”。又記當時李繼昌為左神武大將軍、獎州刺史、權判右金吾街仗司。相信李繼昌父子在這次加恩後即分別獲獎州刺史和康州團練使的加官。又真宗在四月廿四日,特賜宗室蔡州團練使德雍、汝州團練使德文(975—1046)及唐州團練使惟正公用錢各百萬。德雍與德文是秦王廷美的第四子和第八子。
101、《長編》,卷八十九,天禧元年五月戊申條,第2059-2060頁;卷九十,天禧元年七月甲寅至甲子條,第2073-2074頁;八月庚午條,第 2075 頁;九月己酉條,第 2080 頁;《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 163 頁。魏鹹信本來出判大名府,後來得疾被召還,真宗曾在天禧元年七月廿三日往其第省視,五天後魏便病卒。真宗曾對王旦等說,魏鹹信諸子不能承順,他死後魏家必定不睦。又王旦罷相後,王欽若在八月初五繼為首相。王旦則在九月十四日病逝。
102、《長編》,卷九十,天禧元年十月甲申條,第2084頁。
103、《長編》,卷九十,天禧元年十二年戊子條,第2090頁;《宋史》,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太宗荊國大長公主》,第8774頁;卷二百五十七《李崇矩附李繼昌傳》,第8956頁。考宿國長公主的確實誕辰日在十二月哪天不詳,從李繼昌在十二月廿四日獲得知涇州的任命來看,她的誕辰應在十二月中旬以後。
104、《宋史》,卷二百四十八《公主傳‧ 太宗徐國大長公主、荊國大長公主》,第8773-8774頁;《長編》,卷一百七十,皇祐三年三月丙子條,第4086頁。
105、《長編》,卷九十一,天禧二年正月乙未至辛亥條,第2096-2097頁;《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164頁。考《宋史‧真宗紀》稱所謂芝草在正月初一生於真遊殿,大概要等到劉皇後的崇徽殿也生芝草,王欽若才將祥瑞奏報。
106、《長編》,卷九十一,天禧二年二月丁卯至庚午條,第2098-2099頁。按真宗以升州為江寧府,置軍曰建康,然後授仁宗以建康軍節度使加太保而封升王。
107、據《宋史‧真宗紀》所載,真宗在天禧二年二月廿一,即德雍宮火後十七天已往元偓宮視疾。到閏四月二十,真宗再幸元偓宮視疾。但十二天後元偓終不治。據群書所記,元偓字希道,姿貌偉異,沈厚寡言,樂善多藝而知音律。唯據司馬光引述楊畋(1007—1062)的說法,元偓原是太祖的遺腹子,後為太宗收養為己子,並不是真宗的親兄弟。參見《長編》,卷九十二,天禧二年五月甲子條,第2115-2116頁;《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164-165頁;卷二百四十五《宗室傳二‧鎮王元偓》,第8702-8703頁;《涑水記聞》,卷二《蘇王元偓》,第36頁。
108、《長編》,卷九十二,天禧二年六月己未條,第2119頁;《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外戚傳上‧劉美》,第3548頁。
109、《長編》,卷九十二,天禧二年八月丁酉至九月丁卯條,第2121-2125頁;十月壬寅條,第2127頁;《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165-166頁;卷二百四十五《宗室傳二‧漢王元佐附允升、允成》、《宗室傳二‧商王元份附允寧》,第8694-8697頁、第8699頁。按輩分次高的三位宗室德雍、德文及惟正並授諸州防禦使,低一輩的允升(?—1034)、允成(?—1025)及允寧(?—1034)並授諸州團練使。考允升與升成分別是真宗兄元佐之長子和三子,允寧則是真宗四弟元份之長子。真宗冊立太子之禮儀極之隆重,他在八月十六以翰林學士晁迥(951—1034)為冊立皇太子禮儀使,命與李遵勗夫婦交厚的秘書監楊億撰皇太子冊文,以知制誥盛度(970—1040)書冊,陳堯咨(970—1034)書寶。真宗又在同月廿一任命一大批輔佐太子的宮僚:右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樂黃目為給事中兼太子左庶子;升王府諮議參軍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為右諫議大夫兼右庶子;禮部郎中直史館崔遵度為吏部郎中直史館兼左諭德;記室參軍左正言直史館晏殊兼舍人;右正言魯宗道(966—1029)為戶部郎中兼右諭德;玉清昭應宮暨資善堂都監入內押班周懷政為入內副都知兼管句左右春坊事。另外,真宗又委他賞識的參知政事李迪(971— 1041)兼太子賓客。到是年十月十四,真宗又召寇準女婿、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曙(963—1034)還朝,加給事中兼太子賓客,與李迪輔助太子。
110、《歐陽修全集》,第二冊,卷三十三《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端懿)墓志銘》,第491頁;楊傑(?—1090後):《無為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祝先生詩集序》,葉一上至二上。據楊傑的記載,李遵勗曾禮聘名士祝熙載為門館先生,教導李端懿及李端願兄弟,後來他們都被稱為賢公子。
111、李端願是長公主次子,因他的墓志銘不傳,故生年不詳。他字公謹,以母親特恩,和兄長一樣七歲便授如京副使。按長公主生李端懿時年二十六歲,筆者相信公主育他時不應超過三十歲,故他不會與兄長的年齡差距太遠。是故他年幼時,很有可能也隨兄長入宮陪伴仁宗,為此他也得到仁宗特別的恩待。參見《宋史》,卷四百六十四《外戚傳中‧李遵勗附李端懿、李端願傳》,第13569-13571頁。
112、《長編》,卷九十三,天禧三年三月辛酉條,第 2138 頁;《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崇矩傳附李繼昌》,第8956頁;卷四百六十四《外戚傳中‧李遵勗》,第13568頁。考李繼昌當於天禧三年二月底發病,而卒於三月初。《宋史‧李繼昌傳》記李繼昌在天禧“二年冬,卒,年七十二”。參以《長編》所記,李繼昌卒於天禧二年冬之記疑有誤。
113、《長編》,卷九十三,天禧三年四月己亥條,第2144頁;五月己未條,第2145頁;《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外戚傳上‧劉美》,第13548-13549頁;王稱(?—1200後),《東都事略》,收入《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1月版),卷一百十九《外戚傳‧劉美》,葉三上下;魏泰(1050—1110)撰,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 1983年10月版),卷十五,第168-169頁;沈括(1031—1095)撰,胡道靜校註:《新校正夢溪筆談》(香港:中華書局,1975年1月版),卷九,第106頁;據《東都事略》及宋人筆記所載,劉美原名龔美,原職銀匠,是劉皇後前夫,曾為翰林學士錢惟演(977—1034)打造銀器。真宗為太子時納劉後於府中,就讓劉後認劉美為兄長,視為心腹而無間。駙馬都尉石保吉在陳州大治廨舍,修築城壁,並不上奏,他的僮奴輩又假威擾民,給人向真宗告狀,真宗疑石有別情,就派官職只是右侍禁的自京至陳、潁州(今安徽阜陽)巡檢的劉美前往查察。劉美回奏石保吉“世受國恩,擁高貲,列藩閫,營繕過度,拙於檢下,誠或有之,自余保無他患”。於是真宗釋疑。劉美後來步步高升,在大中祥符二年護屯兵於漢州(今四川德陽廣漢),徙嘉州(今四川樂山),又累授各種差遣,並任勾當皇城司,真宗寄以心腹之任。據說真宗屢次委以兵柄,執掌禁軍,以劉皇後懇辭多番而罷,到了天禧三年終於委他出掌禁軍。
114、《長編》,卷九十三,天禧三年六月甲午條,第2149-2150頁;六月戊戌條,第2152頁。按當時首相是寇準的同年好友向敏中。
115、長清郡主在太宗淳化四年(993)三月適太宗朝馬步軍都虞候名將田重進(929—997)之子莊宅使田守信,長公主為其從姊。參見《長編》,卷三十四,淳化四年三月壬子條,第 748 頁;卷九十三,天禧三年六月甲寅條,第2154頁。
116、《長編》,卷九十四,天禧三年十一月辛未條,第2171頁;十二月辛卯至癸巳條,第2173-2174頁;卷九十五,天禧四年正月乙醜條,第2178頁;《歐陽修全集》,第二冊,卷三十三《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端懿)墓志銘》,第491頁。
117、《長編》,卷九十五,天禧四年正月己巳條,第2178頁;三月己卯條,第2186頁;卷九十六,天禧四年九月丙辰條,第 2215 頁;《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168頁。考《長編》記真宗“自中春不豫”,與《宋史‧真宗紀三》所記“二月不豫”吻合。
118、《長編》,卷九十五,天禧四年四月庚寅條,第2187頁。
119、劉美的妻子是錢惟演妹,故錢惟演是劉皇後的姻家。寇準覆相後,一直主張嚴懲劉皇後家人不法者,他請真宗以太子監國,就是要削弱劉皇後的影響力,是故劉皇後要除去寇準。參見《長編》,卷九十五,天禧四年六月丙申條,第2196-2198頁;卷九十六,天禧四年七月辛酉至癸亥條,第2205-2206頁。
120、《長編》,卷九十六,天禧四年七月癸亥至八月癸卯條,第2205-2212頁。據說李迪從容對真宗說:“陛下有幾子,乃為此計。”真宗於是覺悟,沒有再生廢太子之念。宋人認為仁宗得以保存,賴李迪保護之力居多。
121、魏泰(1050—1110)撰,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0月版),卷三,第26頁。
122、《蔡襄集》,卷三十九《墓志銘二‧延安郡主李氏墓志銘》,第708頁。
123、《長編》,卷九十六,天禧四年九月丙辰條,第2215-2216頁;九月庚午條,第2218頁;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十九冊,卷四零二《釋則全‧四明法智尊者實錄》,第324-326頁。按《釋則全》未有記載李遵勗在天禧四年哪一月向真宗陳奏,相信是在九月後真宗病體稍康覆時。據釋知禮(金知禮)的一封謝李遵勗的書啟所記:“正月一日,本州送到敕牒一道,鈞銜一通,蒙恩授知禮法智大師者。”大概李遵勗在天禧四年九月、十月間請真宗賜釋知禮大師號,到天禧五年正月十日敕命送抵明州(今浙江寧波),釋知禮即致書李遵勗致謝。在書啟中釋知禮稱許李遵勗“戎韜穎達,義府淵遊,妙窮西竺之言,密契南宗之意。雅合宸鑒,特秀人文,髦士鹹歸,方來所則,俟光垂統,用葉具瞻”。他又在另一通書啟中讚揚李遵勗“國紀人望,神清鑒明”。金知禮的生平見趙抃所撰的行業碑。趙抃在碑中也記載了李遵勗和楊億為他薦服號之事。金知禮卒於天聖六年正月五日,年六十九。參見《全宋文》,第九冊,卷一七四《釋知禮五》、《謝李駙馬啟》、《謝李駙馬請住世書》,第 12-13 頁;第四十一冊,卷八八九《趙抃八》、《宋故明州延慶寺法智大師行業碑·元豐三年十月》,第286-288頁。
124、《長編》,卷九十六,天禧四年十月壬午條,第2219頁。
125、周起和曹瑋被指為寇準黨,早在九月十一已雙雙被罷樞並逐出朝廷。參見《長編》,卷九十六,天禧四年九月己未條,第2216頁;十一月乙醜至十二月乙酉條,第2222-2228頁;《隆平集校證》,卷九《李崇矩傳附李遵勗》,第280頁;《東軒筆錄》,卷三,第26頁。又朱熹(1130—1200)所編的《五朝名臣言行錄》有關寇準一節,在正文也采用《東軒筆錄》的說法,稱楊億臨終時將有關文件交予李遵勗收藏,而在註文附《龍川別志》之異說。參見朱熹編,李偉國點校:《八朝名臣言行錄》,《五朝名臣言行錄》,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十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版),卷四之二《丞相萊公寇忠湣準》,第121-122頁。
126、《長編》,卷九十六,天禧四年閏十二月乙亥條,第2232-2233頁。
127、《長編》,卷九十七,天禧五年正月丁醜朔至癸亥條,第2239-2240頁;《宋史》,卷八《真宗紀三》,第170頁。
128、《長編》,卷九十七,天禧五年二月丁未、丙辰條,第2241頁;二月癸酉至三月壬寅條,第2243-2244頁。
129、《長編》,卷九十七,天禧五年四月丁未條,第2245頁;十月戊申條,第2255-2256頁。考雷允恭與另一內臣劉從願(?—1048)有份揭發周懷政偽造天書,以此打倒寇準之事有功,得以擢為內殿崇班。雷、劉二人顯然是劉皇後的黨羽。雷允恭在是年十月戊申(初六),以造祥源觀落成有功,再加內殿承制。
130、《長編》,卷九十八,乾興元年二月甲寅條,第2270頁。
131、《長編》,卷九十七,天禧五年四月戊午至五月癸未條,第2246頁;七月丙子條,第2249頁。
132、《長編》,卷九十七,天禧五年八月戊申至辛酉條,第2251-2252頁。
133、《長編》,卷九十七,天禧五年十月壬子至十一月戊子條,第2256-2257頁。
134、《長編》,卷九十八,乾興元年正月辛未朔至二月戊午條,第2268-2271頁。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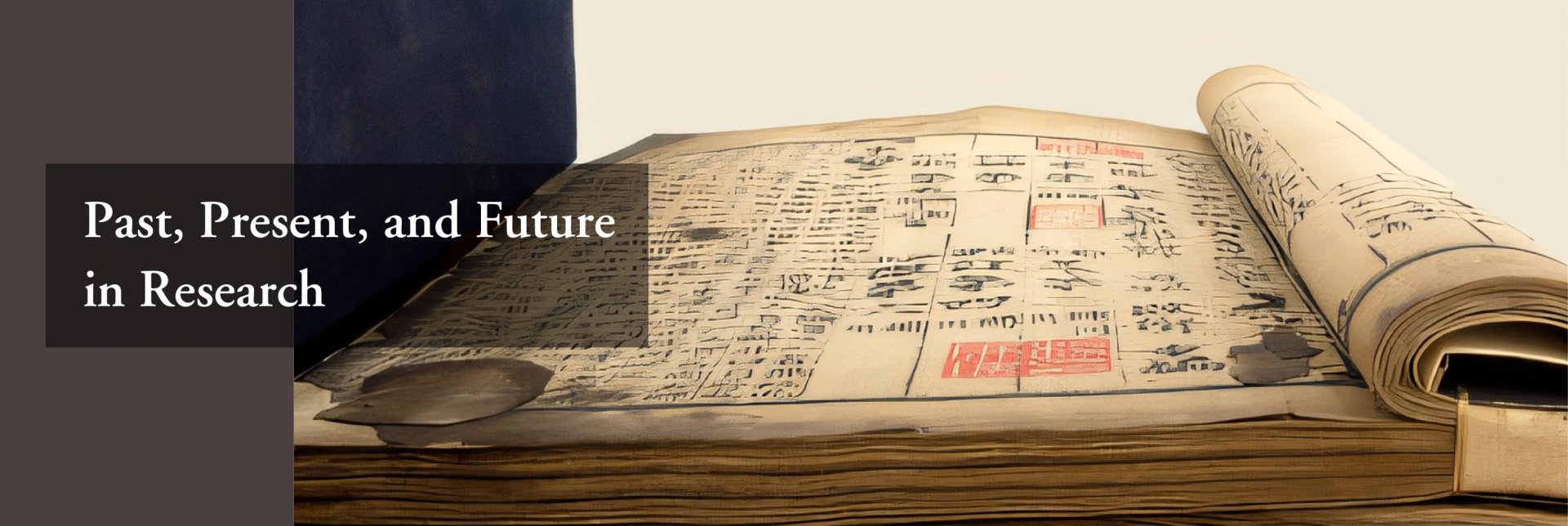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