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公主之楷模:
李遵勗妻獻穆大長公主(下)
獻穆大長公主一直為宋人譽為公主的模楷。她在真宗至仁宗朝,特別是仁宗朝,雖居於宮外,但對宮闈的影響力,卻未可忽視。當夫婿李遵勗卷入以寇準、楊億為首的朝臣與真宗劉皇後的權力鬥爭而失敗時,獻穆大長公主即憑尊貴的地位及其高明的政治手腕,既保護了夫婿一族,又保護了身處險境的侄兒仁宗。仁宗親政後,李遵勗夫妻深受仁宗尊禮,他們夫妻知禮守法,深受朝野敬重,而仁宗與公主姑侄親情深厚,愛屋及烏之下,也對姑姑的親生兒子、他的親表弟李端懿、李端願兄弟另眼相看。公主以高壽過世後,仁宗對李家的恩寵不替,而李氏後人到英宗及神宗之世,仍是深受寵信的外戚。本文上接《華中國學》第二卷所載,續完全篇。
乾興元年(1022)二月二十日,宋廷以仁宗繼位大赦天下,詔百官皆進官一等,涇王元儼及諸皇親優加恩命。二十七日,仁宗的伯父楚王元佐加兼江陵牧,叔父涇王元儼加太尉、中書令兼尚書令,進封定王,充鎮安、忠武節度使,賜讚拜不名。仁宗尚健在的三位姑娘,在三月初五進大長公主:福國長公主進位鄧國大長公主,建國長公主進申國大長公主,長公主自鄂國長公主進位冀國大長公主。宋廷又相應地將鄧、申、冀都升為大國。而大長公主之夫婿李遵勗大概也在這次加恩遷澤州防禦使。1
大長公主是年三十四歲,《宋大詔令集》收有她進位冀國大長公主的制文,制曰:
門下。王者敦自近之教,式於萬邦,宣廣愛之風,親於九族。粵以涼德,昭茲慶圖。服寶訓之惟明,湛至和而無外,乃眷宗屬,首覃茂恩,率循典章,誕告徽命。鄂國長公主,漢闈挺秀,軒曜分華。中禮法於天資,盛言容於閫範。文祖啟運,□事親之孝恭;先聖禦期,應歸妹之元吉。湯沐開賦,珩璜展儀,善循四戒之文,用集六姻之慶。永言治麻,實荷重□。協於剛近之辰,霈此褒嘉之數。進美名於尊顯,易大國之建封。於戲儀服之榮,蓋侔於藩戚;肅雍之道,可厚於人倫,無忘令猷,式保隆懿。可特進封冀國大長公主。2
從乾興元年二月至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獻劉太後一直牢牢掌握大權。因為李遵勗在真宗晚年曾協助寇準、楊億等反對劉太後,所以在這十二年中他們夫婦像涇王元儼一樣韜光養晦,免招劉太後猜忌。據《長編》及《宋史》所記,元儼知道自己“屬尊望重,恐為太後所忌,深自晦密,因![]() 門卻絕人事,不覆預朝謁,或故謬語,陽為狂疾不慧。”3而李遵勗就以編纂佛典《天聖廣燈錄》之大功德,向劉太後宣示他與人為善的態度。不過,李遵勗夫婦也深諳劉太後手段厲害,也適度地接受劉太後的拉攏,沒有擺出拒人於千裏的態度。他們夫婦與劉太後的關系是若即若離,不太親近也不太疏離。正如上一節提到,大長公主還接受劉太後的撮合,讓她的長女延安郡主下嫁錢惟演的次子錢晦。為此,劉太後在晚年還頗信任他們夫婦,在還政仁宗的事上詢問他們的意見。
門卻絕人事,不覆預朝謁,或故謬語,陽為狂疾不慧。”3而李遵勗就以編纂佛典《天聖廣燈錄》之大功德,向劉太後宣示他與人為善的態度。不過,李遵勗夫婦也深諳劉太後手段厲害,也適度地接受劉太後的拉攏,沒有擺出拒人於千裏的態度。他們夫婦與劉太後的關系是若即若離,不太親近也不太疏離。正如上一節提到,大長公主還接受劉太後的撮合,讓她的長女延安郡主下嫁錢惟演的次子錢晦。為此,劉太後在晚年還頗信任他們夫婦,在還政仁宗的事上詢問他們的意見。
劉太後在權力尚未完全鞏固前,對諸皇親均加以籠絡,據載命婦本來都服發髻進見她的,當大長公主與姊姊鄧國大長公主及入見時,劉太後即說“姑老矣”。特命左右賜二大長公主以珍珠錯羅巾縚之,又賜金龍小冠。但大長公主辭不受。劉太後後來再在另一次晉見堅持賜給小姑金龍小冠。大長公主推辭不了,但在誕節及太後及仁宗的上壽,她仍以發髻入見,不穿戴太後所賜的冠。劉太後每每以政事問大長公主的意見,她就機警地只多語及祖宗舊事以諷喻之,而不提出任何意見。劉太後又請她幫助教導六宮,她卻回答說:“吾無德,曷足稱是哉?”聰明地婉拒劉太後半真半假的請求。4大長公主也像兄長元儼一樣,行事小心謹慎,對宮中朝中之事一概不問,免招劉太後之忌。好像劉太後在是年四月開始,給她的家人姻親加官晉爵,大長公主就沒有表示任何意見。5不過,大長公主對宮中發生的事,其實應當心中有數。值得註意的是,司馬光《涑水記聞》曾收錄有來自她次子李端願所述的兩則劉太後攝政後的宮闈秘辛,一則關乎仁宗生母李宸妃之死,一則有關仁宗與劉太後與楊太後的關系。6據此可以推論李端願所知宋宮秘辛當在不少,而大長公主透過兒子自然也會了解宮中狀況。
是年(1022)六月二十二,劉太後顯示她厲害的手段,她利用參政王曾與丁謂的矛盾,接受王曾對丁謂的指控,以丁在營造真宗山陵事上包庇督工內臣雷允恭的罪過,將他重貶崖州(今海南三亞),至於本來是她的走狗的雷允恭也毫不手軟地誅殺。本來是丁謂一夥的馮拯、曹利用,卻各懷鬼胎,對丁來個落井下石。而劉太後的心腹錢惟演,自然秉命行事。劉太後重貶丁謂一黨,以王曾為首的主流朝臣,一方面大快人心,另一方面也讓人認識到這位攝政女主的手段。7劉太後雖然借打倒丁謂而進一步鞏固權力,但礙於王曾等大臣的壓力,她在八月初八與仁宗一同禦承明殿垂簾聽政時,仍令內侍宣諭群臣:“候上春秋長,即當還政。”這當然不是她的本意。群臣得勢不饒人,同年十一月初一,就迫劉太後罷免錢惟演樞使職位。劉太後無奈,只好依從。8
劉太後在翌年(1023)正月初一改元天聖。劉太後因無法讓錢惟演回朝,趁著馮拯有病,就不動聲色地安排當年支持她為皇後的王欽若回朝為相。九月初五,劉太後就以王為首相,代替罷相的馮拯。9十二月十七,劉太後下詔駙馬都尉自今不得與清要權勢官私第往還,仍令禦史台察視之。10按當時健在的駙馬都尉只有王貽永(原名王貽貞,避仁宗諱改)、柴宗慶和李遵勗三人,王貽永出守洺州,在京的唯有柴、李二人,這道詔書針對的究竟是何人?實在耐人尋味。劉太後也許有敲山震虎,警告二人需順從她之意。據楊曾文的研究,李遵勗在天聖年間,潛心編寫佛學名著《天聖廣燈錄》,他除了與翰林學士劉筠(971—1031)繼續交往外,又交結佛門大德如蘊聰(965—1032),後來在天聖四年(1026)還迎他來京師。李還與禪門同道如京畿東路水陸發運使朱正辭、淮南轉運使許式交換偈文,多有來往。而天聖元年狀元宋庠(997—1066)及其弟宋祁(998—1061)與李遵勗均有詩文往還,也許在劉太後眼中,這已是與“清要權勢官私第往還”。11
天聖二年(1024)三月十六,王欽若等上《真宗實錄》一百五十卷,仁宗與劉太後設香案,閱視涕泣。並賜王欽若等坐,勞問良久,又賜宴於編修院,降詔褒諭編修官員。12《真宗實錄》的修成,自然觸動了仁宗及真宗親人的心靈。不幸的是,五月十一日,大長公主的七姊、出家的申國大長公主病篤,仁宗親幸資聖禪院視疾,未幾,申國大長公主卒。仁宗再臨奠,因申國大長公主之喪在真宗禫期,仁宗依制不制服,但仍廢五日朝,謚公主曰“慈明”。大長公主繼喪兄後,又喪同樣篤信佛教的七姊。13
劉太後在九月十五日為仁宗選定以五代名藩郭崇(908—965)的孫女郭氏(1012—1035)為皇後。劉太後所以選中家門已衰落的郭氏為仁宗後,正如她所說:“玆選於衰舊之門,庶免他日或擾聖政也。”她用心很清楚,郭皇後家道已中落,容易為她所控制;而她自己出身寒微,找一戶已破落的家門為後,她心中也好過。本來仁宗喜歡與郭皇後同入宮的張氏(?—1028),然劉太後仍依己意選中郭皇後。值得註意的是,就在決定冊立郭皇後後三天(五月十八),劉太後又派給仁宗生母李氏弟李用和(989—1050)一份優差,命他以供奉官![]() 門祗候任每年一度的契丹主生辰副使。14劉太後心中一根刺,就是仁宗非其所出。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只是沒有人敢向仁宗透露。善待仁宗生母的兄弟,相信是劉太後的另一手準備。十一月廿一,仁宗正式冊立郭後,廿七日,自王欽若以下輔臣均遷官。15仁宗大婚,作為至親的楚王元佐、涇王元儼、鄧國大長公主、冀國大長公主,以及王貽永、柴宗慶、李遵勗三駙馬,依禮自然親臨大典。而大長公主的兒女,也當會隨同父母參與其表兄的大婚慶典。
門祗候任每年一度的契丹主生辰副使。14劉太後心中一根刺,就是仁宗非其所出。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只是沒有人敢向仁宗透露。善待仁宗生母的兄弟,相信是劉太後的另一手準備。十一月廿一,仁宗正式冊立郭後,廿七日,自王欽若以下輔臣均遷官。15仁宗大婚,作為至親的楚王元佐、涇王元儼、鄧國大長公主、冀國大長公主,以及王貽永、柴宗慶、李遵勗三駙馬,依禮自然親臨大典。而大長公主的兒女,也當會隨同父母參與其表兄的大婚慶典。
天聖三年(1025)正月,劉太後一方面加贈郭皇後三代官職,另一方面又給劉美夫婦再加贈美官。16最重要的是,不次提拔她的族人及姻親出任要職。王欽若最能秉承她的意旨行事,有些近戚如明德李皇後的侄兒、東上閤門使李昭慶(993—1063),還曲意奉迎她,將名字改為李昭亮,以避劉太後祖父劉延慶之諱。本來她只令群臣避她父劉通之諱,然拍馬奉迎的外戚多的是。17
五月二十日,仁宗的從兄、楚王元佐第三子濮州防禦使允成(?—1025)卒。劉太後以仁宗的名義,除了贈允成安化節度使,追封鄒國公外,又為了籠絡元佐,兩天後(五月廿二),以允成長兄齊州防禦使允升為澶州觀察使,封延安郡公。18允成之逝,對劉太後可說無足輕重;不過,首相王欽若在十一月三十日病逝,對劉太後專權卻有相當的影響,因繼任首相的王曾和次相張知白(956—1028)都是耿直之人,可不像王欽若那樣事事迎合她。19好像在天聖四年(1026)正月廿六日,王曾便反對授柴宗慶為使相,向仁宗指出在真宗朝駙馬石保吉和魏鹹信皆經歷行陣,到晚年才授使相。柴宗慶有何功勞可得此位。王曾且指將相之任,豈容私請?仁宗接受王曾的意見,命他召柴到中書曉諭一番。20究竟柴駙馬爺向誰私請?顯然他夫婦走了劉太後或其代理人的門路,劉太後大概借此向鄧國大長公主示好,就要仁宗照辦;但王曾不買賬,劉太後也無可奈何。
劉太後也以聯姻的手法拉攏大長公主。相信是她的牽合,在天聖四年二月十二,錢惟演的次子錢晦娶大長公主的長女、年已十七的延安郡主為妻。當時判許州的保大節度使錢惟演,就奏請將錢晦由文階的大理評事轉升為武階大使臣的內殿承制。劉太後和仁宗自然允其奏。21李遵勗夫婦為什麽肯答應這樁婚事?一方面可能錢晦人品不差,22另一方面錢氏也算得上是門當戶對。當然,劉太後的撮合也是重要因素。大長公主人情練達,自然沒有理由推卻這樁帶有政治味道的親事,而與劉太後過不去。值得一提的是,劉太後也以聯姻的方法拉攏大長公主的兄長定王元儼。在她的牽合下,元儼的三子允迪也娶錢惟演女。23
延安郡主在翌年(天聖五年,1027)初正式下嫁錢晦,仁宗加封與他同齡,自小一同長大的小表妹為長壽縣君。然而這宗大喜事過了不久,大長公主的長兄、宗親中地位最尊的楚王元佐卻在是年五月廿四日病逝。劉太後在楚王病重時,親到楚王第視疾。仁宗也隨即往臨奠,並輟視朝五日。仁宗優贈伯父河中、鳳翔牧,追封齊王,謚恭憲。又詔宗室子弟特給假七日,以鹵簿鼓吹導引至永安,陪葬太宗永熙陵。24大長公主自然出席兄長的葬禮,這時她的至親尚在的,只剩下八兄定王元儼與四姊鄧國大長公主。這年十二月初五,宋廷以合祭天地於圜丘的大典,除大赦天下外,又加恩百官。皇親中最尊的定王元儼賜詔書不名,而李遵勗大概在這時進位宣州觀察使。25
天聖六年(1028)二月初六,發生了一宗外戚子弟與宗室子鬥毆的鬧劇。太祖長婿王承衍的兒子內園副使王世融(?—1028後),與其婿東頭供奉官承詡(按:承詡是秦王廷美孫,仁宗從叔德鈞子,屬仁宗再從兄弟)翁婿失和。王世融托其妻有病,奏請劉太後,請承詡過其家,然後借酒,與他二子一同毆打不肖的女婿。法寺以世融上奏所言不實,請追其官勒停。劉太後和仁宗特寬世融之罪,只將他降為內殿承制、監虢州(今河南靈寶)稅。26
同為外戚,李遵勗便守法知禮得多。這年四月初七,他終於獲得出守外郡的機會,宋廷以他自宣州觀察使出知重鎮澶州。劉太後與仁宗在長春殿置酒為他餞行,大長公主自然參加餞行宴,她的兒女尚幼,大概沒有隨夫婿前往澶州。舊制觀察使辭行,皇帝不置酒款待,劉太後破例以此特恩以寵遇李遵勗,相信亦是籠絡他們夫婦的手段。順便一提,李遵勗的好友翰林學士承旨劉筠,也在四個月後離開朝廷出知廬州(今安徽合肥)。27劉太後有機會便擢拔她的親戚,這年六月廿四日,她趁著王曾病告,不在中書時,就迫張士遜等同意破格地將馬季良從太常丞直史館擢為龍圖閣待制,由三丞逕授侍從,引起朝論嘩然。史稱劉太後於政事有所訪逮於大長公主,據載大長公主“多語祖宗舊事以諷”。我們不知道這次劉太後有否像天聖六年召問李遵勗一樣,向大長公主打探朝臣反應。②值得我們註意的是,大長公主的長子李端懿這年已十六歲,據他的墓志銘所記,當他“稍長,出入宮禁,禮如家人。雖燕見,語不及私,數為上陳朝廷闕失,開說古今治亂,多所補益,退而未嘗言。”28歐陽修雖然沒有具體說明李端懿在什麽環境和年月出入宮禁,但筆者相信他在十六歲甚至更早的時候,已經時常出入宮禁進見仁宗。而大長公主當會透過兒子了解仁宗的情況;而也會叮嚀兒子找機會“語不及私”地告訴侄兒宮外的狀況。李端懿“退而未嘗言”,顯然大長公主從小就教導兒子不可泄禁中語。至於下嫁錢晦的延安郡主,也甚有母風,據載她“恭謹持禮,承舅姑,奉祭祀,夙暮不少懈。姻親娣姒,降屈色詞,以相接親疏意。於是諸錢內外悉稱主賢”。她的表現也讓劉太後對大長公主多一點敬重而肯向她諮訪政事。29
九月廿二日,仁宗原本屬意的張才人病重,劉太後就將她晉為美人,張美人在五天後病逝,對仁宗自是一番打擊。劉太後以加張氏名位來安撫仁宗後,又在十月初七,加封她的心腹林氏為蔣國夫人。30
對於逆她旨意的人,哪管是曾經做過她“鷹犬”的,劉太後也不放過。好像在天聖七年(1029)正月十三,她便用極狠辣的手段將樞密使曹利用罷免,然後再在同月丙辰(廿六)將他貶知隨州,更在閏二月初二,授意押送的內臣楊懷敏將曹謀殺於路上。凡是與曹利用親近的人都遭清洗。31這年六月二十,因大雷雨引起玉清昭應宮大火,只剩下長生殿及崇壽殿。首相王曾在二天後引咎請罷,劉太後早就嫌他阻礙她任用姻家近臣,以及她逾制的做法,自然準奏,將王曾罷知青州。32
劉太後在是年九月初三,又改封定王元儼為鎮王,安撫宗室最尊的人。她卻未想到在她淫威之下,仍有小臣秘閣校理範仲淹(989—1052)在同年十一月初九冬至時,上書批評她讓仁宗率百官向她上壽於會慶殿,乃失禮之事。範仲淹後來還上奏請她還政於年已二十的仁宗。33劉太後當然不理範仲淹的奏章,她繼續拔擢她的姻親,貶責逆她旨意的人。好像在天聖八年(1030)四月十二,她便將秉公處置其姻親馬崇正的京西轉運使王彬調職,又在同月廿九召不得人心的錢惟演來朝。到六月廿三又賜劉美的長子、和州刺史劉從德敕書獎諭,並且擢用劉從德的屬吏官職。九月十九日,樞密直學士趙稹(963—1038)因厚結劉美府中一個能出入禁中的家婢,而得到劉太後擢為樞密副使,替補四天前死去的姜遵(963—1030)遺缺。34不過,這年十一月初六,劉太後卻重貶舒王元偁的女婿,仁宗東宮親信的西上閤門副使、勾當翰林司郭承祐(993—1051),將他除名配岳州(今湖南岳陽)衙前編管,其父比部員外郎郭世隆也受坐勒停。郭承祐父子自然有罪,然劉太後將其重責,也多少有警告擁護仁宗的人的意思。35
宋廷的文臣,特別是言官並不完全順從劉太後。天聖九年(1031)正月廿三,在眾言官的彈奏下,劉太後只好將一直借故留在京師不肯赴陳州之任的錢惟演改判河南府,並以加他的兄弟官予以補償。這年九月,權知開封府程琳(988—1056)也不屈於劉太後的幹預,堅持懲治她的姻家王蒙正子王齊雄殺人之罪。36不過,劉太後最受打擊的,卻是她視如己出、年僅廿四的劉從德,在是年十一月廿二病卒於自相州返京的道上。劉太後對從德夭亡悲憐尤甚,只能以錄用劉從德的內外姻戚、門人以至僮隸近八十人作為補償。其中劉從德的姊夫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其表兄集賢校理錢曖(?—1046 後)及妻父王蒙正皆各因劉從德的遺奏得遷兩官。劉太後濫封劉氏姻親官爵,引來言官侍禦史曹修古(?—1033)、殿中侍禦史郭勸(981—1052)、楊偕(980—1049)、推直官段少連(994—1039)的抗議,他們交章論列。劉太後哀痛之余,大發雷霆,下旨呂夷簡將曹修古等重貶。37然而已越來越多朝臣敢於與已步入晚年的劉太後抗爭。
天聖十年(1032)二月廿六,仁宗生母順容李氏卒,年四十六。令劉太後苦惱至極的問題是,應該如何處置李氏的喪事?劉太後在李氏病重的一天才將她晉為宸妃,她本來不想人知道(特別是仁宗),這個在真宗留下的嬪禦中默默無聞的李氏的身世。起初劉太後沒有為李氏治喪,沒想到首相呂夷簡入朝奏事後,在仁宗在場下忽然說“聞有宮嬪亡者”。劉太後將仁宗拉回宮中後,再單獨回來見呂夷簡,責他想離間她母子乎?經呂夷簡痛陳利害,劉太後明白終有一天仁宗會知道真相,於是改變態度,將李氏以皇後之禮殯葬,而且稍後又將李氏弟李用和升官。38
關於李宸妃之喪,司馬光《涑水記聞》引述了大長公主次子李端願的一則說法,批評起初劉太後將李宸妃棺槨鑿垣而出,而瘞於洪福寺,實在不妥。此條資料反映大長公主一家對李宸妃死事之始末相當清楚。說不定是李端願奉母命告訴呂夷簡的。39
這年三月十一日,尚身在澶州的李遵勗尊為師的大德慈照禪師(蘊聰)病卒,李特為他撰塔銘以述其生平。他在這篇塔銘中,憶述已故去的楊億和劉筠“不我暇棄,為方外之交”,又言及他著手撰述後來賜名《天聖廣燈錄》之佛典。李遵勗在澶州,並非一味寄情方外,亦頗有政績。有一次遇上河溢,浮橋將於毀壞,他就督工徒,花了七日建好河堤,保護了州城。另外,他曾經奏上三說五事以論事政。40
同年十一月初六,仁宗改元明道,循例大赦天下,百官進一等。十五日,宰相呂夷簡以下加官外,劉太後又給宗王公主加恩:鎮王元儼拜河陽三城、武城節度使守太師徙封孟王。十七日,鄧國大長公主進封楚國,大長公主自冀國大長公主進封魏國大長公主。廿三日,元儼又徙封荊王,為永興、鳳翔節度使。十二月初九,又追封秦國賢肅長公主為大長公主。李遵勗大概也在這時遷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並且召回京師。據《宋會要》所載,“明道以後,累增獻穆大長公主俸月至千緡,後遂著例雲。”這又是劉太後及仁宗加給大長公主的特恩。41考《宋大詔令集》亦收有她晉位魏國大長公主一道稱揚備至之制命:
王姬有行,成周隆車服之飾;帝女下嫁,西漢疏湯沐之封。永言貴主之賢,蓋有諸姑之重;禮將嚴於築館,義敢後於進邦。敷告治廷,肆颺讚冊。冀國大長公主,柔明早就,婉懿自持。實先帝同氣之親,膺東朝少女之愛,而能問圖史之誡,佩箴管之儀,將從合好之行,以侈宜家之吉。選勳門之裔,得汾陽之善逑。賦連上之膄,荒大名之遐服。如月幾望,在釣惟緡。愛自中流,化由近始。於戲,誦昭陵之聖,知教德之夙成。追光獻之慈,嗟結褵之何及。往膺嘉數,茂協多祥。可特進封魏國大長公主。42
據《長編》所記,李遵勗在“天聖末”曾奏事殿中,劉太後趁著仁宗離座更衣,即屏退左右私下問李遵勗,“人有何言?”李當時唯唯不答。劉太後堅持要他回答時,他就說:“臣無他聞,但議者謂天子既冠,太後宜以時還政。”劉太後卻辯稱:“我非戀此,帝年少,內侍多,尚恐未能制之也。”他又曾經上三說五事以論國政。考《長編》未有具體記載“天聖末”是何年何月?筆者懷疑很有可能就是天聖十年十一月改元明道,李遵勗因召還京師進官而入謝之時。劉太後雖然沒有接受李遵勗婉轉的諫勸,還政仁宗,但似乎這時她倒是信任李的。43
明道二年(1033)二月初九,劉太後服祎衣、花釵冠,乘玉輅以赴太廟。然後改袞衣、儀天冠,以皇帝的禮儀行籍田禮。她大概已意識到來日無多,就不顧物議。仁宗等自然不敢持異議,還讓群臣上奏,給她上“應元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皇太後”。三月初五,以籍田大典,再次加恩百官。初七,劉太後又讓來朝的錢惟演為景靈宮使留京師。李遵勗這時大概也召還京師,並在這次加恩得進拜寧國軍節度使。大長公主的長女也在這時進延安郡主之封號。宋廷方才喜氣洋洋,但才八天後(十三),劉太後卻“不豫”,仁宗奉她的意思,大赦天下,乾興以來貶死者均覆其官,謫者皆得內侍,連丁謂也獲準致仕。但種種近於祈福的做法均無效,稱制十二年的劉太後於同月廿九日卒。44她之死對仁宗和一眾受她猜疑的趙氏皇親無疑是一大解放。
仁宗於明道二年四月親政,到皇祐三年(1051)三月大長公主病逝。在這十八年間,大長公主與仁宗姑侄間關系十分親密,起先是大長公主多方關顧少年的侄兒,特別是仁宗在感情方面與健康方面一度弄得一塌糊塗的時候。到寶元元年(1038)八月,與大長公主伉儷情深的駙馬李遵勗病逝後,仁宗就反過頭來多方關顧照料年過半百,後來並且失明的姑姑。仁宗在康定元年(1040)以後,兒女多人夭折,兼西北兩邊告緊,日子並不好過。大長公主則一如以往,從不幹政,也不許兒子李端懿等接受外郡或禁軍要職,而且和兄長荊王元儼帶頭支持仁宗減免宗室貴戚的公使錢或賞賜以助軍費。是故她直到病逝,一直受到仁宗無比的敬重和尊禮,也贏得朝臣們由衷的佩服。據宋人所記,前代之大長公主原本用臣妾之禮事君主,到宋代就改用家人之禮,而仁宗由始至終,以侄事姑之禮見大長公主,並被宋人奉為家法。45
在劉太後死後,大長公主首先與兄長荊王元儼直接及間接向仁宗揭示他的身世。據群書所記,劉太後死後不久,仁宗的左右便告訴仁宗李宸妃才是他的生母。據《邵氏聞見錄》的記載,多年來雖然備受劉太後刻意拉攏,但仍閉門卻絕人事,不預朝謁的鎮王元儼,在這一關鍵時刻,忽然走出來向仁宗證實並揭露“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而喪不成禮。仁宗聽到叔父如雷轟頂的話後大慟,一方面扣押劉氏族人,另一方面馬上命親舅李用和開棺檢視。幸而當日劉太後聽從呂夷簡的勸告,預先布置一切,將李氏以後禮成服,才消除了仁宗對劉太後加害生母的懷疑和怨恨。46敢向仁宗揭示李宸妃才是仁宗生母真相的“左右”是什麽人?據《涑水記聞》所載,大長公主的次子李端願曾向司馬光言及一則有關李宸妃死時,劉太後初時只肯將她的棺材從宮中鑿垣而出,並瘞於洪福寺的說法。47考李端願在康定元年已任西上閤門使的近職48,他很有可能就是向仁宗透露這則宮廷秘辛的人。即使向仁宗說話的不是李端願,他肯定知道包括這事的不少宮廷秘卒。由此推論,大長公主沒有理由不知內情。以常理推斷,當荊王向仁宗揭示這則秘辛時,仁宗一定向她求證。從仁宗後來的反應,可以推想大長公主當會委婉地說明當年的事實。
大長公主唯一在世的四姊楚國大長公主卻不幸在 1038 年七月十五日卒,仁宗親臨公主宅祭奠,並追封她為晉國大長公主,賜謚“和靜”。49大長公主自然也隨仁宗臨奠。她們姊妹感情如何,史所不載,相信仍是傷感不已的。大長公主的同胞兄妹,到此時只剩下八兄荊王元儼一人。
仁宗繼續清除劉太後的影響力。是年九月初四,既是劉太後的心腹也是大長公主的姻親的錢惟演的平章事頭銜被去掉,仁宗令他離開河南府,赴崇信軍節度使本鎮隨州(今湖北隨州)。事緣禦史中丞範諷劾奏錢惟演不當擅議宗廟事,既為其子郭曖娶郭皇後妹,又想和李用和家聯姻。仁宗自然清楚錢惟演的種種劣跡,開始時還說“先後未葬,朕不忍遽責惟演”,當範堅持非逐錢不可時,仁宗即接納其議,將錢貶降,一天後,再將錢曖奪一官,落集賢校理之職,並令隨惟演往隨州,錢惟演諸子包括大長公主婿錢晦也補外州監當。在錢惟演一家被貶之事上,大長公主相信沒有影響仁宗的決定。她對侄兒的施政,一向是從不加以幹預。50仁宗除了在十月初五將劉太後及生母李太後祔葬於真宗的永定陵外,又向已故的宗室及親屬加恩:伯父齊王元佐至從兄樂安郡公惟正等,先在九月十七至十九加贈王爵;亡兄周悼獻王在十月丙辰(廿四)獲追封為皇太子,同日仁宗母李太後獲封贈三代。十一月初一,仁宗兩位從姑、秦王廷美女承慶郡主封為樂平公主,興平郡主特封為大寧公主;他的從表姑、太祖妹燕國大長公主女長樂郡主高氏以異姓而封為仁壽公主。對於自幼入道卻早夭的姐姐、真宗第二女衛國長公主,仁宗賜號清虛靈照大師,賜名志沖。而仁宗本來鐘情的張美人,兩天後(初三),亦被追冊為皇後,並贈其父供備庫使張守瑛為鄧州觀察使。最後是十一月十四,荊王元儼母太儀王氏獲加贈德妃。51仁宗這些措施,自然得到荊王及大長公主的首肯。據載仁宗親政後,對叔父益加尊寵,凡有大事都請報荊王,荊王一定親自書寫回牘。52相信工筆劄的大長公主也會像兄長一樣親自回答侄兒所問。
相信在李遵勗的推動下,仁宗開始為當年因保護及支持他而被貶死的故相寇準等人平反。寇準首先在十一月十二獲得平反,恢覆萊國公之爵位並獲贈中書令。當年被誣謀反的內臣周懷政也同時獲追贈安國節度使。53最後是李遵勗的摯友楊億,在景祐元年(1034)四月初五獲得平反。因李遵勗與寇準婿樞密使王曙向仁宗申訴,楊億獲贈禮部尚書,賜謚曰“文”。李遵勗更請加賜楊億“忠”字,雖不被接納,但仁宗仍詔送其奏於史館。據《東軒筆錄》所記,李遵勗在楊億卒時,楊托他收藏所撰有關仁宗監國之詔誥。劉太後死後,李遵勗便將這些機密文書證據進呈仁宗,並具陳此事之本末,於是仁宗明白當日是非曲直,感嘆再三,就下詔為寇準等洗雪其冤。54李遵勗還密奏仁宗將劉太後在宮中的心腹晉國夫人林氏遣出宮外,置之別院,並監察她的出入,免得她再像劉太後當權時一樣幹預政事。55
仁宗改正劉太後種種弊政自然叫荊王及大長公主等至親欣喜,但他的一次任性行為卻令人擔憂不止。仁宗因不喜劉太後之故,也不喜歡劉太後為他立的郭皇後。劉太後死後,仁宗無人管束,就放縱情欲,寵幸尚美人和楊美人,而冷落郭皇後。不幸郭皇後也任性,與尚美人相爭,在一次沖突中誤傷仁宗,仁宗聽信覆相的呂夷簡及入內副都知閻文應(?—1039)的進言,在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廿三,竟將郭皇後廢黜。結果引來以孔道輔(986—1039)、範仲淹為首的十名台諫官的抗爭,而大失人心。56在仁宗廢後之事上,他的至親包括章惠楊太後、荊王元儼、魏國大長公主及仁宗舅父李用和態度為何,文獻無證。相信他們對仁宗這一任性行為是無可奈何。
大長公主等擔憂的事果然發生。景祐元年(1041)八月,朝臣間已流傳仁宗溺於酒色的種種失德之事。剛覆相的王曾的僚屬石介(1005—1045)便上書王曾,希望他入朝後能規勸仁宗。57果然,仁宗為酒色所害,弄致“不豫”的險境。在章惠楊太後的決策,入內都知閻文應的執行下,同月十五日,已廢黜的郭皇後及仁宗寵幸的尚美人及楊美人都被驅出宮外。尚美人的家人及討好她的皇城使王懷節均被貶責。58
仁宗出事,禦醫數次進藥都無效,大長公主大概從夫婿李遵勗及出入宮禁的兒子李端懿等處知道情況,就推薦翰林醫學許希為仁宗診治。許提出:“針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因位置危險,仁宗左右都說不可冒險。仁宗身邊的多個內臣都自願受試,結果都無礙,於是仁宗決定依許希的方法治療,三進針而仁宗的病得到治愈。九月初二,仁宗論功行賞,授許希翰林醫官,並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又因其請修建扁鵲廟於京師城西。59
仁宗大病得愈,自然首先要感激大長公主的舉薦神醫。他在同月(九月)十一禦正殿和恢覆常膳。十八日,仁宗詔立曹彬孫女為皇後。據載仁宗本來打算立壽州茶商女陳氏為後,而楊太後也同意;但王曾、呂夷簡、宋綬、蔡齊等宰執均反對由地位低下的人為皇後,結果仁宗妥協。60在立後之大事上,筆者猜想仁宗也征求大長公主之意見,大概大長公主也讚同王曾的看法,於是仁宗不再堅持立他本來喜歡的陳氏女。順帶一談,這年十一月十七日,大長公主親侄、仁宗另一從兄武當軍節度使允寧卒。仁宗身體康覆,即依制往潤王宮臨奠。61
景祐二年(1035)二月十三日,次相李迪在權爭中敗給呂夷簡而被罷,值得註意的是,他本來攻擊呂夷簡私交荊王元儼,為荊王門下僧惠清補官。想不到查證下,行文書的是李迪而不是呂夷簡。真相是呂夷簡巴結荊王,只是他沒有給人拿住把柄和憑據。62仁宗親政後,感念叔父保護的大恩,自然優寵荊王,而荊王的權勢自然是人盡皆知。當然,朝臣對大長公主也不敢輕慢。
四月初三,李遵勗以鎮國軍節度使出判許州,大長公主就沒有隨行。李遵勗抵許州後,便先到亡友楊億在許州具茨山之墓拜祭。他在許州,頗有政績,有一次州民輸租稅,倉官不依時而至,李遵勗親自馳馬至糧倉,收受州民的輸稅,倉官惶恐叩頭認罪,大概此人平時作威作福,今次李駙馬爺在州民前訓責他,就大快人心。李遵勗另一項政績,是本路轉運使揀選士卒補水軍,而不問他們是否勝任,就強補他們隸水軍。李駙馬是貴官,又是三代將家子,自然要改轉運使不合理的做法,他說:“強人所以不能,將何用?”即命部將按視,將不習水者的士卒計十分七八調離水軍。63他在許州的表現,又顯出他將門之後的風範。相較之下,柴宗慶在十月廿一日卻被朝臣劾奏,說他印行《登庸集》一書“詞語僭越”,請毀印板,以免流傳。仁宗命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查察此書,回奏說:“《登庸集》詞語體制不合規宜,不應摹板傳布。”仁宗從其議,命柴宗慶收回眾本,鴉許流傳。柴宗慶這次自討沒趣,這樣的處分已算輕微了。64
被廢的郭皇後在是年十一月初八暴卒,中外都懷疑是已升為入內都知的閻文應所為。仁宗知悉後,既悔恨又深悼,詔以後禮葬,又擢升郭皇後的兄弟官職以稍作補償。是月十五,仁宗大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天下,宗室並與轉官。廿五日,荊王元儼拜荊南、淮南節度大使、行荊州、揚州牧,仍賜入朝不趨,授二州牧自元儼開始。宗室中地位僅次於元儼、份屬大長公主從兄的武勝軍節度使德文授同章事,而與仁宗幼時共學的陳王元份第三子允讓為寧江軍節度使。65同年十二月初八,仁宗又加恩給尊為保慶皇太後的章惠楊太後以及曹皇後三代。相信也在相同時間,仁宗也加贈給李遵勗亡故的長兄太師。仁宗的親表弟李端懿及李端願也大概在這時擢任諸司使臣。66
仁宗在景祐三年(1036)多番施行睦親之政。正月十三,仁宗對幾位至親加以追贈,首先追冊郭皇後為皇後,並命知制誥丁度(990—1053)及內侍押班藍元用(?—1055)同護葬。然後在二月初三,又追贈三位亡故的皇姑許國、鄭國和曹國長公主並為大長公主。67到四月,因李遵勗獻上他編次多年的佛書三十卷,仁宗除賜書名《天聖廣燈錄》外,更應其請親撰序文,高度讚揚李遵勗之功德以及是書的優點:
《天聖廣燈錄》者,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之所編次也。遵勗承榮外館,受律齋壇,靡恃貴而驕矜,頗澡心於恬曠。竭積順之素志,趨求福之本因。灑六根之情塵,別三乘之歸趣。跡其祖錄,廣彼宗風。釆開士之迅機,集叢林之雅對,粗裨於理,鹹屬之篇。68
仁宗又以諸王子孫眾多,既聚居睦親宅,就需要在宗室中置官加以訓導和糾違有過失的。於是在七月十九日置大宗正司,凡宗族之政令,皆由之負責奏告。以他關系親密的寧江軍節度使允讓為知大宗正事,另以彰化軍留後守節同知大宗正事。69
李遵勗在許州任上,除了編次上面提到的《天聖廣燈錄》外,他又應亡友晁迥之子翰林學士晁宗慤(985—1042)所請,在是年七月一日,為晁迥之遺作《昭德新編》三卷撰寫序文。70他又在是年十月十七,上奏仁宗,將《天聖廣燈錄》下傳法院,編入藏經。仁宗自然欣然答允。71
是年十一月初四,章惠楊太後無疾而終。仁宗命知樞密院事王隨為園陵監護使,上謚曰“莊惠”,祝冊文並稱“孝子嗣皇帝”,仁宗又擢太後弟楊景宗(?—1054)為成州防禦使,厚恤楊家。翌年二月初六,將楊太後祔葬於真宗永安陵之西北。72此時,仁宗在宮中已無任何長輩對他的施政加以牽制。
仁宗厚待他的戚裏,但對劉太後的家人就區別對待。景祐四年(1037)二月初九,劉太後之姻親王蒙正,再以不法事被除名,配廣南編管,永不錄用。其女嫁劉從德,詔自今不得入宮內,其子孫不許與皇族為婚姻。73三月廿七,時年十七的劉美次子劉從廣娶荊王元儼女,仁宗就將他自濟州團練使擢為滁州防禦使。74
是年(1037)五月初九,仁宗的俞美人誕下皇子,但當天就夭折,對仁宗是一大打擊。值得一提的是,允讓的第十三子宗實(英宗)從四歲開始,就養於宮中。這年六月廿三,年方六歲的皇侄宗實以左監門率府率特遷右內率府率。據說是楊太後勸仁宗選宗子養於宮中的。宗實到八歲才離開皇宮返本第。75關於王嗣的問題,仁宗有否詢及荊王及魏國大長公主,惜沒有記載。
這年(1037)十二月廿四,一向麻煩多多的駙馬都尉知陜州柴宗慶又被新任陜西轉運使段少連劾他縱其下屬擾民。76他們夫婦與李遵勗夫婦同是貴戚,賢與不肖卻分明。據宋人筆記所載,楚國大長公主曾與妹妹鬥富貴。李遵勗夫婦先往柴宅,柴宗慶夫婦以豪奢穿戴示人,他們的左右卻草草穿戴。到柴宗慶夫婦回訪,卻只見李遵勗夫婦以道裝出迎,唯他們的從人卻以盛裝隨侍。跟著魏國大長公主讓兩個兒子李端懿、李端願出見姨母及姨父,並說:“予所有者,二子也。”柴宗慶夫婦據說頗以為愧,而士論均稱譽李遵勗夫婦。77
景祐五年(1038,十一月改元寶元)初,深受仁宗敬重的姑父李遵勗卻以疾,兩度拜表奏請致仕,並援引唐韋嗣立的故事,請求山林之號。仁宗不許,命翰林學士宋庠撰寫兩道詔書撫慰一番,其一雲:
卿勳伐之華,材猷兼劭。早膺尚禮,實睦近婣。以駙馬之榮,列通侯之籍。望高貴裏,時陟將壇。而能出擅藩宣之勤,居多位著之恪。乃心道素,探頤藝文。余懷所嘉,曷日而既?今乃因晦明之偶沴,援進退之大方,確布書辭,願致官政。矧告旬未幾,年力甫強,謝仕而歸,在禮安據?卿其止念,慮寶精神,招還天和,頃遲藥嘉,慰我虛竚,勿覆文陳。
其二雲:
卿曏苦臒屙,甫淹時晦,特優賜告,用適頤生,屬療治之未瘳,覽控陳之叠至,願還有政,追踵昔賢。高風所存,媮俗知慕。然卿地雖婣密,器實虛恬。情棲道腴,行富天爵。偶嬰無妄之疾,固匪不衷之災。視履其旋,何恙不己?遽歸印綬,殊惻朕心。矧向福未涯,與善無爽。勉輔醫藥,行覆粹和。姑廢沖懷,即斷來表。78
大長公主愛夫情深,聞知李遵勗得病,馬上要往許州探視。她的侍從以制度規定需要稟報仁宗,得到批準才可離京。她已等待不及,不待奏請,便率從人五六名前往許州。仁宗得報,馬上派內侍督沿途各縣邏兵保護她的車輛。抵許州後,她陪侍李遵勗回京療治。仁宗親自到駙馬府臨問,又賜白金五千兩,公主辭不受。延至八月十六,李遵勗卒於永寧坊第,得年僅五十一。他將死時,與僧楚圓以偈文相互提警。他又遺命不要置金玉於棺槨中。仁宗聞訊即臨奠。並輟朝二日,贈中書令,謚和文。據明人《汴京遺跡志》所記,他的墓在開封城東北南神崗。後來他的長子李端懿也附葬於其墓側。79
李遵勗逝世,朝士多有挽詞悼念,翰林學士宋庠便為詞兩首,詞雲:
曲裏猶龍族,西京尚主侯。勳華傳舊鉞,名理寄虛舟。得族真無妄,觀生遂若休。偏嗟荀令沼,回作逝川流。
北第琴樽歇,東原旌旆飛。清風邈無所,此路是長違。野闊車吞響,天愁日抱輝。空余門下客,魚鳥嘆何依。80
魏國大長公主在五十一歲喪夫,自然極端悲痛。李遵勗所撰之《閑宴集》二十卷、《外館芳題》七卷,相信都是“善筆劄,喜閱圖史,能為詩歌”的大長公主與眾子所編定。81她服夫喪期間,衰麻服一直不肯脫。每日都念誦佛書,精誠所感,據說有白燕來她房外築巢。服除後,她不再穿皇家麗服。仁宗為了安撫她,在禁中設宴,並親為她簪花,但她多謝侄兒好意之余,即表示:“自誓不覆為此久矣。”她的長女延安郡主因父喪而悲傷不已,亦因大長公主之故而說:“吾獨有母存乎!”郡主盡孝,凡有新鮮物品,必定先獻給母親才致用。大長公主則每年常將自己一部分的俸錢中厚贈女兒。82因女兒之陪伴,加上仁宗及諸子之安慰,大長公主乃得挨過喪夫之痛。
潞州李氏外戚將門在李遵勗逝世後,就倚靠大長公主支撐而不墜。仁宗愛屋及烏,對他幾個至親表弟自然不次提拔,可大長公主卻沒有因仁宗對她的敬重而為諸子求官。她對親生的兒子李端懿、李端願,庶出的李端憲和李端慤均一視同仁,均嚴加管束,每誡以忠義自守,不要恃她的恩寵而為非。長子李端懿曾多次求外任以自效,但公主均白仁宗不許。83
寶元元年(1038)七月初一,號為賢宗室的同知大宗正事、彰化留後守節卒,仁宗贈鎮江軍節度使,追封丹陽郡王,謚僖穆。84對仁宗而言,自是傷感不已。是年九月十一,仁宗總算有自己家人喜慶的事:已滿周歲的長女封為福康公主(兗國公主,1038—1070),次女封崇慶公主(?—1042)。仁宗為女兒當得多少月俸錢多少的事詢問大長公主,大長公主起初不答,仁宗一再詢問,她才說當年她只得月俸錢五貫。大概她不想侄兒因她之故少給侄孫女月俸錢。仁宗的福康公主“幼警慧,性純孝。帝嘗不豫,主侍左右,徒跣籲天,乞以身代。帝隆愛之”。仁宗喜愛她的程度,就像太宗寵愛魏國大長公主一樣。兩位公主性情頗有相近之處,可惜仁宗後來擇婿錯誤,害了愛女終身。與大長公主擇得佳婿,就有天淵之別。85
西夏李元昊(1004—1048,1032—1048 在位)圖謀侵宋已久,於康定元年(1040)正月廿三,宋軍在延州三川口(約今陜西延安西20公裏處,即今延安安塞縣、延安境內的西川河入延河處)慘敗於夏軍之手。主將劉平(973—1040 後)及副將石元孫兵敗被俘。石元孫是仁宗寵信的外戚子弟,這次兵敗,令宋廷震動不已。86三月廿四,因三川口之敗,仁宗罷免三員樞密使副王鬷(978—1041)、陳執中(990—1059)和張觀(985—1050),而改任三司使晏殊與知河南府宋綬並知樞密院事,值得註意的是,仁宗還特擢駙馬王貽永以保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為同知樞密院事。王貽永是繼錢惟演後第二人以外戚身份出任執政的,他也是宋代第一位駙馬出任樞密使。王貽永以外戚的身份執掌兵符,文臣並無異議,一方面他其實是相臣之後,而“性情慎寡言,頗通書,不好聲技”,他也累任大藩,資歷甚深,素有令譽。87當然,也是仁宗擢用外戚的政策使然。倘若李遵勗不早逝,以他與朝臣之良好關系,與及素有賢名兼有治郡之資歷,特別仁宗與他夫婦的關系,他本來也會像王貽永一樣為仁宗所大用的。事實上,仁宗早已在寶元二年(1039)擢用他的母舅李用和執掌禁軍兵柄,李先自鄜州觀察使徑授殿前都虞侯,翌年(康定元年)再遷永清軍留後、步軍副都指揮使,同年十二月廿二再遷馬軍副都指揮使。88
西疆告急的情況漸次穩定下來後,仁宗在康定二年(1041)七月廿五,賜初生的皇二子名昕,授檢校太尉、忠正節度使、壽國公,置旌節於他以前讀書的資善堂,命端明殿學士李淑(1003—1059)典其書奏。就像真宗培育他一樣。仁宗在兩年前喪子,好不容易再得子,自然高興不已。89
這年九月十六,仁宗以晏殊自知樞密院事改任樞密使,王貽永也相應地改任樞密副使。90是月廿二,因範仲淹之請,仁宗詔三班院、殿前馬步軍司曉諭使臣和諸班、諸軍有武藝諸略者均許自陳。負責選拔的官員,包括翰林學士丁度,入內押班藍元用和大長公主次子、已擢為西上閤門使的李端願。最後選得一百八十人。李端願得到此差遣,一方面他當有相當武藝,另一方面也是仁宗對他的信任。91
這年十月初一,仁宗以侍禦河南郡君朱氏、清河郡君張氏(張貴妃,後謚溫成皇後,1024—1054)並為才人。值得註意的是,仁宗對曹皇後似乎一直無多大感情,反而清河郡君張氏是寵冠六宮。據《長編》所記,張氏父名張堯封,天聖間舉進士第,補石州(今山西離石)軍事推官,未行而卒於京師。張堯封母親是劉太後姻家錢氏女,張氏八歲時,與姊妹三人由錢氏之故入宮。她年長後,就得幸於仁宗。因她性聰敏、機巧挾智、善解人意,仁宗以她為良家子,待遇異於諸嬪,於是累封清河郡君,這年她十七歲便晉位才人。唯《涑水記聞》卻記張氏入宮前,為母曹氏賣於魏國大長公主家為歌舞者,而且嫁給蹇氏,生男名守和。後來大長公主將她納於禁中的仙韶部,由宮人賈氏母養之。仁宗因在宮中宴飲,張氏為俳優,仁宗見而悅之,從此寵幸她。92假若《涑水記聞》這條記載不誤,則仁宗與張貴妃這段愛情可說間接由大長公主促成,大長公主對侄兒感情的關顧可說是無微不至。93
正當仁宗對姑父王貽永委以重任時,另一位尚健在的駙馬判鄭州、武成節度使同平章事柴宗慶卻令仁宗大為惱火。他在部內貪刻,又縱其下擾民,為轉運使所劾,依法當徒一年,仁宗特赦其罪,於十一月初七召他還朝,歲減公用錢四百萬。翌年(慶歷元年,1041)三月,仁宗命他改判濟州,為免他再有差池,特命京東轉運使選一員通判佐估他。但柴宗慶卻稱疾不肯赴任,仁宗大怒,命禦史台劾奏之,詔停所有給他的公用錢。等他病愈後才除他外任。94
慶歷元年二月十一,宋軍再度覆師於好水川(今寧夏固原市西吉縣境內之什字路河川),主將馬軍都虞侯任福(981—1041)以下將校十六人陣亡,士卒萬八千人敗沒。卻禍不單行,同月二十,仁宗次子壽王昕夭折。仁宗傷心不止,贈太師、中書令、豫王,謚悼穆,命端明殿學士李淑護喪事,陪葬永定陵。仁宗並親制挽辭。據載豫王喪禮中,宗室就奠時,均拜伏於位。但知大宗正事允讓認為致哀便足夠了,人以為得禮。到五月十七,仁宗將早夭的皇長子賜名昉,追封褒王,謚懷靖,與其弟豫王同葬於永安陵。95令仁宗稍得安慰,朱才人在是年八月初五,為仁宗誕下皇三子,兩天後,仁宗即遣官奏告宗廟他再得子之喜事。仁宗又在三天後,詔南郊禮近,中外不得以皇子之生再有上貢物品。96
慶歷二年(1042)正月初六,仁宗本來令柴宗慶赴武成軍本鎮(滑州,今河南安陽滑縣),但權禦史中丞賈昌朝(998—1065)以他在鄭州時貪汙不法,若遣他歸本鎮,怕他更會殘民。仁宗本來對這個姑父沒有好感,就接納賈的意見,仍將柴留在京師。97
仁宗對大長公主一家自然優禮得多,雖然因公主的反對,仁宗不能給他幾個表弟外任或好像其他的外戚如李用和、李昭亮、曹琮、杜惟序授以重要軍職及兵職98;但仁宗仍盡量加恩給其皇姑。是年三月十七日,他應大長公主的請,加贈其母故太儀方氏為淑妃。99
是年五月初六,仁宗又遭喪女之痛,張修媛所生的安壽公主夭,仁宗追封唐國公主,成服苑中,群臣奉慰殿門外。同月十六,仁宗第二女崇慶公主又夭亡,仁宗追封楚國公主。到八月初一,仁宗生下才六日的第六女又夭亡。仁宗在不足三個月內,連失三女,可說是極大之不幸。稍為安慰的是,面對遼夏交侵,國庫緊絀的情況下,他的八叔荊王元儼於五月初十帶頭請盡納公使錢於公。仁宗對叔父的如此慷慨,詔以半數還給叔父。因為荊王的表率,曹皇後、嬪禦各上俸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以上亦納公使錢之半。仁宗再下詔皇後及宗室婦郊祀所賜減半以助軍費。100雖然群書不載,但相信大長公主也會像兄長一樣帶頭減公使錢以助仁宗。
大概為了撫慰張修媛喪女之痛。仁宗在是年(1042)閏九月十三,史無前例地將位僅為修媛的張氏的三代加以追封:曾祖東頭供奉官張文漸為寧州刺史,祖試校書郎張隸為光祿少卿,外祖應天府助教曹簡為秘書省著作佐郎。101不幸的是,仁宗之創痛尚未平覆,是年十月初三,宋軍又覆沒於定川寨(今寧夏固原市中河鄉境內),主將殿前都虞侯葛懷敏(?—1042)以下將校十六人陣亡。102更令仁宗痛徹肝腸的是,生才三歲。剛在慶歷三年 (1043)正月初一冊封為鄂王的皇三子曦,卻在翌日(初二)夭亡。103
仁宗未想到,七個多月後,張修媛與他所生、只有三歲的皇第四女,在八月初一才封為寶和公主,五日後又夭折。104張修媛連失兩女,自然哀痛欲絕,並且病倒。她對仁宗說:“所以召災者,資薄而寵厚也。願貶秩為美人,庶幾不以消咎譴。”仁宗只好答允。唯是月十八,生甫兩歲的皇五女也夭亡,仁宗追贈亡女鄆國公主。105仁宗從景祐四年開始,六年間連失三子五女,他年已三十四而皇嗣不立,作為至親的荊王及大長公主,自然也為侄兒擔憂。據《長編》所載,大長公主在“慶歷中”,曾於浴中仆地,傷右肱。仁宗知道後,派內侍責備侍者。大長公主不想加添侄兒之煩惱,就說:“早衰力弱,不任步趨,非左右之過。”故此她的左右獲得免去罪責。106大長公主為什麽會在浴中摔倒?是否為仁宗家事之傷痛以致國事之憂煩,而令她心有所思而不慎摔倒?據載大長公主的兄長荊王在此時曾問他的翊善王渙:“元昊平未?”當王渙回答說:“未也。”他就說:“如此,安用宰相?”以他的身份這麽一說,自然聞者畏其言。107似乎他們兄妹都同時擔憂侄兒的境況。
值得我們註意的是,慶歷三年三月廿一因首相呂夷簡以老病罷相,仁宗趁機改組二府人事,四月初七擢用守西邊有功的韓琦與範仲淹為樞密副使,翌日再以二人之同志杜衍(978—1057)為樞密使。八月十三,以範為參知政事,富弼(1004—1083)為樞密副使,推行有名的“慶歷新政”。仁宗在兩府的人事變動中,將他的姑父樞密副使王貽永留任,並加宣徽南院使。108李用和、李昭亮及曹琮仍任三衙管軍,仁宗信任範仲淹等人推行新政的同時,對他信任的外戚仍寵任不替。唯一例外的是大長公主的幾個兒子,一直未被仁宗委以重任,這當是大長公主堅持不許的緣故。直到是年十月廿九,仁宗才以樞密使杜衍主動提出建議擇外戚子弟試外官,好不容易才擢用其親表弟李端懿以舒州團練使知冀州(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市)。另外李遵勗的侄婿向經(1023—1076)也因大長公主的表奏獲授秘書省正字的出身。109教大長公主喜歡的是,時年三十一的愛子李端懿,雅好儒學,頗有父風,多有與賢士交往。與他交好的歐陽修在他離京赴任前,便以詩相贈,將他比作曾守冀州的本朝名將李漢超(?—977)和李允則(953—1028),詩雲:
今其繼者誰,守冀得李侯。李侯年尚少,文武學彬彪。河朔一尺雪,北風暖貂裘。上馬擘長弓,白羽飛金鍭。臨行問我言,我慚本儒鯫。漢超雖已久,故來尚歌謳。允則事最近,猶能想風流。將此聊為贈,勉哉行無留!110
另杜衍之婿蘇舜欽(1008—1048)亦有詩相贈,詩中曾言他出知冀州,或會令慈親之大長公主淚流,不過又勉自古忠孝不兩立,須及時建功名雲雲:
冠蓋傾動車馬稠,都門曉送李冀州。冀州綠發三十一,趕趕千騎居上頭。眼如堅冰靦河月,氣勁倢鶻橫清秋。不為膏粱所汩沒,直與忠義相沈浮。幹戈未定民力屈,此行正解天子憂。男兒勝衣志四海,寬恥坐得萬戶侯。旆旌明滅朔野闊,笳鼓淒斷邊風愁。孤雲南飛莫回首,下有慈親雙淚眸。自古忠孝不兩立,功名及時乃可收。眾人刮目看能事,著鞭無為儒生羞。111
據歐陽修所記,李端懿在冀州,沒有辜負他的期望,“為政循法度,檢身束下,民以不擾,歲滿召還”。112
這年十二月初八,荊王元儼病重,這時大雨雪,陳、楚之地尤甚。占者說:“大臣憂”。仁宗憂形於色,親臨其臥內問疾,並親手調藥。據說叔侄二人屏去從人交談久之,荊王所獻均是忠言。仁宗賜白金五千兩,荊王不肯接受,並說:“臣羸憊不能治,且死,重費國家多矣。”仁宗聞之嗟泣。翌年(慶歷四年,1044)正月十二,荊王病卒,得年六十。他臨終時仍誡諸子孝友,他怕仁宗怪罪禦醫治病無效,就預先上奏為他們求情。仁宗贈荊王天策上將軍、徐、牧二州牧、燕王,謚日恭肅。仁宗詔取叔父之墨跡及所賦詩分頒輔臣,其余藏秘閣。113
是年已五十七的大長公主喪失至親,自然悲傷不已。二月初九,仁宗另一姑父柴宗慶也卒於京師,仁宗幸其第臨奠,輟視朝三日,遣中使護喪,謚榮密。114至此,仁宗的父系至親,只剩下大長公主,而姑父駙馬,也只剩下王貽永一人。
仁宗在三月初七擢用張修媛的叔父張堯佐(987—1058)以職方員外郎同判登聞鼓院為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即受到諫官余靖(1000—1064)的反對。115仁宗將情感補償於張修媛身上,他的姑姑也會了解體諒,可一眾文臣卻絕不同意。是年五月十四,仁宗只有兩歲的皇七女又夭亡。116仁宗內心的痛楚大概不是所有文臣明白的。七月十九日,仁宗用富弼的建議,封宗室德文、允讓等十人為郡王及國公不等。117這措施大概對敦睦皇親有很大的作用,這應是大長公主所喜見的。仁宗早在八月廿三日,也給大長公主的另一女婿內園副使焦從約(?—1049)一份優差,命他為契丹國母正旦副使。118這年十二月十二,仁宗總算有愜意的事,張修媛為他誕下皇八女(是張氏第三女),仁宗賜名幼悟,號保慈崇佑大師。仁宗夫婦自然希望憑佛法保佑他們的幼女。不過事與願違,這位小公主在不到一年,於慶歷五年(1045)四月又夭折。119
慶歷五年對仁宗來說,是叫人頹喪不已的。除了張修媛的第三女也夭亡外,外戚先後有曹皇後兄曹傅(?—1045)、章懿李太後侄李瑛(?—1045)和曹皇後叔父、馬軍副都指揮使曹琮卒。特別是一向“小心謹畏,善讚謁,禦軍嚴整”而家無余資的曹琮之死,對仁宗控扼軍權,是一重大損失。特別是年閏五月,李用和以老病辭去殿帥之職,在三衙為仁宗把關的外戚心腹,就剩下自步帥升為殿帥的李昭亮。120仁宗尚可依賴的外戚親信,也包括已擢為樞密使的駙馬王貽永。121
偏偏仁宗寵信的外戚及宗室子弟卻不中用,給朝臣嚴劾,先有河陽部署郭承祐及陜州部署魏昭昺為言官痛劾其貪汙及人才猥下,然後是荊王元儼第三子安靖節度使允迪在父喪期間做出違制之事。最後是惟正之繼子左龍武大將軍從黨射殺親事官,被仁宗削爵鎖禁,他後來還自殺身亡。而在三川口之役傳說力戰陣亡的宋軍副將外戚子弟石元孫,在是年五月卻被西夏釋放回來,也教仁宗面目無光。此外,仁宗母舅李用和在退休後獲授宣徽使,他仍不滿足,要仁宗授他使相。禦史中丞王拱辰批評他“無功貪驕”,反對授他使相。仁宗不顧言官反對,才滿足母舅的要求。另外,仁宗明知楊太後弟楊景宗不中用,也知言官一定有意見,這年十月仍將他自成州防禦使擢為徐州觀察使。122然而,最使仁宗無奈的是,因朝臣之傾軋,他所推行的“慶歷新政”也在是年(1045)正月隨著範仲淹和富弼離開朝廷,杜衍罷相而中途而廢。123
大長公主一家在慶歷五年之朝政變局並沒有牽涉在內,據載是年當僧本如在台州(今浙江台州)東北四十五裏的白蓮庵重建佛寺,篤信佛教的大長公主向仁宗請匾額,改名“白蓮寺”。124到了慶歷六年(1046)六月,李遵勗之姻家、參知政事吳育因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不和,而引起政爭,並牽涉李家。吳育之弟娶李遵勗妹,其弟死後,李婦有子六人而守寡。監察禦史唐詢依附賈昌朝,就攻擊吳育不讓弟婦改嫁是為了繼續攀附大長公主一家。吳育出身制科,受知於仁宗,屢被許為賢者,也許大長公主也曾為他說過好話。於是賈昌朝一黨就以此來攻擊他。仁宗為了息事寧人,兩個月後,就讓吳育與樞密副使丁度對調職位,免得吳繼續與賈昌朝爭議。仁宗這番處理,相信也有一點看在大長公主份上。125
這年五月廿四,份屬大長公主從兄的東平郡王德文卒,得年七十二。仁宗在他病重時親自探視,並以太醫所調之藥進之。仁宗親臨哭奠,贈太尉、中書令,封申王,謚恭恪。126真宗一輩的宗室至此皆歿,論輩分和年齡,就以大長公主最尊。
仁宗從是年四月廿一始,既加恩給張修媛母曹氏,晉封她為清河郡夫人,又不次擢升她的叔父張堯佐。對於他母家的外戚,自然也大大加恩。這年七月十二便晉升他的表弟李璋為西上![]() 門副使。他當然不會漏了大長公主的家人,八月十二,錢晦也以六宅使、嘉州刺史獲得契丹國母生辰副使的優差。127
門副使。他當然不會漏了大長公主的家人,八月十二,錢晦也以六宅使、嘉州刺史獲得契丹國母生辰副使的優差。127
仁宗厚待外家的做法,卻不幸弄巧反拙。慶歷七年(1047)五月初二,他沒有考慮女兒之感受,便將心愛的皇長女福康公主許配給其母舅李用和次子李瑋。仁宗想給女兒的豐厚的嫁妝,怕超越舊制,就詢問大長公主當年下嫁李遵勗的體例。大長公主很體諒侄兒,以侄兒只有一個女兒,不應與她當年的情況相比。她認為若說嫁妝多,就不符事實;但若據實說嫁妝少,又怕拂了侄兒之意。於是推說歲月久遠,已不記得當年太宗所贈嫁妝多少。仁宗於是依本意厚贈愛女嫁妝。仁宗本以為報答母家之恩,將愛女許配表弟,親上加親,不想到李瑋貌陋才拙,根本一開始就不為福康公主所喜。相較之下,真宗將大長公主許配給李遵勗就十分登對,琴瑟諧和。不知道仁宗在這事上有沒有咨詢大長公主之意見?大長公主對仁宗這項錯誤的決定沒提出異議,實在是一大遺憾。128
這年十一月廿八,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宋廷發兵平亂。到慶歷八年(1048)閏正月初一,在參政文彥博子及權知開封府明鎬率領下,亂事平定。129宋廷賞功罰過,有舉報大長公主長子李端懿前知冀州時,失察王則之黨妖人李教。二月初九,李端懿自濟州防禦使降為單州團練使。130
當宋廷正在慶祝平定貝州之亂時,宮中的崇政殿親從官顏秀等四人在閏正月廿二日謀變,殺入禁中,焚宮簾,傷宮人,最後才為宿衛所殺。宋廷追究責任,勾當皇城司的楊景宗貶知濟州,另一外戚子弟劉永年亦貶為洛苑使。仁宗本來還想赦免楊景宗等,言官自然堅決反對。在這次宮廷喋血中,仁宗卻以張修媛有扈駕之功而要加恩。幸群臣反對而止。唯一讓仁宗稍感安慰的,是宋人心腹之患的夏國主元昊在是年正月初二為其子所弒。131
是年(1048)三月初六,大長公主的庶子供備庫使李端憲卒,仁宗特贈澤州刺史。本來只有公主親子才有特贈官的恩典,因大長公主對諸子一向並無分嫡庶,故仁宗仍給李端憲特恩。132同月廿七,仁宗在言官的劾奏下,無奈將他寵信的外戚殿帥李昭亮解軍職。但仍不顧眾議,在七月二十將他的心腹郭承祐擢為殿帥,接替李的位置。仁宗又為寵幸張修媛,先在是年四月初六,在言官的反對下,擢升張修媛之叔父張堯佐為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然後在十月十七,以張氏在宮禁之亂中有護駕之功,將張氏晉封為貴妃。到十二月初三舉行冊禮。133
仁宗也在十一月廿九日特賜兩員年長的外戚王貽永和李用和笏頭金帶,這是二府大臣才得賞賜之物。王貽永是樞相,李用和是使相,也算受之有理。仁宗在十二月十八日,也把十年未有遷官的外戚子弟劉從廣自滁州防禦使遷為宣州觀察使,算是對劉太後家人一點照顧。134
大長公主的女婿西上閤門使錢晦在這年十一月做了一件受人稱許的事,他不畏權勢,以他的職責上言,反對首席內臣、景福殿使入內都知王守忠參與大朝會,並座次在朝臣之上。他說容許王守忠(?—1054)這樣,必為四方所笑。最後王守忠不敢參加本來他可以出席的紫宸殿宴會。順便一提,錢晦與延安郡主所生的女兒大概在這年前後因大長公主的推恩而獲封壽安縣君(?—1050)。135
仁宗於翌年(1049)改元皇祐。大長公主是年已達六十二歲的高齡。這年三月初七,她的次子邢州觀察使李端願為人告發私通李遵勗之婢,並且殺驢以享客人。仁宗將他降一官處分。李端願幹出這等違法的事來,自然叫大長公主難過。據宋人筆記所說,曾有卜者李易簡批評他和其兄李端懿“大長公主之子,生而富貴,窮奢極欲”,顯然其貴戚子弟驕奢之習氣早已為人所註目。136不如意之事陸續而來,三月二十三日,大長公主的另一女婿內藏庫副使焦從約卒。因她之故,仁宗特贈他內藏庫使。137
大長公主在皇祐二年(1050)後患上目疾,目不能視。據《長編》及《宋史》所載,仁宗知悉皇姑病情後,首先派內侍帶同太醫診視,並且以各樣的禳襘來禱告。然後令曹皇後、張貴妃及以下之妃嬪均同至公主宅問候。她們到公主宅進拜都用家人禮,並且恭敬地奉藥茗給大長公主。仁宗隨後親臨探視,大長公主的侍從扶著主人迎接,仁宗即請公主先坐,然後設禦座於大長公主座位西邊。大長公主守禮,極力反對侄兒這樣的座位安排。最後仁宗移榻於東南向,大長公主才肯接受。仁宗又當眾親舐皇姑之目,左右侍從大為感動而悲泣。仁宗亦悲慟地說:“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大主,奈何嬰欺疾?”仁宗又顧問李端懿兄弟及其子孫有什麽要求願望。大長公主即加以拒絕說:“豈可以母病而邀賞邪?”仁宗原本賜白金三千兩,她也推辭不接受。仁宗感慨對從臣說:“大主之疾,儻可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他又命在大長公主寢門外垂簾,令從臣前往問候,並募天下能醫皇姑者授以官職,另賜公主禦書金字“大悲千手眼菩薩”,同時又賜玉石金字太宗廟謚138,稍後仁宗又親畫《龍樹菩薩》圖,命翰林待詔傳模,鏤板印行布施,都只為祝求公主目疾康覆。139仁宗對大長公主的感情,儼然兒子對母親的孝敬。仁宗生而不知其母,到知道母親是李宸妃時已是子欲養而親不在,他將懷念亡母的感情移到一直愛護他有加的大長公主身上是很顯然的事,特別是仁宗連“見舅如見娘”的母舅李用和在皇祐二年(1050)七月十一病逝後,就只有大長公主可以給他這樣的移情作用。140
大長公主喪明後,平日深居簡出,而對世事沖淡自若,沒有不甚悲傷怨苦,她的佛教信仰大概令她對病患處之泰然。她大概知來日無多,常告誡諸子說:“汝父遺令柩中無藏金玉,時衣才數襲而已。吾歿後當亦如是。”141她大概已參透了生死。
仁宗除了在皇祐元年(1049)九月不次擢升張堯佐為三司使外,並晉封張貴妃的親人外,142對大長公主的親人也多加照顧,皇祐二年(1050)三月廿二,又給已升為貴州團練使、西上閤門使錢晦一份優差,命他為回謝契丹國信副使,出使遼國。143
宋廷的言官在皇祐二年(1050)六月十六攻倒了仁宗的心腹寵臣宣徽南院使郭承祐後,又繼續劾奏張堯佐不配擔任三司使。144但仁宗不理,在同年閏十一月初六,先授張為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初七,再加他同群牧制置使。翌日,又賜張堯佐兩個兒子衛尉寺丞張希甫及太常寺太祝張及甫進士出身。仁宗這樣任性的做法,引致以禦史中丞王舉正(991—1060)與知諫院包拯(999—1062)為首的台諫官的抗爭。張堯佐見眾怒難犯,在十六日也自請辭去宣徽使及景靈宮使二職。145
就在仁宗被迫向群臣退讓,無法令他的愛妃張氏一家再沐皇恩而心中不快時,大長公主在皇祐三年(1051)正月十三日卻病重,仁宗即往公主第視疾。仁宗在十八日又詔翰林醫官院,每日輪流派醫官一員總領諸科醫官,以備應奉。相信是為了方便醫治大長公主的特別措施。146到三月廿五日,大長公主終於不治,得年六十四,在宋代公主中,她算是高壽。仁宗當日聽到大長公主病篤,即趕赴大長公主宅探視,在途中聞知皇姑已病逝,便到大長公主堂中易服,親自看視皇姑小殮完畢,然後再拜奠慟哭。仁宗隨即下旨輟朝五日,追封大長公主為齊國大長公主,謚獻穆,又賜珍珠飾棺帷與及金銀供器。廿六日,詔他的生日乾元節(四月十四日)罷作樂。廿七日,在宰臣兩度上表固請之下才收回成命。仁宗又想起以前每逢他的生日,大長公主都在前一晚上入宿禁中,第二天早上即為他賀壽。追念前事,想起大長公主之恩情,就遣使持香藥、醴、饌置於大長公主靈柩前。仁宗稍後又親制挽辭,並撰神道碑首曰“褒親旌德之碑”,以報答皇姑之恩德。四月初六,仁宗又加恩給他的表弟及其他親屬:長子華州觀察使李端懿為鎮國軍留後,次子越州觀察使李端願為鎮東軍留後,四子西京左藏庫使、資州刺史李端愨領陵州團練使,諸孫內殿承制李諒為供備庫副使,內殿崇班李評、李說並為內殿承制,長婿東上閤門使、貴州團練使錢晦領忠州防禦使。另外,仁宗又將表妹延安郡主的月俸錢由六萬增至十萬。147大長公主的靈駕在是年六月六日發引前,仁宗再臨公主宅奠祭。148大長公主大概在六月底下葬於開封城東北南神崗李遵勗墓旁。仁宗命李淑撰寫大長公主的神道碑銘,並命王洙(997—1057)書寫碑的隸字。七月初三,仁宗詔開封府,凡因大長公主靈駕下葬而受到踐蹂的田稼,由官員檢視後,給予田稼的農戶減免其租作為賠償。149
朝臣拜祭的和送葬的,因與李家的交情及對大長公主的尊敬,均贈送挽詩祭文,雖然不無溢美之詞,也相當反映士林對大長公主的高度評價。司馬光代兩制官員所寫的祭文雲:
惟靈集慶皇家,作嬪侯族。環珮為節,動顧禮文。蘋藻必親,無違婦職。承天以順,教子以慈。純素柔嘉,自忘王姬之貴;肅雍明智,居為裏戚之規。嗚呼!遐福未終,大期奄及。去白日之昭晰,歸下泉之窈冥。宸極惋傷,具僚增欷。祗陳薄薦,庶達菲誠。尚饗!150
與李家有深厚交情的宋祁也在外郡呈上《慰魏國公主薨表》,表文雲:
臣某言:得進奏院奏報,雲三月二十🖂日魏國大長公主薨,輟朝五日者。姬館淪華,沴生意表。天襟叢惻,禮極哀余。訃問外騰,人倫胥戚。臣某中謝。伏以魏國大長公主,行為媛則,德冠壺彜。宜胙高年,昭祉元吉。胡不憖遺,遽及雲亡。伏惟皇帝陛下,推先聖歸妹之仁,原本朝諸姑之懿。當所置務,易服申慈。愴心幄之長違,賁窀宵而極寵。情兼文盡,孝與治隆。然宵旰既勤,聽斷斯廣。顧禮有限,雖聖弗違,願抑遣於悲懷,勉逢迎於順福。臣適守郡印,不獲奔赴闕座,無任瞻天系聖,竦怛屏營之至。謹遣知兵馬使郭玉,奉表陳慰以聞。151
大詩人名士梅堯臣(1002—1060)也在送葬時贈以挽詩兩首,詩雲:
賢行聞當世,尊隆異故常,每令夫結友,不為子求郎。夜月初沈海,姑星忽殞潢,臨門親祖祭,悲吹起脩岡。
魯館當年盛,秦台此日遙,龍歸終合劍,鳳去不聞簫。挽曲方傳薤,行輀競奠椒,空余漢官屬,泣送馬如潮。152
翰林學士胡宿亦撰挽詩一首,詩雲:
舊築王姬館,新開貴主阡。山林經駐蹕,煙霧隔飛軿。天屬尊惟孝,邦風穆以賢,鸞龍摛翰藻,昭德萬斯年。153
大長公主可說是生榮死哀,仁宗在她病重以至薨逝所表現出的極深感情是其他大長公主或其他宗室所沒有的。事實上光是大長公主在仁宗每年生日一定在前一日進宮留宿,第二天一早為侄兒賀壽的做法,也是朝臣以至尋常百姓不一定那麽體貼的,難怪仁宗對大長公主敬愛備至。
宋廷的文臣對大長公主的評價也始終十分正面的。在大長公主逝世後一年,即皇祐四年(1052)四月,蔡襄為延安郡主撰寫墓志銘時,便稱許大長公主“以賢德輔之(按:指李遵勗),著於天下”。而蔡襄筆下的延安郡主各方面的才德均類似大長公主。154到嘉祐五年(1060)八月,當大長公主已辭世九年,歐陽修為李端懿撰寫墓志銘時,再一次稱許“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女,真宗之妹,今天子之姑,屬親而尊,禮秩崇顯,其淑德美問彰於內外”。155
到嘉祐七年(1062)二月,正如上文所提到,當司馬光勸諫仁宗秉公處置兗國公主(福康公主)與其婿李瑋之紛爭時,就特別引用大長公主的楷模,作為兗國公主仿效的對象,司馬光這一番話,也是宋廷士大夫對大長公主最有代表性的評價:
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子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妒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為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為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156
在尋常百姓家庭中,最小的女兒通常最受父母寵愛,所謂“謝公最小偏憐女”,而兄長常都愛護幼妹。另一方面,做姑母的常疼愛侄兒,不下自己的親生兒女,姑侄的感情通常很親厚。以前的兒童不像今天我們上學,有一大批同齡的同學,可成為總角之交。他們可以擁有的少年玩伴,從青梅竹馬到兩小無猜,除了親兄弟和從兄弟姊妹外,往往就是父系或母系的表兄弟姊妹,好像《紅樓夢》中寶玉的情況。就算貴為太子,也只有少量被特別挑選的貴戚子弟,通常是太子的兄弟、從兄弟或表兄弟,可以“陪太子讀書”。這些與太子有共學同玩之誼的貴家子,通常是帝王後來另眼相看的人。另外,許多人都會註意到,甚至有親身的體驗,一個家族關系是否和諧,婆媳、妯娌之間的相處常是關鍵,許多家族內部的紛爭往往因婆媳與妯娌不和所致。值得註意的是,有時候姑嫂的關系也影響匪淺,今日有些地方,“姑奶奶”或“姑姑”對她的娘家仍有著很權威的角色,不時幹預或影響著兄弟、兄嫂或弟婦以至侄兒及侄媳的家居生活。
獻穆大長公主是太宗的息女,真宗的幼妹,劉皇後的小姑和仁宗的姑娘。她自幼深得父兄的寵愛,下嫁李遵勗並生兒育女後,一直以尊敬翁姑,愛護夫婿,管教兒女並且謙謹守法,待下仁厚的德行,賺得宋人異口同聲的讚美,譽為最有婦德的公主模楷。我們跳過宋臣的虛文溢美,小心檢視下,可以看到獻穆大長公主的很有智慧的行事:第一,她不像幾位姊姊公主及駙馬姊夫的恃勢驕奢,而一直行事小心謹慎,因而得到兄長的寵愛不衰。第二,在當時儒家男尊女卑,什麽“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妻賢不妬”的迂腐禮教下,她一方面能包容夫婿李遵勗有過私通乳母的劣行,以至納妾的行為;但另一方面又能控制夫婿不再逾軌,從而夫妻得以白頭到老,恩愛不替。而不像四姊揚國大長公主那樣“性妬”,絕不容許夫婿納妾而致柴宗慶無子。也不像從侄孫女、英宗蜀國長公主(後謚魏國賢惠大長公主,1051—1080)那樣,逆來順受地容忍夫婿王詵(1048—1104後)縱情聲色,失德敗行,自己既郁郁以終,夫婿也擔著惡名而不容於帝後。157
第三,她堪稱賢內助,她悉心協助李遵勗交結朝內朝外賢士,讓他得到賢駙馬的令名。當李遵勗在真宗晚年介入以寇準、楊億等為首的朝臣與劉皇後之權爭時,也憑她尊貴的地位身份得以不被牽連降罪。到劉太後攝政,她也曉得如何不招皇嫂的猜忌,並且接受她的拉攏,與她劉家聯姻。憑著這有利的身份,她就得以在關鍵時刻暗中保護侄兒,自然也保護了夫家。
獻穆大長公主對侄兒的愛護可說是無微不至的,仁宗親政後,曾因溺於美色,幾乎不起,又是靠她推薦名醫才救回仁宗一命。是故仁宗一直敬愛她,甚至有將她視為親母的移情狀況。當她病目時,仁宗竟像孝子一樣當眾為她舐目,希冀孝感動天,讓她覆明。仁宗顯然已視她為親母。158而每逢仁宗生日,她必定早一晚入宮留宿,翌晨為侄兒祝壽。這一份姑侄情,只怕尋常人家不一定做得到。另一方面,因愛屋及烏,真宗自小便讓獻穆大長公主的兒女入宮與仁宗一同讀書玩樂,於是讓仁宗和李端懿等表兄弟妹建立深厚的情誼,後來李端懿等得到仁宗無比的寵信和重用,便建基於兒時已培育的表兄弟情分。159
李遵勗一族是仁宗至神宗朝最受寵信的外戚家族之一,這個武將家族由李崇矩起家,到李遵勗尚獻穆大長公主而成為外戚。它能夠在眾多外戚將家中脫穎而出,關鍵人物正是獻穆大長公主。她憑著與真宗及仁宗父子的深厚骨肉親情,以及她善於周旋長嫂劉皇後的手腕,讓夫婿一家避過真宗朝晚年到仁宗朝初年屢起的政治波濤。由於她長期明裏暗裏保護仁宗,到仁宗親政後,她的兒孫便得以大沐皇恩,成為政治影響力不可低估的外戚。事實上,章獻劉太後和仁宗均寵信一大批外戚,委以重任。因這些外戚均是與他們關系深厚而深獲信任的人,其中獻穆大長公主的家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宋代儒家士大夫一直以獻穆大長公主為公主的楷模,當然不僅因她“性不妬”,包容夫婿有過越軌行為及納妾的所謂“婦德”,160而是她既知禮守法,行事謹慎且不以富貴驕奢,並且與夫婿廣交方外及儒士外,最重要的是她沒有借著常出入宮禁兼深得仁宗尊敬的機會,而幹預朝政。另外,她也對兒女嚴加管教,不讓他們無功而得高職。宋代公主與歷代公主一樣,因與帝王至親骨肉的關系,常能出入宮禁,她們每為自己及子孫求取恩典,碰上帝王的溺愛及縱容,常會招致朝臣之非議。不過,整體而言,宋室君主尚能不寵愛女兒或妹妹逾度,而宋代的公主也泰半以獻穆大長公主為榜樣,較能守法,不敢為非。宋代公主的具體情況,也許未來更多的個案研究,能進一步發明之。
後記:
本文初稿在2013年5月3日至4日在台北東吳大學舉行的“第九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究會”上宣讀,蒙擔任本文評論人的黃啟江學長賜予寶貴意見,現據之加以修改,謹向黃學長致謝忱。
2013年8月25日香港理工大學
1、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版;下簡稱《長編》,只註卷數、頁碼)卷九八,乾興元年二月已未至丙寅條,第2272~2273頁;三月甲戌條,第2277頁;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版;下只註卷數、頁碼)卷九《仁宗紀一》,第175~176頁;卷二四八《公主傳·太宗楊國大長公主、衛國大長公主、荊國大長公主》,第8773~8775頁;卷四六四《外戚傳中·李遵勗》,第13568頁;《皇宋十朝綱要》,收入趙鐵寒主編:《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卷二《太宗·公主七》,葉三上(第43頁)。按李遵勗在真宗朝最後拜康州團練使,到仁宗朝最初的官位是澤州防禦使,疑是仁宗繼位時所恩遷。又《皇宋十朝綱要》記三長公主封大長公主,鄧國大長公主在三月,唯申國大長公主及冀國大長公主均在乾興二年二月。筆者疑均在三月,“二月”為“三月”之訛寫。
2、《宋大詔令集》亦收有冀國大長公主兩位姐姐鄧國大長公主及申國大長公主的進封制文。參見《宋大詔令集》(中華書局,1962年排印版),卷三六《皇女一·封拜一》、“福國長公主進封鄧國長公主·仁宗即位”;《建國長公主進封申國大長公主依前報慈正覺大師制·仁宗即位》、《鄂國長公主進封冀國大長公主制·仁宗即位》,第191~192頁。
3、《宋史》卷二四七《宗室傳二·周王元儼》,第8706頁;《長編》卷一四六,慶歷四年正月乙亥條,第3531頁。
4、《長編》卷一七○,皇祐三年三月丙子條,第4086頁;卷一一二,明道二年五月癸酉條,第2616頁。當劉太後賜二公主珠璣帕首時,陳王元份的夫人安國夫人李氏,因頭發脫落,便要求劉太後也賜她帕首。但劉太後不允,並且說:“大長公主,太宗皇帝女,先帝諸妹也,若趙家老婦,寧可比邪?”
5、劉太後在乾興元年四月庚子朔(初一),首先封她的心腹、仁宗的乳母林氏由福昌縣君晉為南康郡夫人。然後又在同月初三,授劉美的女婿光祿寺延馬季良以館職。四天後,又加贈她的三代官職。參見《長編》卷九八,乾興元年四月庚子至丙午條,第2278~2279頁。
6、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校註:《涑水記聞》卷八,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53頁。以下只註頁碼。
7、《長編》卷九八,乾興元年六月庚申至丙寅條,第2283~2287頁;卷九九,乾興元年七月戊辰朔至壬辰條,第2291~2294頁;《宋史》卷九《仁宗紀一》,第 176 頁。劉太後罷丁謂,馮拯晉為首相,王曾升任次相,而錢惟演也晉為樞密使,以酬他們除去丁謂之功。原參政任中正因維護丁謂而被貶。
8、《長編》卷九九,乾興元年八月乙巳條,第2296頁;十一月丁卯朔、辛未條,第2299~2300、第2302頁。馮拯以錢惟演是劉太後姻家,不可預政為由,迫劉太後罷錢為保大節度使。劉太後只好以提高錢的班次在駙馬靜難軍節度使柴宗慶之上,略作補償。
9、《長編》卷一○○,天聖元年正月丙寅至庚午條,第2310頁;正月庚寅條,第2315頁;卷一○一,天聖元年八月甲寅至九月丙寅條,第 2331~2333 頁;閏九月戊戌至己亥條,第2336頁。馮拯早於天聖元年正月初五以疾求退,劉太後不允,因她要找一個她完全信任的人為首相。王欽若就是她的理想人選。馮拯卒於閏九月初八,而劉太後的政敵寇準則於同月初七卒於雷州(今廣東湛江)貶所。順帶一提,錢惟演妹、後嫁劉美的吳興郡夫人錢氏,亦於是年五月初三卒。劉太後輟朝三日,並追封她為越國夫人。
10、《長編》卷一○一,天聖元年十二月丙子條,第2344頁。
11、蘊聰後來又得李遵勗上表求請,獲賜紫方袍,再號“慈照”。又與李遵勗詩文往還的大德,尚有釋重顯(980—1052)、釋歸省及廬山歸宗禪院的妙圓大師吳自寶(978—1054)。釋重顯撰《寄李都尉》一詩,詩雲:“水月拈來作者殊,東西南北謾區區。也知金粟李居士,端坐重城笑老盧。”而釋歸省則撰有《李都尉問和尚生日述成十頌》。按《全宋詩》收入李遵勗所撰《送僧歸護國寺》一詩,詩雲:“雷海譚音出世雄,台巖香社冠禪叢。紅爐點雪靈機密,翠徑斑苔道步通。珠水濾羅晨潄凈,豉蒪縈筯午齋豐。歸帆已應王臣供,金地天龍繞舊宮。”不詳李遵勗贈詩何人,及作於何時。據《國老談苑》所記,李遵勗、楊億和劉筠常聚高僧論宗性。李遵勗還命畫工各繪眾人之像,畫成後名曰《禪會圖》。劉筠是楊億以外,李遵勗最尊禮的朝臣。關於這幅《禪會圖》,宋庠曾有詩志之,其序雲:“有釋子以禪會圖貺余者,此圖即今駙馬都尉李公所制,繪故楊大年、劉子儀及都尉、環禪師等,信一時之盛集。瞻嘆不足,因為紀詠。”詩雲:“法集超初地,工毫構妙緣。星占世外聚,月寫相中圓。指指誰標諭,心心自默傳。惟應阿堵處,俱是到忘筌。”又宋庠弟又撰有《隴西都尉禪會圖》一詩,詩雲:“宴場禪集盛,霜幅繪毫工。竺社同開葉,嵇姿宛送鴻。法身寧滯相,世眼願瞻風。廚鑰方傳寶,非專巖壑中。”他又撰有《上李都尉王都尉啟》,說:“伏審肅奉明恩,改書近社,伏惟慶慰。都尉機靈敏裕,履尚詳華。貫九類而有猷。服千齡而逢聖。聯姻沁館,焜照於天潢;按寵韓壇,總提於師節。”宋祁此啟,不詳撰於何時,唯可知他兄弟與李遵勗及王貽永兩駙馬都有來往。參見楊曾文:《宋元禪宗史》第七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37~545頁;曾棗莊、劉琳編:《全宋文》第十七冊,卷三六二《李遵勗·先慈照禪師塔銘並序》,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第354~355頁;《國老談苑》(與《丁晉公談錄》合本)(中華書局,2012年版)卷一《禪會圖》,第61頁;宋庠:《元憲集》(台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有釋子以禪會圖貺余者,此圖即今駙馬都尉李公所制,繪故楊大年、劉子儀及都尉、環禪師等,信一時之盛集。瞻嘆不足,因為紀詠》,葉二上;宋祁:《景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隴西都尉禪會圖》,葉十二上下;卷五二《上李都尉王都尉啟》,葉十五上下;余靖(1000—1064):《武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廬山歸宗禪院妙圓大師塔銘·嘉祐四年》,葉十六上至十八下:傅璇琮等(編):《全宋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冊,卷一四七《釋重顯一·寄李都尉》,第1654頁;卷一六三《李遵勗·送僧歸護國寺》,第1844~1845頁;陳新、張如安(等):《全宋詩訂補》(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全宋詩漏收的詩人》“釋歸省·李都尉問和尚生日述成十頌”,第769頁。以上諸書,後只註頁碼。
12、《長編》卷一○二,天聖二年三月癸卯條,第2353頁。
13、《長編》卷一○二,天聖二年五月丁酉條,第2356頁;《宋史》卷二四八《公主傳·太宗衛國大長公主》,第8774頁;《皇宋十朝綱要》卷二《太宗·公主七·衛國大長公主》,葉三上(第43頁)。
14、《長編》卷一○二,天聖二年九月庚子至癸卯條,第2367頁;卷一○四,天聖四年四月丁巳條,第2405頁;卷一○六,天聖六年九月癸醜條,第2482頁;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三月癸巳條,第2579頁;《宋史》卷二四二《後妃傳上·仁宗郭皇後》,第8619頁;魏泰撰,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卷二,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1~22頁。張氏是太祖朝三司使驍衛大將軍張美(918—985)的曾孫女,劉太後到天聖四年四月,才將她升為才人,她在天聖六年九月病卒前五天,劉太後才將她晉為美人。另據宋人筆記《東軒筆錄》所記,李氏入宮時才十余歲,只有一弟李用和才七歲,姊弟臨別時,李氏手結刻絲囊予之,作為將來相認之物記。但後來姊弟失去聯絡。他窮困極,在京師鑿紙錢為業,後為入內侍省的一個院子收養於家。到李氏生下仁宗後,劉太後派劉美及內臣張懷德查訪李氏親屬,終於憑這物記找到李用和,劉太後告訴真宗,真宗補授李用和為三班奉職,累遷右侍禁、供奉官。
15、《長編》卷一○二,天聖二年十一月乙巳至辛亥條,第2369頁。
16、《長編》卷一○三,天聖三年正月辛亥至壬子條,第2375頁。劉太後將劉美加贈中書令,其妻錢氏加贈鄆國太夫人。
17、《長編》卷一○三,天聖三年正月丙申、二月乙卯至乙醜條,第2375,2377頁;卷一○四,天聖四年七月乙醜條,第2413頁;卷一○五,三月丙辰條,第2438頁。考王欽若與曹利用便以私意提拔或包庇自己的親屬或故舊有恩之子弟,他們其身不正,自然不會阻止劉太後任用她的親屬。劉太後這時所提升的姻親計有崇儀副使田承說,田庸而自專,他在天聖四年七月獲得一份優差,擔任契丹皇後生辰副使,曾妄傳劉太後的旨意。又避劉太後祖諱而改名的外戚還有石保吉的侄兒石元孫(993—1064),他本名石慶孫,也以避諱而改名。參見《宋史》卷二五○《石守信傳附石元孫》,第8814頁。
18、《長編》卷一○三,天聖三年五月辛醜至癸卯條,第2381頁;《宋史》卷二四五《宗室傳二·漢王元佐附允升、允言、允成》,第8693~8697頁。按元佐有子三人,依次為允升、允言(?—1029)和允成,唯群書均未載他們之壽數,故生年均不詳。據說允升思念其弟,日夜悲哀,於是仁宗對輔臣說,楚王元佐是真宗的同母兄,久疾在家,現時允升兄弟如此孝友,就宜特進其官,以慰楚王。
19、《長編》卷一○三,天聖三年七月辛巳條,第2384頁;十一月戊申條,第2393頁;十二月癸醜條,第2394頁。王欽若早在是年七月,因納賄事而為同列所不滿,劉太後為顧全他的體面,就沒有窮究此事,參政魯宗道不忿,在上朝時曾當眾諷刺他,令他羞愧無地。其他輔臣也漸對他不留情面,以眾人之故,劉太後對他也不像以前百般信任,他於是郁郁以沒。劉太後仍念舊,臨奠出涕,贈他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遣官護葬事,賜白金五千兩,錄其親屬及親信二十余人。據說宋朝開國以來,宰相恩恤未有如他厚。又劉太後在十二月初五,就以次相王曾晉為首相,樞密副使張知白晉位次相。
20、《長編》卷一○四,天聖四年正月甲辰條,第2400頁;五月辛醜條,第2408頁。考真宗四弟雍王元份女華原縣主(輩份是仁宗的從姊),在是年五月又為其門客鄭諫求補官職,也受到拒絕。宋廷下詔入內內侍省提舉郡縣主諸院公事所,從今若無例而求恩澤的,就不得奏聞。這相信又是王曾的意思。
21、《長編》卷一○三,天聖三年十二月乙醜條,第2395頁;卷一○四,天聖四年二月己未條,第2401頁;《蔡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蔡忠惠集》)卷三九《墓志銘二·延安郡主李氏墓志銘》,第708頁。據延安郡主墓志銘所記,她要到天聖五年封長壽縣主,才正式下嫁錢晦。天聖四年二月大概只是定親。
22、《宋史》卷三一七《錢惟演傳附錢晦》,第10342頁。錢晦字明叔,雖是貴戚子弟,但他一生任官行事,都有操守,得到仁宗的欣賞。這大概是冀國大長公主肯將愛女許配給他的主要原因。
23、《宋史》卷二四五《宗室傳二·周王元儼附允迪》,第8706~8707頁。
24、《蔡襄集》(《蔡忠惠集》)卷三九《墓志銘二·延安郡主李氏墓志銘》,第 708 頁;《長編》卷一○五,天聖五年五月癸亥條,第2441頁;《宋史》,卷二四五《宗室傳二·漢王元佐》,第8693~8694頁。考延安郡主在天聖五年何月出嫁沒載,唯其伯父楚王卒於五月,她於禮不可能在至親逝世後的的同一年成婚,故筆者認為她應在天聖五年初,至少在五月前出嫁較合理。
25、《長編》卷一○五,天聖五年十一月癸醜至十二月甲戌條,第2456~2457頁;卷一○六,天聖六年四月壬申條,第2470頁;《宋史》卷四六四《外戚傳中·李遵勗附李端願》,第13568頁、第13570頁。按李遵勗在天聖六年四月已官宣州觀察使,相信是這次恩典澤州防禦使遷升的。他的次子李端願年七歲授如京副使,也有可能在這時得此恩典。
26、《長編》卷一○六,天聖六年二月辛未條,第2464~2465頁;《宋史》卷二四四《宗室傳一·秦王廷美附德鈞》,第8674頁;卷二五○《王審琦傳附王承衍》,第8818頁。考《宋史·宗室傳》記承詡是德鈞的第九子,寫作“承翊”,官至內殿崇班。又宗室中,仁宗的再從姑、秦王廷美女鹹寧郡主在天聖六年二月十三日卒,仁宗幸其第臨奠。參見《宋會要輯稿》“禮四十一之十七”。
27、《長編》卷一○六,天聖六年三月己酉條,第2467頁;四月壬申條,第2470頁;八月戊寅條,第2480頁。按劉筠在出守廬州兩年後卒於任上。李遵勗對亡友之家曾加以存恤。又考李遵勗的前任是在是年三月十四已為京西轉運使的楊嶠 (?—1028 後),楊嶠在是月上奏論澶州造浮橋的問題。又李遵勗在澶州的屬下在城廵檢兼管勾駐泊兵馬石元孫,正是駙馬石保吉之侄。關於楊嶠的事跡及石元孫在澶州的職位問題,可參見何冠環:《北宋外戚將門開封浚儀石氏第三代傳人石元孫事跡考述》,載《新亞學報》第三十卷(2012年5月),第111~112頁,註24。
28、《歐陽修全集》(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二冊,卷三三《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端懿)墓志銘》,第491頁。
29、《蔡襄集》(《蔡忠惠集》)卷三九《墓志銘二·延安郡主李氏墓志銘》,第709頁。
30、《長編》卷一○六,天聖六年九月癸醜至十月戊辰條,第2482~2483頁。
31、《長編》卷一○七,天聖七年正月癸卯至二月辛卯條,第2491~2498頁。一向不順從劉太後的參政魯宗道在二月初一病卒,劉太後又罷免與曹利用交好的次相的張士遜,而終於補上呂夷簡為次相。
32、《長編》卷一○八,天聖七年六月丁未至己酉條,第2515~2518頁。
33、《長編》卷一○八,天聖七年九月戊午條,第2522頁;十一月癸亥條,第2526~2527頁。
34、《長編》卷一○九,天聖八年四月甲午、辛亥條,第2539頁;六月乙巳條,第2541頁;九月乙醜條至己巳條,第2544頁。
35、《長編》卷一○九,天聖八年十一月乙卯條,第2547頁;卷一二三,寶元二年三月丙辰條,第2900頁。
36、《長編》卷一○十,天聖九年正月辛未條,第2553頁;九月己巳條,第2566頁。
37、《長編》卷一○十,天聖九年十一月乙未條,第2571頁。考錢曖是錢惟演長子,冀國大長公主婿錢晦長兄。
38、《長編》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二月丁卯條、三月癸已條,第2577~2579頁;孫升(1037—1099)(撰),楊描倩、徐立群(點校):《孫公談圃》(與《丁晉公談錄》合本)(中華書局,201年版)卷上《仁宗生母李淑妃》,第107~108頁;《東軒筆錄》卷四,第43頁。據宋人筆記《孫公談圃》所記,當李氏病逝時,仁宗並不知她是其生母。這時楊太妃(章惠楊太後)病革,仁宗去視疾,楊氏就密告仁宗李氏實為他生母的真相。據說仁宗聽後大慟,即見執政,欲為李氏行服。劉太後不允,眾人也不敢說話,只有呂夷簡對劉太後直言利害,說“陛下萬歲後,獨不念劉氏乎?”於是劉太後大悟,為李氏發喪,但“宮中稍有異說”。到劉太後病逝,仁宗即人派人發李氏之棺,見形色如生,鬢發郁然無少異,於是存撫劉氏族人。孫升這一則筆記所記之事,相信是《長編》所本(按:李燾在註中並未言明);不過,所記章惠楊太後在李氏死時即密告仁宗身世,而仁宗早在劉太後死前已知李氏是其生母的說法,未有被李燾所采用。考楊太後一直是劉太後心腹,在宮中保育仁宗,她不太可能違逆劉太後之意揭露此一大秘密。而據群書所記,仁宗要到劉太後死後,才知悉自己的生母是誰。又據《東軒筆錄》所記,李宸妃之葬,劉太後本來下令鑿內城垣以出靈柩,呂夷簡力爭鑿垣非禮,應開西華門以出靈柩。劉太後初時不允,但呂夷簡警告執行此事的內臣入內都知羅崇勳將來的後果,最後劉太後經羅的苦苦求告,終於答允呂夷簡所請。
39、《涑水記聞》卷八,第153頁。
40、《全宋文》第十七冊,卷三六二《李遵勗·先慈照禪師塔銘並序》,第354~355頁;《宋史》卷四六四《外戚傳中·李遵勗》,第13568頁。考李遵勗上奏三說五事,未載在何時何地。不過,他在天聖六年後出守澶州,似乎他在外上書可能性較高。
41、《長編》卷一一一,明道元年十月戊午至十一月辛卯條,第2591~2593頁;十二月丙午條,第2596頁;《宋史》卷四六四《外戚傳中·李遵勗》,第13568頁;《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57 年影印版),“帝系八之一”。劉太後在明道元年十月戊午(二十)加贈元儼之母昭媛王氏為太儀,志在拉攏元儼。
42、《宋大詔令集》卷三七《皇女二·封拜二》“冀國大長公主進封魏國大長公主制”,第197頁。
43、《長編》卷一二二,寶元元年八月庚辰條,第2878頁;《宋史》卷四六四《外戚傳中·李遵勗》,第 13568~13569頁。考《宋史》李遵勗本傳稱李入奏在“天聖間”。
44、《長編》卷一一二,明道二年二月甲辰至三月壬申條,第2605~2606頁;三月庚寅至乙未條,第2609~2610頁;《宋史》卷一○《仁宗紀二》,第194~195頁;卷四六四《外戚傳中·李遵勗》,第13568頁;《蔡襄集》(《蔡忠惠集》)卷三九《墓志銘二·延安郡主李氏墓志銘》,第709頁。據載劉太後在病重不能言的情況,仍多次牽引其衣。參政薛奎對仁宗說,劉太後是想服袞冕而終,但薛奎認為若順從她的意思,衣以帝服,就無以向死去的真宗交待。仁宗接受薛的意見,只以後服成斂。
45、周煇(1127—1198後)撰,劉永翔校註:《清波雜志校註》(中華書局,1994年版)卷一《祖宗家法》,第15頁;《長編》卷四八○,元祐八年正月丁亥條,第11416頁。考在元祐八年(1093)正月,哲宗(1077—1100,1085—1100在位)召宰執講《禮記》及讀《寶訓》時,宰相呂大防(1027—1097)談到“祖宗所立家法最善”,他就提到其中之一就是仁宗以侄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並說“此事長之法也”。
46、《長編》卷一一二,明道二年四月壬寅條,第2610頁;邵伯溫(1056—1134)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中華書局,1983年版)卷八,第77頁;《龍川別志》(與《龍川略志》合本)卷上,第79頁;《涑水記聞》卷八,第153頁。據司馬光引述李端願另一則說法,仁宗因劉太後管束過嚴,早已怨恨劉太後而親近愛護他的楊太後。
47、《涑水記聞》卷八,第153頁。
48、《長編》卷一二八,康定元年九月甲戌條,第3044頁。
49、《宋會要輯稿》“禮四十一之十七”;《皇宋十朝綱要》卷二“太宗”《公主七·楊國大長公主》,葉三上(第43頁);《長編》卷一一二,明道二年七月戊寅條,第2622頁。
50、《長編》卷一一三,明道二年九月丙寅至丁卯條、甲申條,第2635~2636頁;卷一一五,景祐元年七月乙巳條,第2690頁。考劉太後的另一姻親馬季良在九月廿二,再貶為左屯衛將軍、滁州(今安徽滁州)安置,而錢惟演在景祐元年七月卒於隨州。仁宗雖不喜他,但仍特贈他侍中,命官護葬事。
51、《長編》卷一一三,明道二年九月己卯至十月丁酉條,第2635~2637頁;十月己酉至丙辰條,第2639~2640頁;十一月癸亥朔至丙子條,第 2642~2644 頁;《皇宋十朝綱要》卷三“真宗”《公主二·升國大長公主》,葉二下(第84頁)。
52、《長編》卷一四六,慶歷四年正月乙亥條,第3531頁。
53、《長編》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一月甲戌至戊寅條,第2643~2644頁。
54、《長編》卷一一四,景祐元年四月甲午條,第2672~2673頁;《東軒筆錄》卷三,第26頁;《龍川別志》卷上,第75頁。考李燾據《龍川別志》的記載,以收藏楊億詔誥是王曙,而非李遵勗,但沒有提出有力的理由來否定《東軒筆錄》的說法。筆者認為以李遵勗與楊億的親密關系,而李的駙馬身份,楊億托他收藏牽涉重大機密的文書,較交由後來被貶出外的王曙收藏更合理。又李遵勗此時已遷鎮國軍節度使。
55、《宋史》卷四六四《外戚傳中·李遵勗》,第13568~13569頁;《長編》卷一二二,寶元元年八月庚辰條,第2878頁。
56、《長編》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二月甲寅至乙卯條,第2648~2654頁。
57、《長編》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八月癸亥至庚午條,第2693~2695頁。
58、《長編》卷一一五,景祐元年八月壬申至壬午條,第2696~2697頁;卷一六八,皇祐二年七月丁亥條,第4048頁;卷一六九,皇祐二年十月乙亥條,第4063頁。王懷節是真宗朝陷遼的王繼忠(?—1023後)兒子,他走尚美人的門路而謀求獲管軍之任。考仁宗余情未斷,尚美人後來又覆召入宮。唯何年月再入宮不詳。仁宗在十七年後之皇祐二年七月初二贈她為充儀。她當在皇祐二年七月前已卒。至於楊美人也在皇祐二年十月覆位為婕妤,大概也得到覆召。
59、考《長編》此條記載當采自範鎮(1008—1089)所撰的《東齋記事》。參見範鎮撰,誠剛點校:《東齋記事》(與《春明退朝錄》合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卷一,第5頁;《長編》卷一一五,景祐元年九月戊子條,第2698頁;卷一四五,慶歷三年十二月庚戌條,第3514頁。又許希醫術精湛,不知是否大長公主的推薦介紹,仁宗從兄允升之家看上許的兒子,在慶歷三年十二月十七欲以其為婿。不過,權禦史中丞王拱辰(1012—1085)卻以許希並非士族,與皇族通婚會亂宗室之制,奏上仁宗請罷之。仁宗接受王之意見。
60、長編》卷一一五,景祐元年九月丁酉至乙巳條,第2699~2701頁。按仁宗寵信的內臣、入內都知閻文應子勾當禦藥院閻士良(?—1037後)也反對立陳氏女為後。
61、《宋會要輯稿》“禮四十一之十七”。考景祐元年正月十八日,楚王元佐長子、安國軍節度使延安郡公允升卒。至於允寧則是仁宗叔父陳王元份(後改封潤王)之長子。他們兩人都是魏國大長公主的親侄。參見前註。
62、《長編》卷一一六,景祐二年二月戊辰至庚辰條,第2722~2723頁。
63、《長編》卷一一六,景祐二年四月丙辰條,第 272頁;《隆平集校證》(曾鞏撰,王瑞來校正,中華書局,2012年版)卷九《李崇矩傳附李遵勗》,第 280 頁;《宋史》卷四六四《外戚傳中·李遵勗》,第13568頁。
64、《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二十一”。
65、《長編》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一月戊子至丙子條,第2762~2764頁;十二月辛亥朔條,第2764頁;《宋史》卷二四四《宗室傳一·魏王廷美附德文》,第8674~8675頁;卷二四五《宗室傳二·濮王允讓》,第8708頁。按德文本秦王廷美第八子,因其兄三人早卒,故德文於次為第五。仁宗稱這位從叔為“五相公”而不名。他與楊億交好,楊億卒時,曾為詩十章以悼。仁宗在十二月初一,因眾多言官特別是範仲淹的劾奏,將涉嫌指示禦醫謀害郭皇後的入內都都知閻文應解職,貶為秦州鈐轄,連他的兒子閻士良均逐出京師。
66、《長編》卷一一四,景祐元年閏六月辛酉條,第2681頁;卷一一七,景祐二年十二月戊午條,第2766頁;卷一一九,景祐三年八月丙辰條,第2799頁;寶元元年三月戊戌朔條,第2866頁;《宋史》卷二五七《李崇矩傳附李繼昌》,第8956頁;卷四六四《外戚傳中·李遵勗附李端懿、李端願》,第13569~13570頁;《元憲集》卷二一《駙馬都尉李遵勗兄加贈太師制》,葉三上下;《歐陽修全集》第二冊,卷三三《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端懿)墓志銘》,第491頁。考宋庠此制撰於何時不詳,他在景祐元年閏六月初四已任知制誥,至景祐三年八月十一,仍以知制誥使遼。(按:《長編》此條誤作宋庠之名訛寫作其弟宋祁),到寶元元年(1038)三月初一改授翰林學士。他在整個景祐時期都任知制誥。又李遵勗有兄弟二人,分別是李文晟和李文旦。宋庠這道制文沒說加贈太師的李遵勗兄長是哪一人,只說:“具官遵勗亡兄具官累贈太傅某,寬明莊重,淳深幹敏。克纂堂構,自結本朝。以通侯之世家,備能臣之煩使。預平狂狡,陰濟惠和。或握節聘戎,譽高使表,或剖璋臨郡,政推邊最。”又李端懿自七歲授如京副使後,歷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其墓志沒有具體記載他何年任哪一使職。猜想他到景祐二年應已擢至諸司使臣最低一階的供備庫使。至於其弟大概在這時授如京副使。
67、《長編》卷一一八,景祐三年正月壬辰、二月壬子條,第2774~2775頁。
68、《全宋文》第四十六冊,卷九八四《宋仁宗四十五·天聖廣燈錄序·景祐三年四月》,第14~15頁。
69、《長編》卷一一九,景祐三年七月乙未條,第2796頁;《宋史》卷二四四《宗室傳一·燕王德昭附守節》,第8679頁。
70、《全宋文》第十七冊,卷三六二《李遵勗·昭德新編原序·景祐三年七月》,第353頁。
71、《長編》卷一一九,景祐三年十月辛酉條,第2809頁。
72、《長編》卷一一九,景祐三年十一月戊寅至戊戌條,第2811~2812頁;卷一二○,景祐四年二月己酉條,第 2820頁;《涑水記聞》卷八,第153頁。據司馬光引述李端願的說法,仁宗對章惠楊太後比劉太後要親近得多。事緣劉太後性格嚴厲,動輒以禮法禁止年幼的仁宗起居,未嘗假以詞色。相反,章惠楊太後就以恩撫育仁宗。仁宗苦多痰,劉太後禁蝦蟹等海鮮進禦,楊太後知仁宗喜歡吃,就偷偷藏下給仁宗享用,並說:“太後何苦虐吾兒如此。”仁宗於是怨恨劉太後而親近楊太後,在宮中稱劉太後為大孃,楊太後為小孃。當劉太後死後,就尊楊為太後,曲意奉事楊太後。楊太後弟楊景宗,少為役兵,性兇悍使酒,好以滑槌毆人,人稱為“楊滑槌”,屢次犯法,仁宗均以楊太後之故優容之。仁宗甚至將沒收的丁謂故第賜給他。
73、《長編》卷一二○,景祐四年二月壬子條,第2820頁。
74、《長編》卷一二○,景祐四年三月庚子條,第2825頁。
75、《長編》卷一一九,景祐三年十一月戊寅條,第2811頁;卷一二○,景祐四年五月庚戌條,第2831頁;六月甲午條,第2833頁;卷一二二,寶元元年十月辛未條,第2883頁;卷一二三,寶元二年六月壬申條,第2909頁。宗實在翌年(寶元元年,1038)十月累遷至左領軍衛將軍,他一直由曹皇後養於宮中,直至寶元二年六月十三時年八歲時,才從宮中返本第,並加右千牛衛將軍。
76、《長編》卷一二○,景祐四年十二月辛卯條,第2843頁。
77、吳曾(?—1162後):《能改齋漫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一版),卷一二《柴主與李主角富貴》,第 359 頁。據吳曾所記,兩位長公主都有賢名。柴宗慶因無子,他所積俸緡有數屋之多,未嘗使用。到他死後,都送還朝廷。
78、《長編》卷一二二,寶元元年八月庚辰條,第2878頁;《元憲集》卷二九《賜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為疾病乞致仕不允批答一》、《賜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為疾病乞致仕不允批答二》,葉十三上至十四上。
79、《長編》卷一七○,皇祐三年三月丙子條,第4086頁;《宋史》卷二四八《公主傳·荊國大長公主》,第8775頁;卷四六四《外戚傳中·李遵勗》,第13569頁;《宋會要輯稿》“禮四十一之十七”;李濂(1488—1566)撰,周寶珠、程民生點校:《汴京遺跡志》卷九《陵墓·李駙馬墓、李留後墓》,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143頁。
80、《元憲集》卷三《贈駙馬都尉李和文挽詞二首》,葉九上。
81、《宋史》卷四六四《外戚傳中·李遵勗》,第13569頁。考李遵勗的兩本集子不傳,除了《天聖廣燈錄》外,他傳世的詩文只有《全宋文》所收的幾篇序文和《全宋詩》所收的詩一首《送僧歸護國寺》,參見前註。
82、《長編》卷一七○,皇祐三年三月丙子條,第4086頁;《蔡襄集》(《蔡忠惠集》)卷三九《墓志銘二·延安郡主李氏墓志銘》,第709頁。
83、《長編》卷一七○,皇祐三年三月丙子條,頁4086;《歐陽修全集》,第二冊,卷三三《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端懿)墓志銘》,第492頁。
84、《長編》,卷一二四,寶元二年七月庚寅朔條,第 2918 頁;《宋史》卷二四四《宗室傳一·燕王德昭附守節》,第8679頁。守節輩份是仁宗的從侄,大長公主的從侄孫,性孝謹,其母譙國夫人杜氏有病,他曾刺臂血寫佛經。其舅杜從保卒,他又為鞠養二孤,為其畢婚嫁。他又治家嚴肅,頗通時務,故仁宗委他同知大宗正事。
85、《長編》卷一二四,寶元二年九月甲午至己亥條,第2923~2924頁;《宋史》卷二四八《公主傳·仁宗周陳國大長公主》,第8776~8777頁;《皇宋十朝綱要》卷四《仁宗》“公主十三·周陳國大長公主、徐國大長公主”,葉二下(第126頁)。據《宋史》,福康公主卒於熙寧三年(1070),年三十三,則公主當誕於寶元元年。仁宗封她公主之號,當在她周歲之後。又據《皇宋十朝綱要》所載,福康公主在寶元元年受封,與《長編》所記不符;而其記崇慶公主受封,則在寶元二年九月。疑記福康公主受封之年有誤,現從《長編》所記。又崇慶公主卒於慶歷二年(1042)五月早夭,追封楚國公主,她生年是否同為寶元元年不詳。她在元符三年(1100)三月追封徐國大長公主。另福康公主之母為苗昭容,崇慶公主之母為俞婕妤。關於仁宗問大長公主月俸錢之事,參見前註。
86、《長編》卷一二六,康定元年正月癸酉至庚辰條,第2965~2969頁。關於石元孫外戚子弟的家世及其仕歷,以及其兵敗三川口之始末,可參閱何冠環:《北宋外戚將門開封浚儀石氏第三代傳人石元孫事跡考述》,載《新亞學報》第三○卷(2012年5月),第99~161頁。
87、《長編》卷一二六,康定元年三月戊寅條,第2987~2988頁;《宋史》卷四六四《外戚傳中·王貽永》,第13561~13562頁。
88、宋祁:《景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八《李郡王墓志銘》,葉十一下;《長編》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癸卯條,第3061頁。
89、《長編》卷一二八,康定元年七月戊寅條,第3031頁。
90、《長編》卷一二八,康定元年九月戊辰條,第3042~3043頁。同時擢任樞密副使的還有刑部侍郎杜衍(978—1057)和右諫議大夫鄭戩(?—1049)。
91、《長編》卷一二八,康定元年九月甲戌條,第3044頁。
92、《長編》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月癸未條,第3050頁;《涑水記聞》卷八,第149頁。
93、張氏在慶歷元年十二月丁酉(廿二)再進位修媛。參見《長編》卷一三四,慶歷元年十二月丁酉條,第3208頁。關於仁宗與張貴妃的一段愛情,可參見張明華:《北宋宮廷的〈長恨歌〉──宋仁宗與張貴妃宮廷愛情研究》,載《鹹寧學院學報》第32卷第1期(2012年1月),第22~26頁。
94、《長編》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一月戊午條,第3055頁。
95、《宋史》卷一一《仁宗紀三》,第211頁;卷一三一,慶歷元年二月己醜至己亥條,第3100~3104頁;卷一三二,慶歷元年五月乙醜條,第3127頁。
96、《長編》卷一三三,慶歷元年八月壬午至甲申、丁亥條,第3161~3162頁。
97、《長編》卷一三四,慶歷二年正月辛亥條,第3213頁。
98、仁宗早在慶歷元年四月,便委用在 西邊頗有戰功的曹皇後之權父營琮(938-1045)以定國軍留後為陜西副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副使,太祖男父杜審瓊(897-960)曾撲杜惟序(2—1042 後)為供各庫使領忠州刺史為陜西鈐錯兼巡笞緣邊州。又在十一月以李昭亮白殿前都虞候、感德軍留後、秦鳳副部署兼本路招討經咯安撫副使。後米因韓琦的進言,在慶歷=年正月將李昭亮徙為永興軍部署。而在慶歷二年三月初一前,外戚李用和、曹琮和李昭亮分別擔任馬軍副都揮使、步軍副都揮使及殿前都虞候的三衙管軍要職。到是年十一月十六前,三人已分別擁為殿帥、馬帥和步帥。三衙管軍統由外感出任。參見《長編》卷一三一,慶歷元年四月甲中至丙成條,第3115 頁:卷一三四,慶歷元年十一月王子條,第3196頁:卷一三五,慶歷二年正月癸西條,第3219頁:三月甲辰朔條,第3227 頁:卷一三八,慶歷二年十一月乙西條,第3325頁。
99、《長編》卷一三五,慶歷二年三月庚申條,第3228頁。
100、《長編》卷一三六,慶歷二年五月戊申、壬子、戊午條,第3248,3250,3265頁;卷一三七,慶歷二年八月壬申朔條,第3288頁;卷一四一,慶歷三年五月甲午條,第3381頁;《皇宋十朝綱要》卷四《仁宗》“皇後四·溫成皇後張氏”,葉一下(第124頁);《公主十三·鄧國大長公主》,葉二下(第126頁)。考安壽公主為仁宗第三女,元符三年改封鄧國大長公主,政和四年改封莊順大長帝姬。張修媛誕三女,後來的謚號分別是莊順、莊定和莊謹,安壽公主居長。又荊王願意納公使錢,是他的翊善王渙力勸之功勞。他領荊州、揚州兩節鎮,每年應得公使錢二萬五千緡,一半即是一萬二千五百緡。
101、《長編》卷一三七,慶歷二年閏九月癸未條,第3300頁。
102、《長編》卷一三八,慶歷二年十月癸卯、己酉、辛亥至癸醜條,第3309~3310頁。
103、《長編》卷一三九,慶歷三年正月庚午至辛未條,第3337頁。仁宗在皇三子病重時令學士蘇紳草制封他為鄂王、武昌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但未及宣制,鄂王便夭亡。仁宗贈亡子太師、中書令,謚悼懿。
104、《長編》卷一四二,慶歷三年八月乙未朔條,第3415頁。
105、《長編》卷一四二,慶歷三年八月丁未、壬子條,第3417~3418,3421頁。按鄆國公主母為禦侍馮氏。
106、《長編》卷一七○,皇祐三年三月丙子條,第4086頁。
107、《長編》卷一四六,慶歷四年正月乙亥條,第3531頁。
108、《宋史》卷一一《仁宗紀三》,第215~216頁;《長編》卷一四○,慶歷三年三月戊子至丙申條,第3358~3361頁;四月甲辰至乙巳條,第3363~3364頁;卷一四二,慶歷三年八月丁未、癸醜條,第3417頁、第3421頁。當範仲淹入朝為參政時,韓琦以樞密副使代範出為陜西宣撫使。
109、《長編》卷一四四,慶歷三年十月癸亥條,第3486頁;《宋史》卷四六四《外戚傳中·李遵勗附李端懿》,第13569頁。又據沈括(1031—1095)的記載,神宗向皇後(1046—1101)之母是李遵勗兄李文旦女,亦算是獻穆大長公主的侄女。故此向皇後父向經在慶歷三年以大長公主的表奏,授秘書省正字出身。參見沈括撰,楊渭生新編:《沈括全集》上冊(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長興集十六》(原《長興集》卷二八》《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同州刺史兼禦史大夫知青州兼管內隄堰橋道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兼本州兵馬都總管上柱國河間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實封二百戶贈侍中向公墓志銘·熙寧九年七月》,第120~123頁。
110、《歐陽修全集》第三冊,卷五三《送李太傅端懿知冀州》,第755頁。
111、蘇舜欽撰,傅平驤、胡問陶校註:《蘇舜欽集編年校註》,卷二《送李冀州詩》,巴蜀書社,1991 年版,第138~139頁。
112、《歐陽修全集》第二冊,卷三三《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端懿)墓志銘》,第492頁。李端懿出知冀州前,歷如京副使、文思副使、供備庫使、洛苑使、新州刺史、康州、懷州團練使。卻一直沒有正式擔任外職。
113、《長編》卷一四五,慶歷三年十二月辛醜條,第3512頁;卷一四六,慶歷四年正月乙亥條,第3531~3532頁。
114、《長編》卷一四六,慶歷四年二月壬寅條,第3540~3541頁。
115、《長編》卷一四七,慶歷四年三月己巳條,第3555~3556頁。
116、《長編》卷一四九,慶歷四年五月甲戌至乙亥條,第3609頁。仁宗的皇七女也是禦侍馮氏所出,仁宗在同月十三封她為崇因保祐大師,賜名懿安,但仍保不住幼女於翌日夭亡。
117、《長編》卷一五一,慶歷四年七月戊寅條,第3667~3668頁。
118、《長編》卷一五一,慶歷四年八月壬子條,第3687頁,《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二之四”。焦從約的家世及事跡記載不多,《宋會要》記他在皇祐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內藏庫副使卒。
119、《長編》卷一五三,慶歷四年十二月己亥條,第3725頁;卷一五五,慶歷五年四月辛卯條,第3768頁。仁宗在慶歷五年四月初五封皇八女為鄧國公主,師號如故,稍後又進齊國公主,但仍保不住她的小命。是月即夭折,仁宗追贈韓國公主。張修媛所生三女無一存活。
120、《長編》卷一五四,慶歷五年正月辛酉條,第3735頁;卷一五五,慶歷五年四月丙申條,第3769頁;五月甲申條,第3774頁;卷一五六,慶歷五年閨五月戊子條,第3777頁。後兄曹傅先在正月初四以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卒,仁宗特輟朝二日,贈保信節度使,謚恭懷。然後是仁宗的表弟、李用和子西頭供奉官李瑛在四月初十卒。仁宗亦特輟朝,贈李瑛如京使、榮州刺史。再是曹皇後叔父馬軍副都指揮使曹琮在五月廿九卒。仁宗親臨祭奠,為制挽辭。曹皇後亦一再出視喪事,就曹第成服。仁宗贈曹琮安化節度使兼侍中,謚忠恪。
121、王貽永在慶歷五年六月十四,仁宗以他由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到慶歷六年二月初二,仁宗再加他同平章事。參見《長編》卷一五六,慶歷五年六月戊辰條,第3785頁;卷一五八,慶歷六年二月癸醜條,第3820頁。
122、《長編》卷一五四,慶歷五年正月丁醜,第3739頁;二月癸巳、癸卯至甲辰條,第3746~3747頁;卷一五五,慶歷四月戊子條,第3767~3768頁;五月壬戌條,第3771頁;卷一五六,慶歷五年閏五月己酉條,第3779頁;卷一五七,慶歷五年八月甲子條,第3797頁;十月甲子條,第3803頁;十二月癸醜條,第3810~3811頁;卷一六一,慶歷七年九月癸酉條,第3885頁。魏昭昺是魏鹹信子,份屬仁宗的從表兄,他與郭承祐在慶歷五年二月初六給言官嚴劾,仁宗只好將他們調職。然後在同月十六,安靜節度使允迪在父喪期間,竟然命妓女在宮中日為優戲,給妻昭國夫人錢氏告發。仁宗命入內副都知岑守素到本宮按問得實,就將他降授為右監門衛大將軍,不許朝謁。其妻錢氏亦度為洞真宮道士。再到是年四月初二,從讜射殺親事官。知諫院余靖曾為他說情,但仁宗不報,從讜不久即自殺身亡。又仁宗為了安撫母舅,在是年八月十一,又給他的表弟李璋一份優差,以他自供備庫副使擔任契丹國母正旦副使。又仁宗卻在是年十二月初二,不理言官的反對,覆用郭為殿前都虞候並代副部署兼知代州。仁宗在慶歷七年九月,又再擢楊景宗為建寧軍留後知潞州,特給節度使俸。
123、《長編》卷一五四,慶歷五年正月乙酉至丙戌條,第3740~3741頁。
124、陳耆卿(1180—1236):《嘉定赤城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七《教院三十有一·白蓮寺》,葉十四下。
125、《長編》卷一五八,慶歷六年六月丙子條,第3833~3836頁;卷一五九,慶歷六年八月癸酉條,第3844~3845頁;卷一六○,慶歷七年三月乙未條,第3865頁。考賈、吳二人之爭一直未息,最後到慶歷七年三月乙未,二人一齊被罷出朝廷。
126、《長編》卷一五八,慶歷六年四月癸卯至丙午條,第3828~3829頁;六月丙子條,第3833頁。德文是秦王廷美兒子中最長壽的,他天性畏謹,晚年被足疾不能上朝。仁宗在他卒後三天,又封他的侄兒、德鈞子承簡為徐國公。六月丙子,又封他的長子承顯為康國公。順帶一提,仁宗早夭之姊姊的生母、入道多年的真宗賢妃法正悟真大師杜氏也在七月底卒。仁宗在八月初一,特贈她貴妃。
127、《長編》卷一五八,慶歷六年四月辛未條,第3826頁;卷一五九,慶歷六年七月庚寅條,第3840頁;八月己未條,第3843頁;卷一六○,慶歷七年正月癸未條,第3860頁;卷一六一,慶歷七年七月壬午條,第3881頁。仁宗對張修媛愛寵有嘉,在慶歷七年正月癸未,還將他的叔父張堯佐自祠部郎中擢任戶部副使。到七月壬午,再擢他為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
128、《長編》卷一六○,慶歷七年五月丙子條,第3873頁;吳曾:《能改曾漫錄》卷一二《仁宗厚遣公主》,第347頁。
129、《長編》卷一六一,慶歷七年十一月戊戌至十二月丁巳條,第3890~3893頁;卷一六二,慶歷八年正月甲戌至閏正月庚子朔條,第3902~3906頁。
130、《長編》卷一六三,慶歷八年二月丁醜條,第3918頁;《歐陽修全集》第二冊,卷三三《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端懿)墓志銘》,第492頁;《宋史》卷四六四《外戚傳中·李遵勗附李端懿》,第13569頁。考李端懿墓志所記的妖人作“李校”。據群書所記,這個李校其實在冀州已自經而死,但王則作叛時,卻聲言李校未死,逃在貝州。於是李端懿坐失察貶官。後來討平王則,從叛者並無李校,於是李端懿覆官為防禦使。
131、《長編》卷一六二,慶歷八年正月辛未條,第3901~3902頁;閏正月辛酉至甲子條,第3909~3912頁。
132、《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二之四、十三之八”。按《宋會要》編者稱特贈官予李端憲是“有司之失”,筆者認為這是仁宗給大長公主的特恩。
133、《長編》卷一六三,慶歷八年三月乙醜條,第3937頁;卷一六四,慶歷八年四月甲戌條,第3944頁;七月丙辰條,第3958頁;卷一六五,慶歷八年十月壬午條,第3969~3970頁;十二月丁卯條,第3975頁。
134、《長編》卷一六五,慶歷八年十一月癸亥條,第3975頁;十二月壬午條,第3978頁。
135、《長編》卷一六五,慶歷八年十一月戊戌條,第3972~3974頁;《宋史》卷三一七《錢惟演傳附錢晦》,10342頁;《文恭集》卷一九《魏國大長公主親外孫女錢氏可封壽安縣君制》,葉十九下;《蔡襄集》(《蔡忠惠集》)卷三九《墓志銘二·延安郡主李氏墓志銘》,第709頁。據錢晦妻延安郡主墓志銘所載,其長女適宗室右班殿直趙思覆,封壽安縣君,而先延安郡主兩年而亡。考郡主卒於皇祐四年正月,即壽安縣君卒於皇祐元年至二年間。胡宿所撰之《魏國大長公主親外孫女錢氏可封壽安縣君制》未有記撰於何年月。疑當在皇祐元年前。
136、《長編》卷一六六,皇祐元年三月己亥條,第3991頁。據吳曾所記,李端懿、李端願兄弟問卜人李易簡說:“富貴吾不憂,但問壽幾何?”李易簡不客氣地回答:“二君,大長公主之子。生而富貴,窮奢極欲。又求長壽,當如貧者何?造物者如此,無乃不大均乎?”李於是不肯為二人卜壽。參見《能改齋漫錄》,卷一三《記事·李端懿端願卜人壽》,第389頁。
137、《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一之廿八、十二之四”。
138、《長編》卷一七○,皇祐三年三月丙子條,第4086~4087頁;《宋史》卷二四八《公主傳·荊國大長公主》,第8775頁。大長公主何時患目疾,群書均未載具體年月,唯從仁宗令曹皇後及張貴妃往問候之事看,當最早在慶歷八年十二月初三張貴妃獲冊封後,又據胡宿(996—1067)在皇祐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代中書樞密所上之奏表,談到“近者魏國大長公主虧和感疾”而仁宗“特紆法駕之尊,躬展家人之禮。泫然流涕,親為舐瞳”的事,而稍後所上第二代又說“近以齊國大長公主晦明生疾,奄忽冥升”,筆者認為大長公主失明很有可能在皇祐二年以後。參見胡宿(966—1067):《文恭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代中書樞密院乞乾元節用樂第一表》、《代中書樞密院乞乾元節用樂第二表》,葉二下至五上。
139、郭若虛撰,鄧白註:《圖畫見聞志》卷三,四川美術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頁。
140、《長編》卷一六八,皇祐二年七月丙申條,第4049頁;卷一六九,皇祐二年八月丁卯條,第4057頁;《宋會要輯稿》“禮四十一之十八”。仁宗於皇祐二年七月十一日幸李用和第視疾,入見於臥內,擢其次子西上![]() 門副使李珣為西上
門副使李珣為西上![]() 門使,並以所居賜之,又日給官舍僦錢五千。李用和於同月十九日卒,仁宗再往李宅臨奠慟哭,贈李用和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仁宗特輟視朝五日,制服苑中,謚恭僖。仁宗又親為母舅撰神道碑,篆額“親賢之碑”。仁宗又在八月十三日,將李用和長子李璋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擢為步軍都虞候;次子西上閤門使李珣領文州刺史;駙馬都尉李瑋領保州團練使。但李璋辭不接受。
門使,並以所居賜之,又日給官舍僦錢五千。李用和於同月十九日卒,仁宗再往李宅臨奠慟哭,贈李用和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仁宗特輟視朝五日,制服苑中,謚恭僖。仁宗又親為母舅撰神道碑,篆額“親賢之碑”。仁宗又在八月十三日,將李用和長子李璋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擢為步軍都虞候;次子西上閤門使李珣領文州刺史;駙馬都尉李瑋領保州團練使。但李璋辭不接受。
141、《長編》卷一七○,皇祐三年三月丙子條,第4087頁。
142、《長編》卷一六六,皇祐元年正月辛亥條,第3982頁;三月癸卯條,第3996頁;卷一六七,皇祐元年九月乙未條,第4013~4014頁;卷一六八,皇祐二年六月戊辰、庚辰條,第4045頁、第4047頁;仁宗先在皇祐元年正月十八,將張堯佐擢為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到三月十一,又任他為權三司使。到九月初五,不顧言官的反對,將他真除為三司使加禮部侍郎。仁宗又在皇祐二年六月十三日,贈張貴妃母越國夫人曹氏之曾祖曹旭為秘書丞,祖曹靖為祠部員外郎;又在同月廿五日,特封張貴妃第八妹為清河郡君。
143、《長編》卷一六八,皇祐二年三月己酉條,第4035頁。
144、《長編》卷一六八,皇祐二年六月辛未至丙子條,第4046~4047頁;卷一六九,皇祐二年八月丁巳至己未條,第4053~4056頁。
145、《長編》卷一六九,皇祐二年閏十一月己未至己巳條,第4067~4070頁。
146、《長編》卷一七○,皇祐三年正月乙醜至庚午條,第4077頁;《宋史》卷一二《仁宗紀四》,第230頁。
147、《長編》卷一七○,皇祐三年三月丙子條,第4085~4087頁;四月丙戌條,第4088頁;《宋會要輯稿》“禮三十五之十一、十二”、“禮四十一之一、十八、廿五”、“禮五十七之三十六”、“選舉三十一之十六”;《宋大詔令集》卷一四六《典禮三十一·喪服上》《以獻穆大長公主薨宰相乞聖節舉樂不允批答·皇祐三年三月戊午》,第535頁;《宋史》卷一二《仁宗紀四》,第230頁;卷四六四《外戚傳中·李遵勗附李端懿、李端願、李端愨、李評》,第13569~13572頁;《歐陽修全集》第二冊,卷三三《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端懿)墓志銘》,第491~492頁;《蔡襄集》(《蔡忠惠集》)卷三九《墓志銘二·延安郡主李氏墓志銘》,第709頁;《文恭集》卷一○《代中書樞密院乞乾元節用樂第一表》、《代中書樞密院乞乾元節用樂第二表》,葉二下至五上。考李端懿在平定王則之叛後,因查明沒有失職放走妖人李教,恢覆為汝州防禦使滑州兵馬鈐轄,遷蔡州觀察使。仁宗在皇祐二年九月祀天地於明堂,推恩徙華州觀察使。在大長公主卒後,就起覆為鎮國軍留後。李端懿堅辭,願終喪制。仁宗不許他辭讓新職,許他終喪而仍給他全俸。到他服除後,就拜鎮潼軍留後。至於李端願在皇祐元年三月以過自邢州觀察使奪一官後,到皇祐三年三月已回升為越州觀察使。又據蔡襄所記,大長公主病逝後,長女延安郡主哀戚甚,不再穿戴金玉飾物,日夜涕泣思念亡母,於是容神臒悴。仁宗憐其同齡的表妹,就特加她的月俸錢。這年除多,延安郡主返娘家拜祭亡母,感觸新歲將至而母不覆見,號慟咽絕,左右更相勸慰而不能止。半夜氣懣於胸,第二天返家而病甚。臨終前力戒二子自強以立門戶,又遺命斂葬效法大長公主以簡約。到皇祐四年正月四日卒,得年才四十三。仁宗聞之惻悼不已,輟視朝一天,命中使護葬事。又仁宗又以大長公主之故,封延安郡主之女錢氏為壽安縣君。另仁宗又在皇祐五年(1053)四月十三日以大長公主遺奏詔李端願子李評以供備庫副使召試學士院,從武階官改文階的殿中丞。但他並不滿意所改之官而推辭不就。
148、《宋會要輯稿》“禮四十一之十八”。
149、《長編》卷一七○,皇祐三年七月辛亥條,第4095頁;《宋會要輯稿》“食貨七十之一百六十五”;王欽臣(1034—1101):《王氏談錄》,收入《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三冊,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頁。關於李淑撰寫《獻穆大長公主碑》之事,可參前註。
150、司馬光撰,李文澤、霞少揮點校:《司馬光集》第三冊,卷八○《祭文·祭齊國獻穆大長公主文》,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0頁。
151、楊訥、李曉明編:《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第二冊,《五·宋別集一(續)》,《景文集》卷二五《慰魏國公主薨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2頁。
152、梅堯臣撰,朱東潤(編年校註):《梅堯臣集編年校註》中冊,卷二一《齊國大長公主挽詞二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63~564頁。
153、《文恭集》卷二《齊國大長公主挽詞》,葉十二上。
154、《蔡襄集》(《蔡忠惠集》)卷三九《墓志銘二·延安郡主李氏墓志銘》,第709~710頁。
155、《歐陽修全集》第二冊,卷三三《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李公(端懿)墓志銘》,第491頁。
156、《司馬光集》第二冊,卷二一《章奏六·正家劄子·嘉祐七年二月初四日上》,第583~584頁。
157、蜀國長公主是英宗和宣仁高太後(1032—1093)第二女,神宗的姊姊。她的夫婿王詵是仁宗朝馬軍副都揮使王凱(996—1061)孫,能詩善畫,是北宋有名的書畫大家,與蘇軾(1037—1101)等名士交好,本來算得上長公主的佳配;但王詵卻好色多欲,不顧及妻子的感受。蜀國長公主對待夫婿私通妾婢的態度,雖然與她的祖姑母獻穆大長公主一樣“性不妬”,後果卻完全不同,值得我們註意,可資比較。考蜀國長公主下嫁王詵後,對夫婿之寡母盧氏甚為尊禮,膳饈一定先擇珍異的送給住在駙馬宅旁的盧氏。當盧氏有病時,她每日都親自調和湯藥以進,對於王詵家人姻黨都加以周濟。中外都稱美她的賢德。她沒有阻止王詵納妾,於是“不矜細行”的王詵就放肆,在家中蓄妾婢八人。長公主她管不住王詵,自己卻郁郁成疾。可王詵竟荒唐透頂,在侍妻疾時,居然和妾婢在長公主旁通奸,而這個惡婢竟還多次沖撞長公主,據說王詵還附和這個不知好歹的惡婢。長公主受了如此委屈,卻沒有告訴高太後或神宗。王詵之前曾因坐蘇軾過而被奪官,元豐三年(1080)四月,當神宗探視長公主而問她的意願時,她還為不肖的夫婿說情,請神宗恢覆王的官職。神宗為慰姊心,就將王詵覆官為慶州刺史並聽朝參。長公主在五月戊寅(十六)病篤,神宗親臨探視,並集眾醫處方療治,又親持粥餵長公主進食。翌日(十七),長公主病逝,神宗即親臨望門而哭,賜主家錢五百萬,輟朝五日,派入內副都知蘇利涉(1019—1082)治喪,又追封越國長公主,謚賢惠。長公主的乳母不值王詵所為,就向神宗告發王詵及其妾的惡事。神宗得報大怒,命有司窮治,結果王詵的八婢均決杖,然後配以窯務及車營兵。長公主下葬後,神宗再將王詵治罪,親批示:“詵內則朋淫縱欲失行,外則狎邪罔上不忠。長公主憤愧感疾不興,皇太後哀念累月,罕禦玉食。職詵之辜,義不得赦,可落駙馬都尉,責授昭化軍節度行軍司馬,均州安置。”相較之下,我們可以看到獻穆大長公主較能處理夫婿失德之事,她並沒有像蜀國長公主那樣事事逆來順受,弄到郁郁成疾。李遵勗失德之事被揭發後,她除了一力維護,加以包容外,後來還大方地讓他納妾生子。最重要是她一直能好好管住夫婿,不讓他再犯天條。夫妻二人後來白頭到老,相敬相愛。參見《長編》卷三○三,元豐三年四月辛亥條,第7385頁;卷三○四,元豐三年五月己卯條,第7408~7409頁;《宋史》卷二四八《公主傳·英宗魏國大長公主》,第8779~8780頁;卷二五五《王凱傳附王詵傳》,第 8926 頁。此條資料,蒙黃啟江學長提示,特此致謝。
158、考收於續藏經的佚名所撰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感應傳》便記孝子陳氏僧護其人,在相認失散三十年的母親時,就焚香拜告三寶天地神祗,並取水漱口,與母舐其目,結果其母左右眼都覆明。按大長公主篤信佛教,仁宗以這種方式冀望她覆明倒是合情合理的。又舐母目之故事也見於元人的記載,好像在《金史》及《南村輟耕錄》便記載孝子劉政和丁孝子舐目而教母覆明的故事。參見佚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感應傳》,載《卍新纂續藏經》第八十七冊(No.1632)《史傳部類·史傳部》,卷一《陳昭》;脫脫(篡):《金史》卷一二七《孝友傳·劉政》,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47頁;陶宗儀(1316—1401後)(撰),文顥(點校):《南村輟耕錄》卷七《孝感越楓橋裏人丁氏》,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頁。
159、據宋人吳曾所記,李端懿因自幼侍仁宗學習,所以仁宗“尤篤中外之愛”。當李出守鄆州時,仁宗以詩送行,表達了親密及信任之表兄弟感情,詩雲:“魯館名家子,皇家外弟親。詩書謀帥舊,金竹剖符新。九郡提封遠,一圻甘澤均。純誠宜報國,撫士愛吾民。”參見《能改齋漫錄》,卷一一《記詩·仁宗賜送李良定詩》,第328頁。
160、在現代人眼中,獻穆大長公主的四姊揚國大長公主“性妬”而不容夫婿納妾,是男女平等的體現。反過來說,獻穆大長公主以及蜀國長公主容忍夫婿納妾及私通妾婢,其實可以視為她們對儒家所倡的男尊女卑的落伍迂腐的禮法的妥協,而不足為法。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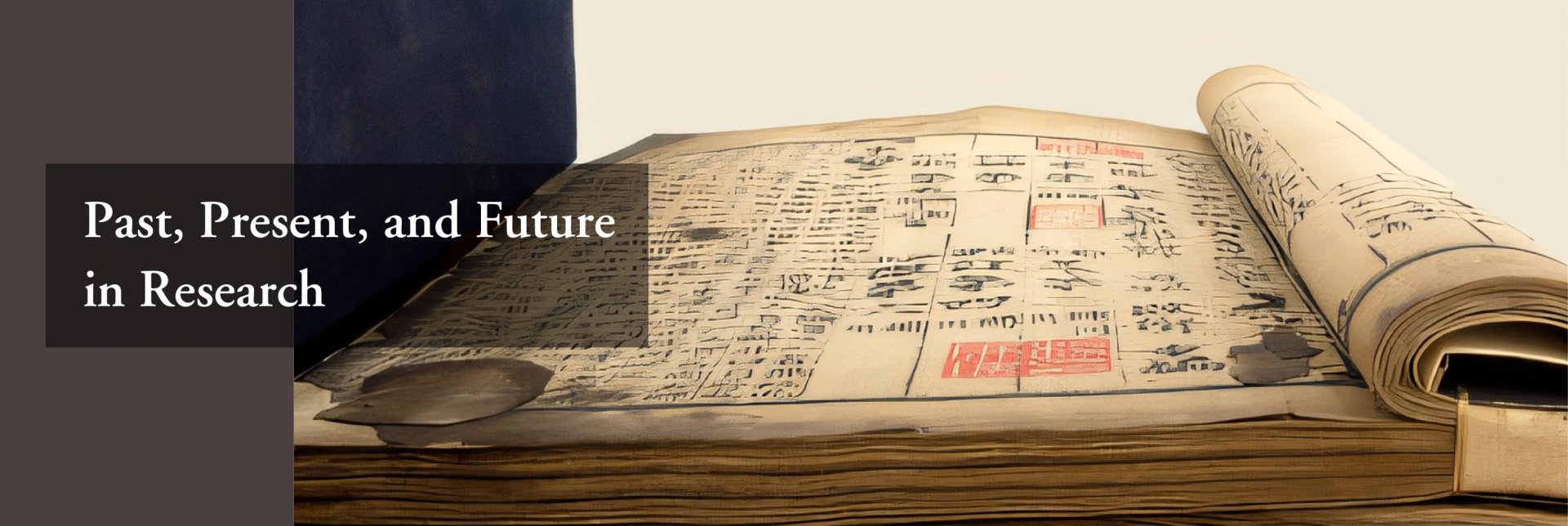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