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學中的情感教育及其文化根源
韓愈說: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師說》) 歷來中國語文科肩負著傳授學生知識和培養個人品德的責任。過往學習課文篇章,主要通過教師的解讀和義理闡發令學生接受(無論是文學藝術的還是道德的)潛而默化的薰陶。根據2021年課程發展會修訂的《中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我們了解到香港的語文政策關注學生品德情意的培養。以上文件的第四點就是講述品德情意教學的目的,稱:“品德情意教育可由感情激發到理性反思,以情引趣,以情促知,進而自我反省,並在道德上自覺實踐。”1此外,在《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2017)中的課程規劃第七點指出: “透過中華文化及品德情意的學習,加強價值觀教育。”2以上兩項條文文字稍有出入,但同樣採用了品德、情意、中華文化等字眼。我們需要明確一點是,學習文學和中華文化是建立個人品德、培養情意的依據。語文教學所使用的文本一般選自古今的詩歌、散文、小說或戲劇的文學作品。
一般來說,情意解作感情3,又可將情與意分開解,指個人情感及個人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觀念和想法。我們要指出的是,語文教學是建立情意、品德其中一條社教化的重要紐帶。在文章開首,我們先作兩點說明:一、本文旨在論述閱讀文學作品與建立情意及品德的內在聯繫。語文教師承擔的工作量沉重,壓力很大,教師的精力多投放於提高學生語文的聽、說、讀、寫四個方面的訓練,兼顧其它的時間並不多。情感教育可以看作是語文教學的分支,也可以獨立起來,成為培養個人情感、品格的成長課程。本文只理論上探討語文教學上情感教育的原理及功效,並不涉及學校課堂上如何實踐、課程設計等具體問題。此有待將來的研究探討。二、情感教育該具普遍意義,由於不同文化對情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性,又不同國家、地區的社會、教育制度不一,故此,本文只以香港的語文教學為例。
無論是小學、中學的中國語文課本,還是大學裡的語文科目,教學的讀本都是古今(外國)文學作品的選編集。我們除去提高語文的閱讀、寫作能力不論,文學是情感教育最好的教材。我們說文學的情感教育功能包括形式及內容兩個方面。
一、從認識論上說──文學可以豐富學生人際之間情感類型的認知。情感是人類在社會活動中相互交流、接觸而逐漸建立起來的。個人與家庭人倫及社會上各種角色之間的關係,構成了一幅廣大而具秩序的社會、文化的情感圖案。個人與外界一切的連結除本能生理反應外,其中構建意義價值及道德觀念的重要因素就是情感作用。互動、交往是建立情感的必要渠道。有以社會學方法研究人類情感的學者認為,人類的情感由一套社會關係所形成而且(情感)將人與人彼此捆綁在一起。4這種觀點有助我們繪製一張情感的社會圖譜,將社會、人際關係及情感交織成一個立體的三維空間。成年人隨著社會經驗、人生歷練的增加,對人、對事有較寬廣、較深刻的理解,待人接物也能掌握分寸。對於青少年來說,由於缺乏生活體驗,對人際之間的情感理解不深,文學作品中記錄的各種不同的情感經驗增補了他們的認識。除家庭倫常的情感如父母、兄弟姊妹、叔伯姨舅之外,對待朋友、同學、老師不用說,我們對待男性、女性、不同年齡、種族的人、陌生人,甚至植物、動物、沒有生命的物件以及自然、天地。我們發現,人類的情感領域是如此的寬廣闊大,也如此的微妙細膩,情感是人類生活的一張巨大的羅網,籠罩著宇宙萬物。我們的意識、價值、意義及身外人、物、事的關係均賴此而建立起來。
二、從情感內容上說──文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不同之處,簡單地說:文學以形像為手段,訴之於讀者的感情;社會學科則重視數據及實證,著重歸納規律,以邏輯、論證為手段,訴之於人的理性。文學的內涵是情感,文學是情感的載體。文學是一部生活體驗的百科全書,它是人類情感千紅萬艷的百花園。文學作家通過人物故事,運用不同的文學手段形象地、生動地傳情達意,打動讀者。通過閱讀作品,讀者體驗人物際遇及其心路歷程,隨著故事的發展而情緒起落波動。這種情感體驗往往結合讀者的知識、自身的經歷及相似的情緒感受而展開。(一)、在認識上,首先體會、理解作品人物的態度及情感反應;(二)、與一己的經驗融和體認,在情感上作出是非、好惡、美醜、道德等判斷;(三)、產生的效果有二:1.增加 (超出一己的經驗) 、擴闊或深化對情感的認知,正如梅內爾所說: “我們也可以借助於藝術品,通過認識其他人的意識是甚麼或可能是甚麼,來擴展我們意識的範圍。”5我們要補充一點,除 “擴展我們意識的範圍”外,還確認、肯定自身過往的情感經驗及態度;2.這種情感判斷的實踐具有教育意味,從個別經驗走向對普遍、一般情理的認同,經思維辨析後最終成為理性認識。(四)、產生感動、喜樂、悲哀、厭惡等的審美愉悅。此種審美愉悅與現實生活存在著某些距離。對於現實與虛構的差異,有研究者提出情感 “不對稱理論”(Asymmetric Emotions),在作品中呈現的情感與現實生活並不相同,例如可怕、厭惡的事情在現實生活中不引起任何愉悅的情緒,但在文學作品中卻相反。6(五)、文學作品展現人類紛繁複雜的情感內容,除了認識論的意義外,閱讀文學作品促進我們思想、情感的成熟,又能引起我們對自己的生命及人類生存狀況的反思,從而推動改善我們的處境及生活。這是文學的善。那麼,文學的本質是甚麼呢? 文學對現實生活描摹的目的是人類對自身幸福的關切(也適用於其他藝術種類),原因是人類天生本然地對自我以及他人甚至全體的生存狀況、福祉的注意。作家創作的興趣如此,引起讀者閱讀興趣的也該如此。所稱自身幸福指人類對生存的認識,藉此以提供改進生活的動因而產生的願望或達成的成果。此可以囊括人類生活內容的全部,包括政治、戰爭、災難、人倫、情感、信仰等生活。值得關注的是,閱讀文學作品所引起不同的情感體驗能夠成為認知、體諒他人感受、情緒的基礎,同理心、憐憫心容易伴隨而生。Norman K. Denzin在談論電影的情感時稱:當人們經歷情感時,他們增進對自身的理解的同時,也增進對別人的理解。7不僅電影如此,相信文學也是如此。
我們對以上的論述作一簡單歸納,綜合而言,文學作品在情感教育上的功效有二:一、拓寬、延伸對情感認知的範圍,增強、擴大讀者在現實生活中的情感體認,提高、豐富情感生活的質量。二、培養、活躍情感判斷,認識(道德)情感的形成與道德行為兩者的關係。
文學作品擴寬和深化我們的情感內涵及使我們在閱讀文學作品的過程中實踐情感判斷。究竟情感在情意和品德培養上起了甚麼作用?西方重視理智的傳統由來已久,對情感採取批判的態度,因為情感的不穩定性損害人類的理性思維及行動,淪為次等價值。柏拉圖不就是要將詩人逐出理想國,因為詩人創作的東西是人類靈魂中最低劣的部份。8近三、四十年西方無論在心理學上或社會學上對情感的研究產生了很大的變化,研究者認識到情感是理性、道德的基礎,沒有了情感也失去了一切。這種對情感態度上的變化為本文論題提供了心理學上的、社會學上的,甚至哲學上的證明。道德的判斷、道德的動機以及道德的行動均源自於情感的作用。對此問題,西方理論家論述得很多,例如,Justin Oakley強調(道德)情感混合認識(Cognitions)、願望(Desires)及情感作用(Affectivity)三者,三者缺一不可。9Rest James則認為道德由四種元素組成:道德感(moral sensitivity)、道德判斷(moral judgment)、道德決定(moral decision making)及道德行動(moral action)。10Justin指出情感是行動的動機。James則認為道德行為不能與認識及情感分開。兩位研究者均主張道德行為與認識及情感緊密相連。舉個例來說,如果我們目睹一位壯漢正在欺負一位老人。首先,我們需要理解眼前發生的事情並進行評估,也許我們隨即產生一種厭惡、義憤的情感。情感或會牽動個人相關的情感和生活經驗,例如由此想到自己的父母、祖父母、親戚、朋友受別人欺負。這種情緒越大,越能激發我們確立動機,採取進一步行動。我們因厭惡情緒而作出道德判斷,之後產生行動動機,再由動機驅使我們行動──出手干預或制止欺凌。11
此處由欺凌事件所引發的情緒十分關鍵,它促使個人作道德判斷,以上事例牽涉兩種情感:同理心(Empathy)和憐憫(Sympathy)。同理心指體會別人的感受和情緒;12憐憫指對別人的遭遇或處境的痛苦表示關切或同情。以上兩者是產生道德行為的動因。此兩種情感對道德形成的重要性,我們嘗試舉Candace Clark的理論為例證說明。Clark的理論架構以同理心及憐憫作為核心元素。她認為憐憫是人際關係中的重要情感。她從憐憫產生的施予者及接受者之間的關係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情感社會學理論。又,她認為憐憫從同理心產生,她將同理心分為三種:一、認識上的同理心;二、肉體經驗上的同理心;三、情感上的同理心。13我們可以說同理心和憐憫是道德行為的驅動力量,讀者可以從文學作品中得到豐富的情感體驗。至此,我們嘗試作一小結,文學與道德的聯結如下圖:
文學
情感判斷
(讚賞、喜悅、同情、厭惡、仇恨、憤怒等情感)
道德
文學作品對讀者產生(引起)的情感薰陶至關重要,由此產生三種結果:一、在認識上說,增強對情感的認知;二、體驗對閱讀時所引起的情感,此後在生活上與別人交往去驗證甚至實踐;三、閱讀時產生/引起的各種情緒,激活情感作用。情感是閱讀文學作品與道德培養兩者連貫的橋樑,增加情感認知及激活情感作用是為在生活上作道德判斷提供良好的訓練。語文教學中的情感教育的基礎就在於此。情感教育的功能有三:
一、不再冷漠,表達對於人類的關懷,這是追求社會幸福的基礎,也是追求世界共榮共存的人性砥柱。情感是建立人與人、人與群體、社會以及自然界關係的必要渠道,也是不同種族、文化、國家之間溝通的起步點。在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為謀求一己或大眾的幸福、為消弭各種爭端矛盾、為建立互利共贏的局面,情感教育作為中小學的基礎教育就顯得非常重要。
二、個人性情及道德培養在社教化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情感教育寄寓在語文教育之中,將教學功效發揮擴大,臻至情意、品格的培養,達到香港教育局制定有關中國語文培訓目標之一加強“品德情意教育”的目的。
三、學習體會、關懷、尊重別人的感受和情緒,在群體裡增加人文精神,抵抗將人物化,漠視人性。
中國人講情感教育具有特殊的文化意義。我們推崇情感擁有深厚的傳統底蘊和悠長的歷史淵源,現在從三個角度論述如下:
一、從道德哲學去講。中華民族是一個講求情感的民族,古代中國是一個道德哲學的王國。我們的道德哲學自古就很發達,孔子倡導的仁學是一種高度珍視情感的哲學思想。孔子認為仁德的根基為孝弟,故稱: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孝弟是對父母及兄長的情感,是人類最基本及最為普遍的情感。此與西方古代重理智的傳統不同。仁德以人類至親密的人倫情感作為基礎,揭示仁德於人具有普遍性意義(知仁),也是平常日見,易於實踐(行仁)。孔子 “一以貫之” 之道是忠和恕,兩字皆從心,前者解盡己、後者解推己及人,兩者都以 “一己之心” 作為衡量的標準。又,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三個 “己” 字。人類具有共同的人倫情感基礎,故此,將己比人是同理心、同情心的人性依據。此為儒家道德哲學的磐石。孔子又說過 “愛人” (〈顏淵〉)及 “汎愛眾” (〈學而〉),相信對人普遍的關愛也出於同理心和同情心。孔子討論過道德與道德行為的關係,他論述孝的時候說過:“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為政〉)。敬的情感(道德情感)是判別子女對待父母是否孝的標準。換句話說,若行為缺乏情感,此行為不能說明行為者具有孝德。情感(道德情感)佔據主導行為的作用。孔子又說過:“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八佾〉),“禮”與“喪”講究“儉”與“戚”的情感態度,缺乏情感行為便失去該有的意義。年代屬戰國中期或稍後的出土文獻《五行》篇講 “行”與“德之行”就是要分清行為與道德行為的區別。沒有道德內涵的行為是一般的行為,內心存有道德情感,形成道德生命而行之於外的便是道德行為。孟子的哲學發揚了孔子重情的道德思想,他提倡:“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告子〉上)。“惻隱”、 “羞惡”、“恭敬”、“是非”是四種道德情感即孟子所稱的四端心。四端心是仁、義、禮、智四種道德行為的基礎。孟子的著名例證,“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公孫丑〉上), “怵惕惻隱”就是指(道德)情感,由此情感而產生阻止孺子入井的動機及行動。若沒有“怵惕惻隱之心”,大概,此孺子便性命堪憂了。
孔子的仁學思想核心強調對人的關懷。愛人的道德勇氣來自於對父母、兄弟愛護、尊重的親情,這種與生俱來的道德情感驅動了對別人的愛護與尊重 ── 一種利他的高尚情操。後來孟子將孔子的思想發揮到極致,孟子懷抱著人倫社會必然合理的信念,他將與生俱來的親情擴展至人類四種重要的道德:仁、義、禮、智,所謂四端心,完成了天道、性善理論。儒學對人的關懷,恩及萬物,是中國文化重視情感的深厚的思想基礎。
二、從祭祀及對生命的歌頌去講。古人祭祀祖先不用說,那怕祭祀天地、山川、河海,並非要避禍求福,祈求回報 (能如此最好),古人的態度乃是對萬物抱有款款情意。我們重本源的觀念自古有之,荀子云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禮論>)我們要祭祀天地、先祖及君師,主要還是要寄託一種飲水思源、報答恩惠的情意。《禮記‧郊特牲》稱的“報本反始”無論祭祀、郊祀、臘祭皆是溯本重源,報答根本的意思。
中國人侍死如侍生,就是將去世的先人視作在生時一樣的去對待,這不是講究有一個死後的世界或祈求神明福蔭的問題,著眼點還是在不忘先人的恩情。荀子有一句話,講得十分精采:“雩而雨 ,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天論>) “雩”當然是旱災求雨,不過,祈雨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古人藉此表示對天一種崇高的敬意。其意義在推崇人文精神。以上對祭祀而言。
在中國哲學裡,我們歌頌“生”之偉大,無論在儒、道、墨思想中有相同的敘述。《繫辭》稱:“天地之大德曰生”、又稱“生生之謂易”;《中庸》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老子》稱:“故道生之,德育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五十一章>)。墨子稱“天之愛天下之百姓"表現於“兼而明之"、“兼而有之"及“兼而食焉"(〈天志上〉)。天道的創生育人的恩情很浩大,古人對天作出熱情崇敬的歌頌本無可厚非。賜予生命是一種偉大的德性,故此,古人認為天具有道德本質。後來,孟子和《中庸》發揮完善了這種思想。所謂的“誠”就是無矯飾造作,保持萬物和諧平衡,生趣盎然。天地對人的恩情、人對天地的敬意,兩者的互動與交融譜寫了一首流動、縈繞於宇宙間的情感樂章。
三、從中國獨特的認識論去講。中國人認識天地萬物的方法倒富有十足的詩意和濃烈的藝術氣息。古人認識世界的直觀方法常指不以理性推理、分析而獲得的情感、思想或觀念,主體往往直接捕捉對象的內在生命。這種直觀的認識方法本極富藝術色彩。藝術創作豐富的想像力是聯結主體經驗世界與自然世界的黏合劑,藝術家在日常事物中發掘具普遍意義的東西,如《易》八種宇宙之間的基本元素:乾、坤、坎、離、艮、兌、巽、震,代表:天、地、水、火、山、澤、風、雷八種平常易見的事物。這八種事物各自在某種意念上廣泛地串聯起一系列的物象及事理。故此,物象具有巨大容量的象徵意義。《繫辭》常講 “觀象”,所謂觀象是指主體對自然萬物的觀察與抽象,抽象是按類別歸納事物的思維過程。古人將天、地、水、火、山、澤、風、雷八種事物視作宇宙的基本要素。由八種基本要素推衍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包羅世界林林總總的道理,展現萬物無窮的變化。這種思維方式包括了抽象、想像及象徵三者。想像是人類以生活經驗為基礎,通過某種類通、近似點對對象進行聯繫,形象地賦與物象豐富的涵義,具有創造及創新特徵。象徵則以具體的物象或事物表達豐富的意涵。R.L.布魯特評論柯爾律治(Coleridge)稱 “一切象徵都必須包括著明顯的矛盾”的觀點時,他作出了解釋: “象徵之所以具有矛盾性是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客體又是思想;既是個體又富有代表性;既是意象又是觀念。”14如果我們將R.L.布魯特的評論應用在 “乾” 的卦象上,乾是一種客觀存在物—天空,同時也蘊含著尊貴、權威的涵意;乾是萬物中個別的客體,同時也代表著君、父、夫、日、尊上等意義;乾代表天,天是一個意象,同時也是一個中國人特定的觀念。據此而知,“觀象”是一種對宇宙認識直觀的方法,此種思維使中國文化思想擁有濃厚的詩學意味。陶淵明有一首詩特能說明這種中國人固有的直觀方法。
結盧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飲酒詩>之五)
從自然境界中所得到的 “真意”,不能以語言描述。不能以語言、理智去表達的,通過對物象的直接把握正是直觀的方法。“觀象”可以翻譯為觀察或觀賞,兩者的區別在後者更多了一層藝術審美的趣味。“觀象”與 “悠然見南山” 有共同的旨趣。《繫辭》云: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 “言不盡意” 道出我們語言的困境,“立象以盡意”是藝術地解決了此問題。物象擁有豐富的象徵內涵,語言難以竭盡箇中的情意,故此,古人不作語言的辨析。這種藝術精神被莊子所吸收,“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莊子.外物篇》) 所謂 “得意而忘言” 就是指突破語言的障礙才能掌握“真意”。中國人對宇宙的情意本來就是一首溫柔敦厚的詩歌,這種深刻的情感難以運用邏輯的語言去界定和歸納,反而詩化了的語言及富於象徵的圖像能作整體把握。故此,古人往往通過大型禮樂歌舞的演練、莊嚴肅穆的祭祀天地河川,來充分地表達這份情意。
我們提倡語文教學中的情感教育需要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三點理由已論述於上),並吸收西方文化及現、當代的研究成果互相參照、印證,以發揚、改進及完善中國文化自身的理論。我們還要將理論應用到現實生活中去,真正做到 “透過中華文化及品德情意的學習,加強價值觀教育”。
本文所論述的情感教育是以文學篇章為研習對象,在教師的指導下,陶冶學生的情感與道德。從個人方面講,外界的人與事對個體的接觸便產生了情感,由於社會文化的制約,人際關係有固定模式。對自我成長、發展而言,培養恰當的情感關係對自我實現至為重要。究竟我們要做個怎樣的人?這是學校教育一個重要的議題。從社會方面講,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賴情感構建、維繫起來,故此,情感教育培養學生的家庭、社會倫理觀念及道德感。這些觀念令社會諧協和睦並為社會締造更大幸福提供良好公民素質的前提。
語文教學其中一種功效是情感教育。情感教育以往只依靠授課老師的潛移默化、苦口婆心,缺乏系統教授。現今教師教學、行政任務繁重,很多時候心有餘而力不足。強調情感教育在語文教學中的重要性很值得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深思。最後,我們對情感教育的功效總結為三點以結束全文:一、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相互責任;二、闡明情感、道德及情感與道德的基礎理論,注重道德培養;三、培養、提高文學的審美能力。
參考書目 :
1. 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2. 楊伯峻,《孟子譯註》,(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3. 柏拉圖著,張竹明譯,《理想國》卷十,(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9年)。
4. H.A.梅內爾著,劉敏譯,《審美價值的本性》,(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5. R.L.布魯特著、李今譯,《論幻想和想象》,(北京:崑崙出版社,1992年)。
6. Ann Daunic, Nancy Corbett, Stephen Smith, Tia Barnes, Lourdes Santiago Poventud, Pam Chalfant, Donna Pitts, Jeisha Gleaton. 2013. Brief Report: Integrating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with Literacy Instruction: An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at Risk for Emotional and Behavior Disorders. Behavioral Disorders, 39 (1), P43-51.
7. Ann Lendrum, Neil Humphrey, Michael Wigelsworth. 2013. Soci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Learning (SEAL) for Secondary Schools: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School-based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18, No.3, Pp 158-164.
8. James R. Rest. 1986. Moral Development—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9. James W. Kalat, Michelle N. Shiota. 2007. Emotion. Belmont: Thomson Higher Education.
10. Jonathan H. Turner, Jan E. Stets. 2005.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 Justin Oakley. 1993. Morality and the Emo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12. Kristjan Kristjansson. 2010. Emotion Education without Ontological Commitment? Stud Philos Edue. 29:259-274.
13. Matthew Kieran. 2013. Emotions, Art, and Immorality. Pp681-702. Edited by Peter Goldie. 2013.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Emo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 Norman K. Denzin. 1990. On Understanding Emotion: The Interpretive-Cultural Agenda. P.85-116. Edited by Theodore D. Kemper. 1990. Research Agenda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腳註 :
1. 課程發展會編,《中學中國語文建議學習重點》(2021年修訂),頁18-19。
2.見《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2017),頁5。教育局網頁: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_R77.pdf。瀏覽日期:2024年8月28日。
3.《現代漢語大詞典》解作:感情和心情。《現代漢語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聯合出版,1987年),第584頁。究竟情感是甚麼?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西方心理學界對情感的定義存在爭議。見James W. Kalat, Michelle N. Shiota. 2007. Emotion. Belmont: Thomson Wadsworth. Pp3-5.
4. 見Norman K. Denzin. 1990. On Understanding Emotion: The Interpretive-Cultural Agenda. P.90. Edited by Theodore D. Kemper. Research Agendas in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5. 見H.A.梅內爾著,劉敏譯,《審美價值的本性》,(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31頁。
6. Matthew Kieran提出情感不對稱論(emotional asymmetries),即現實生活與讀者閱讀作品時產生的情感不相同。見Matthew Kieran. 2013. Emotions, Art, and Immorality. Pp682-3.Edited by Peter Goldi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Emo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見Norman K. Denzin. 1990. On Understanding Emotion: The Interpretive-Cultural Agenda. P.89.
8. 柏拉圖著,張竹明譯,《理想國》卷十,(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9年),第343-362頁。
9. Justin Oakley. 1993. Morality and the Emo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Pp.34-37.
10. James R. Rest. 1986. Moral Development—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Pp3-5.
11. 產生了道德動機不一定驅使行動,兩者之間還有許多因素夾雜其中,如客觀環境、懼怕、顧慮後果等等。換句話說,產生道德動機至行動還有情感反應及理性思考過程。James有論述以上情況,見Moral Development—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Pp15-17.
12. 同理心(Empathy)指明白他人的思想及感受。定義見James W. Kalat, Michelle N. Shiota. 2007. Emotion. P198.
13. 見Jonathan H. Turner, Jan E. Stets. 2005. The Sociology of Emo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56-64.
14. R.L.布魯特著、李今譯,《論幻想和想象》,(北京:崑崙出版社,1992年),第62頁。
All articles/videos are prohibited from reproducing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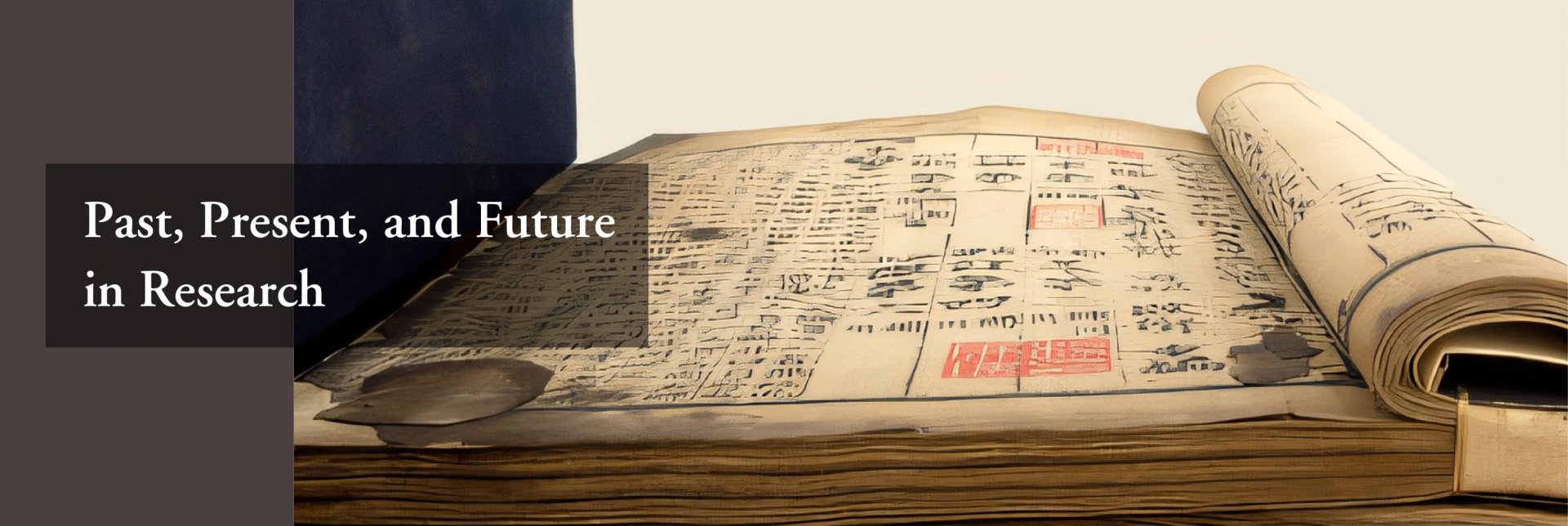



Welcome to leave a message:
Please Sign In/Sign Up as a member and leave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