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勇」的層次
孟子認為「勇」有三個層次:北宮黝自尊的勇、孟施舍忘記生死的勇及曾子與道德配合的勇。能到達第三層次的勇者必然具有前兩者的特質,即重視自己的尊嚴和忘記生死成敗。《禮記.儒行》篇:「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這個自尊不比平常的面子問題,而是受辱。部分掌權者容易墮入權力迷陣,隨意侮辱下屬。但如何能不受辱,就是自己平日處事態度所致。
北宮黝的勇,「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明顯指出北宮黝是不接受任何傷害其自尊的侮辱行為,包括微不足道的語言說話。一個人連自己都不尊重自己,別人會尊重嗎?這就是自尊的問題。人必須自重,別人才尊重你。」
孟施舍的勇是不理生死勝敗,只專心完成任務。這種忘卻生死的勇,已超越恐懼,所謂「除死無大礙」,連死亡都不怕,還有什麼好怕?
兩者的勇,到最後是成就曾子的勇,孟子說:「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
第三個勇的層次是經過深思熟慮,知道自己的行為合乎義,合乎理,則「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此語,直是石破天驚,氣勢澎湃。我們亦應思考,什麼是正確,什麼是不正確?這點是非常重要,因為誤判道德,其行為適得其反。我們最困擾的是,就算經過思考,但我們自己所定的道德標準,是正確的嗎?所以,這「自反而縮」是一個大問題。什麼行為合乎「仁義」?孟子之學稱為「心學」,第一思考點,就是從「心」開展,最直接的判斷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唐君毅先生說:「孟子以養氣之道在集義,而配義與道。道者當然之理,義者知此當然之理而為之,即知理而行之,以合當然之理。故養氣必先『志於道』。」這種氣是「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閒」。我們要留意的是,要培養這種氣,是要時時刻刻想着義和道,否則「餒」,能完善自己的道德行為,能合乎道義,則大勇之行才得到成就。我每每讀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就覺得很沉重。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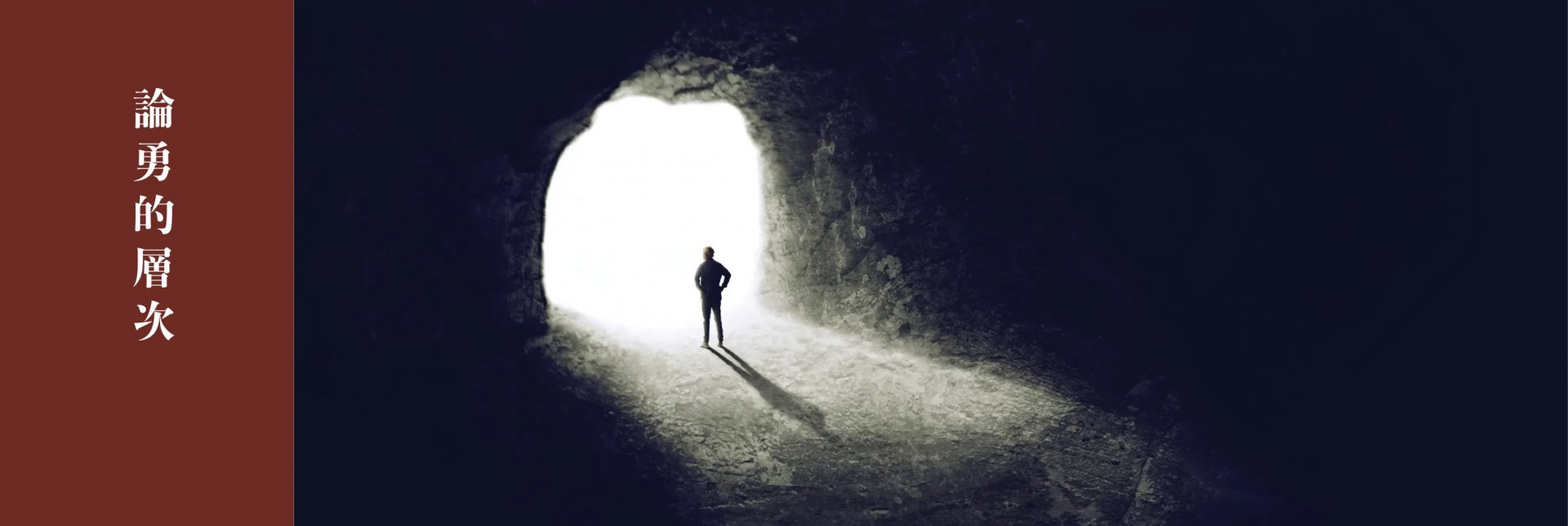



歡迎留言:
請登入/登記成為會員後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