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之際內臣李中立事蹟考
筆者數年前曾撰〈現存的三篇宋代內臣墓誌銘〉一文,當時誤以為現存宋人文集中僅有曹勛(1098-1174)的《松隱集》保存有這三篇內臣墓誌銘。後蒙蘇州大學丁義珏博士在2014年1月賜告,他的北大學弟曹杰先生在孫覿(1081-1169)的《鴻慶居士集》找到第四篇宋代內臣墓誌銘〈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誌銘〉。筆者馬上檢閱該文集,細閱這篇長達1962字的內臣墓誌銘。筆者稍後詢問兩位後起之秀會否就該墓銘作一番考釋,丁、曹兩位隨即表示暫無打算。依筆者之見,此篇墓誌銘的主人李中立(字從之)(1087-1164),他在徽宗(1082-1135,1100-1125在位)朝眾多權勢迫人的內臣群中,雖然名不見經傳,也無重大事功或過惡;惟據此墓銘考述其生平事蹟,特別他在兩宋之際的經歷,再可補充筆者前文的一些看法。特別是從岳珂(1183-1243)對孫覿撰寫李中立墓誌銘的批評,可以解釋宋代內臣墓誌銘所以寥寥可數,其中一個原因是主流士大夫不以為內臣撰寫墓誌銘為是。另一方面,本文希望透過墓銘作者孫覿與李中立的關係,從另一角度略窺宋代士大夫與內臣的關係。雖然前人對孫覿的生平事蹟考述已不少,但孫、李二人關係頗密切,故本文在考述李中立事蹟之餘,也將孫覿在徽欽高孝四朝的仕宦經歷附於其後,以茲比較儒臣與內臣在兩宋之際的亂世其行事立身之道的異同。
孫覿所撰的〈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誌銘〉沒有記載這位字從之的李姓內臣本名。筆者據李中立最後官至利州觀察使及後來復直睿思殿的線索,從與孫覿同時的周必大(1126-1204)的《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一〈乾道壬辰南歸錄〉及《宋會要‧方域三》一條資料,考出李從之本名李中立。他籍隸開封府祥符縣(今河南開封市開封縣)。他在《東都事略‧宦者傳》及《宋史‧宦者傳》均無傳,生平事蹟亦不載於他書,賴孫覿這篇墓誌銘得以知其生平大概。他卒於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二月癸未(廿八),得年七十八。以此上推,他當生於哲宗元祐二年(1087)。他出身於內臣世家,其曾祖父(按:當為養曾祖父,以下同)李言,官至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祖父李舜俞,贈右監門衛將軍。父李鎮(?-1111後),贈保信軍節度使。他的母親孫氏,封建安郡夫人。他在徽宗崇寧元年(1102)十六歲之時,以父任為內黃門。墓誌稱他年少老成,「年甫十六歲,姿莊重有防畛,往來兩宮,目不忤視,進止有常處。」
值得一提的是,在政和元年(1111)至七年(1117)擔任翰林學士的慕容彥逢(1067-1117)在政和年間所撰的制文〈尚衣奉御李鎮可轉一官制〉的內臣李鎮,甚有可能就是李中立父李鎮。該制文云:
敕:具官某,爾職在尚衣,掌於冕服,夙夜秖事,勤恪可稱。序進厥官,惟以示勸。欽予時命,尚其勉哉!可。
慕容彥逢筆下的尚衣奉御李鎮,他「夙夜秖事,勤恪可稱」,就與下面所述的李中立相近,他當是李之父無疑。可惜制文沒有提到他進甚麼官。李中立能獲父任為內黃門,則李鎮的官位似不太低。
他在宮中,先擔任徽宗日常起居進膳的直睿思殿之符寶郎,掌珍藏符寶,後擔任殿中省奉御。他顯然頗得徽宗的信任,孫覿說他「奉御出入禁闥踰二紀,未嘗以一眚挂吏議」,可見他行事小心謹慎。大概在宣和五年(1123),徽宗十三子華原郡王趙樸(按:群書亦寫作趙朴,1109-1124)出閤,徽宗問誰人可以侍奉華原郡王。當看到侍奉一旁的李中立時,就說「無以易卿矣」,即命李中立以入內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兼任華原府都監。不過,李中立侍奉的華原郡王卻享年不永,據《宋會要輯稿》所載,他在宣和五年十一月丁卯(十八)卒。而《靖康稗史‧開封府狀》記,金人在靖康二年(1127)二月要開封府上呈宋宗室名單,將他們擄去塞北。開封府奏狀便說「邠王、儀王早先薨逝」,「儀王樸十九歲」。按《宋會要輯稿》稱華原郡王「薨,追封儀王」。可知儀王就是華原郡王。
華原郡王死後,值得注意的是,李中立又擔任時封康王(即高宗,1107-1187,在位1127-1162)的宮僚。高宗在宣和二年(1120)正月庚申(十九)封廣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十二月壬子(廿二)進封康王。宣和四年(1122)出就外第。李中立大概不是一開始就被委為高宗的宮僚,要到華原郡王在宣和五年十一月死後,才轉任康邸。據墓志銘所記,高宗後來委任他為孝宗(1127-1194,1162-1189在位)的宮僚時,就說李曾為康邸舊臣。他這層淵源,故後來得到高宗的信用。
李中立在宣和初年也頗得當時的皇太子(即欽宗,1100-1161,1126-1127在位)的信任。據墓誌銘所記,在宣和中,河泛石隄,大水暴集於城下。徽宗命皇太子登上城樓視水,命李中立隨行。有申屠生等三十六人扣馬向欽宗說,只要用他的厭勝之法,就可以令水乾涸。但試之不驗,欽宗大怒,說「妄言無行之徒,僥倖水落以貪大功,以冒重賞。」打算奏上徽宗將他們誅殺。李中立從容諫勸欽宗,說:「罔上之罪,死有餘誅,而災變如此,宜加原貸,以塞大異。」欽宗納其言而沒殺這班江湖術士。可惜欽宗沒有吸收這次教訓,後來竟然相信江湖騙子郭京六甲神兵退敵的鬼話。孫覿後來評論此事時,感慨當金兵入寇,朝廷始議殺一二大臣之誤國者,他說當時將相逢欽宗之怒,無一言相救,此例一開,於是併及其黨。他說他們若知曉李中立當日勸諫欽宗不殺之風範,就應該慚愧了。其實孫覿本人在欽宗朝正是猛烈建言要誅誤國大臣之言官;但他後來卻自食其果,被指為朋黨而遭貶。
李中立在徽宗一朝的仕歷,算是無風無浪,他侍徽宗二紀廿四年,最後累官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比起他許多得寵的同輩,說不上顯赫,不過也就逃過改朝換代遭受清算之劫。據孫覿的描述,李中立淡泊名利,一心向佛,「方少年時,給事宮省,固應酣豢酒池肉林富貴之樂,而澹然不受一塵之染。閒遇休沐,則從老師宿學問出世法,修無上道,布衣蔬食,不御酒肉,蓋五十八年。」而尤不可及的,他不像孫覿所說「政和、宣和時,北司諸貴更用事,本兵柄,執國命,或冠樞省,為帝師,或位公孤,號隱相,士大夫操篲執贄,奔走其門,謂之捷徑。」即呼之欲出的權閹童貫(1054-1126)、梁師成(?-1126)那樣招權納勢,而是「畏遠權勢,不立爭地,侍帝側無私謁,出公門無外交,杜門卻掃,人莫見其面。」於是得到佛門同道有識之士的交口稱許,說「李公在家出家,住世出世,殆是過去佛僧也。」
宣和七年(1125),金人以宋敗盟為借口,在十二月戊戌朔(初一)兩路南侵,庚申(廿三),徽宗禪位欽宗,退居太上皇。欽宗在翌年改元靖康。新君繼位後,徽宗所寵的近臣內侍很快便失勢,而曾遭打壓的舊黨臣僚就得到復職。與李中立有交的孫覿,在宣和七年三月與另外五人,被人劾奉元祐之學,並罷守宮祠。才九個月,便在靖康元年正月戊辰(初二)自國子司業除侍御史。而在翌日(己巳,初三)惡名昭著、被太學生陳東(1086-1127)指為「宣和六賊」之一的內臣翊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李彥(?-1126)就首被欽宗開刀賜死,並籍其家財。李中立的主子徽宗在心腹近臣的慫恿下,當金兵渡過黃河後而尚未兵臨開封城下前,就在初三夜與太上皇后、皇子帝姬等,在蔡攸(1077-1126)、童貫、高伸(?-1126)、高俅(?-1126)等心腹及內侍護衛下,率勝捷軍及禁軍各三千出通津門離京南逃。
李中立並沒有隨徽宗南逃,他留在人心惶惶的京師。當時朝臣分做兩派,大部份宰執主張遷都以避金人之鋒,以太常少卿李綱(1083-1140)為首的朝臣則主張堅守京師以待勤王軍入援。欽宗受徽宗南逃的影響,對堅守京師毫無信心。據《靖康要錄》的記載,當李綱與宰執在欽宗前爭論是否遷都時,有領京城所在的一名內侍陳良弼從內殿走出,對欽宗奏稱「京城樓櫓刱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難保守」。欽宗即命李綱與同知樞密院事蔡懋(?-1134)及陳良弼前往新城(即外城)東壁遍觀城壕,然後回奏。蔡懋回奏城濠淺狹不可守,李綱卻認為雖然樓櫓未備,但城壁高,不必樓櫓亦可守。至於濠河雖淺,但若以精兵強弩據守亦可保無虞。欽宗給李綱說服,同意堅守待援。並且任李綱為兵部侍郎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負責京師四壁守具。宋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修樓櫓,掛氈席,安砲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櫑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京師四壁各以侍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官,而諸門皆有內臣、大小使臣分地以守。據載從正月辛未(初五)至癸酉(初七),治戰守之具粗畢。
正月癸酉(初七),金兵已兵臨開封城下,至京城西北,屯牟馳岡天駟監。金兵當晚已進攻宣澤門。甲戌(初八),金人遣使議和,欽宗派同知樞密院事李梲、駕部員外郎鄭望之等使金軍議和。乙亥(初九),金人攻通天、景陽門甚急。又攻陳橋、封丘、衛州門。李綱登城督戰,自卯時至未、申時,報稱殺敵數千(當然是誇大其辭),金兵乃退。另金兵又攻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河相繼而下。宋軍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於城下,擊破火船。但城北守將河東河北路制置使何灌(1065-1126)卻戰死。
丙子(初十),欽宗派皇弟康王(高宗)及少宰張邦昌(1081-1127)使金議和,庚辰(十四)二人始行。作為高宗宮僚的李中立並沒有隨行。據李中立墓誌銘所記,李中立在靖康初受命「分治京城樓櫓守禦之具」,而後以功進某州團練使。李中立在徽宗末年已官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以他的官位,他奉命守城,應擔任四壁提舉官。他立了甚麼戰功而可以陞一級為團練使?墓誌銘沒有說清楚。是不是他在正月初九這場攻防惡戰立功受賞?宋廷在三月癸未(十七),因知樞密院事李綱奏,將京城四壁提舉守禦官以下計八百八十三人等第推恩。李中立很有可能就是在此時獲賞功陞授遙領的團練使。
關於內臣監造樓櫓守禦之具的問題,時任國子祭酒大儒楊時(1053-1135)卻在靖康元年正月兩度上書欽宗,切論不可復用內臣。在他第二通書奏,他點了兩名內臣梁平與李彀(?-1127後),嚴厲指出:
梁平、李彀之徒,皆持權自若,氣焰復熾,未識陛下亦嘗察其所以然否乎?臣謹案梁平嘗為大理寺、開封府承受,結為陰獄,殺無罪之人不可數計。罪盈惡貫,人所切齒,陛下之所知。今復處之御藥院,果何意邪?李彀嘗管幹京城,監造軍器,奸欺侵蠧,無所不至。近興復濠之役,調夫數萬,減尅口食,殘虐百端,役夫至于殍踣,逃亡亦不可勝計。近在國門之外,陛下其亦聞之乎?」
從楊時的奏狀看,被宋廷委任治守城器具的內臣不少,與李中立同姓李的內臣、李憲(1042-1092)子李彀便是負責管幹京城城濠的人,但是像李中立那樣盡心守城有功的內臣不多,而像李彀乘機以權謀私的人卻是多數。楊時提出省臺寺監百執事其實並不乏人,為何要用這些內臣而蹈徽宗朝的覆轍?他指出內臣如邵成章(?-1129後)者,雖人或稱之,以他賢於其徒,但他認為「此曹縱賢,亦不可用,但使之服掃除,通詔令可也。」楊氏之論,代表主流朝臣的意見。故此,欽宗在二月辛丑(初五)下詔罷內侍守城。在宋廷反對內臣的氣氛下,李中立即使曾立功,也不獲重用。
勤王軍在正月甲申(十八)陸續抵達,欽宗堅守京師的信心大增,特別是素著威名的宿將种師道(1051-1126)率陝西路涇原、秦鳳兵號稱二十萬及時趕到。甲午(廿八),太學生陳東再上書請誅蔡京(1047-1126)等六賊。欽宗早在戊寅(十二)令於內侍之家包括童貫之家取銀五百萬兩、金一百萬兩,並將徽宗最寵信的內臣、六賊之一的梁師成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華州(今陝西渭南市華縣)安置。乙未(廿九),欽宗將他賜死於八角鎮。
二月丙午(初十),金兵在收取宋人給予金銀及答允割太原府、中山府(即定州,今河北保定市真定市)及河間府(即瀛州,今河北滄州市河間市)三鎮等苛刻條件後退兵。賊過興兵,宋廷將矛頭指向宣和六賊尚存的另外四人。身為御史的孫覿在二月甲寅(十八)、壬戌(廿六)、三月丁卯(初一)先後多番上奏,嚴劾蔡京、蔡攸父子及童貫等人。欽宗准奏,三人均被重貶。權傾一時的蔡太師蔡京在七月甲申(二十)死於潭州(今湖南長沙市)。八月丙辰(廿三),童貫被誅於南雄州(今廣東南雄市)。九月,蔡攸也被賜死於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徽宗朝三大權閹李彥、梁師成及童貫到這時已先後被誅;不過,行事剛猛,對宣和六賊窮追猛打的孫覿,卻因言太學生伏闕事開罪了少宰吳敏(?-1132)。三月庚午(初四),他以妄論太學生伏闕上書事,被罷侍御史職,責知和州(今安徽巢湖市和縣)。癸未(十七),他被勒令馬上離開京師。六月戊戌(初三),當其政敵李綱罷知樞密院事,出為河北河東宣撫使,率兵援救被金兵包圍多時的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後兩月,再因吳敏罷相,而主和派新任中書侍郎唐恪(?-1127)等上台後,孫覿獲召回朝,並在八月丁巳(廿四)復職侍御史。他這時又專附和議,並晉至中書舍人。在宋人筆下,孫覿為人反覆投機,他在這段日子與李中立有否交往,就史所不載。
因欽宗君臣處事乖張,進退無方,並且不能選派真的有能力的大將統兵救援重鎮太原。九月甲戌(初十),金兵便攻克太原,東西兩路會師。當金兵已過氾水關(即虎牢關或武牢關,在洛陽以東,今河南省滎陽市市區西北部16公里的汜水鎮境內),即將兵臨開封城下時,宋廷派兵設防。孫覿這時上言應接受金人條件,放棄三關故地,以紓一時之急。他的進言卻激怒了宰相唐恪,將他斥責。是月壬午(廿一),令他擔任東壁提舉官,他麾下共統兵三萬人及使臣部將數百員。金兵第一次圍城時有份治守城械具的李中立,這次有否獲委以守城之任,則未見載。乙酉(廿四)金兵再臨開封城,閏十一月癸巳(初二),孫覿被劾守東壁時支軍糧及賞賜不平,自中書舍人降三官為承務郎罷職,由王時雍(?-1127)代之。孫有自知之明,兩天後上書宰相何卥木,稱「某以眇然一書生,豈可使之駕御群黥,守衛城壁?」宋軍苦守一月,欽宗君臣竟相信江湖騙子郭京聲稱可以「六甲神兵」破敵的妖言,開門迎戰,金兵得以輕易破城,宋守軍全面潰敗。閏十一月丙辰(廿五),開封終於失陷。十二月壬戌(初一),孫覿奉命草擬降表,向金人求和稱藩。但金帥完顏宗翰(1080-1137)不納。未幾,徽宗、欽宗及宗室數百人盡被金人擄去。孫覿也在被擄之列。
金人在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正月丁巳(廿七),在軍前取內侍五十人(一說四十五人),各問其職掌後,晚上遣還三十六人,並聲稱只索取徽宗所任用的內臣。二月甲戌(十四),金人再索取內侍、司天臺、僧道及各樣奉侍人等,至庚辰(二十)方暫止。李中立居然僥倖未被金人選中,較早前被亂兵所殺的內侍梁揆十七人中,也沒有他的份兒。大概在金人退兵北還後,李中立與家人遁出危城,逃難南方,最後隱於蘇州(今江蘇蘇州市)附近之太湖洞庭山(今太湖東南)。他在蘇州,自號皎然居士。劫後餘生,據其墓誌所記,他本來有北歸之意;但宋室一直無法匡復中原,故終其一生,他無法重返開封故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李中立與其家人在何年何月,是城破前抑城破後逃離京師?另外,李家又怎樣攜同偌大的家財南逃至蘇州並隱於洞庭山?這一重要事實,孫覿在李的墓誌銘卻並沒有交待,是否諱莫如深?
孫覿本來被拘禁金營。三月乙巳(十五),被金人立為楚帝的張邦昌向金人請求將他釋回。八天後(癸丑,廿三)孫獲釋返京城。四月辛酉(初二),張邦昌命他直學士院。四月丁卯(初八),他與謝克家(1063-1134)秉張邦昌命奉傳國寶往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市)迎立高宗。五月庚寅(初一),高宗繼位。孫覿留任中書舍人,然是月甲午(初五)李綱拜相。孫自知不容於李綱,癸丑(廿四),就自請罷舍人職。高宗因授他徽猷閣待制出知秀州(今浙江嘉興市)。六月癸亥(初五),李綱追究張邦昌僭逆之罪,孫以曾在偽廷供職,被責安置歸州(今湖北宜昌市秭歸縣)。不過,李綱很快便罷相,他的政敵殿中侍御史張浚(1097-1164)在十月甲子(初八)上奏論李綱之罪,其中一罪就是杜塞言路,把臺諫官包括孫覿在內的言官罷斥。十一月庚寅(初四),孫覿因張浚的進言,自降授承務郎充徽猷閣待制復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建炎二年(1128)正月乙巳(二十),因孫覿的要求,高宗授他充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即蘇州)。他有自知之明,兼且為自己屢受攻擊自辯,就向高宗申述他在靖康中先後劾奏蔡京、蔡攸父子罪狀,劾奏蔡行父子棄官而去,奏論李綱不知兵,以及論太學諸生誘眾伏闕為亂等事,聲稱之前受到他劾奏的人或其黨,為了報復,就以他為打擊目標。故此,他選擇離開朝廷以避禍。不過,他熱中功名,並沒有真的想引退。他出守平江府才半年,七月乙未(十三),被貶為提舉杭州洞霄宮的謝克家上疏自辯,力稱他並未附從張邦昌,又自表奉國寶至濟州獻高宗之功。高宗接受繼任宰相的黃潛善(1078-1130)、汪伯彥(1069-1141)的推薦,孫覿得以因人成事,與謝克家同被召赴行在。不過,兩天後(丁酉,十五),殿中侍御史馬伸(?-1128)看不過眼,奏劾二人「趨操不正,姦佞相濟,小人之雄者也」,又指責二人在靖康年間,與李櫂、王時雍等七人結為死黨,附耿南仲倡和議,若有人不主和議,就群起而辱罵之,並威嚇要將不順從的人執送金營,故人皆畏其險。馬伸又說孫覿接受金人女樂,於是草降表時極其筆力以媚金人。馬伸痛劾謝、孫二人是負國之賊,宜加遠竄,請高宗不要再用二人,但奏入不報。八月戊午(初六),孫覿以顯謨閣待制試給事中。馬伸在庚申(初八)再上奏反對孫的任命,但仍然疏入不報。馬伸在九月癸未(初二)因以上言劾黃、汪二人,先被罷御史職,再被責降奉議郎監濮州酒務,並被促上路而貶死道中。
孫覿繼續獲得高宗重用,十月壬戌(十一),因他的上奏,加上黃潛善的推薦,高宗詔他以給事中與翰林學士葉夢得(1077-1148)、中書舍人張澂(?-1143)討論常平法,條具取旨。十一月丙戌(初六),孫再擢為試吏部侍郎仍權直學士院。建炎三年(1129)三月辛巳(初三),孫再晉試戶部尚書。
當孫覿在朝中得意時,才不過四十餘歲、正當盛年的李中立在建炎初年沒有歸朝,而是南遷至洞庭山。他出家資,在洞庭東山稍北之處營建墓壙,買地二十畝,親手植松柏環繞之。又在旁建一佛寺,寺中「重門步廊,穹堂奧殿、齋庖、宿廬、廐庫之屬僅萬礎」,寺內塑有佛菩薩像數十座,又建窣堵波塔高三百尺。他又營建一大經藏,收藏佛經五千四十八卷,均是「寶匳鈿軸,納之匭中」。他作為大檀越,在附近買田十頃,以收入供養僧俗千餘眾。他請得高宗賜其佛寺名「華嚴禪院」,選一時名僧主理之。按此寺規模不小,所費不菲,很有可能李中立早在開封城破前,已將資產轉移江南,不似許多內臣在開封城破前後被抄家籍沒財產。他知幾之舉,教他南遷後,能保有如此家當而可以經營此一禪寺。
李中立所隱居的洞庭山華嚴禪院在甚麼地方?據周必大所記,他在乾道壬辰(八年,1172)三月辛巳(十三),即李中立歿後八年,「粥罷,同鄉老下山行二里,觀韓王墳(按:即韓世忠在蘇州之墳),欲登舟過寶華,而天氣晴和,忽有遊杭塢之興。遂與大兄呼車往焉。約十里,度小硯嶺,入唐子明侍郎(按:指唐煇,?-1145)墳庵。又二、三里至白馬窟窿禪寺(後唐會昌六年置)。飯訖行數里,至夢里皇第宅,聯屬者豪民夏氏也,又數里過支塢嶺,遂至法華院,本皆荒山,中官利州觀察使致仕李中立造塋於此。」據此,可知李中立的墳墓,就是在蘇州(平江府)不遠的支塢嶺的法華院內。至於李中立墓誌銘所記李氏修建的華嚴禪院,與周必大所記李墳塋所在的法華院,是否在同一地方待考。據周必大所記,李中立「捐家貲數千萬,創精舍,十年而成。四山環抱,宛若化城三門,為閣七間,華麗擬宮闕,其間棟宇瓦砌種植,皆稱是主僧慶深聚徒數十,富足無求,亦清福也。門外數百步,即太湖,極目彌天之浸。」周必大記他在此「徘徊不忍去,飲茶於塔院,登李侯(即李中立)之丘,讀孫仲益(即孫覿)所為銘。主僧具飯,投宿客館。」據此可知,李中立經營其近蘇州而面向太湖的精舍,所費極多,以他一個中等官階的內臣,卻能有偌大家財,亦可旁證徽宗朝內臣勢力之大。孫覿沒有說李中立為官如何清廉,只是李中立較為安份,不像童貫、李彥、梁師成等如此招搖,後來給欽宗通通抄家而已。孫覿在建炎二年正月至七月知平江府,他在這半年有否與蘇州相距不遠的洞庭山的李中立往來,墓誌銘未有記載。
就在李中立努力經營其在太湖旁的精舍時,宋廷卻面臨重大危機。首先在建炎三年三月癸未(初五),就在孫覿陞官兩天後,扈從的禁軍統制苗傅(?-1129)及劉正彥(?-1129)因不滿新除的簽書樞密院事王淵(1077-1129)及高宗寵信的入內內侍押班康履(?-1129),發動兵變,先殺王淵,再迫高宗退位並殺康履以下專權內臣多人。叛軍逼高宗禪位其年方三歲的獨子元懿太子(1127-1129),而由隆祐孟太后(1073-1131)聽政,改元明受,史稱明受之變或苗劉之變。孫覿在兵變中奉宰相朱勝非(1082-1144)之命與叛軍周旋。亂事在七月辛巳(初五)以苗、劉二人伏誅,高宗復位後平定。然十天後(丁亥,十五),被冊為太子的元懿太子卻夭亡,稍後,金人又大舉南侵。壬寅(廿六),因金人即將南侵,高宗先請孟太后從杭州率六宮先往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閏八月壬寅(廿六)高宗從建康府(今江蘇南京市)出發前往浙西,經鎮江府(今江蘇鎮江市)往平江府。孫覿在苗劉之亂平後,以龍圖閣直學士出知平江府。九月己未(十四),言官卻劾孫在平江拘催民間崇寧以來青苗積欠,民苦其擾。又劾他曾建議行王安石常平聚斂之法。高宗於是將他罷職,改由資政殿學士李邴(1085-1146)代知平江府。高宗在十月戊寅(初三)離開平江,壬辰(十七)抵越州(今浙江紹興市)。
據李中立墓誌所記,高宗駐會稽(即越州),即遣使召其藩邸舊人李中立來見。使者見到李中立時,李正「被短褐,雜庸保,持鉏蒔藥圃中」。高宗有召,雖然非李所願,但也即日更衣就道。高宗見到他後,即命他供奉殿廬,盡復其舊職。先高宗離開行在的孟太后,在十一月壬子(初八),因金兵來犯洪州,就在辛酉(十七)經吉州(今江西吉安市),乙丑(廿一)再連夜乘舟南走,前往虔州(今江西贛州市)。因金人追趕得急,原護衛孟太后的兵將都潰散,孟太后與元懿太子母潘賢妃(?-1148)以農夫肩輿而行才抵虔州。而高宗也在是月己巳(初一)離開越州往明州(今浙江寧波市)。十二月初,高宗抵明州,甲申(十二),高宗乘船出海逃避金兵。建炎四年(1130)三月甲子(廿二)金兵退後,高宗才自溫州(今浙江溫州市)返回明州,四月癸未(十二),返回越州並駐蹕於此。高宗遣御營司都統辛企宗(?-1145後)、帶御器械潘永思將兵萬人迎孟太后東歸。據李中立墓誌銘所記,高宗以孟太后幸江表久不得問,有旨擇使。這時金騎雖退,暫時不再渡江,但仍據有兩淮,道路仍難行。李中立即慨然請行,乘一軺車,「間關兵火盜賊中,山行水宿,馳二千里,得平江之報還奏。」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宋史》所記,高宗一度失去了孟太后等人的消息,在建炎四年(1130)正月己酉(初六)「詔遣使自海道至福建虔州,問隆祐皇太后艤舟所在。上慮太后徑入閩、廣,乃遣使問安焉。」「遂命中書舍人李正民(?-1151)來朝謁」。相信李中立就是高宗所選派打探孟后等人行踪的使者之一。高宗安返越州後,范宗尹(1099-1136)拜相,以赦書加恩給被貶諸臣自李綱以下,七月乙丑(廿五),孫覿自朝奉郎復職為徽猷閣待制。稍後又有言者稱孫覿曾草降表,罪不當赦。高宗乃詔俟一赦後再取旨。
八月庚辰(初十),孟太后一行返抵高宗駐蹕的越州(紹興府)。高宗翌年改元紹興(1131),四月庚辰(十四),孟太后崩於越州,六月壬申(初七),高宗追冊她為皇太后曰昭慈獻烈。壬午(十七)權欑於越州。八月丁丑(十三)祔神主於溫州太廟。從迎接孟太后返越州行在的慶典,到她崩逝所舉行的喪禮,李中立大概都有參預。當大禮完成後,李中立次子李疇派往閩中任官,李對兒子說「此行不可失」,原來他想借兒子外放福建的機會求退。他隨即向高宗求請祠職,高宗允准,特授他提舉西京崇福宮。高宗在紹興二年(1132)正月丙午(十四)從越州抵杭州(臨安府)後,自此以杭州為都。李中立求祠職,相信在高宗定都杭州之後。李中立陪同兒子赴福建之任,據載他「拄策褰衣,上天姥峰,徑天台,抵雁蕩。遊覽殆遍,遂次莆田。穿雲涉水,窮日夜不厭。閒遇幽棲絕俗之士,談禪問法,樂而忘歸。又將束裝問番禺路。」據上文所提的莆田,李氏父子當是前往興化軍的莆田(今福建莆田市)。
孫覿早在紹興元年二月前已以龍圖閣待制知臨安府。他與李中立有否在杭州見面?暫無可考。這年二月辛巳(十四),從金國歸來的秦檜(1091-1155)拜參政,孫覿以啟相賀,有曰:「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秦檜看了大怒,認為孫在譏諷他。孫也不為宰相呂頤浩(1071-1039)所喜,結果他在十月甲子朔(初一)被罷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呂、秦二人卻不放過孫,他們利用吏部侍郎李光(1077-1159)先前上疏劾孫覿知臨安府時,盜用助軍錢四萬緡之事,將孫下大理寺,並落龍圖閣待制。獄成,孫覿以眾證坐以經文紙劄之類饋過客,計值千八百緡。有司論孫覿自盜當處死。高宗詔免死及決刺,除名象州(今廣西來賓市象州縣)羈管,所過發卒護送,連坐流徒者三十餘人。孫在象州被流放了兩年,他在紹興四年(1134)上書申訴其枉得直,高宗下刑部重議,刑部言孫覿所犯未嘗置對,只是據眾證定罪,於法意人情實在未盡。高宗接納刑部的意見,在八月戊寅朔(初一),詔釋孫覿,並任他自便居住。據《桂勝》一書的記載,他在十月北歸經過桂州(今廣西桂林市),桂州一班地方官自經略安撫劉彥適、提點刑獄董芬、轉運副使陳兗、轉運判官趙子巖等於是月丁亥(十二)與之同遊七星山,壬辰(十七),又餞孫於獨秀山蒙亭。丙申(廿一),孫返常州(今江蘇常州市)前,眾人又於伏波山八桂堂為他餞行。孫覿還在桂州七星山留下五言古詩兩首以抒被貶南方的懷抱。
孫覿赦還不久,九月乙丑(十九),金兵與劉豫(1073-1146)的偽齊已議入寇,金、齊的騎兵自泗州(今安徽宿州市泗縣)攻滁州(今安徽滁州市),步兵自楚州(今江蘇淮安市淮安區)攻承州(今江蘇高郵市)。宋廷震恐,臣僚有勸高宗他幸,惟新任宰相趙鼎(1085-1147)力持不走他方。壬申(廿六),金、齊聯軍分道渡淮。十月丙子(初一),高宗下旨親征。面對金兵的攻勢,宋兵總算尚能應付,大將韓世忠(1089-1151)在十月戊子(十三)敗敵於大儀鎮(今江蘇揚州市儀徵遇大儀鎮)。解元也敗金兵於承州。但金兵在丙申(廿一)攻佔濠州(今安徽滁州市鳳陽縣),十一月丙午朔(初一)又攻克泗州,戊午(十三)再克滁州。宋軍堅持抵抗,金兵終於在十二月癸卯(廿九)撤出佔領已四十七日的滁州,而在翌年(紹興五年,1135)正月乙巳朔(初一)撤出濠州。二月壬午(初八),高宗一行從平江府返抵臨安府。總算度過一場危機。孫覿也在閏二月乙巳朔(初一)獲敘左奉議郎。
孫覿在李中立墓誌銘曾記載這次金兵南犯時,他和李中立的情況。他記:「紹興初,胡馬數萬屯宿、泗,淮海大震。吳人懲建炎暴屍喋血之禍,爭具舟車,徙避深山大澤曠絕無人處。」這時已獲赦而歸隱太湖的孫覿,則說:「予亦詣洞庭西山訪尋佛舍,得水月院,僑寓其中。當是時,觀察李公(按指李中立)臥東山,築室鑿井,若將終焉。予唶曰:中貴人入則侍帷幄,依日月之光,出則持粱齧肥,享玉食華屋之奉。一旦決焉舍去,練布梲杖,與漁樵農圃為伍,而自肆於山水間,此高蹈一世之士。」孫覿說他也想「攝衣起從之,而東、西二山塊湖中,徒步不能達,至是聲問始相聞。」而他說李中立也欣然有招隱之意,但未幾宋金議和,而兩淮皆安堵,竟無緣見到李中立,以為大恨。孫覿集中有〈洞庭西山小湖觀音教院靈泉贊〉一文,顯然孫在墓銘提到的水月院即是洞庭西山的觀音教院。而李中立所居的就是周必大所提的東山法華院附近。
為何孫覿說竟不能在洞庭東山見到李中立?墓誌銘說「而上遣金字牌趨還,復直睿思殿兼持侍官。今上(按:孝宗)出閤日,一詣資善堂,太上皇(按:高宗)曰:『宮僚當得老成詳練有德有言之士,藩邸舊臣如華原府都監李某,此其選也。』又兼資善堂幹辦官。諸臣方悟上召公之意」。《宋會要‧方域三‧資善堂》記:「(紹興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詔:已建資善堂,提點官差主管講筵所邵諤,幹辦官差睿思殿祗候使臣李中立」。據此兩條記載,可以知道是年已四十九歲的李中立在紹興五年五月被高宗急召還朝,擔任年方九歲的孝宗的宮僚。這也從側面看到高宗揀選孝宗為嗣的苦心,連他身邊的內臣也特別找可靠的擔任。
李中立可不戀棧宮中侍奉,過了一段時間,在紹興六年(1136),趁著奏事殿中,就對高宗泣求說:「臣齒髮缺壞,重以足疾不可治,不復侍左右矣。願賜骸骨以畢餘年。」高宗聽後惻然,大概李中立這時真的身體不好,高宗見他去意甚堅,就除授他提舉台州崇道觀,罷宮中職務。李中立在紹興七年(1037)更上書告老,高宗許他守本官武功大夫致仕,這年他才五十一歲。他獲准退休後,置家於湖州吳興縣(今浙江湖州市吳興區)和德清縣(今浙江湖州市德清縣)境上,然後返回他在洞庭東山舊廬,以誦佛書及供養僧徒為事。他又喜歡收藏良藥,以給有需要的人。他施藥數年,許多人一早便登門求藥。李中立因此說:「吾不忍此一方疾痛呻吟之感吾耳,吾製方藥療之。」因他頗知醫理,有見從其他各州縣來求藥的越來越多,李中立乾脆經營一藥肆,「凡山區海聚、殊方絕域金石草木之英、象、犀、龍、麝之珍,雞首、豨苓、牛溲、馬勃之賤,皆聚而有之」。他僱用徒眾數百人,按古醫方書炮製烹煉之法數百種,合成各種藥劑。他計費取值,不求贏利。據稱從浙東至兩淮二江數十州的眾多病人,得到他所製之藥,一飲而見效。孫覿稱許他「殆是仁人用心,固自有物以相之耶。」李中立用他的偌大家財,設肆製藥,以惠民眾,與他建禪寺養僧徒之作為,可以說是他修行的一體兩面。好像李中立以經營藥肆來布施積福,在宋代內臣中可說是罕見一例。李中立從何學得經營藥肆之道,惜孫覿沒有詳言。徽宗朝權傾朝野的內臣梁師成號「隱相」,但梁的「隱」與李中立的「隱」可說是大異:前者是隱身在朝堂後操縱朝政的權閹,後者卻是隱於山野,後來開設藥肆周濟百姓,有點大隱隱於市的大德。
孫覿曾經開罪的秦檜從紹興七年正月復任為樞密使,到紹興八年(1138)晉拜右僕射同平章事仍兼樞密使。當他兩大政敵張浚及趙鼎相繼罷相遠貶後,秦檜就一直獨相至紹興二十五年(1155)十月卒。孫覿在秦檜當政時不獲召用,雖然他交結眾多權貴,包括與秦檜為姻親的外戚信安郡王孟忠厚(?-1157),但並未得到以主和議而得以當權的秦檜的起用。他在給孟忠厚的第七帖說他「辭去十五六年,曳居王門者眾矣,衰老獨無一跡。今茲暫愒里中,尤欲及公未還政路,汲汲圖一見」,隱見他那種不甘寂寞之情。比起李中立自請致仕,歸隱田園,就人各有志了。
孫覿以秦檜當政,畏禍深居二十餘年。他在紹興十三年(1143)以郊恩得到復敘為奉議郎。但在紹興二十年(1150)八月己未(十六),當秦檜進呈前侍從見在謫籍人時,高宗表示孫覿及莫儔(1089-1164)等尚在近地,說應該令他們遠去,以言官嘗論之,認為他們是姦臣逆子,應當屏跡。紹興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甲申(十一)高宗召回與孫有交情的孟忠厚,並令孟押百官班。這大概給孫一大希望。不過,紹興二十六年(1156)正月戊午(十六),孟出判平江府,沒有留在朝中。孫覿要等到五月戊申(初八),當新任宰執沈該(?-1166)、万俟禼(1083-1157)及湯思退(1117-1164)等進呈御史台詳看責降及事故的前宰執并侍從官十五人情犯,請或敘復職名,或給還致仕恩澤。高宗同意,將趙鼎以下給予恩典時,孫就上書自訴。六月壬午(十二),宋廷給他復官左朝奉郎。他仍不滿足,在十一月辛巳(十三)再上書自訴,宋廷就復他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隨即對沈該、万俟禼及湯思退等宰執多人卑詞致謝。直至紹興三十年(1160)四月丁卯(十九),他才上書告老,宋廷復他敷文閣待制致仕,惟三日後又不行。直至紹興三十一年(1161)八月癸卯(初三),孫才取得以敷文閣待制致仕,是年他已八十。翌年(紹興三十二年)二月戊申(十一),高宗路過常州荊溪館(今江蘇無錫市宜興縣城區西南隅),孫覿獲召入見。
李中立依舊隱於呂山。紹興二十八年(1158),其三子李畯陞朝官,剛遇到十一月己卯(廿三)高宗合祀天地於圜丘大典而行的大赦。李中立於是從遙領的團練使官授正任吉州刺史。翌年(紹興二十九年,1159)正月丙辰朔(初一),以韋太后(1080-1159)的八十大壽,高宗詣慈寧殿行慶壽禮,因加恩群臣,李中立再進果州團練使。紹興三十一年(1161)九月辛未(初二),高宗祀徽宗於明堂以配上帝,並大赦天下。李中立再以恩典晉和州防禦使。紹興三十二年(1162)當金主亮(1122-1161,1150-1161)南侵失敗,高宗在六月丙子(十一)禪位孝宗。孝宗登位後大赦天下,李中立又以恩典遷利州觀察使。這是他一生最最高的官位。而其三子李畯也在九月辛丑(初八)自武經郎,以修製奉上高宗所居的德壽宮冊寶,而獲轉一官。
隆興二年(1164)二月癸未(廿八),據說當天李中立感微疾,命人揭西方佛像於前,他潔手焚香,暝然而逝,得年七十八。四月庚午(十六),他的兒孫奉他的靈柩,祔葬於平江府吳縣(今江蘇蘇州市吳中區)南宮鄉覺城山、其續配郭夫人之墓旁,據說這是他自卜的墓地,亦是數年後周必大經過的法華院李氏墓地。相信是他在世最長的第三子、武義大夫監南嶽廟李畯,請得孫覿為其父撰寫墓志銘,然後下葬。
據李中立墓志銘所載,他雖是內臣,仍有妻子作配。元配封恭人宋氏,續配封令人郭氏。他有四子,當然都是養子:長子出家為僧,法號「法空」,次子李疇,官至秉義郎閤門祗候,二人皆早逝。三子李畯,李中立卒時官武義大夫、監潭州南嶽廟。四子李善,官奉議郎、知徽州績溪縣(今安徽宣城市績溪縣)事。李中立有女二人,長適武經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藍師夔,次適承節郎馮暉。他有孫男八人:長曰李作朋,官右承節郎、嚴州桐廬縣(今浙江杭州市桐廬縣)尉;次曰李作舟,官保義郎監婺州(今浙江金華市)都稅務,次曰李作肅,官保義郎監嚴州淳安縣(今浙江杭州市淳安縣)稅;次曰李作霖,官保義郎監行在翰林門司;次曰李作乂、李作哲,應進士舉,再次李作成、李作德尚幼。他有孫女二人:適黃訥、史紹祖。另有曾孫男女五人。
李中立來自內臣世家,他的養子養孫,依照宋代內臣收養子之習慣,可以是閹子,也可以是普通人。從他們的官職,除了孫李作霖官行在翰林門司,似是內臣外,其他不易判斷是否內臣。其中擔任文官的四子李善及長孫李作朋,肯定不是內臣。而兩個應舉的孫兒李作乂和李作哲,也肯定不是內臣。李的兒孫女婿的事蹟均無考,都不是有事功的人物。幸有這篇傳世的墓誌銘,才把他們的姓名記錄下來。另給研究宋代內臣家族的學者,提供第四份(若加上降遼的內臣馮從順和李知順,就是第六份)完整的內臣家族成員資料。
為李中立撰寫墓誌銘的孫覿,按照為人寫墓誌銘的習慣,對墓主李中立稱譽備至,除了稱許李中立「持心忠恕,事君親,交僚友,待族姻,御使卒,惟有一誠。寡言笑,一語出而終身可復」外,在墓銘總結李中立生平則云:
權門眾趨,薨薨聚蚊。暴鬠鎩翮,卒徇以身。哀樂相因,如屈伸肘。壑谷潭潭,門上生莠。富貴於我,視空中雲。得馬失馬,孰為戚欣?猗歟李公,高蹈一世,人勉而天,不見慍喜。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進直殿廬,為中常侍。退處山林,作大居士。乘應舍栰。汎不繫舟。現自在身,得逍遙游。國忠粗報,能事已畢。乞身而去,以全吾璧。覺城之原,萬木蒼蒼。公歸在天,體魄所蕩。既善吾生,亦善吾死,死而不忘,以永千祀。
關於孫覿為李中立撰寫墓誌銘之事,抗金名將岳飛(1103-1142)的孫兒岳珂在其筆記《桯史》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評論,岳珂注意到孫覿這一則特別的墓誌銘:
孫仲益覿鴻慶集,大半銘誌,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之常,不足咤。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璫矣,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大恨,言必稱公,殊不怍於宋用臣之論謚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為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為士大夫不忍為,即日罷去,事頗相類,仲益蓋幸而不及於議也。
岳珂在這則評論指出,孫覿為李中立撰寫墓誌銘,當不是為李的親屬的豐厚潤筆金而像他一貫的作風,隨便為墓主歌功頌德,而是確為李之高風所感而為文;不過,岳珂卻將孫頌讚李中立之論,比作宋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朝權閹宋用臣(?-1100)在徽宗初年卒時所獲過當之論謚,而甚不同意孫覿的做法。岳珂提到他有同僚曾為某人(當也是內臣)作行狀,卻被言者攻擊,說士大夫不忍為此,因而導致此一朝士被罷去。岳說此事與孫為李作墓誌銘頗類似,只是孫覿幸運地沒被言者議論。依岳珂所言,孫覿為內臣作墓銘,是冒著被朝士攻擊的風險的。大概宋廷主流士大夫認為不值得為這些刑餘之人撰寫墓誌銘,更不應為他們說好話。孫覿為李中立撰墓誌銘而被岳珂批評的事,也許可以提供另一旁證,為何宋代內臣墓誌銘如此罕見於宋人文集。當然,眾所周知,岳珂對孫覿有極大成見,既因孫覿為有份誣殺其祖岳飛的万俟禼撰寫墓誌銘,「以諛墓取足,雖貿易是非,至以得不償願,作啟譏罵,筆於王明清之錄,天下傳以為笑」,更為了孫寫韓世忠墓誌時,把岳飛寫為「跋扈」,比之為在靖康之難中降敵而殺害忠良的悍將范瓊(?-1129)。這就難怪岳珂對孫覿為李中立寫墓誌銘,也要大加批評了。當然,朝臣中好像為孫覿文集寫序的周必大,卻和孫覿一樣,對李中立崇敬之餘,又「登李侯之丘,讀孫仲益所為銘」,可見朝臣中對內臣態度並非鐵板一塊。
孫覿與李中立一為儒臣,一為內臣。在兩宋亂離之際,他們均難得享高壽,孫得年八十九,而李享壽七十八。他們都篤信佛陀,前者號鴻慶居士,後者號皎然居士。為此因緣,他們結為知己。二人在宋室南渡後,均退隱深山。不過李中立是知幾棄官而去,孫覿卻是畏禍逃亡深山。李中立在徽宗朝,雖然不比梁師成、童貫、李彥以至楊戩(?-1121)、譚稹(?-1126後)那些權勢薰天的同僚得寵,但他的安份守紀與治事才幹,仍為徽宗所賞,委為近侍的睿思殿祗候,並先後委為華原郡王趙樸的王府都監,以及高宗的藩邸臣屬。因他的安份與知幾,在欽宗繼位後,他沒有像梁師成等成為文臣清算的對像,當宣和諸權閹相繼被誅及抄家後,他還可以帶著偌大的家財與家人安然逃往江南,建立他在深山的安樂窩。孫覿為他寫墓誌銘時,歌頌讚揚他樂善好施,供僧建寺,經營藥肆;卻沒有說明李的財富從何而得。從李中立的個案,可以看到在徽宗朝有權勢的內臣無不廣積財寶,只是童貫之流倒台得快,搜括來的財富成為欽宗以及金人的戰利品而已。
因李中立曾為高宗的藩邸舊臣,當高宗一批信任寵信的內臣如康履等被苗劉叛軍所殺,李彀被言官痛劾而不獲高宗復用後,高宗就想起他的藩邸舊人、能幹而安份的李中立。知道他的下落後,就徵他入朝,委以重任,包括後來打探隆祐太后下落的任務。他一度求退,可高宗仍要急召他回來,擔任他選定的繼承人孝宗的宮僚。若李中立熱中功名,以高宗對他的信任,他大可留在宋宮中執事,成為入內都知。但他選擇退隱,以疾為由求致仕,他才過半百,後來享年七十八,當日稱疾告退,不過是借口。他沒有像不少內臣在杭州大造園林,他寧可回到隱居之洞庭山,經營他的藥肆,以及參禪唸佛,而得以脫離宮廷政治的漩渦。
他這番用心,孫覿在其墓銘中都能含蓄地表達出來,然而諷剌的是,孫覿經歷靖康之難的慘痛,以及徽欽高三朝人事更替時文臣之間的激烈傾軋,他還是多次不甘寂寞,退了又復出,出了又被迫退下,當秦檜死後,他就一再上書申訴,要求宋廷恢復他的官職。在宋人筆下,他除了熱中外,還是一個甚有爭議的人物。朱熹(1130-1200)對他所撰的欽宗朝歷史甚有意見,認為後來洪邁(1123-1202)修欽宗紀多本於孫覿所記,附耿南仲而惡李綱,實所紀失實,而不足取,對他修欽宗降表之媚詞更是不能接受。我們看他的文集中保存的大量與權貴來往的信件,可以看出他一直心有不甘,希望重新回到權力的前台。他到七十九歲,為官五十二年後才上表請致仕,翌年,以「年逾八十,尚玷吏籍,疾病衰殘,耳目昏瞶,犬馬之力不復自效」,才願意致仕。他並沒有像他筆下的內臣李中立一樣,五十一歲便請告退。李刻意遠離政治,孫卻不思引年求退,仍汲汲於仕進。賢與不肖,自有公論。
就在李中立歿後二年,在乾道二年(1166)四月丙戌(十三),殿中侍御史王伯庠嚴劾孫覿,痛斥他:
覿在宣和間,被遇徽宗皇帝,浸階通顯;欽宗皇帝擢授中書舍人,蒙恩最厚。及京城失守,車駕出城,覿於時不能盡主辱臣死之節,乃背恩賣國,取媚虜酋。撫其事實,臣子所不忍言。太上皇帝擴天地覆載之恩,抆拭試用,位至尚書,授以方面。而覿天資小人,不能自改,又以贓罪除名勒停,竄斥嶺外。遇赦放還,累經敘復,不帶左字。為覿者自當屏跡人間,豈敢復施顏面見士大夫,而蠅營狗媚,攀援進取,既復修撰,又復待制。如覿之背君賣國,不忠不義,而處以侍從,可乎?乞降睿旨,將覿落職遠貶,以為人臣不忠不義之戒。
孝宗准奏,將孫覿落敷文閣待制職,只是未將他遠貶。孫覿在李中立的墓銘,一再表揚李的淡泊功名的高節;諷刺的是,他卻被人嚴劾戀棧功名。他曾自稱「交舊委作墓志、行狀數十家,不受一金之餽」;但宋人都說他靠為人撰寫充滿諛詞的墓誌及行狀致富。孫覿是一代的儒臣,然從人品和識見上,依筆者之見,反而不及這一位靠他所撰的墓銘才為我們所知的內臣李中立。
就像筆者在本書第九篇所考述的三位內臣董仲永(1104-1165)、鄭景純(1091-1137)及楊良孺(1111-1164)一樣,李中立是一位在兩宋之際評價正面,而生平事蹟罕有在正史記載的內臣。他的生平事跡以及家族資料有幸靠著文集所錄的墓誌銘得以保存下來。為他撰寫墓誌銘的孫覿,偏偏是備受爭論的儒臣。似乎只有非主流的文臣,才願意為文臣所輕視的內臣撰寫墓誌銘,而且加以表揚,而非帶有偏見的醜化。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王曾瑜教授最近(2015)所撰的〈宋徽宗時的宦官群〉一篇力作,給本文提供了極佳的參考資料,它除了析論徽宗縱容寵信內臣的禍害外,更分別考述童貫、梁師成、李彥、楊戩、梁方平、譚稹、李彀、邵成章等三十名徽宗朝內臣的事蹟。也許李中立在徽宗朝的事蹟不顯,且沒有明顯過惡,他雖有墓誌銘傳世,但仍不在王教授所論之徽宗內臣之列。
近來學界不少人倡導「問題意識」,認為理論架構至為重要,重視宏觀的論述,這自然是治史的一途;但宋代內臣直接的史料像墓誌銘、行狀的太少,要透過內臣個案研究、微觀論述,以作為宏觀論述的基礎,實在不易。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在文集,特別是出土文獻發現更多內臣墓誌銘資料,以嚴謹的史事考證功夫,讓我們對宋代內臣種種有更堅實及深入的認識。
< 原創文章/視頻,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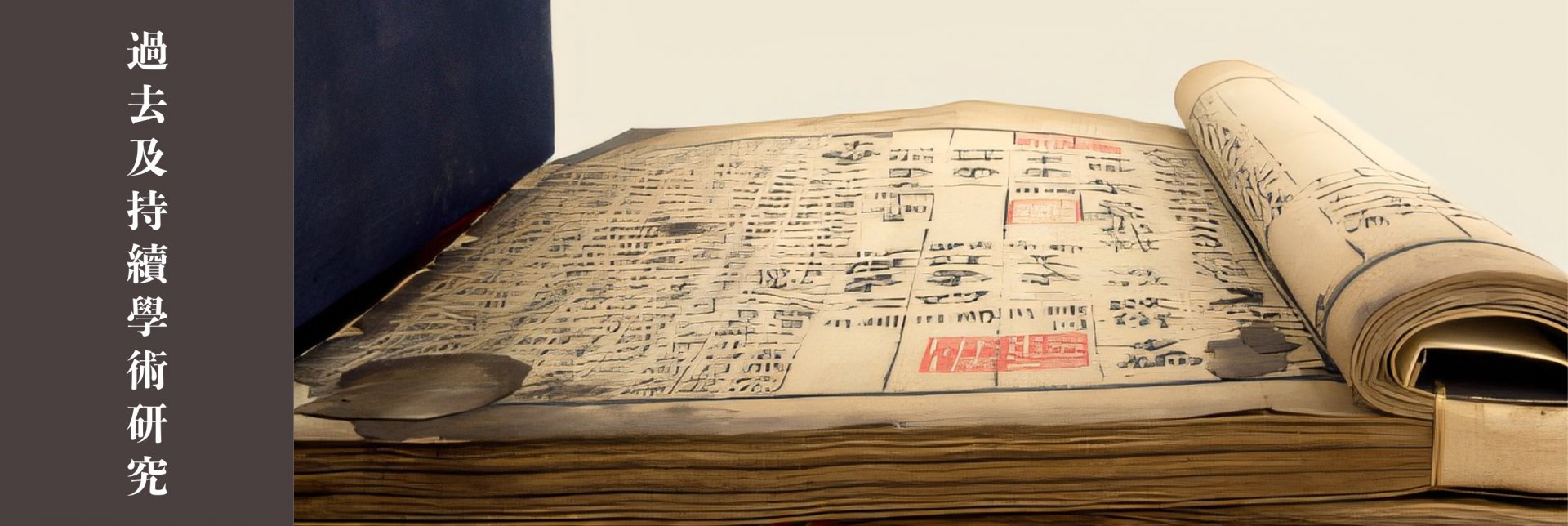



歡迎留言:
請登入/登記成為會員後留言